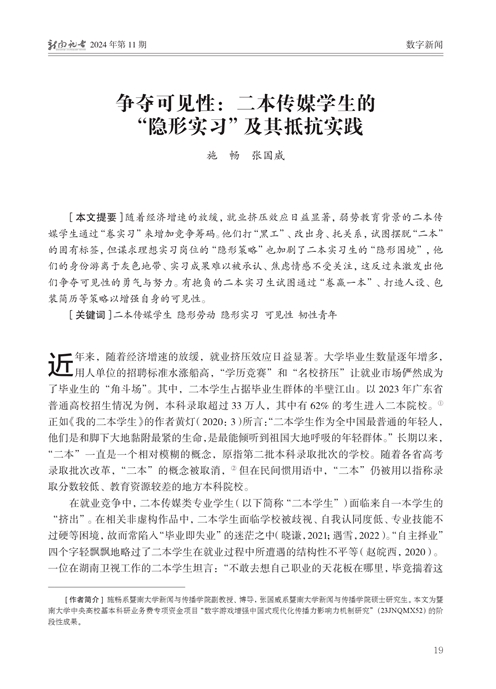争夺可见性:二本传媒学生的“隐形实习”及其抵抗实践
施畅 张国威
[本文提要]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就业挤压效应日益显著,弱势教育背景的二本传媒学生通过“卷实习”来增加竞争筹码。他们打“黑工”、改出身、托关系,试图摆脱“二本”的固有标签,但谋求理想实习岗位的“隐形策略”也加剧了二本实习生的“隐形困境”,他们的身份游离于灰色地带、实习成果难以被承认、焦虑情感不受关注,这反过来激发出他们争夺可见性的勇气与努力。有抱负的二本实习生试图通过“卷赢一本”、打造人设、包装简历等策略以增强自身的可见性。
[关键词]二本传媒学生 隐形劳动 隐形实习 可见性 韧性青年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就业挤压效应日益显著。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用人单位的招聘标准水涨船高,“学历竞赛”和“名校挤压”让就业市场俨然成为了毕业生的“角斗场”。其中,二本学生占据毕业生群体的半壁江山。以2023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情况为例,本科录取超过33万人,其中有62%的考生进入二本院校。①正如《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黄灯(2020:3)所言:“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长期以来,“二本”一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原指第二批本科录取批次的学校。随着各省高考录取批次改革,“二本”的概念被取消,②但在民间惯用语中,“二本”仍被用以指称录取分数较低、教育资源较差的地方本科院校。
在就业竞争中,二本传媒类专业学生(以下简称“二本学生”)面临来自一本学生的“挤出”。在相关非虚构作品中,二本学生面临学校被歧视、自我认同度低、专业技能不过硬等困境,故而常陷入“毕业即失业”的迷茫之中(晓谦,2021;遇雪,2022)。“自主择业”四个字轻飘飘地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所遭遇的结构性不平等(赵皖西,2020)。一位在湖南卫视工作的二本学生坦言:“不敢去想自己职业的天花板在哪里,毕竟揣着这个学历,觉得每往上一步,都可能就是天花板了。”(卢回,2020)换言之,与拥有学历优势的一本学生相比,二本学生不仅面临更为严峻的求职挑战,而且即便入职成功也会遭遇显而易见的职业天花板。那么,学历不占优势的二本学生将如何增强求职竞争力呢?
既然学历出身无法改变,那么实习经历就成了求职竞争的关键筹码。拥有多段高质量实习能够有效提升二本学生在就业市场的求职竞争力。但现实情况是,传媒行业红利不复往昔,难以提供充足的优质实习岗位。如此一来,多数二本学生只能进入规模较小、实力偏弱的企业实习,这也导致他们的求职竞争力大打折扣。于是,摆在有抱负的二本学生面前的难题是:如何进入理想的实习单位以提升求职竞争力?实习结束后,他们又该何去何从?本文循着这些问题,考察二本学生在结构性压力下的现实困境与突围策略。
一、研究回顾及研究方法
(一)传媒实习研究
长期以来,实习被视为进入正式工作前的预热。雇主不仅可以用“先试后买”的方式评估实习生的职业能力与企业适配度,实习也为毕业生提供了就业“软通货”。此时的实习生更像是经历一段长时的试用期,在实习结束后有望获得入职机会。当前,应届毕业生规模逐年扩张,实习人数远超企业所需用工人数,每年能够从实习转正的员工十不存一,甚至有时留下来的可能性为零,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实习生会补上空缺的岗位(宁瑜,2023)。即便如此,实习生们仍前赴后继地投入这场“实习竞赛”之中,不断积攒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实习经历,以增强求职竞争力。
在新闻传播领域,实习不仅是学生增长工作经验的主动选择,同时也是专业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强调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传媒行业,人力资源主管(以下简称HR)尤其看重应聘者是否具有多段高质量的实习经历。在优质实习岗位稀缺和同辈群体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传媒实习生开始愿意接受“低薪”、“无薪”的条件,甚至甘愿“倒贴钱”参与实习。实习生不仅需要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与超额的工作时间,还需要接受自己是“无酬劳动力”的事实(夏冰青,2018)。对“劳动同意”的解释,可以追溯到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所提出的“赶工游戏”,即劳动者通过参与游戏的方式转移注意力以应对枯燥的劳动,从而自愿进行自我剥削(布若威,2008:89)。但实习生并不需要背负沉重的“赶工”压力,直接套用布若威对劳动者自愿工作的解释略显生硬,实习劳动的特殊性促使研究者沿着布若威的思路提出更多关于“制造同意”的解释。有学者提出“制造同意”应更多关注劳动者的主观感受与认同(吴清军,李贞,2018)。如何利用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促使实习生自愿接受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制造同意”的背后,管理者通过关系工作、情感工作和情怀工作制造的幻象引导实习生在冷峻现实中追求剩余快感(贾文娟,钟恺鸥,2018)。实习或为一场“理想游戏”,令实习生背负着他人的高期待,忍受繁重的工作,并时刻满怀热情投身实习劳动(牛静,赵一菲,2020)。此外,实习生还有着“进取自我”的决心,通过延迟满足将困境合理化,企望用眼前的艰苦实习来换取对未来时间的自主掌控(曹璞,姚卉,2024)。掺杂了更多情感因素的劳动关系掩盖了传媒实习劳动中的不平等与不稳定。
上述文献揭示了传媒实习生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其愿意躬身入局的缘由。但这些解释无一例外都将实习生视为一个标准且统一的群体,并忽视了其中教育背景更为弱势的二本学生群体。倘若将实习生群体进一步细分,我们会发现,对于一本学生而言,他们不仅拥有学历优势,而且享有较为丰富的实习资源;对于二本学生而言,他们通常难以进入公众视野,甚至连“制造同意”的基本门槛都难以企及。他们争取实习机会、参加实习工作时的热望与悲伤、挫折与韧性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针对二本学生的研究有必要借用社会学中“弱势背景”的概念工具。“弱势背景”(underprivileged/disadvantaged background)指的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因家庭、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不足或不利条件而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限制,以致个人在获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资源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Dupriez et al.,2012)。其中更具针对性的是“弱势教育背景”(disadvantaged educational background)概念,该术语意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因教育资源不足、教育质量欠佳等不利因素而面临的挑战与限制。劳伦·A·里韦拉(Lauren A. Rivera)发现,在头部企业的招聘中,是否拥有以高端实习为代表的“高端课外活动”(high-statu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经历已成为评估求职者的重要考量,“那些在校园招聘狂热出现后才开始打造业余活动简历的学生太晚着手了”(里韦拉,2019:113-114)。有研究表明,弱势家境的大学生唯有增加社会性投入、突破文化障碍,才有可能摆脱弱势出身(郑雅君,2023:253-254)。手持二本学历的毕业生意味着他们需要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前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攒更优质、更丰富的实习经历以弥补自己与一本大学毕业生的差距。
(二)隐形劳动研究
隐形劳动(invisible work)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之一,意指特定职业或群体的劳动被他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隐形劳动被认为发生在家庭等私人领域,用以描述妇女的家务劳动在文化和经济上被双重贬低的境遇,家庭主妇们承担了家务劳动、母乳喂养、护理照料等大量无偿劳动,但这些劳动在价值评估中却不被计算在内(Daniels,1987)。
20世纪80年代末,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的引入令隐形劳动相关理论更为系统化。此概念被用来解释黑人女性因“黑人+女性”双重弱势身份而遭受的各种歧视与压迫,即便在性别、种族等平权运动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她们亦遭忽略(Crenshaw,1989)。由此,因职业、种族、阶级等因素导致的隐形劳动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尽管归属不同的社会议题,但它们在现实中相互交叉关联(Bohrer,2018)。
女权主义者主张破除女性家务及照护劳动的隐形化,并将其视作一份正式的工作(Elias,2010)。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进而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社会工作环境中的性别不平等加以批判,并关注种族、阶级等权力结构,聚焦经济体系如何制造并延续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Agenjo-Calderón & Gálvez-Munoz,2019;Pearson,2019)。总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女性主义学者旨在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不平等,承认女性劳动并致力于改善交叉的不平等问题,呼吁制定公平公正的经济政策,以增加隐形劳动的工作价值,同时要求对相关劳动做适当补偿(Lokot & Bhatia,2020)。政治经济学者使用“隐形劳动”的概念,呼吁人们重视社会边缘劳动、低薪劳动以及不受法律保护和监管的劳动。
近年来,随着“隐形劳动”这一术语被应用于非性别劳动领域,研究者对隐形劳动的研究发生了情感转向。他们试图超越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将隐形视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予以考察,重点关注隐形劳动者在此过程中的情绪体验与情感历程。譬如,殡仪馆工作人员、屠夫、维修工、清洁工、性工作者等特定职业就被贴上污名化的“肮脏”标签,他们通常对自己的职业闭口不谈,害怕遭受他人的负面评价(Ashforth & Kreiner,1999)。有学者指出,清洁工在得知自己被忽视后会感到羞耻、恐惧和焦虑不安。清洁工们坦言,他们往往被他人视而不见,劳动成果亦被无视,“仿佛你根本不在那里一样”(Rabelo & Mahalingam,2019)。在情感视角中,研究者的视角更为微观,侧重分析劳动者在心理情感方面的不可见和被忽视(Hatton,2017)。
不过,隐形劳动并不能完全概述二本学生的实习困境。因此,笔者进一步提出了“隐形实习”(invisible internship)的概念。这一概念受益于艾莉森·D·韦德哈斯(Allison D. Weidhaas)“隐形劳动”相关论述的启发。她指出,包括实习在内的非正式工作缺乏社会认可,加之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实习劳动者的努力经常被忽视和被低估(Weidhaas,2017)。不过她并没有正式提出“隐形实习”这个概念。
在笔者看来,“隐形实习”是指弱势教育背景的学生在实习阶段所面临的隐形困境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身份的隐形”,即他们在工作中被他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二是“成果的隐形”,即他们的实习贡献不被他人认可;三是“情感的隐形”,即他们在实习中的焦虑迷茫、愤懑不甘等情绪不被他人关注。“隐形实习”这一概念的提出,将隐形劳动延展至非正式工作领域,由此拓展了隐形劳动的应用场景。它试图揭示弱势教育背景的学生在实习中所面临的隐形困境,并强调该群体在反复挫折与失败中不断寻找希望的心路历程,在丰富隐形劳动理论的同时,更兼具现实价值。本研究以“隐形实习”为主要分析框架,考察二本学生的实习历程,以期挖掘、展现二本学生实习过程中更为丰富细腻的情感体验。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深度访谈作为主要研究方法。2023年3月起,笔者对有过实习经历或正在实习的24名二本传媒类专业学生进行访谈,每次1.5到2小时。受访者在大学期间至少有过2段及以上的实习经历,实习时长至少在3个月以上。访谈时间为受访者实习期间或者实习结束半年内。其中,有18名二本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实习,13人拥有3段及以上的实习经历。③本研究所定义的传媒实习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机构,也包括大型互联网公司(以下简称“大厂”)、新媒体公司、广告代理商等相关企业。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第二作者的本科就读于广东一所二本院校,经考研进入如今所在的学校。这为访谈和研究带来一定便利,一方面有助于笔者结识访谈对象以及后续的交流沟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笔者以切身经历为参照,探寻二本学生实习过程中的个体感受与情感体验。
笔者同时采用自传社会学的方法补充和丰富本研究。通过发放自传邀请信和邀请访谈对象书写,本研究共收集了8份由二本学生亲自撰写的自传,其中包含了他们求学经历与传媒实习中的酸甜苦辣。④为了进一步扩大样本,本研究也将《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极昼工作室》等媒体公开发表的关于二本学生的30篇特稿及非虚构写作纳入考察范围,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二本学生在传媒实习中的体验与感受。
二、二本学生找实习的“隐形策略”
为了寻找一份理想的实习,部分二本学生借助打“黑工”、改出身、托关系等策略,刻意隐藏自己的“二本”标签,以期增加获取实习资格的概率。但这种“隐形策略”令他们感到惴惴不安,生怕有朝一日“底牌”暴露。
(一)打“黑工”
“黑工”原指非法入境或持有与入境国家不匹配的签证类型,而非法滞留该地区的劳动者。由于身份的模糊性,黑工游走在灰色地带,不仅劳动成果被盘剥,而且担心哪天会被突然驱逐出境。本文中的“实习小黑工”是指未走常规人事流程而直接参与实习工作的实习生,他们被排除在企业单位的常规管理体系之外。“实习小黑工”与“黑工”的相似之处在于其隐形的工作身份和不稳定的劳动心态。
没有正式的实习劳动协议是“实习小黑工”的主要特征。由于二本学历的限制,小新(大四女生,4段实习)在找实习的平台软件中投递了数十份简历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应,之后通过同校师姐的推荐,小新得以直接进入某省级卫视下的L导演工作室实习,为一档热播综艺做宣发。但这也使小新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师姐的关系能够让小新免除实习面试,留在师姐所在的部门实习;另一方面,由于未经过正式面试,小新担心自身能力无法胜任实习带教老师分配的任务。再三考虑之下,小新还是成为师姐的“实习小黑工”。实习期间,小新尽管参与并完成了多项实习任务,但没有署名权。由于非正式的实习身份,小新的工作任务只能由师姐私聊布置,文案写作、视频策划、广告宣发等各项工作都需要小新亲力亲为。师姐的工作由她分担,她的劳动成果却由师姐独享。“我就像一台无情的供稿机器,我肯定不想‘做黑工’的,但这个经历可以写进我的简历里,尽管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E-F-02)。由于该媒体的正式实习生不仅“无薪”,而且需要交“实习生管理费”,小新的“实习小黑工”身份反而让她省下了一大笔费用。尽管实习作品无法署名,但为了这份实习经历她还是选择接受和妥协。
如小新一样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实习小黑工”亦不在少数。不少受访者透露,越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媒体或公司,实习入职流程就越简陋,就越是缺乏应有的实习保障。“去到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实习生没人管你”(E-F-07)。就连离职时的评语,也多出自二本学生自己之手,“我的实习评语是一张A4纸,上面有一些空白的横线,原本应该是带教老师写的实习评语,都变成你自己写了,你想写什么都可以”(E-F-23)。这样一份看似光鲜亮丽的实习劳动,实际上却是非正式的。
“实习小黑工”的身份令他们感到失落和担忧。一方面,“实习小黑工”意味着二本学生不被视为团队中的正式成员,“割裂感特别强,完全不会对公司有认同和归属感”(E-F-08)。他们的劳动付出得不到重视,甚至被忽视,“做那么多工作,自己却没办法署名,还是会有点失落”(E-F-07)。另一方面,一旦招录的正式实习生增多,“实习小黑工”将失去其利用价值,“人家凭什么用你,图你是‘黑工’吗?”(E-F-02)实习结束后,小新没有拿到实习证明,碎片式的参与也让她对团队项目的了解十分模糊。最终,小新表示自己不敢在简历中凸显这段实习经历。非正式的实习身份令他们失去自我展示的底气。
“实习小黑工”是隐形实习的真实写照,实习生们进行着难以被观察识别、正式认可的劳动。但部分“实习小黑工”并没有对这种隐形实习全盘接受,他们主动增添仪式感,积极更新实习动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隐形实习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虽然没有正式签订实习协议,但部分受访者还是不约而同地保存了入职当天的照片或聊天记录,并且将自己做过的每一份文档材料都汇集起来,反复提醒自己并向他人证明:“我在这里实习过!”(E-F-07)“我在这里写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我在这里留下的痕迹,这都是不可被忽视和抹掉的。”(E-M-04)虽然没有拿到正式的实习证明,但小新在实习结束后还是找师姐拿了一份盖有部门章的空白“实习证明”,小新自己填上了实习评语,其中包括她参与过的所有项目。
除了对实习证明的重视,不少受访者也会通过和同学校的其他同学建立微信群聊来熬过这段隐形岁月。实习期间,他们在群聊里分享近况、抱怨上司、彼此鼓劲。“我们的群名叫‘坏人群’,因为我们经常在群里吐槽工作中的糟心事,这个群简直是我的快乐源泉”(E-F-24)。“群里的朋友会一起帮着参谋,比如稿子怎么写、如何与领导打交道等,有好消息大家也会在群里分享,互相鼓励”(E-M-14)。他们在微信群里惺惺相惜,无形中增强了二本实习生的群体认同。
二本学生也能在隐形实习中捕捉到自己情绪的微妙变化。有学者指出,从事“肮脏”工作的隐形劳动者面临着污名化的困境,并会因从事职业的特殊性而深感自卑(Soni-Sinha & Yates,2013)。“实习小黑工”的非正式身份也让部分受访者失落不已,因为害怕被其他正式实习生取代,他们焦虑地执行没有成果署名权的实习任务。但相较其他隐形劳动者,二本学生也具有一定能动性。他们利用微信群建立一种共同进退、彼此共勉的社交关系,借此缓解“实习小黑工”所带来的焦虑、羞耻与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肮脏”工作者的隐形劳动源于其职业的特殊性,而二本学生的隐形实习是基于自身弱势教育背景的主动选择。他们以隐匿的身份参加实习,积攒实习经历与实习成果。
(二)改出身
“你来自哪所学校”是实习生之间最先聊到的话题。一本学生会主动聊起自己在学校的所见所闻,这在二本学生看来是一种炫耀。二本出身带给他们的更多是自卑,他们通常对自己所在的学校极力隐藏、羞于提及。
二本院校通常是“××学院”。在不少人看来,“××学院”毕业的学生往往“不努力”。“不上进”,有时甚至会被误以为是来自专科院校的学生。舒灿(大四女生,4段实习)在秋招时被一位HR提醒,她的学校以“学院”结尾,这会让很多HR误以为她来自大专院校,故而在初筛时就被淘汰。“我跟她解释了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本科,但她说本科应该叫‘大学’。后来她以学历不匹配的原因把我拒了,确实挺挫败的”(E-F-06)。HR的直言相告给了舒灿启发,她偷偷地把简历上的“学院”改成了“大学”。此后舒灿在找实习时就顺利许多,之后的实习面试HR再也没有就学校问题提出疑问。
学校名称的负面影响也在二本学生的自传中被多次提及。“原本引以为傲的经历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帮助,尽管能看出HR对我很感兴趣,但一旦涉及学校的话题,我就会收到‘岗位要求不匹配’的拒信”(D-M-03)。“辗转找到一位HR,他向我解释,这种情况(收不到面试通知)就是你的学校达不到要求,招聘方直接忽略掉了”(星野,2018)。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常会因二本出身而导致实习面试失利。
二本学生通常倾向于避而不谈自己的毕业学校,这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母校摇摇欲坠的认同感。在他们看来,“××学院”的称呼是对他们高中三年努力成果的否定。“一句二本学校,这个学校就一无是处了”(E-F-15)。“难道在二本学校读书就一定意味着我很蠢、不努力、不上进吗?”(E-F-11)博宇(研一男生,4段实习)戏称自己曾就读于“四非”学校(非985、非211、非双一流大学、非双一流学科),当质疑与自嘲交织,“××学院”成了他们羞于提及的伤疤。
多数二本学生习惯于将自身的困境归咎于“二本”的标签。在他们眼中,二本出身在无形中设定了一个“天花板”,“无论怎么努力,很多机会都像是早就为别人准备的”(E-M-10)。“经常会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的学校背景不够硬,所以我才得不到认可”(E-M-05)。“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不想在大厂和国企上浪费时间,根本进不去”(杨晓倩,2024)。二本学生无法确定考上更好学校的研究生是否有助于自身的未来发展,他们悲观地意识到,“二本”标签已经深深烙印在他们身上,并随着档案的流动伴随他们一生。
部分受访者表示二本身份令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实习生群体。舒灿介绍,在实习单位,同一个学校的实习生会走在一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讨论问题,一起聊八卦。“我跟他们之间感觉有一堵墙,我融不进他们,他们也没有想让我融进去的意思”(E-F-06)。在里韦拉看来,出身于不同阶层必然带来相异的语言风格和互动风格,最终铭刻在每个人的行为习惯之中,你的谈吐交流、举手投足、衣着风格都将暴露你的出身(里韦拉,2019:205-206)。在实习单位,一本学生有自己的小圈子,而二本学生被排除在外,这进一步加深了二本学生的自卑心态。
(三)托关系
多数时候,二本学生想要进入大厂实习并不容易,除非另辟蹊径。在我国语境中,“关系”通常指个体之间互惠互利的社交网络。借助关系,二本学生有望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实习机会。在受访者的描述中,要想去大厂实习,就必须得靠关系,老师、师兄师姐、朋友都可以成为他们关系的来源。关系越广泛,他们可触及的实习单位就越多;关系越过硬,他们进入实习单位就越容易。
希尧(大四女生,4段实习)在大二的暑假多次向大厂投递简历,但屡屡被拒。她并不甘心,转而寻求本校老师的帮助与推荐,但以普通师生关系推荐只能获得内推码,仍需要应对笔试面试的考核。“到HR那关还是过不去,但如果你是企业领导的亲戚,就能免试进入大厂”(E-F-20)。为此,希尧找到与她关系密切的“大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内指导老师L。L老师从企业高管转型为高校老师,拥有丰富的业界资源。L老师为她提供了一个“编造亲戚”的解决方案,如此才能让高层领导“卖你一个人情”,“老师帮我打了一个电话去,说我是她的侄女,结果不用面试就能过去实习,入职时间也任由我选择”(E-F-20)。最终,希尧作为L老师的“侄女”顺利进入广州W公司实习,且被安排到核心业务部门。
有了“亲戚关系”的加持,部分受访者如愿以偿进入大厂实习,但他们依然感到不安。在实习期间,希尧实习任务少、成果要求低,她的实习带教老师有意将她和其他通过正式渠道进来的实习生区别对待,“对带教老师而言,不让你做任何事情对他来说是最省心的,就像安插了一个‘老板的亲戚’在身边,他并不指望我真正参与进来”(E-F-20)。“实习生比正职员工还多,如果出身很普通的二本,又没有经验,那你大概率是关系户”(E-M-13)。“我当时的感觉就很自卑,因为自己是关系户,害怕别人用刻板印象看我,觉得二本学生就是蠢”(E-F-01)。部分受访者害怕“关系”这层窗户纸被捅破,进而影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因此,他们在利用关系获取机会的同时,也在努力通过实际表现证明自己的能力,试图弥补关系依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谋求一份理想的实习,部分二本学生选择隐藏自己的“底牌”。但这种自我隐形的策略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实习小黑工”因为没有“名分”而游离于公司常规业务之外、实习带教老师对“关系户”的有意忽视、学校出身有别带来的社交隔阂等。作为谋求理想实习岗位的“隐形策略”犹如回旋镖一般反过来造成了他们自己的“隐形困境”。不过,有抱负的二本学生并不甘心隐形实习的处境,他们试图突破困境、打破僵局。
三、二本实习生的可见性争夺策略
实习到岗后,二本实习生为了摆脱自身的隐形困境,开始采取“卷赢一本”、打造人设、包装简历等一系列策略,借此争夺自身的可见性。
(一)“卷赢一本”
在大型企业中,二本实习生的数量通常远小于一本实习生。清一色的一本学生给二本学生带来同辈压力的同时也提供了比较的参照系。有受访者坦言,在实习初期,实习带教老师往往对一本实习生表现出明显的偏袒。“一本学生得到的资源和支持明显更多,他们的意见总是会被优先考虑”(E-F-01)。在任务分配和沟通互动中,一本实习生要比二本实习生更容易参与核心业务,并在日常工作中更受带教老师关注。
在实习期间,倘若一本实习生的实际表现与众人的预期不符,甚至相去甚远,那么部分二本实习生便会不失时机地贬损一本实习生,并时刻安慰自己“我并不比一本学生差”(E-M-05)。“你一个985,不也是跟我来同一个地方实习”(E-F-16)。在他人的比较中,二本学生意识到一本学生也是普通人,实际业务能力未必会比自己高多少,由此逐渐克服自卑、找回自信。
“卷赢一本”(E-M-10)以提升能力可见度,是二本实习生争夺可见性的主要手段。博宇在访谈中多次提及能力不如他的一本实习生。在实习带教老师布置的策划案写作中,不少来自985、211高校的大学生或态度敷衍,或延时提交,而他的策划案则受到了带教老师的表扬。在博宇眼中,一本实习生学历与能力的不匹配让他找回了自信。“我觉得大家水平都差不多,有些985学生甚至不如我们二本学生,他们可能会更懒,甚至更‘水’,我们只是在学校名称上有区别,但能力方面可能不会有很明显的差距”(E-M-10)。舒灿周围来自一本院校的实习同事屡次任务未达标,而且态度不好,随即遭到了带教老师的批评,“老师们疯狂抱怨,说985学校怎么会出这样的学生”(E-F-06)。带教老师对一本实习生的批评让舒灿多少找回点自信。
二本实习生对来自境外高校的实习生尤为不满。在不少受访者看来,境外学校虽然学校的综合排名高,但入学门槛低,实际能力或许还不如经历过高考的二本学生。“港大硕士很厉害吧,但他在英国读的本科,这种同学我会先入为主,你就是因为家里有钱,如果没有家里的支持,你大概率也是个二本”(E-F-09)。“刚入职时,老师们可能会留意你的学历背景,但在今后的工作中,二本学生不一定就比英国水硕的同学差”(E-F-24)。在“二本比境外高校学生更强”的信念驱动下,二本学生通过更加努力地完成工作任务,以出色的工作表现来证明自身的能力和价值。
为了获得实习带教老师的认可,二本实习生试图参与更多实习项目,并在其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有时还会以“领导”一本学生为荣。在广东某省级媒体实习的万霖(大三男生,2段实习)就曾被带教老师委以重任。在一次活动中,他作为实习小组的组长带领其他一本实习生开展工作。相较于其他新手实习生的不知所措与无所事事,万霖显得井井有条、老练娴熟。“到了饭点,老师叫我过去吃饭,我说我先把工作对接一下,老师们点点头,当时觉得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和重视”(E-M-18)。在活动结束后,万霖参与了稿件写作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老师给了我500字的报纸版面,这是其他一本实习生都没有的待遇”(E-M-18)。在实际工作中,有二本学生坦言,带教老师一个点赞的表情包能让他们开心一天,“我们知道自己没有一本学生的光环,所以更要通过加倍的努力来弥补”(E-F-06)。原本的自我怀疑在实习带教老师的认可和褒奖中消散。正如他们所言,“只有比一本实习生更强且更努力”(E-F-11),他们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成果才能“被看见”。
“卷赢一本”既是二本实习生克服自卑、争夺可见性的主要方式,也是他们建构优秀自我的一种手段。在这场无声的战斗中,二本实习生将一本实习生视作假想敌,通过超越、贬损他人获得成就感,以此证明自己只是“考学”不如一本学生,但在实践能力方面依然具有优势。同时,二本实习生也借机在实习单位站稳脚跟,表明自己在团队中难以被取代的关键地位。与二本实习生一样,一本实习生同样被“优绩”(merit)裹挟。研究者发现,作为考学竞赛胜利者的一本学生尽管自带光环,但同时也背负着“不想砸了学校招牌”的心理压力(朱丽丽,2024)。不少二本实习生表示只要自己在某一方面能胜过一本实习生,便可收获更多关注。但这种以超越、贬损他人来确证自我价值的逻辑存在着一定风险,一旦有更为优秀的一本实习生出现,他们内心深处的不自信就会卷土重来,自我认同将再一次摇摇欲坠。
(二)打造人设
在进入大厂实习之前,二本学生往往面临被轻视的境遇。不少二本学生坦言,不仅学校的老师不建议他们花费精力进大厂实习,而且家长也对他们抱以较低的职业期待,朋友之间的认可与鼓励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二本学生一旦有机会就拼命想证明自己。部分受访者在进入大厂实习后,会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展演来建构自身形象。他们在照片分享中露出实习单位的名号、图标、工牌等,暗示自己已经进入理想的实习单位,以此打造永不言弃、积极向上的励志人设,从而克服弱势教育背景所带来的自卑。
“打造人设”以提升实习可见度,也是二本学生争夺可见性的主要策略之一。从大一就开始在小公司积攒实习经验的万霖,成功在大二获得了广东某省级媒体的实习“入场劵”。在实习的第一个月,万霖就发了三条朋友圈。第一条朋友圈是万霖入职第一天与报社门口招牌的合影。为了不被他人发现,万霖当天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我当时四处张望,寻找有报社标识的地方,最后发现只有办公室门口适合合影”(E-M-18)。这条朋友圈随即得到数百位好友的点赞,校内老师向他发来祝贺,父母将他视为骄傲,学弟学妹把他作为榜样,“感觉自己很厉害,在假期也没有闲着,能在大二就找到知名媒体实习,这是我的本事”(E-M-18)。第二条朋友圈的内容是署了名字的报纸发稿。尽管这条稿子只占了五分之一的版面,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刊印,万霖仍无比激动,“我花了半个小时在找报纸的最佳拍摄角度,不仅要把自己的名字拍得大一些,而且要露出文章标题”(E-M-18)。第三条朋友圈万霖选择转发一篇署有自己姓名的网络稿件,虽然是一篇通稿,但该文章的阅读量却在半天之内突破十万,“我把报道里所有评论都点赞了,没想到通稿也能得到大家的认可”(E-M-18)。这三条朋友圈让万霖在老师、家人、朋友眼中变得耀眼可见,他既宣告了自己已进入知名报社实习,又向朋友圈的好友展示了自己的实习成果。
实习单位的“金字招牌”为二本实习生的自我呈现提供了筹码与谈资。尽管不少二本实习生的工作枯燥乏味,但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地渴望证明自己。“能够在官方平台上展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E-F-01)。“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给朋友和老师们看,我虽然出身二本,但也有机会去大厂实习,你们少看不起我”(E-M-12)。在朋友圈展演实习经历、打造励志人设的过程中,二本实习生不仅获得了社会认同,而且提升了自我满足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隐形的困境。
(三)包装简历
在访谈中,多数二本实习生将求职简历无人问津的情况形容为“简历被丢到垃圾桶”(E-M-05)。他们坦言,在学历的高墙之下,冠以“××学院”的简历难以进入HR的视野,“我就算有一本的能力又怎么样?他们还是不要我”(E-F-03)。“一本学生的简历不需要包装,HR也会多看几眼”(E-F-01)。这种以效率为先的筛选方式被里韦拉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真相:招聘人员认为“在低标准的候选人中找来找去只为发现一块‘璞玉’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里韦拉,2019:41)。在这种压力下,部分二本实习生会通过设计、夸大、虚构实习经历等方式对简历加以包装,让简历更加亮眼,进而提升求职时自身的可见度。
在不少受访者看来,自己要想获得HR的青睐,“包装简历”是一种必须,而其中的重点就在于对实习经历的包装。有受访者表示,简历不仅需要展示自己的成果,更要表明自己在项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虽然你在实习单位打杂,但你可以将‘参与某项目’改为‘为某项目带来百万营收’”(E-F-15)。此外,一份高质量的实习作品集也能让HR眼前一亮。为了在秋招中尽早拿到offer(工作录用通知书),希尧熬了两个通宵,把自己在校和实习期间的实践作品做成PPT,注明所获奖项,并附上观看二维码,希望借此获得HR的青睐。
为了让求职简历更加亮眼,部分二本实习生在包装简历时也不乏夸大甚至编造自身实习经历。由于平常的自由散漫,子澄(大四男生,0段实习)既没有主动找实习,也没有服从学校的实习安排,临近毕业才开始找工作,他干脆将W师兄的经历写在了自己的简历里。子澄透露,他和W师兄经常一起吃饭和打游戏,进而了解到对方两段大厂实习中的项目流程和基本细节。为了更好地应付招聘,子澄在网上找了专门的简历修改培训机构咨询。该机构承诺对子澄的简历以及后续面试提供全方位包装,以助其斩获心仪的offer。
与子澄一样,找培训机构包装自己求职简历的二本实习生并不少见。“没有HR会去做背调,特别是在校学生的实习经历,只要在面试时顺利答上项目细节以及操作流程等问题,蒙混过关并非难事”(E-M-14)。在二本实习生中,“包装简历”并非个案,在非虚构作品《二本应届生的“假简历”》中,不少二本实习生指望靠培训机构找个好实习、好工作,但随着企业招聘需求的变化与新增岗位变少,原本培训机构宣称的“100%就业率”成为一种文字游戏。据一位在IT培训行业工作了8年的从业者观察,经培训机构包装后的求职者就业率也只能到30%~50%(徐巧丽,2023)。
不过,一个谎言需要用更多谎言去圆。在面试压力下,尽管经过培训机构老师多轮训练,但只要面试官揪住某个阶段的经历深入询问,多数人难以自圆其说。在实际案例中,二本学生把培训机构拿来练手的项目写进简历里,在面试考官的不断追问中多次“卡壳”,最终面试被淘汰;就算依靠“假简历”顺利进入公司,能力与履历的不匹配也让他们在后续的工作中寸步难行,甚至只能把公司项目拿回培训机构求助(徐巧丽,2023)。有受访者坦言,“刚开始包装简历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能进公司,后续靠努力就能弥补差距,后来发现遇到的很多实际中的问题我根本没法解决”(E-F-02)。“心理压力非常大,面试很难,实际工作和简历上写的经历也差距很大”(E-F-24)。简历的包装固然能短期内提高求职成功率,然而,将他人的实习履历“嫁接”到自己身上,这种欺瞒终究难以维持,一旦在面试或实际工作中露馅,作假者只能接受造假带来的苦果。
在包装简历的过程中,部分二本实习生也曾反思造成自身困境的原因。“很不公平,在起跑线就已经落后了,想要靠个人努力追赶上来真的太难了,学校的资源、课程设置、实习机会这些都不是我能改变的”(E-F-02)。“我们天然处于劣势,社会对我们的固有偏见使得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但造假一旦被发现,其实会加深外界对我们的刻板印象”(E-M-13)。部分受访者也承认过度包装简历在伦理道德上颇为可疑,但一想到自身在求职过程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他们更倾向于将它合理化为一种可取的策略。
在顺利获得实习机会之后,二本实习生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自己的能见度。他们既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又要标榜这段实习经历,同时还要包装自己以增加求职竞争力。这其中有精心的经营,有时也掺杂了欺瞒的手段。欺瞒固然有损声誉,但倘或没有剑走偏锋,他们更难以“被看见”。需要指出的是,部分二本实习生在面对隐形困境时并没有逆来顺受,也没有选择“躺平”,而是尝试争夺可见性,这体现了他们的能动性与韧性。只要有机会,他们迫切地希望证明自己的能力,借此为未来的求职就业增加更多的成功机会。
四、讨论:二本实习生的韧性与希望
黄灯(2020:3)曾坦言,“作为二本学生,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便进入了理想的公司实习,多数二本实习生终究无法获得转正的门票,他们依然要面临正式招聘时残酷的筛选。“除了学历够不到,企业对专业技能、外语能力也要求不低,我连基本门槛都达不到”(E-F-06)。“实习了6个月,本以为可以拿到转正机会,结果我连面试通知都没收到”(E-M-14)。对大多数二本实习生来说,这是一份注定留不下来的实习工作,也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面对隐形实习以及实习后难以转正的困境,不少二本实习生逐渐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他们放弃了对心仪工作岗位的执念,或尝试考研提升学历,或考公考编争取“上岸”。
(一)隐形实习中的可见性争夺
在二本学生的实习历程中,为谋求理想的实习岗位,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隐形策略”:或以“实习小黑工”的身份穿梭在工作任务之间,或将“××学院”改为“××大学”以遮掩二本出身,或动用人脉关系绕过严苛的实习招聘。谋求实习机会的“隐形策略”尽管让二本学生进入了心仪的实习单位,但也加剧了他们日后的“隐形困境”。他们心有不甘,并为此感到焦虑迷茫。对二本实习生来说,“二本”不仅是一种负面标签,更是一种日常困境。
本文将二本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隐形困境概括为“隐形实习”。隐形实习既涵盖了处于弱势教育背景的学生在实习中心酸、困顿的情感体验,又包含了他们为提升可见性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二本学生看似可以自由地选择实习或不实习,甚至随时可以中途离开,以此逃避身份、成果、情感上的隐形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但受到就业环境、培养模式的制约,为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二本实习生实则别无选择。
隐形实习的不利处境也令不少二本实习生迸发勇气,调整策略,不断争夺可见性。“卷赢一本”成为二本学生在实习期间的“支线任务”。此外,他们还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中营造励志人设,并试图打造一份理想简历,以彰显自己的实习成果。在争夺可见性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正视自己的短板与不足,也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自我认同。从“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的乐观向上,经由“努力也未必可以成功”的迷惘和踌躇,部分受访者逐渐形成了“不努力的话就一定会输”的心态。尽管学校出身不占优势,但他们没有就此认输,依然有不少二本学生在不断挣扎,尝试转换赛道,努力突围破局。李伟和邬志辉(2023)对此也有类似的观察,二本学生在迷茫和不甘中完成从“外求于人”到“内省于己”的心态转变,通过考研考编等“自救”策略努力摆脱学历困境。
(二)发现二本实习生的能动性
以往关于实习生的讨论主要围绕低薪、无薪、倒贴钱等议题,尤其聚焦不平等、不稳定劳动(Brown & deCant,2014;贾文娟,钟恺鸥,2018;王程韡,杨坤韵,2019;牛静,赵一菲,2020)。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通常是拥有优势教育背景的一本学生,对二本学生并未给予太多关注。得益于黄灯对二本学生的书写,该群体才在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但目前关于该群体的非虚构作品、特稿与调查报告,往往聚焦于二本学生所遭遇的困境,鲜有涉及他们在困境中的调适能力与破局策略。
对二本实习生的重新审视,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困境中的努力与挣扎。隐形劳动的既有研究多强调劳动者对隐形困境的逆来顺受,他们通常只能勉强维持现状而无力改变。而笔者在揭示二本实习生隐形困境的同时,还试图发掘他们身上的能动性。他们深知自己的学历不占优势,但也在积极寻找破局与突围的办法。二本实习生既有与一本实习生比个高下的勇气,有时也会采取带有欺瞒性质的“灰色策略”,如依靠过度包装甚至简历造假来谋取实习或工作机会。这无疑有悖于伦理道德,也扰乱了常规的招聘秩序,部分造假者也因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三)“残酷的乐观”抑或“不认输的韧性”
在竞争过程中,二本实习生被幻想激励但也同时饱受挫败。他们怀揣着改变出身的梦想,积极争取实习机会,希望为自己在今后的就业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然而,当实习结束,即便是二本学生中的佼佼者,预想中的留用通常也难以实现,学历依旧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高墙。在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看来,这正是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乐观主义提供了一种幻想,幻想为弱势个体提供心理满足的同时,也许下了某种承诺;一旦幻想破灭,个体会感受到一种被辜负、被抛弃的体验,经受挫败的同时也将面临严峻的情感危机(贝兰特,2023:71)。尽管有抱负的二本学生在入学后就开始寻找可以靠岸的码头,但当他们耗尽心力拿到若干亮眼的实习经历时,本以为靠岸在即,却猝然发现自己依旧难以企及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前路迢迢,障碍不少,这令他们深感挫败与沮丧。
但“残酷的乐观主义”并不能概述二本实习生情感历程的全貌。鉴于二本实习生展现的能动性,本文强调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不认输的韧性”。“残酷的乐观主义”强调梦想的幻灭,而“不认输的韧性”强调直面不利现实条件,在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中寻找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争取更好的结果,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善。“只有考研上岸,我才可以以自己的实力见人”(E-M-05)。“只有体制内才没那么看学历,与其在大厂惴惴不安,不如退一步,选择自己够得着的岗位”(E-M-12)。项飙曾用“认命但不认输”的人生观来鼓励当代华人青年移民,即正视环境及自身的局限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求改善的可能(项飙,任其然,2017)。在访谈中,笔者也能感受到部分受访者“认命但不认输”的心态,他们面对隐形实习的困境并没有就此“躺平”,而是不断争夺可见性,在可能范围内寻求破局的办法。
必须承认,对大多数二本学生而言,他们有着共同的焦虑。面对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不断缩减的优质岗位、愈发严苛的招聘条件迫使他们卷入“实习竞赛”。在此过程中,他们品尝过自身被认可的喜悦,也经历过隐形实习带来的迷茫与焦虑,在遭遇挫折与失败时仍心有不甘。尽管前面障碍重重,但依然不乏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二本学生在实习中积极主动地争夺可见性,不断证明自己以构建自我认同。就像一位二本学生在自传里所言:“二本也好,名校也罢,在漫长的人生当中,迷茫可能只是一个小坎而已,越过这个坎可以看见更美的风景。选择有很多,可能会做错,但是努力没有错,不努力才是罪过。”(Y-F-02)■
注释
①本文依据2023年广东省各高校招生官网公布的招录人数进行统计,地处广东的二本院校在广东地区录取20.4万人。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2023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本科录取人数33.09万人。
②2014年全国开始本科批合并。在本文中,二本院校指在2013年以前以第二批本科录取分数招生的高等院校。
③在24名访谈对象中,小新、舒灿、博宇、希尧、万霖、子澄的实习故事相对具有代表性,他们故而成为本文的“主角”。每位受访者按照“二本学生(E)+性别(男性为M,女性为F)+序号”的方式进行编码,如“E-F-01”表示序号为01的女性二本学生。访谈提纲包括:(1)实习前的挣扎与纠结;(2)实习期间经历隐形实习的心酸;(3)冲破隐形实习的尝试;(4)实习结束后的计划。
④每位二本学生的自传不少于1000字。自传编码的方式为:自传获取方式(发出邀请信的编码为Y,邀请访谈对象而获取的自传为D)+性别(男性为M,女性为F)+序号,如“Y-M-01”表示序号为01的男性二本学生自传。
参考文献
曹璞,姚卉(2024)。“刷简历”:新媒体实习生的生命时间管理与劳动同意制造。《中国青年研究》,(1),102-110。
黄灯(2020)。《我的二本学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贾文娟,钟恺鸥(2018)。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社会学研究》,(6),159-185+245。
劳伦·A·里韦拉(2019)。《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江涛,李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劳伦·贝兰特(2023)。《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李伟,邬志辉(2023)。“开窍”与“自救”:基于网络民族志的“二本学子”学历突围历程研究。《中国青年研究》,(6),62-69+61。
卢回(2020)。我是二本毕业生,我觉得自己在走钢丝。“我要WhatYouNeed”微信公众号。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y6VVimqmk_7BFP9OfPHlvw。
迈克尔·布若威(2008)。《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宁瑜(2023)。从大一就开始卷实习的大学生们,后来怎么样了?《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4wl4fsTsjzr-GqzYrOSaRQ。
牛静,赵一菲(2020)。“倒贴钱”的实习如何可能?——新闻媒体实习生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与“理想游戏”。《新闻与传播研究》,(4),58-75+127。
王程韡,杨坤韵(2019)。进取与迷失: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社会》,(3),93-122。
吴清军,李贞(2018)。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社会学研究》,(4),137-162+244-245。
夏冰青(2018)。中国媒介产业中实习生的困境研究:以S和X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例。《全球传媒学刊》,(4),116-126。
项飙,任其然(2017)。专访人类学家项飙(上):我们应该“认命”但不能“认输”。检索于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170430-opinion-xiangbiao。
晓谦(2021)。我就不信了,二本又不犯法。《南风窗》旗下微信公众号“勿以类拒”。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OGF5WeZ97Vjom0kBt0NxJA。
星野(2018)。我出身“二本”,为什么你们不看我的简历?《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EyWZcEYDkxG5yEWRRJP2fA。
徐巧丽(2023)。二本应届生的“假简历”。《搜狐新闻》旗下账号“极昼工作室”。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5Xo6e2WpkO0XpeLgTUd_Vw。
遇雪(2022)。为了逃离“毕业即失业”,我做了3个月厂妹。网易旗下账号“人间theLivings”。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wTtrZDHZZ6GEYu3wKpGU1g。
杨晓倩(2024)。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真实故事计划”微信公众号。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UlLvDPYJ9wj383HeOI72zw。
赵皖西(2020)。沉默的二本学生,才是基数最大的打工人。《新周刊》微信公众号。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9WrfBCdboOiCGj5ISvZjKw。
郑雅君(2023)。《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朱丽丽(2024)。985学子焦虑:优绩主义与社会结构下的精英困境。《中国图书评论》,(5),16-28。
Agenjo-Calderón, A.& Gálvez-Mu?ozL. (2019). Feminist economics: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78(1)137-166.
AshforthB. E.& KreinerG. E. (1999). "How can you do it?": Dirty work and 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dent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3)413-434.
BohrerA. (2018). Intersectionality and Marxism: A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26(2)46-74.
Brown, E. V.Jr.& deCant, K. A. (2014). Exploiting Chinese interns as unprotected industrial labor. Asian-Pacific Law and Policy Journal15(2)150-195.
CrenshawK. (1989).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1989(1)139-167.
Daniels, A. K. (1987). Invisible work. Social Problems, 34(5)403-415.
Dupriez, V.MonseurC.Van CampenhoudtM.& Lafontaine, D. (2012). Social inequalities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Influence of social background, school compo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1(4)504-519.
Elias, J. (2010). Mak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 visible: The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migr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7(5)840-859.
HattonE. (2017). Mechanisms of invisibil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invisible work.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31(2)1-16.
Lokot, M.& Bhatia, A. (2020). Unequal and invisible: A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to valuing women's care labor in the COVID-19 response. Frontiers in Sociology5588279.
Pearson, R. (2019). A feminist analy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austerity policies in the UK. Soundings(71)28-39.
RabeloV. C.& Mahalingam, R. (2019). "They really don't want to see us": How cleaners experience invisible "dirty" work.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13103-114.
Soni-Sinha, U.& YatesC. A. (2013). "Dirty work?" Gender, race and the union in industrial cleaning.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0(6)737-751.
WeidhaasAllison. (2017). Invisible Labor and Hidden Work.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1-10.
[作者简介]施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导,张国威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暨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数字游戏增强中国式现代化传播力影响力机制研究”(23JNQMX5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