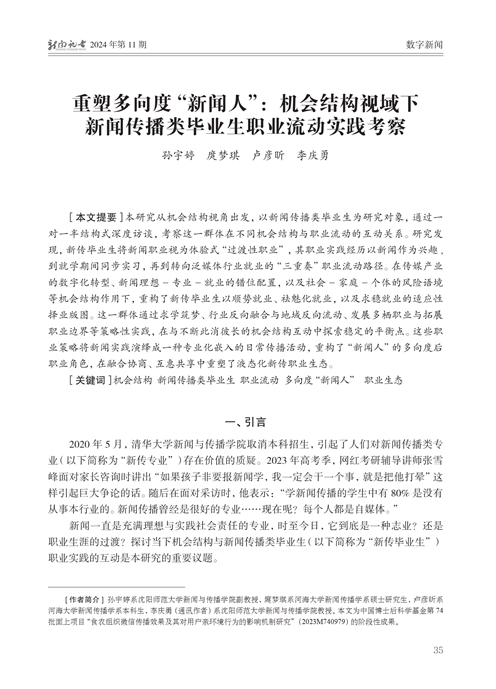重塑多向度“新闻人”:机会结构视域下新闻传播类毕业生职业流动实践考察
孙宇婷 庹梦琪 卢彦昕 李庆勇
[本文提要]本研究从机会结构视角出发,以新闻传播类毕业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一对一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考察这一群体在不同机会结构与职业流动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新传毕业生将新闻职业视为体验式“过渡性职业”,其职业实践经历以新闻作为兴趣到就学期间同步实习,再到转向泛媒体行业就业的“三重奏”职业流动路径。在传媒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闻理想-专业-就业的错位配置,以及社会-家庭-个体的风险语境等机会结构作用下,重构了新传毕业生以顺势就业、祛魅化就业,以及求稳就业的适应性择业版图。这一群体通过求学筑梦、行业反向融合与地域反向流动、发展多栖职业与拓展职业边界等策略性实践,在与不断此消彼长的机会结构互动中探索稳定的平衡点。这些职业策略将新闻实践演绎成一种专业化嵌入的日常传播活动,重构了“新闻人”的多向度后职业角色,在融合协商、互惠共享中重塑了液态化新传职业生态。
[关键词]机会结构 新闻传播类毕业生 职业流动 多向度“新闻人” 职业生态
一、引言
2020年5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取消本科招生,引起了人们对新闻传播类专业(以下简称为“新传专业”)存在价值的质疑。2023年高考季,网红考研辅导讲师张雪峰面对家长咨询时讲出“如果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干一个事,就是把他打晕”这样引起巨大争论的话。随后在面对采访时,他表示:“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中有80%是没有从事本行业的。新闻传播曾经是很好的专业……现在呢?每个人都是自媒体。”
新闻一直是充满理想与实践社会责任的专业,时至今日,它到底是一种志业?还是职业生涯的过渡?探讨当下机会结构与新闻传播类毕业生(以下简称为“新传毕业生”)职业实践的互动是本研究的重要议题。
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一系列新兴媒体的出现,冲击着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机制和传播结构。从2006年到2021年,美国受雇于报业的人数下降了70%,其中新闻编辑室的员工数量减少一半以上,从7.5万人下降为不到3万人(常江,罗雅琴,2023)。传统媒体的式微未必带来数字媒体从业人员的增长,新闻作为一个“职业”的不断萎缩也引发学界与业界对新闻从业者的担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逐渐发展壮大。过去,新传专业学生趋向于精准就业,就业流向较为单一,主要是进入各省市县级媒体单位从事新闻报道或宣传工作(范玉吉,2018)。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单一型人才供需链断裂,时代对复合型、实践型、专业性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形成了日趋多元的职业结构和职业类型。自2014年中国媒体发展进入“融合元年”,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导致传统大众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多以裁员、压缩招聘岗位数额、停刊或者减少出版期数等方式维持企业合理化运营,应对危机。中国持证记者人数也从2014年的25.8万人降为2021年的19.4万人(中国记协网,2014,2022)。新传专业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不再仅限于传统媒体,就业对口率仅保持在20%左右(陶建杰,张志安,2018)。截至2022年,全国有719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包括编辑出版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学等十大专业,全部1391个专业点,29万余名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在新传专业毕业生数量急剧增长与传统媒体就业市场不断萎缩的矛盾中,依托互联网的新业态,新闻职业的边界被打破,新传毕业生的职业流动范围扩大,并呈现多元化态势与泛化的就业特征,泛就业已成大势所趋。
社会转型带来机会结构的转变。不同行动者做出的个体选择与行动受制于结构提供的机会与约束,而个人行动也以自己的方式改变和形塑结构(Merton,1957)。新传毕业生的就业与媒体行业大环境紧密相连。新媒体环境下,从业者的职业性质、职业类型和职业流动具有“转型”意涵(丁方舟,2016)。特别是当下泛媒体化就业已成为趋势,职业流动便成为一种常态。因此,本研究以新传毕业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过程性职业流动切入,从机会结构视角探讨这一群体的职业选择面临怎样的结构性限制与开放性机会?他们如何通过策略性的职业流动实践来突破既有机会结构?最终形塑出怎样的群体性职业生态?本研究为理解新传毕业生的职业流动行为,并将结构限制转化为机会提供策略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机会结构理论及分析框架
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是西方学者解释社会运动发生与演变机制的重要分析工具。默顿将“机会结构”界定为行动的个人和群体实现可指定结果提供各种可能性条件的规模和分布;这些条件包括获取各类资源的条件、获得合法性活动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优势等(Merton,1968)。机会结构强调客观环境对行为的塑造作用,同时新的行为方式又进一步推动结构性要素的改变和重塑(文宏,戚晓雪,2016)。机会结构具有动态性,一方面,结构中的机会和结构性限制是互补的概念,二者此消彼长,受限制的机会会成为约束,限制越少机会越大(Merton1968);另一方面,机会结构在不同的制度结构、经济环境和文化语境下会不时地扩张或收缩(徐媛媛,2023)。因此,区别于从单一层面观察社会现象的概念或理论,机会结构理论重视对社会结构中为特定结果提供可能的各种重要条件的总体性把握,各种机会要素的结构性组合共同构成了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外在环境(张海柱,2021)。20世纪70年代后,机会结构理论逐渐发展出政治机会结构(Tarrow,1988)、经济机会结构、文化机会结构、话语机会结构等重要概念和分析框架(陈阿江,罗亚娟,2022)。
政治机会结构是行动者所处的体制结构和制度环境当中利于集体行动展开的因素(卜玉梅,周志家,2015)。制度结构是行动者资源获取的重要保障,碎片化的制度执行环境能够为行动者创造更多的机会空间;既定的社会位置不仅影响了行动的策略,也影响到行动者所能获得的、可能的资源水平和类型,决定了他们所能利用或开启的机会结构(Spires,2011)。经济机会结构关注特定经济背景下的机遇和限制,包括市场供应情况(Koos,2012)、国家经济结构(Ergas & Clement,2015)、资本积累和分配,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Pellow,2007)等要素。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市场化背景下,经济机会结构以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的形式,深刻影响着特定群体在劳动市场上的行动选择和生存发展,从而推动了职业流动(任远,1997)。文化机会结构关注行动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包括普遍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系统等,以及在与行动者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价值的重塑和引导(Ferree et al.,2002)。话语机会结构是包括政治和社会文化要素在内的“特定社会中的观念框架和意义制造机制”(Ferree et al.,2002)。当行动者面临机会结构的约束时,策略性的话语框架建构或重构有助于实现机会空间的拓展(张海柱,2021)。文化与话语机会结构在理解和预测个体行为的同时,也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在与其他机会结构要素和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也重塑了原有的文化价值和话语体系。因此,从机会结构分析框架出发,探讨何种结构限制和开放机会影响新传毕业生的职业流动,成为本研究分析的重点。
(二)机会结构与新闻人职业流动实践
媒体融合在推动中国传媒业行业形态、组织结构、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同时,引发了传播环境、信息消费、社会文化的根本性变化。相应地,作为新闻人的新闻从业者和其后备力量的新传学子,其职业实践也受到来自传媒产业变革的结构因素与开放机会的双重推拉影响。
影响新闻人职业流动的外部结构性因素,相关研究主要从制度、技术和市场等方面进行探讨。(1)互联网技术、媒介融合的飞速发展暴露出传统媒体体制的禁锢。传统媒体对新闻生态系统的垄断权逐步消解,融资渠道受限和资源不断流失,难以保障其机构成员必需的资源与制度性手段(丁方舟,2016)。而为了顺应数字化转型,传统新闻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繁重的工作负荷,弱化了新闻行业的职业自主性(Reich & Hanitzsch,2013),直接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何映霏,李龙飞,2022),加剧了新闻实践的常规变动。(2)在算法技术和速度驱动的新媒体新闻产制逻辑与消费模式下,虚假新闻大量生产,威胁着新闻从业者实现新闻价值的制度化手段(丁方舟,2016),导致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和社会价值受到质疑(Goyanes,2020;Figenschou & Ihlebak,2019)。自媒体时代的新闻职业典范远不如传统新闻从业者对于新传学子的吸引力(彭增军,2017;陶建杰,尹子伊,王凤一,2021)。(3)传媒产业的变革导致就业市场对“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蔡雯和翁之颢(2016)的研究发现,不仅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进程中对新传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同类型新媒体根据自身定位对人才需求也呈现差异。而当前新传院校的人才培养普遍滞后于业界需求。
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重塑着中国新闻生态系统,也带来了开放的媒体职业生态。已有研究表明,行业泛媒体化、体制外薪酬待遇、媒体实习经历、文化语境等开放机会,为新闻从业者和新传学子寻求自主性新闻实践开创空间。(1)行业泛媒体化。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市场化的就业趋势,网络新媒体行业与体制外新媒体岗位出现职位空缺链,传媒行业的生存空间得以拓展,也成为新闻从业者寻求自主性的选择(陶建杰等,2021)。(2)体制外薪酬待遇。相较于传统媒体对人才需求的下降、工资待遇增长空间狭小,收入与付出难以成正比,体制外丰厚的薪资待遇更能吸引新闻从业者从传统媒体组织向新的数字化生产场域流动(周人杰,2018)。(3)媒体实习经历。韩晓宁和王军(2018)研究发现,相当数量的新传学子通过在媒体行业实习掌握国内新闻业实际就业信息,以此对自己的职业志向重新进行规划。新闻工作也因此被视为“过渡性职业”(陶建杰,张涛,2016;陶建杰,张志安,2018)。(4)文化语境。数字技术重塑着传媒业的文化结构(常江,罗雅琴,2024),一方面,“泛媒体就业”重构了新闻职业生态,在各种泛媒体平台就业并进行信息传播,已被视为中国传媒事业的组成部分(范以锦,2017)。另一方面,在新闻从业者群体与其他社会实体的互动协商中,新闻职业话语被共同建构。“新闻职业”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以“职业为中心”的传统新闻生产体系被解构与重构,“新闻人”(news people)取代职业新闻从业者,成为对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主体泛化的“后职业”指代(常江,罗雅琴,2023)。
新闻人的职业流动不仅是在媒介技术与行业环境变迁驱动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更涉及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对于新闻文化价值的追寻与取舍。随着相当规模的新传毕业生进入商业互联网公司、各类传播平台、自媒体人公众号,以及党政机关等事业单位,并从事内刊、网站或账号运营、舆情分析、市场策划、品牌推广等泛媒体岗位工作,就业理念和新闻人才培养理念在“泛媒体就业”的职业生态驱动下得以重构(范以锦,2017)。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新闻从业者和新传学子两类群体的就业现象,包括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及其影响因素、职业流动类型、群体特征,以及新传学子身份认同和从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而对新传毕业生这一群体的能动性职业实践与机会结构的互动过程,以及他们如何通过策略性行动重塑职业结构仍有待探究。
因此,从机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视角出发深入探究新传毕业生职业流动的复杂动态过程,能够为其职业定位与发展路径提供新的可能性。据此,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1)新传毕业生的职业经历了怎样的流动性实践?(2)机会结构中的机会与限制性因素如何影响这一群体的职业实践?(3)在职业实践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行动策略创造机会,重塑既有结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关注新传毕业生的职业流动,以新传青年就业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立意抽样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4月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规定:青年的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青年年龄上限可以延至35岁,甚至40岁(吴端,2009)。由于本科毕业年龄大概22、23岁,博士毕业30岁左右,本研究综合考虑家庭环境、教育程度、不同教育阶段主修专业、工作类型,以及青年群体职业流动周期等因素,在保证样本多元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年龄设定在22岁到40岁之间。访谈以滚雪球方式获得样本,先以中国东部J省一所综合性211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已经毕业工作的几位学生及青年教师为访谈对象,再经由他们引荐新的受访者,直至资料饱和为止,共访谈21人(表1 表1见本期第39页)。访谈自2023年8月进行至2023年11月,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研究者以录音方式进行,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每次均超过1小时,并对期间内有职业流动的受访者进行追踪访谈,访谈后整理成逐字稿,以探究不同机会结构与这一群体职业实践的互动关系。
四、结构限制与机会开放重构择业版图
本研究受访者普遍经历了以新闻作为兴趣,到就学期间同步实习,再到作为生存考量转向其他行业正式就业的“三重奏”职业流动路径。在传媒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闻理想-专业-就业的错位配置,以及社会-家庭-个体的风险语境等机会结构作用下,重构了新传毕业生以顺势就业、祛魅化就业,以及求稳就业的适应性择业版图(图1 图1见本期第40页)。
(一)新闻业-泛媒体化:数字化转型推动顺势就业
新闻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新闻生产逻辑的改变对传统新闻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传统新闻机构所依赖的运作模式难以为继,组织内部的人事制度限制了新闻从业者的晋升空间,休息时间不固定、体制内的劳动法“隐身”;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与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技能、工作强度和日常工作节奏都远超大众传媒时代,投入产出严重失衡,职业过劳成为普遍常态:
回报其实不是特别高,传媒领域的话,其实在薪资方面都要比很多专业要低。(A4)
毕业进入地方广电,8年工作经验。熬夜加班没有休息,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要时刻准备战斗。(A10)
新媒体的发展使各行各业泛媒体化,岗位需求和人才需求量大,薪酬待遇相较于传统新闻产业具有明显优势,合理化了青年新闻从业者从传统新闻产业向泛媒体行业的流动:
传统新闻媒体工资低,晋升渠道不足,新媒体和互联网行业给了一些机会,但也会选择其中与新传相关的工作,比如互联网运营。(A9)
新媒体行业算是这个专业本科毕业给到的薪资里比较高的了。(A13)
科技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加速,新闻业也进入加速生态(涂凌波,赵奥博,2022)。加速社会下新闻生产逻辑逐渐肤浅化、流水线式,让“快消”新闻的产制合理化,导致新闻价值式微,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成果被数据异化。“以前十天推送一次,现在一天推送十次,哪里能做得出有价值的新闻,基本都是套模板,但是考核还要和流量挂钩,这就是悖论。”(A13)
在流动性高的互联网行业热情消耗得很快,很容易出现倦怠,而数字化下的新闻产业对从业者的职业热情要求越来越高,也呈现出“热消”趋势。热情已不再单纯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规范,而是转变为对新闻工作日常实践的要求,新闻热情已被商品化(Dawson et al.,2023;Lindén et al.,2021)。“我们部门对人才的要求是能具有可持续性的热情+活力,年轻人刚进来都热情洋溢,待个两年就扛不住了。热情一旦不可持续,就要离职了。在互联网大厂,热情是可以兑现的,但在新闻产业里,这是义务,是践行新闻志业的责任,志业怎么能用薪酬衡量呢?”(A10)在普遍低薪+超时工作的环境下,部分青年新闻从业者选择从媒体向泛媒体进行职业迁移。
数字化下的传媒产业对从业者新媒体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呈现出不断追赶的“技术至上”趋势。部分受访者表示掌握编程技术更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从事新媒体行业需要具备技术化生存的技能,包括媒体多元技术、科技多元技术以及议题多元技巧(刘蕙苓,2020)等,以增强自身竞争力减少被裁员的风险。A13就指出,“要不断追赶与学习很多新技术,不然就会被淘汰,但是文科生对新技术的掌握是很吃力的,长久下去会吃不消”。这也预示着,新媒体时代一旦停止或放缓学习便会面临随时被取代的隐患,而长期高度紧张的状态也意味着不得不选择职业流动。由此可见,在传统媒体式微与行业泛媒体化推拉下,在专业相近领域寻找学以致用的工作“顺势就业”,成为多数新传毕业生的职业选择。
(二)理想-专业-就业:错位配置下的祛魅化就业
新传专业具有理想性、包容性与泛化性。其理想性表现在个体对专业的兴趣、对新闻理想的志业追求、对技术与对职业可选择性的想象。如A13表示:“转专业前就特别羡慕那些拿单反、扛录像机拍摄的新闻系同学,很有范儿。我们学的课程相对接地气,很多都是经验得到的有趣议题,拍摄也都室内。”A2也认为,“会特别关注一些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现象,也特别想通过深度报道来为他们发声”。其包容性表现在,专业知识的介入门槛较低、容易上手,文科理科都能学得懂,如A8和A19均是理科背景,硕士才转向新传。其泛化性表现为缺乏专业壁垒,既不需要提前付出可见性代价,又不用像文史哲类专业的可见性失业,可就业岗位的泛化也意味着职业与薪水的平庸,以及个体在劳动市场上的可替代性。“不需要像土木一样风吹日晒,施工驻队、出差,不像学计算机的去爆肝当码农,也不像医学生辛苦随时都要动手术卷入医患关系。差不多毕业,你能够得到的也就是差不多的工作,拿着差不多的薪水”(A13)。
然而,由新闻理想驱动的新闻价值逐渐在后真相时代消解,无论是资深新闻工作者还是刚就业的受访者都表示,实践个体新闻理想不再是就业的考量。“想走这条路的,谁还没个新闻理想,但是现在就业环境这么差,情怀不能变现的”(A1)。“95后”相对来说在职业实践中更为大胆,部分受访者表示毕业后因为新闻理想入行,但实践后发现新闻体制背后的种种限制而选择离职。一些受访者通过读书期间在媒体机构实习来实践新闻理想,但不会选择从事新闻业作为正式职业,只是作为步入职场前的过渡性选择,个体期望通过可试错的流动机会来寻求自身的职业定位。“如果单纯想锻炼,进入媒体行业实习就可以了,实习是个试错的好机会,这样我们这些一直在象牙塔里的小白才能心甘情愿放弃理想面对现实”(A16)。专业泛化与低职业回报祛魅化了个体实践新闻理想的意志,取而代之的实习机会能够让个体在体验试错过程中明确职业志向,进而在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之间做出选择。
(三)社会-家庭-个体:风险语境建构的求稳就业
在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中,稳定职业与社会倡导的理性、体面、有闲、孝道等价值观不谋而合。面对新传人才数量急剧增长与体制外职位趋于饱和的矛盾,体制外的不稳定性日益凸显,机会又转变为约束,驱使他们重回体制内寻求未来的安全感(陶建杰等,2021)。考公、考编成为不少年轻群体梦想的“职业终点”,年轻人开始像父辈一样自发认可“铁饭碗”的价值。正如受访者A20所言,“这两年就业环境真的很差,文科生在我们省顶多就6k+,我读研的意义在工资面前大大折损了,现在工作又不稳定、朝不保夕,互联网裁员多疯狂啊……家里人都劝导说女生嘛选择安稳点的好”。A12也表示,编辑的工作性质并没有因从文案到视频的转换而发生改变,每天伏案经常加班,自己身体吃不消,父母希望她去体制内,自己还在纠结中。
抓住时机及时转向,即便从基层做起,晋升和涨薪很漫长也不敢退出。如A21所述,“本科毕业就签了国企,工作一年不喜欢那种环境,想着及时转型,还好那时候年轻,从最开始的月薪2000多到现在7000多,疫情期间去驻村,半夜两三点起来做志愿者,没外面想的那么轻松。现在办公都要电子化系统,很繁琐,经常加班,就慢慢往上爬吧”。
考公考编看似是逃离就业市场的一种选择,但全身而退去备考又面临经济压力、家庭期待和未知性风险,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青年,暂缓流动和获得体制外的稳定也成为权宜之计。“不到万不得已,我应该很难有勇气辞掉工作去待业备考。如果我还在读书,可以全身心投入还有充分的时间备考……但现在这个年纪恶性循环也会比没有收入好”(A13)。可见,考公和考编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年龄危机已经成为可雇佣性提升的限制因素,很可能以失去就业能力为代价,却不能换来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同时,备考期与社会“脱节”也会陷入再就业的困境,其存在退出机制的再失效(何海清,张广利,2022)。由此,体制外的不确定性、就业市场的话语渲染、家庭期待的牵引,以及个体对可雇佣性的担忧等风险综合作用下,重构了新传毕业生以求稳为核心的适应性择业版图。
五、多向度策略选择重塑职业生态
本研究的受访者将个体对职业的担忧限制转化为不断进行职业实践以寻求个体新的发展机会空间,并通过向上求学筑梦提升可雇佣性、行业内向下扎根的反向融合与地域反向流动获得晋升机会,以及“以自我为企业”向外延展职业空间进而实现自我成就感等多向度策略,在既定结构框架下主动为自身寻求更多维度的发展可能性,重塑出液态化的新传职业生态。
(一)以求学筑梦超越内卷化速度
在当下社会,没有文凭越来越不利于职业嵌入(玛丽·杜里-柏拉,阿涅斯·冯·让丹,1992/2001:59-60),同等硕士学历下的第一学历非211本科又普遍会受到雇主歧视(李彬,白岩,2020)。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年扩招,学历越来越贬值。面对变动迅速、竞争激烈的新闻专业就业环境,近年来,高等教育特别是新闻传播研究生的扩招成为机会,大部分新传毕业生都会以直接读研或工作几年再考研的形式来自我增值,提升可雇佣性。多数受访者表示不仅要在求学时期突出学业表现,拿奖学金、发论文,更要多把握实习机会、组织参与策划活动积累经验、扩展人脉等社会资本。一些受访者在读研时已经感受到整个就业形势对文科生的不友善,一入学就要拼命实习来缓解对未来可能面临失业的焦虑。他们需要学历,更需要有可以赶超时间的速度。读书学知识并非本体,能否在用人单位提升门槛、具备更高竞争力才是受访者追求的。
但提升学历仍旧难以赶超社会变化速度,以读书推迟就业,以时间换取学历,时间推迟与个体增值效应抵消后的增量被放置在整体增值的社会中依旧黯然失色。“本科毕业就能进的企业,等读完三年硕士后门槛也要求是硕士学历了”(A17)。而家庭资源丰富的子女能够通过“先体验,再生产”的形式进行职业实践,即便慢速就业,也会以家庭作为托底。如受访者A4在国外留学时以慢节奏体验不同文化,毕业后也以“松弛感”的节奏来实践流动式就业,更关注在提升学历和经历阶段性就业过程中的个体感受,在不与社会脱轨与追求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寻求平衡。
面对文科专业在就业市场上的整体劣势,受访者普遍意识到学历逐年贬值带来的择业层次“下移”,在机会结构与个体职业实践的张力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宜关系”,以抓住求学筑梦机会,通过学历覆盖的方式扬长避短,暂缓步入职涯的时间,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二)以行业深耕争取融合与流动
尽管新闻业泛化,但还是有受访者表示会选择留下并继续“深耕”,这一群体以职业明确的跨专业者和30岁左右的青年为主。如A8表示当初义无反顾地从医学转为新传专业,此后便一直扎根媒体行业,其所在部门也在积极拓展与新媒体融合的业务,收入和前景都较为乐观。
相较于年轻刚毕业的受访者,30岁左右青年的试错机会有限,其可雇佣性随着年龄逐渐折损。受访者普遍表示不敢过多地投入精力和时间在职业流动上,在职业选择上会存在路径依赖。因此需要权衡经济、家庭以及晋升等因素,即便流动也会在其所“深耕”的领域内,基于利益最大化开展职业流动实践。A13和A15表示深耕多年的领域很难转行,但迫于在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与职业瓶颈,同一行业内部或同一机构的跨地域反向流动也是可行的降维折中策略。由此可见,权威媒体行业的工作,其工作稳定性高便意味着流动性小,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与规律性的日常工作放大了职场阶层感(何海清,张广利,2022),也意味着升迁的困难。因此这一群体选择继续向下扎根与深耕并寻求反向融合与流动来突破职业瓶颈,获取新的机遇和职业晋升空间。
尽管个体在领域内深耕基础上的反向融合与反向流动策略是一种折中适应性职业选择,但却推动了媒体资源在行业与空间维度平衡发展的可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亟需吸纳在传统媒体领域深耕的资深媒体人,以弥补新媒体自身的制度性缺陷(张彩霞,张涵,2022),二者在人才流动中形成了“双向融合”的职业传播生态。同样,相较于媒体资源向大城市集聚的行业生态,地方媒体在资源配置、市场影响力、人才吸引、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地方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进程滞后;而资深新闻从业者的地域反向流动重置了媒体资源的再分配,进而形塑出“互惠共享”的跨地域职业生态格局。
(三)“以自我为企业”的多栖布局与边界延展
“以自我为企业”是指劳动者像经营一家企业一样经营自己,通过技能、经验和职场人脉等方面的积累,以提高自身的“可雇佣性”(Barley & Kunda2004)。部分新传毕业生会在求学期间抓住当下流行趋势并激活自身技能优势,从善用专业技能实践多栖兼职变现,到打造正式副业,再到拓展职业边界。在这一过程中,内在的自我成就感是他们职业可持续经营的关键动力。
一些受访者在求学期间以经营网店、帮人设计海报、进行PS等图像处理赚一些零花钱。如A3表示,“最开始就是给学生会举办活动设计海报,后来他们觉得我做得好,又认真负责,就开始把我推荐给其他需要的同学朋友,在边学边赚钱过程中慢慢就上手了”。受访者A6也提到,“现在陪拍(陪人打卡、拍照)成为一种趋势,准入门槛较低,只要有设备、审美和技术,就可以去开创这个副业,还能发展一下自媒体账号积累粉丝量嘛”。可见,对于掌握相关技能(拍摄、剪辑、运营思维)的新传毕业生来说,社交媒体平台是一种机会,其弱连接的社会资本可触达不同社会群体,技能驱动帮助自身积累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实现自身增值。
一些受访者通过多栖弥合职业缝隙提高自身技能与社会资本,为日后将兼职流动转变为自主创业策略提供可能。如A11从做美术编辑积累设计经验,到成为苹果周边配置供应商;A18从求学期间接拍广告积累资金和客户源,到毕业后创立工作室,同时又额外保持一份清闲的工作来应对风险;A4从传统文科生到国外修读计算传播学的第二硕士,从在电商平台接数据处理单子赚取生活费,到抓住时机回国组建团队创业变现,再到不断拓展校企合作业务,实现文理双栖的边际效益。此外,高校青年教师A4善用跨学科背景开拓交叉领域,以此经营自身的学术多栖之路。
新的职业前景对新传青年创业者来说充满了机会,但也面临着当下的瓶颈期和未来的不确定性。A19毕业后同时也签约了互联网公司,但因为不稳定性而面临裁员危机,决定把考研教辅变为主业。“考研辅导做到一定程度,特别是一直做线上就很难有突破了,现在一方面在扩大业务体量,另一方面和我的合伙人一起成立自修室”(A19)。新传创业青年在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和行业口碑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布局其他相近领域的策略,不断拓展新的职业生存空间。A19也表示出创业过程的艰辛,“你感觉总是一个人在战斗,随时可能撑不下去”。当流动成为职业常态,创业者与成员之间就形成了流动式协作关系,如何在易变性的机会与结构之间“以自我为企业”便成为创业者不断探索新职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必修课。
多栖副业布局与延展职业边界后的创业实践虽然超越了传媒产业的边界,但新传毕业生仍以专业性为中心、以自我为企业开展多向度职业实践探索。他们通过对专业技能的善用、专业知识的内容生产和新媒体的运营传播等开启“液态化”生存技能,解构了传统意义上“以职业为中心”的新闻生产边界,向内延伸与向外拓展了“新闻人”的职业生命线,新闻职业实践也转变为专业化嵌入的日常传播活动。
六、结论、贡献与未来展望
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了新闻生产主体的泛化与各行各业的泛媒体化,模糊了以“新闻”作为职业的边界。新传毕业生将新闻职业视为体验式“过渡性职业”,其职业实践经历了“三重奏”的流动路径,即从以新闻作为兴趣,到就学期间同步实习,再到作为生存考量转向其他行业来实践正式就业。在传媒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闻理想-专业-就业的错位配置,以及在社会-家庭-个体的风险语境等机会结构作用下,重构了新传毕业生以顺势就业、祛魅化就业,以及求稳就业的适应性择业版图。这一群体通过向上求学筑梦、行业反向融合与跨地域反向流动、“以自我为企业”的多栖布局与延展职业生命线等多向度职业实践策略,超越时间、空间、行业和话语界限,力求在不断此消彼长的机会结构间寻找稳定的平衡点,重构了协商式液态化的新传职业生态。本研究的新传毕业生职业流动实践与机会结构互动关系如(图2 图2见本期第46页)所示。
媒介技术与传媒行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机会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个体的角色认知与职业流动。市场理性、算法理性和数据基础设施主导的认知理性,强化了新闻业中的认知范式(Schaetz et al.,2023),导致新传毕业生在求学期间的专业知识、新闻理想、素养技能与现实的新闻运作逻辑脱轨。一方面,面对传统媒体式微与新媒体产制逻辑对新闻价值的违背、高职位要求与低收入回报,以及难以突破的专业泛化瓶颈和需要不断追赶的技术门槛,祛魅化了这一群体对以新闻为志业的职业想象;另一方面,行业泛媒体化的宽口径、在校实习试错机会的增加、体制外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也推动着新传毕业生顺势所趋地从媒体向非媒体行业迁移、从在媒体行业实习到在非媒体机构的泛新闻化部门就业的职业迁移实践。这也印证了新闻被视为一种体验式“过渡性职业”(陶建杰,张涛,2016;陶建杰,张志安,2018),在新传毕业生重构择业版图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在与变动的机会结构互动协商中,新传毕业生多向度的职业实践策略不仅为个体寻求自主性实践开创空间,同时也重构了液态化的职业生态。20~30岁的新传毕业生或是通过求学筑梦提升可雇佣性,在加速与减速之间灵活自由地实践职业过渡期节奏;或是“以自我为企业”发展多栖职业,在“液态化”生存技能与策略性职业行动之间解构了以“职业”为中心的新闻生产体系,重构了“新闻人”的后职业性群体身份意涵。对于30+的群体,社会与家庭对职业风险的默会共识成为职业流动的缓冲,进而选择求稳策略;他们通过在行业反向融合与地域反向流动之间实现个体职业价值与外部资源的共享,重塑了融合互惠的新传职业生态。事实上,无论是在媒体或泛媒体行业就业,还是多栖布局副业到自主创业,抑或是退回体制,新传毕业生的职业实践仍以专业性为中心,在专业技能与个体职业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将新闻实践演绎成日常化的信息传播活动,重新编排出“加速-放缓-适应”的不同阶段新传职业实践节奏。这一职业实践过程拓展了新闻生产原有的话语边界,重构了灵活自由、双向融合、互惠共享、多元共生的协商式液态化新传职业生态。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一是丰富了机会结构理论在职业流动中的应用。特别是在当下传统新闻产业式微与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行业泛新闻化背景下,研究新传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二是本研究以新传毕业生的职业流动作为考察对象,研究结论可以推广到泛文科类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实践。在实践层面,本研究能够为新传毕业生的职业角色定位与发展路径提供新的可能性。即机会结构中的机会与限制因素并非总是矛盾对立,新传毕业生应该激活个体主观能动性,通过多向度的策略性职业实践将结构限制因素转化为机会,突破职业边界,以此在不断变动的机会结构环境中寻找职业流动的平衡点,为个体的自主性新闻职业实践开创空间。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在于,一是目前受访者的选取主要以研究者为圆心的拓展,受限于共同的学习环境,以及受访者之间的交集,未来将扩大受访者的样本来源。二是由于新传专业对口的公务员岗位不多,这也决定了这一群体的访谈样本较缺乏。本研究在公务机关工作的群体基本是刚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或是正在备战公务员考试的,前者处于迈入阶段,很难窥探出这一群体进入体制后的实际职业流动,尽管受访者当下表示“只要稳定就别无他求”,但若面对体制内未知的机会结构限制,又会有怎样的行动策略?未来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卜玉梅,周志家(2015)。西方“话语机会结构”理论述评。《社会学评论》,3(06),74-83。
蔡雯,翁之颢(2016)。融合转型的传媒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传播人才?——对近年传媒业人才需求状况的观察与分析。《新闻记者》,(12),13-18。
常江,罗雅琴(2023)。“新闻人”:数字新闻生产的主体泛化与文化重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119-128+171。
常江,罗雅琴(2024)。新闻实践的“开放时代”:技术成因、结构特征与文化反思。《中国出版》,(14),3-10。
陈阿江,罗亚娟(2022)。机会结构与环境污染风险企业迁移——一个环境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37(04),136-157+229。
丁方舟(2016)。创新、仪式、退却与反抗——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研究。《新闻记者》,(04),27-33。
范玉吉(2018)。泛就业时代的新闻教育。《青年记者》,(07),76。
何海清,张广利(2022)。青年考编现象中的职业想象与内卷实践研究。《中国青年研究》,(12),84-91。
李彬,白岩(2020)。学历的信号机制:来自简历投递实验的证据。《经济研究》,55(10),176-192。
刘蕙苓(2020)。自新闻业出走的抉择:数位时代的记者离职历程研究。《新闻学研究》(台湾),(144),49-96。
玛丽·杜里-柏拉,阿涅斯·冯·让丹(1992/2001)。《学校社会学》(汪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彭增军(2017)。权力的丧失: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人的职业危机。《新闻记者》,(09),65-69。
任远(1997)。社会变革、机会结构变动和职业流动。《社会科学》,(01),56-59。
陶建杰,张涛(2016)。上海地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国际新闻界》,38(08),116-133。
陶建杰,张志安(2018)。过渡性职业:新媒体环境下本科新闻学子的择业意愿及影响因素。《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0(09),160-168。
文宏,戚晓雪(2016)。政治机会结构与民众抗争行为的策略选择——基于兰州市宋村集体土地纠纷的案例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05),25-37+154。
吴端(2009)。青年的虚像与实像——对中国的“青年”概念原创时期特征的探讨。《当代青年研究》,(07),13-18。
徐媛媛(2023)。机会结构与高考专业选择。《中国青年研究》,(04),111-119+152。
曾丽红,吴雁(2015)。新媒体环境下大陆报业新闻从业者工作自主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个体特征变数的考察。《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34),19–55。
张彩霞,张涵(2022)。互联网平台媒体的反向融合逻辑与新传播生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4(02),154-161。
张海柱(2021)。风险建构、机会结构与科技风险型邻避抗争的逻辑——以青岛H小区基站抗争事件为例。《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10(02),31-44。
中国记协网(2014年12月29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全文)。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4-12/29/c_13388085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正式启动。检索于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11/t20221110_983029.html。
周人杰(2018)。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电视研究》,(06),50-52。
周睿鸣,徐煜,李先知(2018)。液态的连接:理解职业共同体——对百余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5(07),27-48+126-127。
BarleyS. R.& KundaG. (2004). Gurushired guns, and warm bodies: Itinerant experts in a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wsonN.Molitorisz, S.Rizoiu, M. A.& Fray, P. (2023). Layoffsinequity and COVID-19: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journalism jobs crisis in Australia from 2012 to 2020. Journalism, 24(3)531-559.
Ergas, C.& ClementM. T. (2016). Ecovillagesrestitutionand the political-economic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 urban case study in mitigating the metabolic rift. Critical Sociology42(7-8)1195-1211.
FerreeM. M. (2002). 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genschouT. U.& IhlebakK. A. (2019). Challeng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Media criticism in far-right alternative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20(9)1221-1237.
Goyanes, M. (2020). Antecedents of Incidental News Exposure: The Role of Media Preference, Use and Trust. Journalism Practice, 14(6)714-729.
KoosS. (2012). What drives political consumption in Europ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globalization. Acta Sociologica55(1)37-57.
Lindén, C. G.Lehtisaari, K.Gronlund, M.& VilliM. (2021). Journalistic passion as commodity: a managerial perspective. Journalism Studies22(12)1701-1719.
MertonR. K. (1957). Prioriti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6)635-659.
Merton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PellowD. N. (2007). Resisting global toxics: Transnational mov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mbridgeMA: MIT Press.
Reich, Z.& HanitzschT. (2013). Determinants of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Autonomy: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Level Factors Matter More Than Organizational On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16(1)133-156.
Schaetz, N.LischkaJ. A.& Laugwitz, L. (2023). Datafication of Journalism: How Data Elites and Epistemic Infrastructures Change News Organizations. Digital Journalism, 1-19.
SpiresA. J. (2011). 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7(1)1–45.
TarrowS. (1988).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4(1)421-440.
[作者简介]孙宇婷系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庹梦琪系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硕士研究生,卢彦昕系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本科生,李庆勇(通讯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项目“食农组织微信传播效果及其对用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2023M74097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