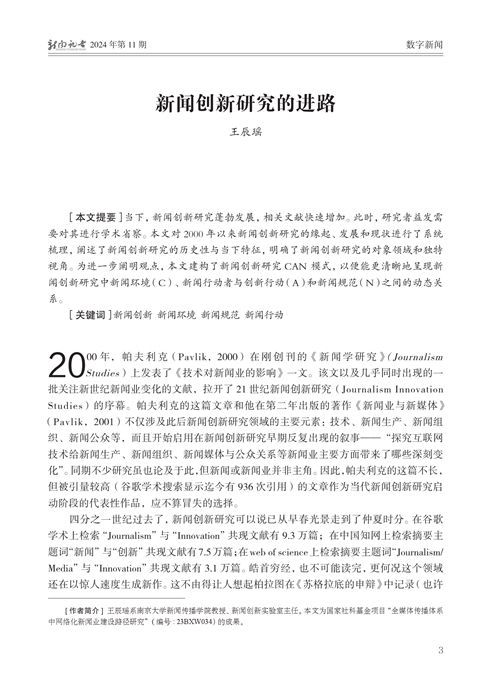新闻创新研究的进路
王辰瑶
[本文提要]当下,新闻创新研究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快速增加。此时,研究者益发需要对其进行学术省察。本文对2000年以来新闻创新研究的缘起、发展和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阐述了新闻创新研究的历史性与当下特征,明确了新闻创新研究的对象领域和独特视角。为进一步阐明观点,本文建构了新闻创新研究CAN 模式,以便能更清晰地呈现新闻创新研究中新闻环境(C)、新闻行动者与创新行动(A)和新闻规范(N)之间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新闻创新 新闻环境 新闻规范 新闻行动
2000年,帕夫利克(Pavlik,2000)在刚创刊的《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上发表了《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一文。该文以及几乎同时出现的一批关注新世纪新闻业变化的文献,拉开了21世纪新闻创新研究(Journalism Innovation Studies)的序幕。帕夫利克的这篇文章和他在第二年出版的著作《新闻业与新媒体》(Pavlik,2001)不仅涉及此后新闻创新研究领域的主要元素:技术、新闻生产、新闻组织、新闻公众等,而且开始启用在新闻创新研究早期反复出现的叙事——“探究互联网技术给新闻生产、新闻组织、新闻媒体与公众关系等新闻业主要方面带来了哪些深刻变化”。同期不少研究虽也论及于此,但新闻或新闻业并非主角。因此,帕夫利克的这篇不长,但被引量较高(谷歌学术搜索显示迄今有936次引用)的文章作为当代新闻创新研究启动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应不算冒失的选择。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新闻创新研究可以说已从早春光景走到了仲夏时分。在谷歌学术上检索“Journalism”与“Innovation”共现文献有9.3万篇;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摘要主题词“新闻”与“创新”共现文献有7.5万篇;在web of science上检索摘要主题词“Journalism/Media”与“Innovation”共现文献有3.1万篇。皓首穷经,也不可能读完,更何况这个领域还在以惊人速度生成新作。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记录(也许是虚构)的苏格拉底的名言:“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柏拉图,2017:83)或许,在新闻创新研究呈现出学术蓬勃发展、文献蔚然大观的繁荣景象时,我们更要有一番省察的自觉:新闻创新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有何独特性?能有何种贡献?等等。因为,一段未经省察的学术道路也是不值得研究者踏足的。
从历史到当下
有意思的是,新闻创新研究者们可能并不认为新闻创新是一个“新命题”。“新闻业的创新并不新”,普伦格和杜兹(Prenger & Deuze,2017)写道,新闻业在不断出现的新媒介(印刷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上持续改变。重要的不是去区分新旧媒介技术的差异,而应去理解那些在特定时刻或特定环境中引发新闻业变革的因素。他们将上世纪50到60年代出现的新闻创新“电视新闻杂志”(television news magazine)与 21世纪后出现的新闻创新“新闻创业组织”(news start-ups)并而观之,发现历史上的新闻创新和当下的新闻创新存在共同的发生因素,如公众和从业者对当前新闻的失望、新闻业内的激烈竞争,以及新闻创新者的个性特征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技术对于新闻业变革固然十分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正如创新理论大师克里斯坦森在企业创新中发现的同样问题:创新活动失败的原因,常常不是因为技术缺陷,也不是因为市场没准备好,而是创新部门的能力与业务不匹配(克里斯坦森,雷纳,2013:147)。
创新,在现代新闻业并不漫长的400多年历史上反复出现,持续塑造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新闻。譬如“采访”,这一现代新闻业高度依赖的工作方法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项19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的“发明”。早期新闻实践很少采用“记者正式向被访者提问并获得回答”这种形式,而多采用“旁听”、“记录”、“非正式交流”等方式获知信息。事实上,19世纪中期新闻界零星出现了“采访”这种创新做法后,有很多报人认为这不够体面,会破坏记者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关系。当时美国总统林肯经常与记者非正式交谈,却几乎没有记者会直接引用他的话。但采访对新闻工作的价值实在太大了,在它被发明出来以后,“这个想法就像野火一样”在全球新闻界扩散开来。1871年《纽约世界报》记者汤普森·库柏(Thompson Cooper)专访教皇庇护九世,成为新闻史上第一场被大张旗鼓宣扬的正式“采访”(Schudson,1994)。
“便士报”的兴起是另一场成功改写了整个新闻世界的创新。1833年9月3日,22岁的印刷商本杰明·戴在纽约创办了早报《太阳报》(The Sun)。当时,美国日报的价格一般是6美分,但《太阳报》一下子把价格打到了1美分。在《太阳报》之前并非没有试图走低价路线的报纸,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陷入到新创办报刊读者少,读者少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不能持续维持低售价的困境中。《太阳报》在商业模式上的真正创新并非低售价,而是本杰明·戴作为一个销售天才创造性地先在报纸上重印已经在其他报纸上刊登过的广告,再去说服尝到甜头的广告商,从而让这份新创报纸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可见,新闻业的创新是一条浩浩荡荡的“行动流”,本杰明·戴们是少数留下了姓名的引领者,更多人则是新闻业持续创新浪潮中的无名行动者。
再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被学界称之为“平民化”的新闻报道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新闻界的报道“语态”,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交流模式。《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的作者,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在回忆90年代以前的新闻时说,“很长时间以来,‘拽大词’、‘高八度’、‘排比句’串缀起来的新闻稿,成为事件‘重大’的一个典型标志,人们从不同的传播工具中听到看到读到的东西,会有惊人相似的语态”(孙玉胜,2003:43)。而1993年开播的央视《东方时空》(尤其是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定位的《生活空间》栏目)和1995年《中国青年报》创办的《冰点》专栏,引领了新闻选择标准的创新,从此“老百姓是生活的主体,也是值得报道的新闻对象”才成为普遍的新闻选题(沈欣,1996)。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于现代新闻业如何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发明”。回溯这些,正如《新闻的发明》一书作者、英国历史学家佩蒂格里(2022:423)在该书结语中提醒我们的:“如今生活在21世纪初这个动荡易变的多媒体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我们也许更容易明白为什么类似的多样化的新闻传播方式似乎完全适用于本书重点关注的四个世纪(指15~19世纪现代新闻业在欧洲诞生并逐渐扩散的这段历史)。”新闻创新,不是一个只关乎当下的、完全由新技术驱动的、“闪闪发亮”的新东西。拒绝去历史化叙述,对新闻创新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打通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不仅可以避免一叶障目的狭隘、沉淀对新事物的狂欢和悸动,更重要的是,它赋予当下的新闻创新研究总体性的问题意识:新闻从来处来,往何处去?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文化形式之一的“新闻”将如何变化,因何变化,有何影响?行动者可如何作为?由此展开的探索,也只有在从新闻的历史演化到当下的新闻创新这一脉相承的思路中才能生动浮现。
当然,21世纪的新闻创新与此前毕竟有很多不同。也只有到了21世纪,甚至是最近15年来,“新闻创新”或“媒体创新”才“突然”成为描述当下急剧变化的新闻现象的统合性概念。如白红义(2018)认为,可把与新闻业的变迁、转型、改革等有关的现象统称为新闻创新,把“创新”作为理解新闻业变迁的透镜。可见,新闻环境剧烈的、系统性的变化,对原有新闻业结构、实践和关系网络造成的密集冲击,不仅产生了“新闻业危机”这一全球现象,也召唤出“新闻创新”这一全球行动。“新闻业危机”话语(Journalistic Crisis Discourses)肇始于美国,研究者较普遍地引用2009年美国皮尤报告数据(Pew,2009),把2008~2009年间美国报业收入下滑23%作为当下新闻业危机开始或明朗化的标志(王辰瑶,2018)。尽管程度和表现有所不同,但其他国家和社会的传统职业新闻很快也感受到技术、经济等因素带来的巨大冲击。以至于研究者认为,(传统)新闻业在收入、吸引力、自主性等多个方面陷入困境的事实“已经无需讨论”(Picard,2011)。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全球新闻界和研究者会不约而同用“危机”(crisis)一词而不是别的词来描述这一现象?吉特林注意到,这是因为“危机”远比一般意义上的“问题”要严重得多(Gitlin,2011)。泽利泽认为,启用“危机”一词,不仅传达了“我们对事物可能展开的方向一无所知”的感受,而且表明这一状态迫切需要干预,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Zelizer,2015)。普遍且紧迫的“新闻业危机”必然要召唤出集体性反应,也即作为“不确定的救赎”的新闻创新(王辰瑶,2016)。
由此,21世纪的“新闻创新”的突然出现和被集体命名,本身就是危机驱动的结果。这既促使当下新闻创新研究快速走向繁荣,也给它招致不少问题。在新的数字媒介环境中,新闻业的创新越来越关乎生存(Nunes & Canavihas,2020),因此,新闻创新无论是作为行动方案还是研究前沿,似乎都无需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但这也导致新闻实践和研究中的“创新”话语被使用得过于广泛,而缺乏真正的共识(Posetti,2018);新闻创新行动的紧迫性亦传导到研究中,产生了大量对新闻媒体“如何反应”的描述性论述,但也存在理论化程度不足的缺憾,以及因为捕捉的经常是行动者的“即时反应”,导致一些新闻创新研究给人留下一直在追逐(不同的)新事物但缺乏对变化持续性观察的印象;此外,这一轮集体性新闻业危机最直接的动因是数字技术,最明显的压力是传统新闻组织能否在经济上存续,因此这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完全可理解的,让当下的新闻创新研究带有很强(也许是“过强”)的技术和商业色彩,比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新闻创新研究的核心是帮助新闻业更好地开展基于技术的商业应用(Ainamo,2006),但这就过分窄化并矮化新闻创新研究了。
由此,我们不得不自省危机驱动下21世纪新闻创新及其研究“繁荣”与“脆弱”并存的现状。虽然新闻创新研究的“表征”经常着落在具体新闻组织、新闻生产方式、新闻文本形式、新闻创新项目的成败上,但其问题的“本质”应超越具体新闻项目和组织的生存危机以及为新闻业自身发展的“谋划”。正如佩蒂格里给《新闻的发明》一书起的副标题是“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回溯历史与当下,新闻业应被视为人类社会公共交往空间中一项重要的认知制度。研究它曾经、正在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造成改变的因素以及这样那样的持续变化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其意义不仅在于新闻业自身,更在于这一公共认知制度与全社会福祉的紧密关联。
从领域到视角
当21世纪新闻业的整体性危机召唤出进入新闻领域的大量新行动者和新行动,当研究界对新闻业外部和内部变革的关注愈发集中,新闻创新研究不再散落于数字时代之前新闻学的各条脉络,而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谈及“领域”是颇有争议之事,似乎有着某种“跑马圈地”不容他人染指的霸道。实则不然,学术研究中的所谓“领域”绝不能是“占山头”,它体现的应是研究者的“自知之明”。如果说“数字化”、“网络化”、“新技术”等是当下新闻研究的普遍背景,“新闻行动者”、“新闻实践”、“新闻文本”等是当下新闻研究的共有因素,那么在共同性之下,找到新闻创新作为研究领域和理论视角的意义,就是要发挥其在聚焦研究对象和发掘研究问题上的独特性,并以此与代表着其他独特性的新闻研究交相辉映。
新闻创新研究什么?十多年来新闻创新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暗示和明示,本身也是学术领域研究意识逐渐清晰自明的过程。创新无疑是行动,并且是打破常规的新行动。尽管在日常语境下,“创新”的使用极为宽泛,但学术研究中对“创新”的理解实不宜过于泛化。“在关于创新的迷思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认为创新就是一种观念”(Kastele & Sten,2011)。空洞的“创新”口号、没有行动的想法、以及仅摆出“创新”姿态的“表演”,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行动。严格“创新”的标准,方可挤出打着创新名义的诸多项目和话语中的“水分”。新闻创新研究的核心对象可概括为新闻领域中各类行动者采用的、对新闻领域产生实际影响的“新行动”(王辰瑶,2021)。在具体考察行动者如何采纳新行动的经验层面上,大量新闻创新领域的研究集中于观察在危机冲击下传统新闻媒体如何应对以及传统新闻业之外的新行动者们如何行事这两类现象。但推动新闻创新研究领域逐渐自明的工作,主要来自于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用“类型化”方法省视、细化新闻创新领域研究对象的努力。
比较重要的如布莱恩等人(Bleyen et al.,2014)提出的“媒体创新类型学”:他们在把媒体创新分为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分为“商业模式”创新、“生产和分发”创新、“使用和媒介服务”创新、“内在形式”创新和“内容核心”创新等5个维度。与前人相比,他们已明确意识到新闻媒体创新更为强调“产品/内容”导向的创新逻辑。技术和商业因素固然重要,但总体上还要为生产的“内容”服务,这抓住了媒体行动的重点和特点。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通过经验观察发展出了更为细化的“新闻媒体创新指数”(García-Avilés et al.,2018)。这个指数对评估新闻创新项目的创新度有现实价值,但不难看出,这种“类型化”总体上还是以在经济管理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套用在新闻领域的新行动和新变化上。也有一些“类型化”工作,有意淡化或去除了这种商业色彩,回归到创新即为新行动的本意。其中一个比较有启发的理论模型是韦斯特隆德和刘易斯提出的分析媒体创新实践的AMI(Agents of Media Innovation)模式。该理论模式把媒体创新实践的主体和行动视为一个4A矩阵,探讨人类行动者(Actors)、物和技术(Actants),以及使用者(Audience)如何在网络中相互作用,进行媒体创新行动 (Activities)。AMI模式认为,前三个A,即Actors、Actants和Audience的不同组合方式会对创新行动(Activities)产生不同的影响(Westlund & Lewis,2014)。AMI模式的优势在于把新闻创新行动放在行动网络中理解,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创新。笔者亦提出过从不同行动目标和行动面向出发,可将新闻创新行动分为“调适性”创新、“关系性”创新和“生产性”创新(王辰瑶,2022)。除了这些从总体上探讨新闻创新研究什么的分类理论模型外,还有一些类型化研究更细致地考察了新闻创新研究中某一局部的样貌,如对新闻业外围行动者的分类等(Hanusch & Lohmann,2022)。
总之,新闻创新研究通过各种“类型化”工作正在逐步厘清这一研究领域的“地图”。画地图的工作之所以能开展,得益于本领域研究数量的快速增长。但类型化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它们也会促使研究者更清晰地看待新闻创新中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与新行动,并能在不同维度上分析新闻创新行动的动因、过程和影响机制。在类型化工作的照映下,新闻创新领域的有些部分,如对特定类型媒体组织如何进行创新行动以及“媒体融合”等特定类型的媒体创新行动的研究,已有气象形盛之感;但有些部分显然还有待开垦,如解释多元新闻行动者如何生成新的关系网络,以及这一并不固定的网络如何与更大的社会网络互动等。新闻创新研究需要从相对单一、描述性的、组织或项目导向的研究,推进到能解释更为复杂宏观的新闻系统变化,推进到机制层面的、以关系为导向的研究新阶段。换句话说,即便我们可以接受“新闻创新”在现阶段被更多视为新闻业面对危机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也应该是社会信息“生态系统层面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媒体自身的解决方案(Nunes & Canavilhas,2020)。
“类型化”这样的旨在厘清新闻创新研究领域的“元研究”可帮助研究者明确“做什么”以及一项具体研究与新闻创新研究整体理论推进的关系,但还不足以解决“为什么做”的问题。新闻创新研究重要吗?这取决于它能提供什么样的独特理论视角。如果理论是指对某种对象提供较为系统的解释,那么理论视角指的是研究者采用何种特定的角度提出问题并进行研究。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曾有句指出进化论为何重要的名言,后被很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引用。杜布赞斯基说:“如果不从进化论的角度思考问题,生物学的一切都毫无道理。”(Dobzhansky,1973)这不是说生物学只有进化论这一个问题,而是说生物学有诸多复杂现象经过进化论的角度透视,就能说得通,产生解释性理论。可见,一个重要理论角度的作用不是取代其他,而是启发和勾连,产生新解释。我们不妨也把杜布赞斯基模板套用到新闻创新上——21世纪新闻领域涌现的诸多新现象以及一些被重新提出的老问题,如“什么是新闻”、“谁是新闻记者”等,如果不经由新闻创新研究的理论视角,也难以被理解。
就现象而言,21世纪新闻领域的创新叙事已经出现了一种难以忽视的张力——一方面,来自(传统)新闻业内部的职业话语和社会对新闻业理想角色与功能的规范话语,似乎并不鼓励各种离经叛道的“创新行动”。多位学者的研究都发现,“新闻工作者倾向于‘规范’新媒体技术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影响,从而压制根本性变革的可能”(Lewis & Usher,2016)。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包括技术、制度和新闻公众所构成的舆论场“风向”的持续变化,造就了新行动者不断涌现,原有新闻行动者不得不调整与改变,整个新闻生态系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导致很多实践中的矛盾、困惑甚至痛苦,也出现了理论解释的双重乏力。大众传媒时代诞生的关于职业规范、新闻生产机制、新闻与社会关系的解释,固然已经无法覆盖野性蓬勃的现实发展,但是,认为新闻业将被外来者“颠覆”,完全以“后工业”(post-industrial)方式打破既有主流新闻专业规范性预期的激进理论,同样无法解释在不同社会语境下为何仍然主要依靠传统新闻媒体中的一部分佼佼者,肩负起对现实世界的公共事务进行真实叙述这一核心使命。更何况,激进理论也难以回答“打破”之后的问题——一个更动态、灵活、流动的新新闻系统将如何维系其自身?例如,对于Deuze和Witschge(2018)提出的颇有启发性的“超越新闻业”(beyond journalism)命题,我们也不妨追问一句:然后呢?毕竟,任何系统如果不能以与其他系统相比的“差异性”维系其构成元素和关系的话,都是不能“持存”的。
创新理论作为研究视角的价值正在于能提供对系统“跃迁”(同时又不消解系统)的解释。它不仅关注新行动及其带来的变化,更要去研究造成变化的条件、方向以及后果,并始终在变化中考虑系统如何“持存”。换句话说,创新理论视角的独特性在于它坚持在规范与变化的关系中去理解一个系统为何会“发展”。而在不同社会领域中进行创新研究,必须考虑特定领域的规范性价值,而不能直接套用最先在经济管理学中发展起来的企业创新理论。如今再以反思性眼光看2012年《尼曼报告》刊登的《打破新闻》一文(Christensen & Skok,2012),就可以看到这种套用方式存在的问题。《打破新闻》运用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享有盛誉的“颠覆式创新”理论解释新闻业的变化,对新闻业界和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该文并非没有考虑“规范”,但直接将企业发展的“增长”规范等同于新闻业发展的“规范”,完全把新闻组织作为企业、把新闻作为商品、把公众作为消费者市场来理解新闻业的变化——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该文的解释会与此后十多年来新闻系统的发展实际存在较大偏差。可见,新闻创新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从新闻规范和新闻领域的新行动的动态关系去解释变化,它既无法被新闻学已有研究范式如“新闻规范研究”、“新闻生产社会学”等替代,也无法被其他社会领域的创新研究范式替代。Schudson(2019)在论证“新闻生产社会学”时曾说,不同的视角都可能在某些关于新闻的问题上比其他视角要更有见地。诚如斯言,“新闻创新研究”的发展也应坚持视角的独特性、提出新问题的敏感性和理论解释的敏锐度,避免扁平、泛化和自我重复式的学术话语。
新闻创新研究的CAN模式
据前论证,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新闻创新研究的CAN模式,以便能更清晰地显示新闻创新研究如何在多重因素考量下把握“规范”与“变化”的关系。
C指新闻环境的变化。这既是这一轮由新闻业危机驱动的全球新闻创新浪潮的缘起,又是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新闻创新势头的动力源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每年发布的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把新闻环境的变化划分为三大类:技术环境的变化、制度环境的变化和新闻使用与舆论环境的变化。新技术的涌现对新闻业的强刺激无须多言,新闻行动者通过采纳各类新技术而进行的大量新行动,是全球新闻创新领域最显而易见的现象。但研究者和行动者亦需警惕这类看似自然又直接的“创新话语”的陷阱,因为由新技术直接驱动的新闻创新同时也在新闻界产生了最多的闲置、空转、包装和表演。新技术出现了,新闻领域的行动者如果不能赶紧“跟上”,就有被淘汰的焦虑和害怕被批评革新魄力不够的担忧。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它在新闻领域激起了“崇拜”、“恐惧”等感受,以及非常强烈的需要做点什么的“紧迫感”(Newman,2023)。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组与表达现实世界,其与新闻工作理念与方法有无根本冲突?其实,面对任何可能影响新闻业发展的新技术,新闻行动者都面临着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发展和部署这种新技术的问题。这需要更多在“嵌入实践的技术”视角(王辰瑶,秦科,2023)下的新闻创新研究,而不是先假定要“热烈拥抱新技术”。在笔者看来,新闻作为一项人类社会的认知制度,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最大价值恰恰是要坚持新闻工作方法,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矫正”。相比于利用人工智能增加新闻生产效率的“小”创新,新闻业更应思考如何对抗人工智能内容冲击公共交往空间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一大创新任务。紧随技术变化之后的制度环境的变化,近年来对新闻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新闻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各种社会语境下的制度设计者、法律和政策制定者,都不可能让新闻系统行动者纯粹自由地行事。而制度变化总体上也与新闻规范的价值——确保事实真实、服务公共利益的方向一致。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指新闻外部环境因素,如相关法律、政策、重要文件等,但外部制度环境与新闻行业制度、新闻组织中的制度也具有相关性,它们以“联动”的方式对新闻行动者的创新行动产生了明显影响。
新闻环境中一个特别需要说明的因素是新闻使用者。毫无疑问,人们在线使用新闻行为的变化、新闻使用的量化指标、新闻态度的即时可见等,都是促使新闻业从观念到实践发生巨大转变的重要原因。使用者,或者说“用户”,与技术组件一样,其与新闻系统的互动都属于网络时代的“新新闻生态”。如果严格按照生态学的理解,“生态”指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生命体与其生存条件的动态关系。那么从新闻创新的角度而言,新闻使用者应该属于新闻系统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是新闻创新的主体。这也是CAN模式与AMI模式的一个显著区别,后者认为媒体创新的主体包括所有非人技术、算法、设备、网络、界面等组件(Actants),也包括不同类别的受众(Audience)。但在CAN模型下,这两者都属于新闻行动者之外的环境因素。理由是,创新是有明确目的性的新行动。现代经济创新理论的一个卓见就是对行动者“创新精神”的强调。熊彼得认为,创新的实现有赖于“企业家”。熊彼得所说的企业家更接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创业者”或者“有创新精神”的行动者。他认为创新始于对原有经济均衡状态的干扰或曰打破,而这种干扰活动发生在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他还认为,“企业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雇主、资本家、实业家,而是主动创新者,哪怕他们只是雇员(熊彼得,2012:62-94)。这给新闻创新研究带来的启发是要坚持“行动主义立场”,不要把一般意义上新闻用户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与由此引发的新闻系统多元行动者的创新相混淆。当然,数字新闻用户中的确有一部分积极使用者有持续参与新闻生产的意愿与行动,对此我们仍然要区分他们的行动逻辑。如在新闻媒体的评论区留言、发表看法,这属于希望实施环境压力促使新闻系统行动者有所改变(也许能激发出新闻行动者的创新);如果是躬身入局,借助传播技术的赋权,开始创办泛新闻类的“自媒体”并能持续的话,此时我们更应该将他们视为新闻系统中的“外围行动者”,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新闻用户。不过他们在新闻系统中的地位很不稳固,很容易从新闻多元行动者网络中又退回为新闻环境中的使用者。
与变化非常大的环境因素相比,新闻规范(N)通常被视为“不变”的部分,这使得数字新闻业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出现了明显的内在张力,也由此产生不少争论。新闻创新研究需要解释而非仅仅罗列这些争论。从创新研究的视角看,新闻规范对于新闻创新来说类似“地心引力”。诸多创新行动能否启动、能走多远、能否持续并扩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新闻规范的关系。但“新闻规范”自身并非完全不变,可将其视为一个从相对容易改变到相对难以改变的光谱。CAN模型将新闻规范分为三个层次,按照变化从难到易分别是:新闻价值规范、新闻角色规范和新闻形式与实践规范。新闻价值规范考虑的是新闻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存在的合理性。“咖啡馆新闻”(指17世纪开始的记者蹲守咖啡馆记录道听途说之事的早期新闻实践)也好,“黄色新闻”(19世纪末美国报业盛行的以耸人听闻和煽情的方式招徕读者的报道风格)也好,它们都曾一度在新闻界风靡并获得消费市场的正反馈,但为何终从当时风头十足的“创新”之举沦为新闻界的反面教材?早期新闻业是在市场需求、媒介批评、报纸竞争、政治压力等诸多混杂因素中“追求真实”(the search for truth)的,尽管这一过程一开始充斥着混乱、矛盾的价值诉求,但在新闻规范性的作用下,“报纸编辑们反复强调这一主题,承诺他们只提供最佳的公正的新闻”(佩蒂格里,2022:306)。全世界的新闻业,不管在现实中实践得如何,但都以“寻真”(truth-seeking)和关注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为价值声称,背后体现了系统差异性的客观规律。新闻,只有主动承载不同于“公关”、“娱乐”、“舆情”、“通告”、“广告”等其他公开信息形式的价值时,才有存在的必要。考虑到当下信息环境的变化,经受过历史检验并在实践中一路发展起来的,追求事实真实与公共服务的新闻文化价值,就更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在不变的价值规范之下,新闻角色规范则可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闻最早的角色功能其实是政治家和商人们的“信使”,后来才逐渐大众化,成为全社会的“瞭望者”。几十年来对新闻记者角色认知的调研证明:瞭望者角色(传播者、记录者、守望者等与瞭望者同义或近义)是现代新闻业建立以来社会共识度最高的角色,也即记者们认为把外部环境中的重要变动报告、传播给其他社会成员是他们最重要的使命。如美国学者从1970 年代开始对全美新闻从业者每10年一次的调查,发现记者的自我角色认知虽然从单一变得多元,但信息传播者(disseminator)这个角色始终存在(马亚宁,2014)。1997年后,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记者的角色认知进行大规模调研,几次调查的结果也发现,“中国新闻从业者始终最看重记录者、传播者的角色”(张志安,吴涛,2014)。
但随着社会对新闻业要求的变化和新闻实践自身的发展,新闻“瞭望”社会的含义正在改变。它不仅指用快速准确的消息“告知”社会成员,还包括提供对社会现实的深层观察、分析、解释,并与其他社会机构互动,让社会成员“理解”当下世界的事实变动。新闻从对信息的简单搬运和记录,发展成一种特定的基于事实的公共知识。这意味着它需要有意愿的社会成员、拿出专门的时间、使用专门的认知方法和技能,才能完成对这类知识的生产。新闻业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中介性的公共空间。从道理上讲,社会产生的信息越多,人与人的交往越紧密,人们之间的意义交流和彼此理解就越需要建立在公认的、可信赖、可言说的空间之中,社会就越需要新闻守望。然而,新闻业要继续履行瞭望者、守望者的角色远比过去困难。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靠新闻记者才能获得事实信息的垄断性被打破了。社交网络上自媒体、精英人士、社会组织机构以及公众无时无刻不在生产和交流关于事实的信息,对新闻权威形成了很大挑战;另一方面,这些新生成的巨量信息以及由社交媒体算法主导的信息传播网络从体量上可能淹没掉新闻工作,导致对公共事务的重要报道无法突破信息泡沫而被大多数公众知晓。想要继续履行社会守望职责,新闻业就不得不通过系统内创新和跨系统的协调创新,克服对现实世界公共事务的真实叙述与社会公共注意力资源不匹配的结构性难题。此外,随着社会复杂程度增加,人们的利益诉求和看待现实的角度益发多元,新闻系统仅仅守望社会、客观观察和记录社会具体事实显然不够,它还应越来越多地肩负起维护社会公共信息交往空间健康的职责,包括在众声喧哗的环境中成为有效的“协调者”和“引导者”,以及在面对“幻象”洪流('image' flood)、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和信息娱乐(infortainment)等新现象时,成为坚定的“校正者”和社会公共交往空间的“维护者”。与此前很多研究认为角色规范与新闻创新矛盾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两者毫不违和。因为在如今的现实条件下,新闻行动者只有通过创造性行动才有可能继续维系传统新闻角色规范并履行新的新闻角色规范,如果“墨守成规”则毫无疑问会让两者都落空。
新闻规范中最易变的层次则是形式与实践规范,也即对新闻(不)可以是什么样、新闻人(不)可以如何做的回答。这个层次的规范正在被大量的创新行动改变,同时又产生了许多争议和不适感。新做法层出不穷:权威报纸在新媒体账号上早已习惯了用“刚刚体”、“小编”,甚至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的短句文本报道新闻;重大事件的短视频新闻,配乐比比皆是;很多按照过去的新闻选择标准完全不可能成为“新闻”的凡人琐事时常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新闻……旧规范则渐渐沉寂:不必说日常在线新闻中已经很少出现“本报讯”这样的电头,也很少看到“编者”这样的称呼了,就拿新闻业发明的独特叙述形式“倒金字塔”来说,这种曾经非常成功的新闻文本结构方式在新闻传播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后也变得不受欢迎了——一项对网络时代受众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受众更喜欢新闻报道按照故事的线性时间叙事而不是“倒金字塔”这种“反故事”的模式(Kulkarni et al,2022)。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都不能仅凭某种新闻形式或工作常规的曾经辉煌与当下落寞,就生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实际上,新闻在“做”与“形”上的规范一直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这本身就彰显了新闻系统内在的活力。这一层次的新闻规范最直接地被新闻系统行动者们的各种创新行动影响,但同时也受制于新闻角色规范和新闻价值规范。因此,正是在这一层次上出现了最多的关于新闻的争议话题。新的报道风格、新的挖掘新闻素材的方法、新的事实呈现方式、新的选题领域、新的新闻发布和传播渠道等新行动,究竟能否上升为新闻系统的形式与实践新规范,的确需要边做边议,在行动中逐渐明确新闻形式和实践的边界。
这方面的经验现象非常丰富。例如新闻媒体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新闻时,在标题中使用“藏露法”一度颇为流行,即故意不交代新闻中最有价值的事实,引导使用者“点击”。对媒体来说,采用这种新式标题方法实属为在环境压力下争夺受众注意力和增加影响考评之“点击”数据的举措,但它是否会就此成为一种新的起新闻标题的“规范”呢?可能很难。这种“创新”的收益会随其扩散而递减,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采用这种做法,受众的新奇感会下降,反感会增加;从更稳定的新闻规范要求看,这种“创新”虽然不违背新闻的核心理念,但多少有点“贬损”新闻的文化价值。它很可能最终会归属于新闻编辑的一些“常用小技巧”,在起标题时偶尔为之无伤大雅,但上升不到新闻形式规范的层次。再比如,2022年东航MU5735空难发生的第二天,《人物》杂志微信公众号迅速推出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们》,成为一篇刷屏的“爆款”。一方面,这篇报道体现出媒体的新闻专业实力:事发后第一时间能公开采访到部分逝者的非直系亲属、朋友,这是快速采访能力的体现;多位记者协同工作并迅速完成一篇逝者群像特稿,这是协同能力和叙事能力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篇报道引发的社会争议非常大,以至于媒体很快删除了稿件。新闻记者、专家、批评者围绕这一报道是否有违新闻伦理进行了较为热烈的网络讨论。从报道文本看,采访信源主要来自外围亲友而非直系亲属,且被访者大多接受了采访,并不存在一些批评者所说的对遇难者家属直接的“悲痛侵扰”。记者采用的被访者提供信息和受害者生前发布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生活内容也都是正面和中性的,没有对死难者的贬低和丑化。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仅仅是网民对新闻报道的误读吗?笔者在课堂上与本科生们讨论这个案例时,发现数字时代的公众会因为这样的报道产生“不适感”,原因也是真实的。不少学生提到,虽然记者使用的部分内容素材是遇难者自己生前主动发布在社交账号上的,或是对外围亲友采访得来的,但一想到这些碎片化的内容会成为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即便没有贬低和丑化,他们也会觉得很“不安”。新闻使用者这种较普遍的代入式“不安”感是过去的新闻伦理规范很少考虑的新情况。如果这样的情况多了,是否会修正新闻的实践规范?这值得研究者进一步观察。在CAN模式中,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些案例位于新闻创新行动与新闻形式与实践规范之间最为活跃、不稳定的圈层中,这一圈层可能也正是新闻创新研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新闻创新研究秉持行动优先的立场,它绝不否认结构、制度或秩序的重要性,但并不接受原有规制对创新行动的先在性,否则就无法解释新闻领域的变化。换句话说,对于新闻创新研究来说,在数字时代谈论什么是新闻、新闻应该怎么做之类的形式和实践规范问题,正需要在大量的新闻创新行动及其产生的争议中探讨。争议不可怕,但需要警惕舆论场上“只争不议”的弊端,新闻创新研究者要避免陷入“争对错”的话语陷阱,而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具有症候性的案例如何启发新闻“规范与变化”之关系的思考上。
新闻创新研究最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CAN模式中的“A”——由新闻领域多元行动者(Actors)及其创新行动(Activities)所构成的生动、蓬勃的经验世界。但正如这个模式所展示的,新闻创新研究的独特视角在于探寻新闻规范与新闻领域新行动的动态关系,由此为数字时代新闻范式的更替和新闻业的发展提供理论解释。对多元新闻行动者及其关系的研究、对多元行动者创新行动的研究都既离不开新闻环境变化这一大前提,更离不开新闻规范的变与不变这一向心力。按照CAN模式,新闻创新研究可不断通过对新经验现象的归纳分析,围绕如下四大类问题推进理论化过程。
第一类,新闻环境变化与新闻行动者和新闻创新行动的关系问题,也即C-A问题。新闻创新研究并不单纯探讨新闻环境如何变化,而要探讨新闻环境的哪些因素可能促使或阻碍新闻领域涌现新行动者、结成行动者之间的新关系、产生某类新闻创新行动。比如我国传统新闻媒体在新媒介形式上开疆拓土,打造新媒体矩阵已经是一种扩散很广的创新行动。但并非所有的新媒介形式都对传统新闻媒体有同等吸引力,也不是用户越多的社交媒体平台就越吸引传统新闻媒体“入驻”。其中原因何在?可能与不同新媒介技术的可供性有关,比如微信公众号对纸媒的内容产品接纳度较高,而小红书则无法承载较长篇幅的文字;也可能与制度对创新行动的认可有关,如是否将某一新媒介形式的账号视为有资质的传播主体,或是否纳入考评体系;还可能与媒体行动者对不同媒介平台用户环境的评价有关,新闻媒体更倾向于在“调性相合”的平台上开设账号而非相反。如此深究下去,才能进一步探索“媒体融合”的客观规律。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包括制度空间的变化对新闻多元行动者网络的影响、新闻行动者对不同技术的采纳方式和采纳程度有何差异、使用者与新闻行动者的关系如何影响新闻创新等,都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第二类,关于多元新闻行动者的类型、行动者之关系的建构与变化、以及不同行动者如何进行不同类型的新闻创新行动的问题,也即A-A问题。这一大类问题其实是把新闻创新放在一个“行动网”当中研究:多元行动者的出现本身就是改变传统新闻业态结构的系统创新,它们的异质性很强,有着不同的“做新闻”路径,相互之间存在着竞争、融合、协作、斗争等不同关系,且还在不断变化中。多元行动者如何通过不间断的创新行动生成新的网络化新闻业是这一类研究问题的核心关切。比如我国传统新闻媒体要实现“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目标,本质上是要在一个传统新闻媒体与其他泛新闻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网络化关系中占据核心位置,成为能实现媒体系统核心社会功能的,能直接或间接触达并影响主体社会公众的,对媒体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有显著影响、起引领和示范作用的媒体。对当下的传统新闻媒体来说,重要的不是被制度保护住一个名义上的“主流媒体”身份,而是如何通过创新行动在多元行动者网络中“争取”真正的“主流媒体”地位。对于其他类型的行动者来说,能否被公众接受、被制度认可(至少是默许)是其能否保有在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中一席之地的关键,它们的创新举措与传统媒体有很大不同,也颇值得研究。
第三类,关于多元行动者之新闻创新行动与新闻规范的关系问题,也即A-N问题。如前所述,新闻规范是新闻创新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脱离新闻规范,就理解不了新闻创新。也可以把这一大类问题视为在“行动流”中研究新闻创新:因为这类问题不仅关注什么行动者做了什么,更关注行动者的创新动力、行动目标、创新成效、创新行动能否持续、扩散及其原因等。或者说,这类问题其实把新闻创新当成一个有机体看待,为何有些新闻创新扩散极快,有些则雷声大雨点小,还有些已经停滞或空转?为何有的新闻创新生命力极强,有的则如昙花一现?可以说,新闻创新背后的“大道”就落在不同层次的新闻规范上。对新闻创新行动流、新闻创新生命周期的考察非常重要,也更加需要历史眼光,如此新闻领域的“守正创新”才会有更大的定力。在对新闻创新行动流持续关注的过程中,研究者既不能用既有规范限定行动,也不能无视规范。新闻创新研究首先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比如现实中有大量新闻创新行动者和创新行动都是“无名无分”的,新闻创新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应轻易裁定它们。而要在密切关注中,围绕这些创新行动的逻辑、目标、价值观、影响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原有新闻规范相呼应,是否会挑战或修正新闻规范等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因此,新闻创新研究的行动优先立场决不意味着价值虚无,更不能随便把其他领域的规范当作新闻的评判标准。比如,研究已经证明假新闻比真新闻更具有扩散能力,难道我们能据此认为诸多假新闻的编造伎俩是新闻创新吗?总之,这类新闻创新研究问题,在探讨创新机制的同时也对新闻创新寄托了价值期许。
第四类,是综合新闻环境、新闻行动者和新行动以及新闻规范的问题,以及在不同语境下比较不同新闻创新模式的问题,也即C-A-N综合问题和C-A-N比较问题。这是在前三类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抽象程度更高的研究。尽管目前新闻创新研究总体上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但不妨做此展望。比如,颇受研究者关注的“未来新闻业”命题,就可视为一个C-A-N综合问题,因为它不仅要观察新闻业行动层面的变化,还要观察新闻业自身的结构的变化,更要将之纳入环境与规范的维度,去研究变化的客观规律、把握变化的可能方向,甚至需要研究者与行动者们密切合作,为新闻创新进行理性规划。此外,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新闻创新模式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甚至可以接续上新闻研究的老传统和大问题。二战后,《传媒的四种理论》横空出世,尽管它有强烈的冷战背景和明显的意识形态错误,但以宏观、综合和比较视角直指核心问题的研究范式,对后续新闻学研究有深远影响。此后,梅里尔(John C.Merrill)、阿特休尔(J.Herbert Altschull)、克里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诺登斯特伦(Kaarle Nordenstreng)等人不断试图“修正”、“超越”乃至“替代”“四种理论”。丹尼尔·哈林(Daniel C.Hallin)与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的《比较媒介体制》以及其后的《超越西方世界的比较媒介体制》中兴了从社会、政治制度与新闻媒体系统之宏观比较视角切入新闻学大问题的传统。然而在21世纪的新闻学研究中,这类大问题、大思考,似乎也随着新闻环境、新闻系统内在的重重变化而少有人问津了。研究者的兴趣转向当下的局部变化,热衷于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这在让新闻研究精细化、科学化的同时,也有失落了大气象、大关切的遗憾。如果新闻创新研究能在以丰富的研究成果充分回应前三类相对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新闻创新模式比较研究,则既可接续上新闻学研究的大传统,又能充分彰显中国式新闻创新的特色。
做如此想,并非空想。仅以新闻创新实验室在《新闻记者》杂志上连续几年发布的《全球新闻创新报告》而言,其实已初见未来可进行全球新闻创新模式比较研究的征兆。比如,从技术环境而言,不同国家的“平台化”程度已经出现了很大差异;从制度环境而言,对新闻媒体的准入、合法性、对平台媒体和使用新技术的约束性等,虽总体是管理趋严,但仍然差别很大;从新闻使用与舆论环境而言,既有仍然相对信赖并愿意付费支持新闻媒体传统的国家,也有新闻信任度从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一路走低的国家比如美国,还有很多在互联网开始普及时新闻媒体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它们的新闻业与其公众的关系存在很多“先天”差异。越是从全球的视野观察,也越能看出中国新闻业自2013年后开始的“媒体融合”创新路径的独特性。
21世纪的全球新闻创新研究已经蓬勃展开,它表现出的学术活力和未来的研究空间,值得研究者们去期待和想象它的各种可能。■
参考文献
[英]安德鲁·佩蒂格里(2022),《新闻的发明》(董俊祺,童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红义(2018)。新闻研究:经典概念与前沿话题。《新闻与写作》,(01),24-32。
柏拉图(2017)。《苏格拉底的申辩(修订版)》(吴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加]迈克尔·雷纳(2013)。《创新者的解答》(李瑜偲,林伟,郑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马亚宁(2014)。美国新闻从业者专业角色观念考察——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新闻大学》,(冬),26-29。
沈欣(1996)。生命的追寻——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新闻界》,(01),43-45。
孙玉胜(2003)。《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三联书店。
王辰瑶(2016年5月5日),《新闻创新:不确定的救赎》。中国社会科学报,A03。
王辰瑶(2018)。反观诸己: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国际新闻界》,(08),25-45。
王辰瑶(2021)。站在新起点上的新闻创新研究,《新闻记者》,(11),3-7。
王辰瑶(2022)。新闻创新的行动主义立场。《全球传媒学刊》,9(04),132-146。
王辰瑶,秦科(2023)。嵌入实践的技术:“自动化”对新闻业意味着什么。《新闻与写作》,(09),92-103。
[美]约瑟夫·阿洛斯·熊彼特(201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邹建平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张志安,吴涛(2014)。“宣传者”与“监督者”的双重式微——中国新闻从业者媒介角色认知、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06),61-75。
Ainamo.A (2006). Innovation Journalism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ommercialization.The Third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Journalism. https://www.academia.edu/30479603/Innovation_Journalism_for_Bridging_the_Gap_Between_Technology_and_Commercialization.
Bleyen.V, Lindmark.S, Ranaivoson.H and Ballon.P.(2014).A typology of media innovations: Insights from an exploratory study.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1(1)28-51.
Christensen.M & Skok.D. (2012). Breaking News: Mastering the art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journalism. Nieman Reports (Fall 2012). https://niemanreports.org/articles/breaking-news/.
Deuze.M & Witschge.T.(2018).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19 (2)165–181.
Dobzhansky.T.(1973).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35(3)125-129.
García-Avilés.J,Carvajal-Prieto.M,Lara- González.A &Arias-Robles.F.(2018) Developing an Index of Media Innovation in a National Market, Journalism Studies19125-42.
GitlinT. (2011). A Surfeit of Crises: Circulationrevenueattentionauthority and deference. In McChesneyR.W. & PickardV. (Eds). 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Hanusch.F & Lohmann.K (2022). Dimensions of Peripherality in Journalism: A Typology for Studying New Actors in the Journalistic FieldDigital Journalism,11(7)1292–1310.
Kastele.T.&Sten.J.(2011).Ideasarenotinnovations.Prometheus29(2): 199-205.
KulkarniS.Thomas, R.Komorowski, M.& LewisJ. (2023). Innovating online journalism: New ways of storytelling. Journalism Practice, 17(9)1845-1863.
Lewis.S & Usher.N.(2016).Trading zonesboundary objectsand the pursuit of news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journalists and programmers.Convergence ,22(5)543-560.
NewmanN (2023).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3-06/Digital_News_Report_2023.pdf.
Nunes.A.& Canavilhas.J(2020). Journalism Innovation and Its Influences in the Future of New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Around Google DNI Fund Initiatives. In Journalistic Metamorphosis Media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edited by Jorge Vazquez-Herrero ,etc. Gewerbestrass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41-56.
Pavlik.J. (2000).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2229-237.
Pavlik. J. (2001). 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New York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ew (2009).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an annual report on American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s3.amazonaws.com/files/journalism/State-of-the-News-Media-Report-2009-FINAL.pdf.
PicardR. G. (2011). The economics and financing of media companies.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osetti. J (2018). Time to step away from the ‘brightshiny things’? Towards a sustainable model of journalism innovation in an era of perpetual change. Journalism innovation project.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nger.M & Deuze.M.(2017). A Histor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ism in Journalism.Pablo J.B.& Auderson.C.W(Eds) In Remaking the New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35-250.
Schudson .M(1994).Question authority: A history of the news interview in American journalism 1830 s–_1930 s_. _Media_Culture and Society(16)565–587.
Schudson,M.(2019). Approaches to the Sociology of News,In Curran. J.& Hesmondhalgh.D(Eds). Media and Society ( 139-165)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Westlund.O &Lewis.S (2014). Agents of Media Innovations: Actors, Actantsand Audiences.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1 (2)10-35.
Zelizer, B. (2015).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5)888-908.
[作者简介]王辰瑶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网络化新闻业建设路径研究”(编号: 23BXW034)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