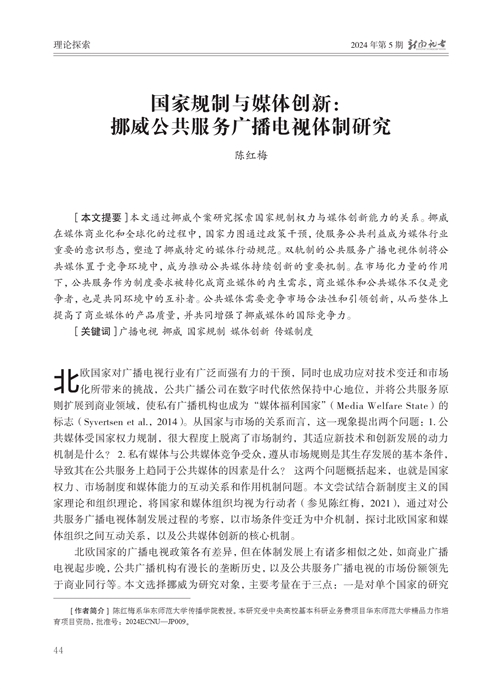国家规制与媒体创新:挪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研究
陈红梅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挪威个案研究探索国家规制权力与媒体创新能力的关系。挪威在媒体商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力图通过政策干预,使服务公共利益成为媒体行业重要的意识形态,塑造了挪威特定的媒体行动规范。双轨制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将公共媒体置于竞争环境中,成为推动公共媒体持续创新的重要机制。在市场化力量的作用下,公共服务作为制度要求被转化成商业媒体的内生需求,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不仅是竞争者,也是共同环境中的互补者。公共媒体需要竞争市场合法性和引领创新,从而整体上提高了商业媒体的产品质量,并共同增强了挪威媒体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广播电视 挪威 国家规制 媒体创新 传媒制度
北欧国家对广播电视行业有广泛而强有力的干预,同时也成功应对技术变迁和市场化所带来的挑战,公共广播公司在数字时代依然保持中心地位,并将公共服务原则扩展到商业领域,使私有广播机构也成为“媒体福利国家”(Media Welfare State)的标志(Syvertsen et al., 2014)。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言,这一现象提出两个问题:1.公共媒体受国家权力规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市场制约,其适应新技术和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2. 私有媒体与公共媒体竞争受众,遵从市场规则是其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导致其在公共服务上趋同于公共媒体的因素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概括起来,也就是国家权力、市场制度和媒体能力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制问题。本文尝试结合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和组织理论,将国家和媒体组织均视为行动者(参见陈红梅,2021),通过对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发展过程的考察,以市场条件变迁为中介机制,探讨北欧国家和媒体组织之间互动关系,以及公共媒体创新的核心机制。
北欧国家的广播电视政策各有差异,但在体制发展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商业广播电视起步晚,公共广播机构有漫长的垄断历史,以及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市场份额领先于商业同行等。本文选择挪威为研究对象,主要考量在于三点:一是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可以较为深入地探析国家、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以技术和社会变迁为语境的互动博弈策略,以及各方行动者的行动逻辑。二是挪威在北欧五国中对广播电视新技术采纳相对保守,其开放无线电广播服务和推出彩色电视均是五国中最晚者,开放电视服务仅早于冰岛(参见Syvertsen et al.,2014:74-75);但是,挪威目前的Netflix、Facebook等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使用率居北欧前列,同时,其公众为线上新闻和公共媒体付费的意愿也是北欧国家中最高者。这种反差或可便于探讨本研究主题。三是挪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在北欧福利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多项欧美跨国比较研究均选择挪威来代表北欧。
本文材料主要来自三方面:1.英语和挪威语的学术著作、期刊文献和硕博学位论文;2.互联网可公开查询的挪威政府机构文件和报纸等媒体文献(均为挪威语),其中,政府文件包括挪威媒体管理局的历年公共广播年度报告和媒体经济报告、文化部媒体政策白皮书、统计局媒体年度报告等;3.路透研究院和欧盟等组织编写的一些资料汇编性质的文献。
一、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
新制度主义学者将国家视为有自身利益目标和实践能力的行动者,认为其行动既受到国家机器内部不同组织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受到其与社会各集团关系的制约,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成为关注要点(埃文斯等,2009)。国家作为拥有巨大权力资源的实体行动者,可以用武力来维护其各种制度规范,同时,在国家与社会的接合点上存在无数个竞技场,国家在这些竞技场内和其他社会力量发生冲突、斗争和妥协,并相互改变。国家或许有强大的存在感,但受限于场域内其他社会力量的各种推力或拉力,与其他社会成分的界限难以划分,且常处于变动中,因此,国家也是社会中的国家(米格代尔,2013)。国家能力体现为与强大的社会行动者进行谈判和合作的能力,而不是建立在违背社会行动者利益的能力之上。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全球化发展导致对国家自主性的质疑。一些学者认为,私有化和限制公共干预使政府丧失部分功能,欧盟等跨国机构的立法则削弱了国家主权(Rhodes,1994)。但对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的深入研究显示,国家权力仍然是重要变量,“所谓的全球经济通常是由国内机构,特别是由国家权力来调节的”,国家制度能力越稳定,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就越强,反之亦然(Weiss & Hobson,2000:53-55)。
组织作为理性系统,通过正式的结构将个体整合为行动的整体,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存在,也是一个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的“适应性的有机体”(Selznick,1948)。技术和任务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组织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组织只能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选择行动路线。经济变迁研究中的演化理论认为,企业可以改变原有的惯例,通过自我演化来适应环境(纳尔逊,温特,1997)。演化的关键机制是学习和创新,企业对外部技术和知识的采纳,以及相关的组织实践(如企业内部的自省性检查,调整与国内外企业机构的关系等)过程累积促成企业认同的转变,而企业的成长受到自身期望水平、企业能力和整体经济专业化水平的限制(de Surie,2008:1-4)。组织还会吸收重要的偶然事件(contigencies)而获得新能力,并扩展任务领域以充分运用其所获得的能力。但组织的成长方向不是随机的,“而是由技术和任务环境的本质特征所引导的”(汤普森,2007:15-17,59)。文化是总体环境的组成部分,影响个人和群体的偏好和价值观,并通过组织设计、战略选择,以及个人和群体的相互作用因素形成了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又反过来强化了组织文化(Tosi Jr. & Slocum Jr.,1984)。
根据上述简略的理论回顾,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理解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三个层次的框架。其一,国家对自身利益目标的坚持构成组织行动的外部环境因素之一,但组织并非完全被动,而是与国家在谈判中进行博弈合作。其二,在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任务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国家和组织都会采取一些权宜性策略。国家策略可以重新塑造组织的外部环境并转化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组织策略则可以吸收环境不确定性中的偶然事件并提升自身适应环境的能力。其三,共享的文化为国家和组织的偏好和选择提供基础性支持。
据此,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国家作为掌握最高层次规则的规划设计、治理和修改的行动者(奥斯特罗姆,2000),在技术变革及其所带来的市场环境变迁的情况下,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因应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行动策略的?2. 从组织权变性角度,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分别以怎样的组织策略来整合国家规制和市场竞争的要求?推动公共媒体创新的机制是什么?3.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的竞争合作关系是怎样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怎样促成媒体认同的转变?
二、挪威社会政治与广电业概况
鉴于国内对挪威的社会政治与媒体发展状况介绍不多,本部分简述挪威的社会政治特征,勾勒挪威广电媒体的整体轮廓,为理解挪威广播电视体制演化提供背景。
(一)民主法团主义的社会语境
在1319年至1905年的漫长时间里,挪威通常与瑞典或丹麦结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05年,挪威脱离瑞典独立。在19世纪末民族独立的运动中,挪威政府最有力的政治支持来自左翼民众,“大众政党和志愿团体提出广泛的社会议程,对公共权威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Osterud & Selle,2006:26)。基于此种背景,国家权力集中、广泛的公民参与,以及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和依赖、工人运动和左翼政党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些在英美自由主义看来颇多矛盾的因素构成了挪威的社会政治特征。
在利普哈特(2012/2017:45)关于民主模式的研究中,挪威属于共识民主国家(基于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的二分法)和非多元社会(基于多元、半多元和非多元的三分法)。就政治经济安排来说,包括挪威在内的北欧国家是民主法团主义的典范。卡岑斯坦(1985/2009:19)将其核心特征概括为国家层面的社会合作理念,相对中心化的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与国家机构、政党之间的非正式的自愿谈判以协调相互冲突的目标。一些学者认为左翼政府、较小的国家规模、经济开放以及共识民主的程度都是法团主义的重要影响因素(参见Lijphart & Crepaz,1991)。
左翼的工党在1935年至1960年代初曾一直主导挪威政府。民主法团主义被认为是工党保持长期竞选优势的重要因素(Rokkan,1966)。由于利益组织和其他企业实体的庞大网络力量的增长,反对党虽然在竞选中失败,但他们代表的利益和事业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影响政府决策。商业领袖甚至认为,工党执政减少了劳工运动所带来的产业动荡。罗康(Rokkan,1966)认为这得益于当时的劳工、农业和渔业群体,以及商业群体的三角力量平衡,每一方都保持了对其余力量的威慑能力。
1970年代开始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改变了这种平衡状态,新政党的出现破坏了原先稳定的政党体系,利益组织增加也使原先集中化的利益集团分散,非正式的议会游说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出现。另外,现代政治常常需要对新挑战做出快速反应,媒体对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也强化了这一点,而法团主义谈判通常进展缓慢,也导致其适用性变差。尽管如此,北欧的商业公司、员工、公共部门的雇员依然有很高程度的组织化形式,仅以工会来说,挪威2013年的工会会员比例为54%(在北欧五国中是最低的,最高的冰岛为83%,芬兰、瑞典、丹麦三国在69%至67%之间),这个数据远高于欧洲大国和北美国家(Christiansen,2017)。总体而言,利益集团在包括挪威在内的北欧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二)广播电视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挪威广播电视业发端于1920年代无线电广播。1925年起奥斯陆等城市陆续出现定期播出的私人收费电台,通常是无线电设备制造商为销售设备而建立,政府颁发许可证对其进行管理。但早期的私人广播公司面临频率资源稀缺、搭便车行为泛滥、技术成本高昂而无法为全国提供普遍服务等矛盾,挪威议会经过多年辩论,最终在1933年立法建立国有垄断性的“挪威广播公司”(Norsk Rikskringkasting,NRK),并同时关闭所有私人广播公司,将其重建为NRK的地方办事处(Syvertsen,1992:38)。这是挪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的起始。
以相关重要制度进展及标志性事件为节点,我们可以将挪威自1920年代以来的广播电视业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时期(详见表1 表1见本期第48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将每个时间节点精确到具体的年份,是以所选择的标志性事件为依据而做的简化表述,并不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事物发展是连续渐进和界限模糊的,极少有断然的转变。
目前,挪威所有的商业广播公司均为外国媒体集团所有。根据挪威媒体管理局的数据(Medietilsynet,2019),2017年挪威电视收视率市场主要份额(不含付费电视频道)被包括NRK在内的四家媒体集团占据(表2 表2见本期第48页),广播收听市场则由NRK(65.6%)、瑞典公司MTG(23.6%)和德国公司Bauer(10.8%)三分。NRK在广播和电视市场均居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Facebook、谷歌等全球性媒体的广告冲击,目前挪威商业媒体的财务状况仍然是健康的。据媒体管理局最新的媒体经济报告(Medietilsynet,2023),2022年挪威商业媒体总收入为223亿挪威克朗,总盈利(因缺乏数据,不含隶属于MTG的流媒体品牌Viaplay)为9.02亿挪威克朗。从广告来说,商业媒体2022年广告收入86亿挪威克朗,虽然较2012年高峰的122亿下跌不少,但较2021年增加了1.8%(约1.52亿)。不过,未来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Facebook、谷歌在挪威广告市场占大头(约100亿挪威克朗),且增幅更高(较上年增幅为8.3%)。
技术发展一直对公共服务媒体存在的合法性和履行社会使命的能力提出挑战。挪威作为一个语言和人口数量在欧洲均不具优势的国家,一方面,语言和文化壁垒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其国内媒体生态环境,国际媒体难以撼动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内人口少(2022年约为550万)市场小,导致公共广播机构资金规模小,也限制了其发展新技术和应对国际媒体挑战的能力。据学者整理的2015~2016年数据(Saurwein et al.,2019),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公共广播公司年度预算分别为73亿、98亿和44亿欧元,而挪威约为6.5亿欧元,与前者差距悬殊。在总体市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挪威的公共广播机构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适应新技术发展和国内国际媒体竞争,从而保持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是国家作为行动者的目标追求、市场力量调节与媒体创新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接下来,本文分别以国家、公共媒体(NRK)、商业公共服务媒体(TV2、P4等)为中心来叙述挪威的广电业发展历程,希望在技术/市场环境变迁的语境中,来展示三类行动者各自所遵从的行动逻辑,以及在诸多重要时间节点上的具体考量和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同时,也能以一种参差照应的方式,更清晰地呈现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关系。本文没有按照上文的时段分期来叙事,除了分期所包含的武断性问题之外,也因为分期容易造成叙事的断裂,从而很难将三类行动者看作各自逻辑连贯的主体。
二、国家自主性:文化利益与国际竞争的平衡
一定程度上,挪威在1933年建立NRK的公共服务广播制度并非有意的设计,而是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结果。赛弗森(Syvertsen,1992)在审查议会辩论的原始材料后认为,除了美国制度作为负面案例所具有的启发价值外,挪威决策者几乎没有参考其他国家(包括英国BBC)的制度。新技术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以及挪威由来已久的文化政策传统,多种力量作用使公共广播制度成为当时社会可以普遍接受的选择。国家主导和基于实践合理性的现代化历程使挪威官员和社会精英普遍具有家长式的启蒙理念(希尔贝克,2014),将广播首先视为启蒙和教育的工具,而不是消费性商品,从而限定了公共广播的文化责任和控制结构。
公共广播公司获得垄断地位和强制许可费的优势,同时也要承担三项义务:以较低的成本向全体人民提供普遍的服务;提供平衡多样的节目内容,履行其文化职责;广播内容要符合国家利益,加强民族文化和认同,避免任何威胁社会秩序或国家安全的内容。在监管结构上,虽然公共广播公司的最终权限来自国家,但有较高程度的业务自主权,政府干预受到法律文件的限制。早期的挪威精英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保留了对广播公司较高的行政控制权,NRK总干事和董事会成员均由议会任命,议会控制公司的主要投资活动、雇员数量和整体发展策略,政府也保留了使用广播渠道传递官方声明和讯息的权利(Syvertsen,1992: 42-4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NRK成为挪威“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制度”。
NRK在挪威广播电视领域的垄断地位维持了近五十年,直到1981年保守党政府上台授予地方集团经营本地(local)广播和电视的许可,局面才被打破。此前并非没有反垄断的情绪和行动,但都被政府忽略和压制下去。挪威在1980年代终结NRK的垄断地位,引入竞争机制,不能简单归因为保守党政府放松管制,这也是国际国内众多因素促成的结果。首先,经济危机带来通货膨胀压力:NRK频繁向政府申请提高许可费标准,用户的综合许可费在1960到1975年间增长了一倍(Syvertsen,1992: 58),而其所能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增益,甚至在商业主义文化力量上升的背景下,被指责为借整体社会文化利益的名义而培育小圈子的价值观和文化(Syvertsen,1997: 13)。因此,打破公共广播电视的垄断地位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极大支持。其次,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新技术的发展动摇了NRK垄断的技术基础,电视媒体国际化也事实上破坏了NRK的垄断性。1970年代末,挪威东部约25万户家庭接入天线系统,在改善NRK覆盖能力的同时也使接收瑞典电视成为可能;1981年欧洲卫星协会决定向电视公司开放卫星服务,随后英国天空卫视重塑了整个欧洲的有线电视网络;1987年瑞典的卫星频道TV3获得在挪威的合法传播权(Syvertsen,1997:26-28,31)。国际媒体的竞争压力及其对挪威文化认同的威胁,使建立新频道以应对国际商业电视潮流成为挪威政治精英的共识。再次,国际商业频道的进入也意味着挪威广告收入外流。因此,1985年保守党提议设立独立的全国性商业电视台TV2,捍卫国家利益是其最重要理由,并得到所有政党的支持。
尽管面对大量工业界和广告界利益的游说压力,在所谓的放松管制阶段,国家对广播电视媒体的规制原则并未改变,仍以发展民族文化和提供普遍服务为核心诉求,只是在维护这一核心原则的策略中加入了竞争因素,试图以竞争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例如,挪威政府1981年开始允许开办地方广播电视,但直到4年后才允许地方电台播出广告,并通过征收广告税的形式来维护那些经济效益较差的电台,以保护本地文化和信息传播(王宇,2016:130-131)。在1980年代关于设立商业电视台TV2方案的辩论中,文化利益和商业利益同等重要。因此,有学者评论,公共服务媒体危机本质上并非由于引入竞争,而是其自身无法适应整体的社会文化变迁,1980年代的媒体系统重组实际上给了公共服务媒体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可以在新的环境中找到和发挥自身的作用,以应对下一轮更严重的冲击(Sondergaard,1996)。
挪威双轨制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格局形成于1990年代。在电视方面,第一个全国性商业电视台TV2在1992年9月正式开播是标志性事件。政府的十年许可协议要求TV2在技术上覆盖全国70%以上的人口,并对时事新闻、挪威语节目、少数民族节目等内容方面作出规定,总体上,这些节目要“有助于加强挪威语言、身份和文化”的认同(Syvertsen,1997:34-37)。作为交换,TV2获得全国电视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因此,TV2实际上是个混合(hybrid)频道,从所有权和财务形式上是商业频道,从节目责任和所获特权角度又比较接近公共服务电视。
在广播方面,挪威政府1987年立法永久许可地方广播公司播放广告后,在诸多商业力量推动下,地方电台事实上播出的是全国性节目,并对NRK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Fossum,1997)。1993年全国商业电台P4建立,正式打破NRK的广播垄断地位。挪威政府通过类似于TV2的限时许可协议要求P4承担公共服务责任。P4迅速取得市场成功,但挪威政府认为其公共服务表现不佳,在协议到期的2002年底将P4许可转授给拥有挪威地方出版公司背景的Kanal 24,又在2003年颁发了新的承担公共责任较少的P5许可,并最终由P4公司获得(Enli & Sundet,2007)。这样,挪威在广播领域除了NRK的三个主要广播频道(P1综合、P2文化和深度报道、P3青少年),还有两个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的全国性商业电台P4和Kanal24(后更名为Radio Norge)。①
1990年代中期开始,互联网普及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媒体融合转型,使广播电视媒体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广播公司向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合法性和许可费特权面临新的争议。欧盟②和挪威国家政策都转向优先保护公共服务媒体,来应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协议将公共广播公司的资金和授权问题交由各国政府决定,同年修订的欧盟电视指令事实上赋予公共广播公司新的特权。挪威在1999年修改《广播法》使NRK更便于从事商业活动,2007年正式启动地面数字电视系统,意味着选择在既定媒体系统里实现技术转变(Syvertsen,2003)。在发展在线业务方面,欧盟要求公共广播公司对其每一项新的在线业务的合法性进行说明,以免干扰市场竞争秩序。但挪威对此政策进行调整,认为公共广播公司是“防御国际竞争和在线无政府状态的最好方式”,支持NRK转型为一家多平台公司,从而承担起“传统的国家建设的理想”(Enli et al.,2013)。
学者曾梳理2000~2007年间挪威政府、大众媒体和NRK的相关文件、报道等材料(Larsen,2014),认为同胞公民话语(fellow citizen discourse)、多元主义话语和新自由主义话语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全国辩论,但受到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理论影响,公共服务媒体被视为实现文化政策目标的工具,NRK则是挪威获得新知识和共同经验的最重要来源。在此语境下,商业媒体也没有对公共服务媒体的基本制度安排提出异议。 2003年,NRK最主要竞争对手TV2曾向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监管局(ESA)提起诉讼,认为挪威法规允许NRK在由许可费资助的广播电视节目和互联网服务上做广告,涉嫌交叉补贴和导致市场不公正。这场诉讼一直持续到2010年,NRK最终退出在线广告市场。但是,正如有学者评论的,NRK在2010年的许可费收入约5.72亿欧元,而每年的广告收入约100万~200万欧元,因而并没有对其造成实质性影响(Moe,2012a)。
值得关注的是,挪威在公共服务媒体制度上的国家自主性并不是体现为强大的控制社会能力,而是来自其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实践理性、论辩理性和启蒙精神,以及在民众运动中形成的国家官员和社会公众的基本信任(希尔贝克,2014)。相关决策通常经过漫长的政治辩论,众多利益相关者展开多边谈判而达成议会共识。决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实践情境而非简单的理论推演,这使政府有可能在媒体的“国家所有权和自由市场竞争之间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将混合媒体(hybrid broadcasters)转变为“纯粹公共服务和纯粹商业媒体之间的桥梁”(Lund & Berg,2009)。1992年商业电视台TV2在其内部通讯中曾解释:许可协议要求的公共服务责任和商业利益并不冲突,一家不受任何政治约束的商业电视台也要遵循大体相同的原则,因为公共服务是获得高收视率进而获得商业成功的最安全的途径(Syvertsen,1997:38-39)。媒体机构和政治精英所共享的公共启蒙、平等主义和社会合作等意识形态使媒体既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又成为国家推动普遍性和平等主义政治理想的重要工具(Enli et al.,2018)。
美国的商业电视文化始终受到挪威政治精英的高度关注和防范( Enli et al.,2013)。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运动波及挪威,美国商业媒体政治报道的犬儒主义和观众民主(audience democracy)后果,使挪威担心独立于政党系统的媒体可能威胁执政精英的言论自由。哈林和曼奇尼(Hallin & Mancini,2004:301)曾预测传媒的法团主义模式有可能向英美自由主义模式趋同。但是,挪威政府依靠其广泛的民众支持和合法性基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趋势。2004年挪威修订宪法第100条,将“出版自由”(freedom of print)修改为“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并加入“国家当局有责任创造条件以促进开放和开明的公共话语”的原则,这被认为是言论自由的“基础设施”,“为国家干预媒体行业和市场提供了宪法保护”(Rolland,2010) 。
与美国式的“第四等级”观念不同,挪威政府更担心媒体所造成的政治破坏,希望媒体成为社会力量的竞技场(arenas),而不是行动者(actors)(Rolland,2008)。由编辑控制的新闻媒体是政治辩论和意见形成的中心论坛,也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基础设施中尤其重要者。为应对数字时代未经编辑的信息传播的挑战,挪威政府在公共广播电视之外也加大了对商业电视的支持力度。2010年挪威政府和TV2签订新协议,将其界定为履行“社会使命”的“商业公共广播公司”,应该确保能被观众看到。2011年政府调整电视发行政策,要求有线电视发行商按市场价支付TV2节目,意在提高TV2的发行收入以弥补受数字媒体冲击而损失的广告收入(Moe,2012b)。2018年文化部向议会提交名为《多样性和适当距离——新时代的媒体政策》的报告认为,媒体市场的全球化意味着挪威语内容面临更大竞争,商业媒体和NRK在提供广泛而多样的挪威语内容上都至关重要。(Kulturdepartementet,2018)挪威政府在坚持其媒体文化目标的同时,也力图通过政策调整来驯化媒体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力量。
三、财务和合法性双重压力下的公共媒体创新
在1980年代,即便没有竞争者出现,面临组织管理结构僵化和外部形势变迁,已有50年历史的NRK也是危机重重。受到二战经历和战后安排的影响③,NRK深具精英主义启蒙观念,雇员终身制和领导层长期不变,使其在几十年中保持相同风格而难以做出变革,这与1980年代盛行的个性化风格相去甚远(Syvertsen,1997:46-47)。1980年代的本地广播和卫星电视开放并未对NRK产生实质性影响,但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并敦促NRK做出某种回应。1982年NRK出台内部政策文件《新媒体形势下的NRK》,重点关注包括英国BBC在内的外国广播公司的竞争,认为NRK有责任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节目,特别是高质量的挪威语节目,确保国民不被外来节目所淹没(Puijk,2016)。
这个时期的NRK主要策略是增加节目供应和在部门层次提高节目的竞争性,但矛盾随之出现。高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意味着高投入,在卫星电视的竞争下,人力成本和节目资源成本(如重要体育比赛的转播权)使NRK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节目销售以及与其他北欧广播公司联合制作节目是NRK增收节支的办法,其他商业活动则效果不佳,或者带来合法性危机,招致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批评(Syvertsen,1992)。在旧的政府监管和组织结构框架下,节目创新也受到限制。例如,学者对NRK电视台重要的公共服务部门“启蒙部”(FOLA)在1980年代中期改革创新过程的研究显示(Puijk,2016),介于新闻部和娱乐部之间的不稳定地位,激发了启蒙部重塑报道领域和拓展节目影响的改革动力,但受制于当时官僚制度和部门阻隔,一些后来成为NRK常规做法的创新计划和设想在当时却无法实现,节目只能朝更传统的方向发展。
国家监管政策的松动是NRK能够适应1990年代商业广播电视竞争的基础。1987年工党政府关于将NRK改组为基金会的建议获得通过。1988年NRK由国有企业转变为“公共公司”(public corporation),董事会获得更多的内部事务自治权,如自主控制预算和薪资水平,为直接与员工进行薪资谈判打开了大门。政府总的控制模式未变,扩展自主权目的在于促进NRK内部改革以提高其作为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对市场反应的灵活性。因此,有学者评论这个时期的政策松动“与其说是为了减少国家控制,不如说是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中减少国家对广播公司所负的责任”(Syvertsen,1992:124-127)。
1987年NRK制定政策文件《 迈向2000年的NRK》,概括了其面向未来的战略重点,除了对于公共服务责任的关注外,也显示了对收视率和受众市场的关注。从1989年开始,NRK对公司结构进行了一系列重组改革,采用市场化的绩效管理、目标管理手段,打破部门界限,所有员工被解聘后重新上岗,对管理层重新招募和培训,推行项目制管理等(Syvertsen,1997:43,47-54)。 结构重组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和节目收视率,也带来了公司新旧管理文化的冲突。随着商业公司TV2的成立和全面竞争,效率提高也没有纾解财务困难,相反,员工薪资攀升和节目活动费用增长等竞争因素带来更严峻的压力。而人们期待公共广播公司履行社会文化义务,对其市场化行为并不认同,在1992年的议会辩论中,对NRK“商业化”的谴责达到高峰,公司甚至被威胁削减许可费和采取更严厉的政治规制(Syvertsen,1992:172)。
相互矛盾的期望和要求伴随公司新旧文化的冲突,典型地体现在员工薪资水平的争议上。从TV3等纯商业电视进入挪威后,NRK即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TV2公司在1991年成立并从NRK招募关键职位员工,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为了留住想要的人才,NRK给他们开出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资,这在当时的管理制度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工资差异化激发了内部员工之间的矛盾,在工会干预下,NRK经历了1990、1993、1994年三次罢工事件,结果先是记者整体工资水平和TV2大体相当,后是全部雇员的工资水平都大大提高,市场导向的差异化工资在NRK难以实现。更加麻烦的是, 作为公共服务机构,NRK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其他公共部门,这在政治上不具有合法性。因此,文化部不得不在1994年出面批评并警告:不合理的工资水平将损害NRK未来提高许可费的预期(Syvertsen,1997:52,99-100)。
随着TV2在1992年正式开播,NRK前期所做的争议重重的市场化努力转变为巩固其政治合法性的资源。由于 TV2开播后面临很大的商业压力,自制节目数量较少,NRK的节目收视率并未受到严重冲击,公众声望也因此获得提高。公众认可是获得政治支持的基础。NRK为争取受众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自制大型娱乐节目、强化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元素等。另一方面,作为公共广播公司的NRK也一直在强化那些能维持和辨识其身份的节目类型,在拓展市场化活动的同时,其新闻和时事节目也有长足发展(Moe,2012a)。
TV2最初是作为NRK的替代性选择而推出,但上述两方面因素结合, 政治精英对NRK在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节目和国家叙事上的地位有了更广泛的支持。政治合法性反过来提高了NRK获得自主性的空间,并进一步增强了其发展市场体系的能力。1996年NRK改制为有限公司,为参与商业衍生活动提供了方便;1997年NRK成立子公司Aktivum负责所有商业活动(Moe,2012a)。1998年NRK又进一步提出要求参与更多商业活动,文化部甚至在议会讨论之前就预先表示支持;对于社会公众和商业对手多有批评的NRK接受商业赞助问题,议会也没有明令禁止(Syvertsen & Karlsen,2000)。
商业媒体不仅是NRK的竞争对手,也是NRK创新学习的对象。尽管挪威政府担忧商业化威胁媒体所承担的社会作用,但实际上,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共享不少职业理念和价值判断。2003~2005年的调查显示(Maaso et al.,2007),挪威不同类型媒体的领导人发展互联网受众参与策略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建立受众忠诚、新收入来源、实验和创新,其中,创新被视为一种文化价值,和创收有同等地位。NRK在2003年推出的电视互动流节目Svisj,即是借鉴和改造商业媒体TVNorge在2002年推出的同类节目的结果(Enli,2005)。2007年推出的面向儿童的小众频道NRK Super,则是NRK对抗美国式商业电视文化和借鉴国际同行经验的结果(Enli,2013)。
在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公司积极进取的开放精神十分重要。1990年代中期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使传媒市场处于非常动荡的状态,NRK因为极高的政治支持而成为挪威数字电视发展的领导者,但对尚处于初期的互联网技术而言,NRK其时既无明确职责,也不能判断其发展走向,却从一开始就积极争取所有相关的发展机会。1995年NRK声称互联网可以更新其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挪威传统文化传播和帮助缩小数字鸿沟;1997年推出第一份互联网报告认为自己应该为所有平台提供内容以服务于用户需求,而不仅仅是广播和电视;1999年推出nrk.no网站,内容不仅有新闻和深度报道,还包括消费、娱乐等(Moe,2008)。挪威广播法并没有清晰界定哪些活动是公共服务,其他媒体对NRK的互联网商业活动也一直有警惕和争议,但在NRK的积极争取下,2004年挪威文化和宗教事务部(MCCA)表示互联网服务是公共广播公司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正式得到挪威议会的确认。2013年,在保守党和右翼进步党主政下,挪威政府曾启动对NRK商业活动和互联网业务的审查,意欲限制NRK利用其许可费优势削弱私人媒体机构的能力。经过四年漫长的辩论、听证和调查论证,NRK仍然得到广泛支持,其职权并未受到重大限制或修改(Sundet & Syvertsen,2021)。
管理学者曾将技术分为延续性和破坏性两类(克里斯坦森,2010),延续性技术不改变市场格局,破坏性技术创新则会在短期内造成产品性能降低,带来新兴的小市场,常被大企业所忽视,从而导致原先市场领先企业失败。1990年代中期以来,移动传播和互联网等破坏性技术创新给所有传统媒体都带来严重挑战。NRK作为一家成熟的媒体机构能适应新技术并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并非源自通常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而是在合法性和财务双重压力下进行组织改革和小心试错的结果。
媒体对新技术通常有“震惊”(shock)和“希望”两种反应(Sundet,2012),一方面担心新技术导致丧失受众和市场地位,产生生存焦虑,一方面又寄望于新技术带来的巨大机遇,可以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对于NRK来说,“生存焦虑”就是维护公共机构身份的合法性,只有保持在新技术领域的关键地位,成为“数字火车头”(digital locomotive),才能对抗商业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威胁,维护表达自由,履行其促进民族、文化和语言认同的社会使命(Sundet et al.,2020)。新技术通常还意味着年轻的用户群体,建立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力也是维护合法性的要求。推动NRK探索新技术的也有财务因素,NRK虽然主要收入来自许可费,但一直存在财务压力并寻求新的商业机会,新技术所展现的收入前景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投资技术试验和生产特制内容的高风险压力(Sundet,2007)。
在组织层面,NRK则采取了稳妥推进的策略,在确保传统的核心内容领域,提供高质量的时事和新闻报道的同时,通过单设新媒体部门或项目来进行新技术试验和新风格的内容生产。这些新的部门和项目里没有严格的流程规定和生产标准,提出建议和尝试新事物的门槛都很低,因而成为NRK的实验创新空间,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创新和试验本身更被看重,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作品(Sundet,2008)。这体现了公共媒体适应复杂环境的权变性。也有学者将此称作“自破坏”(autodisruption)(Evans,2018),即公共媒体基于新技术会带来破坏性影响的信念,在组织内部采取主动行为,在外力破坏之前进行自我破坏,以组织的短期损失来获得长远的收益。因此,尽管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公共媒体危机和边缘化的悲观预测不断,实际上,NRK在经历短暂的低谷后表现出非常强的竞争力,既在传统领域保持了高质量的内容生产,也在新媒体领域居领先地位。
据路透研究院2023年的统计数据(Newman et al.,2023),NRK线下新闻使用率位居挪威第一,为54%;线上新闻使用率仅次于小报VG位居第二,为39%;新闻内容的公众信任度高达80%,居所有被统计的媒体之首。而国际社交媒体中,排名最高的Facebook的新闻使用率为29%,其他如YouTube为13%,Snapchat为11%。公共媒体在新媒体平台的成功意味着其有能力对抗国际新媒体角色的影响。但同时,在数字时代,公共媒体仍然维持其内容多样性和传播普遍性的传统优势。一项针对NRK与挪威其他8家商业媒体2015~2017年在线内容的比较分析显示(Sjovaag et al.,2019),尽管在核心新闻领域(如政治、社会、体育文化报道)NRK和商业媒体内容相似,但它确实增加了新闻的多样性,填补了一些商业媒体报道的空白之处;而相比之下,商业媒体之间的内容相似度更高。这说明公共媒体增加了新闻内容的外部多元性。
四、规制的市场化:商业媒体趋同机制
面对1980年代本地广播和卫星电视兴起的压力,挪威仿照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模式,试图以公共法规来约束商业机构。商业电视TV2和商业广播P4于1992和1993年先后开播,通过签署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的许可协议以换取全国广告市场的专有权。两家媒体很快获得市场成功,但公共服务表现在第一个十年里并不如政府预期。
TV2在1994年实现赢利,1995年总利润达到1.14亿挪威克朗,占电视广告市场份额65%,成为“赚钱机器”。但文化部屡次批评TV2娱乐性过强,儿童和青少年节目质量差,虽然如此,随着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影响力增强,TV2并不看好续签许可证的价值前景,将商业竞争力放在首位(Syvertsen,1997:81-85)。商业广播P4则在商业化的路上走得更远。1996年文化部成立公共广播委员会来评估NRK、TV2和P4的活动是否符合公共服务的原则,P4因未履行公共服务义务而受到最严厉的批评,但P4 认为委员会的批评没有法律效力而拒绝其建议(Enli & Sundet,2004)。
导致政府要求和商业广播机构的自我理解相去甚远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两家商业广播公司在成立之初都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市场立足和赢得商业竞争是生存的首要压力。其次,挪威政府初次尝试管理商业公共服务广播公司而欠缺经验,许可条件的规约无法确保制度意图能被实现,政府也缺少和广播公司及时有效的沟通。这从P4公司在2002年申请许可证续签失败的经历中可见一斑(Enli & Sundet,2004)。
政府和TV2的冲突在1995年底达到高峰。当时卫星电视TVNorge试图和地方电视合作以扩大节目覆盖率,也就是借助地方电视突破TV2对地面电视市场的专有权。1995年初,议会裁定TVNorge的传播活动是非法的,也指出TV2有义务发展地方电视,建议其和地方电视台加强合作。不过,地方电视也受到了包括NRK在内诸多电视机构和媒体公司的重视和争夺,因此,同年秋天,TV2又向政府提议垄断与地方电视的合作,但议会在年底做出了损害TV2在全国市场专有权的决定。研究者认为,该决定根本上还是缘于政府和TV2之间的信任危机,在许可期内,政府对TV2的履行义务问题没有可行的制裁措施,重新规制电视市场以利于其竞争对手,是其仅有的可用的政策工具(Syvertsen,1997:88)。但损害TV2的市场专有权从长远来说也动摇了其承担公共义务的基础。TV2在1999年起用具有丰富采编经验的第三任总编辑,提升节目质量,修复与政府的关系,才于2001年顺利续签了许可协议(Enli & Syvertsen,2017)。
政府的规制政策可以警示商业媒体重视其所承担的公共义务,但是政策工具使用效应复杂,也带来很大限制。2002年政府通过竞标方式拒绝P4公司的许可证续签申请,并将其转授给Kanal24公司是典型案例(Enli & Sundet,2007)。一方面,政府通过更换许可证强调了媒体的公共服务责任,Kanal24因符合条件而赢得P4许可证,但过多的责任要求也损害了媒体经济能力,Kanal24后来不得不寻求新的投资者,改变了原来政府所看重的资本结构;而削减节目成本的需求也使其难以兑现政治承诺,2005年Kanal24就曾因儿童节目义务未达标而受处罚。另一方面,P4公司的商业利益(前十年的经营投资和员工就业)也是政府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2003年政府授予P4公司新的P5许可证,部分原因即是保护商业利益的平衡考虑,但是P5许可证的颁发削减了P4许可证的商业价值,并给Kanal24公司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
政府在TV2、P4的第二轮协议及新的P5协议中对媒体的责任义务规定要具体和繁重得多,同时也加强了对公共广播公司的监管。2004年11月,文化和宗教事务部授权挪威媒体管理局对公共广播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并发布独立报告。2005年议会修订《广播法》引入新的制裁规定,以确保广播公司的节目内容符合许可协议要求,制裁手段包括警告、侵权收费和强制性罚款(Medietilsynet,2005)。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市场结构,也带来了商业媒体未来发展更大的不确定性。TV2的市场份额曾长期保持在30%左右,但随着2007年数字地面电视网络建立,两个纯商业频道TV3和TVNorge的覆盖率大大提高,TV2也建立了一系列不受许可协议约束的针对目标人群的子频道,到2015年TV2主频道的市场份额降到约为18.2%(Mediemangfoldsutvalget,2016)。
2012年,Netflix和HBO等国际流媒体巨头进入挪威市场,带来了受众消费习惯的快速变迁,传统线性电视消费份额下降,订阅视听内容的流媒体服务份额在急速上升。据统计,2016年2月,41%的挪威家庭订购了至少一项流媒体服务,34%的家庭订购了Netflix,而TV2的流媒体品牌TV2 Sumo(现已更名为TV2 Play )在2016年的订阅率为11%,相距甚远(Mediemangfoldsutvalget,2016)。在竞争压力下,TV2采取了流媒体优先策略,大部分内容首发在Sumo,并增加算法等流媒体服务投资,但这带来很大风险,线性电视的影响力和广告收入进一步降低,而流媒体订阅费并不能弥补。为了应对紧张的财务状况,TV2在2016年宣布结构重组,计划到2020年裁减177个职位,④将成本预算减少3.5亿挪威克朗,即2016年预算的10%(Eckblad,2017)。
技术发展和竞争形势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与商业媒体的关系。一方面,由于许可专有权不复存在,政府对商业媒体的规制和要求越来越趋向于采用市场化策略,并采用新的政策工具,对商业广播公司的公共服务内容提供直接补偿资金。另一方面,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公共服务媒体以提供非营利导向的优质内容形象而与商业媒体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公共服务本身成为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媒体品牌(Hoynes,2003)。因此,尽管许可证不再对发展构成限制,但公共服务媒体身份仍然对商业媒体有很强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制度要求在市场化力量的作用下,一定程度上被转化成商业媒体的内生需求。
2010年挪威政府和TV2签署第三轮协议时,TV2采取了两手策略(Sjovaag,2012a),一方面“威胁”政府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则有可能将总部从目前的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迁往首都奥斯陆,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市场化的逻辑主张公共服务的义务要能有助于增加收入,以恢复责任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政府部分认可了TV2的市场逻辑,续签协议保留公共服务的核心要求,但减少了TV2的义务范围。在该协议即将到期的2016年,文化部曾宣布一项为期三年的临时协议,仅保留在卑尔根制作新闻和每日新闻报道的要求,其他要求均被删除,意在充分研究对商业媒体承担公共义务的补偿模型后,再将此临时协议更换为长期协议。但是该项协议无人申请。TV2在申请截止日致信文化部(Sandnes,2016),详述其在公共服务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相对于NRK而言的独特优势,强调在传统收益被破坏后,政府必须在经济上进行补偿。这一消息在挪威引起震动,《挪威日报》(Dagbladet)当日刊发评论《挪威语言和文化的悲惨一天》(Grande & Trettebergstuen,2016),对文化部政策提出强烈批评。文化部随后委托媒体多样性委员会对补偿方案进行调查,并于当年决定同意提供公共补偿,每年不超过1500万欧元(1.35亿挪威克朗)(NOU,2017:7)。2017年文化部宣布开放商业电视公共服务协议的申请,2018年9月,TV2和国家签订为期五年的协议,在中断两年之后,从2019年开始,TV2重新恢复其公共服务广播的身份。⑤
实际上,频道数量激增和竞争加剧激发媒体通过细分市场来加强对目标观众群的关注,而新闻内容作为细分主题具有极高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很早就被TV2作为一种市场整合策略而倚重。2007年TV2推出不受公共服务协议约束的“TV2 nyhetskanal”,这是挪威唯一的24小时新闻频道,既是产品差异化竞争的商业策略,也通过提供“公共品”(public good)而提升了TV2品牌形象和广告价值。在电视数字化后,挪威的两个主要商业频道TVNorge和TV3都削减了成本较高的新闻性内容,TV2成为唯一有常规新闻节目的商业电视。实时直播的优势使“TV2 nyhetskanal”在历次突发新闻和重大事件报道上吸引了大量观众,运营第一年即实现赢利。TV2创办新闻频道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于以硬新闻报道建立其“独立、负责和可信的新闻机构”形象,高质量的新闻生产创造合法性,吸引发行商、广告商和观众,而这又反过来提高了频道合法性(Sjovaag,2012b)
2016年是TV2作为公共广播公司的未来前景最不确定的年份。TV2在给文化部的公开信中表达了强烈的对双轨制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辩护,认为挪威不应再出现垄断的公共广播,而TV2的志向在于“继续成为NRK真正的竞争对手和替代者”( Sandnes,2016)。公开信中关于高质量新闻报道和挪威戏剧制作、成为挪威电视市场数字化发展驱动力等社会使命的叙述,表明TV2在争夺其作为公共服务媒体的努力。因此,有研究者对此评论说:“TV2的媒体形象和价值观不再代表跟挪威媒体文化相对立的因素,而是这个文化中熟悉、安全和成熟的一部分”(Enli & Syvertsen,2017)。2019年是TV2恢复公共服务责任的第一年,挪威媒体管理局对其在新闻报道和承担社会使命上的表现评价积极(Medietilsynet,2020),认为其有“扎实的新闻和时事报道基础”,在调查报道上有系统的工作安排并取得一系列成就,符合其在协议申请中所表达的新闻抱负,并且TV2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不同于NRK,增加了用户媒体使用的多样性。
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竞争能推动媒体从细分市场的角度发展新闻报道,但并不直接推动媒体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协议的规约和居主导性地位的公共广播机构作为竞争对手,是影响商业广播公司发展取向的重要动力因素。以同属于默多克集团的商业频道英国Sky News和美国Fox News为例,研究发现,Fox News以主观倾向性报道和娱乐煽情故事为主,缺乏对公共政策的关注(Morris,2005),而英国Sky News议程和BBC大体相同。学者认为(Cushion & Lewis,2009),BBC作为公共广播公司受到监管框架的约束,有助于维持英国电视新闻的基本标准,并塑造了公众的新闻偏好,这种广播生态的差异是导致Sky News不同于Fox News的原因。
在挪威,NRK一直是TV2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也是政府用以促进公共领域的重要工具,政府构建双轨制公共服务广播框架的目的即在于促进竞争和创新。根据政府要求(Kulturdepartementet,2015),NRK不仅要提供高质量的多样化的内容,还对促进挪威媒体多样性负有独立的责任,政府也对NRK监管以限制其利用强大的公共资金来削弱独立机构的活动能力。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NRK(2017)给自己设定了高远的目标,包括要成为世界级的内容生产者和发布者,参与全球性的市场竞争。NRK的目标和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为TV2设定了标准(Hjertaas,2019)。TV2和NRK近年在节目制作和重大体育赛事转播权购买上加强合作(Enli & Syvertsen,2016)。也就是说,国家规制在技术变革和全球竞争的语境中创造了一个超越竞争的媒体生态系统,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在其中不仅是竞争者的关系,也是一个共同环境中的互补者,公共媒体竞争市场合法性和引领创新,但也有义务成为商业媒体的合作者和促进者,从而整体上提高了商业媒体的产品质量,并共同增强了挪威媒体的国际竞争力。
五、总结与讨论
挪威公共媒体的创新机制体现于国家、公共媒体、商业媒体这三者的复杂互动中。总体来讲,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这些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有其历史和文化的根源。国家制度体现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内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国家与媒体之间的“适当距离”,对维护媒体的相对独立性、专业性和启蒙教育功能至关重要。对外开放政策所创造的市场和类市场竞争,则是此种共识导向的公共媒体能获得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
(一)妥协与开放并存的国家决策
挪威广播电视业从诞生迄今的近百年时间里,不管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还是挪威国家自身的遭遇,都远非平顺。但是,挪威国家在广电业发展中的角色却表现出极强的连贯性。那就是,在新技术采纳上,对内的妥协性和对外的开放性相结合;在媒体监管上,目标的稳定性和手段的灵活性相结合。这两个特征使挪威广电体制演化在表面上有很强的技术驱动的色彩。在每一个重要节点上,挪威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调整似乎都有顺其自然和不得不然的原因,背后体现的则是共识民主制度在应对技术/经济变迁过程中的务实主义的灵活性和柔韧性,从而在坚持政治文化目标的同时,也为公共媒体创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空间。
挪威国内对新技术的采纳和新机构的设立几乎都经过漫长的议会辩论,NRK和后来的TV2的设立、电视服务的引进等莫不如此,这使挪威的媒体政策有很强的保守性。漫长的协商也产生稳健的制度安排,公共媒体NRK在设立之初虽然受到政府的全面监管,但与政府保持了十分关键的“适当的距离”。这包括,政府不能直接控制公共广播的内容,NRK代表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总体利益,而不是成为政府的喉舌;许可费基于公众对广播服务的使用,不受现任政府控制;NRK董事会成员由教会和教育部长提名,由王室而不是政府直接任命,等等。挪威的媒体政策几乎不受执政党更替影响,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与这种稳定性和保守性形成对照的是,挪威在跨国性的新技术和媒体的接受上十分开放,例如,在1980年代开放卫星商业电视服务,与国际技术的最新进展同步。对外开放性及其对国内市场所造成的冲击,使国内制度的变革成为无法回避的必然选择,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技术变革的驱动,实际上仍然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挪威的对外开放政策直接受到诸如欧洲委员会等跨国组织和公约的影响,深层原因则是卡岑斯坦(1985/2009)所说的“小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使其很难采用保护主义策略。脆弱感知一方面强化了挪威国内的合作意识和制度化的对话形式,并通过补偿措施来解决市场竞争逻辑之不足。在传媒政策上,补偿措施体现为一方面坚持NRK的公共服务目标,同时也扩展NRK的内部自治权,使其适应市场竞争,乃至在新技术前景未明时,放任NRK自行探索新的可能性。制度与实践的松散耦合也为国家规制之下的公共媒体创新提供了重要的行为动机。
(二)市场环境对公共媒体的多重涵义
媒体组织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根据外在环境(如国家、市场)和内在条件(自身可供使用的资源)而采取行动。传统经济学从均衡视角和利润/利益最大化假设出发,将企业行为解释为内外条件的函数关系,也就是一种惯例行为(纳尔逊,温特,1997:30)。但是,创新显然是一种非均衡、不连续的现象。经济学演化理论强调组织在面对外部环境变革时,要经历一个不均衡的适应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发展新能力的过程。学习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依赖于具体情境的实践,通常需要形成社区(community)。因此,学习也是融入社区、参与实践和重新构想身份/认同的的过程(de Surie,2008)。从这个角度,市场化环境对公共媒体来说不仅意味着对受众的竞争、可能的获利机会,更重要的是同行和竞争者的存在本身,也是公共媒体学习创新得以可能的条件。
NRK在1960年开通电视服务之初,曾经严重依赖从英美进口的电视剧,但到1960年代中期, NRK开始推出成功的自制节目(Syvertsen,1992:62)。这很大程度上源于NRK高管和制片人作为个体的创新精神。通过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在支持性的文化氛围中,关于节目形式、制作技术等显性知识转移并不困难。但是,面对1980年代的各种批评和潜在的竞争压力,NRK的内部制度改革困难重重,难见成效。事实上,正是通过1990年代的双轨制竞争,NRK才真正建立起与商业媒体全面竞争的能力。这些更微妙的隐性知识只能在情境化的竞争实践中习得。
作为挪威国家实现文化目标最重要的制度工具,NRK既是公共服务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也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行业规范。为了保障NRK稳定的资金来源,挪威议会从2020年起将其筹资方式改为征收普通稅。不过,免于商业压力是NRK提供普遍服务的物质基础,却不足以保障NRK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受众多元需求的充分重视。双轨制的初衷在于构造竞争环境,NRK既要以高质量的节目和公共服务能力来争取政治合法性,也要加强与公众之间的联系,在变化的传播环境中找到平衡点,来加强市场和观众合法性。无意中产生的后果是,竞争环境也培养了NRK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后来数字化语境中的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
规模小而封闭的市场易导致媒体视野和思维的狭隘,丹麦学者伦德(Lund,2005)曾针对北欧媒体介于政治和市场之间的特征, 提出媒体市场的“制度竞争力”问题,认为过于保护国内市场将整体削弱北欧媒体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本世纪 ,Facebook、YouTube和Netflix等社交媒体和流媒体进入挪威带来行业范式转变,并使挪威电视媒体首次直接面对外国企业的挑战(Fossbakken,2015)。竞争极大地提高了NRK的自我期望水平,激发其积极创新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相比于商业媒体,NRK有公共资金的保障且较少赢利的压力,在探索新技术应用和新传播概念上更有优势(Syvertsen,2008),从而成为挪威“数字火车头”并带动TV2等商业媒体的发展。目前,挪威在前沿的流媒体服务上技术成熟,公共服务广播(NRK player和TV2 Sumo)和商业媒体机构(TVNorge的Dplay、TV3的Viaplay、小报VG的VGTV)均创建了自己的流媒体服务,形成全国性媒体和国际媒体混合结构的先进的流媒体市场(Lüders et al.,2021)。
(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转化
通常来说,市场制度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利于社会平等。国家以资源交换或直接补贴的方式来换取商业媒体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商业媒体履行契约关系,这并不违背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挪威(以及其他北欧国家)的公共服务广播制度,实质上是将市场制度和税收/财富再分配的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安排。
这个过程当中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家对文化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坚持和相关制度建设,使服务公共利益成为挪威媒体行业重要的意识形态,塑造了挪威特定的媒体行动规范。TV2等商业广播公司虽然最初是从追求商业利益的角度而承担公共服务义务,但是在国家监管制度约束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激励下,很大程度上也将公共利益内化为自身的追求。这样的制度氛围甚至影响了纯商业机构。挪威的私营媒体普遍认为应当承担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责任,即便是国际媒体集团在挪威的部门也比其他国家有更高的公共利益意识,体现“某种意义上的老式的NRK文化”(Syvertsen et al.,2019)。
意识形态是社会各群体在共同的生活经验中所形成的一些共同态度和偏好(利益)(施克莱,2005:4)。上述现象说明,社会偏好并非既定不变,而是在与制度的互动作用中塑造而成。基于社会共享的关于民主、启蒙、平等主义的观念,挪威国家在协调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建立公共服务广播制度。尽管如此,个人和社会团体不同的偏好/利益,并不因为共识的达成而消失,NRK在垄断期间不断遭遇挑战和批评即是明证。但是,制度的“恰适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具有教育、教化的功能,通过规定哪些行为是适当的,从而在构建共同体及其意义方面发挥作用(马奇,奥尔森,1989/2011)。对于挪威媒体来说,公共价值成为一种“公共领域的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了新技术和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过,制度设计的真正困难在于,在促进偏好一致的同时,也能支持替代性的愿景和对新偏好的探索。就挪威的公共服务广播体制来说,只有放在对外开放政策及其所创造的(类)市场竞争语境下,这种制度促成的意识形态转化才有意义。■
注释
①新P4和P5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0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1年,挪威政府规划将全国广播媒体切换为数字广播(DAB),从过渡期的角度,将许可证直接延长至2017年。 2017年底,挪威关闭全国性FM模拟网而转向数字广播,电台发展从技术上不再受限,自2018年起,挪威不再有承担公共服务义务的商业电台。
②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1972和1994年曾两次公投拒绝加入;但1992年起,作为欧洲经济区(EEA)成员,挪威的广播电视政策受到欧盟法律框架约束。
③二战期间,挪威被德国占领,政府和国王流亡伦敦,NRK伦敦分部曾和英国BBC合作制作战时宣传节目《伦敦广播》,鼓舞挪威人民士气,NRK在人民中获得很高威望。战后,挪威议会任命的 NRK第一任总干事为工党成员Kare Fostervoll,在“民主-民族运动”思想影响下,以提升民智为宗旨对NRK节目和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造。
④据TV2总编辑Olav Sandnes在2016年8月致文化部的关于临时协议问题的公开信,TV2其时约有850名员工,其中约500名是采编人员。
⑤根据挪威媒体管理局2023年6月发布的《2022公共广播报告:TV2中期报告》,由于TV2的公共服务协议将于2023年底到期,挪威媒体管理局已拟定商业公共广播的新协议,并已获得挪威议会的同意。
参考文献
〔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1985/2009)。《迈向更加充分了解国家的大道》。载《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美〕奥斯特罗姆(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陈红梅(2021)。《新闻媒体的新制度主义研究:问题、现状和重建》。《新闻记者》,(4),40-54。
〔美〕卡岑斯坦(1985/2009)。《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叶静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美〕克里斯坦森(2010)。《创新者的窘境》(胡建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美〕利普哈特(2012/2017)。《民主的模式》(第二版)(陈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马奇,〔挪〕奥尔森(1989/2011)。《重新发现制度》(张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美〕米格代尔(2013)。《社会中的国家》(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纳尔逊,温特(1997)。《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施克莱(2005)。《守法主义》(彭亚楠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美〕汤普森(2007)。《行动中的组织》(敬乂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宇(2016)。《北欧媒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挪〕希尔贝克(2014)。《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刘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ChristiansenP.M. (2017). Still the Corporatist Darlings? In P. Nedergaard & A. Wivel (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candinavian Politics (pp.36-48). New York, NY:Routledge.
Cushion, S. & J. Lewis (2009). Towards a “Foxification” of 24-hour News Channels in Britain? An Analysis of Market-driven and Publicly Funded News Coverage. Journalism, 10(2)131-153.
de SurieG.S. (2008). KnowledgeOrganizational Evolutionand Market Creation. NorthamptonMA: Edward Elgar.
Eckblad, B. (2017). TV 2-Sjefen om : – Dette er Toffe Dager. Dagens NringslivJan. 20. https://www.dn.no/tv/tv/tv-2/medier/tv-2-sjefen-om-tidenes-nedbemanning-dette-er-toffe-dager/2-1-31694
EnliG. (2005). Fenomenet SMS-TV. Institusjonelle Strategier og Semiprivat Interaksjon. Norsk Medietidsskrift12(2)116-135.
EnliG. (2013). Defending Nordic Children Against Disney. PBS Children’s Channel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ordicom Review, 34(1)77-90.
EnliG. & V.S. Sundet (2004). “Fornyelse vil vre det Normale”. Mediepolitiske Utfordringer og Markedsakt?renes Strategier i Kampen om Konsesjonen for Riksdekkende Radio (P4) i Norge. Nordicom-Information, 26(1)59–70.
EnliG. & V.S. Sundet (2007). Strategies in Times of Regulatory Change: A Norwegian Case Study on the Battle for a Commercial Radio Licence. MediaCulture & Society29(5)707-725.
EnliG. & T. Syvertsen (2016). The End of Television—Again! How TV Is Still Influenced by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rmediarie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4(3)142-153.
EnliG. & T. Syvertsen (2017). 25 ar med Kommersiell Allmennkringkasting. TV 2s Historie gjennom Redakt?rblikket. Norsk Medietidsskrift24(3)1-17.
EnliG.T. Syvertsen & O. J. Mjos (2018).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Media System.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43(5)601-623.
EnliG.et al (2013). From Fear of Television to Fear for Television. Media History19(2)213-227.
Evans, S.K. (2018). Making Sense of Innovation. Journalism Studies19(1)4-24.
Familie- og Kulturkomiteen (2008). Innstilling fra Familie- og Kulturkomiteen om NRK-plakaten "Noe for Alle. Alltid"Innst. S. nr. 169 (2007-2008)https://www.stortinget.no/globalassets/pdf/innstillinger/stortinget/2007-2008/inns-200708-169.pdfFossbakkenE. (2015). Netflix-feberen Avtar: Etter to ar med Kraftig VekstStagnerer Stromming av TV-innhold i Norge. Det Merker Ogsa Netflix. Kampanje, Feb. 15http://kampanje.com/medier/2015/02/netflix-feberen-avtarFossumH. (1997). The Norwegian Radio Reform. Nordicom Review, 18(1)59-68.
GrandeA.& Anette Trettebergstuen (2016). En Trist Dag for Norsk Sprak og Kultur. DagbladetAug. 4. https://www.dagbladet.no/kultur/en-trist-dag-for-norsk-sprak-og-kultur/60359738
HallinD.C.& P. Mancini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jertaasI.S. (2019). TV-Mediet i Endring – NRK og TV2 i en Strommetid. Master’s thesis, Hogskolen i InnlandetNorway. https://brage.inn.no/inn-xmlui/handle/11250/2619635
HoynesW. (2003). Branding public service: the ‘new PSB’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television. Television & New Media4(2)117–130.
Kulturdepartementet (2015). Open og Opplyst. Allmennkringkasting og MediemangfaldMeld. St. 38 (2014 – 2015). https://www.regjeringen.no/no/dokumenter/meld.-st.-38-20142015/id2423789/sec3
Kulturdepartementet (2018). Mangfald og Armlengds Avstand — Mediepolitikk for ei Ny TidMeld. St. 17 (2018–2019). https://www.regjeringen.no/no/dokumenter/meld.-st.-17-20182019/id2638833/?ch=1
LarsenH. (2014). The Legitimacy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ase of Scandinavia. Nordicom Review, 35(2)65-76.
LijphartA.& M. M.L. Crepaz (1991). 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Democracy in Eighteen Countries: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Linkag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1235-246.
LundA.B. (2005). Institutionel Konkurrenceevne pa Mediemarkedet. Nordicom-Information, 27(4)3-11.
LundA.B. & C. E. Berg (2009). DenmarkSweden and Norway: Television Diversity by Du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Co-Regu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1(1-2)19-37.
LüdersM.V.S. Sundet, & T. Colbjornsen (2021). Towards Streaming as a Dominant Mode of Media Use? A User Typology Approach to Music and Television Streaming. Nordicom Review, 42(1)35–57.
MaasoA.V.S. Sundet & T. Syvertsen (2007). ?Fordi De Fortjener Det?. Publikumsdeltakelse Som Strategisk Utviklingsomr?de i Mediebransjen. Norsk Medietidsskrift14(2)126-145.
Mediemangfoldsutvalget (2016). Vurdering av Modeller for Offentlig Kompensasjon til Kommersiell Allmennkringkasting. Oct.17. https://www.regjeringen.no/contentassets/3ed45ed8d5654dfd8f8188acd8d11ee8/delutredning171016-mediemangfoldsutvalgets_delrapport.pdfMedietilsynet (2005). Allmennkringkastingsrapport for Kringkastings?ret 2004. https://www.medietilsynet.no/globalassets/publikasjoner/allmennkringkastingsrapporter/2004-allmennkringkastingsrapporten.pdfMedietilsynet (2019). Eierskap i norske aviser og kringkastere. https://www.medietilsynet.no/globalassets/publikasjoner/medieokonomi/190109_eierskapsoversikt_aviser_kringkastere.pdfMedietilsynet (2020). Allmennkringkastings- Rapporten 2019. https://www.medietilsynet.no/fakta/rapporter/kringkasting/allmennkringkastingrapporter-2004-dd/
Medietilsynet (2023). Norsk medie?konomi 2018–2022. https://www.medietilsynet.no/fakta/rapporter/medieokonomi/
Moe, H. (2008). Public Service Media Online? Regulating Public Broadcasters’ Internet Servic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Television & New Media9(3)220-238.
Moe, H. (2012a). How to Preserve the Broadcasting License Fee: The Case of Norway.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9(1)55-69.
Moe, H. (2012b). Det Underforst?tte i Mediepolitikken: Eksempelet Formidlingsplikt. Nordicom- Information34(1)23-35.
MorrisJ.S. (2005). The Fox News Factor. Press/Politics10(3)56–79.
NewmanN.et al. (2023). Reuters Institute?Digital News Report 2023.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NOU 2017:7Det Norske Mediemangfoldet. En Styrket Mediepolitikk for Borgerne. https://www.regjeringen.no/no/dokumenter/nou-2017-7/id2541723/
NRK (2017). En allmennkringkaster i verdensklasseDec.1. https://www.nrk.no/oppdrag/en-allmennkringkaster-i-verdensklasse-1.7802563
osterudo.& P. Selle (2006). Power and Democracy in Norwa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rwegian Politic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29(1)25-46.
Puijk, R. (2016). Limits to Change: A Case Study of an Attempt to Innovate?in NRK’s Factual Programming during the Mid-1980s. Nordicom Review, 37(2)99-113.
RhodesR.A.W. (1994). The Hollowing Out of the Stat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Public Service in Britain. Political Quarterly65(2)138–151.
RokkanS. (1966). Norway: Numerical Democracy and Corporate Pluralism. In Robert A.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p.70-115).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lland, A. (2008). Norwegian Media Policy Objectives and the Theory of a Paradigm Shif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8(1)126–148.
Rolland, A. (2010). Modernising Freedom of Speech: The Case of Article 100 of the Norwegian Constitution. Policy Studies31(3)331-350.
RommetvedtH. (2017). Scandinavian Corporatism in Decline. In O. Knutsen (ed.)The Nordic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 (pp.171-192). Bergen, NO: Fagbokforlaget.
Sandnes, O.T. (2016). Vedrorende Ulysning av Midlertidig Avtale med Kommersiell Allmennkringkaster, Aug. 4. http://static.tv2.no/s/files/2016/08/04/20160804125413.pdfSaurweinF.T. Eberwein & M. Karmasin (2019).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Europ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ding and Audience Performance. Javnost - The Public, 26(3)291-308.
SelznickP. (1948).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1)25-35.
Sjovaag, H. (2012a). Regulating Commercial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 Case Study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Norwegian Media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8(2)223-237.
Sjovaag, H. (2012b). Revenue and Branding Strategy in the Norwegian News Market. The Case of TV 2 News Channel. Nordicom Review, 33(1)53-66.
Sjovaag, H.T.A. Pedersen & T. Owren (2019). Is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 Threat to Commercial Media? MediaCulture & Society41(6)808–827.
Sondergaard, H. (1996). Public Service after the Crisis. Nordicom Review, 17(1)107-120.
SundetV.S. (2007). The Dream of Mobile Media. In T. Storsul & D. Stuedahl (eds.)Ambivalence Towards Convergence (pp.87-113). Goteborg, Sweden: Nordicom.
SundetV.S. (2008). Innovasjon og Nyskaping i NRK. En Analyse av Plattform- og Sjangerbruk i Rubenmann-prosjektet” Norsk Medietidsskrift15(4)282-307.
SundetV.S. (2012). Making Sense of Mobile Media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slo.
SundetV.S.K.A. Ihlebk & K. Steen-Johnsen (2020). Policy Windows and Converging Fram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gitalization and Media Policy Change. MediaCulture & Society42(5)711–726.
SundetV.S. & T. Syvertsen (2021). From Problem to Solution? Why It is Difficult to Restrict the Remit of Public Broadc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7(4)499-512.
Syvertsen, T. (1992). Public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BBC and the NRK.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Syvertsen, T. (1997). Den store TV-krigen. Norsk allmennfjernsyn 1988-96. Bergen, NO: Fagbokforlaget.
Syvertsen, T. (2003). Challenges to Public Television in the Era of Convergence and Commercialization. Television & New Media4(2)155-175.
Syvertsen, T. (2008). Allmennkringkasting i Krise – Not! Norsk Medietidsskrift15(3)211–235.
Syvertsen , T. & Gro Maren Mogstad Karlsen (2000). The Norwegian Television Market in the 1990s. Nordicom Review, 21(1)71-100.
Syvertsen, T. et al (2014). The Media Welfare State: Nordic media in the digital era. Ann Arbor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yvertsen, T.K. DondersG. Enli & T. Raats (2019). Media Disrup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How Private Media Managers Talk about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in an Era of Turmoil. Nordic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1(1)11-28.
Tosi Jr.H.L.& J.W. Slocum Jr. (1984). Contingency Theory: Some Suggested Direc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0(1)9-26.
Weiss, L.& J. M. Hobson (2000). 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Strength Revisite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e Asian Crisis? In R. Robison et al (eds.)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crisis (pp.53-74). New York, NY: Routledge.
[作者简介]陈红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资助,批准号:2024ECNU—JP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