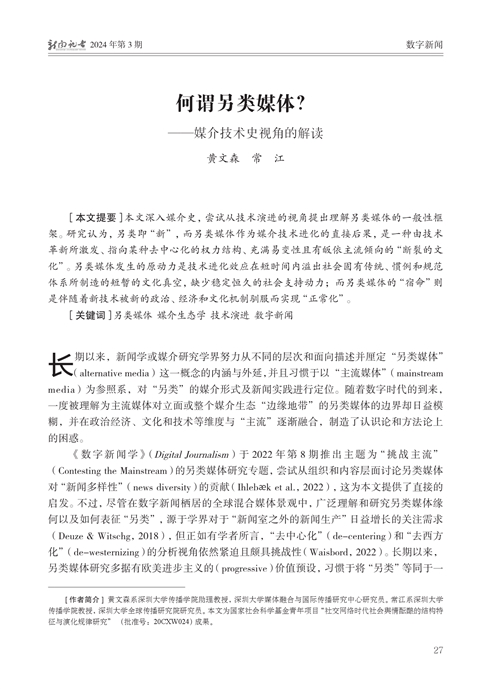何谓另类媒体?
——媒介技术史视角的解读
黄文森 常江
[本文提要]本文深入媒介史,尝试从技术演进的视角提出理解另类媒体的一般性框架。研究认为,另类即“新”,而另类媒体作为媒介技术进化的直接后果,是一种由技术革新所激发、指向某种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充满易变性且有皈依主流倾向的“断裂的文化”。另类媒体发生的原动力是技术进化效应在短时间内溢出社会固有传统、惯例和规范体系所制造的短暂的文化真空,缺少稳定恒久的社会支持动力;而另类媒体的“宿命”则是伴随着新技术被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驯服而实现“正常化”。
[关键词]另类媒体 媒介生态学 技术演进 数字新闻
长期以来,新闻学或媒介研究学界努力从不同的层次和面向描述并厘定“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且习惯于以“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为参照系,对“另类”的媒介形式及新闻实践进行定位。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一度被理解为主流媒体对立面或整个媒介生态“边缘地带”的另类媒体的边界却日益模糊,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维度与“主流”逐渐融合,制造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困惑。
《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于2022年第8期推出主题为“挑战主流”(Contesting the Mainstream)的另类媒体研究专题,尝试从组织和内容层面讨论另类媒体对“新闻多样性”(news diversity)的贡献(Ihlebk et al.,2022),这为本文提供了直接的启发。不过,尽管在数字新闻栖居的全球混合媒体景观中,广泛理解和研究另类媒体缘何以及如何表征“另类”,源于学界对于“新闻室之外的新闻生产”日益增长的关注需求(Deuze & Witschg,2018),但正如有学者所言,“去中心化”(de-centering)和“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的分析视角依然紧迫且颇具挑战性(Waisbord,2022)。长期以来,另类媒体研究多据有欧美进步主义的(progressive)价值预设,习惯于将“另类”等同于一种反主流的破坏性观念,甚至抵抗策略,这很容易带来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另类新闻生产在强化反建制新闻实践的同时,也向极端保守主义的新闻模式敞开了大门,其实际效应不仅对主流建制构成了挑战,而且扩大了媒介意识形态光谱的极化范畴,这一点时常被激情澎湃的研究者所忽视;第二,在非西方的语境下(比如中国),由于存在国家主导的新闻政策与媒体演化结构,另类媒体并不总是居于主流新闻理念与文化的对立面,甚至往往在一种调和性的权力结构的运作下,成为实践创新和行业增长的新动力,而我们目前也缺少对此做出解释的成熟理论。对此,本文可以算是一种探索,尝试跳出执迷于“另类”的观念窠臼,回归“alternative”的朴素本意——“可选择的”、“非传统的”——或更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数字新闻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中西方新闻理念与实践在当下历史条件下体现出的不同面向与潜能。
现有另类媒体研究主要从生产者、内容、组织和系统等方面来识别和确立构成另类媒体的关键维度或共同特征(Ihlebk et al.,2022;Holt et al.,2019;Rauch,2016),少有研究者从技术进化的角度观照另类媒体的历时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盖因理论界或社会行动者更注重“实践”和“行动主义”的推演逻辑而聚焦于另类媒体的“实践本源”(周翔,李镓,2015),抑或是为了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潭而强调技术仅作为塑造另类媒体的“物质条件”而非“必要基础”(罗慧,2010),以至于该领域的媒介技术叙述向来隐而不显。正如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的,欧美学者和媒体专业人士倾向于将另类媒体“自述”的立场作为反对主流话语的标志,以致容易忽略其所依托的媒介技术本身所潜藏的社会变革动力;而这种受限于单一政治和媒体环境的另类媒体研究理论话语,则遮蔽了新技术与传统/主流媒体及其规范理念之间普遍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Ihlebk et al.,2022)。完整的历史与实践认识论的形成有赖于多元叙述视角的交叉验证与相互补充,为避免技术决定论的指控而刻意忽视技术之于文化的生态性影响有可能导致理论的僵化。
为填补上述缺憾,本文将从宏观的媒介技术史视角探讨另类媒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尝试提供关于其观念和实践的“技术中心”叙述。具体来说,本文首先辨析传播技术的不同型态如何培育出相应类型(及风格)的另类媒介,并据此对传统新闻观念与实践构成挑战或修正;再落脚于对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类型学解读,期望据此呼应当下新闻学理论在解释不同行业实践的过程中遇到的技术迷思及媒介归因。本研究尝试超越对具体政治和文化语境的观察,着眼于对理解另类媒体的一般性框架的探讨,同时也力图据此丰富新技术条件下中国本土新闻实践前景与潜能的想象。
一、文献回顾:什么是另类媒体
西方学界对另类媒体的概念化通常采用比较的视角,即注重阐释“与什么相较而言,构成了另类”,而“主流媒体”则作为这种二分法(dichotomy)中的一个对立面存在。在此框架下,另类媒体被感知或践行为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或主流媒体的替代物甚至反抗者(Harcup,2019)。换言之,研究者习惯于将另类媒体置于一种“关系的”(relational)的目镜下加以检视,并认为这些媒体的另类品质主要源自其对某种霸权结构的对抗或某种单一结构的补充。在典型的另类媒体历史与理论叙事中,此类依赖于不受主流媒体支持的外部传播渠道或惯例的媒介系统,试图对主流新闻媒体中代表性不足、被排斥或被边缘化的议程进行另类报道和解释,并通过展现多样化的声音来影响舆论(Holt et al.,2019)。这些概念化方式显然过于简单化。即使从词源的角度看,“另类”也比“非主流”(non-mainstream)有着更加特殊且具体的实践语境和社会意义;而历史和当下的诸多经验表明,另类媒体并不能代表混合媒体系统中所有远离文化、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集体。同时,“另类”与“反抗”(oppositional)亦存在目的上的差异,前者寻求与既有霸权之间的共存,后者与“反信息”(counter-information)、“反霸权”(counter-hegemony)的意图相近,即谋求取代主导意识形态(Atton,2002:19)。
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另类媒体”术语所指涉的对象曾以“激进媒体”、“公民媒体”、“独立媒体”或“参与式媒体”等标签或命名出现,逐渐增强了这一概念范畴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复杂性。例如,霍尔特等(Holt et al.,2019)强调“激进性”是另类媒体的一个重要的认知标签,这类媒体往往被定义为那些在社会运动中出现的规模较小、非科层结构组织的且意在挑战霸权议程、优先事项及其观点的媒体。又如,最早由罗德里格斯(Clemencia Rodriguez)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公民媒体”(citizens' media)概念,在近年来开始被一些数字新闻研究者用于指称另类媒体,代表性学者如戴维斯(Stuart Davis)认为,这一术语可以帮助研究者反思“支配”(domination)与“从属”(subordination)的二元框架,转而从“社区”和“公民性”的视角理解另类媒体流动且复杂的生产经验,进而为通过“挑战社会规范(social codes)、合法身份和制度化社会关系”的实践赋予观念上的合法性(Davis,2015)。近年来,“介入式新闻”(engaged journalism)也被纳入了关于“另类”的讨论,这种新闻被认为是拥有专业背景的新闻行动者在传统新闻编辑室之外进行的生产活动,其目标在于挑战权威专业话语,并在社会运动中放大被边缘化的声音,而其“故意”游离于主流结构之外的后果是对传统新闻逻辑的破坏(Medeiros & Badr,2022)。
上述带有鲜明解释性色彩的概念化路径,折射了另类媒体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功能,但也暗示着单一概念难以统摄丰富的媒体价值和实践维度,其窘境恰如罗德里格斯所反问的那般:如何“用一张照片来捕捉舞者之美”(Rodriguez,2001:4)?为此,有研究者退而采用“覆盖式”(umbrella)的概念来描述另类媒体的典型(ideal):在组织结构、过程和形式上,它们是独立的或为集体所有,拥有横向或自组织管理体系,以小规模运作为主,以非营利和非商业目的为导向,积极使用低廉的再生产和分发技术,广泛从事与社区相关的新闻实践;而在内容上,它们致力于传递多样化、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声音,报道被忽视的问题和事件,倾向于支持社会变革(而非维持现状),倡导特定观点(而非保持中立),期望通过提供信息赋权公民采取行动,而不是将受众视为不参与的消费者(Rauch,2016)。这些另类媒体的特征基本上是在与商业化或主流新闻媒体相对立或补充的广泛领域中定位的,后者在西方国家媒体系统中的宰制性促成了另类媒体的编辑议程及其批评专业新闻的特质(Cushion et al.,2021)。
尽管如此,后来的研究者对另类媒体的类型学划分仍然没有超越克里斯·阿顿(Chris Atton)于2002年提出的分析框架,即从产品和过程来审视“另类媒体何以另类”问题。其中,媒介产品涉及内容和新闻价值、形式、复印技术的创新/改进;社会过程则包括分发、转换的(即“去专业化”)社会关系/角色/责任,以及传播过程和网络。藉由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传播模型,技术(特别是复印术)要素被嵌入阿顿关于另类媒体传播和社会过程的关键维度中,以便解释媒介激进化的可能性。例如,在“印刷”(printing)维度中,对复制技术(reprographic technology)的激进式使用,可能与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业余作家兼印刷工)相伴而生,从而与流行的印刷专业文化相抵触(Atton,2002:28)。
正如引言所指出的,当下的媒体研究者大多从静态和微观层面考察另类媒体本身的内容、生产过程或组织关系,将之与主流媒体进行下意识比较的惯性思维使这些讨论容易陷入“二元本质主义”。究其原因,在于学界把注意力倾注于“另类”之上,而忽视“另类媒体作为新闻业而运作的整体传播机制和媒介大环境”(罗慧,2011)。为此,本文尝试扩展关于“另类”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视角,以生物进化为隐喻,强调新媒介往往通过挑战旧媒介来践行其意识形态偏向的媒介演化规律,主张“另类”的本质就是“新”。这接近于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媒介进化论”(media evolution)思想,认为新媒介是对旧媒介的一种“补偿”和改良,并通过适应人的选择而实现进化,而进化的根本价值目标在于“文化权威的消解和文化生产的去中心化”(常江,胡颖,2019)。具体到阿顿的另类语境,“新的”或“另类的”媒介形式必须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民主沟通的三个方面(Atton,2002:25)——技能、资本化和控制上展现对既有主导性媒介的替代性倾向,即提供“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ed)、“去资本化”(decapitalized)和“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ed)的可能性。
二、另类媒体的物质基础辨析
技术演进视角在另类媒体研究中的隐没并不稀奇。在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主流叙述中,当代通信系统的物质基础或“物质性”(materiality)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Murdock,2018);在欧洲早期的批判性研究中,认为媒介研究的核心在“媒介之外”的观点也并不鲜见。“何以另类”(alternative to what)已然成为另类媒体研究议题发问的基础逻辑,而“何为媒介”却被大多数研究者以不言自明或缺省的方式理解为——“被动受众终将屈服于或用以抵抗大众文化暴政的工具”(Gillespie et al.,2014)。即便是阿顿也刻意与技术保持距离,在强调复制技术对另类实践的重要影响之后,他在其另类媒体研究三部曲的终章《另类互联网》(An Alternative Internet)中并未触及技术的基础性地位,反而试图“问题化”(problematizing)互联网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辩称“互联网应被视为人类过程所建构的而并非自然的现象来研究”(Atton,2004)。至此,阿顿尽管竭力跳出了“主流-另类”的二元对立框架,却又快速滑向了“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这对张力关系的一端。
然而,人类传播的物质条件应当始终是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的逻辑起点,这一理论体系内绝大多数问题最终落脚于:物质所具有的潜能如何转化成为具有实在社会效用的媒介?基于霍尔(Stuart Hall)的“最初决定论”(determination in the first instance),克劳斯·延森(Klaus Bruhn Jensen)曾辩证地看待技术在社会应用中的不确定性,并从“可供性”(affordance)、“嬗变性”以及“技术动量”三个概念出发辨析物质向媒介转变的过程,指出“物质为我们的表征与交流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一旦形成某种媒介形态,物质就获得了一种自我发展的动力”(延森,2012:67)。显然,延森小心地处理着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比较以身体、技术和元技术为物质基础的媒介环境及其变迁,以此启发关于“新”媒介如何在本地、国家或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社区/共同体的讨论。
在这个意义上,延森没有承袭伊尼斯(Harold Innis)的传播偏向论,即特定的媒介有着倚重时间或空间的偏向,“使社会倾向于以特定的方式组织和控制知识”(海耶尔,2019);而是借用了吉布森(James Gibson)的“可供性”概念,强调物质技术仅在最初的阶段决定着传播,其固有的媒介化潜能会随时间推移经历嬗变过程,继而对社会和文化产生结构性影响。在伊尼斯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新媒介挑战旧媒介,例如莎草纸挑战了依赖羊皮纸的教会“知识垄断”,而印刷工业的急剧扩张反过来形成新的垄断和控制,“物质材料在历史转变中一定会被赋予主导的地位”(海耶尔,2019)。与之不同,可供性框架既保持了物质属性决定行为的可能性,也突出了媒介的物理性质与人的知觉和使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将认知范式延伸至社会层面,主张“自然环境中最丰富和复杂的可供性……对于我们而言,是由其他人所提供的”(Gibson,1979:135)。
鉴于此,本文聚焦媒介本身而非媒介传播的具体内容,重申技术在新新闻传播实践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的基础性、生态性角色(常江,2021),并以此为认识论前提,着重从纵向的媒介演化历史进程,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竞争关系中,观察并讨论“新”媒介何以“另类”、如何存续,以此管窥作为社会和文化过程的新闻业/新闻学的技术迷思及后果。
可以预见,从媒介、技术或物质的视角出发,可以丰富另类媒体研究的观念和实践,有助于将我们的聚焦点从微观的、个别的媒体内容或活动切换至宏观的、一般性的媒介生态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所关注的是单数形式的“媒介”(medium)而不是狭隘的、泛论的“媒体”(media),讨论的是媒介、传播和社会的演进及其互动而不是不同地理空间、历史时期和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媒体组织(或变种)及其所中介的社会事件。从这个维度上理解的“另类”,实际上是新的媒介和传播技术所隐含的一种可能性或革命潜力。用媒介生态学理论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嵌入媒介之中的意识形态偏向(或者纠偏),它是“把世界构建成为一种形象而不是另一种形象的倾向,赋予某一事物高于另一事物的价值的倾向,放大某一种技能,使之比另一种技能响亮的倾向”(斯特拉特,林文刚,2019)。
三、技术进化与另类媒体的由来
媒介生态学者都曾论及媒介演进的历史分期,涉及口头、手抄、印刷和电子文化等不同阶段,如今数字时代的到来又重启了对媒介史划分的讨论,促使我们思考数字技术如何中介或嵌入新闻传播活动继而引发广泛的社会变革。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将重新考察大众媒介和数字媒介延伸人类传播能力或变革社会的特殊方式,具体切入另类媒介与新闻实践的交叉点,回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与其所孕育的另类新闻文化之间如何互动、共生。
(一)印刷媒介:复制技术的“补偿”
在西方语境下,作为手抄文本复制的替代,印刷术扮演了莱文森所言的“补偿性媒介”(remedial media)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显露了变革现状的潜力。另类媒介的历史起点始于15世纪,在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机引入欧洲之后,各类刊载新闻和信息的传单、小册子得以大规模生产,为新兴的商业阶层提供航运、银行、战乱等信息,而在那之前这还是世袭贵族的“特权”(Waltz,2005:13)。由于复制效率的提高,17世纪的商业报纸可由单独的个人组合、编辑消息并按特定格式印刷出来,例如1620年出现的第一份英语报纸就是由一名荷兰印刷工人独立印制完成,而后流通至伦敦(麦奎尔,2019:23)。同时,铅锡锑等合金冶炼技术的发展,以及脂肪性油墨、廉价纸张的生产应用都为活字印刷在西欧的流行铺设了坦途。
在中国,印刷术的历史可溯及唐代的雕版印刷术,乃至更古老的印章和碑拓技术。北宋时期(11世纪),由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虽然远早于古登堡印刷术,但由于其当时不足以“补偿”或取代成熟的雕版技术,而未能如欧洲的活字印刷术那般成为主流技术(董子凡,2007)。然则,雕版印刷对手抄本的补充也助推宋代民间“小报”的复制、扩散和商品化。“镂板鬻买,流布于市”的小报突破了官方“邸报”对新闻和时事信息的垄断和封锁,或为在野者所用,刊载不利于当权者的消息而屡遭查禁。可见,新技术虽蕴含补偿或修正旧技术的潜力,但未必终能取而代之。古登堡印刷术挑战的是工坊化的手抄业,而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的“对手”是工艺成熟且顺应汉字书法文化的雕版印刷,前者以摧枯拉朽之势催生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者则在手抄与雕版印刷的夹缝中生存,酝酿下一次复制技术“革命”。
19世纪初,铅字印刷术经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引入并“反哺”中国,雕版印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上海为中心的印刷革命得益于《申报》、《新闻报》等商业报纸对高速印刷机的创新采纳,其中对“夏儿意”、巴德和马里诺尼等品牌滚筒和轮转印刷机的使用甚至领先于传统书商,暗合了近代报刊追求速度、信息容量、大众化的商业逻辑(曾培伦,2018)。例如,1872年美查(Ernest Major)等人筹措兴办《申报》,执白银千余两悉数用于“投资印刷机器、铅字及其他附属设备”,得以达至“报事确而速”。《申报》很快从两日刊改为日报,再利用廉价新闻纸降低售价,最终击败上海最早的中文商业报《上海新报》,致其被迫停刊。戈公振曾在《中国报学史》中描述昔日上海报业“争消息之先后”,“印刷愈迟,消息愈速”,若无备有最高速的印刷机是不可能实现的,故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关于复制技术最精辟的见解莫过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文化理论,他看到了“机械可复制性”(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如何将“艺术的”转变为“政治的”,以致“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贺婧,2020)。机械复制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取代了本雅明式的“灵晕”(aura)艺术,恰如报纸、杂志等印刷品对书写文化的冲击。诚如延森所言,印刷媒介作为一种公共传播平台,具有“不受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所支配的潜在性”(延森,2012:72)。即便已经进入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复印机革命”(photocopier revolution),(Atton,2002:38)依然得以再次展露机械复制的文化势能,使另类出版者或粉丝能够快速且廉价地印刷独立的、非官方发行的“粉丝杂志”(fanzines,也称“迷志”),真实地推动了抵抗主流表达和消费形式的朋克运动。
“相较于印刷术,报纸更可谓一种创新”。由于其所具有的面向读者的实用性和迎合新的社会阶层所需的世俗性(非宗教性),自降生之日起,“报纸便是既有权力的事实或潜在对手,报纸对自身的认知尤是如此”(麦奎尔,2019:23)。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乃至中国近代国人办报的热潮都是这一事实的注脚。大众化商业报纸作为“另类”开始挑战政治组织喉舌的政党报刊,被认为是西方另类媒体历史叙述的近代源头;而当这些“另类媒体”在西方新闻自由体制确立后跃居为“主流”之时,现代意义上的另类新闻实践才真正开启。
19世纪以降,欧美主流商业报刊日渐成长为后来另类媒体所抵抗的“大众媒体”(mass media),其特点在威廉斯关于民主沟通的三点上均有所体现。在专业化上,新闻价值(news values)作为“判断特定信息是否值得报道的标准”,悄然从新兴的大众化报纸“以营利为首要目的的商业环境中”生长出来,个人(报业家、编辑和记者等)的偏见与资本主义固有的意识形态共同“嵌入”新闻编辑室的实践中(Waltz,2005:14-15)。在资本化方面,媒体市场调查和广告的出现,让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观察英国激进报纸消亡的历史中,洞见“市场对媒体内容的影响甚至远超于政府”。这也是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学者对“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极为忌惮的原因——标准化机器生产的文化商品使个人不加批判地接受操纵而放弃抵抗(Waltz,2005:16)。在控制层面,可以参考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资产阶级媒体“制造公共性”(manufactured publicity)的论断:政治组织及其代表对公共讨论的规避致使公共领域被“再封建化”成一座“宫廷”,“在它面前,公共声望得到展示;在内部,却不存在批判性的讨论”(韦斯特,2021:21)。
(二)电子媒介:无线电波的“传播革命”
随着人类对电流的驾驭,19世纪中期的电报以电子脉冲的形式出现,允许信息脱离物理运动(依赖步行、骑马或铁路等)在广泛的空间流通。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作为电子工业的第一个产品,电报对现代生活以及未来技术发展的影响可能被低估。首先,在美国出现的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成为行业寡头垄断市场,为后来的传媒私有制打下根基;其次,电报改变了语言、知识和意识的性质,思想通过“唱歌的电线”(the singing wire)传播,一种新的报道形式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的新闻文学;此外,电报还“扭曲”和改变(但没有取代)了自然地理所形成的连接模式,首次使“传播”(communication)超出“运输”(transportation)的范畴(Carey,1983)。
尽管电报最早应用于铁路交通控制,但旋即成为传递新闻的重要工具。19世纪40年代,如同先前的蒸汽印刷机一样,电报也被美国“便士报”率先引进而成为其打破政党报刊传统的革命利器。其中,《巴尔的摩太阳报》于1846年在全美第一条从华盛顿到该市的电缆线接通后首先使用该项技术;1848年,美国纽约的《先驱报》、《太阳报》、《论坛报》等便士报联合组建了后来称为“美联社”的电报连线机构以搜集新闻。1849年,在法国巴黎开创的电报新闻服务机构“路透社”,开始使用电报替代鸽子、火车等联络方式。在中国上海,《申报》于1881年最早引领报业使用电报,利用长达1000多公里的津沪电报线路传递南北新闻。
对“科技论”持谨慎态度的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承认电报推动了美国19世纪30年代“政治中立”的便士报革命的成功,“但丝毫不能解释便士报的独特内容”(舒德森,2009:28)。然则,在凯瑞的视野里,电报和便士报的发展只是即将到来的“传播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的前兆,预示着“国家或大众”(national or mass)媒体(即主流媒体)的兴起,以及在种族、职业、地区、宗教和其他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中“专门”(specialised)媒体(亦即另类媒体)的发展(Carey,1965)。殊不知,电报已然经由改变书面语言进而重塑了新闻的意识形态,使“客观性”(objectivity)成为新闻业尊奉的圭臬。“客观报道”(objective reporting)被认为肇始于以电报为基础的通讯社,后者要求记者提供任何报纸都可使用的与党派无涉的(即“客观的”)新闻,这一由商业策略转变而来的职业责任意识逐步演变成快速工业化时期西方新闻业的“迷信”(fetish)(Carey,1965)。同时,电报服务还规定了一种近乎“科学”的语言形式,以脱离地方化、地区化和口语化;然而,电报语言的简化和标准化,却造成言说形式和新闻叙事风格(如煽情、幽默或讽刺)的消失,最终使“故事与讲故事的人分离”(Carey,1983)。
广播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其高度集中的发行模式,由权力中心向外扩散而几乎没有回路,同时受到公共部门的严格规制和执照管理。不同于电报,无线电广播在发明之初,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的“野心”就超越了“点对点”传送摩斯密码的基本用途,而是让信号可以摆脱线路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并触达更多的人。广播为此而获得某种“可信性”或“公开性”——电波信号是开放、没有限制的,任何拥有收音设备的人都可以放到“耳朵边上去听”,而不像无线电报那样如同“没有装在信封里、匿名投递的信件”(彼得斯,2018)。广播在成为公众之声之前就如莱文森口中技术进化的第一个阶段——“玩具”,还只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嘈杂的“电磁空间”,直至20世纪20年代被军队、国家和广播公司置于管辖之下。“海盗电台”(pirate radio)用以指代那些无执照的、非商业性的广播电台,作为最广为人知的另类媒体随后在世界各地出现,尤以英国为甚。据估计,在那个年代仅英国就有超过25万人以某种方式参与业余无线电广播。“海盗广播者”(pirate broadcaster)强烈反对国家和商业系统对广播的垄断,并通过普及自制的收音机的方法激励大众对广播的兴趣,见证了电子另类媒介及其相关文化最鼎沸的时期。
无线电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介技术引发了“旧”技术对新进者的恐惧。报纸反对蓬勃发展的广播行业,甚至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成立几年后也被禁止成立自己的新闻部门;在美国,由于对竞争的恐惧,新闻机构停止向电台提供服务,这迫使第一批无线网络(NBC和CBS)建立了自己的新闻部门,与之抢夺新闻受众。英国和美国的广播体制大相径庭,前者由公共服务广播公司(BBC)所主导,后者由市场驱动的商业制度所控制。诚然,建制化和资本化淘汰了业余广播者,但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替代方案(alternatives)”(Coyer,2007)。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离岸”海盗电台(为了躲避国家法律制裁而在国际水域开办的广播电台)到90年代兴起的女性电台,有的人想借此为少数群体发声或建立反机构(counter-institutions),而另一些人只是想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无论何种情况,都印证了“经济实力最弱的人总是依赖低技术、低成本和更易获得的传播形式,即使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只是在使用其所掌握的手段——这也是他们的受众可能存在的地方”(Coyer,2007)。而这一点,在其后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数字媒介:参与性作为意识形态
随着微型集成电路在20世纪70年代的开发,计算机从工业领域逐步渗透进入家庭,个人电脑的普及又为万维网(WWW)的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艾伦·凯(Alan Kay)等研究者曾将计算机描绘为元媒介(meta-media)。简言之,就是数字计算机有可能复制和整合以往其他类型(印刷、电报、广播电视等)的媒介特征。这与麦克卢汉对媒介交替的历史认知相贴合,即旧媒介“包含于”新媒介的形态之中,例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但计算机作为元媒介整合了面对面人际交流,涵盖大众传媒时代的传播特质,它并非视觉所感知的硬件组成,而是“计算和数字化提供的多媒介潜在能力总和”(胡易容,2017)。
20世纪80年代,电子邮件仍是最常见的网络应用。尽管可以传输数字图像,但局限于信息交换标准码(ASCII)所生成的文本,故早期互联网仅能在传播速度上对电报“补偿”。在此期间,一度出现以邮件列表和其他基于电子邮件的激进组织模式,涉及艾滋病联盟、校园刊物、同性恋群体和环境行动联盟等。20世纪90年代,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等人基于尼尔森(Ted Nelson)提出的“超文本”系统创造了万维网,后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算机迷反主流文化的积极分子,曾呼吁普通人争取“控制”在技术精英手中的计算机使用的权利,足见另类精神的“火种”早已埋在数字技术创生的那一刻。伯纳斯-李基于“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构建的网络能够连接世界各地的超文本系统,随着文字、图像和音视频的加入,彻底改变了互联网的外观和使用体验,并诞生了最早一批基于万维网技术的另类媒体网站,如EnviroWeb和NativeNet。
自此,互联网这一所谓的“电子复合体”(electronic complex)为反对群体提供了创造另类文化的途径——“作为其通信、情报和组织的核心,用以展示动员信息、另类新闻、视频流、网络电台、档案、讨论列表、聊天室、公告板和声音文件等”(Atton,2002:133)。1992年,美国的《实用无政府主义在线》(Practical Anarchy Online)是第一本完全以电子形式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期刊,通过订阅形式由编辑向订户发送电子邮件提醒收看更新。1994年,中国与国际的64K网络信道开通后,一些“民间刊物”开始从传统转向网络,刊载“新闻”及个人评论的独立网站短暂出现。其后,互联网技术进步对新闻信息管理制度提出新的挑战,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的严格实施,大量未能被新制度纳入管理轨道的“另类”信息服务或网站被关停或整改。例如,依托多平台传播且独立运营的新媒体产品《好奇心日报》诞生于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2014年,曾被视为与主流商业类信息媒体差异竞争的新兴资讯服务提供者,在4年后因“非法组建新闻采编团队”、“对网络舆论生态造成恶劣影响”而被紧急叫停。
尽管互联网降低了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成本,但小规模、集体结构的另类媒体却因为“短命”和难以触达广泛的受众而遭致诟病。公众参与新闻仍然受到另类媒体专业控制的限制,例如研究者(Ozgul & Veneti,2022)发现土耳其和希腊的独立新闻网站中仅有极个别网站让读者参与新闻选择的过程,大多数媒体依然固守传统的把关模式,只有经过编辑严格审核的新闻才能被传到网站上。可见当下,互联网的传播潜能还没有“回归”延森所期待的“人际传播的互动和多元化的交流模式”(延森,2012:74),更遑论哈贝马斯对自由对话的“公共领域”的理解。
“让更多的人成为积极的生产者”,一直是许多另类媒体核心的文化政治目标,而受众转变为生产者的历史也要早于数字时代。“参与式媒体”(participatory media)由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视频工作室”(video workshops)发展而来,并以当前的互联网实践为进行时,见证了媒体的“民主化”历程。前者以新的便携式摄像机(portapak)技术为手段,让非专业人士得以进入视频生产过程直接表达观点和诉求;后者以2004年奥莱利(Tim O' Reilly)宣称的“Web 2.0”为转型标志。
在Web 2.0的框架下,互联网进入由专业人员创建模式转向所有人参与织网的民主化阶段,更强调用户共同开发、创造和自我服务的“长尾”效益以及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重要性(O' Reilly,2005)。如今,伴随着个人博客、评论区、推荐系统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介形态的层出不穷,越多越多的普通用户创作和传播内容成为可能。相对于传统媒体形式,这些媒介形态具有更快、更自动、更广泛和更公共的受众“反馈”特征(Lee & Tandoc,2017),从而生成一种数字技术所形塑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其核心是“关乎所有用户的集体主义和平等贡献,……更多用户以近似无限的顺序参与其中,以实现群体智慧和福祉的规范目标”(Lewis,2012)。可见,数字媒体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出现了明显的范式转变,新技术赋予受众在新旧媒介交汇的空间中争取参与文化的权力。诚如范·迪克(van Dijck)所理解的那样,当旧媒体占据主导地位时,受众几乎没有直接权力来塑造媒体内容,抑或进入市场与之展开竞争;而以此为目的建立的新的数字环境则“释放了受众自我表达和创造力的需求”(van Dijck,2009)。
在新闻业领域,区别于传统大众媒体工作的替代性实践通常被称为“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这一模式意味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对由传统媒体支持和实现的建制化传播(institutionalized communication)的“去制度化”倾向,即数字技术“允许用户(作为个人或集体)根据其观察或观点生产和传播新闻”,从而形塑超越“现代”(或称“流动现代性”)的新社会秩序(Domingo et al.,2008)。在赛斯·刘易斯(Seth Lewis)的社会-技术视角下,参与性是“个体利用数字文化和技术的动机和可供性来解决群体问题”的一种功能。如果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专家控制”,那么“去专业化”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通过开放沟通系统衍生参与性的“分布式控制”(Lewis,2012)。该文化现象的形成源于越来越多的新闻生产者意识到必须改善与新闻编辑室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努力融入这种“参与伦理”(Belair-Gagnon et al.,2019)。在“去资本化”的倾向上,数字技术在降低跨时间和空间协调人类智慧和行动成本方面具有巨大的潜能,“众包”(crowdsourcing)作为一种知识搜索和问题解决方法,因其低成本接触大量的、多样化的人和故事而在新闻业中崭露头角(Aitamurto,2019),例如美国独立的非营利性媒体ProPublica采用众包方式生产了从孕产妇健康到社交媒体仇恨等诸多新闻报道(Parris Jr,2018)。同时,“自由和开源软件”(F/OSS)文化依赖非货币形式的奖励,在公开、透明的理念下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非私有化目的(Lewis,2012),使得互联网被视为争取信息公开或透明性的工具,譬如“公民黑客”(civic hacking)(Schrock,2016)所代表的参与样态,通过设计、批评和操纵软件和数据来明确地参与政治,以改善社区生活和治理的基础设施。
四、结论与讨论
前文基于媒介技术演化的历史,得出了一个理解和理论化另类媒体的一般性框架:另类即“新”;而另类媒体作为媒介技术进化的后果,在宏大而漫长的社会和文化历史中,首要是一种由技术革新所激发、指向某种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充满易变性且有皈依主流倾向的“断裂的文化”(a culture of ruptures)。另类媒体发生的原动力是技术进化效应在短时间内溢出社会固有传统、惯例和规范体系所制造的短暂的文化真空,缺少稳定而恒久的社会支持动力;而另类媒体的“宿命”则是伴随着新技术被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驯服而逐渐实现“正常化”。
在此,我们以传播实践与权力平衡的媒介类型学结束这段关于另类媒体的技术史叙事。表1列举并说明了不同信息传播环节上发生的技术革命、媒介形态和观念变迁。表格横向上强调生产、传播和接收三种实践过程,并且有一定的时间承续性,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技术演进历程相适应。表格纵向上按照媒介与(经济/政治/文化)权力中心的距离和控制程度进行划分:那些影响力大的媒介往往更受制于管控,实际拥有的自由是有限的,更倾向于在技术嬗变中形成建制化或宰制性的媒体形态;而边缘的、民主化的媒介形式则拥有更多的去专业化、去资本化和去制度化的自由,以及更激进的或补偿性的偏向。
上述发现对于我们在比较的视野中理解数字时代的全球另类媒体实践具有启发意义。由于断裂性(ruptured)或破坏性(destructive),另类新闻实践总是在媒体传统、惯例和规范滞后于技术革新的短暂“时间差”中发生,且始终有着被主流所规训、甚至成为“新主流”的发展趋势。因此,在那些“时间差”更短,亦即“建制”对“社会变动”反应更迅疾、制度环境加诸文化实践的约束力也更强的体制下,另类媒体的“叛逆期”往往也更短,且越晚近出现的另类实践样式越倾向于从一开始就接受自身作为“主流”的调和性补充物的文化政治定位。相比之下,那些另类媒体的“反主流”效应更显著也更持久的社会,通常拥有政治权威较为薄弱、立法或行政流程相对复杂,或资本对政策干预性较强的体制。因此,欧美学界和业界倾向于将“另类”视为“反抗”的化名有其历史合理性,而中国学者也须基于对本土实践的忠实解读形成自身的另类媒体阐释框架。
循沿上述逻辑,基于一种总体上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想,我们可以想象另类媒体实践在全球范围内体现出的多样文化效能和政治潜力如何在更新的技术架构(如仍在想象中的Web 3.0)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以实现一种对于更具多样性的新闻专业文化的创衍。就本文的思考而言,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基于技术演进形成的“另类”和“主流”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动态性特征,而“另类”所扮演的破坏性或调和性角色也是高度语境化的,其历史意义凝结于具体的实践之中而非来源于某些被假设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认知前提,这提醒数字新闻或数字媒体的研究者要警惕“主流-另类”或“旧-新”的静态二元论框架,以“生态(环境)-制度(行为)”的流动性观念体系不断对新的现象做出阐释并避免给出非历史的结论。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本土的数字新闻和媒体实践发展来说,也要尽可能走出对欧美意识形态框架随意“拿来”的简单化思路,要看到进步并不必然来自“对抗式的激进主义”,而新闻和媒体“应然”的社会角色也并不由单一的力量所决定,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念体系下实现对本土理论和实践的准确把握。
与此同时,在一个更宏大和长远的观念体系下,与其说“另类”是“主流”的对立面或补充,不如说它是“未来的主流”在当下的一种初级形式。它固然有着小而美、新而锐的原始魅力,甚至在某些时刻力扫文化建制的陈腐之气,散发出人本的光辉。但它的演化规律却时刻提醒我们人类社会既有主流化机制的强大。对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来说,在数字化营造的科技乌托邦主义氛围中保持对“另类”及其反抗性特质的严肃检视,也是一种重要而攸关的品格。■
参考文献
保罗·海耶尔(2019)。哈罗德·英尼斯的媒介环境学遗产。《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角》(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常江(2021)。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实然、应然和概念体系。《新闻与传播研究》,(9),39-54。
常江,胡颖(2019)。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引导着文明的进步——媒介生态学的隐喻和想象。《新闻界》,(2),4-9。
丹尼斯·麦奎尔(2019)。《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六版)(徐佳,董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董子凡(2007)。古代中国缘何未推广活字印刷。《国际新闻界》,(5),70-73。
哈特穆特·韦斯特(2021)。《哈贝马斯论媒介》(闫文捷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贺婧(2020)。对“灵晕”的呼应:数字复制技术时代的艺术 从本雅明到斯蒂格勒。《新美术》,(10),24-33。
胡易容(2017)。帕洛阿尔托学派及其“元传播”思想谱系:从神经控制论到符号语用论。《国际新闻界》,(8),38-53。
兰斯·斯特拉特(2019)。刘易斯·芒福德与技术生态学。《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角》(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2012)。《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罗慧(2010)。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另类媒体的概念辨析与内涵界定。《国际新闻界》,(5),78-82。
罗慧(2011)。当前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的兴起与走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7-25。
迈克尔·舒德森(2009)。《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约翰·杜哈姆·彼得斯(2018)。无线电广播中的公众之声。《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编;董路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曾培伦(2018)。近代商业报纸何以成为“技术新知”?——以中国活字印刷革命中的《申报》《新闻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12),88-101。
周翔,李镓(2014)。西方另类媒体概念再辨析:基于历史演进与实践的视角。《新闻与传播评论》,(0),1-10。
Aitamurto, T. (2019). Crowdsourcing in journalism.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ton, C. (2002). Alternative Media. London: Sage.
Belair-GagnonV.Nelson, J. L.& LewisS. C. (2019). Audience engagement, reciprocityand the pursuit of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in public media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13(5)558-575.
Carey, J. W. (1965).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3(1_suppl)23-38.
Carey, J. W. (1983).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the telegraph. Prospects8303-325.
Coyer, K. (2007). Mysteries of the black box unbound: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radio. In CoyerK.DowmuntT.& Fountain, A. The Alternative Media Handbook. London: Routledge.
Cushion, S.McDowell-NaylorD.& Thomas, R. (2021). Why national media systems matter: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How UK left-wing and right-wing alternative media critique mainstream media (2015–2018). Journalism Studies22(5)633-652.
Davis, S. (2015). Citizens’ media in the favelas: Finding a place for community-based digital media production in social change process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5(2)230-243.
Deuze, M.& Witschge, T. (2018).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9(2)165-181.
Domingo, D. et al. (2008).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practices in the media and beyon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nitiatives in online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2(3)326-342.
Gillespie, T.Boczkowski, P. J.& Foot, K. A. (Eds.). (2014). Media technolog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Materialityand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HarcupT. (2019). Alternative journalism.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13.013.780.
HoltK.Ustad Figenschou, T.& Frischlich, L. (2019). Key dimensions of alternative news media. Digital Journalism, 7(7)860-869.
IhlebkK. A. et al. (2022).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news media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diversity. Digital Journalism, 10(8)1267-1282.
Lee, E. J.& Tandoc Jr, E. C. (2017). When news meets the audience: How audience feedback online affects new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3(4)436-449.
Lewis, S. C. (2012).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MedeirosD.& Badr, H. (2022). Strengthening Journalism from the Margins: Engaged Journalism in Brazil and Egypt. Digital Journalism, 10(8)1342-1362.
O’ReillyT. (2005). What Is Web 2.0? Design patterns and business model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oftware. O’Reilly. http://oreilly.com/web2/archive/what-is-web-20.html.
Parris Jr, T. How the Public Fueled Our Investigations in 2017. ProPublica.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how-the-public-fueled-our-investigations-in-2017.
Rauch, J. (2016). Are there still alternativ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alternative media and mainstream media in a converged environment. Sociology Compass10(9)756-767.
Rodriguez, C. (2001) Fissures in the Mediascape: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itizens’ Media. New York: Hampton Press.
Schrock, A. R. (2016). Civic hacking as data activism and advocacy: A history from publicity to open government data. New Media & Society18(4)581–599.
Van DijckJ. (2009). 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generated content. MediaCulture & Society31(1)41-58.
Waltz, M. (2005). Alternative and activist med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aisbordS. (2022). Alternative media/journalism and the communicative politics of contestation. Digital Journalism, 10(8)1431-1439.
[作者简介]黄文森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常江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交网络时代社会舆情酝酿的结构特征与演化规律研究” (批准号:20CXW024)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