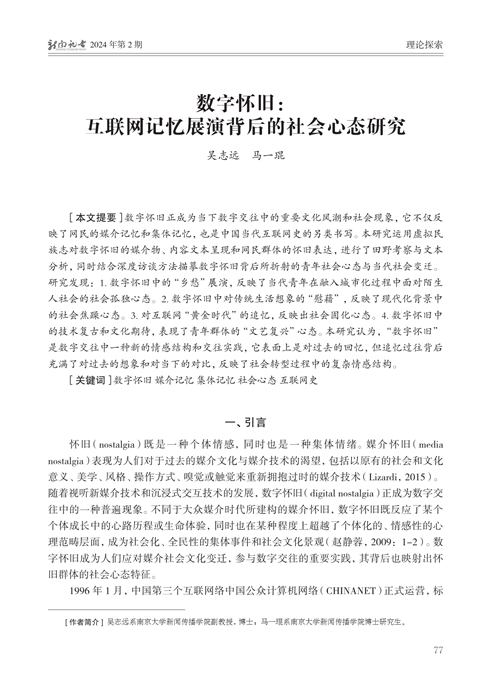数字怀旧:互联网记忆展演背后的社会心态研究
[本文提要]数字怀旧正成为当下数字交往中的重要文化风潮和社会现象,它不仅反映了网民的媒介记忆和集体记忆,也是中国当代互联网史的另类书写。本研究运用虚拟民族志对数字怀旧的媒介物、内容文本呈现和网民群体的怀旧表达,进行了田野考察与文本分析,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方法描摹数字怀旧背后所折射的青年社会心态与当代社会变迁。研究发现:1.数字怀旧中的“乡愁”展演,反映了当代青年在融入城市化过程中面对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孤独心态。2.数字怀旧中对传统生活想象的“慰藉”,反映了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焦躁心态。3.对互联网“黄金时代”的追忆,反映出社会固化心态。4.数字怀旧中的技术复古和文化期待,表现了青年群体的“文艺复兴”心态。本研究认为,“数字怀旧”是数字交往中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和交往实践,它表面上是对过去的回忆,但追忆过往背后充满了对过去的想象和对当下的对比,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情感结构。
[关键词]数字怀旧 媒介记忆 集体记忆 社会心态 互联网史
一、引言
怀旧(nostalgia)既是一种个体情感,同时也是一种集体情绪。媒介怀旧(media nostalgia)表现为人们对于过去的媒介文化与媒介技术的渴望,包括以原有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美学、风格、操作方式、嗅觉或触觉来重新拥抱过时的媒介技术(Lizardi,2015)。随着视听新媒介技术和沉浸式交互技术的发展,数字怀旧(digital nostalgia)正成为数字交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同于大众媒介时代所建构的媒介怀旧,数字怀旧既反应了某个个体成长中的心路历程或生命体验,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个体化的、情感性的心理范畴层面,成为社会化、全民性的集体事件和社会文化景观(赵静蓉,2009:1-2)。数字怀旧成为人们应对媒介社会文化变迁,参与数字交往的重要实践,其背后也映射出怀旧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
1996年1月,中国第三个互联网络中国公众计算机网络(CHINANET)正式运营,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的组网与入网等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大众化、商业化发展之路。“80后”、“90后”与中国互联网共同成长,在今天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有趣的现象是,他们同样也是数字怀旧内容生产、传播和消费的重点群体。在这一集体互动展演式的数字怀旧实践过程中,是什么共同的怀旧媒介因素导致了其传播的可能?其背后又流露出何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本研究运用虚拟民族志方法,通过对数字怀旧的媒介物形式、怀旧内容的文本呈现和网民群体的怀旧表达进行田野考察与文本分析,并辅以对青年群体的深度访谈,来描摹数字怀旧的表现和特征。本研究认为,要深刻理解数字怀旧的社会意义,不能脱离对当代青年群体的怀旧社会动因、个人情感结构和技术文化要素的综合分析。因此,数字怀旧研究不能浅尝辄止于表征性的媒介记忆研究,而应通过对微观个体的深度访谈,管窥其背后更为深邃的社会心态变迁。
二、文献回顾:数字怀旧与社会心态的变迁
(一)数字怀旧与媒介物研究的兴起
怀旧(Nostalgia)最早被认为是一种与乡愁相关的生理病症,到了近代才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正常心理现象得到具体研究(Keightley & Pickering,2014)。研究者认为,怀旧是在社会衰退、经济结构变化时产生的集体现象,可以帮助个体在面临大的人生转变时维持身份(Davise,2011)。怀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情绪的治疗机制,人们用一段治愈创伤的过去经历,营造一个安全和稳定的乌托邦。因此,怀旧的表达方式可能表明一种对快速发展技术的反应,怀旧可能是现代化进步的表现,也可能是某种社会动荡的危机的征兆(Boym,2002)。
在传统类型的怀旧实践中,媒介充当着人们与其旧日经验的中介物(mediator)或入口(portal),即“中介的怀旧”(mediated nostalgia)(Lizardi,2015)。人们既可以基于个人亲身经历,以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及影视小说等大众文化媒介为中介进行怀旧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些媒介和大众文化载体进行个人未亲身经历的历史怀旧(Bolin,2015)。
近年来对于媒介与怀旧实践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媒介的中介化视角,而是将媒介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性的怀旧物,讨论媒介本身作为怀旧对象的可能(Niemeyer,2014)。物质性理论是理解和认识媒介的新视角,媒介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与中介物,成为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丁方舟,2019)。而媒介物处于“物质性”与“关系性/社会性”的关系之中,这二者是任何存在物赋予自己被体验和被认同的两种方式并相互呼应,正是这些关系维持了物的存在(Cooren,2018)。在此意义上,以物质性视角来理解媒介与怀旧研究,就不能仅将媒介视为怀旧实践的技术中介,而要从人与媒介物互动的角度去理解媒介。
在当下数字交往的环境中,数字怀旧实践是将既往中介化与物质性的媒介怀旧类型延伸到数字平台所展开的记忆展演和怀旧实践。相关研究考察了基于不同平台的数字怀旧实践,例如有研究通过考察在闲鱼平台的旧技术物iPod如何籍由二手实践实现再商品化,来探析关于过往技术生活的记忆与知识何以重塑其文化价值(黄顺铭,陈彦宁,2021);有研究则基于迷你四驱车爱好者的QQ群,考察迷你四驱车迷这个因“物”联结起来的趣缘群体如何展开记忆实践(孙信茹,王东林,2019)。同时,还有研究关注到用户基于专门化的怀旧性数字平台开展的数字怀旧实践,比如对《人民日报》“时光博物馆”项目这一专门的怀旧主题数字平台用户实践的考察,探知嵌入到数字媒介场景中的怀旧情感何以带动用户开展怀旧互动展演和情感共鸣(周海燕,2019)。通过前述研究可以看到,数字媒介不仅是记忆的表征载体和传播中介,其本身也可以成为怀旧的对象、物质性设施与互动形式。遵循这一思路,本研究考察用户基于“小红书”等数字平台所展开的数字怀旧实践,包括用户的怀旧展演内容、形式和身份形塑过程。
(二)媒介记忆与互联网史研究
数字怀旧源于媒介记忆(media memory),它关注利用或通过媒介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以及有关媒介的记忆(about the media)(Neiger,Meyers & Zandberg,2011:1-2)。媒介记忆因人们使用媒介而产生,因此它关注个体与媒介的交往,在此意义上,媒介记忆既包括有关媒介的记忆,也是有关回忆者的记忆,具有媒介传记和回忆者自传的双重性质(吴世文,杨国斌,2018)。
随着个体网民成为记忆主体之一,媒介记忆的范畴与内容得以不断丰富,媒介记忆的叙事方式出现了个人化的倾向。在个体层面,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更加聚焦“小我”,微观的记忆视角和常人化的叙事内容,使得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更为丰富,并且生活化程度更高;在群体层面,数字时代的个体记忆因在网络互动中相互碰撞与相互沟通而具有主体间性,“协作式记忆”的书写模式是常见的现象:不仅陌生人之间的记忆通过“偶然相遇”而增加了彼此的记忆重量,而且有些个体已经“忘却”的记忆能够通过在线互动的“提醒”机制被唤醒(吴世文等,2021)。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媒介记忆的受众面向。例如,将媒介记忆中的个体视为“记忆消费者”,强调在具体的语境中解读人们如何参与记忆文本的阐释(谢卓潇,2020);在数字时代媒介记忆实践个人化转型的背景下,媒介记忆研究需要将个体的主体性带回记忆研究领域,聚焦记忆携带者如何与数字媒介互动从而进行记忆实践的问题(王润,2022)。
因此,本研究在扩大对“媒介”认识的同时,着重将时空维度纳入媒介记忆研究,从用户个体记忆、历史变迁和社会情境考察怀旧情感生成背后的社会心态;同时考察“怀旧”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结构,何以联结时空、媒介和公众,进一步深化对当代青年“数字怀旧”背后社会心态的认识。
(三)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的网络表征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杨宜音,2006)。其中,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从社会心态的整体全貌出发,郑雯等(2022)依托“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青年亚文化不断“中心化”并形成以教育程度类聚的独特景观,而这一趋势根植于广泛存在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彰显当下青年群体张扬个性、对抗权威等心态特征。
从青年社会心态的具体文化表征出发,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转型背景下青年社会心态的阶段性变化与网络表达展开讨论。在众多互联网文化表达形式中,网络流行语作为青少年数字生活的日常交流语言,是青少年亚文化的典型景观,背后潜藏着一代人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追求(骆正林,2022);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及其变化也透视着青年群体的社会境遇与社会心态变迁(王佳鹏,2016;2019)。此外,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还会以更为广谱的文化形式进行呈现,比如不同社会时期出现的各种文化思潮,无论是前几年以“废柴”、“葛优躺”等为代表的“丧文化”(董扣艳,2017),还是当下“内卷”与“躺平”共存的思想潮流,都折射出青年群体正承受着社会结构性张力的塑造与寻找动态稳定与平衡的努力(邢婷婷,2023)。可以说,相关研究均基于不同经验现象呈现了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不同纬度意涵,但对于当下愈发蔚然成风的数字怀旧潮流有所忽视,而这也是本研究试图切入的创新性视角。
怀旧作为一种社会心理,也是一种文化潮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成为集体情绪和情感的表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心态的特征和流变。本研究将在分析青年群体数字怀旧实践过程中所流露的情绪体验的过程中,进一步剖析这些碎片化情感表征背后所蕴含的结构性社会心态。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的方法,辅以数字怀旧实践内容的文本分析来进行,具体方法是虚拟田野观察、线上网友互动观察与深度访谈的结合。按照海因(Hine,2000:65)的界定,虚拟民族志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其作为一种致力于独特地理解互联网的重要性及其意涵的方法,来探讨与互联网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卜玉梅,2012)。
为更好地考察数字怀旧的具体实践内容与网民群体的怀旧表达,研究者以用户身份于2022年5月开始在抖音、快手、小红书、微博等平台观察用户的数字怀旧行为与互动讨论内容,经过两个月的观察比较最终选取了小红书平台作为主要虚拟民族志的观察田野。研究者于2022年7月开始,通过文本分析和算法反向推荐训练,梳理出32个小红书平台专注于数字怀旧的账号作为重点观察研究对象①,并于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期间,每天平均用一小时对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粉丝评论和互动等进行参与式观察与田野笔记记录。
考虑到“80后”、“90后”是伴随中国互联网成长,且媒介记忆深刻的一代,作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其社会情绪的释放、社会心态的表达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因此,本研究将这一群体作为重要访谈对象,以理解其数字怀旧实践背后的社会心态与深层感受。具体而言,研究者参照18~35岁的青年标准,适当放宽年龄限制,基于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取了1982年~1998年出生的15位青年作为访谈对象,对每人进行了平均不少于2小时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了解访谈对象的生活环境、个人成长经历、媒介技术使用习惯、数字怀旧实践,以及对怀旧现象的自我评价等。访谈自2022年12月开始,至2023年6月结束,受访者中“80后”8人、“90后”7人,女性7人(用F表示,“80后”3人,“90后”4人)、男性8人(用M表示,“80后”5人,“90后”3人),本科以下学历3人、本科学历5人、硕士学历5人、博士学历2人。职业分布包括学生、工人、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企业职员、公职人员、媒体从业者、教师等。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在访谈本科以下学历人群时发现,这类群体的数字怀旧表达要弱于较高学历者,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口述史表达,因此对其中一些无效访谈对象进行了筛除,下文第五部分还将对这一现象进行适当讨论。
四、制造怀旧:数字怀旧的三种记忆展演实践
(一)对前互联网的“记忆搬运”:媒介物与日常经验的数字怀旧
怀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离不开承载它的物质基础。在互联网诞生以前,传统的怀旧更多诉诸怀念过往的人与事,诸如书籍、照片、电影、服饰等媒介物虽也有其怀旧中介的意义,但总体上对这类媒介物的怀旧诉诸静态的记忆复现。事实上,当某些媒介物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再成为普遍通用的物品,甚至濒临消失时,更容易成为公众回望和追忆的怀旧对象(Higson,2014)。在当下的数字怀旧实践中,媒介物是重要的共同记忆载体。这其中,既包含以往大众媒介时代的媒介物,也包含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媒介物。数字媒介既是怀旧主题传播的中介媒介,又是承载怀旧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也是怀旧实践的数字化互动形式,数字媒介体现出与用户、怀旧议题、怀旧物等多主体交织的综合性的媒介属性(王润,2022),数字媒体技术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记录,还可以作为自我展演与记忆传布的行动性工具出现(刘于思,2018)。通过对小红书平台的怀旧账号和内容进行观察,本研究发现如下几种媒介物,在怀旧的展演中扮演了“记忆搬运”的角色。
1.回忆“经典”:经典流行音乐与“土味”网络音乐
音乐天然具有引起人们对特殊时间和空间的回忆的特质。“老磁带回忆录”是一个拥有5.1万粉丝,获赞与收藏10.4万的小红书账号。该账号的内容为用老磁带机播放的音乐视频,每个视频的文案都是“当年满大街都是这首歌”。磁带曲目均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如刘德华、周华健、叶倩文、姜育恒、王杰等曾经风靡一时的歌手的当年代表作。在其评论区,网民们留言表达“还是那时的声音更亲切”(维C)、“70后走过”(心事舒)、“80后走过”(浅沙月光)、“这个收录机看着好有感觉,小时候谁拎着这么一个在大街上老牛逼了”(蓝哥)。高赞的评论常常和某些共同成长经历有关。“星月白卡带时光”同样是一个以复古歌曲怀旧为内容的账号,拥有7.2万粉丝。网民们会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情感和感悟:“再听到这首歌,仿佛在马路的对面看到了那个青春洋溢的自己”(米米)、“不能再听,热泪盈眶!歌声响起带给我太多年轻时候的回忆!”(Julia)
被网民追忆的不仅仅有流行音乐,2000年初网络歌曲进入一个创作高峰期,许多当年被视为“口水歌”的歌曲同样受到网民的怀念。例如,在“怀念8090年代”的小红书账号中,一条题为《二十年前烂大街的网络歌曲,二十年后再听是不是你的宝藏》的视频音乐帖下,网民评论的高赞留言写道:“以前的歌手都是可以封神的,现在的歌手都是鬼怪”(青鸟飞鱼)、“现在都是看脸的年代,以前才是听歌的年代”(大鹰帝国^_^飞鹰)、“那时候觉得这些歌都好土啊。和现在一比较,明明都不错”(小红薯633AE7EC)。从网友的互动评论中可以看到,当时被视为“土味”的网络音乐,可能内容“土”但却是发自真情的“土”;相形之下,现在的流行音乐经常被视为内容空洞的“精致”,是商品化流水线式的生产与传播。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经典歌曲,还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土味”网络音乐,人们“怀念”的是那个时代朴素动人的情感、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以及生机勃勃的文艺创作面貌,相对而言,这些被怀旧者认为是当下社会中所匮乏的元素。
2.追忆“新鲜”:数码科技产品的新奇与创新
在数字怀旧实践中,一些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旧技术设备成为怀旧的创作内容。吴世文、周夏萍(2022)研究发现,用户追忆自己在与手机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性关联”、“符号性关联”与“拟人性关联”,手机的文化传记因而具有物质性、符号性与拟人性三种表征。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对旧手机、旧随身听、电子词典等数码产品怀旧时,用户会回忆获得新科技产品时的新鲜感和兴奋感:
“苹果”没出来之前的手机造型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当年“苹果4”刚出来确实很惊艳,可是现在满大街一个样,毫无创新。(F1)
文曲星PC220,我上初中时的第一部电子词典。和现在的数码产品比,这款机器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可在当时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科技冲击,那时候我们大部分同学还是在用字典啊,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新奇感和快乐,是现在的智能手机没法带给我的。(M3)
正如受访者的共同感受所言,在当代记忆实践中,媒介技术不仅建构和中介了记忆,其本身也成为追忆的对象。人们追忆过去的旧设备时,追忆的其实是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创新活力,是过去的技术发明所带来的惊艳与震撼。
通过观察还可以发现,用户在网上展示这些旧设备追忆怀旧的同时,也获得了共同成长经验的认同。例如,在小红书平台一条名为《你人生的第一部手机》的帖子下,网民们留下4.5万条评论,高赞评论包括“酷派,当时可火了这个牌子”(小川崎,5883赞)、“我酷派甩飞了,都没坏”(我要偷你裤衩子,604赞),而且每条高赞评论下面都会引发更多网友基于楼主评论进行追评,通过类似“我也是”、“我当时……”的句式展开自己对当时的追忆与个人故事的叙述。可以看到,在数字怀旧场域中,网民们既会向他人展演自己的怀旧记忆,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发表观点和体验,从而实现个体记忆汇聚成集体记忆的“协作式记忆”的怀旧实践。
3.怀念“复古”:前数码时代的传统与时尚
怀旧作为一种消费文化,会在网民心目中和时尚联系在一起。在当下社交媒体文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用户对于过去媒体技术/媒介物的强烈兴趣,CCD相机、黑胶唱片、随身听、录像带和街机电子游戏等模拟制品已成为流行媒体实践的一部分,并通常被描述和标识为怀旧、复古或“复古狂热”的表现。除了对原始模拟媒体技术的重新认可外,各种数字媒体应用程序也在出现,这些应用程序具有类似物的外观和感觉,例如醒图、美图秀秀等应用为用户提供各种复古胶片相机滤镜,通过模拟过去媒介技术的元素,例如胶片颗粒、划痕、闪烁的灯光、模糊的边界和褪色处理,使照片类似20世纪70年代的宝丽来照片、老胶片相机的风格,这些都是在当代记忆实践中对复古的技术化“怀念”。
青年群体是这类前数码技术复古的“主力军”,这类群体实际上并非胶片时代的原生消费群体,相比于“怀旧”所指涉的剧烈社会变动后对曾经拥有的已消失事物或过往黄金时代的眷恋,更偏向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新技术的反思。而这种复古实践,带有一种对现有流行文化的抵抗意味(Magaudda & Minniti,2019):
我身边的朋友同学会去闲鱼、小红书等平台淘零几年的CCD数码相机,拍出那种自带复古感的照片,实际上也是想跳出现在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同质化的网红滤镜的一种尝试吧。(F7)
普通的照片如果加上仿胶片相机的复古滤镜,会一下子变得很有质感和故事感,并且会显得我修图痕迹很自然(因为没有采用那种网红高清滤镜模板),就可以在朋友圈营造一种漫不经心的文艺美女感觉。(F9)
可以看到,受访者对于前数码技术的复古实践并不一定是由对过去的怀旧而驱动的,这种复古实践也有可能是个体在线自我表达和形象塑造的“表演”工具,是个体通过审美区隔从而寻求身份认同的技术中介。
4.想象“童年”:80年代的生活场景再现
空间和场景经常被人们称为具有记忆仓储的作用,能够引发人们的往日回忆与共同体验。正如英国学者D ·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1975)对空间/景观与记忆关系的论述:往日必然存在于现在的景观之中,而往日景观提供了文化连续性。“通过对往日的了解,才使我们学会重塑自己。通过对我们自身经验的了解,我们也能重新设计往日,并取代始终处于被改变或丧失的往日”。关于空间与记忆的关系一直被学者们所关注,已经成为当今记忆研究的重要领域。
记忆和地方/空间的结构性联系最显著地表现在物质文化景观领域。有学者将记忆视为社会行为,并营造了空间的社会特性,与群体认同密切联系(Hoelscher S & Alderman D H.,2004)。这种由怀旧空间所连结的群体认同在本研究的田野考察中也清晰可见。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旧影像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的广告、春晚)、旧街景纪录片、老动画片、旧课本、旧的家庭陈列场景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定生活场景,唤起了该年龄群体用户对过去,尤其是“童年”的想象与追忆。以小红书博主“王蓝莓”为例,这是一个拥有1430万粉丝的账号,主要发布20世纪80年代插画、宣传画的复古动画视频,展现“80后”经典童年剧情与场景。这种复古的风格加上引发“80后”、“90后”共同成长记忆的生活回忆,使该账号得到大量关注与点赞,也引发多位受访者的共鸣:
这个账号的风格我很喜欢,感觉就是我们“80后”小时候上小学的那间教室,那个老师,那个同学。视频里的热水瓶、全国一样的花被单、家具,都很熟悉,让我好怀念啊。(F2)
看这种画风,小时候真是岁月静好啊,想回到过去,真的不想长大。(M5)
可以看到,空间与场景在个体记忆的唤醒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网友基于怀旧博主发布作品所展开的个人生命历程的互动与分享,也描摹出“80后”、“90后”的共同童年印象:淳朴、可爱、简单、物质匮乏但容易感到幸福。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冲击使得城市与乡村的景观面貌都不断更迭变迁,“80后”、“90后”童年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大多荡然无存;加速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步调不断加速,造成了现代生活中人的“异化”,让现代人对于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感到困扰不堪(哈特穆特·罗萨,2018:51-52),在此背景下,人们对于无忧无虑的童年的追忆与感怀,也是对充满压力焦虑的当下的一种逃避与情绪发泄。
(二)对早期互联网的“见证缅怀”:个体互联网生命史的数字怀旧
1.见证“发展”:互联网早期的野蛮生长
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被国际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②自此开启互联网“野蛮生长”的早期阶段。1994年,CN顶级域名服务器运回中国;1996年,中国第一个网吧开张;2008年,中国网民数跃居世界第一,达2.5亿。③这个过程正是中国“80后”、“90后”青少年的成长时期。青少年时期对互联网的个体使用体验,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见证的中国互联网史的集体事件,成为另一种以互联网技术本身为回忆对象的数字怀旧实践。
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对这种早期互联网使用技术追忆的数字怀旧现象,例如吴世文、杨国斌(2018)对消逝的网站进行了追忆研究。吴世文、何羽潇(2021)从媒介、情感和社交关系角度对网民追忆QQ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看,网民个人生命史意义上的互联网数字怀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研究重视。正如杨国斌(2018)所言,“互联网的早期历史,充满了活生生的个人”。随着“80后”、“90后”的成长,他们个体的互联网生命史也正在成为当下数字怀旧的重要研究内容。这些对互联网初期发展的“见证缅怀”,可以作为当代中国互联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微观视角,在这一见证缅怀过程中,也流露出社会心态的变化。
受访者M2在回忆自己的互联网早期使用经验时,提到了“VeryCD电驴”网站,在他的回忆中,强烈表达了这种互联网早期使用经验与个体互联网生命史的联系:
VeryCD电驴可以说是2000年初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下载分享网站,它很传奇,虽然下载速度按现在的网速标准来说很慢,但它能下载到的东西,比现在所有网站都更全,只要在网上存在就可以下载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常用的下载软件就是电驴和电骡,除了买DVD之外,更多的是从VeryCD上面下载。(M2)
与之类似的是,还有多位受访者分享了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如何交织着早期互联网的发展轨迹,比如“第一次触网的经历”,早期的上网方式、体验与情感等个人生命故事,这些个体经历洋溢着互联网进入平民生活之初给人带来的技术震撼与蓬勃活力,而这也构成了他们当下追忆早期互联网个人使用历史时所缅怀的实质所在。
2.缅怀“氛围”:互联网早期的社会活力
当谈及早期互联网的整体环境与使用体验,多位受访者均基于个人的互联网使用经历给予肯定的评价,并流露出缅怀之情:
当年也是电脑病毒肆虐的年代,下载的东西充满了病毒,电脑动不动就要蓝屏和重新装机,往往这个时候就成为男同学进入女生寝室的契机,女同学请男同学去帮忙修电脑,我就去女生寝室给女同学重新装机过五六次吧,跟宿管阿姨说帮忙修电脑也不会被拦着。可以说无论当时的网络环境,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氛围,真的是自由、开放、真诚、朴素,确实会怀念当年的那种环境和氛围,特别是很多东西都已经在当下的社会荡然无存。(M2)
当时网络上极少喷子,网民的素质很高,乐于助人的人真的很多。而且在各个论坛上,很多人发的帖子就接近于现在的网络小说,很勇敢的分享,让你大开眼界。那时候网友线下见面也不会担心人身安全和诈骗。(M5)
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受访者都明确忆及他们所理解的早期互联网的精神与文化,“自由”、“开放”、“真诚”、“共享”、“勇敢”等词汇高频出现,可以说人们在早期互联网环境下生产和创造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这种文化背后彰显的是当时社会的技术创新、生产活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互助。受访者之所以会缅怀这种将互联网视作“家园”的早期互联网文化,还是源于对当下动辄网络暴力、造谣、对峙的互联网环境的不满,对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冷漠的失望,而这种当下互联网的生态环境特征与文化也暴露出一系列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与矛盾。
与前述对前互联网时期的“记忆搬运”不同的是,有关互联网初期的“缅怀回忆”正面临着“缅怀的消逝”的问题。随着早期论坛(例如天涯于2023年5月1日关停)、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的关闭或转型,搜索引擎快照功能的关闭,有关这类网站的“缅怀”零碎地见于网络和新媒体,网民只是在“悼念”、“缅怀”死去的网站和互联网技术时流露个体的同情或怀念。而具有互联网史档案意义的网民生命史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三)“在线乡愁”:社会集体记忆与交往记忆的数字怀旧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创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指出记忆是一种社会群体的产物,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性限制。哈布瓦赫(2002:68-69)认为,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是集体记忆形成的重要机制(Edgerton,2000)。
不断革新的媒介技术通过改变储存和传播记忆的方式(Zelizer,1995;Smit,Heinrich & Broersma,2017),给集体记忆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得益于技术赋权,新媒体用户通过现场见证和在线保存记录,生产了大量的数字记忆,在记忆重大的突发性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Andén-Papadopoulos,2014:148-163)。在数字时代之前,媒介记忆主要由机构化的新闻媒体塑造,而在数字时代,新媒介技术打破了主流话语的垄断,大众书写的“在线记忆”的合法性,建立在技术民主的基础之上——“人人都可言说”的社交媒体为网络接入者赋权,从而使网民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声以及进行“自传式”的记忆书写,最终使得网络记忆书写呈现“民本立场”(陈旭光,2018)。个体网民、组织成为新的记忆主体,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媒介记忆的建构。
在以小红书为代表的自媒体上,草根网民利用简单的技术制造就能够唤起网民共鸣的“乡愁”记忆。通过创造集体记忆的元素,使这种数字怀旧形式和内容拥有广泛的认同。视频博主倾向于直接撷取日常生活素材,采用一镜到底的方式传递家常感。在将生活片段可视化的过程中,短视频不断强化具有浪漫色彩的怀旧记忆,再现个体“生平情境”,以此将媒介内容与乡村文化相联系。破旧的老屋以及当下处于消逝中的村庄物件,经常构成视频不可或缺的要素(王昀,杨寒情,2023)。
这类被加工出来的旧村落、农村老房子影像,制造了数字怀旧中一种特殊的“在线乡愁”内容,勾起了人们对一种世外乌托邦家园的怀念和假想。例如“乡愁”这个拥有1.6万粉丝的小红书账号,它的创作模式是拍摄农村的老房子、小路、农田等自然以及人文风光,记录农村生活。在一条炊烟升起的农村场景视频下,网友留言“多希望,一觉醒来风风雨雨这些年只是梦一场,姥姥、姥爷喊我起来吃早饭”(雲隱);“那时候虽然贫穷,但人都很充实,过年过节亲人都在一起,人情味很浓,现在物质方面充裕了,亲情人情温馨却不见了,好怀念”(钱币狂增值,物以稀为贵)”;“异乡漂泊几十载,再回故乡成外人。门后空留教子棍,已无叮嘱寒添衣”(“清欢”)。
在这类集体记忆的怀旧内容中,家园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元素。尤其是过去的老房子和城市化后的空间形成了冲突。网民们不仅会怀念过去的房子,还会怀念传统的生活方式:“那个时候农村家里的老房子还没有拆,爷爷奶奶都还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夏天一家人就会到外面‘乘凉’,晚上可以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星。”(M7)除此之外,一些城市的老厂房、老街区影像也会形成类似的乌托邦怀旧情景。例如,有受访者在看到一条上世纪90年代苏北街头的视频后,会发出感慨,“那个年代条件虽然艰苦了点,没有那么多汽车,但生活节奏慢,心里没有压力。现在什么都快,成天不知道忙什么”(M3)。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怀旧内容的集体记忆中,偏向于“交流记忆”层面的怀旧和维持,而缺乏仪式性和共同身份认同的文化记忆建构。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指出,交流记忆指的是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日常接触和交流建立起来的记忆,交流记忆的承载者是个体,其存在和延续的手段是口传,因此它是短时记忆(2016:15)。交流记忆主要依靠见证者维持,所以它持续三到四代人的时段,然后逐渐消失。文化记忆包括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定和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通过虚拟民族志的观察不难发现,网民们的怀旧记忆建构,并没有上升为文化记忆,这和大众传播时代的记忆建构有显著的不同。由此也可以发现,这种集体怀旧更多是面向当下的记忆,因此通过对这些怀旧实践的观察,也可以发现,这种情感结构背后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不同角度反映和映射了社会心态的特征及变迁。
五、想象的追忆:数字怀旧实践背后的社会心态分析
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看, 现代怀旧有回归式、反思式和认同式三种不同的层面(赵静蓉,2003)。本研究作为一项经验性的研究,希望发现这类回归式、反思式和认同式怀旧行为背后的当下意义。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宏观的社会心理状态。在数字怀旧展演实践的背后,当下的社会心态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回忆与想象作用。换言之,正是在同当下的对比中,对过去的回忆才得以展开,对互联网往事的追忆才蔚然成风,对乡愁记忆的制造才有可能形成产业。
(一)陌生人社会:“乡愁”展演背后的社会孤独心态
“孤独感”是人类普遍的情绪体验。Weiss(2002)指出孤独感体验来源于个体与外界的隔离,加强并获得与他人亲密的社会联结可以帮助个体摆脱孤独。而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孤独的存在形态从个人的情绪体验演化为一种“群体性孤独”,即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所描绘的人们沉迷于线上社交关系而线下彼此疏离的社会现象,孤独感作为现代社会的显著心理症候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显著拉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201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上升到52.6%,平均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④当代青年在数字怀旧的“乡愁”展演实践过程,诉诸对城市化社交关系的消解,用对传统的人情关系、交往关系的回忆表达当代青年在融入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孤独心态。
随着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大中型城市。许多原本生活在中小城市的小镇青年,在数字怀旧中常常会在“思乡”的情绪中表达对老物件和乡土空间的怀念:
我喜欢看抖音上的农村房屋改造后的场景,过去的建筑模样、大红的对联、挂在桂花树上的红灯笼、有水有菜园有躺椅,还有一家人在这里生活,小孩在玩耍、大人在做饭。一家人共同生活的氛围很容易引起共鸣,因为自己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呀,看到这样的视频内容就会很亲切,会想起小时候和家人的温馨画面。现在工作很忙,经常也不在父母身边,有时候真是焦头烂额,又感觉力不从心,所以看到这些视频就会发呆,想想自己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个去处,还能有这样的体验,必会是一个美妙的经历啊。(M6)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促使人们逐渐走出传统社区,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交往,而互联网的出现则增加了人们跨越地域与各式陌生人相遇的机会(张娜,2015)。由于身处城市的陌生人社会,青年群体会通过在数字怀旧展演中与有相同生活经历的“陌生人”建立熟悉感。在虚拟网络空间,人们倾向于将接触或互动的他人视为“陌生人”,进而认为可以将自己内心深层次的想法或感受袒露给虚拟空间的“陌生人”,通过这种与“陌生人”的深层次真实交流实现自我表达,并逐步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感(汪雅倩,2019)。比如有受访者提到:
我会把自己关于过去的一些照片和旧电子产品发到小红书这样的平台上,因为小红书的算法推荐机制很灵敏,很快就会有一些和我有共同经验的人回复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找到一种熟悉感。(F4)
可以看到,青年人数字怀旧的“乡愁”展演,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也是对传统人际关系的怀念,表现了一种社会孤独心态。有实验研究表明,媒介技术怀旧对孤独个体建立积极自尊和社会联结发挥着有效作用(杜璇,刘于思,2022)。在本研究的访谈中可以发现,越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群体,越容易流露出“城市空心病”的情绪和心态。大城市青年群体在物质富足、事业稳定的情况下,内心却感到空虚、无聊、平淡。他们面对着物质的饱和和超越,但无法找到真正感兴趣和有热情的事情来投入时间和精力,或者是缺乏人际关系的支持和愉悦感,这种孤独感也会让其选择通过数字怀旧来排解。
(二)传统的“慰藉”: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焦躁心态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根本特点就是其不稳定性,社会本身具有的结构性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等)是形成社会焦躁心态的主要原因(马寄,2014),焦躁也成为当下社会负面心态的主要表现。怀旧则是对加速社会的反叛,对于奔波焦虑的现代人而言,对过往美好“传统”的追忆,是抚平焦躁心态的有效慰藉。
“传统”是数字怀旧展演中的重要元素。在有关“80后”集体生活、集体记忆的数字怀旧展演中,内容创作者会将过去定义为传统,将“乡土情结”与“传统传承”相联系。乡土以人地关系的和谐为基调,自然、宁静、平和、亲密是乡土精神状态的一般表现,乐天知命、享受日常生活是乡土生命态度的朴素内涵。可以说,乡土对多数现代人来说是一种精神意象,是离开乡土漂泊的游子的乡愁意象,是现代人批评现代生活和人的异化问题时的参照。乡愁中的乡土是一种审美性质的乡土,是乡土文化的抽象表现(萧放,2023)。在本研究的田野考察中,不少博主在日常作品拍摄过程中,通过制造充满田园乌托邦式的生活镜头,配以唤起共鸣的怀旧文案,实现对现代化加速进程中的网民的心灵慰藉。
除了制造乡愁,对“传统”的追忆还包括通过旧影像、传统手工艺作品、老物件等来展开。这种怀旧短视频的创作内容风格以“治愈”为关键词,大多配以舒缓的音乐、柔和的色调与不疾不徐的剪辑节奏,给观看者以放松心情、精神疗愈的感受。人们在这种对传统生活的怀旧中,不仅仅是怀念过去,也会和当下生活节奏的紧张、生活的焦躁心态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不少怀旧短视频中,过去的“春晚”、童年时代的老动画片都扮演着这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怀旧展演元素:
在爆竹声中,伴随着《春节序曲》的背景音乐,赵忠祥和倪萍的经典春晚开场白主持词……总之那个年代的春晚,是过年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团圆时光。不像现在,虽然过年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可是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年味,大家可能都各自玩手机,聚在一起也是聊工作、收入这些比较现实的话题。(M8)
现在经常会在小红书上搜寻一些小时候记忆中的动画片,那时候国产动画片充满了中国画的风格,比如经典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那时候动画片的配音也都很走心。(F5)
与之类似的怀旧展演元素还有很多,比如“80后”、“90后”上学时用的旧教科书。“语文书 景行”是小红书平台一个专门分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学人教版语文书的账号,创作者会将当年的经典课文、插图配上音乐或朗读进行怀旧展演,而网友们在怀念这些旧教材时纷纷感怀过去、追忆童年:“这熟悉的课文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无忧无虑,真幸福”(小詹)”、“那是个单纯美好的时代”(手心里的温柔);“感谢博主,让我们得以回顾童年那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happylee)。
前述对过去传统的追忆与怀念,对当下现状的遗憾与不满的情绪体验,在访谈中屡有提及。可以看到,社会心态是主体对客观经济条件的一种主观体验与感受,而并不直接对应客观经济条件,也即物质条件的提升与幸福感的体认强度并不同步。随着社会的变迁、个人境遇的改变,人际关系的疏远与生活压力的陡增使得个体心态波动而易于失衡。尤其是在当下数字交往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媒介无时不在的侵入已经彻底打破了主体的宁静状态,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接收和传播信息使得人们处于一种兴奋、紧张、焦躁的情绪体验中(叶虎,2023)。数字怀旧中对传统生活想象的“慰藉”,反映了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焦躁心态。
(三)缅怀“黄金时代”:“网事”追忆中的社会固化心态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地域流动和阶层上升的重要拉力,贫富差距逐步拉开(张文宏,2018),同时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对于财富积累的作用日益减弱(付宇,桂勇,2022),特别是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他们正陷入难以突破的结构性困境。在对互联网早期“网事”的回忆中,吴世文、杨国斌(2018)研究发现,在网友看来,消逝的网站所代表的时代,是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这种对消逝的“黄金时代”的追忆,固然表达了对过去的一种怀旧情绪,往往也是一种批判现实的策略。
通过对青年网民的深度访谈,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网民在追忆“网事”过程中,表现出不满于现实却又无力打破的社会固化心态。在抖音平台一段有关崔永元早年节目主持的怀旧影像视频留言区,网友“火爆杂碎FM”留言:“复古成为人们的集体意识,一定不只是情感滤镜那么简单。那些年我们看到时代与社会发展,更多可能性,也有更多选择。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那些与自己不再相关,发展放缓了脚步,红利也突然被拉住缰绳无法下沉。我们怀念曾经的美好,更多是怀念那时候人的心气儿,他们相信比怀疑更多,他们认真比虚无更多,他们的选择比压抑更多,而这个时代越来越容不下较真的人。能脱离环境的人绝无仅有,小崔老师在那个年代的从容写意,到今天的百折不回,个体命运与社会变化映照着,总是让我们这些矫情的人感到唏嘘。”可以看到,个体在承受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下,对上个社会时期与历史阶段的缅怀实则是倾诉当下所遭遇的个体困境的无奈。当个体的努力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无法追赶社会加速的脚步,青年人的挫败感与无力感便进一步增强,自我实现的效能感进一步降低,个体前进的动力也会被进一步削弱。
社会固化心态不仅体现在个体困境层面,在宏观社会层面,当下固化僵硬的社会机制也令人怀念早期互联网发展史中所涌现的创新活力与流动可能。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创业发家史上,诞生了许许多多充满传奇色彩的网站和人物。而这些网站和人物,或是在技术的浪潮中被淘汰,或是在资本的力量下蛰伏或转型。网民在追忆这段早期互联网创业和发展野蛮生长的时期时,也会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带入到回忆中。在一条关于“曾经很好,但现在消逝的App”的留言下,网民们在回忆人人网、虾米音乐、蘑菇街、快播、天涯等已经消失的网站和App的讲述中,表达出对当时社会创新的动力、技术发展环境的肯定与缅怀,而这种情感在本研究受访者的讲述中也有所体现:
在我最早的互联网记忆中,高中时有个很火的网站叫“闪客帝国”,当时诞生了许多flash创作的大神。那个年代的互联网就像美国的淘金潮一样,充满了希望。虽然从今天看,有些技术已经淘汰了,但在当时给了社会许多机遇和和可能。(M1)
现在各个行业都很“卷”,同质化的竞争,真正的创新驱动力不足,不像早些年,各行各业都是神仙打架。感觉现在没有什么新的机遇所以人们才怀念20年前。(M6)
从网友互动与访谈中均可以发现,“发展”、“创新”、“突破”是屡被提及的词汇,“突飞猛进”与“天翻地覆”经常用以描绘互联网给社会带来的巨变,构成了个体对早期互联网怀旧的主线。正如有学者总结20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中国技术与商业的创新史,更是一部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社会文化的创新史”。⑤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快速变迁,引发个体对中国互联网“黄金时代”的频频追忆。
(四)怀旧的文化期待:技术复古背后的“文艺复兴”心态
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本文在这里借用“文艺复兴”的概念,来描述数字怀旧背后的文化期待。数字怀旧中的技术复古和文化怀旧,显示出当代青年的“文艺复兴”心态。技术复古其实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模拟呈现过去的媒体技术,即“技术怀旧”(Technostalgia)。而这种记忆实践并不是由对过去的怀旧所驱动的,而是在过去和现在、模拟和数字、档案和表演之间进行中介,媒体技术不仅构建和中介了记忆,而且成为记忆本身的对象(Heijden,2015)。正如Ann Mack(2014:77-78)所言,“随着数字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似乎越来越迷恋物理和触觉。我们正在接受老式打字机、手表、实体书以及与朋友和亲人面对面的时间等东西——这些已经在数字时代过时的东西。随着我们在数字世界中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重视我们没有花在屏幕前的时间——我们与真人真事相处的时间”。
如前文所述,在快速转型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青年群体却频频在数字平台开展各种怀旧实践,抒发对过去时代美好想象与追忆的同时,也表达着对现实生活的迷茫与不满,这本身就是对主流文化潮流的一种抵抗,例如受访者M1就分享了他的文化复古心态:
在抖音上,我关注了一个叫“梁大官人”的博主,他会讲述复古歌曲背后的故事,就会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比如我小时候听音乐,用磁带卡带,家里不会有条件给你买随身听。索尼超薄卡带机,1998年才见到,一千多块钱。当时那种先进科技带给你的震撼,音质的震撼,令人身心愉悦,印象深刻,也是现在无法再现的。现在很多手段都可以听歌,但没有当时的那种感觉了。当时喜欢的一盘磁带可以反反复复听好多遍,但你看现在,还会反复连续听一张专辑吗?太难找到这种愉悦感了,现在什么东西都太富足,但幸福感的阈值也大大提高了。反正我2000年以后的歌基本都不听了,感觉现在的歌手注重包装、音乐的效果大过歌手的唱功,是跟上个时代的音乐不能比的。我现在专门会去买老式唱片机,买几张黑胶唱片,有不同于现在的感受。(M1)
从“数字怀旧”的媒介实践中,可以发现怀旧作为一种文化潮流,也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化抵抗风格。伯明翰学派认为,“风格传递一种重要意义的差异和建立认同”(Dick Hebdige,1979)。风格是一种对认同的追求与建构,即通过风格区隔亚文化群体与其他群体(尤其指主流群体),以及区分亚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指主流文化),亚文化具有“风格化”的特征。因此,亚文化曾被定义为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因而具有抵抗的特质。亚文化的“抵抗”采取的不是激烈与极端的方式,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主要体现在审美、休闲、消费等领域,是“富有意味和不拘一格的”,是通过展现特别的风格来“抵抗”霸权以及主导文化与价值观(Ken Gelder,2011:13)。总体来看,数字怀旧作为一种复古亚文化,流行于小众人群。例如,在本研究的访谈过程中发现,学历层次与怀旧情感的表达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对于一些居住于文化生活较为匮乏的小镇的低学历青年而言,数字怀旧更多是一种线上观看到的现象,而他们亲身参与数字怀旧的表达和实践要弱于高学历城市青年。城市青年群体的文化怀旧,涉及音乐、动画、影视作品乃至教材插图,在这种怀旧分享互动中,形成了相对小众的文艺复古亚文化。这种风潮和当下青年对文化产品的同质化、类型化发展的厌倦心态有关,表现了青年群体不满足于当下的“文艺复兴”心态。
六、结语:数字交往范式中的数字怀旧
从传播技术发展层面,整个社会的交往方式正在步入数字交往范式,即虚拟社会中的交流-行动(杜骏飞,2021)。在数字交往的过程中,抖音、B站、小红书等数字平台成为数字交往主要载体,其中平台智能技术嵌入数字交往的同时为其演化提供了新条件(别君华,2023)。在这样的社会和技术背景下,网民的内容创作也适应平台化发展的逻辑越来越多地诉诸情感共鸣。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互联网连接了一切社会关系——人际、人-物或物-物的关系,并在所有真实物与数码物共筑的网络空间内,构建出当代中国丰富而澎湃的各种情感图式(曾一果,2023)。本文研究了数字交往中怀旧这种独特的情感,并认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怀旧,数字怀旧本身构成一种新的情感图式。基于经验性研究基础,本研究对数字怀旧作一个概念的基本界定,即:在数字平台发生的对传统与当下生活想象的记忆重构与现实展演,它既是一种数字交往实践,也是一种面向当下的情感结构。
回顾怀旧研究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媒介从被视为充当怀旧实践的技术中介,即“中介的怀旧”(mediated nostalgia)( Lizardi,2015) ,逐渐扩展到将媒介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性的怀旧物的层面,讨论媒介本身作为怀旧对象的可能(Niemeyer,2014),直至当下数字怀旧综合了中介化或物质性的媒介怀旧类型,此时的媒介兼具了中介性与物质性,并深深嵌入到怀旧实践的建构之中。在此历程中,用户的创造性怀旧实践赋予了媒介以文化和社会意义,用户个体记忆的微观视角与时代变迁、社会历史情境的宏观背景得以勾连。
因此,数字怀旧有如下特征:(1)基于数字平台开展的记忆展演与怀旧实践。(2)不同于传统的媒介记忆,数字怀旧既包括了中介化的媒介怀旧,(3)也包括了物质性的媒介怀旧。(4)最为重要的是,数字怀旧还是基于当下现实的一种实践中的交往记忆。
数字怀旧在数字平台成为普遍的传播和展演,反映了这种社会意识具有较为广泛的受众心理基础。事实上,近年来,怀旧文化在中国社会普遍涌现,面向“80后”、“90后”的怀旧文化蔚然成为产业,说明总体的社会情感结构从一种面向未来的情感结构转向面向过去的情感结构。
雷蒙·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情感结构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它所要处理的是那些悬而未决的元素,一种始终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高颖君,2015)。怀旧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性症候,“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怀旧天然与时间的断裂和冲突有关。作为一种现代性情感结构,20世纪的电影媒介中有大量怀旧主题的表现,而这类“怀旧”,多与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生存境遇、主体性的困境、资本权力的压迫有关。在塔可夫斯基的《乡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和过去形成强烈冲突带来的压抑感。怀旧电影通过历史元素的堆砌试图还原曾经具有确定性的历史情境,实际上是个体为了弥合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尝试,是主体已经消逝之后为了栖居现代而不得不回溯过去的一种选择(高静,2021)。
本研究认为,数字怀旧打破了传统怀旧情感结构的“深沉叙事”,“旧情可待成追忆”,在数字平台上发生的怀旧展演,不再诉诸强烈的现代性抗争和后现代反叛,而表现为一种与当下和解的情感慰藉,进而使这种怀旧情感结构成为社会心态的宣泄方式。也正因如此,在数字交往中,怀旧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结构(缅怀追忆“黄金时代”),也成为一种交往实践(怀旧分享),是平台新的数字劳动形态(返乡青年的“乡愁”展演),更是一种文化风格(青年群体的“复古”展演)。
在这一背景下,数字怀旧未来将成为数字交往过程中一种独特的“后视镜”意义的社会心态映照。本研究基于经验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该现象进行研究,目的并不局限于呈现媒介记忆。媒介记忆背后根植着社会文化和社会心态的变迁,记忆是在外部结构性力量和自我想象的过程中不断被建构的。因此,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网民们倾向于某些内容的数字怀旧?为什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发展环境被人们重新怀念?哪些共同的情感结构导致了过去的文化风格重新得到了复古流行?为什么2000年初的互联网浪潮被人们视为“黄金年代”?
以社会心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本文尝试从媒介物、怀旧内容呈现和网民怀旧表达层面对数字怀旧的情感诉求进行了分析。同时,本研究也从横向和纵向比较了数字怀旧背后的社会心态流变,即:社会孤独心态、社会焦躁心态、社会固化心态和“文艺复兴”心态。数字怀旧对这些社会心态的映射,充满了今昔对比,这些心态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下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表达。在客观的数字怀旧展演中,我们看到了对当下的比照,而在网民主观的数字怀旧情感表达中,我们更看到了这种追忆的“想象”成分。因此,对于本研究而言,未来除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分析这些心态背后的社会动因之外,还需要联系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性变迁,思考如何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找到面向当下的平衡,分析这种“想象”何以形成,又将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账号昵称分别为:“老磁带回忆录”、“影像历史”、“怀旧人”、“乡愁”、“江南寻梦”、“忆乡思远”、“小默哥文案”、“时光游记”、“艾怀旧爱收藏”、“一土旧时光”、“六一同学”、“杨富贵老师”、“80年代博物馆”、“收藏童年”、“孙嘉茵”、“乾途无量”、“大海时光机”、“有啥回忆”、“回忆动漫小电视”、“磁带往事”、“大孟”、“古董手机之家”、“怀旧8090”、“念旧时光”、“星月白卡带时光”、“念乡人:手机原创摄影”、“FM8090时光音乐台”、“王蓝莓”、“语文书 景行”、“晗老师摄影 晗老师胶片社”、“艳红怀旧杂货铺”。
②新浪科技: 《南方周末: 互联网经济10年凉热( 1994-2004 )》,2004年4月22日,http: / /tech. sina. com. cn /i /w / 2004-04-22 /0849352828. shtml,2018年12月20日。
③毛锦伟: 《互联网二十年》,《解放日报》2014年4月28日17版。
④地理沙龙号:《截至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63.89%,城市数量达到687个》,2021年9月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981854822980057&wfr=spider&for=pc。
⑤周民生:《中国互联网激荡20年》,《华兴时报》2014年4月18日,11版。
参考文献:
阿莱达·阿斯曼(2016)。《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别君华(2023)。平台化数字交往:基于技术可供性的情动实践。《青年记者》,(04),22-25。
卜玉梅(2012)。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和伦理。《社会学研究》,(06),219-220。
陈旭光(2018)。逻辑转向与权力共生 : 从网络流行体看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新闻与传播评论》,71(3),71-85。
丁方舟(2019)。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新闻界》,(01),78。
董扣艳(2017)。“丧文化”现象与青年社会心态透视。《中国青年研究》,(11),23-27。
杜璇,刘于思(2022)。念往昔以慰孤独:媒介技术怀旧对青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5),51-60。
杜骏飞(2021)。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新闻界》,(12),79-87。
高颖君(2015)。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6),689-692。
高静(2021)。我们还能怀旧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怀旧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03),37-45。
哈特穆特·罗萨(2018).《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顺铭,陈彦宁(2021)。旧技术物的“重生”:一个线上平台的 iPod 二手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10),92-109。
刘于思(2018)。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南京社会科学》,(05),122。
骆正林(2022)。网络流行语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人民论坛》,(10),80-83。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2010)。《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孙信茹,王东林(2019)。玩四驱:网络趣缘群体如何以“物”追忆。《新闻与传播研究》,(01),24-45。
陶东风,胡疆峰(2011)。《亚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佳鹏(2016)。在狂欢感受与僵化结构之间——从网络流行语看网络青年的社会境遇与社会心态。《中国青年研究》,(04),83-89。
王佳鹏(2019)。从政治嘲讽到生活调侃——从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看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中国青年研究》,(02),80-86。
王昀,杨寒情(2023)。制造“乡愁”:乡村视频博主的内容生产与职业身份生成。《社会学研究》,(01),205-225+230。
王润(2022)。媒介与怀旧: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与实践进路。《新闻与写作》,(02),32。
汪雅倩(2019)。“新型社交方式”:基于主播视角的网络直播间陌生人虚拟互动研究。《中国青年研究》,(02),87-93+72。
吴世文(2018)。互联网历史学的前沿问题、理论面向与研究路径——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国斌教授访谈。《国际新闻界》,(08),59-75。
吴世文,杜莉华,罗一凡(2021)。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转向与挑战。《青年记者》,(10),9-10。
吴世文,何羽潇(2021)。媒介、情感与社交关系:网友的QQ记忆与技术怀旧。《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9),144-150。
吴世文,杨国斌(2018)。追忆消逝的网站:互联网记忆、媒介传记与网站历史。《国际新闻界》,(04),6-31。
吴世文,周夏萍(2022)。人与“媒介物”的相遇:手机的文化传记与记忆场景。《新闻记者》,(04),73。
萧放(2023)。重返乡土:中国乡土价值的再认识。《西北民族研究》,(03),83-87。
谢卓潇(2020)。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携和消费。《国际新闻界》,(01),154-176。
邢婷婷(2023)。“45?青年”:张力之下的青年境遇及其社会心态。《探索与争鸣》,(02),32-44+177-178+182。
杨宜音(2006)。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04),117。
叶虎(2023)。加速社会视域下数字媒介主体异化的文化批判。《南京社会科学》,(05),155-166。
余建华(2014)。网络社会心态何以可能。《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25。
赵静蓉(2009)。《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静蓉(2003)。《现代怀旧的三张面孔》。《文艺理论研究》,(01),81-88。
张娜(2015)。熟悉的陌生人:青年群体网络人际关系的一种类型。《中国青年研究》,(04),64-68。
郑雯桂勇黄荣贵(2019)。论争与演进:作为一种网络社会思潮的改革开放——以2013-2018年2.75亿条微博为分析样本。《新闻记者》,(01),51-62。
周海燕(2019)。作为媒介的时光博物馆:“连接性转向”中的记忆代际传承。《新闻界》,(08),15-20 。
周海燕(2014)。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09),39-40。
曾一果(2023)。丰富而澎湃:互联网世界的“情感图式”。《传媒观察》,(06),1。
Andén-PapadopoulosK. (2014). Journalism, memory and the “crowdsourced video revolution”. In: ZelizerB. &Tenenboim, K. (Eds.) Journalism and Mem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olin, G. (2015). Passion and nostalgia in generational media experi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9(3)250-264.
CampopianoJ. (2014). Memory, temporality& manifestations of our tech-nostalgia Preservation.Digital Technology & Culture43(3)75-85.
CoorenF. (2018). Materializing Communication: Making the Case for a Relational Ontolog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8(2)278- 288
Davis. Fred. (2011).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The collective memory reader, (5) , 446-451.
Dick Hebdige.Subculture.(1979).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Methuen.
EdgertonG. (2000). Television as historian: An introduction. Film &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30(1)7-12.
Heijden,T. (2015). Technostalgia of the present:from technologies of memory to a memory of technologies.Europea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Necsus 4(2).103-121.
HigsonA. (2014). Nostalgia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heritage filmsnostalgia websites and contemporary consumers. Consumption Markets & Culture.17(2)120-142.
HineChristine.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Hoelscher SAlderman D H. (2004). Memory and Place: Geographies of a Critical Relationship.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5(3)347-353.
Keightley. E. & M. Pickering. (2014).Technologies of memory: Practices of remembering in analogue and digital PhotographyNew Media & Society16(4) , 576-593.
Lizardi, R. (2015). Mediated Nostalgia: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ntemporary Mass Medi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Lowenthal D. (1975). Past Time,Present Place: Landscape and Memory.Geographical Review,65(1)1-36.
Magaudda. P. & S. Minniti. (2019).Retromedia-in-practice: A practice theory approach for rethinking old and new media Technologies,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25(4)673-693.
NeigerM.Meyers, O. &ZandbergE. (2011).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NiemeyerK.(eds.) .(2014). Media and nostalgia: yearning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sing-stoke-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mitR.Heinrich, A. & Broersma, M. (2017). Witnessing in the new memory ecology: Memory construction of the Syrian conflict on YouTube. New Media & Society19(2)289-307.
Van Baarsen B.(2002). Theories on coping with loss: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on adjustment to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following a partner’s death in later life.Journal of Gerontology:Social Sciences, 5733~42.
Van DijckJ. (2008). Digital photography: communicationidentity, memory. Visual communication7(1)57-76.
Zelizer, B. (1995). 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2(2)214–239.
[作者简介]吴志远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马一琨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