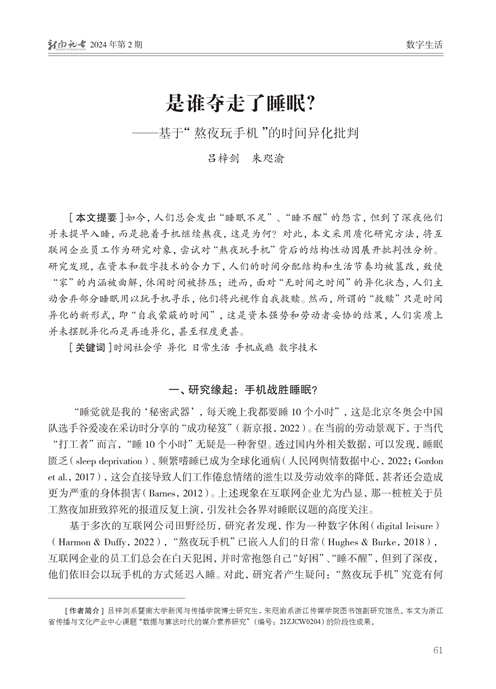是谁夺走了睡眠?
——基于“熬夜玩手机”的时间异化批判
吕梓剑 朱咫渝
[本文提要]如今,人们总会发出“睡眠不足”、“睡不醒”的怨言,但到了深夜他们并未提早入睡,而是抱着手机继续熬夜,这是为何?对此,本文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将互联网企业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对“熬夜玩手机”背后的结构性动因展开批判性分析。研究发现,在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合力下,人们的时间分配结构和生活节奏均被篡改,致使“家”的内涵被曲解,休闲时间被挤压;进而,面对“无时间之时间”的异化状态,人们主动舍弃部分睡眠用以玩手机寻乐,他们将此视作自我救赎。然而,所谓的“救赎”只是时间异化的新形式,即“自我蒙蔽的时间”,这是资本强势和劳动者妥协的结果,人们实质上并未摆脱异化而是再造异化,甚至程度更甚。
[关键词]时间社会学 异化 日常生活 手机成瘾 数字技术
一、研究缘起:手机战胜睡眠?
“睡觉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每天晚上我都要睡10个小时”,这是北京冬奥会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在采访时分享的“成功秘笈”(新京报,2022)。在当前的劳动景观下,于当代“打工者”而言,“睡10个小时”无疑是一种奢望。透过国内外相关数据,可以发现,睡眠匮乏(sleep deprivation)、频繁嗜睡已成为全球化通病(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2022;Gordon et al.,2017),这会直接导致人们工作倦怠情绪的滋生以及劳动效率的降低,甚者还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身体损害(Barnes,2012)。上述现象在互联网企业尤为凸显,那一桩桩关于员工熬夜加班致猝死的报道反复上演,引发社会各界对睡眠议题的高度关注。
基于多次的互联网公司田野经历,研究者发现,作为一种数字休闲(digital leisure)(Harmon & Duffy,2022),“熬夜玩手机”已嵌入人们的日常(Hughes & Burke,2018),互联网企业的员工们总会在白天犯困,并时常抱怨自己“好困”、“睡不醒”,但到了深夜,他们依旧会以玩手机的方式延迟入睡。对此,研究者产生疑问:“熬夜玩手机”究竟有何魔力,以至于人们宁愿舍弃本就不多的睡眠,主动且固执地跳进“晚上熬夜-白天犯困”的循环套圈?若想解答此疑惑,首先需回归学界对睡眠议题的探讨。
当前,有关睡眠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睡眠不足的后果以及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两个方面(Aldhawyan et al.,2020;Demirci et al.,2015)。其中,伴随智能设备的普及,手机使用对睡眠的影响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如睡前手机发出的光亮及长时间使用会扰乱人体的昼夜节律、降低睡眠质量等(Tamura et al.,2017;Moulin & Chung,2017)。也有部分学者以时间/时空为研究切口,对熬夜现象展开探索。如学者陈晨(2021)依托时间社会学视角,认为“熬夜”是人们争取个人时间,实现对组织化制度之脱嵌的结果。陈纬等(2023)基于田野调查,将青年产业工人的睡眠节律分为安定者、娱乐者、焦虑者、孤勇者四种类型,其中“娱乐者”指向了“熬夜玩手机”的情况。上述研究均描摹了当代青年的睡眠生态与熬夜群像,但并未对“熬夜玩手机”现象展开详尽的时间结构分析。
此外,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2021:27)有关“睡眠终结”的论著也为本文提供了启发。他认为,“对于24/7式资本主义的完全实现而言,睡眠是仅存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它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种‘自然障碍’。睡眠不可能被消灭,但可以被破坏,被剥夺”。那么,睡眠被谁破坏?又被谁剥夺了?克拉里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认为资本正在取缔我们的睡眠,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无眠世界。那么,对于“熬夜玩手机”的原因,答案也是这样,或者只是这样吗?
基于以上追问,本文聚焦“熬夜玩手机”的时间社会结构属性,从日常生活的整体视角出发,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第一,在睡眠愈发不足的情境下,人们为何依旧选择牺牲睡眠以换取“手机时间”?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结构性动因?第二,“熬夜玩手机”是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律?它又如何影响当代人的睡眠景观?综上,本文将基于时间社会学视角,依托“时间异化”(time alienation)理论,以互联网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该群体“熬夜玩手机”的背后动因,①进而剖析当代人的时间管理问题。
二、理论探讨:生活在异化之中
(一)“异化”概念的内涵流变
“异化”是理解资本主义运作和诊断社会病态的关键概念,是学界当前广泛应用的经典术语。
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异化”理论的启蒙下,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异化”观。他认为,“异化”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是一种人类自身创造的状态;围绕存在本质和从属关系,其囊括了“对象化”、“异己化”、“丧失”和“统制性”等内涵(吴宁,2007:111)。马克思(2021:62-83)将“异化”聚焦于劳动经济领域,进而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强调劳动异化的四个方面,即“劳动产品同人相异化”、“劳动活动同人相异化”、“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如今,“异化”概念早已不局限于生产经济领域的狭隘范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个体自律意识的增强,在自然中心主义向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下,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科技融合背景下人之生存境遇问题,“异化”概念顺而被扩展至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总体批判(韩升,段昀辉,2023;张翔,蔡华杰,2022)。依此趋势,学界分化出针对阶级主体和个体性主体的两种批判路径。
第一种路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延承马克思对阶级主体的批判。作为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聚焦科学技术的极权统治,认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马尔库塞,2008:9),而该形式所支撑的工具理性正逐渐“从解放人、确证人的本质的文化力量转变为束缚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张翔,蔡华杰,2022),由此“社会衍生出一套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马尔库塞,2008:11)”,旨在以整体的力量对人的本真进行压制。然而,“科技异化”的论域并没有系统性说明“‘技术理性’在个体的生活中有着怎样的作用机制,也没有探讨它在使人们享有现代生活的一切便利的同时,又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和隐忧”(罗萨,2022:导读6-7),因此,对个体性主体的批判面向也就成为异化研究的另一路径。
该路径聚焦于个体的生活形式与生命体验,认为异化已渗透进人的全部日常。例如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已成为资产阶级宰制下的异化中心,是现代性压迫最深重的领域,在此形势下,当代人的家庭生活、休闲时间和文化活动再难逃离组织化(吴宁,2007:162-171)。鉴于此,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引申为一种疏离于本真状态的“神秘化”(mystifiée),认为日常生活已沦为“能够回放、浓缩和‘表现’真实观众生活的戏剧表演”(列斐伏尔,2018:125),这是一种“让人麻木不仁、难以察觉的意识的自我欺骗”(李溪源,施琴,2022),是“对现实的伪装和倒置的一般化过程”(鲁宝,2021)。不过,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仍停留于对日常生活异化的统述,并未依照日常的具体现象对异化进行细分。
西曼(Melvin Seeman,1975)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通过对马克思、阿多诺、默顿等相关理论的梳理,西曼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将异化划分为六种类型,即“无力感”(powerlessness)、 “无意义感”(meaninglessness)、 “无序感”(normlessness)、“文化疏离感”(cultural estrangement)、“自我疏离感”(self-estrangement)、“社会孤立感”(social isolation)。此分类无疑用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将异化内涵具体化。
(二)时间异化:社会时间视角下的“异化”概念
现今,后现代社会下个体所面对的日常生活的种种弊端愈发凸显,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异化批判的旨趣和任务由“如何解放”瞄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最为代表(郑作彧,2021)。
耶吉(Rahel Jaeggi,2014:6-31)率先指出前人“异化”理论中的本质主义缺陷,顺而从关系视角将“异化”视为当下社会的一种诊断,即“无关系的关系”(relation of relationlessness),其症状包括:主体存有无力和缺乏自由的生活感知,以及遭遇与自我和世界之关系的贫乏状态等。异化之下,个体将无法有效体验自身,世界也将变得不真实、毫无意义且格外冷漠。然而,耶吉虽翻新了“异化”的概念,实现了批判理论与大众真实生命体验的契合,但她“并没有回答为何现代社会尤其会造成异化”(郑作彧,2021)这一拷问;对此,罗萨(Hartmut Rosa)转接了该任务。
在耶吉异化诊断的基础上,罗萨从时间社会学视角,指出社会竞争、永恒的应许以及加速循环招致的当代社会之“加速”症结(罗萨,2018:29-41),进而再探了价值维度的五种新异化类型。作为类型之一,时间异化意指一种加速社会下降级的“体验短/记忆短”的时间模式,其会造成“体验时刻越来越丰富,但生命经验却越来越贫乏”的无效生活状态(罗萨,2018:133-139)。该诊断无疑导向了研究“异化”的时间视角,揭示了种种异化现象背后暴露的时间问题;然而,作为人之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的要义甚是丰富,罗萨的“时间异化”理论仍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在马克思的论域里,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也是人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恩格斯,1979:532)。过去,人们借由时间制度与世界建立持续、日常的连接,展开交往并协调社会行动(黄月琴,黄宪成,2023);而今,人们却逐渐丧失时间自主性,被拽入时间加速、时间焦虑、时间过度道德化的无尽深渊。作为“人与世界之关系全面异化”的集中表现(姜华,崔嘉晟,2022),时间异化无疑成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拦路虎”。要想诊断其中的病理,光靠罗萨阐述的“时间异化”之保守内涵是行不通的。
第一,“加速”和“时间”并不是罗萨真正关心的主题,他只是企图借助社会加速的表象,探求现代性的核心逻辑,以此作为自身批判理论的出发点(Rosa,1998),因而他并无进一步发展该理论的意图;第二,在罗萨的理论视域里,异化最根本的问题是时间的剥离,而非资源占有或分配矛盾,因而他的异化观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上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保守主义,他对异化的批判并不彻底,这也意味着将“时间异化”简单概括为一种价值体验的降级是远远不够的(姜华,崔嘉晟,2022);第三,面对复杂的时间问题,社会加速只能作为“时间异化”的一种特质,它的表征绝不仅限于此。
如学者所提,学界亟需一种既包含资本批判逻辑,又涉及价值维度的更为具体、细化的“时间异化”理论(吕梓剑,戴颖洁,2022);顺此,依循对个体性主体的批判路径,本文参照耶吉“无关系之关系”的异化定义,结合马克思的剥削批判面向以及罗萨的价值批判面向,将“时间异化”界定为“无时间之时间”的状态。
首先,参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间异化”指向一种蒙受不自由的他律的时间支配关系,常体验为时间的失控感和剥削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劳动异化的视域下,作为一种资源和商品,同具交换属性的自我时间会连同人的劳动活动,在资本支配的生产关系中转化为一种带有剥削性的异己力量(叶琳,2016)。因此,在参与劳动实践的时段内,主体的自我时间实则沦为了资本的附属,这是一种支配关系下的“无时间”状态;过度工作、无薪加班更被视作资本加之于劳动者的时间盗窃(time theft)(Swann & Stanford,2016:2)。其二,伴随流动空间的生成,劳动与休闲的时间分界逐渐消弭,随之而来的是“即时”生产制、弹性工时制、时间压缩等数字劳动景观的生成(吴鼎铭,胡骞,2021),最终“休闲时间不再是工作异化的补偿,反而成为劳动时间的储备军”(Erickson,2017)。面对自我时间掌控权的丧失,人们会体验到一种“无时间”的失效感(包括无助感、贫乏感与无意义感)(姜华,崔嘉晟,2022),这便顺延出“无时间之时间”的第二层感知。
时间体验的失效感是时间稀缺和社会加速的体现。在劳动时间的挤压下,人们会因可供自我支配之休闲时间的压缩而产生时间恐慌,进而人们会以争分夺秒的功利姿态增加短时间内的事件体验和完成数量,这便导致“体验过多而经验不足”的意义降级状态(罗萨,2018:133-139)。例如,人们会通过倍速播放(王杰,来昕,2022)、观看电子榨菜(孙珉,吕雯思,2023)等方式来最大化利用休闲时间,其结果是人们与生活本真的疏离(Harmon & Duffy,2022),对迟缓节奏的排斥,原本纯粹的休闲时间在忙碌、加速与焦虑的交织中被肆意填塞,终而无奈流逝。
由上总结,“时间异化”的“无时间性”体现在:第一,时间从属的异己支配,即个体的自我时间转变为他律的劳动时间,在此情境下,个体会产生束缚、失控的时间感知;第二,时间体验的意义降级,即个体的自我时间陷入加速与稀缺的异化状态,进而导致个体出现时间的恐慌感、无力感与无意义感。两重内涵并非各自独立,可将其绑定为遵循承接或因果逻辑的连带关系。因此,本文强调的“时间异化”是批判语境下现实情况与主体感知的过程照应,绝非单纯的概念集合。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2001:566-568)提出的“无时间之时间”的概念。在卡斯特的论域中,“无时间之时间”指向网络社会崛起后时间所呈现的压缩性、瞬时性与无序性,其反映了连续时间被切割成“当下”和“现在”的一种客观状态。因此,本文牵涉的时间异化之“无时间的时间”内涵并未借鉴卡斯特的观点。
那么,回归本文疑问,“熬夜玩手机”作为一段特定时域,其是否影射了时间异化的问题?对此,本文将依托“时间异化”理论,尝试探讨该习惯背后的行为动因,借以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本真自我。
三、研究方法
2022年5月至6月,作者围绕“睡眠”议题,在国内知名互联网“大厂”W的“视频脚本创意策划”部门进行了实地调研。第一个月,作者以单纯的观察为主,观察内容包括公司规章制度、企业文化氛围以及员工生活作息、日常表现、私下闲聊内容等。经一个月的熟识后,作者在前期田野的基础上,邀请了12位员工作为研究对象。②作者参考“时间记事分析法(time diary studies)”(郑作彧,2018:229),要求每人记录自己6月份(6月1日至6月30日)的相关行为(包括起床时间、出发时间、通勤时间、到家时间、上床时间、正式睡觉时间等)的对应时间点。研究结束后,作者会取众数作为该行为的常规时间点,以判断个人的日常时间分配。调研结束后,作者依据田野经历及时间记事表,拟定了相应访谈提纲,对12位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对熬夜的看法、熬夜玩手机的原因、工作时避免犯困的方法、回家后的日常生活安排等。
需要说明,由于W公司不同部门的工作性质不同,访谈对象的上下班时间、午休时间也各不相同(但皆为双休),即便是同部门内,不同岗位、不同身份的员工,其工作作息也不尽相同。因此,作者在分析过程中更注重参考各行为区间的时段(或时量)而非某具体时间点。根据调研资料,本文研究对象均为租房者,均存在睡前玩手机的习惯,且均于0点后正式入睡(以正式闭眼入睡时间为准)。入睡时间最早为B,为00:30;最晚为H,为凌晨2:00。为扩大样本,2023年6月20日至7月3日期间,作者通过目的性抽样,又对8位有熬夜玩手机行为的互联网企业正式员工展开半结构式访谈(包括记录与睡眠有关的重要时间点),待访谈内容趋近饱和后,作者对相关材料进行了语音转文字输出。访谈对象信息参见表1(*为非W公司员工)。
四、被偷走的时间:休闲时间的日常异化
时间社会学从劳动性质和从属关系角度,提出“三元时间”类型,认为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由薪资劳动工作时间(工作时间)、非薪资劳动事务时间(私人事务时间)以及复原与文化时间(休闲时间)组成的“三元时间社会”(Rinderspache,2005)。其中“非薪资劳动事务时间”是一种绽放性时间,能否对其充分管理是彰显个体是否“时间富裕”、是否具备时间自主性的重要标志(郑作彧,2018:54-58)。在此划分中,睡眠似乎被默认归入“复原与文化时间”的类别,即一种休闲时间;但作者认为,睡眠虽起着休养身心的作用,但它是一件日行之事,是生理必要的休息时段;加之,睡眠过程中人会处于一种“意识真空”的状态,无法体验时间的流逝感与掌控感,因此有必要将其独立划分为某个部分,以区分休闲时间的范畴。综上,本文在“三元时间”的基础上,将个体日常的时间结构划分为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私人事务时间以及睡眠时间四个部分,并以此为参照对“熬夜玩手机”现象之背后动因展开分析。
(一)“时”竞天择:作为“殖民机器”的工作时间
经统计,本文面向的受访者其夜间纯睡眠时长恒定在6至8小时区间,平均为6.9小时,若按照科学的睡眠量标准(6~8小时),他们理应不存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但在访谈和田野观察中,员工们确实表现出“白天起不来”、“上班会犯困”、“每天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甚至多数人还表示8~10小时是最理想的日睡眠时长。那么,如今为何生理上8小时的睡眠时长已无法满足当代劳工的睡眠需求?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日常时间分配中寻迹线索。
步入后工业时代,依托《劳动法》(普遍为“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8小时”)的出台,时间结构开始转向工作与休闲泾渭分明的标准化状态(郑作彧,2018 :45-46)。在此结构下,假如我们以法定的8小时工作时长、科学的8小时睡眠时长作为每日标准时间参照,那剩余8小时则自动留于休闲时间与私人事务时间,这样的平均分配体现了时间协调的平等性(见图1)。然而,任何时间类型都具备侵占其他领域的帝国主义特征(Lewis & Weigert,1981),为将时间效益的天平倾向于己,贪婪的资本不断设法掠夺劳动者的休闲时间,由此伴生了一种弹性化的时间结构。在此结构下,工作时间先天占据了时量的优势。
然而,面对工作时量的扩增,人们并未践行早睡的承诺,反而在“熬夜玩手机”中延缓入睡。由此推测,人们明明满足了科学要求的日睡眠量(6至8小时),却仍倍感困乏的原因在于,弹性化时间结构下过量的工作时间与用于复原的睡眠时间的不平衡;即当工作时间溢出之时,睡眠时间并未相应增加,反而被主动缩短(图1 图1见本期第67页),这便导致日操劳度远超休息时量,进而诱发睡眠匮乏的精神反噬。
可见,时间生态也自带一套排列优先级的“时竞天择”之法,而睡眠总是居于“时间生态链”的底端,人们一旦有其他时间需求,它将优先被分割让位。那么,作为生理必要的休息时间,人们为何在睡眠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选择“熬夜玩手机”?基于此问,本文将围绕私人事务时间与休闲时间之异化展开解答。
(二)何以为“家”:作为“杂合体”的居家时间
在日常生活研究中,“家”是日常空间秩序的基础感知,是日常生活独有的象征(Felski,2000:81-85)。然而,过去被视为“心之所向”的“家”已经变味。如今,移动技术的介入让工作时间也掺杂进“家”之中,“家”不再是分割工作、完全自由的心安之所,它退化为一个混杂多元时间的复杂空间,这主要体现于“回家到上床前”这段时间。依此,本文将从个体角度来阐述当代“居家时间”③的复杂成分。
成分一,作为过渡工作与家庭场域的缓冲时间。在访谈中,许多人表示,由于白天的奔波劳累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躺平”,他们需要借此缓解一日的疲劳:“回家当然就想摆烂呀!就啥事都干不了,主要是真的很累”(J);“到家后其实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什么的,但是每次累得都瘫在床上,就一直瘫着啥也不干,一点都不想动”(G)。然而,“躺平”并不是正式的休闲活动,它只是人们用于舒缓工作“后劲”,以备进入正常休闲状态的缓冲阶段。
成分二,作为资本俘虏的劳动时间。在资本的逻辑里,“休闲时间必须被利用起来,并且要以某种方式把它和工作联系起来;否则,它会成为使人分心的危险之物”(哈萨德,2009:110)。如前文所述,凭借移动技术,私人时间可被随时转化为组织时间,工作的基因被条件反射性地注入“每时每刻”,即便到家,人们仍需处理各种临时下达的工作,无法拒绝,不能拖延;一旦如此,意味着他们的休闲时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如受访者G表示:“回家后,负责人每天九点半左右都会跟我通过一个线上对话来对盘,每次都要聊20分钟左右”。可见,当代劳工已深陷时间协调不对等的窘境,“何时何地”突破时空的桎梏,皆沦为资本的备用劳动域。就此,“家”的内涵发生解构,它不再是遮蔽工作的象征之所,也不再是远离工作的“精神慰藉”,而是退化为一个仅仅以“家”为名的复杂场域。
成分三,作为私人事务的承载时间。按照时间社会学的定义,私人事务时间原是囊括个人工作、照顾与养育、公事参与等丰富内容的自我掌控时段(郑作彧,2018:55-56)。然而,由于精力的消解以及时间的匮乏,人们在两点一线的往复轨迹中难有余力参与其他培养性活动,继而私人事务时间被完全窄化为处理家庭琐事的乏味时段:“每天回家都快八九点了,我回家还要完成毕业论文,搞搞之后就差不多快十二点,主要现在天气热了,还得洗衣服啥的,就很烦,回家了还得折腾”(C)。私人事务时间的意义窄化恰恰照见了人们时间管理的无助感、累赘感以及匮乏感。当“处理家庭琐事”的时间占比凸显后,“家”便异化为一种负担,沦为人们开展休闲活动的变相阻碍。
综上,由于移动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嵌入,资本势力开始侵入人们的家庭日常,原本纯粹的居家时间也因此遭受异化,主要体现在:第一,时间的难控性。由于下班时间的不固定以及任务指派的随机性,居家时间的混杂成分愈发凸显,令个体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第二,时间的无效性。由于为己享用的休闲时间已所剩无几,若再被其他原子事件填充,不免会造成居家时间的杂乱、跳跃和动荡,进而加重时间体验的危机感和破碎感。对此,为尽可能减少休闲时间的损耗,人们需要加速完成临时工作以及家庭琐事,这便导致时间被各种忙碌与焦虑装塞填充。最终,原本令人向往的居家时间与所属主体愈发疏离,降级为一段“无时间之时间”。为重拾时间的自主性,人们放弃对居家时间的执念,希冀找寻一片新的“休闲净土”。就此,“睡眠”成为人们开发时间资源的目标。
五、睡前的手机时间是一种救赎还是异化?
“睡眠”总是被轻视的。过去,一些哲学家认为,鉴于意识和意志的优先地位,睡眠无助于人们运用理智或求知,因而它缺少一定价值(克拉里,2021:19)。在宗教徒眼中,时间是需要高度敬重的东西,只有劳动才是对时间的救赎,不必要的长时间睡眠是一种浪费,是一种罪大恶极(韩炳哲,2017:185-186)。较之于睡眠,人们对休闲寄予了厚望,因为人们只有具备充裕的休闲时间,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它是自由化且人性化的(唐任伍,周觉,2004)。放眼当下,人们对睡眠和休闲的态度似乎依旧,睡眠不止是资本的对立面,现在它也成为人们享乐的障碍,人们恨不得一直保持清醒,将睡眠时间全部投入休闲娱乐,而“熬夜玩手机”显然是最好的例证。
(一)与生活和解:作为“心灵摆渡”的手机时间
“熬夜玩手机”是人们对休闲时间的补偿实践。如上文所述,当下班到家,干完额外工作,忙完私人琐事,留给人们的休闲时间已然寥寥。为保证每日的休闲时量,人们会选择玩手机的方式来填补休闲的空缺,而先前的缓冲蓄能恰好补给了新的能量,使他们又有了保持清醒的精力条件,至于熬到何时,因人而异。那么“熬夜玩手机”究竟有何魅力,以至于人们宁愿解除生理调节(bioderegulation),付出隔日精神不振的代价?
1.治愈的时间:“关了灯才有心灵疗愈的时间”
在社会加速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企业员工所负载的事务量已远超科技加速的速率(罗萨,2018:26-28),这直接造成过度工作、频繁加班的“忙碌运动”。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模式,员工们需要一定的宣泄时间来复原内心的“工作创伤”。然而,当回到“心之所向”的家时,他们又需要马不停蹄地奔向额外的工作以及家庭的琐事,他们几乎没有间歇地忙碌着。直到深夜,待一切处理完毕后,他们才有自己支配的“疗愈时间”。此时,面对狼狈不堪的身体以及疲于旋转的大脑,徜徉手机世界成为他们最划算、最省力的休闲方式:“白天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可能需要在夜晚关掉灯以后,才有一个自己心灵疗愈的时间。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刷什么,但我还是想玩手机,就是熬夜嘛”(H);“就是逆反心理,因为我白天都在工作,没有时间去干想干的,我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只有我看够了想看的,才会觉得心情舒畅些,才能好好入睡”(B)。可见,为了宣泄压力、追赶社会步伐、重拾时间掌控感,人们将净化心灵的任务寄托于“手机时间”,试图实现精神上的自我疗愈。
2.独处的时间:“夜深了,只想一个人静静”
数字时代下,“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媒介化生存”的写照,“在线”与“连接”似乎总是绑定的。为了避免与世界脱节,防止“断连”成为一种时刻的任务,人们需用尽浑身解数确保手机的充足电量。但随之而来的是实时呼叫的工作指令、令人倦怠的社交压力以及铺天盖地的垃圾信息;即便是居家时间,也浸满了这些忧扰。显然,现代社会充斥着“连接过载”(connection overload)(LaRose et al.,2014)的隐忧,当私人时间被曝光为“无时无刻”的公共时间,人们将渐失纯粹的独处时光。更矛盾的是,在私人空间,人们希冀断连,却又想保持在线。不过,这并不是妄想,“熬夜玩手机”满足了这一愿景。
在传统意识里,深夜是专属睡眠的,人们总会默契达成互不干扰的协定,这为“保持在线,暂时断连”提供了契机。此时,私人时间不再是社会组织的“共有财产”,手机的消遣作用可以发挥至最大化;即便真有“不识时务者”发送消息,人们亦可装作“已睡”不予回应:“有时候就很想一个人静静,只有躺床上了我才能心无杂念地玩手机”(E);“有时候我和别人说自己要睡了,不聊了,不一定是真的睡了,我就是想再一个人刷刷手机,然后睡觉”(K)。看来,深夜作为配置睡眠的专属时段,天然有着一层屏蔽连接的保护膜;为贪图每日难得的清静,人们会挤压部分睡眠时间,创造“在线却断连”的宝贵时机,以满足沉浸式的独处需求。
3.鲜活的时间:“在手机中找到了自我”
费尔斯基(Rita Felski)曾将当代城市比作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混乱迷宫”,但在日常生活的旅行中,人们往往会“选择走熟悉的道路,借同一路线来管理空间和时间”(Felski,2000:91-92)。依其之见,人们的日常已被自动划为一方“囚牢”,每日同样的路线,同样的周遭,同样的行动,两点一线的往返是百无聊赖的缩影。当昨天、今天和明天反复重演,日常生活也就无异于能够回放的“戏剧表演”(列斐伏尔,2018:125);当故事的意外消解于时间的预知性之中,对明天的期待自然也就失去意义。
为摆脱时间的枯燥感和无意义感,有研究对象曾试图突破这框定的日常,只为探求时间的可能性与未知性。例如G会试着以绕路的方式改变通勤路线以增加室外时间;H刚实习时,会试着下班后约同事去排球场运动。然而,“可能性”的探索终归是一种“偶尔”,她们一致认为这些尝试是徒劳的,额外制定的线路将换来更加疲惫的身体以及更少的休闲时间。相较之下,“熬夜玩手机”则是性价比最高的消遣方式。凭借手机,人们能在短时间内进行消费、游戏、刷剧等操作,不费体力便能感受“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幻想世界,这是他们在单调日常中找到的一丝慰藉:“晚上我会刷刷淘宝,看看抖音,有时候追剧的话可能把整集追完了再睡……在这段时间,我才真正有时间掌控感,觉得很痛快”(C)。可见,睡前的手机时间让生命的时间线重新迸发活力,此时,人们能够重获久违的自我效能感与时间充实感。
如上,员工们的日常早已被各种非自在的异化时间所铺满,其一天似乎都笼罩在“无时间”的阴霾中。其结果是,人们丧失了生活的掌控感、时间的价值感以及生存的成就感,居于一种深重的与本真疏离的异化状态。作为生命政治权力的主体,为了重拾时间的宰制权,人们选择主动开拓“深夜”这一净土。此时,手机化作灵魂摆渡者,将人们引渡向那治愈、清静又鲜活的时光彼岸。在人们眼里,休闲是比睡眠更重要的,在休闲时间越发被榨干的境况下,“熬夜玩手机”无疑成为救赎人的“恩赐”时光。正向来看,它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细微迹象,是真实自我之觉醒的积极表现;那么,它是否可以视作人们克服异化的一种能动表现,一种方式手段?还是说,此时段依旧是处于异化的,它并没有被消除?或许,我们可以借耶吉和罗萨所指的克服异化的方式进行分析。
(二)异化并发症:作为自我蒙蔽的手机时间
在探讨“如何实现美好生活”这一议题时,耶吉和罗萨各自提出了消除异化的方式。在此,本文参照两位的观点,对“熬夜玩手机”的行为性质加以评判。
首先,耶吉基于实践角度,提出了“化用”(appropriation)的概念,它是一种与自我和世界建立关系,让自我和世界为己支配的实践方式;通过“化用”,人们能够解决问题,让生活形式得以避免异化(Jaeggi,2014:44-48)。套用该说法,“熬夜玩手机”确实是人们基于休闲时间的缺失所展开的精神补偿;即借机重建与时间的掌控关系,并试图解决时间无力感和失控感等异化问题。但是此番行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异化,它只是暂时性的精神麻药,以自我安慰、自我麻痹的姿态,缓解异化带来的各种负面感知。这种做法无异于对异化的适应、纵容和妥协,最终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熬夜玩手机”并不能被视作一种“化用”方式。
那么,它是罗萨所谓之“共鸣”吗?显然更不是。依罗萨之见,“具有生命力的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并不是掌控事物,而是在共鸣中与事物连接,通过自我效能感面对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探究”(罗萨,2022:54)。罗萨描绘了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我与世界相互回应”的世界关系;在其视野里,“支配”、“化用”、“控制”才是真正导致异化的元凶,因此他反对任何企图“掌控世界”的行为(郑作彧,2021)。顺其逻辑,作为人们用于掌控时间所衍生的时段,“熬夜玩手机”自然是不被认可的刻意制造异化的过程。需要说明,本文只想借两者之见评判睡前手机时间的异化本质,并不想在此探究消除异化的正确路径,也不想去争辩耶吉和罗萨的观点孰对孰错。
由上观之,本文认为,与其将“熬夜玩手机”视为自我救赎、反抗异化的手段,不如将其视作休闲时间缺失、日常时间异化所招致的“并发症”,这意味着该时段依旧是异化的,甚至这种异化更为隐蔽,更不易被察觉。
第一,在过去,休闲时间是给定的,人们只需思考如何利用时间,“实现个人发展”依旧是休闲的要旨;而今,前文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操劳的问题,已从“如何利用休闲”转向“如何获得休闲”,从“高级的自我发展”转向“初级的心理愈合”。显然,人之休闲的发展梯度与价值程度皆发生了断层式降级,这亦是需求异化、时间异化的写照。
第二,由于“熬夜玩手机”依旧处在有限的时效范畴,为在短时间内体验更多的电子项目,人们往往会采取压缩事件时长的方式来寻求自我掌控的快感:“如果是刷剧、刷综艺,我一定会开倍速,争取多看几集,如果我一晚上就看一集,那就太浪费了”(N);“我现在晚上都不太看电影原片,电影一部就要90分钟以上,看一个晚上我都不用做其他事了,所以我会直接去搜电影解说,这样就能多看几部”(S)。当“熬夜玩手机”时段被各类子事件填充,人们会愈感时间的加速与休闲的短暂,其结果依旧是时间意义的降级。
第三,通过前文的种种描述,可以发现人们将“熬夜玩手机”视作一种自我保护、减缓工作矛盾的“安全阀”(廉思,唐盘飞,2018)。通过此“安全阀”,人们可以将白天压抑的种种不满进行转嫁宣泄,以达到维护关系、适当减压、调节情绪的功效。然而,这种转嫁释放的结果是,人们将自身作为报复对象,即矛盾和敌意由资本转接到了自身,人们在熬夜过程中消耗自身的时间和精力,付出损伤身体的代价:“网络上有种说法,就是‘报复性熬夜’,我白天没自己的时间,那我晚上必须得搞回来,不过我也知道熬夜带来的危害,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去熬”(M)。因此,“熬夜玩手机”本质上是一种转嫁式的报复性熬夜,由于社会中存在各种结构性压力,势单力薄的人们无法对主导权力作出直接抵抗,只能通过报复自身来产生慰藉。
第四,对睡眠时间的主动剥夺意味着劳动者将不只是时间异化的受害者,他们在“熬夜玩手机”的过程中,亦扮演了肇事者、纵容者的角色,这直接体现在“二阶问题”的制造上,即“日常弥漫的睡意”。当“熬夜玩手机”成为一种习惯,当晚睡早起成为一种常态,睡眠不足引发的“睡眠债务”(Rupp & Wesensten et al.2009)将不断累加,最终“睡意”将遍布人们的清醒时刻:“上班时候就是睡不醒,整天犯困,迷迷糊糊,一有睡觉的机会,譬如地铁上、午休的时候,我都不会放过,但是你问我会早睡吗,我还是不会,我已经习惯了”(M)。因此,人们在工作之余,还要时刻与睡意抗衡,这一“二阶问题”的生成无疑暴露了生活形式存在的内部问题。那么,互联网企业员工在工作期间又是如何清除睡意的?
调研发现,以“咖啡”代水已成为多数员工的解困之策:“我以前都不喝这么多咖啡,来了公司之后发现自己喝的频率变多了,而且公司不是都有提供咖啡自助吗,我发现基本每个工位大家都放着杯咖啡”(I)。此外,争分夺秒保证午休效益最大化也是他们维持精力、抗击睡意的重要途径。例如部分员工倾向通过提前就餐,或是订外卖、吃打包餐、先补觉后进食等错峰就餐方式,来减少排队所浪费的时间。另外,为寻求清静,提升睡眠质量,正式工多会在办公室空旷位置摆设私人躺椅,并自配耳塞、眼罩、毯子等周全装备。然而,到了深夜,清醒与睡意的战役仍在继续,人们并未及时止损,反倒一味追求清醒,只为延长治愈式的手机时间。
由上观之,睡前的手机时间依旧是异化的时段。只不过,相较于“无时间之时间”,它似乎又给予人们一定的时间掌控感,但是掌控背后却仍存在无效、无意义、加速等异化体验,还会招致身体健康受损、精神萎靡不振等代价。鉴于此,本文延展出“时间异化”的第二层内涵,即“自我蒙蔽的时间”,这种时间会给人有时间的念想,产生“镇定剂”的功效,致使人主动深陷异化而不自知,甚至乐此不疲、沉浸其中。在此时段内,人们会产生时间的麻醉感,感觉自己有时间,从而暂缓当日累积的时间恐慌感。因此,“自我蒙蔽的时间”是“无时间之时间”达到一定异化程度后引发的异变,它是更为隐蔽且程度更深的异化(区别可参考表2 表2见本期第73页)。
六、结论与讨论:谁是元凶?手机,资本,还是自我?
如上,本文探讨了“熬夜玩手机”时段的异化实质,即作为“自我蒙蔽的时间”。那么这是由谁引发的?手机?资本?还是劳动者?对此,本文将用排除法逐一分析。
首先排除手机之嫌。综观技术发展的长河,“技术善恶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支持者认为,通过技术的使用,劳动中所包含的严酷的体能运用能够被最小化,其中智能和“科学性”的部分大大提升这也预示技术的发展终将带来劳动者主体性的解放(塞耶斯,2020:33)。反对派认为,由于社会存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技术必然会沦为资本控制人的工具,从而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赵爱霞,王岩,2021)。依本文情境,本文则更倾向于“技术中立论”。研究发现,当资本利用手机盗取劳动者的注意力和休闲时间时,手机便产生了服务于资本的意识形态;而当劳动者依托手机开拓为己享用的熬夜时光时,手机又发挥了“摆渡人”的治愈作用。可见,技术本无涉价值,关键在于“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Mesthene,1970:60)。当然,可能会有人以“手机成瘾”为由解读“熬夜玩手机”现象,但“手机成瘾”理应表现为对手机的长时间依赖,如果仅凭某个时段来下“手机成瘾”的论断,难免以偏概全。
那么,元凶是资本吗?如克拉里之见,资本主义确实觊觎着人们的睡眠时间,他们会制造各种消费需求,来提升休闲的诱惑力,从而铲除睡眠障碍(Davies & Niemann,2002)。这些方式包括制造营销噱头、赋予某日特殊含义等。如“6·18”大促当天,部分受访者的入睡时间明显比平时晚,他们会特地为抢购、消费而熬夜。但是这种情况仍是少数,获取休闲时间依旧是触发人们“熬夜玩手机”的主导性需求,而且正是人们有了休闲需求,才会给资本攫取用户时间的可乘之机(Harmon & Duffy,2022)。顺此逻辑,资本好像也并非原罪。
所以,一切是人们作茧自缚?表面上看,“熬夜玩手机”的确是人自发、主动的行为,但是按照结构性分析,这种主动、自发又是休闲时间异化后连带的结果,就此而言,资本好似又被推为了罪魁祸首。事实上,资本也好,自我也罢,这样的答案显然是片面的。若从主客观层面分析,与其将睡眠缩减的责任简单归咎于一方,不如将其视作资本时间控制手段之强化和劳动者时间免疫系统之弱化共同招致的结果。
一方面,借助移动技术,人们的劳动场域已从“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蔓延至“流动空间”(spaces of flows),随同其中的“劳动同意”心理也逐步内嵌于休闲在内的全域时刻,这意指了资本更为深重的时间控制手段。另一方面,人们的时间自主性自配有灵活的免疫系统,起着时间维护和调控的作用。而今,在各种社会结构性压力下,人们的时间认知逐渐单维化,行为安排逐渐发条化,他们将自身绑定在日常单一的可能性之中,将日常圈定于既定的日程轨道内;面对劳动时间的侵占以及时间道德化的枷锁,他们已然麻木,已然精疲力竭。久而久之,随同反抗意识的淡化以及排解能力的弱化,时间免疫系统难承负荷,濒临崩溃,只能寻求“增援”,通过开采备用的睡眠时间来委曲求全。由此,“熬夜玩手机”既是人们惰于反抗,在维持现状基础上做出的妥协与让步,也是人们追寻本真之路上苟延残喘式的自我挣扎与自我救赎。
然而,劳资的时间之战终究是你退我进、此消彼长的过程,劳方一味地退缩、迁就和忍让,只会换来资方的变本加厉,其结果将导向劳动时间的持续扩张以及睡眠时间的不断后延,资本终将是这场战役的既得利益者。或许,真如克拉里所预言,终有一日,睡眠时间会被开发殆尽,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淘汰体系下,人们将进入一个24/7式的“全天候异化”的世界(克拉里,2021)。
总而言之,作为当代日常生活压抑之重、时间异化之深的缩影,“熬夜玩手机”展现了人们对休息时间的向往、对时间掌控权的渴求。当“熬夜玩手机”成为日常,当休闲时间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这无不映射了人们生活压力之繁重,节奏之紧凑,生命之虚无。要想重拾时间的自主性,追求实质的美好生活,我们就必须放大和折射日常生活,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日常生活。因而,本文希冀于通过对互联网企业员工之时间图鉴的绘制,将“熬夜玩手机”现象进行结构性剖析,旨在使其从不透明性中解蔽出来,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本真自我,真正意识到其时间异化的实质。■
注释:
①根据人类生理及内分泌规律,通常将入睡时间超过23点界定为熬夜。
②在互联网“大厂”W中,由于正式工与实习生之间存在很强的身份壁垒,作者在以实习生身份进入田野后,很难找到配合度高的正式员工。为扩大参考样本,本研究在后期补充了8位互联网企业正式员工的访谈内容,以确保研究的充分性。此外,需要说明,实习生的生活节奏与睡眠情况同样具有适用性和代表性,他们也是互联网企业整体睡眠情况的缩影,能体现员工整体的工作节奏与劳动强度,原因有三:第一,实习生在一个月的实习后,已能够适应互联网企业的工作环境,其之后的生活节奏基本保持恒定状态;第二,本研究面向的实习生多为即将毕业的应届生,虽然实习生的工作任务无法比拟正式工,但他们为了转正或者完成个人KPI,也承担着一定的工作焦虑与同辈压力,他们也有着与正式工相似的工作处境;第三,实习生需要和正式工一样严格遵守部门的时间表以及规章制度。
③为有效表述“家”的意义构成以及私人事务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异化,本文所指的“居家时间”并非完整的“家庭时间”,而是单指“到家到上床前”这段时间。
参考文献:
陈晨(2021)。熬夜:青年的时间嵌入与脱嵌。《中国青年研究》,(08),29-35。
陈纬陈书妮兰荷伊(2023)。时空视域下青年产业工人的睡眠节律与生成机制——基于对重庆市20位产业工人的访谈。《中国青年研究》,(07),5-14。
[德]哈特穆特·罗萨(2018)。《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哈特穆特·罗萨(2022)。《不受掌控》(郑作彧,马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韩炳哲(2017)。《时间的味道》(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韩升,段昀辉(2023)。本质主义异化观的论争及反思——由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对马克思的误读展开。《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1-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2008)。《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亨利·列斐伏尔(2018)。《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月琴,黄宪成(2023)。粉丝公益传播中的时空套利与“数据人”异化:数据主义批判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07),55-74+127。
姜华,崔嘉晟(2022)。时间异化:异化诠释的新模式——罗萨异化理论评析。《理论月刊》(01),5-12.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卡尔·马克思(1844/202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研究出版社。
李溪源,施琴(2022)。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与当代生活。《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108-114。
吕梓剑,戴颖洁(2022)。时间争夺战:“已读”背后的时间政治与异化感知——以钉钉App为例。《新闻记者》, (10),60-71。
鲁宝(2021)。日常生活的神秘化意识及其批判性超越。《山东社会科学》,(10),36-46。
廉思,唐盘飞(2018)。社会安全阀视域下的网络直播功能探析——基于北京网络主播青年群体的实证研究。《中国青年研究》,(01),48-55。
[英]曼纽尔·卡斯特(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乔纳森·克拉里(2021)。《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河西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2022)。《<2022年职场人群春季健康状态解析报告>重磅发布》。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dcT5LtYheYTIgLNHzzUJxg。
孙珉,吕雯思(2023)。日常生活媒介化:基于“电子榨菜”的思考。《当代传播》,(03)98-102。
唐任伍,周觉(2004)。论时间的稀缺性与休闲的异化。《中州学刊》,(04),26-30。
王杰,来昕(2022)。倍速播放:青年闲暇时间的消费与异化。《当代青年研究》,(04),36-42。
吴鼎铭,胡骞(2021)。数字劳动的时间规训:论互联网平台的资本运作逻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1),115-122+171。
吴宁(2007)。《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新京报(2022)。《谷爱凌分享成功秘诀:每天睡足10个小时,保持热爱》。检索于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4430510814599.html。
[英]肖恩·塞耶斯(2020)。《马克思与异化:关于黑格尔主题的论述》(程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叶琳(2016)。被异化的时间及其扬弃的可能——对马克思时间观内在逻辑的追问。《河南社会科学》,(12),22-27+123。
[英]约翰·哈萨德(2009)。《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翔,蔡华杰(2022)。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对“异化理论”的重构及当代启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1),91-99。
赵爱霞,王岩(2021)。算法推荐与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云南社会科学》,(03),112-118。
郑作彧(2018)。《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郑作彧(2021)。化用的生活形式,还是共鸣的世界关系?——批判理论第四代的共识与分歧。《社会科学》,(03),53-67。
Aldhawyan, A. F.AlfarajA. A.ElyahiaS. A.Alshehri, S. Z.& Alghamdi, A. A. (2020). 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poor sleep quality in social media users among freshman college students. Nature and Science of Sleep , 279-288.
BarnesC. M. (2012). Working in our sleep: Sleep and self-regulation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 2 (3)234-257.
Demirci, K.Akgonül, M.& AkpinarA. (2015). Relationship of smartphone use severity with sleep quality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 4 (2)85-92.
DaviesM.& NiemannM. (2002). The everyday spaces of global politics: Work, leisurefamily. New Political Science , 24 (4)557-577.
EricksonB. (2017). Marx, Alienation and Dialectics Within Leisure.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Leisure Theory , 457-471.
FelskiR. (2000). Doing time: Feminist theory and postmodern culture . NYU Press.
GordonA. M.Mendes, W. B.& PratherA. A. (2017). The social side of sleep: Elucidating the links between sleep and social process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26 (5)470-475.
HarmonJ.DuffyL. (2022). Alienation from leisure: Smartphones and the loss of presence. Leisure/Loisir , 46 (1)1-21.
HughesN.BurkeJ. (2018). Sleeping with the frenemy: How restricting ‘bedroom use’of smartphones impacts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 85 , 236-244.
JaeggiR.(2014).Alienation.trans.by Frederick Neuhouser and Alan E.Smi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RoseR.Connolly, R.LeeH.Li, K.& HalesK. D. (2014). Connection overload? A cross cultural study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edia connec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 31 (1)59-73.
Lewis, J. D.WeigertA. J. (1981).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 Social forces , 60 (2)432-462.
MestheneEG.(1970).Technological change: 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
MoulinK. L.ChungC. J. (2017). Technology Trumping Sleep: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and Sleep in Late Adolescent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 6 (1).
RosaH.(1998).Identitat und kulturelle Praxis:Politische Philosophie nach Charles Taylor,Frankfurt/New York:Campus.
RuppT. L.WesenstenN. J.Bliese, P. D.& Balkin, T. J. (2009). Banking sleep: realization of benefits during subsequent sleep restriction and recovery. Sleep , 32 (3)311-321.
SeemanM. (1975). Alienation stud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1)91-123.
Swann,T.&StanfordJ.(2016)。Excessive hours and unpaid overtime: An update,Centre for Future Work,Canberra:Australia Institute.
TamuraH.NishidaT.TsujiA.& Sakakibara, H. (2017). Association between excessive use of mobile phone and insomnia and depression among Japanese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 14 (7)701.
[作者简介]吕梓剑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朱咫渝系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本文为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中心课题“数据与算法时代的媒介素养研究”(编号:21ZJCW02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