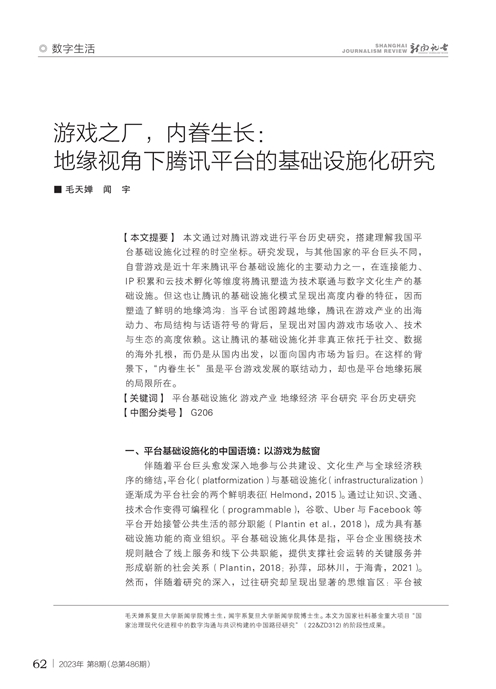游戏之厂,内眷生长:地缘视角下腾讯平台的基础设施化研究
■毛天婵 闻宇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腾讯游戏进行平台历史研究,搭建理解我国平台基础设施化过程的时空坐标。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的平台巨头不同,自营游戏是近十年来腾讯平台基础设施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连接能力、IP积累和云技术孵化等维度将腾讯塑造为技术联通与数字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但这也让腾讯的基础设施化模式呈现出高度内眷的特征,因而塑造了鲜明的地缘鸿沟:当平台试图跨越地缘,腾讯在游戏产业的出海动力、布局结构与话语符号的背后,呈现出对国内游戏市场收入、技术与生态的高度依赖。这让腾讯的基础设施化并非真正依托于社交、数据的海外扎根,而仍是从国内出发,以面向国内市场为旨归。在这样的背景下,“内眷生长”虽是平台游戏发展的联结动力,却也是平台地缘拓展的局限所在。
【关键词】平台基础设施化 游戏产业 地缘经济 平台研究 平台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平台基础设施化的中国语境:以游戏为舷窗
伴随着平台巨头愈发深入地参与公共建设、文化生产与全球经济秩序的缔结,平台化(platformization)与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逐渐成为平台社会的两个鲜明表征(Helmond, 2015)。通过让知识、交通、技术合作变得可编程化(programmable),谷歌、Uber与Facebook等平台开始接管公共生活的部分职能(Plantin et al., 2018),成为具有基础设施功能的商业组织。平台基础设施化具体是指,平台企业围绕技术规则融合了线上服务和线下公共职能,提供支撑社会运转的关键服务并形成崭新的社会关系(Plantin, 2018;孙萍,邱林川,于海青,2021)。然而,伴随着研究的深入,过往研究却呈现出显著的思维盲区:平台被更多地视为封闭、孤立、以自身业务拓展为核心的经济主体,统合的是以平台为中心的合作者关系,相应地却忽略了在跨越国界、地域、技术系统的地缘关系中被重塑的平台角色(Qiu et al., 2022)。
因此,地缘视角成为一个崭新的维度,可以帮助我们定位一个国家中平台基础设施化范式的时空坐标。20世纪90年代冷战之后,跨越地缘的经济关系逐渐取代政治较量,成为主导世界新秩序最主要的力量。地缘经济以国际集团化、跨国贸易、缔结国际经济联盟的形式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并逐步建立世界性的经济网络关系(李敦瑞,李新,2009;安虎森,郑文光,2016;李正,陈才,熊理然,2014)。伴随着以腾讯、Facebook、Google为代表的平台巨头逐步深入文化生产,通过掌握平台数据库和网络接口,平台能够为跨越国界的文化生产者提供创造、分发、营销和货币化内容产品的经济和物质支持(Poell et al., 2021:52)。平台巨头的基础设施化开始改变传统跨国集团、产品出海的运作逻辑,重塑地缘经济的运作模式。
那么,中国的平台经历了怎样的本土生长历程,又如何跨越地缘落地生根?平台游戏产业也许是透视这一问题的舷窗:在中国,以腾讯、网易等“游戏之厂”为代表,自营游戏在平台巨头本土扎根和海外扩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本土内生的角度上看,不同于与GAFA等大型海外平台以投资入股的方式参与游戏产业,我国平台自主研发的游戏在其内部的生态架构中占有极高的比重,其在盈利收入上也高度依赖自营游戏。以腾讯为例,2021年腾讯的网络游戏收入占总体增值服务收入的59.77%,占集团总收入的31.08%。而在2015年,这两个比重分别达到70.15%与54.71%(腾讯控股,2016,2022)。在地缘拓展之中,伴随着平台基础设施化进程的加深,游戏产业在我国逐渐脱离了其作为娱乐产品的狭隘角色,开始通过平台出海、文化传播、跨境扶贫让平台的触角跨越地缘。伴随着游戏产品成为国风出海的主要载体,以《王者荣耀》为代表的平台游戏产品开始在国内文化产业的内部生长、弥合区域之间的文化鸿沟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上发挥重要作用(邓剑,2022;何威,曹书乐,2018)。
因此,本文通过腾讯游戏为个案聚焦于中国平台基础设施化的独特实践。值得强调的是,不同于以往研究关注特定的App如何成为基础设施,本研究的重点在于透过腾讯游戏产业理解中国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历史线索与地缘结构。具体来说,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有二:其一,腾讯的游戏产业如何参与腾讯平台基础设施化的进程?游戏的生产、发行和技术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赋予了这一进程怎样的特征?其二,腾讯的基础设施化模式如何重塑其地缘策略?透过这一个案,我们如何在中国语境下反思平台基础设施化与地缘经济的理论张力?
二、地缘视角下的平台基础设施化研究
平台基础实施研究的地缘视角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平台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中介服务中,数据、内容和资本的流动可以在平台企业的主导之下跨越地理的边界流动,并以此形成能够被世界范围内的公司与国家接入的全球数字基础设施(De Reuver et al., 2018;van Dijck, 2021)。在平台最原始的定义中,其基础设施的特性体现在平台是具有支撑、中介功能的实体(Gillespie, 2010),而伴随着数字平台业务范围的拓展,平台凭借对数据、算法、参与接口的掌控可以厘定广告商、生产者、分发商甚至实物交易的商业模式、所有权和合作协议,开始取代物流、交通、金融等传统线下的基础设施服务(van Dijck et al., 2018:4)。具体来说,平台基础实施化研究的地缘视角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议题:平台如何打破线下基础设施的地理边界、平台基础设施化如何重塑地缘政治格局。
其一,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打破了行政区域的地域限制,将社会服务和公共职能嵌入自身的平台生态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下,Facebook与谷歌地图以其内容的可编程性开放了用户对其平台建设的参与,打破了传统企业的边界资源,让实体交通和社会交往打破了地缘和身边社会圈层的局限,让平台与基础设施的边界愈发模糊,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Plantin, 2018;Helmond et al., 2019),甚至开始逐步成为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社会基础设施的搭建者(刘战伟,2022)。面对中国实践,淘宝平台在搭建过程中面对支付与物流的功能建设承袭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叙事(段世昌,2021),“健康码”的出现不仅联结了人与行政系统的沟通和互认,更有不同地区数字系统在数据格式、接口的标准化统一(李梦颖,2022)。
其二,在全球平台基础设施布局的背后,也蕴藏着全球信息秩序的争夺。以5G网络技术、全球平台贸易秩序的制定为代表,基础设施的添置本质上是不同平台系统体系面对全球数据和资源市场的竞争(Tang, 2020;Vila Seoane, 2020)。人才流动与跨国贸易让平台与国家脱离孤立的散点,也让平台基础设施化的进程不仅成为本土的信息技术表征,也成为国际的经济驱动力(Hong & Harwit, 2020)。这一进程也直接体现于我国互联网治理延展的历史脉络之中。从2005至2020年,在我国的政策文本中,“基础设施”逐渐在顶层设计中兼具区域协同和全球合作发展的外部效应(姬德强,朱泓宇,2021)。
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平台游戏生产因为具有本土内生和海外拓展的双重职能,见证着平台跨越地缘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其产业自身的平台化一方面意味着游戏的制作、设计、开发、艺术音乐配套等原本孤立的分工逐渐被统合在一个平台生态之中(Johnson & Woodcock, 2019);另一方面,游戏的平台化塑造了一种可连接的商品化形式(connective commodity),将玩家的级别提升、产品的商品化渠道与游戏的连接元素融合于一身(Nieborg, 2015),并以其与影视、音乐的联动能力逐渐模糊数字文化产业内部的边界(朱春阳,毛天婵,2022)。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平台分发能力的增强,游戏产业与平台跨境的基础设施化进程相生相伴,平台因而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产权以及进入跨国市场的机会。相应地,平台公司重新定义自身内部的市场、服务与平台边界,在其他区域制定本地化和支持策略,来扩展自身的生产和流通网络(Kerr, 2017:12-13)。
但是,上述两个研究脉络也因而拥有视角上的盲点:过往研究集中关注平台基础设施化的主要特征,尤其是“跨越地缘的平台基础设施具有怎样的特点”,但相应地忽略了这些特征的成因,尤其是基础设施化跨越地缘的动力机制。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语境,以平台游戏产业为个案,通过剖析平台游戏产业的成长策略如何与其跨越地缘的基础设施布局彼此塑造,以此总结平台基础设施化的中国范式。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平台历史研究(Platform Historiography)的方法聚焦于腾讯游戏的个案。作为关注平台企业长期沿革的研究方法,平台历史研究由平台研究学者Helmond首提,将平台视为企业主体、技术中枢与平台生态的规制制定者,由此将平台的技术报告、算法体系、公开话语和投资行为等平台史料构成对其在技术、市场机制沿革的勾勒(Helmond & Van der Vlist, 2019)。为探究平台游戏与平台基础设施化之间的关系,本文搭建了对其分析的时空坐标:腾讯游戏的发展进程如何与腾讯基础设施化的历史线索彼此塑造?依托于游戏的基础设施化模式如何影响腾讯的跨越地缘?本文具体纳入分析的史料包括2004—2022年腾讯的年度报告,2010年以来游戏产业版号审批、自营游戏收入及出海数据,2008—2022年腾讯在中国游戏大会与自身游戏公开大会的演讲,以及腾讯公开的部分海外投资情况等公开文本,以此梳理出游戏出海背后平台基础设施处理地缘经济的基本实践。
三、用户、IP、技术:游戏如何推动平台基础设施化
作为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平台企业之一,腾讯的主要业务涵盖线上社交、文化生产、技术终端等多个行业,其基础设施化的进程也随之延伸出多个触角。例如微信以其用户规模广泛地参与到货币金融、公共治理、社会交往等社会功能之中,通过增强个人联系、群体的搭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交往模式(Harwit, 2017),甚至成为中国网络社会的“移动操作系统”(Chan, 2016)。在以腾讯视频为代表的数字文化生态之中,腾讯通过收购阅文集团,以垄断网络文学IP的形式让自身成为网文改编影视剧的主要引擎,把握了数字文化生产的核心资源(朱春阳,毛天婵,2022)。在这两则案例的背后表明了,腾讯的整体基础设施化进程总体秉承着基于某一“超级App”成为流量、数据和收入的端口,来为集团进一步的金融化和对公共生活的渗透赋能(Jia et al., 2022)。
腾讯的基础设施化之路迄今也经历了近十年的历史。在2015年的公开信中,马化腾提出腾讯的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并将其含义定义为“连接器”(腾讯开放平台,2015)。随后,其基础设施的定义延展为“云、地理位置服务、移动支付、大数据和安全能力”(腾讯开放平台,2016)。尤其在这之中,“云”因为延伸出孵化合作伙伴生态共同体的概念而成为基础设施的核心要义(腾讯开放平台,2017)。伴随着平台生态的进一步发展,基建也更加衍生出软件服务的职能(极点商业评论,2020),并先后让腾讯云成为“支持合作伙伴发展的生态基础设施”(腾讯开放平台,2016),腾讯视频成为“视频产业的赋能基础设施”(刘旷,2019)。
但有趣的是,上述腾讯的基础设施化足迹均伴随着其自营游戏作为最为核心的支持动力。早在2013年,腾讯开放生态的早期建设中,产生收入的应用均来自于娱乐和游戏(腾讯科技,2013)。马化腾在发表腾讯的“连接器”与开放宣言之时,格外强调了与Facebook等平台不做游戏、只连接游戏开发者不同,腾讯仍然将自研游戏保留为了解腾讯自身生态的端口(腾讯开放平台,2014)。更为重要的是,腾讯的游戏技术成为其进行云开发、腾讯技术硬件打造的重要科技来源(楚云帆,2023)。游戏甚至超出娱乐商品的功能,而成为腾讯在基础设施化的进程之中的技术工具,为其积蓄连接能力、参与文化生产、培育数字技术提供重要动力。具体而言,腾讯游戏对于其基础设施化进程的推动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腾讯的平台生态之中,游戏是腾讯获取用户资源、联结创业合作者的重要窗口。成为一个“连接器”是腾讯实施开放战略的主要方式之一(毛天婵,闻宇,2021),也是腾讯在游戏领域不断发展的基础。腾讯陆续成立了GAD腾讯游戏开发者平台、腾讯游戏学堂、GWD腾讯独立游戏孵化器,并推出青年游戏人作品孵化平台“花火计划”(竞核,2020),为创业者提供技术资源、投资合作等全方位帮助,推动中小团队进行游戏产品创新,开发优质游戏内容。腾讯在游戏领域的连接不限于创业者,而且通过产业研究、学科建设与科研合作,搭建“产学研”体系(腾讯游戏学堂,2020),例如开设腾讯游戏高校美术创意大赛、腾讯游戏高校创作大赛等。这样一来,腾讯与行业创新者、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共同投入游戏创新,挖掘游戏价值。除了创新者之外,腾讯关注用户价值,搭建平台并邀请玩家参与价值共创,实现用户间的连接。早在2009年腾讯就打造了游戏工会,搭建“全平台玩家之间的社区”,使玩家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腾讯游戏,2011)。2016年,腾讯成立游戏玩家创作联盟,使玩家升级为游戏产业深度参与者,进行内容创作(腾讯游戏,2019a)。2020年,腾讯上线游戏官方社区“闪现一下”App,搭建和用户互动的平台(TechWeb, 2020)。为了实现更好的连接,腾讯每年举办腾讯游戏嘉年华(后改为TGC数字文创节)、腾讯游戏开发者大会、腾讯游戏年度发布会,构建连接游戏开发者、游戏从业人员、游戏玩家和科研机构的平台。
其次,腾讯于2011年通过腾讯游戏板块首提“泛娱乐”战略,最早通过游戏的IP积累,得以打破“影、游、动”的文化生产边界,使其成为数字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在2011年,腾讯首次提出以IP打造为核心的“泛娱乐战略”,是“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多领域共生打造明星IP的粉丝经济”,其最终目的是“在建立和完善各个垂直领域产业生态的同时,将横跨这些领域实现明星IP的自由穿梭共融共生”(新浪游戏,2015)。游戏是腾讯在泛娱乐战略的布局起点,是“IP的源头”,被进一步创作为动漫、小说等形式,扩展了游戏的IP世界,游戏成为“泛娱乐体验的一环”(36氪,2017)。2018年,“泛娱乐战略”被升级为“新文创战略”,“扮演起链接C端、B端与G端市场的重要角色”(刘俏,2021)。持续打造爆款IP的能力被认为是腾讯游戏的“护城河”(新浪财经,2020),同时游戏也是腾讯泛娱乐战略与IP的出发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IP成为打通原本相互独立的内容领域的重要力量,实现“影游联动”,产业边界“基于泛娱乐生态共融共生”(36氪,2017)。以王者荣耀为例,从游戏IP出发,通过吸引用户价值共创,打造《你是我的荣耀》的小说,并改编为电视剧,开发出IP衍生作品《代号:启程》和《代号:破晓》(GameLook, 2020a)。在这个过程中,腾讯吸引玩家和创新者参与IP打造,形成了文学、影视、动漫等多领域的互通,完成王者IP的更大布局。
最后,平台游戏是腾讯云、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工具最早的服务领域和调试之所,在虚拟现实的场景建设中,游戏脱离了娱乐产品的狭义定义,成为技术工具运转的背景与环境。自2007年起,腾讯就开始“尝试用云来服务游戏开发和运维”(赵宇新,2015),在2010年因为偷菜游戏认识到服务器的重要性,正式进军云计算领域(一点财经,2020)。2013年,腾讯云上线并“正式向互联网应用开发者全面开放”(严苛,2020),最初的“服务对象是围绕腾讯生态的游戏公司”(腾讯科技,2015),为合作伙伴提供技术资源、流量资源、产品资源等各种资源,推动游戏产业迅速发展。随着业务的发展,腾讯从游戏领域朝金融、文旅、安全等各个领域不断延伸,扩展产业版图。2020年5月,汤道生宣布腾讯在“未来五年将投入5000亿用于新基建的布局”(一点财经,2020),并重点关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事实上,游戏已经成为和前沿科技互相驱动、互相创造的“超级数字场景”,AR、VR和云游戏等技术“将迭代游戏的体验及生产方式”,并为游戏行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环球网,2022),游戏被认为是“AI最佳的研究场所”(GameLook, 2021),游戏技术对芯片、5G和XR这些互联网重要基础设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大约为14.9%、46.3%和71.6%(环球网,2022),在游戏领域深耕研发的技术在未来将有机会应用于各个行业与领域,成为平台基础设施的支撑和保障。
因此,腾讯游戏的个案刷新了我们对于平台基础设施化动力的理解:传统的平台研究认为,平台基础设施是平台数据库和网络,以及访问这些系统的网关、接口、工具和相关文档。而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平台基础设施为文化生产者提供了创造、分发、营销和文化产品货币化的经济和物质支持(Poell et al., 2021:52)。文化生产者需要让产品符合平台分发的技术标准,才能接入平台的基础设施功能,参与数据共享,来获取平台的技术支持和跨域推广(Bechmann, 2013)。但透过腾讯的个案,我们发现游戏的生产并非单向依赖于平台基础设施的分发,反而成为基础设施接口汇集、数据积累和技术操演的主要基础,反向推动基础设施化进程的成长。
四、内眷式基础设施的诞生:平台游戏与地缘鸿沟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在腾讯的个案中,游戏在文化资本、技术孵化和合作者培育等维度深入推进腾讯成为文化生产和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尤其当“游戏助推基础设施化”成为区别于大多数平台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一特征对该平台生态的成长有何影响?在本土市场,这首先体现为腾讯在流量与收入的比重中对游戏产业的高度依赖。如2021年,腾讯抢占了全国57.82%的流量与用户时长,其中游戏与衍生生态占比73.71%(刘道明,许孟婕,2021)。而在收入贡献上(见表1),自2010年起,游戏稳定占据着腾讯30%及以上的总收入比重,2012—2015年这一比重甚至超过50%。但是相应地,于国内扎根的平台游戏却面临着尖锐的地缘鸿沟:在轰轰烈烈的出海浪潮中,于国内热门的国风游戏面对着较大的文化折扣难题,销量明显受阻(曾培伦,邓又溪,2022)。同样据近年来的腾讯财报显示,从2018年Q3到2021年Q3,腾讯游戏的海外收入虽稳步增长,但增长较为缓慢,体量较为有限,其海外收入在游戏整体收入的占比一直未超过25%。
透过这一明显的地缘差距,我们发现平台文化生产与平台基础设施的融合程度越高,其自身的文化生产就越会对公司拥有的网络和系统产生路径依赖(Poell et al., 2021:58)。而对于腾讯而言,这一依托游戏的“平台基因”,让它的基础设施化进程呈现内眷化的特点,即腾讯的技术支持、生态支撑均依赖其在国内市场的基础,甚至其海外布局也是为了在国内市场获取更多的正当性。而在游戏产业的个案中,这一内眷化的特征具体有以下三个维度的体现:
首先,“内眷化”的基础设施体现为,游戏的海外拓展源于国内基础设施的支撑受阻,而非其主动的海外布局。比对腾讯的海外营收、历年公开信与国产游戏版号过审数量三则史料,我们发现在2010—2021年的10年中,2018年是腾讯自营游戏开始外拓的转折节点,但这一转折却根本上植根于国内游戏版号的停发。如表1所示,2018年我国停发游戏版号8个月,我国国产游戏版号从2017年的9177个锐减至2055个。但如表2所示,同样在2018年,腾讯大批量增加对海外游戏公司的投资和占股。于平台战略上,2018年腾讯面对游戏产业盈利能力的受阻,将其文化产业的“泛娱乐”更新为“新文创”。与单纯强调IP以游戏和文学符号打开对影视综行业的联动能力不同,新文创将IP的连接能力拓展至文化产业与旅游行业、传统制造业,通过延伸文化产品能够辐射的市场提高其基础设施化的价值(腾讯研究院,2018)。因此,审视2018年这一事件节点,腾讯的上述三项转型举措更多的是对2018年国内游戏产业发展受阻的临时回应,而并非系统组织的海外拓展。
其次,腾讯公开的话语结构之中,“内眷式基础设施”体现为平台的海外拓展被放置在继承文化传统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话语框架之下。而这一框架本质上仍是面对国内市场,有助于营造平台的企业形象,获得加深国内基础设施化的正当性。虽然在公开的演讲中腾讯多次强调了游戏在出海目标城市的本地化思维(GameLook, 2022a),并具体阐述了腾讯在海外发行中对海外用户的玩法、用户习惯、审美差异的探索(GameLook, 2020b)。但是所占篇幅更多的是,腾讯在介绍出海产品中会强调其承载着“故宫、敦煌”等传统文化元素(新华社客户端,2018),拥有人文、情感联结和本土文化认同(腾讯游戏,2019b;GameLook, 2020a)的功能,承担着推动中华文化底蕴走向海外的使命(竞核,2021)。游戏出海也与游戏的“技术能力”、“育人能力”(环球网,2022)一起构成腾讯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游戏出海被腾讯赋予了“国风出海”的特征,并非真正意在弥合不同地域市场中的文化差异,但这一策略却最直接地反哺了腾讯游戏在国内的市场形象,反而有助于游戏在国内的拓展。
最后,更重要的是,在平台的海外投资之上,“内眷化的基础设施”主要体现为平台的海外布局集中在孤立的产品与工作室出海,但并未涉及基础设施层面社交数据和用户积累的跨境支持。在海外游戏市场,以Google、苹果为代表的平台企业通过控制游戏上架应用商店、在Facebook等高频应用程序中打广告等形式控制游戏的跨区域市场分发(Steinberg, 2019;Nieborg, 2017)。其游戏产品的跨国传播依赖着相关平台的跨国流量补给,但是目前腾讯公开的海外布局主要包括与当地平台合作、建立海外研发工作室,在产品内容和形式上做本地化,尤其是在北美地区的多个工作室仍较多地停留在开发板块。其于2021年刚刚开设的海外发行品牌Level Infinite,本质上较多充当海内外游戏产品的市场连接器,但是缺乏系统的平台社交生态对自研游戏的支持和补充。同样,腾讯游戏的资深团队也曾提及游戏出海除了面对文化符号的本地化,其产品出口到东南亚部分信息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还要面对高清画质不适配该国网速与手机设备等多种挑战(GameLook, 2022b)。这都显示着,腾讯平台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在用户积累和算法布局上真正地植根海外,而是依旧依赖本国的平台生态开展主要业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游戏所面临的地缘鸿沟只是一个个案,在其背后我们发现内眷式基础设施的本质是自营游戏支撑的国内用户、数据和技术生态塑造了平台发展范式的路径依赖。尤其透过游戏产业的海外布局动力、话语结构和海外投资,平台更倾向于向内生长,而并未进行充分的海外扎根,这也相应地限制了平台生态之中的合作者与产品的海外拓展之路。
五、结论:“内眷”之后如何?
本研究以腾讯游戏的平台历史为个案,探索其与腾讯基础设施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与历史线索。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的平台巨头不同,自营游戏是腾讯平台基础设施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连接能力、IP积累和云技术孵化等维度,将腾讯塑造为技术联通与数字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但这也让腾讯的基础设施化模式呈现出高度内眷的特征,因而带来鲜明的地缘鸿沟:当平台试图跨越地缘,腾讯在游戏产业的出海动力、布局结构与话语符号的背后呈现出对国内游戏市场收入、技术与生态的高度依赖。这让腾讯的基础设施化并非真正依托于社交、数据的海外扎根,而仍是从国内出发,以面向国内市场为旨归。在这样的背景下,“内眷生长”虽是平台游戏发展的联结动力,却也是平台地缘影响的局限所在。
对于“内眷式”基础设施的反思不应止于游戏产业,在腾讯的个案中“泛娱乐”与“新文创”早已通过IP将文化产业内部的细分行业连接在一起,“游戏出海”也与“国漫出海”、“影视剧出海”共享共同的平台历史基础。本文试图通过以平台游戏为个案,探索平台基础设施与地缘关系的理论联系,尤其试图剥离传统对于平台基础设施研究的内向视角,认为其只是局限于某一封闭市场或是特定区域的经济主体。平台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是因为其通过提供技术工具、广告服务、协助文化产品的分发和货币化而取代了原有传统文化生产基础设施的职能(Poell et al., 2021:75)。而这一基础设施特性不仅根据国家与平台的不同而拥有地缘差异,更决定了平台如何在产品出口、团队出海、全球发行的基础上连接地缘关系。虽然腾讯依然通过腾讯云等渠道布局海外的基础设施配置,但我们所讨论的平台基础设施的影响力如何跨越地缘,本质上是讨论平台如何将自身的连接能力、用户共创的反哺能力拓展到海外,以此为基础更有利于文化产业扩张其在海外的影响力。
“内眷”之后如何?对于未来平台社会的成长而言,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一同展望。一方面,当平台对于国内的数据生态,尤其是某一单一产业在流量与收入上占据较大比重,在公共经济秩序层面是否会产生垄断的隐忧?同样,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过分依托于某一热门行业是否有利于企业内部业务多样性的生发?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平台生态拓展,抑或是文化价值的传播,海外影响力的诞生都源于是否有足够扎根的基础设施作为数据和用户体系的支撑。因此,伴随着平台跨越地缘,我们也应关注到平台基础设施是否一同有序成长,而这从根本上决定着平台能否实现以连接驱动创新的技术价值与社会使命。■
注释:
①国产网络游戏版号过审数量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统计而得;腾讯游戏营收和腾讯游戏营收占腾讯总营收比重来源于腾讯控股2010年至2022年的年度报告,前者为报告中的数据,后者根据报告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②参见21世纪商业评论(2022)。腾讯游戏,海外投了1000亿。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042896087494966&wfr=spider&for=pc。
参考文献:
21世纪商业评论(2022)。腾讯游戏,海外投了1000亿。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042896087494966&wfr=spider&for=pc。
36氪(2017)。腾讯程武:非常认同以游戏思维去解决社会问题,已开始布局“功能游戏”。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7193510612105809&wfr=spider&for=pc。
安虎森,郑文光(2016)。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内涵——地缘经济与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南京社会科学》,(04),5-14。
楚云帆(2023)。对话腾讯马晓轶:AI十字路口与游戏产业的未来。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kwVegJC6ju70PzjcDYHlDw。
邓剑(2022)。中国当代游戏史的思想谱系:从本土现代化到资本与市场逻辑。《探索与争鸣》,(02),163-176+180。
段世昌(2021)。从“寄生”到“共栖”——淘宝平台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新闻记者》,(07),86-96。
GameLook(2020a)。TGDC | 腾讯互娱刘星伦:从《王者荣耀》出发,用情感架设IP的桥梁。检索于http://www.gamelook.com.cn/2020/12/407268。
GameLook(2020b)。TGDC | 腾讯周嫚:海外市场发行的制胜法宝。检索于http://www.gamelook.com.cn/2020/12/406962。
GameLook(2021)。TGDC | 腾讯游戏AI研发中心总监付强:从绝艺到绝悟到开悟,AI技术助力科技向善。检索于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6A0DHPK00。
GameLook(2022a)。TGDC | 杨奇:回顾CoD Mobile海外实践,浅谈研发思维迭代。检索于http://www.gamelook.com.cn/2022/08/493372。
GameLook(2022b)。TGDC | 万维静、邹俊怡:手游海外发行洞察——东南亚和中东新兴市场的机遇与挑战。检索于http://www.gamelook.com.cn/2022/08/493740。
环球网(2022)。腾讯夏琳:激发游戏创新活力,助力产业可持续发展。检索于https://m.huanqiu.com/article/49FNLteor1p。
何威,曹书乐(2018)。从“电子海洛因”到“中国创造”:《人民日报》游戏报道(1981-2017)的话语变迁。《国际新闻界》,(05),57-81。
姬德强,朱泓宇(2021)。作为发展与治理话语的“基础设施”——基于2005—2020年的政策文本分析。《中国新闻传播研究》,(03),145-164。
竞核(2020)。腾讯夏琳:拥抱行业变革机遇,助力新一代游戏开发者。检索于http://www.coreesports.net/13617.html。
竞核(2021)。TGDC|腾讯夏琳:构建行业发展新势能,开拓游戏多元价值。检索于http://t.10jqka.com.cn/pid_187258437.shtml。
李敦瑞,李新(2009)。地缘经济学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01),42-48。
李梦颖(2022)。数字基础设施:隐藏在健康码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基于对内地31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码演化过程的可视化分析。《新闻记者》,(04),46-59。
李正,陈才,熊理然(2014)。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特征探析。《世界地理研究》,(01),10-18。
刘道明,许孟婕(2021)。【国金消费*数据】互联网月报:游戏行业政策影响几何?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DqUeKcMQhvvGgxNZY992Gw。
刘旷(2019)。产业赋能的十字路口,腾讯视频战略摊牌。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Vt8nZ1nxzlaO3sXe54Bgxw。
刘俏(2021)。拆解腾讯IP帝国:从“泛娱乐”到“新文创”的十年扩张。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PLDaAN10Yf-UBzWMn_u1Eg。
刘战伟(2022)。凸显什么?遮蔽什么?——作为隐喻的“平台”:连接、中介与基础设施。《新闻记者》,(06),54-66。
毛天婵,闻宇(2021)。十年开放?十年筑墙?——平台治理视角下腾讯平台开放史研究(2010-2020)。《新闻记者》,(06),28-38。
澎湃新闻(2020)。十年磨砺,生态终成巨头征战To B最大增长曲线。检索于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9178470。
孙萍,邱林川,于海青(2021)。平台作为方法:劳动、技术与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S1),8-24+126。
TechWeb(2020)。腾讯马晓轶:未来游戏产业也要做好自己的“新基建”。检索于https://www.chinaz.com/2020/0628/1150814.shtml?ivk_sa=1023197a。
腾讯控股(2016)。腾讯控股有限公司2015年报。检索于https://www.tencent.com/zh-cn/investors/financial-reports.html。
腾讯控股(2022)。腾讯控股有限公司2021年报。检索于https://www.tencent.com/zh-cn/investors/financial-reports.html。
腾讯开放平台(2014)。马化腾:开放加速 腾讯开放平台创业公司总估值超2000亿。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OuVUUathW1lHkjLoE8FkAA。
腾讯开放平台(2015)。马化腾:给合作伙伴的一封信。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uHNGWgrOAfVRWHqFsYYeQA。
腾讯开放平台(2016)。Pony给合作伙伴的一封信。检索于《2016互联网创新创业白皮书》。
腾讯开放平台(2017)。Pony给合作伙伴的一封信。检索于《2017互联网科技创新白皮书》。
腾讯科技(2013)。刘炽平:腾讯希望借助微信将开发者带“出海”。检索于http://people.techweb.com.cn/2013-07-03/1307223.shtml。
腾讯科技(2015)。BAT全球化系列之企鹅帝国。检索于https://xw.qq.com/tech/20151223007138/TEC2015122300713807。
腾讯游戏(2011)。腾讯游戏总裁任宇昕:打造优秀原创游戏品牌。检索于https://game.qq.com/webplat/info/11/791/1664/201101/90849.shtml。
腾讯游戏(2019a)。赋能人才与技术 腾讯游戏玩家创作联盟探索数字文创的多元未来。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eaFpdyA7XDFLy8W5cR7SqA。
腾讯游戏(2019b)。腾讯游戏副总裁刘铭:逐梦的路上看远方。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ybKdlS1bGPuwSEDwPfMxfg。
腾讯研究院(2018)。程武:新文创,实现更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和IP构建。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8hGLYbderttWB4cjseH0Vw。
腾讯游戏学堂(2020)。腾讯游戏学堂重磅发布:与清华、浙大达成合作;首推青年人才扶持计划。检索于https://gameinstitute.qq.com/news/detail/107。
新华社客户端(2018)。腾讯郭凯天:负起时代使命 开创全新未来。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721032960825344&wfr=spider&for=pc。
新浪财经(2020)。腾讯游戏的护城河是什么?IP和游戏也是相互塑造的关系。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137732947404400&wfr=spider&for=pc。
新浪游戏(2015)。腾讯游戏副总裁蔡欣产业年会发言致辞。检索于http://games.sina.com.cn/y/n/2015-12-15/fxmpnuk1527118.shtml。
严苛(2020)。腾讯云:蜕变的十年。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ynyyi9xoGxr_Sk5yVQNpAA。
一点财经(2020)。浮潜十年,腾讯云起。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plMTUDLzGqhaEihf-5h5LA。
赵宇新(2015)。腾讯游戏云的领先之道精于游戏,更懂游戏——专访腾讯副总裁邱跃鹏。《互联网周刊》,(08),30-31。
朱春阳,毛天婵(2022)。数字内容生产平台化进程中的创新网络治理现代化研究——以IP为关系协调枢纽的考察。《学术论坛》,(03),123-132。
曾培伦,邓又溪(2022)。从“传播载体”到“创新主体”:论中国游戏“走出去”的范式创新。《新闻大学》,(05),94-104。
BechmannA. (2013). Internet profiling: The economy of data intraoperability on Facebook and Google. Mediekultur: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55)72-91.
ChanC. (2016July 24). Money as message: How WeChat got users to adopt payments as a way to grow its network. Retrieved from http://a16z. com/2016/07/24/money-asmessage/.
de Reuver, M.Sorensen C.& Basole R. C. (2018). The digital platform: a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3(2)124-135.
Gillespie, T. (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12(3)347-364.
HarwitE. (2017). WeChat: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dominant messaging app.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0(3)312-327.
Helmond, A. (2015). The 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 Making Web Data Platform Ready. Social Media + Society1(2)1-11.
Helmond, A.Nieborg D. B.& van der Vlist F. N. (2019). Facebook’s evolution: development of a platform-as-infrastructure. Internet Histories3(2)123-146.
Helmond, A.& van der Vlist F. N. (2019). Social media and platform historiograph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mg-Journal for Media History22(1)6-34.
HongY.& Harwit E. (2020). China’s globalizing internet: historypowerand governance Introduc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3(1)1-7.
Jia, L.NieborgD. B.& PoellT. (2022). On super apps and app stores: digital media logics in China’s app economy. MediaCulture & Society44(8)1437-1453.
Johnson, M. R.& Woodcock J. (2019). The impacts of live streaming and Twitch. tv o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Media Culture & Society41(5)670-688.
KerrA. (2017). Global games: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policy in the networked era. New York: Routledge.
Nieborg, D. B. (2015). Crushing Candy: The Free-to-Play Game in Its Connective Commodity Form. Social Media + Society1(2)1-12.
Nieborg, D. B. (2017). Free-to-play games and app advertising: The rise of the player commodity. In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studies of advertisinged. by Hamilton, J. F.BodleR.& KorinE.38-51. New York: Routledge.
Plantin, J. C. (2018). Digital traces in context| google maps as cartographic infrastructure: From participatory mapmaking to database mainte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489-506.
Plantin, J. C.Lagoze, C.EdwardsP. N.& Sandvig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20(1)293-310.
Poell, T.Nieborg D. B.& Duffy B. E. (2021). Platform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Qiu, J. L.Yu P. K.& Oreglia E. (2022). A new approach to the geopolitics of Chinese internet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5(16)2335-2341.
Steinberg, M. (2019). The platform economy: How Japan transformed the consumer intern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angM. (2020). Huawei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The Geopolitics of Exterritorial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44556-4577.
Van DijckJ. (2021). See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Visualizing platformiz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New Media & Society23(9)2801-2819.
Van DijckJ.Poell T.&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ila Seoane, M. F. (2020). Alibaba’s discourse for the digital Silk Road: the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3(1)68-83.
毛天婵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闻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沟通与共识构建的中国路径研究”(22&ZD3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