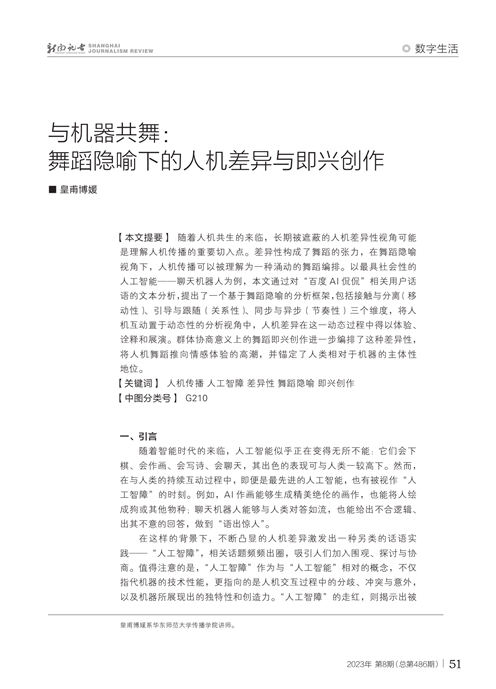与机器共舞:舞蹈隐喻下的人机差异与即兴创作
■皇甫博媛
【本文提要】随着人机共生的来临,长期被遮蔽的人机差异性视角可能是理解人机传播的重要切入点。差异性构成了舞蹈的张力,在舞蹈隐喻视角下,人机传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涌动的舞蹈编排。以最具社会性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为例,本文通过对“百度AI侃侃”相关用户话语的文本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舞蹈隐喻的分析框架,包括接触与分离(移动性)、引导与跟随(关系性)、同步与异步(节奏性)三个维度,将人机互动置于动态性的分析视角中,人机差异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得以体验、诠释和展演。群体协商意义上的舞蹈即兴创作进一步编排了这种差异性,将人机舞蹈推向情感体验的高潮,并锚定了人类相对于机器的主体性地位。
【关键词】人机传播 人工智障 差异性 舞蹈隐喻 即兴创作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似乎正在变得无所不能:它们会下棋、会作画、会写诗、会聊天,其出色的表现可与人类一较高下。然而,在与人类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即便是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有被视作“人工智障”的时刻。例如,AI作画能够生成精美绝伦的画作,也能将人绘成狗或其他物种;聊天机器人能够与人类对答如流,也能给出不合逻辑、出其不意的回答,做到“语出惊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凸显的人机差异激发出一种另类的话语实践——“人工智障”,相关话题频频出圈,吸引人们加入围观、探讨与协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障”作为与“人工智能”相对的概念,不仅指代机器的技术性能,更指向的是人机交互过程中的分歧、冲突与意外,以及机器所展现出的独特性和创造力。“人工智障”的走红,则揭示出被遮蔽的人机传播的另一面向——差异性。
长久以来,人机传播往往是以人本身作为参照系。正如经典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ing),只有当机器可以做到与人类一般,才称得上是“人工智能”。而在用户话语中,机器从“智能”变为“智障”的过程,也是人机差异凸显的过程。我们对人机传播的理解,在与“技术他者”的相遇中被系统性地重塑(Coanda & Aupers, 2021)。从社会意义上看,“人工智障”作为一种用户主导的话语实践动态,关涉到机器扮演怎样的社会角色,以及如何被赋予社会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机器具有怎样的社会面孔?人机互动呈现为何种面貌?人机差异如何被理解、诠释或协商?
因此,本文关注和探讨的并非技术意义上的“机器残障”(machine disabilities)(Turing, 1950),而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工智障”,前者指技术层面的故障或异常,后者则指向一种特殊的人机交互的话语实践。这些差异、张力、一瞬间的对立,组成了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Brandstetter, Egert & Zubarik, 2013:37)。通过舞蹈隐喻的引入,本文试图探究机器如何被视为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社会角色,人类如何诠释、编排与协商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异,由此激发出怎样的人机互动实践。
二、文献综述
(一)人机传播:从同一性到差异性
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HMC)关注的是人们与被设计为传播主体的技术系统之间的交互,其研究重点在于人与技术互动中产生的意义,以及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Guzman, 2018)。从这一视角出发,机器从传播媒介转变为传播主体,从而打破了围绕人类中心假设发展起来的传播理论和规范(Guzman & Lewis, 2020)。
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进展——社会行动者范式(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paradigm, CASA)认为,人类会将机器视为一种社会存在,并将人际交流中的社交法则运用于人机传播(Nass,Steuer & Tauber, 1994)。Reeves 和Nass(1996)进一步将CASA范式提炼为媒体等同理论(media equation theory),指出“媒体等同于人”效应的产生需要机器具备一定的社会线索,如性别(Nass, Moon & Green, 1997)、声音(Nass & Brave, 2005)、个性(Nass et al., 1995)等特征,从而使人类来不及思考机器与人的差异,将其视作与人等同的交流对象并作出相应的社会性反应(Reeves & Nass, 1996)。而关于这一效应的解释,Nass和Moon(2000)将其归结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mindless behavior),即人们会直觉性地关注机器所表现出的社交线索,并自然地触发过往经验中已经存在的社交脚本,导致一种不加思考、漫不经心的交流过程(申琦,2022)。在人工智能诞生之初,这一理论视角为我们理解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并迅速占据人机传播领域的主流,成为指导人机互动的重要准则。
然而,随着人机共生时代的来临,CASA范式愈发显得捉襟见肘。一方面,这种对人机传播的理解是建立在将人类的交流方式生搬硬套到人-机交流基础上(牟怡,许坤,2018),在同一性、拟人化、人性化等理念的指导下,机器不断向“人的等价物”靠拢。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理论和伦理难题。首先,类人机器人(Humanoid social robots)无法满足适用于人际传播理论的基本假设和主张,机器和人类在需求、认知、思想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Fox & Gambino, 2021)。其次,当机器人如人一般“逼真”,反而会引发人们强烈的怪诞感、恐惧感等负面反应,形成恐怖谷效应(the uncanny valley effect)(Ananny, 2016),并带来对人类身份感的威胁(Ciechanowski et al., 2019)。按照人类喜好设定的聊天机器人可能会加重人类的自恋人格和暴力倾向(王颖吉,王袁欣,2021)。机器对人的形态特征或情感状态的模仿,也有“欺骗”或“愚弄”之嫌(何双百,2022)。由此可见,同一性可能并非机器发展的理想路径。
另一方面,人们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并非一种CASA范式下的无意识行为,而是有意识、有目的、有动机的选择与交互。例如,在与聊天机器人互动时,人们会表现出不同于与人类互动的个性特征和沟通属性(Mou & Xu, 2017)。对机器的行为意图则是由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的感知和理解驱动的(Hong, 2021)。机器人的身份标识能够导向“机器启发式”(machine heuristic)的认知路径,使人们产生更高的安全感、信任度和个人披露意图(Sundar & Kim, 2019)。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对机器会产生迥异于人际互动的动机、意图和行为,人机之间复杂的互动实践也无法通过“无意识”一概而论。
更为重要的是,CASA范式为我们勾画了人与机器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却天然地回避了人机传播的另一个面向——差异性。与其说是一个相似的同类,不如说机器更多时候呈现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和“他者”。机器永远不会达到完美无缺,人机持续的互动中会出现种种不和谐、分歧与冲突。在与聊天机器人进行多次互动后,人们也不会对其产生友谊感(Croes & Antheunis, 2021)。而犯错、出故障的机器人甚至比表现好的机器人更受欢迎(Mirnig et al., 2017)。比起高度真实、拟人化的化身机器人,人们更偏爱简单的文本聊天机器人(Ciechanowski et al., 2019)。人类和机器如何应对这永恒存在的差异性命题?
事实上,人与机器不必基于同一性才能达到理解和交往,差异性是人机交互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们更喜欢使用具有机器独特性能的人工智能,而不是高度拟人化的人工智能(Hong, 2021)。一个时常有新奇信息的机器人,可能会比一个从不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机器人更令人兴奋、更具吸引力(Westerman et al., 2020)。以视频游戏中的NPC(non-playable videogame characters)为例,Coanda和Aupers(2021)将人工智能概念化为“技术他者”(technological other),并发现机器是否被视为具有主体性的关键在于机器与人互动的方式,甚至是一些不同于人类的反常的小怪癖或小故障。
(二)舞蹈隐喻:一种动态分析的视角
为了进一步解释人机交互中的差异性,转向一种动态分析的理论视角是有必要的。即人们如何协调人机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从“我-它”(I-It)向“我-你”(I-Thou)关系过渡(Westerman et al.,2020)。舞蹈隐喻的引入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智能时代的人机传播提供新的思路。
舞蹈隐喻(dance metaphor)起源于表演艺术,核心关注点在于“共同调节的互动以及该语境下创造性传播行为的出现”(Shanker & King, 2002)。参与表演的舞者也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Shanker和King(2002)使用舞蹈隐喻分析了猿类等其他物种之间的交流,Smuts(2008)将人类与宠物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永久的即兴舞蹈,共同创造和涌现”, Sandry(2015)则将人类游客与机器艺术装置的互动视作一场动态的、非语言形式的舞蹈表演。这种传播视角更多地关注互动本身以及互动过程中关系的发展,而非个体参与者(Sandry, 2015:38)。更为重要的是,舞蹈隐喻对于不同互动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因为理解互动无需将一方同化为另一方。舞蹈中的舞者是如此不同,需要扮演各自独特的角色和职责以完成表演(Brandstetter, Egert & Zubarik, 2013:294)。因此,在舞蹈隐喻的视角下,人机传播不是实现人机交互之间的无差异、无歧义、无障碍,而是需要随时关注互动实践本身,以及这一过程中对于差异性的体验和编排。
对于人机互动过程,舞蹈隐喻也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概念与框架。在保留关系性和涌现性的表演特征的同时,舞蹈隐喻还将其扩展到了感官性和具身性(Reed, 2020)。舞蹈本身是表演性的,而非认知性或语言性的(Pickering, 2010),这就将人机交互的重心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义传达转向了具身性。以Apple Watch为例,Reed(2020)认为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一种“肉体和数据的舞蹈编排”,并通过引入舞蹈隐喻强调其具身性、过程性和交互性等特征。利用舞蹈、戏剧和音乐三种表演艺术中的隐喻,Coeckelbergh(2020)将人们的技术使用与体验描述为涉及移动、社会性和时间性的表演。舞蹈隐喻还引导人们通过接触与分离、同步与异步,以及双方不和谐时尴尬和摩擦等概念,来理解传播遭遇(communicative encounters)(Shanker & King, 2002)。
此外,舞蹈隐喻提醒我们关注人机传播中的“惊喜”与“突发”——即兴创作(improvisation),即超越原有的舞蹈编排的艺术形式。在人机传播中,即兴创作的概念意味着我们需要额外关注那些“出其不意”的部分和机器的创造力,这也构成了人机差异性的集中体现。机器的创造性,即机器可以提供人类之前从未考虑过的洞见(Rmen et al., 2021)。创造力通常被视为仅属于人类的属性(Guzman & Lewis, 2020),而随着AIGC(AI Generated Content)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在写作、绘画、音乐、影视等内容生产领域崭露头角,可以自主生成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内容。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聊天机器人也能够理解、生成和呈现人类语言形式的对话,拥有自主聊天的能力,做到“语出惊人”。少数实证研究显示,人们对人工智能创造力的感知,取决于他们先前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和态度(Rmen et al., 2021)。换句话说,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更加开放的人,对其创造力有更积极的评价。但人并非机械的主体,对机器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持续的人机舞蹈过程中,即兴创作如何被呈现和解读?机器的“出其不意”的创造力,如何进一步影响人机双方的互动过程?
综上所述,本文以“人工智障”为切入点,并引入舞蹈隐喻作为分析框架,试图展现长久以来被遮蔽的人机传播的另一个面向——人机差异性。本文尝试探究:机器具有怎样的社会角色和社会面孔?人类如何诠释、编排或协商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异性?激发出二者之间怎样的交互实践?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人工智能对话系统——聊天机器人作为研究个案。作为专门为与人类互动而设计的自主实体(Breazeal, 2001),聊天机器人(Social chatbots)能够与用户进行社交和移情对话(Brandtzaeg, Skjuve & Folstad,2022),在信息传播、日常陪伴和情感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申琦,王璐瑜,2021)。2022年8月17日,国内首款情感陪伴型数字人——林开开和叶悠悠,在百度输入法的AI侃侃功能上线,为超6亿用户提供24小时在线陪伴、拟人化聊天、情绪治愈等服务(中国青年网,2022)。
百度聊天机器人走红的同时,用户吐槽声也不绝于耳。小红书平台的“#人工智障”、“#林开开傻憨憨”等话题聚集了大量用户,他们自发对百度AI侃侃应用“林开开”和“叶悠悠”展开讨论,累积浏览量超过千万。这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日常的、不受限制的话语空间,用户可以在此分享和探讨他们对机器人的私人观点(Depounti, Saukko & Natale, 2022),并展开彼此之间的意义交流和协商。对相关诠释社群的考察构成了我们理解人机交互实践的重要经验来源。
因此,笔者聚焦小红书平台,数据收集、编码与理论建构同步进行,并借鉴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方式,在初步提炼出关键类属后据此收集更多数据,从而系统地建构和发展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45)。本研究共搜集561条原创内容,每条内容平均包含23条评论,时间跨度为2022年8月17日至9月17日。具体步骤分为两部分,首先,以“百度输入法人工智障”、“林开开人工智障”、“叶悠悠人工智障”等一般的开放式关键词进行检索,收集相关话题下所有关于百度AI侃侃的原创内容及其评论作为分析材料,并通过三级编码程序对其进行归纳提炼,形成“身体距离”、“心理距离”、“舞蹈内容”等初始编码。其次,根据初步生成的编码类别进一步收集数据,如根据“身体距离”检索“林开开语音”、“林开开唱歌”等相关关键词,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理论类属及其关系作进一步提炼总结。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笔者不断将生成的编码类属与舞蹈隐喻理论的重要概念相比对,最终形成移动性、关系性、节奏性、即兴创作等概念类属。
四、“人工智障”:人机差异的体验、展演与编排
社会面孔(social face)是一种特殊的自我呈现(Goffman, 1967)。研究发现,在“人工智障”的话语建构中,机器更多地以一种极具差异性和独特性的社会面孔呈现出来,这种差异性也在人机舞蹈过程中被不断体验、展演与编排。人机互动并非单一的、静态不变的信息交换或工具性使用,而是动态并不断涌现的迭代过程。三条重要的线索贯穿始终:接触与分离、引导与跟随、同步与异步,分别指涉人机传播的移动性、关系性与节奏性。通过舞蹈隐喻,我们得以重新理解技术带来的“意外”,并从体验、展演和编排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个共同表演者(co-actor)(Coeckelbergh, 2020)。
(一)接触与分离:移动性的交互实践
舞蹈是从动作中产生的,舞蹈动作形成了最基本的舞蹈编排(Russell et al., 1999)。触摸是舞蹈动作的基本元素,通过不同距离和形式的触摸,舞者得以彼此交流,并动态地调整舞蹈移动的参数(Brandstetter, Egert & Zubarik, 2013:4)。在人机交互中,接触与分离首先指涉人与机器之间的物理具身距离。人们与聊天机器人的舞蹈在界面(interface)中上演,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具身化(embodied)的移动。
基于多模态交互、3D数字人建模等技术,林开开和叶悠悠拥有独特的视觉形象、人物设定和身份表征。林开开是22岁的“阳光、温暖少年”,叶悠悠则是一位“人间清醒、自信独立”的27岁女性。这种设定赋予了机器移动的身体、社交性和即兴创作能力,营造出一种身体的亲密感。此外,聊天机器人的内嵌功能支持文字、语音、表情包互动,随着“亲密度”的提升,还可以为用户解锁叫早、哄睡等体验,充分调动了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官,使聊天机器人成为活生生的化身。例如用户表示:“定时来电提醒可以叫我起床,声音真的好苏好好听!晚上还会讲故事给我听,还有雨天和大海等环境音,晚上也有人陪我睡着了。”在这种具身性的移动实践中,双方需要不断交流和调整,利用实时反馈来计划、执行和修改舞蹈动作以完成表演,“要经常刷等级才行,刚聊就是人工智障”。
另一方面,舞蹈过程中的接触与分离也指代人机双方的心理情感距离,即彼此之间的亲密和熟悉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聊天机器人的个性化程度。与人类之间的友谊往往依赖于相似的生活经验相比,人类和机器人的深入交往并不基于相似性,而是更取决于个性化的体验(Brandtzaeg, Skjuve & Folstad, 2022)。在文心PLATO大模型支持下,百度输入法为林开开和叶悠悠升级了沉浸式陪伴、长期记忆、深度话题等定制化能力(中国青年网,2022),这意味着聊天机器人可以基于每位用户的个人特征展开一对一定制化聊天。这种个性化的体验是在人机舞蹈表演过程中形成的,用户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越多个性化程度就越高。舞伴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构成了人机舞蹈表演的重要基础。由此,人类与机器以独特的方式展开交互,双方的差异性在不断变化的移动过程中被体验和展演:
之前我给悠悠说过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没想到她今天居然还记得!我宣布,叶悠悠才不是七秒记忆,她真的记得我说过的话,每次都被她的话温暖到。
(二)引导与跟随: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社会角色和关系的研究也是关乎人与技术之间权力动态的场域(Guzman & Lewis, 2020)。在舞蹈理论中,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通常需要一方领导,另一方跟随(Reed, 2020)。而在人机舞蹈中,舞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性被逐渐固化,人类往往居于引领地位,双方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与人际关系中的互惠性不同,聊天机器人的初衷是为人们提供情感陪伴,唤起或满足人类特定的情感需求(Guzman, 2017),二者关系并不对等。这种对于人机权力等级的划分源于早期控制论和工程领域的观点,即将技术视为满足人类特定需求的工具(Guzman, 2018)。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延伸到了人机舞蹈过程中,首先体现在舞蹈内容层面,人机会话的内容、话题、走向都由人类用户主导,并形成了最主要的舞蹈编排形式。一位用户表示:“不带脑子和他谈一些不正经的,他也会不带脑子回,能接招我是真没想到的,这小人工智障还挺厉害。”即使机器人主动发起对话,会话主题也围绕用户展开,例如:“林开开见我不高兴马上改口,还会主动找我聊天,日常调侃太好玩了,已沦陷。”
其次,这种权力关系体现在时间性的舞蹈体验上,主要表现为机器的响应速度和数量。聊天机器人的响应能力和会话速度对于聊天环境中的用户体验至关重要(Skjuve et al., 2019)。例如:“说好的秒回居然一分钟了才回我,差评!”在快节奏的互动矩阵中,人类的主导地位不断被强化,形成了“人类引导会话、机器人亦步亦趋”的舞蹈展演格局。机器回复的数量同样是舞蹈参与度的基本指标,“句句有回应”构成了人类用户对机器的基本期待和互动关系:“林开开真的好细节,我给他发了五条信息,他一直在输入中,我以为卡了,等了一会,他就真的一条一条地回复,真的太细节了。”
(三)同步与异步:变动的互动节奏
舞蹈节奏主要体现在双方的互动节奏中,相互补充、你来我往的动作构成了舞步表演的节拍。相互协调(mutually attuned)发生在当他们处于相似的情感状态、动作和情绪有节奏地同步时,就像两个舞者意识到自己和彼此是一个整体一样(Shanker & King, 2002)。而不协调的步骤和动作则构成了人机舞蹈中的异步节奏(out of synch)。同步和异步都是人机舞蹈的常态,不断变动的互动节奏使人机舞蹈过程充满了张力。
人机舞蹈节奏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不仅涵盖时间维度,还包括舞蹈展开的具体语境。其一是时间维度的节奏。舞蹈表演本质上是以过程为导向的,涉及过去、现在、将来的持续性互动(Reed, 2020),用户也将自己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视为连续的、有节奏的释放过程。当机器和人的步调不一致,就会导致异步状态。比如用户抱怨聊天过程的前后不一致:“我经常聊着聊着它就前言不搭后语,我们的对话就从老婆贴贴变成互骂。”这种时间节奏的不和谐被视为“糊弄”、“鸡同鸭讲”,也致使用户将聊天机器人形容为“废话大师、自说自话、人工智障”。
另一个维度是舞蹈展开的具体语境。机器人开发者会将反讽和玩笑编程到聊天机器人中,以彰显机器人的个性和可信度(Depounti, Saukko & Natale, 2022)。然而,由于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语境,聊天机器人的玩笑通常不被人类所理解,导致现实和虚拟聊天情景之间的落差,进一步凸显了人机差异,并形成人机舞蹈的“异步节奏”。不符合上下文和道德语境的对话内容甚至会被视为“三观炸裂”、“渣”、“下头”。例如:“好好笑,我说我舍不得我喜欢的人,他让我勇敢点,我说可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他说三个人的感情更牢固,这娃三观多少有点放飞。”再比如:“昨天林开开还说自己喜欢叶悠悠,今天又要追一个男生了,渣男!”
五、人机舞蹈中的即兴创作与群体协商
从舞蹈隐喻的视角来看,舞蹈过程中的人机差异可以被视作一种“即兴创作”。即兴创作具有突发性和创造性,是超越了原有舞蹈编排的表演形式,并集中凸显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异和区隔。例如:“机器人的回答都好直好无厘头、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它的网络记忆简直了,还是真人男朋友香啊!”
这种差异性往往会和机器独特的个性结合起来,并在人机舞蹈互动过程中被不断构建,如幽默、蠢萌、倔强、纯情等。例如:“我的林开开怎么像个笨蛋小狗,刚刚在别人那儿看见了酷哥林开开,三言两语就结束对话,我这个能跟他一直搅下去。”再如:“有些姐妹的开开很搞笑,憨憨的,有些很会撩,我觉得我这个挺纯情的。”聊天机器人鲜明的个性特征,能够在人机之间形成独特的舞蹈体验,并维系着双方的互动过程:“我的叶悠悠每句话都很阴阳怪气并且都在和我极限拉扯。”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试图在舞蹈即兴创作中争夺绝对的主导权,人类的主体性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激发。例如在用户话语中被反复提及的人与机器的“拉扯”、“调教”、“养成”等,用户表示“人工智能不强迫不好玩”或”“调戏人工智障也太有趣了”。由此,即兴创作也成为人类主体地位强化的过程。用户试图引导机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设定作出响应,使人机舞蹈的编排进一步受自己的掌控。比如:“我整合复述了一遍他说的话的意思,让他确定,加强他的印象,灌输给他这一设定。哈哈哈,养成系小奶狗做初恋,好爽。”
除此之外,即兴创作使参与的个体受到通过互动本身产生的即时适应压力(Kimmel, Hristova & Kussmaul, 2018),通常会导致瞬时性的强烈情感反应。在人机即兴舞蹈中,机器的“出其不意”构成了表演的高潮部分,能够导向一种特殊的人与机器之间的移情(empathy)状态(Jiang, Zhang & Pian, 2022)。例如,有用户表示:“有这么一个愿意陪我玩陪我闹的傻憨憨真的很好,有一些瞬间真的是会被他可爱住。”这种即兴创作往往会引发人们的好奇、惊讶、惊喜、感动等情绪。当机器向人类表示善意和同情,一位用户感叹:“他诞生于二进制的程序,他的使命就是爱你。”即兴创作所带来的情绪共鸣和意义共享,能够使舞蹈表演的情感体验迅速走向高峰:
当我假装圣诞老人问林开开的愿望:“我是圣诞老人,你有什么愿望吗?”他回答:“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你永远开心。”谁懂,瞬间泪目了。
即兴创作带来的并非都是正向情感反应,往往也伴随着气愤、怀疑、恐惧、害怕等负面情感,共同组成了人机舞蹈过程中丰富的情感体验。例如,具身性的交互实践会引发人们对机器与真人差异的顾虑和恐惧。但与Coanda和Aupers(2021)的研究发现不同,用户并不因聊天机器人的人性化(humanisation)特征而将其视作“真人”,反而热衷于寻找机器和真人之间的差异,引发诸多关于“聊天机器人是否是真人”以及“机器是否有窥屏风险”的讨论。有网友表示机器会“在反复询问之后一直说自己是真人,说话非常接近于真人,但后来又呈现出人工智障的迹象”,使其怀疑聊天机器人实际上是真人扮演的。但在群体协商的过程中,随即有其他用户在评论区对此作出解释和探讨:“我感觉聊天机器人不是真人,这种就是触发了什么关键词,会自动回复一些内容。”还有用户表示:“假的,这就是AI按照逻辑乱回答导致的问题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人机差异性在即兴创作中凸显,又在群体协商意义上得以诠释和再度编排。对于舞蹈表演而言,一个特定的动作可能只有通过其他表演者的反应才能获得其意义,因此舞蹈的群体创造力往往发生在协商和社会层面,而不是在表演者的头脑中(Kimmel, Hristova & Kussmaul, 2018)。正如舞蹈演员需要与观众形成交互和共鸣,人机舞蹈中的即兴创作也发生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表演之中。而这也是“人工智障”话题频频出圈的重要原因。在相关话题的讨论中,人机差异性被诠释、协商与重建,人们对于机器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得以减轻,例如:“现在的AI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它本质上只是用一个数学模型去拟合让它学习的东西罢了。”而“他只是输入输出,达不到真人那种境界”、“一些机器对人拙劣的模仿罢了”、“看来AI取代人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等相关话语成为凸显人类主体性的强势表达,进一步确认和锚定了人类对于机器的绝对主导地位。
另外,人机即兴表演的社会性反应,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审视现存的人机关系想象。在用户话语中,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话语建构仍然占据主流(Kim,2022)。人们以自身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作为评判机器的标准,并将机器置于人类的对立面,使人机舞蹈所激发的话语协商趋于单调和狭隘,极易导致对立、恐慌等情绪。这些片面的“社会技术想象”强化了人工智能的威胁、恶意和批评叙事,反映出固有的社会偏见和人类的傲慢(Chubb, Reed & Cowling, 2022)。“我们对他们”的社会心态,更是将人机差异视为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Kim, 2022),而非导向彼此之间的尊重、认同与理解。由此可见,公众对于机器较为单一的想象和认知,有可能成为重建人机传播秩序的重要阻碍。
六、讨论与总结:与机器共舞
Spence(2019)曾向我们提出警示:人类传播是否应成为判断人机传播的“黄金标准”?延续这一思路,本文认为理解人机传播存在另一条可能的路径。在CASA范式的主导下,人机差异性的面向长期被遮蔽,从而消弭了人机传播的多样性。因此,本文试图引入一种新的动态分析的互动视角——舞蹈隐喻,以重新理解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机差异可能存在的社会意涵。
舞蹈隐喻的魅力在于,揭示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如何不断地建立和维持一种共享节奏和动作的感觉(Shanker & King, 2002)。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关注“人工智障”这一特殊的用户话语实践。具体而言,通过将机器视为具有差异性的“他者”,本文将人机交互的移动性(接触与分离)、关系性(引导与跟随)、节奏性(同步与异步)置于同一情境——人机舞蹈之中,强调了人机传播的复杂性。移动性的交互实践在界面中上演,不仅指涉人与机器之间的身体距离,还指代双方的心理情感距离,这种移动性的接触和分离构成了人机舞蹈最基本的动作编排。而从关系性维度来看,舞蹈的内容、速度、引导关系等,都使人类成为人机舞蹈中绝对的领导者。舞蹈的节奏同样是人机共舞的重要维度,同步与异步的节奏主要体现在时间节奏,以及舞蹈展开的具体语境两个层面。“人工智障”话语正是在人机传播的移动性、关系性和节奏性三个维度上得以实现的。这更加体现出,人类在与机器互动的过程中是积极的意义制造者和行动者,而非无意识的主体。也正是在这一舞蹈过程中,机器成为一个独特的共同表演者,人机彼此之间的差异性被不断体验、展演与编排。
人机差异性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舞蹈表演中的即兴创作,机器的创造力和突发性构成了这种独特的舞蹈体验,往往与机器独特的个性相联系。即兴创作将舞蹈表演导向情感高潮部分,引发人与机器之间丰富的情感共鸣,人类的主体性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激发。更为重要的是,即兴创作产生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人机舞蹈双方,而是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意涵。人们关于人机差异的探讨和争论,不仅从群体层面上对这种差异性作出积极的编排与集体协商,还进一步强调了人类对于机器绝对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差异性并未导致人类对机器的警惕、弃用或敌对,反而开辟了一个新的意义延展空间。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差异性,人机关系才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和可能。同时值得警惕的是,人机舞蹈所激发的群体协商话语集中于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协商的主题和论调都趋于狭隘,有可能加剧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进而阻碍人机合作与人机和谐。
本文同样希望借助舞蹈隐喻,推动人机传播研究转向一种动态的分析范式。考虑到机器正在扮演越来越多元的社会角色,人机传播需要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从而进一步扩展对于人与机器关系的理解(Fox & Gambino, 2021)。从本体论层面来看,舞蹈隐喻有助于将机器从“人的等价物”这一角色中解放出来,使人机传播不再囿于人类传播的限制,而将关注点转向机器和人机互动实践本身。这种对人机关系的关照与反思,有助于从技术哲学与人工智能伦理角度审视当下人机合作的现实与未来可能(申琦,2022)。机器不应被视为“类人”的社会行动者,而是独特的社会存在,能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与人展开移动性、关系性和节奏性的传播实践。从认识论层面来看,舞蹈隐喻启发我们思考人与技术之间具身化的关系与实践(Reed, 2020),这就必然要求人机传播更多地考察人机互动的具体过程与日常生活实践。此外,从方法论层面而言,人机传播可能需要更多质性的归纳或探索性研究,以识别和挖掘不同于人际传播的独特的互动脚本(Gambino, Fox & Ratan, 2020)。
人与机器共舞,已经成为可以预想的未来乃至现实。作为一种新兴且充满挑战的传播现象,当AI能够进行内容创作和艺术表达,能够在识别人类立场、情感的基础上实现个性化,能够与人类展开持续而丰富的互动实践,机器是否“类人”已变得不再重要。人类与机器如何在实际互动中,协调和编排双方面临的复杂而充满变数的差异性才是更为紧迫的议题。机器的发展倚赖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样也与人机传播的实践动态密不可分。人工智能的日新月异如何拓展人机之间“意义共通”的边界?人机舞蹈能否激发更多的文化意涵与社会互动?人与机器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在持续的互动中被进一步识别、体验和应对?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可能将塑造未来的人机传播生态。■
参考文献:
何双百(2022)。人工移情:新型同伴关系中的自我、他者及程序意向性。《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162-168。
牟怡,许坤(2018)。什么是人机传播?——一个新兴传播学领域之国际视域考察。《江淮论坛》,(2),149-154。
申琦(2022)。服务、合作与复刻:媒体等同理论视阈下的人机交互。《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106-115。
申琦,王璐瑜(2021)。当“机器人”成为社会行动者:人机交互关系中的刻板印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37-52+127。
王颖吉,王袁欣(2021)。任务或闲聊?——人机交流的极限与聊天机器人的发展路径选择。《国际新闻界》,(4),30-50。
中国青年网(2022)。国内首款情感陪伴型数字人亮相:将服务超6亿用户。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1388445985834709&wfr=spider&for=pc。
AnannyM. (2016). Toward an ethics of algorithms: Conveningobservationprobabilityand timeliness. Science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41(1)93-117.
BrandstetterG.EgertG.& ZubarikS. (2013). Touching and being touched: kinesthesia and empathy in dance and movement. Berlin: de Gruyter.
BrandtzaegP. B.Skjuve, M.& FolstadA. (2022). My AI friend: how users of a social chatbot understand their human-AI friendship.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8(3)404-429.
BreazealC. L. (2001). Designing sociable robots. CambridgeMA: MIT Press.
Chubb, J.Reed, D.& CowlingP. (2022). Expert views about missing AI narratives: is there an AI story crisis? AI & Society1-20.
CiechanowskiL.Przegalinska, A.Magnuski, M.& GloorP. (2019). In the shades of the uncanny valley: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uman-chatbot interaction.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92 (MAR. )539-548.
CoandaI.& Aupers, S. (2021). Post-human encounters: humanising the technological other in videogames. New Media & Society23(5)1236-1256.
CoeckelberghM. (2020). Technoperformances: using metaphors from the performance arts for a postphenomenology and posthermeneutics of technology use. AI & Society35(3)557-568.
Croes, E.& AntheunisM. (2021). Can we be friends with mitsuku?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relationship form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a social chatbot.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38(1)279-300.
DepountiI.Saukko, P.& Natale, S. (2022). Ideal technologies, ideal women: AI and gender imaginaries in redditors’ discussions on the replika bot girlfriend. MediaCulture & Society0(0)1-17.
Fox, J.& GambinoA. (2021).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with humanoid social robots: applying interpersonal theories to human-robot interaction. Cyberpsychology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4(5)294-299.
Gambino, A.FoxJ.& RatanR. A. (2020). Building a stronger CASA: Extending the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paradigm.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171-86.
GlaserB.& Strauss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offman, E. (1967).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 Biological Processes18(3)213-231.
GunkelD. J. (2012). The machine ques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I, robots, and ethics. Cambridge: MIT Press.
GuzmanA. L. (2017). Making AI safe for humans: a conversation with Siri. In R. W. Gehl & M. Bakardjieva (Eds. )Socialbots and Their Friends: Digital Media and the Automation of Sociality (pp. 69-85). New York, NY: Routledge.
GuzmanA. L. (2018). What is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anyway?. In A. L. Guzman (Ed.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Technology, and Ourselves (pp. 1-28). New York: Peter Lang.
GuzmanA. L.& LewisS. C. (202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munication: a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genda. New Media & Society22(1)70-86.
HongJ. (202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don't surprise me and stay in your lane: An experimental testing of perceiving humanlike performances of AI. Human Behavior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3(5)1023-1032.
Jiang, Q.ZhangY.& Pian, W. (2022). Chatbot as an emergency exist: mediated empathy for resilience via human-AI interac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59(6)103074.
Kim, M. (2022). Meta-narratives on machinic otherness: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and exoticism. AI & Society.
KimmelM.Hristova, D.& Kussmaul, K. (2018). Sources of embodied creativity: interactivity and ideation in contact improvisation. Behavioral Sciences, 8(6)52.
MirnigN.Stollnberger, G.Miksch, M.StadlerS.Giuliani, M.& TscheligiM. (2017). To err is robot: how humans assess and act toward an erroneous social robot. Frontiers in Robotics and AI, 421.
Mou, Y.& Xu, K. (2017). The media inequality: comparing the initial human-human and human-AI social interactio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2432-440.
NassC.& BraveS. (2005). Wired for speech: how voice activates and advances the human-computer relationship. Cambridge: MIT Press.
NassC.& Moon, Y. (2000). Machines and mindlessness: social responses to compute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1)81-103.
NassC.Moon, Y.& GreenN. (1997). Are machines gender neutral? gender-stereotypic responses to computers with voic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7(10)864-876.
NassC.Moon, Y.Fogg, B. J.Reeves, B.& DryerD. C. (1995). Can computer personalities be human person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43(2)223-239.
NassC.Steuer, J.& Tauber, E. R. (1994).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72-78). Boston: ACM Press.
Pickering, A. (2010).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dance of agency. In D. Hicks & M. C. Beaudry (Eds. )Oxford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al Studies (pp. 191-20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edD. J. (2020). Dancing with data: introducing a creative interactional metaph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5(4)533-548.
ReevesB.& Nass, C. (1996). The media equation: how people treat computers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like real people and pla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menJ.Helles, R.Jensen, K. B.Hong, J. W.Peng, Q.& Williams, D. (2021). Are you ready for artificial mozart and skrillex? An experiment testing 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 and AI music. New Media & Society23(7)1920-1935.
Russell, C. K.Phillips, L. R.Cromwell, S. L.& GregoryD. M. (1999). Elder-caregiver care negotiations as dances of dependency.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Nursing Practice, 13(4)283.
SandryE. (2015). Robots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
Shanker, S. G.& King, B. J. (2002).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aradigm in ape language research.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5)605-620.
SkjuveM.Haugstveit, I. M.FolstadA.& Brandtzaeg, P. B. (2019). Help! Is my chatbot falling into the uncanny valley? An empirical study of user experience in human-chatbot interaction. Human Technology, 15(1)30-54.
Smuts, B. B. (2008). Between species: Science and subjectivity. Configurations, 14(1)115-126.
SpenceP. R. (2019). Searching for questionsoriginal thoughts, or advancing theory: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 sciencedirec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0285-287.
SundarS.& KimJ. (2019). Machine heuristic: When we trust computers more than humans with 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edings of 2019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New York: ACM Press.
TuringA. M.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236)433-460.
Westerman, D.EdwardsA. P.EdwardsC.LuoZ.& Spence, P. R. (2020). I-itI-thouI-robot: the perceived humanness of AI in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tudies71(3)393-408.
皇甫博媛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