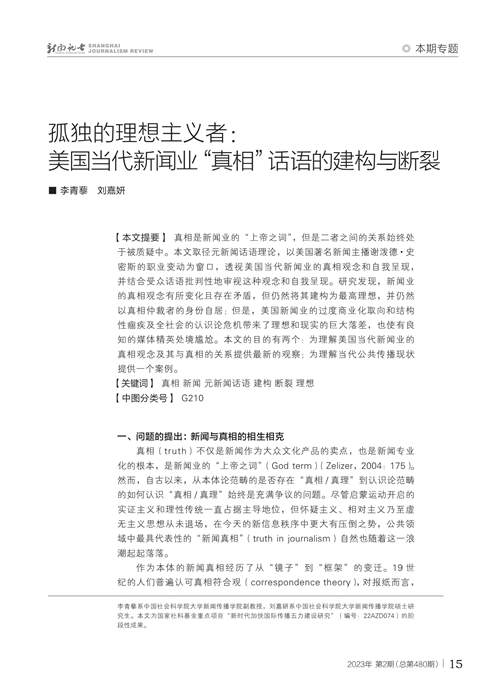孤独的理想主义者:美国当代新闻业“真相”话语的建构与断裂
■李青藜 刘嘉妍
【本文提要】真相是新闻业的“上帝之词”,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被质疑中。本文取径元新闻话语理论,以美国著名新闻主播谢泼德·史密斯的职业变动为窗口,透视美国当代新闻业的真相观念和自我呈现,并结合受众话语批判性地审视这种观念和自我呈现。研究发现,新闻业的真相观念有所变化且存在矛盾,但仍然将其建构为最高理想,并仍然以真相仲裁者的身份自居;但是,美国新闻业的过度商业化取向和结构性痼疾及全社会的认识论危机带来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也使有良知的媒体精英处境尴尬。本文的目的有两个:为理解美国当代新闻业的真相观念及其与真相的关系提供最新的观察;为理解当代公共传播现状提供一个案例。
【关键词】真相 新闻 元新闻话语 建构 断裂 理想
【中图分类号】G210
一、问题的提出:新闻与真相的相生相克
真相(truth)不仅是新闻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卖点,也是新闻专业化的根本,是新闻业的“上帝之词”(God term)(Zelizer, 2004:175)。然而,自古以来,从本体论范畴的是否存在“真相/真理”到认识论范畴的如何认识“真相/真理”始终是充满争议的问题。尽管启蒙运动开启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传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思想从未退场,在今天的新信息秩序中更大有压倒之势,公共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新闻真相”(truth in journalism)自然也随着这一浪潮起起落落。
作为本体的新闻真相经历了从“镜子”到“框架”的变迁。19世纪的人们普遍认可真相符合观(correspondence theory),对报纸而言,像科学家那样去描述事实,就等于反映了社会的真相(帕特森,威尔金斯,2014/2018:23)。那时,报纸常以“镜子”命名,意为新闻是现实的镜像(Zelizer, 2004:31)。进入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人们了解到,语言只是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而非世界本身,实用主义者则指出,真理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发明,是一个证实的过程,绝对真理只是一个理想,从而对启蒙运动的真相观提出了挑战。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公关业的兴起使人们切实了解到,事实可以受人摆布,真相可以被建构。在李普曼(1922/2006:256)充满洞见地指出新闻与真相并不能等同之后,新闻学的经典研究一再为此提供佐证,“镜子观”在学界随之消亡。如今,学者们普遍同意,存在论范畴的新闻真相是经过建构的,它是在各种影响因素制约下的“再现之真”(李玮,蒋晓丽,2018),是“相对于现有证据来说的最具可能性的陈述”(科瓦奇,罗森斯塔尔,2001/2014:34),在这个“陈述”中,必然存在陈述者的判断和阐释,“真相只可能是最接近于现实”(Lisboa & Benetti, 2015)。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新闻报道能否以及如何做到“真相真实”(杨保军,2008a)也相当模糊。杨保军(2008b)指出,“真实”是认识论范畴的概念,“事实”与“真相”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概念,所谓“新闻真实”即指“新闻作品( 报道) ”与“所报道对象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在“符合”困境带来的认识论危机中,西方新闻业的回应不是召唤一个更加主观、更重视叙事的新闻界,而是加倍专注于客观性,以提高他们作为专业的“真相仲裁者”(the arbiters of truth)的标准(Anderson, 2018),最终,客观性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代替真相成为新闻业的目标(Anderson & Schudson, 2019)。但是,客观性范式既无法解释新闻真相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其越来越机械的执行也与“符合”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学者们纷纷以不同的认识论赋予新闻真相以合法性。由于新闻报道的是日常的经验世界,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认识新闻真相,它是去伪存真的“过程真实”,是“有机真实”,同时伴随着“现象真实”、“本质真实”、“具体真实”、“整体真实”、“瞬间真实”、“无限真实”、“单一真相”、“语境真相”(科瓦奇,罗森斯塔尔,2001/2014;王辉,2012;王亦高,2015;虞鑫,2018;杨保军,2020)等复杂的理解和争议。特别是近20年来,由数字技术推动的公共领域为公共表达和多种多样的信仰社群提供了机会,以科学理性作为唯一合法模式来规范知识的现代工程崩溃,新闻和真相的概念不再是新闻工作者单方面决定的对现实的准确描述,而是一个集体过程(Hermida, 2012;Waisbord, 2018),是建立在“探究社群”的协商和共识之上的“复杂真相”、“对话真实”、“协商真实”(姜华,2022;杨奇光,周楚珺,2021),以及在受众中实现的“信任真实”、“见证真实”、“具身真实”(操瑞青,2017;杨保军,2017;金圣钧,2021;华维慧,2020),并被推向价值论层面。美国学者克里斯琴斯指出,作为新闻专业核心的真相不应局限于认识论,而是首先成为价值论的问题(Christians, 2007:209);王辰瑶(2021)也认为,“‘新闻真实’应当成为新闻业发展演化的价值罗盘”。
迄今的研究多从哲学层面和规范性视角出发,围绕“新闻”与“现实”之间的表征关系及其合法性加以探讨,却鲜有对新闻工作者自身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经验性研究。科瓦奇和罗森斯塔尔(2001/2014:42-47)访谈了大量新闻工作者,发现“‘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相负责’已经成为人们绝对一致的看法,但是人们对于‘真相’的含义却不甚了解”。两位作者并未进一步追问。李青藜(2021)对美国新闻业的一个热点事件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美国新闻社群对“真相”的认知以“事实”为基础,或强调“公开”,或强调“核实”,或采取怀疑主义态度,导致社群在实践和话语领域的双重分裂。既有文献数量极少,无法充分呈现从业者的视角,而从业者如何理解自己从事的工作、如何建构职业理念决定着他们的日常实践(Deuze, 2005),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究和提炼无疑能够扩大和丰富对新闻生产的认识,深入理解当下的公共传播现象。
二、个案与方法:透视美国当代主流新闻的真相观念
福柯(1972/1998)强调,话语既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又具有生成性的功能,生产各领域的科学知识,建构话语的主体、知识的对象乃至社会现实。新闻的日常工作就是话语实践,这些话语一方面反映和建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在反映和建构新闻本身的社会意义和角色。美国新闻学者芭比·泽利泽(Zelizer, 1993)将话语研究引入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的评估和讨论,她指出,新闻工作者通过对关键公共事件(key public events)或热点时刻(critical incidents)的集体阐释团结成为一个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这些事件并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在话语中赋予它们意义的个人和群体的投射。由此,新闻工作者选择热点时刻并运用话语加以阐释,从而勾连职业实践和新闻权威,并对原有的范式进行强调和修补,传播、挑战和协商实践边界。他们生产的这种共享话语便标志着他们如何将自身视为新闻工作者。卡尔森(Carlson, 2016)进一步提出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理论,即“评价新闻文本、新闻文本的生产实践或接受新闻文本的条件的公共表达,用于解释围绕新闻的意义是如何发展的”。该理论将行动者(actor)、场所/受众(site/audience)和主题(topic)与定义制定、边界工作和合法化的过程联系起来,将新闻置于一个不断围绕新闻及其更大的社会地位构建意义的话语领域中。
本文以元新闻话语理论为方法论,首先将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播小大卫·谢泼德·史密斯(David Shepard Smith Jr., 1964-)的离职和入职视为热点时刻(hot moments),深度考察不同行动者由此产生的话语文本。著名新闻人的离职、退休、逝世会触发大量言说,行动者通过评价人物的品质、地位、职业实践来重申、修正或挑战原有的职业理念与规范角色(Carlson, 2012;白红义,2014;陈楚洁,2015)。
史密斯在1996年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成立时即加入,先后担任突发新闻部门首席主播和执行编辑,其主持的下午3点档电视新闻节目在同时段节目中保持收视率第一。他经常公开纠正福克斯新闻台言论节目主持人的事实错误,2016年之后,他是该电视台中少数几个批评特朗普的资深记者之一,由此显得与该电视台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2018年,史密斯与福克斯签订了1500万美元年薪的合同,但合同未到期便于2019年10月突然离职,成为主流媒体关注的重大新闻。正如《福布斯》(Forbes)报道:“当所有主流媒体的突发新闻都是关于一位著名新闻主播的时候,你知道这对媒体来说不是寻常的一天。”一年后,史密斯加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CNBC)财经频道,担任首席新闻主播,主持每日晚间新闻节目《谢泼德·史密斯新闻》(The News with Shepard Smith),同样引发媒体热议。围绕史密斯的职业转换产生了大量话语文本,成为典型的“热点时刻”,为我们的深度观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窗口。
此外,迄今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将受众话语纳入研究视野。卡尔森(Carlson, 2016)指出,新闻是一组社会关系,新闻意义的建构需要新闻界内外不同角色的合作与协商,因此,在元新闻话语中,新闻人只是众多行动者中的一员,与其他行动者共同塑造了人们对新闻的理解,因此,本文同时考察受众生产的话语文本。
其次,本文将话语发生的场所设定为新闻场所,即公开发表于新闻媒体中的报道、评论和受众的公开评价,它们直接触达受众,是一种机构性话语(institutional discourse),即以职业背景和机构语境为主要依托的言语互动,它发生在机构场所或制度下,参与者具有特定的机构身份,同时受到机构规则制约,并带有明确的机构目标(郭佳,2015)。机构性话语是记者向公众传达其理想和信仰的一种方式(Ferrucci, 2021),同时,数字时代的受众并不是被动地观看,而是可以通过留言、评论参与“表演”,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不同行动者的话语交锋,这些内容都可以直接触达受众,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三,本文将研究主题限定为围绕“真相”观念的话语建构。对概念的理解是多元的,不同的理解决定了新闻实践的方式(Zelizer, 2004;Vos & Craft, 2017;Ferrucci & Taylor,2018;Powers, 2018),本文通过历时的互文性考察探寻话语的显在意义和潜在内涵,从而批判性地审视话语建构的目的和修辞策略。
史密斯的离职和入职声明均以“真相”为核心,并被广为引用,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经验性材料;对不同行动者在不同热点时刻的话语交锋和历时性考察则有助于在经验层面阐明一个主题的意义范围。藉此,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1.美国新闻业如何理解和公开阐释“真相”概念?
2.受众如何评价主流新闻业的这种话语建构?
3.如何理解主流新闻业的话语建构与断裂?
本文在谷歌新闻(Google News)平台上,以Shepard Smith为关键词,基于三个节点时间——史密斯宣布离职、宣布加入CNBC、节目开播——收集了来自新闻场所的不同行动者的话语文本,包括媒体报道、评论和受众的跟帖。①我们首先通过“语义场”理论,②考察“最小语义场”——围绕“truth”节点词,从词汇、词汇搭配、语法(即分句,或简单句)进行分析,了解媒体话语建构了何种真相观念。其次考察“篇章”,将句子与文本的其他部分相结合,以呈现概念界定、使用、形塑的方式,并据此生成了怎样的知识对象体系和关系。第三,考察“互文性”,对文本进行反复细读,经过多次阐释性循环,理解文本的内容;之后采取归纳法进行开放式主题编码和主题总结(库卡茨,2014/2017:15-20),并再次阅读,对主题进行修正,在共时与历时的维度上呈现主题的特点与变化;最后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研究文本中显性内容的存在和隐性内容的缺失,以回答研究问题。
对主题进行归纳和分析发现,美国主流新闻业在每个时间节点的话语实践都呈现出高度同质性,表现出的戏剧化转变也完全一致。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用“赞美”与“反抗”来命名其主题;在第二、三阶段,用“忽视”与“无奈”进行命名。与此同时,受众评论呈现出多元观点,且与媒体的话语建构并不一致。我们以此为参照,深入探讨社会成员对真相的认知以及真相与新闻、真相与社会的关系。
三、事实与观点:真相观念的坚守与变迁
在全部56篇媒体报道中,“真相”一词共出现84次。剔除无关内容,共出现75次,集中于史密斯的离职、入职时的个人声明及对其的广泛引用之中。媒体对史密斯的评价高度一致,均是正面、积极的,引用史密斯声明就是一次次的背书。尽管所有文本都没有对真相进行概念化阐释,但通过语义分析即可发现话语生成的意义。
1.作为本体的真相:事实与观点
2019年10月11日,史密斯在节目结束前突然宣布了离职决定,引爆媒体圈。所有报道此事的媒体都引用了史密斯告别词中的最后一句话:“即便是在我们当下两极分化的国家里,我仍然希望事实获胜。真相永远重要。新闻和新闻工作者将蓬勃发展(That the truth will always matter. That journalism and journalists will thrive)。”多数媒体还同时引用了另外一句话:“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写了一份历史的初稿,并努力将它传递给你们,同时在语境中和视角下,不带恐惧或偏好地向当权者说出真相(while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without fear or favor, in context and with perspective)。”
2020年7月,史密斯与CNBC签约后的声明——“我很荣幸能继续追求真相,无论是为了CNBC的忠实观众,还是为了那些几十年来无论顺境逆境都一直关注我报道的人”,以及CNBC主席马克·霍夫曼(Mark Hoffman)的表态——“谢普的职业生涯建立在诚实地发现和报道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很高兴他将继续在CNBC追求真相”,也被媒体广泛引用。
在广受引用和认可的史密斯声明中,与真相紧密相邻的概念是“事实”、“公正”、“语境”和“视角”(见表 表见本期第20页)。
其中“事实”一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词汇,甚至多于“真相”。从搭配的动词“寻找”、“讲述”、“核查”等来看,这些事实都是不依赖于观察者而存在的外部现实,可以被观察者发现,并被证实或者证伪。
不过,孤立的事实和信息碎片不但无法产生意义,反而可能扭曲真相,因此,“语境”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近80年前,一群美国学者即明确提出应当报道“关于事实的真相——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新闻自由委员会,1947/2004:12)。
此外,“不带恐惧或偏袒”这个短语由《纽约时报》创始人阿道夫·S·奥克斯(Adolph S. Ochs)创造,1896年,他在收购《纽约时报》时承诺该报“真诚的目标是……公正地发布新闻,不带恐惧或偏袒,不考虑所涉及的党派、教派或利益”(Dunlap, 2015)。这个短语后来成为习惯用语,在新闻、司法等领域广泛使用,暗示揭露黑暗、挑战权力,与美国新闻业的警句“向权势者说出真相”相关联,彰显了新闻的职业自主性和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规范性角色。
以上三个概念都由来已久,反映了传统的符合论真相观:新闻工作者独立挖掘、采集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真实发生的事实,并将事实要件置于语境之中加以发布,力图使新闻话语和事实的本体存在相符合。
值得注意的是“视角”这个全新的提法。“视角”意味着“观点”。尽管符合论在哲学和实践中都已遭到根本性挑战,但是在自由主义媒介制度下,新闻机构仍坚持中立的商业报道、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特别是美国的新闻业格外强调客观性、强调事实与观点分开(哈林,曼奇尼,2004/2012:244),在这种传统下,史密斯的“视角”表述显得标新立异,而新闻社群对此不但没有异议,反而纷纷称赞史密斯坚持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是特朗普时代“少数的几个理性声音之一”。
2.观念的坚守与变迁
以史密斯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新闻工作者围绕“真相”形成的话语反映了在实在论和符合论基础之上的观念变化。
新闻(news)的本原是事实,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因此新闻真相是实在论(realism)的,怎么强调事实要件的准确、真实都不为过。特别是进入21世纪,数字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大到不可知的海量事实,和真假难辨的信息一起涌入公共传播领域,稀释了以事实为基础的优质新闻。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另类事实”这种不负责任的“扯淡”文化,一方面削弱了社会精英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使人们对事实和真相产生犬儒主义态度。但是,正如瑞典哲学家维克福什(2020/2021:79)提醒的那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关于物体和事件的多数经验陈述都是客观上为真或为假的,“另类事实”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因为事实就是世界的样子,而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种。在这种传播环境中,新闻业的真相话语格外突出“事实”,强调新闻真相是以“符合”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既关系到严肃新闻的生存,也是对诸如特朗普之流的“另类事实”的反抗。
不过,真相不是事实的简单堆砌。从哲学角度而言,事实和价值无法一分为二, “事实的描述和评价能够而且必定被缠结在一起”(普特南,2006:28)。这一方面表现在“认识的价值本身也是价值”,在不可穷尽的事实中选择报道哪一个就体现了价值判断。媒体“不可能将所有事情都告知受众;但在决定哪些问题应该包括进来,哪些应该被忽略的时候,他们绕过了什么才是恰当的问题这一议题”(甘斯,1979/2009:395-396)。另一方面表现在人类语言中很多术语无法简单地归类为“观察术语”或者“理论术语”。例如,特朗普在“说谎”,这是事实,还是判断?史密斯是“真实的记者,报道了真实的故事”,是描述,还是评价?显然,对于美国新闻业而言,坚持主客观二分法的符合论真相观既无法说服自己,也无法取信于公众。在本案例中,传统上赋予符合论以合法性的“客观”、“平衡(balanced)”和“公正(fair)”不但没有出现在“真相”的最小语义场中,而且在全部语篇中的出现次数也少得可怜(见表 表见本期第21页)。
于是,史密斯公开亮出了“有视角/观点的真相”这个更实事求是的观念,也就是坦然承认了新闻真相中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
事实上,在日常实践中,史密斯也从不忌讳观点的表达。2012年5月3日,史密斯报道完一则政治新闻之后评论道:“政治如此奇怪,令人毛骨悚然。现在我知道了,政治和现实之间甚至不存在最松散的关系。”主流媒体纷纷称赞“没人说过比这更真实的话”(Forbes, 2012)。
在相信“另类事实”的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史密斯变成了“由一个人组成的事实核查机构,定期驳斥特朗普及其党羽在福克斯新闻台的言论节目中提出的不准确的说法”。事实核查本身是有争议的,因为挑选什么事实进行核查仍然是主观的,史密斯的事实核查则更具争议:他不是指出各方的不准确断言,而是专门针对特朗普和他的门客进行核查。这使他在福克斯新闻台更加特立独行、观点鲜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史密斯高调宣示的“有视角/观点的真相”,主流媒体始终称赞有加,并评价他是“非党派的”(nonpartisan)。结合史密斯的报道风格可以发现,新闻工作者承认新闻真相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但是价值判断有高下之分。出于党派之争的价值判断令人不齿,而基于诚实、真诚、同情、善良等普遍的人性之善做出的价值判断则值得称道。
在美国学者哈林(Hallin, 1992)看来,“记者的声音和判断必须得到更诚实的承认”。坚持承认自己的主观性并开放相关的价值判断,或许终究能够取得受众的理解,遗憾的是,史密斯的表述存在前后不一的矛盾。节目开播后, “视角”一词被隐去。CNBC介绍:“史密斯说,他不想告诉任何人如何思考。他只是想报道事实,这样人们就可以自己拿主意了。”史密斯则表示:“我希望我们能提供有背景的每日新闻。我没有高人一等地跟他们说话,也没有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思考。”新闻的议程设置和铺垫效应理论已经证明,媒体不但能够告诉人们“想什么”,而且可以告诉人们“怎么想”。况且,你已经承认自己报道的真相是有观点、有视角的,又怎么能避免对受众的引导企图呢?节目开播后的受众评论也表明,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令他们失望。史密斯的前后矛盾体现了主流新闻业在认识论上的摇摆,但在机构性话语中的表述已足以显示变化的趋势。
话语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费尔克拉夫,1992/2003:59),严肃新闻的生存根本就在于为人们提供有关世界的真相,这一点必须保持不变,但对真相的理解经历了变化。从启蒙运动对事实的盲信,到用客观性维持符合论的合法性,再到坦然承认“视角/观点”,这种相对于哲学和社会思潮来说实属滞后的变化,对新闻业而言则是观念上的进步。作为“以言行事”的人类,新闻话语所表征的“世界真相”存在立场和观点并非原罪,坦承这一点也是“真相”。只是这个立场不是数百年前政党报时期的党派之争,而是基于普遍人性的善与美德。
作为本体的真相无疑是理想化的表述,在现实中,这样的真相有着怎样的命运?
四、话语的转向:从赞美、抗争到忽视、无奈
在所有话语中,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真相是新闻业的理想、规范,用于区分好新闻/坏新闻、称职的记者/不称职的记者。在史密斯的三个时间节点上,主流新闻业的话语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戏剧化转向,为我们理解史密斯和他的“真相”在现实中的遭遇提供了绝佳窗口。
1.赞美“真相”和精英的反抗
史密斯离职时的话语实践集中于对史密斯/真相的赞美和针对新闻求真困境的斗争。
所有媒体都高度评价史密斯的工作,“整个媒体行业的记者和主播们都认为,史密斯是一名记者、新闻主播、领导者和讲真话的人(truth teller)”。他的离职是为了“捍卫新闻业的衣钵”,为了“真相”,他的离开“标志着在像福克斯这样的频道中没有说出真相的空间”。
这些话语将史密斯建构为“真相”的化身,赞美史密斯,就是赞美真相;同样,史密斯的遭遇,就是真相的遭遇。在媒体话语中,史密斯一直与自己所在的机构及其代表的政治威胁、党派斗争进行抗争,最终他选择放弃高薪、毅然离职是长期以来抗争无望的结果,渲染了理想主义者的反抗。
福克斯新闻台和CNN、 MSNBC并列为美国三大主要有线新闻频道,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新闻来源之一,其整体受众人数排名第一。遗憾的是,福克斯新闻台吸引受众依靠的是鲜明的保守主义党派特征和煽动性的言论,而不是优质新闻。其言论节目对待事实十分草率,充斥着民粹主义模式和党派偏见,以至于“改变了美国公共领域的政治逻辑和新闻的真相标准”。20年来,多项实证研究表明,与那些主要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的人相比,福克斯新闻台的观众更容易被误导,并持有不正确的观点(Bartlett, 2015)。
在媒体话语中,多年来,福克斯新闻台的新闻部门在史密斯、卡尔·卡梅隆(Carl Cameron)等“真正的记者”的带领下,还是保留了“新闻报道的一面”,坚持“与现实挂钩”,并与言论部门的意识形态做斗争。不过,福克斯新闻台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边缘化史密斯的异端邪说”,将他的节目从黄金时间转移到下午3点。有人认为,福克斯新闻台之所以容忍并重金挽留史密斯,是为了将他的存在作为一种公共关系策略——福克斯新闻台经常在人们将它指责为“特朗普的宣传机构”时将史密斯当做挡箭牌,利用他的硬新闻报道与对事实和真相的坚守来维持其作为信息来源的可信度。
特朗普总统上任后,这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特朗普与福克斯公司的执行董事长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关系密切,福克斯新闻台的一些员工和撰稿人都在白宫工作;福克斯的言论节目主持人经常为特朗普辩护,而且越来越多地批评新闻部门的记者,让他们感到沮丧。史密斯还经常受到总统本人的攻击,而福克斯新闻台并没有支持史密斯,在特朗普主义盛行的机构文化氛围中将他孤立,同时也把整个新闻部门边缘化了。
在主流媒体看来,压垮史密斯的最后稻草有三个:一是史密斯与特朗普头号支持者、言论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之间的公开争执。事件发生后,福克斯新闻台的高管告诉史密斯不要再攻击卡尔森,“如果他再这么做,他就被停播了”。二是史密斯离职前,福克斯新闻台的新闻部门报道了一项不利于特朗普的民调,为此,特朗普在推特上猛烈抨击史密斯和该台“不再为美国提供服务”。三是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长私下会见了鲁伯特·默多克,尽管史密斯的发言人表示这与史密斯的离职没有关联,但仍然引起了“特朗普用政治权力赶走史密斯”的猜测。
媒体话语将这三件“巧合”之事纳入报道框架,制造了善与恶之间的二元冲突,实际上是指责机构导向和政治氛围的双重压迫逼走了史密斯和他代表的“真相”。不过,史密斯在自己的新闻节目中高调宣布离开,显示他并未以失败者自居,而是将离去作为最后的抗争,并将不忘初心,“开始新的篇章”。
对此,所有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不但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史密斯、声讨福克斯新闻台和特朗普政府,而且在特朗普嘲讽史密斯离开是由于“低迷的收视率”时纷纷指出,根据尼尔森(Nielsen)的收视率数据,史密斯的节目平均观众数轻松超过了他在CNN和MSNBC的竞争对手,与史密斯并肩奏响了一曲雄壮的“真相颂”。
2.忽视“真相”与精英的无奈
2020年7月8日,史密斯宣布加入CNBC,9月10日,他的黄金时段新闻节目开播。与史密斯离职时的媒体热度不同,在这两个节点时间,媒体报道的篇幅大幅减少,显示关注度下降,且话语焦点转向商业策略和收视率。史密斯和他的“真相”虽然还在坚守,并依然赢得共同体的尊重,但已经黯然失色,成为曲高和寡的独唱。
史密斯的签约声明显示,他追求真相的初心始终未变,并希望在CNBC找到理想家园,“我知道我为我的新闻节目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媒体话语也回顾了史密斯在福克斯新闻台的坚守和抗争,但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CNBC的节目改革策略和史密斯的加入为其带来的商业利益。
与福克斯新闻台相比,CNBC是一家观众少得多的电视网络。不过,该频道“能够接触到那些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节目的高收入高管,这让它对广告商来说很有价值”。史密斯的加入为CNBC的黄金时段节目阵容增添了名气,对CNBC改革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和市场价值,通过硬事实和真相来抗衡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上的进步观点和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右倾主持人。毕竟,对于商业电视网络而言,“收视率才是王道。企业就像‘鲨鱼’,他们只是朝着钱的方向移动”。
在这个阶段,已经有人唱衰史密斯及其“真相”:“史密斯‘实事求是先生’的方式不太可能引起轰动——尤其是在新闻业的传统观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因为,“主播的表现当然都将根据其收视率来评判,这可能会达到令人沮丧的程度”,至于新闻价值,“可以撇开不谈”。此外,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背景是,在邀请史密斯加盟之前,NBC环球首席执行官杰夫·谢尔曾在私下谈话中表示,他正在考虑将CNBC的黄金时段转向右翼脱口秀节目。这表明,对于CNBC而言,节目的意义在于收视率,史密斯的知名度和他的“真相”只是可以售卖的商品,是在竞争中打出的差异化战术。
2020年9月30日,史密斯的新闻节目正式开播。在接下来一个月,只有8篇关于史密斯和他的“真相”的报道。其中,CNBC发表了一篇宣传稿,主要介绍史密斯的新闻生涯,在线杂志Deadline、《华盛顿邮报》介绍了他的第一期节目内容,其余5篇都聚焦于收视率走低问题。
CNBC的节目宣传稿是史密斯的个人特写,导语中说“他不想告诉任何人如何思考。他只是想报道事实,这样人们就可以自己拿主意了”。接着介绍他既往的人生和工作经历,特别突出了他身为同性恋的“个人真相”,指出“他在新闻和生活中的成功来自于对真相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工作。他甚至不得不在这一过程中了解自己的个人真相”。这篇报道是所有媒体中唯一提到史密斯性取向的报道,这种将私人事务公开化的举动似乎是为他在工作中追求真相的人设背书,但难免有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之嫌,反而损害了史密斯的真诚。
Deadline和《华盛顿邮报》介绍史密斯的第一期节目“聚焦于‘事实’和‘真相’(这两者都是其座右铭的一部分),绕过专家小组和意见”,但同时也有“最接近权威的评论”和对新闻事件的“深入剖析”,显示了其对真相的“语境”、“视角”的理解。
其他媒体都在详细分析其收视率。第一期节目的收视率令人振奋,尽管“他在直播的第一个晚上并没有能够抓住他在前雇主福克斯新闻台享有的观众”,但是“击败了其在福克斯商业网络上的竞争对手,总体上获得了30.8万名观众”。开播一周后,节目收视率走低,“自9月30日推出以来,CNBC 的《谢泼德·史密斯新闻》为知名嘉宾呈现了一个时尚的硬新闻节目,同时收视率持续下降”。
新闻和观点类博客Mediaite在报道了收视率低迷的事实之后提到,其高级编辑在史密斯入职时曾预测,尽管史密斯的新节目可能会“很棒”,但很少有人会看到它。“史密斯非常出色。他的正直无可挑剔。他无所畏惧地传递消息。他在采访不同阵营的新闻人物时毫不留情,但他的新节目完全绝望地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有线电视新闻观众通常会更热衷于意见和争论,而史密斯的福克斯新闻台观众中很少有人会跟随他到CNBC。这一预测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预测以及史密斯节目的收视率相互印证,显示新闻工作者深谙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从离职、入职和节目开播,史密斯追求真相的信念没有变,呈现出的新闻没有变,他所在的阐释共同体对他的敬慕也没有变,但是评价的标准却变了。在这一阶段,面对收视率这一“多数人的暴政”、面对史密斯的坚持,新闻工作者不再充满激情地赞美和支持史密斯与政治和机构压力“抗争”,而是更加现实且理所当然地叙述真相理想在市场逻辑下的尴尬,没有一家媒体表示出遗憾或者惋惜,更不要说反思了。有人评价:“这不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这是非道德的。”这样的语境使得史密斯的理想主义声明显得十分孤独;而CNBC对史密斯的赞扬则是一份商业广告,将史密斯和他代表的“真相”从道德意义上的理想转换为工具理性的商品。这是市场化媒介环境的内在困境,而新闻工作者对此无能为力。
五、主动的受众:多种声音,一种期待
史密斯和他的社群热情地表示,他们是寻找和讲述真相的人(seek and tell truth),在重重困境中,既向权势者“说出真相”,又将真相告诉“迫切需要”的观众。不过,对于一个要建立文化权威的专业而言,社会的接受是必要条件(Carlson, 2016)。社会若不接受,媒体报道的“真相”便失去了意义。那么,受众是否接受史密斯所代表的新闻业建构的真相?
1.话语的盲点和主动的受众
在本文的样本中,受众始终是模糊的甚至是隐形的,他们或存在于新闻工作者的想象之中,或是收视率所呈现出来的抽象数据。通过媒体话语,我们得知福克斯新闻台是一家以新闻专业水准衡量十分糟糕的媒体,其言论部门党派立场鲜明,且罔顾事实,但是收视率却很高;史密斯在福克斯新闻台的收视率轻松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但这只是因为“整体而言,福克斯新闻台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但他的时段是福克斯日间节目中收视率最低的”。事实上,史密斯在直播评论和报道中批评总统和他的主张时会引起一些观众的愤怒;我们得知,“史密斯的粉丝们很高兴他在福克斯主持节目”,但他们并不是福克斯的核心观众,特朗普才是那些讨厌史密斯的忠实观众之一。
媒体没有告诉我们的是,既然福克斯新闻台的内容质量如此之差,为何吸引了全美最多的受众?那些“核心观众”究竟是谁?既然史密斯是真相的完美化身,为何无法吸引到最多的受众?史密斯的粉丝又是谁?
史密斯入职时,CNBC管理层希望他的硬新闻报道和实事求是的风格能够抗衡其他竞争者,提高收视率,但是有人预测这种做法会失败。节目开播后,持续走低的收视率似乎印证了这种“失败”。对此,CNBC解释道:“我们从观众那里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CNBC不仅是普通新闻领域的新进者,而且新闻观众也是习惯的产物,要改变这些习惯需要很长时间”,并请求观众“今晚再次收看CNBC,了解更多事实、真相和谢泼德·史密斯的新闻”。
在所有涉及受众的话语中,看不到具体的“人”。1970年代,社会学家甘斯前往主要的全国媒体新闻编辑室开展田野调查。他起初认定,作为商业雇员,新闻工作者在选择和生产新闻时一定会将受众纳入考量范围,结果“很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实际的受众几乎一无所知”(甘斯,1979/2009:294)。本文的样本表明,“受众”至今仍然是媒体话语中的盲点。
幸运的是,数字媒体时代,受众可以在媒体网站的报道后留言、发表评论,我们也可从中一窥具体的“人”的观点。在搜索评论时,发现在56篇报道中,仅有7篇报道有评论。这7家媒体有权威传统媒体《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也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网络原创媒体Slate、Mediate、Deadline。媒体影响力决定了每个报道的评论数量多寡。此外,受众会根据自身偏好选择日常接触的媒体,因此,媒体倾向与受众评论倾向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例如,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支持史密斯的受众达到三分之二,而在支持特朗普的媒体中,尽管新闻本身表达了对史密斯的支持,但是受众评论却显示出截然相反的倾向。
不过,不论媒体自身倾向如何、报道文本的观点如何,评论区都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声音,显示受众并没有被媒体主导,而是根据自己的信念、需要、喜好来判断和评价媒体内容,表现出充分的主动性。
2.多种声音,一个期待
与媒体话语在三个节点时间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不同,一个个具体的受众在评论区的生动发言既有对文本观点的支持和延续,也有激烈的反对,还有脱离文本的自我发挥,它们与新闻文本共同构成了关于史密斯与真相的“话语地形”。
在史密斯离职的第一阶段,受众评论中赞美声与质疑声齐头并进,其中还夹杂着对“真相”和媒体行业的讨论。支持史密斯的评论基本与媒体的态度保持一致,肯定了他的新闻工作,认为他是“正直”、“理性”的人。例如,用户Rebelrona称史密斯为“福克斯唯一的理性声音”;用户Bruce1253认为史密斯“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从事一项要求人们坚持对或错的特定观点的工作。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报道,但你知道他致力于寻找和报道事实”。而批评者的态度完全相反,认为史密斯是以“报道事实”作为掩护,实则是“观点的输出者”。例如Uncle+Sam说:“听谢泼德的话已经越来越难了。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讲真话的人,但是,他对总统的敌意却被掩盖得很深。”用户foxxy认为,相对于福克斯新闻的多数职员,史密斯看起来是在讲述真相,但是,“他对自己的报道一直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总是带着偏见”。
此外,在这一阶段,也有受众跳脱出纯粹的赞美和批评的两极分化,表达了自己对“真相”和媒体行业的想法。例如,用户CLARE称:“我们看到史密斯先生通过重复事实来呈现一些议题。事实不是真相,事实就是事实。真相是一种信念,随着更多的事实而改变。”有受众表示媒体本身就不值得信任,一切都是利益驱使,timmrush称他并不关心像史密斯一样的新闻主播是不是在报道真相,“他呆了好几年,拿了很多钱”。还有受众认为不应把“史密斯报道事实”的做法写得那么伟大和崇高,“请停止使用谢泼德·史密斯的圣徒传记。是的,他不像福克斯的其他工作人员那样右倾,但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掩盖福克斯是一个真正的新闻台的谎言”。
在史密斯加入CNBC和新节目开播这两个阶段,媒体话语从新闻逻辑转向商业逻辑,但不少受众不管是支持还是质疑史密斯,都表达了对事实、真相的期待。支持史密斯的用户centralrd4表示,“只有离开福克斯‘新闻’,史密斯才能从事真正的新闻工作”。质疑史密斯的用户Bessie Mento在看过史密斯的新节目后认为节目内容“被宣传为只是新闻。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如此的有偏见,以至于他们还不如称它为民主党的进步宣传部门” 。
节目开播后,媒体话语集中于收视率问题,但受众则更多地评价史密斯和节目所报道的“真相”。用户Hal质疑史密斯此前在声明中持续提到的新节目将会继续报道真相和事实的说法:“在节目首播之前所有‘没有观点,没有议程’的修辞发生了什么?”用户duggersd认为史密斯并不是因为“报道真相”才受到关注,而是因为他在福克斯新闻时“是一个对立的声音,所以就很容易被听到”,离开福克斯新闻后,他“只是说着同样事情的另一个声音,而一千个其他声音同时在说,就不太可能被听到”。
综上所述,受众对媒体报道、对媒体行业和从业者各有看法,对真相的认知与媒体有分歧,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纷乱,但一以贯之的核心主旨是期待和呼唤真相。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观察媒体话语和受众话语,我们可以分析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此案例中,新闻工作者在第一个阶段运用机构性话语形成了高度一致的阐释共同体,其自我认知——是真相的化身、真相的仲裁者,其最高职责就是“发现”、“追求”、“讲述”事实与真相,以满足“人们的迫切需要”。这个作为最高理想和新闻产品的真相是基于特定价值判断对事实的选择和组合,并以非党派、人性之善赋予这种价值判断以合法性,以此对抗政治威胁与组织压力。在第二、三阶段,自我认知演变为收视率的追逐者,真相从理想异化为商品,大大消解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外,如果将媒体平台视为阐释共同体表演的“前台”,我们不得不关心这种“表演”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从“台上”的话语实践来看,媒体精英的视野中没有作为“人”的观众,从“台下”的反馈来看,他们建构的自我身份和真相观念也并没有在观众中产生充分的共鸣,甚至遭到一些受众的嘲讽和攻击,这种自我呈现和传受关系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白式的。如果再考虑到“新闻弃儿”③的存在,这种自我感动、自我陶醉意味就更加明显。话语缺位之处,就是权力运作之时,媒体精英必须面对自己的盲点。
1.大众传媒与权力机构的合谋
“以事实为中心的话语”与媒体的商业化高度相关。商业性媒体需要受众和广告,因此侧重于新闻,聚焦于事实的呈现。在美国新闻业的“高度现代主义时期”,经济上的成功意味着新闻机构“世俗”、商业化的一面与它“神圣”、公共服务的一面并不冲突,记者们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没有怀疑或矛盾”的身份认同(Hallin,1992),一如本案例中第一阶段的媒体话语。但是,即便是在高度现代主义时期,这种宣称也饱受质疑。1980年代之后,放松管制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媒介垄断和超级竞争更加严重地打压着新闻部门的求真实践,其中,电视领域的变化最为剧烈。
美国的电视行业中,新闻从来就不是“资产的核心”。1980年代之后,西屋电气(Westinghouse)、迪士尼(Disney)、美国在线(AOL)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大公司收购了主要的网络和有线电视频道,新闻业在这些大公司里只占很小一部分。老板们对账本底线更感兴趣,只把新闻当作赚钱的机器,全方位打压新闻部门的民主理想,收视率成为衡量电视新闻业的标准。
此外,商业化并不意味着媒体停止在政治中扮演角色,事实上,在1870年代,大型报业公司已跻身美国最大的制造公司之列,作为商业机构,“媒体和‘人民’的关系如同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人民的关系一般”(尼罗等,1995/2008:18),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媒体成为独立的政治玩家(哈林,曼奇尼,2004/2012:204)。这种角色决定了一方面它们的话语必然处于“合法”区域之内,不可能“代表人民”从根本上挑战社会体制;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放弃自身的建制派地位,机构话语必然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合法性。例如,媒体对特朗普总统和福克斯新闻台的抨击是在美国的民主框架中进行的,它们批评的是破坏民主制度的总统,而不是美国的根本政治体制;是破坏新闻传统的个别机构,而不是生产这种扭曲性媒体的土壤。
尽管市场逻辑要求媒体淡化公开的党派性,但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美国媒体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正在逐步加强其党派性,其表征现实的意愿和能力大打折扣。这种情形正是哈贝马斯(1990/1999:240-242)所指出的“大众传媒与权力机构的合谋”。二者塑造出公共领域的假象,议会变成了“公共讲坛”,全国人民通过广播和电视来参与这个公共领域,但是广播和电视有倾向性地歪曲辩论情况,使程序过程变成了展示过程。
以福克斯新闻台为例:该台的崛起和成功恰好迎合和引领了美国电视新闻业的两个取向——党派性和煽情性。在1996年成立之时,美国主流媒体存在明显的自由主义偏见,要想满足对保守媒体的需求不容易。随着电信管制的放松和技术进步,共和党政治顾问和制片人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说服澳大利亚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出资建立一家保守派电视新闻网络。福克斯新闻台“从一开始承袭的就是默多克报业帝国中共同的理念和特点——煽情、耸动、戏剧化式的新闻报道风格”(王菊芳,余万里,2008)。在“9·11”事件中,福克斯新闻台彻底放弃了客观、中立的面纱,一举击败了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CNN,成为收视率最高的新闻频道,并在此后一直凭借其鲜明的观点和态度保持这一优势。根据2020年的最新数据,在三家有线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室支出中,CNN 的支出基本保持不变,MSNBC 的支出增长了3%,福克斯新闻台的支出却下降了4%(PEW, 2021),由此也印证了史密斯事件中媒体对福克斯新闻台的责难:“舆论制造者的人数远远超过记者的人数,而舆论制造者对迎合人们的偏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感兴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冲击” ④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扭曲。美国绝大多数主流媒体从2016年起开始激烈反抗和批评特朗普,史密斯则是特朗普啦啦队中的异类。无论对自由主义媒体,还是对史密斯,这既是对抗特朗普主义和假新闻的正义之举,也是吸引读者的好方法:与伏地魔和他的黑魔法战斗是精彩的剧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业在 2016 年竞选期间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朗普式的镀金时代”,新闻机构发现他们对特朗普的报道越多,他们的 Chartbeat⑤数字就越好(Lepore, 2019)。媒体报道和受众评论中都有人指出,史密斯在福克斯的收视率高是因为福克斯新闻台的收视率整体最高,而且他是福克斯新闻台一个不同的声音,反倒因此吸引了受众。事实上,史密斯的出走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与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冲突性也不无关系。
更糟糕的是商业化体制带来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福克斯新闻台的商业成功改写了美国电视新闻报道的“游戏规则”,CNN 和MSNBC 不得不加强观点类和辩论类节目,形成“福克斯化”倾向(史安斌,邱伟怡,2017),CNBC的节目策略也表明了这一点。结果,有良知的记者不管出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对收视率和利润的追逐。真相,对于记者个人或许是理想,但是对于机构媒体,其实自始至终都是商品。
2.认识论分歧和危机
在本案例中,高度一致的媒体话语与多元取向的受众话语存在撕裂。所有话语中仍然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对真相的肯定和渴求,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本能需求和现代新闻业的信息工具属性所决定的。但是,共识止步于此。具体到新闻实践,由于媒体“并不打算照看全体人类”(李普曼,1922/2006:243),因此对于媒体应当报道怎样的真相可谓言人人殊。新闻真相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由特定价值体系生产的事件组合,实际上是“本质真实”的概念。在本案例中,媒体话语承认新闻真相中价值判断的存在,相对于机械的符合论和客观性,这一点已经是观念和态度上的进步。但是,这其中仍然存在几个根本的认识论问题:
首先,如果说构成真相的事实都因“事实与价值的缠结”、难以穷尽和转述变形而导致“符合”困境,那么,作为本质真实的真相就是更加高度抽象化和哲学化的论述,在新闻实践中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从更广泛的社会范畴来看,究竟什么是“本质真实”难有定论,结果很容易被人利用“来达到自己心里预设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被践踏的,恰恰是新闻真实本身”(王亦高,2015)。
其次,受众与媒体的认识论错位。从受众话语中可见,很多受众对新闻业的期待仍然是机械符合论意义上的单一真相,并不接受观点/视角的表述。尽管媒体用“非党派”、“人性之善”来赋予对真相的价值判断合法性,但是对于价值多元的社会群体来说却存在异议。“在社会存在阶级分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一个共享的言论自由机制和一套被普遍认定的‘真相’”(王维佳,2018)。特别是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精英身份决定了他们与受众的距离。“最具伤害性的偏见极少得到讨论——即阶级产生的偏见”(Cunningham, 2003)。这些人经常被要求报道他们生活中不曾经历过的事件和问题,导致与受众之间的系统性脱节。
第三,受众并不都是理性的,高收视率并不等于真相和优质新闻。例如,福克斯新闻台的忠实观众——特朗普将主流媒体一概斥为“假新闻”,在听到福克斯新闻台报道了对自己不利的民调结果后转而批评该台,表现出缺乏面对真相的勇气。这种怯懦并不是特朗普独有,而是当代公共传播领域的突出特征,即“后真相”认识论。据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福克斯的忠实观众中超过八成以上为信奉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中心论的保守主义者,大都拒绝多元文化,不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信奉非理性的“超级爱国主义”(转引自史安斌,邱伟怡,2017)。
最后,媒介即隐喻,“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波兹曼,1985/2004:20)。波兹曼在1980年代即指出,电视文化取代印刷文化的后果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了严重危害。电视认识论将无聊的东西变得充满意义,助长语无伦次和支离破碎,实际上创造出一种“假信息”,使人们“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情,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波兹曼,1985/2004:139)。而此后,技术进步带来的超级竞争导致电视新闻日趋青睐制作成本低、收视率高的节目,极大地改变了记者收集和报道新闻的方式。这些“纯粹是作为商业产品来生产的节目将‘真实’和‘虚构’的素材交织在一起:通过纪录片素材和再创作的结合来报道‘真实事件’,大量使用音乐和视觉效果,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Hallin, 1992)。
2021年,史密斯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采访时表示,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是真相的仲裁者”(arbiters of truth)。这固然是值得尊重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既无视自身在结构和形式上的根本缺陷,还将受众矮化成为“二等旁观者”(凯瑞,2009/2019:74),同时也并没有得到受众的普遍认可。
批判性地审视美国当代新闻业的真相话语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它。在本案例中,作为体制存在的媒体——无论是福克斯新闻台,还是CNBC,都并未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追求和维护真相,甚至成为新闻求真的阻碍和桎梏,然而现实证明,摧毁内嵌于现代制度的体制化新闻并不会产生以事实为基础的倾听、协商、宽容、理性的更好蓝图,反倒有可能加剧反认知立场。在福柯(2009/2016:3)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真相体制,现实、主体、权力和真相的关系从来都是缠结的,“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必然的、让人变得更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个体的伦理自觉就成为关键之处。
作为个体的记者如史密斯体现出充分的伦理自觉:他将真相视为最高理想,为了说出真相而不畏强权、不贪恋高薪,也不为了迎合受众而改变初心。当然,作为“直言者”,史密斯或许对自己的认识还不足,还需要更加真诚、前后一致:坚持坦承自己的报道是“有视角的真相”,并必然具有引导性——作为以言行事的人类,作为有局限的个体,这绝非原罪,只是需要进一步敞开“视角”。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追问:在美国当代新闻业的真相体制中,史密斯这样具有伦理自觉的个体究竟能抗争到何种程度?新闻工作者也需要养家糊口,对于史密斯这样的明星主播来说,以离职表达抗争,“开始新的篇章”并非难事,但是那些将史密斯视为榜样、“仅仅是因为有史密斯的存在才坚持留在福克斯”的新闻部门普通工作人员如何在恶劣环境中坚持事实和真相?如何在更广阔的公共传播视野中对体制化新闻进行分析?这是我们继续思考和讨论的方向。■
注释:
①样本说明:1.谷歌新闻(Google News)收录媒体的基本标准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可信度、一贯制作与新闻相关的原创内容,以及遵守谷歌新闻网站的新闻政策。2.节点时间之后的时间段选择出于如下考虑:宣布离职和入职是突发事件,随之产生了大量话语文本,三天时间足以为有言说愿望的行动者提供发言空间;节目开播后的收视情况需要较长的时间段观察,因此选择了开播后一个月的时间段。3.报道的媒体之中,既有传统媒体《华尔街时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美联社等,又有知名杂志《好莱坞报道》、《名利场》、《滚石》、《福布斯》等,还有网络原创媒体Politico、The Hill、The Wrap、Mediate等。4.受众是元新闻话语的生产者之一,本文将媒体报道的受众跟帖作为元新闻话语的经验性材料,但是多数媒体没有开放评论区,因此仅将受众评论作为参照。
②现代语义学兴起的标志是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提出的语义场理论。“语义场”借用物理学中“场”的概念而来,是指语义的类聚,它认为,一个词跟全体词在语义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通过比较、分析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才能确定这个词真正的内涵。根据语义要素建立语义场,大的语义场下面可以分出小的语义场,小的语义场下面还可以分出更小的语义场,乃至最小的语义场,同一语义场的词语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一个词义范围的扩大或缩小都会受到周围词语的影响(叶文曦,2016)。
③所谓新闻弃儿,是指在相当长的持续时间内,被动或者主动放弃了对主流媒体的严肃新闻消费的人。前一类是被主流新闻所“遗忘”的那些人,多数是老年人、少数族裔、边远地区人群,和在城市也大量存在的贫民。后一类是由于有了更多的消费可能、或者认为新闻有害,过度的负面信息影响身心健康而自觉逃避新闻的人。2019年,这类人在美国的比例达到41%。如果限定为主流媒体的严肃新闻,这个百分比大致在三分之一(彭增军,2021)。
④指特朗普上任之后与主流媒体之间的斗争为主流媒体带来大量新增的订阅量。
⑤2009年成立于美国的一家科技公司,向全球出版商提供实时网络分析,显示不断更新的网络流量报告,告诉编辑人们正在阅读哪些故事以及他们正在跳过哪些故事。
参考文献:
【瑞典】奥萨·维克福什(2020/2021)。《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汪思涵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白红义(2014)。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6),46-60。
白红义,李拓(2017)。新闻业危机应对策略的“正当化”话语:一项基于中国媒体宣言的探索性研究。《新闻大学》,(6),51-61+152。
【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2014)。《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操瑞青(2017)。作为假设的“新闻真实”:新闻报道的“知识合法性”建构。《国际新闻界》,(5),6-28。
陈楚洁(2015)。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12),26-45。
【美】丹尼尔·C·哈林,【意】保罗·曼奇尼(2004/2012)。《比较媒介体制》(陈娟,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2018)。《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第8版)(李青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14年)。
郭佳(2015)。机构话语与专门用途语言的关系探析——以话语共同体为考察维度。《外语学刊》,(4),49-52。
【德】哈贝马斯(1990/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美】赫伯特·甘斯(2009)。《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洪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9年)。
华维慧(2020)。从诠释到具身:虚拟现实技术对新闻真实的再生产。《新闻界》,(11),86-93。
姜华(2022)。复杂真相与意义生成:论杂合体新闻业的新闻真实及其实现。《新闻界》,(5),15-26+39。
金圣钧(2021)。从“共同回应”到“真实体验”——数字化传播环境下“见证真实”的理解转向。《新闻记者》,(12),17-30。
【美】兰斯·班尼特(2018)。《新闻:幻象的政治》(第9版)(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青藜(2021)。“真相”的重申与困惑:从“史密斯vs法罗”之争看美国当代媒介伦理问题。《中国新闻传播研究》,(1),209-222。
李玮,蒋晓丽(2018)。从“符合事实”到“社群真知” ——后真相时代对新闻何以为“真”的符号哲学省思。《现代传播》,(12),50-58。
【美】迈克尔·舒德森(1978/2009)。《发掘新闻》(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法】米歇尔·福柯(1998)。《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
【法】米歇尔·福柯(2009/2016)《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II》(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尼尔·波兹曼(1985/2004)。《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1992/2003)。《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彭增军(2021)。从此萧郎是路人:新闻的弃儿。《新闻记者》,(5),61-66。
史安斌,邱伟怡(2017)。美国电视新闻业的复苏与隐忧。《青年记者》,(7),85-87。
王辰瑶(2021)。“新闻真实”为什么重要?——重思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古老的新问题”。《新闻界》,(8),4-11+20。
王辉(2012)。瞬间与无限:新闻真实的两种理解方式。《国际新闻界》,(2),45-50。
王菊芳,余万里(2008)。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崛起与美国保守主义。《美国研究》,(4),105-117+5。
王维佳(2018)。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恐惧。《新闻记者》,(5),17-22。
王亦高(2015)。新时代应警惕“新闻本质真实论”。《新闻与写作》,(7),58-61。
【美】沃尔特·李普曼(2006)。《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德】伍多·库卡茨(2014/2017)。《质性文本分析》(朱志勇,范晓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美】希拉里·普特南(2006)。《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美】新闻自由委员会(2004)。《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保军(2008a),如何理解新闻真实论中所讲的“符合”.《国际新闻界》,(5),43-48。
杨保军(2008b)。事实·真相·真实——对新闻真实论中三个关键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新闻记者》,(6),61-65。
杨保军(2020)。准确理解新闻的“整体真实”。《新闻界》,(4),35-42+5。
杨奇光,周楚珺(2021)。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理念流变、阐释语簇与实践进路。《新闻界》,(8),12-20。
叶文曦(2016)。《语义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约翰·C·尼罗,威廉·E·贝里,桑德拉·布拉曼,克利福德·克里斯汀,托马斯·H·古贝克,史蒂夫·J·赫勒,路易斯·W·利博维奇,金·B·罗佐(1995/2008)。《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周翔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虞鑫(2018)。语境真相与单一真相——新闻真实论的哲学基础与概念分野。《新闻记者》,(8),30-37。
【美】詹姆斯·凯瑞(2009/2019)。《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dersonC. W. (2018). Apostles of certainty: Data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oub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C. W. & Schudson, M. (2019). Objectivity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Wahl-Jorgensen, K and HanzitschT(eds. )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2nd ed). ICA Handbook Series . Routledge , Oxon.
BartlettBruce(2015). How Fox News Changed American Media and Political Dynamics检索于https://papers. ssrn. com/sol3/papers. cfm?abstract_id=2604679.
BroersmaMarcel(2010). The Unbearable Limitations of Journalism: On Press Critique and Journalism’s Claim to Tru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2(1)21-33.
Carlson, Matt (2012). Rethinking Journalism Authority: Walter Cronkite and ritual i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Studies(4)483-498.
Carlson, Matt.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ChristiansClifford G. (2007). Media Ethics in Educatio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9(4)179-221.
CunninghamBrent (2003). Re-thinking Objectivity. 检索于https://archives. cjr. org/feature/rethinking_objectivity. php.
Deuze, Mark(2005). What is journalism? :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 , 442-464.
DunlapDavid W. (Aug. 142015). 1896:| ‘Without Fear or Favor’. 检索于https://www. nytimes. com/2015/09/12/insider/1896-without-fear-or-favor. html.
FerrucciPatrick & Taylor, Ross(2018). Access, Deconstructed: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Photojournalism’s Shift Away From Geophysical Acc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42(2)121-137.
FerrucciPatrick(2021). Joining the Team: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Paradigm Repair, the Athletic and Sports Journalism Practice, Journalism Practice, 16(10)2064-2082.
Forbes(2012). 检索于https://www. forbes. com/sites/erikkain/2012/05/08/fox-news-host-politics-is-weird-and-creepy/?sh=28844aed6328.
HallinDaniel C. (1992). The Passing of the“High Modernism”of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2(3)14-25.
Hermida, Alfred(2012). Tweets and Truth: Journalism as a discipline of collaborative verifica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6(5-6)659-668.
LeporeJill(2019). Does Journalism Have a Future? 检索于https://www. newyorker. com/magazine/2019/01/28/does-journalism-have-a-future
LisboaSilvia & BenettiMarcia(2015). Journalism as Justified True Belief. Brazilian Journalism Research, 2(2)10-28.
Munoz-TorresJuan Ramón(2012). Truth and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natomy of an endless misunderstanding. Journalism Studies13(4)566-582.
Pew(2022). 检索于https://www. pewresearch. org/journalism/2022/06/14/journalists-sense-turmoil-in-their-industry-amid-continued-passion-for-their-work/.
PowersElia(2018). Selecting MetricsReflecting Norms: How journalists in local define, measureand discuss impact. Digital Journalism, 6(4)454-471.
Vos, Tim P. & CraftStephanie (2017).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tic transparency. Journalism Studies18(12)1505-1522.
WaisbordSilvio(2018). Truth is What Happens to News: On journalism, fake news, and post-truth. Journalism Studies19(13)1866-1878.
Zelizer, Barbie(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3)219-237.
Zelizer, Barbie(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李青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嘉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快国际传播五力建设研究”(编号:2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