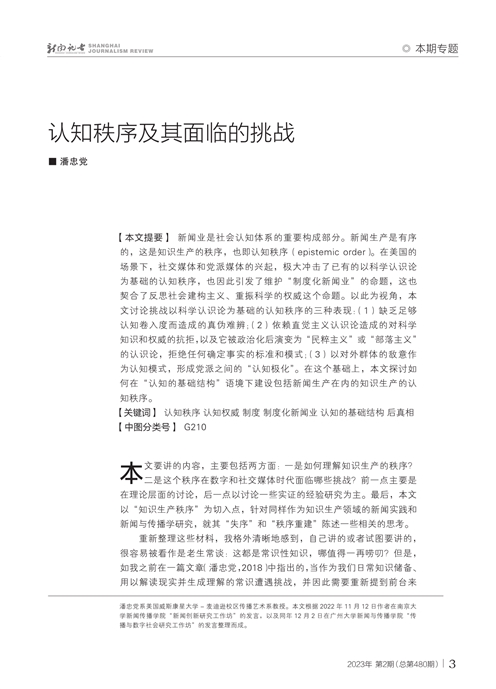认知秩序及其面临的挑战
■潘忠党
【本文提要】新闻业是社会认知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新闻生产是有序的,这是知识生产的秩序,也即认知秩序(epistemic order)。在美国的场景下,社交媒体和党派媒体的兴起,极大冲击了已有的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秩序,也因此引发了维护“制度化新闻业”的命题,这也契合了反思社会建构主义、重振科学的权威这个命题。以此为视角,本文讨论挑战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秩序的三种表现:(1)缺乏足够认知卷入度而造成的真伪难辨;(2)依赖直觉主义认识论造成的对科学知识和权威的抗拒,以及它被政治化后演变为“民粹主义”或“部落主义”的认识论,拒绝任何确定事实的标准和模式;(3)以对外群体的敌意作为认知模式,形成党派之间的“认知极化”。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探讨如何在“认知的基础结构”语境下建设包括新闻生产在内的知识生产的认知秩序。
【关键词】认知秩序 认知权威 制度 制度化新闻业 认知的基础结构 后真相
【中图分类号】G210
本文要讲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理解知识生产的秩序?二是这个秩序在数字和社交媒体时代面临哪些挑战?前一点主要是在理论层面的讨论,后一点以讨论一些实证的经验研究为主。最后,本文以“知识生产秩序”为切入点,针对同样作为知识生产领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就其“失序”和“秩序重建”陈述一些相关的思考。
重新整理这些材料,我格外清晰地感到,自己讲的或者试图要讲的,很容易被看作是老生常谈:这都是常识性知识,哪值得一再唠叨?但是,如我之前在一篇文章(潘忠党,2018)中指出的,当作为我们日常知识储备、用以解读现实并生成理解的常识遭遇挑战,并因此需要重新提到前台来讨论时,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处在某种“失序”状态,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无所矩。若如此,重述常识、重建规章就不是祥林嫂式的絮叨,而是社会建设所亟需。
既然是重述常识,就难免讲些浅显的大白话,在一个时髦词汇层出不穷的学术环境下,这会显得缺乏“思想深度”,甚至有些“过时”。但是,言之有物和推崇学术时尚是两种不同的追求,虽然并非一定不相容,但时常会相左;思想深度并不来自无节制地引经据典,也不来自对公认“大师”的追崇。言之有物来自言之有据——经验证据的“据”,来自脚踏实地的现实关怀。对于新闻与传播学者来说,这就意味着选择经验研究,以及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展开理论升华,同时也意味着选择那些至少可能关照我们如何展开、提升和丰富公共生活的课题。
知识生产是有序的
我们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为例切入,探求其中可能蕴含的启迪。2022年10月23日,我在该报的网站上看到了这篇题为《他们的美国正在消失,如同特朗普,他们坚信自己被骗了》的报道。这是该报“民主面临挑战”系列报道之一,两位作者都曾获普利策奖,其中Michael H. Keller是专长计算新闻(computational journalism)的调查记者,David Kirkpatrick也是位调查记者,有担任《纽约客》事实核查员、报道阿拉伯之春、被《纽约时报》派驻华盛顿等经历。
两位作者知识背景和技能的组合,应是成就这篇报道的关键。报道以统计数据的视觉呈现、多张新闻照片和点面结合的文字叙事,展现了美国在得益于全球化数十年间一些小镇和乡村被忽略的现状。在这些地方,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变,从几乎全部为白人到不同程度(大比例甚至近半数)为非白人移民。这些地方的文化生活(譬如运动项目、节庆日的仪式、社区活动等)和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白人与非白人分享社会空间和地方行政权力。这些地方的经济曾经依赖制造业或采矿业,它们给这些小镇及附近的乡村提供了保障中产生活的稳定就业,但是在过去近30年间,这些行业萧条、企业撤离,留下的不仅是大面积失业,而且在有些地方是常年挖矿所遗留的黑肺病,雪上加霜的是,地方经济的衰退也使得本地的医疗服务得不到补充。凡此种种,令生长在单一白人中产社会、曾经沉浸于“美国梦”的本地居民深感失落。因此,特朗普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诉求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他们格外有吸引力:这些地方很多白人成为特朗普狂热的支持者,反映他们的情绪和意愿、代表他们的参众议员绝大多数也是白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包括8名参议员、139名众议员),不仅没有谴责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攻击国会山的暴动,而且投票拒绝认证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通过采用多种表现形态的生动叙事,这篇报道揭示了美国民主乱象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其中的经验材料分析、逻辑推理,与一篇扎实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论文并无二致,虽然它没有运用什么抽象的理论概念或提出什么理论。不仅如此,报道的网络版还提供了方法附录,详列这篇报道的数据来源、数据处理人员的名单、数据处理中的统计步骤等。
这些文本特征,无一不凸显了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 2018)所言:新闻实践(journalism)与社会学是相邻学科,①它们不仅研究和报道所面对的社会,而且都采用经验主义的取向。虽然提供的信息或知识类型不同、服务的直接对象不同,各自采用不同的运作程序、不同的语汇和话语风格,但它们遵循一些相同的认识论规范,譬如追求事实的客观和准确,践行专业群体同意且采纳的研究方法,而且相互引用对方、相互吸纳对现实的考察和洞见。
更进一步说,新闻实践和社会学都是知识生产的领域。当然,它们运作的场域有很大不同,新闻生产场域的他治力量更为强大(Bourdieu, 2005)。一个社会的知识生产领域还包括科学的基础和应用学科、学院和非学院(如政策咨询、市场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等,它们都以搜集各种经验材料、探寻各种未知、形成不同形态的理解和意义、建构社会的知识体系为核心职责。这些知识生产领域的集合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认知系统,有学者将其称为“认知的基础结构”(the epistemic basic structure)(Kurtulmus, 2020)。这些机构或领域各有特点,各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但它们共享一些基本的认知规范,各自以这些共同的规范为基础,形成符合其领域特性的专业文化和运作程序,其中包括资料或数据如何采集、分析及整合,结果如何报告,如何论证其中的知识宣称等。
一个社会必须有认知的社会分工(epistemic division of labor)。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有专家,在不同领域、各自担当不同角色的专家。但是,不同领域之间、专家和外行之间、学者和公众之间,须得在共享基本的认知规范这个基础上相互交流,对社会的“真相探寻和报道机构”按章运作持有基本的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分享信息、体现专家的公信力、采纳专家的建议、认可公共政策的正当性。譬如,我们身体不适会去请医生诊治并遵从医嘱;我们会关注气象预报,并根据对天气变化的预报调整自己的行动;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我们会遵守公共卫生的政策规定,哪怕这么做给自己带来极大不便。这些行为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具有良性结构和运作的社会认知体系,它是社会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Zagzebski, 2012)获得广泛认可并分布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基础。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才会有理由信任专家,相信他们直接或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也会对各种公共机构,如新闻媒体、疾控中心、各级环保部门、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等,持有必要的信心,通常称为“公信力”。有了这些,我们才可能展开相对理性、文明的公共生活(Chambers, 2021)。②
新闻业是这个知识生产体系中的一员,它的基本功能,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1948)所说,是“监测”,也就是观察、分析并及时报道社会状况,为社会相关各部门或行动者采取行动提供信息资源。③李普曼把这个机制称为搜集和提供社会状况的情报(Lippmann, 1922/2015)。新闻业相对独立的知识探寻和真相追求,在整个认知分工体系中至关重要,它可监督各个知识生产领域,它可传递可靠的信息,通过所传递的信息和自身的运作,它可影响整个社会的公信力水平及其分布。新闻业若被资本或权力所挟持,这个体系的运作秩序就可能被破坏(Schiffrin, 2021)。
简单地说,新闻生产是有序的、遵循规范的。这似乎是不必重复的话,但是,经过各种“建构主义”思想的洗礼,再经过“后真相”的种种病灶给人带来的所谓“验证”,似乎我们对这常识性表述有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我此前已多次讨论了新闻业需要坚持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实践的专业规范(潘忠党,2021),不再重复。这里我想特别探讨的是新闻生产中的认知秩序。
这个秩序,指特定形态和内容的关系,包括新闻从业者与新闻源、新闻报道对象的关系,也指展开这些关系、依赖它们采集和制作新闻的行事规则,还指新闻媒体内部围绕新闻生产的组织关系和运作规则。构成这秩序或使其落于实处的,是新闻编辑室内的约定俗成、师傅带徒弟式的代际传递的规矩(Breed, 1955),是从业者共同遵守的职业理念,以及很多成文的政策规定或结构性的关系。我在此要特别强调专业机构内部以及专业机构与社会整体约定俗成的信念和规矩,这是因为,第一,这些是新闻业自主力量的理念和价值源泉;第二,它们与组织和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力量之间存在着必要的张力。
美国新闻学者休梅克和瑞兹(Shoemaker & Reese, 2014)曾提出“影响的阶层模式”(hierarchy of influence model),以概括由不同分析层级组成的新闻业运作秩序。当然,在“新闻的社会建构”这一话语框架内,他们将其表述为各个层级影响新闻选择和制作的力量。用布尔迪厄的语言,这其中很多是新闻场域的他治力量,有扭曲事实、服务特殊利益的作用。这样的论述路径,很容易与福柯所说的“真相”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实现手段之一等论断(Foucault, 1980)发生共鸣。但在我看来,这种福柯导向的解读未必可取,因为泛权力或权力泛化的思路,容易导致认知的虚无主义,包括否定经验的事实和真相本身。如此即等于取消作为知识的新闻、消解对于新闻优劣的评价和区分。
讨论这其中的“秩序”维度,既是抵御这种虚无主义的认识论,也是针对社交媒体时代“公共空间”的失序现象(Bimber & de Zúniga, 2020),重振制度化新闻业(the institutional press)的关键(Reese, 2021)。所谓制度化新闻业,包括但不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机构新闻媒体”(在我国大致就是国有新闻媒体),它指的是遵循以认知秩序为基础的制度(institutions)而运作的新闻业,包括机构和实践。按照制度主义的基本定义,这里的制度包括成文或正式的规章,也包括在更大范围、弥漫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非正式的约定(Lauth, 2015)。但是,制度又往往跟机构密不可分,因此常常被译作“机构”。
瑞兹(Reese, 2021:57)将这些元素集合起来,对institution提出了一个包含甚广的界定,其中显然包含了制度和机构这两重含义:
一个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成型为一个相互嵌入的网络,由规则、活动、角色、技术、规范和群体共享的意义框架所组成,它们共同维系制度的内在统一、持久性,及其价值。
我们可将这些元素浓缩为秩序,包括行动的规则和结构性的关系。如同瑞兹(Reese,2021)指出的,这个界定下的制度或机构,与一个专业所遵循的专业价值观相匹配,为社会生活的展开所必需。因此,特定内涵的制度值得维护,构成它的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值得在具体社会条件下一再阐释,并与它所激发、支持并维系的实践相联系。对这“特定内涵”,我曾多次论述,并将之与以专业主义模式为规范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在社交媒体和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所能够并应当扮演的角色联系起来(参见潘忠党,陆晔,2017)。
需要再聚焦探讨的是“认知权威”。我曾引用美国新闻学者如卡尔森(Carlson, 2017)的论述探讨“新闻业的权威”,认为它是一种认知的权威,其基础是掌握了第一手、可验证的经验观察,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遵循逻辑的解读。而这些观察的获取,如本文开头引述的《纽约时报》报道所呈现的,遵循了特定的规则、启用了具有认知验证作用的关系网络(如可靠的新闻源、真实在场的报道对象、数据搜集和处理的专家等),因而具有令人信服的事实性(facticity)。④由此可见,新闻业的认知权威,根植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落实为业内共识,以及共同遵循的行事规则和程序。这些元素及其相互勾连皆来自经验科学的求知和求真模式。也就是说,新闻业的认知权威,是“赛先生”的认知和伦理权威(Brown, 2009)在新闻业这一特殊“真相探寻”行业的体现。而这样的认知权威,正面临来自社交媒体和党派新闻媒体的挑战(Benkler et al., 2019;Bimber & de Zúniga, 2020),我们必须加以维护。
就新闻学研究而言,这也是在各种“建构主义”盛行多年后的一种反思。对我很有启发的是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案例。晚年他反思自己所开启并参与塑造的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领域,尤其是该领域对于社会认知意识的影响,以及后者对一些民主乱象的可能滋养,包括“后真相”一词所概括的社会状态;他担心自己参与搭建的社会建构主义话语正在被另有图谋的行动者所篡用,于是不仅反思“批评的限度”(Latour,2004),而且以捍卫科学及其所代表的认识论为新的使命。在一次访谈中(de Vrieze, 2017:159)他说:
我们必须重振科学的权威。这也许是与当年我们展开对科学的研究时相对立的议题。现在,科学必须重新赢得尊重。但是,答案(与当年)却是一致的:我们必须呈现科学展开的行动过程。
显然,反思社会建构主义并不是断然否定它,而是看到它作为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路径虽然帮助我们分析知识生产秩序中的问题,包括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运作,但是并不能消解以经验科学为基石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规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行事规则、运作程序,和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简单地说,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及其认识论是趋向经验主义,而非虚无主义。
综上,知识生产的秩序,依据的是“赛先生”的逻辑及其认知权威。这是一套相互嵌入的制度,形成体系,并结构化为社会的“认知分工”系统,成为我们日常获取知识、形成判断、作出选择、采取行动的基本秩序。⑤
难辨和不辨真假:社交媒体和党派极化时代的挑战
这个秩序正面临挑战,在一些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失序”。在不同社会,因为不同的历史境况,挑战的来源、构成和指向有所不同。受个人研究领域的局限,本文主要讨论认知心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的一些相关研究,它们针对的主要是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揭示的是跟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党派政治极化密切相关的“失序”现象(Bennett & Livingston, 2018)。
第一个方面的失序状态是信息生态中信息杂芜、真假难辨,挑战人们的认知信任(Mercier, 2020)。这是数字媒体时代的一个突出问题,但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问题。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社交媒体带来了“未经编辑的公共空间”(the unedited public sphere) (Bimber & de Zúniga, 2020)。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即为行动者提供的行动可能性,包括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发布者,而且可能隐蔽信息出处、虚构信息发布者身份、操纵社会关注和偏好程度的指标等,落实为人们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这些行为的广泛出现,可能造成认知秩序的混乱、观点的市场无法正常运行,因为,辨别真伪变得格外困难,公信力的基础遭到侵蚀,知识生产的权威遭受削弱,公众展开理性商议所必须的通用货币——事实,以及分布于认知分工体系中的认知信任(epistemic trust)——贬值。在美国,数字技术和党派极化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由党派利益驱动、以迎合不同受众群体的宣传和操纵为诉求的众多渠道,它们参与构成了当下的信息生态,在这里,党派诉求压制事实呈现,党派政治高于事实准确。在这些渠道的包围下,主流新闻媒体,因为要追求独家新闻和党派平衡,极易受到政治运作策略的操纵,失去自己的独立判断。在这样的信息生态中,公众难有判断真伪的基础,难以践行检验真假的共享方法(Benkler et al., 2019)。
这些宏观层面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除了媒体环境和信息生态的上述蜕变外,我们还可以在微观层面,了解人们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认知过程,并从中看到数字媒体带来的挑战。在这个层面,很多人关注选择性接触、关注和接收,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关注的是,个体大多在一种低认知卷入(cognitive involvement)的状态下使用媒介,经常情况下,人们会以“不经意地学习”(inadvertent learning)方式从媒介渠道获得信息片段。这种个体与信息渠道之间的连接关系并非一定都是负面的,因为“偶发性学习”(incidental learning)是信息在社会扩散的必要元素,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可能有助于缩小因教育水平或兴趣程度而造成的“知沟”(Shehata et al., 2015)。但是,低认知卷入也意味着个体趋于懒惰,不能积极调用其已有的认知资源分析并鉴别所摄入的信息。譬如,在一项研究中,认知心理学家蓬尼库克和兰德(Pennycook & Rand, 2019)以两个网上实验的证据显示,面对大量脸书新闻帖子,参试者个人的党派倾向并不能帮助他们鉴别其中的真伪,无论新闻标题是否与他们个人的党派倾向一致,但是,那些倾向于展开反思式思维(reflective reasoning)——即以逻辑思考和判断来检视并矫正直觉反应的人,则能更好地辨别真假新闻。在另一项研究中,采用类似接触并判断脸书新闻帖子的方法,蓬尼库克等(Pennycook et al., 2020)展开了两项线上实验,以考察人们对有关新冠病毒的真假信息的判断和分享。其中一项实验显示,人们相对比较成功地辨别真假信息,但这并不一定体现为他们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真实信息,人们的信息分享行为可能还有其他社交动机的驱动(Kümpel et al., 2015)。蓬尼库克等在他们的第二项实验中显示,只要有一个辨别真假信息的练习提醒人们,他们就会相对更多地分享真实新闻,降低分享虚假新闻的概率。
可见,我们每个人的认知卷入和对信息真假保持警觉,在缺乏职业把关人维护信息构成的数字和社交媒体空间,成为去伪存真的一道格外重要的防线。蓬尼库克等人的研究,以及其他很多学者展开的“纠偏”(debiasing)和提升“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的研究(Lewandowsky et al., 2012),为我们就如何应对这方面的“失序”提供了一些可应用的理论资源。这也就是说,真假难辨形式的失序,不一定导致对于规范性认知模式本身的颠覆,因此,各种帮助人们提升其认知警觉(epistemic vigilance)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素养培育有可能收到一定成效。
与真假难辨的信息生态直接关联的是第二个方面的失序状态,体现为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认知权威被消解,以“赛先生”为师的认知模式被部落主义或民粹主义的认识论(tribal or populist epistemology)所取代。通俗地说,就是以“民科”替代科学。
这种与科学对立或至少抵御科学的认识论,可能表现为两种关联密切的形态。第一种表现为基于日常生活体验的“直觉主义”倾向(intuitionist orientation),它是一种思维风格,往往在教育程度不高、处于社会经济中下层的群体中格外普遍。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缺少科学素养的培育,更缺少获取并运用这一素养的生活缘由。他们持续地处于高度不确定、不安全的生活处境,在某种随时陷入困境的边缘;与制度的受益者或维系制度的“精英”相比,他们自觉是“他者”,或者被看作“他者”。因此,他们有一种根植于自己生活体验的与“精英”对立的定位,但又直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的道德力量;他们往往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体验更为可靠,或更具有认知的确定性。这种体验,伴以民间信仰和/或宗教信仰所提供的论证话语以及社群支持,使得他们形成“直觉主义”的思维风格。
美国政治学家奥利弗和伍德(Oliver & Wood,2018)在《着魔的美国》(Enchanted America)一书中,通过分析多项对美国选民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梳理了直觉主义思维风格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直觉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风格分属不同群体,这是美国深层次的“政治分裂”。这两种思维方式,代表了在多个方面的两种不同倾向:依赖经验证据抑或个人直觉,运用逻辑推理抑或情感和信仰,尊重事实抑或(宗教或政治的)层级权威,保持认知开放抑或认知封闭。调查显示,倾向于直觉主义思维的人,同时也倾向于相信神幻或超自然的力量,相信民间科学,倾向于政治上保守和传统价值观念,倾向于相信阴谋论,倾向于白人身份认同。在新冠疫情席卷美国期间,这些倾向也表现为反对社交隔离、公共场合佩戴口罩、接种疫苗等针对公共健康的管理措施。
第二种表现是这种直觉主义思维的政治化,它与强烈的、近乎全方位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相结合,形成所谓的“部落主义认识论”(Greene, 2021;Roberts, 2017)。这种结合首先是一种党派政治的策略运作,在美国的政治场景下,它表现为保守主义势力发展党派媒体、改造共和党并推动其执行保守主义政策的政治运动(Jamieson & Cappella, 2010)。服从党派政治的逻辑,“部落主义认识论”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以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话语逻辑,讲述普罗大众与精英、保守派与非保守派、共和党与民主党等(隐含在表层之下的还有白人与非白人群体对立的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比如,著名保守派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多次在他的节目和写作中宣称,美国有两个不同的“宇宙”,一个是现实的宇宙,一个是“谎言的宇宙”,前者由美国人民、保守派、共和党人构成,后者的构成则是政府、学术界、大众媒体和科学;前者信奉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而后者是敌视美国的“全球主义者”(the globalists)。
这种“部落主义认识论”不仅与他们所认定的“全球主义者”为敌,而且反对任何普适主义(generalism或universalism),如林博等服务政治的话语运作,不断强化“我族”或者“内群体”(in-group)的视角和利益、个人的体验和直觉作为真相或事实判断的可靠基础,正当化认知的自负(epistemic arrogance),也就是独掌真理的自以为是态度。如此形成了一种风气和政治文化,美国哲学家麦克·林奇(Michael Lynch, 2019)将之概括为“无所不知的社会”(know-it-all society)。这个风气之形成,也是信息生产和流动更加民主化、更加开放的一个巨大副作用,也就是认知过程的民粹化。民粹主义认识论与科学认识论相冲突。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认知的自我中心立场(epistemic egocentrism):我感知的世界是真实的,我相信的权威才是真权威,我不需要反思自己可能的偏见,因为我没有偏见,我是公正、理性的具身;而他人,那些不同意我所感知的世界的人,要么是愚蠢,要么是上当受骗,要么就是不可救药地心怀偏见。这种倾向,被心理学家们概括为“天真的现实主义”(naive realism)(Moskowitz, 2005)。但是,当这种心理倾向被政治逻辑所裹挟,或者说被政治冒险家们所鼓动,就可能成为一种认知的恶习(epistemic vice),即认知的自负,一种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唯我独尊的认知态势,这使得民主商议和真理探寻无从展开(Lynch, 2018)。
认知失序的第三个方面以前一个为基础,并增添了党派之争中的群体间动态,以及运作其中的情感机制。我将这个表现概括为“认知的极化”(epistemic polarization),它是以党派归属为基础的政治极化逻辑的一个延伸,或者就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政治极化可以有不同的构成,一种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同,表现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策选择差异增大,两党支持者们的态度差异难以调和。另一种是以党派归属为基础,党派之间的互动以群体间动态关系(intergroup dynamics)为杠杆,其中既有“内群体”的认同和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包括亲近内群体或以内群体为起点的认知偏好(epistemic bias),也有“外群体”的负面化(out-group negativity),包括将外群体视作“他者”,夸大其立场的极端倾向、放大其与内群体立场的距离,强化针对外群体的负面情感,甚至道德化内外群体的差异,认为外群体在道德上有亏。这种以党派身份为基础的政治极化,并非一定表明两党之间在政策选择甚至意识形态立场上有很大差异,而是以对外群体的负面或敌意情绪为基础的内外区分,因此被称为“情感极化”(Iyengar et al., 2019),它造成了美国社会当下的局面,即选民们在很多议题上观点相似却无法共处(Mason, 2015)。有些学者把这种以群体身份认同为基础、以有你无我的敌对逻辑展开党派间互动的政治极化概括为“政治宗派主义”(Finkel et al., 2020)。
表现在认知范畴,“政治宗派主义”就是两党支持者们各守其党派归属,各自坚持自己的“事实”以及事实评判的标准,坚信自己认定的专家和信息渠道(包括新闻媒体)。更广义地说,两党支持者们以党派身份统领其他身份(superordinate identity),坚持这个身份带来的认知标准(epistemic criteria),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认知信任。如此一来,党派之间的政治极化不仅是情感上的相互敌视,而且是在认识论层面运作于不同的“认知宇宙”(epistemic universes)(Marks et al., 2018)。
我和我的博士生涂方静在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中,通过分析皮尤研究中心搜集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这个现象。这个调查数据是皮尤研究中心设立并维系的“美国趋势样本”(The American Trend Panel),样本量1万人左右,来自美国50个州,统计加权后对美国选民整体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我们分析的数据,来自对这个样本在2019年9月到2020年9月这12个月期间展开的5次问卷调查,其中前两次发生在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前,后三次是在疫情期间。我们采用在2019年9月的调查中对自变量的测量,包括被访者的党派归属、对他党敌意情感、对他党成员人格缺陷等的评价;采用在其他4次调查中对各种认知信任和信息可靠度评价的测量作为因变量,这些测量包括对全国性主流新闻媒体、地方新闻媒体、科学家、医生、疾病防控中心、地方政府官员、特朗普当局等的信任,对来自这些渠道的新冠疫情信息的评价等。
结果显示:第一,不出所料,两党的支持者们分属不同阵营,在所有这些渠道信任和信息评价上展现了显著的“党派鸿沟”;第二,对他党的敌意——包括情感和人格评价——扩大了“党派鸿沟”;第三,这个敌意情感的强化作用,在共和党支持者们当中比在民主党支持者们当中程度更高;第四,对于渠道的信任——在更抽象的概念化层面,这是认知信任的一部分——是党派身份影响新冠信息评价的中介机制。
这些结果说明,新冠疫情自从2020年初开始在美国蔓延后,这个公共卫生危机在党派极化的政治环境中立即被政治化。正是由于认知极化的机制,即在政客和媒体上党派吹鼓手们的操控和推动下,人们以党派身份为基础、以敌视对立党派及其支持者的情绪为强化剂,而形成认知判断,使得通过民主商议达成共识、在共识基础上采取有益于全民的公共卫生举措变得难以实现,所以才有了美国2020—2021年的抗疫乱象和民主乱象。
这里描述并分析的三种认知失序现象,依据的是对美国社会现状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至少在方法论层面追求的是揭示普适的规律,因此,至少它们能为我们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失序问题提供一些启示。第一种失序的表现,即公众对于辨别真伪缺乏足够重视、在个体获知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管控(self-regulation),显然不是仅限于某个社会的现象。它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活跃的信息环境中格外凸显,这在我国也不例外。第二种失序的表现是“民粹主义”或“部落主义”认识论盛行,在中国也有所体现,虽然具体形式与美国不同。对于以个人体验、本地观察和“民科”权威对抗科学知识、批判专业人士等现象,我们大多耳闻目睹过;通过如微信群、朋友圈分享未经验证甚至完全无法验证的信息,宣扬某种偏方的神奇效果,是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以网络和社交媒体为渠道,各种“民科”、“民粹”的知识宣称得以肆意流通,对抗科学知识及其认识论,我们大约也不陌生;而对制度化信息渠道——新闻媒体——的失职和失声,或者网络和社交媒体流传的信息造成“新闻反转”、削弱“认知信任”的基础等现象,不少学者和业界人士也已有分析。至于第三种失序的表现,显然更流行于美国多党政治体制,但是,基于内外群体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群体间关系的“部落主义认识论”,则并不仅限于美国,在我国各种领域也有所表现。当然,这些问题还需要展开进一步的经验考察,才能得到更加准确的结论。
结语:不限于新闻生产的认知秩序
新闻业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行业,这是从李普曼(Lippmann, 1922/2015)到帕克(Park, 1940)都已论述过的话题;新闻业是描述经验现实的一个知识生产行业,对此,包括塔克曼(Tuchman, 1978)和甘斯(Gans, 1980)在内的社会学家们也展开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但是,新闻业,如同研究它的新闻学,还有众多基础和应用的经验研究领域,以及其他搜寻经验观察、发掘其中规律或真相的社会实践(譬如市场调查、司法调查),都是经验知识的生产领域、真相探寻的行业,都需遵循社会共享的认识论规范。对此,中文学界的论述至少不够突出和系统。将新闻业置于这样一个知识获取和扩散的体系中展开规范层面的探讨和经验层面的考察,分析它如何践行并以自己的实践形塑社会的认知秩序,这在新闻与传播学界不够凸显,至少与伴随网络和社交媒体而发生巨变的信息生态相比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试图提出一个研究议题,以系统地探索如何可以有效地应对包括上述三种形态在内的认知失序。
本文还试图反思我们知识构成中的各种建构主义话语。知识生产是个社会的过程,受制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真相生成有赖于一个社会特定的“真相体制”(truth regime)(Foucault, 1980);关于经验现实的知识,或者说社会现实,是“社会建构”的产品;关于现实或真相的宣称,常常是服务权力和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这些都是我接受的理论观点,当然是在特定语境下,而非不假思索、漫无边际地接受。需要警觉地反思的是契合的语境和必要的限制条件,而这些都跟“事实”和“真相”的概念有关。在我看来,这些论点部分地构成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路径,但它们并没有消解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和真相,其中的经验研究更是以其自身的实践,表达了对事实与真相之存在和可知的认识论预设;⑥
其次,这些论点及其所总结的经验观察,恰恰也论证了经验知识(在此姑且将之用作事实和真相的同义词)生产遵循可知的秩序展开这一基本论点。
这里的秩序,即是认知的秩序,我将之简单地统称为制度。就新闻形态的知识生产而言,这是新闻生产的制度(Reese, 2021);但更广义地说,这是知识生产的秩序。它包括:(1)约定俗成或成文的规范与规则;(2)行事的程序或流程;(3)将这些具身为社会结构的组织及其内部关系;(4)令这些元素有效而且合理化的其他社会关系,譬如记者与新闻源的关系、新闻媒体组织与其他组织或团体的关系等;它们共同使得在具体社会情境下的新闻生产过程(5)有“常规”可循;如此构成的“常规”,体现了(6)特定社会共享且相对稳定的价值观(enduring values)( Gans, 1980),包括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事实/真相观,以及检验事实/真相的认识论原理和方法步骤。用劳奇(Rauchi, 2021)的话说,这些价值观、原理和认知规则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的“知识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有此内核的制度,如瑞兹(Reese, 2021) 所说,值得维护,且必须维护。
那么这样的“宪章”从何而来?它的权威和它所赋予的权威具有什么性质?简单的答案是,“知识的宪章”来自各个专业生产行业约定俗成的专业共识,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一个专业场域的自治力量(Bourdieu, 2005);各个知识生产行业在认知分工体系中各领其专门领域,在真相探寻过程中,功能性地形成认知维度的相互依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相互信任及合作(Tam, 2021),由此而构成一个社会的“认知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为每一位认知自主的个人,即消费者、公民和生活世界的行动主体,提供了机会,以获取可靠(包括事实准确、合乎逻辑)的知识,参与社会的理性讨论,以此形成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善(the common good)的界定,以及实现二者的行动步骤,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行动选择(Kurtulmus, 2020)。
显然,在理想世界中,这个基础设施相对独立于经济和政治体系,它的基本框架,即劳奇所说的“知识的宪章”,是商议形成的约定,体现为各个知识探寻领域的内部自治所倚赖并采用的业内行事规范(譬如,学界的同行匿名评审、开放科学等规范)。一个行业的认知权威,来自其行业自治的透明和有效程度,来自业内成员遵循行业规范的表现。这种专业领域内部和各领域相互之间所遵循的规范,还须成为并体现全社会所基本接受的认知规范,成为如何获知、交往的共识,这才构成所谓“知识的宪章”,由此各领域专业人士才可能在社会具有认知权威;规范形成的专业自治和社会协商机制,既维系“认知的基础设施”,也保障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中的民主商议;由此建立“民主的权威”(Estlund, 2008),并反过来保障各知识生产专业的认知权威。
因此,提出“认知的秩序”这个命题,即是重新呼唤“赛先生”和“德先生”,以之提升直觉主义的认识论,摒弃部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认识论。落实在日常的交往,就是使我们少为谎话、废话、空话、官话、胡话所累,⑦使我们可以更多地相互信任,使我们更加愿意并且可能信任专家、信任我们可能托付自己或家人性命的专业医护人员,使我们至少能相对信任来自专业信息渠道(包括新闻媒体)的信息,并有机会展开“明亮的对话”。■
注释:
①通常journalism在这个语境下可译作“新闻学”,但是,它跟社会学或其他基础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它首先是新闻生产及其实践,“新闻学”是对之的研究。甘斯指的是前者,即以新闻采写为手段呈现社会。本文讨论的也是前者,虽然我展开讨论这个行动和过程属于后者。因此,本文用“新闻实践”或“新闻业”指称journalism。
②这并不等于说,公共生活的展开,或更进一步民主过程的运作,必定建立在已经验证的事实基础之上。谎言或不实报道在历史的变革中,包括民主化的过程中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Rosenfeld,2019)。但是,此处讲的是,第一,通常而言,谎言或无视真相不能成为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础;第二,即便在谎言被误以为真的特定时刻,也是因为社会大多数人共享的认知规范在起作用,被误导而做出了误判。“指鹿为马”虽可暂时成功,但它绝成不了可虚位事实或真相的证据。
③拉斯韦尔是位结构功能主义者,运作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中。在当下中文学术话语中,这个出身以及由此而来的论述足以被鄙视和批判。其实我们不必如此。来自美国的东西未必一定携带了美帝霸权,搬自欧洲大陆的学说同样也是需要消化的舶来品;论述现代化过程的社会理论未必一定就已陈腐到必须扬弃,闪耀着后现代或其他后学时尚的论断也同样需要我们探寻其生成并获取意义的特定语境。针对不知何为范式就大谈范式革命或者纯粹为思想的前卫而大谈范式创新的学术运作,我建议践行者们先缓一缓,静下心来,开放视野,观察日常现实,采纳自己真理解了的、适合所展开研究的理论和概念,提出并解答问题。科学研究是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而非脱离经验世界的不间断“革命”或“创新”。在这个过程中,理论,无论来自何方,都应当是我们运用的资源,而不是我们追崇的偶像或信条。
④参见Tuchman(1978)对“事实性网络”(web of facticity)概念的阐释,以及对此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如何体现的描述。塔克曼(1978/2022)。《做新闻》(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⑤也许有人会怼道,“我赞成科学,但我反对科学主义。”这话听上去很睿智,我也大致赞同。但是,我觉得需要语境,需要更加逻辑缜密的理解。现代科学为我们提供的,除了关于经验世界的可检验知识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认识经验世界、检验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的认识论模式。但它不是也不宣称自己是人类知识的唯一模式,或者科学真相(或真理)是唯一形态的真相(或真理)(参见Baggini, 2017)。将“科学”和“科学主义”相对立的这种表述,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话语策略,为的是为独特主义的(particularist)甚至是反科学的认识论正名。它的一种庸俗表达是,“人文学科啊,见仁见智吧!”这听上去也貌似无大错,但是,显然真相、事实,尤其是对知识宣称可能共享的评判标准和必要,被釜底抽薪了。
⑥当然,它们也没有消解事实或真相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本体论领域的讨论,譬如,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2005)到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 2006)的“集合论”(assemblage theory),更趋于形而上,这不仅超出本文论述的范畴,而且也超出了我的学术能力。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这些理论都强调关系、关联,以及展开其中并形塑它们的行动,由此而形成动态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是具有高度哲学抽象的社会理论而非关于本体论的哲学理论,这大约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⑦对新闻文本和学术文献中的这些认知失序症状,我们都不陌生。至少在本文针对的领域,简化但又婉转地说,造成它们的是新闻和学术的生产遵循公关推广逻辑而展开的实践模式,是体现部落主义认识论的知识生产资源的配置结构。
参考文献:
潘忠党(2018)。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新闻记者》,(5),4-16。
潘忠党(2021)。走向有追求、有规范的新闻创新——新闻业的危机及认知的危机。《新闻记者》,(11),8-20。
潘忠党,陆晔(2017)。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10),97-124。
Baggini, J. (2017). A short history of truth (Kindle e-book edition). London: Quercus Editions, Ltd.
Benkler, Y.FarisR.& RobertsH. (2019). Network propaganda: Manipul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nett, W. L. & Livingston, S. (2018). The disinformation order: Disruptive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3(2)122-139. DOI: 10. 1177/0267323118760317
BimberB. & de ZúnigaH. G. (2020). The unedited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22(4)700-715. DOI: 10. 1177/1461444819893980
BourdieuP. (2005). The political fieldthe social science field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n R. Benson &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pp. 29-47). London: Polity Press.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4)326-335.
Brown, T. L. (2009). Imperfect oracle: The epistemic and moral authority of science.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arlson, M. (2017).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sS. (2021). Truthdeliberative democracyand the virtues of accuracy: Is fake news destroying the public sphere? Political Studies69(1)147-163. DOI: 10. 1177/0032321719890811
DeLanda, M. (2006).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 Continuum.
De Vrieze, J. (2017). “Science war” veteran has a new mission: Bruno Latour was a thorn in scientists’ sides. Nowhe wants to rebuild trust in their work. Science358(6360)159. DOI: 10. 1126/science. 358. 6360. 159
Estlund, D. M. (2008). Democratic authority: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nkelE. J.Bail, C. A.Cikara, M.et al. (2020). Political sectarianism in American: A poisonous cocktail of othering, aversion, and moralization poses a threat to democracy. Science360(6516)533-536. DOI: 10. 1126/science. abe1715
FoucaultM. (1980).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p. 109-133).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ansH. J.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GansH. J. (2018). Sociology and journ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ontemporary Sociology47(1)3-10. DOI: 10. 1177/0094306117744794
GreeneA. R. (2021). Tyrannytribalismand post-truth politics. In M. Hannon & J. de Ridder (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pistemology (pp. 74-84). London: Routledge.
Iyengar, S.Lelkes, Y.Levendusky, M.Malhotra, N.& Westwood, S. J.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2129-146.
JamiesonK. J. & Cappella, J. N. (2010). Echo chamber: Rush Limbaugh and the conservative media establish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ümpelA. S.KarnowskiV.& KeylingT. (2015). News sharing on social media: A re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on news sharing userscontentand networks. Social Media + SocietyJuly-December1-14. DOI: 10. 1177/2056305115610141
Kurtulmus, F. (2020). The epistemic basic structur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7(5)818-835. doi: 10. 1111/japp. 12451
LasswellH. 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L.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pp. 37-51).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LatourB. (2004).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30225-248.
Latour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uth, H. J. (2015).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J. Gandhi & R. Ruiz-Rufino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p. 56-60). Milton Park, UK: Routledge.
Lewandowsky, S.EckerU. K. H.SeifertC. M.SchwarzN.& Cook, J. (2012). Misinformation and its correction: Continued influence and successful debia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3(3)106-131. DOI: 10. 1177/1529100612451018
LippmannW. (1922/2015). Public opinion. 2015 eBook editionStart Publishing LLC.
Lynch, M. P. (2018). Arrogancetruth and public discourse. Episteme, 15(3)283-296. doi:10. 1017/epi. 2018. 23
Lynch, M. P. (2019). Know-it-all society: Truth and arrogance in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arks, J.CoplandE.LohE.Sunstein, C. R.& Sharot, T. (2019). Epistemic spillovers: Learning others’ political views reduces the ability to assess and use their expertise in non-political domains. Cognition18874-84.
Mason, L. (2015). “I disrespectfully agre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tisan sorting on social and issue polar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59(1)128-145.
Mercier, H. (2020). Not born yesterday: The science of Who we trust and What we believ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skowitz, G. B. (2005).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OliverJ. E. & Wood, T. J. (2018). Enchanted America: How intuition and reason divide our politics. Chicago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kR. E.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5(5)669-686.
Pennycook, G. & Rand, D. G. (2019). Lazy, not biased: Susceptibility to partisan fake news is better explained by lack of reasoning than by motivated reasoning. Cognition18839-50. https://doi. org/10. 1016/j. cognition. 2018. 06. 011
Pennycook, G.McPhetresJ.ZhangY.Lu, J. G.& Rand, D. G. (2020). Fighting COVID-19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scalable accuracy-nudge interven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31(7)770-780. DOI: 10. 1177/0956797620939054
RauchiJ. (2021). The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 (Kindle e-version).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eese, S. D. (2021). The cri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press.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
Roberts, D. (2017). Donald Trump and the rise of tribal epistemology: Journalism cannot be neutral toward a threat to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it possible. Voxhttps://www. vox. com/policy-and-politics/2017/3/22/14762030/donald-trump-tribal-epistemology.
Rosenfeld, S. (2019). 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chiffrin, A. (Ed. ) (2021). Media capture: How moneydigital platformsand governments control the n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ehata, A. HopmannD. N.Nord, L.& Hoijer, J. (2015). Television channel content profiles and differential knowledge growth: A test of the inadvertent learning hypothesis using panel dat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32377-395. DOI: 10. 1080/10584609. 2014. 955223
Shoemaker, P. J. & ReeseS. D. (2014). 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 New York: Routledge.
Tam, A. (2021). A case for political epistemic trust. In K. Vallier & M. Weber (Eds. )Social trust (pp. 220-241). New York: Routledge.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Zagzebski, L. T. (2012). Epistemic authority: A theory of trustauthorityand autonomy in belief.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潘忠党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本文根据2022年11月12日作者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研究工作坊”的发言,以及同年12月2日在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与数字社会研究工作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