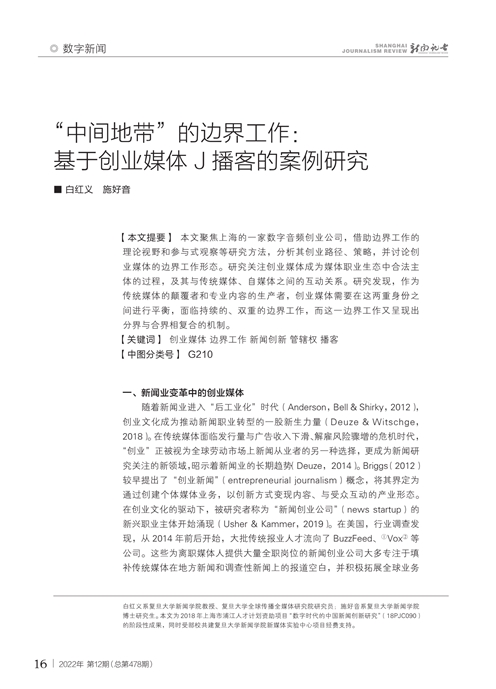“中间地带”的边界工作:基于创业媒体J播客的案例研究
■白红义 施好音
【本文提要】本文聚焦上海的一家数字音频创业公司,借助边界工作的理论视野和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分析其创业路径、策略,并讨论创业媒体的边界工作形态。研究关注创业媒体成为媒体职业生态中合法主体的过程,及其与传统媒体、自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作为传统媒体的颠覆者和专业内容的生产者,创业媒体需要在这两重身份之间进行平衡,面临持续的、双重的边界工作,而这一边界工作又呈现出分界与合界相复合的机制。
【关键词】创业媒体 边界工作 新闻创新 管辖权 播客
【中图分类号】G210
一、新闻业变革中的创业媒体
随着新闻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Anderson, Bell & Shirky, 2012),创业文化成为推动新闻职业转型的一股新生力量(Deuze & Witschge, 2018)。在传统媒体面临发行量与广告收入下滑、解雇风险骤增的危机时代,“创业”正被视为全球劳动市场上新闻从业者的另一种选择,更成为新闻研究关注的新领域,昭示着新闻业的长期趋势(Deuze, 2014)。Briggs (2012)较早提出了“创业新闻”(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概念,将其界定为通过创建个体媒体业务,以创新方式变现内容、与受众互动的产业形态。在创业文化的驱动下,被研究者称为“新闻创业公司”(news startup)的新兴职业主体开始涌现(Usher & Kammer, 2019)。在美国,行业调查发现,从2014年前后开始,大批传统报业人才流向了BuzzFeed、①Vox②等公司。这些为离职媒体人提供大量全职岗位的新闻创业公司大多专注于填补传统媒体在地方新闻和调查性新闻上的报道空白,并积极拓展全球业务(Jurkowitz, 2014),由此成为西方新闻研究的前沿议题。
相对而言,创业文化在中国新闻业内的生发情况与西方大有不同。由于对新闻生产执照的发放有严格限制,专业新闻的采制很难在“非公资本”的初创公司中完成。大部分退出机构、成立创业公司的媒体人,基本上都要“与新闻告别”。因此,中国的“新闻”创业实践整体上较为零碎、分散,学术界定也较为模糊。既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创业新闻”表现出聚焦垂直领域(niche)、行业趋势(industrial trends)、海外新事(newness from overseas),从而规避禁区的特点(Wang, 2019; Deng & Yan, 2022)。还有学者使用“脱媒主体”(杨保军,2015)、“传媒创业”(曾繁旭,王宇琦,2019)、“线上新闻作坊”(李东晓,2019)等概念来指涉这部分脱离专业新闻机构的媒体内容生产者。就中国本土的情况来说,“新闻创业”确实面临着一定的现实瓶颈,而“内容创业”又明显受到了传统新闻业资本和惯习的介入与影响。因此,借鉴曾、王所提出的“传媒创业”概念,本文使用“创业媒体”(media startup)一词来概括当下介于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本土传媒创业形态,并与英文学界的“新闻创业公司”这一研究概念进行比照和转化。
对媒体创业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新闻职业话语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反思。不少研究将创业视为传统新闻业转型和超越的一种形态,关注其中商业主义与专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Deuze, 2017),或将创业媒体看作“创新推动者”(agents of innovation)(Carlson & Usher, 2016)。Chadha(2016)发现,创业新闻工作者在积极地创造全新职业身份的同时,仍保留对传统专业新闻的职业认同,揭示了创业新闻职业主体身份建构和认同形成的复杂性。近年涌现了更多聚焦全球创业媒体案例的研究,考察其内容生产与传统新闻室的关系,及其构筑自身职业地位的话语和实践(Stringer, 2018; Wagemans, Witschge & Harbers, 2019; Chew & Tandoc, 2022)。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学者使用“先锋”(Hepp, 2016; Hepp & Loosen, 2021)、“超越新闻”(Deuze & Witschge, 2020)等概念来统摄以创业组织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职业形式,强调要对传统新闻职业范式之外的“其他路径”(other ways)进行全面认识,以“生成”(becoming)的动态视角破除“二元”(业内/业外)局限(Deuze & Witschge, 2020: 32)。
尽管制度环境和市场生态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者们也关注到创业思维和创业组织为新闻业带来的变化。不少学者关注到传统媒体机构内部和外部媒体市场中的多个创业媒体案例,讨论其商业模式、新闻室文化转型程度等,进而追问其对新闻职业文化的影响(Zhang, 2019; Deng & Yan, 2022; Fang & Repnikova, 2022)。然而,由于中国创业媒体的地位模糊,大多数创业者难以进入主流的专业新闻话语体系,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创业模式选择和身份认同问题。陈楚洁(2018)就曾提出,从结构、文化、话语的视角考察媒体创业者建立职业认同的研究仍相当缺乏,呼唤更多基于本土实例的探讨。因此,对本土媒体创业实践和创业组织的聚焦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当下中国的新闻职业生态变革。而由于它们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冲破既有新闻边界、协商构筑自我边界的过程,边界工作这一中层理论就为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分析工具。从这一视角切入研究,并非是“为了解释边界而创造边界”(Carlson, 2015: 13),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内部分化显著的中国媒体职业生态中,各职业主体协商互动的动态过程。
二、创业媒体作为边界工作者
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常被用于讨论职业主体试图界定自身生态位置的文化过程(刘思达,2017:8)。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Gieryn(1983)提出,用以分析历史上科学共同体建立自身权威的话语实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边界工作也被引入新闻研究领域,常用于讨论新闻业应对各类业内危机和业外威胁对既有边界产生冲击的现象(白红义,2015a)。不少研究依据Gieryn提出的三种边界工作类型(扩张、驱逐和自主性保护)讨论新闻业的边界工作实践(Carlson, 2015),其他呼应新闻边界和权威问题的研究关注修辞性策略、记忆建构、话语斗争等在报道实践和职业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Zelizer, 1990; Meyers, 2004; Eldridge, 2014),但大多聚焦于话语层面的分析。
边界工作理论之所以常被用于解释新闻职业群体的权威建构问题,与新闻业的“弱自主”(布尔迪厄,2005/2017:35)特性密不可分。同样关注职业自主性的阿伯特(1988/2016:12)提出管辖权(jurisdiction)概念,将其视作解读职业划定领域范围的核心。由于形成完全、固定的管辖权的可能性总是有限的,职业主体总是处在一个相互或内部竞争、协商管辖权的动态的生态系统中。从“争夺”、“划界”的角度看,“管辖权冲突”理论与边界工作概念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是,阿伯特更强调关注“职业工作到底做什么”和“职业间竞争互动从而协商边界”的动态过程。在新闻研究领域,此前已有学者尝试将边界工作与管辖权建立勾连(Schudson & Anderson, 2009)。刘思达也指出边界工作理论与“管辖权冲突”的联系,认为职业工作领域的管辖权冲突正是边界工作的一种类型;但是,边界工作不只是“自我区分”(self-distinction)的机制——社会边界是一个模糊和弹性的区域范围(ambiguous and elastic areas),因此他又提出了包括边界模糊和边界维系在内的边界工作类型(Liu, 2015)。
在对本土新闻业的研究中,陈楚洁和袁梦倩(2014,2015)较早引入了边界工作的概念,讨论中国新闻记者对内驱逐“越轨者”、对外强调专业优势以重塑文化权威与合法性的话语实践,并将其应用于纪许光微博反腐这一具体案例。此后几年的研究也基本延续了这一特点,通常以某个具体的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为案例,分析新闻业对此做出的反应。例如陈楚洁(2015)和白红义(2015b)的研究各自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和“南都口述史”为切入点,研究记者社群如何通过纪念话语、集体记忆来建构职业边界。王源(2019)和曹林(2019)则分别以新京报新闻奖颁奖辞和流量媒体制造的争议性“热点时刻”为例,分析传统媒体精英维系权威的边界工作。最近几年,研究者们也注意到新技术嵌入新闻业后对新闻边界产生的影响,以今日头条(刘双庆,2019)、UGC内容(黄春燕,尹连根,2022)、数据分析(王斌,温雨昕,2022)等为对象分析相应的边界工作策略。尽管边界工作针对的对象以及表现出的策略均有所不同,但这些研究讨论的从事边界工作的主体依然都是新闻媒体。
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正遭遇着更复杂的边界工作场景,不仅传统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效应正在减弱,而且在主流媒体之外,有更多主体参与进了对专业边界的争夺和协商之中,这也随即促成更多边界工作类型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少数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新闻媒体之外的一些边界工作者。例如,有研究发现,受众会通过一些特定的修辞策略建构自己作为边界工作者的权威(Kananovich & Perreault, 2021)。尽管受众维护的依然是新闻业的边界,但这一现象表明,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一些所谓的非新闻行动者也可以从事边界工作实践,直接影响着新闻边界的变动。创业媒体也是一类新兴边界工作主体,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对新闻创新和新闻边界的研究都能有所推进。
一方面,作为新闻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对新闻创业公司的研究一般将其作为一种典型的组织层面的创新,着重分析新闻创业公司的形成、风投资本对新闻创业公司的影响等问题。然而,新闻创业公司是新闻场域中的“新入场者”,它的进入势必会导致既有的新闻边界发生变动。有学者发现,创业媒体在将自己纳入新闻场域并享受与之而来的红利时,也强调传统主流媒体的过失与不足、标榜自身的不同,存在“反向”(in the reverse direction)的边界工作(Buozis & Konieczna, 2021)。陶文静(2017)对欧美创业新闻研究进行的元话语分析也发现,西方创业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正呈现出明显的“边界融合”现象。虽然有少量研究注意到了创业媒体从事边界工作的可能性,但它们究竟如何进行边界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尤其是在非西方语境下的创业媒体。
另一方面,边界工作虽然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逐渐成长为新闻研究领域一个较有影响力的中层理论,但近年的新闻边界研究仍存在一些弱点和不足,包括从时间和物质维度对边界的探讨缺乏、比较研究薄弱,以及规范维度的讨论不足等(白红义,李拓,2020)。创业媒体这一新兴的边界工作主体则具有补充既有研究薄弱之处的潜力。首先,从历时维度来看,透过创业媒体的产生和发展,能够洞察传统新闻边界的变化甚至消失,以及新边界建立的过程,补充既有研究从某个标志性的热点时刻切入的静态视角。其次,深入研究创业媒体的边界工作,能够破除既有研究“多把边界工作视为一种应激式的反应机制”(白红义,李拓,2020)的局限,从而更进一步启发对新闻边界“规范性”的探讨。
总之,中国创业媒体的发展为边界工作理论提供了更为复杂的分析对象,有可能提炼出一些独有的边界工作策略。而这就需要先适当越过既有的新闻职业权威话语,进入到对本土创业媒体生产实践的洞察中去,然后再回到对其专业价值观树立和职业话语生成的讨论上来。如此,方能看到中国媒体职业生态内部的现实分化和竞争互动,以及创业媒体所展现出的“模糊和弹性”的边界工作发生区域。
本文就将聚焦创业媒体中的一个典型——J播客,讨论其作为新型传媒内容生产者的边界工作形态。J播客是位于上海的一家成立于2018年的数字音频媒体创业公司,其创始人和大量员工均从传统媒体人转型而来。随着加入创业行列,他们的工作领域从文字、电视新闻生产,转向了数字音频内容生产。起初,J播客是一个完全的“自媒体”,主要基于公众号和音频平台个人账号发布内容。但经过短短几年发展,通过成立公司、扩建团队和确立营收模式,J播客逐渐形成了规模化和组织化的内容生产能力,向“机构”的形态演变。不论是吸收传统媒体人才,还是采用播客媒介的创业形式,J播客的发展与海外报业转型、媒体创业的趋势均有所呼应。③因此,J播客诞生于新闻人的职业流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海外媒体创新动态向国内传播等多重进程的交汇点,具有典型性。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本文旨在讨论新闻生态系统中的新兴行动主体——创业媒体是如何通过边界工作来创造和维持自身的管辖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第一,J播客如何通过建立创业实体的过程成为一个划定管辖领域的边界工作主体?第二,J播客如何通过特定的边界工作实践创造出一个拥有专属管辖权的“中间地带”?
为了探讨这一新兴新闻行动主体的边界工作形态,本研究对J播客的内容生产实践进行了参与观察。在研究对象知晓本研究目的和意图的前提下,笔者于2021年7月至12月以实习生身份深度参与了该公司的内容生产、内部培训、招商会谈以及年会筹办等工作环节;并与该公司内容生产团队12人中的7人进行了时长为1.5—2.5小时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样本同时包含了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与普通员工、具有传统媒体工作经验者与校招新人、编辑与制作人。以上访谈样本从职位、经验、分工上各不相同,具有代表性。访谈问题围绕研究问题展开,旨在深度了解访谈对象的专业教育背景和职业选择经历,其工作内容如何随从业媒体类型和内容生产领域的变化而流变,其如何认知、理解自身职业身份,以及对于当下国内外媒体产业变动的看法等。此外,作为媒体创业领域的“明星公司”,对该公司的公开报道材料也比较丰富,亦为本研究所用。对于以上所有质性材料的处理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方法进行了编码和分析。
三、制造边界:创业媒体如何成为媒体机构
对于创业媒体J播客来说,“从无到有”的创业过程是与既存媒体争夺、协商获得管辖权的过程,更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体边界工作的特殊面向。所有职业都是“在构建社会边界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实体”(Liu, 2018),但对于早已确立起社会声望的传统新闻业来说,其社会边界的建构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因此,既往对于新闻边界工作的研究,实则更多是在探讨“危机”之下的边界维系方式。然而,对于在媒体生态系统中新生的创业媒体来说,其成立和发展的边界创造过程也应当被视作边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媒体处在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中间地带”这一特殊社会空间位置,它们的边界工作并不是受到挑战时才出现的应激式反应,而是一个伴随创业始终的历时性
过程。
阿伯特(2016)曾在《职业系统》中论述,法律对职业管辖权的规定需要漫长的过程,且相当静态。因此,那些在舆论领域和工作场所中对模糊之处的争夺,正是不同职业争夺管辖权的关键之处。西方语境中,新闻媒体的专业权威建构就紧密围绕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展开。而中国新闻领域的主导话语体系较为混杂,反而是从业者与新闻机构之间的正式雇佣关系在职业边界的确认中至关重要,即人们更倾向于认可“体制内媒体人”(“单位人”)的职业权威(Tong, 2015)。为了生成自身合法的职业边界,创业媒体往往也需要将自身建构为一个“媒体机构”,既在媒介形态、业务内容等方面不同于既有的传统媒体,又在组织规模和专业性上超越自媒体,从而占据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中间地带”。
对成为“媒体机构”的追求,成为中国创业媒体在管辖权争夺中的一个突出特征。J播客就体现出这一特点,它在创业近四年间的发展相当迅速,随着团队规模扩大和节目数量扩充,商业订单和原创节目两条内容生产线逐渐步入正轨,完成了从自媒体向组织化媒体机构的转化。本节将从J播客成立创业实体的方式、确立工作内容与专业价值观的自主过程切入分析,讨论其建立在工作实践上的边界工作。
(一)创业实体凝聚:专业资源的流动与重组
创业媒体虽然是媒体职业生态中新生的主体,但其最初的职业形态仍从传统媒体中脱胎而来。创业实体的凝聚及其进一步塑造自身成为专业机构的过程,伴随着既有新闻场域中专业资源向创业组织的流动和重组。
从创业团队来看,J播客创始人均是从传统媒体离职的专业从业者,此前分别在上海当地的知名印刷、电视新闻媒体中担任记者、编辑。在体制内媒体的工作经历和认知变化使其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经验以及具体的创业意向,直接转化、作用于其创业实践。
在机构媒体工作时,J播客创始人就关注到了本土专业媒体内容市场中“缺少的内容”。以IN1所在的某电视媒体财经新闻频道为例,其对宏观经济的解读性报道在选题常规中有所欠缺:“从节目版面的需求来讲,前方有一手的信息,比如说政策出来之后,是需要配合解读的……(虽然)政策不是每天都有,但是宏观经济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在发生。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有人去分析的,所以我就发现这里有一大块没有人去cover(报道),然后我就跟领导说我可以去跑这一块,后来就变成我在做这一块”(IN1)。
此外,领域相关、形式不同的外媒报道也启发了IN1转向差异化的内容生产:“我那时候喜欢看外媒,会有很多关注中国经济或者全球经济的东西,但是国内的媒体是不做的……我就去看它们在做什么、最近在讨论什么、都采访谁,我也去想办法做……慢慢也会学到一个视角”(IN1)。
传统新闻机构生产内容覆盖的缺漏为差异化专业内容的生产提供了空间,促发掌握专业技能的媒体人向更自由灵活的工作组织迁徙,J播客创始人也进入了生涯“徘徊期”,即一边考虑离开传统媒体,一边寻找、酝酿新的职业选择。由此,产生了J播客创业实体的最初形态:两位意欲离职的媒体人开始合作一档播客节目和一份聚焦播客的行业通讯(IN1;IN3)。
除创始人之外,J播客初创阶段的员工主要由两类人员构成:一类是两位创始人从传统媒体中连带而出的社交关系,即本文所称的“旧媒体人”;另一类是被播客这一早先流行于海外的媒介形式吸引而来的兴趣导向型员工,即“新媒体人”。前者在专业技能上支撑了J播客早期的节目策划和生产,在选题撰稿和剪辑分发等操作上解决专业壁垒;后者则一般是拥有较高学历背景,对“用声音表达”具有热情,或对特定垂类内容保有浓厚兴趣和知识特长的“志愿者”,也就是俗称的“为爱发电”(IN1;IN7)。
加入J播客的“旧媒体人”大都曾供职于传统新闻媒体或有为其供稿的经历。他们熟悉机构媒体的工作流程,有稿件操作经验,同时在特定话题领域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如J播客某商业栏目的一位编辑曾是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界面新闻”的商业记者。负责其他栏目的制作人中,也有不少人分别曾在“36氪”、“GQ”、“第一财经”等媒体任记者、编辑。这些拥有专业媒体从业经验的员工,此前均有固定的报道条线和关注的垂直领域,如文化出版、商业财经等。这些“旧媒体人”或因为报道口径的限制,或出于传统媒体影响力下滑带来的危机感,又或是受到“移植”、“复刻”英文播客的启发(IN3;IN1),最终离开机构媒体,加入J播客。而“新媒体人”则大都是通过应届校招进入J播客的。从教育背景来看,他们大部分毕业于新闻传播类或其他相关专业,如中文、语言学、历史等,并大多在官方媒体或其他中外市场化媒体中从事过稿件采写、运营编辑等基础的媒体工作。
“旧”、“新”媒体人的不断加入标志着媒体专业资源向创业组织的迁徙,使J播客在成立后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内容制作范围不断扩大、制作能力不断提升。2018年到2021年间,J播客发展出了涉及历史、文学、艺术、商业、体育和社会纪实等多领域的数十档节目,账号粉丝近20万,各平台累计订阅近70万次,收听超过2000万次,④成为初具规模的媒体组织。
(二)确立产制常规:重建专业工作法
在职业竞争确立对工作内容管辖权的生态视角下,“专业人士做什么”(what do professionals do)的工作内容本身受到了更多重视(Liu, 2018)。对于创业媒体来说,非体制化的身份使其难以在法律规章等更正式的社会环节中固定其成为专业内容的管辖者,因此,同化、转化媒体的专业技艺对于其管辖权的争夺和建构至关重要。如何在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和生产流程的可行性之间达成平衡,成为边界工作的主要目标。而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对既有的媒体专业工作法进行适应性的重建。
受制于核心内容生产团队的较小规模,J播客的内容生产采取专题化、项目化的方式,以保证节目质量和数量的稳定。在策划类型上,早期出于制作成本和听众收听习惯的考虑,J播客制作的大部分节目是“对谈类”,即通过主播的自然对话呈现信息和故事。但随着制作团队的扩大,J播客开始将制作重心调整到“叙事类”播客的制作上,即通过有设计的脚本写作并辅以声效变换,交替使用访谈、自述、旁白等多种叙述形式进行叙事。向叙事类节目的转型,使得节目更接近“媒体质感”(IN1),即通过脚本写作、编辑、剪辑、声效设计等塑造故事或信息的传播样态,从而让听众感受到节目是“被创作的”,取代“对谈类”节目带给听众的“随意感”。
追求专业的“媒体质感”这一表述直接指导着J播客的内容生产,并反映其对自身职业角色的规划和期待,标志着其与数量更广泛、规模更小的“自媒体”的根本不同:“在内容流程操作上面,我们也希望引入一些传统媒体的那种‘正常的采编思路’去做,而不是像一些公众号”(IN3)。
在这一生产理念驱动下,J播客规划并形成了一套“类机构媒体”的工作法。首先,在立项的流程和周期上,以聚焦特定话题领域的节目为工作单位,类似于传统新闻的条线划分。根据节目更新频率要求,定期进行开选题会、写稿、编辑、音频制作、发布的流程。这一工作流程的最终目标是“保持稳定更新”、“不开天窗”(IN1),即达成更新质量和频率都相对稳定、可控的“工业化”内容生产。
其次,从内容选题来看,其节目在体裁和篇幅上均类似于解释性报道(interpretive reporting)或评论专栏。这既因为受制于不具新闻采编资质下的现实选择,也是能够保证前述更新频率和品质“双稳定”的策略性安排。这类“软性”内容淡化时效性,但也会选择从热点新闻的“第二落点”甚至“第三、第四落点”(IN5)切入为节目引流,但本质上是从相对中长期,或更深度、侧面的视角解读新闻话题。这类内容虽与“新闻一线”背道而驰,但稳定地提供深度解读类内容以帮助用户了解“复杂的世界”,也被视作一种专业性的表征(舒德森,1978/2009:131-135)。
另外,所谓“媒体质感”的达成还要求水准稳定的后期声音制作。J播客的音频节目在基础剪辑和片头片尾包装之外,还加入了音效设计、原创配乐以及广告点位。单集节目开头统一的“声标”以及中插的其他旗下节目广告,无一不在向收听者提示其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整体形象,成为其标志自身特质的手段。
这套以传统机构媒体工作常规为蓝图而重建的专业工作法,正是J播客试图在“保持专业”和“完成可持续的生产目标”之间达成平衡的一种规范的建构。在这一被重建了的专业工作法之上,另一种专业价值观也在创业媒体中显现出来。
(三)好内容也是好生意:向商业开放的专业价值观
对于秉持“客观中立”角色的传统媒体而言,在面对广告、公关时往往需要建立“防火墙”。但对于生产团队更小,生产内容更“软”、更垂直的创业媒体来说,可持续营收模式的建立要求专业性和商业性的融合而非对抗(Deng & Yan, 2022)。在J播客的案例中,创业媒体正表现出了对从前被视作“敌对世界”(hostile worlds)的商业市场的开放态度,并试图将“实现成功的商业变现”纳入其专业价值观的诉求之中。
在J播客的营收构成中,品牌播客和平台采购节目的订单收入占总收入九成以上。这部分节目订单实现的盈利所得,再被用于支持公司内部其他原创节目的生产。这类节目由J播客内容团队根据品牌和平台提供的项目选题,完成创意策划、脚本撰写、采访录制、声音设计、后期包装等一系列流程,最终成为品牌宣传矩阵中的一环或平台独家的专栏。通过直接将内容制作这一专业技能转化成用以出售的服务和产品,创业媒体力图在“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和“为品牌宣传良好形象”之间达成双赢。
这种商业模式迎合了商业品牌寻找赞助内容(sponsored content)“新领地”的需求(Lynch, 2021),类似于“原生广告”(native ads),即将与品牌相关的内容以相对自然的方式呈现,在商业赞助的前提下向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促使其接受。对于品牌方来说,相比在传统新闻领域寻找赞助和公关内容的空间,与J播客这类内容制作机构的合作阻力更小,能以更体面的形式吸引到更多用户的关注和接受。对于内容制作方来说,商业项目盈利支撑下的其他内部节目则能够以相对自由的形式创作,不受外部力量干涉。
在这一商业性与专业性相融合的创新专业价值观指导下,J播客的内容生产得以在中国媒体生态中的不同话语体系之间“游走”。在与消费品牌或电商平台合作的情境下,J播客生产的节目直接成为品牌和平台商业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但相比单纯的广告片而言,这类播客节目则侧重于采访故事、挖掘解释性信息等内容。而在与金融投资公司、纪实报道媒体等专业主体合作时,J播客又能够制作出类似宏观经济报道、纪实调查报道的声音内容。把制作媒体内容产品的专业能力“打包出售”是J播客的运营法则,这种专业的实践形态与传统媒体大相径庭。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创业媒体的J播客并不能也不会直接生产驻扎新闻一线的原创报道,但却始终在考虑信息和故事传播的专业标准与自主营利二者的“共赢”。
四、创造“业界”:创业媒体如何管辖“中间地带”
如前所述,从组织形态和运作流程上,J播客已经从内部逐步确立起属于自己的职业边界,但受制于较小的公司规模、并不完全的执行力,以及中国市场内相对空白的创业经验,这类创业媒体仍然面临着规范化、行业化的难题,直接影响其未来在媒体生态中的生存境况和发展趋势。因此,确立行业身份、形成职业归属,完成独属“播客人”的职业文化生产,成为这类创业实体形成后的核心任务,也构成了边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以“创造‘业界’”来概括这类创业媒体依凭新兴媒介或商业模式来创造职业共同体话语空间的实践。
创业媒体当下正处于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中间地带”,决定了其所从事的边界工作面临着“双重边界”。而这一双重的边界工作也并不止于“边界划分”的机制,而是包含了“区别”与“借力”的复合机制,并同时在话语的和非话语的层面上展开。在J播客的案例中,“新”、“旧”媒体人共享一套围绕专业内容创业者的工作常规和认同话语,与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不断进行着分界、合界的边界工作,从而建立新的职业权威、吸纳更多资源。
(一)借助符号与仪式的认同凝聚
建立在生产流程之上,J播客对自身业内身份、其员工对自我职业身份的认同,也产生了相应的建构机制和表征。作为创业媒体,J播客在建构业内身份时,同时调用了专业主义和创业文化两套话语资源,为自己划定“中间地带”。
在节目详情页中所标注、简介的制作团队信息,成为J播客标识自身职业身份的一个典型表现。这一“身份简介”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标注制作人或编辑的“前媒体人”身份,如“前资深商业记者”(商业主题播客)、“前新闻从业者”(文史主题播客)等;另一类是标注制作人或编辑的“垂类专家”身份,且往往采用更活泼和非正式的修辞方式,如“长期关注消费、营销和好玩的商业故事”(商业主题播客)、“科幻迷”(科幻文学主题播客)等。这些身份标签成为内容创作者建立与节目内容相关联系的最直接、简单的方式,既体现了在此话题上的专业权威,又打破了专业媒体的“严肃面孔”,标志其作为创业媒体的文化属性。
借助仪式的文化生产则突出表现在J播客从成立之年起每年举办的行业年会。这一年会从2019年到2021年已经举办四届,概况如(表2 表2见本期第25页)所示:
通过线下活动来积累品牌声望并不新鲜,但J播客主办年会的特点在于致力于建立“播客人”(podcaster)的群体认同,强调播客作为一种新媒介、新产品在各类内容传播和商业开发中的角色。近两届年会中更加入了播客平台、软件等产品发布和推广环节,意在对外展示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生态。在年会议程中,J播客更多将自己呈现为一个传布者、组织者的角色,其自身的节目与产品在议程中反而被淡化。与其他垂直类内容年会相比,J播客主办的年会围绕播客、音频这一媒介形式,让“做播客”、“做播客产品”的群体“有确定下来的意思”,从而建立“创业同行”的概念(IN1)。
在致力于建立以播客为中心的独立业界叙事之外,年会这一仪式性聚集也展演着与其他媒体组织的“边界融合”。一方面,每届年会基本都有传统媒体的意见领袖或知名人士加入与播客创作相关的分享,如2019年美国公共广播站记者、制作人Emanuele Berry的参与,2021年前央视、凤凰卫视记者、主持人陈鲁豫和前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的参与。这些业界知名人士的“站台”,也成为J播客所调用的符号性资源,强调着播客业态与传统专业媒体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在播客业内,机构化的创作者仍是少数,年会仍会邀请大量个人特色鲜明、自带高黏性“粉丝”群体的自媒体主播参与。借助年会这一仪式场合与自媒体创作者进行亲密互动,从而提升主办方J播客在播客领域的权威性和认知度,亦是一种合界的实践。
(二)争取“中间地带”的话语建构
在职业文化的生产中,分界的工作机制让创业媒体得以与他者形成区分,而合界的工作机制则让创业媒体同时享受与既有职业权威紧密关联的社会资本。分界与合界复合的边界文化生产共同维护着创业媒体所在的边界区域。对创业媒体来说,这个边界地带是处在传统专业媒体和广泛的自媒体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位置使得创业媒体能够在秉持一定专业性的同时,拥有更自由广泛的创作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导致创业媒体需要通过种种文化生产来争取自己并非天然显著的专业身份。
通过关注创业媒体如何向大众“自我介绍”的创业宣言,Carlson和Usher(2016)揭示了创业新闻公司加入元新闻话语表达的方式。创业宣言等理念性的文本可以被视作解释性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其内核是关注新闻专业表现、规范性假设和适当实践等问题,成为创业媒体重建职业边界和争取合法性的工具。类似地,J播客也通过向公众发布理念性的文本来试图生产自主的职业文化。J播客对外发声的最主要渠道是其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是聚焦播客产业领域的行业通讯。这一通讯的雏形是J播客创始人在个人公众号上写作和编译发布的播客业界动态(IN1),之后成为公司运营部门的一项保留业务。该通讯的主要内容包括编译海外播客行业动态,编发国内播客、数字音频、流媒体产业新闻,并在年末等时间节点发布统计、盘点类的原创内容,如统计过去一年中新增的中文播客数量、洞察中国数字音频市场发展趋势等,成为播客这一领域内较为可信和丰富的信息“集散地”。
在该公众号发布的四百余篇推文中,有三类较典型的内容。第一类是溯源职业文化的推文,一般出现在制作幕后和年会盘点等板块。通过引介优秀播客案例的幕后制作故事、树立典型,这类文章加强了对“何为专业”的阐释,包括“讲故事的技巧”、“播音质感的塑造”、“明星主播的打造”等。此外,这类内容还偏向将“播客人”的职业形象与更宏大的媒体专业历史相勾连。比如,在2021年以“对话”为主题的年会前夕,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谈话类节目的‘不惑之年’,从锵锵开播前说起”的原创推文。该文追溯了中文广播电视节目改革的诸多标志性的历史时刻,如珠江广播经济电台的“珠江模式”、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等,从广播电视节目形态范式转型的视角,赋予“对话”节目以专业正义,从而完成播客类媒体产品专业性的自我溯源和历史建构。
第二类主要内容可以被概括为“行业现场”,包括公众号内的“播客现场”、“播客行业洞察”、“国内播客行业动向”等标签。这类推文内容一般包括海内外音频制作公司的成立、并购新闻,主要流媒体平台与播客相关的业务动态,以及和播客传播相关的研究和行业报告等。使用“现场”这一栏目标签,意味着将读者和用户带入了一个被营造起来的行业空间领域,向读者宣告“播客”是一个正在生发、活跃着的内容领域。通过不断在“播客现场”中展示行业内的主体(创作者、平台、资本等)以及不断发生的新事件(新节目、新纪录、新明星等),J播客不断完成着拣选热点事件从而向读者积极展示行业现状的边界工作。
该公众号的第三类重要内容则主要传播J播客所秉持的创新专业价值观。在公众号中,有一个单独的下拉菜单用于介绍和展示“音频营销”案例,此外还有多个推文标签用于解说、展示“品牌播客”这一概念,比如“品牌怎么做播客”、“行业播客厅”等。这类内容反复突出作为商业订单的品牌播客同样能够向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故事,并同时为品牌、平台、机构提供传播企业理念和形象气质的传播价值。这一叙述模式实际上是对其“好内容也是好生意”创新专业价值观的再现。
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推文,这些文本所传达的意涵均在于呈现播客作为一个蕴藏潜力的职业领域正在蓬勃发展,融合了商业性的创新专业价值观也正在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用,并同时不断将播客和更广泛的媒体职业话语相勾连。这正体现出J播客作为创业媒体试图通过塑造专业标准、热点时刻、共同记忆等方式不断生产和扩大其所处的“中间地带”这一边界区域,创造专属“播客业界”的话语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在媒体行业剧烈变革的当下,创业媒体作为新兴职业主体,如何承接既有的或创造全新的职业地位与权威,又将对媒体生态产生哪些影响,成为近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聚焦创业媒体J播客加入这一讨论。透过该案例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的创业媒体正在积极构筑自身的职业边界,从而加强在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合法性。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创业媒体借力从传统媒体连带而出的专业义理和操作方法来规范自身的工作常规和方法,并通过提供与传统媒体相差异的内容建筑自身的管辖权范围;同时,依托特定媒介或者商业模式,并借助线上平台和线下活动,创业媒体亦在生成新的媒体职业认同话语。
在对J播客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创业媒体所从事的边界工作具有过程性和双重性的特点。所谓“过程性”是指不同于媒体生态中既有的、保有职业声望的职业主体,创业媒体的边界工作并不是在“抵御入侵”和“回应冲击”的逻辑中完成的。相反,伴随着创业实体的建立,其边界工作是一个持续进行中的历时过程。对像J播客这样的创业媒体来说,确立对内容管辖的边界,对内是一个确证自我、培训团队的过程,对外是一个树立职业权威、吸纳资源的过程,整体上是一个主动的、开拓的职业化进程。随着技术、资本、制度等多种条件的变化,创业媒体的边界工作仍将是一个持续的进程。
所谓“双重性”是指创业媒体处于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中间地带”,面临“两重边界”。一方面,创业媒体通过移植、改造传统媒体的工作流程,借用、复用从传统媒体中连带而出的专业技能、人际关系等文化资本,调用相关的符号和话语,从而强化与自媒体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创业媒体也借助创业话语,开创出售内容制作能力的商业模式、组织以媒介或产品为中心的职业社区,从而标示与体制内媒体的差异。这既是中国现行传媒业执照式的管理机制使然,也是媒体人寻找内容创作更大自由空间的自主选择。此外,“中间地带”的职业处境决定了创业媒体的边界工作绝不是简单的“领地划分”,而是一个存在着复杂的借用、共生等状态的复合过程,即亦存在“合界”或“模糊边界”的机制。以J播客来说,一方面,它通过与其他媒体职业主体边界相模糊来使自身合法化,如改造传统媒体的工作流程、调用“专业媒体人”相关的符号系统和话语资源等。另一方面,它也围绕新媒介、新商业模式,划定新的职业社区,并将传统媒体有所忽略或生产不足的内容纳入自己的管辖领域。处在“中间地带”的创业媒体既不同于散漫自由的个人创作者,也不同于专业新闻人,更不同于“耳目喉舌”式的宣传工作者,而是一股借力多方以建筑自身的力量。本文所发现、探讨的“中间地带”的边界工作,并不维护传统新闻业的权威,也不是传统新闻业危机话语的转化,而是一种保持专业性的同时,争取差异化内容生产的折中探索。
任何职业的确立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边界本就模糊的媒体职业而言更是如此。在当下中国的媒体职业生态中,执照化的管理体制、宣传话语复合专业理念的职业教育,以及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都没有为创业媒体提供优渥的职业化土壤。但在媒体职业生态的视域中,创业媒体争夺管辖权,从而为社会提供信息和故事流通价值的这一职业初衷是不变的。因此,吸收市场化的创业话语,同时借力传统媒体的专业基因,成为其建筑自身的方式。这类“已经广泛存在但在制度空间里没有正式地位的新闻现象”(王辰瑶,2021),将成为拓展新闻创新研究的重要个案,提示新闻研究始终需要回到媒体生态系统这一更大的视野中去,关注传统主流媒体之外的其他社会信息服务提供主体及其工作形态。
借助边界工作的理论资源,本研究讨论了创业媒体的生产常规确立和职业文化生产的过程,意在补充边界工作理论在新闻学领域的应用。通过聚焦创业媒体这一职业生态内的新兴主体,讨论其生成中的、持续的边界工作,本文避免了将边界工作视作“冲击—回应”的简化讨论。研究有待拓展之处有:其一,正如阿伯特(2016)指出,技术因素对于管辖权的生成和争夺具有重要影响,而本文对J播客依凭数字音频这一媒介技术创业的特性问题未加讨论。其二,本文主要讨论了以创业媒体为行为主体的边界工作形态和机制,而由国家等外部主体介入参与的“维界”机制(刘思达,2017)仍有待补充。其三,是本研究将J播客视作一个职业主体整体的视角局限问题。对内部从业者存在“代际分化”的创业媒体来说,“新”、“旧”媒体人之间职业认同生成的差异性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美国新闻聚合网站,2006年在纽约成立,最初以借助算法从而提供“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热点新闻著称,2011年后逐步开设原创调查报道部门。当前,BuzzFeed新闻频道旗下雇佣超过一百名全球记者,并在墨西哥、印度、日本等地设有记者站。
②美国媒体创业公司,2011年在华盛顿和纽约成立总部,2014年推出在线新闻网页Vox,以数字多媒体内容和解释性报道著称,口号是“Vox explains the news”。
③与此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史安斌,薛瑾:播客的兴盛与传媒业的音频转向,《青年记者》,2018年第16期,第76-78页;辜晓进:“报业播客”爆红背后的大众传播演进逻辑——纽约时报成功进军音频世界的启示,《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9期,第36-44页。
④该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7月。统计方法说明:由于播客广泛采用RSS开源技术发布和订阅,订阅和播放数难以直接统计。此处仅统计了中国大陆地区五个主流音频播放平台(喜马拉雅、荔枝、网易云音乐、QQ音乐、小宇宙APP)中,以“J播客”认证账号所发布的节目专辑数据。因各平台审核机制和页面展示方式不同,“J播客”在不同平台账号上架节目数量和可统计的数据类别不尽相同,具体统计情况如下:账号累计关注数18.3万(全部五平台累计),上架节目累计播放量2295.3万(喜马拉雅、荔枝、网易云音乐、QQ音乐累计),上架节目累计订阅量69.2万(网易云音乐、QQ音乐、小宇宙APP累计)。
参考文献:
安德鲁·阿伯特(2016)。《职业系统》(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白红义(2015a)。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新闻记者》,(7),46-55。
白红义(2015b)。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南都口述史”研究。《国际新闻界》,(12),46-66。
白红义,李拓(2020)。“边界工作”再审视:一个新闻学中层理论的引入与使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147-156。
曹林(2019)。扩张、驱逐与维权:媒体转型冲突中的三种博弈策略——以兽爷、咪蒙、呦呦鹿鸣争议事件为例。《新闻大学》,(6),19-31。
陈楚洁(2015)。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12),26-45。
陈楚洁(2018)。“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新闻记者》,(3),4-22。
陈楚洁,袁梦倩(2014)。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5),55-69。
陈楚洁,袁梦倩(2015)。社交媒体,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以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为例。《新闻大学》,(5),139-148。
黄春燕,尹连根(2022)。合作·隔离·让渡——机构媒体应对UGC策略研究的边界视角。《新闻记者》,(9),3-16。
李东晓(2019)。界外之地:线上新闻“作坊”的职业社会学分析。《新闻记者》,(4),15-27。
刘双庆(2019)。从排斥到分化:基于今日头条的新闻边界工作研究。《新闻记者》,(7),75-84。
刘思达(2017)。《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
迈克尔·舒德森(2009)。《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2017)。政治场、社会科学场和新闻场。《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罗德尼·本森,艾瑞克·内维尔主编,张斌译),31-48。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陶文静(2017)。结盟、重组、民主功能坚守——欧美数字新闻创业机构研究中的专业建构转向。《新闻记者》,(9),53-64。
王斌,温雨昕(2022)。修复与交融:基于数据分析的中国新闻业边界工作考察。《新闻与写作》,(9),67-78。
王辰瑶(2021)。站在新起点上的新闻创新研究。《新闻记者》,(11),2-7,20。
王源(2019)。扩张与驱逐:媒体内部的新闻边界工作——以新京报年度新闻奖颁奖辞为例。《青年记者》,(17),25-26。
杨保军(2015)。“脱媒主体”:结构新闻传播图景的新主体。《国际新闻界》,(7),72-84。
曾繁旭,王宇琦(2019)。传媒创业研究:一个新兴领域的研究脉络与中国议题。《新闻记者》,(2),87-97。
Anderson C. W.Bell, E. & Shirky, C. (2012). 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 Adapting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
BriggsM. (2012).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How to build what’s next for news. Thousand Oaks: CQ Press.
BuozisM.& KoniecznaM. (2021). Conservative news nonprofits: Claiming legitimacy without transparency. Journalism, DOI: 10. 1177/14648849211056145.
Carlson, M. (2015). In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In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ed. by CarlsonM.& LewisS. C.1-18. London: Routledge.
Carlson, M.& UsherN. (2016). 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For-profit digital news startup manifestos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 4(5)563-581.
ChadhaM. (2016). What I am versus what I do: Work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in hyperlocal news startups. Journalism Practice, 10(6)697-714.
ChewM.& Tandoc, E. C. (2022). Media Startups Are Behaving More like Tech Startups—Iterative, Multi-Skilled and Journalists That “Hustle”. Digital Journalism. DOI: 10. 1080/21670811. 2022. 2040374.
DengM.& YanY. (2022). Striking the balance between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ercialism: A cross-case study on news start-ups in China. Journalism, 23(11)2471-2488.
Deuze , M. (2014). Journalism, media life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society.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36(2)119-130.
Deuze, M. (2017). Considering a possible future for Digital Journalism. Revista Mediterránea de Comunicación/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8(1)9-18.
Deuze, M.& Witschge, T. (2018).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9(2)165-181.
Deuze, M.& Witschge, T. (2020). Beyond journ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ldridgeS. A. (2014). Boundary Maintenance and Interloper Media Reactio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journalism's discursive enforcement processes. Journalism Studies15(1)1-16.
FangK.& RepnikovaM. (2022). The state-preneurship model of digital journalism innovation: Cases from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7(2)497-517.
GierynT. (1983).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781-795.
HeppA. (2016). Pioneer communities: Collective actors in deep mediatization. MediaCulture & Society38(6)918-933.
HeppA.& Loosen, W. (2021). Pioneer journalism: Conceptualizing the role of pioneer journalists and pioneer communiti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re-figur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22(3)577-595.
Jurkowitz, M. (2014). The growth in digital reporting: What it means for journalism and news consumers. Pew Research Journalism Projecthttp://www. journalism. org/2014/03/26/the-growth-in-digital-reporting.
KananovichV.& PerreaultG. (2021). Audience as Journalistic boundary worker: The rhetorical use of comments to critique media practice, assert legitimacy and claim authority. Journalism Studies22(3)322-341.
Liu, S. (2015). Boundary work and exchange: The formation of a professional service market. Symbolic Interaction38(1)1-21.
Liu, S. (2018). Boundaries and professions: Toward a processual theory of action. Journal of Professions and Organization, 5(1)45-57.
Lynch, L. (2021). Sponsored Content in 2020: Back to the Future?. Digital Journalism, 9(7)991-999.
MeyersO. (2004). Israeli journalists as an interpretive memory community: The case study of “Haolam hazeh”. Ph. D. dis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udsonM.& Anderson, C. (2009). Objectivity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journalism. In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108-121. New York: Routledge.
StringerP. (2018). Finding a Place in the Journalistic Field: The pursuit of recognition and legitimacy at BuzzFeed and Vice. Journalism Studies19(13)1991-2000.
TongJ. (2015). Chinese journalists’ views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producers and journ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boundary work of journalis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5(6)600-616.
Usher, N.& Kammer, A. (2019). News Startups.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DOI: 10. 1093/acrefore/9780190228613. 013. 827.
WagemansA.Witschge, T.& HarbersF. (2019). Impact as driving force of journalistic and social change. Journalism, 20(4)552-567.
WangW. (2019). Chinese Government’s Partition Management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Journalistic Ecology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h. D. diss.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7(4)366-376.
Zhang, S. I. (2019). The business model of journalism start-ups in China. Digital journalism, 7(5)614-634.
白红义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施好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201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创新研究”(18PJC090)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