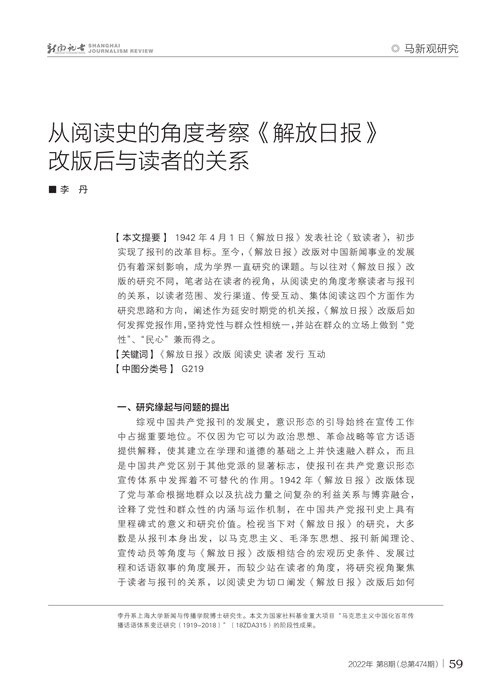从阅读史的角度考察《解放日报》改版后与读者的关系
■李丹
【本文提要】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初步实现了报刊的改革目标。至今,《解放日报》改版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仍有着深刻影响,成为学界一直研究的课题。与以往对《解放日报》改版的研究不同,笔者站在读者的视角,从阅读史的角度考察读者与报刊的关系,以读者范围、发行渠道、传受互动、集体阅读这四个方面作为研究思路和方向,阐述作为延安时期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改版后如何发挥党报作用,坚持党性与群众性相统一,并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做到“党性”、“民心”兼而得之。
【关键词】《解放日报》改版 阅读史 读者 发行 互动
【中图分类号】G219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综观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发展史,意识形态的引导始终在宣传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因为它可以为政治思想、革命战略等官方话语提供解释,使其建立在学理和道德的基础之上并快速融入群众,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显著标志,使报刊在共产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体现了党与革命根据地群众以及抗战力量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与博弈融合,诠释了党性和群众性的内涵与运作机制,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研究价值。检视当下对《解放日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报刊本身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报刊新闻理论、宣传动员等角度与《解放日报》改版相结合的宏观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话语叙事的角度展开,而较少站在读者的角度,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读者与报刊的关系,以阅读史为切口阐发《解放日报》改版后如何彰显党性和群众性的关系。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致读者》宣布正式改版,学者对此篇改版社论更多聚焦于新闻思想、报刊史论等面向,而笔者更多关注“读者”二字。《致读者》中提到,“没有广大的读者的赞助和鞭策,报纸要办得好,是不能想象的”(解放日报,1941年4月1日)。事实上,《解放日报》改版是否成功,能否实现报纸改版所要达到的目标,与读者息息相关。重视报纸与读者的关系,是阅读史的核心。聚焦中共报刊的阅读史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李金铮对《晋察冀日报》阅读史的考察是最早关于中共报刊阅读的研究成果(李金铮,2018)。近期,董昊、王建华(2021)对《新华日报》的发行、阅读和编者互动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证。关于《解放日报》阅读史的研究,王强从“改造读者”的视角对《解放日报》改版的考察是目前仅见的成果(王强,2022)。而报纸改版不仅影响内容和版面,也使得读者卷入一场由“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的新闻变革。与其他中共报刊相比,《解放日报》改版后成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中枢,在政治对报纸重塑的基础上构建出最初的党报理论,突出党性与群众性相结合,体现报纸自身的特殊价值。在此背景下,《解放日报》改版使报纸的发行范围、阅读方式与传受互动产生哪些改变?读者的阶层划分与阅读方式有什么勾联?阅读后怎样与报纸产生互动?站在读者角度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有助于理解党报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真实意图与运作机制。
鉴于此,本文以《解放日报》为切入点,改变以往对报纸的研究路径,将“读者”和“阅读”作为重点纳入报纸的研究脉络,从侧面反映共产党政策在革命根据地的实施效果,以及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对补充报刊史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意义。
二、《解放日报》改版前后的发行策略
根据地时期的党报发行策略形式多样,例如邮发、征订、代派等(田中初,2017:44-50),《解放日报》通过多种方式建设通讯网推动发行工作,在报纸内容与读者之间建立联系。《解放日报》初创时,工作人员较少,没有设置发行科,仅设有编辑部和经理部,经理部负责发行工作,但人员不足编辑部的十分之一,因此,暂时委托延安北门外的新华书店办理外埠邮购业务。1937年—1941年,县城之间交通困难且费用较高,往来县城常常需要几天时间(马克·塞尔登,2002:157)。人员不足与交通困难是创刊初期影响发行的重要因素。此外,电台广播也是扩展读者范围的一种方式。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钟紫,1984:413)。毛泽东经常为《解放日报》撰写文章,由新华社对外传播。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受众范围有限,主要面向解放区民众,据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傅英豪回忆,“延安电台电力小,收听效果不好”(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2000:132)。改版之前,在客观条件与媒介技术双重影响下读者的范围有限。
西北中央局认为,过去没有充分利用《解放日报》成为指导工作的主要工具,还有个别地区党员干部对报纸表示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1990:463)。1941年,为了解决图书报刊运输困难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成立运输司令部,把运送报刊和运送军用品列为同等重要地位。建立普遍的发行网,扩大党、政、军、民、学、敌占区和友党友军中的发行工作。”到1942年,报纸发行量从创刊时的7000份增加到1万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3:147)。
1942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负责陕甘宁边区的图书报刊发行工作,并在边区建立分支店,每县均有一分店,发行之书籍、报纸、杂志每月都有增加,5个月来发行书报达8万份(解放日报,1941年8月16日)。陕甘宁边区以延安新华书店为中心,形成覆盖全边区的发行网络(赖伯年,1998:243-244)。1943年边区新华书店成立一周年之际,该店散布在边区各地的推销处共有22处,发行了大量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纸,其邮购科的“基本读者”已有二百多名,书报发行共计百万份(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1943年,毛泽东在参观生产展览会时,特地赶到新华书店的展览帐篷,指出“发行工作是项艰苦且光荣的任务,要努力做好发行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3:147)。为了满足偏远边区的读者购买报纸的需要,新华书店设立了邮购部,通过边区通讯站向读者寄送报纸,也经常组织小贩、合作社和乡村团体代销报纸。
1943年3月,新华书店经理宋玉麟提出:“‘文化下乡’必须要有‘书报下乡’,让农村读者有报可读”(叶再生,2002:820)。新华书店发行工作开始从偏重城市推销转变到分散的农村读者(解放日报,1946年10月22日)。新华书店在边区各县和地区设立代销点,对于偏远地区,书店通过八路军兵站、边区通讯站、邮购、通讯下乡等方式发行报刊(马倩,2015)。新华书店安定分店在各区建立分销处,以“来者欢迎,不来者送上门去”为工作口号(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3日)。除此以外,在抗战时期以货郎担作为流动摆摊的散卖方式,适应了偏远落后地区的报刊发行。1946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群众今天是很需要书报的,这方面的推广还是不够。根据下乡的货郎担邵伯云同志跑过延安、延川、子长、延长的经验,每跑一个月要比各县书店同样时间内推销数超出一倍”(解放日报,1946年3月13日)。可见,《解放日报》以新华书店为发行载体,真正推动了发行工作深入群众,将政治思想和革命战略向农村读者进行传播。
另外,除了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也存在部分《解放日报》的读者。国民党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文化封锁,为了使解放区的报刊避开国民党的严苛审查,一方面使用挂号的方式从国民党的邮政局寄送报刊;另一方面,新华书店通过陇东设立的发行站或地下交通线运输,将报刊转发至成都、重庆、广西、云南等地的国民党统治区(周宝昌,1983:103)。总之,这种有组织、有层次的报刊发行方式,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书报检查制度,适应于当时边区的革命战争环境。
为了解决邮政撤销后报刊发行困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边区设立了通讯站及分站,总站设在延安,其工作范围主要在边区境内并衔接晋西北(齐心,1988:57)。在发行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努力加强边区各地通讯站的效率,各县建立发行登记制度,并负责规定县区乡报纸的运送方法,提高由县到区乡的发行速度(解放日报,1945年1月11日)。1941年8月,边区通讯站对运输线路进行改革,改为运输昼夜兼程班,提高发行速度。通讯站的设立丰富了《解放日报》的发行渠道,拓展了边区由市到县、乡甚至解放区外联系紧密的网状运输线路。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报纸发行网络,覆盖整个边区,《解放日报》的最高发行量达到7600份,自办发行范围大约为方圆30公里(田中初,2017:52)。不过,尽管《解放日报》多元化的渠道提高了报刊发行速度,但是抗日战争时期,与其他党报的发行量进行对比,不难看出《解放日报》的发行量仍然不高(见上表)。
《解放日报》发行量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员不足和缺少交通工具。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中也提到,“通绥德的汽车可以载运客商,而不允带运几十斤重的邮件,几千里邮线,工人日以继夜地运输奔跑,每月只有十五元津贴”(解放日报,1942年2月1日)。“边区通讯站寄件速度太慢主要原因是通讯工人不敷分配,八九十人步行长达数千里交通线,遍及三千余县间的高山曲径,欲求迅速传达是不可能的。另外,交通线是日夜接力传递,一个工人病倒了,就会影响报刊送达时间”(解放日报,1942年8月7日)。此外,边区通讯站尚不够健全,两天的路程报纸十几天才送到,一张报纸送到延安以外的读者手里,新闻已变了旧闻(李得华,1941)。外在条件与内在因素的双重阻碍下,《解放日报》的发行量与发行速度受到制约。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将“联系群众”和“增强党性”作为报纸改版的主要靶向。《解放日报》改版后加强通讯网络建设,恰恰体现了报纸深入群众的特殊意义和存在价值。陆定—(1981)认为,在改版之前报纸同地方党和群众没有组织关系,《解放日报》编委无人参加西北局的会议,在县、区、乡没有通讯员,这时的报纸没有完全进入群众的生活场域。1942年9月,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要求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与报馆取得直接联系,负责组织所管地区内的通讯员工作,并检查党报的发行情况(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1990:463)。在各级党委建立报纸通讯网,达到每区有一个通讯员。尚无通讯员之各区,应即物色适当人员充任(张若筠,1994:143)。同时培养工农兵通讯员,到1944年2月,《解放日报》已拥有600多人写稿的通讯员网络。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下,《解放日报》大力发展通讯员组织,据统计,1944年11月边区通讯员近2000人,其中工农通讯员达到1100人,通讯员帮助推销报纸,报纸被传播到陕甘宁边区的每个角落(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0:246)。在此之前,很少有报刊鼓动读者作为“通讯员”,“通讯员”意味着读者与报纸之间建构出一种情谊,并非以往单一的买卖关系,将读者定位成“报纸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字为报纸的发展贡献出智慧和力量。1944年《解放日报》社论中提到,“要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的通讯员统统组织起来”。所谓“有组织”和“无组织”对应了网络结构中的“党内”和“党外”。“统统组织起来”表明发行网络由内而外的延伸,报刊发行以吸纳基层人员写稿的方式,在大众化媒介的动员下,卷入报纸的内容生产(黄伟迪,2019),在作者即读者的身份转换下演变出一种新的发行形式。
三、延安时期的读者群体与阅读形式
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曾说,“《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在十年之内,要有一百四十万人的三分之一能够看《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113)。1941年延安县从邻县拨了一万人,总人口达到5.5万人(解放日报,1941)。以《解放日报》7600份的发行量作为参考,地理范围包含31个县,每个县收到报纸245份,平均224人拥有一份报纸。据李金铮教授的统计显示,1934年《申报》发行15.59万份报纸,分布于27个省份,根据全国总人口4.4亿估算,平均2820人拥有一份报纸(李金铮,2018),比《解放日报》少得多。报纸的影响力与读者息息相关,读者的分布意味着《解放日报》当时的传播影响力的范围划分。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将采访科扩大为采访通讯部,通讯员总人数达到1030人,报纸发行范围涵盖31个县区。《解放日报》在边区发行县域通讯员人数最多的是绥德县(49人),最少的是神府县(4人),平均数25人以上的县区有13个,平均数以下的县域有18个(吴东兴,2018)。从《解放日报》边区通讯员的分布可以看出,读者已覆盖边区各个县域。虽然《解放日报》的发行也涉及其他地区,甚至是国统区,但占比较小,读者分布仍以整个边区为主。另外,读者的构成也值得关注。《解放日报》改版后加强与读者的沟通,设置“读者往来”、“信箱”等栏目,通过对资料梳理,显示出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农民、工人中皆有读者。
首先,党政机关干部是重要的读者群体。1942年10月28日,《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一文中写道:“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中央档案馆,1991:453)。说明《解放日报》对党内宣传、人员教育有着重要意义。1946年8月17日,中宣部发布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讨论〈解放日报〉两篇社论的通知》中指出,“望党内外根据《解放日报》刊登的《七个月总结》和《粉碎蒋介石进攻》两篇社论组织广泛讨论”(中央档案馆,1996:632)。另外,1946年11月发布的一则通知中也提到“望将戌支《解放日报》社论《论战局》一文,在党内、军队内群众中传达讨论,鼓舞斗志”(中央档案馆,1996:644)。
其次,事业单位员工、学生也具有读报的能力。中央研究院读者理丝同志读《解放日报》第22期中柯山的《日本革命运动史话》,对罢工人数统计提出了疑问,“罢工次数占全年二百分之一不到,但人数却占了百分之六十,使我怀疑统计数字的正确性”(解放日报,1942年8月21日)。中央党校的读者针对防疫工作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文章中表示,“关于捕鼠问题在贵刊上多次提倡,望贵刊能够建议卫生行政方面,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并负起实际领导责任”(解放日报,1942年5月18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读报之后经常对报刊提出积极的反馈。学生群体也会根据周边环境对《解放日报》提出相关意见与建议,延安大学学生李在藻读郭涛同志关于农村负担合理问题的一篇文章后向《解放日报》提出一些意见,认为“郭涛同志引用材料正确性非常值得怀疑”(李在藻,1942)。抗大时事小组的成员说道,“我们这里很多同志对报纸的兴趣很高,但常识太少,难有教员帮助开会讨论”(解放日报,1945年4月1日)。
最后,工农群众也是一类读者群。工艺实习厂的一名读者说道,“读了老雷同志的‘医务工作者的反省’以后,必须反对各业中样样都懂,样样不精的人”(解放日报,1945年1月25日)。一位炭厂工作者看到《解放日报》上一篇关于炭窑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以作领导炭窑工作的同志参考(解放日报,1945年7月22日)。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同志读了《解放日报》一篇文章纠正其称呼,写道,“希望延安的同志纠正对少数民族农民同志称呼‘苗子’、‘达子’等不对的名称”(韩璋,1942)。乡支书孟庆成总要问:“《解放日报》上发出什么了?”当他把吴满友加紧开荒的消息带回去,他的队员们喊起来:“咱们午上也不休息,再上一次报吧!”乡干部和村民们把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名字看作一件大事(解放日报,1943年6月12日)。这表明,以工农群众为代表的读者群体将《解放日报》与日常生活相勾连。此外,从整理的读者意见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单位的《解放日报》读者分布,例如一五五师习西留守处、中央研究院、曲于县委、靖边县委、金盆湾、延大、自然科学院、西北党校、边师、甘泉县一区区委等(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9日)。
改版前,《解放日报》对读者的想象不贴合实际,博古认为《解放日报》是大报,应该着眼全世界,要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这一做法引起广大读者不满,读者李微提出:“贵报刊登大量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我是很难看懂的,这些对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联系很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8:10-11)。对读者的想象偏差,造成阅读内容的错误预判,自然会导致读者解读时的千变万化。据统计,《解放日报》对读报的报道集中在1944年,1941年—1943年关于读报的文章较少。阅读《解放日报》关于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与1944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内容发现,前者未涉及关于读报组的内容,而后者明确提出,“推广民办小学及读报识字组”(张睿,2021)。
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中提到,“随着边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报纸在群众中的作用已日益增强,全边区有一万多群众加入读报组”(陕西省档案馆,2016:423)。也许有人要问:“报纸我一个人读好了,何必要成立小组?”须知道,一个人读报知识有限,但集体读报可以集思广益有商有量。不但可以在讨论中解决困难,并且可以互相交流心得。更重要的是集体读报可以推动工作,加强组员的集体观念和团结互助(解放日报社编辑部,1951)。读报员通过阅读、宣讲报纸的内容,使读者在听报的过程中有更多情感卷入,强调了读报的集体性和组织性。各个不同的读者群体,包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军人、工人、农民都自发建立起读报组进行阅读活动(见图1)。
党政机关人员主要以集体阅读的方式成立读报组,乌阳区委召集全体干部商议学习问题,张德任读报组组长,每次《解放日报》社论由他讲解,早上集体学习,晚间讨论(解放日报,1944年4月12日)。车会区区委要求在群众大会上、学校里、冬学里、自卫军中进行读报工作(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8日)。从某种程度上看,建立读报组是激发群众阅读兴趣的有效方式之一,八分区政治部在离东各村建立读报组,执行一字一弹的运动,要求读报者也日益增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2日)。有的读报组是为了解决党员对报纸内容不够重视而专门设立的,如有的地区认为部分党员对党报关心不够,需设专人帮助干部读报(解放日报,1942年9月28日)。
军队建立集体读报制度,在集体读报的过程中开展识字运动。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公布后,驻军刘堡团决定以连为单位实行集体读报制(解放日报,1942年10月6日)。每个连队的班排都设有读报组长,在山上休息的时候,大家自觉聚拢听报读报,遇到不认识的字,马上找教导员询问(解放日报,1944年5月30日)。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日、伪军占领区开展的武装小分队,通过读报的方式为村民传播正确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武工队在敌占区村庄建立秘密读报组,读报活动开展后,敌占区群众及时了解抗战形势和解放区情形,他们深信中国有毛泽东的领导,抗战一定能胜利(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2日)。
与以上情况相比,普通工农群众自发组织的读报组最具有特色。平山卸甲河等村每天晌午或晚上,读报组员拿着报纸向端着碗饭的老乡们讲述农业常识、国家大事(解放日报,1943年8月29日)。皖南柳州村的农民读报组员读报后都反映,“从前的报纸是反动派办的,我们听都听不懂,听了也没有用,现在报纸是我们自己的了,读了很有味道”。报纸经常刊登读者来信反映群众的意见和生活,上海国棉十九厂的读报组,看见自己的稿子在报纸上登了出来,高兴地说,“现在报纸真是自己的了,过去反动派的报纸,我们工人要写稿子登出来,真是想也不要想”(解放日报社编辑部,1951)。马家沟读报组的三间平房,已经成为劳动者的俱乐部,每当黄昏读报时,农民三三两两从窑洞走出来吆喝着:走呵!读报去了(解放日报,1944年3月31日)。有的村子还对读报人数、方式、时间设定要求,甘泉民教馆一边发动商人订报,一边组织读报组,现在商人中订报者已有二十三家,全市商人五十三家编了四个读报组(解放日报,1944年5月21日)。每次报纸下乡后,吴堡留家沟区一定要读给群众听,要求每乡有七十人听报(解放日报,1943年11月5日)。每次读报时,马骥就先把报上的标题读一遍,群众说读哪一段就读哪一段,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改俗话代替,读完一段再把大意讲一遍,每次读两三段,读完后群众提出意见讨论,每次所费时间大约四十分钟(昌之,1944)。
集体读报根据各类读者群体的诉求产生不同的效果。其一,读报有助于识字、提高文化水平。吴堡刘家沟区五六两乡,为了落实群众教育工作,发起读报竞赛活动。延县朱家沟炭工利用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读报,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解放日报,1944年4月3日)。延家川二乡的识字班,一共有二十二个娃娃,由先生给学生读报,每天最多识十个字,最少识一个字(解放日报,1944年4月17日)。合水县城区民教教育馆,近期组织了五个读报识字组,民教馆同志组织民众集体读报。防疫运动中,人们最爱读卫生常识的文章,他们把卫生常识、治牛病的办法记下来贴在墙上(解放日报,1944年8月11日)。另外,清真寺和教会也积极推广读报活动,边区清真寺推行读报活动,每礼拜五在寺上教回民读报识字(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2日)。庆阳三十里铺天主教教堂,在每次做完礼拜后自发进行读报,听众最少三四十人,多则一百余人(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日)。其二,读报增加民众的生产劳动热情。当业富区助理员拿着解放日报给模范乡长米如礼朗读时,米家兄弟的劳动热情不可抑制得高涨起来(解放日报,1943年6月12日)。苏哲说道,“看到《解放日报》登载晋察冀边区创造出积肥模范和英雄,是个很动人的例子”(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0日)。农民群众通过读报增加了劳动生产经验,真正理解读报的用处。报纸通过读报组有力地教育着群众,三乡东庄慕消财,从前不参加变工生产,经读报教育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热心公益的好公民了。九甘目沟群众魏得富,在开始听读报时,他埋怨说:“别村都不读,光咱村读怎行?”现在他高兴地说:“大事情也懂下了,字也识下了,药方子也学得了,真是好事情”(解放日报,1945年1月24日)。还有的村民已经将读报作为一种习惯,北岳区读报组已经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乡村读报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一天不读报闷得慌”,已经成为多数群众的感觉(解放日报,1943年9月12日)。其三,读报帮助群众形成正确的政治意识。不论工人、里弄居民、学生、农民、机关工作者、战士,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报纸中获得极大的好处。可以明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可以知道新社会的很多新道理。在四区区委的帮助下,马家沟村组织了读报组,村民说:“过去不读报,一满黑洞洞的,现在读了报,毛主席给咱老百姓计划的什么,咱们都知道了”(解放日报,1944年3月24日)。
除了集体阅读以外,还有一些个人阅读体验。改版后,《解放日报》出版了专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提出阅读分层原则,“区分不同人群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高华,2000:153)。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解放日报》的新闻宣传在各根据地起到榜样的作用。陈克寒回忆说,《解放日报》是我们学习的报纸,在根据地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王敬,1984:118)。秦纯一在《我所体会的延安整风精神》中写道:“1944年春,学习《解放日报》的社论,每个人的觉悟提高了,党性也增强了”(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1989:245)。胡绩伟学习改版文件后说,“看到《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变化,才清楚理解到党报是党和人民喉舌的道理”(王润泽,2009)。
个人阅读是读者自身的行为,不仅强调报刊对传者的意义,更重视读者对报刊本身以及新闻价值的需要。而作为主流阅读形式的读报组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军队、农村宣传动员的重要方式,是一种具有仪式性、组织性、集体性的媒介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并与生产、生活合二为一,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涌现的革命场景。
四、“信箱”:读者与报刊的互动及反馈
《解放日报》自改版以后宣传内容与方向出现较大调整,读者阅读后的反馈与报刊宣传内容直接形成互动关系,读者对报刊反馈的前提,是需要了解报刊为读者所呈现的内容包括哪些?报刊以向“完全党报”的路径转变为目标,不同时期所宣传的重点随着政策和抗战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解放日报》改版前宣传重点放在了国际新闻,据统计,改版前的三个月共发社论83篇,关于国内与根据地的共49篇,直接与整风运动相关的仅有2篇,1942年4月—5月间,共发社论51篇,关于国内的是41篇,其中16篇是报道整风运动的(黄旦,2008:269)。1942年主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风运动、苏德战争;1943年侧重点在于抗击第三次反共高潮宣传战、贯彻“内外有别”的宣传方针、大生产运动、宣传劳模运动、政策宣传、惠民政策;1944年宣传民主运动、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发展私人资本主义;1945年—1946年重点宣传贯彻党的“七大”,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偏向宣传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揭穿蒋介石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王敬,1998:107-361)。除此之外,还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路线方针、国际政治、边区实况、批判“左”倾错误、民众动员、科教文卫、军事状况、劳动模范、抗日战争形势、爱国主义等。
针对报纸各类宣传内容,资料显示读者大多作出了积极的反馈。总体来说,读者对报纸宣传内容产生认同,并根据报纸中的教育内容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实现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引导和动员的效果。1943年4月5日的通讯《向军队看齐》,写出了农民的心声,读报以后许多村子组织南泥湾的战士同农业劳动英雄们展开竞赛,推动了生产运动。1943年4月12日,《解放日报》一版发表了彭德怀副司令给“欧团”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指出战斗、生产和教育的关系,前方战士阅读后受到大大的鼓舞,纷纷响应号召(王敬,1998:244-245)。还有的群众讨论报纸上的内容,说道,“共产党连二流子都可以改造为好人,我们更要努力劳动,不然真对不起毛主席对咱们的好谋划”(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1946:8-9)。1945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妇女阎桂芳的文章,介绍其参与纺织生产,还带动其他人的劳动积极性,引起子长当地的群众热议,有的读者将这条新闻读给自己的妻子(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1日)。可以看出,文章塑造了妇女的劳动形象,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44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对于改进和提高报纸关于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的报道,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敬,1998:269)。对比报纸宣传内容来讲,读者反馈的信息较少,大部分来源于回忆录、读者来信、文献史料等,但从搜集到的读者反馈的资料中可以反映出,报纸的宣传内容对读者的生活、教育以及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读者对报纸宣传内容作出直接的反馈,《解放日报》还设立“读者来信”专栏,鼓励读者用写稿的方式提出意见或建议,形成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笔者对1942年4月1日之后的读者往来、从读者中来、信箱、读者园地栏目做了梳理和统计,共计相关文章391篇,划分为5个主题(详见下表)。
统计数据显示出,《解放日报》改版后与读者的互动频率远远高于改版前,改版前的读者信箱中“军事类”的占比高于1942年之后。报刊改版后,1944年—1946年与读者的互动达到了高潮,特别是1945年,与读者互动率达到了50%。从互动主题来看,改版后读者的关注点聚焦于“边区生活”与“科教文卫”,对“军事”的关心较少。值得关注的是,1946年读者增加了对“政治政策”的关注,从以往的6%—8%的互动率,提升至17%,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读者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与素养。
《解放日报》改版特别重视读者意见,改版前夕,记者莫艾深入群众进行采访并收集约50人的反馈意见,被访问对象当中有农民、部队教员、学生、工人、妇女工作者、知识分子等。南区居民对报纸提出意见:一、本报并没有讲出老百姓的真心话;二、农民不识字也都不看报,如果能有人读报就更好了。纺织厂职工三十名,能看报的只有两人,工人说:《解放日报》太深奥了(莫艾,1942)。报纸改版消除了阅读中的张力,不再局限于传者意识的理念灌输。正如《解放日报》编辑王揖回忆改版工作时说,“《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质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闻改革,已远远超过任何版面变化的范围”(丁济沧,苏若望,1989:59)。
在读者与报刊互动的过程中,读者的表达偏向于两种形式。一类是读者阅读后的感想。1944年9月10日,读者任堔读了李望淮同志的《安塞秋冬两季工作如何进行?》一文,认为应在准备工作中增加“整理仓库”一项,需召集仓库主任检查仓库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9月10日)。编辑会根据读者的感想和疑问,对每个问题展开解释与回复,形成与读者良好的互动关系。另一类是读者提出的改进意见。1942年4月25日,信箱栏目刊登了一篇读者对鲁迅图书馆的批评与意见,读者认为图书馆的借书制度和管理员态度亟需改正。于10日后,《解放日报》刊出图书馆接受读者的批评,针对图书馆管理问题、借书时间、借书窗口大小作出答复(解放日报,1942年4月25日)。还有读者建议增加报纸的印数,“编辑同志:开展‘提高文化、扫除文盲’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多出报纸,增加《解放日报》和《群众报》的份数”(尹达,1944)。除了读者提改进意见,还有一些单位针对提出的意见,与读者互动交流。边区通讯站工作人员读了《解放日报》4月6日信箱栏,对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回复,并表示“欢迎各县区单位多向我们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我们改正通讯站工作”(解放日报,1945年5月5日)。比如新华书店总店的工作人员读了《解放日报》19、25日的“信箱”栏目,回复道,“对读者的关怀表示感谢,对不足之处作出回应”(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0日)。报刊作为沟通互动平台,将传者与受者通过阅读的方式结合起来。
此外,笔者认为《解放日报》以“典型报道”的方式宣传劳模,也是改版后加强与读者对话的另一种创新模式。1943年2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一封劳动模范杨朝臣向吴满友发出的挑战信,第二天又发表了吴满友的回信,并对此进行深入报道。报纸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对劳动的热情与先进事迹,形成有效的引导作用,激发读者参与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结语
《解放日报》改版形成了延安时期党报独特的宣传模式与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研究价值。对读者而言,获取报纸是阅读的前提。报刊发行状况直接影响读者的范围与阅读的选择。受到环境因素和经济条件等不利条件的制约,创刊伊始,《解放日报》发行遇到诸多阻碍。改版后,整合多种发行手段实现报刊与读者的结合。值得一提的是,各地区不断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通过他们与读者建立广泛的联系,拉近报纸与读者的距离,真正起到促进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作用。反观之,基层通讯员的网络建设,呈现出“作者即读者”的意涵,在写作中对组织的感知和判断不断内化,将个体融入党报意识,通讯员网络孕育出适应现实条件的阅读与发行模式。以发行范围锁定读者群体,《解放日报》改版后拥有多样化的读者群,其中农民群众最具代表性。共产党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与乡村精英作用,通过集体阅读方式,动员广大群众读报,形成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读—听”系统和社会网络,在互动中强化了组织与群众的关系(蒋建国,2021)。此外,依据层级开展个人阅读分层,将文本的特性与读者体验相结合,聚焦性阅读有助于实现不同革命群体的稳定性。报纸改版重视读者意见,实现传者和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读者是报刊内容、风格、形式变化的最终接收者和反馈者,从读者的层面最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集体组织者”运用党报与群众沟通的效果和意义。
对比其他中共党报阅读史的研究,可以明显看出《解放日报》的特殊性。《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强调报刊的运作机制和外部环境变化,对读者阅读感官的影响。而《解放日报》通过报刊的改版,重建与读者的关系,是内在逻辑的改变。这种改变最大限度发挥了思想整合、坚持党性与联系群众的媒介功能,将读者阅读构成一种媒介实践,即由内部改版外延至发行、阅读和互动,呈现出党报与读者彼此依存的关系。从阅读史的角度考察,可以揭示读者如何看待和理解《解放日报》改版,以读者的认知和价值标准判断改版后强调“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的意义。■
参考文献:
昌之(1944)。一个农村读报组的创办。《解放日报》,9月24日第2版。
丁济沧,苏若望(1989)。《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董昊,王建华(2021)。发行、阅读与编者互动:重庆《新华日报》的阅读史。《新闻与传播研究》,(12),21-34。
高华(2000)。《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韩璋(1942)。尊重少数民族。《解放日报》,6月10日第4版。
黄旦(2008)。《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伟迪(2019)。协作生产:革命时期党报通讯员的网络建构与技术改造。《编辑之友》,(12),88-93。
蒋建国(2021)。中共延安时期读报组的知识共享、群体互动与社会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2),151-167。
解放日报(1941年4月1日)。致读者。《解放日报》,A1。
解放日报(1941年8月16日)。边区各县遍设书店。《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3日)。新华书店安定分店组织读报组。《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2年2月1日)。改善通讯站工作。《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5日)。关于鲁迅图书馆的批评与答复。《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2年5月7日)。读郭涛同志「农村负担公平合理问题」后。《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2年5月18日)。防疫工作应该切实推行。《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2年8月7日)。加强通讯交通。《解放日报》,A1。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1日)。关于日本工农斗争的统计。《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2年9月28日)。讨论西北局党报决定。《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2年10月6日)。刘堡团集体读报。《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9日)。读者对本刊的意见一束。《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边区新华书店一周年发行书报百万份。《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3年6月12日)。延县各区宣传科长重视阅读本报。《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3年8月29日)。读报工作普遍深入民间。《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2日)。北狱区群众热爱报纸 读报工作普遍开展。《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3年11月5日)。吴堡刘家沟区推行农村读报运动。《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2日)。各村成立读报组。《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8日)。车会区开展读报运动。《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3月24日)。读报组推进了生产。《解放日报》,A1。
解放日报(1944年3月31日)。读报组将续在各村成立。《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4月3日)。延县朱家沟炭工创造增产煤炭新方法。《解放日报》,A1。
解放日报(1944年4月12日)。区级干部热心写稿读报。《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4月17日)。提倡大家读党报。《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5月21日)。组成商人俱乐部读报组。《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5月30日)。战士们自动读报识字。《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8月3日)。合水城区读报组办得好。《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1日)。通过学生、读报组推行卫生运动。《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9月10日)。整顿仓库。《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日)。组织天主教堂读报组。《解放日报》,A1。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2日)。边区回民文化发展。《解放日报》,A1。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0日)。新华书店总店关于读者来信的答复。《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0日)。积肥和卫生。《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2日)。敌占区成立秘密读报组。《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5年1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5年1月24日)。新正一区重视读报。《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5年1月25日)。不安心工作的同志请想一想。《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5年4月1日)。寇松钱等等。《解放日报》,A4。
解放日报(1945年5月5日)。希望对通讯站多提意见。《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2日)。对炭窑工作的几点补充意见。《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1日)。〈大家来办自己的报〉介绍子长瓦市黑板报。《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6年6月18日)。改进书报发行工作。《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22日)。新华书店书报下乡面向农村读者。《解放日报》,A2。
解放日报社编辑部(1951)。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C25-2-5-37,9月10日。
赖伯年(1998)。《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西安:西安出版社。
李得华(1941)。加强通讯站工作。《解放日报》,11月10日第4版。
李金铮(2018)。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近代史研究》,(4),4-25。
李在藻(1942)。读郭涛同志“农村负担公平合理问题后”。《解放日报》,5月7日第4版。
陆定一(1981)。陆定一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新闻与传播研究》,(3),1-8。
[美]马克·塞尔登(2002)。《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莫艾(1942)。本报革新前夜访询各界意见。《解放日报》,4月2日第2版。
齐心(1988)。《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选编》。西安:三秦出版社。
陕西省档案馆(2016)。《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0)。《陕西省志·报纸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田中初(2017)。《革命情境中的大众传媒与乡村民众:以“群众办报(1920-1949)”为视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敬(1984)。《陈克寒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敬(1998)。《延安〈解放日报史〉》。北京:新华出版社。
王强(2022)。改造读者—基于阅读视角对《解放日报》1942年改版的再考察。《新闻大学》,(2),71-83。
王润泽(2009)。重塑党报:《解放日报》改版深层动力之探析。《国际新闻界》,(4),105-111。
吴东兴(2018)。《延安〈解放日报〉通讯网建设研究》。延安大学。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1990)。《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1989)。《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二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叶再生(2002)。《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北京:华文出版。
尹达(1944)。大量制造印刷纸。《解放日报》,8月2日第2版。
张睿(2021)。《“群众办报”:思想史与阅读实践中的理论构建》。西北大学。
张若筠(1994)。《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03)》。北京:中央档案馆。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2000)。《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8)。《新闻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3)。《毛泽东在陕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1946)。《活跃在农村的读报组》。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199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
钟紫,赵玉明(1984)。《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周宝昌(1983)。《新华书店在延安初创时期》。上海:学林出版社。
李丹系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传播话语体系变迁研究(1919-2018)”(18ZDA3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