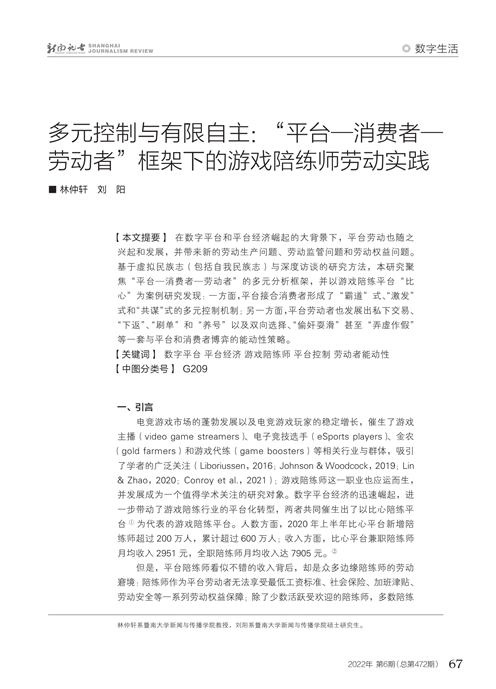多元控制与有限自主:“平台—消费者—劳动者"框架下的游戏陪练师劳动实践
■林仲轩 刘阳
【本文提要】在数字平台和平台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平台劳动也随之兴起和发展,并带来新的劳动生产问题、劳动监管问题和劳动权益问题。基于虚拟民族志(包括自我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聚焦“平台—消费者—劳动者”的多元分析框架,并以游戏陪练平台“比心”为案例研究发现:一方面,平台接合消费者形成了“霸道”式、“激发”式和“共谋”式的多元控制机制;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也发展出私下交易、“下返”、“刷单”和“养号”以及双向选择、“偷奸耍滑”甚至“弄虚作假”等一套与平台和消费者博弈的能动性策略。
【关键词】数字平台 平台经济 游戏陪练师 平台控制 劳动者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G209
一、引言
电竞游戏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电竞游戏玩家的稳定增长,催生了游戏主播(video game streamers)、电子竞技选手(eSports players)、金农(gold farmers)和游戏代练(game boosters)等相关行业与群体,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Liboriussen, 2016; Johnson & Woodcock, 2019; Lin & Zhao, 2020; Conroy et al., 2021);游戏陪练师这一职业也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一个值得学术关注的研究对象。数字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带动了游戏陪练行业的平台化转型,两者共同催生出了以比心陪练平台①为代表的游戏陪练平台。人数方面,2020年上半年比心平台新增陪练师超过200万人,累计超过600万人;收入方面,比心平台兼职陪练师月均收入2951元,全职陪练师月均收入达7905元。②
但是,平台陪练师看似不错的收入背后,却是众多边缘陪练师的劳动窘境:陪练师作为平台劳动者无法享受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加班津贴、劳动安全等一系列劳动权益保障;除了少数活跃受欢迎的陪练师,多数陪练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等待”消费者下单,处于劳动“待命”时间长而劳动报酬低的状态;同时,在与平台的收益分成问题博弈上,陪练师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需要相应做出让步,需要被比心平台抽取20%甚至30%左右的收入佣金;此外,在与消费者的矛盾纠纷中,陪练师往往也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需要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甚至不合理要求。一面是光鲜亮丽的平台经济盛况与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另一面是不尽如人意的劳动窘境,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指向了本研究关切的核心问题——平台劳动中的劳动控制与能动性如何展开?
二、文献回顾
(一)平台时代的多元控制
数字平台、平台经济和平台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平台研究(platform studies)也随之成为学界方兴未艾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吸引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Gillespie, 2010; van Dijck et al.,2018; Plantin et al., 2018; Nieborg & Poell, 2018; Nieborg & Helmond, 2019;孙萍,2019)。其中一个重要研究进路就是探讨数字平台如何成为经济配置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如何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劳动结构、平台积累与资本增殖(Helmond, 2015; Chen & Qiu, 2019; Plantin & Punathambekar, 2019;姚建华,2020)。
这一研究进路更具体指向了数字平台(比如所谓的GAFAM: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Microsoft)对平台劳动者(Platform labor)的控制,特别是这种控制机制背后的权力关系问题(Gillespie, 2010;van Doorn, 2017; Plantin et al., 2018; Nieborg & Helmond, 2019)。这是因为,平台凭借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获得控制权,从而在与平台劳动者的权力博弈中处于支配性地位(Mcintyre & Srinivasan, 2017; Plantin et al., 2018; Rosenblat & Stark, 2016;齐昊等,2019)。平台主导规则的制定,并有权对违反规则的劳动者进行惩罚,而劳动者几乎无权参与平台规则的制定,缺乏规则商议与劳动协商的空间(吴清军,李贞,2018)。而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发展,一些数字平台(如Uber)还能进一步利用算法实现对劳动质量、劳动绩效和劳动价值的监督、控制和评估(Rosenblat & Stark, 2015)。某种程度上,平台经济发展实质是对生产关系、劳动关系和传播关系的重构,而且数字技术越发达、平台化程度越高,平台劳动者异化程度越高、平台控制力更强(Plantin et al., 2018;张铮,吴福仲,2019)。
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平台完全垄断了对劳动者的控制,总会有平台之外的其他行动者的多元控制。比如,有学者强调国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国家通过政策干预介入对数字平台的监管,并在其中实现了对平台劳动者的监管,平台甚至只是起到代理或者中介的角色(Li, 2012; Cunningham et al., 2019)。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平台形态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参与到平台信息流通与交易的多边市场中来,出现越发复杂的多元控制问题(齐昊等,2019; Karatzogianni & Matthews, 2020)。其中,平台消费者便成为多元控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正如姚建华所分析的:“他们(众包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受到了来自任务发起者(即消费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这种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不仅包括任务发起者对托客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强有力的影响,而且还涉及平台对托客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强制退出的‘霸权式’管理”(姚建华,2020:25)。
不过,平台消费者对劳动者的控制也不是绝对垄断和霸权的。这是因为,数字平台与各用户(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一种多元多边博弈的复杂关系(van Dijck et al., 2018),比如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往往也存在着利益摩擦,从而给劳动者的个体能动性留出空间和可能。这进一步启发我们在“平台—消费者—劳动者”框架下探索平台时代的多元控制问题,并特别留意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个体能动性问题。
(二)劳动者的个体能动性
实际上,即使面对平台时代的多元控制,平台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非常活跃的因素,始终保有其应有的个体能动性,以及一定的工作积极性、自主性和主体性(庄家炽,2019; Fan, 2021; Mao, 2021)。比如,网约车司机会在平台之外再使用其他应用程序,从而能在一种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高价)订单,而且还能规避平台惩罚(Chen, 2018);外卖骑手也会通过与站点负责人刷单、与同伴合作、与餐厅负责人交好等方式,争取一定的劳动自主空间(Sun & Chen, 2021)。在这一能动过程中,合作、希望、梦想、创意和情感话语等因素都起到了积极作用(Kuehn & Corrigan, 2013; Alacovska, 2019; Karatzogianni & Matthews, 2020)。
具体到中国语境,新近已经有很多学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特别侧重情感劳动视角,以及与情感紧密相关的认同感和满足感。在这一视角下,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某种程度上都是非物质的情感劳动者,一方面要生产、压抑或改变自己的情绪状态以迎合顾客的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则又以喜爱和激情作为驱动力而获得满足感和认同感(胡鹏辉,余富强,2019)。更重要的是,平台劳动者在劳动中认同感的获得,一定程度上也催生和促进了其能动性以及对平台的反抗意识(赵璐,刘能,2018;涂永前,熊赟,2019; Sun & Chen, 2021)。
具体到游戏领域,学者主要集中于“金农商业”(gold farming businesses)相关的“金农”(gold farmer)和游戏代练(game boosters)的研究(Lee & Lin, 2011; Tai & Hu, 2018;胡冯彬,2020)。在金农企业这种劳动密集型“现代血汗工厂”(modern-day sweatshops)之内,金农与代练的劳动具有重复性高、强度大、时间长、薪资低和安全保障差等特点(Dyer-Witheford & De Peuter, 2009;De Peuter & Young, 2019)。不过,一些金农和代练也能积极发挥能动性,利用游戏漏洞、外挂软件等技术手段“巧妙地作弊”(skillful cheating)以获取额外收入(Liboriussen, 2016: 318),或者通过使用特定身份话语,自主决定时间安排与工作环境等方式,构建积极的职业身份认同(Lee & Lin, 2011),或者利用自身资源获取客户,并注册多个账号以规避限制和审查(Conroy et al., 2021)。
上述文献回顾带给我们的启发是,需要同时关注平台控制与劳动者能动性这两条主线,因为这二者的互动揭示了劳动控制的新形态与劳动实践的新特征。因此,本研究将在“平台—消费者—劳动者”的多元框架下,关注游戏陪练平台劳动控制的新形态,以及平台多元控制下游戏陪练师的能动性表现。具体而言,本研究将主要探索以下研究问题:平台方如何实现对陪练师的控制与监督?消费者在其中充当着怎样的角色?面对平台与消费者的多元控制,陪练师如何进行能动性的应对?
三、研究方法
因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虚拟民族志(包括自我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笔者选取国内规模最大的比心陪练APP平台作为田野,并以消费者的身份进入田野进行虚拟民族志观察(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4月1日),主要观察陪练师们主页上的自我形象呈现,包含头像、自我介绍、日常动态等,并与其进行日常互动。在此基础上,挑选特定的有代表性的陪练师(主要从接单量与好评率两个维度来分别挑选陪练师,如接单量大与接单量小的;好评率为100%与好评率较低的),进行深度观察和互动,经过筛选后下单购买其陪练服务,进行消费者角色的自我民族志体验,也为下一步的深度访谈奠定基础。
同时,笔者也通过自我民族志,以陪练师的身份体验平台劳动者在复杂劳动情境中的实践,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体验和反思:一是平台方与陪练师的关系,特别是平台对陪练师的监督、激励、奖惩机制等;二是消费者与陪练师的关系,特别是消费者对陪练师的预期要求、挑选标准、劳动者—消费者关系定位、消费者与陪练师的具体互动行为等;三是面对平台与消费者的多元控制,陪练师发展出哪些能动性策略。笔者作为陪练师进行自我民族志过程中始终带着这些问题进行反身性的思考与记录。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就上述问题先后对19位陪练师和消费者进行深度访谈。受访者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四、“平台+消费者”的多元控制机制
平台不仅是追逐利润的排他性商业组织,往往也承担着国家监管的代理角色(Li, 2012; Cunningham et al., 2019)。因此,比心平台在推进商业化的同时也积极寻求自我合法化,据此制定相应的平台规则与机制。一方面,比心平台建立起严格的审查机制,并不惜以“封号”作为惩罚机制,以减少平台利润流失和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比心平台也建立起一套游戏化、差异化的奖惩机制,用以激发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自发使用平台进行交易以便于平台监管。然而,这两种手段仅能在平台内部发挥作用,难以介入平台之外的实际陪练过程,因此,平台还引入消费者评价机制、退单与举报机制,借此间接介入劳动过程,实现对平台劳动者的远距监管(吴清军,李贞,2018)。
(一)平台的“霸道”式控制:审查、封号与“有苦没法说”
与其他数字平台不同,陪练师虽然是在比心平台上接单,但其实际工作空间和劳动情境却是在平台之外的各个具体游戏之中。因此,比心平台实际面临两重特殊压力,一是平台难以实际介入陪练过程导致的监管难问题,二是平台难以杜绝陪练师和消费者私下交易导致的利润外流问题。为此,比心平台更倾向于在其所能掌握的环节实行“霸道”式控制,以最大限度保障平台安全和场内交易。
首先,平台对劳动者拥有审查与封号的特权,审查与封禁暴力和色情等敏感内容,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性。人民网曾曝光比心陪练的一些女陪练师主动向消费者兜售视频裸聊等“深夜服务”,随后,上海市网信办等部门严肃约谈了比心负责人并责令其开展全面整改。对此,比心加大了平台的监管力度,建立了实时风控平台和内容审核平台等,通过“封号”手段打击平台内部的涉黄交易。李女士提到:“如果涉及色情会封号的,平台有一个检测的东西,一检测到哪些敏感字眼的话,就会给你封号。”王先生也提到:“平台风控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你出现敏感词汇,有可能会被检查到,所以说尽量避免这些敏感词汇。”其风控机制是人工智能筛查与人工审核确认相结合,若劳动者使用平台与消费者聊天涉及色情信息(如笔者曾尝试发出“一起睡吗”等关键词),平台人工智能会自动识别并发出警告,同时将其送往人工审核,一经查实有涉黄等违规信息,则立即封号。根据比心平台官方微博声明,截至2020年8月21日已经永久封禁涉黄账号累计超过2万个。
其次,平台还同步打击违规行为以保障利润不外流,主要是禁止陪练师私下添加消费者联系方式、私下交易、引导代练、转单等,若平台判定陪练师出现违规行为,则立即封号。实际上,由于平台抽成高、限制多,一些陪练师与消费者更倾向于通过平台认识彼此并获取联络方式后,绕开平台进行场外互动和交易。陈先生解释道:“平台会收20%的手续费,少的话感觉还行,但是金额大了就感觉越想越亏,100块钱给他扣了20块钱。所以我们是倾向于走微信……然后平台上面(提现)的钱也得要等很久才能到账,所以有时候会商量好,反正你微信转我,我也给你便宜一点,大家都合算。”但对平台而言,其提供交易中介服务必然要从交易金额中抽成作为盈利的来源(谢富胜等,2019),所以这种场外私下交易实际上造成了平台的利润外流,会被平台定性为违规交易而严厉打击。对此,王先生提到:“很早的时候,我刚做陪玩,那时候不会整,老板一说加微信,我发了微信号,后面就被平台给封号了。”李女士也提到:“有一次是因为在平台上被查到通过别的平台交易,好像是把微信号码发上去了。比心一旦敏感了就会有提醒你,一提醒的话,比心那边会查,一查就直接封掉了。”
以上情况都是陪练师确实做出了违规行为,但也存在“误封”的情况。郑先生讲述了他被“误封”的经历:“比心这东西还有监管的比较严,动不动就封你号,你某个话说错了,可能就是‘哔’,直接给你封号……我这号两周被封三次,今天刚好被封,平台说我转单,说我接完单给别人打。我自己单子都很少了干嘛给别人打?反正平台就给我封了,我这边也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证据来判定。我估摸着可能是因为老板点完单之后,有一个匿名小调查,就会说陪练师有没有转单之类的。但是因为有的老板他不看那些东西,因为跟他没啥关系,就随便瞎点一下,打完就拍屁股就跑了。”陪练师遇到“误封”的情况,有时会向平台发起申诉,但是由劳动者发起的申诉往往无济于事。郑先生解释:“比心非常不合理,动不动就瞎封,然后你申诉也没有用。上次是因为我就发布了一条信息,就想找一个陪玩,然后我这边就发了一个单子,上面写的我就说找一个有微信群的,平时自己玩也挺没意思的,我想找个群唠唠嗑啥的。然后第二天平台就说我引导别人代练。我发一个陪玩信息就引导别人代练了?然后我就去申诉,但是啥用没有,申诉功能我觉得就是个摆设。很多情况下,就是说对我们陪玩啊很不公平,有苦没法说,平台白白封了我三天。”
由此可见,平台凭借其支配性地位特别是其对平台规则的垄断性控制权,可以通过审查和封号对劳动者进行非常“霸道”的控制。这固然是平台承担国家监管代理的角色,即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干预等监管平台,而平台需要就此加强对平台劳动者的监管(Li, 2012; Cunningham et al., 2019),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并不惜以临时或永久封号作为处罚,从而实现了国家在远距离上对平台劳动者的监管。这一过程中,平台既保障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安全,也建立起交易界线防止利润外流。但是,落实到平台层面过于简单粗暴的监管控制,甚至连对“误封”的申诉都得不到回应,让劳动者“有苦没法说”,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体验,也忽略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二)平台的“激发”式控制:劳动时间和活跃度
由于平台“霸道”式控制压缩了劳动者的协商空间,此时,如何激发劳动者积极性,随之成为平台需要面对的问题。为此,比心平台以计算系统作为劳动控制的常态中介,建立了一套以“大神分”为核心的考核管理系统,将陪练师在平台的信息回复速度、活跃度等均纳入考核,把劳动过程划分为细密的、可供计算的操作形态,以实现对劳动者的监督与奖惩。具体而言,平台主要通过特定的激发机制,激发陪练师自发积极劳动并接受其劳动控制,特别是劳动时间和活跃度两个维度的控制。
在劳动时间控制方面,比心平台通过“我可以秒接单”功能(之后简称“秒接单”)实现对陪练师劳动时间“超额”而又“零散”的占用。平台凭借其组织信息传递和社会交往的优势(谢富胜等,2019),能够将大量劳动者聚集起来并纳入其生产体系,形成充足的廉价劳动供给,迫使平台劳动者陷入激烈竞争而处于劣势地位(吴清军,李贞,2018;张铮,吴福仲,2019)。因此,陪练师往往需要通过开启“秒接单”功能以获取更多的曝光量,从而提升其在平台的可见性(visibility);相应的,由于订单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劳动者被迫让渡大量时间进行漫长的等待。同时,“秒接单”内嵌了惩罚机制,陪练师1分钟之内未回复消费者消息就会被扣大神分1分,15分钟内未接单导致订单超时则会被扣大神分8分,因此,陪练师为了规避惩罚而被迫成为消费者信息的“秒回者”和随叫随到的“服务者”。刘先生解释道:“我刚开始来平台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找我,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发现开启‘我能秒接单’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但是那时候还不太懂,开启之后有个老板(比心平台陪练师对消费者的常用称呼)来找我聊,我当时正好在吃饭没看手机。结果一看发现没秒回,就差了三分钟,平台就给我扣了大神分。当时真的气死了,三分钟至于吗?后来我就尽量注意嘛,开启‘秒接单’之后,一时等不到老板来下单,就守在手机前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分散一些注意力,隔一会儿就瞄一下有没有接单信息。虽然这样大神分不容易被扣,但是说实话,挺影响我正常的生活的,我正打着游戏,消息来了,我得马上退出游戏给老板回信息,体验真的特别差”。
赵先生也表达了对平台惩罚机制的不满:“比心的这种秒接单扣分的行为就很离谱,不开秒接单吧,我才刚起步,没人来;我开吧,谁能没有个疏忽或者急事儿呢?万一一分钟没回复,分又会被扣,本来曝光就低,还给我雪上加霜。一分钟不回就扣太严格了!”因此,受访者纷纷表示,每天花费在平台上的时间非常之多。陈先生表示:“一般不开秒接单就不会在平台的‘陪练师’页面出现的,所以我只要闲下来的时候,就手机不离手,打开那个平台,每天在平台会花很多时间。”唐女士表示:“一个月30天,然后就偶尔休息两三天,这样偷个懒。每天早上起来已经麻木了,醒来第一反应就是先登陆比心……自己的时间肯定是比较少的,一直在打游戏。”郑先生表示:“我每天睡醒了就开始接单。基本上是每天时间都花在了这个平台和游戏上。”
因此,虽然平台劳动者的劳动场景与劳动过程转移到了数字平台上,融合了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在劳动形式上看似给予劳动者自行安排的自由度,但是,平台推出“秒接单”功能并将其纳入“大神分”的考核中,劳动者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等待和断续零散的时间分配,模糊了劳动者生活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谢富胜等,2019),加剧了对劳动者的时间剥削。实际上,“让人等待”正是权力的一种体现(孙萍,2019:53),劳动者在漫长的等待中成为权力关系中明显弱势的一方;平台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同时给劳动者传递“随叫随到”的观念,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时间自主权”,实现平台对时间秩序的重塑,重构“服务”与“被服务”的权力关系,最终加速平台资本的积累与扩张。
在劳动活跃度控制方面,平台通过“登陆天数”、“主动接单情况”和“每周推荐任务的完成”三方面的劳动活跃度来计算考核“大神分”。就“登陆天数”而言,陪练师在平台上的活跃天数越多,能够接到单的概率就越大,但对平台的依赖性就越强;就“每周推荐任务的完成”而言,平台所推荐的任务均致力于提升陪练师对平台任务的了解和操作,帮助陪练师更好地进行平台劳动。这两者的考核还相对简单直接,而“主动接单情况”的考核则较为复杂。平台设有“抢单中心”,让消费者在上面发布个人陪练需求,然后让一些符合要求的陪练师来回应与自荐,使消费者得以在众多陪练师中甄选和下单。梁先生解释道:“大神分真挺重要的,大神分不高不能包天、也不能打优惠的折扣之类的。所以每天都登录、做任务这些都是最基础的……而且如果你这周做了,下周不做,大神分就会变低……如果实在没有老板找我下单,我就会去抢单大厅,发语音抢单。他们(消费者)会发布一些要求,比如声音好听、技术高、幽默、话多之类。反正我抢单的时候都会话很多,语音发老长了。总之你活跃一点,肯定能接到更多单子,大神分也更多,雪球就滚起来了”。
在这样的活跃度考核压力和危机感下,陪练师被迫卷入激烈的劳动竞争并积极完成平台任务,以获得更高的大神分。而不同数字平台之间往往无法实现数据互通,劳动者在平台间切换、转移的成本非常高,从而形成劳动者对平台的依附性(谢富胜等,2019),比心平台亦是如此。大神分只是比心平台的内部考核和证明体系,无法转移到其他同类平台,因此陪练师在提高大神分的过程中花费的时间精力越多,沉没成本越高,越难以离开比心平台,即其“平台黏性”(platform adhesion)(Sun, 2019: 313)越高,使平台得以最大限度控制陪练师的劳动行为进而提升平台收益。
不同于传统劳动控制实践,数字平台的劳动控制往往更为隐蔽(宋嘉伟,2020;张一璇,2021);比心平台也不例外,它还巧妙地通过游戏化与差异化的管理机制,对劳动者进行隐蔽的控制。“游戏化”具体体现在陪练师提升大神分的过程,被平台模拟为提升“游戏段位”(垫底陪陪—比心新秀—接单达人—陪练精英—金牌大神)的过程,而平台每周更新的大神分排行榜,则体现陪练师之间的梯位变动,激励劳动者“打怪升级”以获得更高的分数。对此,梁先生表示:“我现在每天都盯着大神分,涨了就是红色,跌了就是绿色,就跟股票一样,感觉很刺激。它哪一天涨了,我就很有成就感,它要是掉了,我会感觉好像股票赔钱了,就会很舍不得,所以基本我不会让它掉的……我现在就很希望能登上大神分榜,感觉很厉害。”可见,劳动者在追逐大神分的“游戏”中获得了乐趣甚至快感,弱化了其对平台控制的认知(孙萍,2019)。而“差异化”的管理机制,体现在平台对处于不同大神分层级的陪练师进行特权的区别划分,包括陪练师在平台的基础曝光、定价特权、定价折扣和资质申请。如陈先生解释的:“你的(大神)分少了,你的价格就会降。比如说你基础的600大神分的时候,英雄联盟一把是10块到15块,最高能到15块。然后我大神分到700的话它又会涨一个档次,比如说就能接到20块到25块钱了……而且大神分总体上升之后,其他的游戏价格也会上涨。比如说我大神分600分,接王者荣耀一局只有5块钱,然后大神分到了700分就是7块钱,然后到800分大概就是13块钱……我肯定想把大神分提到800,谁不想价格涨一涨”。
由此可见,平台对劳动者游戏化的激励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某种程度上享受到了乐趣,特别是大神分成为陪练师衡量自我价值与塑造工作认同的重要因素;平台差异化的管理机制,则促使劳动者努力自我管理以得到更高的大神分,从而获得更多平台特权。这种情况下,平台的劳动控制更为隐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劳动者不自觉的认可。就这样,平台通过“激发”式的控制,不仅实现了对平台劳动者潜移默化的自我控制,实际也指向了平台经济对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深度重构(谢富胜等,2019;张铮,吴福仲,2019;Karatzogianni & Matthews, 2020)。
(三)平台与消费者的“共谋”式控制:消费者评价、退单与举报机制
由于平台的“霸道”式和“激发”式控制只能在平台内部发挥作用,难以介入陪练师与消费者的实际陪练过程,因此,比心平台还与消费者一道,“共谋”式控制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平台主要是通过引入消费者评价、举报与退单机制,实现平台与消费者对劳动者的共同监督与控制。
首先,由于游戏平台的实时性支持,平台消费者对劳动者的服务评价几乎是完全实时的,而且贯穿并影响整个劳动过程,成为劳动者的工作标准。相较传统的“售后评价”,这种实时评价机制显然指向了更深刻的劳动控制,迫使陪练师更加以客户为本位地保障服务质量。当笔者在游戏中取得了较差的成绩,消费者伊先生表示“你怎么又第八了啊,你是不是在瞎玩”,迫使笔者马上致歉并更加投入地继续提供服务。而且,在游戏陪练过程中,消费者还可以随时提出新要求。在笔者接待消费者龚先生时,龚先生原本说“不用给我垫分③什么的,咱俩玩得开心就行”,但在游戏过程中,消费者临时改变了对陪练师的要求,“你还是帮我垫垫分吧,不然要掉级了”。杨女士也表示,“有一次本来老板是下单让我陪他玩的,结果玩到一半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一个人就跟他们7个人一起玩,我真的好尴尬,说话吧,很害怕没人回应,不说话吧,又被差评,太难了”。
其次,由于平台的倾向性支持,平台消费者对劳动者的服务评价甚至是一种“主观裁决权”,即带有主观色彩地评价陪练师在游戏内的技术发挥是否高超、服务态度是否良好、互动是否积极等。笔者在某比心大神的评价区,看到了一位消费者的差评“与标价不符,迟到早退素质低下,大家别点,真的好菜,点了都会后悔”,而陪练师对其差评回复道:“下了一小时的单子,陪你打了100分钟,还欠了40分钟,我只让你补半小时的单子,你都要跑单。说什么要我发照片才能补单,我拒绝了你就对我恶语相向,游戏里谈笑风生,打完游戏翻脸不认人,你是真的双面人,我只是一个老实的陪陪,简简单单的接单子,付出自己的劳动,拿到自己应有的报酬,但是你却欺负我。遇到你真是晦气”。
由此可见,消费者的评价并不一定有客观的标准,而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判断。有一些消费者甚至会以评价与投诉为工具,换取更多权力,比如要求“一带多”、发“凉快的照片”等。郑先生提到:“陪玩一般不就一对一,最多老板再叫一个朋友。结果我一个老板,带着三个朋友,然后找你一带四,带不动就给你差评。我说实话,陪玩没有什么人权的,跟畜生差不多了,真的,你老板也不拿你当人的。”林女士也表示:“有时候真的很无奈,我辛辛苦苦陪老板玩几个小时,结果打完人家要求我发凉快的照片给他看看,我一开始遇到这种就很抗拒嘛,就拒绝他,结果他说‘你不怕我差评吗’,真的太苟了,花了几个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就很生气,随便他怎么差评。”
同时,消费者还拥有“退单”和“举报”的权力。“退单”即消费者在下单后退款,一是交易过程中发生意外情况导致订单无法完成,双方协商一致完成退单;二是消费者对陪练师的服务不满意,消费者发起退单。在实际的交易情境中,“退单”成为一些消费者“吃霸王餐”的手段,唐女士提到:“会出现这种恶意退款的,没有办法。申诉的话,比心它不给你通过,你就没有办法。之前我遇到一个老板,跟你打的时候特别好,然后出来之后去平台退单。这种没办法。你又不好去说什么,然后你就问他为什么退单,他就已读不回……我遇到三次这种白嫖情况,没有办法,申诉也没用,平台肯定是向着他们的。”对此,郑先生也深有感触:“比心就完全维护老板的利益,从来不会维护陪玩的利益。我之前遇到老板恶意退款,陪他打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他直接退款了,我这边要申诉客服。因为是老板提供的账号,我上他号跟他双排打的,没截那个战绩图,但是聊天记录都有,老板也承认打了,然后比心这边就直接给他退了150,我一分钱没拿到,白白打一晚上。没招啊,就一分钱拿不着,就打了一宿一分钱拿不着。”此外,消费者还享有“举报”的权力,而且举报类别多样,包括政治、色情、侵权、转单、标价与实际不符、脱离平台交易、侮辱诋毁、广告、使用外挂等。劳动者一旦被消费者举报,经过后台人工核实之后,会受到封号的惩罚。可见,对劳动者而言,举报的后果非常严重。陈先生提到:“我去年一开始接陪玩的时候,老板就说可以转微信,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人家这样说我才知道的,然后就没在平台下单,打算走微信。我那时候陪他打了一天的英雄联盟,一局十几块,至少也得有100多块钱,他就是不付,然后还把我的微信给举报了,然后把我比心也拉黑了,比心封了我半个月……申诉也没有用。”陪练师做出违规、违法的行为固然容易招致举报,然而,一些想要“挑刺”的消费者也会利用平台的倾向性支持,找各种理由举报陪练师。李女士提到:“比心上有好多那种不正常的人,比较难搞的……那些人要求你又要唱歌,又要怎么样的,就是你一达不到他的标准,然后他就会投诉你,然后一投诉的话,像比心查的比较严格,一接到举报的话直接把你封掉了。”可见,在消费者与劳动者出现纠纷时,消费者退单与举报的权力也是强势甚至霸道的,劳动者的申诉与反抗往往是无济于事且“无法改变”的。正如李女士提到的:“有时候也挺不公平的。老板想举报你的话,平台首先就会指向你,不管你怎么申诉,这个结果都是无法改变的。之前有过这样的事情。玩游戏的过程中是游戏维护,停顿了几分钟,其他的时间都是在陪他玩的。但是他那边的话显示是语音中断了,就好像意思就是他下单我没有陪他玩一样,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中间断了几分钟而已。然后他举报我,我给公司平台那边的客服打电话了,那几天一直在沟通,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已经判定过的结果是无法再申诉的,也是无法改变的’”。
因此,消费者可以主观地决定服务评价以及是否退单或举报,而陪练师为了避免消费者做出负面反馈,通常会努力提升服务质量,付出情感劳动,进行情感管理与展演。邓先生表示:“这玩意其实挺受气的,昨天我有一个女老板点我玩,她一个朋友特别不会说话,她说陪玩在外面干不下正经活了,才会来做陪玩。但是我没办法反驳她,就很无奈的地方,没办法纠正老板的错误……有些老板事情很多,比如我声音小了,他听不清楚,他就会埋怨你什么的,就是那种脾气特别不好,而且事还特别多的,会让人特别生气,但是这就是一个伺候人的行业,为了赚钱,你没有办法,就算有不好的情绪,当下也不能爆发出来。”王先生也表示:“就相当于做服务生一样的,还要照顾别人感受。你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要想办法调节,要调节不好的话,尽量还是不要继续接单,带一些情绪玩游戏的话,玩着玩着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可见,为了避免消费者的差评、退单与举报,陪练师不得不进行消极情绪控制以及积极情感展演,以迎合消费者的情感需求(胡鹏辉,余富强,2019;涂永前,熊赟,2019;梅笑,2020)。
由此可见,由于平台提供的实时性和倾向性支持,消费者借助平台的差评机制,得以在劳动博弈中相较劳动者处于更有利甚至是主导地位;而平台劳动者为了避免消费者的主观差评,不得不尽可能满足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劳动者的自我剥削,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就这样,平台与消费者二者“共谋”,不断培育劳动者的服务意识,使得消费者获得更优的服务和更高的满意度,进而更可能成为“回头客”甚至“常客”而不断增加平台“交易”,平台则能够争取更大市场攫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然而,即使劳动者付出优质的服务,也并不能完全避免消费者的退单与举报;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可能不仅拿不到劳动报酬,还会被消费者举报乃至被平台封号。这时候,平台通过消费者评价机制将部分监督权和管理权转移给消费者(刘战伟,李嫒嫒,2021),从而将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了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吴清军,李贞,2018),而平台反而成了双方矛盾纠纷的“仲裁者”(沈锦浩,2021:63)。然而这一“仲裁者”往往实质性地倾向于消费者一方,而劳动者向平台的申诉往往得不到回应,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整体而言,在“平台—消费者—劳动者”的结构中,平台是处于主导性地位的。平台完全掌握规则的制定权(消费者和劳动都被排除在外),并借此建立起“霸道”的审查与惩罚机制,以保障自身合法性并防止利润外流;同时用一套“大神分”核算系统,在有限度地赋能劳动者的同时,更是形成了一套“游戏化”和“差异化”的管理模式,刺激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提升劳动者自我管理的能力,从而实现平台自身的“激发”式控制。而消费者介入对劳动者的劳动控制,实际也是平台方精心的制度设计;在平台与消费者的“共谋”关系中,平台实际是“主谋”。消费者相对劳动者而言看似是占据了相对主导位置,但本质上是充当了平台控制的延伸和代理,因为其评价、举报与退单机制实际是平台规则中的重要一环,是以平台的实时性和倾向性支持为前提的。这也暗示着,“平台—消费者—劳动者”之间实际并不是牢固的“铁三角”关系,而是动态的接合关系,处于不断的解接合与再接合的过程之中,这也给下文进一步讨论劳动者的能动性策略留出了结构性的空间和可能。
五、有限自主:劳动者的能动性策略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多元控制,劳动者并未成为完全受操纵的原子化个体。面对远距离控制的平台与相对弹性的消费者,陪练师们往往能在其劳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与平台和消费者博弈的能动性策略,有限化解平台的审查、封号、抽成与考核,同时避免与消费者产生纠纷,灵活处理其与消费者的关系,构建积极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升自身的游戏和工作体验。
(一)应对平台的审查、封号、抽成与考核
平台在与劳动者的权力博弈中处于支配性地位,而劳动者往往会调动话语、技术和社会资源来自我赋权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Sun & Chen, 2021)。平台会对色情敏感内容进行审查,但是一些陪练师们已经逐渐发展出“暗号”与“行话”,如“凉快的照片”、“带颜色的照片”、“非绿色的服务”等,避免使用敏感关键词从而绕开平台的审查。此外,很多陪练师对比心平台的抽成行为有所不满,通常会希望添加“老板”的微信,使得“老板”后续下单时绕开平台,直接微信支付。贾女士提到:“(平台)尽量能绕就是绕开的,因为客户那边他们充值的话是1:0.7充值的,应该付给我们的钱还要抽20%。目前这块能走微信就走微信。”李女士也表示:“其实很多人会绕开平台接单的。像一般想挣钱的话,会想办法通过让你微信下单之类的。平台要扣30%的,像几个小时的单还可以,有一些一天就下好多个小时,一扣就要扣好几十,那样就不划算了……平台吃了我好多钱。”因此,在实践中,当陪练师与消费者想要私下交易时,为了避免平台的关键词审查,发展出了不同的加微信策略。一是以发语音方式绕过平台关键词监测从而互通微信号,李女士提到:“平台是查不到语音内容的,所以我聊天的时候就喜欢发语音。”二是采用“转移阵地”的方式。因为平台无法介入具体的游戏陪练情境进行审查和监管,一些陪练师会选择在游戏互动中发微信号,在获取消费者联系方式的同时,规避平台的审查和处罚。王先生提到:“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不会整,有被老板举报过。然后去年跟今年我都没有被举报过了,因为很注意这方面,老板一说加微信,我直接问他要游戏ID。我不会发他微信,要在游戏里面讲。”
由此可见,前文我们所提到的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共谋,并不是绝对的“铁杆”关系,消费者与劳动者也可能撇开平台而私下交易达成某种临时的共谋。这不仅挑战了平台与消费者的“共谋”式控制,实际也给原本结构化的“平台—消费者—劳动者”关系留出一定的弹性空间。同时,为了应对平台的封号惩罚,陪练师也发展出了相应的开“小号”应对策略。李女士提到:“陪玩们基本上都有好多个号的。我自己的小号不多,就两三个。本来只有一个的,然后被封掉了,就又找了几个号开始培养。”郑先生表示:“我肯定有小号啊,为啥?因为比心这东西监管得比较严。动不动就封号……封号了你就得用另一个比心号去接单,必须得准备两个小号,这样才能保证每天都接单。”因此,面对平台的“霸道”式控制,“养小号”已经成为众多陪练师的必要策略选择。
此外,一些陪练师在熟悉平台规则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返点”(即在比心平台虚假下单,返还现金,也简称“下返”)策略,使得陪练师能够一边在平台接单以提升其大神分,一边免遭平台的高额抽成,拿到较高比例的劳动报酬。对此,王先生解释道:“我有加一些微信群,群里有固定的收这种比心币的,或者要求刷单的这种人。比如说你接了120块的单子,被平台抽成20%,到手差不多100个币,用100个币兑换成比心币,可以得到112.5个比心币,再拿这112.5个比心币去给别人刷单,他微信直接返给你112.5,这样相当于120块的单子,到手112.5左右,赚到了客单价的差不多94%,还是挺高的。”
同时,为了应对比心平台针对陪练师的精密考核体系,陪练师之间还会形成“联盟”,互相“刷单”、互送好评,从而提升“大神分”与“好评率”,提升账号的质量与权重。这一过程也被陪练师们称为“养号”。对此,陈先生表示:“可以就是说找别人互送单子,就两个互刷,虽然说会亏一点,但是单数上去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去下单。也有的就是自己拿小号去刷单。”唐女士也表示:“号都是花钱养的,偶尔会和别的陪玩一起去刷单,也就是互相刷单。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是花钱找别人给我下单这样子。一个月养号大概也就花一两百块出头。”李女士提到:“我之前有找过别人刷单,就是花钱找别人刷单。一般刷单是连续三天以上才有效果。”王先生表示:“他们很多都是工作室的,也有一些是自己手上有好几个号的,女的一般都是要养很多比心号,她们花一些钱把自己比心号上多刷一些单子和好评,就可以同时聊更多老板,搞很多微信。”
陪练师与消费者之间利用话语和技术等资源,绕过平台“私下交易”,是对平台审查机制的挑战;陪练师之间利用人际和社会资源进行“下返”、“刷单”、“养号”等行为,是对平台抽成机制、大神分机制与评价机制的挑战。短期来看,这些行为是陪练师们在严格的劳动控制之下,充分调动自身资源发展出的实践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个体能动性,也有利于提高陪练师的经济收入。但是从长远来看,有些策略如“虚假下单”、“虚假好评”等又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甚至使得一些服务质量较差但又善于利用各种规则漏洞的陪练师获得更多机会,“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平台与陪练师的长远发展。
(二)处理与消费者的关系:双向选择与“偷奸耍滑”
由于消费者垄断劳动评价权,因此,能否处理好以及如何处理好与消费者的关系,从而在劳动控制下获得更好的工作体验,成为陪练师需要面对的问题。这就要求陪练师尽量预先规避与消费者消极的关系互动,并且积极构建良好的关系互动。与空姐、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不同,陪练师拥有选择消费者的权力,即陪练师可以对消费者设置“准入门槛”,对服务对象做出筛选,规避“苛刻”的消费者;在同时有多个消费者邀约时,陪练师也可以自主决定接待优先级,调节与不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在筛选服务对象方面,唐女士提到:“比心上跟你讲话那种感觉就好像高人一等的那种老板,那是真的蛮离谱的,跟你说话就是用那种命令的语气,这种我就不太会接……这种老板不太正常。”刘先生也表示:“之前有一个小学生来找我询单,说叫他‘爸爸’,他就会下单。我估摸着他是看抖音看多了,抖音上就有这种视频,什么喊‘爸爸’,喊‘老公’就下单,什么缺德玩意儿……别说接单了,我压根儿就没回这个人,跟这种傻子说话浪费生命。”由此可见,陪练师会设置“准入门槛”,即事先评估消费者,以拒绝看起来无法“合作愉快”的“老板”,一方面可以规避与消费者消极的关系互动,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差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陪练师的游戏和工作体验。
自主决定接待优先级方面,陪练师有时会同时接到多个消费者的陪练邀约,当陪练时间冲突无法协调时,陪练师可以自主决定先接待谁,临时拒绝部分邀约。王先生提到:“比如像我先跟新的老板打的时候,老客户他找我了,一般我会陪新老板打完这一把,如果老客户那边还在等我就去那边,然后跟新老板说我这里有事情,没办法继续玩了,下次有空再一起。肯定是以老客户为主,这个东西你不能先来后到,要不然的话,新来的不一定能找你打下一把。但是老客户他会一直找你,所以还是以老客户为主比较好。”笔者在比心平台的陪练过程中,也曾遇到接单冲突,并在自我民族志中记录到:“我先跟一个回头客口头约定好了21:45玩游戏,但是21:25有个客户来问我玩不玩英雄联盟,英雄联盟打一局大多都要20—40分钟,跟老客户的约定会冲突,虽然我很心动,但是还是觉得要守信用,就拒绝了这个客户。等大概21:50的时候,老客户来找我玩,我跟他讲,为了他我拒绝了另一个老板,他夸我‘你这也太好了吧,我迟到自愧不如啊’。哈哈哈,虽然可能失去了认识新的小哥哥的机会,但是老板夸我,我是很开心的,而且信守承诺的体验真的很棒。”因此,这一选择给笔者带来了积极的情感体验,不仅拉近了与老客户的关系,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肯定,获得了良好互动体验,同时对自身信守承诺产生了自我满足感。
此外,少数陪练师可以进行自主的时间安排,在时间不方便的情况下拒绝接单,以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杨女士提到:“如果玩了很久,身体特别累的时候,或者不想说话的时候,老板找我,我就不接单了,然后也会把平台的秒接单给关了。”唐女士提到:“以前刚做陪玩的时候,玩游戏经常会影响到休息,比如我中午想睡觉,或者晚上想早点睡,结果他过来找我通宵。但是现在基本上生物钟很规律,都是到点了就睡,如果老板想让陪他玩晚一点,我就会跟老板说身体不舒服之类的。”可见,一些陪练师能够设立好劳动的时间边界,避免工作对生活的过度侵占,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系,这体现出劳动者具有一定的劳动自主性,能够相对自由地选择服务对象、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梅笑,2020)。
此外,“偷奸耍滑”这一弱者武器也是平台劳动者常常采用的抗争策略(张铮,吴福仲,2019:11)。陪练师们面对工作压力时也会“偷奸耍滑”以获得喘息之机。对此,唐女士提到:“游戏过程中觉得自己打累了就故意输了,比如说打吃鸡就死掉,然后下棋的话就第8这样可以偷偷懒。有时候下棋下到打瞌睡。老板如果感觉不对劲他会问你在干嘛,你就找一个理由搪塞一下就好了。老板跟你说话,你听得见你就回他一句就好了。然后打起来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说话。而且遇到那种老板和朋友一起,根本就不需要你说话,默默偷懒就行。”可见,陪练师在具体劳动情境中可以灵活处理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通过“偷懒”获得相对舒服的劳动体验。
一些陪练师的“偷奸耍滑”手段更为特别,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老板谈恋爱”上,增加灰色收入。王先生解释道:“你以为光打游戏能赚什么钱?像我这种苦命的,就是纯手打挣钱的。她们包装朋友圈跟比心页面是为了什么?基本上就为了跟老板谈恋爱的,因为只有这种谈恋爱你才能来钱来得最快。就是那种我不明说,但是我暗示,特别是女生,男生也有。因为这都有话语的,都有话语教学一样的,怎么去让老板主动接近你,让老板自作多情的觉得你对他有意思啥的,然后给你套近乎,然后你就顺着他说,顺水推舟地去答应,然后那些女的套路,基本上比如像暗示你她要点外卖,喝杯奶茶啥的,然后加微信。一般职业陪玩的女的,低于3万都是低收入,我认识的简直太多了,半年买车的太多了。”此时,陪练师与消费者之间的“感情”成为陪练师情感劳动创收的工具,唐女士提到:“有些老板会发红包。有的会多一些,有的会少一些。一般不会收超过2000块钱。到时候万一跟老板出现了什么很不好的事情,老板找你要钱,没办法你还得退他钱。超过2000块钱是可以告的,可以立案的,所以如果是超过2000块钱以上的东西就会让老板直接往比心号里送礼物……这不是快到520了嘛,我已经有几个520礼物在路上了……是不同的老板送的。”此时,辛勤陪练、多劳多得不再完全是陪练师的信条,更多的是把赚钱寄托在吸引消费者转账、送礼物之上,让消费者为其“感情”买单。同时,她们一边经营着与消费者的“感情”,一边与消费者有着清晰的界线,不愿意与消费者真正产生感情,对此,唐女士解释道:“陪玩大部分都不可能去跟老板产生感情的,这算是行业的共识。如果是老板喜欢我的话,我大部分想法就是可以圈钱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我喜欢老板,第一反应肯定是,他不是可以白嫖了吗?陪他打游戏都不用花钱了。所以不愿意和老板产生太多感情,心里会划清界线,眼里只有钱,没有感情,掉钱眼里面了。”可见,部分陪练师工作时有着明确的心理界限划分生活与工作、亲密关系与工作关系。
同时,在平台的激烈竞争之下,有些陪练师们也会“弄虚作假”,使用游戏外挂等“作弊手段”。对此,贾女士表示:“我以前玩吃鸡点陪玩的时候遇到挂,游戏开挂挺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连续几发子弹,你枪都不带抖一下……就是技术菜,又想带老板赢。”杨先生表示:“绝地求生的陪玩你知道吗?大部分都是挂,你知道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叫什么10个比心11个都是挂……一个个比职业选手都厉害了,真那么厉害的都去打职业了。说白了就是开挂,在老板面前找存在感。”同时,陪练师们也会通过“变声器”、“声卡”等工具,用虚假的声音包装自己,迎合消费者的喜好与需求。对此,李女士表示:“声卡的话会根据你的声音调,女孩子的话就是大家喜欢的什么御姐音、萝莉音之类的,有条件的话买一些好的设备,就根本让人听不出来的那种。”唐女士也表示:“要求试音的老板会比较多,有的老板他可能会想听御姐音或者萝莉音啊或者不同的声音,然后你就根据他的要求,用声卡调就对了。”此外,陪练师们还用虚假的照片、视频等包装手段,吸引和满足消费者。王先生表示:“大部分陪玩都会去把自己包装,用一些网图或者是包装一下,也有些真的,但是很少,比例很低的。”张先生提到:“我头像也不是本人啊,陪玩基本上都会找网图。你去排行榜乍一看,哪个像真人?那些女陪玩的头像,哪能认得清哪个是哪个,感觉长得都一样。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美女呢?基本都是假的。”笔者加入两个“比心下返群”后,也发现群里不仅有虚假照片,还有虚假视频出售,甚至包括各种“颜色套图”。
由此可见,面对相对弹性的消费者,陪练师可以发挥双向选择的机制,预先筛选掉“苛刻”消费者以规避消极的关系互动,并且发展出“偷奸耍滑”甚至“弄虚作假”的策略以提升自我劳动体验、构建良好关系互动。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劳动者还能建立起劳动时间边界、亲密关系边界等,能动地进行“边界斗争”(border struggles)(Mao, 2021: 9)。然而,劳动者“偷奸耍滑”甚至“弄虚作假”的手段,表面上是陪练师依托各种资源发展的个体能动性策略,但其背后的虚假行为,不仅带来类型化、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也扰乱了陪练平台与陪练市场的秩序。
六、结语与讨论
在数字平台和平台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平台劳动也随之兴起和发展,并带来新的劳动生产问题、劳动监管问题和劳动权益问题。本研究的比心陪练APP便依托数字平台提供了新的劳动机会、劳动方式与劳动场景,同时催生出新的劳动控制机制,但也展现出新的劳动反抗空间和可能。一方面,平台接合消费者形成了多元控制机制:首先,平台通过审查和封号对劳动者进行非常“霸道”的控制,让劳动者“有苦没法说”;其次,平台通过建立差异化、游戏化的数字考核系统,对劳动者进行“激发”式的控制,即激发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提升服务质量;最后,平台还通过引入消费者评价、退单与举报机制,实现平台与消费者对劳动者的“共谋”式控制,迫使劳动者付出情绪劳动,使消费者获得更优的服务,平台也得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在与平台和消费者的权力关系不平衡的情况下调动话语、技术与人际资源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Sun & Chen, 2021),发展出一套与平台和消费者博弈的能动性策略:一是通过私下交易、“下返”、“刷单”和“养号”等对平台各种监管机制做出针对性回应;二是通过双向选择、“偷奸耍滑”甚至“弄虚作假”对消费者做出针对性回应。
上述研究发现呈现了平台、消费者和劳动者的三方互动关系,实际指向了“平台—消费者—劳动者”的三元分析框架,这相对传统的“平台—劳动者”、“平台—消费者”二元关系框架都有所突破,因此对当前学界方兴未艾的平台研究和数字劳动研究都有所启发。对平台研究而言,除了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批判算法研究、文化研究等视角(Gillespie, 2010;Plantin et al., 2018;Nieborg & Poell, 2018;Nieborg & Helmond;2019;孙萍,2019;谢富胜等,2019),还需要一个由内而外的视角,深入平台内部进行细致的互动关系研究,并从内部、互动、关系的视角去重新检视和反思现有的平台研究。对于数字劳动研究而言,尽管“控制vs.反抗”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一是需要对“控制”和“反抗”各自内部的复杂性进行更细致的实证考察,比如具体什么样的控制与怎样的反抗;二是需要对貌似截然二元的“控制”和“反抗”寻找更加多元的行动主体,即在理所当然的“平台—劳动者”之外寻找诸如“消费者”等其他重要行动主体;三是同样需要关系视角的研究,特别是多元、动态的关系视角,即在既有丰富的劳动过程研究之外,在平台背景下还要特别关注劳动关系研究特别是多元交织的劳动关系研究。
除了上述理论贡献,本研究希望对现实问题也有所观照。近年来平台劳动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北大博士,送了半年外卖”、“处长体验送外卖”等事件和文章备受关注甚至成为“刷屏”文章,引发社会关于平台劳动的讨论热潮。而在“平台—消费者—劳动者”的多元框架下,平台是占据主导性关键地位的,是解决包括平台劳动权益问题在内的许多现实问题的关键,因此还是要抓住“平台治理”这个关键节点。这时,“国家”作为“平台—消费者—劳动者”背后更关键性、主导性的行动者便浮现出来了,因为国家不仅直接监管平台,也借由平台监管劳动者,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保持距离的治理”(Zhang & Ong, 2008: 3)。但是,在“平台—消费者—劳动者”的既有不平等关系结构之下,国家是否要继续在远处保持距离,甚至是利用平台的“代理作用”而退到更远的距离,还是要积极介入而对数字劳动者有更多的人文关怀?这是未来值得继续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比心陪练APP(简称“比心平台”)是一个游戏陪练数字平台,在比心平台上,经过技能资质认证的游戏玩家(又称“大神”、“陪玩”、“陪陪”)可开通游戏陪练的技能服务,其他玩家(又称“老板”)则可根据自身游戏喜好和需求,在APP上选择“大神”购买游戏陪练类型和时长,之后各自登陆游戏,达成线上一对一的游戏陪练服务。
②《“比心”全职电竞陪练平均月入高达7905元,中国电竞行业积极影响及未来业态预测》,https://xueqiu.com/1796693497/167768129。
③“垫分”:在游戏陪练服务情境中,消费者快要输掉比赛出局时,陪练师在游戏中选择“投降”,即可提前出局,提升消费者排名。
参考文献:
陈龙(2020)。“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10(6),117-139+248。
胡冯彬(2020)。边缘的游弋:中国网络游戏代练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新闻记者》,(7),38-45。
胡鹏辉,余富强(2019)。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38-61+126。
刘战伟,李嫒嫒(2021)。自主与妥协: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新闻记者》,(8),61-72。
梅笑(2020)。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社会杂志》,40(2),111-136。
齐昊,马梦挺,包倩文(2019)。网约车平台与不稳定劳工——基于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调查。《政治经济学评论》,10(03),204-224。
沈锦浩(2021)。互联网技术与网约工抗争的消解——一项关于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的实证研究。《电子政务》,(01),57-65。
宋嘉伟(2020)。“肝动森”:休闲玩工的形成——对《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的数字民族志考察。《新闻记者》,(12),3-19。
孙萍(2019)。“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45(6),50-57。
涂永前,熊赟(2019)。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青年研究》,427(4),5-16+98。
吴清军,李贞(2018)。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社会学研究》,33(4),137-162。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2019)。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2),62-81+200。
姚建华(2020)。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研究——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例。《新闻大学》,(7),17-32+121-122。
张一璇(2021)。劳动空间在延伸——女性网络主播的身份、情感与劳动过程。《社会学评论》,9(5),236-256。
张铮,吴福仲(2019)。数字文化生产者的劳动境遇考察——以网络文学签约写手为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0(3),35-44。
赵璐,刘能(2018)。超视距管理下的“男性责任”劳动——基于O2O技术影响的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研究。《社会学评论》,(4),26-37。
庄家炽(2019)。资本监管与工人劳动自主性——以快递工人劳动过程为例。《社会发展研究》,(2),25-42。
Alacovska, A. (2019). “Keep hoping, keep going”: Towards a hopeful sociology of creative work.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7(5): 1118-1136.
ChenJ. Y. (2018). Thrown under the bus and outrunning it! The logic of Didi and taxi drivers’ labour and activism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New Media & Society20(8): 2691-2711.
ChenJ. Y.& QiuJ. L. (2019). Digital utility: Datafication, regulation, laborand DiDi’s platformization of urban transport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6)1-16.
ConroyE.KowalM.Toth, A. J.& Campbell, M. J. (2021). Boosting: Rank and skill deception in esports. Entertainment Computing36100393.
CunninghamS.CraigD.& Lv, J. (2019). China’s livestreaming industry: Platformspolitics, and preca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2(6): 719-736.
De Peuter, G.& YoungC. J. (2019). Contested formations of digital game labor. Television & New Media20(8): 747-755.
Dyer-Witheford, N.De Peuter, G.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U of Minnesota Press.
Fan, L. (2021). The forming of e-platform-driven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How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changed china’s garment industry supply chains and labour relations. China Perspectives, (1): 29-37.
Gillespie, T. (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12(3): 347-364.
Helmond, A. (2015). The 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 Making Web Data Platform Ready. Social Media + Society1(2): 1-11.
Johnson, M. R.& Woodcock, J. (2019). “It’s like the gold rush”: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professional video game streamers on Twitch. tv.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3): 336-351.
Karatzogianni, A.& Matthews, J. (2020). Platform ideologies: Ideological production in digital intermediation platforms and structural effectivity in the “Sharing Economy”. Television & New Media21(1): 95-114.
Kuehn, K.& Corrigan, T. F. (2013). Hope labor: The role of employment prospects in online social p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1(1): 9-25.
Lee, Y. H.& LinH. (2011). “Gaming is my work”: Identity work in internet-hobbyist game worker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25(3): 451-467.
Liboriussen, B. (2016). Amateur gold farming in China: “Chinese ingenuity” independence, and critique. Games and Culture11(3): 316-331.
LiH. S. (2012). The platform of spoof videos: The case of Tudou. com. Cultural Science5(2): 153-168.
Lin, Z.& Zhao, Y. (2020). Self-enterprising eSports: Meritocracyprecarityand disposability of eSports playe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3(4): 582-599.
Mao, J. (2021). Bordering work and personal life: Using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ur’ to understand ethnic performers’ work in southwest China. China Perspectives, (1): 9-17.
Nieborg, D. B.& HelmondA. (201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acebook’s platformization in the mobile ecosystem: Facebook Messenger as a platform instance. Media Culture & Society41(2): 196-218.
Nieborg, D. B.& PoellT. (2018).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 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 New Media & Society20(11): 4275-4292.
Plantin, J. -C.Lagoze, C.EdwardsP. N.& Sandvig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20(1): 293-310.
Plantin, J. -C.& PunathambekarA. (2019). Digital media infrastructures: pipesplatformsand politics. MediaCulture & Society41(2): 163-174.
Rosenblat, A.& StarkL. (2016). Algorithmic labor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 case study of Uber’s dri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0: 3758-3784.
Sun, P. (2019). Your ordertheir labor: An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s and laboring on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3)308-323.
Sun, P.& Chen, J. Y. (2021). Platform labour and contingent agency in China. China Perspectives, 1(124): 19-27.
Tai, Z.& Hu, F. (2018). Play between love and labor: The practice of gold farming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20(7): 2370-2390.
van DijckJ.PoellT.&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DoornN. (2017). Platform labor: On the gendered and racialized exploitation of low-income service work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6): 898-914.
Zhang, L. & OngA. (2008).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林仲轩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阳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