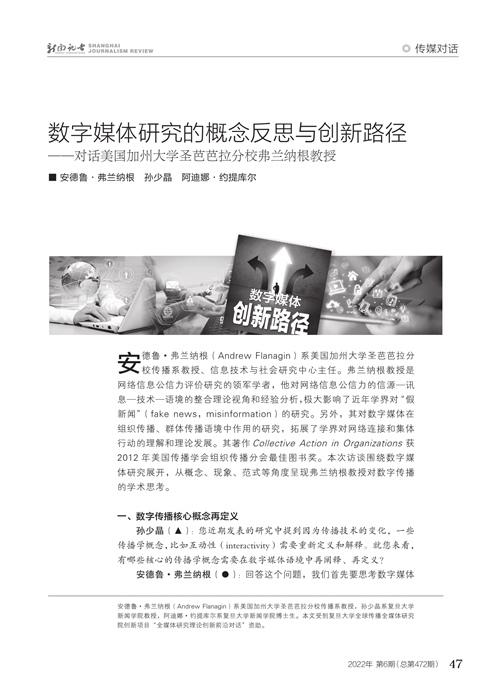数字媒体研究的概念反思与创新路径
——对话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弗兰纳根教授
■安德鲁·弗兰纳根 孙少晶 阿迪娜·约提库尔
安德鲁·弗兰纳根(Andrew Flanagin)系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传播系教授、信息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弗兰纳根教授是网络信息公信力评价研究的领军学者,他对网络信息公信力的信源—讯息—技术—语境的整合理论视角和经验分析,极大影响了近年学界对“假新闻”(fake news, misinformation)的研究。另外,其对数字媒体在组织传播、群体传播语境中作用的研究,拓展了学界对网络连接和集体行动的理解和理论发展。其著作Collective Action in Organizations获2012年美国传播学会组织传播分会最佳图书奖。本次访谈围绕数字媒体研究展开,从概念、现象、范式等角度呈现弗兰纳根教授对数字传播的学术思考。
一、数字传播核心概念再定义
孙少晶(▲):您近期发表的研究中提到因为传播技术的变化,一些传播学概念,比如互动性(interactivity)需要重新定义和解释。就您来看,有哪些核心的传播学概念需要在数字媒体语境中再阐释、再定义?
安德鲁·弗兰纳根(●):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数字媒体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首先,“互动性”(interactivity)正在发生改变,并且涵盖多重意义。使用“互动性”一词时,我们必须明确它的定义。在过去,互动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而现在,互动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也可以被称为互动。所以当我们提及互动性的概念时,一定要考虑到数字媒体的新现实环境。
另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核心概念是“能动性”(agency),也就是“所接收的信息由谁负责”的问题。比如,当人们使用一个工具时,是否完全了解这些工具代理商能够看到什么。我们知道Facebook就是通过用户的数据来产生利益的,但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也并不了解自己的隐私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保护。这种有关自主能动的意识,会影响人们对各类技术工具的使用行为。
“瞬时性”(ephemerality)是我想到的第三个概念。Snapchat(中文一般译为“阅后即焚”)作为瞬时性媒介的代表,能够非常生动地描述信息是怎样在短时间内消逝的。有趣的是,信息的这种瞬时性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在网上发布的内容,可能在其去世几年后都不会消失。对此,欧盟甚至还制定了相关的网络信息法规。另一方面,现在不断涌现出一些专业工具,用于永久删除网络信息,或者永久保存网络信息。所以说,“瞬时性”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概念。
如果结合数字媒体技术的背景来说,“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概念也需要重新审视。Bruce Bimber、Cynthia Stohl和我一起开展了一项针对大型组织成员的研究。我们挑选了美国境内三个集体行动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政治行动组织Move On,这三个组织的风格完全不同,但都非常有影响力。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并没有让组织成员变得更团结。这与以往的研究是相矛盾的,过去的研究通常会强调,只要提供合适的工具,组织成员就会为了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也就是更团结。但我们发现这并不成立,工具无法影响成员的团结程度,但确实会影响他们的参与风格(participatory styles)。这种参与风格包括了组织成员间的沟通形式,也包括了他们追求集体目标的程度。所以,数字媒体产生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它不仅可以丰富组织成员的选择,还能增强他们的能动性。也就是说,数字媒体没有让人们的行动变得相似,而是允许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反思数字媒体的用途、人们的使用行为,以及人们对数字媒体的感知时,需要被重新定义的概念词汇不在少数,同时这些词的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都需要被重新审视。
▲:学界经常用“新媒体”(new media)、“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数字媒体”(digital media)、“生成型媒体”(emerging media)等宏观术语来概括当下的传播环境,但是我发现您经常使用的术语是“在线技术”(online technology)或者“新技术”(new technology),您认为这两种术语的区别在哪里?使用不同术语的意义是什么?
●: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些术语都不够好,它们并没有完全描述我们所讨论的传播环境。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对“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一词提出异议,因为它犯了强调技术的错误,所以我建议用“数字中介”(digitally mediated)或者“数字传播”(digital communication)来代替它。虽然这两个词不完美,但它们更广泛,更通用,也没有强调任何一种技术。
当然我也不会使用“新技术”(new technology)一词,我更倾向于使用“当代技术”(contemporary technologies),因为“新”的定义随时会发生变化。老实说,我在尝试使用较为通用的术语,而不用一种明确的方式来描述现在的传播环境,因为我认为这种明确的方式根本不存在。“数字”(digital)一词比较起来是安全的,它指的是比特和字节、0和1,这正是我们现在得以交流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数字”也不够好,因为它不够具体。所以,我认为每个术语都有自己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足够好的那一个。
二、数字传播的多维融合
▲:您提到因为技术的改变,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正在不断地融合,而将两者分割开来对未来的传播学研究来说没有任何益处(Flanagin, 2017)。我想问的是,技术带来的传播融合除了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层面上发生,在其他传播层面是否也存在融合?这在理论和概念构建上有什么含义?
●:我在读研究生之前做过五年的程序员。程序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职业,只能编写代码,而不能共享代码。即使是同一家公司的员工,他们也不会分享彼此的代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程序员们在非常积极地开放源代码,他们免费分享各种类型的代码,而且代码也在这种共享的过程中变得更有效。所以当我观察这些程序员,会发现他们在组织内外的交流变得没有界限,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之间随意切换。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还是组织传播、群体传播,这中间的界限是多样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我们需要跨越界限来思考“为什么”的问题,是为了让公司获得利益?还是为了让个人获得名声?这让我很着迷,并且我认为这些界限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
由这个现象展开,我和我的同事认为公共物品理论应该增加新的类型,即在线公共物品(online public goods),比如通讯基础设施、数据库、社交网络等。这个类型的公共物品在1990年代开始流行,且与过去研究的物质的公共物品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支持在线公共物品的观点,我们首先证明了互联网的连通性(connectivity)是公共的。连通性是指互联网通过通信技术连结个体的属性,比如电子邮件就是非常典型的连通性表现形式之一。其次,我们认为个体在访问公共数据库时具有相同的权利。可以说,我们从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角度重新构想了公共物品理论。
同时,我们试图进一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主动为这些在线公共物品做出贡献。我们通过对组织网络的研究,提出了“构成性投资”(formative investment)的概念。构成性投资是指在主动构建在线公共物品时付出的努力,比如主动创建维基百科词条,或者主动建立一个信息数据库。按照以往的理论,个体应该鼓励他人建立公共物品而不是自己主动建立,因为这需要消耗太多精力,且对组织者毫无益处。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致力于创建在线公共物品的组织和个人,实际上都获得了相当大的下游利益(downstream benefit)。比如,更受尊敬、更具有号召力、更好的名声等。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在线公共物品的构成性投资从长远来看其实是会带来利益的。
总结来说,技术手段改变了人们做某些事情的可能性和潜力,这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技术只是推动(facilitate)某种行为的发生,而不是决定(dictate)某种行为。技术赋予人们更多的能动性,但并不会让人们做任何原本就不会做的事情。
▲:您认为“大众人际传播”(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是否可以概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现象?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词。我知道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在很多研究中都对其进行过讨论,甚至对大众人际传播做出分类。但我觉得这种直接合并两个名词的做法过于简单,因为这根本无法准确描述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
现象。
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割开来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工具提供了很多功能,打破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核心区别。所以现在,人际传播看起来很像大众传播,而大众传播有时又很像人际传播。比如,两个人在Twitter上交谈,有成千上万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在交谈,此时这种交流不再是人际传播,而是大众传播。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界限正在瓦解,所以没有必要再错误地将他们区隔。
▲:数字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持续可用性和沉浸式使用。当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工具,并且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其他人和其他信息时,对我们自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最近的研究探讨了网络如何改变人们对自身能力的认识,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传播效果。首先,基于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的背景,我们得出结论:很多认知能力都是以信息资源的持续存在为基础的。语义记忆是指对一些思想、概念、事实的回忆,也就是大脑中已经被储存的知识。之后,我们研究了人们如何分辨来自网络的外部信息和来自记忆的内部信息,发现人们通常会认为网络上的信息正是他们已经掌握的信息,并以此来夸大自己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说,认知自尊(cognitive self-esteem)通常会膨胀,让人相信自己比实际更聪明。人们认为自己的记忆力比较强,不是因为真的聪明,而是因为可以上网,拥有一个让人“感觉聪明”的工具。换句话说,网络信息的便利性,让人们在网络信息和个人知识之间划上了等号,并且影响了自我认知。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中随时可用的信息,会让人们低估任务难度且高估自己未来的任务表现,也就是夸大认知能力、增强自己的认知自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其中的机制是怎样的?我们正在做的研究表明,知晓感(feeling of knowing)解释了数字媒体使用和认知自尊之间的关系。知晓感是指对无法回忆起的信息是否真的存在于脑海中的判断。在心理学中,这种“我记得我知道这件事”的感觉,被称为“就在嘴边”(tip of the mouth feeling)。问题是,这真的能解释认知自尊吗?我们发现网络搜索行为能够增强人们的知晓感,并进一步影响认知自尊。举例来说,当人们在网络上搜索信息时,会有一种强烈的“我知道这件事,但我不记得了”的感觉,然后搜索结果会加强这种感觉,并让人们更加确认自己对这件事的了解,同时提高对自身认知能力的自信。
三、数字信息评价与心理感知
▲:在您之前的研究中,信息可信度(credibility)是一个重点。您认为信息可信度,或者媒体公信力,是否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来进行重新定义呢?
●:我认为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信度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有关可信度的研究,最早是聚焦网站,之后才开始聚焦社交媒体等其他信息源,并逐渐划分出经验可信度、来源可信度和信息可信度等类型。
可以说,可信度的研究变得更复杂了,而且我认为情况会变得更糟。我说的更糟,其实也是更有趣,会涌现出更多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来自人工智能的信息可信度?这些信息看似来源于真实,但其实是无中生有。此时,信息来源的问题就变得比较棘手。以往讨论信息来源时,我们能够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识别、理解和回应信源。但是现在,我们甚至会对同一个信息来源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反应。所以我们还能讨论信息来源吗?或许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信息来源在你我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可能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让我想到了Sundar(2008)做的研究,他很细致地探讨了人们对于各类信息来源的感知。其实单独思考一下人工智能现在的定义和相关的复杂现象,我们就该意识到关于可信度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跟信息可信度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模糊性(ambiguity)。比如,在Miriam和我做的可信度研究中,我们不会去探讨信息的准确性,因为可信度与信息本身的准确性没有关系,而与感知有关系。一部分信息接收者会认为这个信息可信,而另一部分接收者会认为不可信,这里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同样,对于“模糊”一词,也不需要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这也取决于接收者的认知,比如他们是否认为某件事物是模糊的?是否了解某件事物的来源和用途?是否清楚算法与人的差异,以及算法的工作原理?所以我们只能从接收者的角度理解“模糊”,考察人们到底在想什么,到底产生了怎样的认知。
同时,我的研究还用了心理学特征(psychological traits)来解释人们的信息评估策略,比如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等。其中一个研究发现,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较高、思维灵活、喜欢思考、对他人观点保持开放态度的这部分人,在评估信息可信度时,更倾向于使用分析式策略(analytical strategy),而不是启发式策略(heuristic strategy)。因为他们更喜欢深思熟虑,所以会使用多个方法来判断信息是否准确,或者是否可信。
▲:我看到您还会做一些有关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的研究,在开展相关研究时,您的研究重心放在哪些问题上?
●:我认为虚假信息的研究重点在于,人们对有害信息(bad information)的反应。Miriam和我最近研究了有害信息的分享动机,探讨人们是否会出于好意来分享这些已被证实的有害信息(Metzger, Flanagin, Mena et al., 2021)。以往的研究认为,分享有害信息是不对的,因为这会延长有害信息的存活时间。但我们发现人们会出于一些好的动机,故意分享这些有害信息。比如人们会用分享信息的方式来教育他人,让其他人也意识到这些有害信息的荒谬之处。
所以在研究有害信息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它的传播情境。人们对这类信息的分享,可能并不是出于信任,而是恰恰相反。在做这类研究时,我们需要探讨更深层次的动机问题。
比如通常认为,人们会在网络上说一些原本不会说的话,会对其他人更刻薄,会产生很多充满恶意的行为。这个观点更像是技术决定论的话术,仿佛是工具让你产生了某种行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于是开始研究这些网络工具,发现网络敌视行为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而网络技术并不是其中的重点。如果我们询问当事人“你为什么要在网络上发表充满敌意的话语”,他们会告诉你,自己的言论并没有充满恶意,并且说“没那么糟糕,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在互相开玩笑”。但是现在的相关研究,并没有把这种“看似恶意,实则友好”的现象考虑在其中。
▲:您最近有关地理空间一致性(geospatial concordance)的研究指出,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想象物理和空间距离。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该视角与媒体研究的结合?
●:这个观点来自于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这是一个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离一个物体的距离越远,对其的想象就会越抽象,而离得越近,想象就会越具体。这个理论是多维度的,我只是选择了其中的空间和地理距离,但是这个理论也提到了时间距离(temporal distance)、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甚至是假设距离(hypothetical distance)。
比如社会距离,它是指个体与某个事物在社会上的距离,该距离的远近会让人们产生对事物或抽象或具体的看法。在社交媒体语境中能够很容易观察到这种社会距离,比如网络亲密度(network closeness)就是社会距离的表现形式之一。两个用户之间的关注和互动,比如谁关注了谁,谁回馈关注了谁,可以视为判断网络亲密程度的标准,当然也可以视为社会距离的测量指标。
时间距离也是一样。阅读网络信息的时间和对网络信息做出回应的时间,是可以被分开考虑的。这些时间差可能会因媒体而异、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还有假设距离,也就是个体对某件事发生概率的想象。我们可以结合社会互动来理解这一类距离:当你在Twitter上关注某个名人并发送私信,你会想象他们阅读私信的情景,这种想象阅读和实际阅读之间的距离就是假设距离。这些距离虽然是心理上的,但从传播的角度看,它们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
四、数字媒体研究的创新路径
▲:结合您的研究经验,您认为数字媒体研究存在哪些误区,或者研究范式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结合过去25年的研究经历,我总结了几条数字媒体研究的注意点。当然你们也可以持不同的态度。第一,研究对象需要强调现象,而不是工具(emphasize the phenomenon not the technology)。在我今天谈到的所有研究中,你可能会注意到,我几乎从未提到某个具体工具,我没有提到Facebook、Snapchat,或者Twitter。当然我研究这些工具,并在我的研究中使用它们的数据,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研究过它们。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说“我研究技术,但我又不研究技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主张研究某种现象,而不是某种具体的工具或者技术。技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们也是短暂的,会不停地改变,不断被取代。所以,与其研究随时会发生变化的某种技术,不如研究这种技术带来的现象。这些现象是超越技术存在的,而其中的技术是新还是旧,这并不重要。
我所说的我们不应该研究Facebook或Twitter,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使用来自Facebook或Twitter的数据,而是我们应该始终关注这些技术带来的现象,也就是对其中的瞬时性、互动性保持关注,因为这才是关键,而Facebook或Twitter可能明天就会改变。在给本科生上课时,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不会告诉你们如何制作网页,或者如何制作电子商务网站,因为你们要记住:技术会不断变化,而如何理解现象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研究过程需要聚焦跨越技术平台的中介作用(focus on mediation across technologies)。在研究数字媒体时,我提倡多关注媒介的中介作用,研究人员应该了解各个技术包含的关键现象是什么。例如,你可以通过Snapchat的数据来研究网络技术中的瞬时性。在这里,Snapchat只是瞬时性的典型代表,并不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对象。再比如,我们随处可见的媒介可供性,很多媒介都能够通过技术为人们提供交互活动,而这其中的重点就是媒介的中介作用。媒介技术的发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心理、行为机制以及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而研究某个具体媒介会使研究主题变得狭隘。因此,我们需要跨平台考察现象,并衡量媒介发挥的中介作用。
第三,研究理论需要关注技术底层的逻辑(the underlying theoretical mechanisms)。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理解时间和空间的运作模式,并从使用、影响、效果的层面解读当前的技术并预测未来的技术。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超越技术的事物都会一直延续下去,而理论正好为这种延续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因为理论是关于人类行为模式的,且与时间无关。反观技术,它只是达成目标的工具。
我还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技术是最有趣又最无趣的东西”。最有趣是因为,技术很迷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很多前所未有的机遇。最无趣是因为,它们只是工具,只是某种心理或行为机制产生的结果。你们可能不会赞同我的看法,但我的研究的确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某种程度上讲,技术的确是更短暂、更不持久,也没有那么重要的。
▲:您强调传播学研究应该重视整体情境,而不是单一技术平台。那么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普及的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情境或者现象是哪些?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讨论中,已经涉及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比如信息来源、互动性、能动性、社会距离等概念都在发生改变。而且我认为AI或者AR等技术环境,都是新近研究的发展方向。那里正发生着很多真正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
对我来说,我们思考的重点应该在于这些瞬时交流片段(meteoric communicative sessions)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它们是否还包含了其他未知的事物?这些交流形式都是崭新的,而且完全是由技术提供的。当然也不能说他们是全新的,没有什么是完全新的,只是现在有了更复杂、更有效、更具有操控性的形式。
我曾研究了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提出的“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概念。这个概念是指技术,包括技术的设计、技术的结构,实际上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所以从“技术代码”的概念逆向思考,如果说社会的价值都已经体现在了技术当中,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审视技术考虑其体现的社会价值究竟是什么,而且这些价值可能会因地而异、因国而异。虽然这是哲学概念,但我意识到用这种思路考察当前的技术变化是很有启发性的。■
参考文献:
FlanaginA. J. (2017). Online social influence and the convergence of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3(4)450-463.
Metzger, M.Flanagin, A.Mena, P.JiangS.& Wilson, C. (2021). From Dark to Light: The Many Shades of Sharing Misinformation Onlin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9(1)134-143.
SundarS. S. (2008). The MAIN model: A heurist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effects on credibility (pp. 73-100). MacArthur Foundation Digital Media and Learning Initiative.
安德鲁·弗兰纳根(Andrew Flanagin)系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传播系教授,孙少晶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阿迪娜·约提库尔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本文受到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创新项目“全媒体研究理论创新前沿对话”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