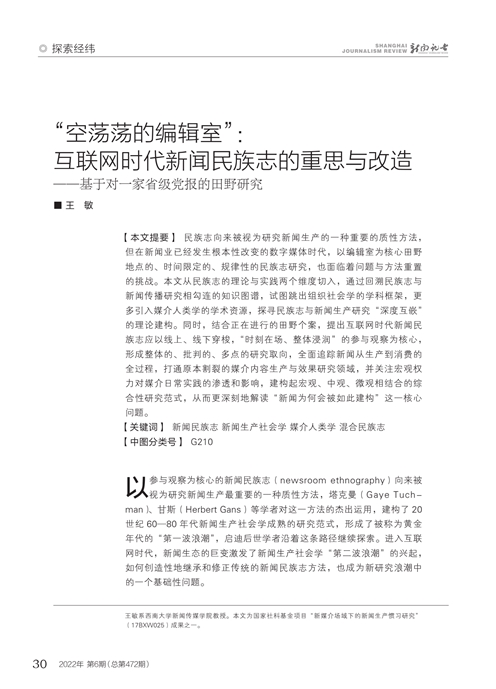“空荡荡的编辑室”:互联网时代新闻民族志的重思与改造
——基于对一家省级党报的田野研究
■王敏
【本文提要】民族志向来被视为研究新闻生产的一种重要的质性方法,但在新闻业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数字媒体时代,以编辑室为核心田野地点的、时间限定的、规律性的民族志研究,也面临着问题与方法重置的挑战。本文从民族志的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切入,通过回溯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研究相勾连的知识图谱,试图跳出组织社会学的学科框架,更多引入媒介人类学的学术资源,探寻民族志与新闻生产研究“深度互嵌”的理论建构。同时,结合正在进行的田野个案,提出互联网时代新闻民族志应以线上、线下穿梭,“时刻在场、整体浸润”的参与观察为核心,形成整体的、批判的、多点的研究取向,全面追踪新闻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打通原本割裂的媒介内容生产与效果研究领域,并关注宏观权力对媒介日常实践的渗透和影响,建构起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范式,从而更深刻地解读“新闻为何会被如此建构”这一核心问题。
【关键词】新闻民族志 新闻生产社会学 媒介人类学 混合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G210
以参与观察为核心的新闻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向来被视为研究新闻生产最重要的一种质性方法,塔克曼(Gaye Tuchman)、甘斯(Herbert Gans)等学者对这一方法的杰出运用,建构了20世纪60—80年代新闻生产社会学成熟的研究范式,形成了被称为黄金年代的“第一波浪潮”,启迪后世学者沿着这条路径继续探索。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生态的巨变激发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第二波浪潮”的兴起,如何创造性地继承和修正传统的新闻民族志方法,也成为新研究浪潮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2021年3月,笔者获准进入一家省级党报(后文简称M报)融媒体中心,计划进行为期一年的民族志考察。在这里,塔克曼眼中记者编辑们展示选题的“黑板”,已经变成了十几米长的中央厨房大屏幕。而以往繁忙、杂乱、充满着接电话、讨论、聊天声音的编辑室,却常常一片静寂、人影寥寥,只能偶尔听到敲击键盘的声音。面对“空荡荡的编辑室”,笔者开始焦虑,塔克曼式的“经典的老派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观察方式”(白红义,2017),是否还能继续适用?或者说,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业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数字媒体时代,我们能否继续使用民族志方法对转型中的新闻业进行研究?
本文一方面结合田野个案,从实践角度思考和回应新闻民族志对于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研究的适用性问题,并尝试对传统的新闻民族志方法进行改造,以应对数字新闻生产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将重新梳理新闻民族志的理论源流,探寻新环境下民族志与新闻生产研究“深度互嵌”的理论建构,为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社会学寻求理论、视域、方法上的突破。
一、理论溯源: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研究的勾连
一般认为,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研究方法肇始于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郭建斌,2003)。作为人类学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民族志也逐渐被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广泛借鉴。民族志和新闻传播学的勾连,或者说民族志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理论旅行,主要走了以下两条路径:
一是新闻生产社会学,以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以新闻室为田野,主要由一批社会学家引领。他们深受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学派职业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将新闻业视为一种现代职业,致力于从组织层面探究媒体机构对于工作的合法性控制以及相关的文化和制度建构。因此,运用民族志方法对新闻生产过程进行实地观察,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在新闻机构里进行长时间的观察,甚至当起记者,然后根据观察所得,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新闻制作过程做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理论意义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新闻内容如何受各种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因素影响”(李立峰,2009:1)。基于此,新闻生产社会学“第一波浪潮”中的学者们得出的主要结论,也与职业社会学研究高度一致。休斯认为,为便于控制和提高效率,组织机构会尽可能将工作任务常规化,这一观念直接影响了塔克曼、甘斯等提出“常规主导新闻生产”的结论,即新闻生产是高度常规化的,有固定的模式可循,按照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分工、合作和流水线生产,从而促使媒介工作者达到组织的预期目标(王敏,2018)。
二是媒介人类学,也称媒体人类学或民族志传播研究,即以民族志方法研究传播实践,以媒介、传播和社会生活互构的情景场域为田野。米哈伊·柯曼(Mihai Coman)提出,“媒介人类学”概念具有双重涵义:首先是指媒介作为工具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其次才是指使用人类学方法(民族志)对媒介在文化中的作用进行考察(Coman, 2005)。张放(2018)认为,柯曼所说的第二重意涵,才意味着人类学民族志与传播研究真正建立起了关联。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有少数人类学者尝试对媒介内容进行人类学分析,而第一个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实地考察媒介生产的奠基性成果,则是美国人类学者霍顿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发表于1950年的《梦工厂好莱坞——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电影制造业》(Hollywood, the Dream Facto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 at the Movie Makers)。鲍德梅克对好莱坞电影工业产业链上的各环节和主体进行了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考察,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所获取的现场资料,对电影生产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系统进行了互动式的考察,提出“生产好莱坞电影的社会系统对电影的内容和意义有着显著影响”这一结论。
有意思的是,尽管媒介人类学的开端从关注媒介生产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系统开始,但“生产”这条线在后来这一学科的发展路径中却逐渐隐没。20世纪70年代,以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电视受众研究为代表,“受众民族志”(audience ethnography)成为媒介人类学中备受瞩目的领域:重视受众,用民族志方法来验证传播学主流范式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如电视涵化效果等。有研究梳理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与民族志“合流”的脉络演进,以四本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成果为依据,可以看出重点关注媒介使用及其影响的媒介人类学,较之媒介生产/制作研究,在我国的学术谱系中仍占据压倒性优势(陈刚,王继周,2017)。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和鲍德梅克对于生产的关注有诸多类似之处,可以纳入媒介人类学范畴,甚至认为在中文传播研究中,最早使用“民族志”方法的就是1990年代中后期潘忠党关于新闻生产的系列研究(郭建斌,2019)。在此种意义上,传播实践的范畴涵盖较广,包含媒介内容的生产、传输和使用等各环节。这启发了一种理论想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上述两条路径是否存在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对话和交流,是否有利于将新闻生产研究放置到更大的学术框架背景中来审视,调用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从而在实践中修正以往使用民族志方法的误区?
二、新闻生产研究使用民族志方法之反思
以往学界对于新闻民族志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民族志难以分析权力运作的缺陷。 “第一波浪潮”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媒介中心主义色彩,聚焦于中、微观的媒介组织和个体生产者层面,无法触及新闻生产背后的权力运作和社会结构(Cottle, 2007)。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民族志方法难以观察到新闻机构内部的高层运作和外部的宏观政治经济维度等影响因素,也即伊达·维利希(Ida Willig)所说的“不可见的结构”(Willig, 2012)。那些真正决定新闻生产的深层影响因素,尤其是宏观的、外部的、隐形的力量,无法通过民族志获取的经验材料挖掘出来。对权力问题视而不见,或无力将之有机整合到研究之中,被认为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经典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新闻生产的早期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权力问题有一定的关注,比如陆晔(2002)运用媒体田野调查资料,从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层面,分析21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尤其重视微观的动态实践,从而理解和揭示实践活动背后权力关系的“深层游戏”逻辑,可以说是在中国语境下反拨了西方新闻生产经典研究中对于“权力”、“控制”等问题的忽视或者执着于专业主义共识的单一解释。后来出现的几项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开拓性成果,比如张志安的《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研究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互动机制,阐释编辑部作为一个新闻场域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勾连,强调强化政经路径,重视媒体背后的权力逻辑(张志安,2006)。但如何以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支撑起权力问题探讨,始终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路径的一个难点。梁君健(2018)认为,越偏向于探讨权力和结构的影响,民族志所能够提供的资料和支撑相对越少。民族志事实上成为“第一波浪潮”学者们的一种论证策略,即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和方式推导出最终结论之后,再以民族志经验材料进行印证。基于此,民族志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结论之间的配合并非天衣无缝。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新闻民族志遭遇到另一重挑战。由于数字新闻生产不再局限于新闻编辑室的实体空间、生产主体也不再局限于专业生产者,新闻生产研究中的“新闻室中心主义”(newsroom-centricity)受到质疑。一些学者提出,随着新闻生产的数字化、移动化,新闻室作为物理生产空间的地位在下降,其作为核心田野地点也需重新考量(白红义,2017)。安德森提出“爆掉新闻室”(blowing up the newsroom),认为新闻室已经失去了以往在新闻生产中的中心地位,许多新闻工作是在传统新闻室外展开,同时,记者也不是形塑新闻室的唯一主体,应当拓展新闻生产研究的视域,聚焦于更广泛的新闻生态系统(Anderson, 2011: 151-160)。梅亨代尔(Mehendale, 2020)研究印度媒体的播客生产,起初采用传统的新闻民族志方法,后来由于新冠疫情爆发,记者们都在家上班,他失去了观察点,但同时也深刻感受到,没有新闻室照样可以进行新闻生产,这使得他重思新闻民族志的方法论。总之,田野的改变引发了新闻民族志作为核心研究方法的危机,即传统以新闻室为核心田野地点的、时间限定的、规律性的参与观察,收获可能极为有限。
基于此,“第二波浪潮”中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传统民族志方法的改造。安吉拉·克里斯蒂(Christin, 2020: 171)在巴黎和纽约的两个网络编辑室进行民族志考察,由于研究对象是成天盯着屏幕的网络记者,她提出传统的民族志方法必须要和其他方法相结合,比如追踪记者发布的Twitter内容及其他社交媒体信息、爬取所研究的媒体内容数据库进行量化内容分析等,并和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的资料相互补充和校正,以获得更为准确、全面、深入的研究资料。凯特琳·佩特(Petre, 2021: 204—205)在2011-2015年间展开了一项关于点击率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的研究,包括进入两家媒体Chartbeat和Gawker进行参与式观察,以及对纽约时报员工的25次访谈。她在田野调查中感受到,由于员工的互动大多在网上进行,因此在编辑室的参与式观察较难有收获,于是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最具突破性的是争取到进入Gawker两个核心网络工作群组的机会,尽管只被允许呆5天时间,但这让她可以全天候观察编辑室的工作流程,尤其是观察用户数据对从业者新闻工作的影响,和线下观察到的材料相互印证。尼基·厄舍(Nikki Asher)将短期田野调查、访谈与多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研究互动新闻。她称自己进行的是“广泛而非深入的观察……尝试在被压缩的时间内去最大化地实现民族志观察”(厄舍,2020:265-266)。不过,对比“第一波浪潮”学者们的研究方式,会发现厄舍的研究与经典的新闻民族志方法实际上已相去甚远。一是田野调查的时间,虽然厄舍没有明确统计,但从书中可以看到,在她所调研的14个编辑室中,停留时间少则半天,最多也不过一两个星期;二是在参与观察和访谈两者间,主要偏向于访谈。这在正统的人类学家眼中并不是在做民族志,更恰当地应该称之为“访谈法”,而实际调查时间则被视为检查田野资料可靠性的重要指标(郭建斌,2017)。
笔者认为,对传统媒体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新闻民族志的反思以及改造的尝试,还存在一个盲点,那就是新闻生产社会学以往主要是在组织社会学的框架下,以社会建构论为理论支撑,将民族志单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操作层面上与新闻传播研究进行机械拼接。这导致“新闻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人类学民族志的精神内核,忽略了民族志内在蕴含的理论关怀、问题意识和批判性,同时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本身的转型和变化也缺少关注。在研究实践中,民族志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人类学所强调的整体论和情景主义,在这样一种工具性的征用中被淡化了。这直接影响到新闻民族志在研究权力和社会结构等深层问题上难以充分发挥。潘忠党(2007)提出,民族志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研究取向。回到上述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相勾连的知识图谱,尽管人类学越来越关注媒介问题,但新闻生产研究和人类学之间始终若即若离,缺少深入的理论对话。如果说新闻生产社会学在互联网时代面临“再出发”的使命,那么摆脱对于组织社会学的单纯依赖,更多地汲取媒介人类学的理论资源,将新闻民族志不仅作为研究方法,更是作为研究取向进行改造,真正实现“嵌入式”观察媒体生产、传播与社会生活的互构关系,探寻新闻生产背后的权力支配体系,建构起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范式,将有望为新闻生产社会学打开一个更为宏阔的研究格局。
三、数字时代的新闻民族志:基于田野的思考
笔者以对M报的民族志考察为例,基于新新闻生态下田野的变化,反思传统的新闻民族志方法应用于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研究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而探索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民族志方法进行改造,使之更好地适应数字新闻生产研究。
(一)田野的拓展:从“新闻室”观察到全过程观察
20世纪70年代新闻生产社会学“第一波浪潮”研究,也被称为“新闻室观察研究”,原因就在于核心田野地点是媒体编辑室。这也是以往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被指责过于“媒介中心主义”的因素之一,即单纯通过参与观察媒介组织及其从业者所获取的田野资料,不足以解释新闻生产。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编辑室作为新闻生产物理空间重要性下降的背景下,有必要拓展传统的参与观察法,将主要限定于新闻室生产行为的实地观察,拓展为线上、线下结合,追踪新闻生产、传播、消费的整个环节,尤其是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相互作用、相互杂糅的状况,探索外在于新闻生产过程的社会因素对内容生产机制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将原本在新闻场域之外的新行动者纳入研究视野。互联网技术为这样一种“追踪”策略提供了便利与可能性,因为媒体产品的阅读量、转发、评论等,很多都实时呈现在网络平台上,而不像以往隐藏在“黑箱”中,不仅研究者,甚至连媒体生产者都不甚了解。
与此相对应,涵盖生产端与发布端的线上田野成为笔者获取资料的重要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端的微信平台,包括微信工作群、微信聊天与微信朋友圈。微信作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交媒体,不仅深度嵌入数字化新闻生产,成为组织日常生产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编辑室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刚进入M报就明显感受到,与“空荡荡的编辑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报社微信工作群异常活跃,讨论选题、审稿、校对、人员调度等各种生产活动都在群里进行。于是,笔者的观察重心很自然转移到线上,通过加入部分微信工作群,全天候观察新闻生产,并结合与从业者的微信聊天以及对从业者微信朋友圈使用的观察,随时记录田野资料。二是发布端的报社各个新媒体平台。目前,M报已拥有自建平台网站、客户端,并入驻微信、微博、抖音、知乎、B站等多个第三方平台,形成较为完整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对一些重点选题,笔者会追踪其在各个平台上的传播情况,包括转发、评论、点赞等,进行多平台信息收集,与生产环节获得的田野资料相互补充和校验。
这样一种对于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观察,汲取了媒介人类学“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研究思维。郭建斌(2014)认为,田野点同时具备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含义,因此“多点”并非单纯指田野观察点的数量增多,而是强调探究共处于一个“体系”中的不同点之间的关系或勾连。“多点”对新闻民族志的启迪,不仅指向空间意义上田野的拓展,更意味着研究问题视域的重构,将单一的“生产”观察与传播、消费相勾连,形成对数字新闻生产更为完整的认知。同时,编辑室实地观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线上田野工作的基础,帮助研究者进入线上田野以及理解线上行动者互动的深层含义。如何穿梭于线上线下,捕捉从业者能动的策略性实践,获取、解读更为复杂多元的田野资料,关注新闻如何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以及上述传播链条如何反作用于媒体生产常规的改变,揭示新闻生产的“深后台”,是线上田野工作对新闻民族志超越方法论意义上的挑战。
(二)“关键事件”与“追踪”策略
关键事件是发生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田野作业者可以用来分析整体文化的事件,具有较强的隐喻性,为审视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关键事件可以是突发的,比如土著部落中的一场火灾,也可以是常规的,比如现代办公室中的表决、电脑分配等(费特曼,2013:106-109)。在数字化新闻生产中,选择某些关键事件,借鉴马库斯所说的“追踪人,追踪事,追踪隐喻,追踪情节、故事或寓言,追踪生活史,追踪冲突”具体策略(郭建斌,2014),追踪观察报道的全过程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联,有助于体察隐藏在日常新闻生产表象下的权力、观念、博弈等,尝试为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和日常新闻实践之间的勾连提供有说服力的经验材料及阐释。
笔者以M报2021年高考报道作为一个关键事件,追踪了报道的生产、传播、消费以及再生产的全过程,并持续关注其对报社生产常规的影响。高考是一个周期性热点,报社对于高考报道已经形成了一套惯例,但2021年一个“高考女孩”的爆款短视频却激起了一场编辑部“地震”。该视频是M报教育条线记者蹲守在一个考点外拍摄的。当第一场语文考试结束后,一个女孩抢先飞奔出考场,气喘吁吁但兴高采烈地说“我好牛,我就想第一个接受采访”。条线记者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视频时长只有20秒左右,谈不上什么拍摄技巧,也没有进行后期剪辑制作,属于比较原生态的目击新闻短视频。视频发到审稿工作群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被当作一个不太重要的花絮新闻发到微博上。在第二天报纸上,也只登了一个小豆腐块式的短评配稿。没想到,这条短视频竟然迅速在网上疯传,当天晚上几大央媒纷纷转载。还没等报社反应过来,视频已经冲上微博热搜。到了第二天下午,编辑部才匆忙整合了一篇微信稿,强调“首发媒体”身份,同时综合了三大央媒转载、多家媒体跟进、网上传播反响巨大等信息,相较于原创视频本身,形成了一定的内容增量,迅速获得2.3万阅读量。微博上该话题阅读量超过2000万,评论上千条。
笔者综合使用了线上线下参与观察、访谈、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对这一关键事件进行动态追踪和研究。一是通过参加编辑部会议、与编辑部成员谈论该报道,以及采集微信群中编辑部成员关于此报道的讨论,获取田野资料;二是汇集报纸和客户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以及其他媒体相关转载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三是对拍摄该视频的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报社管理层在中央厨房会议上专门对这次报道事件进行了反思,用“失败”来形容报社对高考选题的处理,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高考报道的“惯常思维”:一是未能领会从高层到民众“以平常心看待高考”的态度转变;二是对“主流热点”把握不当,不能抓住机会将热点做深做透,获得最好的传播效果。这条短视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效应,甚至形成报社内部的一个新的生产“常规”,在讨论到某些选题、产品思路的时候屡屡被提及,希望能仿效这个视频效果,拍到轻松、有趣、生活化、富有人情味的视频和图片,改变以往主要聚焦于事件、场景、政策等的报道常规。而且,越来越重视从产品传播中挖掘素材,比如网友的精彩评论、调侃等,进行相关话题的再生产。
由一个20秒短视频引发的报道事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观察新媒体环境下省级党报如何整合“宣传逻辑”“、“新闻逻辑”与“流量逻辑”,建构和修正对“主流热点”的理解,实现“混合情感传播模式”(张志安,黄剑超,2019)的转向,其背后来自国家意志和民众心态的驱动因素,以及新媒体多平台运作的架构下,如何在首发与二次传播、原创稿与综合稿之间循环往复、信息叠加,推动热点的传播扩散。笔者认为,这并非一个孤立的个案,还应当置于“新党媒共同体”的场域中,分析省级党报与央媒、其他省级党报之间新的竞合规则,以及由此形成的以资源整合、相互模仿、相互引流、快速抓取热点为特征的“综合稿”生产方式,即在获取独家新闻几乎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多方引用甘斯所说的“同行消息来源”(甘斯,2009:157-158),媒体从相互蹭热点、相互引流中获益。
研究者恰好身处“关键事件”现场这种独一无二的、民族志意义上“到过那里”的经历,不仅有助于采集事件相关资料,更为宝贵的是可以直观感受从业者在此事件中的反应和态度,比如“震惊”、“愤怒”、“急迫”、“懊悔”、“惶恐”等,与从业者形成一定的情感共鸣,真正理解他们的新闻选择。而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必须将所有经验材料置于更大的社会情景和文化结构之中,挖掘影响新闻生产的深层次因素,才能“超越个案”(卢晖临,李雪,2007),尝试完成舒德森提出的将文化的、组织的与文本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任务(黄典林,2018)。
(三)田野资料的突破及问题视域的拓展:以编辑室控制研究为例
与以往主要采集文字、图片资料不同,通过线上田野可以原生态记录包括对话、图片、语音、视频、动图、表情符号、文件等各种资料。因此,资料分析方法也需要多元化。比如,由于工作群中获取最多的资料是对话,而线上对话相比面对面交流,具有不同的传播特性,同时包含隐喻、反语、一语双关等多重意涵。基于此,借鉴常人方法学的谈话分析、“录像分析”方法对自然状态下社会互动的研究思维,以及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考察编辑部成员在不受外界干扰情况下的实时互动与情感连结,可以补充实地参与观察难以获取的一些田野资料,包括媒体管理者顶层控制、记者和管理层之间的日常冲突、对“禁令”的维系与突破、效率与权力约束下记者的能动性等。甘斯(2009:90)所说“(研究者)不能进入编辑或制片人批评下属的场合”的难题,在线上田野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沃伦·布里德(Breed,1955)描述的在传统新闻生产流程中常见的“痛骂和蓝铅笔批示”已绝大部分转移到了线上,尤其是微信工作群当中。微信群中的任何互动行为,所有群成员都可感知、可围观,不管他们与这一互动是否相关。也就是说,批评和表扬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公开可见了。
田野资料的突破进一步影响到问题视域的拓展,有助于延续、丰富、修正以往新闻生产社会学领域的一些经典研究,比如编辑室控制问题。布里德的经典研究《编辑室的社会控制:一项功能主义研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聚焦于“编辑室如何实施和强化控制”,除分析现代职业中比较普泛的控制因素,比如机构权威、强制权力、对上级遵从的义务、向上流动的渴望等之外,更强调编辑室控制是以从业者潜移默化地接受组织价值观的方式来隐性地实施,从而形成一种新闻专业的社区控制力量(Breed,1955)。1970年代新闻生产社会学“第一波浪潮”的学者们也认为从业者会比较一致地遵循新闻“常规”(routines),事实上延续了布里德的研究结论,共同导向罗伯特·默顿(Merton, 1959)所说的“行为遵从”(behavioral conformity )和“观念遵从”(attitudinal conformity)。社会控制在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的形成与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功能主义范式下,从组织层面解析编辑室的控制问题,对从业者一致性与遵从的强调,形成了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研究传统。
笔者观察到,在M报内部,传统组织权力结构中的一些控制性力量在弱化,但新技术条件下编辑室互动的可见性、可记录性与可追溯性特点,使得工作群作为虚拟编辑部,强化了基于互联网特性的新型控制,主要带来了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秒回”文化,二是“保持队形”策略,三是“监控”朋友圈。这三点都不同程度地强化了沃伦(Donald Warren)总结的“可见性”(visibility)这个与权力实施密切相关的特征(Warren, 1968),使得时间管理、地点管理和任务管理以一种更具弹性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削弱了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控制感和自主性,强化了编辑室控制机制。但另一方面,从业者也发展出一套适应微信互动特点的博弈和协商机制,包括适时沉默、延迟回复、微信朋友圈分组等,让自己在不直接对抗编辑室规则的前提下,成为戈夫曼所说的“心存不快、言不由衷,但仍然以友好态度示人”的表演者(戈夫曼,2008:186)。同时,微信群中经常使用的表情符号、玩笑、段子、斗图等,提供了一种强化或者弱化感情色彩、缓解紧张、化解摩擦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编辑室平等、协商的氛围。
笔者认为,引入以微信工作群为主的线上田野资料,有助于在一个更加复杂的在线环境中考察个体互动的微观现实,进而探究其对编辑室控制机制的影响,呈现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张力,揭示出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新闻行业“奖赏性权力”(reward power)的弱化,编辑室控制更多是在互动中实施。这对以往主要基于功能主义范式、从组织层面研究编辑室控制机制的传统,形成了一定的补充和革新。类似地,对把关机制、新闻业“时间性”等经典问题的研究,线上田野都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资料,激发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思考。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引进民族志的意义不仅在于参与观察所获得的“局内人视角”,更在于改变、丰富新闻生产研究的问题结构。
(四)以参与观察为核心的混合民族志(hybrid ethnography)
多种研究方法混合使用,历来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的一个研究传统。被称为新闻生产社会学“第一波浪潮”三大经典的《做新闻》、《什么在决定新闻》和《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只有塔克曼的《做新闻》采用了比较纯粹的新闻室观察的经验材料。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有三分之一篇幅来自对媒体产品的内容分析,而这些分析与新闻室观察的田野资料并无太多直接关联。作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员,吉特林亲身参与了示威等各种组织活动,新左派运动本身就是他个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他在《新左派运动与媒介镜像》一书中,并没有提出自己使用了参与观察法,而是强调“彻底的质化研究”(吉特林,2007:21,229-231)。可见,即便“第一波浪潮”最核心的研究方法是参与观察,但也并不拒绝其他研究方法。一项文献计量研究显示,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大陆传播民族志研究论文中近一半使用了“混合民族志法”,也就是将民族志与问卷调查、文本分析、口述史等方法综合使用。但该研究也警示,在多种研究方法混合使用中,参与观察被弱化了,与人类学民族志原有的研究旨趣和关怀相悖(陈刚,王继周,2017)。它所带来的一个操作层面的表现就是田野时间大大压缩,乃至几乎没有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更多倚重访谈和焦点小组等较“省时高效”的方法。
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研究中,民族志框架下多种研究方法的混合使用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特性,新闻产品内容、传输渠道、传播效果基本可以实时呈现,因此将访谈、新闻产品内容分析、从业者日常会话分析等方法结合进来,观测特定选题制作的全过程、时间线、发布平台与受众使用,对比编辑部内部生产、把关、评价机制与受众反馈数据,有助于打通原本割裂的媒介内容生产与效果研究,更真实地解读“新闻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一核心问题。比如,基于对前述“综合稿”生产的研究兴趣,笔者采集了2021年8月1日至12月31日间M报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共计889篇,重点对其中的140篇综合稿进行内容分析,同时结合新闻民族志考察获得的田野资料,探究综合稿如何成为互联网时代专业媒体一种新的内容生产方式。虽然基础性的研究资料来自产品内容分析,但包含线上与线下的参与观察,对于研究者理解综合稿的生产动因以及实际操作中的能动性策略,仍然是不可取代的研究方法。
郭建斌(2017)认为,“参与”比“观察”更重要,没有参与他者生活的观察并非民族志。在互联网环境下,研究者“参与”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由于新闻生产大量在数字平台上进行,让纯粹“局外人”式的观察变得事实上无效,只有真正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才可能了解其实际运作逻辑,同时也才更有可能获准加入核心工作群,开展线上田野工作。当然,如何参与、参与到何种程度,要视研究者对新闻业务的熟悉程度、能够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媒体机构的意愿而定。同时,线上田野方式也不完全等同于被动式“潜水”,更需要积极的参与。从加入报社融媒体中心的核心工作群开始,笔者一直在揣摩如何在不干扰编辑部日常工作流程的前提下,寻找契机为编辑部提供有价值的资讯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参与工作群互动,转发、评论、点赞新闻产品,以及寻找话题与编辑部成员在社交媒体上单独交流等,以维持在编辑部场域中适度的存在感和持续互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线上田野仍需贯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思维——合作而非掠夺,在互动中生产知识。
四、总结
进入互联网时代,稳定、连续、结构化的媒介生产和消费体系已不复存在,因此“第一波浪潮”时代那种以编辑室为核心田野地点的、时间限定的、规律性的新闻室观察,也面临问题与方法重置的挑战。如果说,“第一波浪潮”学者以精彩的民族志工作,揭示出“新闻是被建构的产物”,“第二波浪潮”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将核心问题转向“新闻为何会被如此建构”这一更深层的追问。事实上,“第二波浪潮”的学者们已经因应数字时代新闻业的根本性变化,试图对传统框架进行改造,避免新闻生产研究的“内卷化”。但相对来说,以往更多是从理论或方法论层面来进行的,对作为新闻生产社会学核心研究方法的新闻民族志探讨并不深入,亦缺少与个案密切结合的实践印证。在操作中,新闻民族志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这直接影响到新闻民族志在研究权力和社会结构等深层问题上难以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从民族志的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切入,试图跳出单一的组织社会学学科框架,更多引入人类学、尤其是媒介人类学的学术资源,从研究视域、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以及具体操作等层面,对新闻民族志进行调整和修正。
从理论维度上,通过回溯20世纪40年代发端的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研究相勾连的知识图谱,可以看到由社会学家开创的新闻生产社会学,与主要由人类学家推进的媒介人类学或民族志传播研究,形成了两条似乎并不交叉的学术路径。尤其在新闻室观察研究崛起的1970年代,以“受众民族志”为代表,媒介人类学开始全面转向接受研究,两条路径更是渐行渐远,缺少深入的理论对话。作为一个深受芝加哥社会学派田野研究传统影响的学者,甘斯就拒绝被贴上人类学家的标签,而是称自己为一个主要使用参与观察方法的社会学家(Gans,1999)。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两条路径出现了重新碰撞和交流的契机,借以充分挖掘人类学的学术资源和方法论视角,寻求民族志与新闻传播学的深度共鸣与融合。
从实践维度上,本文结合正在进行的田野研究,将新闻民族志不仅作为研究方法、更是作为研究取向进行改造,认为面对“空荡荡的编辑室”,互联网时代的新闻民族志应以线上、线下穿梭,“时刻在场、整体浸润”的参与观察为核心,形成整体的、批判的、多点的研究取向。并综合使用访谈、新闻产品内容分析、从业者日常会话分析等方法,动态追踪新闻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打通原本割裂的媒介内容生产与效果研究领域,在此过程中将原本在新闻场域之外的新行动者纳入研究视野。同时,视角落点不能仅仅局限于媒体和生产者的层面,而要延伸到更宏观的、结构性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宏观权力对媒介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展示田野现象和国家力量的联结点,真正实现“嵌入式”地观察媒体生产、传播与社会生活的互构关系,探寻新闻生产背后的权力支配体系,建构起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范式,从而更深刻地解读“新闻为何会被如此建构”这一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7)。在新闻室做田野:作为方法的新闻民族志研究。《现代传播》,(4),61-67。
陈刚,王继周(2017)。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民族志进路的逻辑、问题与重塑。《现代传播》,(7),36-42。
大卫·M.费特曼(2010/2013)。《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郭建斌(2003)。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新闻大学》,(2),42-45。
郭建斌(2014)。“电影大篷车”:关于“多点民族志”的实践与反思。《新闻大学》,(3),45-50。
郭建斌(2017)。雾锁田野:如何在媒体机构内做田野调查——兼对《什么在决定新闻》的方法学梳理。《新闻记者》,(5),61-69。
郭建斌(2019)。民族志传播研究的概念、理论及研究取向——基于中文相关文献的纲要式讨论。《新闻大学》,(9),1-14。
黄典林(2018)。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国际新闻界》,(6),68-87。
梁君健(2018)。秒表可以测出重量吗?——基于民族志方法论的新闻生产社会学再思考。《新闻记者》,(8),62-74。
卢晖临,李雪(2007)。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118-130。
李立峰(2004/2009)。什么在决定新闻: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经典之作。载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陆晔(2002)。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研究。《信息化进程中的传媒教育与传媒研究——第二届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汇编(上册)》,158-166。
尼基·厄舍(2016/2020)。《互动新闻:黑客、数据与代码》(郭恩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欧文·戈夫曼(1959/200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忠党(2007)。作为深描的民族志。载于郭建斌编:《文化适应与传播》(代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托德·吉特林(1980/2007)。《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王敏(2018)。从“常规”到“惯习”:一个研究框架的学术史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9),68-80。
张放(2018)。传播学史视域下媒介研究“民族志转向”之辨及其价值探析。《南京社会科学》,(6),108-117。
张志安(2006)。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4-5。
张志安,黄剑超(2019)。融合环境下的党媒情感传播模式:策略、动因和影响。《新闻与写作》,(3),78-83。
AndersonC. W. (2011). Blowing up the Newsroom: Ethnography in the Age of Distributed Journalism, in DomingoDPaterson, CP (eds. ) Making Online News: Newsroom Ethnography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Internet Journalism. New York, NY: Peter Lang.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326-335.
Christin A. (2020). Metrics at Work: Journalism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 of Algorithm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man, M. (2005). Media anthropology: An overview. Media Anthropology Network Working Paper Series, 17-24. Available at: https://www. easaonline. org/downloads/networks/media/05p. pdf
CottleS. (2007). Ethnography and News Production: New(s)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Sociology Compass1(1)1-16.
GansH. J. (199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the era of “Ethnograp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28(5)540-548.
Mehendale, S. G. (2020). All ears! Tracing journalistic podcasting in India through newsroom ethnography. Media Anthropology, (12). Available at: https://media-anthropology. medium. com/all-ears-tracing-journalistic-podcasting-in-india-through-newsroom-ethnography-560bfa337808
MertonR. (1959). Social conformity, deviation and opportunity-structures: a comment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Dubin and Clowar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177-189.
Petre C. (2021).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Click: How Metrics Are Transforming the Work of Journalist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rrenD. (1968). PowerVisibility and Conformity in Formal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6)951-970.
WilligI. (2012). Newsroom Ethnography in a Field Perspective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14(3)372-387.
王敏系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介场域下的新闻生产惯习研究”(17BXW025)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