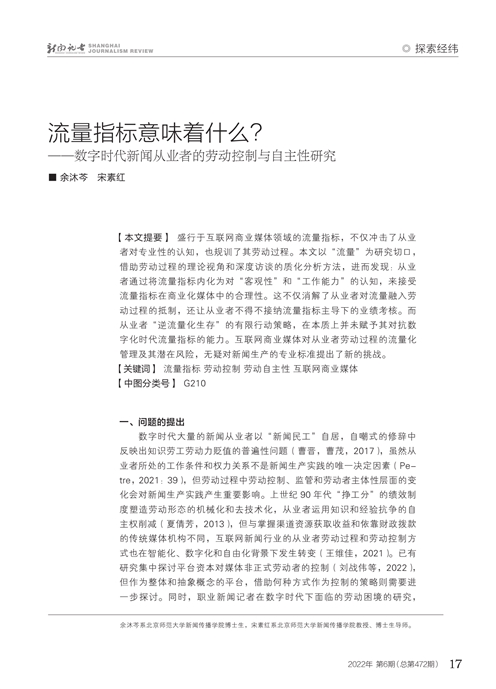流量指标意味着什么?
——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的劳动控制与自主性研究
■余沐芩 宋素红
【本文提要】盛行于互联网商业媒体领域的流量指标,不仅冲击了从业者对专业性的认知,也规训了其劳动过程。本文以“流量”为研究切口,借助劳动过程的理论视角和深度访谈的质化分析方法,进而发现:从业者通过将流量指标内化为对“客观性”和“工作能力”的认知,来接受流量指标在商业化媒体中的合理性。这不仅消解了从业者对流量融入劳动过程的抵制,还让从业者不得不接纳流量指标主导下的业绩考核。而从业者“逆流量化生存”的有限行动策略,在本质上并未赋予其对抗数字化时代流量指标的能力。互联网商业媒体对从业者劳动过程的流量化管理及其潜在风险,无疑对新闻生产的专业标准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流量指标 劳动控制 劳动自主性 互联网商业媒体
【中图分类号】G210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时代大量的新闻从业者以“新闻民工”自居,自嘲式的修辞中反映出知识劳工劳动力贬值的普遍性问题(曹晋,曹茂,2017),虽然从业者所处的工作条件和权力关系不是新闻生产实践的唯一决定因素(Petre, 2021:39),但劳动过程中劳动控制、监管和劳动者主体性层面的变化会对新闻生产实践产生重要影响。上世纪90年代“挣工分”的绩效制度塑造劳动形态的机械化和去技术化,从业者运用知识和经验抗争的自主权削减(夏倩芳,2013),但与掌握渠道资源获取收益和依靠财政拨款的传统媒体机构不同,互联网新闻行业的从业者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方式也在智能化、数字化和自由化背景下发生转变(王维佳,2021)。已有研究集中探讨平台资本对媒体非正式劳动者的控制(刘战伟等,2022),但作为整体和抽象概念的平台,借助何种方式作为控制的策略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职业新闻记者在数字时代下面临的劳动困境的研究,对于理解新闻行业的观念变迁也富有意义。
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当今全球的新闻生产实践,也推动了新闻业朝向“可量化”方向的发展(Zamith, 2018),受众分析数据已经成为当代新闻媒体机构保持竞争力和评价的重要标准(Vu, 2014)。相较于前互联网时代基于个人意愿的读者调查,数字时代对用户行为轨迹的实时追踪,促使“想象与近似”的受众向精确受众转变。随着从业者对用户兴趣与需要更加深刻的把握,受众分析数据被用以追逐更大的流量。“流量至上”的标准对媒体商业模式和价值取向层面的冲击成为学术界探讨和批判的对象,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流量指标对新闻编辑室内部组织结构层面的改变,包括从业者个体如何调整日常劳动过程和角色定位以适应无处不在的数据分析要求(Lamot et al., 2021)。对流量的认识仍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但不可否认流量指标已成为观察数字时代新闻生产劳动变化的重要视角。
本文聚焦于互联网商业媒体的新闻从业者,将流量视作新闻媒体的一种劳动管理策略,沿着劳动过程的理论脉络,探讨流量指标如何被理解并纳入评价标准,从业者劳动过程中受到怎样的控制以及从业者自主性的行动策略。
二、文献综述与关键理论
(一)劳动过程控制研究:平台劳动与新闻劳动
劳动过程研究旨在揭示微观生产情境中的支配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理论的三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208)。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本目标在于生产并隐藏剩余价值。探讨企业内部的技术和控制是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问题,具体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面向:一是以马克思和布雷弗曼为代表,注重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下资本管理控制。布雷弗曼在继承马克思对于劳动过程分析基础上提出“局部工人”和“设计与执行分离”的概念,并指出其结果是劳动者在知识技能垄断下的“去技术化”(布雷弗曼,1978:71-72)。二是以布若威等人为代表关注劳动者主体性及意识形态形塑的微观过程研究。布若威等提出劳动者的驯服与甘愿并非依靠强制力的血汗控制,而是被“赶工游戏”的同意机制制造出来(布若威,迈克尔,2008:89)。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型垄断平台的出现,工业化体系下稳定和长期的雇佣关系的改变带来研究对象的拓展,包括家政工、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媒体实习生和音乐平台的用户等(梁萌,2017;孙萍,2019;陈龙,2020;牛静,赵一菲,2020;翁旭东,姜俣等,2021),对于劳动者的控制研究总结出了“数字控制”、“情感劳动”、“理想游戏”等手段,还有学者认为对于数字零工的创意工作者,劳动过程中的兴趣、玩乐、公平与希望遮蔽了平台剥削与控制的本质(刘战伟等,2021)。综合来看,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在布若威“赶工游戏”理论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但与西方社会中国家力量外生于资本—劳动的框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力量内嵌于劳动过程的控制之中(王星,2012)。数字技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意识形态对劳动者主体意识的控制并非是并行的,以技术之名营造的自由平等的工作氛围本身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效果,互联网新闻从业者劳动过程中的内在逻辑需要进一步探究。
与上述多数处于服务业和非正式工作中的劳动者相比,互联网新闻从业者的劳动性质应该如何界定?隐含精细化和标准化管理过程的数字劳动最初被用于强调信息传播产业对用户的劳动剥削(Fuchs, 2009),后来也纳入传统雇佣关系中的脑力劳动者,如新闻记者。也有学者将新闻从业者划入知识劳工的范畴(吴鼎铭,2015),因为他们能够进行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递,行使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形塑社会的影响力。事实上,互联网新闻从业者兼具数字劳工和知识劳工的双重特性,一方面他们基于新闻业公共性的责任,传播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内容;另一方面新闻生产流程需要遵循一套专业主义的集体性规范实践,这种独特身份使之区别于平台的一般劳动者,既有对于劳动过程控制的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互联网新闻从业者群体。
有学者指出在技术发展之下新闻工作真正成为24小时不间断的劳动(García Avilés et al., 2004),新闻永远处于生产、消费和更新的状态中,记者被迫沦为不知疲倦的“转轮仓鼠”(Starkman, 2019)。弹性时间和空间的结果是工作和生活界限的消融(曹晋,许秀云,2014),人工智能嵌入新闻业让记者和机器之间面临尴尬的劳工分工(白红义,2018)。新闻从业者的劳动强度加大并沦为技术的奴隶,但技术并非是引发新闻业一切变革并对从业者进行全面宰制的直接原因(王行坤,2017),技术如何控制劳动者的生产活动从而产生更精细的剥削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诞生的“流量”成为新技术条件下新闻影响力的表现形式,“流量逻辑”逐渐成为新闻内容生产的主导(陈昶文,2019),10万+铺设了资本世界的游戏规则,也在一定意义上深刻影响了新闻生产的过程(刘涛,2020),需要我们从流量的角度切入对新闻劳动过程的考察。
(二)数据化的受众:从订阅量到流量
流量(Traffic)是在线媒体中受众访问媒体时的总体活动,主要构成要素包括访问量、独立访客、页面浏览和访问时长等(Kim & Desai, 2021)。媒体对受众数据的分析并非新现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新闻机构借助系统的读者调查、发行量等数据来追踪受众人口统计学特征、兴趣偏好和消费习惯(Beam, 1995)。但出于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坚守和编辑自主权的保护,记者并不信赖受众分析的数据并有意对受众反馈边缘化(Gans, 1979)。互联网的发展推动受众数据监测的普遍化,以营利为目的的平台技术公司掌握了海量用户数据资源,媒体依赖平台来获取流量已成为公开的事实。新闻机构超过80%的流量推荐来自Facebook和谷歌,其原因主要是平台开始将自己定位于为用户获取新闻内容的载体,媒体也将平台视为走出经济困境的机会(VanNest, 2016)。媒体对平台流量的依赖会导致占主导地位的平台算法逻辑对新闻媒体产生“同构”影响,进而导致媒体采用平台的优先级和价值观(Caplan & boyd, 2018)。平台化趋势的发展推动“可量化新闻报道”的出现,即转向实时的、个性化和定量化的新闻生产实践(Carlson, 2018),也由此带来对从业者表现的评价和薪酬标准的划分。可以看出,流量指标背后是一种让新闻生产合理化和纪律化的力量,数字在新闻业中形成从业者共享的认知体系。针对流量与新闻生产关系的探讨,现有研究集中在受众分析数据如何作用于新闻生产的价值判断、内容质量、组织结构以及从业者的工作惯例等方面,并围绕流量指标对新闻业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展开争论。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流量驱动策略让记者承担不断加速和无间断的内容生产并处于高压的精神状态中,影响着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的劳动条件(Blanchett Neheli, 2018)。Petre(2021)在其新作中将数据分析工具用作观察复杂新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切口,认为流量工具设计的趣味性和游戏性、指标含义的模糊性制造了从业者的“自愿参与”和沉迷其中,编辑垄断着数据的解释权并形成一种柔性有效的管理策略。但流量指标的含义对于不同新闻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下的媒体来说有所不同(Christin, 2020:20),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内部对于流量指标的应用也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相对而言流量对传统媒体整体影响较小(Meese & Hurcombe, 2021)。在记者和编辑角色不断融合的互联网新闻媒体,流量对从业者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自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基于本土化的经验现象予以回答。
回顾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从马克思以来的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问题,无论是马克思指出劳动者需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以满足制造剩余价值的目的,还是布雷弗曼认为劳动过程的去技术化造成劳动者设计与执行的分离,再到布若威揭示无处不在的劳动控制造成自愿服从,都表明控制在劳动过程中的重要性。劳动过程的控制不仅有权利压制的一面,也有劳动者获得自我认同的一面。既有对平台劳动者的控制研究中,缺乏对于互联网商业媒体从业者劳动过程的独特性和在地性的解释,数字时代下的流量指标不仅影响着新闻内容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从业者的劳动过程。本文借助劳动过程理论,以流量概念作为切口,尝试探讨和解释互联网商业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控制问题,从而拓宽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为数字新闻业的发展提供思考。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从2021年7月到2022年4月对20位互联网新闻从业者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长约1小时,共获得一手访谈资料10万字左右。深度访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阐释空间,能够帮助研究者捕捉到受访者的主观思想、情绪反应和行为背后的隐含意义,同时在受访者的选取上尽量体现典型性与异质性。本研究中的受访者选取自不同领域的媒体,根据粉丝数量、知名度和社会认可度涵盖从影响力较大到一般等不同层次,年龄从22—45岁不等,分别有8位男性和12位女性。考虑到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媒体与流量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和复杂,本文的访谈对象“互联网新闻从业者”是指互联网商业媒体中从事一线采编工作的正式员工。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所有受访者均使用化名。传统媒体时代常常存在着编辑和记者角色的明确区分,但在互联网商业媒体普通记者和编辑角色愈发出现融合的趋势,因此不再单独区分,以下简称为从业者。
四、流量认知:客观性与工作能力的双重面向
面对流量至上引发新闻业负面影响的批评,互联网商业媒体通常不会直接承认重视流量的倾向。目前来看,流量数据分析工具主要来自媒体自行开发和第三方技术支持,收集的数据种类主要分为站内数据和社交媒体平台数据。通常情况下,一家媒体会同时使用几种不同的分析工具并更加关注在平台上的数据表现。然而,流量数字的大小和升降是一回事,数字背后的含义则是另一回事。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商业媒体的从业者来说,流量指标所指代的内容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含义,从业者对流量指标的认知和态度不仅能够反映媒体的立场,还影响其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
(一)客观性的指代
对数字的信赖一方面反应出从业者认为流量指标用以指导新闻报道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折射出他们对受众数据分析具有客观性和理性的价值观。传统媒体时代编辑如何对新闻报道做出判断被认为是一种“黑箱式”的操作,依赖于从业者具有神秘性的内在经验,而流量指标的意义在于能够为管理者提供看似客观的判断依据并免受外界的批评。受访者表示流量指标是内容选题和定位用户的辅助工具,却很少意识到数据反过来对其劳动过程的影响:
流量是可以标准化的东西,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东西在,如果一篇文章的阅读量和互动量很大,我觉得是一个正向反馈,首先精神上得到很大鼓励,其次也会反思是哪一个点踩对了,大家这么感兴趣,如果流量低了,下一次选题的时候就会尽量剔除掉类似的选题。我也更加了解我的用户,比如他们是男是女,在哪个地区,年龄有多大。(受访者,XH)
流量肯定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客观判断的,这没有什么疑问吧,因为你的东西就是给用户看的,用户的态度就代表着对你内容质量的认可度。(受访者,QX)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不太会去考虑流量,但关键在于部门的方向一直在变,之前出了一期XX的专访阅读量很高很成功,领导觉得这个话题可做,但后来发现再也写不出那样的爆款了,很迷茫。(受访者,JY)
流量数字背后细分的用户群体指向的是商业价值,而非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客观性的话语模糊了商业媒体追求营利的目的,从业者在流量的指挥棒下调整下一篇选题的方向,从新闻价值的仲裁者简化成为用户喜好的数字代言人,领导层根据流量的高低决定媒体目标定位。但以流量数字的上升作为内容成功的信号,并不能保证下一个10万+的可复制性,“受众可能会从娱乐事件中获得对政治价值的反思,但指标可能无法衡量出这种跨领域的影响”(Wang, 2017),看似客观的判断标准事实上隐藏着深刻的不确定性:
有时候你的选题可能要采访5个人10个人,你花了1周才写完,而他写了一个没有营养的话题只花了1个小时,最后发现你的点击量只有3万,他的点击量有8万,搁谁都会觉得不舒服和可惜吧。(受访者,YB)
在市场竞争和生存的压力下,流量指标背后的算法和受众在把关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指标的客观性成为互联网商业媒体内部的文化氛围和评价标准,从业者的情绪随之起伏摇摆,但他们很难意识到所谓客观性的流量指标对自我的规训和控制,反而加深了对自己表现不佳的苛责。
(二)工作能力的象征
获得高流量的意义不仅在于潜在的商业价值,对于部分从业者来说也被认为是工作能力体现的衡量标准。“稿件的分数会根据阅读量、互动量浮动,这些评价都是交给用户的,你拿不到好的分数证明你写的不好或者说稿件出了什么问题”(受访者,FX)。将工作能力的评价交给流量指标暗含着从业者对工作产生的认同并不倚赖与工作本身的关系(埃伦·拉佩尔·谢尔,2021:82),而是交给商业媒体机构,但依靠机构创造从业者对于工作能力认定的满足感,也意味着个体对于劳动过程掌控的失败:
选题会上很少直接说流量这个词,但在复盘会上哪篇文章表现很好,主编或者领导就会说谁这天数据特别好,然后把数据说出来,再让负责采写和编辑这篇稿子的人讲讲经验,下一次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流量高和流量低的稿子都会点评一下。(受访者,QX)
韦伯指出,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将价值和意义的非理性来源合法化,与每一项科学化目标的达成相伴随的是“超越”,这种过程永无止境(马克斯·韦伯,2004:166)。过去衡量新闻报道是否优秀的标准包含更多内在价值,而从业者默认了流量与工作能力挂钩所带来的即是韦伯所描述的对下一个更高流量目标无休止的追随,也塑造了他们工作中对于加班文化妥协或顺从的习惯:
媒体这个行业没有人不加班吧,有时候你熬夜到凌晨两点跟自己较劲,想着怎么去组织材料,怎么去遣词造句,才能把它写好,这时候你会觉得这也是个人的成长,不完全只是加班吧,月末再拿到好稿奖的那一刻会感到很值得。(受访者,DL)
从业者心甘情愿献身于高强度的劳动本身并无对错,“感到值得”的“好稿奖”主要由主编或部门领导评定,但“参考的首要指标就是阅读量”(受访者,JY)。流量指标成为商业媒体中一种新的工作伦理,赋予日复一日争分夺秒的劳动过程以价值和意义。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权力斗争(齐格蒙特·鲍曼,2021:16),但对于从业者来说“提高与流量交手的能力”是一场自愿的“蒙召”(埃伦·拉佩尔·谢尔,2021:96),他们并非陷入流量追逐的游戏中获得乐趣,而是将对事业的热爱和成长的期许无意识地嵌入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过程中。尽管蒙召者并没有领取更高的薪水,但面临更大的挑战。在“流量等同于工作能力”的话语之下建构起一套以劳动者个人能力为中心的市场理念,从业者面临劳动条件的苛刻和环境的恶化也仅仅是因为工作能力达不到市场需求,遮蔽了本该受到公正对待的劳动权利。
无论是“客观性”的标尺还是“工作能力”的象征,从业者对流量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流量标准进入商业媒体建立合理化的过程,但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商业媒体如何制造出从实践导向到管理方式的一套流量化标准使从业者主动或被动陷入自我循环的境地之中,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五、流量何用:劳动过程中的隐性与透明控制
与布若威关注工厂物理空间劳动不同,数字时代商业媒体对从业者的劳动控制既体现在隐性的行业意识形态制造上,促使流量追求形成自由合理的文化氛围,也体现在透明规则制度的订立上,划定工作的标准和职责,二者共同作用加深流量指标对从业者劳动过程的管理。
(一)隐性规训:内容生产中的价值遮蔽
布尔迪厄区分了艺术和文化领域的两种逻辑,一种是基于同行认可和专业声望的自主逻辑,另一种是基于市场成功和外在标准的异质逻辑(Zuckerman, 2003)。然而,事实上流量指标被制造成专业性认可和商业性成功兼具的混合逻辑,隐蔽地主导了从业者内容生产的过程,减轻他们对内容价值产生的反思与怀疑。
1.选题自主:流量目标契合下的悖论
互联网商业媒体常以“探索内容的边界”、“自由独立的创作”等理念吸引从业者的加入,在无形中将商业利益的实现置换成从业者对于新闻业的情怀梦想、自由书写时代的愿望。与国外许多新闻编辑室中处处充满色彩鲜艳实时滚动着流量数字的电子屏幕不同,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工作的场所中并没有类似的屏幕,他们不会刻意查看流量,更在乎做好本职工作,但流量指标编织在从业者寻找选题、制作标题和如何推送的每一个环节中:
流量和内容质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我们是做内容的,如果一个写稿的人天天想着流量的问题,那肯定是写不好稿子的,在我们这受流量影响比较大的是做运营的同事。(受访者,XH)
流量的压力更多是对于整个团队的压力吧,主编需要对数据负责,而不是某一个人。(受访者,QY)
从业者试图表明流量对内容的影响很小,但在商业媒体中采编与运营之间的“墙”并非密不透风,运营和内容生产虽然是两班人马,但稿件数据的好坏却是公开的。受访者DL表示:“我们会跟运营有一些合作,比如他们会告诉我们现在主要在推哪个方面的话题。”尽管数据表现的压力看似是由整个团队共同承担,但负责内容生产的从业者仍需在流量指标的导向下把握和调整选题方向。相对于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更加严格的规定,商业媒体为从业者提供自主独立写作的空间,赋予他们对劳动过程的相对控制权,但“自主”的前提是与商业媒体流量目标的契合:
平时会看看微博、小红书还有其他些平台的热搜榜来寻找选题,大家都这样做,比较节省时间。(受访者,YB)
努力与流量划清界限的同时,从业者也呈现出一种自主性悖论。在热搜榜上寻找新闻话题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常规操作,但热搜榜背后是用户的点击量和关注度:一方面从业者希望能够免于外部因素的压力自由写作,另一方面又依靠数据指标帮助他们判断什么样的新闻值得做,结果反而加深了流量指标对从业者寻找选题的控制。
2.观点自洽:标榜原创深度的欺骗
数字传播时代免费模式和补贴模式带来的盈利方式逐渐式微,互联网商业媒体更加强调做好优质内容。商业媒体将对流量的追求代替为原创深度观点的生产,给从业者的创意性劳动涂上虚幻的美学色彩,所谓的原创深度观点更多体现为新闻价值和流量思维的巧妙融合。正如文森特·莫斯可认为这一类高端优雅和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和精英阶层特有的标志(文森特·莫斯可,2014:207-212)。从业者在商业媒体的渲染之下,倾向于劳动带来“内在满足”的愉悦体验,转向对于隐含着流量意识形态的写作规则认同:
那种很Low很营销风格的内容我们是看不上的,主编常常跟我们说,要有观点输出和立场表达,其实就是能够更好地调动情绪,如果你整篇文章只是这个事件的叙述总结,大家看了肯定也不想转发,点进去也没什么感受,你必须要能给到你的粉丝刺激,比如说成功引战,让他们留言点赞,也可以提高数据。(受访者,FQ)
开会的时候领导会和我们强调不要做流量王国的奴隶,不要用八卦小报的方式追求流量,更期待和被认同的是你能创造出经典的流行热词,带领一个热点话题。(受访者,QX)
互联网商业媒体并不会赤裸裸地用流量数据告诉从业者应当生产什么样的内容,而是将流量的追求隐藏在鼓吹内容的“实验性”和“先驱性”的修辞中。从业者告别低俗博眼球的内容风格转向更具原创性的观点输出,但观点中常常包含制造对立和引领话题的策略性商业诉求,“在传播中获得流量”和“以流量为目的”的矛盾被无形中规避。不追求流量的标榜实则是为了拓宽受众面,以长期收割更大的流量。商业媒体促使从业者更多凸显观点的自洽而非内容的客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流量逻辑对其劳动过程的管理。
3.形式中立:劳动商品化思维的隐藏
商业媒体通过对文章标题、配图等形式上的包装以期获得更大流量的做法并不新鲜,大多数从业者将新闻内容和形式分开对待,认为“好的产品就需要好的推广”,为了提升流量而对新闻内容进行包装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业共识,推动从业者将新闻的商品化转向视作理所当然:
你们看到的只是一篇新闻报道,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个环节都像是产品生产一样,标题、配图和引入的话都十分关键,做好这些都能很好地扩大新闻价值。就好比你去超市买菜,包装漂亮的肯定愿意买的人就多。(受访者,JD)
从业者把对点击量的优化过渡到对新闻价值的加强无疑是一种概念偷换。新闻价值重点强调的是事实的内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受众普遍关注的性质。德里达提出“置疑”的概念进一步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理解给出参考,即不是急着透过辩证确定问题的边界,而是持续思考并暂时搁置(Hansen, 2012:678-694),记者不断与读者协商,保持提问的状态,寻找与公众最相关的话题。点击量大的新闻未必是好或重要的新闻,流量数据也只能勾勒出热度趋势的轮廓,事件之间被忽略的联结、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则依靠从业者具体漫长的实践,而非商品化思维下的“一锤子买卖”。
之前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比较平淡,领导觉得打开率不好,后来就改成《她又丑又作,凭什么?》,时间长了你也能感觉到它(所在媒体)并不是真正为女性说话,只是为了媚粉。(受访者,FQ)
新闻形式和传播的选择并不是中立的,历史上文章的排版、布局和格式都塑造着公众的参与(Petre, 2021:128)。打造新闻内容被认为与社会责任和公众利益有更紧密的关联,而内容的推送形式仅仅是提高传播力的载体,从业者的专业主义判断并不会因此受到侵扰(Hanusch, 2017)。但事实上一种新闻的呈现风格成为行业的标准,其内在规范性的价值和假设也会被视作理所当然。提升内容的传播力是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应变之道,但互联网商业媒体为获取流量让新闻内容变得轻松、有趣的包装手段,可能会掩盖真正严肃尖锐的社会问题,而从业者恰恰不能丧失的是如何处理和平衡此种有争议问题的反思。
(二)透明控制:日常管理中的规则订立
商业媒体通过话语的裁剪和氛围的营造让从业者建立起选题自主、内容独创和形式中立的认同,消解了对流量融入劳动过程中的反抗,这一过程体现出互联网商业媒体制造出“流量同意”进入劳动过程中的隐蔽性,从业者在自愿与无意识中接受作为意识形态的流量指标管理。除此之外,与之并存的是内部调节机制的构建,如通过绩效机制、晋升淘汰机制和弹性工作机制等实现,在透明的标准之下实现对从业者的劳动控制。
1.浮动的天花板:绩效考核的去标准化和不确定性
互联网商业媒体采用基于流量指标的绩效考核制度具有去标准化和不确定性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时期,媒体按照见报量考核采编人员,写稿篇数和长度决定报酬的考核和分配方式,造成记者为“挣工分”而拼命赶工。计流量考核的制度,则基于阅读量、点赞量和转发量等标准来衡量,看似透明公正的运作方式背后实则是商业媒体对于数据考核标准的操纵,从业者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下接受个人劳动的定价:
现在基本按照稿件字数多少给钱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或者说写完几篇稿子只是你这个月要达到的基本工作量,但你要想在基本工资以外拿钱,就要看流量,5万+以上是有效稿件,才会给你稿费,所以经常写废稿。(受访者,HW)
作为评价从业者劳动质量的重要尺度,看似客观的流量指标,通过商业媒体订立的“有效稿件”的标准而去标准化。5万+流量以下的劳动被定义为无效劳动,因此从业者需要付出比传统计件制考核更多的额外劳动。以流量指标作为薪酬管理的标准,表面上看是将权力完全交给用户,用户与从业者建立直接的联系,但谁在解释和定义标准的问题无法回避,隐身幕后的商业媒体依旧在借流量之手实施劳动控制:
每篇稿子都会有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是根据你拿到的流量浮动的,无论你一个月写多少稿子,只要你超过了2000阅读量,OK,你就安全了。(受访者,FQ)
不断变动的绩效标准成为“浮动的天花板”。依据商业媒体的薪资规定,稿件分数越高能拿到的奖励就越高,但与稿分同时作为考评标准的还有从业者的等级,即同样一篇稿件分数会因为从业者等级的高低而获得差异较大的待遇,从业者等级考核的标准会因其业务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怎么样评判业务能力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布雷弗曼认为工厂的“去技术化”通过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剥夺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掌握(郑广怀等,2015),从业者虽然能够在工作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上享有一定的自由,但在对劳动成果的定位上仍处于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如同受访者lA所说:“你和所有人一起努力,并不意味着你能挣得更多,你要和同你一样优秀的人比较才行。”劳动付出与薪酬之间的关系掌握在商业媒体手中。
2.数字科层制:淘汰的忧虑与进取的自我
在互联网商业媒体中,绩效考核与晋升淘汰的紧密挂钩是管理者用以激励和控制从业者的重要手段。部分受访者提到末位淘汰的压力促使他们在工作中更加进取努力,而淘汰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流量指标。不想掉队的唯一选择就是拼命工作,由于关系到去留问题,从业者即使感到被剥削也不得不默默承受:
我们两个月会看一下你任务完成的情况,主要是看你稿件的阅读量是不是在三端都超过头部,如果你低于公司划的及格线,你就会进入一个复活计划,上面会给你两个月时间进行补救,如果还是没有达到,就会被淘汰。而且对于不同记者来说也不一样,普通记者达到及格分可以拿到所有工资,对于等级高一些的人,就只能拿到70%,但如果你超过很多,能拿到很高的奖励。(受访者,NX)
遭到降薪或者解聘的从业者通常会转向对自身的检视,面临“无法给公司带来盈利”的焦虑和对劳动价值无法自证的怀疑中。以流量指标为参考的淘汰机制除了让从业者陷入随时被解聘的风险之中,还在潜移默化中将劳动商品化的观念输送给从业者,即让他们认为劳动力必须转换为利润才有价值,失败的劳动者则没有资格主张其劳动权益:
每次开会领导就会跟我们说这里的晋升渠道是非常完善的,如果你总是能写出爆款,可以先转正,再去当主管,然后是副主编、主编,比如会给你开放接商务稿件的权利,稿酬也会不一样,也让你去参加一些内部培训授课,但你本身的任务也不能落下。(受访者,HW)
流量数据搭建起从业者阶梯式的进步期许。象征着公平透明的流量数据并没有推动互联网商业媒体扁平化架构的完善,反而作为垄断性的生产要素加强了内部垂直化的科层控制逻辑,形成新的“数字科层制”。传统科层组织中权力来自于管理者制订的规则,而在数字时代流量数据也参与到从业者晋升体系的构建中,不同级别的从业者根据流量评估获得更多的奖金或更多的学习机会。
3.模糊的控制:弹性工作制下的常态规范
互联网技术盛行下的弹性工作制本质是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梁萌,2019)。如果说绩效指标和晋升淘汰规则是在从业者劳动过程中确立规范,那么弹性工作制下相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里则体现的是常态规范的控制。福柯认为就生命权力而言,人们不再寻求一个最优模式,而是对常态的不同曲线进行测定,规范化的操作将调整这些常态的不同分布,使最不利的转变为最有利的(福柯,2018:78-79)。规范意味着最有利的常态,常态规范没有确定的内涵,通过调整排除的手段指向良好的运行,规范对象超越个体的身体变成不断流动状态下的群体(郑广怀,范一杰,2021)。从业者无需坐班,在工作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灵活性和自主性,具体的行为和动作不再被监控,但“弹性”却作为一种模糊可变的概念,在商业媒体整体性目标上不断调整,从业者无法具体确定完成任务的基本边界,不得不投入大量额外的精力和时间:
虽然一般都是快中午才开工,但我其实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得起来,因为新一天的热点出来了,一边吃早餐一边刷热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赶快综一篇放到头条,晚上10点多是流量的高峰,所以你看现在11点了我还在写稿。(受访者,YZ)
领导不会直接跟你说加班,我们提倡的是自主、尽责、高产,但开会的时候里我们也一直在刷手机,盯着看有哪些热点不能漏,万一你错过了,即使你在开会,你也推脱不了,领导追责下来他才不会管你在讨论业务还是在干嘛。(受访者,XQ)
常态规范来自从业者本身的参与,他们在不断无休止的加班和追热点中构建着“弹性”的概念。“尽责”的潜台词意味着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就是不负责任,在“赶工游戏”中不配合的人将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并受到资本的矫正,但在常态规范下不能适应“追热点”的人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将被淘汰出局,也因此在不断招募和不断解雇下的“零工记者”正在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重要特征。
六、“逆流量化生存”:有限自主性的行动策略
从业者主动拥抱或被动接受流量作为劳动过程管理的重要标准,呈现出隐形条件附加的内容写作、加速的工作节奏和不固定的工作时间,巨大身心压力之下的从业者也并非完全被动,他们通过自我的主体实践,呈现出不同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一定程度上是从业者对流量化管理的对抗,但本质上并未赋予他们对抗流量时代的能力。
(一)自我认同:夹缝中的艰难争取
对于刚入行的从业者而言,他们一面希望能在工作中获得经验积累和能力增长,另一方面情感上尽管对以流量指标作为工作完成重要的衡量标准并不认同,但为了适应整体的节奏步伐,构筑起职业的护城河,选择迂回式的主张和寻求心理认可:
我们确实有商业化的追求,但不会完全就是流量怎么大怎么好,会有一个拉扯在里面。比如定稿之前一般会有三个阶段:出方向、出大纲、出稿。我们会在前两个方向上尽量多争取内容上的要求,比如客户非让我们写“躺平”这个话题,我们不想写怎么办?首先就会给对方提供底线标准,表示用一个网络热词撑起一篇文章不行,必须要有好的切口和转折。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商讨。(受访者,QX)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有很大的流量焦虑,后来渐渐的就麻木了,因为有时候一篇稿子本身没多少价值,深度上也不够,但它就是突然爆了,甚至作者自己都感到很意外。所以后来大家心态都放平了,觉得只要同行认可就行,互相吐槽或者戏谑地安慰对方没准下次就轮到你中奖了。(受访者,JY)
在与客户博弈的过程中,从业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把握稿件的方向,融入自我的表达和关切,从而在日常流量数据逻辑以外获得一定的心理成就感和自主操作的空间。而从业者相似处境和工作经历带来的不满情绪,能够激发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瓦解冰冷的流量权威。在共识形成和情绪宣泄的集体认同下,从业者逐渐形成对自我工作的认可,得以减轻“追流量”带来的心理压力。
(二)达成共谋:逃避流量压力的技巧
互联网商业媒体中采编和运营的岗位并不是截然分开,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一人会身兼采访、编辑和运营数职,在紧迫产出的数字压力之下从业者不会对此产生抵抗和冲突,而是常常采取“数据维护”行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共谋:
比如这次的目标是需要我们团队在微信公众号上达到100万的阅读量,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投几个真能给到你30万阅读量的号,而且又有一定声誉,比如新华社、央视新闻这类。你花了一大半的钱获得了比较真实的数据,剩下的钱就可以投给一些注水账号,买到你需要的流量,其实就是造假,如果没人讲领导也就大概看一眼。(受访者,TS)
我的前同事离职的原因是刷流量被另外一个同事举报了。我们是阅读量5万奖励600块钱,他把自己那些4.7—4.8万的稿子买到5万,可能花了100块,就可以挣差价,没想到做月报的时候被发现了。(受访者,YD)
从业者将工具理性的内涵注入日常的工作实践中,在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中满足目标的要求和职场的期待,利用规则的漏洞,策略性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数据维护”行为实际指的是从业者为达到一定的流量指标进行的集体或个人数据造假。团队基于集体共同利益达成非正式的结盟,以实现对流量数据压力的逃避,但这种关系又是脆弱和不稳定的,当有人选择追求自己的利益会引发从业者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使合作关系面临解散,导致原子化的从业者无法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协同实践。
(三)跳槽或转行:职业选择的自我调适
当基于媒体机构的流量追求导致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不断遭到损害,数据指标成为新闻影响力的重要判断标准,无形中影响着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和未来职业规划,一些从业者表示“不想再为10万+打工”,主动选择跳槽或转行,以寻求新的工作环境:
我可能还是会去非虚构,比如像谷雨、湃客,这是比较符合我的调性的,在这里每天写的东西感觉特别无聊。(受访者,JY)
转向非虚构写作成为从业者跳出流量枷锁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对新闻特稿理想的一种方式,体现了从业者自主性的发挥。在他们看来,非虚构写作意味着能够书写活生生的人并挖掘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意涵,这种写作需要长时间与所观察的对象接触、熟悉和联结,是“逐流量而生”的热点文章所无法实现的。然而,加入非虚构阵营的从业者也面临着记者身份剥离与作家身份排斥的身份认同困境(刘蒙之,刘战伟,2021)。此外,非虚构写作平台也逐渐纳入商业媒体的传播逻辑,热点选题与受众偏向的衡量依然在影响着内容写作,身处这一行业的从业者自主性发挥十分有限。因此,面对不断被挤压的个人发展空间和时间,离开媒体行业寻求“稳定”成为从业者的另一种选择:
可能会出国读个博也可能会考公务员,总之以后考虑成家了就不会在媒体了,想稳定和想挣钱都没法一直当记者,只能是积累经验。(受访者,LA)
轻薄短小的内容生产让新闻工作逐渐沦为套路化、机械化的简单操作,也印证了布雷弗曼提出的“劳动者均质化”效应(夏倩芳,李婧,2017),随着从业者达到一定年龄需要在家庭与工作间保持平衡,只有选择出走才能逃离流量考核的宿命,表面充满自主性的转行背后实则是从业者难以适应高强度劳动的权宜之计。
七、结语
本文从流量和劳动过程控制的视角切入,探究流量指标如何作为数字时代商业媒体的管理手段控制从业者的劳动过程。以量化的形式对劳动进行评估体现了“数字泰勒主义”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新闻从业者的劳动被纳入国家文化事业的范畴,媒体机构的权威和从业者个人的声望掺杂在劳动过程中,使得这一群体面临的规训和控制更加隐蔽。从业者对流量指标“客观性”和“工作能力”的理解实则是流量“制造同意”的结果,“客观性”和“工作能力”的内化背后是商业媒体的控制手段。为了摆脱困在流量的境地,从业者利用迂回式的自我争取、寻求同行之间的心理认同以及流量造假的共谋,实现自主性的探索,但这种自主性只是为在精细化的数字指令下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大部分从业者既无力对抗也不愿逃脱,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
与布若威提出“赶工游戏”主要存在于工厂内部的竞争情境不同,本文认为数字时代互联网商业媒体中对从业者的“同意制造”不仅在劳动场所和劳动过程中产生,更来自于整体行业的意识形态文化塑造。计流量制下的劳动商品化观念和“客观”、“工作能力”、“透明”、“公正”等话语指代渗透在行业的意识形态之中,制度设计和作为共享文化的流量指标共同结合塑造了从业者的认识,造成从业者的劳动困境,不公正的劳动待遇和受损的劳动权被转化为个人问题,这种隐蔽的剥削更加深入、彻底和难以突破。但仅仅是“剥削—解放”的框架(丁未,2021)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力,从业者的劳动过程是不断流动循环的过程,充满着合作、共谋、隐忍和逃离等复杂的演绎。
流量指标不仅作为互联网商业媒体的管理手段控制着从业者的劳动过程,也引发流量文化下对于数字时代新闻业的进一步思考。流量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受众的喜好,对于流量指标的重视体现了传播议题设置的主导权由知识精英过渡到普通大众,也推动了新闻业用户导向的参与式文化兴起,由此提供了构建更为广阔新闻实践空间的可能性,即形成职业与非职业、专家与大众交织互动的新模式。追求“点击”与“分享”是新闻媒体服务于公众兴趣的表现,这在专业正确和商业正确层面无可厚非。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从业者将流量指标内化为专业标准并接受流量指标的考核,这就意味着数字时代互联网商业媒体生产具有病毒式传播潜力的故事将成为主流。互联网商业媒体以流量为导向的内容生产,无疑对新闻生产的专业标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或许是当下乃至未来的互联网新闻内容生产需要重点关注并予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埃伦·拉佩尔·谢尔(2021)。《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秦晨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白红义(2018)。当新闻业遇上人工智能:一个“劳动—知识—权威”的分析框架。《中国出版》,(19),26-30。
布雷弗曼(1978)。《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布若威,迈克尔(2008)。《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曹晋,曹茂(2017)。“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当代传播》,(6),32-36。
曹晋,许秀云(2014)。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93-105。
陈昶文(2019)。“流量逻辑”如何影响内容生产?——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实证考察。《新闻春秋》,(5),13-20。
陈龙(2020)。“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6),113-135。
丁未(2021)。遭遇“平台”:另类数字劳动与新权力装置。《新闻与传播研究》,(10),20-38。
福柯(2018)。《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萌(2017)。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5),47-59。
梁萌(2019)。弹性工时制何以失效?——互联网企业工作压力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学评论》,(3),35-49。
刘蒙之,刘战伟(2021)。边缘与游离: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身份认同研究。《媒介批评》,(00),257-279。
刘涛(2020)。融合新闻选题:“信息逻辑”与“流量逻辑”的对接。《教育传媒研究》,(1)20-24。
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7),42-58。
刘战伟,刘蒙之,李媛媛(2022)。从“赶稿游戏”到“老板游戏”:互联网平台中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66-85。
马克斯·韦伯(2004)。《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牛静,赵一菲(2020)。“倒贴钱”的实习如何可能?——新闻媒体实习生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与“理想游戏”。《新闻与传播研究》,(4),58-75。
齐格蒙特·鲍曼(2021)。《工作、消费主语和新穷人》(郭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孙萍(2019)。“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6),50-57。
文森特·莫斯可,凯瑟琳·麦克切尔编(2014)。《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维佳,周弘(2021)。流量新闻中的“零工记者”:数字劳动转型与西方新闻记者角色的变迁。《新闻与写作》,(2),14-21。
王星(2012)。西方劳动过程理论及其中国化。《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66-76。
王行坤(2018)。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8),94-104。
翁旭东,姜俣(2021)。一种隐蔽的展演劳动——音乐流媒体平台中的自我展演与数字劳动。《新闻记者》,(12),68-80。
吴鼎铭(2015)。“公民记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以“数字劳工”理论为研究视角。《新闻界》,(23),4-9。
夏倩芳(2013)。“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9),28-36。
夏倩芳,李婧(2017)。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困境及其形塑机制。《学术研究》,(4),43-55。
郑广怀,范一杰(2021)。从确立规范到常态规范: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控制。《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0),36-47。
郑广怀,孙慧,万向东(2015)。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社会学研究》,(3),170-19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BeamR. A. (1995). How Newspapers Use Readership Research.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16(2)28-38.
Blanchett Neheli, N. (2018). News by Numbers: The evolution of analytics in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6(8)1041-1051.
CaplanR.& boyd, danah. (2018). Isomorphism through algorithms: Institutional dependencies in the case of Facebook. Big Data & Society5(1)1-12.
Carlson, M. (2018). Confronting Measurable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6(4)406-417.
ChristinA. (2020). Metrics at W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errer-ConillR.& Tandoc, E. C. (2018). The Audience-Oriented Editor: Making sense 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wsroom. Digital Journalism, 6(4)436-453.
Fuchs, C. (2009).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4(1)69-87.
GansHerbert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1st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arcía Avilés, J. A.León, B.SandersK.& Harrison, J. (2004). Journalists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 Workflow and multi‐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Journalism Studies5(1)87-100.
Hanusch, F. (2017). Web analytics and the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journalism culture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platform-specific influences on newswork.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0)1571-1586.
HansenE. (2012). Aporias of digit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14678-694.
Lamot, K.PaulussenS.& Van AelstP. (2021). Do Metrics Drive News Decisions? Political News Journalists’ Exposure and Attitudes Toward Web Analytics. Electronic News, 15(1-2)3-20.
Meese, J.& Hurcombe, E. (2021). Facebook, news media and platform dependency: The institutional impacts of news distribution on social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23(8)2367-2384.
MoyoD.Mare, A.& MatsileleT. (2019). Analytics-Driven Journalism? Editorial Metric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Online News Production Practices in African Newsrooms”. Digital Journalism, 7(4)490-506.
Petre, C. (2021).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Clic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arkmanD. (2019). The hamster wheel.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8October. Available at: http://www.cjr.org/cover_story/the_hamster_wheel.
VanNest, A. (2016) . Where is your site traffic coming from? Parse. ly, 14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s://blog.parse.ly/post/5194/referral-traffic/.
VuH. T. (2014). The online audience as gatekeeper: The influence of reader metrics on news editorial selection. Journalism, 15(8)1094-1110.
WangQ. (2017).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Understanding journalism as process in China’s participatory culture. Journalism, 18(4)501-517.
ZamithR. (2018). Quantified Audiences in News Production: A synthesis and research agenda. Digital Journalism, 6(4)418-435.
Zuckerman, E. W. (2003). The critical trade-off: Identity assignment and box-office success in the feature film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2(1)27-67.
余沐芩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宋素红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