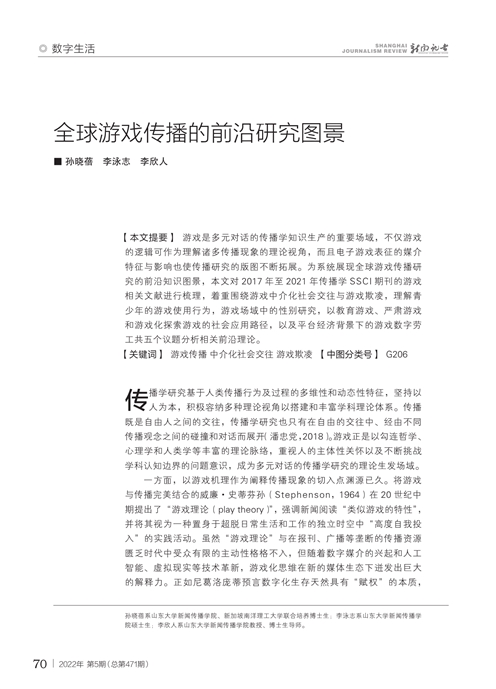全球游戏传播的前沿研究图景
■孙晓蓓 李泳志 李欣人
【本文提要】游戏是多元对话的传播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不仅游戏的逻辑可作为理解诸多传播现象的理论视角,而且电子游戏表征的媒介特征与影响也使传播研究的版图不断拓展。为系统展现全球游戏传播研究的前沿知识图景,本文对2017年至2021年传播学SSCI期刊的游戏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着重围绕游戏中介化社会交往与游戏欺凌,理解青少年的游戏使用行为,游戏场域中的性别研究,以教育游戏、严肃游戏和游戏化探索游戏的社会应用路径,以及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游戏数字劳工共五个议题分析相关前沿理论。
【关键词】游戏传播 中介化社会交往 游戏欺凌
【中图分类号】G206
传播学研究基于人类传播行为及过程的多维性和动态性特征,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容纳多种理论视角以搭建和丰富学科理论体系。传播既是自由人之间的交往,传播学研究也只有在自由的交往中、经由不同传播观念之间的碰撞和对话而展开(潘忠党,2018)。游戏正是以勾连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丰富的理论脉络,重视人的主体性关怀以及不断挑战学科认知边界的问题意识,成为多元对话的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生发场域。
一方面,以游戏机理作为阐释传播现象的切入点渊源已久。将游戏与传播完美结合的威廉·史蒂芬孙(Stephenson, 1964)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游戏理论(play theory)”,强调新闻阅读“类似游戏的特性”,并将其视为一种置身于超脱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独立时空中“高度自我投入”的实践活动。虽然“游戏理论”与在报刊、广播等垄断的传播资源匮乏时代中受众有限的主动性格格不入,但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革新,游戏化思维在新的媒体生态下迸发出巨大的解释力。正如尼葛洛庞蒂预言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网络时代的个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跳脱组织框架以独立的社会行为体在“自由活动的空间”中获得“自由流动的资源”,人的游戏心态被激活(喻国明,耿晓梦,2019)。另一方面,如何理解游戏媒介及其社会影响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支,游戏集人际交往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于一体,麦克卢汉(2011:315-328)认为游戏既是人们阐释和补足日常生活意义的直觉的延伸,也是能够集合多人公共参与的社会自我的延伸。在智能传播时代,随着游戏技术的革新,游戏表征出了某些其他数字媒介无法具备的意义生产模式,践行着特有的媒介效果产生逻辑。总之,传播生态的更迭和游戏技术的更新换代为游戏融合到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不仅游戏的逻辑可作为理解诸多传播现象的理论视角,同时电子游戏表征出的传播新形态和新特征也不断扩展着传播学的研究版图。由此,可以认为,传播与游戏的交织正沿着“游戏作为传播逻辑”和“游戏作为传播媒介”两条路径向前演进。
虽然本土传播研究与游戏的学术“对话”逐渐增多,从本世纪初以认识电脑游戏的媒介特征、阐明电脑游戏的虚拟建构以及探讨电脑游戏的意义生产等,刻画了游戏作为新兴传播研究领域的雏形(何威,2003),到以游戏勾连传播研究的理论路径和核心议题探索,以为仍处于蛮荒阶段的本土游戏研究提供借鉴(周逵,2016),再到目前在游戏的本体、应用、影响以及政策法规等细分领域,涌现百花齐放的成果(何威,李玥,2021)。但是,国内游戏研究仍需放眼全球,考察近年来国际传播学中游戏研究的演进脉络,挖掘具有创新性的前沿理论,以国际视野审视国内游戏传播研究的发展。因此,本研究致力于探索近年来全球传播学在游戏领域的研究中围绕何种热点议题展开,并贡献有启发性的知识基础。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的Communication—SSCI类目中五年影响因子大于2的68本期刊为样本文献来源,输入检索式“TS = (game) OR TS = (games) OR TS = (gaming) AND SO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以高级检索目标文献,时间段设置为“2017年至2021年”。检索结果显示共有34本传播学SSCI期刊发表了有关游戏研究的文章,排除editorial material、 book review、review等文章,确定目标文献838个(见表1)。
针对筛选确定的期刊文章,利用CiteSapce软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这是探索某研究领域发展历史或现状的代表性方法,它能够帮助研究者宏观把控复杂的知识网络和知识节点的交互、演化、衍生等情况。采取“关键词共现”的方式考察五年研究的核心议题,在CiteSapce软件中将“Node Type”设置为“keyword”,在设置完相关参数后运行关键词可视化,然后在可视化界面辅助人工相似词合并,如将“digital game”、“video game”和“computer game”合并为“digital game”,表2展示了近五年游戏传播论文共现的高频关键词(频次≧15)。
整体上,近年全球游戏传播研究的关键词分布虽然多元,但各研究议题类型相对集中。分析结果显示:5年关键词“social media”(频次57,中心度0.08)、“verbal aggression”(频次17,中心度0.05),以及“social interaction”(频次16,中心度0.01)指向游戏的社交媒体属性以及玩家间的社会交往和言语攻击,归结为“游戏中介化社会交往与游戏欺凌”议题;关键词“adolescent”(频次40,中心度0.03)、“motivation”(频次28,中心度0.04)指示了青少年的游戏行为及其动机,即“青少年游戏使用研究”议题;“gender”出现频次最高(频次63次,中心度0.06),表明游戏中的性别问题得到极大关注,即“游戏场域中的性别研究”议题;关键词“game design”(频次22,中心度0.05)、“gamification”(频次22,中心度0.03)着重突出了传播理论驱动的游戏设计及其应用的效果,归结为“教育游戏、严肃游戏以及游戏化”议题;关键词“labor”(频次17,中心度0.09)反映了数字游戏劳动的相关议题,体现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学术观照,即“数字游戏劳动研究”议题。
在这些游戏传播研究前沿议题中,既有游戏中介化社交、游戏与青少年成长、性别研究等经久不衰的社会议题,又有游戏应用、数字游戏劳动此类随技术与社会发展而涌现的热点话题。以此为参考选定关键文献进行阅读、分析与评估,能够较为全面细致地描摹出游戏传播研究知识生产的前沿图景。
二、游戏传播研究的前沿议题
(一)游戏中介化社会交往与游戏欺凌
学者们对游戏社交的理解多建立在较为成熟的社会形成论视角上,沿着游戏的社交可供性与用户的创造性使用相融合逻辑,不仅探讨了常态化的游戏社交所搭建或影响的社会联系,同时也为治理游戏欺凌提供了理论路径。
在常态化的游戏社交中,学者们一分为二地探讨游戏在强关系维系和弱关系搭建方面的成效,这是吸取了社交媒体研究所呈现的差异化效果的经验。一方面,学者们认为,游戏社交虽然能够扩大人们的弱关系搭建范围,但这种低效社交的质量提升却面临重重阻碍。通过引入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Nguyen等(2021)将游戏视为一种低临场感的媒介。“社会临场感”指“人际互动中,人们感受到交流对象的显著性和亲密性程度”,较高的临场感意味着媒介能够负载更多富有情感意义的社交线索,这对于通过媒介建构社会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显然,在多数人的媒介性能与沟通需求的评估中,游戏被定位为“非亲密”媒介。然而,用户的创造性便在于,考虑到情感匮乏的游戏社交体验,游戏在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中多被用于连接现实社交圈层以外的弱关系,不过这种媒介分配似乎也存在“关系隐患”,替代理论(displacement theory)提示人们,无意义的游戏社交往往会取代维持亲密关系的时间,甚至会破坏现实关系以及降低生活的幸福感(Liu et al., 2019)。替代效果是作用于第三方而产生的,即与玩家有亲密关系的亲人或朋友感知到游戏损害了他们之间的关系,Hellman、Karjalainen和Majamaki(2017)以“利益冲突”(clashes of interest)概念描述了现实存在的强关系与游戏中介的弱关系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以关系亲密性和承诺为核心,并体现在就每日日程安排、长期目标优先次序、交流时间分配以及关系的自主权四个方面的谈判。
即便游戏社交的情感体验并不理想,但增强现实(argument reality, AR)技术的应用极大突破了游戏在社会关系搭建上的地域性结构限制,使优化游戏社交有迹可循。通过贯通线上与线下空间,AR游戏为人们描绘了通过游戏社交获取强关系的前景。在中介化传播中,兴趣等因素可以替代共处同一位置对于人际互动的重要性,AR游戏作为一种位置媒介,以鼓励玩家走出家门探索现实空间新意义的机制聚合了共同的游戏热情与现实空间的相遇,从而使作为促成社交关系重要因素的相似性和临近性共同起作用(Vella et al., 2019)。不过,AR游戏促成的社交关系仅是一种桥接社会资本的积累,一旦互动减少,这种社会资本会迅速衰减,那么,面对面互动到底能够为游戏中介化关系的维持和增进添加多少砝码呢?Lai和Fung(2020)以跨越十年的深度访谈探索游戏友谊的演变给予了回答,研究发现,面对面互动作为游戏社交促成的信任感和亲密感的验证,能够重申虚拟关系向现实世界的转化,不过,转化的成功率最终需要取决于双方对参与成本(侵占现有关系)和收益(附加情感)的理性计算。
当被应用于既有强关系的人际互动时,游戏呈现出完全迥异的社会效果。在此,近年学者们并未太过关注同伴或恋爱关系,而是着眼于家庭游戏与亲子关系讨论,这可能是基于多数家庭对子女问题性游戏行为的担忧,就游戏使用引发的亲子冲突(parent-child conflict)也是损害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威胁。但是,如果父母能够克服道德恐慌,与子女共同游戏,是否能够营造更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Wang、Taylor和Sun(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以游戏为纽带的亲子互动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关系质量,亲子游戏的频率与家庭满意度和亲密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家庭满意度调节了亲子游戏与家庭亲密度的关系,相比亲子关系和睦的家庭,沟通不良的父母和子女从中受益更多。共同游戏(co-play)既能使亲子间保持情感和身体上的联系,同时,通过营造私人想法和情感披露的家庭沟通氛围,父母能够与子女公开交流游戏使用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子女会感知到更多的自主权,这对于子女成长过程中协商亲子关系是至关重要的(Meeus et al., 2020)。正如Hoffman(2019)所认为的,虽然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强调媒介技术属性匹配特定群体的身份特征以促进交流互动,但突破隔阂是实现良好沟通的前提,由此,游戏提供的集体合作、话题制造和模拟感受等功能亦可被视为一类社交可供性,即为敞开心扉的交流创造相互理解和亲密感受的前提。
以游戏欺凌为代表的负面游戏社交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新的关注话题。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游戏欺凌视为网络欺凌在游戏空间中的延伸,沿袭网络欺凌的研究脉络解释其成因,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SIDE)和网络去抑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ODE),这些理论以技术中心论的视角强调游戏欺凌是游戏匿名状态下身份规范和行为抑制被隐退的后果。但近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相比网络欺凌,游戏欺凌呈现出诸多差异性。
第一,网络喷子(troller)从单一的言语攻击延展到游戏策略攻击且二者相互交织,后者指以“团队杀戮”和“团队封锁”为代表的阻碍团队目标的游戏行为,该群体也被冠以新的称号,即英语世界中的“悲伤者”(griefer),以及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地区分别被称为“白眼”(white eyes)和“演员”。不同于既往研究将游戏欺凌视为一类偏激人格的“肇事群体”的“越轨玩法”(deviant play),近年学者们逐渐将目光移至捕捉社交敌意(social hostility)在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传递过程,以理解游戏欺凌背后的情境驱动力。Cook(2019)从需求理论(demand theory)出发,认为游戏欺凌根源于玩家与游戏之间、玩家相互之间的需求不平衡,前者指在游戏难度与玩家能力非匹配状态下,玩家因游戏体验无法满足认知和身体需求从而游离于心流状态之外,此时,他们会因无聊而挑衅其他玩家以增加游戏乐趣或成就感;后者则体现为以欺凌的方式刺激其他玩家产生反馈,从而满足欺凌者非正常化的社交需求。
第二,虽然SIDE和ODE都提示了群体规范缺失对游戏欺凌的诱导作用,但欺凌也可能是一种框定和规范游戏社区的新途径。Graham(2019)援引“边界维护”(boundary maintenance)的概念表明,游戏欺凌驱逐了游戏世界的边缘群体,如女性、新手等,从而塑造了游戏圈层的边界。同样,Cook等(2018)发现,游戏社区在某种程度上促成并延续了欺凌,旁观者往往会加入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骂战,却很少采取制止行为。由此而言,狭隘和排外的游戏文化应该是游戏欺凌的根源。
第三,在网络欺凌中,往往多次受害经历才会促成从被欺凌者到欺凌者的转化,然而,这一循环周期在游戏欺凌中升级至仅需一次互动。基于胁迫行为理论(coercive action theory),欺凌作为一种对“局外人”行使强制力的手段,可能会导致被欺凌者服从或报复的两极化结果,但在高度兴奋与即时反馈的游戏情境中,负面情绪和报复心理的恶性去抑(toxic inhibition)更易被激活,最终演变为“负面互动的升级循环”(Cook et al., 2019)。实际上,一些学者更担心长期暴露于有害游戏环境会使人们丧失对社交攻击应有的道德判断,Grizzard等(2017)的纵向实验证实,重复游戏会诱发玩家对反道德行为的脱敏(desensitization to moral violations),这种脱敏效应还会延续至未来的游戏经验中。Fox等(2018)在考察玩家游戏日记时佐证了此观点,他们发现,相比经验玩家,新手玩家会报告更多的游戏欺凌受害经历。除了新手玩家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技能贬低(skill disparagement)之外,这可能是因为游戏欺凌在反复游戏过程中被习惯化,从而降低了社交攻击引起情绪波动的敏感度。
(二)青少年游戏使用研究
青少年游戏使用是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的社会议题,近年研究在长期为传播学所关注的三个方面:“如何认识青少年的游戏使用”、“如何理解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如何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游戏”提供了新的发现和思考。
在如今的媒介化世界,游戏以其娱乐性、虚拟性以及情感沉浸等特征,成为青少年应对日常生活压力和情绪转移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媒介应对(media coping)为视角的游戏研究应运而生。应对本质上指个人为管理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而采取在认知或行为层面上的努力,分为问题集中型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与情绪集中型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两种。区别在于问题集中型应对着眼于造成压力的问题本身,情绪集中型应对针对压力所激发的不良情绪,因此,为情绪宣泄而使用游戏往往被视为青少年的一类情绪集中型应对。与先前研究认为宣泄动机的游戏行为有益于自我调节相反,Verheijen等(2020)认为,将游戏作为情绪集中型应对会导致不良适应,通过对705名荷兰青少年的调查发现,青少年很难借助游戏真正达到情绪改善的目的。不仅如此,卷入游戏的青少年的不良适应还表现在身份混淆方面,Kurek、Jose和Stuart(2017)的实证研究证实,相比普通用户,重度游戏玩家呈现出更高程度的错误自我感知(false self-perceptions)以及更低的真实性。游戏的身份塑造功能会依靠帮助青少年寻找到特定的社交网络而实现,这在他们的周围环境之外建立社区意识以及具有相似思想的社会支持系统。从这个意义而言,适应不良便是过度沉迷于游戏世界加剧了与现实世界的经验冲突的一种反映。
无论是情绪调整,还是身份认同,不良适应的游戏动机共同指向了青少年特殊的社会心理需求,这也部分解释了青少年的游戏过度使用。按照Kardefelt-Winther(2014)的补偿性互联网使用模型(model of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游戏可以有效且即时作用于心理补偿”的不良认知会屏蔽感知依赖性使用的负面影响,并进而转化为过度使用。但是,考虑到游戏依赖根本上是为青少年时期的特殊需求所驱动,那么,游戏过度使用是会伴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改善的短暂越轨现象,还是如医学研究所认为的一种需要外部干预的稳定性病理问题,即网络游戏成瘾(Internet game disorder)?为回答这一问题,Rothmund等(2018)以纵向研究对比一年间德国中学生的游戏使用变化并发现,于多数青少年而言,高强度的游戏使用仅是成长中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并非一种呈现精神紊乱的稳定性病症。游戏使用程度的不稳定性可能源于青少年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发展动机变化,比如,暴力游戏生动逼真的竞技场景满足了男孩子在某一时期探索男性气质的需求,但当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发展兴趣转向浪漫关系时,暴力游戏无法再提供适宜的经验学习而被弃置。
这种“游戏情景能够提供成长学习的体验”的认识也成为学者们思考如何使游戏在青少年成长中承担正向角色的突破口。注重现实叙事的游戏设计,即指向青少年的生存现状甚至是困境似乎更为理想。实际上,青少年认为能够促进对自我与社会反思的游戏体验才是有意义的,他们处于试图确定自己是谁以及身处何种社会位置的成长阶段,这些反思性的游戏体验可以满足对身份发展和同伴关系需求的思考,并改善幸福感(Daneels et al., 2020)。具有独特的自反性与元叙事特征的游戏会鼓励青少年批判性地反思游戏场景和自我角色,同时始终清醒保持“自己身处游戏中”的意识,Whaley(2018)将此种状态的游戏体验称之为“远距离参与”(distanced engagement),这为在规避游戏沉迷风险的前提下探索游戏为青少年社会化发挥正向作用提供了路径。
家庭教养在青少年游戏使用中的角色同样不可忽视。传播学研究中,父母干预理论(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以强调家长在子女理解媒介信息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勾勒了具体的干预措施,成为解决青少年媒体使用问题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视角。所谓父母干预,是指针对子女的媒体使用,家长为规避风险以及获取益处而采取的监督或指导策略。父母干预理论诞生于电视媒体时期,建构了限制型干预(restrictive mediation)、积极型干预(active mediation)和共同使用(co-use)三大措施框架。但鉴于游戏的互动性和沉浸性,游戏的影响比电视更为显著,游戏等级检查(game rating check)等新的干预策略逐渐出现以适应游戏特征,父母干预理论需要进行补充以捕捉当今家庭的数字媒体景观的复杂性。通过对新加坡41个家庭的深度访谈,Jiow、Lim和Lin(2017)发现,游戏使用的父母干预呈现为把关(gatekeeping)、讨论(discursive)、调查(investigate)和转移(diversionary)四种策略,相比规范子女游戏接触的“把关”和亲子间就游戏使用公开对话的“讨论”策略,“调查”与“转移”更能体现出为适应游戏特征的干预调整,“调查”指代为有效实施干预而进行的信息搜索和技能获取,而“转移”则意为引导子女从事其他活动以远离游戏。父母通常不会孤立地使用任何一种特定的干预措施,而是根据情况有选择地同时应用多种策略。但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干预措施,“保护”与“理解”应该是解决青少年游戏使用问题的家庭教养核心所在(Mikko,2021)。Mikko认为,长久以来,受媒体营造的道德恐慌等影响,父母的游戏干预更侧重于“保护”青少年免受父母感知的游戏风险,这体现为限制游戏行为作为主流的干预措施,而非共同游戏或寻求游戏素养的提升。但是,若父母能“理解”游戏行为和文化,弥合游戏相关的代际差异,则可能衍生出更多有效的干预手段以减缓游戏问题上的家庭冲突。Harrison等(2019)提示家长,实际上,父母感知的问题性游戏行为,可能仅仅是青少年的一种借助媒体的感觉策展(sensory curation)行为。在正常的环境下,人的大脑可以准确捕捉感觉信息,并过滤非相关信息,从而避免感觉过载。媒体感觉策展理论(media sensory curation theory)认为,当环境信息与自身感官需求不一致时,媒体能够搭建临时环境捕捉或阻止某种感觉信息输入以辅助实现多感官平衡与整合。由于青少年在很多时候需要听从父母安排选择环境,这使他们常会遭遇家庭氛围与感官需求的失衡,这时,游戏使用成为实现感官平衡的有效途径。
(三)游戏场域中的性别研究
电子游戏自诞生起就与性别关系密切,主流游戏文化长期以超男性气质的性别规范为标志,暗示甚至明示女性为工具化的形象,游戏一度被视为性别最不平等的场域。虽然女性游戏市场不断攀升,但以厌女症为表征的有害技术文化(toxic technoculture)在其中似乎并未弱化,游戏玩家的性别身份鸿沟也未显著窄化,这使致力于追求性别平等的研究者们重新思考游戏性别文化的塑造和演变,以及探讨女性玩家建构身份主体性的可能性。近年来,相关研究从游戏的技术特征出发,重申了形塑有害游戏环境的结构性力量,尝试从社会规范、组织运转和日常经验等方面作出解释。
学者们留意到固定的游戏设计往往与父权制思想相吻合,并在“娱乐至死”中消解了女性挑战或颠覆的可能性。Liu和Lai(2020)通过考察MOBA游戏和乙女类游戏(女性向游戏)发现,这些游戏潜移默化地将女性玩家整合到男性规范的浪漫理想中,这是因为前者复制了再生性别话语形塑的女性形象,女性玩家遵守了游戏的规则便相当于同意了在男性定义的世界中竞争,而后者则迎合了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女性主体性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女性退出了被定义的世界,但出于其本质上对父权制的悲观主义,创造了另一个女性退缩的世界。虽然乙女类游戏的核心机制倡导赋权女性的自我表达,但符合男性凝视的女性角色外观和叙事模式又限制了这种自主权,同时正常化了父权制在女性游戏世界中的强制执行力,这与“倒退的性别政治”(regressive gender politics)的理念基本吻合(Cummings, 2018)。Cote和Mejeur(2018)认为,游戏的社会竞争属性决定了其对传统社会男性气概的传承并非偶然,大部分的电子游戏强调快速反应、积极对抗与压制征服,同社会规范对男性的推崇和女性的压迫别无二致。
性别差异游戏文化的产生也可能为组织生产规律所解释。具备劳动实践属性的网络游戏延续了传统的社会组织架构,其中游戏公司处于权力等级的顶端,玩家通过技能训练和虚拟交往实现社会资本积累和阶层跃升。那么,当生产本身被具有某种身份标签的群体控制并掌握话语权后,从外部很难影响到行业领域,这导致以男性为主的游戏开发者倾向于制作出符合男性凝视的女性角色,并在无形中维持了男性主导游戏的刻板印象(Gandolfi & Sciannamblo, 2019)。实际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游戏体验中频繁接触过分性别化的游戏化身(avatar)都会诱发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效果,即严重依赖于外表,而非个性和个人能力的自我感知(Vandenbosch et al., 2017)。由此,也就不难理解Cote(2018)的忧虑:大量充斥在游戏世界中的极具夸张与性暗示的女性化身会扭曲女性玩家的身份认同,从而内化性别歧视的螺旋,根本上阻断了女性地位自我提升的动力来源。
玩家的日常社会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有害游戏文化的建构。基于游戏世界为男性与女性赋予并不对等的社会资本,女性在日常游戏实践中需要付出更多的经验和金钱,以获取男性的准入,这一过程本身便是父权制观念强化。Vilasís-Pamos和Pires(2021)发现,虽然女性有意将自己定义为“玩家”以挑战男性权威,然而她们的游戏行为却不得不受制于家庭规范,在传统认知中被界定为“与维护家庭秩序相悖而行”的游戏行为显然是不被接纳的。此外,在体验游戏时,女性很大程度上会遭受来自男性的语言攻击,Ortiz(2019)将其认为是一种框定性别边界的话语实践。这种实践直接促进了有害游戏文化的社会性建构,因为参与游戏文化并共享对这一文化的理解并不意味着行动者就会直接建构与该文化相关的社会身份,但性别歧视相关的日常游戏体验会加速内化女性作为边缘玩家身份的意义。诚然,女性玩家群体也发展出一系列应对言语攻击的策略,如游戏退出、远离陌生人、隐藏性别、技能与经验提升以及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Cote, 2017)。但实际上,现阶段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会变相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因为逃避与妥协依然是女性玩家的主流姿态,虽然游戏的可供性催生了采用男性化的昵称和化身的性别隐藏策略,但这也无意中增强了女性在游戏空间中的不可见性,使女性和少数支持她们的男性玩家感知到更强大的男性敌意而转向沉默的螺旋。女性玩家的象征性堙灭使游戏场域中的性别平等更难以实现。
可见,男性在游戏话语场域中的原生优势异常坚固,虽然女性玩家群体内孕育着一定的反抗力量,但成效并不显著,整体状况的改善应该寄希望于更为开放的游戏文化。Cote(2021)认为包容性的游戏文化不能仅停留在主流玩家对更多元的游戏内容的接纳,由于游戏设计对性别身份的塑造会深刻影响女性如何定位自我,应该是重新定义游戏文化的突破口。Fox和Tang(2017)同样强调了运营主体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们引入规避职场毒性行为(toxic behavior)的思路,指出组织的反应是预防和减轻不良后果的重要环节,作为游戏社会中最具权威性和惩治能力的组织——游戏公司若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无疑会助长对女性不利的游戏氛围,因为组织的被动或无能暗示了性骚扰在这里是被接受和正常化的。
(四)教育游戏(educational games)、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与游戏化(gamification)
作为借助游戏元素吸引、指导与激励玩家的游戏应用,教育游戏、严肃游戏与游戏化的研究体现了学者们对于如何发挥游戏的正向社会引导的思考与探索。三类游戏应用有着不同的预期目标:教育游戏旨在利用娱乐媒体(游戏)作为教育信息的载体,以传达知识、影响态度等,而严肃游戏致力于借助与玩家互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在现实世界的行动或态度,从而达到说服目的,相比而言,游戏化则突破了游戏本体的范畴,强调在非游戏语境中创设类游戏化体验以影响用户的行为价值感知,从而激发对目标行为的行动力。前沿国际研究基于成熟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模式,将传播理论驱动的游戏设计置于实验室环境中,以评估游戏应用的潜能。
教育游戏的研究逐渐脱离了与课堂教学效果的比较视角,转向探索教育游戏相比其他媒体教学技术(如教育视频)的优势。同时,研究重点也从以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为内容的学习主题升级为发掘游戏学习高级概念的能力。首先,认知偏误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短板,这源于人类在日常判断与决策时习惯性地应用心理捷径或经验法则,并可能导致系统性错误或偏见。但推理的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y of reasoning)提示到,增强逻辑思维可有效调节惯性思考,从而避免认知偏误。受此启发,学者们将逻辑思维锻炼的思路应用于教育游戏中,结果证实,相比视频教学,教育游戏在认知偏误减轻上的短期与长期效果均表现不俗(Martey et al., 2017a; Rhodes et al., 2017)。其次,教育游戏为协调游戏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路径,虽然游戏常被研究的是其负面的道德影响(如攻击性),但是游戏可以仿拟道德环境,允许玩家参与道德决策也能够服务于玩家在现实生活所需的道德知识学习(Piittinen, 2018)。通过考察道德学习相关传播理论及其在游戏中的应用,Schrier(2019)建构了道德教育游戏的设计原则框架,其中,“允许促成恰当的选择与结果”意味着游戏允许玩家做出相关道德选择或决定,以及“支持社会互动与社区传播”强调以同情、照顾社区其他玩家与非玩家角色(NPCs)锻炼道德表达技巧。以游戏互动学习道德表达贯穿于玩家对游戏叙事与人物的强烈参与之中,从而支持了玩家的情感关系的产生、反思,获得超越单纯娱乐的身心体验,而这又会基于增强选择能力的游戏机制得到加强(Daneels et al., 2021)。既然如此,那么何种设计元素是保证游戏学习效果的关键呢?长久以来,教育游戏设计一直存在着参与度与注意力之间的矛盾,因为探索性的游戏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干扰理解的额外认知负载(additional cognitive load),Martey等(2017b)认为可玩性与教育性的平衡需要摒弃既往将教育游戏区别于其他学习模式的研究视角(如“寓教于玩”),而应该关注学习者理解和应用具体知识所需技巧的差异。总体而言,在复杂知识的游戏学习过程中,牺牲部分参与度而增加用于学习的认知资源是可取的。
在严肃游戏方面,学者们不断扩展应用领域以证实游戏在公共议题社会动员上的效果,比如,严肃游戏的美学呈现可为玩家提供直观的环境变化图景,从而培育他们对于现阶段环境政策的参与度(Abraham, 2018);对移民信任感的培养可以借助体验移民主题的严肃游戏实现,体验移民角色增强了与其的亲社会联系,并降低了偏见(Bouchillon & Stewart, 2021)。但是,严肃游戏能够成为引导公众态度和公共参与的适宜平台,前提是公众的采纳与接受。Jacobs(2021)以综合阐述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等传播理论分析了可能影响严肃游戏使用与接受的因素,并强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借用娱乐游戏和纯教学媒体的知识来解释人们如何体验严肃游戏”和“需要建立统一的严肃游戏接受和采用的理论,还是应该对不同类型的游戏、不同背景的玩家群体做出不同的解释”应该是需要考虑的两个突出问题。此外,严肃游戏能够具备刺激公众深层对话的能力也是关键,但Radchuk等(2017)在考察了科学传播的87款游戏之后却给出了遗憾的答案:由于社交激励机制在游戏设计中的缺失,此阶段的严肃游戏仅可实现信息获取与咨询的浅层参与。针对严肃游戏在大范围普及中的短板,Fisher(2020)提出实现社会动员效果,其关键节点在于严肃游戏的生产与传播环节,也就是说,需要将UGC的理念渗透到严肃游戏制作中,具体包括公众投票的游戏议程、本地叙事的游戏内容,以及社区集合参与游戏的“创新与扩散”等。
传播研究并未过于关注游戏化的应用效果,而是在理论层面反思游戏化概念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悖论。游戏化的行动激励需要依靠创设可感知的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价值体系多呈现为以任务为中心的成就达成系统,这种固化的行为引导模式可能会催生已感知的因果关系,从而减少了用户的自主感,但自主感恰恰又是行为自驱的能量来源,由此,Bateman(2018)将游戏化视为“游戏的僵化”(stultification)。复杂议题与行为的游戏引导效果不仅为游戏化设计所塑造,也会受到目标用户群体的内部因素和更广泛的社会动态所影响(McKernan, 2021),这对未来的游戏应用研究极具反思价值。
(五)数字游戏劳动(digital game labor)研究
近年来,移动设备和在线分销平台的普及应用重新配置了游戏的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促成了新的游戏商业模式。数字游戏劳动研究不再将产业变化单一地视为对劳动的剥削或解放,而是在“作为创意劳动的专业生产”、“作为爱好劳动的‘产消合一’”以及“作为职业劳动的游戏消费”方面展现了数字游戏劳动的特殊性。
在创意游戏生产方面,数字劳工研究致力于不断扩展行业生产的可见性,力图在更为多元的研究对象中探讨结构性因素下的“不稳定性劳动”(precarious labor)。纵观近年研究,从大型游戏公司开发人员到独立游戏制作者凸显了研究对象的转向。作为一种不依附于大型游戏公司的自主劳动,研究独立游戏制作不仅可以透视经济不稳定性与自主文化创意之间张力,也能够深入理解以“酷儿”(queer)为代表的边缘群体如何凭借灵感劳动争取文化的主体性。表面上看,独立制作的劳动模式似乎能够摆脱资本剥削,在一定意义上为劳工赋权,但研究者们对独立游戏制作者的地位和处境却并不乐观:由于非正规劳动者的身份,独立游戏制作者往往需要为应对社会歧视而付出大量额外的情感劳动,以及缺乏必要的产权保护迫使他们随时承受被游戏公司窃取灵感工作的代价(Ruberg, 2019; Pelurson, 2021)。不过,不稳定性劳动也可能是职业化游戏工作的入场券,Ozimek(2019)将游戏外包工作视为一类“希望劳动”(hope labor),即为了在未来获得更稳定的正规就业机会,甘心游离于大型游戏公司的边缘,并从事着报酬不足的工作。实际上,“希望劳动”的概念潜藏着不稳定性劳动的循环逻辑,因为将“依靠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此类话语的内化实则助长了自我剥削,即便身处大型游戏公司亦如此。Cote和Harris(2021)通过对游戏开发相关媒体文本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揭露了游戏开发人员内化“紧缩(crunch)”即加班文化的逻辑。他们发现,媒体会将“紧缩”形塑为来自外部强制的“糟糕紧缩”和指导自我提升的“良好紧缩”,受此影响,劳工将争取“良好紧缩”乐观地视为一种提高工作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劳动实践,但这实则阻碍了摆脱加班文化的生产结构的重构,由此,“残酷的乐观”(cruel optimism)劳动关系被塑造,即劳工期望为改善工作环境的努力并无实际意义。
生产性与消费性劳工是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两大分野,但游戏行业发展逐渐模糊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游戏模组制作者的出现便是代表。所谓“模组”(mod),是指粉丝玩家根据个人喜好对游戏的修改版本,Kücklich(2005)以“玩工”(playlabour)的概念刻画游戏模组制作者,凸显了粉丝玩家作为“产消合一”者的爱好劳动。通过在游戏主题虚拟社区以及玩家社群中的互动,以攻略分享、亚文化周边制作以及模组创作等,粉丝玩家们践行着无酬的劳动,不过,近年Steam等平台开始鼓励玩家有偿上传模组,付费模组似乎成为资本积累的另一种新的形式。Joseph(2018)将脱胎于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视为理解模组经济的有效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主义通过“空间修复”机制剥夺新的或未充分开发的地域以更高效积累资本的过程,而资本在数字空间的渗透本质是将剥夺性积累拓展为“数字空间修复”。Joseph认为,在付费模组之前,模组的生产以玩家众筹作为资金来源,这框定了模组是游戏社区的自主生产,但分销平台主导的模组付费剥夺了“作为爱好的劳动”,以往借助社区存在的粉丝生产不得不受制于平台提供的可接近性和可见性,在多(玩工)对少(平台)的商业模式下,平台所有者在模组生产链中掌握了特权地位。
不同于“玩工”为情感回报与社会资本积累而自愿劳动,在游戏消费场域中,还存在一部分以游戏消费作为职业劳动的群体,玩游戏于他们而言是一份有偿工作,这类群体包括游戏主播、金币农夫与电竞选手。第一,直播平台通过为独立游戏、小众游戏等提供可见性和附加寿命等重塑了游戏市场的权力关系,在当代游戏生态系统扮演着新的政治经济角色(Johnson & Woodcock, 2019)。然而,由于直播平台的流量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深度社交的可供性,主播们需要为保持社交活跃度和情感反应付出大量情感劳动,Woodcock和Johnson(2019)将这种情感劳动视为一种新型的表演,因为主播们在利用游戏技巧和个性之外,正逐渐利用角色表演的戏剧性,寻求与观众互动的独特方式。第二,“金币农夫”(gold farmer)指通过玩游戏获取虚拟战利品和金币并将其转卖给其他玩家以获取报酬的一类人。他们往往聚集于设立于酒店、住宅等“代练工作室”有组织地工作,这将劳动过程从工厂转移到社会,形成了一种新兴的“社会工厂”。流水线式的“打金”(goldfarming)偏离了自愿给予的剥削分析框架,因为“打金”使玩家的游戏技能和经验实现商品化,全球资本家因此无法垄断粉丝生产的情感劳动。但Tai和Hu(2018)认为,资本并不会因金币农夫的劳动而遭受损失,因为提供虚拟资产和服务的交易也是粉丝玩家的主要买点和激励因素,这甚至会提升全球资本的利润率。第三,作为职业游戏玩家,电竞选手以为电竞游戏文化共创价值成为平台经济的重要角色,但电竞选手同样面临不稳定性的问题。一方面,基于电竞生态为顶级选手预留的狭窄空间,为承担维持高水平的风险成为不稳定性的来源。电竞选手往往需要付出大量不可见的衔接工作以适应核心网站和游戏系统的多种改变,但其中的悖论在于,交叉平台的衔接工作又成为一种影响专业水平发挥的负担(Witkowski & Manning, 2019)。另一方面,电竞选手的不稳定性还表现在职业生涯的不可持续性。虽然在职业生涯末端时,电竞选手的玩家影响力往往能够为与平台的重新谈判提供契机,但由于“明星效应”本身为资本所打造,Johnson与Woodcock(2021)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与资本的交易既是剥削性的,也是短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正呈现出把“权力平衡”从劳动中转移出去的趋势。
三、总结与展望
本文讨论的五大议题折射出近年来国际游戏传播研究的重点,但其中也暴露出某些研究不足。首先,基于与传统社交媒体的比较,游戏中介化社交研究强调游戏在沟通社会关系中展示出的技术特性与功用,但这也使研究很难绕开社交媒介的理论范式,缺乏考量游戏机制驱动的游戏中介化社交的理论独创性。其次,为合理引导青少年游戏使用,相关研究视角需要从“认知”深入到“体会”,不仅要考虑青少年的特殊成长阶段以及媒体使用偏好,又要注意游戏相关的代际差异以及以往媒介经验的适宜性。而在性别议题上,权力结构、男性霸权主义与女权主义几乎成为游戏性别研究的主流知识背景,但过分强调游戏机制和权力结构与父权制社会的契合性容易陷入对游戏本身的偏离,这表现为淡化女性对游戏社区的贡献,以及男性的游戏内驱力的缺位等。再次,随着游戏类型组合边界的扩展,电子游戏的工具属性提供了娱乐与教育相结合的可能性,但游戏的引导效果受游戏设计与玩家游戏行为相组合的动态影响,机械化的任务与成就系统限制了游戏引导功能的发挥空间与引导方式,进行分众化的效果考量,以及与其他活动的搭配纳入研究规划势在必行。最后,随着平台经济的演化与发展,以及劳动者主体性的增强等,数字游戏劳工研究应该不仅将数字游戏视为发现平台经济在劳动商品化、劳动异化等经典问题上的特征表现场域,也应该是更新及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场域。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子游戏中的社会文化属性日益膨胀,“理解游戏”对国内游戏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现状尤为重要。自主研发游戏样本量较少且多集中于手游领域,热门游戏的内购产品成为付费增长点,电子游戏市场结构和玩家消费习惯与国外差异明显。然而,着眼于轻量化休闲娱乐的国内市场同样关注玩家的社交需求与沟通体验,游戏出版审查机制突出了游戏的消费属性,更强调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游戏的社会价值,期待游戏能够在平衡玩家娱乐生活中承担对玩家的教化任务。同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为国产游戏提供了大量素材,相对内敛包容的文化环境使得女性进入游戏圈层的实践更为轻松;全球化又使得国内玩家拥有更多机会接触国外3A级游戏作品,优胜劣汰的市场格局间接带动了生产厂商对游戏创意与技术革新的关注。将西方游戏前沿理论结合国内游戏政策、玩家习惯、平台结构、消费模式开展研究,并“因地制宜”地根据本土的社会现状予以辨析和修正,使传统社会议题与游戏相关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学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这一本土化研究工作具有巨大的传播学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何威(2003)。建构与交互:对新媒介电脑游戏的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何威,李玥(2021)。2020年中国数字游戏研究述评。《文艺理论与批评》,(3),135-145。
马歇尔·麦克卢汉(2011)。《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潘忠党(2018)。走向反思、多元、对谈的传播学。《国际新闻界》,(2),47-52。
喻国明,耿晓梦(2019)。从游戏玩家的类型研究到未来线上用户的特质模型——兼论游戏范式对于未来传播研究的价值。《当代传播》,(3),26-30。
周逵(2016)。作为传播的游戏:游戏研究的历史源流、理论路径与核心议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7),25-31。
Abraham, B. (2018). Video game visions of climate futures: ARMA 3 and implications for games and persuasion. Games and Culture13(1)71-91.
Bateman, C. (2018). Playing work, or gamification as stultificatio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1(9)1193-1203.
BouchillonB. C.& StewartP. A. (2021). Games-based trust: Role-playing th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of immigrants. New Media & Society23(3)479-496.
CookC. L. (2019). Between a troll and a hard place: The demand framework’s answer to one of gaming’s biggest problem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7(4)176-185.
CookC.Conijn, R.SchaafsmaJ.& AntheunisM. (2019). For whom the gamer trolls: A study of trolling interactions in the online gaming contex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4)293-318.
CookC.SchaafsmaJ.& AntheunisM. (2018). Under the bridge: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online trolling in the gaming context. New Media & Society20(9)3323-3340.
CoteA. C. (2017). “I can defend myself”: Women’s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harassment while gaming online. Games and Culture12(2)136-155.
CoteA. C. (2018). Writing “gamers”: The gendered construction of gamer identity in Nintendo power (1994-1999). Games and Culture13(5)479-503.
CoteA. C.& Harris, B. C. (2021). The cruel optimism of “good crunch”: How game industry discourses perpetuate unsustainable labor practices. New Media & Society.
CoteA. C.& Mejeur, C. (2018). Gamers, gender, and cruel optimism: The limits of social identity constructs in The Guild. Feminist Media Studies18(6)963-978.
CoteA. C. (2020). Casual resistance: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video gaming’s gendered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audience percep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70(6)819-841.
CummingsK. (2018). Gendered choices: Examining the mechanics of mobile and online girl games. Television & New Media19(1)24-41.
Daneels, R.MallietS.Geerts, L.DenayerN.WalraveM.& Vandebosch, H. (2021). Assassinsgods, and androids: How narratives and game mechanics shape eudaimonic game experience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9(1)49-61.
Daneels, R.Vandebosch, H.& WalraveM. (2020). “Just for fun?”: An exploration of digital games’ potential for eudaimonic media experiences among Flemish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14(3)285-301.
FisherJ. (2020). Digital gamesdeveloping democraciesand civic engagement: A study of games in Kenya and Nigeria. MediaCulture & Society42(7-8)1309-1325.
Fox, J.GilbertM.& Tang, W. Y. (2018). Player experiences in a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A diary study of performance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Media & Society20(11)4056-4073.
Fox, J.& Tang, W. Y. (2017). Women’s experiences with general and sexual harassment in online video games: Rumination, organizational responsiveness, withdrawal, and coping strategies. New Media & Society19(8)1290-1307.
GandolfiE.& SciannambloM. (2019). Unfolding female quiet in wargames: Gender bias in Metal Gear Solid V: The Phantom Pain from representation to gameplay. Feminist Media Studies19(3)331-347.
GrahamE. (2019). Boundary mainten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rolling. New Media & Society21(9)2029-2047.
GrizzardM.TamboriniR.Sherry, J. L.& WeberR. (2017). Repeated play reduces video games’ ability to elicit guilt: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experiment. Media Psychology, 20(2)267-290.
HarrisonK.VallinaL.CoutureA.WenholdH.& MoormanJ. D. (2019). Sensory curation: Theorizing media use for sensory reg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media conflict. Media Psychology, 22(4)653-688.
Hellman, M.KarjalainenS. M.& Majamaki, M. (2017). “Present yet absent”: Negotiating commitment and intimacy in life with an excessive online role gamer. New Media & Society19(11)1710-1726.
Hoffman, K. M. (2019). Social and cognitive affordances of two depression-themed games. Games and Culture14(7-8)875-895.
JacobsR. S. (2021). Winning over the players: Investigating the motivations to play and acceptance of serious game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9(1)28-38.
JiowH. J.LimS. S.& LinJ. (2017). Level up! Refreshing 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 for our digital media landscape. Communication Theory, 27(3)309-328.
Johnson, M. R.& Woodcock, J. (2019). The impacts of live streaming and Twitch. tv o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MediaCulture & Society41(5)670-688.
Johnson, M. R.& Woodcock, J. (2021). Work, play, and precariousness: An overview of the labour ecosystem of esports. MediaCulture & Society.
JosephD. J. (2018). The discourse of digital dispossession: Paid modifications and community crisis on Steam. Games and Culture13(7)690-707.
Kardefelt-Winther, D. (2014).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internet addiction research: Towards a model of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351-354.
KücklichJ. (2005). Precarious labor: Modder and the digital game industry. Fibreculture, 5(1)1-5.
Kurek, A.Jose, P. E.& Stuart, J. (2017). Discovering unique profiles of adolesce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use: Are ICT use pre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identity and behaviour development?.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1(4).
Lai, G.& Fung, K. Y. (2020). From online strangers to offline friend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video game players in Hong Kong. MediaCulture & Society42(4)483-501.
Liu, D.Baumeister, R. F.Yang, C.& Hu, B. (2019). Digital communication media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4(5)259-273.
Liu, T.& LaiZ. (2020). From non-player characters to othered participants: Chinese women’s gaming experience in the “free” digital market.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19.
MarteyR. M.Shaw, A.Stromer-GalleyJ.Kenski, K.& StrzalkowskT. (2017a). Testing the power of game lessons: the effects of art and narrative on reducing cognitive bia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81635-1660.
MarteyR. M.Stromer-GalleyJ.Shaw, A.McKernan, B.Saulnier, T.MclarenE.Rhodes, M.FolkestadJ.Taylor, S. M.Kenski, K.CleggB.& Strzalkowski, T. (2017b). Balancing play and formal training in the design of serious games. Games and Culture12(3)269-291.
Meeus, A.EggermontS.& Beullens, K. (2020). Digital distraction or stimulated self-disclosure: Preadolescents’ mobile device use in the family contex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5(5)328-345.
McKernanB. (2021). Digital texts and moral questions about immigration: Papers, Please and the capacity for a video game to stimulate sociopolitical discussion. Games and Culture16(4)383-406.
Mikko M. (2021). Crooked views and relaxed rules: How teenage boys experience parents’ handling of digital gam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9(1)62-72.
NguyenM. H.Gruber, J.Marler, W.Hunsaker, A.FuchsJ.& HargittaiE. (2021). Staying connected while physically apart: Digital communication when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are limited. New Media & Society.
Ortiz, S. M. (2019). The meanings of racist and sexist trash talk for men of color: A cultural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studying gaming culture. New Media & Society21(4)879-894.
OzimekA. M. (2019). Outsourcing digital game production: The case of polish testers. Television & New Media20(8)824-835.
PelursonG. (2021). Cathartic corridors: Queering linearity in Final Fantasy XIII. Continuum35(1)43-57.
Piittinen, S. (2018). Morality in Let’s Play narrations: Moral evaluations of Gothic monsters in gameplay videos of Fallout 3. New Media & Society20(12)4671-4688.
Radchuk, O.KerbeW.& SchmidtM. (2017). Homo Politicus meets Homo Luden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erious life science gam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6(5)531-546.
RhodesR. E.KopeckyJ.BosN.McKneely, J.GertnerA.Zaromb, F.PerroneA.& Spitaletta, J. (2017). Teaching decision making with serious games: An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ames and Culture12(3)233-251.
RothmundT.Klimmt, C.& Gollwitzer, M. (2018). Low temporal stability of excessive video game use in Germ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 30(2)53-65.
RubergB. (2019). The precarious labor of queer Indie game-making: Who benefits from making video games “better”?. Television & New Media20(8)778-788.
Schrier, K. (2019). Designing games for mor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building. Games and Culture14(4)306-343.
StephensonW. (1964).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Tai, Z.& Hu, F. (2018). Play between love and labor: The practice of gold farming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20(7)2370-2390.
Vandenbosch, L.DriesmansK.TrekelsJ.& EggermontS. (2017). Sexualized video game avatars and self-objectification in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gender congruency and activation frequency. Media Psychology, 20(2)221-239.
Vella, K.JohnsonD.ChengV. W. S.DavenportT.Mitchell, J.Klarkowski, M.& Phillips, C. (2019). A sense of belonging: Pokémon GO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Games and Culture14(6)583-603.
Verheijen, G. P.Burk, W. J.Stoltz, S. E. M. J.van den Berg, Y. H. M.& CillessenA. H. N. (2020).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aspects of video game play behavior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 32(1)27-39.
Vilasís-Pamos, J.& PiresF. (2021). How do teens define what it means to be a gamer? Mapping teens’ video game practices and cultural imaginaries from a gender and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17.
WangB.Taylor, L.& SunQ. (2018). Families that pl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Investigating family bonding through video games. New Media & Society20(11)4074-4094.
WhaleyB. (2018). Who will play Terebi Gēmu when no Japanese children remain?: Distanced engagement in Atlus’ Catherine. Games and Culture13(1)92-114.
Witkowski, E.& ManningJ. (2019). Player power: Networked careers in esports and high-performance game livestreaming practices.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25(5-6)953-969.
WoodcockJ.& JohnsonM. R. (2019). The affective labor and performance of live streaming on Twitch. tv. Television & New Media20(8)813-823.
孙晓蓓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李泳志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李欣人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