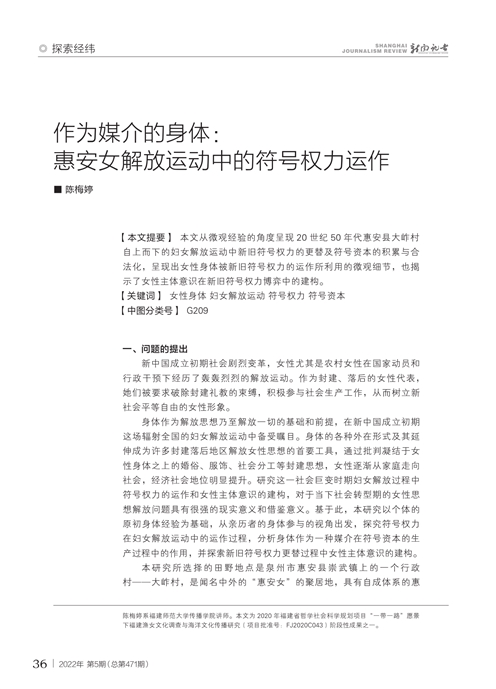作为媒介的身体:惠安女解放运动中的符号权力运作
■陈梅婷
【本文提要】本文从微观经验的角度呈现20世纪50年代惠安县大岞村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新旧符号权力的更替及符号资本的积累与合法化,呈现出女性身体被新旧符号权力的运作所利用的微观细节,也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在新旧符号权力博弈中的建构。
【关键词】女性身体 妇女解放运动 符号权力 符号资本
【中图分类号】G209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剧烈变革,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作为封建、落后的女性代表,她们被要求破除封建礼教的束缚,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工作,从而树立新社会平等自由的女性形象。
身体作为解放思想乃至解放一切的基础和前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场辐射全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备受瞩目。身体的各种外在形式及其延伸成为许多封建落后地区解放女性思想的首要工具,通过批判凝结于女性身体之上的婚俗、服饰、社会分工等封建思想,女性逐渐从家庭走向社会,经济社会地位明显提升。研究这一社会巨变时期妇女解放过程中符号权力的运作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对于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女性思想解放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以个体的原初身体经验为基础,从亲历者的身体参与的视角出发,探究符号权力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运作过程,分析身体作为一种媒介在符号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并探索新旧符号权力更替过程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
本研究所选择的田野地点是泉州市惠安县崇武镇上的一个行政村——大岞村,是闻名中外的“惠安女”的聚居地,具有自成体系的惠安女文化传统。因其传统文化中特殊的长住娘家婚俗、惠安女服饰、“男渔女耕”的性别化分工等体现出明显的禁锢女性的封建落后思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典型对象,因此选择该村进行社会巨变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中符号权力运作和女性主体建构的研究具有典型代表性。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对大岞村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的田野调查,以及在2021年4月补充的对10位村民的跟踪访谈。本研究采取了“滚雪球抽样”的方法,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在样本的选择上尽可能包括各性别、各行业、各年龄段的村民。总共访谈大岞村村民67人,其中男性34人,女性33人,男性代码为M,女性代码为F。
二、文献综述
(一)身体与媒介
彼得斯《交流的无奈》所对比的对话与撒播两种交流观念中,身体就是区分彼此的关键元素之一。苏格拉底代表的“对话”交流观念思考的是人与人、灵魂与灵魂、身体与身体的交流,“交流必须是心灵与心灵的对接,要在有形体的人之间进行,在亲近的互动中进行,交流必须要适合参与交流的每个人”(彼得斯,2003:41)。这意味着身体在场是交流的前提条件。在传播仪式观视角下,媒介不仅限于大众媒介,一切信息的承载物都可称之为媒介,而身体作为一种媒介远远早于任何一种媒介。麦克卢汉的经典媒介观“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就是围绕身体的延伸及其影响展开的。基特勒认为麦克卢汉将媒介视为“延伸”的观点仍然将人类身体置于一切事物的核心,麦氏试图从身体的视角出发考察技术,而非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考察身体(盖恩,比尔,2015:108)。希林(2011:1)也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呈现出一种双重双向性,即身体是媒介技术的源泉,也是它们的定位场所。总而言之,身体是媒介之母,麦克卢汉从身体的视角出发考察技术,就是为了让在技术中迷茫的人类回归身体并获得救赎。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的身体为交流、交往、创造而存在,因交流、交往、创造而进化(赵建国,2013)。同时,文化与信息又负载于身体这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载体上。
身体问题在社会学中的研究显得更为成熟。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术界涌现了一股身体研究的高潮,身体社会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最初身体是作为自然的而不是社会的现象被看待,因此早期关注社会秩序的社会学家并不把身体视为研究对象。希林介绍了作为“自然物的身体”,自18世纪以后,身体的自然主义观点对人们如何看待身体、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将身体视为自我和社会的上层建筑所依赖的前社会生物学基础(Shilling, 1993:41)。如性别不平等就是女性身体“虚弱”和“不稳定”的直接结果。对身体的关注要归功于人类学家的努力,道格拉斯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身体”的概念,即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麻国庆,2010)。Mauss(1973)认为身体是被文化所塑造的,通过“身体的技术”,个体经历了文化社会化的进程。在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下,社会学领域将身体作为文化对象来对待,而福柯有关身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奠定了身体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福柯(2012:27)认为,“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而且只有被驯服的生产力才是有用的力量,被驯服后的“政治身体”是作为中介物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个体的身体如何受到社会政治力量的牵制,社会政治力量又如何通过身体的规训达到监控的目的。目前一种折衷的且普遍被认可的观点认为身体是自然与文化之间对话的产物,身体既存在物质性的现实,又是具备文化属性的研究对象。
特纳归纳了身体研究的三种传统,第一种传统认为身体是一套社会实践,把身体看做是通过社会实践得以实现和成为现实的潜能。第二种传统把身体概念化为一个符号系统,把身体视为社会意义或社会象征符号的载体或承担者。人类学家比社会学家更加关注身体问题,特别是关注身体在仪式过程中传达文化与意义的作用。第三种传统将身体理解为代表和表现权力关系的符号系统,尤其体现在性别与身体的研究中。无论哪一种身体研究的传统,都隐含着身体作为媒介、作为意义的载体、作为符号系统的意味,身体在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身体既是一个符号象征的系统,也是一个权力的载体。在高度现代化的环境中,身体越来越倾向于成为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的核心(Shilling, 1993:1),但身体并不等同于肉体,奥尼尔(1999:3)区分了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他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并正在加以思考的交往身体就是我们的世界、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的总的媒介。这种思想源自梅洛庞蒂(1962:146),他在《知觉现象学》中写道:“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有时,它被局限于保存所必须的行动中,因而它便在我们周遭预设了一个生物学的世界;而另外一些时候,在阐明这些重要行动并从其表层意义突进到其比喻意义的过程中,身体通过这些行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核心。”这意味着身体不仅仅是生理的身体,更是交往的身体,并通过交往建构意义。
(二)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
布迪厄(1999:170)早就对符号权力作过明确的界定,他指出符号权力通过言说建构已有的秩序,使得人们看与信,强化或转换对世界的看法,并加强或转换对世界的行为乃至世界本身,几乎是一种魔幻的权力,人们通过它获得的与通过力量(无论身体的还是经济的)获得的一样多,而这些都是通过转换的特定功能完成的。因而,符号权力只有在被认识到,也就是说其人为性被误识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作用。根据布迪厄及符号权力相关研究者的观点,不难发现符号权力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软性暴力,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其隐蔽性正是来源于其被合法化、被误识的过程。正如华康德(1995)所言:“所谓符号权力,即意义和意蕴系统所具有的,通过将压迫和剥削关系掩藏在自然本性、善良仁慈和贤能统治的外衣下,掩盖并因此强化这些压迫与剥削关系的能力。”符号权力的隐蔽性使其能够发挥比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更有效的作用,但隐蔽性的获得必须以支配关系的合法化为前提,而合法化从根本上又是通过误识实现的。所谓误识,是指社会行动者在符号权力的支配下,把符合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本质上是任意的某种真理误以为是普遍真理(朱国华,2004:109)。将误识中所蕴含的支配秩序内化进个体的心智结构,从而实现被支配者的驯化。由于文化的隐蔽性更强,符号权力常常借用文化的外衣实现任意性的误识。文化的区分功能并不被人们所察觉,文化在日常经验和常识的遮蔽下,悄然无声地配合着、巩固着权力支配结构(张意,2003)。那么符号权力是如何被误识的?如果说符号资本是产生“误识”的客观现实基础,那么“惯习”则是人们对符号权力维持这种“误识”的主观心理基础(章兴鸣,2008)。
首先,符号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以符号资本的垄断性占有和持续性积累为客观现实基础的。布迪厄(1977:183)指出,符号资本是有形的“经济资本”被转换和被伪装的形式。符号资本可以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那样进行积累,根据符号资本所掩盖的功利事实,也即符号的合法化事实,所积累的符号资本越多,那么就越有可能拥有更大和更多的符号权力(罗生全,2008:86)。然而,符号资本建立在去功利化的基础上,其重要性在于其表面上对经济资本的否定,它所赢得的权力建基于道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其一旦被还原为政治或经济资本,它的基础顷刻之间便会瓦解(芮必峰,陈诺,2013)。可见,虽然符号权力本身来源于象征性的虚拟的符号资本,但后者往往来自于物质性资本的伪装、转换或变形,它将任何形式的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符号资本与物质性资本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关系,即尽管符号资本是无法摆脱物质层面的,但却又必须以对物质性资本的否定为前提,并且符号权力的增长与合法化符号资本的积累程度成正比。同时,有学者意识到情感在符号资本建构中的重要性,柯林斯(2009:86)指出互动仪式中关键的过程是参与者情感与关注点的相互连带,它们产生了共享的情绪/认知体验,充分的身体集聚、高程度的相互关注和情感共享使参与者建构集体团结感、道德感以及成员身份的符号资本。特纳也指出如果人们的积极情感被唤醒,会对符号对象给予奖励性支持,认同其符号表征的合法性,有利于符号资本的建构;反之,消极情感体验会阻碍人们对于符号表征的认同,消解符号资本建构的社会意义(高丽华,吕清远,2017)。
其次,惯习作为一种变化中的倾向系统,使符号权力更自然地在被支配者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惯习是指一种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塑造结构的结构发挥具有塑造结构能力的结构的功能(Bourdieu, 1990:53)。惯习之所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主要在于它是一种时间性结构,是历史和未来事件发生联系的中介。它脱胎于历史,包含了历史当中的各种感知、行动和生活方式并使之得以存在和延续(何少娴,尤泽顺,2017)。因此惯习无意识地将社会结构内化为被支配者的内部结构,并无限接近于被支配者的先天结构,让被支配者在主观意愿上主动维持误识。同时,惯习往往在场域中发挥作用而非独立存在,具有符号系统的独立生产与流通功能的场域深刻影响着惯习的倾向系统。更确切地说,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布迪厄,华康德,1998:133-134),其结构是由活跃的资本的特殊形式的分布结构来定义的,其原动力存在于彼此冲突的各种各样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和不对称性之中(包亚明,1997:147-153)。场域根据不同的运行法则内化不同的符号资本以形成个体的惯习,个体凭借惯习在场域中展开权力斗争,在惯习的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作用下,“误识”被嵌入被支配者的心智结构中,建构他们的社会化自我,为维持符号权力搭建主观心理基础。
综上所述,符号权力分析与“误识”、“符号资本”、“惯习”、“场域”等术语是紧密相关的。物质性资本伪装、转换或变形后转化为象征性的符号资本,同时情感因素在符号资本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为“误识”的产生提供客观现实基础。在场域中发挥作用的惯习则在个体主观的心智结构上施展倾向性影响,而符号权力本质上是通过合法化了的误识实现的,它在符号资本、惯习、场域的综合作用下生产与再生产。
三、从身体开始: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惠东地区妇女包“巾仔”、长住娘家、早婚、包办婚姻等陋习在解放性话语中被树立为“封建”、“落后”、“迷信”、“压迫”的典型代表,是亟待改革的对象。1950年代到1960年代政府通过镇反、土改、民主改革等运动和贯彻宣传《婚姻法》,从惠安女的日常身体实践层面介入,开始了“破旧立新”的改革运动,包括摘掉“巾仔”、“新娘子回夫家”、“妇女下海捕鱼”、建设“惠女水库”等一系列涉及身体改革的运动。
(一)摘掉“巾仔”
惠安县一份1952年的资料中记载:“沿海地方妇女头上都戴着大帽子。解放前这里的已婚女性在结婚、外出做客或回夫家时都要梳“大髻”:“插上各种银制的花:一个髻模,一支扁白,头尾档各1支,上下股二式各4支,蟳匾1支,福字2支,梅花带链2支,银插子1支带3条链子,还有各种颜色和式样的绒花。把头插得满满的,同时还用一条5尺长的黑丝巾从髻边向后垂下,至衣沿等长,巾的两端用3寸宽的黑帛接着,并让缝纫匠用绿丝绒缝各种花纹图案”(陈国强,石亦龙,1990:199-200)。在政府的强制措施推动下大岞村的惠安女摘掉了“巾仔”,但她们的头部装饰并未就此消失,另一种简化的头饰——头巾——替代了“巾仔”。在1990年代以前,这种头巾一般选白底绿花、绿底白花或蓝底白花的棉布或的确良布,以二尺裁成正方形。佩戴头巾可以遮住脸颊的大部分面积,因此头巾也继承了“巾仔”的部分符号意义,如表达女性羞涩的姿态以及象征与丈夫保持距离,成为惠安女遮掩面容的新的符号设备。
一个午后,已经87岁的退休妇女干部F23正与三个老姐妹一起在大岞村老人协会打四色牌,对她这个年纪的惠安女来说,经历了解放以来在当地女性身上发生的所有变革。在她的叙述中,摘掉“巾仔”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女性不愿意摘掉这个又重又繁琐的“巾仔”的关键在于其特殊的符号意义。解放前,当地女性在婚后就要梳起“巾仔”,特别是一年中寥寥可数的几次回夫家的时候。因为“巾仔”装扮起来极其麻烦,因此戴着“巾仔”的已婚女性去夫家时根本不可能到床上睡觉以免弄乱“巾仔”,而需站在床边直至过零点后返回娘家,有的甚至就这样站了十多年。一旦被旁人发现你的“巾仔”已乱,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在当时,与丈夫的亲近行为仿佛是很糟糕很丢脸的事情。F23很是唏嘘地说:“以前结婚有那个头发(巾仔),不可以跟老公睡觉,头发不能乱,很痛苦”(访谈材料:20180329)。因此,这套“巾仔”就是当地女性证明自身清白的一套符号设备,一旦要被摘除,她们也就失去了自证清白的符号。惠东的妇女乃至全县的妇女,贞操感十分重,她们受一种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影响:①
旧社会的东西都要改掉,改的时候很痛苦的,以前有这种习惯(戴巾仔)。解放以后两三年就改掉了,按照事实来说,是改了以后比较好。(F24,80岁,访谈材料:20180329)
那个时候我们有看到那些干部拿着剪刀,本来我们这里的妇女有戴着像帽子一样的头饰,还有把她们女孩子穿的那个贴背,就把这些都剪掉,挨家挨户去剪这些。那个时候这个叫做破除封建迷信,妇女要解放,不能够再戴这个巾仔了。(M7,73岁,访谈材料:20180208)
从当地女性与男性亲历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亲历者而言摘掉“巾仔”的过程是痛苦的,她们中的有些人通过逃跑或隐藏来躲避这种改革。政府对当地女性的解放运动从“头”开始,也正是因为了解“巾仔”在当地女性心中的符号意义,摘掉“巾仔”是解放女性的第一步。但摘掉“巾仔”的过程显然并不轻松,因为实际上要改变的是“巾仔”所透露出的女性身体信息,掏空“巾仔”原本附着的“与丈夫保持距离”的意味,而代之以摘掉“巾仔”后与“封建”、“落后”、“压迫”相对的“开放”、“进步”、“解放”的含义,“巾仔”虽然变成了空洞的形式,但其代表的符号权力却并不会突然消失。符号意义的转变是妥协的、逐步的,在意义未被掏空以致巨变之前,承载意义的形式可以被替换。“巾仔”施加于身体的符号权力被隐匿起来,其原有的符号权力被惠安女用来替代“巾仔”的“头巾”继承。
(二)“新娘子回夫家”
婚姻是定义一个群体进化状态的关键特征(Charles, 1995:43-44),无怪乎大岞村的长住娘家的婚俗实践被当作落后典型。解放性话语中将“新娘子回夫家”界定为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挖掉封建根子的革命。当地几个退休的老干部记得1960年代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让新娘子回夫家。比如让新娘子去清理老村前面那条肮脏的西房溪,给她们安排事情做就可以让她们在夫家多住一两个晚上;让新娘子去村里的养殖场、米粉厂工作,从而让她们留宿在夫家;让新娘子参加学习班,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让新娘子来开妇代会,让妇女干部给她们做思想工作。但有些女性依然会躲起来,让干部叫不到人。相似的情形在与大岞村风俗近似的小岞镇也有发生,小岞分团前内工作队1965年的报告《高举反封建旗帜,改变已婚妇女常住娘家的封建陋习》中描述了新媳妇一开始来参加训练班时的装扮:“一开始来的新媳妇还装着‘新人’模样,人人穿上花边新衣服,个个头戴斗笠,头低着只爱织毛衣、织渔网做自己的副业。” ②这套装扮鲜明地表达了她们不愿回夫家的立场,后来工作队先做通当地女性姐妹头的思想工作,再通过一带一、一带多的方式让她们转变了想法,典型的标志便是她们脱下斗笠,不再穿着新衣回到夫家。但可惜成效是短暂的,在大岞村也有类似的新媳妇学习班,学习班结束之后她们又回娘家去了。
73岁的大岞村退休老干部M7曾经当过叫新娘子回夫家的“红娘”,那时村里的每个干部都被分配到相应的邻村去叫人,他是带队到离大岞村有七八公里远的前桉村,喊前桉村里嫁到大岞村的新媳妇回夫家,让她们不要再住在娘家。尽管这个村在当时是红旗单位、先进单位,妇女的思想相对其他村更开放一些,但还是有很多妇女不愿意过来,她们躲在家中,村干部也束手无策。当然也有许多愿意回来夫家的,他将这些妇女描述为“觉悟比较高的”、“比较进步的”(访谈资料:20180203)。以她们的现身说法和影响力带动其他“比较落后的”一同改掉长住娘家的风俗。尽管收到了短期的效果,但“移风易俗”的活动结束后很快又故态复萌。正如弗里德曼(Friedman, 2006:69)所说,虽然在惠安东部解放性话语很快被整合进当地的日常交谈中,但它对实际行为和认同方式的影响并不明显:
叫都叫人家,然后自己跑回去(娘家)。讲老实话,我带头是带头,我过去嘛,11点偷偷跑过来(娘家)。人家不知道,早一点跑来人家会知道,等人家睡觉我就偷跑过来。我去丈夫家给他挑水什么东西,给他干好过来,我偷偷跑过来,人家不知道。人家知道(的话),技术员不给他(丈夫)出海。早上的时候邻居看见我说,你怎么在娘家,没有到他家?我说有啊,我刚刚回来。(F18,77岁,访谈资料:20180326)
那个时候她有住一段时间,当时有个工作给她做。当时我们大队建的那个米粉厂,她在那个米粉厂那里干活。后来她走了,她要生孩子了才回来住。(M22,76岁,访谈资料:20180322)
尽管政府“移风易俗”的运动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作用并不彻底,但惠东地区的村民学会了将长住娘家的婚俗描绘为封建的、压迫的存在。长住娘家婚俗在女性身体互动中的形式虽然没有变化,但意义已经开始松动。解放性话语所创造的强大的意义系统使得大岞村民重新理解和体验他们的婚姻实践。在这场“新娘子回夫家”的运动中,身体是当地女性表达自身思想的核心媒介,她们或是躲避来叫她们回夫家的干部,或是假意回夫家后又偷偷返回娘家,或是在妇女干部的带动下脱下斗笠换下新衣但之后又故态复萌,她们用身体的微观实践建构起海洋渔村的女性对长住娘家婚俗的坚持,对传统社会行为准则的遵从。但她们所表现出的抗争意愿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反而透露出她们对社会中女性内在理想规范的屈从。显然,长住娘家的婚俗已经出现向妇女解放运动妥协的迹象,大岞村的惠安女开始换下新衣,不再装着“新人”模样,身体符号透露出她们思想松动的迹象,但传统惠安女服饰和长住娘家婚俗施加于身体的符号权力依然是一股顽固的软性的力量,解放性话语的符号权力还需要积累符号资本。
(三)“妇女下海捕鱼”
大岞村曾尝试过组织妇女参加海上的渔业生产,据记载,1956年派了10个妇女随船出海参加辅助劳动,1959年派了20个,结果都因体力不适应,会晕船,没有成功(周立方,1992:89)。1960年—1963年,又组织了一条妇女船,但最后也不了了之。在解放前的封建时代当地就有“妇女不上三甲坛,下船去不是捕不到鱼,就是会翻船出事故”的思想,这样的旧思想也成为政府“移风易俗”运动的一部分。在惠安公社岞山支部1960年发布的《巾帼多面手捕鱼女英雄——惠安大岞女捕鱼模范张结花妇女船的先进事迹》中,重点描述了4位青年妇女以柔弱的身躯,战胜了学习摇橹等捕鱼技术的艰难,战胜了深海的8级大风,不顾身体的疼痛,不顾晕船呕吐,捕鱼产量常常超过男渔民的故事。③4人一起被称为“青年妇女中学习文化的尖兵”。
妇女下海捕鱼将勇于讨海的女性与“进步”、“解放”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塑造捕鱼“女英雄”的形象。F18在21岁的时候下海跟着大船去舟山捕鱼,主要是在小舢板上摇橹,当时她已经结婚了,但还没有生育小孩,因此还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的自主权,并不需要经过丈夫的同意。她年轻的时候胆子比较大,当时的书记让她下海她便去了,但后来她怀孕生子便没有再去讨海了(访谈资料:20180326)。据84岁的F31回忆,那些下海捕鱼的妇女比较有男人的性格,不软弱。她自己并没有下海,对她而言,下海捕鱼的妇女是少数也是异数(访谈资料:20180405)。妇女下海捕鱼的运动高潮也很快过去了,一方面是男性劳动力足够充足,另一方面也与女性生理有关,男女平等的理想追求与现实情况产生了矛盾。当时大船上男性渔民居多,因此还特地为这些下海捕鱼的女性专门隔了一间厕所和一间卧室,但大家还是觉得很不方便:
破四旧强调女人要去游泳,什么都要像男的,那时是一个高潮,一个运动。你不跟上不行,你不跟上人家会说你落后,人家就不和你在一起。(M19,72岁,访谈资料:20180319)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里妇女解放,妇女也有去下海捕鱼。女的也做船老大。妇女船有两条,专门是女人去上面捕鱼,好厉害,也有去浙江捕鱼。那个船老大现在也80多岁了。技术都是靠男人教她的。(M26,62岁,访谈资料:20180117)
在当时的大岞社区的村民眼中,妇女下海捕鱼是与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特殊事件,并没有整合进他们的日常观念中。在这里,大岞村民对女性身体的刻板印象及日常观念与解放性话语试图塑造的符号权力产生矛盾,无法使他们产生“捕鱼女英雄”的符号共识,因此在无法达成共识情况下,解放性话语并没有对妇女解放运动尤其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起正向推动作用。
(四)建设“惠女水库”
早在1950年代末,政府就将参与劳动与性别解放联系在一起,除了鼓励妇女下海捕鱼,还组织惠安女建设“惠女水库”(即乌潭水库),据惠安县档案馆1964年的资料《惠安妇女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记惠女水库的建设》中记载,参加水库建设的惠安妇女达3.5万多人,占全场员工4.1万多人的85%以上。参加过惠女水库建设的F18和F23都印象深刻地回忆起当时出工干活的苦,而这种吃苦精神正是政府重塑惠安女劳动意义的切入点。通过强调惠安女建设“惠女水库”过程中不畏艰险、不畏苦难、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质,塑造惠安女“劳动能手”的形象,提升惠安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惠女水库建设中所宣扬的“七女斩三龙”、“八母亲高空抬巨石”、“老买姑三战惠渠”等典型事例,以及3000多名女功臣、女标兵、女先进生产者和红色巧姐妹,旨在通过描绘惠安女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展现她们在艰难任务面前或抗洪抢险中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的精神,而惠安女的艰苦劳动便是她们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的标志。这种劳动力意义的转化在1980年代末大岞避风港建设中被进一步强化:
当时都是靠人力,几乎没有什么机械,几乎都是女的去。男的都去捕鱼了,都不在家。那个时候在那边女的都会开拖拉机,什么都会。(F32,55岁,访谈资料:20180406)
我们这边惠安女比较贤惠。这种大石头,8个人就一起抬起来了,渔港都是她们建起来的。有20多个人是男的,他们是专业管理的,体力(活)都是女的干的。(M26,62岁,访谈资料:20180117)
1987年,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去参观大岞避风港的工程时,只见上千个女工在劳动,没有一个男工,而监工的却都是男的(乔健,1992:263)。声势浩大的大岞避风港的共建场景,凸显了当地女性勤劳能干的身体、吃苦耐劳的精神,但这种意义被重塑的劳动力却依然被笼罩在男性不在场的“阴影”下,勤劳、贤惠、能干的惠安女的从属地位并未彻底改变。段学敏(2013)通过对惠女水库工程中女性及“惠女精神”的重新审视,也发现传统解读视角遮蔽了惠安女性在惠女水库工程实践活动中遭受的性别的不平等对待,男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从当地人的叙述中意外地发现,大岞村的惠安女将这种不平等对待转化为“贤惠的惠安女”的自我认知,代表“劳动能手”的女性身体所生产的符号权力利用了大岞村民对女性身体的刻板印象及日常观念,促使女性达成“贤惠的惠安女”的符号共识和误识,并促进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
四、身体作为媒介:惠安女解放运动中的符号权力运作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国家的解放性话语建构为“封建”、“落后”、“迷信”、“压迫”典型代表的惠安女传统文化拥有垄断性占有和持续性积累的符号资本。受包含复杂历史性权力关系网的惯习的影响,惠安女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各种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内化为传统文化场域中的行动者的心智结构,使惠安女传统文化所隐含的符号权力无意识地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发挥支配作用。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需要为解放性话语积累足够的符号资本以对抗传统文化的符号权力。大岞村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质上完成了对所有行动者尤其是被支配者的认知系统再造的过程。即删除旧误识,改变旧惯习,确立新的意义与共识,重塑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章兴鸣,2008)。具体表现为符号体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原先被视为异端的符号体系如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劳动力价值对等,经过惠安女摘掉“巾仔”、“新娘子回夫家”、“妇女下海捕鱼”、建设“惠女水库”等符号斗争活动后上升为被普遍认同的新“误识”,而曾经被视为正统的符号体系如女性身体贡献小、价值低等旧“误识”则被塑造为异端。符号体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符号权力运作的直接结果,在此过程中,支撑新“误识”的符号资本如何获得?身体发挥怎样的作用?符号权力的合法化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
(一)为新“误识”积累物质性资本
身体被看成是一个符号象征系统、话语途径,作为一种表意资源和言说方式,身体与语言构成同质的符号网络(唐青叶,2015)。大岞村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废除遮蔽面部的“巾仔”开始,政府通过禁止佩戴、没收“巾仔”等强制手段从物质性层面否定了身体佩戴“巾仔”的合法性,但受惯习的影响,大岞村民依然遵从传统文化符号权力的支配,他们利用简化的“头巾”继承“巾仔”的符号资本。另一方面,政府组织“新娘子”参加集体劳动、社会工作等来创造她们在夫家生活的便利条件,这让惠安女获得了回到夫家敢吃、敢睡觉、敢工作的物质实惠。同时学习会、妇代会等集会中由仪式互动所产生的集体兴奋的情感和关注能够促进惠安女对新身份(即解放性话语中的平等女性)的认同,从而为新获得的物质性资本创造转换和变形的条件。通过集体活动为解放性话语创造一个独立的场域以积累新的符号资本,旨在从工作和思想领域削弱甚至消除传统文化的符号权力。
显然,符号资本的消耗与积累都不能摆脱物质性资本,摘掉“巾仔”、“新娘子回夫家”等改革活动在否定旧“误识”的物质性资本的同时也为新“误识”积累新的物质性资本,身体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首先,身体是否定旧“误识”的物质性资本的关键载体。“巾仔”作为惠安女自证清白和凸显贞操感的符号设备,是通过对女性面部的遮挡和身体的控制发挥作用的,“长住娘家”的婚俗也是通过限制身体的自由处置权实现的,否定惠安女身体佩戴“巾仔”和停留娘家的合法性,就直接消解了旧“误识”的物质性基础。其次,身体是为新“误识”积累物质性资本的起点。解放性话语让惠安女在集体活动中获取敢吃、敢睡觉、敢工作的切身利益,体验与其他女性交流、共同关注及产生共鸣的正向情感,从而将身体上的实质性满足转化为物质性资本,并为物质性资本伪装、转换或变形为符号资本创造条件。因此,身体作为一种物质层次上的媒介,为新“误识”物质性资本的积累提供基础性力量。
(二)为新“误识”生产符号资本
大岞村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先从挖空旧“误识”的符号资本入手,旧“误识”的核心在于为男性与女性预设了价值等级,即抬高男性劳动力价值并贬低女性劳动力价值,因此政府组织“妇女下海捕鱼”活动通过女性弱小身体与其强大捕鱼能力之间的鲜明对比,将女性打造为捕鱼的女英雄、巾帼多面手,将男性的劳动能力与女性的劳动能力等同起来,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试图改变旧“误识”中“女子无用”的思想。可见,新“误识”的符号资本就是从物质性资本即女性身体的捕鱼能力变形而来,并且否定了旧“误识”的物质性资本,即男性劳动力价值远优于女性。但在女性身体柔弱、男主外女主内等根深蒂固的文化惯习影响下,“捕鱼女英雄”的符号共识的建构意图未能一蹴而就,说明漠视被支配者传统文化场域中固有的惯习是无法生产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符号资本的。塑造惠安女“劳动能手”形象的建设“惠安水库”活动是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社会公共领域充分肯定了惠安女勤劳能干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将对物质性资本的否定体现为弱化男性身体在该活动中的作用,这样的做法使新“误识”中蕴含的社会结构接近于被支配者的被塑造结构的结构,即新“误识”巧妙地将旧“误识”中对女性身体的刻板印象及日常观念,转化成为自身服务的符号资本,同时集体劳动中所产生的积极情感也促进其合法化的过程,从而使惠安女潜移默化地接受新“误识”的支配。
(三)新“误识”与女性主体意识建构
福柯(2012:27)的权力理论让我们看到权力作用于身体的运作方式,他指出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而且权力运作的方式也不仅仅是压制,挑逗与刺激也可能成为新的控制手段。与之相对应的,被支配者在面对新生权力的各种新政时,也会选择隐匿、躲避、妥协、抵抗等处理方式,这意味着被支配者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符号权力的支配,符号权力是以参与其中的成员主动地达成共谋为先决条件的(傅敬民,2010),而被支配者的参与和共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主体意识的建构。
首先,解放性话语单方面强制建构的“摘掉巾仔”符号的进步意义并没有实现,旧“误识”的符号权力采用隐匿的运作手段,表面上服从于解放性话语,但实际上使用“头巾”作为遮掩身体的替代品来确保符号权力的继续运行。因此,一方面“头巾”所继承的符号权力极大地阻碍了妇女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妇女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打下基础。其次,传统惠安女服饰和长住娘家婚俗施加于身体的符号权力采用假意妥协的手段,将符号权力转向后台运行,因此从表面上看新“误识”的符号权力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短暂的促进作用。再次,妇女下海捕鱼的身体行动并没有培养出女性生活在社会中的感觉,缺乏符号共识的情况下,新“误识”的符号权力对妇女解放运动不起作用。最后,符号权力的实现是基于共识或“误识”的生成,新“误识”的符号权力利用了鼓励女性劳动的运作方式,促使女性达成“贤惠的惠安女”的符号共识或“误识”,因此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在此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大多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直到她们被国家鼓励而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并在自身劳动能力被普遍认可的共识和“误识”的共同作用下走向了主体意识的觉醒。“贤惠的惠安女”内化为她们的自我认同,这样的自我认同促使她们在解放性话语的符号权力生成过程中主动参与和共谋,并且促进惠安女基于对女性形象、女性劳动力价值的反思。这股由内而生的觉醒力量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催动下,才逐步形成开放、自由、进步的女性主体意识。
五、结语
本文从微观经验的角度呈现出20世纪50年代大岞村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新旧符号权力的更替及符号资本的积累与合法化,呈现出女性身体被新旧符号权力的运作所利用的微观细节,也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在新旧符号权力博弈中的建构。符号资本的消耗与积累都不能摆脱物质性资本,将物质性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需要顺应不同场域的运行法则。身体作为一种物质层次和符号层次上的媒介,为新“误识”物质性资本的积累提供基础性力量,也为新“误识”符号资本的生产创造关键性力量。解放性话语已经被整合进当地村民的日常交谈话语中,但只有当新“误识”的符号权力利用了鼓励女性劳动的运作方式,促使女性达成“贤惠的惠安女”的符号共识和误识时,女性才开始走向主体意识的觉醒。
总而言之,新“误识”的符号权力作用于女性身体,其符号权力的运作方式从显性的控制、干预发展为隐性的鼓励、刺激,后者的方式更为缓和但效果却更显著,促使符号共识的建构从失败逐渐走向成功。在显性的控制、干预阶段,虽然解放性话语并没有彻底改变大岞惠安女关于婚俗与服饰的具身化实践,但已经被整合进当地村民的日常话语中,大岞人学会了将不落夫家的婚俗和传统惠女服饰描绘为封建的、压迫的存在。至此,围绕身体生成的物质性层面上的符号共识已经形成,符号权力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而在隐性的鼓励、刺激阶段,鼓励女性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并认可女性劳动力价值使深度的符号层面上的符号共识得以建立,从而促进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建构。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解放过程中符号权力的运作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有利于反思符号权力与女性主体意识建构之间的微妙关系,丰富身体政治学的现实实践,也为当下社会转型期女性性别角色的转变与政治、经济、社会传统文化等多方力量的互动提供历史借鉴。■
注释:
①摘自福建省惠安县档案馆。陈清发,林瑞峰(1991)。从惠安地方历史探索惠东地区长住娘家陋习的原因。
②摘自福建省惠安县档案馆(1965)。高举反封建旗帜,改变已婚妇女常住娘家的封建陋习。
③摘自福建省惠安县档案馆(1960)。巾帼多面手 捕鱼女英雄——惠安大岞女捕鱼模范张结花妇女船的先进事迹。
参考文献:
包亚明主编(199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彼得斯(2003)。《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布迪厄(1999)。论符号权力。引自《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贺照田主编)。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陈国强、石亦龙主编(1990)。《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段学敏(2013)。《惠女水库工程的女性主义批判》。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呼和浩特。
傅敬民(2010)。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评价。《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04-117。
高丽华,吕清远(2017)。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网络媒体投身社会公益的祛魅研究。《新闻界》,(7),58-62。
何少娴,尤泽顺(2017)。建构、场域及符号权力:布尔迪厄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东南学术》,(6),226-232。
华康德(1995)。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对布丢《国家精英》的讨论。《国外社会学》,(4),28-37。
克里斯·希林(2011)。《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兰德尔·柯林斯(2009)。《互动仪式链》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生全(2008)。《符号权力支配下的课程文化资本运作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重庆。
麻国庆(2010)。身体的多元表达:身体人类学的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43-48。
米歇尔·福柯(2012)。《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2015)。《新媒介:关键概念》(刘君,周竞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乔健(1992)。惠东地区长住娘家婚俗的解释与再解释。引自《惠东人研究》(乔健,陈国强,周立方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芮必峰,陈诺(2013)。“符号权力”的消解与重建——央视3·15晚会“大概8点20发”微博事件的分析与思考。《新闻记者》,(5),33-36。
唐青叶(2015)。身体作为边缘群体的一种言说方式和身份建构路径。《符号与传媒》,(10),53-64。
约翰·奥尼尔(1999)。《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章兴鸣(2008)。符号生产与社会秩序再生产——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的政治传播意蕴。《湖北社会科学》,(9),50-52。
张意(2003)。符号权力和抵抗政治——布迪厄的文化理论。《国外理论动态》,(3),30-35。
赵建国(2013)。传播学视野下人的身体。《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2),11-16。
周立方(1992)。大岞男女劳动分工及妇女的地位。引自《惠东人研究》(乔健,陈国强,周立方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朱国华(2004)。《权力的文化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Bourdieu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rles, F (1995). “The Naxi and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pp. 43-44 in HarrellS.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riedmanS (2006). Marrigethe market, and State Power in Southeastern China. 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uss, M (1973). Techniques of the body. Economy and Society1:70-88.
Merleau-Ponty, M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ShillingC (199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陈梅婷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2020年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愿景下福建渔女文化调查与海洋文化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FJ2020C043)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