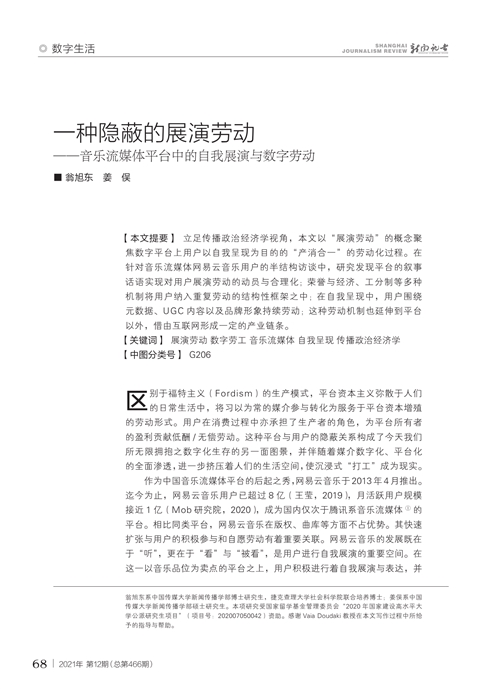一种隐蔽的展演劳动
——音乐流媒体平台中的自我展演与数字劳动
■翁旭东 姜俣
【本文提要】立足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本文以“展演劳动”的概念聚焦数字平台上用户以自我呈现为目的的“产消合一”的劳动化过程。在针对音乐流媒体网易云音乐用户的半结构访谈中,研究发现平台的叙事话语实现对用户展演劳动的动员与合理化;荣誉与经济、工分制等多种机制将用户纳入重复劳动的结构性框架之中;在自我呈现中,用户围绕元数据、UGC内容以及品牌形象持续劳动;这种劳动机制也延伸到平台以外,借由互联网形成一定的产业链条。
【关键词】展演劳动 数字劳工 音乐流媒体 自我呈现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206
区别于福特主义(Fordism)的生产模式,平台资本主义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将习以为常的媒介参与转化为服务于平台资本增殖的劳动形式。用户在消费过程中亦承担了生产者的角色,为平台所有者的盈利贡献低酬/无偿劳动。这种平台与用户的隐蔽关系构成了今天我们所无限拥抱之数字化生存的另一面图景,并伴随着媒介数字化、平台化的全面渗透,进一步挤压着人们的生活空间,使沉浸式“打工”成为现实。
作为中国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后起之秀,网易云音乐于2013年4月推出。迄今为止,网易云音乐用户已超过8亿(王莹,2019),月活跃用户规模接近1亿(Mob研究院,2020),成为国内仅次于腾讯系音乐流媒体①的平台。相比同类平台,网易云音乐在版权、曲库等方面不占优势。其快速扩张与用户的积极参与和自愿劳动有着重要关联。网易云音乐的发展既在于“听”,更在于“看”与“被看”,是用户进行自我展演的重要空间。在这一以音乐品位为卖点的平台之上,用户积极进行着自我展演与表达,并通过这一方式源源不断地为平台创造价值。
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运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网易云音乐平台进行实证考察,挖掘和理解用户在以自我呈现为主要内容的媒介参与中的劳动及其生产关系。在理论创新方面,文本试图以“展演劳动”(displaybour)的概念探索数字平台中“工作”与“生活”的新边界,在网易云音乐的具体语境中提炼两者的转化过程。
一、劳动的边界:关于数字劳动的文献综述
技术乐观派将“产消合一”(prosumption)视为数字网络的一种革命性变化,并主张拥抱其在媒介赋权与传播民主化中的无限可能(Burgess & Green, 2018;Jenkins, 2012;Bruns, 2008),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批判则从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视角揭开了媒介数字化、平台化图景的另一面。数字劳动的相关研究认为,数字技术使“产消合一”的用户视自己为社会性和创意性的主体,同时也使他们成为服务于平台所有者利益增殖活动的客体(Allmer et al., 2015)。平台资本主义并不主要依靠公司员工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对个人及公众的信息资源与社交关系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实现垄断。一方面,用户通过平台可供性实现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另一方面,他们的媒介参与为平台创造新的使用与交换价值。用户的日常媒介活动成为最终服务于平台价值生产与积累的一种无偿劳动形式(Gandini, 2021)。
从较早的“受众商品论”(audience commodity)(Smythe, 1981)、“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Lazzarato, 1996),到近年的“免费劳动”(free labour)(Terranova, 2004)、“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Fuchs & Sandoval, 2014),劳工研究的发展脉络鲜明地揭示出后工业社会生产模式以及生产关系的显著变化。传统福特主义中不被视为工作形式的、体力劳动以外的智力性、情感性活动及其产品逐渐进入价值生产的领域,包括游戏、休闲、人际关系在内的大量个人生命经验被纳入资本再生产中。相关研究共同指出,劳动的边界正日渐模糊,有薪工作时间与其他用途的时间交融在资本再生产的体系之中(Comor, 2015)。这一特征的形成则很大程度源于数字版本的“甘愿制造”(manufacturing consent)。有学者指出,平台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呈现出低异化、高剥削的特征(Fisher, 2012)。一方面,自由主义话语将数字平台建构成充满娱乐快感与生活乐趣的休闲天堂,以及促进广泛连接与交流,推动自由、平权以及自我实现的乌托邦;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的可供性使用户网络实践由“只读”模式走向“读写”模式(Lessig, 2008)。数字平台使用户在媒介参与/价值生产中(认为)获得更多的决定权和控制力,以此实现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召唤和加速“去异化感”(de-alienation)的过程,从而使其自愿、自发地拥抱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宰制。
然而,劳动内涵的不断扩展与丰富同样造成了另一个问题的显现。日渐宽泛的范畴正使数字劳动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无法有效服务于对特定社会活动的批判与分析(Gandini, 2021)。在福克斯和桑多瓦尔(2014)看来,涉及数字媒体技术与内容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的所有形式的劳动都属于数字劳动。不论是媒介产业中的脑力劳动者、“产消合一”的消费者,还是诸如采集用于制作手机的锡石矿工、电子设备制造流水线上的组装工人之类体力劳动者,都应被视为数字劳工。而麦克切尔和莫斯可(2013)则认为数字劳工应从属于宽泛定义的知识劳工。姚建华与徐偲骕(2019a)指出当前传播研究中存在有关劳动概念泛化、混用的问题,这使得相关研究对其解释对象面临丧失具有排他性的独占阐释优势的风险。而从现有对平台用户“产消合一”的批判研究来看,除“玩工”理论(playbour)聚焦“玩”的劳动化外(宋嘉伟,2020;蔡润芳,2018;Kücklich, 2005),同属闲暇时间中贡献创造性的其他媒介活动则大多被笼统置于“数字劳动”的概念下,忽略了特定媒介技术“中介化”下所形成劳动控制的具体情境与微观政治,难以对诸种多元且异质的劳动形式进行精准描摹与有效解释(姚建华,徐偲骕,2019b)。对于平台资本主义价值生产方式的思考,我们有必要保持诸如日常活动正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受到“无尽剥削”的想象力(Fuchs, 2010),同时也应关注日常生活不同面向中的具体劳动形式,进一步揭示数字劳动的普遍性与特定情境下的异质性。当下,技术、身体、社会实践正空前嵌入数字化、个体化的场景之中,唯有更加突出对场景的重视,才能在个人与技术、用户与平台、生活与劳动等多种关系中深入辨明数字劳动生成的多元要素与影响变迁(张志安,姚尧,2020)。
二、隐藏的“展演劳动”:自我呈现中的劳动
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的概念由戈夫曼(2016)提出,他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表演的过程。作为数字化生存中的重要维度,自我呈现是驱动用户进行媒介参与的重要动力。而网络世界则赋予人们身份实验更大的空间。只有通过“文本表演”(textual performance)(Sundén, 2003)“写出自己”,个人才能“完全意义上得以在网络中存在”(Liu, 2007)。
无论是基于“自我呈现”的研究(Webster, 2020;田甜,2019),还是近年得到发展的“自我策展”(self-curation)(Abidin, 2016)、“自我追踪”等(self-tracking)(Lupton, 2016),这些研究均关注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到自我重构的过程之中。霍根(2010)认为,平台媒体中用户的自我呈现与戈夫曼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舞台表演(performance)已有所区别,而是更接近于展览(exhibition)的形式。用户通过自拍、vlog、签到等方式设计、建构个体形象,并有选择地陈列想要展露的信息。因此平台本身提供的媒介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
这些在平台媒体中围绕自我呈现展开的广泛媒介实践塑造起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展演劳动(displaybour)。展演劳动本质是一种无偿劳动或弹性劳动,它与用户身份和本真性(authenticity)紧密连接,是用户在区分、定义、构建以及展现自我的自我驱动过程中产生的自愿劳动。它在身份的展现与被看中创造价值,并在用户对身份的消费与焦虑中维持再生产。
展演劳动是平台资本主义下一种具有鲜明主体性色彩的结构性劳动。借由数字平台,用户获得了可以实时修饰、调整自我以塑造理想化身份的可能性,这种有意识的、能动的形象管理使个人对自己的平台身份有更强的主导权与控制力,在自我构成的过程中获得主体性,同时也遮蔽、消解了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感。从福柯(2015)的自我建构理论来看,自我是通过支配技术(technologies of domination)和自我技术共同作用所建构的结果(李姗姗,2008)。在平台媒体中,这种支配技术与自我技术融为一体。通过同自我、他人的区分来定义自我,是平台媒体公开性、社交性、互动性得以实现的基础逻辑。因此用户被鼓励通过平台预置的可供性框架进行信息登记、标记分享,以及发布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等活动,从而将用户以特定方式从事自我呈现的劳动合法化。个人的每一种自我呈现与表达,都在实时互动环境中被监视、评价,并随时会反馈回个体,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推动身份的再生产。这一平台系统使得用户被置于一种强迫性的反身性(reflexivity)之中,思考、定义和展现自己成为用户平台使用中的一项隐形义务(Fisher, 2012)。这种主体化与客体化共同构建起展演劳动过程中的同意机制,使用户在一套由本真、自我的道德话语与参与、民主的权力话语构建的自我规训框架中实现对平台控制的内化。
平台媒体正在以自我呈现的自由与规则实现或加速着闲暇的商品化过程。如果说“玩工”是游戏产业的生命线(Taylor et al., 2015),那么产消者的展演劳动是支撑数字平台运转与增殖的重要劳动形式。要进一步揭示平台媒体对于展演劳动的剥削,必须进行更加情景化的在地分析。本文选取音乐流媒体平台网易云音乐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平台媒体中用户自我展演背后劳动的生成机制,从而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RQ1:网易云音乐用户如何在音乐流媒体平台上进行展演劳动?
RQ2:在用户进行展演劳动的过程中,用户的生产同意如何形成?
RQ3:用户与平台间的互动实践如何巩固/抗拒这种生产关系?
三、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基于北京(6)、哈尔滨(2)、澳门(1)、长沙(1)、广州(1)、合肥(1)、青岛(1)、泰兴(1)、乌鲁木齐(1)、张家口(1)以及海外(3)等多个地区共19人次的数据收集。2021年2月至4月期间,研究者首先主要围绕网易云音乐、百度贴吧进行参与式观察,同时搜集、阅读网易云音乐使用条款,网易公司的企业年报,有关中国数字音乐消费的第三方行业报告。访谈工作主要在2021年5月进行。根据《2020中国移动音乐行业报告》(2020)、《2019—2020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研究报告》(2020)、《网易云音乐2016上半年用户行为大数据》(2016)对网易云音乐平台活跃用户群体的分析,研究确定选取18—35岁、使用网易云至少1年以上的用户作为研究对象。被访者包括8名男性,11名女性,来自中学、高校、银行、传媒公司、软件公司、铁路系统等多个领域,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具有多样性。
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用户基于网易云音乐的基本使用情况,包括账号基本信息、使用动机、常用功能、聆听场景、对于平台的整体认知等。第二部分主要涉及用户在平台上的自我展演活动以及相应的数字劳动。第三部分聚焦于用户对于自身劳动的感知与认识。因被访者个人使用经历不同,访谈时间从30分钟到60分钟不等。平均访谈时长约为45分钟,访谈总时长共计866分钟。所有访谈在征求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随后根据语音识别软件讯飞听见转换为逐字稿,访谈内容中提到的网易云用户名称、其他流媒体平台均进行匿名化处理。根据录音进行对照整理后,共得到文字性资料13.7万字。基于福克斯和桑多瓦尔(2014)提出的针对数字劳动的分析框架,两位研究者分别对访谈逐字稿进行阅读,并结合前述理论讨论进行开放式编码(Saldana, 2021),提取浮现的主题线索。两位研究者在讨论和对比后形成共识,最终形成研究发现。
四、生产关系的形成:展演劳动的动员与制度化
(一)平台元叙事下的劳动动员
作为一款突出社交属性的音乐流媒体平台,网易云音乐将用音乐进行展演与连接作为平台使用的元叙事。正如其宣传口号“音乐的力量”所示,平台试图让用户在“自由控制与塑造自我”的意识与环境下积极进行自我呈现,以此将用户媒介参与同平台经济目标深度勾连。具体来看,网易云音乐至少通过以下三种平台角色的建构来实现对用户积极劳动的广泛动员。
1.作为传达特定意义的中介
在受访者的媒介使用中,网易云音乐是情感、经验与意义具象化呈现的重要中介,期望目标接收对象能够结合与音乐以及平台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解码过程中补全所表达的信息,从而达成意义共享。在访谈样本中,用户以平台内或平台间(如将网易云音乐链接转发至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的音乐分享作为自我呈现形式,一方面通过可见的内容形态(如歌曲链接、封面、分享的文字、表情符号等)满足个体动态标记的需要;另一方面利用音乐委婉、隐晦的表达特征,既实现针对特定对象的清晰化表意,同时也在语境坍塌的环境中以模糊化的手段实现对“局外人”区隔,实现层级化的交流愉悦和自我形象维护:
比如……通过这个歌正好说出了我的一些思考的时候,可能就是针对和我亲近的人分享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更知道这首歌在说什么。比如说有一天我和我妈吵架了,我凌晨3点分享了一首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共同喜欢的一首歌,我妈看到就知道我因为吵架没有睡着,或者我在求和了。(D12)
正是此类被用户用于自我呈现、沿用户关系网络与跨平台链接蔓延的平台产品,实现了平台能见度与流量的延展。
2.作为自我建构的新场所
网易云音乐本身作为一种资源和场所,使用户得以进行自我建构,进而实现印象管理并获得个体身份认同。惠蒂(2007)认为,自我的建构包括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与应然自我的建构,这三类自我分别代表着个体或他人所认为真实的、所期待的以及认为其应当具有的自我表征。网易云音乐为用户提供了混合式自我建构的可能性。一方面,网易云音乐平台区别于其他主要的自我呈现场所(如社交媒体平台)中强关联的特征,以更加隐蔽的身份线索以及弱现实连接属性为用户自我呈现提供了自由度。
另一方面,网易云音乐成为用户通过文化品位来实现区隔的重要渠道。品位是个人特征的展现,也是社会关系的指示,人们依据品位对自己进行定位,同时也被别人定位(蒋淑媛,罗娴妮,2019)。网易云音乐中的品位彰显从用户选择并进入平台时就已起始,小众、文艺、年轻化、高品质等话语成为用户身份认同与自我呈现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据网易云音乐2021年发布的招股书显示,其平台用户“90后”占比高达89%,拥有23万余名独立音乐人(网易云音乐,2021)。网易云音乐最初的品牌口号为“听见好时光”,其中蕴含着通感式、文学化的表达风格以及对于诗意化美好日常生活的追求。受访者D09感到网易云音乐的风格和其他软件有比较大的区别,整个平台都有一种向“文艺范”塑造的感觉。D13则直言,“比××平台要好一些,××音乐是太商业了,说白了我觉得有一些太俗了。”(D13)
3.作为连接与互动的社区
网易云音乐同时也在努力凸显其音乐社区的功能与定位,鼓励用户在音乐产品与自我呈现的连接中不断寻求和建立广泛的社会连接与认同。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用户通过流媒体音乐服务形成维持友情互动的强连接、因音乐趣缘凝聚的弱连接,以及不以社交期待为目的、具有随意性与偶然性的缺场连接(Hagen & Lüders, 2017)。在连接的基础上,用户往往会产生对于社会归属感与情感共鸣的期待,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作为一名通过网易云音乐发布原创音乐的创作型用户,受访者D02在日常使用中有意识地利用平台社群性来推广自己的音乐:
听众或者其他的音乐人都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聊天什么的。我自己想发歌了,就发一些预告视频片段,增强和朋友、音乐人的互动,提升一下热度。(D02)
此外,在平台社区中,“用网易云音乐的”和“用其他音乐流媒体的”、“听小众的”和“听流行的”与“有品位的”和“没品位的”、“懂自己的”和“不懂自己的”相连接,这样的叙事话语进一步驱动用户在持续的自我呈现与建构中巩固对个体与群体身份的认同感。受访者D09谈到自己的使用体验表示更享受“一个频道中的默契”:
有时候别人可能发一个电影原声音乐,就有人会(在评论区)玩梗……大家像互相说黑话一样,会有那种暗爽的感觉。(D09)
(二)展演劳动的制度化
以平台技术可供性为支撑,网易云音乐通过“自我塑造”、“自由展现”的叙事话语在用户甫一使用平台时便为其预置了一套“适宜”的用法,在鼓励用户不断将日常生活痕迹写入平台使用经验中完成劳动的合理化以及对展演劳工的广泛动员。与此同时,网易云音乐平台通过多种规则体系对用户劳动进行统筹和管理,组织用户进行高度重复劳作,根据平台生产需求与计划完成相应的生产任务。如此,用户零散的展演劳动得以实现理性化、规模化与制度化。
1.荣誉与经济:基本的游戏规则
从最新版本的网易云音乐平台②来看,荣誉与经济体系构成平台引导和驱动用户持续进行展演劳动的基本逻辑。荣誉体系主要与用户在平台内的成长相关,包括用户等级、任务勋章、榜单排行三类,其分别有具体的量化指标支持。以用户等级来讲,只有达到一定的任务指标,用户才能升级,并在用户账号名后显示特定标志,成为对用户在平台内成长与成就的标定与显示,使用户得以获得直接性的自我满足,激励其进行重复劳动。受访者D14在访谈中坦言有时甚至不是为了听歌,而仅仅是为了特定级别的那个数字:
也不是说特别想升到10级。③但我也有点强迫症,你就差一点就等级爆表了,那我干嘛不(升)呢?但是(网易云)这个听歌的要求很过分,要有几千首。我直接挂机,磨着磨着就10级了。(D14)
在经济体系上,用户的每一次发布、分享、评论等活动,都能为自己赚取虚拟货币“云贝”。用户也可以在云贝中心领取特定任务赚取“云贝”。赚到的“云贝”可以用来兑换商品或消费折扣,也可以通过花费“云贝”把自己喜欢的歌曲推上平台热搜,让更多人看到。“云贝”需要通过劳动换取,这无疑将用户限定在劳动者的位置上,其本质上是平台用以和展演劳工交换劳动成果的支付形式。
2.“音乐合伙人”:“工分”制下的免费劳动
2021年,网易云音乐推出“音乐合伙人”机制。网易云音乐基于对用户的大数据分析,在头部活跃用户中定向邀请10万人成为网易云平台的“音乐合伙人”。用户可以获得会员资格,决定平台官方推广曲目,并在所推广歌曲下留名。条件是“合伙人”每天需要对平台定额配送的五首原创歌曲进行打分和评价。平台则会根据“合伙人”每天的任务完成情况和评价准确度发放相应积分,每个周期内得到足够的积分才能保证继续拥有“合伙人”以及“永久黑胶会员”的头衔与权益。网易云音乐用一种精英化、神秘化的会员制隐喻将用户吸收入具有明确约定形式的生产关系框架内,通过人力劳动以优化网易云音乐的核心推荐功能。而除了上述“权益”外,用户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劳动报酬。D18是受访对象中唯一获得“音乐合伙人”资格的用户。作为平台忠实用户,她用“折磨”一词形容自己的体验。D18认为,平台分配的原创歌曲质量参差不齐,另外由于平台的算法问题,按照自己客观感受的打分却并不能获得较高的积分,这让她不能理解。而由于正态分布④的原理,往往中庸地打出3星⑤反而能获得较高的积分。这使得很多用户刚听歌曲前奏就草草打出3星,以这种形式进行抵抗。在参与式观察中,部分用户将“音乐合伙人”戏称为“音乐打工人”、“分奴”,这一机制更被调侃为“兼职工作”、“主人的任务”、“三星堆遗址挖掘现场”。
3.弹性用工关系下的“网易音乐人”
鉴于平台在“音乐社交”模式上的成功,网易云音乐致力于加强用户社区与流媒体音乐业务间的纽带。作为扭转自身在歌曲版权劣势的重要途径,网易云音乐着力通过培养和扶持原创音乐充实自身内容生态。2018年网易云音乐推出“云梯计划”,以让更多用户以及音乐爱好者职业化。平台对用户原创、改编以及翻唱的高人气作品进行推广,并且依据歌曲的播放、收藏等数据以广告分成、现金激励、数字专辑售卖,以及虚拟货币奖励的形式支付酬劳。参与这一激励计划并申请成为“网易音乐人”的用户则需要让渡自己的知识产权,授权平台使用。在受访者中,D01、D02、D15存在向平台上传原创作品的行为。他们指出平台奖励计划的框架下存在两种授权协议。平台独家授权限定用户在约定的时间内只能将歌曲发在网易云平台。而非独家合约尽管不具备排他性,但用户在签约期内不能自由对上传音乐进行删除或下架。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公司成功地以低廉的价格甚至零成本管理具有技术背景的劳动力群体”(Postigo, 2003)。用户被纳入平台内容生产的弹性用工关系之中,成为平台音乐产业的“劳动后备军”,原创作品被打上网易云音乐标签而待价而沽。用户社区也成为平台获取新创意与新思想的庞大试验田。
五、展演劳动的生产:基本类型及其延伸
(一)展演劳动的三种基本类型
网易云音乐用户通过多种方式被动员、纳入展演劳动的场域之中,这使得劳动力(用户)与生产工具(平台)之间呈现繁复错杂的组织与互动关系。因而通过生产过程穷尽展演劳动的诸种类型较为困难。而当把视角从“如何生产”转向“生产什么”,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些围绕自我呈现的多元劳动在劳动成果上具有较为集中的指向。围绕元数据、用户生成内容以及品牌形象的生产,用户展演劳动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1.围绕元数据的劳动
用户通过点亮红心、云贝推歌等方式展现自己聆听的在场与品位的在线。这种只需要偶尔动动手指的便利性操作使用户得以实时登记和表达自己的场景碎片与情感瞬间,同时将记录个人数字踪迹的元数据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平台算法(algorithm)。用户的数据让渡使算法得以不断分析用户喜好与需求。这些基于一定规模群体的、重复的、序列性聆听实践,不断生产出从用户中来、到用户中去的“众创音乐类别”(crowd-generated music categories)(Airoldi, Beraldo & Gandini,2016),使平台变得更加“人性化”(D04、D14)、“更懂用户”(D06、D14、D16),实现音乐与目标用户群体风格与品位的动态适配与塑造,推动用户的进一步自我披露与呈现。在平台极力推广的“公开”、“发现音乐的力量”的理念下,用户以牺牲个人数据隐私为代价投喂算法,为平台资本主义注入源源不断的“数据燃料”(Murdock, 2011)。而当用户将日常聆听与粉丝行为相连接,向平台算法输入特定的元数据甚至成为用户一种有意识的情感劳动:
很在乎我“爱豆”是不是我的年度最爱歌手……我会注意控制我的听歌情况。因为我很怕,万一哪天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听了个“鬼畜”之类的歌曲,万一它就成了我年度歌单的首位了呢,这就不合适,所以我就会冲一波“业绩”……因为肯定想让最喜欢的歌成第一。(D04)
2.围绕用户生成内容的劳动
在强调音乐社交与分享的平台环境下,网易云音乐鼓励用户积极进行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而所生产的内容则被平台用于生产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或者成为商品化内容的载体(姚建华,徐偲骕,2019b)。尽管近年来网易云平台陆续加入直播、Mlog音乐短视频等功能,但从受访者的使用经验来看,这些功能却并不常用。在音乐聆听与展演的实践中,网易云音乐用户主要进行歌单、评论与原创音乐三种内容的生产。
第一,用户在聆听实践中创建并精心整理与展演的歌单,成为网易云音乐算法推荐的重要补充。收藏一份优质的歌单,意味着一般用户与歌单主人之间构建起一种软性的连接,使前者可以从往往“品位更好”(D11、D12)、“涉猎更广”(D19)的一部分用户得到人工推荐与整理:
你知道×××吗,他是专门做音乐鉴赏方面的音乐达人……我真的还对他分享的音乐、视频蛮关注的,毕竟他听得比我多很多……一般他分享的我都会比较喜欢。(D18)
第二,“众包”式生产的用户歌曲评论形成网易云音乐平台聚集流量、实现商业增殖的重要途径。用户评论的原创内容集中于对当下情绪的表达、对生活经历的回忆、对词曲以及歌手的艺术赏析。这些具有浓郁情感体验和品味隐喻的评论不仅实现用户的持续卷入与情感共鸣,同时也成为网易云音乐市场营销的重要着力点。网易云音乐曾多次凭借用户生产的精彩评论内容进行地铁营销活动,还与农夫山泉、瑞幸咖啡等品牌进行跨界联名合作。
第三,用户生产的原创音乐以及如电台、博客等音频作品。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虽然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力,但他们所产生的,以及潜在的利润和价值却绝大部分归属公司(Ritzer & Jurgenson, 2010)。从网易云音乐的用户服务条款(2020)来看,用户生产内容被视为向平台提供内容的自愿行为,提供内容的同时自动授权平台免费“使用、传播、复制、修改、汇编、改编、再许可、翻译、创建衍生作品、出版、表演及展示此等内容”。同时条款声明网易公司对用户发布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使用网易云音乐即视为默认接受这些条款。用户承担了平台一定的劳动,廉价甚至无偿地为平台创造价值,却需要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其劳动成果及个人权益并未见合理保障。
3.围绕品牌形象的劳动
除了关于元数据以及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用户还“免费”承担了品牌的市场推广。个人的社交关系网络成为网易云音乐平台营销的免费渠道。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向好友、或公开分享音乐,几乎成为所有受访者的日常。他们还不断延展着网易云音乐的官方叙事,为其建构出更为丰富、立体的社会形象。用户在这一过程中也在不断确认和强化自身作为“云村人”对平台的归属感与忠诚度。这种与自我身份建构与群体认同有关的自发展示极具吸引力,它们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新用户的加入,推动着“用网易云听歌”成为一种具有群体动力的文化潮流。在受访者中,D03、D07、D09、D19明确表示自己最初选择网易云音乐是因为“朋友推荐”、“大家都在用”,同时也会选择向他人推荐这一平台。这种自发推广对于平台公司来说收益巨大,毕竟市场推广费用是互联网公司最大的开销成本之一。
这三种展演劳动类型的内在关系在于,它们实际上都是在建构和维护自我形象与网络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有/无意识的活动。这些平台用户投入感情、收获满足的自我劳动,客观上被作为连接者而非实际生产者的数字平台转化为商品或生产资料。网易云音乐用户实际上被卷入平台价值链中消费、生产和市场三个关键环节,个人的活动印迹与活动成果被数字平台以几乎为零的成本所占有,成为源源不断吸引另一部分新用户,以进行如此循环往复劳动与转化的筹码,这成为网易云音乐平台通过产消合一行为创造价值的基础。
(二)平台外展演劳动的延伸
除了在平台上的积极劳动,围绕用户自我呈现的劳动也延伸到网易云音乐以外,借由互联网形成一定的产业链条。与大多数平台用户离散的、无意识的生产相反,这些劳动具有更为明确的动机,并逐渐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隐形产业。
在有关数字游戏“玩工”的相关研究中,“金币农夫”(Dibbell, 2006)或“网游代练”(邱林川,2013)是游戏产业链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指通过人工代玩的方式帮助玩家获取装备、提升级别以换取报酬的廉价劳动(吴鼎铭,2015)。研究发现,网易云音乐用户群体间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劳动形式:用户在淘宝、微店等电商平台购买虚拟服务,买家则会在规定的时间自动发货,将外挂软件下载链接及密码发送给用户。用户即可凭此在软件上登录自己的网易云账号,实现在平台的自动签到以及听歌打卡,完成网易云音乐的升级任务。与“金币农夫”的人工代劳不同,这种“数字经纪”通过调用平台的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完成操作,即通过机器人模拟用户在账号的元数据日志中刻录数字痕迹,帮助用户快速升级。在网上商店中,卖家根据需要提供从包天到包年不等的服务套餐供用户选择,并承诺提供售后服务,解决软件的维护、升级以及封禁的问题。
由于网易云平台对于用户原创音乐的奖励机制同样以歌曲播放、点赞以及评论数据为标准,因此“数字经纪”也被用于赚取平台收益。在百度贴吧“网易云音乐”中,这类信息往往以“交流”、“学习”、“教学”的标题出现,有的卖家将其描述为当下“很火”的“项目”。一部分卖家则并不会直接出售代挂软件,而是以“全托”的形式,全权帮助买家打理自己的音乐人账号。在一位卖家的服务介绍中,一个网易云音乐账号一天可以赚300—500元人民币。
第二种劳工类型是“音乐代工”。他们为用户提供原创音乐的编曲、制作、代唱等服务。用户最低只需要花200元到300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首由“音乐代工”代为制作的“原创”歌曲。与“数字经纪”相同,作为消费者的网易云音乐用户是这类服务的主要买家。他们往往被网易云音乐的激励计划所吸引,购买歌曲主要是为了达到申请网易音乐人的门槛,日后通过播放量、浏览量的代刷达到平台要求,获取资金奖励。这些“音乐代工”不少由网易云音乐用户转变而来,或本身自己也拥有网易音乐合伙人账号。他们主要通过百度贴吧、知乎发布广告,通过QQ、微信等方式与买家联系、沟通业务。一位卖家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服务概括为“网易云薅羊毛”。一位“音乐代工”的微信朋友圈显示,忙的时候会忙到凌晨一两点。
第三种是“应援打投”,这类劳工往往具有平台用户与偶像粉丝的双重身份,通过重复购买数字专辑、播放歌曲或MV的方式不懈地为偶像打榜、投票。在“数据拜物教”的逻辑下,粉丝用户将“做数据”作为与偶像联结的情感纽带(庄曦,董珊,2019),在刷播放量、刷排名、刷销量的单一劳动中不断为偶像制造正面数据。D05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位明确表示参与“应援打投”的用户。在她看来,自己的劳动就是为了让自家“爱豆”在平台榜单上有更好的名次与曝光度,“他们的歌排在第一,就说明人还有歌都是有魅力的”;同时展现“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年还爱着他们”。此外,在组织雇佣关系缺失和粉丝主体性增强的条件下,粉丝用户以后援会的形式进行自我组织,通过分工合作共同为偶像应援:
电子专辑下面有一个榜单,可以显示头像,就能看到谁对这张专辑的贡献最大……我们会去集资,然后用一个账号去买专辑,这样(我们的)排名就能往上走很多。(D05)
对于这种集体劳动中的组织运行方式,D05从没有怀疑过:
我觉得是一种最质朴的信任……没有人觉得后援会会造假、欺骗别人。(D05)
作为个体的粉丝用户通过金钱、时间与情感的不断投入收获了心理上的满足,而流媒体平台、版权公司、艺人及经纪公司则作为实际获利者内部分配并占有了这些由用户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六、结论与讨论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本文聚焦于音乐流媒体平台中用户自我展演这一特定面向,试图探索在特定语境中用户“产消合一”行为的劳动化过程,深化对平台用户与平台公司之间权力关系的思考与理解。在对网易云音乐用户群体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四点。
第一,作为日常媒介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自我呈现所展开的“展演劳动”是网易云音乐平台的重要价值来源。用户为平台创造了可观的内容资源,以个人元数据的让渡协助平台改善算法,完善使用体验,同时也为平台吸引来更多用户。第二,存在用户被纳入一定的机制进行重复劳动的事实,而这种劳动关系则被用以强化主体性的技术可供性与意识形态建构所形成的去异化感遮蔽。第三,用户的劳动成果及知识产权被平台以廉价甚至免费的形式征用,而用户自使用平台伊始即被视为自动接受承担因自己所发内容所引起的一切风险,这是不对称的劳动权力关系的直接体现。第四,围绕“展演劳动”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劳动分工,这一方面展现了围绕自我呈现的进一步产业化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用户对平台中生产关系的调适与抵抗。我们可以用一个模型将网易云音乐平台内外围绕“展演劳动”的一系列生产关系与生产政治作进一步可视化呈现(见图1)。
在德语中,“劳工”(Arbeit)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奴隶”(arba)一词(Weingart, 1997,转引自Fuchs & Sandoval,2014);英语中的“劳工”(labour)本义也与苦役、苦难、疼痛关联(Williams, 1983:176-179)。这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得以认识、理解劳动的坐标。而伴随着平台经济下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以看似更加温和、柔性的形式出现的劳动使人们更加难以察觉和辨识。本文并非意在描绘出一个数字音乐平台价值生产的全部图景,而是尝试在一个特定的媒介使用情景中探讨数字经济下生产与生活、劳动与休闲日益模糊的边界。必须承认用户在平台上积极的自我呈现中收获了乐趣与满足,但思考谁才是这一过程背后最大的赢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用户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如库克里奇(2005)所指出的,“自我规训的框架使人们在信息社会将休闲活动定义为新的劳动形式成为可能”,或“用‘自由’和‘规则’来描述劳动成为可能”。随着数字劳工研究由“生产的政治”转向“生产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并重(姚建华,徐偲骕,2019b),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向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成为新的研究方向。而当日常媒体使用与数字劳动缝合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劳动视作休闲”可能比“为了生计而玩”更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和反思。■
注释:
①2016年7月,拥有酷我音乐和酷狗音乐的中国音乐集团和腾讯旗下的QQ音乐合并,并于2017年更名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TME)。我国数字音乐市场头部的三大品牌由此成为一家。
②本文写作时网易云音乐最新版本为8.2.60。
③网易云音乐的用户等级共分为1-10级。升级需按要求完成累计听歌数与累计登陆天数两项指标。如达到10级需累计听歌20000首,登陆平台800天。听歌量指累计播放的不同歌曲数量,同一首歌重复播放次数不纳入计算。为防止用户刷数据,平台规定只有用户每天听的前300首歌曲纳入记录。
④正态分布,统计学中重要的概率分布模型。正态分布曲线的高峰往往位于均数所在的位置,即在一定样本中,与样本平均数越接近的分布越密集,相反与平均数差值越大的数量越少。
⑤在“音乐合伙人”机制中,合伙人可以给予歌曲1-5星的打分。平台则会综合大数据对合伙人的打分质量进行评定,给予相应积分。每月达到320分才能维持合伙人资格以及会员权益。而在受访者访谈以及线上观察中,不少用户反馈打均分三星获得的积分最高,按照自己真实感受的评价反而不一定能获得高分。
参考文献:
艾媒大文娱产业研究中心(2020)。2019-2020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研究报告。检索于https://report.iimedia.cn/repo1-0/38995.html,2021.6.10。
蔡润芳(2018)。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剥削逻辑——论游戏产业的“平台化”与玩工的“劳动化”。《新闻界》,(2),73-81。
蒋淑媛,罗娴妮(2019)。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演化及其逻辑。《中国青年研究》,(11),5-12。
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2013)。《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李姗姗(2008)。福柯的自我建构理论及其教育意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68-173。
米歇尔·福柯(2015)。《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Mob研究院(2020)。2020中国移动音乐行业报告。检索于https://www.mob.com/mobdata/report/117,2021.10.23。
欧文·戈夫曼(2016)。《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邱林川(2013)。《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嘉伟(2020)。“肝动森”:休闲玩工的形成——对《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的数字民族志考察。《新闻记者》,(12),3-19。
田甜(2019)。《社交媒体的品味展演与主观阶层认同——以青年群体的微信使用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论文。上海。
王莹(2019)。最前线|网易云音乐用户数破8亿,与腾讯音乐的市场争夺战远未落幕。检索于https://www.36kr.com/p/1724145090561,2021.6.10。
网易公司(2020)。网易云音乐服务条款。检索于https://st.music.163.com/official-terms/service,2021.7.20。
网易云音乐(2016)。听歌多元化时代到来——网易云音乐2016上半年用户行为大数据。检索于https://www.163.com/tech/article/BV6C55C500097U88.html,2021.6.18。
网易云音乐(2021)。网易云音乐招股书。检索于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1/103466/documents/sehk21052600997_c.pdf,2021.6.20。
吴鼎铭(2015)。《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武汉。
姚建华,徐偲骕(2019a)。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数位劳动研究的内涵、现状与未来。《新闻学研究》,(141),181-214。
姚建华,徐偲骕(2019b)。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141-149。
张志安,姚尧(2020)。互联网平台劳动的社会影响及研究启示。《新闻与写作》,(12),65-69。
庄曦,董珊(2019)。情感劳动中的共识制造与劳动剥削——基于微博明星粉丝数据组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6),32-42。
AbidinC. (2016). “Aren’t these just youngrich women doing vain things online?”: Influencer selfies as subversive frivolity. Social Media+ Society2(2)1-17.
Airoldi, M. , BeraldoD. , & GandiniA. (2016). Follow the algorithm: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music on YouTube. Poetics571-13.
AllmerT. , SevignaniS. , & ProdnikJ. A. (2015). Mapping approaches to user participation and digital labour: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Reconsidering Value and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 (pp. 153-171). Palgrave MacmillanLondon.
Bruns, A. (2008). BlogsWikipedia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Peter Lang.
Burgess, J. , & GreenJ. (2018).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John Wiley & Sons.
Comor, E. (2015). Revisiting Marx’s value theory: A critical response to analyses of digital prosumpti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31(1)13-19.
Dibbell, J. (2006). Play Money: Or, How I Quit My Day Job and Made Millions Trading Virtual Loot: Basic Books (AZ).
FisherE. (2012). How less alienation creates more exploitation? Audience labour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 10(2)171-183.
Fuchs, C.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6(3)179-196.
Fuchs, C. (2012).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 10(2)692-740.
Fuchs, C. , & Sandoval, M. (2014). Digital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 framework for critically theorising and analysing digital labour. 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 12(2)486-563.
Gandini, A. (2021). Digital labour: an empty signifier? MediaCultureSociety43(2)369-380.
Hagen, A. N. , & LüdersM. (2017). Social streaming? Navigating music as personal and social. Convergence23(6)643-659.
Hogan, B. (201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 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30(6)377-386.
Jenkins, H. (201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Routledge.
KücklichJ. (2005).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5)https://five. fibreculturejournal. org/fcj--025-precarious--playbour--modders--and--the--digital--games--industry/accessed on 10 June 2021.
Lazzarato, M. (1996). Immaterial labour. In P. VirnoM. Hardt(Ed.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pp. 133-15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essigL. (2008). Remix: Making Art and Commerce Thrive in the Hybrid Economy: Penguin Press.
Liu, H. (2007). Social network profiles as taste performanc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3 (1)252-275.
LuptonD. (2016). You are your data: Self-tracking practices and concepts of data. In Lifelogging (pp. 61-79): Springer.
Murdock, G. (2011).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giftsand public Goods. In J. WaskoM. Graham, & H. Sousa(Ed. )The Handboo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pp. 13-40). Oxford: Wiley Blackwell.
Postigo, H. (2003). From pong to planet quake: Postindustrial transitions from leisure to work.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6)593-607. ?
RitzerG. , & JurgensonN. (2010). Production, consumption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10(1)13-36.
Saldana, J. (2021). The Coding Manual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Sage.
ScholzT. (2017).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Labou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SmytheD.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Ablex.
TaylorN. , BergstromK. , Jenson, J. , & de CastellS. (2015). Alienated playbou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EVE online. Games Culture10(4)365-388.
Terranova, T.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Pluto Press.
Webster, J. (2020). Taste in the platform age: music streaming services and new forms of class distinctio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3(13)1909-1924.
WhittyM. T. (2008). Revealing the “real” me, searching for the “actual” you: Presentations of self on an internet dating sit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4(04):1707-1723.
WilliamsR. (1983). Key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翁旭东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博士研究生,捷克查理大学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姜俣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硕士研究生。本项研究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2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号:202007050042)资助。感谢Vaia Doudaki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