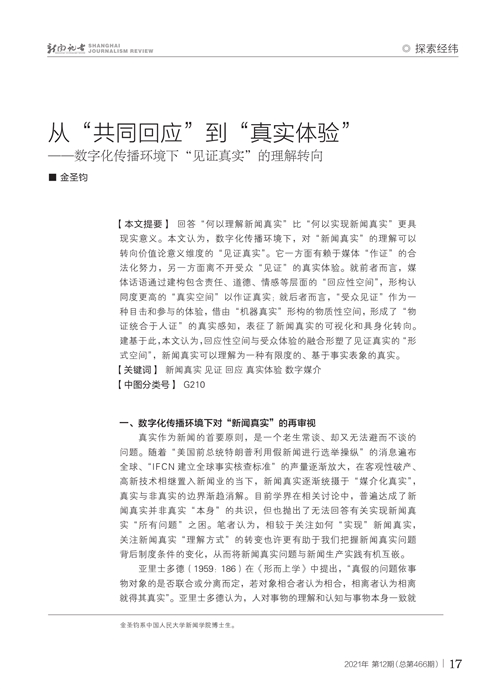从“共同回应”到“真实体验”
——数字化传播环境下"见证真实"的理解转向
■金圣钧
【本文提要】回答“何以理解新闻真实”比“何以实现新闻真实”更具现实意义。本文认为,数字化传播环境下,对“新闻真实”的理解可以转向价值论意义维度的“见证真实”。它一方面有赖于媒体“作证”的合法化努力,另一方面离不开受众“见证”的真实体验。就前者而言,媒体话语通过建构包含责任、道德、情感等层面的“回应性空间”,形构认同度更高的“真实空间”以作证真实;就后者而言,“受众见证”作为一种目击和参与的体验,借由“机器真实”形构的物质性空间,形成了“物证统合于人证”的真实感知,表征了新闻真实的可视化和具身化转向。建基于此,本文认为,回应性空间与受众体验的融合形塑了见证真实的“形式空间”,新闻真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有限度的、基于事实表象的真实。
【关键词】新闻真实 见证 回应 真实体验 数字媒介
【中图分类号】G210
一、数字化传播环境下对“新闻真实”的再审视
真实作为新闻的首要原则,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无法避而不谈的问题。随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利用假新闻进行选举操纵”的消息遍布全球、“IFCN建立全球事实核查标准”的声量逐渐放大,在客观性破产、高新技术相继置入新闻业的当下,新闻真实逐渐统摄于“媒介化真实”,真实与非真实的边界渐趋消解。目前学界在相关讨论中,普遍达成了新闻真实并非真实“本身”的共识,但也抛出了无法回答有关实现新闻真实“所有问题”之困。笔者认为,相较于关注如何“实现”新闻真实,关注新闻真实“理解方式”的转变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新闻真实问题背后制度条件的变化,从而将新闻真实问题与新闻生产实践有机互嵌。
亚里士多德(1959:186)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真假的问题依事物对象的是否联合或分离而定,若对象相合者认为相合,相离者认为相离就得其真实”。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对事物的理解和认知与事物本身一致就达到了“真”,是一种真理符合论的视角。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最早的“现象真实”到“本质真实”;从“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到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以及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与对象的符合”(杨保军,2006:8),一段时间以来,对于新闻真实的认同停留在真理符合论的认识之中,追求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的“镜像”,难以脱离19世纪中后期实证主义思想的束缚。盖伊·塔克曼(1978/2021:40-50)在《做新闻》中提到,受众看到的新闻事实是新闻机构布置的“新闻网”所筛选的结果,其观点虽然将新闻机构视为单一的传播主体,但仍在那个时代进步性地认识到新闻真实的相对性。新闻事实并非全部的客观事实,而是一部分具有新闻价值属性的事实(杨保军,2017),这样的事实在“被反映”的过程中亦会受到技术、修辞、把关等复杂外部因素等影响,因此新闻能否完全准确地反映事实、能否达到认知与事实的一致难以准确界定,符合论下新闻真实本身的“客观实在性”故而无从言及。
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和传播权的下移,如今的受众从信息“接收者”角色转向集新闻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一体的新闻“产消者”角色(Bruns, 2008),受众对新闻的阅读、使用、分享等行为对于新闻机构的意义更为重大,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从间接变为直接(白红义,2019)。由此,关于新闻真实的讨论开始注重新闻生产中的“受众”或称“用户”,即新闻真实性同样可以指称从受众的视角出发而产生的“相对和部分意义上的真实性”(沃尔夫冈·韦尔施,1998/2008:149)。此类讨论根据研究者对受众角色、地位定位层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第一类讨论将受众定位为与从业者等同的地位,关注从业者与受众之互动。有学者提出,新闻真实是不同主体之间互动和对话的结果,植根于“三元主体”(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脱媒主体)的形成,同时,新闻真实观念实现了由“客观真实观念”向“对话真实观念”的转变(杨保军,2017),诸如“节点真实”、“有机真实”、“前瞻真实”等概念相继出现。第二类讨论则是将受众定位至更高层次,认为新闻真实指的是新闻的真实“效应”,即收受者准确理解并相信传者的真实报道才能最终达到真实,即“信任真实”(杨保军,2018;李唯嘉,2020)。
从“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到有学者提出“信任是新闻的生命”(操瑞青,2017),新闻真实不再是纯粹的认识论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囊括受众心理、情感的价值论问题。克利福德·克利斯琴斯(Christians,2015,转引自刘沫潇,2020)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援引海德格尔的“无蔽”①概念,主张用“对被覆盖事物真正、真切的披露”的观点来理解真相,并据此提倡新闻业要坚持“阐释的充分性”原则。这种“阐释充分性”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体现为“作为知识的新闻”(Park, 1940)转换成一种受众习得的真知。受众感知到真知的价值,从而接受并从主观层面建构了新闻“作为知识的合法性”,最终达到新闻真实;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看,受众要求新闻是真实的,而新闻作为一种“公共记载”(Park, 1955:71-81),应充分阐释尊重基本事实的“社会合理性”以及尊重主流情感认知的“社会合情性”(郭景萍,2006),从而得到受众在事实和情感层面的双重认可,以实现自身地位合法性的建构,达到信任的真实。因此,在媒体深融的时代,仅仅在“后台”保证内容真实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前台”来“展现”真实(李唯嘉,2020)。
随着智媒时代来临,高保真的技术带来的超真实将真实转化为一种精确性的幻觉。鲍德里亚通过考察“仿真”的历史谱系,提出了“拟像”的概念,并以此指涉现代媒介技术将现实世界建构为一个超真实的、自我模拟的“仿真”世界,致使真实与虚拟之间界限的“内爆”(让·鲍德里亚,1979/2011:48-49;1994:31-32)。因此,受众对真实性的判断越来越依赖自身对新闻内容和媒体建构的感知、认识和行动范畴。在这个“虚拟”范畴里,“可经验”的东西被人们当作认知世界中”确定”的存有而被经验为真实性,受众因而更容易在当前、过去或将来的被给予物中形成“理解、意向或想象的真实性的关系”(马丁·塞尔,1998/2008:220-221),即主体的需要、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论范畴。由此,新闻真实其实是一种“真实效果”(陈卫星,2004:217),也可以延伸理解为受众的主体性本身对真实的“检验”(阿兰·巴迪欧,2016/2020:10-11)。在新技术加持下,这种对真实的“检验”正发生着从“离身真实”到“具身真实”的转变。诸如图片、影像等传递新闻内容等“离身真实”的呈现,虽然达到了“视界融合”,但是离身接触形成的体验真实、经验真实均处于弱连接状态(华维慧,2020);而“具身真实”则是基于技术建构的“机器真实”对身体的嵌入,有学者认为,新技术如VR通过创制拟真情境,经由临场感赋予,与受众感官身体相连,提升了受众对新闻的可信度感知和分享意愿(Sundar, Kang & Oprean, 2017)。不过综观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受众的感官身体虽然成为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但是其在新闻真实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关注。既有研究中,学者华维慧(2020,2021)分别从虚拟现实技术和VR新闻的真实性逻辑展开用户身体与新闻真实关系的探讨,学者谢新洲(2020)则从社会机器人智媒体的角度探讨感官与真实的再造。除此之外,鲜有其他学者使用一定篇幅阐释与此相关的问题。
基于上述总结和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新闻真实与新闻媒体、受众之间的关系变化,使得新闻真实的保障更注重于“前台”的呈现,而把握新闻主体的“在场”、注重新闻真实“可信度”的感知亦是数字化传播环境下理解新闻真实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因此,笔者提出“见证真实”的说法,在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对数字化传播环境下新闻真实理解方式的转变做进一步阐发。
从字面意义上看,“见证真实”作为一个动宾短语隐喻着主体性,强调主体对真实的见证行为,以及数字化传播环境下技术和见证主体角色、地位的变化对新闻真实理解转变的影响。本文无意以“见证真实”回答数字化传播环境下“如何实现新闻真实”的问题,而是在阐释何为“见证真实”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时代的“见证真实”转向因何产生,以及这种转向之下新闻生产与传受主体间的关系变化致使新闻真实的表现形式和理解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二、“见证新闻”与“见证者”:概念来源与角色认知
从概念本身出发,“见证真实”的说法来源于何处,如何理解“见证”与新闻主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见证真实”的概念有据可循。在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出现之前的纯新闻时代,“有人证实”是恪守新闻规范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在我国新闻学界中,曾有学者提出,“新闻报道的内容应该是由他人所提供或者记者自身亲历目击的新闻信息或者新闻事件”,新闻真实体现为一种“依据真实”(吴晓春,2005)。“依据真实”概念中强调的“目击”与“见证”的意涵有相似之处,为本研究即将展开讨论的“见证真实”提供了理论参考。但是,此观点一方面容易落入“有闻必录”的实践导向,最终丧失媒体公信力(孙婷,陈堂发,2020),另一方面,媒体记者对于新闻事件的“目击”能否被认为具有“新闻真实性”亦是一个仍需探讨的问题,这也是笔者在下文选取“媒体作证”进行论证的原因之一。
其次,有学者曾将“见证新闻”作为新闻的第七要素提出,“见证新闻”即“有人证实”新闻的发生(刘建明,2016)。一方面,它依据新闻见证者对新闻内容的陈述,是新闻公信力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在判断新闻是否可信时,只了解信源远远不足,还必须辨别和评估信源所提供的证据(大卫·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2011/2014:99)。在日常的新闻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到“见证新闻”的新闻话语,几乎所有新闻消息的开头多有诸如“据伤者胡某所言”的“当事人言”、“据目击者王明(化名)透露”的“旁观者言”,以及如“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哈利·洛克发表声明表示”的公众人物或有关部门“宣告者言”,以此证明受众眼前的这条新闻并非媒体杜撰,而是有人可以证明它的发生。在这里,无论是当事人、旁观者还是官方宣告者,都起到了见证新闻事件发生、提供“真实话语”和塑造受众真实认知的关键作用,故而可以统称为新闻事件的“见证者”。下面这条新闻反映了见证新闻的话语实践:
新华社阿布贾7月5日电(记者郭骏)尼日利亚西北部卡杜纳州一所中学5日遭武装分子袭击,大量学生和教师被绑架,其中27人随后被安全部门解救。
卡杜纳州警方发言人穆罕默德·贾里格5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当天凌晨袭击卡杜纳州奇昆区一所中学……
另据尼日利亚媒体援引校方负责人的话报道,超过140人在此次袭击事件中遭绑架。
卡杜纳州教育部门5日表示,该州13所学校已接到通知临时关闭。
突发事件报道中,记者很难保证第一时间在场,因此本条新闻通过引述警方发言人的官方声明和当地媒体的报道完成对袭击事件的内容概述。报道中,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的内容仅涉及校方“当事人”的采访,以现场见证者的言论配合官方的权威宣告强化了报道的真实性。新华社在本条新闻中做的上述“转发式”处理(刘建明,2016),能够对新闻内容的真实性起到有力的证实作用。
由此,“依据真实”和“见证新闻”的概念就是笔者提出“见证真实”的主要理论来源,这两个概念的共同价值在于其强调记者的证据意识,即媒体通过自我印证达到新闻真实。但仍需明晰的是,仅以“见证”的词义来表征新闻真实的意义变化仍不完整。随着新闻生产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传受双方距离的凝缩,数字化传播环境下保障新闻真实的条件不再由单一主体生产的“见证内容”决定,而是与新闻主体生产和接收的双向实践密切相关,这种制度条件的变化也引发了笔者对见证主体,即“见证者”的关注。Peters(2001)将新闻见证者分为三类:新闻叙述中的公民证人、通过媒体观看新闻的受众以及新闻从业者。随着用户地位的提升,今天的受众更加寻求自身的可见性,更愿意也更有能力通过新技术手段见证新闻事件的发生,因此新闻叙述中的公民证人即“目击者”成为见证者的合法性不言而喻。但是,Peters分类中提到的新闻从业者(媒体)可否作为“见证者”呢?
Frosh和Pinchevski(2009:1-19)认为,媒体见证的含义可分为两层,一是媒体通过报道中“目击者”的引入,记者自身充当“作证人”的可能性;二是受众作为新闻事件的“证人”,见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可以发现,在Frosh和Pinchevski的概念中,媒体见证的过程可以被总结为“媒体作证”和“受众见证”两个部分。笔者认为,在新闻现场中,媒体记者的身份与受众相同,是旁观者,而非亲历者,如果在新闻报道中,记者在非特殊情况下扮演了目击者的角色,那么则会引发真实性的质疑。如Zelizer(1992)所言,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善于使用叙事来巩固他们相对于其他阐释群体“讲真话”的地位,并通过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及实践技术形构“正当性”(李东晓,2019),而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不仅需要考虑多元的权力主体,亦不能保证自己对“事实”的判断与认识完全真实,即不同时空下的不同主体对同一事件的认识很难做到完全一致(操瑞青,2017),因此媒体更无法“自己为自己作证”。综上所述,目击是一种强调和保障新闻报道真实性权威的文化实践,它可以对事实作出断言,而记者的在场则是对事件真实性的一种“保证”(Zelizer, 2007:408)。在媒体见证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自身承担的不是“见证人”,而是一种“作证人”的身份,在报道目击者真实话语的同时,承担着证明真实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见证新闻”对二手资料依赖性强,二手资料作为一种特殊信源,会影响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接近性。数字化传播环境下,融合了高新技术的新闻产品带来的感官交互和具身体验,在受众端弥合了二手资料带来的传受主体间隔,一定程度上成为保障受众端“感知”新闻真实的重要条件,亦是后文“受众见证”部分的阐发向度之一。
结合上述研究以及笔者对“见证新闻”中见证者角色的探析,“媒体作证”和“受众见证”作为“见证真实”的主要阐发维度有必要结合现实情境进行探讨。虽然这二者难以涵盖阐发“见证真实”的所有维度,但是,“媒体作证”和“受众见证”全面关照了见证新闻中的见证主体,包含了新闻生产、技术嵌入、价值伦理等关键层次的动态变化,是数字化传播环境下对新闻真实的“见证”转向最具阐释力的两个维度。
三、媒体作证:新闻真实的“回应”转向
(一)“媒体作证”之意涵:基于目击证据的媒体合法性建构
“作证”并非仅有字面的一维含义,在西方新闻学研究中,往往将“作证”(bear-witnessing)与“目击见证”(eye-witnessing)进行比较研究。从词汇组成来看,作证的英文是“bear-witnessing”,“bear”的意思是产生、忍受或承担,因此“bear”可以将“witnessing”限定为一种被动的、工具性的实践。“目击见证”(eye-witnessing)则是一种主动的、自身受到影响的实践(Tait, 2011),即目击见证可以指涉某人在特定的时刻,从他们特定的位置直观看到的东西(Burke, 2001)。
第一代关于目击见证的学术研究首先出现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和心理学领域。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目击见证的概念强调的是对创伤事件的亲身体验,目击证人的描述起到了让受害者相信他们没有被抛弃和遗忘的作用(Andén-Papa dopoulos & Pantti, 2013)。Lilie Chouliaraki(2009)在对两段战争镜头的分析中简要区分了目击见证和作证,第一段镜头描述了塞浦路斯人英勇的牺牲,第二段镜头则是直接记录了巴格达的爆炸。与第二段不同,第一段呈现了“被美化的”英雄般的死亡。我们可以得知,作为屠杀的目击见证者不可避免地要观看事件的发生,也要同时参与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描述,此处的目击见证是一种非常规的、紧急的状态(Peters, 2008:47);而作证则意味着要把这个事件看作一个普遍真理,它超越了杀戮的事实本身,并与描述痛苦时刻的道德感相呼应(Chouliaraki, 2009)。
通过上述关于早期战争的目击见证研究,我们首先可以得知,从媒体自身来看,目击见证是一种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新闻工作者可以建立起自我形象,寻求新闻工作者自身意义的同时,有助于构建新闻媒体的权威(Allan, 2013:58;Zelizer, 2007);其次,从媒体和受众的关系来看,“存在”是目击的本体论基础(Peters, 2001:710),这也就决定了目击见证(eye-witnessing)需要超然和客观,即需要从事实、准确性和真实性的角度来理解,不与道德和情感挂钩(Carlson, 2009)。与目击不同,作证(bearing witness)需要基于事实和目击的证据,并尝试高于事实本身,通过引发情感体验使受众深刻体会“见证”的现实,从而激发受众的行为产生(Tait, 2011),最终建构职业的合法性。
(二)“媒体作证”的真实转向:回应性话语与“真实空间”的形成
基于上一节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与目击见证相比,“媒体作证”不仅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还包含道德、情感等更细微的感知层面。媒体作为证人角色,除了揭露事件的真相,还讲述着目击者观察和经历的故事,并传达对所发生事件的道德判断(Hausner转引自Wieviorka, 2006:390),为用户的真实感知建构更丰富的层次。那么诸如道德、情感等元素如何作用于“媒体作证”的实践?新闻真实的“见证”转向何以形成?
现实中,媒体对诸如暴力事件、社会安全问题的报道并不能阻止此类问题的重现,因此Zelizer(1998:10)认为,在情感和道德之上,“媒体作证”的核心是“责任”。“责任”意味着,我们需要把“作证”定义为一个比“亲眼所见”意义更深入的词汇,因为亲眼所见并不意味着要承担责任。那么,如何理解责任?在这里,责任应该被理解为“回应能力”(Tait, 2011)。笔者认为,随着用户在新闻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如今媒体“新闻网”的编织不再局限于网眼大小,每个用户都能从大大小小的“网眼”中完成回应,宣告着“全世界都在说”的用户新闻时代来临(刘鹏,2020)。因此,媒体形构的回应性话语空间,不仅需要媒体自身的技术生产力,还需要通过受众的回应加以“验证”。由此,对回应能力的阐释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当媒体作为“回应者”时,回应能力可以指通过塑造一个有“移情性质”的话语空间来回应报道中目击者对事件的描述以及受众可能产生的质疑(Oliver, 2004)。另一方面,对于受众而言,“回应能力”可以理解为对媒体报道的内容产生适当同理心的“反应能力”(Boltanski, 1999:xv),并能够在媒体塑造的话语空间中清晰地表达出这种反应。
本文认为,这种“回应性”话语空间呈现出四元互构的特征。话语空间大致由话语生产、话语关系、话语条件和话语符号构成(赵贺,鞠惠冰,2020)。数字化传播环境下,作为“回应者”的媒体所建构的话语空间展现出:以目击者话语和记者叙事话语构成的复合型话语资源与新闻实践中习得的“受众回应偏好”等经验性话语资源相结合的新闻话语生产;数字公共平台中媒体回应和受众反馈共同“可见”的对等话语关系;以数字媒体技术为依托的媒体回应性话语产制条件;以可视内容为载体,更易于与受众形成感官回应和共情渲染的媒体作证式话语符号。由此形成四元互构的特征。“媒体作证”的责任主体虽然是媒体,但是其责任的实现是通过媒体和受众(或用户)双方共同完成的,数字技术保障了媒体回应性话语空间形成的真实性,其形成的技术性观视也提升了受众的反应能力和对媒体作证实践的“浸入程度”。此时,见证真实的转向体现为双方“共同回应”构建的一个事实更清晰、话语认同度更高的“真实空间”。
综上所述,“媒体作证”是技术介导下,新闻生产者基于目击者和事实,将目击的第一手“证据”材料变为叙事,同时将情感和道德融入“责任”后产制的回应性话语空间。一方面,“媒体作证”强调了以证据为依托的新闻话语生产才能够赋予客体真实和意义,同时也承认了新闻作为文本信息本身的局限性,即从先前“新闻文本”和“记者言说”的作证实践转变为“真实空间”中传受双方相互见证的实践;另一方面,“媒体作证”也反映出真实性如何为复杂的社会惯习所影响,即新闻报道如何建构一种能够被新闻主体认知惯习识别的“真实空间”,在“有效”作证的同时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地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媒体作证”并非指涉媒体一味地偏向用户端而引导受众沉浸于媒体建构的真实。“媒体作证”强调证据意识,始终基于“真实”的目击陈述,②在媒体履行作证责任的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新闻生产的规范修辞结构。
四、受众见证:新闻真实的“体验”转向
在技术中介化背景下,社交媒体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基于情感化真相(emotional truth)的拟态环境,人们对真相的判定标准不再局限于事实本身(史安斌,杨云康,2017),而是基于“媒介化的真实”。从受众见证的角度理解,无论是前文提及的Peters对于“见证者”的分类,还是Zelizer对于“媒体见证”的分类,二者均将受众分为“作为目击者”的受众和“作为参与者”的受众两类。笔者认为,这两类受众的见证实践分别表征了新闻真实的可视化和具身化转变,二者共同保障了“媒介化真实”的合法性,继而完成“受众见证”的全过程。同时,可视化和具身化基于感官身体的体验感知,二者构成了新闻真实的“体验性”转向。
(一)真实的可视化转向:作为“目击者”的受众见证
如今,作为目击者的受众已经不需要媒体作为把关中介来决定谁有资格成为目击者(Ashuri &Pinchevski, 2009:139;Thomas, 2009:101),他们比过去更愿意主动卷入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对信息进行主动的解码,并提供解释性的语境,Das(2011)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解释性参与”。解释性参与之下,视觉作为跨越语言偏差和陌生对象之间认知壁垒的有效方式,催生了目击图片、短视频等“可视化”内容,成为受众见证的主要形式。以此形塑的“可视化”真实兼具“再现性”与“体验性”特征(常江,2017)。笔者认为,可以从受众生产的“可视化目击内容”以及媒体对这种内容的“使用”两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媒体使用目击者可视内容通过引导受众对“新闻现场”的见证形构真实。在“人人都是新闻生产者”的当下,可视化技术不再为媒体独有。由于媒体难以短时间搜集完整的新闻素材,部分新闻媒体会寻求自媒体、独立内容生产者以及目击者原创可视内容的授权许可或协商收编。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在内容勘误、技术核验和目击者隐私保护的基础上,使用受众目击生产的可视化内容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当下受众对“新闻现场”和“即时性”的需求,对于标记新闻现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Ellis, 2009)。另一方面,使用受众生产的可视内容为新闻机构提供一种存在感,即一种“第一时间在场的真实”,以加强新闻机构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性认知(Zelizer, 2007:412),推动对话式新闻的生产。尽管这种“存在感”本身可能因为目击内容细节的模糊而遭到事后质疑,但是对于媒介素养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的大众而言,可视化内容塑造的“真实感”和“易读性”能够使受众迅速实现自身“主动卷入”的愿望,他们急于追求意义阐释因而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内容本身,因此通过使用受众目击素材营造的媒体“存在感”不会轻易消失。
其次,可视化目击内容通过增强新闻内容本身的接近性,营造出一种真实“光环”(Williams, Wardle, Wahl-Jorgensen, 2011 ; Wardle, 2014)。这种接近性一方面体现在可视化内容形构的“具象”真实。即可视内容突出了文本所不具备的声与形,更易于理解和认知,形成了新闻生产的“通俗化转向”( Turner, 2010:22,转引自王敏,扶小兰,2019);另一方面,这种接近性则体现于目击内容“业余化”塑造的“缺憾真实”。正因为受众作为目击者自主生产的视频或图像有模糊、摇晃、失真的质量缺陷,其业余性反而强化了可视化内容的真实感,体现为一种“未经处理的真实性”(王敏,扶小兰,2019),相反地,高品质的现场视频反而会被认为是媒介制造的“现实幻象”。业余的可视化内容增强了受众对新闻现场第一人称视角的体验性感知,缩短了地理距离带来的感知空隙和新闻文本带来的意义局限,因而越来越成为人们选择性接触的信息载体。
当然,以上两者的共性在于,无论是受众见证“新闻现场”认知的真实还是可视内容本身接近性营造的真实,都是经由受众体验形成的感知。因此,真实的“可视化”转变与真实情感和第一人称体验的权威性也变得密不可分(Chouliaraki, 2010)。
除此之外,我们仍需注意,目击文本的业余化也标志着一个以“怀疑阅读”和“虚假目击”为特征的时代逐渐来临(Smith, Watson, 2012),“虚假证人”时代悄然临近。“虚假证人”(false witness)指的是新闻记者或编辑在接收到一段用户生产内容后会自动带入“内容错误”的假设(Wardle, 2014:29),体现为一种媒体对受众目击内容缺乏信任的猜疑文化:
首先,用户提供内容的质量难以保证,包括真实性、个人偏见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因此,在以“数字优先”为发展趋势的新闻机构中,记者必须变得更加“精通技术”(Belair-Gagnon, 2015,转引自Johnston,2016),以充当“侦探”或“专家”角色(Barot, 2013; Browne, 2014),这意味着记者不仅需要精通社交媒体,还需要精通核证技术,以及在工作中增加诸如填写“用户内容核对表”(UGC checklist)(Johnston, 2016)等必须的审核规程。与此同时,这种管理和审核也占据了大量时间(Singer, 2010),影响了记者核心新闻工作的进展及个人职能的履行,挑战了既有的职业惯例。
其次,部分记者倾向于认为用户生产内容挑战了既有的专业主义规范和职业合法性地位。专业记者通常认为“受众无法胜任记者的角色”,因此对受众目击内容的专业性报以质疑态度,并认为对来自用户的内容应该进行明确标记(Singer, 2010),以将记者和用户生产的内容区分。
不过,用户生产内容的价值属性使之与“虚假证人”时代下专业内容的竞争并非呈对立关系,而是表现为新闻真实“体验”转向之下媒体作证与用户回应二者关系的有机充实。一方面,受众对于新闻体验的建构来源于真实性与相关性的感知(Drakopoulou, 2011),用户原创可视内容的“接近性”赋予了受众真实性的感知,而受众目击内容中拍摄的时间、地点以及目击者的在场则赋予了相关性感知,亦在突发性事件中起到了为记者“提供信息源”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用户生产内容本身具有吸引流量和引发“多种声音”讨论的潜力,吸引受众和获得收益的同时,有助于将报道内容从“记者认为受众想知道的”转化为受众“想要知道的”和“感兴趣的”,提升了专业媒体对受众的回应能力,即“媒体作证”的能力。
由此,“可视化”的真实转向将“受众见证”和“媒体作证”有机联结起来,受众通过兼具即时性和在场感的目击内容见证新闻事件的发生,形塑新闻真实性的体验感知,为媒体作证形构了更充实的“回应”空间。同时,记者的新闻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即在内容生产者之上,附加了更具技术含量的内容“鉴别者”角色,新闻实践中的专业主义变迁,也开始转向对“媒体作证”与“受众见证”二者距离的把握。
(二)真实的具身化转向:作为“参与者”的受众见证
可视化的真实虽突破了距离的阻隔,但仍来自于二维平面,是一种离身在场的视觉真实。随着高新技术和智能机器嵌入新闻生产,“身临其境的见证”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Frosh, 2016; Nash, 2017)。“身临其境”是受众“参与见证”的主要方式,在参与见证的实践中,机器作为技术载体通过创制数字界面生成的“对新闻事件物理上和时间上接近的体验”,既塑造了用户对现场存有即“其境”的感知,又呼唤了受者的积极参与和回应。笔者认为,受众见证的真实,其实是通过体验“机器真实”,形成真实之于用户身体感官的嵌入,达成“物证统合于人证”的见证过程。
首先,“机器真实”通过建构符号化的现场体验,形成受众见证的“参与真实”。数字媒体的生产实践中,现场体验仍是“媒体见证”概念的核心(Nash, 2017)。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例,在某种程度上,虚拟现实由技术生产在场体验的能力定义(Steuer, 1992)。虚拟现实是数字机器通过建构大量高像似性的视觉符号,对新闻现场的再生产。对于用户而言,他们通过VR技术赋予的行动“假肢”以及数字界面给予的“操纵自由”,形成从不同位置观看新闻现场的能力。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拟真符号繁杂多变,受众从不同位置接收到的视觉刺激太多,需要识别的符号太多,高度像似的视觉符号所涵盖的内容更显庞杂,如通过设置互动符码,要求用户做出表演性的回应(如接触界面、做手势、看镜头等),人们因此更容易沉浸于符号化的拟真现场,从而忽视对符号的解释(毛湛文,丁稚花,2021)。由于对意义的忽视,只要机器能够生产出足够拟真、复杂的新闻现场,受众的见证文本与自身“想象参与”的体验(Frosh, 2011)趋于等同,那么就会形成受众对真实的“回应”。这种“参与真实”是受众对“现场体验”的见证,它来源于机器真实的转译,是一种符号化的知觉真实。
其次,机器作为真实之“物证”通过建构物质性空间逐渐统合于用户之“人证”,形成真实的“具身”转变。通过数字界面,VR技术对新闻现场空间的建构实质上是对空间物质性的建构,受众感知的真实是经由一种强烈的物化体验或称之为“场景幻觉”(Popat, 2016),形成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的过程。本体感受即我们感觉到的身体朝向、位置,以及感知刺激的本领,本质是一种固有的具身意识(Popat, 2016)。在现象学关系论的框架中,③具身性站在人、技术、生存世界的关系视角,指涉人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技术融入自己的经验中,通过技术来知觉,并由此转化了自己的知觉和身体感觉(唐·伊德,1990/2008:373)。唐·伊德以“眼镜”为例,阐明了戴眼镜的人如何将眼镜这一技术具身化。他认为眼镜的技术很容易让体验者看到一个被重新修正的世界,自然地融入到体验者自身的知觉—身体的经验之中,成为日常的一部分,而眼镜技术本身在此刻已经“抽离而去”。在这里,技术的“透明性”是具身性实现的物质条件(唐·伊德,1990/2008:375)。在新闻作品中,智能机器形构的“现场体验”亦是通过技术的透明性,深入地、全方位地嵌入人类的感官身体当中(谢新洲,何雨蔚,2020),通过塑造知觉真实,将来自机器之物证与用户之人证融为一体,机器真实也随之被统合于用户见证的体验之中。因此,相对于离身性的见证(可视化的目击见证),受众具身性的参与见证可以用如下的变化表示:
〈受众—机器/媒介技术—对真实的见证〉→〈(受众—机器/媒介技术)—对真实的见证(体验)〉。
以新华社云南分社的全景VR新闻《“斯那定珠”传奇》④为例,该新闻作品围绕“一条天路,一个梦想——藏族‘愚公’斯那定珠传奇”展开,结合实地取景,对斯那定珠先生倾尽一生的“巴拉村”进行了全景化构建,全面形塑了真实的具身化转变。
当受众进入VR技术构建的巴拉村场景之后,屏幕的局限随之消失。通过鼠标的按压、拖拽、放缩全景,受众忘却技术本身,将身体浸入VR呈现出的720度俯瞰之中,VR技术因而变得透明化。接着,受众完全依据自己的意愿操纵场景界面中的视觉符号标识,点击全景画面中闪烁的多个引导箭头进入不同的区域,以第一人称视角突破了记者元语言的限制(见图1、图2)。同时,结合不同场景中的声音和场景中的人物设定,受众自然地调动感官身体体验作为“物证”的场景符号,完成了从“观看者”到“体验者”的转变(华维慧,2020),凝聚了“自我参与的真实感”。
如图1中的文字标签所示,亲自“走进”这里的受众可以以留言标签的方式留下自己想说的话,不同受众的留言标识集合形成的情感网络,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虚拟在线和情感共在,受众的身体由后台转向前台之时,对真实的认知方式也实现了从抽象认知到互动感知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天路”场景中镶嵌着一个“新华社采访现场”箭头,受众进入VR采访现场后,可以看到斯那定珠和新华社记者们的目光共同看向镜头,给予受众亲临新闻现场的对话体验,缩短了情感距离(见图3)。同时,各位记者和斯那定珠先生都以真实的面貌呈现,在感官体验中凝聚着“媒体作证”的意涵,此刻,机器形构的“物证”因媒体记者之“人证”与受众之“人证”的相遇,化身为透明化的“体验”中介。
认知依赖人的身体、环境以及主体经验(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1980/2015:56-83)。VR技术加持下,人与媒介的关系范式发生转变,随着身体被推向前台,新闻叙事时空的场景化借助身体与技术环境的互动延展了受众的认知,强化了认知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殷乐,2020),因此,感兴趣的受众不需要跨越地理的阻隔,而是感官“旅行”进行身体介导,在机器构建的“假肢”体验中,实现了真实的具身化转变。
当然,真实的具身化转变除了体现于VR新闻,还实现于穿戴设备、全景直播、大屏互动等诸多形式,并非每类选题都适用同一种呈现方式,也并非每一位受众都能通过参与《“斯那定珠”传奇》中同类型的具身体验形成真实的知觉。笔者选择此案例因其具有典型性。对于作为“参与者”的受众而言,《“斯那定珠”传奇》给予受众自由探索的空间,在探索新知中调动感官身体认知事实,在场景切换中体验真实。媒体通过虚拟场景中的标记设置、知识互动、场景切换等“物证”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临场感和现实感,将“物证”寓于用户的“身体之证”之中,同时媒体自身的“在场”也构筑了“媒体作证”的效果,营造出一种媒体与受众“共同见证”的体验真实。
五、结语:从“见证真实”的理解转向对新闻真实边界的反思
走笔至此,笔者在这里对前面所论述的内容进行总结。笔者认为,随着虚拟现实、5G网络、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赋能新闻生产,新闻内容可以为受众提供从信息获取到知识体验再到理解接受的金字塔形结构的价值增值路径(Picard, 2010,转引自杭敏,2017)。在“技术中介化”和“新闻真实边界消解”的现实背景下,探讨如何“实现”新闻真实很难有结果,关注新闻真实“理解方式”的转变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明晰新闻业的发展进路和制度条件变动。笔者认为,“见证真实”转向的提出有以下几点意义:
首先,“见证真实”提供的是一种理解转向,注重对这种转变过程的分析。新近研究中关于新闻真实的说法,如信任真实、假设真实、理解真实、有机真实等虽进步性地融入了技术变革和收受主体地位转变的思考,但大多强调的是“如何实现新闻真实”的描述,都可以归纳为一种“互动真实”的结果。正因为注重转向的过程,“见证真实”不仅关注“接收领域”,而且关注逐渐被置于从属地位的“生产领域”,并注重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与距离变化。
其次,“见证真实”转向的提出兼顾了新闻真实探讨中的“变与不变”。这种转向的提出并非追逐求新、抛弃旧思,而是在“依据真实”和“见证新闻”的理论基础上,以新闻生产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的“证据”作为“见证真实”的事实保障,并结合技术、主体、生产关系等制度条件的变化展开论述。
最后,“见证真实”转向告知着,在“人人拥有自我真相”的“认识论民主化”时代,价值论维度的探讨对于理解新闻真实问题的重要性。“见证真实”转向的论证过程中看似出现较多诸如“认知”、“感知”等具有认识论色彩的词汇,但其实笔者是在强调如今的新闻真实应是一个包含受众情感、心理因素,回答“能否帮助了解现实世界”的价值论问题,体现为以“回应”和“体验”为核心的,理解新闻真实的全新方式。
一方面,“回应”指涉“媒体见证”层面的真实转向,涵盖了新闻生产中技术实践、专业规范和职业伦理等方面的探讨。笔者认为,“媒体作证”的实现,是技术介导下,新闻生产者基于目击者和事实,将目击的第一手“证据”变为叙事、将情感和道德融入“责任”后产制的回应性话语空间。首先,“媒体作证”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与“媒体见证”的区分,强调媒体应当作为新闻中的作证者而非目击见证者;其次,它既涵盖了媒体对“目击”真实性的专业主义要求,同时也兼顾了“新闻真实”的相对性,注重媒体责任以及与受众的联系,强调真实是媒体话语建构的“真实空间”中双方的共同回应、相互见证。
另一方面,“体验”指涉“受众见证”层面的真实转向,分别对应真实的可视化转变和具身化转变。笔者认为,可视化的真实转向对应了如今“专业与业余”鸿沟消弭的趋势,它通过视觉刺激构筑的接近性体验与“虚假证人”时代专业媒体对用户生产内容的“怀疑阅读”充实了“受众见证”和“媒体作证”的关系,保障新闻体验的真实性。除此之外,具身化的真实转向根源于“机器真实”对物质性空间的形构,体现为第一人称“参与真实”之体验的形成和机器之物证统合用户之人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感官身体在新闻真实中起到的作用应当引起重视。随着有机体和技术系统的互嵌,“赛博格”的用户将感官知觉重新整合进入主体当中,媒介越来越成为感官的媒介(谢新洲,何雨蔚,2020)。感官身体是具身体验的基本单位,亦是受众对新闻内容“价值增值”和“真实感增值”感知的依凭。
回归到“见证真实”本身,“见证真实”转向主要来源于见证主体在新闻生产和接收实践中的变化。相较于单一化传播主体垄断的时代,如今新闻生产的用户导向使得“受众见证”越来越成为新闻真实判定的标准,“受众见证”的重要性看似统摄了“媒体作证”。由前文所述,受众见证主要体现为新闻真实的“体验”转向,可视的和具身的真实转变都来源于技术介导下体验形式的革新。但是,这种体验形式来源于媒体生产,是传受主体相互建构和回应的结果,所以受众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受媒体技术和媒体话语,即“媒体作证”建构的“回应性空间”影响。在新闻生产制度规范和媒体数字化驱动之下,回应性空间与受众体验的融合,内嵌于各种话语、影像和文本符码的组合,本质上建构了新闻真实的“形式空间”。
拉康(1975:85)认为,真实是形式的绝境。阿兰·巴迪欧以初等数论为例做了进一步阐释,他阐释道,我们在做乘法的时候,因为我们确信结果会是一个有限数字,并不存在一个最终的数字。但是遵循我们计算条件的数列是没有尽头的,它是有限计算中隐藏的无限,无法进入形式化之中,因此是形式化的绝境(阿兰·巴迪欧,2016/2020:31)。由此,到达完全的真实并非通过形式化的应用,而是当我们探索对于这个形式化来说不可能的某物时,才能到达真实。应用于可视化新闻产品,它表现出的真实力量并不属于视觉化产物本身,而是在它以外之物的基础上被构建,才会达到高保真和高卷入度。因此,外视域空间即镜头之外的世界是可视化新闻产品的无限,它包括没有入画的一切可能性,以及营造视觉感官的技术空间。我们所看到的并非真实本身,而是真实的形式外表,即真实之真实。
笔者并非想通过上述讨论将新闻真实纳入不可知论的范畴,而是为了阐释“见证真实”与“完整真实”的边界。我们感知到的最强有力的真实,往往是真实的外表以及萦绕这个外表的表象出现之时刻,如镜头中目击者的阐述和目击者的情态。这并不是说真实的外表不真实,而是指涉能被我们感官捕捉到且足够满足认知需求的真实的一部分。“见证真实”转向中表征的回应性和体验性的真实转向,近似于学者杨保军(2020)曾论及的“部分真实”,只不过从见证主体的角度考虑,这种部分真实在数字化传播环境下,更趋近于有限度的、基于基本事实的表象真实,寓于最易被知觉的“形式空间”中。因此,对数字化传播环境下新闻真实边界的理解,或许可以转化为对新闻产品所建构“形式空间”知觉的真实与否,和表象真实对应的基本事实存在与否的辨析。
最后,本文“见证真实”的提出仅是笔者转换思路的一次尝试,是笔者对数字时代关于新闻真实“理解”转向的一些粗浅思考。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也做了一些详略的处理,对“见证真实”转向的诠释使用了较多的笔墨,对其值得商榷之处的反思可能并非面面俱到。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使得如今的新闻形式更加新颖、多元,而关于新闻真实问题的思考始终需要跟随新闻生产的变化持续关注,制度、技术、内容之外,责任、伦理和边界或许将成为更有价值的思量之维。■
注释:
①“无蔽”来源于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一文中对真相的讨论,即不隐藏,不遮蔽。海德格尔认为,“无蔽”中的真相与非真相关联在一起,“错误和被掩盖的东西”也属于“真相的原始本质”。
②“真实的目击”这里指的是,“媒体作证”不能基于媒体夸大、编造、或者受到资本牵制的目击内容,要保证目击内容本身的真实性。数字化传播环境下,多以不经后期处理的视频、图像等“可视化证据”呈现。
③唐·伊德认为,可以从相对论的角度理解现象学,现象学和相对论一样,都考虑经验者和经验领域的相对性关系。
④本案例选自新华社云南分社的VR新闻作品,链接为:https://720yun.com/t/7b52bmzkccg?scene_id=536695,最后访问于2021年9月13日。
参考文献:
阿兰·巴迪欧(2016/2020)。《追寻消失的真实》(宋德超译)。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
白红义(2019)。点击改变新闻业?——受众分析技术的采纳、使用与意涵。《南京社会科学》,(6),99-108。
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2011/2014)。《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陆佳怡,孙志刚,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操瑞青(2017)。作为假设的“新闻真实”:新闻报道的“知识合法性”建构。《国际新闻界》,(5),6-28。
常江(2017)。蒙太奇、可视化与虚拟现实:新闻生产的视觉逻辑变迁。《新闻大学》,(1),55-61+148。
陈卫星(2004)。《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
盖伊·塔克曼(1978/2021)。《做新闻》(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景萍(2006)。社会合理性与社会合情性—对人性化社会何以可能的一种思考。《学术交流》,(10),135-139。
杭敏(2017)。融合新闻中的沉浸式体验—案例与分析。《新闻记者》,(3),76-83。
华维慧(2020)。从诠释到具身:虚拟现实技术对新闻真实的再生产。《新闻界》,(11),86-93。
华维慧(2021)。边界突破与真实重构:论VR新闻的真实性逻辑。《编辑之友》,(2),71-75。
李唯嘉(2020)。如何实现“信任性真实”: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基于对25位媒体从业者的访谈。《国际新闻界》,(4),98-116。
李东晓(2019)。界外之地:线上新闻“作坊”的职业社会学分析。《新闻记者》,(4)15-27。
刘建明(2016)。新闻的第七要素及新闻见证者。《新闻爱好者》,(11),20-24。
刘沫潇(2020)。全球视野下的新闻真实探索:理论阐释与实际考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
刘鹏(2020)。“全世界都在说”:新冠疫情中的用户新闻生产研究。《国际新闻界》,(9)62-84。
马丁·塞尔(1998/2008)。实在的传媒和传媒的实在。载西皮尔·克莱默尔(主编)。《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毛湛文,丁稚花(2021)。符号拼接与界限消失:“内爆”视角下可视化新闻报道的视觉批判。《青年记者》,(10),26-29。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1985/2015)。《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让·鲍德里亚(1979/2011)。《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史安斌,杨云康(2017)。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国际新闻界》,(9),54-70。
孙婷,陈堂发(2020)。保证与核证:新闻真实的实现路径。《新闻爱好者》,(12),14-18。
唐·伊德(1990/2008)。《技术与生活世界-第5章“纲领一:技术现象学”》(韩连庆译),载吴国盛(主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王敏,扶小兰(2019)。目击者视频:融合路径与伦理挑战。《新闻与传播评论》,(6),45-54。
沃尔夫冈·韦尔施(1998/2008)。“真实”—意义的范围、类型、真实性和虚拟性。载西皮尔·克莱默尔(主编)。《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晓春(2005)。新闻真实性的重新审视。《当代传播》,(4),45-48。
谢新洲,何雨蔚(2020)。重启感官与再造真实:社会机器人智媒体的主体、具身及其关系。《新闻爱好者》,(11),15-20。
亚里士多德(1959)。《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杨保军(2006)。《新闻真实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保军(2017)。再论“新闻事实”—技术中介化的新闻事实及其影响。《新闻记者》,(3),22-30。
杨保军(2020)。准确理解新闻的“整体真实”。《新闻界》,(4),35-42+5。
殷乐,高慧敏(2020)。具身互动: 智能传播时代人机关系的一种经验性诠释。《新闻与写作》,(11),28-36。
赵贺,鞠惠冰(2020)。话语空间与叙事建构:论突发事件国际舆论场域中的中国话语权。《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12),51-55。
Allan, S. (2013). Citizen witnessing: Revisioning journalism in times of cri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ndén-PapadopoulosK.& Pantti, M. (2013). Re-imagining crisis reporting: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and citizen eyewitness images. Journalism, 14(7)960-977.
AshuriT. , & Pinchevski, A. (2009). Witnessing as a field. In P. Frosh & A. Pinchevski (Eds. )Media. witnessing: Testimony in the 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 London: Palgrave.
Baudrillard.B J.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lair-GagnonV. (2015). Social Media at BBC News: The Re-Making of Crisis Reporting. New York: Routledge.
Boltanski, L. (1999). Distant Suffering: Morality,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eM. (2014). “Verifying Video. ” In Verification Handbook: A Definitive Guide to Verifying Digital Content for Emergency Coverage, edited by Craig Silverman45-51.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Burke, P. (2001). Eye-witnessing: The use soft images ashistorical evid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runs, A. (2008). BlogsWikipediaSecond Life and Beyond, NY: Peter Lang.
ChristiansC. G. (2015). Introduction: Ubuntu for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30(2)61-73.
Carlson, M. (2009). The reality of a fake image: News normsphotojournalistic craftand Brian Walski’s fabricated photo. Journalism Practice, 3(2)125-139. doi:10. 1080/17512780802681140.
Chouliaraki, L. (2009) Witnessing war: economies of regulation in reporting war and conflict.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2215-226230.
Chouliaraki, L. (2010). Ordinary witnessing in post-television news: Towards a new moral imaginatio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7(4)305-319.
Das. R. (2011) . Converging Perspectives in Audience Studies and Digital Lite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4) :343-360.
Drakopoulou, S. (2011). User Generated Content. An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qualities and elements of authenticity and immediacy in UGC.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ing Research Paradigms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Nov 2011 - 24 Nov 2011.
Frosh, P. & Pinchevski. A. (2009) Media Witnessing: Testimony in the 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rosh, P. (2011). “Telling Presences: Witnessing, Mass Media and the Imagined Lives of strangers. ”In Media Witnessing: Testimony in the 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edited by Paul Frosh and Amit Pinchevski, 49-7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Frosh, P. (2016). The mousethe screen and the Holocaust witness: Interface aesthetics and moral response. New Media and Society20(1)351-368. doi:10. 1177/1461444816663480.
Jacques Lacan. (1975). Le Savoir et la Véritéin Le Séminaire, Livre XX: Encore, Paris: Seuil.
Jean Baudrillard.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JohnstonL. (2016). Social news= journalism evolution? How the integration of UGC into newswork helps and hinders the role of the journalist. Digital Journalism, 4(7)899-90.
Lisette Johnston (2016). Social News = Journalism Evolution?Digital Journalism, DOI: 10. 1080/21670811. 2016. 1168709.
NashK. (2018). Virtual reality witness: exploring the ethics of mediated presence. 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 12(2)119-131.
OliverK. (2004) Witnessing and Testimony. Parallax 10(1): 78-87.
ParkR. E.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5(5)669-686.
ParkR. E. (1955). SocietyNY: The Free Press.
PetersJ. D. (2001). Witnessing. MediaCulture & Society23(6)707-723. doi:10. 1177/016344301023006002.
PetersJ. D. (2008). An afterword: torchlight red on sweaty faces. In: Frosh P and Pinchevski A (eds) Media Witnessing: Testimony in the 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icardRobert G. (2010)“Value creation and the future of news organizations: Why and how journalism must change to remain releva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diva-portal. org.
Popat, S. (2016). “Missing in Action: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Theatre Journal68 (3): 357-378.
SingerJ. B. (2010). Quality Control. Perceived Effects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on Newsroom NormsValues and Routines. Journalism Practice, 4 (2): 127-142.
SteuerJ. (1992). Defining virtual reality: Dimensions determining telepres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2(4)73-93.
Smith, S. , & Watson, J. (2012). Witness or false witness: Metrics of authenticity, collective I- formations, and the ethic of verification in first-person testimony. Biography-An Interdisciplinary Quarterly35(4)590-626.
SundarS. S.Kang, J.& Oprean, D. (2017). Being there in the midst of the story: How immersive journalism affects our perceptions and cognitions. Cyberpsychology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1)672-682.
TaitS. (2011). Bearing witnessjournalism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MediaCulture & Society. 33(8)1220-1235.
ThomasG. (2009). Witness as a cultural form of communication. In P. Frosh & A. Pinchevski (Eds. )Media witnessing. Testimony in the 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Trushar. (2013). UGC: Source, Check and Stay on Top of Technology. BBC College of Journalism, 17 December 2013. Accessed 29 June 2014. http://www. bbc. co. uk/blogs/collegeofjournalism/entries/1fbd9b88-1b29-3008-aae6-1cab15e13179.
TurnerG. (2010).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media: The demotic turn. Sage Publications.
WardleC. (2014). Verifying user-generated content. In C. C. Silverman (Ed. )Verification handbook: A definitive guide to verifying digital content for emergency coverage, 24-33.
Wieviorka, A. (2006). The witness in history. Poetics Today27(2)385-397. doi:10. 1215/03335372-2005-009.
WilliamsA.Wardle, C.& Wahl-Jorgensen, K. (2011). “Have they got news for us?” Audience revolution or business as usual at the BBC?. Journalism Practice, 5(1)85-99.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elizer, B. (1998). Remembering to forget: Holocaust memory through the camera’s ey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elizer, B. (2007). On “having been there”: “Eye-witnessing” as a journalistic key word.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4(5)408. doi:10.1080/07393180701694614.
金圣钧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