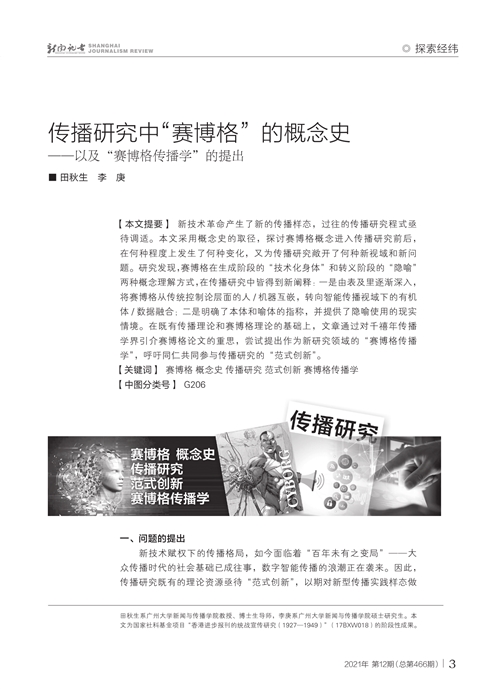传播研究中 “赛博格”的概念史
——以及“赛博格传播学”的提出
■田秋生 李庚
【本文提要】新技术革命产生了新的传播样态,过往的传播研究程式亟待调适。本文采用概念史的取径,探讨赛博格概念进入传播研究前后,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何种变化,又为传播研究敞开了何种新视域和新问题。研究发现,赛博格在生成阶段的“技术化身体”和转义阶段的“隐喻”两种概念理解方式,在传播研究中皆得到新阐释:一是由表及里逐渐深入,将赛博格从传统控制论层面的人/机器互嵌,转向智能传播视域下的有机体/数据融合;二是明确了本体和喻体的指称,并提供了隐喻使用的现实情境。在既有传播理论和赛博格理论的基础上,文章通过对千禧年传播学界引介赛博格论文的重思,尝试提出作为新研究领域的“赛博格传播学”,呼吁同仁共同参与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关键词】赛博格 概念史 传播研究 范式创新 赛博格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技术赋权下的传播格局,如今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大众传播时代的社会基础已成往事,数字智能传播的浪潮正在袭来。因此,传播研究既有的理论资源亟待“范式创新”,以期对新型传播实践样态做出更有力的回应与阐释。学者们已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尝试:黄旦(2015)以媒介为重点和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倡导报刊(媒介)史的新范式;刘海龙(2018)和孙玮(2020)从不同角度,呈现出身体议题对传播研究的创新价值。
上述研究虽具备建设性,但多以宏观视野下的整体思辨结构成文,而作为新传播实践具体表征和近年来传播学界重要聚焦点的“赛博格”,则提供了让相关知识图谱进一步纵深演进的可能。国外传播学界自2000年开始引介“cyborg”(Gunkel, 2000),并在近年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研究成果;国内的苏涛和彭兰(2019)也选定“赛博格时代的传播图景”作为年度新媒体研究综述的标题。不过,由于赛博格概念本身极其复杂,传播研究者在某种程度缺乏共通的意义空间,这无疑会对其进一步的理解和运用造成偏误。由此,需要解决的赛博格—传播议题如下:赛博格在进入传播研究前后,该概念究竟于何种程度发生了何种变化?一体两面来看,新概念的接受又为传播研究敞开了何种新视域、新问题?
概念史的研究路径,可能会对上述议题的回应有所裨益。概念是对意义的聚集,是对历史过程中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集中体现,并在一定语境中为了特定目的而使用(李宏图,2012)。同时,概念亦是“问题的纪念碑”和“思想的出口”,通过对词义出处、延续或变化的查考,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作用(方维规,2013)。由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考泽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开创的概念史通过研究关键且多义的概念在时空中的接受、转移和扩散,即对概念做历时性和语境化的考察,以揭示其是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关键要素。目前,概念史的研究实践在传播领域方兴未艾,研究者曾对“电视”、“互联网”和“舆论”等重要概念进行过新视角下的解读(邓绍根,2015;方兴东,钟祥铭,彭筱军,2019;段然,2019)。前人的累累硕果,为“赛博格”的概念史考察提供了有益参照。
综上所述,我们确立了本文的基本考察维度:一是现象层面,需要搜集并分析辞典、数据库、学界论著和业界报道等材料,厘清赛博格的概念是由何人、何时提出和发展的,其意涵在进入传播研究前后经历了何种变化;二是机理层面,主要探讨赛博格概念进入传播研究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概念的提出者和发展者是怎样的人?他/她处于怎样的时代和文化共同体之中?种种因素是如何影响概念流变的?三是概念的能动性或者说建构性,即探讨赛博格是如何在不同阶段和情势下,激发了现实关照下理论延展和重构的可能,尤其要重点探讨当概念进入传播研究以后,是如何命名了智能传播的实践和回应了范式创新的需求。
二、进入传播研究前的赛博格(1960年至2000年)
(一)概念的产生(1960年的“实验”):作为“技术化身体”的“赛博格”
远在希腊神话里的“喀迈拉”和科幻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赛博格的形象就有端倪可查,然而相关概念的成型,离不开20世纪下半叶特定的政治需求和军事工业的支撑。一般认为,“赛博格”的概念由美国航天医学空军学校的曼弗雷德·克林斯和内森·克兰(Manfred Clynes & Nathan Kline,1960)提出。在上世纪美苏冷战背景下的太空飞行实验中,两位科学家在小白鼠身上安装了可自动注射化学药剂的渗透泵。他们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赛博格与太空》(Cyborgs and Space)(可在由Chris Gray等主编的1995年版的《赛博格手册》(The Cyborg Handbook)里查询此文)里,从“控制论”(cybernetics)和“有机生物体”(organism)两词各取前三个字母,为这只特别的白鼠赋予新名:“cyb-org”。同年7月出版的《生活》(LIFE)杂志,还专门刊登了“Man Remade to Live in Space”的赛博格特辑。
“cyb”源自控制论的英译“cybernetics”。它的希腊词源是kubernētēs(掌舵者,操纵者)和kubernan(掌舵,驾驶,操纵,控制),柏拉图常用其指代对城邦政治的操控术(G·克劳斯,1981:17)。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2017:1)曾在1948年的著作里正式提出控制论——一项关于在人、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讯的科学研究。后来的韦氏词典也延用此种解释(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ow people, animals, and machines control and communicate information)。①值得注意的是,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源于他在二战期间的军用研究。他认为驾驶熟手已与飞机的机械装置融为一体,所以作为一种“技术凝视”(technological gaze)的防空预警器,可以利用敌人/敌机的飞行习惯,来预测其未来航向并予以精准打击。而“org”则语出有机生物体的英译“organism”,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2005:338-341)在他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专门开辟了相应章节。“organ”的希腊词源是órganon,拉丁文叫organum,皆指工具器械。英文的organism作为衍生词在17世纪出现,它普遍的现代意涵源自18世纪博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发展,主要指涉生物的生长。待到19世纪,其常被用于带有保守色彩的政治话语中,隐喻社会是由器官组成的身体,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认为此种有机的(organic)凝聚具有功能相互依赖的意涵。
综观克林斯和克兰实验的初衷,和“cyborg”的两个出处——控制论“cybernetics”加有机生物体“organism”,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技术化身体”(technologized body)的相应特征。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曾对此做过精妙阐释:“最早可追溯到人类驯化火以后,技术对人的身体,以及人所生存的周围环境开始了深远的影响。人运用技术来转化其所处环境之时,也就开始改变自身及其肉体的潜能”(希林,2011:193)。他将“技术化身体”分为三种具体类型:“诉诸修复技术的身体替代(physical substitution);旨在补充并提高身体与环境结合的能力的身体拓展/改进(physical extension /enhancement);摆脱生物身体局限的虚拟身体共同体转变 (communal/political transformation)”(希林,2011:204)。1960年的“实验”主要属于第二类,旨在通过药物或外科手术对军人的身体机能进行增强,解决呼吸、失重、新陈代谢和辐射效应等问题,形成成熟的自稳态系统(his own homeostatic systems),使他们在严酷的太空环境和军备竞赛中能更好地生存。不难发现,此时人们对赛博格的理解,还停留在一种相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定位,技术装置是“为我所用”,起到辅助和拓展的作用。从1996年开始收录“cyborg”的《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Reference Dictionary)给出了赛博格在此意义上的解释:“人的机体性能经由机械拓展从而超越生理限制的新身体。”
随着冷战的“回暖”,这种“技术化身体”的赛博格实验,逐渐从军用转向范围更普遍的民用。从人造假肢、人工耳蜗到心脏起搏器,此类技术手段重构了肉体的某种物理属性,为很多残障人士带来了福音。首位被法律承认的赛博格——英国艺术家尼尔·哈比森(Neil Harbisson, 2017),因先天严重色盲,决定在自己颅骨处安装能“听见”色彩的电子天线。②他在接受《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的专访时说,“与神经控制设备相结合,我已然成为一种技术形态”。③多伦多的电影制作人罗伯·史彭斯(Rob Spence)在事故中失去右眼,选择在同样的位置安装一个装有无线摄像机的电子眼,并用它拍摄了名为Deus Ex: The Eyeborg Documentary的纪录片。④此外,这种技术增强还被进一步用在对分子级身体(molecular body)的理解和编码中,诸如现代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使“将身体作为机器,对更微观的零件进行架构和操纵”的笛卡尔主义得以复兴(张灿,2018)。“增强进化论”的鼓吹者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 2007:2)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设想不谋而合,“人类通过发展以及利用技术,从而提升自我的心智、身体和潜能,从根本上改变和设计人的条件,这种做法是合理且正当的”(斯威特,2015)。而谨慎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2017:131)则不想目睹“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对此反驳道,“人性是承载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其界定了人最基本的价值,并提供了人作为一个稳定和持续的物种之根基。技术的滥用则会改变人性及后代特征,人体重铸之际乃灵魂死亡之时”。
由此我们发现,在赛博格概念的生成阶段(1960年至1985年),其提出者是两位航天科学家,而占主导地位的理解方式是“技术化身体”。赛博格的提出有着上世纪40年代维纳“控制论”的理论滋养,但更离不开特定政治环境下军备竞赛的需求,即要用技术手段打造一批能适应太空环境的“未来战士”。而当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后,相应的技术实践也逐步向医疗等民用领域开放;另一方面,赛博格的技术构想又作为一种“思想性力量”引发了后世关于增强进化论和超人类主义的伦理争论。
(二)概念的转义(1985年的“宣言”):作为“隐喻”的“赛博格”
赛博格自1960年提出以来,多被当作一个新潮科技词汇来使用,将其本身视作“技术化身体”的概念理解方式,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直至1985年,哈拉维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上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它(指赛博格)是控制有机体、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社会现实和科幻小说式虚构着的创造物(Haraway, 1991:149)。”她大胆指出,基于控制论思想而产生的赛博格是一种颠覆性的存在论隐喻。隐喻(metaphor)在韦氏词典里被定义为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修辞术,即通过一个单词或短语以一事物替代另一事物,以此暗示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相似性或类推性。⑤当然,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中有关词汇的问题,还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和认知的基本方式。“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并不仅仅在语言中,也在思想和行为中。它构造出我们所感之物,我们如何在世间生存并与别人相关联”(莱考夫,约翰逊,2015:1-3)。也就是说,作为“隐喻”使用的“赛博格”,不再只是关涉自身的“实体即本体”,而增加了作为指代他物的“喻体”维度。《哈拉维读本》(The Haraway Reader)也明确写道:赛博格不仅是生物意义上肌体机能的技术改造,更是在社会学、认知科学、军事话语等历史—文化实践中完成的象征界改造(唐娜·哈拉维,赵文,2021)。
再回到1985年的文本中。哈拉维认为科技改变和模糊了自然及其人们习以为常的界限,实现了三次关键性和突破性的“隐喻”:首先是对人类与动物界限的颠覆,对两者的区分愈发困难且没有必要。其次是人与机器之间不再泾渭分明。恰如媒介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2011:61)所形容:“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哈拉维(1991:152)对此强调,“20世纪晚期的机器完全模糊了这样的差别:自然与人工、思想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等等。机器令人不安地栩栩如生,而我们自己却令人恐慌地了无生气”。于是,来自上帝之手的人体已然和来自人类之手的机器裹挟在一起,形成了崭新的混合实体(hybrid entities)。最后,由信号、电磁波、光谱片段构建的微电子设备的广泛运用,表明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正被打破。“赛博格是以太,是精华……它们在政治上就像在物质上那样难以看清”(Haraway, 1991:153)。显然,哈拉维对赛博格的关注点,并非对基本概念的精确界定,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极具延展性的思想资源,以批判性地观照技术变革和政治生活。于是,作为多重隐喻的赛博格,“构建起边界战争和历史转变的无限可能”(Haraway, 1991:150)。
被引用数千次和翻译为十几种语言的“赛博格宣言”是20世纪末学术界的传奇(Hayles, 2006)。而哈拉维在接受访谈时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认为标题的命名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Marx’s Communist Manifesto)某种意义上的致敬。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女权运动(US socialist feminism)和新左派运动(new Left movements)是该文重要的文化历史背景,而拥有灵长类动物学家转至科学史学家的学科背景,让她对各种情境中的“非人”因素(the various non-humans on the scene)始终葆有兴趣,这是“赛博格宣言”的写作缘由(Gane, 2006)。
如果说,哈拉维的“宣言”是一个后现代意义上复杂而多元的文本,那么其中的“赛博格”则是一种绝妙的隐喻。这既体现在文章诸如“喀迈拉”(chimeras)、“本体论”、“反讽的政治神话”等具体表述方式上,更体现在“赛博格隐喻观”为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灵感火花。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作为哈拉维及其赛博格思想最重要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就将该概念视为一个历时性特定和偶然的术语,而非稳定的本体论(Hayles, 2006)。自我的身体是人类最初操控的“假肢”(artificial limb),那么在各种情形下寻找可资扩展或替代的新型假肢,就成为“赛博人”生活之隐喻(海勒,2017:3-4)。1999年,海勒将自己过往十余年的重要论文集结成书,缘于英语文学和化学的双重专业背景,她既能对赛博格相关科幻作品进行批判性解读,亦能从前沿的控制论和信息科学汲取养分,这也导致她同时关注赛博格物质性的存在样态和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在线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海勒,2017:6)。她更是大胆断言,目前诸如面对计算机屏幕的职业键盘手、由光纤显微镜引导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以及电子游戏厅的青少年玩家等新兴从业群体的出现,使他们成为隐喻化赛博格(metaphoric cyborgs)的几率大幅增加,目前美国至少10%的人口已为赛博格(Hayles, 1995:322)。
在赛博格概念的转义阶段(1985年至2000年),将其作为喻体而非“技术化身体”实体的认知方式占据主流,1985年“赛博格宣言”无疑是开启此种转向的关键节点。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中,以哈拉维为代表兼具科学训练和人文素养的理论家们,在赛博格“技术与身体结合物”的意涵外,开拓了其政治文化的符号化隐喻,以及对历史社会的全面性表征。同时,内涵获得极大丰富的赛博格概念,既作用于像《攻壳机动队》(1995)、《黑客帝国》(1999)等科幻电影为代表的“数字化文艺复兴”(潘汝,2020)创作实践当中;更是频繁出现在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如女性主义研究(Braidotti, 1994;Sandoval, 1995;Howell, 1995)、文化研究(Featherstone & Burrows, 1995)、电影研究(Pask, 1995;Larson, 1997)、文学批评(Clayton, 1996;Lindberg, 1996;Williams,1998)、科幻小说研究(Harper, 1995;Davidson, 1996;Siivonen, 1996)、哲学和宗教(Brasher, 1996)、人类学(Downey, Dumit & Williams, 1995)、跨学科研究(Shanti, 1993;Biro, 1994;Porush, 1994)以及计算机信息科学研究(Turkle, 1995;Reid, 1996)等。
总体来看,赛博格概念在进入传播研究之前,有两个关键的节点。首先是概念的正式提出,源于1960年冷战背景下两位科学家的太空实验,主要将其理解为“技术化身体”的“实体”;其次是概念的意义转移,源于1985年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以哈拉维为首的大胆宣言,主要将其理解为“隐喻”,这两种理解方式都为后续相应的理论和实践赋予可能。不过,如果固守“技术对人增强”的工程学出发点,已不能很好概括各项研究对概念的多维度使用,也遮蔽了概念本身的思想性和丰富性;而太过“漂浮的能指”,可能很大程度上会导致“词”与“物”的分离,使概念本身面临合法性危机(李国栋,2020)。严格来说,这两种理解方式都存在着进一步阐释和完善的空间,而2000年传播研究对赛博格概念的引介则恰好为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来自传播学科的重要贡献。
三、进入传播研究后的赛博格(2000年至今)
(一)概念初入传播研究(2000年贡克尔的“你我皆博格”)
赛博格进入传播研究的时间节点和标志性事件虽不像1960年概念生成的“实验”和1985年概念转义的“宣言”那般明显,但概念本身进入传播研究后的变化和对传播研究的启发却意义深远。笔者以“cyborg”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平台SSCI论文库的communication专题、SAGE数据库的Communication & Media Studies专题,以及Google Scholar里以communication为关键词进行联合检索,发现2000年任职于北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系的大卫·贡克尔(David Gunkel),⑥在当时属于SSCIQ1区的《传播理论》期刊上发表论文《你我皆博格:论赛博格和传播命题》(“We Are Borg: Cyborgs and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Gunkel, 2000),可能是最早将赛博格引介到传播研究的学人。当然,笔者这个判断也有来自同仁的交叉验证(Merrick, 2007)。此后,贡克尔一直深耕于技术哲学和机器伦理方向,出版了数种相关专著和数十篇相关论文,也带动了诸如安德里亚·古兹曼(Andrea Guzman)等本系青年教师发表相关领域的高被引顶刊文章。
具体来看2000年的这篇论文。贡克尔以哈拉维对赛博格概念的贡献和影响做引,判断人们当下对赛博格在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传媒领域之前景开始有所期待。他首先对1985年的“宣言”发问:“我们怎么就已经是赛博格了?我们能以何种方式融入这种理论化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体之中?”接着,他结合自身所在的传播研究进一步思考:“这种混合对传播学科意味着什么?对于以人类交流为主旨、以人类个体为基本分析单元的学科而言,这个还没到‘人’又不止是‘人’的复杂角色会带来什么后果?”由此,他对这两个具有紧密逻辑关联的议题,以“人类之终结”(The End of Man)和“传播之主题”(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为小标题展开论述,认为赛博格是“生存在边界”(living on border lines)且打破将人类主体与其传统对立面(如动物或机器)二元区分的混合体,作为西方特定历史和意识形态语境下的后现代思想和后殖民理论的构成基石(cornerstones),对传统人文主义之“人”的概念和定义造成极大侵蚀。他以香农和韦弗的《通信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作为现代传播科学形成的标志(Fiske, 1994:6),认为传播研究的起源是对“自然”形式的远程通信技术及其机制的探索,传播学总是且已是一种赛博格程序(part of a cyborg program)。如哈拉维所言,“赛博格是文本、机器、身体和隐喻——在传播方面进行理论化和从事实践”(Haraway, 1991:212)。贡克尔总结道:赛博格不构成一个先验的并积极参与传播过程的可视化主体,相反,其本身受制于并最初就被交互化的传播所界定和激活。凭此方式,赛博格对“主体性概念、传播活动和他们被感知的关系”都造成根本性变革:首先,在一定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赛博格主体,往往是关系型的,可变的,基本是非实质性的;其次,赛博主体性不完全起源于有意义的传播活动,但其本身即是交流的产物;最后,单个的博格实体只是矩阵内的节点,而赛博格则是基于关系在网络中构建或重构的整体。
贡克尔的这篇文章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前瞻性,但仍有两点遗憾:其一,他所依据的理论前提较为单一,且最后并未在传播实践层面很好地展开赛博格主体潜能之探讨;其二,在接下来十余年内,传播学界几乎搁置了这个极为重要的议题,没能及时进一步研讨和挖掘这座理论富矿。反而,这段时间内,在计算机通信领域(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和人机交互领域(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赛博格—传播议题激起了较大的回响。杰拉尔德·格林伯格(Gerald Greenberg, 2007)发表《机器人话语:技术对通信的转化》,证明赛博格为传统的CMC研究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肯尼思·弗莱施曼(Kenneth Fleischmann, 2009)亦认为HCI的发展趋势之一是人类和计算机日益融合,这会导致赛博格之间的交互,并探讨了这种趋势的社会和伦理影响。2010年,在第26届计算机安全应用年会(ACSAC)上,四位研究者通过特定的分类系统,探讨在Twitter账户上互动用户的赛博格属性,修改后的论文(Chu, Z; Gianvecchio, S; Wang, H & Jajodia, S, 2012)于两年后被收录在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数据库上,至今已超过670次被引。持续关注“计算机与人际关系”的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 2011:152)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亦将赛博格诠释为个人与通信设备耦合以实现在线化生存的主体。当然,从积极一面来看,这些探讨为传播研究对赛博格的重新发现进行了“理论蓄力”。
再看如火如荼的传播实践。业界经常有新兴技术的“元年”判断,比如说2016年是区块链元年、2017年是人工智能应用元年、2018年是物联网元年、2019年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元年等。⑦当然,具体的时间可能会因为依据标准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近些年确实是新兴技术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从原始局域网的“点对点传播”,到如今5G背景下的“万物互联”,新的技术变革为传播实践带来无限的可能——诸如手机、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智能物件成为身体的电子器官,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用扫码支付而不是现金结账,沉浸于体感游戏里对再现身体的掌控,通过大众点评或全球民宿记录自己的生活轨迹,佩戴运动手环获得身体数据的及时反馈等。赛博格无疑是这些可能中既足够前沿又能命名实践的良好理论资源。2016年,“沉寂已久”的传播学界终于重新注意到赛博格—传播议题,和2000年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一方面形成了初步的学术共同体,开始群策群力;二是相关议题有了较好的延续性,在接下来每年都有相应文章在重要的传播研究期刊发表。值得关注的是,国内传播学者也迅速意识到赛博格理论资源的可塑性,在2017年亦开始引介和使用。这个阶段的最大贡献,要属对概念原本“技术化身体”和“隐喻”的两种意涵进行了重要的完善。
(二)作为“技术化身体”的“赛博格”的完善:由表及里,从人/机器互嵌到有机体/数据融合
在智能传播阶段,数据成为信息流通最重要的元素,各类智能硬件和软件与人类实现了数据驱动下的智能互联(方兴东,严峰,钟祥铭,2020)。进入传播实践的赛博格,也由表及里,从传统控制论层面的人/机器互嵌,逐渐转向智能传播视域下日常的有机体/数据融合。换言之,技术人工物不再只是内在于身体,增强肉体的某种物理属性;而是已然高度具身于身体,从而扩展人的生存空间以及建构身体的精神属性。不少学者捕捉到,碳基身体同硅基身体作为新兴技术的源泉和定位场所,数据作为有机体状态、行为、需求的底层逻辑,塑造出智能传播图景中典型的“交互型”赛博格实体。
数据新闻专家乔纳森·斯准(Jonathan Stray)在2016年秋冬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更是大胆地抛出“Cyborg Age”的说法。他分析了路透社针对社交媒体启动的News Tracer项目,该系统通过实时抓取和分析有价值的网络新闻,并分配给每个群集“准确度”和“新闻价值”的评级,让记者和机器达成人机协作甚至是深度融合的状态。可以说,这是对过往新闻传媒业的理念和生态的一种颠覆,从而开创所谓“赛博格纪元”。⑧而较早将赛博格引入国内传播研究的赵睿与喻国明(2017),也是将网络上的对话机器人(Bot)理解为赛博格的一种具体应用形式,认为作为“广义上人机协同的代名词”的赛博格,在虚拟的交互场景能有效进行机器与人的对话,同时也可以实现对真实场景的信息连接与资源聚合。有传播学者借助“生活史”(històries de vida)的研究方法,通过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的传播实践案例,将年轻人在各种移动场景使用的智能设备,阐释为他们的感官与大脑的延伸。也就是说,当我们日常使用手机与外界交互时,已成为不折不扣的赛博格(Anton, 2017),这也契合了《兰登书屋词典》(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对其的第二重解释“使用电子或机械设备的人类”。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迪·昆茨曼和埃斯皮纳·米亚克(Adi Kuntsman & Esperanza Miyake,2019)批评传统的“数字脱离”(digital disengagement)在赛博时代已然失去解释力,认为学界应重新探索人与技术、算法和数据、社交同网络之类的链接关系。两位研究者认为“人体—设备—传感器—软件—数据配置”的集成系统,在重新定义何为现实的同时,也使得赛博格成为各种设备和整个信息世界的交流媒介(a meso-level medium)。这其中,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汉斯·艾森鲍姆(Hans Asenbaum, 2018)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赛博格的源流,反映了人类与机器、自然与技术的特有纠葛。集中出现在女性主义理论、技术研究和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概念,描摹了一幅幅将机器义肢和器官融入肉体凡胎中的场景,随着心脏起搏器和整形手术等应用日益增多,这种技术加强型的赛博格已成为现实。然而,在新的电子环境中,其更多指代人们通过使用数字通信设备而实现的日常赛博格化(everyday cyborgisation)。换言之,在如今的传播实践中,赛博格式的身体看起来由那些智能电话、运动手环、头戴式设备等硬件所包裹,本质上则是由不同传播途径所汇集的数据所浸润。
(三)作为“隐喻”的“赛博格”的完善:明确了本体和喻体的指称,提供了隐喻使用的现实情境
对赛博格另一种概念属性的传播学拓展也价值不菲。如前所述,哈拉维的隐喻虽极具理论洞见,但其本体和喻体的指称不明,以及过于抽象的表述方式,为探讨的进一步落地造成障碍。而传播学者能立足于更具体且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导向的讨论,更有力地回应赛博格隐喻背后的种种思考(阮云星,高英策,贺曦,2020)。
德国卡塞尔大学的皮纳尔·图兹库(Pinar Tuzcu, 2016)着眼于数字化进程对女性身体—主体政治定位带来的影响。她先后分析了德国移民女性、土耳其库尔德女性和美国黑人女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后,用“赛博地理学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 geographies),代替了原先单一的“白人女性团结”标签(#SolidarityIsForWhiteWomen hashtag)。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伊丽莎白·埃尔赛瑟(Elizabeth Ellcessor, 2016)则运用数字文化理论和临界残疾研究的成果,用“Alex”的案例揭开了网络上“赛博格伦理骗局”(cyborg hoax)。她犀利地指出赛博格式的“残疾”主体更像是无所不在的隐喻透镜,通过它可以管窥网络媒体既有规范条例背后的意识形态。印度喀拉拉邦帕拉卡德政府维多利亚学院的斯里普里亚·巴拉克里什南(Sreepriya Balakrishnan, 2016)则将“赛博格”主体性定位为一种将人类身份整合为更具文本性、存档性和可访问性的数字化主体性,籍此来分析个体、机械系统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美国东北大学的梅丽尔·阿尔珀(Meryl Alper, 2018)采用极具包容性的质性研究方法——感官民族志(inclusive sensory ethnography),以解释赛博主体如何与新媒体进行更全面的多感官(包括且不限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接触。来自北欧南丹麦大学的多特·布罗加德·克里斯滕森和赫尔辛基大学的明娜·鲁肯斯坦(Dorthe Brogard Kristensen & Minna Ruckenstein, 2018)通过长期对丹麦在线“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社区成员的追踪,发现赛博式的行动者与技术可以共同进化(human-technology interaction)。国内学者吴倩(2019)以媒介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切入VR/AR技术下的“新阅读”,探讨人机互嵌的赛博人是如何打破传统身心二元的认知范式,从而转向身体知觉与心灵意识共同参与的具身阅读中。孙玮(2018a)认为,媒介融合正迈向主体层面的融合,这造就了“赛博人”,而它蕴涵有“重造社会系统并改变人与世界之关系”,反过来亦影响了当前的传播实践和社会系统。她结合自己城市传播的研究旨趣,既将其看作移动网络中技术与人融合的节点主体,又将其视为后人类时代的元媒介和起聚合作用的终极媒介。孙玮(2018b)还探讨了赛博人的主体/主体性,指出它与当前移动网络时代的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技术要素密切关联。拥有智能身体的赛博人作为主体而展开传播实践,由此创造了与前两种意识主体和身体主体截然不同的在场状态。彭兰(2019)借助深度伪造(deepfake)、脑机互联、数字化永生和权力认知等案例进行伦理反思,并对未来赛博人的数字化生存形态,以及智能时代人机协同乃至共生的关系进行畅想(彭兰,2020:369-382)。
(四)“赛博格”对传播研究的激发:作为新研究领域的“赛博格传播学”
如上所述,近些年的传播研究,对赛博格“生成”和“转义”的两种概念进行了系统完善,如孙玮和彭兰等学者,在有限的篇幅内也敏锐捕捉到赛博格概念的能动性,这些结论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不过,对于当前呈现“内卷化”(involution)的趋势,且亟待理论和范式突破的传播学而言(李金铨,2019:91-93),可能更值得思考和挖掘的点在于:赛博格,这个丰富的理论资源,能激发传播研究何种“范式创新”的可能性。下述的行文,将从2000年那篇标志着“赛博格进入传播研究”的论文再出发,结合之前的传播理论和赛博格理论,同时基于当前新技术赋权下的传播实践,探讨作为新研究领域的“赛博格传播学”之合法性。
贡克尔(2000)的核心观点在于,“赛博格不是依据传播学科既有的方法和技巧去研究和理解的新对象,而是重定义了人类主体性和人类传播研究主题”。有学者说,以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为代表的经典传播学,强调定量和统计方法的训练,聚焦对媒介效果的实证研究,反复验证以议程设置为代表的十几个大众传播理论(李金铨,2019:74-88),交流被视为人类独有的特征,而技术在传播中的作用被降级(Rogers, 1997)。这自然衍生出两个问题:其一,如果将赛博格只作为这样的传统路径下的又一个“新对象”,已不妥帖;其二,当智能的机器/技术/数据/设备/物成为传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将肉身的“人类”视为唯一的传播主体,亦不合适。大众传播之后,新的传播形态亟待被命名和被诠释。
贡克尔的同事安德烈·古兹曼和来自俄勒冈大学的塞思·刘易斯(Andrea Guzman & Seth Lewis,2020),关注到既有的传播理论与新兴技术之间的这种脱节,判断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HMC)作为交流型人工智能(communicative AI)的一部分,可能成为新的主导性传播形态。他们总结道:第一,人们将他们的设备和应用视为传播者;第二,人们与这些技术相连,进而与自己和他人相连;第三,人机传播模糊构造出人、机器和传播的本体论界限。这篇论文勾勒出智能传播时代的隐约轮廓,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尝试。不过,即使引入技术的因素,两位作者还是倾向于将技术和人类皆视为不同类型的传播者,而无论是从具体的传播实践还是抽象的传播理论考量,人机并行乃至人机共生是总体趋势,很多时候不能也无需将诸多传播主体划分得那么清晰。特别是有机体/数据深度融合且具备当前乃至未来隐喻潜质的赛博格,能在节点内部实现交互(类似于真正反身性的自我传播),或与庞大社交网络的任何其他节点实现交互。这样的赛博格,可以认为是再造的智能传播主体,也可以看作感知和交互的媒介、技术辐射和社会连接的界面。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得以重塑,泾渭分明的不同行业得以联结。接下来,笔者试举一个案例加以说明。
这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典型情境——佩戴口罩的消费者在进入商场之前,需要向安保员展示智能手机里的“绿色”健康码,并接受其手持红外仪的“体温正常”核验,如此方可通行。不难觉察,在此类传播实践当中,初始的主体往往需要现代技术物的深度加持和信息交换,才具备相互联结、体认和交往的可能。具体来说,虽然消费者用包裹着的防护用具遮蔽了自我的面容乃至其他传统意义上的身体特质,但这种看似在政治—文化制度安排下个体“隔离病毒”的姿态,其实可能也蕴涵着自我同他者实现正常连接的渴望。隔离是连接的隐喻,遑论有的护具自身亦安装有数字芯片。再通过向此时此地拥有监察权力/职责的对方呈现随身移动设备的相关数据,技术具身的个体因而有着比单纯的生物体更快捷和更准确的可识别性。再来看安保员,除了采取相似的防护措施,最后还需借助红外测温仪(可看成智能的媒介/技术对自然身体及其感官的融合,因此监查者同样达到技术具身的形态)来判断来访者是否符合既有的健康标准。若各项条件都符合,消费者和安保员便经过高效的交互(呈现健康状态、风险等级和密接数据等信息),共同完成这项位于“入口处”的新型传播活动(达到快速通行、防止拥堵和避免交叉感染等目的),这也为他们各自后续可能的交互(诸如消费者的闲逛式购物和安保员的随机性巡查)奠定了基础。赛博格的身体已然与技术高度融合,即使平常状态下未必得以完全彰显,但在诸如2020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大事件中,它们能很好地适应新技术设备的嵌入式使用和新的传播场域的规范性要求(从历史的维度,可与2003年非典时期的防疫形态和疫情中的“非技术化身体”作对比),实现了赛博格—传播形态的复数逻辑,也建构了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的全新样态。
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作为一种新研究领域的“赛博格传播学”,以期更好地命名如火如荼的新型传播实践。当然,学术研究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赛博格跨领域”的理论构想亦是如此,其重要的支撑来源于加里·唐尼、约瑟夫·杜米特和莎拉·威廉姆斯(Gary Downey; Joseph Dumit; Sarah Williams,1995)三位学者,在人类学转换范式与更新议题的背景下,于1992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提交具备较高影响力的《赛博格人类学》(Cyborg Anthropology)文本,他们认为其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而非只是一次精英圈层的学术实践。此文首先判断新兴的赛博格人类学将会探索这三个相关领域:一是作为文化活动的当代科技研究;二是对作为传统人类学主体和对象的“人”之批评;三是研究机器和其他技术是如何参与人类学的现存领域并获取知识生产的代理权。其次是论述赛博格人类学与科技研究(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和女性主义研究的关联,认为其将提供理解和批评性干预的策略。最后谈到赛博格人类学面临的两种潜在风险——即如何对学术理论和流行思想负责,如何抑制自身“如何存在”(defining itself out of existence)的内部矛盾。浙江大学阮云星和高英策(2020)遥相呼应,他们在“研究方向”一栏明确标注“赛博格人类学”,以“赛博格人类学:人工智能与智识生产”为题申请到了“双脑计划”交叉创新项目,并在《开放时代》等刊物陆续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赛博格人类学的核心关注点,在理论层次上,要针对有关控制论与后现代立场中的人之新主体性问题,及其相应的人—机混合关系问题,展开本体论取向的分析及相关知识论、方法论探索;在经验分析层次上,完整意义的赛博格人类学应基于赛博格隐喻的原理与呈现形式,广泛检视当代的高新科技生产与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通过民族志研究反思“不言而喻”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新要素与新逻辑。
有了“赛博格人类学”的良好借鉴,将“赛博格传播学”提上传播研究的日程,就显得顺理成章。初生的“赛博格传播学”,有可能从以下方面为传播研究带来新气象:
研究对象层面,作为“实体”的赛博格多是可观测的,就像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终日活跃在参差的传播网络里,恰如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 2016:4)所言,“携带移动设备的主体化身为活的光标,整座城市空间俨然成为交互界面”。而作为“隐喻”的赛博格,则由更多元化的“本体”和更场景化的“喻体”所共同形构。如同规约外卖骑手配送时间的平台算法和网约车司机嘀嘀作响的微信群,赛博格之“本体”不仅是目之能及的“所是”,它也存在于与之相应的语言、思想和行为之中。赛博格之“喻体”则依托现实具体的传播情境,用科技之“笔”勾勒出关系之“线”,最终“你我皆赛博格”,微微一笑,确认彼此数字化生存的世间程式。
理论层面,可以重新定义诸如“5W”模式的传播者和受众(传受一体化、节点化,且由单独的人或机器转变成更为宽泛的人—机复合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无限的数据流联接和重塑技术化身体,共同进行网状传播),传播效果(打破固有的传播时空观,微观和宏观的影响往往趋近乃至等同)。
方法层面,传统的哲学思辨和历史研究、参与式观察为代表的定性研究、计算传播为潮流的定量研究、案例分析为支撑的伦理研究等,都能有效地参与到该领域的讨论之中。
研究议题层面,围绕当下乃至未来传播实践的现象表征、逻辑机理和伦理法规,最终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如何沟通和共处”等跨学科、多学科的基础性命题,做出来自传播研究重要的回应和贡献。
当然,传播研究博大精深,无论是对学术边界的探索抑或是对学术基础的夯实,既需要先行者“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勇气和好奇心,更需要有志同仁“众人踩出阳光道”的检验、论证和推进,才能更好展现“作为基础社会过程和解释基本模型”(克雷格,2015)的传播学科面对特定议题的自主贡献,激发传播理论对新型传播实践的观照和对话,为当前乃至未来的传播研究敞开无限可能的新视域和新面向。
综上所述,2000年,赛博格被美国学者贡克尔极富前瞻性地引入传播学界,但相关的赛博格—传播议题,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于传播研究有所停滞,反而在CMC和HCI领域有所进展;随着新计算、通讯和交互技术的发展带给传播实践的变革,2016年伊始,赛博格重回传播研究;2017年开始,国内传播学界也引入此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初步的学术共同体,并能对相关议题展开持续的讨论。这段时间的主要成果,是结合自身领域的特征对概念进行了两种新阐释。与此同时,通过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回溯以往的传播理论和赛博格理论,以及在对贡克尔文章基本观点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种从对象、理论、方法、核心议题等层面,可能改变乃至重塑传播的“赛博格传播学”,对传播研究所号召的“范式创新”做出呼应。■
注释:
①参见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cybernetics。
②参见http://m.youtube.com/watch?v=ygRNoieAnzl。
③参见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7/04/worlds-first-cyborg-human-evolution-science/。
④参见http://m.youtube.com/watch?v=TW78wbN-WuU。
⑤参见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metaphor。
⑥贡克尔个人网站参见http://gunkelweb.com/index.html;个人学术档案参见https://scholar.lanfanshu.cn/citations?user=wsRSDvsAAAAJ&hl=zh-CN&oi=sra。
⑦参见Tapscott, A. & Tapscott, D. (2017). How blockchain is changing fina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 2-5等。
⑧参见Jonathan Stray.(2016). The age of the cyborg.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cjr.org/analysis/cyborg_virtual_reality_reuters_trac-er. php.4。
参考文献:
邓绍根(2015)。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7),41-45。
段然(2019)。“舆论/public opinion?”:一个概念的历史溯源。《新闻与传播研究》,(11),94-110。
方维规(2013)。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东亚观念史集刊》,(4),101-170。
方兴东,钟祥铭,彭筱军(2019)。草根的力量:“互联网”(Internet)概念演进历程及其中国命运——互联网思想史的梳理。《新闻与传播研究》,(8):43-61。
弗朗西斯·福山(2017)。《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克劳斯(1981)。《从哲学看控制论》(梁志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旦(2015)。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12),5-19。
克里斯·希林(2011)。《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凯瑟琳·海勒(2017)。《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宏图,周保巍,孙云龙,张智,谈丽(2012)。概念史笔谈。《史学理论研究》,(1),4-21。
李金铨(2019)。《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国栋(2020)。对“赛博格”进行概念考察。《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7-07(004)。
刘海龙(2018)。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国际新闻界》,(2),37-46。
雷蒙·威廉斯(2005)。《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罗西·布拉伊多蒂(2016)。后人类(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罗伯特·T.克雷格(2015)。《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于嵩昕,李瑄译),载于《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六辑:“新传播与新关系——中国城乡变迁”,谢静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2011)。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诺伯特·维纳(2017)。《控制论》(郝季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兰(2019)。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新闻记者》,(12),4-12。
彭兰(2020)。《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潘汝(2020)。身体·主体·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经典科幻电影的“赛博格”想象。《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46-54。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2015)。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阮云星,高英策(2020)。赛博格人类学:信息时代的“控制论有机体”隐喻与智识生产。《开放时代》,(1),162-175。
阮云星,高英策,贺曦(2020)。赛博格隐喻检视与当代中国信息社会。《社会科学战线》,(1),30-37。
孙玮(2018a)。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6),4-11。
孙玮(2018b)。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12),83-103。
孙玮(2020)。传播再造身体。《新闻与写作》,(11),5-11。
苏涛,彭兰(2019)。反思与展望:赛博格时代的传播图景——2018年新媒体研究综述。《国际新闻界》,(1),41-57。
唐娜·哈拉维,赵文(2021)。秩序中的视像变化:灵活的策略、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以及灵长类再视觉化。《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38-52。
吴倩(2019)。从意识沉浸到知觉沉浸:赛博人的具身阅读转向。《编辑之友》,(1),20-24。
威廉·斯威特(2015)。转化人类主义与人格的形而上学(计海庆译)。《哲学分析》,(4),99-108。
张灿(2018)。技术化身体的伦理反思。《中州学刊》,(8),91-97。
赵睿,喻国明(2017)。“赛博格时代”的新闻模式:理论逻辑与行动路线图——基于对话机器人在传媒业应用的现状考察与未来分析。《当代传播》,(2),13-16。
AsenbaumH. (2018). Cyborg activism: Exploring the reconfigurations of democratic subjectivity in Anonymous. New Media & Society20(4)1543-1563.
Alper, M. (2018). Inclusive sensory ethnography: Studying new media and neurodiversity in everyday life. New Media & Society20(10)3560-3579.
Anton, R. R. (2017). Smartphones As an Extension of the Human Cyborg: the Case of the Youth from Aragon. Analisi-Quaderns De Co-municacio I Cultura , (56)101-115.
Braidotti, R. (1994).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aidotti, R.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
Brasher, B. E. (1996). Thoughts on the status of the cyborg: On technological socialization and its link to the religious function of popular culture. Journa1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4809-830.
BiroM. (1994). The new man as cyborg:Figures of technology in Weimar visual culture. New German Critique, 6271-110.
BalakrishnanS. (2016). Historicizing Hypertext and Web 2. 0: Access, Governmentality and Cyborgs. Journal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s, 11(2)102-118.
Clayton, J. (1996). Concealed circuits: Frankenstein’s monsterthe medusa, and the cyborg. Raritan1553-69.
Chu, Zi; GianvecchioS; Wang, H; JajodiaS (2012). Detecting Automation of Twitter Accounts: Are You a HumanBotor Cyborg? IEEE Transactions on Dependable and Secure Computing9(6)811-824.
DavidsonC. (1996). Riviera’s golemHaraway’s cyborg: Reading neuromancer as Baudrillard’s simulation of crisis. Science-Fiction Studies23188-198.
DowneyG. L. , DumitJ. , and Williams, S. (1995). Cyborg anthropology. In C. H. Gray (Ed. )The cyborg handbook(pp. 341-346). New York:Routledge.
GunkelD. (2000). We Are Borg: Cyborgs and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 10(3)332-357.
Ellcessor, E. (2017). Cyborg hoaxes: Disability, deceptionand critical studies of digital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19(11)1-17.
Fiske, J. (1994).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2nd ed. ). New York: Routledge.
FeatherstoneM. , & BurrowsR. (Eds). (1995). Cyberspace, cyberbodiescyberpunk: 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London:Sage.
GaneN. (2006). When We Have Never Been HumanWhat Is to Be Done?: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3(7-8)135-158.
GeraldS. G. (2007). Cyborg Discourse: Technology's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Booknotes Quarterly. 38(1)5-26.
GuzmanA. L. & LewisS. C. (202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munication: A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genda. New Media & Society22(1)70-86.
Haraway, D. (1990). SimiansCyborgs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aylesN. K. (1995). The life cycle of cyborgs: Writing the posthuman. In C. H. Gray (Ed. )The cyborg handbook (321-340). New York: Routledge.
HaylesN. K. (2006). Unfinished Work: From Cyborg to Cognisphe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3(7-8)159-166.
HarrisJ. (2007). Enhancing Evolution: The Ethical Case for Making Better Peop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perM. C. (1995). Incurably alien other:A case for feminist cyborg writers. Science-fiction Studies22399-421.
HowellL. (1995). The cyborg manifesto revisited: Issues and methods for technocultural feminism. In R. Dellamora (Ed. )Postmodern apocalypse: Theory and cultural practice at the end (199-218).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KristensenBM. & RuckensteinM. (2018). Co-evolving with self-tracking technologies. New Media & Society20(10)3624-3640.
KuntsmanA. & Miyake, E. (2019). The paradox and continuum of digital disengagement: denaturalising digital sociality and technological connectivity. MediaCulture & Society41(6)901-913.
Kenneth, R. F. (2009). Sociotechnical Interaction and Cyborg-Cyborg Interaction: Transforming the Scale and Convergence of HCI.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5(4)227-235.
LarsonD. (1997). Machine as messiah: Cyborgsmorphs, and the American body politic. Cinema Journal36(4)57-75.
LindbergK . V. (1996). Prosthetic mnemonics and prophylactic politics: William Gibson among the subjectivity mechanisms. Boundary, 23(2)47-83.
Manfred E. Clynes & Nathan S. Kline. (1960). Cyborgs and Space. Astronautics, (9)26-27 & 74-75. reprinted in Gray, Mentor & Figueroa-Sarrieraet al. (1995). The Cyborg Handbook. New York:Routledge, 29-34.
McQuire, S. (2016). Geomedia: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errick, K. A. (2007). The cyborg is the message: A monstrous perspective for communication theory. Ames,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askK. (1995). Cyborg economies: Desire and labor in the terminator films. In R. Dellamora (Ed. )Postmodern apocalypse: Theory and cultural practice at the end (182-198).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orushD. (1994). The rise of cyborg culture or the bomb was a cyborg. Surfaces, 4(205)1-32.
RogersE. M. (1997).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Free Press.
ReidE. M. (1996). Text-based virtual realities:Identity and the cyborg body. In P. Ludlow (Ed)High noon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Conceptual issues in cyberspace (327-346). CambridgeMA: MIT Press.
SandovalC. (1995). New sciences: Cyborg femin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oppressed. In C. H. Gray (Ed. )The cyborg handbook (407-422). New York: Routledge.
ShantiA. (1993). Cyborgs in the n-dimension: The heretical descent of non-Euclidean geometry. Constructions857-82.
SiivonenT. (1996). Cyborgs and generic oxymorons: The body and technology in William Gibson’s cyberspace trilogy. Science Fiction Studies23227-244.
Turkle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Tuzcu, P. (2016) . “Allow access to location?”: Digital feminist geographies. Feminist Media Studies16(1)150-163.
Turkle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WilliamsD. (1998). The politics of cyborg communication: Harold InnisMarshall McLuhanand The English Patient. Canadian Literature, 15630-55.
田秋生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庚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香港进步报刊的统战宣传研究(1927—1949)”(17BXW0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