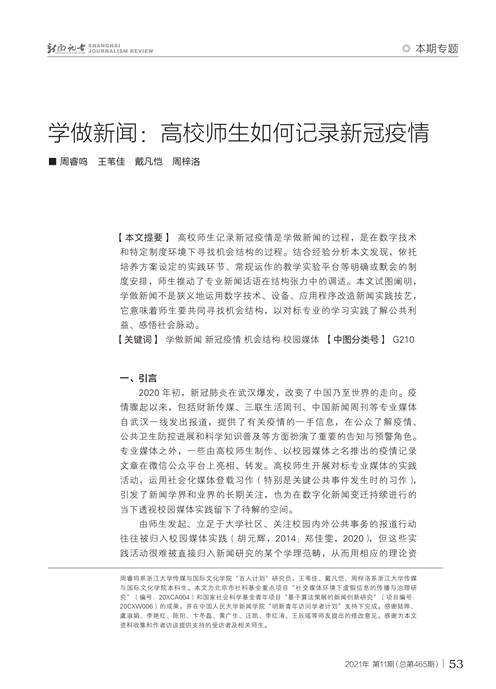学做新闻:高校师生如何记录新冠疫情
■周睿鸣 王苇佳 戴凡恺 周梓洛
【本文提要】高校师生记录新冠疫情是学做新闻的过程,是在数字技术和特定制度环境下寻找机会结构的过程。结合经验分析本文发现,依托培养方案设定的实践环节、常规运作的教学实验平台等明确或默会的制度安排,师生推动了专业新闻话语在结构张力中的调适。本文试图阐明,学做新闻不是狭义地运用数字技术、设备、应用程序改造新闻实践技艺,它意味着师生要共同寻找机会结构,以对标专业的学习实践了解公共利益、感悟社会脉动。
【关键词】学做新闻 新冠疫情 机会结构 校园媒体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走向。疫情骤起以来,包括财新传媒、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专业媒体自武汉一线发出报道,提供了有关疫情的一手信息,在公众了解疫情、公共卫生防控进展和科学知识普及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告知与预警角色。专业媒体之外,一些由高校师生制作、以校园媒体之名推出的疫情记录文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亮相、转发。高校师生开展对标专业媒体的实践活动,运用社会化媒体登载习作(特别是关键公共事件发生时的习作),引发了新闻学界和业界的长期关注,也为在数字化新闻变迁持续进行的当下透视校园媒体实践留下了待解的空间。
由师生发起、立足于大学社区、关注校园内外公共事务的报道行动往往被归入校园媒体实践(胡元辉,2014;郑佳雯,2020),但这些实践活动很难被直接归入新闻研究的某个学理范畴,从而用相应的理论资源加以解读。从现象上看,它秉持师生的观察视角,带有鲜明的大学社区特色,但又无法接入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等理论脉络,因其不具有自发的、无专业规训乃至对抗的特征。尽管校园媒体实践的习作显露准专业的色彩,但它又与制度化、专业导向的新闻实践明显不同,前者在组织规模、生产节奏、实践理念系统表述等方面都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它是校园内的试验田,承载着教师引导和/或学生互助打磨新闻技艺、体悟专业角色的功能;它简单纯粹,规模可大可小、节奏时快时慢,在自外于新闻机构结构制约的实践中有意无意地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成果。一句话:学做新闻是校园媒体实践的本色。
结合高校师生如何记录新冠疫情的若干个案,本文旨在解读学做新闻这一意象及其过程,关注以校园媒体之名展开的实践活动。具体地说,本文关心的是这些个案的疫情记录如何可能。个案的分析单元是依托高等院校开展的、对标专业新闻机构生产活动的校内组织。这些组织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有支撑实践活动开展的社会空间,例如由教学院系依托培养方案和课程搭建的新闻实践训练环节,或由教学院系和党政部门归口管理的学生组织;第二,成员以学生为主,配备有以指导之名参与其间的教师(包括基于教学或在教学之余提供专业实践指导的教师,以及指引学生社团运作的教工);第三,实践活动具备专业导向,生产活动应尽可能地秉持学生视角、体现学生的思考,由学生主要完成。喉舌导向、宣导大学形象和利益的实践活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二、学做新闻:寻找机会结构
学做新闻这个意象易激发望文生义的理解,即有意尝试新闻实践甚至立志成为未来新闻人的学生们学习新闻技艺的实践活动。本文赋予这一意象的涵义不止于此。借助威利斯(Paul Willis)的名著《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本文界定的学做新闻除了学习新闻技艺,还指向高校师生在所处的结构制约之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过程。在《学做工》中,威利斯将目光对准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工业城市当中的中学生,考察了这些少年如何子承父业。威利斯以民族志的方法切入文化,考察中学生们如何理解自身处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少年们的工人阶级身份在学校教育体系中被内化,进而再生产了以其为基础的阶级关系(威利斯,2013)。这为本文考察学做新闻带来些许启示:首先,尽管本文关注的是数字媒体兴盛当下的中国高校学子,但与威利斯考察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子弟一样,本文放眼的主要行动者同样具有学徒身份和底色,要在学习的过程中锤炼新闻技艺、增长专业禀赋和意识。其次,学做新闻的活动是学徒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是她们在学习中具体落实抽象的新闻专业理念的过程。通过实作,她们把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理念和技能代入实践加以体悟,完成构想、对标、编织如何做新闻的意义生成、自我诠释和身份建构。第三,与威利斯的考察类似,作为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学校既为学生搭建了释放主观能动性的舞台,又通过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和相关纪律构成了制约。学生的能动性不是无边无际的,在学校这个活动场景中,他们不得不在面临的结构约束中发现行动的可能。这就是说,学做新闻是社会实践更是文化实践。解读这样的文化实践需要立足于学校这个活动发生的主要场所,回答高校师生以校园媒体之名实践专业新闻话语如何可能的问题,即:学做新闻的高校师生面临何种结构及内蕴的权力关系;上述结构如何为师生学做新闻创造了便利的话语实践和制约条件;面对这些条件,师生洞察了什么机会、准备了什么资源,在什么时空情境下开展了话语实践。
机会结构为进一步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学者们一度关心政治机会结构,即行动者所处的体制结构和制度环境当中利于集体行动展开的因素,探察这些分属不同层面的客观因素(即权力关系及其配置)如何促成集体行动接近乃至达成目标。简单说来,政治机会结构是集体行动面临的政治环境(Eisinger, 1973),是可被变量化并加以学理分析的权力关系及其配置(卜玉梅,周志家,2015)。随着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转移,机会结构的文化维度进入研究视野。在关注了德国、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发生的右翼暴力之后,考夫曼斯(Ruud Koopmans)等人提炼出话语机会,将政治机会结构和集体行动的框架观点联系起来探讨暴力和公共话语的联系。他们发现,右翼暴力的不同公众可见度、共鸣和合法性显著影响了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暴力发生率(Koopmans & Olzak, 2004;Koopmans & Muis, 2009)。
机会结构本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概念。2002年,在共同编著的《形塑堕胎话语》(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一书中,费里(Myra Marx Ferree)和她的合作者们在考夫曼斯等人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话语机会结构,将其代入堕胎议题如何在德美两国的公共话语中形塑的考察。费里等人在此界定的话语机会结构是对特定语境的总称,它为理解德美两国不同的集体行动者如何就堕胎问题展开公共话语上的框架竞争创造了背景墙。作者们认为,话语机会结构是更广泛的政治机会结构的一部分,后者指的是行动者可利用的所有制度和文化条件(access point);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话语机会结构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某些行动者和框架在公共话语中得到凸显。费里等人同时认为,作为引导和组织话语的制度和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大众媒体是上述意义创造过程的核心(Ferree, Gamson, Gerhards & Rucht, 2002)。
机会结构(特别是话语机会结构)是研究者探究集体行动何以可能的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被广泛运用在传播与集体行动的探讨当中。伴随数字传播技术的演进,研究者关注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如何共同营造了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4),社会化媒体对重要社会运动,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社会运动做出了何种贡献(Loudon, 2010; Molaei, 2015),以及民粹主义政客如何使用媒体策略、在社会化媒体或报纸中处理可供动员的问题并达成目标(Ernst, Esser, Blassnig & Engesser, 2019),等等。研究者们亦挪用费里及其合作者们理解的话语机会结构,探讨特定议题和事件如何在公共空间中被多重行动者形塑,例如选择性接触的机会结构(Skovsgaard, Shehata & Stromback, 2016)、记忆机会结构(白红义,2019),不同国家的政党运用社会化媒体谈论或强调的不同内容如何有助扩大支持者获得信息的机会结构(Popa, Fazekas, Braun & Leidecker-Sandmann, 2019),等等。研究表明,机会结构(特别是话语机会结构)是适宜考察政治传播活动和公共话语如何被多重行动者推拉形塑的分析工具。
本文沿用费里及其合作者意义上的话语机会结构,但又有所不同。本文的解读处理着与费里们类似的话语机会结构——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语境如何为某一议题凭借某种框架进入公共空间创造了可能;在此背景下,与行动者开展话语争锋的有哪些玩家、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制约、在这种制约之下采取何种策略能动地实践。可以说,学做新闻就是高校师生如何寻找机会结构,在结构制约中寻找专业新闻话语落地的条件。不同之处的核心是互联网技术为学做新闻活动立足之结构带来的变化。费里等认为,大众媒体在围绕特定议题开展意义制造、形塑公共话语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这在新闻业尚未经历系统数字化改造的时期的确如此;历史地看,德美两个具有联邦结构的现代工业民主国家拥有类似的媒介体制,这在作者们的考察中操作地指向了私人拥有的、政治独立的报纸,这一点在作者们考察时回溯的三十年里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互联网技术恰恰为学做新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如果没有微信公众平台这样的社会化媒体登载终端,高校师生学做新闻的活动恐怕很难走出大学社区,他们的习作也就谈不上成为公共空间流动和可资谈论的文本。然而,进入公共空间的高校师生又面临着微妙而复杂的结构处位:身处高校、借势互联网、对标专业媒体,这使得学做新闻不得不在借助技术登入公共空间时妥处其立足高校和新闻业之间制造意义的紧张关系。
综上,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便是:以校园媒体之名开展的学做新闻实践活动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回答,在新闻业仍在经历数字化变迁的背景下,高校师生学做新闻的机会结构是什么,如何调适并将专业新闻话语付诸实践。解析机会结构意味着在话语上洞察以下面向:第一,高校师生面临什么样的结构,技术、高校、新闻业共筑了什么有利和限制因素;第二,在上述利好和限制因素下,高校师生如何发现和蓄积便利行动的长期基础性条件;第三,在特定历史时刻,高校师生使用何种策略和战术,抓住瞬时机会开展新闻生产。
本文首先选定新冠疫情在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爆发的2020年上半年作为关键公共事件发生的热点时刻。在这个给定的时间段内,本文凭借两个指标选择加以解读的校园媒体个案:第一,2020年上半年创作的疫情记录习作是否获得过由高等院校、新闻机构等主办的学生(校园)媒体大赛或作品评选奖;第二,疫情记录活动和习作是否被高校同行关注、提出协作请求,被知名的媒体评论和观察组织关注、探讨。据此,我们选取了来自四间高校的四个个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来编辑部(以下简称“未来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UC新闻坊”(以下简称“RUC新闻坊”),还包括南玛都大学泰利观察(以下简称“泰利观察”或“泰利”)和珊瑚大学桑卡瞭望(以下简称“桑卡瞭望”或“桑卡”)。为避免破坏二者当前的运作状态,我们对泰利和桑卡这两个个案进行了匿名处理;为保护所有学生受访者的利益,我们对她们亦予以匿名处理。
我们综合相关文本和访谈资料开展案例分析。分析材料来自:(1)四个个案2020年上半年通过旗下微信公众号公开发表的疫情记录文章逾百篇;(2)未来编辑部部分指导教师同我们分享的带批注的习作修订稿,共十余篇;(3)学生成员与指导教师的反思性言说,来源于媒体评论和观察组织的采访、学术期刊约稿、线上讲座等;(4)面向学生及指导教师的访谈,计13人次。
三、个案解读:疫情记录何以可能
(一)捕获“天时”:抓住记录疫情的瞬时机会
对于新闻业而言,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报道的契机,甫一出现就牵动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提升了报道的可能。尽管这一机会出于历史偶然“从天而降”,但它仍需有心者伺机捕捉。未来编辑部启动防疫观察项目的过程展现了师生捕获“天时”,抓住记录疫情的瞬时机会。
首先是师生在疫情到来时刻内化于心的专业召唤。从2020年1月26日首次发稿到2020年6月18日,防疫观察项目共发稿86篇,不到两天即推出一篇新作。百余天中,不同年级(本科、研究生及各年级的不同分布)、不同学科背景(新闻传播学院、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等)的同学追踪了从2019年12月下旬到2020年6月中旬发生在武汉、湖北各地市,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疫情进展,回忆、记述、采写了被打乱的生活节奏、忙中有序的疫情应对、不同社群的安危和际遇。防疫观察不是专业新闻机构发起,学生亦不是专业新闻人。尽管如此,在召集学生参与该项目时,指导教师们呼吁用专业的力量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王辰瑶,2020)。一呼百应源于师生对专业召唤的共同体认。防疫观察项目的首倡者周海燕说,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她刚刚离开新闻界前往高校任教,原本非常希望带学生做些报道,但是学生都被关在校园里,最终一事无成。疫情结束后,她开始反思为什么不能在学校里进行报道——当时有短信、有移动电话,其实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当新冠疫情来袭,她的首要想法就是弥补当年错失带领学生记录历史的遗憾(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8月28日)。类似地,莎莉嘉①同学受访时回忆,寒假离校后,她在偏远家乡见证了医疗系统中的父母如何投身日益紧张的地方防疫——参与搭建发热门诊、协调不同科室的防疫物资、通过大量CT检查提供确诊依据等。这些工作触动了她并让她意识到,家乡马上要经历如十几年前非典那样的事,因此她要记录父母当下的忙碌:一个小地方的医疗系统如何应对这场疫情,这个系统如何决策、如何运转。她认为,这个记录的功能无论对当地居民还是对她个人都有意义。师生的话共同显示这么做的意图是“向公众报告”(王辰瑶,2020),履行社会责任。正应了周海燕就防疫观察讲的下面这段话(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8月28日):
校园媒体一定不能够止步在校园之内,而是要走出校园。同学们在准新闻人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去认知、理解和承担自己作为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媒体工作者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就是通过报道来实现公共服务;一个是对内,就是大学的本源——培养人。
这段话表明,对未来编辑部的师生而言学做新闻就是对标专业。对标有双重面向:对外,通过报道实现公共服务;对内,培养人。通过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师生试图扮演的专业身份及想象的社会角色得以显影。正如老师们调用的专业新闻话语所说:“当出现这种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为社会记录下来一点什么”,“要用专业的力量来做点什么”(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7月18日)。
第二个在疫情骤起时浮现的瞬时机会是师生的空闲时间。疫情甚嚣尘上时适逢农历新年,师生几乎悉数放假离校。在这个时刻返校或以其他形式碰面重聚不论从节庆还是防疫安全的角度都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确认的是师生有空,甚至出于难以确定的返校时间将长期有空。有鉴于此,这场由指导教师激活的防疫观察便在线上拓展开来。6位指导教师在线协作搭建临时采编指挥机制,共同指导选题酝酿、采写推进和稿件编辑,并通过教师指导的数个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每日习作。被迫中断的正常学业为本在课余时间开展的学习实践匀出了可观的时间,师生皆可从容地安排实践活动。一个可供观察的指标是习作分阶段的发布频率:以2月17日(不含当天)南大启动线上授课的日期为报道涉及时间的统计中点,约40—45篇习作记录了此前的事件。除了说明疫情骤起初期的严峻程度极受师生关注,催生了不少文章,另外一层推论便是双方得闲、因时而作。
第三重被师生捕获的瞬时机会本属空间上的限制。疫情初期的严峻形势使包括学生在内的大部分居民被限制在诸如小区等管控区域。为尽快抵达事件发生的核心,防疫观察一开始仅面向人在湖北的同学发出了报道倡议;2月5日以后,防疫观察将志愿学生的招募范围扩增至所有“想在此时亲身参与观察记录当下中国最重大社会事件的同学”,这时学生成员才由20多人增加到180人左右(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7月18日)。以2月5日(不含当天)为报道涉及时间的统计中点,此前约16篇文章中有13篇关注湖北疫情,此后的文章逐步扩展到全国乃至全球其他国家。另外,考虑到疫情本身的危险,把学生实践的安全放在首位(王辰瑶,2020),项目以纪实为主要叙事文体,强调学生一手观察。这一选择容忍了学生在信源拓展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例如行动范围受限的学生仅能依赖自己既有的人际网络,通过电话、互联网等渠道进行采访。这让防疫观察零碎地分布在家乡、校园等学生暂居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学生们相近的人生经历使得议题和叙事框架呈现同质性。此外,初期的防疫观察还显现出个体叙事主导的特征:观察和自述多使用第一人称,偶有直接的情绪展露和观点表达。随着项目的推进,情感、观点的表达变得克制,以第三人称写作的防疫观察数量增多,作者逐渐从文本中退场。防疫观察还表现出对包括各地卫健委在内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和新闻媒体等体制内信源的偏向。这展示了项目运用学生的地理分布、叙事文体的选择和动态微调的编辑理念破解其空间限制,努力贴近事实性信息呈现、剥离观点表达,控制报道的主观区间,做到内容真实准确、文从字顺,在告知公众的同时训练学生报道的基本能力和素养(王辰瑶,2020;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8月8日)。
疫情记录不能靠捕捉“天时”一蹴而就。表面上看防疫观察是一个临时项目,实际上它是未来编辑部常态运行的延伸,不能全归于临时起意(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7月18日)。未来编辑部是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教学实践课程设计的特色板块(有学分的“第二课堂”实践课程),是由多位老师、多组学生、多个微信公众号构成的多个发布终端组成的制度安排。参与未来编辑部实践的同学们彼此合作、相互学习;指导老师们也在多年的共同工作中加深了解,配合默契。有了这样的长期准备,防疫观察项目快速形成了定选题、指导写作、改稿、初审、终审、排版、美编、推送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出现了具有专业导向型媒体特色的选题会;作为编辑的指导教师像专业新闻人一样把关审稿,通过可追溯的痕迹让学生能像在专业媒体工作时一样看到稿件是如何修订的(白净,2020)。这样的安排确保了师生在重大突发事件下相对从容地召集学生、调动资源、分配工作(王辰瑶,2020)。抓住疫情记录的瞬时机会需要学做新闻的师生长期培育、蓄积寻找机会的基础条件。
(二)塑造“地利”:蓄积记录疫情的基础条件
捕捉记录疫情的“天时”要靠长期塑造的“地利”支撑。未来编辑部展示了师生如何抓住疫情记录的瞬时机会,而来自RUC新闻坊受访者的讲述则展示了师生如何长期准备学做新闻的基础条件,等待瞬时机会。
2020年上半年RUC新闻坊发出60余篇推文,其中关系到新冠疫情(包括因疫情而变的生产生活领域及其秩序)的有28篇。这些习作中,《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和《1183位求助者的数据画像》这两篇数据新闻收到最多关注,不仅微信推文阅读量以万计,收到来自读者的大量反馈和互动,而且在中国数据内容大赛等数据可视化作品评选中获得专业嘉奖。参与创作的两位学生受访者告诉我们,两篇习作中的前者源于指导教师方洁在选题酝酿期间梳理疫情报道消息来源的提议,后者则要从参与创作的其他老师获得数据集说起。访谈中,两位受访者均把这两篇疫情记录习作赢得的“天时”放在RUC新闻坊长期形成的“地利”中解读。
基础条件之一是约定俗成的制度安排。方洁和两位学生受访者均表示,新闻学院对RUC新闻坊给予充分信任,相信指导教师有充足的智慧和艺术来引导、把握表达的尺度,鼓励师生的专业导向实践并乐见其成。方洁透露,2020年,学院提升了对RUC新闻坊的资助,鼓励他们成立工作室,将其作为创新团队加以扶持。在方洁看来,这表明学院认识到了RUC新闻坊作为一项品牌的意义——学业两界的口碑折射了学做新闻的高度,显示了新闻学院的教学水准和学生的业务潜力。RUC新闻坊作为新闻系教学实践平台并未内嵌到教学活动中,不靠教学任务运转,也不靠学分等潜在收益召集学生,但它的良好运转和不断推出的习作向学生发出了专业召唤,并给这种召唤提供了安放的空间。以这种召唤为纽带,指导教师通过授课等日常教学活动物色潜在的学生成员,后者亦可以通过RUC新闻坊定期的纳新活动加入其间。
基础条件之二是架构对标专业媒体的组织生产流程。按照方洁和两位学生受访者的说法,加入新闻坊的学生三三两两自愿成组,以星期为单位负责RUC新闻坊当周的公号文章制作。理论上,值周的学生小组负责当周的选题酝酿、资料收集和文章撰写;实际上轮值又非一成不变:通过微信群等线上渠道,师生随时可以集思广益,提出破题的新见解和新思路。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旨在“雨露均沾”,确保学生获得大体相同的技艺锤炼机会,另一方面为诸如新冠疫情这样重大新闻事件降临的特殊时刻留出机动安排的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受访者们共同认可的师生权力关系。顾名思义,指导教师可行指导之实,在学生实践过程中扮演支配性角色。但在RUC新闻坊中,指导教师有意保持开放心态,为学生学习、打磨专业技艺提供了试验乃至试错的空间。方洁告诉我们,这种心态并非开始就有,而是在指导RUC新闻坊运作过程中慢慢转变而来的,伴随了她对自身角色的动态理解:
其实我原来一度无法容忍,甚至觉得招来的学生就应该快速上手,但是我后来一想,你本身就是个校园内的媒体,要给学生一定成长空间。有些学生成长得很快、特别好,他会特别感恩这段时间,因此他会对我们这个公众号有更强的归属感。这样的孩子其实挺多。如果没有给他成长空间,那这不是跟社会上的媒体没什么区别吗?没有所谓的培养人、教育人的功能,只把人拿过来当工具,又不给他什么东西,对不对?其实你能给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包括他们跟同辈学习的过程。
指导教师的开放心态提高了学生参与尝试的能动性,为师生在数字媒体兴盛条件下再理解和实践专业新闻话语提供了创新的机会。方洁曾表示,无论是新闻的真实性还是客观性等原则,这些我们曾经认为无可挑剔的基本原则在当下都面临着挑战(腾讯传媒,2021年4月8日)。用学生受访者的话说这首先是网感——议题上把握互联网用户关切什么,叙事上把握互联网用户的情感流向何处。学生受访者兰恩②说她常常从非虚构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中感悟标题的风格,并把它代入到RUC新闻坊的实践当中。被代入的还有她的社会化媒体使用体验,“知道哪些词它可能现在有热度,哪些词就是烂梗,用了稿子就完蛋了”。基于社会化媒介接触的体验影响了兰恩在一题一议的实际操作中实践专业话语的战术。兰恩分享了这样一则故事:2020年她试图围绕月经贫困做篇稿件。起初,师生没有就如何推进这个议题达成一致。但兰恩没有放弃,她与几位学生成员一起开列了详细的选题计划,说明这篇稿件可以讨论的议题、打算引述的信源、叙事上的基调等。后来,这份选题计划兑现成了《降价吧!卫生巾》。她把类似的师生互动称为“battle”——要用实践步骤和清单说明计划是可操作的。当然她亦明言,师生间的讨价还价要归功于淡化了支配色彩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指导教师的包容与克制。
基础条件之三是叙事文体的长期摸索和选择。如前所述,RUC新闻坊颇受关注的两篇疫情记录习作皆是数据新闻作品。这不是赶时髦,而是RUC新闻坊历经四年逐渐清晰的选择。新闻坊一出生就是数字化的:微信公众平台向师生提供了面向公众的机遇,也促使他们不断思考如何在议题和叙事文体选择上扬长避短。他们可继续以校园媒体之名自居,但在社会化媒体上,如此自居无法复制在大学社区内部坐拥的、同质社群共有的议题回响;与其他创作者相比,学生因其生活经历的单薄还或多或少面临信源拓展的局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自2015年6月创办起,RUC新闻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注重做新闻传播学界的前沿观察,关注业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加以学理思考(腾讯传媒,2021年4月8日)。简言之,做“关于新闻界的新闻”既回避了学生拓展自身信源网络的困难,将解析新闻生产的后台作为信源“富矿”,又发挥了新闻学院日常教学培养过程中学理地分析、批判媒体实践的长处。这一被学生受访者玛娃③称为“轻学术”的议题选择使得RUC新闻坊持续关注新闻界的表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引发用户关注。后来,新闻坊逐渐提高选题的时效性。在推出《如何讨论刀刺辱母者案?》和《江歌案的舆论焦点与反思》以后玛娃觉得,类似的舆情分析让大家“初尝流量的甜头”。
做“关于新闻界的新闻”是RUC新闻坊后续制作原创数据新闻的先声。学生受访者说,经过所谓舆情分析的锤炼,学生们逐渐习得了以内容分析等量化应用社会研究方法协作解读新闻文本的技能,包括提出问题、编码、描述,及解读分析结果的技能。在日积月累的尝试中,她们还把握了议题选择和叙事上的技巧,即如何用通俗的表述把学理分析的结论传达给社会化媒体用户。上述准备促成了2019年9月20日的作品《分析周杰伦75775字歌词后,我们用他最爱的词重写了〈说好不哭〉》。参与撰写这篇稿件的学生成员兰恩说,稿件推出一段时间之后的阅读量达到了3.8万次,“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点击量,应该是史上的新高”。这次采写让兰恩感到了RUC新闻坊的变化:从前想走“学院派的路线”研究别的媒体怎么报道新闻,这一次是直接试做新闻,“大家都很兴奋”。用方洁的话来说,这次尝试让大家看到了做带有时效性稿件的影响力和可能性(腾讯传媒,2021年4月8日)。议题关切的奏效、社会影响的良好反馈激起了师生的共鸣,良好且热络的协作氛围一直延伸到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记录。
疫情初期的时间窗口缺少的只剩破题的切入点。以《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一文的缘起为例:一如过去,这是一篇数据新闻,一次对新闻业的检视和观察;它有推出记录的时效,2020年1月底2月初正值疫情肆虐。这就是兰恩回忆的,当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评鉴新闻报道质量、转发交换佳作却不知自己该从何入手时,方洁最先提出做一篇有关消息来源文章的动议。这次量化描述统计的核心关切是,通过观察2020年1月国内媒体刊载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对同一话题消息来源的选择偏好,讨论其传播立场、意识形态等,并探究这种选择带来的不同影响(人大新闻系,2020年2月11日)。师生取得共识后大家着手开始工作,克服困难和压力,包括科学抽样、保存数量庞大且随时可能无法找回的样本、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得出并表达结论、控制表态的尺度等等(腾讯传媒,2021年4月8日)。玛娃记得,写到最后的时候,她、兰恩与方老师商量把结论提前、把数据和文献综述插进去,以通俗化的结论表述带动全文,淡化它的学理色彩,为普通读者着想。如此成就了RUC新闻坊微信公众号“10万+”阅读量的篇目之一。它也显示,有了动态调整、因地制宜、长期塑造的“地利”,抓住记录疫情的“天时”便水到渠成。
(三)孕育机会的结构
高校师生学做新闻的过程往往被视作校园媒体的建设过程。在新冠疫情这场足以称之为全球性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此间诞生的学生优秀习作不免被视作校园媒体的高光时刻,成为躬身实践的师生们开展反思性言说、书写话语权威和共同记忆叙事的凭据。反思性言说与优秀习作一起,似乎打包成了一套可移植的校园媒体实践的成功经验。然而,校园媒体这一称谓自身蕴含的张力在为学做新闻的心有戚戚者支撑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他们对标“先进”、想象“我们也行”的来源。实际上,当记录的机会“从天而降”,师生要抓住这个“天时”;想要抓住“天时”要靠长期蓄积的“地利”;“天时”、“地利”打包而成的长期与瞬时机会又深植于高校师生面临的结构处位当中。它富含张力,既是帮助师生塑成打磨新闻技艺之基础条件的有利因素,又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甚至左支右绌的现实约束。
校园媒体不是媒体。这是实然的判断。当我们谈论媒体时,我们指的是作为公共部件的制度化的社会机构。作为内嵌于媒介体制的组织,媒体按照预设的、成体系的理念和原则有节律地运作和实践。它以事实性信息为基础提供公共服务,融通多方利益、推动公共事务、促进社会进步。它是现代社会特征和秩序的象征。中国特定的媒介体制使媒体具备了在地特征:它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新闻工作,肩负着舆论导向的使命和任务。即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媒体商业化、集团化的改革时期,党的喉舌仍然是中国媒体的底色;“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强调的是市场作为服务受众和组织运作资金配置的手段,而不是收归并听命于资本、唯受众是从的利润收割机。简单说,作为公共部件的中国媒体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历史语境中显示了它被体制和商业两种逻辑牵引的二重性。校园媒体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它们可以成为高校和师生的扩音器,但它身处高等教育界而非新闻界,接受的是高等院校及其下辖党团组织和/或教学部门的领导;它与党的宣传和/或网信系统在校外的派出机构存在政策和业务指导关系,但双方并不存在直接隶属关系。它们不是市场主体,无法进行市场运作。它们不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也不是欧美意义上的第三方社会力量。它们是高校教学部门开展新闻教育的模块,或者党团部门所属并指导的学生社团。这些教学模块和学生社团承担着可能包括但又不限于新闻实践的主要任务,如通过实践活动授予学生修读的学分或向校内外推介大学动态和形象;借助它开展的新闻实践可能缺乏固定的、可系统论述的理念和原则加以规定和约束,没有明确的生产的常规节律,成员频繁更替、组织松散。但不论怎么说,在学生培养或学生社团相关制度约束下,它们多是师生凭借对媒体活动的兴趣、对校内外公共事务的热忱,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的实践。这反映了借校园媒体之名学做新闻的结构处位:它是非主流的,因为支撑学做新闻的高等院校及其组织架构并未在媒介体制中得到制度安排;它又是主流的,因为不论将来是否有志成为新闻人,在大学社区内做新闻所打磨的不是旁门左道式的另类技能,而是试着以新闻观照现实的手艺、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
校园媒体实践是话语交织的想象。如上文引述的文本和访谈资料显示的那样,它接纳了师生在热点时刻之下记录特殊时期日常生活的本能冲动。无论是反复推敲文本以遵从基本的客观事实、贯彻科学和精确报道之原则、共同体会报道当中的主观区间,还是就特定议题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来回讨价还价,师生都被这种冲动驱使。这是内化于心的召唤,包含了他们赋予并言说校园媒体社会功能与角色的定位。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师生对标新闻机构以及当下和过往那些可为典范的新闻人及篇目,抓住机会铺陈自己想象专业的蓝图。这便是将专业新闻话语付诸实践的尝试。需要指出的是,校园媒体往往同时承载了想象的另一面,即展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园生活,借助这方天地呈现学生讴歌时代、阳光向上的积极风貌,展示师生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取得的尖端科学成果,也包括在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历史考验面前遵从和寻求大局、上下一心、同声共气的自觉意识和目标。它帮助勾画了大学社区的总体形象,成为师生寻求和强化社群认同的情感之源。两种相互交织的想象恰是专业新闻话语和宣传话语试图在学做新闻中落地的写照。
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抬升了学做新闻所处结构内蕴的张力。在互联网技术尚未应用到高校新闻教育和学生社团学做新闻的实践环节之前,校园媒体实践习作多靠高校党团宣传部门管辖的周期性刊印的报纸发布,或通过校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这些刊发终端覆盖的范围有限,几与大学社区重合。换言之习作即使刊发,它的社会影响也几乎是确定的,不会超出大学社区这个较为同质的社会空间。然而,当诸如微信公众平台这样的社会化媒体成为师生学做新闻首选的登载终端,它便跨出了大学社区的社会边界。躬身其间的师生当然可以继续把她们运作的微信公众号视作大学社区内的试验田,可习作一旦被推送就会即刻走出校园,成为可供公众平台上所有用户接触的文章——社会化媒体不会为大学社区特供什么技术条件来区分大学内外。对学做新闻的师生来说这是利好,除了方便大家以数字手段协同生产,更给师生提供了直接介入非校园议题的机会,通过习作影响更广泛的公共议程;但对作为微信公众号最终把关人的高校教学和党政部门来说,学做新闻的利好可能意味着确实的或未预的困境:一方面,这些未被吸纳到媒介制度安排中的作坊要在追寻专业和形象展演之间不断调适;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作坊已经在事实上走出校园、面向公众,不同的话语社群既可以把它们看成高校的“正统”代言人,又可以把它们想象成社会化的、学生的“另类”自留地。对高校各部门来说可能不得不考量的,是习作可能激发的多元异质社会思潮与意见表达带来的潜在后果。这就是学做新闻的结构矛盾:技术既为学做新闻创造了面向社会、影响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又制造了高校作为官僚制的治理逻辑掣肘新闻专业逻辑的潜在冲突。
因此,结合上文案例我们试图阐明的是,学做新闻不是狭义地运用数字技术、设备、应用程序改造新闻实践技艺,也不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对如何采写编评进行锤炼。它意味着参与其间的师生要共同寻找机会结构:抓住瞬时机会,譬如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造就的公共言说之机会,放假在家、得闲而作的机会,虽被隔离但可就地取材开展线下纪实或线上数据收集和寻访的机会。捕捉这些瞬时机会端赖长期蓄积的基础条件,例如对学做新闻抱有浓厚兴趣、保有记录热点时刻和历史瞬间之冲动的学生,召集、引导学生开展空中新闻协作的教师们,以及师生或学生们为瞬时实作开展的有意无意的长期试验,包括叙事文体和关注议题的选择,群体协作的方式与程序,对新闻价值、舆论动向和社会心态的交流研判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试验性活动所需的稳定的制度安排,无论这种制度安排是明确规定还是约定俗成。基础条件反映了结构上的影响因素,即学做新闻的深层矛盾,也就是师生可感知的、高校作为官僚制的治理逻辑与新闻专业逻辑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当中,师生要有充足的战术(tactics),通过面向公众的社会化媒体调适、支撑专业新闻话语的实践空间,才能推动学做新闻的展开。
泰利观察和桑卡瞭望提供了一些反向论据。这两个学做新闻的团体都在新闻传播院系中成长,以院系校园媒体形象示人,以学生社团名义运作。两家发展的历史纵深长短不同,但都有可供自我言说、树为典范的作者和作品(包括记录疫情的作品),并在国内的校园媒体案例评选等活动中获得嘉奖。不过,对来自泰利观察和桑卡瞭望的受访者而言,在分别为各自“供职”的校媒成长历程和所得荣誉感到欣喜和自豪的同时,她们也流露出了对当下及未来的忧虑。她们的叙述展示了她们为记录疫情捕捉瞬时机会的尝试,也袒露了两个团体长期孕育基础条件过程中出现的波动乃至断裂。换句话说,泰利观察和桑卡瞭望的实践活动折射了它们面临的结构上的制约。
来自泰利观察的受访者证实,与未来编辑部和RUC新闻坊不同,泰利观察不是培养方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学生无法通过它获得学分。指导教师是形式上的:对泰利观察的正常运作负责,但在具体新闻活动的专业指导上缺位。尽管如此,学生成员们依然年复一年地坚持夯实泰利运作的基础条件,即依靠学做新闻的兴趣和热忱“用爱发电”。她们构造了组织运作的新老交替层级:“新人”一年,“老人”再一年;“新人”学习酝酿选题,“老人”尝试敲定和推进选题;“老人”执行采编、“新人”练习并帮衬;在此基础上,各报道组负责人借每周一次的例会把好报道关。从被招新到成为学徒,从学徒成长为中坚的高级学徒乃至负责人,在受访者看来都是自己的事。泰利观察还有一重亮点:那些已“退休”的“老人”——特别是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或互联网内容创作,对包括疫情记录在内的新闻实践仍抱热情的“老人”,会为当前“供职”的同学提供选题或采写建议。妮妲④和塔拉斯⑤都记得“退休”“老人”苏拉⑥的贡献:她们认为,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报道正是苏拉“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结果。苏拉则说,在她加入泰利观察的时候,上一级掌舵的“老人”也这么做;虽然告别岗位,但她仍然关切生产节奏和稿件质量。然而泰利观察的局限在受访者看来也是明显的。塔拉斯谈到泰利观察有自己的“做稿模式”,即对标某知名媒体的深度报道及其拟仿过程。通过这个“模式”,大多数新手可以逐渐摸索到新闻如何生产,但是成员们的“任期”普遍很短,最长两年一到就要“退休”——尚未入门者当下是学徒,一年后就变成全方位的师傅,教别人写稿、决定选题的走向。塔拉斯说,虽然升了一个年级,但其实大家在新闻路上都刚刚开始;这种新老交替层级使得泰利观察更多依赖负责人——她的叙事文体偏好、对生产节奏的把握、在重大新闻事件出现时召集大家协作的成效都会影响泰利观察的表现。正如妮妲说的:
大家可能还是太年轻,懂的都不是很多,更多凭借一种热情的驱使做事。但是很多时候,你的能力并不能支撑你去做那些事情,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现在看的话,我觉得指导老师还是挺有必要的,最好不是那种很居高临下的,最好是真的给你一些专业上的指导。
妮妲的话看起来是在呼唤一位能够在具体新闻活动上给予专业意见的指导老师,但如果并置解读她和塔拉斯的话可以看出,泰利观察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孕育学做新闻机会结构的基础条件虽经学生勉力维系仍不免波动,显示其缺乏有效调适、支撑专业新闻话语的战术——这种战术未能被学生有效习得,只好寄托给缺位的指导老师。这可以解释泰利观察抓住瞬时机会记录疫情的一个尴尬细节:在泰利观察微信公众号上获准登载的疫情记录文章不及她们完稿总量的十分之一。
上述尴尬亦发生在桑卡瞭望当中。曾经的学生成员洛克在访谈时感叹自己看着RUC新闻坊成长起来,认为桑卡瞭望早年和RUC新闻坊都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强调运用数据新闻等叙事文体和数字媒体环境拓展生存空间与社会影响。但他认为,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制度土壤让两家校园媒体最后划出了不同的轨迹。同为前学生成员的海棠认为,桑卡瞭望一度具备了强大的诱惑力:以对标舆论监督报道的形式介入校内事务,关注学生的切实利益——这让她认识到媒体可以影响公共议程。与泰利观察一样,桑卡瞭望的学生成员勉力坚持“用爱发电”,借着被海棠称为有强大诱惑力的、内化于心的召唤维系组织运作。但在海棠看来,今天的桑卡瞭望无法比肩往昔的原因,除了组织的数字化改造难言畅顺,不得不说的是专业新闻话语空间的压缩——有与泰利观察一样记录疫情的尴尬瞬间可供佐证:习作质量受相关评选嘉奖和肯定,但稿件在社会化媒体上正式登载率较低。洛克和海棠的话共同表明,桑卡瞭望面临着与泰利观察同样的问题,即孕育机会结构之基础条件的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了制度安排的不稳定和调适专业新闻话语上的失能。
四、余论
通过回顾高校师生如何记录新冠疫情,本文结合经验材料解读了高校师生学做新闻的过程。这也是解读新闻业数字化变迁的背景下,以校园媒体之名开展的学生新闻实践活动如何可能。学做新闻是师生寻找机会结构的过程,也是他们运用社会化媒体这一技术手段跨出校园、面向公众,在高校内对标专业媒体、调适专业新闻话语的过程。
高校师生在学做新闻过程中感受着深层的结构张力。这是高校作为官僚制的治理逻辑与新闻专业逻辑之间的矛盾,显示互联网技术既为学做新闻的师生创造了面向社会、影响公众议程前所未有的机遇,又制造了上述两种逻辑的潜在冲突。身处这样的张力当中,师生要有充足的战术,通过面向公众的社会化媒体调适、支撑专业新闻话语的实践空间,才能推动学做新闻的展开。
机会的涌现深植于上述结构张力之中。个案分析显示,学做新闻的可能在于师生抓住瞬时机会,譬如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造就的公共言说之机会,放假在家、得闲而作的机会,虽被隔离但可就地取材开展线下纪实或线上数据收集和寻访的机会。捕捉这些瞬时机会有赖长期准备的基础条件,例如学生对学做新闻、追寻专业理想抱持浓厚兴趣,教师有能力召集、引导学生相互协作,以及师生们基于上述兴趣和协作有意无意进行的长期试验,包括因地制宜的叙事文体,动态调整的协作方式与程序,师生及学生间对新闻价值、舆论动向和社会心态的交流研判等等。不可或缺的还有这一试验性活动所需的稳定制度安排。
威利斯(2013)通过《学做工》深描了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他的田野调查透着同情的理解,展示了资本主义教育体系中的劳工子弟如何在学习实践中维护了既有的权力关系和利益。他指出,从民族志视角理解社会结构的考察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譬如劳工子弟在何种条件下对文化生产的洞察可能转化为他们的政治意识和实践,并被动员起来中断而不是强化社会再生产。尽管本文讨论的学做新闻和威利斯笔下的学做工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但后者还是启发我们,学习和实作不只是技艺习得,它还包括对社会结构的真实洞察。本文选取的若干个案均来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以高校师生的名义展开论述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尽管如此本文仍试图通过它们寻求一些面向所有高校学子的普遍反思,即如何超越绩效导向,在校内新闻试验田里触摸鲜活的公共议题、把握社会脉动,重拾专业技艺、习得结构化的理性表达,完成价值层面的、新闻工作应有的召唤与自我召唤,在批判与反思中自我成长。这是本文通过个案探讨试图达成的目标。■
注释:
①莎莉嘉(化名),未来编辑部防疫观察项目学生成员,2021年7月3日接受了作者的在线访谈。
②兰恩(化名),RUC新闻坊学生成员,2021年6月2日在北京接受了作者的面对面访谈。
③玛娃(化名),RUC新闻坊学生成员,2021年6月1日在北京接受了作者的面对面访谈。
④妮妲(化名),泰利观察学生成员,2021年8月12日接受了作者的在线访谈。
⑤塔拉斯(化名),泰利观察学生成员,2021年8月10日接受了作者的在线访谈。
⑥苏拉(化名),泰利观察学生成员,2021年8月11日接受了作者的在线访谈。
⑦洛克(化名),桑卡瞭望学生成员,2021年6月18日接受了作者的面对面访谈。应其要求,访谈没有录制,被引述的话已由本人复核确认。
⑧海棠(化名),桑卡瞭望学生成员,2021年6月22日接受了作者的面对面访谈。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9)。记者节话语中的角色模范:中国新闻业的记忆机会结构研究(2000-2018)。《国际新闻界》,(9),60-83。
白净(2020)。如何给学生修改疫情观察稿件。《中国记者》,(3),62-64。
卜玉梅,周志家(2015)。西方“话语机会结构”理论述评。《社会学评论》,3(6),74-83。
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4)。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16-126。
胡元辉(2014)。超越校园——大学实习媒体转型社区媒体之探讨。《传播研究与实践》,4(2),55-92。
人大新闻系(2020年2月11日)。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取自微信公众号“RUC新闻坊”,2021年8月15日查阅。
腾讯传媒(2021年4月8日)。人大“RUC新闻坊”:不止于校园媒体。取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2021年8月15日查阅。
王辰瑶(2020)。防疫观察在线实践项目是如何开展的。《中国记者》,(3),60-62。
威利斯(2013)。《学做工》(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郑佳雯(2020)。开放的探索:事实核查实践与公共生活的相互依存——以“NJU核真录”为例。《新闻记者》,(8),20-31。
钟智锦,林淑金,刘学燕,杨雅琴(2017)。集体记忆中的新媒体事件(2002-2014):情绪分析的视角。《传播与社会学刊》,(40),105-134。
EisingerP. K.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11-28.
Ernst, N. , EsserF. , Blassnig, S. & Engesser, S. (2019). Favorable Opportunity Structures for Populist Communication: Comparing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ians and Issues in Social MediaTelevision and the Pr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4(2)165-188.
FerreeM. M. , Gamson, W. A. , Gerhards, J. , & RuchtD. (2002). 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opmansR. & Muis, J. (2009).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im Fortuyn in the Netherlands: A discursive opportunity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8(5)642-664.
KoopmansR. & OlzakS. (2004). Discursive Opportunities and the Evolution and Right-Wing Violence in Germa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0(1)198-230.
LoudonM. (2010). ICTs AS AN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 SOUTHERN SOCIAL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in South Africa.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3(8)1069-1098.
MolaeiH. (2015). 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media to the succes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Indonesia.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8(1)94-108.
PopaS. A. , FazekasZ. , BraunD. , & Leidecker - Sandmann, M. (2019). Informing the Public: How Party Communication Builds Opportunity Structur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37(3)329-349.
SkovsgaardM. , ShehataA. , & StrombackJ. (2016). Opportunity Structures for Selective Exposure: Investigating Selective Exposure and Learning in Swedish Election Campaigns Using Panel Survey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1(4)527-546.
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7月18日)。南大学子防疫观察项目是如何开展的?取自微信公众号“remix计划”,2021年8月15日查阅。
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8月28日)。周海燕:校园媒体的社会功能。取自微信公众号“remix计划”,2021年8月15日查阅。
Remix教育编辑部(2020年8月8日)。郑佳雯:新闻如何解释复杂的科学问题。取自微信公众号“remix计划”,2021年8月15日查阅。
周睿鸣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王苇佳、戴凡恺、周梓洛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本科生。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交媒体环境下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治理研究”(编号:20XCA00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算法策展的新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CXW006)的成果,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明新青年访问学者计划”支持下完成。感谢陆晔、虞淑娟、李艳红、陈阳、卞冬磊、黄广生、汪凯、李红涛、王辰瑶等师友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为本文资料收集和作者访谈提供支持的受访者及相关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