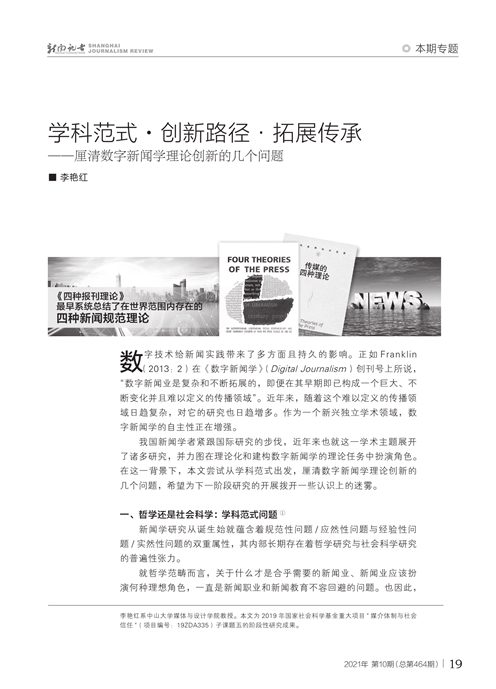学科范式·创新路径·拓展传承
——厘清数字新闻学理论创新的几个问题
■李艳红
数字技术给新闻实践带来了多方面且持久的影响。正如Franklin(2013:2)在《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创刊号上所说,“数字新闻业是复杂和不断拓展的,即便在其早期即已构成一个巨大、不断变化并且难以定义的传播领域”。近年来,随着这个难以定义的传播领域日趋复杂,对它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学术领域,数字新闻学的自主性正在增强。
我国新闻学者紧跟国际研究的步伐,近年来也就这一学术主题展开了诸多研究,并力图在理论化和建构数字新闻学的理论任务中扮演角色。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从学科范式出发,厘清数字新闻学理论创新的几个问题,希望为下一阶段研究的开展拨开一些认识上的迷雾。
一、哲学还是社会科学:学科范式问题?
新闻学研究从诞生始就蕴含着规范性问题/应然性问题与经验性问
题/实然性问题的双重属性,其内部长期存在着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性张力。
就哲学范畴而言,关于什么才是合乎需要的新闻业、新闻业应该扮演何种理想角色,一直是新闻职业和新闻教育不容回避的问题。也因此,如Hallin所言,“传播学领域,尤其是新闻学研究在本质上具有很强的规范属性”(Hallin & Mancini, 2004:13)。《四种报刊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1984)最早系统总结了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四种新闻规范理论,自此,有关新闻规范性问题的争鸣就一直贯穿于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面向。西方社会对新闻规范性问题的主流思考嵌入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中,构成了自由主义的规范性理论学说。这套学说以新闻自由和知情权概念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关于新闻应该如何运作以最好地服务于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包括第四权力、看门犬、民意代表以及一套指导新闻业日常操作的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等。这一理论在过去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挑战,既包括理论界内部的挑战,如社会责任理论、激进民主理论、商议民主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均曾为思考新闻的规范性价值提供了另类路径;也包括现实实践形成的挑战,如19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出现的“公共新闻”运动(public Journalism/civic Journalism)更多体现了来自新闻实践者内部的反思潮流,并催生了建构以公民参与和对话为核心的新闻规范性角色的理论化努力;除此之外,与全球新闻业研究的接轨以及比较研究范式的采用,也促使更多美国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基于英美经验所形成的主张与实践并不具有普适性,从而接受更加多样的规范性概念。
但是,1960年代以后以一系列新闻生产社会学著作的出版为标志,以描述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和新闻生产过程为任务的新闻业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社会科学的范式下进行的。与前述对于规范性问题的探讨不同的是,这一波由社会学家主导、在美国新闻业“黄金时代”所诞生的新闻学研究潮流开启的是社会科学范式的经验研究,其目的是理解新闻业在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律,以及新闻业与社会政治之间呈现何种互动关系。21世纪以来,以《新闻学研究》(Journalsim Studies)和《新闻学:理论与实践》(Journalism: Theory & Practice)等几种聚焦新闻业研究的期刊为主要阵地所展开的当代新闻学研究,仍主要循着这一社会科学的道路,其目的主要是对新闻业在当代世界的运行、运作及其影响提供理解和解释。
上述双重属性构成了新闻学研究的独特魅力,它使得作为社会科学的新闻学研究天生就具有了规范性意义上的价值和重大性。但与此同时,双重属性的纠缠也可能为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任务带来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在于,就两种范式而言,它们为新闻学研究提出不一样的核心研究问题,有不同的理论化方向,也有自身学科范式所决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二者使命不同,如若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两个目标均难以实现。
作为哲学的规范性新闻学研究,它的核心围绕应然性问题展开,大致可以表述为:(理想的)新闻(业)应该行使何种角色?新闻业应该如何运行(才合乎需要)?新闻业应该如何认识和报道世界(方法论、认识论)?遵行哪些伦理原则(伦理学问题)等等。因此,规范性新闻理论创新的主要任务是形成新闻业究竟应该如何运行、如何行使其理想角色的学说。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新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则围绕实然性问题展开,大致可以这样表述:新闻业究竟在如何运行?(在当下或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会如此?以及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后果?这意味着,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定位下,新闻学理论创新的任务是形成关于新闻业究竟如何运行、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如何产生其社会政治或文化影响的实然性学说。
因此,本文希望提出的第一个看法是,学术界在展开数字新闻学研究之时,首先需要明确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学科属性:究竟是要在社会科学范式还是在哲学范式下进行理论创新?最有益的方式应该是,它需要学者形成更加明确自主的意识,学术界也应依此形成不同的知识社群,在不同的学科范式下,按照各自的学科规范去完成理论批判、建构和创新的任务。
我们或可以新闻学研究中的“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为例来帮助阐明两种学科范式为何应该予以区分。近年来,“情感转向”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和讨论的一个热门主题(e.g., Beckett & M. Deuze, 2016; Duncan, 2012; Hassan, 2019),在不同学者所发表的各种关于情感转向的阐述中,它至少夹杂着三个层面的意涵:一方面,它是对于新闻学研究之现状的一种实然性判断,即学者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关注情感在新闻生产、文本和受众当中的角色,新闻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从仅仅关注事实、信息和框架到开始关注情感的转向。与此同时,它也是对于新闻业本身之发展和变迁现状的判断,即随着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新闻的生产和文本正在出现日益情感化、主观化和个人化的趋势,这不仅在新闻场域的新兴入场者,如个人博客、创业媒体、公关营销类公众号等所创作的新闻文本中有显著表现,同时也表现在传统机构型新闻媒体在适配社交媒体平台时所进行的文本呈现当中(e.g., 刘昌德,2020; Lischka, 2021)。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学术文章往往也夹杂着或内含一些应然性判断和倡导,如体现出对“情感转向”的价值上的默许或倡导,以及对传统上以客观中立作为认识论的专业理念的否定和质疑。笔者并不是否定这种对理性主义新闻观的批判,而是认为,将三种不同类型的判断混杂在一起讨论,而不对规范性和实然性问题予以区分的话,并不利于将情感因素纳入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轨道。事实上,无论从规范性角度还是从社会科学角度,“情感化”的主题都具有各自理论化的空间。就规范性角度而言,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以及数字时代新闻表现的日趋情感化,均为重访基于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新闻规范性理论提供了契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情感的规范性价值的简单肯定,而应以一种审慎批判的态度,按照哲学研究的范式来建立对于传统新闻业研究所立足的理性化基本假设的反思,围绕新闻业/实践是否应该容纳主观、在何种程度上容纳主观、如何践行主观等问题来建构和改造新闻规范性理论。从社会科学角度,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也为学术界进一步阐明新闻业情感化的具体表现、动力过程及后果,进而阐述数字时代情感化如何改变了新闻业的系统和运作,以及对整个社会公共生活意味着什么进行理论化提供了契机。但是,如果将两类问题不加区分地混杂在一起讨论,则很容易走向对情感作为规范性价值的简单肯定和欢呼,既无助于实现哲学规范性意义上的理论建构目标,也无助于在社会科学路径上将这一概念所开辟的知识积累理论化。
在现实中,由于作为社会科学的新闻学研究并非完全中立,而是往往植根于特定的对于规范性问题的观念和假设,这就使得在研究任务中对二者的区分变得更加困难。例如,传统上许多新闻业研究都根植于一些规范性的观念和理论,尤其是那些与新闻在社会上所承担的角色相关的观念和理论,这包括:新闻业应该将受众当作知晓的公民,有能力提升公民意识,促进公众对于何为好新闻何为坏新闻等的参与(Benson, 2008)。当人们在这些理念下提出研究问题之时,就意味着对这些价值观念的强化,而导致忽略对这些价值的反思。数字时代确实为反思植根于传统新闻学研究中的规范性假设提供了机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数字新闻学研究在展开对传统新闻概念的反思之时,却又同时携带甚至植入了新的规范性理念,这些新的被想当然认可的规范性理念由于缺乏足够的哲学论证,可能让学术思考走入误区。
Kreiss和Brennen(2016)对近20年间发表的数字新闻学文献的研究发现,尽管这些从事经验研究的文献很少明显表达自己的价值主张,但是其背后却存在一些共享的规范性价值,作者将其概括为四种:一是参与,在数字和社交媒体技术可供性的条件下,学者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受众参与就是合乎需要的,新闻业应该让受众参与进来;二是去机构化/去制度化,面对网络连接的新闻生态,学者们倾向于支持打破传统媒体的专业管辖权,侵蚀传统媒体的守门人权力,挑战组织层级结构,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让新闻业的过程去中心化;三是创新,学者们认为新闻业应该是创新的,紧跟上技术变迁的步伐,以满足日益网络化的公众的期望,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媒介商业环境;四是创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学者们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具有创业精神,在新的新闻生态中,他们需要能够成为创业者,建立自己的受众群体,自己筹资,并且在社交媒体时代建立自我品牌。两位学者认为,上述对规范性价值的理论化存在诸多缺陷,由于缺乏严谨的哲学论证,而是想当然地被合理化,这些看法所内含的一些偏向均未能得到揭示。例如,在对“参与”这一价值的论证进行批评时,作者认为,参与被想当然地接受为一种开放民主的价值表现,然而这种对于参与的看法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角度得到理解的,它仅仅强调个体参与而忽略了社群的参与。除此之外,“围绕数字新闻业所进行的规范性理论化并未能完全认识到,参与、去制度化、创新以及创业精神等均可能侵蚀新闻业的其他有价值的角色”(Kreiss & Brennen, 2016:311),作者于是质问:参与、去中心化、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真的有助于新闻业向公众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以及多元观点吗?真的有助于监督政府以及其他权力主体,促进治理,作为精英与公民之间的制度通道以及提供对公共议题进行讨论和论辩的论坛吗?因此,数字新闻学研究者需要对所持的规范性假设更具反思性,同时对其他学者的规范性认识可能如何影响自己的工作保持反思。
与上述特定规范性理念被“想当然”接受的实证性研究大量兴起的现状相反的是,在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学术社群内部,真正对新闻规范性理念展开哲学研究的范例却很少,或者说,规范性概念很少得到真正哲学意义的严谨讨论。根据学者Steensen等(2019)对近十年来三本最重要的新闻学英文学术期刊的分析,他们发现,尽管有关规范性概念例如客观性以及伦理等这样的关键词在很多学术文章中都被采用,但这并不说明这些文章是真正意义的哲学探讨,相反,这些文章大多是放在社会学的框架之下,作为一种专业实践而得到讨论的,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新闻业是否应该客观、应该遵循何种伦理,而是新闻业所遵循的客观性实践模式或认知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说明,新闻传播学者在哲学训练上的缺乏使得新闻学研究规范性理论始终裹足不前,这也显示了当代新闻业研究的盲点。Steensen和Ahva(2015)以及Steensen和Westlund(2020)均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去讨论与新闻业的本质有关的基本问题,新闻学研究就应该向伦理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学习。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化可能有赖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双轨发展,在缺乏学科范式意识的前提下将二者混淆无助于理论创新。由于笔者的学术训练主要为社会科学范式,下文主要在社会科学的范畴下讨论理论创新问题,期望未来有更多学者在哲学范式下提出见解。
二、社会科学范式下的理论创新路径
若明确将数字新闻学研究置于社会科学范式,就需要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来进行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学术领域,需要首先界定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应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只有更多的学者围绕这些核心问题展开研究、进行知识积累,才具备理论化的基础。数字新闻学研究迄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并且概念丰富的研究领域,拥有它自己的问题议程以及研究方式。那么,什么才是数字新闻学研究应该回答的核心问题呢?
(一)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笔者尝试用三组实然性提问来概括数字新闻学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数字新闻学研究主要应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而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学说的建立应该是在对这三个层面问题的综合回答基础之上的抽象:
(1)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与传统新闻业具有哪些重大差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意味着对新闻业变迁进行经验上的描述和勾画(empirical mapping),是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基础范畴。
(2)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迈向解释,即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变化?如何解释新闻业在数字时代所发生的变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牵涉到一个核心要素——技术,但是技术并非直接和决定性地塑造新闻业,因此如何将技术在新闻业变迁中的角色理论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挑战。
(3)第三个层面的问题迈向对后果意涵(implication)的分析,即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变迁意味着什么?它可能产生哪些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影响?尤其是它如何重构了公共生活?如Hermida(2016:92)所言,“勾画这个(受众参与的)网络连接的混杂的媒体环境,理解其对于新闻和公共生活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事业”。
那么,今天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对上述三个问题是否提供了充分的回答呢?现有的研究在上述三个层面问题上的分布如何?就笔者的观察,近年来研究者围绕上述问题做出了诸多贡献,但这些贡献似乎更多集中在第一个层面。学者们通过各自的方式描述并勾勒了新闻业所发生的根本性甚至是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是多层面的,这包括:在经济层面,原有以广告为主的商业模式和资金来源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迫使媒体和记者越来越关注新闻的商业面向,不得不陷入追寻新闻的商业价值、探寻消费者付费意愿和建立付费结构以及探索非市场的资金支持模式的议题中来(e.g., Picard,2011 & 2016);从事新闻生产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新闻场域出现多元行动者,用户成为重要的内容生成者,公民目击正在为突发性事件捕获强有力的影像(Allan, 2013),网络连接的公众在新闻创作、调研、反应、混合和流通过程中扮演着值得关注的新角色(Hermida et al., 2014; 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 2012; Russell, 2013),而大众媒体时代的消息来源(source)则选择直接向公众发言而不再依赖传媒中介,进而淡化甚至消解了与传统机构媒体的边界(Calson, 2016);传统机构化的新闻生产过程也发生了变化,新闻生产过程加速(王海燕,2019;陈阳,2019),尽管受到主流媒体抵抗,但受众参与成为可能(Borger et al, 2016; Domingo, Quandt & Heinonen, 2008);出现了网络连接的新闻业(networked journalism),新闻编辑室与业余人员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通过数字连接的新形式的合作(Jarvis, 2006),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专业控制与开放参与之间的张力(Lewis, 2012);受众测量技术的实时化则正在改变新闻业的自我理解以及新闻业对受众的想象,并可能改造传统的新闻价值,“流行性”(popularity)成为新的新闻价值(Carlson,2018);新闻的内容和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迁,出现了数据形式和纯视觉形式呈现的新闻,编码、大数据以及全球连接性促使做新闻和新闻生产的方式方法都在发生变革(Pavlik,2017),传统的对新闻客观报道的叙事方式受到挑战,越来越情感化和个人化的叙事形式则被接受和吸纳进来(Kuiken et al., 2017; Wahl-Jorgensen, 2016 & 2020),等等。可以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更替迭代,新闻业的图景已经大为不同。
相对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问题取得的成果则要少得多,这也是今天数字新闻学理论建构的缺失环节所在。诚然,学者们已经尝试提出诸多概念来阐述所观察到的新闻业的变化,如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s)(Anderson, 2016; 张志安,汤敏,2018)、液态新闻业(liquid Journalism)(Deuze, 2008; 陆晔,周睿鸣,2016)、网络连接的新闻业(Jarvis, 2006)、环绕声新闻业(ambient Journalism)(Hermida,2010)、用户新闻学(刘鹏,2019)等概念的提出,均是在阐述变迁的层面提供总体性理论/概念的努力,它们均为重新审视新闻业打开了新的视角。但是,对于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相关的分析则有显著不足。比较常见的是技术中心论的观点,即用技术的变革来解释今天新闻业出现的变化。学者们很自然地将技术的变化,如互联网或web2.0的出现视为新闻业迈向新闻生态系统、液态新闻业、网络连接和出现环绕声新闻等的原因。这一解释当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是简化的技术解释并不利于深化对数字新闻业的理解,需要进一步阐释技术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新闻业。
在分析中更多地容纳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能够帮助我们超越简单的技术解释。Wahl-Jorgensen(2014 & 2016)对当代数字新闻业情感转向的分析是很好的范例。他从多个动力过程为当代新闻业的情感转向提供了解释。他认为,数字时代出现越来越多情感化和个人化的叙事形式,这与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可供性有关:数字技术催生了日益增长的用户生成内容和公民新闻,业余的、未受过训练的普通人往往以个人化和具身化的方式对新闻事件进行描述。但是,Wahl-Jorgensen并没有停留在这一一般性的技术解释,而是进一步看到了商业与技术结合对情感化转向的影响,他发现,数字技术也将公关和市场营销这一类商业化的、天生就带有情感化倾向的内容带进来,参与机会的拓展使得这些多形式的情感表达也外溅到新闻生产实践之中,进而使得新闻生产实践日益情感化。Wahl-Jorgensen更进一步从文化和认知的角度提供理解,他认为,与上述过程相伴随的是它所催生的新的认知方式、新的新闻叙事方式导致了公众和新闻从业人员都更能够接受新的对于“何为真相”的新主张。对这一转变,作者认为应放在更广义的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以及新闻业自身的变迁脉络中来理解:一方面,整个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情感表达并不一定必然侵蚀公共领域的理性,反而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能够促进新形式的参与;另一方面,从新闻业发展史来看,主观新闻(confessional journalism)(Coward, 2013)的兴起是过去几十年间新闻表达不断发展的趋势。上述趋势随着数字新闻业和社交媒体的出现被加速并得到承认。由此,Wahl-Jorgensen所提供的解释并非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而是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技术—认知—文化的框架,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对象,下一阶段数字新闻学理论就应该提供更多类似多层次多维度的解释。
除此之外,进行社会科学的条件性提问也有助于增进对于现象之原因的分析。以Anderson(2016)的新闻生态系统概念为例,他试图用这个概念表述在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一种典型状态——在一个相似的空间当中,彼此关联的各个单位均参与到新闻报道的过程之中,产生连接并各自拥有自己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我们可以通过追问这一概念存在的“条件性”来进一步清晰界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可以追问在不同国家或社会背景下,由于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并不相同,数字新闻业的“网络连接性”或“生态性”是否会有不同表现?即便在同一个社会,围绕不同的事件,由于存在不同语境,这些不同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所体现的“网络连接性”或“生态有机性”是否也会体现出差异?或者,在数字技术不断更迭的背景下,比如随着微信对微博的替代,以及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视频直播媒体的流行,是否均改造了这种“生态性”、“连接性”或“液态性”的实质?笔者认为,在具体语境下进行追问和比较性研究的尝试将有助于超越对总体性概念的描述,迈进到对于新闻生态系统内部更深入细致的理解。通过具体的案例去观察和描述不同语境下上述概念的表现及差异,并尝试阐释这些概念所描述现状的前因后果,将能够为数字新闻业的理解提供更丰富和多元的知识。因此,将宏大概念操作化,使之成为可观察的对象,进行社会科学的条件性追问,迈向默顿所说的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以及增进更为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是破解此类“宏大理论/概念”困境的方法论路径。
围绕第三个面向的研究同样较为不足。在笔者看来,今天的数字新闻学理论尚未能对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变迁究竟给我们的公共生活带来哪些挑战,又存在哪些契机,提供丰富且令人信服的回答。不过,其实绝大部分数字新闻学研究者都是关注变迁后果的,或者说关注这种变迁将带来什么是绝大部分学者内心的关怀。因此,就笔者的观察,在数字新闻学的文献当中,对后果问题的探讨往往被融入第一个面向的研究之中进行探讨,学者们往往通过观察和分析新闻业的变迁本身来进一步理解这种变迁的深层意涵。这种情形很普遍,也很有价值。例如,近年围绕“可测量新闻业”(measurable journalism)所展开的相关研究就体现了这一路径。关于受众测量技术如何塑造新闻业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不仅聚焦于第一个层面,如描述基于社交平台的受众测量技术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正在如何被新闻组织采纳这样的描述性问题(Cherubini & Nielsen,2016);而且关注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这将意味着什么。于是,学者们试图通过观察新闻组织究竟如何展开对于受众以及新闻业的想象、如何处理这一技术导入所带来的张力、如何形成对于受众的反馈机制,甚至如何调整他们日常的新闻决策,改变他们的守门人角色,形成对传统新闻价值的改造等(Usher, 2013; Vu, 2014;Zamith, 2016),来理解受众测量技术究竟将给新闻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如根据Carlson的概括,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可测量新闻业”将带来两种未来,一种是通过对新闻价值的改造,使得新闻业彻底沦为“以受众为中心的受市场逻辑主导的彻底自由放任”(audience-centered free-for-all governed by market logic)(Tandoc & Thomas, 2015:251);另一种可能是赋能新闻组织,使得他们对新闻内容的创造更符合受众兴趣,进而有助于提高新闻业的影响力。这两种观点分别植根于各自对于这一变迁进程的描述和分析,也构成了两种观点的论辩。
然而,仅仅聚焦于生产层面尚不足以完整和系统地理解数字新闻学的后果和影响。超越学术研究中的这种“生产偏向”,才能更完整地理解后果问题。有两个方向的努力可能颇为重要:一是迈向对新闻文本的研究,二是增加或者将对受众(新闻消费者)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整合进来。下文会专门对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二)数字新闻学理论化的目标和路径
在厘清何为学科核心问题以及对现有研究现状作出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提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目标。理论是对经验知识的高度概括和精炼,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下,笔者尝试将数字新闻学理论化的目标阐述为:提出理解、分析和解释/阐释数字时代新闻业/新闻生态之运行和变迁及其后果的学说。
这样一种综合性理论学说的建立可能有赖于学者们在具体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上进行理论化。在笔者看来,社会科学的理论化往往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一是演绎法,从宏观理论中得出假设然后用经验材料去检验它,这种理论化的方式往往将理论理解为一些一般性的规则、法则;第二种是归纳法,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总结、归纳和抽象而形成理论,这种理论化的方式往往将理论理解为可观察的模式的累积知识,这种累积知识往往是在由以往相似案例的经验研究以及围绕相同主题发展的扎根理论所构成的“地方性研究前沿”的基础上形成的(Mj?set, 2006, 转引自Steensen & Westlund (2020:57);第三种是抽象思辨的方法,这种方式往往被理论家采用,他们根据个体的直觉观察或基于他人的大量经验研究,形成一些抽象的理论架构来理解一些相对宏观的社会现象,如产生理论概念来架构和阐释现代性的面向等。理论建构的目标有赖于三种路径所形成的知识之间的不断互动与对话。
学者Steensen和Westlund(2020)通过对近年来围绕数字新闻学研究主题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学者们所运用的三种主要方式,恰恰对应了上述三种理论化路径。第一种作者称为实用主义—参与性的理论运用路径(pragmatist-participatory attitude towards theory),这种路径在其研究样本中占一半以上,主要是基于对经验材料的系统分析,扎根理论即是最具代表性的,对应了上述“归纳法”。第二种是引入跨学科的理论视角烛照当前的经验材料,并在此基础上与这些跨学科理论对话,或丰富这些理论命题,通过运用特定的理论棱镜来审视数字新闻业。这一路径与上述“演绎法”有一定对应性。第三种模式是直接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或相关的概念讨论,这对应的就是上述的抽象思辨方法。
在上述三种路径中,第三种路径即概念化的工作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往往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理论所指。理论的基本元素是概念,因此,发展敏感化的概念来捕获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复杂性,用它来描述和解释数字新闻业,定义和阐述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理论的基础。如上文所述,近年来,数字新闻业研究领域已经涌现出不少这样的优秀尝试,但是,仅仅停留在概念上可能并不利于理论化,理论化还有赖于概念化工作与经验研究工作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这恰恰是今天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化困境所在。如Steensen和Westlund(2020)所指出的,在今天的数字新闻学研究中,概念化的工作与经验研究相对脱离,不少概念变成“无所不包”(catch-all)的概念之后,并未能很好地进入经验研究得到检验,或者未能通过启发新的问题意识为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打开空间。下文尝试以Hybridity(混杂性)这个概念为例,来帮助理解从概念化到理论化的困境问题。Hybridity概念建立在这样的观察的基础上,即,传统存在于新闻与娱乐、公共事务与流行文化、事实与虚构形式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e.g. Chadwick, 2013; Harrington, 2008; Thussu, 2007; Zelizer, 2009)。因此,这一概念表达了学者们对今天这种边界被消解的、越来越复杂的新闻实践的一种观察,是学者们用新的方式来讨论当下这种稳定和变迁并存之多样现状的努力。这一概念成为有效分析各种新闻业实验、创新、背离和转型之形式和过程的工具,在这里,传统的分类被拓展、重新组合或被颠覆(Chadwick, 2013; Stross, 1999)。可以说,这个概念的提出确实敏锐地捕捉到了今天数字时代新闻实践变迁的重要倾向。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命名上,停留在阐释何为Hybridity,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来阐释和描述目前新闻场域的复杂性上,甚至停留在对这种混杂现状的美化或欢呼上,这个概念的理论意义就不大。理论化的下一步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来协助经验观察和用它作为棱镜来观察多样的混杂的实践形式。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理论化则有赖于学者们发展新的问题意识,寻找这个概念的解释性价值(explanatory value)。例如,Tamara Witschge等(2019)在他们关于Hybridity概念的反思性文章中就提出,学术界更应该去探讨混杂实践究竟是如何出现或何以被形塑的?它们究竟如何与那些传统上存在的分类相关联?如果说混杂是对既有边界的破坏的话,那么新的秩序何以建立?混杂将可能行使什么样的修辞和实际功能?如果能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就会进一步推进有关Hibridity的理论论述。
理论化的另一个困境在于三种理论化路径之间缺乏对话。Zelizer(2004)早在21世纪初期就提出,新闻业的研究尽管引入了各种跨学科视角,但是这些理论棱镜并没有帮助提供一种关于新闻业的整体性的内在紧凑的看法,而是像是这些学科的“继子”,在其他学科停留却没有获得足够合法的地位。这说明,对新闻学研究来说,仅仅引入跨学科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这些透过跨学科理论棱镜所形成的对于新闻业的认识,能够通过不断对话而形成具有内在系统性的看法之时,才可能对新闻学的理论化产生贡献。根据Steensen和Westlund(2020)的研究,近年来数字新闻学者在引入跨学科理论方面是有明显拓展的,最常使用的包括各种社会学理论和政治科学理论,然而,这些跨学科理论棱镜在提升对于数字新闻学的洞察,或在与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对话方面仍不乐观。
对中国学者而言,如果我们希望在社会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进行理论建构或创新,同样需要遵循上述基本路径。其中,经验研究仍是理论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对中国学者而言,要加入到理论创新的队伍当中,关键还是如何运用好中国本土的经验资料。本土经验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学者所据有的最独特的资源,对中国学者而言,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政治体制及嵌入其中的独特传媒体制、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平台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年互联网发展密切相关的独特的受众参与文化等,均构成了中国数字新闻实践展开的独特语境。因此,勾勒在这一制度和场域环境下数字化的新闻实践如何展开,将中国新闻业/新闻生态在数字时代的变迁嵌入对上述图景的理解之中并尝试概念化,同时发展概念之间的关系,用以阐述中国语境下数字新闻业的动力过程及影响,将是中国学者对数字新闻学理论建构有所贡献的基础。中国学者应该在数字技术与中国社会的独特互动中发展出理解技术和社会变迁的学说。
三、对传统新闻学概念的反思与拓展
正因为数字新闻学研究脱胎于传统新闻学,它的理论化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即是如何对待和反思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如何重新厘清数字时代新闻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反思工作构成了今天数字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
(一)传统新闻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假设
如前文所述,当代西方新闻学研究往往根植于一些特定的概念框架或基本假设,这些理念虽然并未明显表现在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中,但却往往被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和假设,指导并架构了新闻学者提出研究问题。这些观念包括关于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组织,以及谁是新闻记者等基本问题的看法。也包括一些“想当然”的区分,如Reese和Shoemaker (2016:7)的描述,“传统新闻学研究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旧的区分的基础上,例如,将受众/业余与专业人员、实践与感知、生产与消费、技术与人、实在与虚拟、私人与公共、事实与虚构、真相与谎言等进行严格的区分”。数字技术兴起所带来的新闻图景的转变,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上述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区分展开反思。
下面笔者尝试将传统新闻学研究这些基本看法以理想类型的形态总结如下:
(1)对新闻场域的看法:传统新闻学研究倾向于将新闻场域看作是稳定不变的。也正因此,在1960—1970年代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社会学家们在众多新闻编辑室通过民族志研究所得到的发现几乎完全一致。例如发现不同新闻组织所采用的新闻常规和新闻价值观基本一致,擅长解释不变的制度主义视角因此成为最恰当的对这种一致性予以解释的理论观点。其次,传统新闻学研究尤其是美国经典的新闻学研究还倾向于将新闻场域视为与其他场域之间具有清晰边界的场域,它被认为拥有较高的自律性,而较少受到他律,作为事实性报道行业,它显著区别于受到经济场域强大影响的娱乐行业等。
(2)对新闻组织的看法:传统新闻学研究往往假定新闻组织的基本形态是机构化/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由受过专业训练、秉持相似专业理念且拥有较高自主性的专业人员组成,同时具有等级化结构,并受到行业协会约束等特征,它们构成了新闻供给的垄断性主体,且组织之间高度同质。
(3)对新闻和新闻形态的看法:传统新闻学研究倾向于将新闻(news)视为制度化/机构化新闻业的产品,偏重于关注理性化、以硬新闻为主的新闻形态。由于新闻的规范理论假定“硬新闻”才能扮演告知公众和服务民主的目标,其他形态的新闻往往被主流关注排除或边缘化。
(4)以新闻编辑室为中心的研究视角:由于上述看法,传统新闻学研究是围绕新闻编辑室展开的,揭示专业新闻人员所遵循的规则并形成常规化的实践模式是传统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对新闻编辑室的民族志研究因此构成主流的研究方法。
上述这些看法在传统新闻时代被当成自然而然的观念接受,并且架构了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对象、范畴以及研究问题的方向。当然,在传统新闻研究时代,对其质疑也并不缺乏,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质疑在当时仍然主要存在于少数学者和学术社群当中,并没有形成潮流。直到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媒介环境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信息生产和传播现状的颠覆性改变,才逐渐让学者们认识到,原来传统新闻业研究是建立在特定假设的基础上,而这些假设在数字时代显得如此不符合现实因而应该予以反思甚至抛弃。可以说,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化意识即起源于这种变化的经验现实所带来的“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或者说,数字化让传统新闻业所基于的假设和理念被“陌生化”了,因而产生了质疑和反思的可能。
(二)数字新闻学提出的反思需求
超越构成传统新闻学之基础假设的这些概念前提,将视野投向那些被传统新闻学概念遮蔽的对象和主题,进而重新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术主题,可能是数字新闻学理论建构的第一环。在这个方面,笔者认为现有的学术文献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下文希望通过这种梳理为新闻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化工作厘清认识。
具体而言,数字新闻学的发展在以下方面提出了质疑和反思的需求:
(1)调整关于新闻场域的看法:数字时代带来了持久并巨大的变迁,要求数字新闻学者改变静态观,采取动态和动力学的看法,将学术观察的重点从对现有制度不变的描述和解释转向对变迁的描述和解释。与此关联,数字实践和平台的爆炸式增长以及与此关联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等,也使得新闻业的制度边界不再清晰,新闻场域与权力和经济场域以及其他场域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这也对数字新闻学的研究提出要求,不能再视新闻场域为独立自主不受外在影响的完全依靠“自律”(autonomy)的场域,而需要将视野投向外场域、相邻场域,以及与这些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新闻场域的“他律”(heteronomy)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混杂实践。
(2)拓展对何为新闻业主体的看法: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专业新闻业不再垄断新闻的供给,出现了包括博客、网络原生媒体、创业媒体(news start-up)以及对新闻材料进行汇聚、重新包装或精炼的新闻聚合机构(news aggregators)等在内的众多新兴行动者,这些在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媒体组织的异质的组织,以及他们之间所形成的松散耦合的关系和结构,构成了“混杂的媒介体系”(hybrid media systems)(Chadwick, 2013)。这使得传统上对新闻组织和新闻记者的定义不再适用。数字新闻学研究需要将这些新闻场域的新入场者(new entrant)全部纳入观察,它们构成了新闻生态系统的重要行动者。
(3)超越以理性、事实和硬新闻为主的新闻形态观:在传统新闻研究中受到重视的硬新闻其实仅是新闻生产的一个很小的维度,新闻业研究的这一硬新闻偏向早年就曾受到批评,如Dalhgren(1992)和Zelizer(2004)均认为,主流新闻学所研究的仅仅是当代新闻业“材料/物质”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忽视了那些不同形式、不同场所的新闻实践类型。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在数字时代传统“硬新闻”所占份额不断下降,硬新闻以外的新闻形态越来越普遍,自媒体上流行的是情感化、主观化的表达,受到自媒体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社交媒体可供性的影响,传统机构媒体也在经历情感化转向,日益重视情感互动。针对这一现状,学者所要做的并不是基于原教旨的新闻观念予以批判,而是应将此类多样的新闻表达形态同样纳入观察和研究。
(4)超越新闻编辑室中心论: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以新闻编辑室为中心,然而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已经远远超越编辑室这一空间:媒介组织/专业人员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增加,二者在信息创作过程中形成了更多跨越数字化新闻过程各个阶段(信息采集、过滤、处理和编辑、分发和阐释过程)的协作关系;全球范围内媒介组织之间的连接也与日俱增,组织与组织之间形成更多协作性的关系;于是,新闻记者像普通公民一样,成为整个网络新闻生态中的节点而已(nods)。这就要求研究者超越新闻编辑室的边界观,转而采取一种后编辑室(post-newsroom)概念,正如英国新闻学者安德森(Anderson)所倡导的,随着数字时代新闻业的技术、文化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新闻业的研究应该超越传统的新闻编辑室中心的民族志研究,研究网络、组织、社会群体和机构等这些让新闻生态系统运行的主体(Anderson, 2010 & 2011)。
(5)从新闻生产中心拓展到新闻分发/流通与阐释:在传统新闻研究中,受众仅被视为专业新闻的接收者,所受重视不多。但是在数字时代,受众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角色也更加多样,这不仅表现在受众通过公民新闻或用户参与的方式直接参与新闻的生产,更表现在随着社交媒体平台这个混杂的媒介空间的出现,受众作为多元行动者通过分发和阐释新闻,检查/监督和争议有关新闻专业工作,以及通过与其他行动者如制度化的新闻机构或记者等产生互动等多元方式,参与到社交媒体时代社会性的意义协商过程中来(Hermida,2016)。因此,对数字新闻学研究者而言,研究的任务不仅包括对受众消费模式的考察,如偶然性新闻消费(accidental news consumption)、新闻消费的社会推荐模式(socially recommended)等,而且应该考察随着社交媒体作为新闻的分发、流通和阐释空间的兴起,受众正在如何形成新的习惯,受众阐释如何参与到广义的集体性意义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更进一步的受众研究则应与传播学的“效果研究”进一步融合。在过去,这类关于读者新闻接触及其对于读者认知、态度和观念形成等的影响往往被划分在心理学导向的效果研究的范畴,而不被新闻学研究所吸纳,但是随着公共领域进一步呈现为网络连接的状态,呼唤二者的融合和对话将显得颇为关键,如此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新闻业的变迁如何塑造和影响读者的观点形成,进而影响民粹主义、虚假新闻传播以及政治极化等当代重大政治文化现象的变迁发展。
(6)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在传统新闻学研究中,技术几乎是不可见的,并没有成为重要的变量进入学者们的研究和理论化当中。这一状况需要在数字化条件下得到改变,由于技术变量的导入,要求学者们引入一些能够将技术元素纳入并且长于分析变迁的理论流派。近年来,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物质主义的理论、新闻生态理论和可供性理论(affordance theory)等都为技术如何塑造新闻业的分析中发挥作用,提供框架。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出目的是为了理解新闻的建构,淡化传统新闻业研究聚焦制度化的新闻业的现状,关注处于情境化社区内的多元行动者所从事的与新闻有关的实践(Domingo et al., 2015);可供性理论则被用来强调特定技术的可能性(或局限性)如何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得到应用(Conole & Dyke, 2004)。除此之外,数字时代新闻系统的改变也要求学者们超越过往以组织为中心的社会学视角,将新闻业看作是一个系统,在组织与宏观政治经济之间探寻一些能够提供中层分析的视角,如制度主义、场域理论和生态理论等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e.g, Ryfe, 2016; 白红义,张恬,2021)。数字技术对新闻业财政基础和商业模式的冲击也呼唤增加与经济学科相关的理论引入,以更好地理解新闻业市场竞争的变迁如何改造和影响了新闻业本身。
上述观念的改变为数字新闻学的经验研究和概念化工作打开了诸多空间,在笔者看来,沿着这些被打开的空间,面对更为广义且更具包容性的研究对象,在传统新闻业研究的主题之外开发新的学术主题,围绕前面所提出的数字新闻学最核心的三个层面的问题展开研究,将是形成和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的必要路径。
四、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关系:连续而非断裂
数字新闻学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术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新闻学研究要完全摆脱传统新闻学,笔者甚至认为,在断裂和革命话语主导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当下,强调它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连续性反而更有必要。如Schudson在接受常江访谈时所说,“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未来的新闻研究,它都应该和过去一样,紧密围绕着如何想象、界定和规范好的新闻、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这些问题展开”(常江等,2020:18)。
对连续性的强调有助于数字新闻学者不再把数字新闻学作为一个孤立的学科领域来处理。数字新闻学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受到很多领域的影响,但它主要还是脱胎于新闻业研究,也可以被置放在更广义的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之中。因此,强调对新闻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将有助于数字新闻学的发展。但是,如Steensen和Westlund(2020)的研究发现,由于数字新闻学研究总是强调变迁,这导致其在学术传统的继承上呈现断裂状态。他们分析发现,近十年来发表的数字新闻学文章偏向对新近文献的引用,引用的文献大多为2010年以后的,而对之前的文献较少引用。这表明数字新闻学研究强调当下和未来,而很少去检视与过去之间的关联。这一与学科历史的断裂,将给数字新闻学研究带来新的风险。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和未来,笔者认为数字新闻学研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传统新闻学研究保持连续:
首先,研究对象及所观察的对象应有连续性。传统新闻业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机构化/制度化的媒体组织,这些组织在数字时代新闻场域或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的角色和功能可能有所削弱或改变,但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因此,对它们的观察和研究应该构成数字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肯定的是,尽管变迁的话语很强大,国内外数字新闻学研究者都仍然重视对这一范畴的研究。近年我国已有不少成果都得自于对这类传统机构媒体的观察,包括他们如何运用新型的数字技术进行新闻创新,如何进行跨媒体的新闻编辑部融合,如何将受众测量纳入新闻编辑流程,如何规范记者对于社交媒体的采用,如何采纳并将自身适配于数字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形成并建立与大型平台互联网公司的互动关系等(e.g.,陈阳,2019;李艳红,2017;王海燕,2019;陆晔,周睿鸣,2016;王辰瑶,喻贤璐,2016)。研究对象的连续性还表现在,需要检视当下被认为“新”的现象在过去的存在。很多当下被视为“新”的现象其实在历史上都存在。也正因为对此的清醒认识,近年来几个数字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主题中,多位学者都有意识地将历史的视角吸纳进来,如关于“情感转向”的分析、关于“混杂新闻业”的分析,以及关于“可测量新闻业”的分析等,都通过检视这些在当今看起来颇为新鲜的现象在历史上的表现,通过与历史连续性的勾连,提供了理解这些“新”现象的历史文化脉络。
其次,问题意识应有连续性。新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与公众利益关联的信息究竟如何被生产出来,这套制度如何被建立,以及这意味着什么?如前文所述,这一问题同样也应该成为数字新闻学的基本问题。事实上,今天数字新闻学者也主要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进行努力的。但是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今天的数字新闻学体现了较强的技术导向,这一偏向可能导致对其他重要问题的忽略。就笔者的观察,今天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存在“生产偏向”、“文本缺失”的问题。例如,在传统新闻学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的“框架分析”在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研究中基本消失了,这表面上看是研究方法的转移,实则是问题意识的缺失。关于新闻业究竟如何为社会建立意义和提供知识,如何塑造人们所处的符号世界,这一直是新闻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意识之一,它是帮助我们理解新闻业意味着什么的重要途径,但是这一问题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框架分析方法在当下的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却很少被践行,导致意义建构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知识盲区。正如Steensen等(2019:336)的判断:“对于未来查阅数字新闻业研究的读者来说,如果他/她希望在这本杂志中找到2010年代的观念和文本是如何在新闻文本中被建构的、新闻业如何为它所服务的社会和文化创造意义、如何作为一个知识创造的系统起作用,以及这些问题如何与历史发展相关联,会感到深深的失望。”
导致这一问题意识缺失和偏移的原因可能在于学术界更急切地渴望找到一种普适性的方式来勾勒新闻业变迁的规律,包括“网络连接的新闻业”、“新新闻生态系统”、“环绕声新闻业”(Ambient Journalism)、“液态新闻业”、“用户新闻学”等概念都是这样的尝试,但是如传播学5个W理论给我们的启示,要整体性地了解传播现象,不仅需要研究传播者,而且需要研究传播内容、受众、语境和效果等各个方面。在数字新闻学的下一个十年,希望有更多学者能够重新捡拾起这些被忽略的环节,将它们置于具体的语境中予以分析。在将与文本和意义有关的问题意识重新带回的同时,我们也呼唤重新回到地方性知识的积累。对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化有赖于对不同地域和国家、不同社会条件下各种新闻文本建构所达成的知识积累,如此才能帮助我们更为完整地认识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多重面向。
第三,理论视角应有连续性。传统新闻学研究中得到重视的那些理论视角可能同样适用于对数字新闻业的研究,因此,数字新闻学并不必然意味着找寻崭新的理论来替代旧有的理论。Steensen和Westlund(2020)通过对学术文献的调查实证分析发现,早年新闻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理论取径其实在今天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制度、结构化、场域和资本等概念被强调,体现了数字新闻业是一个受到多重力量塑造的制度和专业。只不过,数字时代为更加多样的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应用场景。他们的研究也同样提示我们,应该重新捡拾起那些在传统新闻学研究中受到重视而在今天的数字新闻学研究中被忽视的理论视角,例如来自人文学科传统的批判文化理论、话语理论、叙事分析与风格理论(genre theories)等。
当采用归纳的方法进行理论化之时,学术界同样不应该完全抛弃传统理论,更有益的方式是将其纳入数字化语境,批判并发展它。美国学者Reese和Shoemaker等将他们早年提出的层级影响理论(the Hierarchy of Influences Model)放在新的数字化条件下重新理论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和榜样。在1996年出版的《中介化信息》(Mediating the Message)一书中,两位学者提出了著名的分析层级影响的模型来梳理形塑媒介内容的多重因素。这一模式将塑造媒介内容的因素区分为从微观到宏观五个层级,分别是:个体、常规、组织、社会制度和社会系统。针对学术界在数字时代寻找新理论的潮流,两位学者于2016年发表文章认为,针对数字图景的变迁,学者的任务并不是批判这个理论的过时或无用,而更应该思考和探讨在今天的数字时代背景下,这个理论框架是否缺失了新的维度、它的概念前提是否需要得到调整、如何将新的维度吸纳进来,使之适用于新的媒介环境。Shoemaker和Reese(2013)由此重访这一理论观点,探讨了这一理论哪些内容应该调整、哪些应该被保留,以及如何将旧的与新的整合协调起来。他们认为,尽管存在概念流的转变以及空间转向,层级影响的理论观点仍然是一个有用的组织模式和标准,它可以被用来观察媒介力量之间的去稳定化以及彼此之间的联合,并且同样具有解释性力量。不过,针对数字化之后新闻图景的转变,层级影响理论需要更加强调层级之间(个体、常规、组织、制度和体制)的网络连接交互的以及多种方向的联系。因此,从两位学者对他们的理论的反思来看,一个基本的命题仍然是延续的,这就是社会结构定义并且支持了媒介化的空间,进而定义了话语空间,它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出现而发生本质的变化。连续而非断裂反倒构成了他们进行数字新闻学理论创新的源泉。除这两个学者,其他如Sharon Meraz和Zizi Papacharissi (2016)以及Peter Bro (2017)等均曾经重访传统新闻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如议程设置、信息守门和框架理论等,探讨了这些概念以及它们所立基的理论、方法论和经验基础在21世纪究竟如何可能继续发生意义并且与当下产生关联。
第四,价值关怀应有连续性。早年的新闻学研究一直抱持着一种朴素的理想,就是关注新闻与信息民主、新闻在塑造公共文化上的核心价值以及新闻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等。除自由主义之外,多样的价值关怀和规范性理念,如进步主义、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和人文主义等,都曾构成新闻学理论的价值锚,为探讨新闻业如何塑造公共生活提供价值起点。数字技术的出现并不天然颠覆这些价值,而是值得在数字时代延续。如Robinson等(2019: 374)所言,“规范性意识”(normative awareness)应该是数字新闻学者的一个使命。他所说的规范性意识,一方面是指研究者需要对自己所持的规范性假设保持警惕和反省,另一方面则是指在展开自己研究的时候,应该受到价值规范的指引,如此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但是,在数字时代保持这一连续性似乎更具挑战,这是因为,技术所激发的乐观图景和想象也许很容易自然合理化一些价值,如Kreiss和Brennen(2016)等批判的,“参与”和去中心化等价值往往很容易被不加质疑地拥抱。因此,面对技术的影响,学术界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该建立在继续维系一直依赖的价值关怀的基础上,始终追问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变迁究竟如何重构公共生活。任何方向的概念化和理论努力最终都应该回到这一价值轨道当中来,如当讨论新闻的时间性、运用时间性概念来考察数字新闻业之时,就需要追问时间性的改变究竟如何塑造公共信息的提供和消费,进而如何形塑公共生活。当然,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何为公共性,何为公共生活,尚需以更具包容性(inclusive)的框架来理解,而不能停留在传统上较为窄义的理性化形态上,以避免理性偏见所带来的研究偏向;二是关于技术如何塑造公共生活,追问的方向既应该是正向的,如技术能否扩大信息民主和赋权,同时更应该是反向的,对技术的反公共文化角色展开深入反思。如Schudson(常江等,2020)所言,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是消极的和侵蚀性的,因此,采取批判研究的视角,去辨识、勾勒和揭示那些由于技术变迁所导致的错综复杂的信息传播现象中存在的“伪民主”,可能是数字新闻学研究更重要的任务,也是数字新闻学理论的重要一环。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如果说数字新闻学在第一个十年因为强调变迁及与传统的断裂而有所收获的话,在下一个十年,有意识地推进有关连续和传承问题的思考,必将有助于数字新闻学发展得更加丰富和完善。
五、结语
本文从学科范式的特点出发,讨论了今天进一步展开数字新闻学研究所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重点放在如何进行理论化和理论创新上。本文提出,通过厘清四个基本问题,将有助于数字新闻学研究下一步的理论化任务:1.应该明确究竟在何种学科范式下进行理论创新;2.倘若明确了社会科学范式下的理论建构目标,就需要遵循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规律;3.对传统新闻学研究背后的基本概念或假设保持反思;4.对新闻学研究的传统仍然应强调连续而非断裂。
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化关乎数字新闻业的未来,当学者们在谈论数字新闻学的未来之时,似乎难逃二元争论:一方是技术未来主义,对技术所带来的变迁充满乐观想象,另一方则是技术怀疑主义,对技术的侵蚀性角色始终保持警惕。那么,数字新闻的时代,究竟是一个黄金时代,还是一个取悦受众的专业贫瘠化的时代?这是《Routledge数字新闻学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结语中Toby Miller(2016)的发问。一方面,人们看到了传统严肃新闻业的衰落,难以担当信息守门人的角色。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新闻场域涌现出众多的新闻行动者,尤其是数字赋能条件下公民新闻的成长、网络连接的新闻业,以及新闻协作的多样形态;看到数字透明性的增强,受众参与的兴起。数字技术赋能了机构化以及新兴的新闻行动者,使得他们有机会探索多样的表达形态,如数据沉浸式新闻;受众测量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媒体可以更为精确和即时地了解受众需求和偏好,并可能按照他们的偏好和需求来安排新闻的生产。但是人们也看到,与社交媒体、平台经济和大数据技术兴起相关联的是新闻价值导向迎合、读者霸权(readers’ hegemony)进一步崛起,社会进一步走向娱乐化、琐碎化和最大公约数化;新闻消费的自主性与新闻多样性的增强在西方社会正在塑造政治极化,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同时兴起。上述的二元悖论不仅在西方社会存在,在许多方面它们在中国社会也有所表现,而且似乎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持续存在,造成迷雾一般的现实,进一步增强我们对于不确定时代的感受。
Miller(2016: 593)认为,“将历史学与当代性并置,将政治经济学、民族志与对技术的采纳和多媒体技能并置,这才是不确定时代给我们最好的指引”。对此,我的理解是,我们需要的,也许并非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而是既考虑过去,也考虑未来;既考虑文本,也考虑文本与语境之间关联,在不同的文化社群、民族国家、传播环境和历史时代展开多元研究。数字新闻学理论架构的目标,并不是追求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理论学说,在这里,理论应该是复数,是theories,它应该是上述这些多元研究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行动。■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社会科学是指广义的社会科学,它不仅包括窄义的以实证主义为出发点所发展的量化研究传统,更包括后实证主义、阐释学派和批判学派等这些范式对实证主义的发展和补充。因此这一社会科学是与人文学科具有较丰富的交融的学科范式,其目的是理解和认识人类的社会活动。
参考文献:
白红义,张恬(2021)。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4),109-132。
常江,克里斯·安德森,迈克尔·舒德森,托德·吉特林(2020)。新闻学的未来:数字生态与全球语境——中、英、美三国新闻学学者的对谈(下)。《新闻界》,(11),14-20+61。
陈阳(2019)。每日推送10次意味着什么?——关于微信公众号生产过程中的新闻节奏的田野观察与思考。《新闻记者》,(9),23-31。
李艳红(2017)。在开放与保守策略间徘徊:不确定性逻辑下的新闻创新。《新闻与传播研究》,(9),40-60。
刘昌德(2020)。小编新闻学:社群媒体与通讯软体如何转化新闻业。《新闻学研究》,(1),1-58。
刘鹏(2019)。用户新闻学:新传播格局下新闻学开启的另一扇门。《新闻与传播研究》,(2),5-18+126。
陆晔,周睿鸣(2016)。“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7),24-46。
王辰瑶,喻贤璐(2016)。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以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新闻记者》,(3),10-20。
王海燕(2019)。加速的新闻: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工作的时间性变化及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10),36-54+127。
张志安,汤敏(2018)。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新闻与写作》,(3),56-65。
Al-RawiA. (2017). News values on social media: News organizations’ Facebook use. Journalism, 18(7)871-889.
Allan, S. (2013). Citizen witnessing: Revisioning journalism in times of cri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ndersonC. W. (2010). Journalistic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local news: The briefhappy news life of the“Francisville Fou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7(3)289-309.
AndersonC. W. (2011). Blowing up the newsroom: Ethnography in an age of distributed journalism. In DomingoD. & Paterson, C. (Eds. ). Making Online News-Volume 2: Newsroom Ethnographies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Internet Journalism(pp. 151-160). New York: Peter Lang.
AndersonC. W. (2016). News ecosystems. In Witschge, T. , Anderson, C. W. , DomingoD. , & HermidaA.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pp. 410-423). Sage.
Beckett, C. , & DeuzeM. (2016). O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Social Media + Society2(3):1-6.
BensonR. (2008). Journalism: normative theories. In Donsbach, W. (Ed. ).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6) (pp. 2591-2597). New York: Wiley.
BorgerM. , Van Hoof, A. , & SandersJ. (2016). Expecting reciprocity: Towards a model of the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on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18(5)708-725.
Bro, P. (2016). Gatekeeping and agenda-setting: Extinct or extant in a digital era?. In Franklin, B. , & Eldridge II, S. (Eds. ).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pp. 75-8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arlson, M. (2016). Sources as news producers. In Witschge, T. , Anderson, C. W. , DomingoD. , & HermidaA.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pp. 236-249). Sage.
Carlson, M. (2018). Confronting measurable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6(4)406-417.
ChadwickA. (2013).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rubini, F. , & NielsenR. K. (2016). Editorial Analytics: How News Media Are Developing and Using Audience Data and Metrics. Digital News Project 2016.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August 202021from https://www. digitalnewsreport. org/publications/page/6/.
ConoleG. , & Dyke, M. (2004). What are the affordanc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LT-J: Research in Learning Technology, 12(2)113-124.
CowardR. (2013). Speaking personally: The rise of subjective and confessional journalism. Hounds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DahlgrenP. , & Sparks, C. (Eds. ). (1992).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Sage.
Deuze, M. (2008).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news work: Liquid journalism for a monitorial citizen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18.
DonmingoD. , MasipP. , & Costera Meijer, I. (2015). Tracing Digital News Networks. Digital Journalism, 3(1)53-67.
Domingo, D. , Quandt, T. , Heinonen, A. , PaulussenS. , Singer, J. B. , & Vujnovic, M. (2008).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practices in the media and beyon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nitiatives in online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2(3)326-342.
DuncanS. (2012). Sadly missed: The death knock news story as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grief. Journalism, 13(5)589-603.
FranklinB (2013). Editorial. Digital Journalism, 1(1): 1-5.
HallinDC. & P. Mancini2004. Introduction. In Hallin, D. & Mancini P.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ngtonS. (2008). Popular news in the 21st century: Time for a new critical approach?. Journalism, 9(3)266-284.
HassanR. (2019). Digitality, virtual reality and the‘empathy machine’. Digital Journalism, 8 (2)196-212.
Hermida, A. (2010). Twittering the news: The emergence of ambient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4(3)297-308.
Hermida, A. (2016). Social media and the news. In Witschge, T. , Anderson, C. W. , DomingoD. , & HermidaA.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pp. 81-94). Sage.
Hermida, A. , LewisS. C. , & Zamith, R. (2014). Sourcing the Arab Spring: A case study of Andy Carvin’s sources on Twitter during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3)479-499.
JarvisJ. (2006). Networked Journalism. Buzz Machine. Retrieved August 202021from http://www. buzzmachine. com/2006/07/05/networked-journalism.
KuikenJ. , Schuth, A. , Spitters, M. , & Marx, M. (2017). Effective Headlines of Newspaper Articles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Digital Journalism, 5(10)1300-1314.
KreissDaniel & J. S. Brennen (2016). Normative Models of Digital Journalism. In Witschge, T. , Anderson, C. W. , DomingoD. , & HermidaA.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pp. 299-315). Sage.
Lewis, S. C. (2012).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Lischka, J. A. (2021). Logics in social media news making: How social media editors marry the Facebook logic with journalistic standards. Journalism, 22(2)430-447.
Meraz, S. , & Papacharissi, Z. (2016). Networked framing and gatekeeping. In Witschge, T. , Anderson, C. W. , DomingoD. , & HermidaA.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pp. 95-112). Sage.
MillerT. (2016). Epilogue: Digital Journalism: A golden agea data-driven dreama paradise for readers—or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a profess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pp. 589-594). Routledge.
Mj?set, L. (2006). No fear of comparisons or context: on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omparative Education42(3)337-362. as cited in Steensen, S. & Westlund O. (2020). What i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Routledge.
PapacharissiZ. , & de Fatima Oliveira, M. (2012). Affective news and networked publics: The rhythms of news storytelling on# Egyp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2(2)266-282.
Parks, P. (2020). Toward a humanistic turn for a more ethic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21(9)1229-1245.
PavlikJ. V. (2017). Data, Algorithms, and Code: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m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age. In Franklin, B. , & Eldridge II, S. (Eds. ).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pp. 265-273). Routledge.
PicardR. G. (2011). The economics and financing of media compani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icardR. G. (2016). Funding digital journalism: The challenges of consumers and the economic value of new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pp. 146-154). Routledge.
Reese, S. D. , & ShoemakerP. J. (2016). Media sociology and the hierarchy of influences model: A levels-of-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19(4)389-410.
RobinsonS. , LewisS. C. , & CarlsonM. (2019). Locating the “digital” in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Transformations in research. Digital Journalism, 7(3)368-377.
Russell, A. (2013). Innovation in hybrid spaces: 2011 UN Climate Summit and the expanding journalism landscape. Journalism, 14(7)904-920.
RyfeD. M. (2016). News institutions. In Witschge, T. , Anderson, C. W. , DomingoD. , & HermidaA.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pp. 370-382). Sage.
Siebert, F. , Peterson, T. , & SchrammW. (1984).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oemaker, P. , & Reese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2nd ed. ). New York: Longman.
Shoemaker, P. J. , & ReeseS. D. (2013). 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 New York: Routledge.
Sparrow, B. H. (1999). Uncertain guardian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teensenS. , & Ahva, L. (2015). 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 Digital Journalism, 3(1)1-18. ?
SteensenS. , Gr?ndahl Larsen, A. M. , H?gvarY. B. , & Fonn, B. K. (2019). ?What Doe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Look Like? Digital Journalism, 7(3)320-342.
SteensenS. & Westlund O. (2020) . The theories: How digital journalism is understood. In SteesenS. & Westlund O. (2020) . What i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pp. 55-71). Routledge.
StrossB. (1999). The hybrid metaphor: From biology to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2(445): 254-267.
Tandoc Jr, E. C. (2014). Journalism is twerking? How web analytics is changing the process of gatekeeping. New media & society16(4)559-575.
Tandoc Jr, E. C. , & Thomas, R. J. (2015). The ethics of web analytics: Implications of using audience metrics in news construction. Digital journalism, 3(2)243-258.
ThussuD. K. (2007). News as entertainment: The rise of global infotainment. Thousand Oaks, CA: Sage.
Usher, N. (2013). Al Jazeera English online: Understanding web metrics and news production when a quantified audience is not a commodified audience. Digital Journalism, 1(3)335-351.
VuH. T. (2014). The online audience as gatekeeper: The influence of reader metrics on news editorial selection. Journalism, 15(8)1094-1110.
Wahl-Jorgensen, K. (2014). Changing technologies, changing paradigms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Emotionality, authenticity and the challenge to objectivity. In ZimmermanC. & SchreiberM (Eds. ). Technologies, media and journalism(pp. 264-283)Campus/Yale University Press.
Wahl-Jorgensen, K. (2016). Emotion and journalism. In Witschge, T. , Anderson, C. W. , DomingoD. , & HermidaA.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pp. 128-143). Sage.
Wahl-Jorgensen, K. (2020). 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 Digital Journalism, 8(2)175-194.
WitschgeT. , Anderson, C. W. , DomingoD. , & HermidaA. (2019). Dealing with the mess (we made): Unraveling hybriditynormativityand complexity in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20(5)651-659.
ZamithR. (2016). On metrics-driven homepages: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ity and prominence. Journalism Studies.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Sage.
Zelizer, B. (2009). Introduction: Why journalism’s changing faces matter. In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 (pp. 1-10). New York: Routledge.
李艳红系中山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项目编号:19ZDA335)子课题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