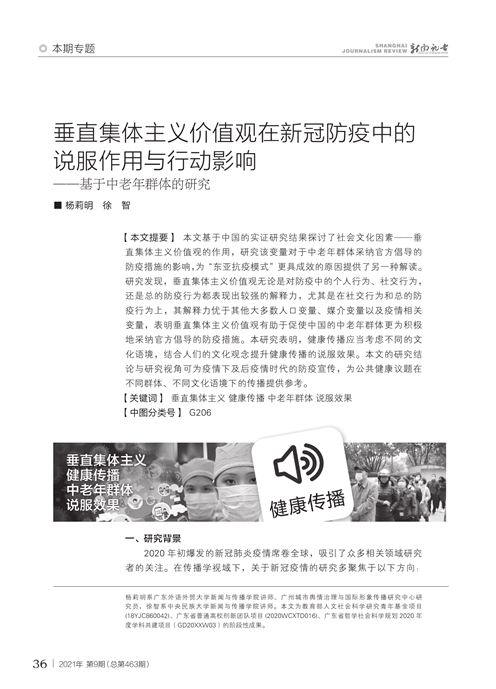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新冠防疫中的说服作用与行动影响
——基于中老年群体的研究
■杨莉明 徐智
【本文提要】本文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作用,研究该变量对于中老年群体采纳官方倡导的防疫措施的影响,为“东亚抗疫模式”更具成效的原因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研究发现,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无论是对防疫中的个人行为、社交行为,还是总的防疫行为都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在社交行为和总的防疫行为上,其解释力优于其他大多数人口变量、媒介变量以及疫情相关变量,表明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有助于促使中国的中老年群体更为积极地采纳官方倡导的防疫措施。本研究表明,健康传播应当考虑不同的文化语境,结合人们的文化观念提升健康传播的说服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与研究视角可为疫情下及后疫情时代的防疫宣传,为公共健康议题在不同群体、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垂直集体主义 健康传播 中老年群体 说服效果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背景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吸引了众多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在传播学视域下,关于新冠疫情的研究多聚焦于以下方向:不同媒介公信力的对比(张洪忠,梁爽,王競一,2020);媒介使用对受众心理健康(Chao et al., 2020)、对受众疫情感知和个体行为(闫岩,温婧,2020)的影响;新冠信息过载对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的影响(陈琼,宋士杰,赵宇翔,2020);对公共信息传播模式作出反思(彭兰,2020);或是关注风险感知等相关因素的影响(Abdelrahman, 2020;He et al., 2020;章燕等,2020);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的媒体使用与信息寻求行为(贺建平,杜宝珠,黄肖肖,2021)以及中国公众的防疫行为、信息获取与风险感知(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等。诚然,媒介与信息传播对健康行为有重要作用,但当新冠疫情在全球广泛传播时,研究者需要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视角,关照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和不同群体间的更多研究维度。近年来越来越多健康传播研究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因素,许多研究都证明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对健康行为意向或相关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Yu & Shen, 2013; Dillon & Basu, 2016; Chang & Basnyat, 2017; Shafer, Kaufhold & Luo, 2018; 邱鸿峰,彭璐璐,2016)。有学者认为东亚国家能有效抗击新冠疫情是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Fan, 2020; Han, 2020; Murphy, 2020; Rosker, 2021; 新民晚报,2020-04-30),因而当研究新冠防疫宣传效果时,也应将文化因素考虑进去。这不仅有助于探索健康传播研究的新视角,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众沟通以及全球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抗疫宣传也能提供思路。
本文尝试超越媒介与信息的视角,以文化价值观作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切入点,关注中国社会主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公众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重点研究了其中一个维度——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作用,通过定量研究方法,测量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于人们采纳政府所倡导的防疫举措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我们选择了中老年群体。因为在研究肇始期以及疫情早期,中老年群体是健康传播的重点人群,年轻人与家中长辈就“是否应该出门活动”、“过年是否应该聚餐”、“是否应该佩戴口罩”等问题产生冲突,引发了诸多网络讨论和媒体关注。国家卫健委明确指出,老年人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和高危易发人群,相关部门要将这一人群的疫情防控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01-28)。并且,中国的中老年人是受到具有传统文化根基以及作为社会规范和核心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深远影响的典型人群,故选择在该群体中探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作用,以理解文化价值观对于人们采纳官方倡导的防疫举措的影响,从而在文化层面扩展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并为公共卫生议题的科普和健康行为的宣导提供新的思路。
二、文献综述
经典社会学理论存在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两种不同的取向。韦伯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进程与结果进行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2019:119),指出社会行动是社会学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要研究社会,就要把握社会行动。社会行动指的是“行动中的个人给他的表现附加了某种主观意义”(韦伯,2019:119),即在内涵上指的是以其他人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的行动,只有通过理解和阐释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探求其行为目的、意义和价值才能认识社会。该理论取向突出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相对于韦伯的社会行动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认为个人的行动会受到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塑造和制约。帕森斯指出,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出于对社会共同价值取向的依附,做出趋于相似的行动,服从社会期望,从而通过共享规范,使个人联结成社会,使得社会系统得以运作(Parsons, 1951:41)。而吉登斯打破了前人的“结构—行动”二元对立,认为对于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行动者和结构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吉登斯,1998:89):个人的行动受到社会系统的制约,与此同时,行动者在互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又重构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互相建构的关系。
从“二重性”的视角来看,健康行为虽出于个人意愿,但是同样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传播的社会维度来看,健康行为受到微观个体性因素、中观群体性因素、宏观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喻国明,潘佳宝,Kreps, 2017)。群体/社会对个人健康行为决策产生的影响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个人与家人朋友的交流会对疫苗接种意向产生影响(郭小安,王天翊,2020);个人健康行为除了受到对不健康行为后果的担忧及健康行为益处的影响,还受到社会规范以及外部生态环境的约束、健康传播层面等影响(郭沁,2019);“意见领袖”在老年人健康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老年人通过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及社会嵌入与健康信息共享行为正相关(Liu, Yang & Sun, 2019);在健康传播的说服效果上,他者取向策略(即有利于他人、社会)比自我取向策略(即利于自我)表现出更强的说服力(Kelly & Hornik, 2016;陈经超,黄晨阳,2020)。不过,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他者”产生的效果有所不同:在美国的研究中,与自己社会距离较近的他者和作为陌生人的他者所产生的说服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异(Kelly & Hornik, 2016),但是在中国作为家人的他者产生的效果是最显著的(陈经超,黄晨阳,2020),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所导致的差异。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近年来跨文化视野下的健康传播研究加入了对文化因素的考虑,包括对民族文化差异的研究,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对健康和健康行为的理解差异(苏婧,李智宇,2019)。有研究表明,文化背景因素会对受众的疫苗接种(Yu & Shen, 2013)、临终关怀(Dillon & Basu, 2016)、日常健康管理(Chang & Basnyat, 2017)、乳腺组织捐献(Shafer et al., 2018)、艾滋病歧视及安全性行为(邱鸿峰,彭璐璐,2016)等方面产生影响。
在新冠疫情相关研究中,文化价值观同样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研究表明,具有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国家的民众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口比例较低,从而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较低(Huynh, 2020);中国居民的疫情防护可能受到经济因素和儒家价值观的影响(Xu et al., 2021)。一些中外学者认为,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能够比西方国家更为成功地应对和控制疫情是因为儒家文化的根源(Fan, 2020; Han, 2020; Murphy, 2020; Rosker, 2021; 新民晚报,2020-04-30),而与各国政治制度的自由程度无关(Mayer, Schintler & Bledsoe, 2020)。一派主要从政治上作解读,比如Murphy(2020)将之归因为东亚的精英阶层需要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维护政权合法性,Han(2020)认为儒家思想使东亚民众更信任和服从国家,不排斥大规模的数字监控;另一派如香港城市大学范瑞平教授则从伦理学角度进行反思,认为儒家天命美德伦理、家庭主义、和谐主义使东亚国家采取积极的抗疫举措,否决有违孝道和仁爱的“群体免疫”策略(Fan, 2020)。本文作者认为,控制疫情的关键在于个人行动自由与社会公共安全之间的矛盾,儒家文化以家庭伦理关系为核心来形塑社会关系,形成“家国天下”观,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因此范瑞平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以人伦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结构恰如费孝通所言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序差”(费孝通,1985:25)。以伦理为本位,“以家庭关系推广发挥,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梁漱溟,2005:73)。通过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使个人嵌入于社会伦理关系网中,导致“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一个中国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梁漱溟,2005:82)。因而中国文化传统始终表现出以群体融合个体的倾向,强调个人从属于群体,一旦发生利益冲突,个体或个体所属的某个小群体的利益必须服从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换言之,就是将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唯一参照物,要求社会的个体成员无条件服从社会需要(孙英春,2008:116)。这种倾向即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社区或群体的和谐,个人与群体、社会联系紧密,相互依赖程度高,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种经济利益上的关系,而是道德的关系,强调了个人对家族、组织或社会的忠诚(孙英春,2008:111-112)。
近代以来,儒家伦理虽然受到政治运动、社会思潮和社会转型的冲击,但它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一脉相承,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普及提供了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标准得以弘扬,并且它还表现为一种社会公德,着眼于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协调,并以此支撑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崔家新,池忠军,2019)。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主义更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成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对个人来说不是遵循不遵循的问题,而是必须服从的一种命令式的规范要求(马永庆,2016)。青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并逐步稳定的关键时期(张进辅,2007),当代的中老年人出生、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生活、生产、消费等都要服从国家的计划和安排,集体主义价值观给他们的成长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虽然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个人主义逐渐增强,集体主义不再是政治命令式的社会规范,但它依然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道德原则和主流价值观。
在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防疫宣传策略,通过各类媒介渠道倡导个人做好防疫措施,早期宣传的防疫举措主要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外出、不串门、不聚会聚餐这五种行为。若要配合官方的防疫宣传,个人可能要在日常习惯和生活便利上作出一些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会形成一定的冲突,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缓和的作用。
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提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是用于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四个维度之一(Hofstede, 1980:220)。特里安迪斯(Triandis)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水平(即horizontal, 强调社会成员身份地位平等)和垂直(即vertical, 强调个体间的不平等和权力关系中的等级)这两个维度,从而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划分为水平个人主义、垂直个人主义、水平集体主义、垂直集体主义这四种类型(Singelis et al., 1995; Triandis, 1995)。
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两个维度中,相对于水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所认可的社会成员身份平等、互相依赖、不轻易屈从权威,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表现为认同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关系,强调群体内团结一致,提倡个人为集体服务、奉献甚至牺牲。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体现的是家庭成员间的凝聚力、责任感以及牺牲精神,还有对群体决策的服从(Triandis & Gelfand, 1998)。从辛格利斯(Singelis)等学者所使用的量表(Singelis et al., 1995)来看,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测量更偏向于家庭语境,在题项中“集体”多以“家庭”、“家人”为参照,这亦符合中国人“重视亲属团体和家庭生活,对家庭有较强的责任感”(孙英春,2008:116)的特点。并且,家庭是大多数人主要的隔离场所,在疫情下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而,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测量适用于此研究情境。有关研究也表明,垂直集体主义倾向是一个会对健康行为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邱鸿峰,彭璐璐,201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否与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有关?
根据防疫行为是否涉及与人交往,作者进一步将官方倡导的五种行为分为个人行为(戴口罩、勤洗手)和社交行为(外出、串门、聚会聚餐),以探讨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两类不同的行为的作用:
RQ-1: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否与中老年人防疫中的个人行为有关?
RQ-2: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否与中老年人防疫中的社交行为有关?
个人的健康行为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风险感知。研究表明,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信息、疫情严重程度主要通过风险感知对公众的风险传播行为起作用(章燕等,2020),风险感知是个人在新冠疫情期间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的预测因素之一(Abdelrahman, 2020),个人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感知与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和行动相关(闫岩,温婧,2020)。并且,在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中,人们对健康信息的认知需求(牟怡,张林,2020)或是寻求信息的动机的强烈程度(Kim & Jung, 2017)也同样会产生影响。还有许多学者关注了媒介接触与信息来源的影响(Chao et al., 2020; He et al., 2020;郭小安,王天翊,2020;张洪忠,梁爽,王競一,2020;闫岩,温婧,2020;陈琼等,2020),发现不同类型的媒介在疫情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人口统计特征中,性别(Kim & Jung, 2017; Abdelrahman, 2020)、年龄(Xu et al., 2021)、文化程度(李海月等,2012;李凤萍,喻国明,2019)、社会经济地位(Kim & Jung, 2017)等因素都被证明会对健康认知和健康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也在研究中纳入了对上述变量的考量。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及其实施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调查实施的时间为2020年2月7日至2月17日,由于疫情期间不便登门,调查主要通过寒假回家过年的大学生将问卷发给家中符合条件的亲人填写,要求一户只调查一人,并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于年龄及对应人群的划分(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要求受访者年龄需在45周岁及以上。比起通过微信或调查网站发布问卷,这种方式可较好地保证问卷的填写者符合调查要求,并且有学生在旁,可及时答疑和提供指导,避免中老年人因为不明白或不会操作而误填,从而获得较好的填答质量以及保证问卷的回收效率,同时也能获得来自于全国多个省市的调查样本,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根据95%的置信度和4%的允许抽样误差范围,可计算出需要样本约600个。最终问卷共计回收720份,根据完成用时、年龄限制、填答逻辑一致性等多重标准的严格筛查,去除无效问卷175份,保留有效问卷545份,遍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效回收率为75.69%。本文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通过AMOS24和SPSS24来完成。
(二)变量的设置
1.因变量的设置
本文所研究的防疫宣传说服效果与行动影响是通过测量受访者遵循官方所倡导的五种防疫举措的程度来体现的,五种举措对应五个指标:戴口罩、洗手、散步逛街、串门、聚会聚餐。在调查中,我们要求受访者自我报告自疫情发生以来自己日常生活中采取上述五种行为的频率,以五级量表的形式进行测量,后三种行为需先进行反向编码再统计,得分越高表示越积极采纳官方倡导的防疫行为,说服效果越好。如前所述,防疫行为可分为个人行为和社交行为两类。个人行为指戴口罩和洗手,将戴口罩的频率得分与洗手的频率得分相加求平均值,可生成“个人行为”这个变量;而社交行为则是指外出散步逛街、串门、聚会聚餐,将三种行为频率反向编码后的平均值作为“社交行为”变量的取值;上述五种行为的平均值即“总的防疫行为”这个变量。个人行为、社交行为和总的防疫行为将作为三个因变量用于后续的统计分析。各项行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2.自变量的设置
本文中的自变量可分为媒介接触变量、疫情相关变量、价值观变量和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1)媒介接触变量
包括大众媒体变量、新媒体变量、人际传播变量。在大众媒体变量的测量中,受访者需要回答分别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社区宣传获知新冠疫情信息的频率,从“从不”到“天天”频率分五级递增,依次赋值1至5,四项的平均值即为大众媒体接触变量。而新媒体变量的测量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分别询问受访者通过新闻网站、百度等搜索引擎、手机新闻应用(APP)、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获知新冠疫情信息的频率,并将这五项得分相加求平均值,生成新媒体变量。人际传播变量的测量则是询问受访者分别通过与子女后辈的交流、与同辈的交流获知新冠疫情信息的频率,两项的平均值即为人际传播变量。媒介接触变量的统计结果参见表2。
(2)疫情相关变量
疫情相关变量包括寻求信息动机和风险感知。寻求信息动机这个变量是通过询问受访者对疫情信息的主动关注度来测量的,从“完全不关注”到“十分关注”五级递增,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寻求疫情信息的动机越强烈。风险感知的测量则是让受访者评估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风险有多高,以五级量表的形式从“非常低”到“非常高”对风险进行评估,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认为自己受到传染的风险越高。这两个变量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3)价值观变量
主要指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测量引用了辛格利斯等提出的量表(Singelis et al., 1995),该量表被国内外众多学者所引用,并且证实了总体上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某些条目不太适合中国人群,因而做了进一步修订(王永丽,时勘,黄旭,2003;黄任之,姚树桥,邹涛,2006;黄任之,肖晶,姚树桥,2007;李花芳,张红静,2017)。然而上述研究者对中国化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量表的修正都是建立在未成年学生或青年学生的基础上,是否适用于不同年龄群体的中国人,尚有待讨论。因此,作者在参考上述学者的中文量表的基础上,采取中英对译的方式,将英文版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量表(Singelis et al., 1995)翻译成中文版。该量表共有8个题项,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该量表的模型作了修正,保留了前四条题项(见表3),使之拟合更佳。经验证,由4条题项所构成的模型的卡方值为5.858,显著性概率值p为0.053,大于0.05,NC值为2.929,小于3,表示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GFI和AGFI的值分别为0.995和0.974,均大于0.90,RMR值为0.022,RMSEA值为0.060,小于0.08,表明整体模型的适配度良好,即由四条题项构成的量表的效度良好。经信度检验,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00,表明信度较佳。
(4)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本次调查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常住地。其中,有效样本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53岁,其余人口特征分布情况参见表4。
四、数据分析
(一)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人口统计特征的关系
从表3可知,有效样本中受访者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均值为4.03,标准差为0.764,表明中国的中老年人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处于较高的水平。而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的中老年人在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上是否表现出显著差异?我们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常住地作为自变量,将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在分析之前,已将性别、职业、常住地这三个分类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人口特征变量中,只有性别、文化程度、收入这三个变量表现出了显著性,即中老年男性受访者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显著高于中老年女性,文化程度越高的中老年人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越高,而收入越高的中老年人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反而倾向于降低。年龄、职业、常住地与受访者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与防疫行为的关系
为了检验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不同的因变量的影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三个因变量:个人行为、社交行为、总的防疫行为,依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这三次的回归分析中,自变量均为人口统计变量、媒介变量、疫情相关变量和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这四类变量。我们以多层回归的方式进行分析,在第一层的回归中加入的自变量是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媒介变量和疫情相关变量,第二层回归则是在第一层回归的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个变量,以对比该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还对感染风险和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数学形式的转换以调整变量分布,使之能够更好地拟合回归。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6中回归方程的标准化系数Beta值及其显著性可知,对于个人行为来说,显著的自变量包括寻求信息动机(β=0.244,p<0.001)、新媒体(β=0.178, p<0.001)、性别(β=0.162, p<0.001)、常住地(β=-0.127, p<0.01)、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β=0.117, p<0.01),可见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于个人层面的防疫行为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相对来说作用不如其他变量,比如寻求信息动机的强烈程度、新媒体接触频率以及人口统计特征更能预测个人行为。
对于社交行为来说,显著的自变量包括收入(β=-0.166, p<0.01)、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β=0.156, p<0.001)、文化程度(β=0.118, p<0.05)、感染风险(β=0.097, p<0.05)。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仅次于收入的第二大影响变量,其解释力甚至超过了对自己可能感染病毒的风险的评估,表现出对带有社交性质的群体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
对于总的防疫行为来说,显著的自变量包括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β=0.172, p<0.001)、寻求信息的动机(β=0.169, p<0.001)、新媒体(β=0.153, p<0.01)、文化程度(β=0.130, p<0.05)、性别(β=0.129, p<0.01)、收入(β=-0.120, p<0.05)、常住地(β=-0.101, p<0.05)、感染风险(β=0.089, p<0.05)。在综合考虑官方所提倡的五种防疫行为的情况下,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更为突出,超越了其他自变量,是对于总的防疫行为来说最具预测力的首要因素。
综上可知,在所有的自变量中,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唯一一个对三个因变量(个人行为、社交行为、总的防疫行为)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的预测力的变量。从三个回归方程的有关系数来看,在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媒介变量、疫情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再加入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个变量后,可以使三个回归方程的R方分别提升1.2%、2.2%和2.7%,并且加入该变量后F值的变化量也很显著,可见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于个人行为、社交行为和总的防疫行为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社交行为和总的防疫行为的解释力尤为显著。
因此,针对前面提出的研究问题,可作出如下回答: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有关,具体而言,它与中老年人防疫中的个人行为、社交行为都是有关的,并且表现出正向的相关关系,这表明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越强的个人,越倾向于采纳官方倡导的防疫行为,并且,该变量对社交行为的影响比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跳出了以往健康传播研究常用的媒介中心主义的既有研究框架(苏婧,李智宇,2019),尝试理解个人行动背后的社会意义,探讨了文化价值观对个人防疫行为的影响。围绕着“东亚抗疫模式为何更具成效”这个问题,范瑞平等学者从儒家伦理的角度作出了回答。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的考量,提炼出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个变量。相较于儒家伦理,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中国传统文化特征、道德标准与政治原则于一体,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受到推崇,因而更接近中国的国情和社会语境,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并且,本文通过量化研究的方式验证了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促使个人采纳官方倡导的防疫行为上发挥的作用,从而为“东亚模式的成功”提供了实证,同时亦有助于在健康传播中建立以说服性传播为核心的跨学科理论体系和规范的效果评价体系(芮牮,刘颖,2020)。
以受到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影响的中国中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本文研究了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该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采纳官方所倡导的防疫行为的影响。总体而言,防疫宣传在中老年群体中所取得的说服效果是比较好的,在五级量表的测量中,无论是个人行为、社交行为还是总的行为的均值都不低于4.60。五种具体行为中略低的一项是散步逛街行为(均值4.28)。这可能是因为散步是中老年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因而说服效果较其他行为差一些,这表明针对中老年群体的防疫宣传应适当地加强关于散步行为的指引和劝导。研究发现,中国中老年群体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普遍比较高,这种价值观受到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低的中老年男性,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越强。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无论对个人行为、社交行为还是总的防疫行为都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说明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越强的个人,越积极采纳官方倡导的防疫行为,防疫宣传的说服效果越好。尤其是在社交行为和总的行为上,其解释力优于其他大多数人口变量、媒介变量以及疫情相关变量。而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社交行为的解释力强于个人行为,作者推测是因为戴口罩等个人行为较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如疫情早期口罩紧缺),导致自变量的作用受到抑制,而外出等社交行为相对而言在较大程度上是个人意志可以决定的行为,因而价值观变量能够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
正如前文所言,本文所测量的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主要反映的是个人对于以家庭为主的集体的归属感与责任感。越重视该集体利益,越倾向于在个人利益上作出一定的让步,采纳更多的个人防御行为(戴口罩、洗手),约束和减少自己的社交行为(外出、串门、聚会等)。这不仅与中国社会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文化传统有关,亦与中老年人的生命周期特征有关:家庭关系与家庭利益对于中老年群体的意义显然比年轻群体更具复杂和深重的内涵。另外,疫情爆发时,家庭成为主要的隔离场所,防疫公共话题的引入、大屏媒介的重启、子代的回归这三者相互作用使得家庭强连接关系得到增强(王冬冬,陈舒婷,2021)。这些因素使得家庭这一集体在疫情下显得尤为重要,最终促使中老年群体听从健康科普和防疫倡导,戴起口罩放弃聚会。这一结论与陈经超和黄晨阳(2020)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即在中国,当家人作为“他者”时“他人取向”的健康传播策略产生的效果是最显著的。因此,政府、医疗机构与健康传播组织在针对中老年人这一典型的垂直集体主义观念较强的群体进行健康信息和健康行为的宣导时可重点诉诸家庭利益,或比其他诉求(如诉诸个人利益或社会利益)更具有说服力。除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之外,后疫情时代的防疫宣传(如劝服接种疫苗)亦可参考以家庭为诉求的沟通策略。中国社会以家庭伦理关系来形构社会关系,以家庭推及社会,形成“家国天下”观,家与国被视为一脉相通的利益共同体。同时,作为社会规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个人要融入集体,在集体利益面前做出个人利益的让步,服从群体决策,从而解决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共安全利益之间的两难。因此中国民众更愿意服从国家在疫情期间的管控,国家亦易于主导抗疫形势,不像西方社会民众抱有个人自由至高无上的信念,对政府管理手段介入日常生活十分排斥,导致疫情管理失控。这正是文化价值观在面对全球危机时展现的力量。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健康传播应当考虑不同的文化语境,结合和利用人们的文化观念提升健康传播的说服效果。当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之时,无人能置身事外,全社会需要被动员起来共同抗疫。集体主义价值观能调和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因此防疫宣传应当考虑和利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作用。这一结论基于中国,但并不仅适用于中国。正如特里安迪斯(Triandis)和盖尔芬德(Gelfand)所言,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共存在同一国家、文化,甚至个人身上(Triandis & Gelfand, 1998),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受众在垂直集体主义维度上同样是有所表现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同样可以探讨这一变量的影响。本文可为公共健康议题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提供可参考的路径,但由于篇幅所限,仅讨论了垂直集体主义这一个维度,未来的研究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不同维度开展跨文化比较,也可在不同的代际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中开展对比研究,结合质化研究方法,深挖文化意涵,以进一步理解文化价值观对健康传播的影响。■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
陈经超,黄晨阳(2020)。“自我取向”还是“家人取向”?——基于中国情境的大学生流感疫苗接种健康传播策略效果研究。《国际新闻界》,(6),98-113。
陈琼,宋士杰,赵宇翔(202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过载对用户信息规避行为的影响:基于COVID-19信息疫情的实证研究。《情报资料工作》,(3),76-88。
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新冠疫情下中国公众的知与行——基于“全国公众科学认知与态度”调查的实证研究。《新闻记者》,(5),3-13,96。
崔家新,池忠军(2019)。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演进历史与新时代发展。《思想理论教育》,(11),59-64。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郭沁(2019)。健康行为的社会规范性影响和从众心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80-92。
郭小安,王天翊(2020)。新媒体接触、健康信念与HPV疫苗接种意向。《新闻与传播研究》,(6),58-74。
贺建平,杜宝珠,黄肖肖(2021)。城市老年人新冠肺炎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基于扩展的信息寻求综合模型。《新闻记者》,(3),63-75。
黄任之,肖晶,姚树桥(2007)。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潜结构在大中学生中的验证。《中国心理卫生杂志》,(6),393-394。
黄任之,姚树桥,邹涛(2006)。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中文版信度和效度的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6),564-565,563。
李凤萍,喻国明(2019)。健康传播中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信息渠道对知沟的交互作用研究——以对癌症信息的认知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143-150。
李海月,吴双胜,杨鹏,张奕,黎新宇,王全意(2012)。北京市郊区老年人传染病相关知识、行为和技能现状。《中国预防医学杂志》,(1),51-54。
李花芳,张红静(2017)。中文版文化价值取向量表信效度检验及其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09),122-127。
梁漱溟(2005)。《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2019)。《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永庆(2016)。集体主义话语权的重构。《道德与文明》,(4),106-113。
牟怡,张林(2020)。个体差异与信息特征对健康信息信任和行为意向的影响——基于ELM的实验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8),137-142。
彭兰(2020)。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对新冠疫情期间新媒体传播的反思。《新闻界》,(5),36-43。
邱鸿峰,彭璐璐(2016)。集体主义文化与艾滋歧视报道的第三人效果。《新闻界》,(21),11-20。
芮牮,刘颖(2020)。健康传播效果研究的缺失与路径重构。《新闻与写作》,(8),59-67。
苏婧,李智宇(2019)。超越想象的贫瘠: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全球传媒学刊》,6(3),4-33。
孙英春(2008)。《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永丽,时勘,黄旭(200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结构的验证性研究。《心理科学》,(6),996-999。
新民晚报(2020-04-30)。《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抗疫东亚模式》。检索于https://new.qq.com/omn/20200430/20200430A0M49X00.html。
闫岩,温婧(2020)。新冠疫情早期的媒介使用、风险感知与个体行为。《新闻界》,(6),50-61。
喻国明,潘佳宝,Kreps,G.(2017)。健康传播研究常模:理论框架与学术逻辑——以“HINTS中国”调研项目为例。《编辑之友》,(11),5-10。
张洪忠,梁爽,王競一(2020)。官方渠道、人际传播、自媒体: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渠道公信力分析。《新闻与写作》,(4),37-42。
张进辅(2007)。论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与引导。《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82-87。
章燕,邱凌峰,刘安琪,钟淑娴,李介辰(2020)。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模型研究——兼论疫情严重程度的调节作用。《新闻大学》,(3),31-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01-28)。《关于做好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检索于http://www.nhc.gov.cn/lljks/tggg/202001/96e82ba8a14d41b283da990d39771493.shtml。
Abdelrahman, M. (2020). Personality traits, risk perception, and protective behaviors of Arab residents of Qatar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https://doi. org/10. 1007/s11469-020-00352-7.
Chang, L. , & BasnyatI. (2017). Exploring Family Support for Older Chinese Singaporean Women in a Confucian Society. Health Communication32(5)603-611.
ChaoM. , XueD. , LiuT. , Yang, H. , & Hall, B. J. (2020). Media use and acut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74102248.
DillonP. J. , & Basu, A. (2016). African Americans and hospice care: A culture-centered exploration of enrollment disparities. Health communication31(11)1385-1394.
Fan, R. (2020).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81-107.
Han, B. (2020). We cannot surrender reason to the virus. Retrived from https://write. as/0hwmokmqr13vm2fw.
HeS. , Chen, S. , Kong, L. , & LiuW. (2020). Analysis of Risk Perceptions and Related Factors Concerning COVID-19 Epidemic in ChongqingChina.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doi: 10. 1007/s10900-020-00870-4.
Hofstede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Sage.
Huynh, T. L. D. (2020). Does culture matter social distancing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Safety Science130104872.
Kelly, B. J. , & Hornik, R. C. (2016). Effects of framing health messages in terms of benefits to loved ones or others: An experimental study. Health Communication31(10)1284-1290.
Kim, J. , & Jung, M. (2017). Associations between media use and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on vaccinations in South Korea. BMC Public Health, 17(1)700.
Liu, M. , Yang, Y. , & SunY. (2019). Exploring Health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A Social Support Perspective. Health Communication34(14)1824-1832.
Mayer, J. D. , SchintlerL. A. , & BledsoeS. (2020). CultureFreedomand the Spread of Covid-19: Do Some Societ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Have National Anti-Bodies? World Medical & Health Policy, 12(4)498-511.
MurphyR. T. (2020). East and west: Geocultures and the Coronavirus. New Left Review, 122(Mar-Apr)58-64.
Parsons, 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Illinois: The Free Press.
RoskerJ. S. (2020).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 relational ethic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sian Philosophy, 31(1)64-77.
ShaferA. , Kaufhold, K. , & LuoY. (2018). Applying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and an integrated behavioral model to promote breast tissue donation among Asian Americans. Health communication33(7)833-841.
SingelisT. M. , Triandis, H. C. , Bhawuk, D. P. , & GelfandM. J. (1995).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 theoretical and measurement refinement. Cross-cultural research, 29(3)240-275.
TriandisH. C.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TriandisH. C. , & GelfandM. J. (1998). Converging Measurement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1)118-12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Age Standardization of Rates: a new WHO standard. Retrived from http://www. who. int/healthinfo/paper31. pdf.
XuX. , Chew, K. A. , Xu, X. , Wu, Z. , Xiao, X. , & Yang, Q. (2021). Demographic and social correlates and indicators for behavioural compliance with personal protection among Chinese community-dwellers during COVID-19: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J Open, 11:e041453. doi:10. 1136/bmjopen-2020-041453.
YuN. , & Shen, F. Y. (2013). Benefits for Me or Risks for Others: A Cross-Culture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Message Frames and Cultural Appeals. Health Communication28(2):133-145.
杨莉明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智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860042)、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2020WCXTD01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0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20XXW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