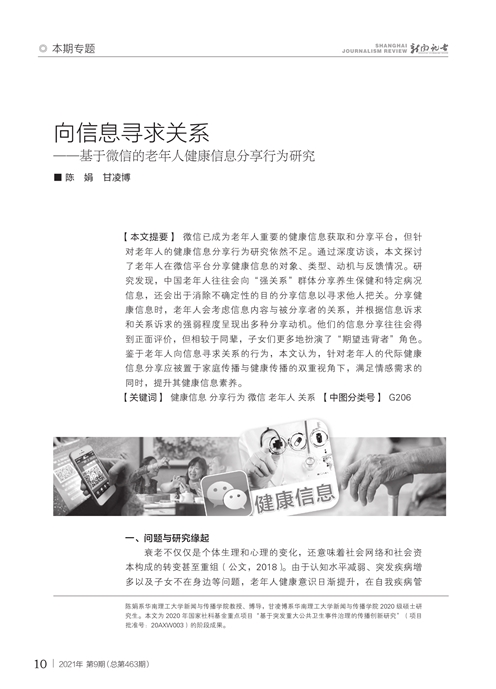向信息寻求关系
——基于微信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陈娟 甘凌博
【本文提要】微信已成为老年人重要的健康信息获取和分享平台,但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依然不足。通过深度访谈,本文探讨了老年人在微信平台分享健康信息的对象、类型、动机与反馈情况。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往往会向“强关系”群体分享养生保健和特定病况信息,还会出于消除不确定性的目的分享信息以寻求他人把关。分享健康信息时,老年人会考虑信息内容与被分享者的关系,并根据信息诉求和关系诉求的强弱程度呈现出多种分享动机。他们的信息分享往往会得到正面评价,但相较于同辈,子女们更多地扮演了“期望违背者”角色。鉴于老年人向信息寻求关系的行为,本文认为,针对老年人的代际健康信息分享应被置于家庭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双重视角下,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提升其健康信息素养。
【关键词】健康信息 分享行为 微信 老年人 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与研究缘起
衰老不仅仅是个体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还意味着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构成的转变甚至重组(公文,2018)。由于认知水平减弱、突发疾病增多以及子女不在身边等问题,老年人健康意识日渐提升,在自我疾病管理、医疗保健、心理健康等方面有较强的健康需求(高冰洁,张宁,2020)。2017年《社交网络赋能报告》的数据表明,微信是老年人使用最频繁的社交软件,老年人利用微信在虚拟社会网络之中重建包容性的“共同存在”(周裕琼,2018),并可以寻求和分享他们感兴趣的健康信息,也可以就收到的健康信息进行回应。在社交媒体上,社交互动促进了健康信息的分享,为健康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Wang et al., 2020)。
《第47次互联网使用报告》显示,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提升至26.3%(CNNIC, 2021),加之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龄化传播研究出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迹象(周裕琼,谢奋,2021)。在这些研究中,针对健康信息寻求行为(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的研究层出不穷(吴丹,2015;朱姝蓓,2015;赵栋祥,马费成,张奇萍,2019),但对健康信息分享行为(health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处于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老年群体。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具有什么特点?他们为什么通过微信分享健康信息?其信息分享行为有没有达到目的?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跨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对中国老年人基于微信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展开研究,并就其背后的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与代际沟通优化路径进行探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社交媒体与信息分享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可以被视为人际网络的在线强化版(何塞·范·迪克,2013/2021),它是基于网络的服务,允许个人、社区和组织通过创建、共同创建、修改、分享和参与用户生成的易于访问的内容(McCay-Peet & Quan-Haase, 2017)。Talja(2002)把信息分享定义为一个总体概念,涵盖了从共享偶然遇到的信息到协作查询和检索等广泛的协作行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分享已成为用户获取和使用信息的主要途径(汪奋奋,邓胜利,2016)。有些学者认为,信息分享过程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即向他人提供信息和接受信息提供者提供的信息(Savolainen, 2017; Sonnenwald, 2006),也就是将信息分享作为一个包含信息提供和接受方面的通用概念。还有学者对“信息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和“知识分享”(knowledge sharing)进行概念分析,认为二者作为交流活动时的相似度高于内在的差异度(Savolainen, 2017)。以上这些概念都对信息分享进行了定义,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共享”是一个清晰指向。
Pilerot(2014)的实证研究揭示,设计人员通过分享行业的专业信息来遵守感知到的社会规范、达成某种共同理解以及与他人建立专业关系。由于传播是一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传递与知识共享行为(刘海龙,2014),信息也就沿着社会关系网在人们当中流传(汤姆·斯丹迪奇,2013/2019:7),因此,对于个体来说,在利用即时通信进行个体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己的人脉资源的积累与扩张(彭兰,2019)。
在健康传播领域,社交媒体则不仅仅是健康信息共享的渠道,信息流和关系互动也在社交媒体上相互促进(Wang et al., 2020;Tayebi et al., 2019)。
(二)老年人与在线健康信息分享
当前,社交媒体正逐渐渗透到老年人群体中,网络以及相关的新媒体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健康信息来源(公文,2018)。Wang等人(20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健康信息分享已经成为老年人在微信上日常交流的重要活动,这些健康信息分享活动主要表现为转发、咨询、回复、发布四种具体方式。Liu等人(2019)认为,健康信息分享是一种有目的的向他人传递健康信息的行为,属于支持性交流,旨在使他人受益,并建立或巩固理想的社会关系,中国老年人感知到的家庭社会支持和社会嵌入度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正相关。王一迪(2020)通过深度访谈探究老年人伪健康信息转发行为,发现老年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健康信息的行为有助于开启群体聊天的话题,引发讨论并达成一致,形成群体内部的认同。除此之外,针对不同类型的健康信息,老年人很可能采取不同的信息分享行为,这些分享行为或许具有不同于健康信息需求行为的特殊性。
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背后的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令人担忧,包括认知层面的健康素养与信息分享层面的健康信息素养(health knowledge literacy)。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5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明显低于年轻群体,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国家卫计委,2021)。健康信息素养可以理解为能够识别健康信息需求、信息来源并通过信源检索相关信息、评估信息质量及适用性,以及分析、理解和使用信息来做出良好的健康决策的一组能力(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21)。数据显示,触发微信的谣言防护机制的用户中,50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四成,远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腾讯科技,2018),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层面,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都值得我们关注。
然而,当前针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老年人所分享的健康信息类型及其社群互动关系(Wang et al., 2020; Liu et al., 2018)。有学者提出,社群互动关系应该作为社会资本研究的第三种维度,对应Nahapiet和Ghoshal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结构、关系和认知三维度中的结构维度,侧重于研究行动者的联系对象以及如何联系(贺建平,黄肖肖,2020)。因此,准确描绘老年人在什么情境下,给什么人,分享什么样的健康信息,便成了正确理解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基础,也是研究者走进老年人数字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本研究拟提出研究问题一:
基于微信,老年人会向谁分享健康信息?以及分享什么样的健康信息?
(三)老年人虚拟信息分享动机
在虚拟社区中,信息分享动机是指个体共享信息的内在驱动力(Boudreau et al., 2003)。有学者总结个体行为分享动机可以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包括:自我提高、娱乐、帮助他人、社交、工具性需求;外部动机包括:外在奖励、社会认同、形象等(姜雪,2014)。郭琨等人(2014)认为分享行为也与自我效能有关,认为更大的自我效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在线健康信息共享。
基于社会支持视角,许多学者对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进行了研究。Ware等人(2017)发现,在线分享健康信息为老年人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和情感支持,减少了老年人使用过程的脆弱感。王一迪(2020)发现中国老年人在分享健康信息时,既存在向他人提供信息支持的动机,也存在向他人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的动机。Pan(2018)发现在线健康交流社区能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感以及改善健康状况。一些患病老年人会通过在线交流健康信息来获得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高冰洁,张宁,2020)。
除了社会支持,维持或促进与他人的关系也是中国老年人分享健康信息的重要动机(Wang et al., 2020)。“关系”被看作是一种人际之间的连接(Liu et al., 2008),在中国语境下有特定的文化意义。Luk等人(1999)提出关系是一种强有力的给予他人恩惠的社会义务,体现在帮助他人、回馈他人祝福、避免尴尬和信任他人。将此关系运用于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上,他们存在哪些分享动机?如果他们对关系有所诉求,那么他们又希望获得什么样的关系?由此,本研究提出问题二:
基于微信,老年人对健康信息分享动机有哪些?不同的分享动机又分别呈现了什么样的诉求?
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用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来概括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而Savolainen(2017)曾针对日常环境中的信息分享行为进行研究,认为相较于“传递观”的单向性,从“仪式观”来探讨信息分享更强调参与和互动的意义,更强调双向交流的重要性。作为一种社会交流形式,信息分享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参与者既是信息的提供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Savolainen, 2017),因此,信息分享不是一种单独的行动,而是一种集体和协作的努力(Bao & Bouthillier, 2007)。当老年人出于不同动机将健康信息分享给他人后,一场围绕信息而展开的集体协作和对话才刚刚拉开序幕,被分享者往往会对来自老年人的信息分享做出回应和反馈,而这种反应也是信息分享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为何有些老年人在完成信息分享后便不再继续分享,有些却会持续分享并乐在其中?来自被分享者的反馈在这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已有研究观察到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会直接影响用户是否愿意持续分享信息(姜雪,2014),因此,在考察老年人的分享行为时,有必要将被分享者的反馈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考虑进来,把信息分享行为看作是一种动态往复的信息流动和人际互动过程。
有研究表明,来自被分享者的积极反馈会对老年人起到激励作用,提高他们对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自我效能感(Wang et al., 2020)。为他人提供信息支持的老年人亦可以获取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成为社交群组内健康方面的“意见领袖”,这给老年人带来更多的激励与满足,使得他们更愿意继续分享信息(王一迪,2020)。
不过,老年人的分享动机并不总是如其所愿得到满足,有研究发现,违背期望的反馈会使老年人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不仅会抑制后续的信息分享行为,还会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当出于情感支持动机分享的信息遇到了辟谣和反驳时,老年人分享的动机不仅没有得到满足,还会使老年人从情感层面断定对方不是能产生共鸣的人,从而拒绝后续的人际来往(王一迪,2020)。老年人围绕健康信息与子女交流时,有时会将不符合自身期望的子女反应视作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双方持有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引发一场又一场的“代际之役”(唐乐水,2020)。
由此,我们关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时,除了信息分享动机,还需要考虑其分享动机是否得到了满足,以及动机满足与否会对老年人的认知态度和后续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问题三:
分享行为实施后,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动机是否得到满足?对老年人的认知态度和后续行为而言,动机的满足与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三、研究方法
由于质化访谈方法更善于描述和解释,并且更加关注情景和研究对象,适合于理解过程性的问题(董晨宇,段采薏,2020),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法。由于生理原因(如花眼等视力问题)以及认知原因(如阅读速度慢、难以理解问卷内容等),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事先确定好问题与答案选项的问卷调查等量化方法常常无法完成,或者拒绝合作(孟伦,2013:19,转引自公文,2018),本研究所选择的半结构化访谈可以让研究者在较为自然的对话语境中,获得老年人对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看法,并就一些需要追问的话题及时询问老年人群体,获得较为丰富的资料以供后续分析。
本研究的访谈问题主要包含以下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具体问题包括年龄、职业、学历、是否为本地居民,身体基本情况等;其次,询问了老年人对微信的使用情况,具体包括使用时间、使用功能、微信联系对象和联系频率、微信联系他人的方式、交流内容等;第三,询问了老年人对微信的健康信息接触情况,具体问题包括消息源、是否存在消息把关人、对信息质量是否进行判断及判断因素等;第四,询问了老年人对微信的健康信息分享情况,具体询问了老年人分享信息的方式、频率、分享动机、分享后反馈情况以及反馈对后续分享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滚雪球抽样和目标式抽样获得样本。首先对研究者所熟识的老年人进行访谈研究,随后通过参与访谈的老年人介绍其同龄人参与访谈的方式增加样本数量,结合目标式抽样所遵循的原则选取有效样本。为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特意选择居住在中国大陆不同规模的城市中的老年人进行访谈。在上述抽样原则的指导下,研究者在2020年3月19日—2020年4月3日期间对26位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见表1),访谈对象均拥有至少半年以上的微信使用经历。访谈对象年龄在56—82岁之间,平均年龄68岁。
本研究严格遵守学术研究伦理,在访谈前会告知访谈对象本研究的访谈内容及目的,以及访谈过程中的录音行为,告知访谈对象拥有自愿参与、匿名原则、随时退出等权利,询问访谈对象是否愿意参与本研究。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本研究会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并对访谈过程录音,后期整理成文字材料。每次访谈时间在30—50分钟左右,平均不少于40分钟。为使访谈对象在访谈过程中保持放松,访谈主要在访谈对象家中进行,对于部分不便接受线下采访的访谈对象,选择线上视频或语音通话的方式进行访谈。
四、研究发现
(一)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类型
社会情感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认为,老年个体的需要更多地指向亲密关系(Charles & Carstensen, 2007,转引自闫志民等,2014)。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微信社交网络主要基于现实社会中的“强关系”,这与此前的研究发现一致(周裕琼,2018;Wang et al., 2020)。他们对健康信息的分享行为也主要发生在与子女、配偶、亲友等强关系的社会交往中。老年人往往通过分享信息到群聊、分享信息给个人、回复信息、发布朋友圈等不同方式进行健康信息的分享。
具体来说,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分享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1.作为集体关切的养生、保健信息分享
年龄增长使老年人体会到了身体机能的退化,这使他们比年轻人更注重身体保养,微信上常见的养生和保健类信息便得到老年人的关注和青睐。例如S2在受访时提到对养生的重视:
健康信息也在交流。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都特别注重养生和健康了,所以说也都在交流。谁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帖子也会发到圈里,发到朋友圈也发到我们个人。现在健康第一位嘛。(S2)
老年群体对养生保健信息普适性偏好逐渐成为一种同辈人的集体关切,相比于向子女分享养生保健类信息,老年人更热衷在同辈聚集的微信群或朋友圈中分享有关养生保健的健康信息。一些老年人在分享养生保健信息时,已经会依据自身经验或信息特征对其进行事实核查。S1会将“是否推销商品”作为核查信息真实性的一种手段,如果信息涉及推销商品,那么他不会分享该信息:
那个节目都是老中医讲的一些(知识),这我们觉得很认可。但他一看这广告才知道他是在卖药,而不是单纯(地)传播。(S1)
2.针对特定对象、特定病况的信息分享
与养生保健类信息的普适属性不同,某些健康信息涉及老年人自己或其亲友所患疾病。此时,分享者往往采取私聊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分享健康信息。当分享者本人患有与被分享者同样的疾病时,分享者会将自身感受作为信息核查标准,如果健康信息对自己有效,那么他们会认为这则信息是“可信的”,然后将信息分享出去。S2患有高血压,她同患高血压的同事会把自己的吃药情况分享给S2:
比如说他觉得我血压高,但是他(指同事)最近吃这个药比较好使,这个药方比较好,他会发给我们。我呢,要是看到了,比如说我觉得我同事有的是糖尿病了,我看好我也会发给他。(S2)
而当分享者并不患有特定疾病时,信息核查往往依照分享者自身对信息内容的主观感受。与S2不同,S3本身身体健康,但其姐姐心脏不太好,S3在分享心脏有关的健康信息时,只是依照自己对信息的观感,当认为该信息有可信度时,就会分享给她的姐姐。
有访谈者被亲友告知自身经验存在局限性,他们会使用百度来确认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而有些老年人会通过降低特定疾病健康信息分享频率来规避误导他人的风险:
像我们分享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与锻炼有关的东西。现在并不是说某一种药作用如何,这些东西我不太去转发。(S7)
3.出于消除不确定性的健康信息分享
有时,老年人也会分享一些自身不确定的健康信息。公文(2018)发现,如果对健康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较低或者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无法判断健康信息内容的真伪,老年人可能会选择回避这些健康信息。但在本研究的访谈中,一些老年人提出,他们会将自身不确定的健康信息分享给他们认可的微信好友,往往是其亲友或有医疗背景的人,让他们代替自己核查信息真实性:
你也知道网络现在内容也比较多,广告比较多。一般孩子也告诉我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有些判断不是那么准确。我们看到其他信息会往家族群里面先转一下,然后我们让这些亲人子女来判断一下,我们再去转发。(S1)
在这个过程中,被分享者充当了健康信息和老年人之间的把关中介,他们负责对健康信息的质量进行把关,进而影响到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后续分享行为。
(二)老年人信息分享动机类型
研究发现,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分享既存在信息诉求,又存在关系诉求,二者共同影响了老年人的分享动机。信息诉求意味着对健康信息质量的追求,信息诉求高的老年人往往会在进行信息分享前对信息进行核查,虽然有些核查方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经验性。关系诉求意味着对人际关系的追求,关系诉求高的老年人会有意识地通过信息分享拉近与被分享者之间的关系。在健康信息分享的语境中,这种推动关系的努力有时会表现为向他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有时会通过信息分享这种行为本身得以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诉求和关系诉求往往共存于老年人的分享动机中,二者并非相互对立排斥的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动机中,两种诉求的显著性会有所不同。根据两类诉求在动机中的不同呈现,本研究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动机分为以下五类:
1.基于关系的信息利他
当信息分享者了解到其贡献的信息对他人有用时,就会增加其分享信息的信心和频率(李枫林,周莎莎,2011)。持有信息利他主义观点的分享者希望其分享的信息能够对被分享者起到积极的信息支持作用。此时,分享者往往会重视信息的真实性,在分享前对信息的质量进行核查,只是这种核查有时因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而存在漏洞。S7在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健康信息时,会将信息分享到群里,希望向群里朋友提供健康建议:
用微信分享的话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发到微信群里嘛,大家都可以看到。就那么10个人,而且都是平时应该是觉得玩得来的、在一起的那几个人,无话不谈的人。尤其是开心的事儿,分享一下子。有些是健康的东西,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好,你们也试一下。(S7)
老年人出于对信息的信任而进行转发,意图分享给更多人知晓,这是“利他”思维下的行为特征(王一迪,2020)。但若仅从信息利他主义来解释中国老年人的分享动机,未免太过单薄。访谈发现,中国老年人确实存在通过信息支持他人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始终基于传受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关系的信息利他”,分享行为始终深嵌在双方的关系网络中。这种动机既存在较强的信息诉求,又存在较强的关系诉求,老年人希望这些经由他们分享的,在他们看来有价值的信息,为那些他们重视的人提供参考和支持。
费孝通(2013:25)提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呈现“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血缘或地缘划分关系远近。在个体的认知图式中,中国人对自我、亲人持有积极的情感,而对陌生人持有消极的情感(袁晓劲,郭斯萍,2017)。本土的实证研究也部分验证了人际关系存在“差序格局”,暗示亲缘关系在中国社会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陈经超,黄晨阳,2020)。除了亲缘关系之外,同质化特征也会拉近老年群体心理情感上的距离。由于心理上的接近性,朋辈支持对增强老年人的积极心理发挥着更大作用(刘入豪,邱乾,2020)。S1随子女来到北京,平时负责在家里照顾孙辈,在他看来,有助于家人和朋友的健康信息肯定要做分享,但一般朋友就无所谓了:
交给他还是要看一下的,叫他来判断,(我)只是提个建议。就是说对家人、朋友有关的,一般朋友无所谓……就很好的朋友、家人那些在医疗保健这方面觉得很可行的东西肯定就要做(分享)。(S1)
对关系的重视不仅会导致老年人对分享对象的选择,还会对信息的真实性判断产生一定影响。一些老年人会根据分享者与自己的亲密程度判断信息的真实性,以人际关系来衡量信息的重要性。但也有受访者提出,人际关系不能用来判断健康信息的真实性,他们会依据信息内容质量和行为难易程度来对信息进行判断:
我不会因为信息是姐姐发的,就比别人发的更信任,因为姐姐也和别人一样是转发的,她也没有亲身体验过。(S26)
“基于关系的信息利他”体现了中国语境下老年人提供信息支持的特殊性,即并非纯粹利他的信息分享,而是在差序格局中向他人提供信息支持。邱林川(2013:195)认为,老年人对信息的获取和分享是以家庭等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对他们来说,给予他人信息支持时必须考虑与被分享者的人际关系。
2.基于关系的情感支持
除了“基于关系的信息利他”,老年人对关系的重视还体现在通过健康信息的分享为他人提供情感支持,促进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分享动机下,大多数老年人对信息内容的准确性并无太高的要求,对信息内容的核查往往依照个人经验,更多地希望通过分享行为本身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关心和鼓励,这类动机具有较弱的信息诉求和较强的关系诉求特征。
情感支持在许多当代亲密关系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它解决的是我们存在的核心问题: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所向往的事物、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恐惧和我们最深切的感受(Burleson, 2003)。有研究表明,情感支持有助于减轻人们因疾病而产生的心理压力(Wright, 2002),接受情感支持的人可以更快地从各种疾病和伤害中恢复过来,甚至在与心脏病和乳腺癌等苦难作斗争时可以活得更长(Spiegel & Kimerling, 2001)。
人在老年阶段从同辈群体中获取情感上的支持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刘素素,庄明莲,2014)。在访谈中,许多老年人提及他们会通过彼此分享健康信息来表达对他人的关心和支持。S9表示,他会将自我感觉较好的信息分享给关系较好的朋友,表达一下关心,但对于朋友是否会采纳信息,他并不在意。
Wang等人(2020)发现,关系取向会显著影响老年人在微信上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中国老年人中存在“你发一条信息给我,我再转发一条给你”的“礼物式”健康信息分享现象,构成了一个有来有往的情感支持互惠机制。有趣的是,这种“互惠”机制往往存在于同辈群体之间,大多数的老年人会优先将健康信息分享给同辈的亲朋好友,其次才是子女。在对子女进行健康信息分享时,老年人会抱有一种纠结的心态。一方面,基于父母的身份和责任,他们希望通过分享健康信息表达对子女的关心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对自己的健康信息分享是否被年轻人采纳产生怀疑。因此,部分老年人会倾向于不对子女分享他们看到的健康信息,有些老人虽然还会分享,但并不对子女采纳抱有太多期待:
自己觉得有道理的就分享,但很少,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信息时代,我们看到的,挺多都是假的,或者真假难辨,老年人容易被忽悠。为了家人的健康,还是愿意(分享)的,他们看不看是他们的事,我们当父母的尽到责任就行了。(S20)
普特南(Putnam, R. D)认为,移动性会破坏社会关系的根系,造成社会资本的流失(Putnam, 1995),而微信则为随迁老年人群体提供了维护固有社会关系的新路径,健康信息的分享增加了彼此的共同话题空间,维系了老年人固有的社会关系:
几乎每天我们群聊。有山东的同学,有天津的,我们就群聊,大概在(下午)3:00—5:00,我们约定的时间,反正就是说说话、开心聊聊天,反正我岁数大了,这样有什么心里话都说说,都蛮开心的。……我们一些好朋友,小学的一些同学,因为我们天南海北的都有,也不会经常见面。(S3)
3.基于社会规范的自我心理调适
行为预测整合模型(The Integrative Model of Behavioral Prediction, IMBP)显示,感知到的社会规范,即个体认为周围人对特定行为的看法以及是否愿意在这一行为上与周围人保持一致,会影响到人们实施某项健康行为的行为意向(芮牮,刘颖,2020)。周裕琼(2018)发现在微信采纳和使用方面,主观因素(对微信特征和风行程度的感知)影响都大于客观因素(人口变量和健康水平)。当老年人通过自身的实践和观察,认为分享健康信息已成为一种主流风尚时,出于对“落伍”的恐惧,他们会倾向于向亲友等微信联系人分享健康信息,努力与其所感知到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以缓解年龄增长和技术习得性无助而产生的心理落差。这种符合社会规范的分享尝试更像是老年人的自我心理调适,即通过分享健康信息来增强自我认同和自我效能。在访谈中,持有这种动机的老年人并不十分看重所分享信息的质量,他们对信息话题的重视远超过信息质量。在关系诉求方面,他们也并不打算通过分享信息为他人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也没有太多与他人拉近关系的意图,而是试图通过分享信息,保持自身与周围的一致。这种分享动机呈现出主我与客我的精神互动,而没有凸显“关系诉求”的人际属性和互动属性。因此,本研究认为,这种“基于社会规范的自我心理调适”具有较低的信息诉求和较低的关系诉求。
S23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在日常的健康信息接触中会关注保健知识,有时会将看到的信息分享给家人:
关注点在话题。比如吃什么对哪里有好处、什么时候睡觉比较合适、一个晚上睡多久,这些话题我比较信任……分享健康信息,会有与社会接轨不落伍的感觉,我就是个不甘心落伍的老年人吧。(S23)
4.基于关系的分享“仪式”
出于对关系的维持动机,老年人往往将健康信息作为一种社交货币,通过信息的分享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维持意不在提供情感支持,也不在于拉近分享双方的关系,而仅仅是作为社交场合中的寒暄和谈资,避免在对话中出现尴尬沉默。此时,健康信息作为一种谈资,成为话题的开场白或者是某种由头。有学者曾研究推特上的转推功能发现,信息的转发和分享更像是一种参与传播对话的手段,转发分享不仅是为了将消息发布给观众,还在于验证和与他人互动(Boyd et al., 2010)。这种分享行为更多地成为一种“仪式”,其信息诉求和关系诉求都比较低。S16提到,并不会特意就某一健康信息发起谈话,而是在偶尔的聊天过程中,与朋友分享相关的健康信息:
这个是比较少,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会提出来探讨。但是要专门地把某一个事情拿出去跟人家探讨,纯主动是没有的。只是偶尔在聊天的时候,会谈到某一个近况方面的信息,这个时候来探讨。(S16)
5.基于信息的事实核查
许多老年人艰难地迈过了数字鸿沟的两大层面——接入沟和使用沟,却在使用素养沟处遇到更大的挫折,如何评估健康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一直是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在线内容消费者面临的挑战。有时,一些老年人意识到自己无法独立判断信息真伪,便会借助他人力量,分享有关的健康信息,请求他人一起讨论和核查信息真实性。这种动机具有很高的信息诉求和较低的关系诉求。除了前文提及的S1外,S5也会通过分享健康信息和他人讨论信息的真实性:
咱们一看这条消息觉得挺适合自己就挺好的,养老的健身的这些东西,完了互相给发一下。有时候互相探讨,有时候和老头子说一说,这事是真的假的。互相就会聊一聊。咱们就还是按照咱们自己的想法生活吧。(S5)
总结发现,在分享健康信息时,中国老年人群体往往基于信息诉求和关系诉求表现出不同的信息分享动机。这些动机与分享内容和分享对象密切相关,也与老年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展现出的复杂心态有关。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制作了老年人群体的信息分享动机框架(见表2)。
(三)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动机反馈
研究发现,被分享者对信息的反馈往往会对分享者的分享动机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后续分享行为产生影响(Liu et al., 2008;王一迪,2020)。基于此,来自被分享者的反馈情况以及老年人对反馈的感受可以作为检验标准,以衡量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动机是否得到满足以及老年人心态和行为的变化。
总体而言,老年人基于不同动机分享的健康信息往往会得到被分享者的正面评价,这些正面评价会给老年人带来精神激励和满足感,使他们愿意继续分享健康信息。当健康信息出于“利他”动机被分享给其他人,被分享者往往会表达对老年人的感谢和肯定。例如S5在分享健康信息后,她的同辈群体会给她点赞,有的还会评论“这个写得挺好的”,双方还有可能针对健康信息以及其他的健康相关信息进行探讨和交流。但由于对信息效果的检验往往需要时间,而信息的反馈又需要一定的及时性,所以,即使分享者分享时的信息诉求比较高,被分享者的反馈往往还是以情感评价为主。当信息出于消除不确定性的目的被分享时,被分享者往往会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评价。这种把关与筛选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补偿了由信息焦虑以及信任危机而导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公文,2018),老年人也会根据把关人的意见选择继续分享健康信息还是放弃分享。当信息作为寒暄谈资出现时,对话的持续往往就意味着信息满足了其分享的动机,双方会就与健康有关的话题展开或长或短的交流,从而发起并维持当前对话,延续彼此的社交关系。
当然,并非所有的分享动机都会得到满足。有时,老年人分享的信息并没有得到被分享者的反馈,或者反馈数量寥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老年人会反思是否自己分享的信息存在问题,并有意识地减少类似信息的后续分享。S2在访谈中表示,如果分享的信息反馈不好的话,她会将其视为对他人没好处,并会有意识地减少后续的分享:
绝对不分享对人没好处的,就是反馈不好的就不分享。如果要是发现是造谣或者是什么的,我的数据就删除了,就不再关注。(S2)
有时,老年人分享的信息还会得到“辟谣”,比如S1曾经觉得某则健康信息不错,“觉得有意义”,分享到群里之后,他的子女反映说信息是假的:
他们都一般(是)西医,他们告诉我们说不要相信我们发的一些推送。……有时候我们发到群里,他们马上给我发过来:这是骗人的,不要相信不要去做。(S1)
这就意味着,在对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的反馈中,子女比老年人同辈群体更多地扮演了“期望违背者”的角色。首先,相较于同辈人群,子女往往在与父辈的交流中,充当“信息反哺者”的角色,他们会向老年人分享他们所认可的健康信息,但却更少地对来自于老年人的信息分享作出反馈,即使有反馈,其中的情感支持表达也相对较少,更多的回复旨在传递“信息已收到”:
他们只发个收到了,或者一个表情,如果是面对面的会讨论,远程就没了。我觉得他们忙的时候根本就没认真看,有时候可能也会觉得烦。(S20)
其次,子女会比同辈更频繁地向老年人指出信息中的问题所在,还有的时候,当老年人向子女分享一则“很有价值的”健康信息后却得知子女们早已浏览过相关信息。当老年个体的高期望遭遇子女的“冷”态度时,期望的落空很可能使老年个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孤独感(闫志民等,2014),这些反馈常常使老年人减少后续的分享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同辈群体更少拥有信息纠错的能力,而更多是碍于情面和关系,倾向于避免因信息质量而与分享者产生纠纷,维护分享者的面子而在信息质量上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社会情感选择理论认为,年龄的增长与从生活中获得情感意义的动机增加有关,还与扩大视野的动机减少有关。当老年人意识到时间的有限性时,他们更倾向于消解生活中的负面情绪,而更注重积极的信息认知(Carstensen et al., 2003)。这种态度会使得一些健康谣言犹如“皇帝的新衣”,在老年人的“同温层”中畅通无阻。
五、结论与讨论
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随后,人口老龄化(aging population)趋势不断加快。“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预计突破3亿人,人口结构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可以说,“老之将至”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和社会必须直面的挑战,对此,周裕琼(2021)提出,应将研究的重心从“老年传播”转向“老龄化传播”,把“老龄化”视作宏观的基础结构和持续的动态过程。
然而,虽然“老龄化”在人口结构特征中越来越突出,老年人在现代社会发展和公共参与方面却越来越边缘化。根据联合国新编写的年龄歧视问题报告,针对老年人群体的年龄歧视已成为一项全球性挑战,世界上二分之一的人持有年龄歧视态度,这会导致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社会每年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世界卫生组织,2021)。当新媒介技术赋权年轻人,其社会资本得到不断扩充的时候,老年人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收窄,对老年人的“数字排斥”也会随之加剧,疫情期间,健康码的推广与使用便是老年人应对“数字鸿沟”问题的集中爆发。今天人们的健康与自由,不仅体现为现实空间里的状态,也体现为数字空间里的状态,而能在数字空间里“健康生存”、自由通行的老年人少之又少(彭兰,2020)。
作为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回应,国务院办公厅(2020)于2020年11月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规划出台了对老年人更为友好的数字包容性社会建设方案,旨在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方面推动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改善老年群体的数字生存境况。
如果说《实施方案》旨在改善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老年人的智能技术使用门槛,帮助老年人更方便地迈过数字鸿沟的“接入沟”和“使用沟”的话,本研究则意在探讨跨过“接入沟”和“使用沟”后,老年人在“使用效果沟”尤其是“素养沟”层面的表现以及遇到的新问题。消除“接入”和“使用”鸿沟仅仅是一个起点,提升老年人的使用素养和水平才是问题关键。
本研究以已学会使用微信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研究这一群体基于微信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发现,在学会使用微信的社交功能和分享功能后,中国老年人往往会在线上重构他们的“强关系”社交网络,并向同辈群体和亲友分享养生保健和特定病况信息,还会出于消除不确定性的目的分享信息以寻求他人把关。在分享健康信息时,老年人会基于信息内容及被分享者的关系,根据信息诉求和关系诉求的强弱程度呈现出多种分享动机。消息分享后,反馈会成为判断老年人分享动机是否被满足的标准,并影响到老年人的心情及后续分享行为。也就是说,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分享并非一种盲目无序的行为表达,而是一种面对复杂信息环境的理性行为选择。而作为健康信息素养的一部分,信息核查意向不仅受到学历水平的影响(国家卫计委,2021),还会受到老年人在分享信息时所持有动机的影响。其中,当老年人希望所分享信息能够帮助其重视的人,或出于不确定性而分享信息进行信息核查时,老年人群体往往会较为认真地进行信息的事实核查,体现出一定的健康信息素养。而当他们出于情感支持、自我心理调适以及将健康信息作为“社交货币”进行分享时,他们可能会忽略信息的真实性。
然而,未经事实核查的健康信息一旦分享出去,很可能使他人轻信并二次传播。在访谈中有老人表示,只要是其亲属发来的健康信息,他都不怀疑信息的真实性。还有的老人表示,即使感觉朋辈分享的信息真实性存疑,也会出于面子而放弃纠正,反而是诉诸积极的情感反馈或冷处理。换言之,作为“社交货币”的健康信息可能会在亲密关系的加持下,缺乏行之有效的纠错机制。如要打破这种已形成闭环的传播定势,我们需要借助一定的外来力量,如社区和老年组织可以定期举办健康信息的科普活动,在提高老年人对虚假信息敏感度的基础上,提升其核查健康信息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子女在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过程中扮演了更多的“期望违背者”角色,他们更少向老年人反馈自己对所分享信息的感受,并更频繁地指出老年人所分享信息中的错误。作为“差序格局”中最为紧密的亲缘关系,当代子女与其亲辈在围绕健康信息沟通时的表现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尊老敬老”传统,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礼仪人伦”社会规范,这也使得老年人在向子女分享健康信息时,并不像朋辈之间那么积极。传统和社会规范在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被消解,原因何在?当老年人借微信的信息分享寻求关系的重建时,代际沟通所在的家庭场域又能否被寄予希望,作为推动老年人健康信息素养提升的新阵地?
黄佳鹏(2020)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呈现出“联合式”特征,青年群体逐渐取代传统老年群体成为家庭权力和话语的主导者。传统家庭既有的伦理关系和家庭结构,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濒临破产,甚至有可能倒置(周裕琼,2018)。一些年轻人希望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在线上关系中扮演“科学权威”角色以扶持亲代现代化进程(安利利,王兆鑫,2020)。而作为对数字反哺的回应,一些老年人会在智能手机的购买和使用问题上听取子女的意见(洪杰文,李欣,2019),但却不愿意完全遵从子女的意见,尤其是在健康领域。有时,他们会将年轻人的不同意见视为“挑战权威”,并通过否定子女消息来源(如新媒体)的权威性来否定年轻人的文化反哺(唐乐水,2020)。相较于在数字接入沟和使用沟层面的巨大差距,健康话题往往受到传统和现代、民俗与科学等多方力量的缠绕影响,老年人群体似乎还可以凭借自身过往的生活经验与作为长辈的权威身份,借微信的信息分享寻求双方关系的重建。
然而,子女和亲辈之间对家庭话语权的角力并不能否认老年人的健康认知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比例高达66.47%,由祖辈参与照料0—3岁儿童的比例占总数的60%—70%(广州日报,2014)。在祖父母辈普遍养育/参与养育孙辈的社会现状下,老年人的健康认知及行为并不会因其健康信息的分享行为在子女那里受挫而得到改变。事实上,老年人向信息寻求关系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可能是提升老年人健康信息素养的绝佳切入口。在缩小数字鸿沟的路径中,代际反哺被视作中国语境下较为可行的路径(周裕琼,2018;朱秀凌,2015;公文,2018)。相对于同辈群体,子女与其老年亲辈同属于一个家庭结构,关系更为紧密,因担心面子问题而忽略错误信息的心理负担相对也较小。无论是出于健康目的还是情感考量,代际沟通都更有可能有针对性地向老年亲辈进行健康信息分享,从根源上截断健康谣言的传播链条。
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居家养老依然是我国老年群体主要养老形式,我国90%左右的老人居家养老(央视新闻,2021)。维护家庭场域的信息正常流通,促进家庭成员的互相理解,对于我国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此,针对老年人的代际健康信息分享应被置于家庭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双重视角下,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达到提升其健康信息素养的目的。
首先,在围绕健康信息进行代际沟通时,作为信息优势方的子女有必要承担起“信息反哺者”的角色,针对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关切和实际需求,分享对其有价值的健康信息。其次,子女也应意识到老年亲辈在分享信息时的多种诉求,尤其是在信息诉求外对分享双方关系的诉求,承担起“情感支持者”的角色。有学者提出,“贵和”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精神,特别重视“情”,而“诉诸于理”的传播方式是不合适的(朱秀凌,2018)。然而,针对健康的“信息反哺”势必涉及“理”的传递与共享,这就要求子女在“情”与“理”之中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注重情感和信息的双重反哺。既要积极地参与到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行动中,又要有意识地回应老年人分享行为中的情感需求,在反哺过程中注重方式和姿态,让中国当代的家庭传播成为推动老年人健康信息素养提升的优势路径,促进代际间的彼此理解和价值共适。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本文采取了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方法,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后续研究予以验证。其次,受被访者数量及被访者主观性影响,本文虽已提出五种健康信息分享动机,并按照关系诉求和信息诉求强度予以分类,但并不能保证已涵盖所有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动机,现实实践中是否还存在本文没有提到的分享动机,这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考察。■
参考文献:
安利利,王兆鑫(2020)。孝道与平权:数字鸿沟中的文化反哺与再哺育——大学生与父母在微信平台上的亲子关系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4),111-117。
陈经超,黄晨阳(2020)。“自我取向”还是“家人取向”?基于中国情境的大学生流感疫苗接种健康传播策略效果研究。《国际新闻界》,42(6),98-113。
董晨宇,段采薏(2020)。反向自我呈现: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研究。《新闻记者》,(5),14-24。
费孝通(2013)。《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高冰洁,张宁(2020)。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现状与前沿展望。《图书馆学研究》,(6),9-16+77。
公文(2018)。触发与补偿: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国际新闻界》,(9),47-63。
广州日报(2014)。带孙子的老年人比例达66.47%隔代抚养引深思。检索于http://edu.cnr.cn/pdtj/yw/201408/t20140828_516313211.shtml。
郭琨,周静,王一棉,袁瑛,刘丽琼(2014)。个人特征、社交网络信息分享态度和分享行为—一项基于人人网的研究。《现代情报》,(1),159-166。
国家卫计委(2021)。202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升至23.15%。检索于http://www.nhc.gov.cn/xcs/s7847/202104/6cede3c9306a41eeb522f076c82b2d94.shtml。
国务院办公厅(2020)。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检索于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24/content_5563804.htm。
何塞·范·迪克(2013/2021)。《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贺建平,黄肖肖(2020)。城市老年人的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以社会资本为中介。《新闻界》,(8),57-66。
洪杰文,李欣(2019)。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国际新闻界》,(10),50-74。
黄佳鹏(2020)。联合式家庭:新冠肺炎“家庭聚集型”传播及其防控的经验启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3-51。
姜雪(2014)。虚拟社区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图书馆学研究》,10,18-24。
李枫林,周莎莎(2011)。虚拟社区信息分享行为研究。《图书情报工作》,55(20),48-51。
刘海龙(2014)。中国语境下“传播”概念的演变及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8,113-119。
刘入豪,邱乾(2020)。老年人数字鸿沟中被忽视的朋辈影响。《青年记者》,(36),31-32。
刘素素,庄明莲(2014)。城市老年人退休后的角色适应与老有所为:香港社区老年人的定性研究。《社会工作》,4。
孟伦(2013)。《互联网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北京。
彭兰(2019)。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国际新闻界》,41(2),20-37。
彭兰(2020)。“健康码”与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现代视听》,(6),1。
邱林川(2013)。《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芮牮,刘颖(2020)。健康传播效果研究的缺失与路径重构。《新闻与写作》,(8),59-67。
世界卫生组织(2021)。联合国报告称年龄歧视是一项全球性挑战。检索于https://www.who.int/zh/news/item/18-03-2021-ageism-is-a-global-challenge-un。
汤姆·斯丹迪奇(2013/2019)。《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唐乐水(2020)。代际之役:新冠疫情家庭冲突场景的叙事分析。《当代青年研究》,(3),12-17。
腾讯科技(2018)。微信老年用户超6100万,老人也过智慧生活。检索于https://xw.qq.com/tech/20181016013129/TEC2018101601312900。
汪奋奋,邓胜利(2016)。信息技术对健康信息行为的影响——系统综述。《信息资源管理学报》,(3),15-24。
王一迪(2020年11月)。老年人缘何分享伪健康信息?—基于社会支持视角的研究。北京论坛·健康传播分论坛丨医疗、人文、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2020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
吴丹,李一喆(2015)。不同情境下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检索行为与认知研究。《图书馆论坛》,35(2),38-43。
闫志民,李丹,赵宇晗,余林,杨逊,朱水容,王平(2014)。日益孤独的中国老年人:一项横断历史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2(7),1084-1091。
央视新闻(2021)。九成老人居家养老“物业+养老”模式破局养老难题。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4887712528091109 & wfr=spider & for=pc。
袁晓劲,郭斯萍(2017)。中国人人际情感的差序格局关系:来自EAST的证据。《心理科学》,40(3),651-656。
赵栋祥,马费成,张奇萍(2019)。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现象学研究。《情报学报》,38(12),1320-132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1)。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周裕琼(2018)。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7),66-86+127-128。
周裕琼,谢奋(2021)。从老年传播到老龄化传播:一个边缘研究领域的主流化想象。《新闻与写作》,(3),30-37。
朱姝蓓,邓小昭(2015)。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查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图书情报工作》,59(5),60-67。
朱秀凌(2015)。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基于对福建省漳州市中学生家庭的实证分析。《新闻界》,(11),47-53。
朱秀凌(2018)。家庭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演进和发展路径。《国际新闻界》,(9),29-46。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Health and Medical Reference Guidelines[EB/OL]. http://www. ala. org/rusa/resources/guidelines/guidelinesmedical#_ftn32021-04-18.
Bao, X. , & BouthillierF. (2007). Information sharing: As a type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In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CAIS/Actes du congrès annuel de l’ACSI.
BoudreauJ. , Hopp, W. , McClainJ. O. , & Thomas, L. J. (2003).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oper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5(3)179-202.
BoydD. , Golder, S. , & LotanG. (2010January). Tweettweetretweet: Conversational aspects of retweeting on twitter. In2010 43r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pp. 1-10). IEEE.
BurlesonB. R. (2003). The experience and effects of emotional support: What the study of cultur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can tell us about close relationshipsemotion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10(1)1-23.
CarstensenL. L. , Fung, H. H. , & CharlesS. T. (2003).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and the regulation of emo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Motivation and emotion27(2)103-123.
Charles, S. T. , & Carstensen, L. L. (2007).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ging.
Liu, M. , Yang, Y. , & SunY. (2019). Exploring health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A social support perspective. Health communication34(14)1824-1832.
Liu, Y. , Bian, J. , & AgichteinE. (2008July). Predicting information seeker satisfaction in community question answering. InProceedings of the 31st annual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pp. 483-490).
Liu, Y. , Li, Y. , TaoL. , & Wang, Y. (2008). Relationship stabilitytrust and relational risk in marketing channels: Evidence from China.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37(4)432-446.
Luk, S. T. , FullgrabeL. , & Li, S. C. (1999). Managing direct selling activities in China: A cultur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45(3)257-266.
McCay-PeetL. , & Quan-Haase, A. (2017). What is social media and what questions can social media research help us answer.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media research methods13-26.
Pan, S. (2018).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s formed in a senior-oriented online community on older particip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1(2)135-154.
Pilerot, O. (2015). Information sharing in the field of design research. 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20(1)n1.
PutnamR. D. (2000).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InCulture and politics(pp. 223-234). 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
SavolainenR. (2017).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as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22(3)n3.
SonnenwaldD. H. (2006). Challenges in Sharing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Examples from Command and Control. 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11(4)n4.
Spiegel, D. , & KimerlingR. (2001). Group psychotherapy for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support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survival. In C. D. Ryff & B. H. Singer (Eds. )Emotionsocial relationshipsand health (pp. 97^12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lja, S. (2002). Information sharing in academic communities: Types and levels of collaboration in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use.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3(1)143-159.
TayebiS. , Manesh, S. , KhaliliM. , & Sadi-NezhadS. (2019).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communic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 and Network Science3(3)245-268.
WangW. , Zhuang, X. , & Shao, P. (2020September). Exploring health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of Chinese elderly adults on WeChat. InHealthcare(Vol. 8No. 3p. 207).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
WareP. , Bartlett, S. J. , ParéG. , Symeonidis, I. , Tannenbaum, C. , Bartlett, G. ,…… & AhmedS. (2017). Using eHealth technologies: interestspreferencesand concerns of older adults. Interactive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6(1)e3.
WrightK. (2002). Social support within an on-line cancer community: An assessment of emotional supportperception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and motives for using the community from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3)195-209.
陈娟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甘凌博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传播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0AXW003)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