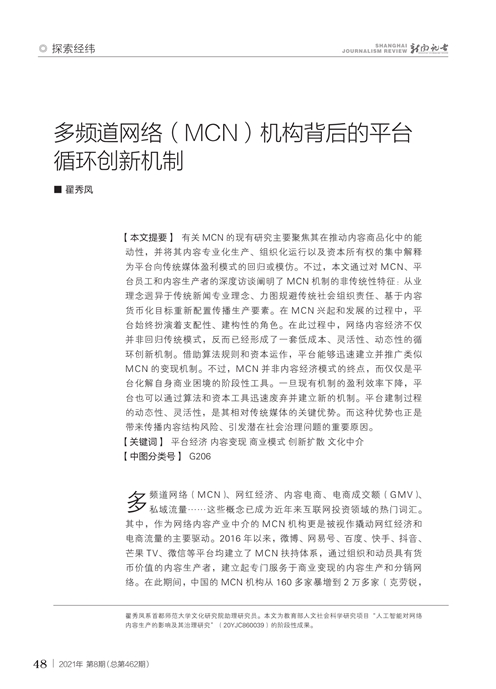多频道网络(MCN)机构背后的平台循环创新机制
■翟秀凤
【本文提要】有关MCN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其在推动内容商品化中的能动性,并将其内容专业化生产、组织化运行以及资本所有权的集中解释为平台向传统媒体盈利模式的回归或模仿。不过,本文通过对MCN、平台员工和内容生产者的深度访谈阐明了MCN机制的非传统性特征:从业理念迥异于传统新闻专业理念、力图规避传统社会组织责任、基于内容货币化目标重新配置传播生产要素。在MCN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平台始终扮演着支配性、建构性的角色。在此过程中,网络内容经济不仅并非回归传统模式,反而已经形成了一套低成本、灵活性、动态性的循环创新机制。借助算法规则和资本运作,平台能够迅速建立并推广类似MCN的变现机制。不过,MCN并非内容经济模式的终点,而仅仅是平台化解自身商业困境的阶段性工具。一旦现有机制的盈利效率下降,平台也可以通过算法和资本工具迅速废弃并建立新的机制。平台建制过程的动态性、灵活性,是其相对传统媒体的关键优势。而这种优势也正是带来传播内容结构风险、引发潜在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平台经济 内容变现 商业模式 创新扩散 文化中介
【中图分类号】G206
多频道网络(MCN)、网红经济、内容电商、电商成交额(GMV)、私域流量……这些概念已成为近年来互联网投资领域的热门词汇。其中,作为网络内容产业中介的MCN机构更是被视作撬动网红经济和电商流量的主要驱动。2016年以来,微博、网易号、百度、快手、抖音、芒果TV、微信等平台均建立了MCN扶持体系,通过组织和动员具有货币价值的内容生产者,建立起专门服务于商业变现的内容生产和分销网络。在此期间,中国的MCN机构从160多家暴增到2万多家(克劳锐,2020),MCN的市场规模从8亿元一度增长到168亿元(国元证券,2020)。那么,平台为何积极推动在内容生产者和平台之间增加中介机构?MCN在平台内容经济中扮演了何种角色?MCN从诞生、发展到淘汰的过程,体现出平台经济何种内在的运行机制和创新优势?
为了厘清这些问题,笔者选取了国内5家大型网络内容平台①(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花椒直播、YY直播)和5家MCN机构作为调研对象,并对13名相关从业者(4名MCN管理者、6名签约MCN内容劳动者、3名上述平台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自2017年11月延续至今,以便追踪和跟进MCN的发展状况。这些一手资料与优兔网(YouTube)早期将MCN正式化的历程,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讨论基础。
一、MCN机构:一种回归传统的实践?
MCN(Multi-Channel Networks,多频道网络)机构一般通过签约、孵化或收购的方式,将具有变现潜力的内容劳动者灵活组织起来,并以机构名义与网络平台及广告商对接,通过内容策划、商业推广等方式促进内容变现并实现利润分成。在MCN出现之前,研究者们从市场主体、市场动力、商业模式、技术基础等视角剖析社交媒体巨头的货币化实践,并将之概括为以算法和数据为基础的参与式传播范式。随着MCN的出现,其推动的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则被很多研究者视作一种向传统媒体模式的回归。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中始终萦绕着两个尚未被阐明的商业悖论。
(一)平台内容经济的两个商业悖论
以往研究认为,网络平台造就了一种新的内容经济形态。在市场主体方面,媒体消费主体变成了兼具被动和主动特征的产消一体者:既非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被文化工业所利用的受众,也非英国文化研究中意义的积极生产者。Web 2.0时代的用户在主动获得互动乐趣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其提供的数字内容也被网站所有者剥夺从而转变为经济价值,这也因而吸引了广告商对动态用户数据和消费行为的兴趣(Goran, 2011:127)。在市场动力方面,学者既将社交媒体的自组织性视作内容经济和传播民主化的基础动力,同时也警惕将互联网视作天生民主的乌托邦观点。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德斯·弗里德曼(Des Freedman)和娜塔莉·芬顿(Natalie Fenton)强调,技术潜力的实现取决于其实践路径,而非预先定义。弗里德曼尤其反对对社交网络自组织性和非稀缺性的过度炒作。他认为,在极大提高的资本主义所有权和生产效率面前,非等级组织的同侪生产力量已被大大抵消了(James et al., 2016:69-120+18)。
在商业模式方面,马克·安德列耶维奇(Mark Andrejevic)以网络平台的商业化诉求为前提,分析了社交媒体环境下内容商业盈利范式的显著变化:一方面,平台希望用户持续生成数据,以便它们能捕捉这些数据并将之用于商业营销活动。这个过程“既不是通过共享参与,也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协商,而是通过消费的日益加速”;另一方面,“无节制的”、“用户生成的业余内容可能不符合广告的要求”,因为广告主需要的是以商业价值为目标的专业制作内容(Andrejevic, 2009)。这一洞察已触及内容平台发展的关键问题:商业化的营销需求和“业余”内容之间的矛盾甚至敌意。学者们发现,正是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平台内容生产的特征也开始发生转变:简·伯吉斯(Jean Burgess)的研究表明,优兔网上的内容生产呈现出“业余媒体正式化”(Jean, 2013)的趋势,最初尚未被商业目的填充的、仍存有不确定性的文化空间正在从广泛的参与式传播退回到主流传播范式(Jean, 2015)。乔安妮·莫雷阿莱(Joanne Morreale)将这个过程称为“夺权”而非“赋权”的过程——看似自由的传播劳动换来的是“创造性的控制”(Joanne, 2014)。而这些商业模式的技术基础正是基于算法对社会互动性质的深刻改写。如约瑟·范·迪克(Jose van Dijck)所言,在“连通性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这一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用户因其社会互动需求而被牢牢锁定在平台的“商业性连接”中;按需定制已不仅是满足用户需求的艺术,而成为一种可以有意识地设计用户需求的工程科学,控制因而变得更加隐蔽而高效(van Dijck, 2013:170)。
这些研究勾勒出平台内容经济赖以发展的基本要素:以用户的免费劳动和自发性参与为基础,平台得以实现一种基于数据资本和算法优化的商业变现模式。不过,受限于网络内容产业实践发展的程度,这些研究留下了两个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关键商业悖论:①参与式传播尽管为平台积累了社交数据,但其随意性又无法满足平台/广告商明确的商业目标。那么,如何使参与式的产消一体者服务于平台的商业需求?②从社交互动数据中挖掘的用户兴趣虽然提供了内容货币化的可能,却难以保障持续的、稳定的消费需求。那么,如何不断引导、制造、驱动用户的消费欲望?简言之,平台如何高效组织商业生产?如何持续促进消费加速?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因而以上研究难以真正解释平台内容商业模式的特殊性和内在优势。
不仅如此,新的商业现象也开始挑战甚至颠覆以上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一方面,内容生产者不再是完整的、缺乏区分的同质化用户群体,驱动内容产业的劳动也不再仅仅是基于产消一体的“免费”劳动,一个新的以内容生产变现为目标的“收费”内容生产群体正在兴起,并构成了平台内容产业的重要劳动力要素;另一方面,内容生产已不止于自组织性或自发参与的分享冲动,而是通过MCN实现了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的人力资源调动。以下新近研究有助于理解MCN所带来的生产机制变化,并开始触及上述两个有待探讨的商业悖论。
(二)MCN背后未被阐明的平台优势
国内外学者有关MCN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MCN在推动内容产业变化中的能动性、内容生产从业余到主流的特征、标准化生产中的不平等关系,进而探讨该过程的经济动因及其回归传统的趋势。然而,这些分析对于解释平台的颠覆性优势仍然显得乏力。
现有关于MCN的研究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MCN在自我兴起中的能动性以及平台作为单纯的文化空间提供者。有学者将MCN的诞生描述为从参与式到主流范式的“新近的、骤然的商业化”,在此过程中,平台则更多提供一个过程发生的“文化空间”(Jean, 2013;2015)。有学者更进一步阐述MCN的“良性”作用及其提供的民主化可能,如弥补“创作者不受平台重视的缺失”,使“名声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fame)这样一种社交资产从传统需要被仰视的意见领袖手中,转移到无需仰视的平民网红受众(胡泳,徐辉,2020)。其次,MCN代表了内容生产过程从业余到主流/正式化的过程,并通过科层制的重建加速内容的商业化。在此过程中,平台上的参与式传播个体,会在传统媒体机构的包装下成为“专业人士”,成为传统媒体广告营销的参与者,从而使“参与式生产的潜力被引导成为消费的一部分”(Joanne, 2014)。拉蒙·洛巴托(Ramon Lobato)则将MCN视作数字视频生态的关键变化以及社交平台成为一个完全市场的节点。他认为,混乱的内容环境带来了中介组织化生产的必然需求;MCN在顶级内容生产者和受众之间增加了一层中介管理层,驱动内容文化从非正式化变得正式化,从而使自身成为规范、稳定并推动内容经济的显著力量(Lobato, 2016)。再次,MCN所推动的生产标准化也伴随着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学者普遍认同,MCN带来了短视频生产方式的转变。MCN以工业化的方式组织视频生产,即在选题策划、脚本创作、拍摄、剪辑等各阶段实施专业化分工、标准化制作和流程化管理(黄楚新,郑智文,2020),并将继续推动其“五化”:专业化、技术化、精细化、垂直化、系统化(郭全中,2020)。帕特里克·冯德拉(Patrick Vonderau)则指出,MCN以特许经营的方式人为加剧渠道的稀缺性,这加剧了内容生产者与平台间关系的不平等以及内容生产者承受的压力(Patrick, 2016)。最后,一些学者指出,网络平台正在通过MCN大规模吸收传统媒体资本,这种重资本的倾向是平台“引入传统媒体逻辑”的一种趋势(Holt & Kevin,2013)。
以上研究呈现了网络平台和MCN在内容产业发展主张上的变化:重新强调内容生产的专业化、建立科层制机构以及发挥传统媒体在融资并购中的作用。这三点通常被视为传统媒体集团所具备的特征或优势。诸多学者关注到这些变化,并将之归纳为平台向传统模式的回归或模仿。如坎宁安等人认为,平台在内容生产中倡导专业生产和引入中介力量,代表了平台商业模式与传统媒体模式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平台积极适应传统媒体产业基础的努力(Cunningham et al., 2016)。不仅如此,“旧媒体”大举向社交媒体投资以及“新媒体”自身对专业化生产和广告销售的重视,正使社交媒体陷入到传统媒体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窠臼:UGC被边缘化、所有权集中、版权限制、对广告的重视、对全球信息流通的阻碍等。因而,平台没有带来媒体环境的革命,而仅仅构成了媒体环境演变的一部分(Jin, 2012)。有学者进一步讨论了MCN实践的内在动因。冯德拉认为,这种正式化是平台在一以贯之的商业化诉求下对视频内容重新金融化定价的必然结果(Patrick, 2016)。周逵和史晨使用“正当性的互嵌”阐述了中国互联网平台助推广电MCN的动因:对商业性平台而言,“广电系主流媒体的入驻可以大大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增强其针对体制内进行表达的话语资本”,从而缓解其政策合规性焦虑(周逵,史晨,2020)。不过,坎宁安等人也指出,这种连续性同时伴随着商业模式的争论(contestations),即硅谷商业模式对好莱坞商业模式的创造性破坏(Cunningham et al., 2016)。在笔者看来,这种看似连续性下所隐藏的创新性和破坏性,恰恰是理解MCN在平台商业模式中的角色的关键视角。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未在描述两种商业模式差异的基础上对平台商业模式的特征加以归纳和总结。这也正是本文在结论中试图加以推进和补充的内容。
总体来看,以上现有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相对集中的观察视角:一方面是观测对象,或集中于MCN与内容生产者之间的互动,或聚焦特定主体(广电业)的MCN实践模式,而较少关注平台在MCN发展中所扮演的建构性角色;另一方面是观测内容主要集中于内容生产的操作流程和狭义场域,并未深入探讨平台作为基础设施提供者的关键角色。因此,尽管这些研究触及了MCN在组织内容生产中的效率优势(以中介角色提升生产标准化,从而服务于内容增值),却仍然未能解释关于平台内容经济的两个根本问题:
第一,网络平台内容经济的关键创新优势到底是什么?以上研究将内容专业化和组织化解释为对传统媒体制度框架和商业模式的回归,暗示平台并未建立一种新型的、颠覆性的商业逻辑,且其盈利模式仍高度传统化。然而,内容平台攻城略地、抢占传统媒体注意力资源的现实却强烈地表明平台的商业逻辑或许并非模仿传统这么简单。事实上,以“内容—电商”模式为代表的、区别于传统广告的盈利模式已经崛起并带来了显著的金融价值。因此,有必要跳出“MCN—内容生产者”之间的互动框架,对平台大力推行MCN的动因加以分析,以明确平台商业逻辑的根本优势所在。第二,对平台而言,在持续促进消费加速的过程中,MCN机构是不可替代的吗?一方面,MCN在内容劳动者的筛选和意识形态塑造中起到显著作用,加速了内容变现;另一方面,在常换常新的平台经济概念中,MCN能否具备持续的生命力仍有待讨论。因此,需要将平台这一核心主体与网络内容产业的微观实践相结合,在经验性观察中获得以上问题的答案。鉴于此,本文将回溯平台发掘并推动MCN的历程,探析MCN在实现平台商业诉求中扮演的角色,进而阐明MCN背后的平台经济创新优势。
二、平台支配下MCN内容生产的非传统性
内容平台的开放性通常被理解为用户通过广泛参与打破传播渠道的垄断,而较少涉及平台在商业实践中如何选择性地对参与式潜力加以调用;内容平台的经济优势则多被解释为平台型企业的常见特征(如垄断倾向、市场集中、边际成本低等),而尚未对内容平台建制过程的灵活性优势加以深入分析。事实上,在MCN机制诞生、发展和竞争淘汰的整个历程中,平台始终扮演着积极的建构性角色,通过对参与式潜力的选择性调用、对商业模式的正式化和建制化,形塑着平台内容经济的方向和形态。在此过程中,MCN着力围绕内容货币化目标展开实践,并呈现出诸多与传统媒体运行机制的不同之处。
(一)平台驱动下MCN雏形的诞生与兴起
内容货币化(monetization)的渴求根植于网络平台的资本基因之中。在优兔网成立伊始,其创始人与投资方红杉资本(Sequioa Capital)之间便就该网站的发展战略达成了共识。双方认为,用户生成视频的爆炸式发展将迅速助推优兔网成为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主导者。一旦完成用户积累,优兔网应即转向对新兴商业模式的探索:一方面通过改进产品的社交互动功能,增加用户和内容的活跃度和留存度;另一方面大力开发用于内容变现的盈利工具,并倡导用户参与式、创造性使用这些工具。这份备忘录②同时提出了被当下内容产业奉为圭臬的垂直策略,即开发针对“目标垂直市场”(Target vertical markets, 如eBay拍卖、房地产、汽车、体育等领域)的特殊定制功能。为此,优兔网开始大力推广商业功能,如参与式视频广告、品牌频道、内容ID管理系统、内容广告、视频传播分析工具、电子商务工具、移动广告等。借助这些功能,用户或第三方机构可以介入平台的广告后台,实现广告匹配、共享分成、监测侵权内容等功能。
可以看到,优兔网基于自身商业战略对参与式传播的主体进行了区分:一方面通过社交参与的形式收集进入商业性连接的用户信息,即积累消费者数据;另一方面鼓励用户创造性探索尚不确定的、潜在的商业价值点,即开放性商业实验。这类开放性实验的优势在于,平台并不预设特定的发展模式和盈利方式,而是在一个动态变化的内容产业中摸索具有盈利潜力的实践。MCN早期雏形的出现,佐证了开放性实验的有效性。
随着用户参与的持续,一些善用平台商业工具的初代网络红人零散涌现出来,他们开始利用自身影响力分享美妆、购物经验,影响用户的内容旨趣与消费行为。与此同时,一个名为“下一个网络”(Next New Networks)的原创视频分发中介于2007年成立并迅速崛起。该机构并不直接制作视频,而是将大量的创作者聚集起来,为他们提供播放渠道和广告机会。这正是MCN机构的早期雏形。渠道聚合提高了制造爆款的能力,该机构每月的视频点击甚至达到了2亿次,广告收益也随之增加。
优兔网动态监测全网的视频数据,迅速捕捉到下一个网络的组织效能,并着手在全平台倡导这一经验。2009年,该平台开始大力倡导以专业内容生产联合为基础的MCN机构。2011年,优兔网直接出手收购了“下一个网络”,并开始实施“YouTube Next”计划。该计划为视频创作者提供经费和制作培训,推动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以更加商业友好的内容提升变现效率。此外,一系列内容生产的评价规则也通过平台官方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如收益共享计划、观看时间分成算法、超级留言和商品货架等功能。随着MCN机构不断增多并持续获得平台的官方特许权限,内容中介组织下的规模化、工业化内容生产实践开始了。
MCN的诞生和被发现的历程,是平台主动倡导参与式、开放性的货币化实验,进而将成功经验正式化的过程。可见,平台的开放性不仅在于社交表达的平民化,更在于对用户商业探索的激励;平台倡导的参与性并不意味着提供一个忽视经济价值的文化空间,反而是希望发掘内容货币化的新机制。通过MCN机构,平台得以大规模推广其实验成果,并将内容产业扩张中的风险分散到第三方机构和内容劳动者身上。
(二)MCN内容劳动中的“去新闻专业理念”
新闻专业理念通常包含着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多种内涵。一方面,新闻记者诉诸集体性的身份和文化、保留一定的主体性和权威性、能够在经济利益之外强调社会公共诉求(Beam, 1990),这些进步性的价值倡导构成了新闻专业理念的重要内涵。另一方面,按照话题、地域等方面来安排新闻生产,并采用特定的写作体例,使传统新闻生产具有一定的标准化特征,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商业化对新闻生产的要求(Tuchman, 1978:22-23+63-65)。就MCN对从业者价值观和标准化操作的倡导而言,其在现象上与新闻专业理念对特定价值观和操作规范的倡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这种相似性更多局限于对新闻业“专业化”这一概念的挪用。就其实践的动因和本质而言,MCN机构的实践与传统新闻媒体的专业理念迥然不同。
首先,MCN诞生于平台试图解决其盈利模式困境的努力中。随着用户和视频达到数以亿计,如何处理一个日益混乱且庞大的内容空间变得十分棘手。普通用户的内容输出不连续,质量参差不齐,病毒化传播潜力弱,因而变现能力有限。尽管优兔网在2008年获得了2亿美元的收入,但只有3%的视频为平台贡献了收益(Wie & Chang, 2009)。为了化解商业化的营销需求和业余内容之间的矛盾,平台选择由MCN对内容劳动者加以培育。通过制造一套创新扩散的话语,MCN得以将网红成功学的意识形态及操作范式传达给内容劳动者,从而驱动一个高度竞争的内容经济市场。
其次,MCN保障了平台意识形态在内容劳动者中的统一传达。这种意识形态没有面向社会价值的诉求,而是围绕平台注意力经济加以建构。一方面是关于网红成功学的想象。在平台的塑造中,大V是兼具浪漫和权力的代名词:网红意味着公众的认可、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点石成金的变现能力;成为网红/大V的权力不再是特权阶层和明星的专属,只要愿意跟随平台和MCN机构的指导,就可能复制网红们的成功。另一方面是关于创意劳动和创业精神的渲染。在平台的话语中,网络自媒体生产意味着灵活的劳动时间、超越雇佣关系、挑战资本权威、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创意劳动”(翟秀凤,2019);而大量的加班和无薪劳动,为了追逐热点不眠不休,正是“勤劳致富”③创业精神的应有之义。
为了调动内容劳动者的积极性,平台与MCN将网红经验提炼为用以推广的行动指南,以推动变现实践的创新扩散。在各大平台的年度峰会上,行业大佬、幕后推手和新晋网红齐聚一堂,见证平台为最具商业价值的内容劳动者和MCN颁奖。获奖者分享 “流量变现”、“粉丝经济”、“跨界电商”的经验,讲述内容劳动者单打独斗的困境,传授成功MCN机构的生存规则。④平台也会在峰会上宣布新一年的百亿补贴和扶持计划,并向所有人宣告:平台的传播优先权是一种流动的特权,只有那些最具盈利能力的机构和个人才能获得。一系列有关内容产业的话题和想象经由MCN传递给内容劳动者,网红成功学也因而被根深蒂固为整个平台的文化规范。
再次,MCN复制了一整套来自平台的人员筛选和评价体系,这不同于传统新闻业基于内容质量和同业认同所开展的声誉评价。尽管平台能够按照影响力量化指标(如粉丝数、阅读/观看量、内容基本类型)对内容劳动者进行基本区分,但这种相对粗放的筛选难以精准锁定内容变现的方向,也无法匹配广告/电商客户的个性化营销需求。作为平台过滤系统的延伸和补充,MCN机构能够依托平台数据,持续遴选具有内容变现潜力的生产者,并将他们吸纳到内容市场之中。MCN的创始人们坦言,“MCN存在的价值应该是帮助红人去变现”,“有价值流量的评判标准是以商业为导向的”(克劳锐,2020);“主要是就是看他的内容适不适合接广告,领域够不够垂直,有没有变现前景”。⑤与此同时,MCN对内容生产者的评价也与平台的KPI(关键绩效考核)体系相一致。除了常用的内容传播指标(如CPM千人曝光成本、CPE单人互动成本、CPD单次推广成本等),平台和MCN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商转化指标(如转化率、曝光度、广告回报率等)作为衡量内容变现效果的核心指标。
平台和MCN一方面通过公开的议程设置,将成功网红描述为人人皆可复制的商业机遇;另一方面则通过严苛的商业标准来遴选内容产业的职业后备军。这些网络原生的内容劳动者既倾心于内容市场的经济刺激和成名想象,适应算法量化指标的支配逻辑,又完全脱敏于传统媒体从业者的劳动福利和专业理念,因而成为网络内容产业的理想劳动主体。藉由MCN对职业劳动者的遴选和组织,平台得以选择性地调整内容供给结构,从而适应高度资本化的内容市场需求。
(三)MCN与平台的风险控制和责任规避
尽管MCN倡导内容劳动者的重新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MCN和平台能够承担传统组织机构的责任。相反,MCN这一管理层和中介层的出现,反而强化了不稳定劳动和劳动控制,使得平台得以规避大量的管理和法律风险。
对平台而言,管理庞大的内容用户群体,不仅需要巨大的人力成本,还意味着不确定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而借助MCN的中介角色,平台得以实现成本和风险的转移。一方面,MCN通过介入内容选题、生产和传播的全流程,使内容生产服务于商业效果评估,并建立了相应的惩罚机制。受访的MCN广告部门员工谈到,“我们会明确把广告题目或者电商产品的特点告诉创作者,创作者则会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设计场景,在很自然的过程中把想广告的信息传达出去”。⑥不仅如此,MCN机构也会对广告营销的效果加以跟踪。如在直播中,主播展示广告的形式和内容(如口播还是文字形式、广告次数、持续时间等)会有专门的MCN人员负责监督。如果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就会触发约定的大广告主惩罚机制,主播能够获得的分成会相应扣除。可见,与传统新闻业中编辑团队与广告团队的相对独立不同, MCN及其广告团队实际上已经将内容生产过程内化为广告营销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MCN直接与大量内容劳动者确立合作关系,从而使平台得以规避因管理海量劳动者带来的成本和风险。一项针对512家MCN机构的调查显示,MCN机构旗下签约的内容生产者从10人到500人以上不等,其中45%的MCN机构的签约规模在100—300人,签约300人以上的达到了18%(克劳锐,2020)。不过,MCN与劳动者之间的协议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合同,而仅仅是约定了合作意向和分成方式的合作协议。因此,MCN无需履行为劳动者提供底薪、办公场所、五险一金、带薪假期等劳动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某MCN管理人员谈到,“目前市面上大多是这种签约方式。劳动合同太麻烦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在我们公司是没有底薪一说的,一分钱都没有。创作者就是要靠内容变现的分成来赚钱”。⑦通过这种方式,MCN能够以规避劳动法规的方式,快速调动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平台内容市场。
除此之外,MCN还扮演着诸多功能性角色,例如,承担内容审核功能,防止内容生产触及敏感或违法议题;以竞业协议限制内容分发的平台,保障平台的独家版权和收益权;代替平台处理内容版权纠纷等。为了保障MCN有效发挥以上作用,平台通过规则强化着MCN的“官方权威”。例如,某直播平台会要求内容生产者与平台和MCN签署“双协议”。“如果一个人想做直播,不仅要跟平台签约,还要跟中介签约,否则我们就相当于没有在平台认证。没有认证的人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而且平台的很多推广资源是直接给公会(即网络直播行业的MCN机构,作者注)的,不加入公会就得不到这些资源。如果有公会帮忙,就更有可能拿到首页推荐位。这种稀缺资源一般的小主播是根本不可能拿到的。有了首页推荐,吸引游客的效率就会明显增加”。⑧而一旦内容生产者决定与MCN解约,平台将冻结内容生产者的账号,以保证MCN对账号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因为MCN与内容生产者之间的合约通常会明确规定,内容劳动者要无条件配合MCN承接的广告植入、电商直播等商业业务;如果内容生产者拒绝MCN的商业安排,可能会面临账号冻结、失去前期积累的风险,还会面临高达数百万的违约赔偿甚至法律追责。⑨
借助MCN,平台得以降低其管理内容市场的成本,以高度灵活的方式调动劳动力资源,并获得他们内容的独家版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由于平台和MCN都拒绝与大多内容生产者签署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因而这些合作关系可以随时建立或解除。这不仅使平台的风险得以分散化和社会化,而且增加了平台依据自身战略、开展各种盈利实验的便利性。
(四)平台对传统媒体生产要素的吸纳和重新配置
MCN机构证明了其吸引资本的显著效能。除迪士尼以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制作者工作室(Maker Studios)的知名案例外,华纳、贝塔斯曼、德国媒体巨头ProSieben、法国传媒集团Canal Plus、梦工厂动画、美国赫斯特传媒集团、传奇娱乐公司也纷纷斥资入场。除传统媒体集团外,Upfront Ventures、Greycroft Partners、Downey Ventures等风险资本,马来西亚政府战略投资基金Astro Overseas以及新加坡电信提供商SingTel也成为MCN机构的投资者(Mediakix, 2020)。在中国市场,除腾讯、微博、阿里、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之外,红杉资本、经纬创投、辰海资本、梅花创投、真格基金等也纷纷向MCN机构注资。
尽管传统媒体的注资体现出一种平台与传统媒体资本之间谋求合作的趋势,但这却难以被解释为平台向传统媒体的回归。一方面,从资本价值链来看,传统媒体及风险投资注入MCN的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直接助益于平台的内容变现;对传统媒体而言,其投资的目的是通过战略性收购,在日益缩水的广告份额中寻求打入网络市场的支点。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显著的趋势是,内容平台正在通过收购并购,将少数最具商业价值的MCN纳入自身的资本矩阵中。据不完全统计,过去5年中国MCN市场的近百起投资案例中,腾讯共投资14起,新浪微博投资7起;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哔哩哔哩、快手等平台也先后入资了头部MCN机构(三金娃娃,2020)。至此,平台已不再仅仅是MCN赖以生存的网络基础设施提供者,同时也成为头部MCN机构的资本所有者。
平台对传统媒体的吸纳不只局限在资本要素,还体现对人才要素、行业操作规范、体制内传播权限的整合和调用。在近年来的广电MCN实践中,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驱动下拥抱市场和技术条件兼备的商业平台,而平台则积极谋求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抖音等平台专门成立广电合作部,负责对接各大卫视,并派出专人对传统广电机构的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平台属性、算法机制、短视频剪辑特性、竖屏拍摄方式、如何起标题等一整套操作规范(周逵,史晨,2020)。在平台推动下,较为成功的广电MCN已经在娱乐、剧情、母婴、美妆等常见的商业领域有了显著的经济收益,这些领域正是平台所长期倡导的垂直领域。通过主动介入广电MCN的媒体融合进程,平台不仅能够按照自身需求调整传媒业的操作规范,影响甚至改写传统专业主义范式下的评价标准;而且能够藉此规避甚至打破牌照管理对采编权限的限制,使具备采编权的广电机构成为平台上的原创内容生产力量。
平台的商业战略始终围绕着对传播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吸纳一批具有忠诚度的内容生产者,打破传统媒体对传播资源和渠道的占有,规避内容获取中的知识产权争端,提升将传播渠道为我所用的能力。正如各种互联网新兴概念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一样,MCN同样扮演了为平台吸纳和整合传统生产要素的角色。对传统媒体而言,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并加入媒体融合的进程,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战略选择;而对平台而言,其不仅没有回归传统的生产模式,反而进一步实现了对传统媒体资本的重新配置,并强化了自身对体制内传媒资源的调用能力。不仅如此,传统媒体的加入,意味着平台的商业形态获得了合法性的确认,也意味着平台能够通过算法推动传统媒体向平台经济的调整和适应,从而提升自身经济资源的获取能力。
三、结论:MCN背后的平台循环创新机制
MCN是平台内容经济模式的终点吗?从2016年到2019年,MCN经历了内容数量和产业规模的爆发性增长,平台则积极推动这一过程,并未对这种增长表现出抑制倾向。然而,2020年至今,大量MCN机构已经在激烈竞争中倒闭;多位受访MCN运营者谈到,平台正在逐渐“收权”,将一度下放给MCN的权限收回平台,并重新“放权”给内容生产者来竞争这些曝光资源。⑩一名平台内容运营部门负责人表示,除了那些最具盈利价值的头部MCN,“其他机构对平台而言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11]那么,迅速兴起并激烈淘汰的MCN对平台的商业模式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以看到,MCN机制经历了从诞生兴起、大规模扩散到激烈淘汰、头部集中的发展历程。如前所述,一些学者捕捉到MCN的专业化、机构化及其对传统资本的吸纳能力,将这一过程理解为由MCN所驱动的对传统媒体模式的回归。诚然,MCN发展的现象表征与传统媒体机制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如重新强调内容生产的专业化、建立具有组织和管理功能的科层机构、发挥传统媒体的资本集中作用、重视从业者的统一意识形态和标准化流程。然而,如前文所述,这些变化在性质和趋势上则体现出显著的非传统性:MCN强调的专业化,本质上与传统媒体在新闻专业理念中所论及的价值观念迥然不同,而更多是一种基于眼球经济逻辑开展的职业化实践;MCN本身也并非媒体机构中固定的部门,而是一种随时可以建立和解散的第三方市场中介;而其对传统媒体资本、人员等要素的调用,不仅没有增加传统媒体在产业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反而强化了平台作为上游产业主体对下游产业链要素的调用能力;MCN所推崇的从业意识形态和细分操作流程,与依托传统新闻院校开展的人才培养也并不相同,而更多是市场主体在业务需求下规训从业主体、提高盈利效率所采取的流水线培训策略。在这一意义上,现象和从业概念的相似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MCN的发展动因及其在平台经济中承担的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跳出对内容生产微观过程的关注,将MCN置于平台内容经济的背景中,我们会发现上述解释思路忽略了平台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关键优势所在:高度灵活、动态性的循环创新机制。如(图1 图1见本期第57页)所示,通过算法规则和资本并购等方式,平台动态地介入MCN发展的各个阶段,成为MCN兴起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内容平台的关键优势,正在于其商业模式基于一个无成本/低成本、实验性、动态性的尝试、调整和矫正过程,并能迅速建立和推翻各种商业机制——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平台的“循环创新”机制。
这一“循环创新”机制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社会化变现实验”阶段。在完成用户原始积累之后,平台开始通过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实现对自组织性的利用:一方面,不断完善产品社交功能,以保持用户黏性,持续积累用户行为和消费数据;另一方面,大规模推广用于内容变现的算法程序和营销工具,鼓励用户对商业工具的创新性使用。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内容生产者逐渐从网络意见领袖转型为消费主义网红,并探索出一些卓有成效的商业变现经验,而试错的成本被融化在个体的参与性活动中。平台持续监测并敏锐捕捉其中的成功案例,并开启这一机制的第二阶段:“实验结果制度化”阶段。平台通过平台规则和算法规则将这些偶发性的、自发性的商业探索经验固定下来,并以曝光权限下放、现金补贴等方式吸引内容生产者的参与。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早期的MCN诞生了。此后便是第三阶段:“大规模创新扩散”。通过大规模倡导MCN,平台得以统一劳动者的意识形态、推广标准化的生产流程、规避可能的管理风险,提高对劳动力、资本等各项生产要素的调取能力。一旦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中涌现出具有显著金融价值的个体或机构,平台“收割实验成果”的第四阶段便到来了。在此阶段,平台一方面通过MCN持续吸纳传统资本和体制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迅捷收购将最具商业价值的优胜者纳入麾下。随着头部MCN成为平台资本矩阵的一部分,平台则通过回收权力的方式开启新一轮社会化变现实验。从这个意义上,MCN并非平台内容经济模式的终点,而仅仅是平台化解自身商业困境的阶段性工具。随着内容经济的发展,已经被制度化的经验会因平台战略调整而被升级、改写甚至废弃。换言之,一旦出现更具效率的组织机制或更具金融增长性的盈利模式,MCN必然会面临转型甚至会被替代。
平台的创新机制是一个能够反复循环的“开放实验—结果制度化—创新扩散—成果收割”过程。而这套循环创新机制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原因即得益于智能算法提供的技术基础。借助算法工具,一个MCN中介可以同时跟踪几万个内容生产者的粉丝数量和收益情况,根据量化评分为其匹配曝光工具和商业资源。这种低边际成本且高度自动化的管理是传统的文化产业中介所无法实现的。如坎宁安所言,硅谷模式相比好莱坞模式的主要差异之一即在于网络平台谋求实现盈利/广告分发的自动化、永久测试性和快速迭代(Cunningham et al., 2016)。依托算法调整,平台不仅能实现动态的数据和趋势监测,而且能够将实验的结果快速制度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通过发挥自身在商业决策和资本运作中的灵活性,平台能够推动传媒资源按照自身盈利模式进行流动和配置,从而引导市场主体(内容生产者、MCN机构等)加入新兴内容经济增长点的开拓之中。如此循环往复,平台得以使其技术工具和市场规则始终与新兴的商业盈利点保持着紧密的互动。
平台建制过程的这一动态性优势,正是以成本高昂、反馈滞后、数据缺失、制度僵化为特征的传统媒体机构所难以企及的:由于原有的内容生产流程(报纸印刷等)、科层机制、人员保障(相对规范的劳动合同)中的运行成本,传统媒体在媒体转型中面临着显著的成本困境;由于缺乏即时性的内容/广告传播和反馈机制,传统媒体的反馈效率和广告传播效果在广告市场竞争中备受压力;由于缺乏广泛的用户数据统计能力,以收视率为代表的抽样统计面临着来自平台实时数据(单一平台动态数据、多平台数据库交叉对比、用户使用行为大数据积累、消费数据与内容获取行为的匹配等)的正面竞争;而受制于自身的管理机制、决策惯性和资本所有权属性,传统媒体机构难以像平台一样迅捷建立/废弃新的机构或者机制,亦或频繁开展大规模的资本并购。正是这些相对优势/劣势,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平台何以在传媒市场竞争中攻城略地,对传统媒体的市场地位形成了显著冲击。可以说,内容平台对MCN的倡导不仅并非回归传统媒体盈利模式,反而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能够灵活调用生产要素的循环创新机制。
不过,正如MCN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平台的循环创新过程也蕴含着不确定的悖论和风险。一方面,内容生产者自发的创造性潜力可能被商业逻辑过滤或拒斥,从而使网络内容结构日益窄化。由于平台倾向于将传播优先权赋予特定的商业内容,因而所谓热点内容也并非海量受众的自发选择,而往往是获得传播特权青睐的结果。如前所述,为了获取平台给予MCN的独家曝光资源和专属内容服务,大量内容生产者被迫从自雇佣的创作主体加入到平台内容经济的工业化流程,成为MCN账号矩阵的构成部分;而能够获得平台“热门流、视频流以及独家推荐位”的内容,则主要是那些“变现能力最强的垂直领域,母婴、美妆、体育、金融、旅游、健康医疗等等”。[12]传播权利的高度不平等会弱化内容生产者的创造活力,而这种创造活力本身既是平台赖以开展货币化实验的基础力量,也是网络内容多元化和丰富性的重要支撑。更重要的是,平台内容结构的日渐窄化,会使非商业、公共性、严肃性内容的传播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虽然已有研究者讨论过内容生产者或用户运用自身力量,对平台及其算法进行抵抗或协商的可能性。不过遗憾的是,个体协商带来的“微小的差异”(Velkova & Kaun, 2019)何以聚沙成塔恐怕不容乐观。由于这些抵抗无法改变平台掌握着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基础设施的根本现状,亦无法穿透披着商业机密外衣的算法黑箱,因而其在反抗理念上的象征性和启发性意味可能超越了其在实践中的可复制性。正如科特所言,“网红不违反规则;相反,他们遵守规则并认识到这是在游戏中取得成功的唯一手段”(Cotter, 2019)。
另一方面,平台循环创新的目的在于低成本获得劳动力、资本等资源,并打破传统行业的既有规制,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侵权和生产资料使用边界的重新塑造”(胡凌,2016)。广泛的无薪和低薪劳动正是平台经济创新中不可忽视的侵权现象。随着资本集中于少量头部机构,大量中小MCN已经运转困难。然而,挣扎中的MCN不仅没有退出市场,反而还在持续增加签约数量,试图以低成本的大量签约押注个别账号的偶然火爆,以实现扭亏为盈。在这片“不受管制的、狂野的数字西部”(Mann, 2014),以劳动剥削和经济利益冲突为诉求的合同纠纷在持续上演。在此过程中,治理的对象以创新的面目隐含在新兴概念背后,因而变得难以识别;而类似激发平台自身的治理诉求,使其主动发挥公共责任的解决方案也因而变得苍白。未来的传播治理能否关注平台经济循环创新带来的新兴治理风险,能否在保持平台创新活力的同时避免其对现有经济秩序、产业规制和劳动保障体系的冲击,还需要持续的跟踪观察和深入探讨。■
注释:
①本文研究对象聚焦于以网络内容生产传播为主要业务类型的平台,而非以劳动匹配(如滴滴打车)、电商销售(如淘宝、京东)等业务为主的平台。因此,文中所论及“平台”均指称网络内容平台。本文的深度访谈自2017年11月延续至今,日期与地点根据与研究对象沟通确定,每次访谈时间为2小时-3小时。
②这部分内容可参见Viacom与YouTube诉讼案的文书。Viacom International vs. YouTubeInc. Case No.1:07-cv-02103(LLS). Document 194. Declaration of Roelof Botha. Mar 18201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Botha exhibits 1-3。
③MCN机构G公司CEO访谈。G公司主要在母婴和美妆两个垂直领域开展内容生产,总公司位于北京,分公司位于哈尔滨。其中分公司签约内容生产者30人以上,月均收入从3千元到1万元不等,主要来自平台流量分成和百万粉丝级别账号售卖分成。据该CEO自述,“勤劳致富”一词,是他在分公司开会时常常向员工提及的价值理念。访谈时间2018年12月10日。
④典型案例如历年新浪微博V影响力峰会的相关报道,部分如http://ent.sina.com.cn/zt_d/2017ylvfh/,http://ent.sina.com.cn/s/m/2019-08-05/doc-ihytcerm8732167.shtml,http://video.sina.com.cn/p/ent/m/c/doc/2017-12-07/171167579435.html,http://video.sina.com.cn/p/ent/m/c/doc/2017-12-07/170367579427.html。
⑤MCN机构G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员工P访谈。该员工负责在各大社交平台寻找适合该公司内容矩阵的内容生产者,联络他们并与他们签署合作协议。访谈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
⑥MCN机构S公司的广告业务人员A和签约短视频内容生产者X访谈。S公司主要业务为以城市女性为主要受众的短视频内容生产,已于2018年获得千万级A轮融资。访谈时间为2019年3月28日。
⑦MCN机构S公司CEO访谈,访谈时间为2019年3月25日。
⑧YY直播平台主播N访谈。截至访谈之时,该主播在YY平台做主播时间为2年,粉丝数为6.3万人,每天直播时间约为8小时。访谈时间为2018年1月7日。
⑨参见林晨同学的自我陈述视频(《亲身经历,曝光某些公司有多黑暗》,2020年4月13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V411o7VZ?from=search & seid=4541643553707713383,2020年9月1日)。截至2020年9月1日,该视频获得856.2万播放,15.5万弹幕。
⑩MCN机构O公司管理人员B和X访谈。O公司旗下签约主播主要在YY直播和花椒直播两个平台直播。截至访谈之时,旗下签约主播60余人,其中月流水50万以上的为1人,月流水10万左右的为3-4人,月流水3万左右的为20人,月流水1万左右的为40人。月流水额并非主播所能获得的实际收入,而是主播与公司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一般主播分成比例为3-5成,拥有更多粉丝数和流水额的主播分成比例会相对高一些。访谈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
[11]网络平台X下属内容运营部门负责人M访谈。据该负责人介绍,该平台自2016年开始正式引入MCN扶持机制,并曾与超过5000多家MCN机构签订扶持计划。但在2020年以来,该平台逐渐减少了与MCN机构的签约数量,并且更加重视对少数头部MCN机构的曝光资源倾斜。访谈时间为2020年11月30日。
[12]MCN机构M公司负责人L访谈。该负责人表示,严肃新闻、历史内容等内容领域的变现能力有限,市场上的MCN公司一般不会进入此类领域,他们所选择的主要是平台给予支持力度较大的一些强变现领域。访谈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此外,新浪微博对MCN的支持政策,可参见微博小秘书,《微博垂直MCN合作计划》,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04078283131912,2017年5月5日。新浪微博重视并持续增加针对头部垂直领域的流量倾斜。如新浪科技。《微博2017年赋能自媒体收入207亿30亿基金扶持MCN》,http://tech.sina.com.cn/i/2017-12-05/doc-ifypikwu0083616.shtml,2017年12月5日;又如蓝鲸财经。《微博:提升头部垂直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对中长尾领域进行流量支撑》,https://ishare.ifeng.com/c/s/7orOhu3hqdB,2019年8月4日。
参考文献:
郭全中(2020)。MCN机构发展动因、现状、趋势与变现关键研究。《新闻与写作》,(3),75-81。
国元证券(2020)。新流量、新消费兼论直播电商与MCN。2020年5月24日。检索于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54533.html,2020年9月2日。
胡凌(2016)。“非法兴起”:理解中国互联网演进的一个视角。《文化纵横》,(5),120-125。
胡泳,徐辉(2020)。网红社交资产如何改变商业模式。《新闻界》,(8),48-56。
黄楚新,郑智文(2020)。粉丝经济背景下短视频的内容生产探析。《中国编辑》,(6),15-19+41。
克劳锐(2020)。2020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白皮书。2020年5月27日。检索于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45815.html, 2020年9月1日。
三金娃娃(2020)。MCN资本局大起底:造不出独角兽,撑不起百亿市值!。2020年7月22日。检索于https://new.qq.com/omn/20200722/20200722A0X25700.html,2020年9月1日。
翟秀凤(2019)。创意劳动抑或算法规训?——探析智能化传播对网络内容生产者的影响。《新闻记者》,(10),4-11。
周逵,史晨(2020)。正当性的互嵌:广电MCN机构的创新动因与模式分析。《新闻与写作》,(10),47-56。
AndrejevicM. (2009). Exploiting YouTube: Contradictions of user-generated labor. In Snickars, P. & Vonderau, P. (eds. )The YouTube Reader, pp. 406-423. Stockholm: 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BeamR. A. (1990).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as an organizational-level concep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21)1-43.
CotterK. (2019). 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 How digital influencers and algorithms negotiate influence on Instagram. New Media & Society21(4)895-913.
CunninghamS. , CraigD. , & Silver, J. (2016). YouTubemultichannel networks and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new screen ecology. Convergence122(4)376-391.
Goran, Bolin. (2011). Value and the Media: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Digital Markets. London: Ashgate.
HoltJ. & KevinS. (eds. )(2013). Connected viewing: Sellingstreaming& sharing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James, C. , NatalieF. , & DesF. (2016). 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JeanB. (2013). YouTube and the Formalisation of Amateur Media. In Hunter, D. , Lobato, R. , & Richardson, M. , et al, (eds. )Amateur Media: Social, Cultur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pp. 403-413.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JeanB. (2015). From “broadcast yourself” to “follow your interests”: making over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8(3)281-285.
Jin, K. (2012).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YouTube: from user-generated content to 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 MediaCulture & Society(34)53-67.
JoanneM. (2014). From homemade to store bought: annoying orange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YouTube.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14(1)113-128.
LobatoR. (2016). The cultural logic of digital intermediaries: YouTube multichannel networks. Convergence22(4)348-360.
MannD. (2014). Welcome to the unregulated wild, wild, digital West. Media Industries Journal. 1(2)Retrieved at https://quod. lib. umich. edu/m/mij/15031809. 0001. 206/-welcome-to-the-unregulated-wild-wild-digital-west?rgn=main; view=fulltext; q1=1Sep 12020.
Mediakix. (2016). What is a YouTube MCN?. Feb 2. Retrieved at http://mediakix. com/2016/02/what-is-a-youtube-mcn-and-what-it-means-for-youtube-influencers/#gs. o0MS1cQSep 12020.
Patrick, V. (2016). The video bubble: Multichannel network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YouTube. Convergence22(4)361-375.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Van D.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pp. 1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elkova, J. & Anne, K. (2021). Algorithmic resistance: media practic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air.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4(4)523-540.
Wie, G. & ChangK. J. (2009). Where are YouTube headed?. Apr 20. Retrieved at http://10. asiae. co. kr/Articles/view. php?tsc=001001002 & a_id=2009042008325928427Oct 202017.
翟秀凤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工智能对网络内容生产的影响及其治理研究”(20YJC86003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