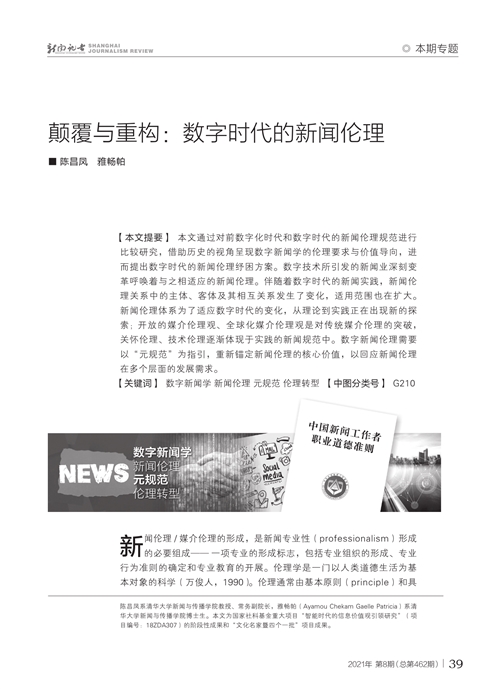颠覆与重构: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
■ 陈昌凤 雅畅帕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前数字化时代和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规范进行比较研究,借助历史的视角呈现数字新闻学的伦理要求与价值导向,进而提出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纾困方案。数字技术所引发的新闻业深刻变革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闻伦理。伴随着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新闻伦理关系中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适用范围也在扩大。新闻伦理体系为了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从理论到实践正在出现新的探索;开放的媒介伦理观、全球化媒介伦理观是对传统媒介伦理的突破,关怀伦理、技术伦理逐渐体现于实践的新闻规范中。数字新闻伦理需要以“元规范”为指引,重新锚定新闻伦理的核心价值,以回应新闻伦理在多个层面的发展需求。
【关键词】数字新闻学 新闻伦理 元规范 伦理转型
【中图分类号】G210
新闻伦理/媒介伦理的形成,是新闻专业性(professionalism)形成的必要组成—— 一项专业的形成标志,包括专业组织的形成、专业行为准则的确定和专业教育的开展。伦理学是一门以人类道德生活为基本对象的科学(万俊人,1990)。伦理通常由基本原则(principle)和具体规范(rule)组成。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些与其职业活动相适应的伦理规范(黄瑚,2011),亦即新闻伦理,它由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构成,通常会形成守则(code)、准则(guideline),主要目标是引导和帮助新闻工作者在日常新闻生产和分发的任务中快速地做出伦理相关的决定,以自律的形式规范新闻传播活动。数字新闻业对传统新闻伦理带来诸多挑战,本文将从数字新闻业的变革入手,通过比较数字时代与前数字化时代新闻伦理的相关问题,研讨数字时代新闻伦理面临怎样的挑战、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伦理观。
一、数字新闻业呼唤新闻伦理新范式
数字新闻业的兴起通常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互联网的出现和最早的商用网络浏览器Netscape和微软的Internet Explorer的推出(Scott, 2005),技术变革的前奏则是通信技术从模拟转向数字、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出现。数字化技术目前最主要的运用是数据技术、智能技术和移动技术,它带来的是即时交互传播。从近25年的媒体实践来看,新闻业的数字化过程主要走过了以下三个阶段:首先是“网络化”——媒体通过数字技术接入互联网,实现了信息与信息的联接;其后是“数据化”——媒体通过数据化建设不断丰富内容(比如将媒体的历史数据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结构化处理建设成数据库);再者是“云端化”——媒体建设“数据云”并进行“开源”,打开数据的接入和输出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并从共享中迅速增加数据的容量和链接。
“数字新闻业”催生了“数字新闻学”。新型新闻实践和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呼唤着数字新闻学的飞速发展(Waisbord, 2019)。数字革命以多种方式改变了新闻业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数字化带来了速度、创新、复杂性、社交性、联通性、可存储性、可搜索性,尤其是新闻业的灵活性(Duffy & Ang, 2019)。
数字时代新闻业在多方面发生了堪称“质”的变化。首先,数字媒体革命使众多新行动者参与了信息生产和发布的过程。公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运作工具、可以制作“自媒体”,参与信息生产、流动的过程,通过博客、各类社交平台等创作内容、报告信息、评论时事。这些“媒体”的技术基础是Web2.0。Web2.0时代网络新闻和网络媒体发生了诸多变化:非专业人员在新闻生产领域的深层渗透,网络新闻内容结构的变革,网络新闻生产专业分工的细化与合作模式的多样化,以及网络受众新闻消费模式的多元化与社会化(陈昌凤,常江,2016)。博客及其之后变迁的新形态——尤其是移动化技术带来的新形态,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接受者或二者兼之。每个人在合法范围内可以自己决定传播的频率、内容的多少。它打破了传统的传播模式,改变了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各环节特征,颠覆了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角色,而且冲击了大众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交互传播。尤为重要的改变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机器作为新的参与者,也加入了数字信息生产、分发、互动的队伍(张梦,陈昌凤,2021),自动化新闻成为数字新闻业的一个显要的发展形态(Lewis, Guzman & Schmidt, 2019),除了新闻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的报道,社交媒体机器人、聊天机器人、推荐算法、预测算法,以及多种智能工具在新闻编辑部的运用,变革了新闻实践,也正在变革新闻业的属性(仇筠茜,陈昌凤,2018a)。
第二,数字革命带来了新闻业的结构性变革,催生了新型新闻业以替代传统媒体,媒体格局不再由传统的客观、独立的新闻业所独占(常江,何仁亿,2021)。最常见的替代性媒体是运用数字技术打造的平台型、终端型媒体,包括社交平台。它们通常并不生产专业性新闻,但是成为专业媒体的发布平台、公众的信息传播和获取的平台,比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平台也在做新闻。另一类是新闻记者个人创建的博客和网站,其中一些运作不再依赖专业媒体,而依赖基金会和公民的捐款。新技术使得众多新型媒体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向更广泛的用户提供信息生产和分发服务,催生了非常规类型的新闻业,比如非营利性的新闻业,而传统的新闻机构反而受制于经济困境(Ward, 2014)。数字化工具使得一些企业有机会聘请记者做“品牌新闻业”,甚至使“党派新闻业”在西方重现,同时着眼于某些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新闻网站开始泛滥(Meyers, 2020)。
第三,数字革命促进了全球互联(Ess, 2017)。在数字时代,新闻媒体的内容、覆盖范围和影响力已经走向全球化(Ward, 2014)。在内容方面,新闻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全球性问题和事件;就覆盖面而言,媒体现在能够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生产面向全球受众的报道和故事;就影响而言,由于新闻媒体现在已遍布全球,它们所生产的故事也具有超越国界的影响(Ward, 2016)。
上述三方面的变革,对传统新闻专业伦理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新闻伦理关系中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三方面均发生变革,新闻伦理适用范围正在扩张,以及新闻伦理观念与方法在元规范(protonorm)层面需要重新审视。事实上,支撑传统新闻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框架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逐渐失效,真实、客观、专业主义等新闻学元话语(meta-discourse)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实践者、研究者和用户的质疑,这导致新闻研究出现了“对象发生本质变化”的危机(常江,2020)。下面我们将从前数字化时代新闻业(pre-digital journalism)的伦理观入手,探讨数字时代需要的新闻伦理观。
二、前数字化时代新闻伦理的变迁:以西方为例
在新闻伦理规范中,基本原则体现了核心价值观,是新闻传播者在调整职业活动中各种利益关系时必须遵循的“第一把标尺”。应当强调的是,新闻伦理、媒介伦理通常与新闻传播功能密切相关。因此,新闻伦理原则很可能随着媒体体系的转向而有所改变,也很可能随着新闻业不同时期的变迁而发生变革。新闻传播伦理的基本原则,最先奉行的是新闻自由的原则,该原则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提出、在夺取政权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后确立的(黄瑚,2011)。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逐渐被社会责任思想所取代(斯拉姆等,1980;新闻自由委员会,2004),社会责任论发展成为西方新闻传播伦理的基本原则。在数字新技术运用于新闻业的时代,在伦理迭代过程中,之前的伦理原则依然发挥着作用。比如有学者分析了欧洲多个国家的新闻伦理守则,发现新闻自由仍被视为核心价值(Hafez, 2002)。
关于西方新闻伦理的变迁,学者沃德(Ward)提供了一个分析性的研究,用以说明新闻伦理规范的路径、主要原则是如何随着新闻业功能的变化而发展的。沃德特别强调了西方在自由主义理论兴起时期,新闻业引入了“看门狗”功能,确立了新闻媒体的独立和自由等原则;之后在商业化大众媒体的发展中引发对不受监管的新闻界的一系列担忧的背景下,客观性原则上升为新闻伦理的主要理想;再后来,由于解释主义和行动主义新闻的复兴,以及新技术的兴盛,对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后现代怀疑论兴起,传统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开始走下坡路(迈克尔·舒德森,李思雪,2021)。
在实践中,多个国家和地区、众多新闻业界组织和媒体都制订了各自的新闻伦理守则,这些制度化文本体现着新闻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著名媒介伦理学者克里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与其合作者认为,新闻守则作为新闻从业者的一种自我反思的工具具有重要价值,它帮助新闻从业者了解其工作的本质,并将其实践与更广泛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联系起来(Christians & Nordenstreng,2004;克里斯琴斯,2014)。
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SPJ)是美国成立最早的覆盖较广的新闻专业组织,于1926年公布了其新闻从业者行为准则。该准则经过多次修订,如今被该组织在网上列出的修订有4次——包括20世纪20年代、7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时间上大致契合沃德所论述的新闻业功能变迁,其中前两次可以被视为前数字化时代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守则的代表。1926年SPJ确立的新闻专业工作标准(canons)包括六个方面: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实、真实与准确,公正、平等对待,庄重。1973年修订的《伦理守则》(Code of Ethics)在前言中强调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服务于真相,六个方面更新为:责任,新闻自由,伦理,准确与客观,平等对待,守诺。从中可以看出,在前数字化时代,新闻界确立的职业守则,作为一套专业性的话语,数十年中并无本质的变化,均包括“新闻自由”这一伦理原则,均强调了新闻活动中的义务伦理(责任,准确,真实与客观,平等对待)、新闻工作者的美德伦理(独立,诚实,庄重与守诺),但是其中一些话语在式微,较明显的是兴起于大众报业时期、20世纪初即被纳入规范的“客观性”,经过数十年的新闻实践,逐渐从新闻伦理规范中淡出。
但是,进入数字新闻业时代,有关新闻伦理规范、原则类型的争论日益激烈,反映了当今转型中的新闻伦理的复杂性。其中一些问题有待全方位地思考,诸如:数字化改变了新闻业的本质,那么谁可以被称为新闻工作者(Knight, Geuze & Gerlis, 2008)?什么样的内容生产和分发才可以被称为新闻业?非专业的新闻报道者是否应遵守与专业记者相同的伦理规范和守则(Ward, 2014)?
三、数字时代新闻伦理面临的挑战
数字革命引发了新闻伦理的一系列新问题(Ward & Wasserman, 2010)。上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开始广泛运用于新闻业后,带来前述三个结构性的重要变革,催生了传统新闻伦理的深层挑战:被赋权的公众成为传播主体,即原先新闻伦理关系中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替代性媒体出现,即原先新闻伦理关系中的客体也发生了变化;相应的,新闻伦理关系中的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全球化传播成为潮流,意味着需要适用更广大范围的新闻伦理。如此大的变革,又促使我们要审视既有新闻伦理观念与方法—— 一种元规范层面的深省或建构。
第一,数字技术对公众的赋权,催生了大量的“非专业传播者”,使得原先对训练有素的专业从业者所确立的新闻伦理规范难以发挥作用。新闻伦理关系中的主体变成了“乌合之众”,“非专业传播者”对媒介规范和伦理的认识水平远难比肩专业从业者。大众参与了信息生产和发布,造就了一种新的传播形态,被卡斯特称作“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Castells, 2007)。大众通过博客、微博以及维基百科等技术产品,能够以“我”为中心生产信息和内容,并且通过网站实现数字内容的传播和共享,它既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征——因为全球网民都可能成为某一信息的潜在受众;又是一种“自传播”——内容自主生产(self-generated in content)、接收自主选择(self-selected in reception)、发布自主导向(self-directed in emission)。由此大众传播时代的伦理规范受到挑战。传统的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媒体机构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缩小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节点,记者也成为空前扩大的传播网络中的一小部分(Bardoel, 2005)。非专业的一般公众对媒介规范和伦理的认识水平较低,几乎未受任何专业训练的公众成为人际互动网络中的众多节点(陈昌凤,王宇琦,2016)。大众为主体的社交媒体还原了人际交流模式,将信息的传播嵌入关系网络,实现了“次生口语文化”(second orality),强调具体的情景、移情、参与以及日常生活的体验等,因此信息的客观性也受到明显的影响(翁,2008)。
第二,替代性媒体带来了更多复杂的伦理问题。过去传统媒体时代一套伦理规范即能大致确立的伦理标准,已经不适合数字时代复杂的新闻伦理关系中的客体——它们不再是有共同宗旨目标、有相近专业文化认同的专业媒体。最典型的替代性媒体是社交媒体,它们传播了丰富繁杂的信息,并且在公众中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但是新闻伦理对它们并没有约束力(黄雅兰,陈昌凤,2013)。它们还时常被用以发布虚假信息、偏向信息、仇恨或有失庄重的信息。它们成为信息发布的重要平台,并加剧了信息发布时效竞争,也使得专业记者传播谣言、不准确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可能性增加;它们也已经成为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获取新闻和信息的重要平台,挑战着对新闻业至关重要的验证和事实核实过程(Hermida, 2012)。
第三,数字技术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上媒介伦理的开放性特征,使得全球化语境下的受众组成更加复杂。他们可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的多元化背景使得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媒介伦理核心价值观——即伦理原则可能有所不同,对传播与媒介规范的理解也相异。一些传统的媒介伦理规范因此受到挑战,如客观、公正等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解读。
四、数字时代新闻伦理的纾困方案
首先需要说明,尽管新闻伦理规范滞后于数字新闻实践,但传统媒体时代的某些价值观念在数字时代的新闻业中仍有需要,亦即颠覆和重构中的并非价值观,而是维护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有学者研究了世界多国的新闻伦理准则,发现所关注的99种新闻职业守则中,只有9种包含了对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规范内容,尽管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在21世纪编写或修订的。这一方面说明目前伦理规范的滞后,另一方面,这些多数来自西方国家的涉及数字时代的规则表明,传统新闻业的一般原则(价值观)仍适用于数字新闻业,即“在线媒体享有相同的权利,并且必须遵守与传统媒体一样的规范、承担责任”(Diaz-Campo & Segado-Boj, 2015)。
第一,面对数字时代新闻伦理关系中主体多元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一个将媒介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考虑在内的媒介伦理(Couldry, 2010)。沃德等学者开始倡导“开放的媒介伦理”(open media ethics)和“全球化的第五等级”(a global fifth estate),以此打破“传播者—受众”的二元划分,强调公众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Ward, 2010)。传统的媒介伦理并没有考虑受众,公众在传播中的角色未得到重视,媒介伦理是封闭的,仅仅关乎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人。数字时代的媒介伦理则需要与所有传播流言、事实和观点的人相关。传播的内容和规范不再掌握在少数职业媒体手中,一般的网民也能够而且应该在规范的制定过程中有所参与,从而形成一个所谓“第五等级”,它是对西方所谓“第四等级”——主流媒体的补充。开放的媒介伦理着眼于数字时代受众身份的转变,以一种尚不严密的逻辑试图解决非专业的社会大众成为传播主体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在实践方面,各类自媒体平台所制订的伦理规范,便是主体面向大众的规范,如社交平台不断更新其使用规则,如Facebook、Twitter和微博等平台,不断完善其规则,其中不乏用户使用的伦理规范。
第二,数字时代新闻伦理关系中替代性媒体广受质疑,开放的伦理观正在成为实践应对的模式。专业媒体为了应对替代性媒体的挑战,已经意识到制订新规范来约束其从业者对替代性媒体使用的重要性。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自2008年以来纷纷制订社交媒体使用规则,英国的《卫报》、BBC等也相继在2010年和2011年出台了社交媒体使用指南。比如关于信息源的规范,美联社等作出规定:不能简单罗列来自社交网站的引语、图片或视频,绝不能把个人网页上的姓名和发现材料的网址作为引用的出处。若要在报道中使用照片、视频或其他多媒体内容,必须先验证其真实性;社交网站上的虚拟账号猖獗,要注意核实。美联社还规定不准在社交网站上抢发新闻(Associated Press, 2011)。美联社在2012年以前已经修订了三次《社交媒体使用手册》。在这些规范中,都强调维护媒体声誉和利益的重要性,要求公私分明,社交媒体的工作账号和私人账号要分开,要求内外有别,不能透露公司内部信息泄露公司秘密,对于社交网站发起的“运动”要保持警惕、持客观中立的立场等等。路透社要求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能始终保持专业姿态,要遵循准确、不偏袒、真实的规范。BBC、《洛杉矶时报》都要求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须注重真实性。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其伦理与价值委员会在研究了美国主流媒体中已有的社交媒体使用指南后,于2011年5月发布了《针对社交媒体的十条最佳行动指南》,其中包括:传统的媒介伦理观仍然适合网上活动,对于通过社交媒体获得的消息记者一定要进行核实(陈昌凤,王丹薇,2012)。
第三,关于数字时代全球化语境下新闻伦理适用范围扩张的问题,学界也在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是克里斯琴斯的“全球媒介伦理”(global media ethics)理论 ,也被称作普世媒介伦理(universal media ethics)。克里斯琴斯对数字时代的媒介伦理作了多角度的思考,集中于三个方面:后现代社会转型、伦理的哲学基础的转变,以及传播技术的演化。其一,在后现代社会中,孕育了印刷媒介的现代性正在消解,伦理的理性主义正在被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取代。其二,印刷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建立在以理性和逻辑为特征的启蒙认识论基础上,一旦这种认识论受到质疑,那么相应的媒介伦理也将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此应当将伦理建立在更加牢固的本体论基础上(Christians, 2010)。其三,数字传播技术使得当今的媒体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全球化,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为媒介从业者提供共同行为准则和对媒体认识全球化的媒介伦理。全球媒介伦理理论确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国际化的、跨文化的、具有性别包容性的、种族多元的媒介理论”(Christians, 2008)。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融合观点(Wasserman & Rao, 2008),强调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种族和性别差异的、对于传播的所有参与者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媒介伦理观(陈昌凤,王宇琦,2016)。沃德也在其对于开放的媒介伦理的论述中提出,应当允许一些情绪化的、甚至非理性的关于伦理规范的争论,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会引起人们对一些媒介伦理核心价值理解的差异(Ward, 2010)。目前在回应全球化语境下的伦理方面,实践性规范还较少。
在实践伦理方面,一些伦理规范也对数字技术的挑战进行了呼应。如SPJ在1996年修订的《伦理守则》包括四大方面:寻求真相并报道之、最小伤害、独立行事与负责。首次加入“最小伤害”这样契合数字时代人文关怀的规范。近年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自动化新闻业的出现也引发了伦理的讨论,其核心问题包括:提升用于训练算法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Dorr & Hollnbuchner, 2016);要重视算法设计者或用于训练算法的数据自身的偏见可能导致的偏见和歧视(Mittelstadt et al., 2016);需重视算法的不透明问题(仇筠茜,陈昌凤,2018b)、问责制问题(Mittelstadt et al., 2016);对于个体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挑战(Dorr & Hollnbuchner, 2016)。为了回应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在最新修订的SPJ《伦理守则》(2014)中,新增了“透明度”的伦理规范。
五、数字时代新闻伦理的建构路径与“元规范”
如何建构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仅从结构和个性化角度加以讨论。
从结构的角度探讨数字时代新闻伦理的建构问题,主要是关于“分散”(fragmentation)与“整合”(integration)的观点。分散主义者主张对于新闻业的主要目标、标准和准则应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分散主义者怀疑统一的新闻伦理的可能性(Ward, 2014),因为每个记者都根据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开展工作(Ward, 2016)。整合主义的观点主张记者可以跨平台和跨文化共享一些目标、价值观和原则,这些目标、价值观和原则的统一也是必要的。整合主义路径承认共享规范和原则的多样性和差异的重要性,通过整合的方法寻求差异中的统一、提倡将统一性和多样性视为恒久的新闻伦理(Ward, 2016;Ward, 2014)。相似的观点还包括有学者倡导伦理多元性、承认关于伦理规范和实践的观点的多样性,因为它们与某些共享的标准和价值观有关(Ess, 2017)。有学者认为,要使新闻伦理框架在数字时代取得成功,它必须同时具备稳定性和灵活性(Fairfield & Shtein, 2014)。分散主义观点其实过于自由主义和理想化,也是建基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将记者视为理性主义行动者,将新闻业生态视作理想的专业化生态,明显缺乏现实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整合主义路径体现了一种较为全面的伦理观念,但是如何落实于实践中,则取决于新闻业界的行动自觉。
个性化的角度实际上是从数字化或去人格化的角度,提供了数字时代新闻伦理的另一种建构框架。对新闻伦理采取去个性化的方法,意味着使用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的所有新闻工作者的伦理框架。同前数字时代一样,基于此观点制订的伦理守则也因此与平台和文化无关(Ward, 2014; Ward, 2016)。这种方法就是制订常规的伦理守则、职业道德准则,例如SPJ(2014)的伦理守则,以及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IFJ)的《全球新闻工作者伦理宪章》(2019),内容分别写有类似“协会宣布这四项原则为新闻事业的伦理基础,并鼓励所有媒体在所有人的实践中使用这四项原则”、“此国际宣言规定了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研究、编辑、传播和评论中的行为准则……”等等。相较而言,个性化的方法可使每个新闻工作者或媒体组织建构自己的自定义伦理准则(Ward, 2014),同时为不同的记者和媒体组织采取一些共同的、普遍认可的一般原则而提供共同基础和整合的空间。在线新闻协会(Online News Association, ONA)的“建立自己的伦理规范”项目可能是个性化新闻伦理规范中最受欢迎的实用示例之一。该项目采用所谓的DIY(自己动手)伦理规范,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提供了自主权和灵活性,可以创建满足其需求的伦理规范”。用户在特定平台上创建账户后,将被要求查看并接受某些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是特定新闻伦理规范的基础;然后用户被要求选定他们实践的新闻类型(客观型与观点型),其余部分包括根据用户的工作来确定要添加到代码中的其他原则。这项工作通过与平台上提供的45个模块进行互动完成的,这些模块为用户选择的特定伦理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点。这是面向记者的一种有益尝试,对将公众作为媒介伦理主体也有借鉴意义,有必要进行公益化的推广和行动。
数字时代新闻现象纷繁多元,并且背后的逻辑错综复杂,因而试图对一个个现象进行规范是难以产生实质性作用的。我们需要一种伦理思想的指引,亦即“元规范”的规范。著名学者克里斯琴斯为此提出将“生命的神圣性”(sacredness of life)作为伦理的元规范(protonorm),即把生命本身的存在、尊严和神圣性作为伦理的根本原则,这样就能够赋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全球伦理以普遍性(universal)和内在性(intrinsic)(Christians, 2010),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真实、人的尊严和非暴力作为媒介伦理规范。克里斯琴斯致力于建立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的统一的媒介伦理原则的框架,其框架与西方前数字化时代新闻伦理所基于的专制主义者框架不同,他的方法承认存在多元观点——尤其是在文化层面。他的观点与上述分散主义者不同,是利用不同伦理观之间存在的共性,来整合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媒介伦理。有一点是学界普遍认可的,即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更复杂;而一种新的、首要基于伦理话语的专业主义,正在数字技术的冲击和“刺激”下不断成形(常江,2019)。■
参考文献:
常江(2019)。规范重组: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体系建构。《新闻记者》,(8),37-45。
常江(2020)。数字新闻学:一种理论体系的想象与建构。《新闻记者》,(2),12-31。
常江,何仁亿(2021)。客观性的消亡与数字新闻专业主义想象:以美国大选为个案。《新闻界》,(2),26-33。
陈昌凤(2016)。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再读《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新闻春秋》,(3),4-13。
陈昌凤,王丹薇(2012)。社会性媒体时代传媒如何自律?《新闻界》,(12),3-5。
陈昌凤,王宇琦(2016)。公众生产信息时代的新闻真实性研究。《新闻与写作》,(1),48-52。
仇筠茜,陈昌凤(2018a)。黑箱: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格局嬗变,《新闻界》,(1),28-34。
仇筠茜,陈昌凤(2018b)。基于人工智能与算法新闻透明度的“黑箱”打开方式选择。《郑州大学学报》,(9),84-88。
黄瑚编著(2011)。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实用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雅兰,陈昌凤(2013)。自由的困境:社交媒体与性别暴力。《新闻界》,(12),58-61。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2014)。《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孙有中、郭石磊、范雪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迈克尔·舒德森,李思雪(2021)。新闻专业主义的伟大重塑:从客观性1.0到客观性2.0。《新闻界》,(2),4-12。
万俊人(1990)。《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韦尔伯·斯拉姆(1980)。《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沃尔特·翁(2008)。《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闻自由委员会(2004)。《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梦,陈昌凤(2021)。智媒研究综述: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应用及其伦理反思。《全球传媒学刊》,(1),63-92。
Associated Press. (2011). Social Media Guidelines for AP EmployeesRetrieved April 102021from https://www. ap. org/assets/documents/social-media-guidelines_tcm28-9832. pdf.
Bardoel, J. (2005). Beyond Journalism: A Profession Betwee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Sage.
CastellsM. (2007). Communication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238-266.
ChristiansC. G. (2019). Media Ethics and Global Justice in the Digital A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ristiansC. & Nordenstreng, K. (2004). Social Responsibility Worldwid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1)3-28.
ChristiansC. G. , RaoS. , Ward, S. J. & WassermanH. (2008). Toward a global media ethic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cquid Novi, 29(2)135-172.
ChristiansC. G. (2010). The ethics of universal being. In Ward, . S. J. A. & Wasserman. H. (eds. ) Media ethics beyond bord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Routledge6-23.
Couldry, N. (2010). Media ethics: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media producers and media consumers. In Ward, . S. J. A. & Wasserman. H. (eds. ) Media ethics beyond bord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Routledge59-72.
Díaz-Campo, J. & Segado-Boj, F. (2015). Journalism ethics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How journalistic codes of ethics have been adapted to the Internet and ICT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32(4)735-744.
DorrK. N. & Hollnbuchner, K. (2017). Ethical challenges of algorithmic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5(4)404-419.
Duffy, A. & AngP. H. (2019). Digital journalism: Definedrefinedor re-defined. Digital Journalism, 7(3)378-385.
Ess, C. (2017). Digital media Ethic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Retrieved April 42021from https://oxfordre. com/communication/view/10. 1093/acrefore/9780190228613. 001. 0001/acrefore-9780190228613-e-508.
Fairfield, J. & Shtein, H. (2014). Big Data, Big Problems: Emerging Issues in the Ethics of Data Science and Jour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9(1)38-51.
García-Avilés, J. A. (2014). Online Newsrooms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Exploring Digital Journalists’ Applied Ethic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9(4)258-272.
Hafez, K. (2002). Journalism Ethics Revisited: A Comparison of Ethics Codes in Europe,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Muslim As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19(2)225-250.
Hermida, A. (2012). Tweets and truth: Journalism as a discipline of collaborative verifica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6(5-6)659-668.
KnightA. , GeuzeC. & Gerlis, A. (2008). Who is a journalist. Journalism Studies9(1)117-131.
Lewis, S. C. , Guzman, A. L. & SchmidtT. R. (2019). Automation, journalism, and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of humans and machines in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7(4)409-427.
MeyersC. (2019). Partisan News, the Myth of Objectivityand the Standards of Responsible Journalism 1. In Media Ethics, Free Speech,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219-239.
Mittelstadt, B. D. , Allo, P. , Taddeo, M. , WachterS. & FloridiL. (2016). The ethics of algorithms: Mapping the debate. Big Data & Society3(2)https://doi. org/10. 1177/2053951716679679.
MoyoL. (2015) Digital age as ethical maze: citizen journalism ethics during crises in Zimbabwe and South Africa, 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36(4)125-144.
Scott, B. (2005).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Digital Journalism. Television & New Media6(1)89-126.
SPJ (2014). SPJ Code of Ethics.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Retrieved April 102021from https://www. spj. org/ethicscode. asp.
WaisbordS. (2019). The 5Ws and 1H of Digital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7(3)351-358.
WardK. (2018). Social networks,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Kantian ethics: apply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o Cambridge Analytica’s behavioral microtargeting.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33(3)133-148.
WardStephen J. A. (2016). Digital journalism ethics.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164-178.
WardStephen J. A. & WassermanH. (2010). Towards an Open Ethics: Implications of New Media Platforms for Global Ethics Discours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5(4)275-292.
WardStephen J. A. (2010). Journalism ethics. Retrieved April 22021from https://www. supportuw. org/wp-content/uploads/wwa_2010_ward_journalism. pdf.
WardStephen J. A. (2014) Radical Media Ethics, Digital Journalism, 2(4)455-471.
Wasserman, H. & RaoS. (2008). The glocalization of journalism ethics. Journalism, 9(2)163-181.
陈昌凤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雅畅帕(Ayamou Chekam Gaelle Patricia)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项目编号:18ZDA307)的阶段性成果和“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