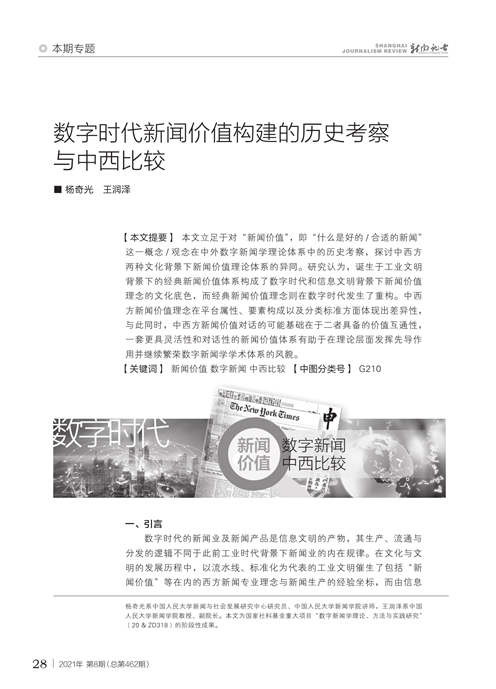数字时代新闻价值构建的历史考察与中西比较
■杨奇光 王润泽
【本文提要】本文立足于对“新闻价值”,即“什么是好的/合适的新闻”这一概念/观念在中外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中的历史考察,探讨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下新闻价值理论体系的异同。研究认为,诞生于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经典新闻价值体系构成了数字时代和信息文明背景下新闻价值理念的文化底色,而经典新闻价值理念则在数字时代发生了重构。中西方新闻价值理念在平台属性、要素构成以及分类标准方面体现出差异性,与此同时,中西方新闻价值对话的可能基础在于二者具备的价值互通性,一套更具灵活性和对话性的新闻价值体系有助于在理论层面发挥先导作用并继续繁荣数字新闻学学术体系的风貌。
【关键词】新闻价值 数字新闻 中西比较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及新闻产品是信息文明的产物,其生产、流通与分发的逻辑不同于此前工业时代背景下新闻业的内在规律。在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以流水线、标准化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催生了包括“新闻价值”等在内的西方新闻专业理念与新闻生产的经验坐标,而由信息技术所形塑的数字文化则一方面继承了工业文化中有关新闻价值体系的理念脉络,另一方面又对经典理论不断进行着反拨、调适甚至重构。
自19世纪西方新闻业对中国古老的交流观念体系产生冲击以来,中西方新闻学之间产生了多样的互动关系,也形成了较为复杂与多变的问题,中西新闻比较建构的是一种比较方法论体系(单波,2013)。在“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中西方新闻业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越来越频繁,作为信息文明与数字文明产物的数字新闻则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对于新闻学核心问题、关键概念与重大议题的关切,包括如何重新界定新闻(Carlson, 2017:13;常江,田浩,2021),以及如何想象和设计新的新闻学理论体系(Steensen et al., 2019;常江,2020)。关于“什么是新闻”这一问题的追问在数字新闻时代依旧具有重要意义(Harcup & O’Neill,2017)。在数字时代,由英美等国家创设的经典新闻学理论体系在数字新闻业快速变革的业务实践中受到了一定冲击,与此同时,包括中国等在内非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观点也为中西新闻对话增添了新的经验材料。总体来看,饱受争议的新闻价值及其构成体系迎来了理念调适、观念更新和理论重构的新契机,同时这也为中西方新闻的学术对话以及夯实新闻学在数字文明背景下的合法性根基创造了历史机遇。
本文基于质化文献分析展开思辨性研究,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探究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形成背景与理论体系,立足于对“新闻价值”,即“什么是好的/合适的新闻”这一概念/观念在中外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中的历史考察,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新闻价值理论体系的异同。本研究不同于一般描述性的比较研究,而是重点基于新闻价值的历史演变过程,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在学理层面深入探讨数字时代中西方新闻价值体系建构的历史基础及其互通的可能空间。
二、新闻价值研究的学术脉络
新闻价值(news values或news worthiness)是体现新闻规范和新闻专业性的核心理念,是新闻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要素,其体现在新闻选择和“新闻判断”(journalistic judgement)的过程中并用来说明一般性的事实何以成为新闻(Gans, 2004:78;Motsaathebe, 2020)。与其说新闻价值反映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要和偏好,不如说新闻价值反映了新闻生态环境中复杂的经济因素、组织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文化因素(Pompper, 2021)。需要明确的是,“新闻价值”不同于“新闻的价值”,前者是指“以新闻为内容主体的价值取向”以及“新闻事实对于受众的作用和效用”(郑保卫,刘新利,2010),后者则是指“新闻对人的价值,对由人构成的社会的价值”(杨保军,2020)。
有关新闻价值的分类(亦表述为新闻价值要素的构成、新闻价值判断标准,以及新闻价值体系等)问题是研究者广泛探讨的核心议题。李普曼(Lippmann, 1922:159)较早提出了新闻价值分类的说法,但影响最为广泛的经典分类标准是由学者Galtung和Ruge(1965)首创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新闻价值的构成出现了五要素说、六要素说、十二要素说甚至二十要素说。21世纪以来,学者Harcup和O’Neill曾先后于2001年(主要针对传统报业)和2017年(针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两度通过实证研究对Galtung和Ruge提出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进行了评估和批判,并提出了更符合当前新闻实践需要的新闻价值分类标准体系(contemporary set of news values)。除上述两位学者外,Schultz(2007)等学者也对历史上经典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分类问题表达了批评意见并提出更为前沿的分类标准主张。然而,将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序列化”的做法潜藏着巨大风险,在Wahl-Jorgensen和Hanitzsch(2009;2019)主编的两版《新闻学研究手册》(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中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明。鉴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是不断变化的,因而机械地将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总结为“若干条”的形式会阻碍我们在变动的语境中“评估和理解什么是新闻”(O’Neill & Harcup, 2009)。在该书最新一版中,O’Neill和Harcup(2019)进一步指出,数字技术通过重塑“记者—用户(受众)”的关系扭转了既往新闻选择的过程,因此,不同新闻媒介平台上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需要进行细致区分。
相较新闻价值本身的分类及其标准,“谁”在贯彻和执行新闻价值的评判准则同样不可忽视。记者进行新闻选择和新闻价值判断的自主性程度取决于他们所供职媒体机构的类型及其自身在机构中的位阶。基于场域和社会资本等理论,学者Bourdieu和Wacquaint(1992:280)指出,记者的行为边界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不同层级的记者和编辑享有不同的编辑权利,具有更大话语权的记者和编辑在新闻选择、新闻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也有更大的决定权。在新闻选择的过程中还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突发因素的干扰,这可能导致业已确定刊登的新闻稿件被临时撤下,也可能会使已经被放弃的新闻内容再次被使用。前人研究提醒我们,新闻价值的判断体系从诞生之时起便充满着易变性,且这种易变性对数字新闻生产依旧产生着实际的影响。
近年来,中西方学术界有关新闻价值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1)关注记者为何选择某一具体事件进行报道(而非其他事件),此类研究主要根据新闻内容的属性(如正面新闻或负面新闻)探究其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学者Shoemaker(1996)曾指出,“坏事儿”(bad news)天然就具有新闻价值,这是由于人们的生理本能就是倾向于找寻环境中的潜在威胁;学者Gans(2004)也指出,负面新闻的内容通常涉及揭露政府或企业的腐败行为,而这也正是民主社会中新闻行业理应发挥监督功能的表现——新闻记者“看门狗”(watchdog)的角色是被广泛接受并深深嵌入在新闻业自身的文化范畴之中的。与“坏事儿”相反的是“好事儿”(good news),Hartung和Stone(1980)将“好事儿”型新闻定义为“大多数当地报纸的读者都会对事件的发生感到满意或感到高兴的事件”,这些新闻故事的价值取向通常是积极或乐观的。
(2)聚焦可能影响新闻价值判断的组织、文化、技术和经济等因素。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保持的惯习、为了争取独家新闻而采取的竞争策略、媒体所有者和广告主的影响,以及新闻从业者对于自身职业角色的期待等因素均会影响新闻价值判断的过程(Harcup & O’Neill, 2017;Schultz, 2007)。例如,在技术层面,当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在欧美国家逐渐普及时,多数研究者认为电视新闻不过是广播新闻的一种“视觉形式”(Jacob, 1954)而已,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而言,其并不会因为技术的变革和媒介载体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这是由于研究者们认为新闻价值具有超越一般技术平台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学术界甚至发出警告——诸如电视等新技术的出现会违背既有的新闻价值判断体系。
(3)基于前人学术研究成果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体系做出总结、归纳以及反思,这也是国内学者常采取的一种研究思路。黄旦(1995:166)认为西方经典新闻价值中的“时新性”无疑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脱离了“时新性”其余四种要素即便都具备也不能称之为新闻;王润泽、张凌霄(2019)从新闻实践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新闻价值的西方话语生产路径并反思了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西方学者Caple和Bednarek(2016)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总结了新闻从业者的不同话语实践并从中归纳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
尽管上述涉及新闻价值的研究历久不衰,但多数研究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聚焦于特定新闻媒体或议题,难以对新闻价值的学理逻辑做出整体性解读,基于中西比较视角的学理性研究则更为少见。新闻价值取决于赋予它们价值的特定社会文化体系,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评估新闻价值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Bednarek & Caple, 2017:51)。对于中西方新闻业关于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性而言,其“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张斌,张昆,2011)。单波(2015)更加明确地指出,在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化”与“去西方化”是交织演绎的两种文化心态。然而,基于中西方比较视角的研究又多建立在对新闻文本具体内容的考察之上,目前较少有学者对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开展历史性的和体系化的中西比较式研究,这不利于促进中国与西方在数字新闻学领域的学术对话。
三、数字时代中西方新闻价值的体系建构与内涵比较
从新闻实践的历史经验来看,新闻价值的确立不是新闻行业发展进程中一蹴而就的产物,而是与媒介技术革新、新闻产品的创新,以及整个新闻产业规模扩大相伴生的结果。在西方手抄新闻时代,以威尼斯手抄小报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业以能否满足手工业者以及航运市场的信息需求等为主要价值判断准则。而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脉络看来,经典意义上的新闻价值是在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印刷时代才被广泛讨论和接受的(王润泽,张凌霄,2019)。数字时代,新闻的内容与生产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从一个工业社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物逐步进化为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生产结果——新闻开始成为一种产品,其不再仅是代表着某一媒体的品牌,而更关注作为产品的质量以及用户的真实需求,新闻业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变对中西方新闻价值的体系构成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形成背景与体系建构
在探究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之前,我们有必要重回工业时代厘清新闻价值这一本身便带有大工业生产烙印的理念是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兴起、确立,并对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产生影响的。19世纪以来,滚筒印刷机、轮转印刷机的使用促使报纸的产量和规模显著提升,与此同时,西方报业经历了从“党报”向“商报”的转型,廉价报纸发行量的扩大以及对于读者群体的竞争促使西方新闻业进一步将新闻选择的过程标准化。新闻是工业生产线上标准化、流程化的一种商品,新闻价值的确立则有助于推动新闻生产效率的提升,这直接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新闻业对于新闻价值各类“要素说”的理论阐释。
对于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而言,学者Brighton和Foy(2007:29)较早指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因媒介形态而异,包括“关联性”(relevance)、“话题性”(topicality)、“组合性”(composition)、“期望性”(expectation)、“不寻常性”(unusualness)以及“外部影响性”(external influences)等要素,应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体系的构成部分。学者McIntyre(2016)则认为,包括“人类兴趣”(human interest)、“娱乐性”(entertainment)等在内的常见的、宽泛的新闻价值标准应该进行细分和再定义,从而更好适应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判断的标准。在实证研究层面,学者McIntyre(2016)分析了美国主要登载正面新闻的网站(例如Good News Network、Happy News、Daryn Kagan、Odewire以及Huff Post Good News等),这些网站上的新闻报道基本都着重强调经典新闻价值理论中的娱乐价值(entertainment)和情感价值(emotional impact),报道内容往往与人们的善良行为或英雄行为相关。其中,视频类新闻常通过大量呈现儿童或是宠物的视觉形象来唤起受众的情感,这与传统媒体侧重负面新闻的价值取向构成了较大不同。
新闻价值判断产生的逻辑起点发生在记者、编辑决定在版面上发表何种内容的时刻,在这一决策的过程中,作为“把关人”(gatekeeper)的新闻从业者们有意无意地在找寻符合新闻定义的价值要素(White, 1950)。新闻价值判断的过程亦是新闻选择的过程,“把关人”们基于共同的标准对新闻内容进行评估和取舍,同时预测何种新闻价值取向的新闻报道能够引发公众兴趣(Shoemaker & Reese,2014)。在受众层面,新闻价值的判断是“通常人性的选择标准”(general human selection criteria)的一部分,因此新闻价值的判断本质上符合人类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模糊的,因此近年来数字新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致力于将经验式的回答理论化为学理性的体系。数字时代新闻价值体系的构建主要是在批判和重构经典新闻价值理论体系的层面展开,不同学者提出了适应数字时代新闻学生态的价值体系框架。学者Shoemaker和Reese(2014)较早对经典新闻价值体系进行反思,之后学者Harcup和O’Neill(2017)基于当今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重访了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新闻价值要素体系并对其进行了修正,其中特别强调了社交媒体对于经典新闻价值要素的冲击。在微观论证层面,García-Perdomo(2020)以实证研究方法探究了什么样的新闻价值会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引发更多的受众关注,而持批判性立场的Pompper(2021)则质疑了数字时代背景下经典价值中的“时新性”要素。
总体上看,数字时代西方新闻价值的研究可以分为“本质”、“认知”、“社会”和“话语”四个维度(Makki, 2020),这四个维度构成了数字新闻价值的四种体系:“本质”立场的研究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报道内在、固有且独立于新闻记者之外的;“认知”立场强调新闻价值是新闻从业者和受众心理活动的一种结果;“社会”立场的持有者则认为新闻价值是媒体组织结构和日常生产关系的结果;“话语”立场则着重分析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话语实践的方式建构新闻价值。以“话语”立场为例,学者Bednarek和Caple(2017:51)以及Dahl和Flottum(2017)等人将新闻价值的生成逻辑借由语言符号的话语实践分析(简称DNVA:Discursive News Values Analysis)进行了系统解释,Caple和Bednarek等学者(2016)进一步对新闻从业者的话语实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认知的新闻价值观”(cognitive news values)这一概念,主要用以说明和解释数字时代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选择时的认知路径。
(二)数字时代中西方新闻价值的构建比较
诞生于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经典新闻价值体系本身便具有中西比较的可能性,其比较的结果则构成了数字时代和信息文明背景下中西方新闻价值理念的文化底色。在中国,以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和皇帝起居等为主要内容的古代邸报,在新闻选择上突出了维护政治统治的价值取向。尽管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新闻业对于中国近代新闻的影响不可忽视,但真正决定中国近代新闻价值取向的还是中国文人和社会历来重视政治传播的文化传统。例如,徐宝璜(1919:18)对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就体现着中式文人的思维特点。他在《新闻学》中谈到:“新闻之价值云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顾为价值较高之新闻;再如,基于中国本土立场,潘公展(1929:5)也曾用五对关系——“事的关系”、“人的关系”、“时间的关系”、“地的关系”、“文的关系”来描述中国新闻业对于新闻选择和新闻价值判定的标准。
数字时代中西方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和构成体系既具有共性,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而言,中西方均注重冲突性和感官体验,中国更加注重借助基于平台属性特点的算法调节工具将公共价值纳入新闻价值判断的体系之中。
数字新闻强调新闻故事的娱乐价值以及情感价值,而包括《纽约时报》等在内的传统新闻内容强调的是新闻事件的冲突性,秉持传统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媒体机构多认为涉及政治丑闻、经济波动、社会冲突的新闻更具有新闻价值。与此同时,西方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与传统新闻价值的差异性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更为凸显,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选择会更加依赖目标受众的兴趣和喜好而非沿循传统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Tien Vu, 2014),“可分享性”(shareability)(Harcup & O’Neill, 2017; Hermida et al., 2012)和“可视听性”(audio-visuals)(Dick, 2014)等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重要构成要素。“不寻常性(unusualness)”“猎奇性”(singularity或novelty)(Bender et al., 2016:128)等以偏离正常情况作为新闻报道核心内容的做法,进一步体现出数字新闻价值判断呈现的新面向。从媒介使用习惯层面来看,受众在社交网络上点击、分享、点赞和评论是另一种传播新闻的形式,其对传统新闻价值观念构成了新的挑战(Tenenboim & Cohen, 2013)。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受众对窥视他人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解释了García-Perdomo(2018)等学者实证研究的结论——具有“人情味”(human interest)的新闻故事是迄今为止最受西方公众欢迎的数字新闻产品类型。除了“人情味”要素外,“实用性”(usefulness)也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新闻价值判断的新要素,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新闻机构倾向于频繁发布“Top10名单、榜单、技巧”等具有明显实用导向内容的原因。
对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价值判断而言,“推荐具有公共价值的信息”和“治理低质量信息”是同等重要的工作,因而对于平台运营者来说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需要善用智能算法(彭兰,2020)。同时,新闻价值的判断直接影响着新闻的体裁,“软话题(如娱乐和奇闻)+硬话题(如生活/社会)”的组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引发较多关注和转发,而单一领域的新闻报道(如体育报道)则会降低用户互动的频度。因此,数字时代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相当于是对用户兴趣的预测,对于新闻价值的精准把握和取舍有利于新闻媒体获取更多的受众注意力。然而,有关新闻价值的判断和决策过程却一直难以被语言描述成一套稳固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当一些记者被问及如何确定一件事情具有新闻价值时,记者的回答往往是“我一看就知道了”或是“因为它本来就有价值”的直觉式、经验式回答(Schultz, 2007)。尽管决策新闻价值的过程看起来是主观的,但中西方记者、编辑和其他从业者在实践中参照了一套灵活可变的新闻价值判断体系。
2.对于经典新闻价值要素而言,“时新性”、“接近性”等要素均被中西方所解构,中国新闻业更注重将是否具备沟通性和共情性作为新闻价值判断的依据。
在新闻产品社交化的语境下,传统新闻价值中的“时新性”和“接近性”等要素似乎并不会增加用户分享的可能性,最常见的以“时新性”为第一价值导向的新闻报道甚至会削减社交媒体用户互动的次数,片面追逐“时新性”还被认为是可能妨害权力平等的危险做法。例如,美国新闻媒体曾将一名不幸死亡的非洲裔美国女消防队员描述为“第一位”在通常由男性担任的工作中殉职的人,Pompper(2021)指出,将“第一位”作为新闻价值时新性的考量可能会加重全社会对于少数群体的污名化印象,因此经典新闻价值要素中的时新性要素应该引发新闻从业者的警惕。同理,在犯罪新闻报道中过分强调“冲突和戏剧性(conflict / drama)”可能导致新闻的煽情化结果(Cushion et al., 2017)。与之相似的是,中国学者也指出,数字新闻时代,“时新性”转向一种强调受众感官参与的“迫切性”,“接近性”理念中的“地理接近性”也在逐渐被消解。
基于数字时代的特点,自媒体平台上价值更加多元化,这也使得新闻价值的取向需要不断适应平台发展和变化。中国新闻业注重对自媒体平台上的新闻价值进行引导,其中“沟通性”与“共情性”成为新闻价值判断的首要考量。“沟通性”与“共情性”价值取向的形成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和”理念,以往以“真实”为价值诉求和操作准则的观念正在让位于以“沟通”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在认识和评价西方新闻价值理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土化的解读,20世纪20年代,邵飘萍曾对比分析了德国和英美在新闻价值取向的差异,他认为德国喜欢科学研究,因而德国报纸不如英美国家“喜读煽情挑发之纪事”(邵飘萍,1924 / 2008:156)。新中国成立后,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对于新闻价值的探讨较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闻媒体在调查性报道和监督报道的新闻生产实践中参与社会转型进程,一些媒体机构还通过组织评选新闻奖的方式来表明自身对于新闻价值判断的立场(Zeng, 2013)。研究表明,包含“人民公仆”、“爱国主义”、“自我奉献”、“敢于牺牲”等价值要素的新闻更易获得中国社会和公众的肯定。这也反映出中国新闻业的一种文化底色,特别是在面对互联网平台上信息的冲突与对抗时,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业以是否具有“沟通性”和“共情性”作为评判新闻是否有价值的依据,这将有助于消弭意见对抗带来的社会冲突。
3.西方对于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划分更为具体和细致,中国新闻价值的判断体系则更为宏阔且注重突出新闻价值判断促进社会治理的现实效用。
西方经典新闻学理论体系中有关新闻价值要素的划分出现了细致化特点。李普曼在《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将“耸人听闻性或煽情性”、“接近性”、“关联性”、“明确性”、“事实性”等属性描述为新闻价值。目前学术界认为最为经典的一种分类标准则是由学者Galtung和Ruge(1965)提出的——新闻价值具体包括“时新性”、“不寻常性”、“影响”、“接近性”、“显著性”、“冲突性”、“灾难性”。另根据Schultz(2007)的分类,有六种新闻价值要素最为重要——时新性、相关性、可辨识性、冲突性、情感性、独家性。
数字时代西方学术界对于新闻价值构成要素划分已经远远超越了既往的“五要素说”和“六要素说”等,学者Harcup和O’Neill将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归类为以下15个方面:(1)“排他性”(exclusivity):新闻机构通过采访、信件、调查、民意测验等方式获取独家新闻报道线索;(2)“负面性”(bad news):选择带有特别负面色彩的故事,例如死亡、受伤、失败和失业等;(3)“冲突性”(conflict):例如选择与争论、分裂、罢工、打架、叛乱和战争等有关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4)“惊喜性”(surprise):选择具有惊喜色彩或是不寻常色彩的新闻故事;(5)“视听性”(audio-visuals):选择引人注目的照片、视频、音频或其他可用于可视化的新闻素材;(6)“可分享性”(shareability):主要是指在新闻价值判断过程中优先考虑哪些内容更容易促使受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分享;(7)“娱乐性”(entertainment):挑选包含有性、娱乐、体育、动物、搞笑幽默等内容的新闻报道;(8)“戏剧性”(drama):指充满戏剧性的新闻报道文本,诸如弃车逃逸以及涉及逃跑、事故、营救和法庭案件的事件;(9)“可持续报道性”(follow-up):新闻内容有延展空间,具备可持续报道的可能;(10)“精英性”(the power elite):选择与有权势的个人、组织、机构相关的新闻事件;(11)“相关性”(relevance):类似于经典新闻价值要素中的“接近性”,具体指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与受众的生活经历或集体记忆相关;(12)“规模性”(magnitude):类似于经典新闻价值要素中的显著性,即与更大规模的受众群体相关或能引发显著关注的极端行为或现象;(13)“名人性”(celebrity):与名人相关的新闻故事;(14)“正面性”(good news):带有积极色彩的新闻,例如从灾难中复苏等;(15)“机构议程性”(news organization’s agenda):对于新闻价值的考量应符合新闻机构在意识形态、商业诉求或政治立场的议程设置需要。针对细分新闻类型,学者Cocking(2018)以旅游类新闻为例提出了适用于该类新闻价值要素的分类标准:(1)“魅力性”(appeal),(2)“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3)“可辨识性”(identification),(4)“积极性”(positivity),(5)“宾至如归性”(at home/out there),(6)“历史感”(history),(7)“时新性”(timeliness)。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政治新闻中涉及总统自身的新闻天然具有价值,因此美国媒体必须报道特朗普有关的新闻(Parks, 2020)。
尽管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呈现的面向与印刷时代有所不同,但是新闻价值的生成逻辑依然未脱离现代新闻业诞生的工业文明背景。不论是西方新闻业对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多样化、具体化的分类,还是对于某一些要素的强调,这一思维过程折射出数字新闻仍然对于规模效应和生产效率有着迫切的需求。目前中国学者对于数字新闻价值的分类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从文化层面指出,中国文人对言论权威的建构总是与“天下为公”的理念相联系(单波,2015)。在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研究方面,刘雯、黄宇鑫(2020)曾对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从以下四方面做出了判断——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转向;真实核查向“探轶”推断转向;空间接近向心理审判转向;个体体验向公共话语转向。总体来看,不论是中国学界还是业界,对于新闻价值的讨论仍旧以强调社会责任、注重社会效益为目的,能否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以及服务于国家发展为目标是中国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对于新闻价值判断秉持的重要标准。
四、中西方新闻价值在数字时代互通的可能性
不论是手抄新闻时代还是印刷新闻时代,东西方在新闻价值判断的问题上遵循了一定的相同逻辑思路——新闻价值的选择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工业时代的新闻价值是已然状态,体现着工业时代的文化价值,因此工业时代的新闻价值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结果的经验性总结。诞生于工业时代的新闻价值既是新闻业成熟之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而形成的“产品说明书”,同时也是对新闻行业合法性的解释乃至辩护的依据。对于中西方而言,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显著差异已被历史证明,但是数字时代的到来和正在进行中的信息技术革命则为未来中西方新闻价值的互通提供了可能空间,我们也仍旧可以根据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去推测或者去引领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毕竟新闻价值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的价值和人的价值而独立存在。
从中西比较和对话的立场出发,中西方新闻价值在数字时代互通存在可能性,这是因为,关于新闻价值本身及其分类的必要性得到了中西方学者们的认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诞生于工业文明背景之中的西方新闻价值理念对近代中国新闻业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延续至数字新闻时代。19世纪,西方新闻价值理念即已对中国新闻业构成了影响,以营利为目的的《申报》(1872)在《本馆告白》中即将新闻选择的标准描述为:“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有时西方报纸的新闻价值标准甚至直接成为中国报人办报办刊的行业圭臬,王韬(1874 / 2002:172)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就写道:“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中西方新闻业同样注重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以及围绕新闻价值开展学术研究,正如学者García-Perdomo(2018)等所指出的,对新闻价值开展类型划分与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数字技术背景下理解数字新闻生态的本质。数字时代,中西方学者关注经典新闻要素中的趣味性、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但也对“时新性”等理念进行了批判——西方新闻业主张将“时新性”调整为“实时性”,中国新闻业则强调“有抢有压”,对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的报道会做出延迟发布的考虑,而并非以“时新性”作为价值判断的首要标准。此外,崇尚“分享性”(shareability)亦成为中西方数字新闻价值判断的另一共识。“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不再是独家或者原创性新闻,而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以及转化转换数据的能力和水平”(黄旦,2015)。一些西方学者也指出,对于数字新闻而言,能否获得更多的点击量以及能否成功诱发用户的分享行为会影响新闻从业者的新闻选择和价值判断过程,追求点击量的背后则笼罩着浓厚的消费主义色彩(García-Perdomo et al., 2018; Marwick & Boyd, 2011),这使得新闻价值判断的过程受到广告经济效益的影响,换言之,能否获得流量变现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判断的最新要素之一。Hermida(2012)等学者在对加拿大社交媒体用户的分析中也发现,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新闻已经成为新闻体验的“核心价值”,数字时代的新闻受众不再从记者或新闻机构的社交媒体帐户上阅读新闻,而更可能从朋友和家人推荐的社交媒体链接上阅读新闻。从上述中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分享性”这一数字时代的新新闻价值判断标准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五、结论与讨论
新闻价值是中西方学术界历来关注的焦点性议题,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出发,“尽管中西新闻比较充满矛盾与困难,但它依然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思想动力”(单波,2015)。基于数字时代和信息文明的特点,在承认中西方新闻价值观念差异性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妨大胆设想,数字时代新媒介的出现使得中西新闻价值的对话有了更为便利的介质和清晰的路径,即便对于数字新闻价值体系的“设想”会是一项危险、尴尬甚至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中西方新闻价值对话的可能基础恰恰在于中西方新闻价值具有的互通性,而其更深层次的逻辑根源则在于文化的沟通、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上。
基于新闻价值这一理念在中西方社会中的历史流变,本研究认为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呈现出了中西差异,但也显现出了共识基础。新闻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不应、也不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新闻媒体的日常实践过程,但在数字新闻时代,基于新闻媒体机构自身不同的定位特点,一套更具灵活性、对话性和可塑性的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应该在理论层面发挥先导作用——数字时代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国家新闻与地方新闻、官方新闻与民间新闻等应该具有符合时代主旋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能够增益人类福祉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
当然,我们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现有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新闻从业者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新闻价值,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仍然严重依赖从业者的直觉思维,甚至还有不少学者直言对于新闻价值的任何分类都是徒劳的(Herscovitz, 1993; Harcup & O’Neill, 2017)。即便我们不能通过现有的学术研究总结出关于新闻价值如何判断的理论化准则,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关于新闻价值的持续性研究是没有价值的。必须重申的是,如前文所述,没有任何一种有关新闻价值要素的分类能够具有普遍适应性,不论是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新闻价值要素体系,还是信息文明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重构与调试,都将会产生持续性争议。囿于新闻生产过程中资源和时间的限制以及从业者自身主观的、无意识的影响,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亦将总是处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之中并映射出不同国家新闻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点。换言之,正是因为新闻价值争议性特点的存在,才使得新闻价值能够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议题并为繁荣数字新闻学学术体系的理论风貌提供可能空间。■
参考文献:
常江(2020)。数字新闻学:一种理论体系的想象与建构。《新闻记者》,(2),12-20+31。
常江,田浩(2021)。生态革命:可供性与“数字新闻”的再定义。《南京社会科学》,(5),109-117+127。
黄旦(1995)。《新闻传播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黄旦(2015)。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1),75-88。
刘雯,黄宇鑫(2020)。从个体困扰到公共议题: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标准的流变。《传媒》,(3),93-96。
潘公展(1929)。新闻概说。转引自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上海联合书店。
彭兰(2020)。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新闻界》,2020,(1),30-38。
单波(2013)。中西新闻比较的问题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9),33-49。
单波(2015)。中西新闻比较与认知中国新闻业的文化心态。《学术研究》,(1),32-40。
邵飘萍(1924/2008)。《邵飘萍新闻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申报(1872)。《本馆告白》。5月4日1版。
王润泽,张凌霄(2019)。新闻价值的西方生产路径与话语权的确立。《现代传播》,(11),42-46。
王韬(1874/2002)。《弢园文录外编(卷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徐宝璜(1919)。《新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
杨保军(2020)。论新闻的价值根源、构成序列和实现条件。《新闻记者》,(3),3-10。
张斌,张昆(2011)。中西新闻价值观“异”“同”的文化学阐释。《文化前哨》,(1),43-45。
郑保卫(2007)。《新闻理论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ednarekM. & CapleH. (2017). The Discourse of News Values: How News Organizations Create Newsworth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derJ. R.DavenportL. D.Drager, M. W. & Fedler, F. (2016). Reporting for the Media. 9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P. & Wacquaint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ightonP. & FoyD. (2007). News Values. London: Sage.
Caple, H. & Bednarek, M. (2013). Delving into the Discourse.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Caple, H. & Bednarek, M. (2016). Rethinking News Values: What a Discursive Approach Can Tell U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Discourse and News Photography. Journalism, 17(4): 435-455.
Carlson, M. (2017).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cking, B. (2018) News Values Go on Holiday. Journalism Studies19(9)1349-1365.
Cushion, S.LewisJ. & CallaghanR. (2017). Data Journalism, Impartiality, and Statistical Claims: Towards More Independent Scrutiny in News Reporting. Journalism Practice, 11(10)1198-1215.
DahlT. & FlottumK. (2017). Verbal-visual Harmony or Dissonance? A News Values Analysis of Multimodal News Texts on Climate Change. DiscourseContext & Media20124-131.
DickM. (2014). Interactive Infographics and News Values. Digital Journalism, 2(4)490-506.
Galtung, J. & Ruge, M.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goCuba and Cyprus Crises in Four Norwegian Newspap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264-90.
GansH.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García-Perdomo, V.Salaverría, R.KilgoD. K. & Harlow, S. (2018). To Share or Not to Share: The Influence of News Values and Topics on Popular Social Media Con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and Argentina. Journalism Studies19(8)1180-1201.
HarcupT. & O’Neill, D. (2001). What Is News? Galtung and Ruge RevisitedJournalism Studies2(2)261-280.
HarcupT. (2015). Journalism: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3rd ed. London: Sage.
HarcupT. & O’Neill, D. (2017). What Is News? News Values Revisited (again). Journalism Studies18(12)1470-1488.
Hartung, B. W. & StoneG. (1980). Time to Stop Singing the “Bad News” Blue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119-26.
Hermida, A. Fletcher, F.Korell, D. & LoganD. (2012). ShareLike, Recommend: Decoding the Social Media News Consumer. Journalism Studies13(5-6): 815-824.
HerscovitzH. G. (1993). Similarities in News Values between U.S. and Latin American Mass Media Model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ulletin, 2813.
Jacob, S. I. (1954). Broadcasting House. London: BBC Written Archives Centre, T16/119/3.
Lippmann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Marwick, A. E. & Boyd, D. (2011). To See and Be Seen: Celebrity Practice on Twitter.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17(2)139-158.
Makki, M. (2020).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Values: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Iranian Hard News Reports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15(3)308-324.
McIntyreK. (2016). What Makes “Good” News Newsworth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33(3)223-230.
Motsaathebe, G. (2020). Re-imagining News Values and Labels of Controversies with Reference to Political Scandals, Communicatio, 46(1)21-39.
O’Neill, D. & Harcup, T. (2009). News Values and Selectivity. In: Wahl-Jorgensen, K. and Hanitzsch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1st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pp. 161-174.
O’Neill, D. & Harcup, T. (2019). News Values and News Selection. In: Wahl-Jorgensen, K. and Hanitzsch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pp. 213-228.
Parks, P. (2020). The Ultimate News Value: Journalism Textbooksthe U.S. Presidency,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Donald TrumpJournalism Studies21(4)512-529.
Pompper, D. (2021). On Re-considering The First as a News Value to Avoid Stereotyping,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32(1)1-23.
Schultz, I. (2007). The Journalistic Gut Feeling. Journalism Practice, 1(2)190-207.
Shoemaker, P. J. (1996). Hardwired for News: Using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to Explain the Surveillance Fun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6(3)32-47.
Shoemaker, P. J. & ReeseS. D. (2014). 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 (3e). Routledge.
SteensenS.et al. (2019). What Doe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Look Like? Digital Journalism, 7(3)320-342.
Tenenboim, O. & CohenA. A. (2013). What Prompts Users to Click and Com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Online News. Journalism, 16(2)198-217.
Tien Vu, H. (2014). The Online Audience as Gatekeeper: The Influence of Reader Metrics on News Editorial Selection. Journalism, 15(8): 1094-1110.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T. (Eds). (2009).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1st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Wahl-Jorgensen, K. and HanitzschT. Eds. (2020).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2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Weaveret al. (2007).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White, D. M. (1950). The “Gate 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27383-396.
Zeng F. X. & Li Y. H. (2013). A Mission Beyond Journalism: Advocacy and Media Practices of Award Giving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4)419-435.
杨奇光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王润泽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20 & ZD3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