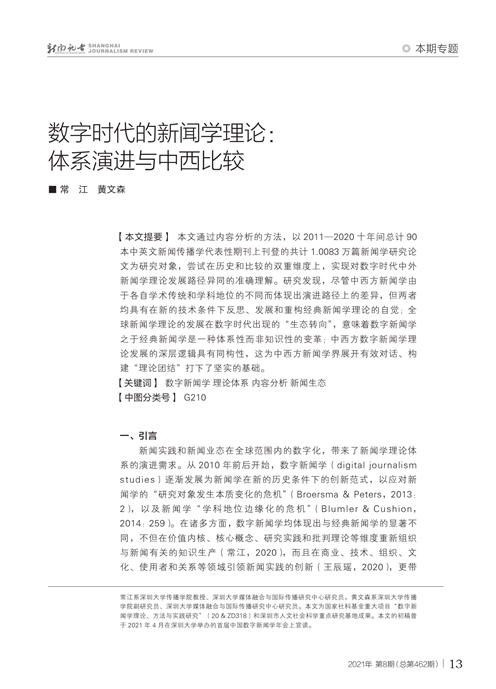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演进与中西比较
■常江 黄文森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以2011—2020十年间总计90本中英文新闻传播学代表性期刊上刊登的共计1.0083万篇新闻学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尝试在历史和比较的双重维度上,实现对数字时代中外新闻学理论发展路径异同的准确理解。研究发现,尽管中西方新闻学由于各自学术传统和学科地位的不同而体现出演进路径上的差异,但两者均具有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反思、发展和重构经典新闻学理论的自觉;全球新闻学理论的发展在数字时代出现的“生态转向”,意味着数字新闻学之于经典新闻学是一种体系性而非知识性的变革;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理论发展的深层逻辑具有同构性,这为中西方新闻学界展开有效对话、构建“理论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数字新闻学 理论体系 内容分析 新闻生态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新闻实践和新闻业态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带来了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演进需求。从2010年前后开始,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逐渐发展为新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范式,以应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本质变化的危机”(Broersma & Peters, 2013: 2),以及新闻学“学科地位边缘化的危机”(Blumler & Cushion, 2014: 259)。在诸多方面,数字新闻学均体现出与经典新闻学的显著不同,不但在价值内核、核心概念、研究实践和批判理论等维度重新组织与新闻有关的知识生产(常江,2020),而且在商业、技术、组织、文化、使用者和关系等领域引领新闻实践的创新(王辰瑶,2020),更带来了总体性研究视角向“用户”的转移(刘鹏,2019)。这一新闻学新范式的发展,尤其关系到我们藉由新闻理解社会与历史进程的路径,因而超越单纯的“理论创新”和“解释创新”范畴,具有认识论(epistemology)上的重要意义(Ekstrom, Lewis & Westlund, 2020)。
不过,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在数字时代的“范式升级”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数字”和“新闻”的关系问题。亦即,“数字”在新闻学理论体系革新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具体而言,对于新闻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数字”是一个新的“变量”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它与“新闻”之间的关系又发生在本体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哪些层面?清晰界定“数字”和“新闻”之间的“张力”(Duffy & Ang, 2019),是我们准确锚定新闻学理论体系过去十年的发展逻辑的前提。第二,研究范式的“超本地性”(trans-localness)问题。亦即,应当如何看待基于不同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下的数字新闻经验产出的理论观点并对其进行整合,从而使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新范式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已有深入的探讨,此处不再赘述。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数字新闻学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尽管数字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接受是一种全球范围的实践,但针对这种实践的自觉的理论探索,却肇始于2010年前后的英国和西北欧国家。在总体上,数字新闻学范式的崛起既是欧洲新闻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体选择的理论突破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全球新闻学界对美国功能主义与信息论研究传统的厌倦与反思(Domingo, Masip & Meijer, 2015)。目前,对数字新闻学的体系性探索正在成为全球性的潮流,“捷足先登”的欧洲理论因语言和机缘优势,几乎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数字新闻学理论的发展,须在相当程度上不断与欧洲理论进行对话,以实现在彼此观照、相互借鉴的基础上的自足生长,进而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经验”在全球数字新闻实践领域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培育了富有特色的本土研究传统(Li, 2018),但由于缺少跟西方主流理论的有效对话,中国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在实际上处于较为隔绝的“地带”,难以生产出具有跨语境解释力的理论。
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一项纵贯分析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文献研究,对数字时代新闻学主流理论的演变情况做出准确的描摹和深入的解释;并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探索将数字新闻学建设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本文期望在主流脉络、核心概念、基础认识论等范畴厘清数字时代中外新闻学理论发展路径的异同,以实现“知己知彼”,为后续的对话、合作乃至“理论团结”做好观念准备。
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以2011—2020十年间总计90种中英文新闻传播学代表性期刊上刊登的共计1.0083万篇新闻学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尝试在历史和比较的双重维度上,实现对数字时代中外新闻学理论发展路径异同的准确理解。
(一)数据来源
我们以新闻与传播学类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15种期刊名称作为文献来源,通过中国知网(CNKI)分别检索并获取这些期刊2011年至2020年所有发表文献的基本信息,检索时间为2020年12月23日,获取包括作者、标题、关键词、摘要、发表时间等字段在内的共4.4239万条记录。为了筛选新闻学研究论文,我们以“新闻”为过滤词检索标题和关键词,并剔除卷首语、短评、摄影等内容类型,最终获得3465条论文记录作为中文分析的原始数据。
根据2020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收录的传播学类92种期刊目录,我们选取影响因子超过1.0的75种期刊作为文献来源,通过Web of Science分别检索并获取2011年至2020年所有发表文献的基本信息,包括作者、题目、摘要、发表时间等字段,检索时间为2020年12月27日,共获取4.1125万条记录。同样地,我们以“journalism”和“news”为限定词过滤标题和关键词,筛选并获得类型为“article”(不包括书评、编辑评论等)的研究论文记录6618条,作为英文分析的原始数据。
(二)数据处理及方法
关键词和摘要是出版物中最核心的“主题”和“观点”指标,因此适合追踪特定领域潜在的理论发展趋势(Steensen & Ahva, 2015)。对此,我们将主要采用词频分析和内容编码的方式对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和摘要文本进行细致的处理。
1.词频分析。作为国际学术论文写作规范的组成部分,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国家标准局,1978),每篇论文可选择3—8个关键词;对于英文论文,关键词除了单词也可以是词组或单词首字母缩写,一般用于描述研究主题、对象、方法和结果应用等论文的重要元素(APA, 2020)。本文根据不同的分隔符(如逗号、顿号或空格)切分文献数据中的关键词,并按照期刊或年份划分词集进行词频统计和描述性分析。
2.内容编码。为了比较中外新闻学研究视角和理论使用的差异,本研究对样本摘要中所涉及的“学科视角”、“理论显性”和“使用理论”进行人工编码。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考虑到英文文献数量约为中文的两倍,首先确定中文和英文文献摘要抽样比例分别为20%和10%,然后按照不同年份随机抽取对应比例数量的文献,最终获得中英文摘要数量分别为694和662篇。循沿斯廷森(Steen Steensen)和阿瓦(Laura Ahva)的研究思路,依据泽利泽(Zelizer, 2004)对新闻学关联学科的分类,将学科视角划分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经济学、哲学、法学、技术研究和其他共十类。理论显性是判断文献中理论使用是否明显的指标,编码为“是”、“否”和“部分”三类(Steensen & Ahva, 2015)。其中,当摘要仅提及某些理论概念或术语,但未明确表示使用特定理论时,编码为“部分”。4名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两两分组,经培训后分别对中英文摘要进行独立编码,其中中文编码者间信度(Cohen’s kappa)在0.950以上,英文编码信度均在0.852以上,不一致选项由编码者经过讨论协商达成一致。“使用理论”需要编码员从摘要文本中提取具体的理论名称,如“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场域理论(field theory)等,最终由两位作者复核并对理论进行合并,使用频率3次以下的理论被纳入“其他”(other)选项。
三、研究发现
(一)论文及关键词分布
分析关键词的目的在于勾勒近十年中外新闻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旨趣、关注热点的发展与转向。经统计,如图1所示,十年之间(2011—2020年)国内CSSCI15种期刊中发表“新闻”相关研究论文总数为3465篇,平均每年论文数量约为346篇,从2011年的328篇到2020年的292篇,整体趋势趋于平稳且略微下降。75种传播学SSCI索引期刊在此期间共发表相关新闻学研究论文6618篇,平均每年约为662篇,从2011年的370篇增长至2020年的849篇,论文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以每年68篇①的速度增长。
具体来看,中文期刊中《新闻界》发表新闻学相关研究最多,达到493篇,占其2011至2020年刊发文献总量(2840篇)的17%;《新闻记者》次之,为456篇,占其统计文献总量2380篇的19%,可见这两种刊物已经成为国内新闻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平台。在英文期刊中,《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和《新闻学》(Journalism)刊发新闻学研究论文数量居多,两者均为专门研究新闻实践和理论的国际性期刊,分别刊发与“新闻”直接相关的论文751篇(83%)和684篇(62%);而以“数字新闻”为主要旨趣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创刊于2013,7年之间发表相关论文多达424篇(71%)。可见,国内外冠以“新闻学”(journalism)之名的期刊确为新闻学研究之“重镇”。相较之下,国外期刊的专门程度更高,前3种期刊的相关研究均超过60%,而该比例对于中文期刊均低于20%。这或许与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研究议题的多元化有关——编辑出版、传播学等方向的研究占比历来更高(廖圣清等,2019)。
作为学术写作规范的关键词提炼,其选择和组合的方式体现了个体研究者对研究核心概念或对象的把握,而集体研究者共用或共享术语则构成了特定学科领域对特定范式的想象。因此,比较高频复现的关键词可折射中外新闻学研究兴趣差异之一斑。由(图2 图2见本期第17页)可见,中文关键词以宏观的、概括的研究“领域”或理论“视角”为主,如“新闻生产”、“新闻教育”、“新闻出版”、“新闻传播”、“新闻学”、“新闻业”、“新闻出版业”等领域,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媒介(体)融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性新闻”、“新闻自由”等视角。然而,英文高频关键词却呈现一种更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对象”/“议题”和“方法”取向,例如“social media/news media”、“newspaper”、“Twitter/Facebook”、“online news”、“journalist/audience”等对象,“political communication”、“climate change”、“media effect”、“gender”、“fake news”等议题;“content analysis”、“framing”、“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等关键词反映了国外新闻学研究以经验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论范式(Loffelholz, 2008)。
(二)关键词演化
为了纵向勾勒中外新闻学研究旨趣或“热词”的演变趋势,图3展示了近十年核心关键词频数的时间分布情况。本研究所选取的14个中文关键词呈现了三种不同的趋势:
(1)衰减(即频数峰值在2015年以前,且历经峰值后快速下降)。如“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由”两个传统的新闻学理念均在2013年之后渐次下滑至“低谷”;关键词“新媒体”和“媒介融合”在2015年盛极一时,概因2014年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开启了“新媒体融合元年”,学术风向因时而变,但近些年来特定概念的热度已然褪尽。
(2)先升后降(指词频起步于较低水平并于2015年后出现减势)。例如,关键词“大数据”和“数据新闻”在2011年和2012年均尚未出现,却于2014年和2016年分别达至峰值,以2012年美国“大数据发展和研究计划”为标志性事件,在业界实践引领下,国内学界追逐进入“大数据”时代(喻国明等,2013);伴随国内媒体对数据新闻实践的本土化探索,研究者开始探索“大数据”和“数据新闻”对于媒体的价值及其引发的理念变革(方洁等,2016)。2017年以降,新闻学的“数据”热潮始现消退迹象。另一方面,虽然以“新闻教育”为关键词的研究数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发展持续平稳,足见“教育”其不可或缺的根本地位;以此为参照,“新闻出版”和“新闻生产”有着相似的发展律动,均在2013年和2017年达到局部和全局的峰值。但“新闻出版”的波动可能主要受政策的影响,如以2013年“署局合并”(即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节点,研究者纷纷关注大部制改革对新闻出版的影响(吴锋,屠忠俊,2013),而2017年的热度上升或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出台有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新闻生产”作为位列第一的高频词,以其为关键词的年均发文量约为13篇,2017年的极值与特定期刊对相关稿件选用的偏好有关,如《中国出版》当年刊文多达9篇,另外仅《新闻记者》2017年第5期开设的“新闻生产与田野调查”专题就囊括5篇相关论文(如李赛可,2017;张伟伟,2017;张志安,2017)。
(3)逐渐上升(即关键词频数保持上升态势,且峰值出现在2015年之后或尚未出现)。与“媒介融合”的减势相反,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官方表述中的“媒体融合”概念,既出于政治考量,也反映了学界对概念认知的深化,即媒体融合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还关涉经济、主体、内容、规范等多层面(韦路,2019)。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兴起于2016年,关于机器写作、算法、智能媒体等技术与新闻生产嬗变的研究一度层出不穷,在2018年达至高潮,继而进入低潮转向对价值、伦理与规范的反思(陈昌凤,师文,2019)。“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主导我国新闻业的新闻观或唯一的主导性新闻意识形态(杨保军,2017),以此为关键词的研究论文数量近十年来持续上扬。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建设性新闻”自2019年以来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作为一种根植于积极心理学、强调问题解决导向、主张以信息生产介入社会变革的实践体系(白红义,张恬,2020;常江,田浩,2020),业已成为当前国内新闻学研究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支。随着马新观、建设性新闻、中国特色新闻学等学术观念的发展,以“新闻学”为旨趣的研究逐渐增加,折射了新时代新闻学体系建构的理论自觉和想象力的形成。
近十年来,由于英文期刊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其关键词整体上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不同关键词可大致划分“议题”、“方法”和“媒介”三类。
(1)在议题方面,与21世纪初新闻类博客的兴起紧密相关,“citizen journalism”(公民新闻)描述了一种完全由关注新闻事件的用户生产,且不受专业新闻判断和把关影响的新闻模式,它的出现“消除了职业记者的权威”(Kperogi, 2011)。作为一个“缺乏清晰性和概念化”的表述,“citizen journalism”近年来被许多研究者使用,然而一篇以其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章,可能在标题中使用其他诸如“参与性”(participatory)的术语(Wall, 2015)。或许正是这种定义的模糊性,使其经过了一段上升期(2011—2015)后转向式微。随着数字技术对新闻实践和产出范围的扩大,“digital journalism”(数字新闻)一词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创刊的Digital Journalism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teensen et al., 2019);2019年39篇以其为关键词的研究中,有8篇来自该刊当年推出的专题“Defining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定义数字新闻学),旨在对“数字新闻”概念及其研究路径做出清晰的界定和差异化的辨析。目前,“digital journalism”被认为是“想象新闻与公众之间最佳联系的最新通道”(Zelizer, 2019),从而成为国际新闻学研究新的增长点。“气候变化”和“性别”议题皆为西方新闻研究的重要话题,关键词“climate change”和“gender”的出现频度近十年间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媒体报道与“气候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Science Communication等几本期刊,研究关注的国家和媒体类型越来越多,但仍然以西方国家和纸媒为主(Schafer & Schlichting, 2014)。关于“fake news”的研究论文从2017年的1篇骤增至2018年的23篇,并持续增长至2020年的47篇,这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假新闻在社交媒体、谷歌搜索和新闻媒体上的泛滥紧密相关。“假新闻”被作为一种诋毁、攻击和剥夺政治对手合法性的手段,已成为西方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Farkas & Schou, 2018)。对此,研究者聚焦于假新闻的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案,生产、平台、广告补贴和消费等领域是主要问责和补救的焦点(Carlson, 2020)。
(2)在方法方面,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和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近十年间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或分析框架。其中,使用关键词“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最多(346篇)且增长幅度最大,从2011年的13篇增至2020年的44篇,该方法是一种“对显性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Berelson, 1952),对随机抽样、可靠性的规范化操作,以及对计算机编程的运用将有利于研究复现和方法扩展(Lacy et al., 2015)。最近,结合情感分析、主题模型、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的自动内容分析方法(Boumans & Trilling, 2016;Burggraaff & Trilling, 2020),为应对海量的数字新闻数据提供了新的机遇。相较之下,“framing”的升势自2017年以来略有回落。“框架”作为“信息编码、解释和检索的认知工具”(Pan & Kosicki, 1993),其所形成的“framing analysis”是一种建构主义方法。与内容分析有所不同,前者将新闻文本视为意义建构过程中与个体记忆交互的、有组织的符号,后者则视之为“可客观识别其意义的心理刺激物”。因此,“framing”可作为“建构和加工新闻话语(news discourse)的策略或话语本身的特征”(Pan & Kosicki, 1993),与“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结合使用于同一研究之中(Kogen, 2015;Teresa, 2020)。但区别于框架或内容分析的定量取向,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将权力和意识形态引入新闻报道分析,以一种反身的(reflexive)、参与的形式定性评价特定话语,并指责其所维持的社会、文化或政治错误(Carvalho, 2008)。经统计,每年明确使用该方法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均值(10篇)上下波动,虽涨幅较小但上升潜力较大。
(3)在媒介方面,2011年以来,媒介类型关键词中的“internet”数量持续走低,年均篇数不足10篇;对代表传统媒体的“newspaper”的研究自2016年起亦略有下滑。与此相反,以“social media”为关键词的研究论文数量以605篇居于首位,且经历2016年和2019年两次大幅攀升;相应地,“Twitter”作为“social media”概念的一个“实例”,整体增幅虽不及前者,但两者有着相似的波动规律;而研究者对“Facebook”的关注度一直低于“Twitter”,同时两者的差距在逐年减小。
(三)学科视野
新闻学是一个广泛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汲取理论资源的年轻学术领域,其学科传统涵盖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语言研究和历史研究等的多元方法和视角(Zelizer, 2004)。经过对随机样本的编码和统计,本研究试图回答中外新闻学研究是否有相同跨学科模式,或者受不同的学科源头的影响,并考究中外新闻学理论使用及其演化的差异。
如(图4 图4见本期第21页)所示,国内新闻学的学科视角主要以史学(106,15.27%)、哲学(86,12.39%)、社会学(83,11.96%)和语言学(78,11.24%)为主。其中,新闻史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邓绍根,2015)。近十年来,以近代报刊史为研究中心,学界从事件史、人物史、地方史、断代史、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等领域深入考察,研究范式不断更新,这一时期的新闻史学“攀登至新的高峰”(张晓锋,程河清,2019)。近年来,哲学取向的新闻学研究方向涉及传媒伦理(周海燕,2015)、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喻发胜等,2019)、新闻专业主义(李岩,李赛可,2014)等哲学原理,乃至对建设性新闻(吴飞,李佳敏,2019)、算法新闻(冯月季,2020)等新近领域的本体论或认识论问题的学理延展。社会学视野下的研究聚焦于新闻(知识)生产(薛可等,2019;龙小农,2018)、新闻场域(常江,文家宝,2016)、社会性别(张敬婕,2016)等领域。语言研究也是新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涉及新闻框架(邓秀军,申莉,2017)、新闻话语(邵培仁,王昀,2015)、新闻叙事(潘亚楠,2020)、新闻写作与修辞(张恒军,孙冬惠,2011)等角度或面向。
对于英文文献,将近三分之一(183,27.64%)的分析样本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框架,而超过五分之一(157,23.72%)研究则选择了政治学的分析视角。这与以往的研究(Steensen & Ahva,2015)结果基本一致,即社会学和政治学仍然是主导西方新闻学研究的两大背景学科和理论源泉。新闻学与社会学的渊源始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将新闻学引向“权力、控制、结构、制度、阶层和社区”等命题(Reese, 2016)。社会学视角暗示着将新闻理解为一种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并从一系列宏观的社会系统理论探索“新闻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它重要,以及是什么使它不同于其他传播形式”(Ahva & Steensen, 2020)。而政治学传统视新闻为一种塑造公共话语的民主力量(democratic force),或修饰以“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的隐喻,将其界定为“民主的守护者和公众舆论与政府之间的中介者”(Ahva & Steensen, 2020)。值得注意的是,与上一个十年有所差别,“技术”从相对边缘的位置(Steensen & Ahva, 2015)上升为排名第三的学科视角,近十分之一(65,9.82%)的相关研究暗示着媒介技术作为考察对象的技术“转向”正在酝酿形成,这部分得益于数字技术对新闻实践和研究领域的介入(Steensen & Westlund, 2021)。相对地,“文化分析”的研究有所减少(58,8.76%),这类研究关心诸如“新闻如何可能”、“记者如何认识自己”等问题,将新闻实践和产品与权力、意识形态、种族、性别和日常生活等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文化分析视野里,新闻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形式,“通过话语塑造着我们和我们的世界”(Ahva & Steensen, 2020)。
相较之下,国内外的新闻学研究展现了截然不同的跨学科景观。从学科分布来看,为了刻画新闻学研究的跨学科的多样性,本研究借鉴香农和韦弗(Shannon & Weaver, 1949)的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公式测量多样性指标,即H分值。②该分值表示“跨学科多样性”,采用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论文分布越均匀,H分值就越大。计算结果显示,国内新闻学研究的跨学科多样性H分值为3.057;而对于国外新闻学研究,该值为2.580。由此可见,相比于国外新闻学对极个别学科的倚重,国内新闻学理论来源学科的分布更为均匀。具体而言,国内新闻学的范式或理论视野更偏向于人文学科(以史学、哲学和语言学为主)的研究进路,而国外新闻学依赖于社会科学(即社会学和政治学)所提供的理论支柱。
除了上述主导性学科外,国外新闻学的历史(6.19%)、经济(3.78%)、法律(1.06%)和哲学(0.91%)研究视角长期以来处于次要地位,与斯廷森和阿瓦(Steensen & Ahva, 2015)对2000至2013年的文献摘要分析结论相符。而在中文语境下,政治学(5.62%)、文化分析(4.90%)和法律(4.03%)等探索视角在新闻学理论、方法或应用层面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从理论含量来看,国内新闻学论文摘要中明确使用具体理论的不到七分之一(13.26%),五分之一(19.45%)的摘要中仅“部分”提及使用理论,超过三分之二(67.29%)的论文摘要没有提及任何理论。英文论文摘要中,三分之一(33.38%)使用了特定理论,该比例与此前对西方传播学研究(Bryant & Miron, 2004;Kamhawi & Weaver, 2005)理论使用情况统计的结果基本符合,均为三分之一,暗示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有着相似的研究风格(Steensen & Ahva, 2020)。另外,将近五分之一(18.73)仅提及相关理论概念或术语,约近二分之一(47.89%)没有使用任何理论。
(四)理论演化
经过对抽样文献摘要“使用理论”的编码和统计,(图5 图5见本期第23页)分别展示了中文和英文新闻学研究中使用理论及其变化情况。读图可知,国内外新闻学研究者都比较关注的10个理论框架为:“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把关理论(Gatekeeping)”、“框架理论(Framing)”、“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新闻价值(News value)”、“新闻客观性(Objectivity)”、“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
其中,“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客观性”和“新闻价值”是传统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和根本性问题。“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从业者所恪守并赖以生存的“共同规范、规则和实践体系”(Hanitzsch & ornebring, 2020)。尽管近年来“新闻业正在被消解”,但该话语资源仍然具有规范新闻实践的重大意义(迈克尔·舒德森,2021;潘忠党,陆晔,2017),而被国内外新闻学者不断“重访”。经统计,中英文摘要中该理论使用占比分别达到9.30%和5.15%,且前(2011—2015)后(2016—2020)5年占比均衡(见图5)。“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要素,长久以来因被指摘为保护新闻记者回避风险或批评的“策略性仪式”而颇具争议(Tuchman, 1972)。尤其进入数字时代,以客观性为主要依据的新闻职业边界日渐模糊,国内外学者的焦点也开始分散,出现从“客观性”范式向“透明性”(Hellmueller et al., 2013)或“介入性”(常江,何仁亿,2021)转移的风向。具体表现为,“新闻客观性”和“Objectivity”的占比分别低至2.33%和1.52%,尤其是近五年国内关于客观性的研究论述从7.46%降为0%。“新闻价值”是记者进行新闻选择的基本规则或“先决条件”,影响“哪些事件、议题或故事可以成为新闻”(Harcup & O’Neill, 2001)。近五年(2016—2020年)来,国内对新闻价值的考察明显不如前五年(7%),占比已不足1%。然而,“News value”的占比却有所上升(从2.34%到3.47%),国外学者认为新闻价值依然值得研究,因为它作为记者“共享的操作性理解”(shared operational understanding),为新闻受众呈现“媒介化的世界”(Harcup & O’Neill, 2017)。
“框架理论(Framing)”(13.33%)、“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4.55%)和“把关理论(Gatekeeping)”(3.94%)是国外新闻学研究使用最多的传播学经典理论。既是理论又是方法范式的“framing”,在不同时段英文研究中的使用占比均超过13%;而在中文语境下,“框架理论”的使用仅占所有理论的3.72%,而且近几年有下降(从5.97%到2.70%)的趋势。“议程设置理论”(McCombs & Shaw, 1972)和“把关理论”(White,1950)都是从个体与组织层面理论化新闻学的“中层”(middle-range)理论(Ahva & Steensen, 2020),前者提供了一个分析新闻如何塑造公共领域,以及公众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后者则是对信息选择和加工的社会决策过程的理论化。与议程设置理论在国外新闻学研究中的流行(4.55%)不同,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关注度明显下降,从4.88%降至0.68%。尽管流行观念中的把关“正在衰落、濒死或已经消亡”(Vos, 2020),但把关理论过去十年在国内外新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彰显,占比分别为3.72%和3.94%。在新的数字环境中,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个体用户、算法和平台在把关理论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把关的机制和过程(Singer, 2014;Wallace, 2018;黄雅兰,陈昌凤,2017),暗示着这个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学理论的“复兴”(Vos, 2020)。
此外,“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和“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属于上述九大学科中语言取向的理论视角。话语理论在国内外新闻学研究中均占据优势地位,分别为位列第三(7.44%)和第二(10.00%)的理论;国内新闻学研究采用叙事理论的比例(5.12%)比国外(3.03%)略多,且有上升趋势(从4.48%到5.41%)。上述两种理论的方法分别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前者关注话语或谈话和文本的结构及功能,后者是指对具有故事形式的(新闻)文本进行分析。
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外新闻学研究方向发生了“生态转移(the ecosystem shift)”(Reese, 2016)。其中,“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的理论占比分别为1.86%(从1.49%到2.03%)和2.42%(从1.56%到2.97%),而且表现出增长的趋势。“media ecosystem”一词最早可追溯至2001年,而后于2010年出现在新闻学期刊上,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地理社区或围绕一个特定的问题,从事新闻生产,甚至是新闻消费的个人、组织和技术的整体”(Anderson, 2016)。
国内外新闻学研究理论使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内最关注的理论框架或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2.09%),从4.48%增加至15.54%;“建设性新闻”(5.12%)和“中国特色新闻学”(2.79%)也是国内独特的新闻学理论视角,尤其是建设性新闻领域的“平地崛起”,从2019年起陡增至7.43%,一跃成为最流行的新闻学理论之一。国外新闻学者更关注传播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比如“selective exposure”(选择性接触)、“knowledge gap”(知识沟)、“third person effect”(第三人效果)、“democracy theory”(民主理论)、“public sphere”(公共领域)、“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等等。
四、结论与讨论
经前文对2011—2020年中外新闻学理论研究脉络和比较差异的分析,我们得以较为清晰地描摹出过去十年间主流新闻学理论体系发展演进的基本特征;而由于这十年正是全球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被数字化进程大幅度“改造”的关键时期,以及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新范式的“肇兴期”,故我们也能据此对中国和西方新闻学界应对这一潮流时所体现出的差异做出深入的解释。
首先,我们要看到在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路径上,中国和西方体现出了本质的差异。总体上,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体现出重实务、重政策、重规范的特征。体现在理论发展的路径上,一方面,中国新闻学界更加注重从新技术驱动的前沿实践(如数据新闻、算法新闻等)中不断形成伦理和价值层面的规范理论,并致力于将这些规范理论应用于不同的实践范畴;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媒体政策和主导性意识形态在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但有力地影响了学界对于西方理论加以借鉴的标准(如对建设性新闻的深入考察),而且也培育了完全有别于西方的独立的创新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而西方新闻学的发展则体现出重理论、重方法、重解释的特征。与中国相比,西方新闻学界较为因循“在新的媒介条件下检验并发展主导性理论与方法论”的路线,体现出高度稳健(因而也相对保守)的成长策略,对新概念和新理论的提出十分谨慎;其对“数字新闻”的研究,更多具体化为立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对新现象和新业态做出解释,并十分注重将这种解释工作限定于经验主义的框架之内。
其次,中西方新闻学理论在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固然体现了两种文化语境和学术传统对于“理论”、“学术”以及“研究”等概念的不同界定方式(张威,2001),但更重要的是,其折射出了新闻学在中西方不同的学科地位。中国的新闻学无论在理论化路径上还是理论话语上,都较少受到其他学科的直接影响,这种形式上的“独立性”既源于中国本土学术的哲学思辨和道德规训传统,也源于国家体制所决定的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独特性属(常江等,2020);相较之下,新闻学在西方自始至终被视为传播学(尽管美国和欧洲对于传播学的主流理解并不一致)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其“独立”倾向始终受到主流学界的警惕(常江,何仁亿,2018),而且其理论发展深受主导传播学发展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框架的影响(Chang,Gitlin & Schudson, 2020),这种约束令西方新闻学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受到观念、方法和规范上的诸多限定,使得任何新概念和新理论在提出后都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反复的检验。
再次,中外新闻学界在过去十年中,均体现出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反思、发展和重构经典新闻学理论的自觉。尽管中西方新闻学过去十年的发展拥有不尽相同的路径,但在一个方面却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重构新闻学经典理论,使之获得对数字新闻实践的实际解释力。如前文所述,这些经典理论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话语、新闻叙事、新闻价值、新闻把关、新闻框架、新闻生态,等等。这些理论尽管拥有不同的内涵和形式,但它们背后的认识论却是同构的,那就是新闻(news)作为一种公共信息产品、新闻业(journalism)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在价值上的独特性。换言之,在过往一个多世纪中,正是上述理论的持续发展和更新,不断强化新闻区别于其他媒介内容的公共档案和历史文化价值(Fink & Schudson, 2013),以及新闻学区别于其他信息类学科的鲜明的人文属性(Zelizer, 2000)。
最后,全球新闻学理论的发展在过去十年中体现出“生态转向”(the ecological turn),这一转向不仅体现在包括“新闻生态”在内的理论话语的增殖,也体现在“技术分析”在新闻学研究视野中的地位日益显著。这或许意味着数字新闻学与经典新闻学相比,将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反思功能主义范式,更加关注总体性技术环境下的不同元素的互动方式,并通过积极与技术哲学、媒介环境学和话语理论展开对话的方式,实现对自身研究传统的更新,力求在新的外部条件下践行新闻学对历史和社会做出的“承诺”(Robinson, Lewis & Carlson, 2019)。以“生态的”话语替代“功能的”或“效能的”话语,同时也昭示着新闻学对既有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比如以德勒兹式的“根茎思维”取代信息论的“板块思维”(Anderson, 2016),或对经典的“新闻室民族志”进行从理论化路径到操作规范的改进(克里斯·安德森,2021)。
综上,本文认为,中西方主流新闻学理论在数字时代演进的具体路径虽然不尽相同,但支配其演进的基础逻辑是较为一致的。一方面,数字新闻学之于经典新闻学,首要是一种体系性而非知识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在概念框架、阐释话语和理论化风格等诸多方面对经典新闻学进行着本质性的改造;数字新闻学并非通过扩充或更新传统理论资源来解释“数字的”的新闻实践,而是将“数字”视为一种本质性的思想内核,实现对经典新闻学的结构重组和价值重建,这在中西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脉络中均得到显著体现。另一方面,数字新闻学由于“绑定”了全球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深度数字化进程,因而在理论的观照面和渗透力上均较经典新闻学有显著的提升,其发展同时受到与技术分析相关的多个前沿学科、特定社会语境的学术传统,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新闻业发展趋势的国家话语的影响,这些因素既是数字新闻学理论自由生长的制约因素,也为这一新范式与不同传统或前沿的观念和话语的对话预留了巨大的空间。
在上述逻辑的支配下,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研究者拥有展开有效对话的坚实基础和构建“理论团结”的实现前景。如何建立更加顺畅的理论对话机制,共同提炼和解决全球新闻业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共通问题,并致力于提升数字新闻学理论话语在总体人类知识架构和一般性社会生活层面的解释力,是一个虽紧迫,却令人兴奋的议题。■
注释:
①英文期刊论文数量随年份增加趋势的拟合直线(即图1上方的虚线)的斜率为68.384(R2=0.929),表示理论上时间每增加一年,论文数比前一年增加68篇。
②H分值的计算公式为:H=-∑inpi(log2pi)。其中,pi是指第i个学科视角(i=1,2,……,n)的论文数占所有九个学科视角(不包括“其他”)论文总数的比例。如果每个学科视角的论文占比均为1/9,那么H值达到最高3.170(即log29);如果某个学科视角的论文占比为100%,其余学科为0%,则跨学科多样性最差(H=0)。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20)。作为“创新”的建设性新闻:一个新兴议题的缘起与建构。《中国出版》,(8),3-8。
常江(2020)。数字新闻学:一种理论体系的想象与建构。《新闻记者》,(2),12-20+31。
常江,何仁亿(2018)。迈克尔·舒德森:新闻学不是一个学科——历史、常识祛魅与非中心化。《新闻界》,(1),12-17。
常江,何仁亿(2021)。客观性的消亡与数字新闻专业主义想象:以美国大选为个案。《新闻界》,(2),26-33。
常江,克里斯·安德森,迈克尔·舒德森,托德·吉特林(2020)。新闻学的未来:数字生态与全球语境(上)。《新闻界》,(10),4-10。
常江,田浩(2020)。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体系: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中国出版》,(8),8-14。
常江,文家宝(2016)。中国语境下的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基于对《新闻调查》(1996-2006)的个案考察。《国际新闻界》,38(3),91-113。
陈昌凤,师文(2019)。智能算法运用于新闻策展的技术逻辑与伦理风险。《新闻界》,(1), 20-26。
邓绍根(2015)。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新闻与写作》,(10),9-12。
邓秀军,申莉(2017)。反转的是信息而不是新闻——框架理论视阈下微信公众号推文的文本结构与内容属性分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9(1),132-137。
方洁,颜冬(2013)。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国际新闻界,(6),75-85。
冯月季(2020)。反叙述:算法新闻的符号哲学反思。《编辑之友》,(1),74-78。
国家标准局(1987)。国家标准GB 7713—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http://www。gb688。cn/bzgk/gb/newGbInfo?hcno=823B8654959A5225AAEC439933BC2D20。
黄雅兰,陈昌凤(2016)。“目击媒体”革新新闻生产与把关人角色——以谷歌新闻实验室为例。《新闻记者》,(1),42-49。
克里斯·安德森(2021)。没有历史的技术:民族志、物质性与新闻业的变迁。《新闻界》,(5),4-12。
李赛可(2017)。在希望的田野上步步深入——基于地方新闻网站红网之民族志研究的反思。《新闻记者》,(5),34-44。
李岩,李赛可(2014)。新闻专业主义的悖论探析。《新闻界》,(1),11-16。
刘鹏(2019)。用户新闻学:新传播格局下新闻学开启的另一扇门。《新闻与传播研究》,26(2),5-18+126。
廖圣清,朱天泽,易红发,周源,于建娉,谢琪如(2019)。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议题、方法与理论(1998—2017)。《新闻大学》,(11),73-95+124。
龙小农(2018)。知识生产者:记者社会角色的另一种想象。《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0 (8),26-33。
迈克尔·舒德森,李思雪(2021)。新闻专业主义的伟大重塑:从客观性1. 0到客观性2. 0。《新闻界》,(2),5-13。
潘亚楠(2020)。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创新叙事——以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作品为例。《编辑之友》,(8),75-79。
潘忠党,陆晔(2017)。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39 (10),91-124。
邵培仁,王昀(2015)。基层:再现与终结的底层映像——“走转改”新闻实践中的基层报道。《新闻大学》,(4),51-59+115。
王辰瑶(2020)。新闻创新研究:概念、路径、使命。《新闻与传播研究》,27(3),37-53+126-127。
韦路(2019)。媒体融合的定义、层面与研究议题。《新闻记者》,(3),32-38。
吴飞,李佳敏(2019)。从希望哲学的视角透视新闻观念的变革——建设性新闻实践的哲学之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6 (S1),97-105。
吴锋,屠忠俊(2013)。我国新闻出版与广电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2013年“署局合并”之透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5(5),1-6。
薛可,孟筱筱,宋锋森(2019)。差异与互补:官方与民间社交媒体的新闻生产对比研究。《新闻记者》,(5),67-74。
杨保军(2017)。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及其基本关系。《新闻大学》,(4), 18-25+40+146。
喻发胜,张唐彪,鲁文禅(2019)。普遍联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哲学基石及其实践价值。《新闻与传播研究》,26(4),5-24+126。
喻国明,王斌,李彪,杨雅(2013)。传播学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范式。《新闻记者》,(6), 22-27。
张恒军,孙冬惠(2011)。网络新闻标题的语言特色。《新闻界》,(2),86-88。
张敬婕(2016)。制作出性别敏感的新闻是否可能?——基于对北京市10家媒体机构40位媒体从业者的深访。《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8(2),67-71。
张威(2001)。比较新闻学:界定、依据和研究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4),19-32+95。
张伟伟(2017)。田野调查的身份转变与调适——新闻生产田野观察的方法学反思。《新闻记者》,(5),26-33。
张晓锋,程河清(2019)。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1949-2019)。《新闻与传播研究》,26(8), 24-42+126。
张志安(2017)。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田野观察和案例研究——从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谈起。《新闻记者》,(5),17-25。
周海燕(2015)。重建新闻的公共性共识是否可能?——从近期的传媒伦理争议谈起。《新闻记者》,(3),42-47。
AhvaL. & Steensen, S. (2020). Journalism theory. 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T. (Eds.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2nd Edition) (pp. 38-54). New York, NY: Routledg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ition). https://doi. org/10. 1037/0000165-000.
AndersonC. W. (2016). News ecosystems. In Anderson, C. , Witschge, T. , DomingoD. & HermidaA.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pp. 410-423). London: SAGE.
Berelson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York, NY: Free Press.
Blumler, J. G. & CushionS. (2014). Normative perspectives on journalism studies: Stock-taking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ism, 15 (3)259-272.
BroersmaM. J. & PeterC. (2013). Rethinking journalism: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 public good. In Peters, C. & Broersma, M. J. (Eds. ). Rethinking Journalism: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a Transformed News Landscape (pp. 1-12). Oxon: Routledge.
BryantJ. & MironD. (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4 (4)662-704.
Boumans, J. W. & Trilling, D. (2016). Taking stock of the toolkit: an overview of relevant 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 approaches and techniques for digital journalism scholars. Digital Journalism, 4 (1)8-23.
BurggraaffC. & Trilling, D. (2020). Through a different gate: an 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 of how online news and print news differ. Journalism, 21 (1)112-129.
Carlson, M. (2020). Fake news as an informational moral panic: the symbolic deviancy of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3 (3)374-388.
CarvalhoA. (2008). Media (ted) discourse and society: rethinking the framework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ism studies9 (2)161-177.
Chang, J. , Gitlin, T. & Schudson, M. (2020). Reflecting on forty years of sociologymedia studiesand jour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Todd Gitlin and Michael Schudson. Sociologica14 (2)249-263.
Domingo, D. , MasipP. & Meijer, I. C. (2015). Tracing digital news networks: towar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the dynamics of news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use. Digital Journalism, 3 (1)53-67.
Duffy, A. & AngP. H. (2019). Digital journalism: definedrefinedor re-defined. Digital Journalism, 7 (3)378-385.
Ekstrom, M. , Lewis S. C. & Westlund, O. (2020). Epistemologies of digital journalism and the study of misinforma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22 (2)205-212.
FarkasJ. & SchouJ. (2018). Fake news as a floating signifier: hegemony, antago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falsehood. Javnost-The Public, 25 (3)298-314.
FinkK. & Schudson, M. (2013). The rise of contextual journalism, 1950s-2000s. Journalism, 15 (1)3-20.
Hanitzsch, T. & ornebringH. (2020). Professionalism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journalistic roles. 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T. (Eds. ).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2nd Edition) (pp. 105-122). New York: Routledge.
HarcupT. & O’Neill, D. (2001). What is news? Galtung and Ruge revisited. Journalism Studies2 (2)261-268.
HarcupT. & O’Neill, D. (2017). What is news? News values revisited (again). Journalism Studies18 (12)1470-1488.
Hellmueller, L. , VosT. P. & PoepselM. A. (2013). Shifting journalistic capital? Transparency and o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ism Studies14 (3)287-304.
LacyS. , Watson, B. R. , RiffeD. & LovejoyJ. (2015). Issues and best practices in content analysi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2 (4)791-811.
LiK. (2018). Convergence and de-convergence of Chinese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ism, 19 (9-10)1380-1396.
McCombs, M. & Shaw, D. (1964).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36 (2)176-187.
Kamhawi, R. & Weaver, D. (2003).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from 1990 to 1999.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0 (1)7-27.
Kogen, L. (2015). Not up for debate: US news coverage of hunger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7 (1)3-23.
Kperogi, F. A. (2011). Cooperation with the corporation? CNN and the hegemonic coopta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through iReport. com. New Media & Society13(2)314-329.
LoffelholzM. (2008). Heteregeneous-multidimensional-compet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journalism: An overview. In Weaver, D. H. , SchwarzA. & Loffelholz, M. (Eds. ). 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 Theories, MethodsFindings, Future (pp. 15-27).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an, Z. & Kosicki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10 (1)55-75.
Reese, S. D. (2016). 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Nussbaum, J. F. (Ed. ).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S. , Lewis S. C. & CarlsonM. (2019). Locating the “digital” in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transformations in research. Digital Journalism, 7 (3)368-377.
Schafer, M. S. & SchlichtingI. (2014).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fiel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8 (2)142-160.
Shannon, C. & Weaver, W.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ingerJ. B. (2014). User-generated visibility: secondary gatekeeping in a shared media space. New Media & Society16 (1)55-73.
SteensenS. & Ahva, L. (2015). 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 an exploration and introduction. Digital Journalism, 3 (1)1-18.
SteensenS. , Larsen, A. M. GHagvar, Y. B. & Fonn, B. K. (2019). What doe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look like?. Digital Journalism, 7(3)320-342.
SteensenS. & Westlund, O. (2021). What i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TeresaC. (2020). Steeled for the challenge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gendered news frames of Hillary Clinton in battleground coverage of the 2016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37 (1)30-42.
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7660-679.
Vos, T. P. (2020). Journalists as gatekeepers. 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T. (Eds. ).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2nd Edition) (pp. 90-104). New York: Routledge.
WallM. (2015). Citizen journalism: A retrospective on what we know, an agenda for what we don’t. Digital Journalism, 3(6)797-813.
Wallace, J. (2018). Modelling contemporary gatekeeping: the rise of individualsalgorithms and platforms in digital news dissemination. Digital Journalism, 6 (3)274-293.
White, D. M. (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27 (3)383-390.
Zelizer, B. (2000). What is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1 (1)9-12.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Sage Publications.
Zelizer, B. (2019). Why journalism is about more than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Journalism, 7 (3)343-350.
常江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文森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20 & ZD318)和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本文的初稿曾于2021年4月在深圳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数字新闻学年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