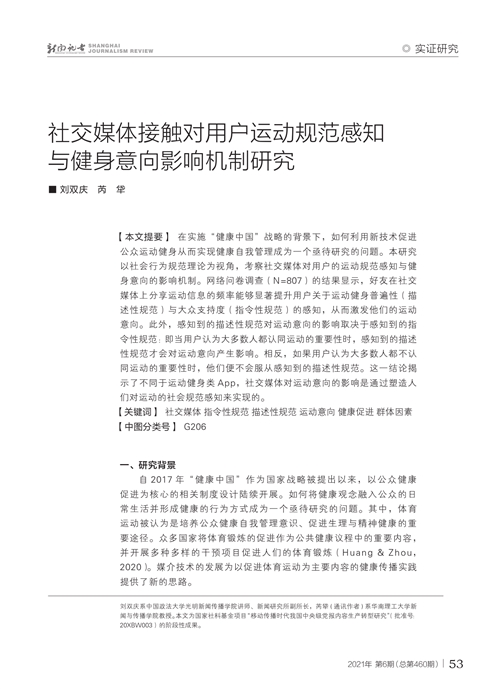社交媒体接触对用户运动规范感知与健身意向影响机制研究
■刘双庆 芮牮
【本文提要】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新技术促进公众运动健身从而实现健康自我管理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以社会行为规范理论为视角,考察社交媒体对用户的运动规范感知与健身意向的影响机制。网络问卷调查(N=807)的结果显示,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能够显著提升用户关于运动健身普遍性(描述性规范)与大众支持度(指令性规范)的感知,从而激发他们的运动意向。此外,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对运动意向的影响取决于感知到的指令性规范: 即当用户认为大多数人都认同运动的重要性时,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才会对运动意向产生影响。相反,如果用户认为大多数人都不认同运动的重要性时,他们便不会服从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这一结论揭示了不同于运动健身类App,社交媒体对运动意向的影响是通过塑造人们对运动的社会规范感知来实现的。
【关键词】社交媒体 指令性规范 描述性规范 运动意向 健康促进 群体因素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背景
自2017年“健康中国”作为国家战略被提出以来,以公众健康促进为核心的相关制度设计陆续开展。如何将健康观念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并形成健康的行为方式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其中,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培养公众健康自我管理意识、促进生理与精神健康的重要途径。众多国家将体育锻炼的促进作为公共健康议程中的重要内容,并开展多种多样的干预项目促进人们的体育锻炼(Huang & Zhou, 2020)。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以促进体育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健康传播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运动健身类App与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为促进运动健身提供了新的选择(Meng, 2016;Zhu et al., 2017)。就国内情况而言,相对于运动健身类App,社交媒体的覆盖面更广。根据2021微信公开课的数据,微信用户已经达到10.9亿(陈体强,2021)。此外,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与社会动员功能比运动健身类App更强。因此,许多运动健身类App都与社交媒体合作,实现了运动数据的共享。一项关于国内177个运动健身类App的研究揭示,只有26%的运动健身类App提供用户之间建立关系网络或形成网络社区的功能。然而,大约40%的此类App提供用户在社交媒体中分享运动数据的功能(Huang & Zhou, 2020)。例如,以悦跑圈、Keep为代表的健身App鼓励用户在微信、微博、QQ上分享他们的运动状况。与此同时,微信也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使用户可以了解到每天自己及微信好友行走的步数。运动健身类App与社交媒体的结合, 说明了新技术主导下的运动健身正受到社会群体因素的影响。换言之,社交媒体并非仅仅通过提供专业知识、专业指导促进人们形成锻炼习惯,而是通过营造一种身边人都在运动的氛围以激发用户的运动热情。因此,代表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的群体因素在社交媒体促进用户健身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是探究了影响人们使用健身App的主要因素(崔洪成,陈庆果,2020)、人们如何选择健身App(骆意,2017;王茜,2018),以及这些健身App如何影响人们的运动习惯(张明新,廖静文,2018;刘传海,王清梅,钱俊伟,2015;何军,黄宏芮,2017)。然而,针对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人们健身意向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考察。
基于此, 本研究选择社交媒体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会行为规范理论(Theory of Normative Social Behavior)(Lapinski & Rimal, 2005;Rimal & Lapinski, 2015)作为理论框架,从群体层面揭示社交媒体对个人健身意向的影响,并探讨如何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健康传播。此外,本研究以运动健身为研究语境(Context),试图解释社交媒体如何通过影响人们对社会规范的判断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意向,从而从社会行为规范理论视角对社交媒体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作出进一步阐释。
二、文献综述
(一)社交媒体、社会影响与社会行为规范
以往相关文献显示,运动健身类App和社交媒体在运动健身的促进中主要发挥两大类作用。其一是提供专业知识、专业服务的工具属性。作为一种工具,运动健身类App为用户提供消耗的卡路里、运动距离等数据,帮助用户更科学地进行健身,培养其健身意向与运动习惯(Zhu et al., 2017)。国外相关研究表明,运动健身类App最核心的两个功能是模仿学习与自我监督(Belmon et al., 2015)。而针对国内运动健身类App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绝大多数运动健身类App具有教学展示(模仿学习)和自我监督两大功能(Huang & Zhou, 2020)。相关研究发现,用户对这些功能的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能对运动健身类App使用产生积极态度(骆意,2017)。
此外,运动健身类App与社交媒体还通过社交和社会动员以实现健康传播与健康促进的效果。例如,一项基于健身App用户数据的研究表明,用户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影响其锻炼行为(Meng, 2016)。因此,传播学者对运动健身类App与社交媒体的这种网络社区属性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归纳出三种与网络社区属性相关的影响机制——社会支持、社会比较、社会竞争。首先,有学者发现,运动健身类App与社交媒体中用户交换的信息支持、情感支持等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会对其健身行为产生积极影响(Korda & Itani, 2011)。第二,有研究指出,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关于自身形象的照片会致使用户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形体与好友的形体进行比较(Arroyo & Brunner, 2016)。这种比较会提升个体的健身意向(Peng et al.,2019)。最后,与社会比较相关的是,社交媒体可能会引发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ng)的形态,由此促进健身意向(Zhu et al., 2017)。
值得一提的是,运动健身类App与社交媒体在健身促进中发挥的两大类作用恰好对应影响健身行为的个体层面(提供专业知识和服务)和群体层面的社会影响因素。本研究试图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社交媒体对个体健身施加社会影响的另一种机制——社会规范(Social Norm)。社会行为规范理论指出,社会规范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Lapinski & Rimal,2005;Rimal & Lapinski, 2015)。特别在“集体主义”文化相对盛行的中国社会中,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可能远胜于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和大众媒体一样,社交媒体也能营造一种拟态环境,通过重新建构拟态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了社会行为规范理论作为研究视角,试图在群体层面上解释社交媒体对个人健身意向的影响。
(二)社会行为规范理论:运动社会规范和运动意向
社会行为规范理论( Theory of Normative Social Behavior)由Lapinski和Rimal于2005年基于社会规范这一概念提出。社会规范这一概念指出,由于人类的社会属性,人类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社会规范行事(Cialdini, Reno & Kallgren, 1990)。社会规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某个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环境(Cialdini, Reno & Kallgren, 1990。因此,Cialdini等人(1990)强调,社会规范具有边界性;某一群体内的社会规范只会影响这一群体内的个体而不会影响所有人。此外,社会行为规范理论还将社会规范分为两类:描述性社会规范(Descriptive norm)和指令性社会规范(Injunctive norm)。前者被定义为绝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情,后者则被定义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合理的事情(Cialdini, Reno & Kallgren, 1990)。因此,描述性社会规范反映出某个行为的普遍性,指令性社会规范则反映出大众对某个行为的支持度(Park & Smith, 2007)。
在此基础上,Lapinski 和 Rimal(2005)进一步阐明了社会规范对行为的影响机制。他们指出,社会规范可以分为真实的社会规范(Actual Norm)和感知到的社会规范(Perceived Norm),前者指的是实际存在的社会规范,后者则是人们对实际存在的社会规范的一种判断,是对群体性因素的内化(Lapinski & Rimal, 2005)。虽然前者更真实客观,但Lapinski 和Rimal(2005)却认为后者对人类行为影响更大,因为人们总是按照自己对实际情况的判断行事。这一论断获得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一些关于饮酒行为的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生总会高估校园里真实的喝酒社会规范,这种误判导致他们为了融入校园生活而过量饮酒(Borsari & Carey, 2003;Perkins & Wechsler, 1996)。因此,影响美国大学生饮酒行为的并不是校园里真实的饮酒规范,而是这些大学生认知中的校园饮酒规范(Borsari & Carey, 2003;Perkins & Wechsler, 1996)。此外,在健康传播领域中,该理论还被用于控烟(Lee et al., 2007)、环保公益(Gockeritz et al.,2010;Goldstein et al., 2008)和青少年性行为(van de Bongardt et al., 2015)等研究。
对于运动健身而言,虽然已有研究考察社会行为规范理论对于运动健身的影响(Carpenter & Amaravadi, 2019; Okun et al., 2002),但对于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个体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塑造这一关键问题却未做出解释。Lapinski 和 Rimal(2005)认为,社会行为规范理论未就个体对相关社会规范的判断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他们认为涵化理论为从媒体的视角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本研究将首先解答,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用户对运动社会规范的判断——包括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社会规范和指令性运动社会规范。然后,本研究将进一步考察用户对这两种运动规范的判断如何影响他们运动健身的意向。
(三)媒体塑造的运动规范及其影响
在媒介化社会的背景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判断越来越依赖媒体的塑造。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依靠大众媒体建构出的拟态环境了解社会现实(李普曼,2016:21)。例如,通过分析美国黄金时间的电视节目内容,Gerbner发现这些节目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内容,而收看这些暴力节目越多的观众认为现实世界越不安全(Gerbner, 1998)。Shrum(1995)发现,受众使用媒体的时间越长,不但对现实环境的判断与媒体建构出的现实(以下简称“媒体现实”)越接近,而且这种判断是基于他们的下意识反应。换言之,长期接触媒体可以使受众将媒体现实内化为自己认知的一部分,从而影响受众认知和相关行为。
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也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具体到健康行为,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有关某一行为的信息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这一行为的普及程度(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大众对这一行为的认可程度(指令性社会规范)的判断。例如,Rui 和Stefanone(2017)发现,社交媒体用户对饮酒的社会规范的判断受到他们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发的喝酒照片和视频数量的影响;好友社交媒体主页上饮酒的照片和视频越多,用户越容易认为多数人都认为喝酒是可取的(指令性社会规范)。Duong和Liu(2019)发现,社交媒体上有关电子烟的信息与人们认为电子烟的普及程度(描述性社会规范)呈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相关研究,笔者认为,社交媒体上用户好友分享个人运动信息的频率将影响他们对运动社会规范的判断。首先,如果用户的好友经常分享运动信息,会给用户留下一种印象,即他的社交圈中很多人在锻炼。这种有关运动普遍性的判断正好是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其次,如果用户的好友经常分享运动信息,用户可能会认为,他的社交圈中很多人都认同锻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对运动支持度的判断,恰好是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正向影响了运动的描述性规范的判断。
H2: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正向影响了运动的指令性规范的判断。
其次,社会行为规范理论的后续研究表明,两种社会规范对人类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指令性规范代表了大多数人如何看待某一行为,因此指令性规范可被视为有关行为准则的风向标(Lapinski & Rimal, 2005;Rimal & Lapinski,2015)。相反,描述性规范仅仅表明多少人正在做一件事,所以描述性规范并不能作为行为准则的判断依据。因此,指令性规范应当比描述性规范对人类行为产生更强的影响。例如,关于环保公益(Goldstein et al., 2008)与控烟(Lee et al., 2007)的实证研究侧面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设。这两项研究表明,指令性规范是描述性规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调节变量(Goldstein et al., 2008;Lee et al., 2007)。具体来说,人们并不盲目服从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追随大多数人做某件事。相反,只有当感知到的指令性规范较高时,描述性规范才会对人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因为指令性规范较高表明一个人认为大多数人都支持某件事,所以他才会追随大多数人(描述性规范)去做这件事(Goldstein et al., 2008; Lee et al., 2007)。相反,当指令性规范较低时,描述性规范对人类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时人们认识到大多数人并不支持某件事,所以他们并不会盲目跟风(Goldstein et al., 2008; Lee et al., 2007)。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是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与运动意向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当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较高时,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对运动意向产生正向影响;当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较低时,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对运动意向不产生任何影响。
H4: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对运动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了一个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H1和H3)和一个中介效应模型(H2和H4)。图1与图2展示了这两个模型。
H5: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通过影响用户对运动的描述性规范的判断来影响用户的运动行为,这一中介关系受到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的调节。
H6: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通过影响用户对运动的指令性规范的判断来影响用户的运动行为。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与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问卷星收集数据。笔者将目标人群限制在健身App的使用者,因为与普通人群相比,该人群的健身意向可能受到社交媒体和健身App的双重影响。通过在数据分析时控制健身App的使用频率,可以排除健身App的影响,从而发现社交媒体对塑造个体运动意向的独特作用。根据文献综述,运动健身类App与社交媒体是当前两类用于运动促进干预的代表性新媒体平台。前者更多是在个体层面为个人健身提供工具性服务,提高其健身意愿;后者则是在群体层面促进个体的运动意愿。这一研究设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健身App和社交媒体作用的机会。
根据极光大数据的调查,截至2018年6月,我国健身App用户年龄分布如下:25岁及以下占45.4%,26-35岁占40%,36岁及以上占14.6%。本研究因此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抽样。收到样本840份,去掉无效问卷33份,总计有效问卷807份。最终样本中,25岁及以下者占44.6%,26-35岁占40.4%,36岁及以上占15%,基本与上述年龄分布比例一致。
所有受访者中,男性为364名,占总数的45.1%。超过七成(72.7%)的被访者有大学本科文凭,13.9%的被访者有专科文凭,8.4%的被访者有硕士及以上文凭,4.1%的被访者有高中文凭,0.7%持有初中文凭,0.1%只有小学文凭。家庭收入方面,近四成(39.7%)的被访者家庭月收入在12501-38500元之间,26.4%的被访者家庭月收入在8001-12500元之间,15.9%的被访者家庭月收入在5001-8000元之间,8.8%的家庭月收入在3501-5000元之间,5.6%的家庭月收入在38501-83500元之间,2.5%的家庭月收入低于3500元,1.2%的家庭月收入超过83501元。这些家庭收入的区间来自于毕马威2017年对中国家庭收入的调查结果。
表1展示了样本数据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相关基本人口统计数据的差异。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相关基本人口统计变量,我们的样本教育程度偏高、年龄偏低。这也许是因为运动健身类App用户存在教育程度高、年龄偏低的特点。
(二)问卷设计
被访者要求对接下来一个月他们会坚持运动的可能性做出评估(1=完全不可能,5=非常有可能)。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会坚持锻炼(M=4.36,SD=0.76)。
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由5道李克特量表问题测量。被访者要求评估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自己朋友、同事或亲戚分享他们运动健身时的图片、文字、运动数据、健身前后对比的图片,以及关于运动的励志文字或图片的频率:1=从来没有,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是(Cronbach’s α=0.77, M=3.19, SD=0.69)。
两种关于运动的社会规范的判断由Park 和 Smith (2007)的社会规范量表改编而来。运动的描述性规范(Cronbach’s α=0.79,M=3.65, SD=0.83)和指令性规范(Cronbach’s α=0.67, M=4.24, SD=0.58)均由3道李克特量表问题测量。
本研究有五个控制变量:性别(1=男,2=女)、受教育程度(M=5.84, SD=0.67)、家庭收入(M=4.14, SD=1.20)、年龄(M=28.56, SD=6.94)、健身App使用频率(Cronbach’s α=0.75, M=3.21, SD=0.72)。首先,许多研究表明,健身习惯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越关注健康,也就越积极健身。因此,需要控制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运动习惯的影响。此外,由于本研究的目标人群是健身App的使用者,而健身App的使用可能会影响人们对运动社会规范的判断和他们的运动意向。例如,使用健身App越多,人们可能认为有越多的人在运动,这些人本身可能也越容易养成运动的习惯。因此,笔者将健身App的使用频率也纳入了控制变量的范围。最后,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健身App用户分布存在差异,本研究将年龄也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统计方法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调节的中介模型和一个中介模型。所以,本研究采用Process Macro 3.0检验研究假设。前者由Process Macro 3.0第14号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H1, H3, H5),后者由Process Macro 3.0第4号中介模型检验(H2, H4, H6)。
四、研究发现
数据统计的结果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调节的中介模型。首先,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性别、年龄和健身App使用频率之后,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仍然对描述性运动规范的判断产生了正向影响(β=0.36, p<0.001, R2=0.29, F(6,800)=55.65, p<0.001)。H1得到支持。
第二,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调节了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对于运动意向的影响(β=0.07, p<0.05)。因此,H3得到支持。
最后,由于调节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1,0.09】(β=0.03),不包括0,因此调节的中介效应也是成立的。当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较低时,经由描述性运动规范中介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运动信息的频率对运动意向的影响是不显著的(β=0.02,95%置信区间:【-0.02,0.05】)。当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较高时,该中介效应是显著的(B=0.06,95%置信区间:【0.02,0.10】)。所以,H5也成立。
控制变量方面,家庭月收入越高的人,运动意向越强烈(β=0.07, p<0.05),但其对运动的描述性规范判断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对运动的描述性规范判断产生积极影响(β=0.02, p<0.001),但对于运动意向影响不显著。教育程度与性别对这两者的影响均不显著。健身App的使用频率对描述性运动规范的判断(β=0.21, p<0.001)和运动意向(β=0.34, p<0.001)的影响均为正向。
中介模型也得到了验证。首先,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性别、年龄和健身App使用频率之后,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仍然对指令性运动规范的判断产生了正向影响(β=0.19, p<0.001, R2=0.09, F(6,800)=12.59, p<0.001)。H2得到支持。
其次,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对运动意向产生了正向影响(β=0.11, p<0.001,R2=0.23, F(7799)=33.95, p<0.001)。H4得到支持。
最后,经由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中介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运动信息的频率对运动意向的影响是显著的。因为其95%置信区间(【0.01,0.04】)不包括0(β=0.02)。所以H6成立。
控制变量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认为大众对运动的支持度越高(β=0.08,p<0.05),但其对运动意向的影响不显著。家庭月收入越高的人,运动意向越强烈(β=0.10, p<0.01),但其对有关指令性运动规范的判断影响不显著。年龄与性别对两者的影响均不显著。健身App的使用频率对指令性运动规范的判断(β=0.08, p<0.05)和运动意向(β=0.37, p<0.001)的影响均为正向。
五、总结与讨论
尽管新技术影响了普通人的运动健身方式,但绝大多数国内研究都聚焦于运动健身类App(何军,黄宏芮,2017;刘传海,王清梅,钱俊伟,2015;骆意,2017;王茜,2018,张明新,廖静文,2018),且较少有研究从群体层面因素研究社交媒体对健身行为或意向的影响。随着运动的社会网络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越来越突出,本研究选择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探索社交媒体如何对用户个人施加影响。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对运动意向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人们对运动的社会规范的判断来实现的。
首先,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性别、年龄和健身App的使用频率五个变量之后,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直接影响了用户对运动规范的判断。好友分享运动信息越频繁,人们便认为运动越普遍(描述性规范),也认为大众对运动的支持度越高(指令性规范)。因此,社交媒体上由好友分享的运动信息可以影响人们对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规范的认知和判断。
这个结论与之前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此前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体(Nan & Zhao, 2016)和社交媒体上的内容(Carpenter & Amaravadi, 2019; Dana & Michelle, 2011; Duong & Liu, 2019; Rui & Stefanone, 2017)可以影响人们对有关某一行为的普及程度及支持度的判断。这些研究结果可以通过社会建构理论进行解释。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社会中既定的“知识”先于个人的经验存在,并且能够经过客观化等一系列过程实现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09:1-3)。而媒体具有现实建构的功能,即通过运用符号手段建构媒介现实,从而影响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因此,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通过其发布的媒介内容和讯息建构符号世界;人们也是通过这个符号世界去认识真实的社会。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曾提出大众媒体具有社会约束的属性,即大众媒体有能力填补“个人态度”与“公共道德”之间的间隙,从而避免人们偏离社会规范,实现维护主流道德标准的目的(Lazarsfeld & Merton, 1960:492-512)。本研究的发现是对这一结论的进一步延伸。具体而言,本研究和之前一系列研究(Carpenter & Amaravadi, 2019; Dana & Michelle, 2011;Duong & Liu, 2019; Rui & Stefanone, 2017)都指出,社交媒体会影响人们对社会规范的判断。大量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学的一项基本假设是,人类的社会属性会促使其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因为集体的智慧往往也适用于个体和小群体(Lapinski & Rimal, 2005)。因此,社会规范具有规训个体、统一思想的作用(Rimal & Lapinski, 2015)。在社交媒体环境下,鉴于社交媒体已成为获取信息与互动交流的主要渠道(张洪忠,石韦颖,2020),因此,社交媒体也同大众媒体一样,具有统一思想认识、规范个体行为的潜质,也因此具备了社会约束的功能。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规范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传播而被建构(Lapinski & Rimal, 2005;Rimal & Lapinski, 2015),由此实现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的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的社会约束功能稍有不同。大众媒体是一种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向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传播者居于主导地位,而受众被动地接受大众媒体灌输的信息。因此,由大众媒体进行的社会约束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心理阻抗(Psychological Reactance)理论认为,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自由选择被侵犯时,他们会以种种形式反抗外界环境对自由的约束(Brehm & Brehm, 1981)。因此,由大众媒体进行的社会约束可能在规训的过程中遭到个体的反抗。相反,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是由用户主动发起的。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中的虚拟社区的形成是一个自我组织的过程(Self-organizing Process;Meng,2016)。社交媒体中的用户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与社会实践建构规范,从而发挥规范群体行为的作用( Dana & Michelle, 2011; Duong & Liu, 2019; Rui & Stefanone, 2017)。这一过程缺少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机制。因此,社交媒体的社会规范往往是由用户自行主导。用户通过生产并分享内容,在社交媒体上营造出一种氛围,即某一行为很普遍或享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度。这种氛围会影响其他用户对社会规范的判断,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规范了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社交媒体的社会约束主要依赖用户完成。相较于大众媒体,这种社会约束的强制性色彩较弱,可能引发的个体反抗较少,因此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用户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运动信息的频率对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的影响(β=0.36)比对感知到的指令式运动规范的影响更强(β=0.19)。这一研究结论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论不一致(如Rui & Stefanone, 2017)。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并不了解自己的社交圈中有多少人正在锻炼,而社交媒体的运动分享功能恰好可以为用户提供这一信息(Carpenter & Amaravadi, 2019)。相反,指令性规范指的是大多数人是否赞同某一行为。具体到运动这一行为上,几乎所有人都了解并认同运动的重要性。因此,人们并不需要通过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运动信息来判断运动的指令性规范。相比之下,Rui 与Stefanone(2017)的研究对象是喝酒。相对于运动健身而言,人们对喝酒这一行为存在一定争议。例如,喝酒在很多社会中都被认为是社交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喝酒、特别是酗酒又被认为是有违道德的。因此,在Rui与Stefanone(2017)的研究中,社会对目标行为的评价是存在一定争议的。这时,人们可能更依赖于平时接触的媒体对有关这一行为的社会规范作出判断。据此,笔者推断,社交媒体对两种社会规范判断的影响应当取决于具体的目标行为。如果该行为是存在一定争议性的(如喝酒),社交媒体可能对指令性社会规范的影响更强。但如果该行为不存在任何争议性(如运动),社交媒体对描述性社会规范的影响可能更强。
此外,本研究对两种社会规范如何影响运动意向也进行了解释。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对运动意向的影响取决于感知到的指令性规范。只有当感知到的指令性规范高的时候,即用户认为大多数人都认同运动的重要性时,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才会对运动意向产生影响。相反,如果用户认为自己身边的很多人都不认同运动的重要性时,他们便不会服从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这一发现再次体现了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对行为影响的局限性(Goldstein et al., 2008; Lee et al., 2003)。人们并不会盲目跟随大多数人做某件事,相反,他们会根据感知到的指令性社会规范去做大多数人都认为正确的事。另一方面,任何情况下,感知到的指令性规范都会激发人们的运动意愿。这一发现再次体现了两种社会规范的区别;描述性规范只能为人们提供参考的依据,只有指令性规范才会成为人们的行事准则。因此,指令性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更强。这一发现与以往相关文献结论相一致(Goldstein et al., 2008; Lee et al., 2003),并通过提供运动健身这一新的研究对象,拓展了该理论机制的适用语境。
基于这个结论,联系到前文笔者做出的推断,如果社交媒体对具有争议性行为的指令性规范影响更强,那么,社交媒体在社会约束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一方面,通过营造、影响拟态环境中的舆论,社交媒体可以影响人们对指令性社会规范的判断,进而统一人们对具有争议性行为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可以影响人们对指令性社会规范的判断,社交媒体能营造出一种假象,即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某一行为。这样,持不同意见的人可能迫于压力选择沉默,这就体现了沉默的螺旋的作用(Noelle-Neumann, 1974)。因此,社交媒体的社会约束功能,可能是涵化效应、社会规范、沉默的螺旋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后,本研究将健身App的使用频率作为控制变量,从而可以在排除健身App的影响之后,了解社交媒体对有关运动的社会规范的判断和运动意向的独特影响。这一研究设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健身App和社交媒体作用的机会。总体上,在影响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和指令性运动规范上,健身App的作用(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β=0.21, p<0.001;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β=0.08, p<0.05)不及社交媒体(感知到的描述性运动规范:β=0.36, p<0.001;感知到的指令性运动规范:β=0.19, p<0.001)。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规范的边界性造成的。Cialdini 等人(1990)指出,社会规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个群体的社会规范并不适用于另一个群体。由于社交媒体已成为辅助线下社交的重要工具,社交媒体上的多数好友都是现实中的朋友。所以,人们可通过社交媒体上好友发布的信息推断出身边人的社会规范。但是,健身App上形成的网络社群更多是基于健身的共同兴趣,属于超越地域的趣缘性社交。因此,从健身App上好友发布的信息不一定能直接推断出“身边人”的社会规范。更大的可能是,人们通过推断健身App用户中的社会规范来推测身边人的社会规范。
在对运动意向的直接影响上,健身App的作用更强,因为社交媒体对运动意向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使用健身App越频繁,人们运动的意愿就越强。反之,社交媒体的最主要属性仍然是互动、社交与社会动员,所以主要通过向用户施加关于运动的社会影响进而达到促进健身的效果,而不能对用户的运动意向施加直接影响。
从健康传播的角度看,本研究也丰富了健康促进的理论文献。本研究不但考察了社交媒体对于运动意向影响这一国内研究较少涉及的问题,而且从社会规范的角度丰富了新技术对健康行为影响的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不但突破了在个体层面对运动健身类App影响个体健康管理的探讨(张明新,廖静文,2018;刘传海,王清梅,钱俊伟,2015;何军,黄宏芮,2017),更是对群体层面新媒体如何通过向个体施加社会影响促进其健身运动的研究的进一步拓展(Arroyo & Brunner, 2016; Korda & Itani, 2011; Meng, 2016; Zhu et al., 2017)。通过指出社交媒体对个人运动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建构社会规范完成的,本研究对群体层面上新技术对个体健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拓展。
除了以上理论贡献,本研究对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运动干预乃至广义的健康行为干预都提供了一些思路。既然社交媒体能影响人们对社会规范的判断,政府和社会团体就应该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建构有关运动和健康的社会规范。具体来说,政府和健康宣教机构可以鼓励用户分享运动健康的文字、图片和视频,鼓励他们分享自己运动健身的状况和健康管理的心得体会,调动他们参与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政府和健康宣教机构还应当积极引导社交媒体上有关运动和健康管理讨论的舆论,重点放在引导公众认识运动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通过这些举措,营造出一种大多数人都在参与健身和健康管理(描述性规范)并认同健身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指令性规范)的氛围。
本研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本研究的样本仅局限于健身App的使用者,并未覆盖所有人。虽然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已经控制了健身App的使用频率,但这一样本仍然可能影响本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如前文所述,与我国人口相比,本研究的样本受教育程度偏高且年龄偏小。所以,未来的研究可匹配全国人口的特征,检验本研究提出的模型是否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其次,运动的指令性规范的信度只有0.67,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内部效度。此外,本研究对社交媒体上用户分享运动信息的频率的测量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问卷调查法,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偏差。更精确的测量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来实现。
综合本研究的发现,社交媒体通过改变人们对运动社会规范的判断来影响人们的运动意向。因此,通过鼓励用户生产和分享内容,社交媒体建构了一个拟态环境,在潜移默化中通过影响人们对宏观层面的社会规范的判断,以用户相互影响的方式完成了社会约束的目的。社交媒体的这一属性为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健康促进开辟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参考文献: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09)。《现实的社会建构》(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体强(2021)。微信十周年,2021微信公开课Pro和张小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答案?检索于https://news.163.com/21/0121/12/G0S68VMB00019OH3.html。
崔洪成,陈庆果(2020)。移动健身App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究。《首都体育学院学报》,32(1),75-81。
何军,黄宏芮(2017)。运动类APP对体育锻炼行为促进和体育习惯养成的影响。《体育世界》,(3),62-63。
极光(2018)。《健身运动app用户规模过亿,女性占比超六成》。检索于http://www.sohu.com/a/243359370_100012744。
刘传海,王清梅,钱俊伟(2015)。运动类APP对体育锻炼行为促进和体育习惯养成的影响。《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9(3),109-115。
骆意(2017)。基于TAM的大学生移动健身APP使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9(1),72-77。
王茜(2018)。社会化、认同与在场感:运动健身类APP用户的使用动机与行为研究。《现代传播》,40(12),149-156。
张洪忠,石韦颖(2020)。社交媒体兴起十年如何影响党报公信力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7(10),39-55。
张明新,廖静文(2018)。健身运动app使用对用户跑步意向的影响——以计划行为理论为视角。《新闻与传播评论》,71(2),85-98。
ArroyoAnalisa; BrunnerSteven R. (2016). Negative body talk as an outcome of friends’ fitness post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body surveillance and social comparison as potential moderator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44 (4)216-235.
Belmon LS, Middelweerd ATe Velde SJ, Brug J. Dutch Young Adults Ratings of Behavior Change Techniques Applied in Mobile Phone App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JMIR Mhealth and Uhealth. 2015 Nov3(4)e103.
Borsari, B.& CareyK. B. (2003). Descriptive and injunctive norms in college drinking: A meta-analyt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64331-341.
Brehm, S.S.& BrehmJ.W. (1981).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control.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Carpenter, C. J.& AmaravadiC. S. (2019). A big data approach to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norms: Reporting one’s exercise to a social media aud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236-249.
CialdiniR.B.Reno, R.R.& Kallgren, C.A. (1990).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Recycling the concept of norms to reduce littering in public pla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1015-1026.
DanaM. L.Michelle, L.S. (2011). Adolescent alcohol-related risk cognitions: The roles of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25(4)708-713.
Duong, H.T.& LiuJ. (2019). Vaping in the news: The influence of news exposure on perceived e-cigarette use norm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50(1)25-39.
Gerbner, G. (1998). Cultivation analysis: An overview.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1175-194.
Gockeritz, S.SchultzP.W.Rendon, T.Cialdini, R.B.GoldsteinN.J.& Griskevicius, V. (2010). Descriptive normative beliefs and conservation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ersonal involvement and injunctive normative belief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514-523.
Goldstein, N. J.Cialdini, R. B.& Griskevicius, V. (2008). A room with a viewpoint: Using social norms to motiv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hotel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472-482.
WeaverJ. (2013).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and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organizations being truly social. Public Health Reviews351-18.
Huang, G.& Zhou, E. (2018). Time to Work Out! Examining the Behavior Change Techniques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Mechanisms that Predict the Popularity of Fitness Mobile Apps with Chinese-Language User Interfaces. Health Communication34(12)1502-1512.
Korda, H.& ItaniZ. (2011). Harnessing social media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behavior change.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14(1)15-23.
LapinskiM. K.& RimalR. N. (2005). An explication of social norms. Communication Theory, 15127-147.
LazarsfeldP.E. & Merton, R.K. (1960). Mass communication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W.L.Schramm (ed.)Mass Communications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ee, C.GeisnerI.LewisM.NeighborsC.& LarimerM. (2007). Social motive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escriptive and injunctive norms in college student drinking.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68714-721.
LittDana M.; StockMichelle L. (2011). Adolescent alcohol-related risk cognitions: The roles of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25(4)708-713.
MengJ. (2016). Your health buddies matter: Preferential selec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on weight management in an online health social network. Health Communication311460-1471.
Nan, X.& Zhao, X. (2016).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descriptive and injunctive norms in the effects of media messages on youth smo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156-66.
Noelle-Neumann, E. (1974).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443-51.
OkunMorris A.; Karoly, Paul; Lutz, Rafer (2002). Clarifying the Contribution of Subjective Norm to Predicting Leisure-Time Exercise.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Behavior, 26(4)296-305.
ParkH. S.& SmithS. W. (2007). Distinc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normspersonal descriptive and injunctive normsand societal descriptive and injunctive norms on behavioral intent: A case of two behaviors critical to organ don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194-218.
PengC.T.Wu,T.Y.Chen,Y.& AtkinD.J.(2019).Comparing and modeling via social media:The social influences of fitspiration on male instagram users’ work out intention.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99156-167.
Perkins, H.W.& Wechsler, H. (1996). Variation in perceived college drinking norms and its impact on alcohol abuse: A nationwide study. Journal of Drug Issues, 26961-974.
(2018) Social media use continues to ri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plateaus across developed ones: Digital divides remain, both within and across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ewglobal.org/2018/06/19/social-media-use-continues-to-rise-in-developing-countries-but-plateaus-across-developed-ones/
Rimal, R.N.& Lapinski, M.K. (2015). A re-explication of social normsten years later. Communication Theory, 25(4)393-409.
Rui, J. R.& StefanoneM. A. (2017). Assessing drinking norms from attending drinking events and using social network sites. Proceedings of The 50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3736-3745.
Shrum, L.J. (1995). Assessing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elevsion: A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 on cultivation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4)402-429.
van de Bongardt, D.ReitzE.Sandfort, T.& Dekovic , M. (2015).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ree types of peer norms and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9203-234.
PengT. Q. (2016). An examination of users’ influence in online HIV/AIDS communities. Cyberpsychology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19(5)314-320.
Centola, D. (2015). Efficacy and causal mechanism of an online social media intervention to increase physical activity: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2651-657.
Zhu, Y.G.Dailey, S. L.Kreitzberg, D. & BernhardtJ.(2017). “Social Networkout”: Connecting Social Features of Wearable Fitness Trackers with Physical Exercis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2(12)974-980.
刘双庆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新闻研究所副所长,芮牮(通讯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移动传播时代我国中央级党报内容生产转型研究”(批准号:20XBW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