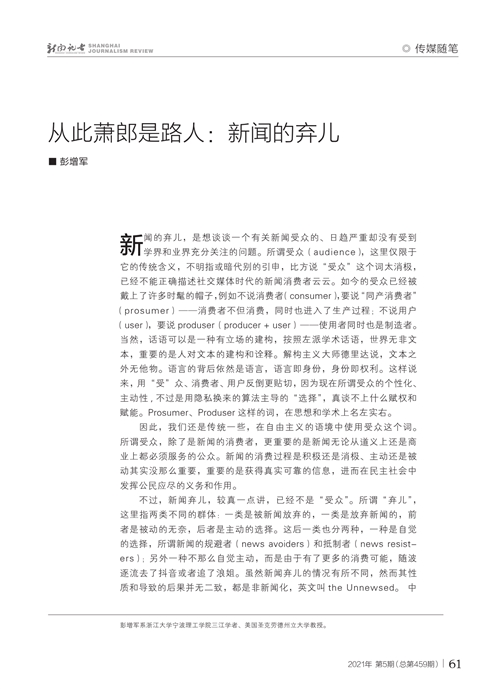从此萧郎是路人:新闻的弃儿
■彭增军
新闻的弃儿,是想谈谈一个有关新闻受众的、日趋严重却没有受到学界和业界充分关注的问题。所谓受众(audience),这里仅限于它的传统含义,不明指或暗代别的引申,比方说“受众”这个词太消极,已经不能正确描述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消费者云云。如今的受众已经被戴上了许多时髦的帽子,例如不说消费者(consumer),要说“同产消费者”(prosumer)——消费者不但消费,同时也进入了生产过程;不说用户(user),要说produser(producer + user)——使用者同时也是制造者。当然,话语可以是一种有立场的建构,按照左派学术话语,世界无非文本,重要的是人对文本的建构和诠释。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语言的背后依然是语言,语言即身份,身份即权利。这样说来,用“受”众、消费者、用户反倒更贴切,因为现在所谓受众的个性化、主动性不过是用隐私换来的算法主导的“选择”,真谈不上什么赋权和赋能。Prosumer、Produser这样的词,在思想和学术上名左实右。
因此,我们还是传统一些,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中使用受众这个词。所谓受众,除了是新闻的消费者,更重要的是新闻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商业上都必须服务的公众。新闻的消费过程是积极还是消极、主动还是被动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进而在民主社会中发挥公民应尽的义务和作用。
不过,新闻弃儿,较真一点讲,已经不是“受众”。所谓“弃儿”,这里指两类不同的群体:一类是被新闻放弃的,一类是放弃新闻的,前者是被动的无奈,后者是主动的选择。这后一类也分两种,一种是自觉的选择,所谓新闻的规避者(news avoiders)和抵制者(news resisters);另外一种不那么自觉主动,而是由于有了更多的消费可能,随波逐流去了抖音或者追了浪姐。虽然新闻弃儿的情况有所不同,然而其性质和导致的后果并无二致,都是非新闻化,英文叫the Unnewsed。 中文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叫“非闻者”、“脱闻者”?似乎有些别扭。先不纠结,就说Unews是新闻与公众的脱钩吧。
无论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数字智能时代 , 新闻同自己的目标对象脱节都是致命的。何况在社交媒体社会数字化生存中,连一个网络小博主都知道要接触黏连(engagement)。新闻弃儿的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必然导致新闻受众的彻底流失,专业新闻成为一种仅供精英和权力阶层享用的奢侈品。只要稍微脑补一下新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就不难明白这不仅仅关乎个体身心——比如新闻弃儿在信息时代的生存,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
这里我们简单讨论一下新闻弃儿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包括产生的原因以及救赎的可能思路和途径。而在新闻的弃儿中,讨论的重点放在那些主动、自觉抛弃和抵制新闻的人。从这一点来说,文章的题目叫新闻的弃者似乎更合适。然而,如果深究,新闻的弃者也好,弃儿也罢,归根结底,都是新闻业失范造成的遗弃。成为路人的萧郎,原也是因为“你若无心我便休”,所以题目还是用了比较顺口的新闻的弃儿。
谁在断舍离
受众流失乃老生常谈。互联网出现以后,传统新闻业失去了垄断地位,相对于过去,受众有了更多选择,因此,有关受众流失讨论的基调通常是:新闻生态改变导致新闻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落伍,是个大环境大气候问题。然而,新闻的弃儿虽然也是受众流失,却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第一类弃儿,是新闻沙漠化的直接后果,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新闻业遗弃。比如美国许多报纸主动劝退了远郊、农村的订户,因为发行成本太高,同时也放弃了对这些地区的报道。而后一大类可以说是受众的主动放弃,其中一大部分属于不爱新闻爱“绯闻”,为更愉悦的信息所吸引,而另外一部分则是自觉地逃避或者抗拒新闻,理由是新闻有害,不但满足不了信息需求,相反,过度的负面、负能量影响身心健康,天下苦秦久矣,于是造反,以至于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草根行动。有不少学者甚至为之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比如美国媒介心理学者杰克逊(Jodie Jackson)的《你读什么你就是什么:为什么改变媒体食谱可以改变世界》(You Are What You Read: Why Changing Your Media Diet Can Change the World)和瑞士作家杜拜礼(Rolf Dobelli)的《别看新闻:更幸福、更平静、更睿智生活宣言》(Stop Reading the News: A Manifesto for a Happier, Calmer and Wiser Life)。看作者背景,杰克逊有保守主义倾向,对自由派的新闻界不太友好可以想见,但是,讨论问题不应该以背景废观点,而更应该看其观点有没有道理。至于瑞士这位小说家,可能有人会质疑他算不上学者,但人家也是正经的经济哲学博士。他先前的一本《如何清晰思考》(How to Think Clearly)据称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销售百万册。也许有人说这更说明他不是严肃学者,是机场畅销书作家。好吧,让鄙视链发扬光大。然而,即使如此,躲避和抗拒新闻这个话题都引起了畅销书作家的注意,难道不更说明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吗?
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先对新闻的弃儿做个大致的界定。新闻的弃儿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无非是说被新闻放弃和放弃新闻的人。然而,如果去研究、去理论、去说事,就得有证据,有证据就不免要数据,要数据就得去测量,测量就得较真,较真就必须定义,而且要有操作性定义。你说新闻弃儿,怎么就算弃了?是三天不看电视还是三周不看手机?正如在冯小刚电影《天下无贼》中,刘若英教大款傅彪学英文,教一句:“You should be sorry to me。”傅彪舌头缠绕半天,磕巴地问:“怎、怎、怎么就to me了?!!!”
丹麦学者斯科加尔德(Morten Skovsgaard)和瑞典学者安德森(Kim Andersen)在一篇研究论文中给新闻规避者(news avoidance)做出如下定义:“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出于厌烦或者选取其他内容而导致的新闻的低消费。”我们这里把这个定义扩展和限定一下。扩展是想要包含那些被动放弃的,限定是要限定一下新闻的外延,收窄成对主流媒体严肃新闻的消费。笼统说新闻范围太大,娱乐新闻也是新闻,朋友圈消息也是新闻。当然这涉及如何定义的问题。因为讨论新闻弃儿的立足点是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在比较几种宽松和严苛的定义后,还是觉得舒德森的定义比较契合:“新闻指由新闻工作者提供的有关公共利益的新近发生的信息。”由此可以说:新闻的弃儿指在相当长的持续时间内,被动或者主动放弃了对主流媒体的严肃新闻消费的人。这里用放弃而不是低消费,也是考虑到操作上的方便。
当然,在具体的操作定义上,依然还有难点。比如说这个持续的时间应该多长,就需要通过概念的辨析和增加操作性定义的效度和信度来确定。前面提到的那篇北欧学者论文,在文献综述中总结了几种方法,简单说有两种,一种最省事,就是直接给出选项,问你是新闻的寻求者(news seeker)还是新闻的规避者(news avoider);另一种是绕个弯儿,不直接让你选帽子戴,而是问你新闻的消费情况,然后通过统计手段,找出一个中间值,然后把那些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算做新闻规避者。
那么,具体是何许人在断舍离呢?
新闻的弃儿首先是由于新闻沙漠化,被新闻所遗忘,掉入数字鸿沟的那些人。从绝对人口数量来讲,在全球范围是巨大的。多数是“老、少、边、穷”,即老年人、少数族裔、边远地区,和即使在城市也大量存在的贫民。后一类新闻规避者和抗拒者有多大规模呢?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新闻消费报告显示,2019年是全球平均人口的32%,2020年为20%。2020年有疫情特殊情况,因而2019年的数字应该比较可靠。而在美国,新闻规避者达到41%。当然,牛津报告中对规避者的定义比较宽泛,指新闻消费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的人,并不是完全抛弃新闻,所以,完全断舍离的人数可能要少一些。然而,牛津报告对新闻的定义也比较宽泛,如果限定为主流媒体的严肃新闻,那这个百分比估计又会膨胀一些,所以说大致在三分之一应该差不多。
在新闻的规避者中,人口特征是两低一高:年龄低、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放弃者中女性多于男性。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新闻的弃儿中,特别是新闻抵制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所谓的“蓝白美”——蓝领白种美国人,即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人阶层。美国劳工中,将近8000万人的小时薪酬不到15美元。也许国人对此没有概念,这样比较一下也许更清楚些:大学里勤工俭学的研究生助教每小时都要差不多50美元外加学费减免。这些“蓝白美”曾经是美国新闻受众的基本面,也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选票争夺的基本面。进入新世纪以来,“蓝白美”阶层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中非但没有受益,相反,其收入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而这个劳动阶层长期被两党所忽略,只有在需要选票时才被想起。共和党原本就代表保守有产阶级,而民主党也在逐步靠近技术和新兴资产阶层。同理,美国主流新闻界也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放弃了对这部分人的关注,如《纽约时报》曾有五位记者跑劳工新闻,而现在只有一个,小一些的报纸更是一个没有。而这部分人构成了2016年特朗普崛起的基本票仓,即使2020年的选举,特朗普的选票也有近7500万,只比拜登少700万而已。特朗普2016年的意外获胜,跌碎无数眼镜,引起学界对这部分劳动阶层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展田野研究,发表论文和专著。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赫迟谢尔德教授(Hochschild)的《家园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说这是一群“被遗忘、背叛、侮辱,愤怒的人”。北爱荷华大学传播系教授马丁(Christopher Martin)在新近出版的《再无新闻价值:主流媒体如何抛弃了工人阶级》(No Longer Newsworthy: How the Mainstream Media Abandoned the Working Class)一书中,对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工人阶层的忽视和背弃的原因、过程和后果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这个劳工阶层的分布,同新闻沙漠高度重合,也同新闻弃儿高度重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说美国主流媒体是人民的公敌,会引起那么多的认同和响应。
破碎的负面
造成新闻弃儿的原因很多。被遗弃的第一类,为新闻沙漠化的直接后果,不消多说。而主动放弃新闻的逃避者,从现有的调查研究结果来看不外乎下面几种原因:
排在首位的是新闻过多过滥。信息超载,人被湮没在资讯的深潭,呼吸急促,脑仁膨胀。传统媒体时代,普通受众早报纸晚电视,真正用于严肃新闻的时间最多一个小时左右,而现在,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刷屏,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24小时都在算计你,算计着你的胃口和口味,让人上瘾,欲罢不能。
其次是新闻无用,新闻肤浅、碎片化,一地鸡毛,基本是无关无用信息。所谓的个性化,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憧憬的Daily Me,实际上daily的都是别人家的事,是冲浪的姐姐或是吐槽的大叔。如果是真的Daily Me,也许应该是我的家人在干什么、老人的身体如何、孩子们怎样、老婆或者老公的心情好吗、我的宠物狗是不是需要体检、我朋友圈的人除了发朋友圈凡尔赛,还在干什么……
再而是对新闻媒体缺乏信任。最近几次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只有可怜的30%左右。新闻的生命是真实,而缺乏公众信任的真实不说没有价值,起码大打折扣。缺乏信任就更容易转向阴谋论,成为虚假新闻的温床。虚假新闻成本更低,而且更合大众口味,可谓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也真,真应了马克·吐温吐的一句槽:不读报纸,一无所知;读了报纸,一无所是。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普通受众对于新闻的来源并不关心,即使上了当,多半也会随口归罪于主流媒体。
还有一个原因是新闻过度负面。只有阴影,没有阳光,让人抑郁。这也许真是个问题。据美国心理学会的一项研究,约有半数的美国成年人由于新闻导致焦虑。大家都知道,健康的最大朋友是睡眠,最大的敌人是焦虑。焦虑使人免疫力下降,更易染病,更易早逝。
以上原因,大都可以理解,也不难同情。但是,最后一条有些触动神经。难道新闻的本质不是坏消息吗?俗话说,阳光灿烂不是新闻,暴风骤雨才是新闻。这难道有错?公众的看门狗,难道是用来报平安无事的?难道应该正面报道为主?这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应该承认,新闻存在所谓的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即所谓报忧不报喜。负面甚至可以说是新闻的传统“美德”。据说有一次,美国总统约翰逊对于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忍无可忍,挥舞着最新一期《时代》周刊对该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Luce)喊:“本周有20万少数族裔得以注册投票,30万老年人有了政府医疗保险,这里没有只言片语!”卢斯回答:“抱歉,总统先生,好消息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
从根本上说,负面新闻和正面新闻这些说法本身就不太严谨,容易成为随意的标签,被简单化和庸俗化。比如,2014年,俄罗斯有一家新闻网站,叫《城市报道》(city reporter),为了纠正负面偏差,决定在一天时间内,报喜不报忧,整个网站充斥着风景这边独好的标题:“雪后道路畅通”、“地下通道节前按时完工”等等,结果,阅读量骤减三分之二。
新闻的负面偏差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新闻的负面偏差不仅有理论根据和逻辑,而且有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理由,监控生存环境的威胁和危险乃生存本能和必需品。
当然,负面偏差除了自然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人为的推动。比如说,新闻界对负面新闻有一个自我激励机制,负面报道等于高质量报道的同义语,各类新闻奖的获奖报道几乎百分之百都是负面新闻。当然,不是说这些优秀的新闻报道不该奖励,然而,道理就怕反过来讲:严重的问题不在于你鼓励什么,而是你不鼓励什么。
实际上,问题不在于负面偏差,而在于如何报道负面;不是负面报道多与少,而是好与坏。负面的报道决不是为了负面而负面,负面报道的目的是激发社会良知,产生同理心,进而形成舆论,形成政治压力,从而实现正面效果。应该注意的是,解决负面偏差并不等同建设性新闻、解决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无论是解决还是建设,前提都是负面新闻,没有问题或者有问题没有揭露,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解决。
受众所抱怨的负面不是负面本身,而是负面报道的琐碎且肤浅。如今大数据可视化,可以报道得非常具体、非常漂亮,然而,数据中的人呢?政府在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负面新闻碎片犹如乐高拼图,大家只是在重复添加各种碎片,却无人去把这些碎片拼成一个有意义的图。
比如说,2007年夏天,美国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上的35号高速公路大桥垮塌,高速行驶的车流栽入河中,死伤150多人。几十家新闻媒体全力开动,全天候现场直播,死难的悲哀,幸存的侥幸,救人的英雄,悲壮感人。然而,在突发新闻报道以后,特别是各种误传和谣言充斥社交媒体之时,更为重要的新闻,恐怕是事故的原因以及即刻的危险。是否还有这样的危桥存在?在哪里?我开车通过的这座桥的安全状况如何?再如,最近美国各个城市都有歧视亚裔的恶性事件发生。游行示威、各界谴责,这些报道都很重要,然而,公众特别是亚裔更急切需要知道的是:我的社区有没有同类的事件发生?所在地的警察局有没有加强对某些地段的巡逻?新闻负面的庸俗化还在于其监督警示作用止步于鸡零狗碎,比如说某某好莱坞明星在商店偷窃被抓,而权贵通过修订税收政策堂而皇之地盗窃国库却无人报道。
后果与责任
新闻弃儿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那些新闻沙漠中的弃儿恰恰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处在信息生物链的末端。传统媒体十几年的危机与转型的结果是:70%的地方新闻机构消亡,形成新闻沙漠,转型成功的只是少数几个占有各种优势资源的新闻大鳄。而这些成功的新闻媒体却更加商业化、精英化和阶级化。新闻媒体逐渐转型成订户付费和广告并重的模式,而无论是广告还是付费墙,从商业逻辑和实践上都是以金钱歧视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新闻机构的从业人员也在逐渐精英化。传统媒体时代,记者多来自于草根阶层,多数出身于公立州立大学,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的新员工更多来自常春藤名校。
新闻规避者和抗拒者看似是主动的选择,其实也是因为对主流新闻媒体不满的无奈,并非完全放弃新闻,他们依然有信息需求需要满足。而这些人脱离了主流媒体以后,转向的是廉价的非专业的替代新闻,从而进入回音壁和信息茧房。这是造成社会分裂和另类真相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规避者不仅仅脱离社会,而且逐渐游离于家庭、朋友和同事之外,政治冷漠,玩世不恭,相当一部分产生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是美国心理学家赛里格曼(Seligman)首先提出的,指通过不断的挫折和失败而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随着新闻的荒漠化、抽象化和精英化,普通老百姓感觉到不到新闻的温度。新闻不但没有赋能,反而让人更加迷茫、抑郁和无助。当然,新闻的这个负面影响,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格伯纳(Gerbner)的涵养理论、波兹曼(Postman)的《娱乐至死》都是在讲这个问题。当然,那个时期的谴责对象多限于电视。
新闻弃儿问题该如何解决呢?造成新闻弃儿的原因不同,也需要不同的应对路径。
首先是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辨析和修正。比如如何认识新闻的负面偏差?赋权和赋能究竟是不是新闻的使命?新闻除了做看门狗外,是否还应该做导盲犬?这些问题以往讨论得相对较少,学者和业界甚至消费者都默认新闻负面偏差的理所当然,将中立、客观同赋能对立起来,任何偏离都被看做离经叛道、非专业。
再就是要把理论的修正落实到技术层面,比如如何增加新闻的相关性和建设性来超越新闻的负面偏差。
第三个最为根本,也是难度最大的,是如何在体制层面上改革。比如如何通过政策导向,消除新闻荒漠和信息鸿沟。作为公共产品的新闻,如果仍然完全依照商业模式运行,就必然是主观为金钱,客观顺便为公众。体制方面的变革,各种途径都可以尝试,比如通过立法打破平台垄断、保护公民隐私。难度太大的系统工程可以从小处开始,比如政府对大学的助学贷款可以向新闻传播专业倾斜,可以如同支持师范生那样,在学费上优惠,以吸收更多草根阶层的学生加入新闻传播领域。
新闻的根本目的在于赋能,这应该不难理解。你去问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新闻系的学生:你为什么要干新闻?回答恐怕不会是为了报道负面新闻或者做公众的看门狗,肯定还有重要的后半句,比如为了社会公平正义、为无声者发声等。
长期以来,无论学界还是业界,存在一个约定俗成的新闻有益的假设前提,却很少关注新闻造成的负面影响。受众对新闻的规避和抗拒,用行动传递了一个信号:如果放弃新闻成为一种主动的选择,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从此萧郎是路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萧郎不是单个的人或者一代人,新闻消费看起来是一种选择,实际上更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当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的家长都在规避和抛弃新闻的时候,你能指望下一代成为自己的受众?当然,也不能为了取悦受众而放弃新闻的使命。诚然,新闻有很强的负面偏差,但是,新闻(Journalism)是一个社会的疫苗,虽然有各种副作用,然而它维护的却是整个社会的健康。正如集体免疫才能抵抗瘟疫一样,新闻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民众。1999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说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不仅仅是煽情的口号,而应该是新闻的根本目的所在。恶行的惩处,正义的生长,才是最大的正能量。当然,如果新闻业铁了心要躲在付费墙里数钱,那自当别论,就不要再提什么公共服务。大家还是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吧。■
彭增军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