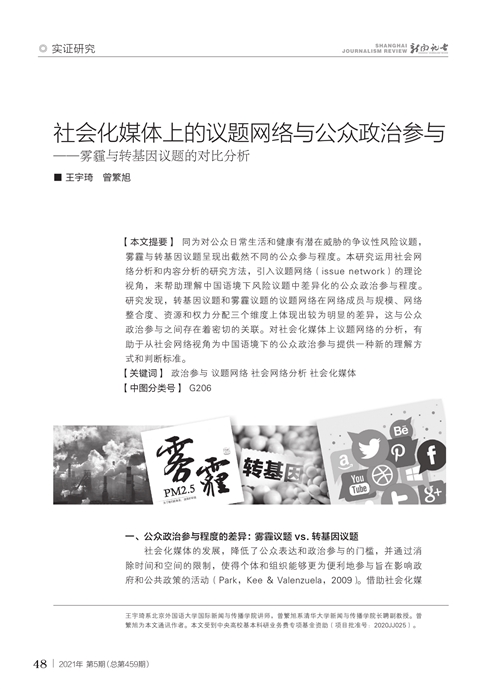社会化媒体上的议题网络与公众政治参与
——雾霾与转基因议题的对比分析
■王宇琦 曾繁旭
【本文提要】同为对公众日常生活和健康有潜在威胁的争议性风险议题,雾霾与转基因议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公众参与程度。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的理论视角,来帮助理解中国语境下风险议题中差异化的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研究发现,转基因议题和雾霾议题的议题网络在网络成员与规模、网络整合度、资源和权力分配三个维度上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与公众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对社会化媒体上议题网络的分析,有助于从社会网络视角为中国语境下的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和判断标准。
【关键词】政治参与 议题网络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化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差异:雾霾议题vs.转基因议题
社会化媒体的发展,降低了公众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门槛,并通过消除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个体和组织能够更为便利地参与旨在影响政府和公共政策的活动(Park,Kee & Valenzuela,2009)。借助社会化媒体平台,公众得以表达政策诉求、进行线上动员,甚至影响政策过程。①
在借助社会化媒体进行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公众表达越来越呈现出个人化、生活化的特征(Castells,2009: 53-69,412-415)。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公众讨论的议题更多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相连,借助个人化的表达框架和参与方式,对环境、健康、公民权益等议题及其相关的公共政策展开讨论。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不同议题中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同为对公众日常生活和健康有潜在威胁的争议性风险议题,雾霾议题与转基因议题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公众参与程度。事实上,在以下三个维度,转基因议题呈现出更为积极的政治参与:
第一,政治参与的目标。更有效的政治参与活动,往往意味着参与者有更为明确的目标诉求,且参与者会在参与过程中向政策制定者传播充分的信息和支撑性观点,以试图影响决策者(Verba,1967)。在转基因议题中,公众以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出发,呼吁建立更为严格的转基因审批、监管和惩戒制度、②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呈现出相对明确的政策诉求;而相比之下,雾霾议题的公众参与则更多表现为对空气污染现状的担忧,而尚未形成明确、具体的政策诉求。
第二,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这一衡量指标被已有研究多次提及,它涉及公众参与行为是以个人形式开展,还是以更具凝聚力的集体行为方式开展;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参与行为,往往会给政策制定者带来更高的压力(Ekman & Amna, 2012;Verba, 1967)。在转基因议题中,反对转基因推广、开发和商业化的线下活动时有发生,③普通民众和具备较高社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共同参与到行动中。④
而在雾霾议题中,公众参与更多表现为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零散化、个人化意见表达,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参与活动较少。
第三,政治参与的主动性。Verbal等人 (1973) 指出了不同政治参与形式在参与主动性方面的差异,比如,选举等参与形式所需主动性较低,而一些集体行动则需要更强的主动性,甚至需要承担额外的风险(胡荣,2008)。与转基因议题中时常发生的线下反对活动相比,公众基于社交媒体就雾霾议题进行的线上讨论所需的参与主动性较低、风险也较小。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在理论层面,本文引入“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的概念,来帮助理解转基因议题和雾霾议题中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差异。本文希望回答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作为公众参与程度迥异的议题,雾霾和转基因议题各自形塑的议题网络是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这两个议题网络中:
1.网络的规模和成员构成如何?
2.哪些话语主体在议题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
3.议题网络中话语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紧密?
4.议题网络内部的争论焦点和话语框架分别是什么?
二、文献回顾
(一)公众政治参与的研究转向:从个体特征到社会互动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公民通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以影响政府行为或改变政策后果的活动,其中既包括选举、投票、听证等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也包括游行、抗议等线上和线下的公民行动(Brady, 1999;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
已有对于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普遍强调个体特征的差异对于民众是否进行政治参与的影响。其中,参与者的年龄(Gil de Zúniga et al., 2021)、社会经济地位(Teney & Hanquinet, 2012)、政治效能感(刘伟,2020)、社会资源(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等要素,都被认为与政治参与行为紧密相关。具体到中国语境下,有研究特别指出,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公众而言,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社会中上层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对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在其他社会群体中的影响则较小(崔岩,2020)。此外,媒介接触和使用,特别是利用媒介进行新闻信息获取,将会显著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水平(曾凡斌,2014)。
这些学术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政治参与研究,它们充分强调了个体力量和自主性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认为拥有更高社会身份和更多社会资源的公民更有可能进行政治参与(Campbell, 2013)。但是,这样的研究路径会忽略政治参与的集体面向和社会互动,并淡化参与行为本身的政治属性(Fenton & Barassi, 2011)。
因此,有学者指出,仅仅依靠个体层面的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政治行为;在强调个体政治主观性在政治参与中重要地位的同时,也需要审视个体之间的互动和社会联系(Scheufele et al., 2004)。对政治参与的理解,需要超越个体特征,转而探讨社会互动特别是社会网络对于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Campbell, 2013)。这些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以及借助其展开的政治讨论和人际交流,会对其中成员的政治态度和倾向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其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行为(McClurg, 2003;Kenny, 1992)。而网络的规模、网络关系的强弱、讨论的形式、观点的异质性等各项指标(Valenzuela, Kim & Gil de Zúniga, 2011;Knoke, 1990),则成为解释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因素。
(二)议题网络:理论视角与具体维度
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的理论路径,为我们理解公众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思路。沿着这一路径,我们将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Heclo, 1978)这一概念引入公众政治参与研究中,试图探讨议题网络的差异是否能成为理解政治参与程度差异的一种新的理论可能。
在社会化媒体上,拥有共同特征、兴趣和政策偏好的人群得以借助社会化媒体联合起来,形成全新的社会关系,并持续就公共议题展开讨论(郑雯,黄荣贵,2015)。类似这样由对特定政策议题感兴趣的人们组成的交流网络,被称为“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Heclo, 1978),其中的成员既包括政府官员、立法者、商人,也包括学者、记者及普通民众;他们持续就现有政策进行讨论和批评,并生成关于新政策的想法(McFarland,1987:146)。
作为一种松散的政策网络(Rhodes,2006),议题网络是非正式、不稳定的(Waarden, 1992)。其主要特征表现为:(1)参与者不受限制,因而网络成员数量众多,身份差异也较大;(2)成员之间缺乏共识,存在冲突,意见无法整合和统一;(3)议题网络中没有核心的权威或权力中心,因此决策非常困难(Rhodes, 2006;Marsh & Rhodes,1992)。
为了考察不同议题中议题网络的差异,本研究结合Marsh和Rhodes (2002)和Montpetit (2005)的分析框架,从以下三个维度考察议题网络的特征:
第一,网络成员和规模。一些研究证实了网络规模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认为在政治参与较为积极的议题领域中,政策网络的规模相对较大(Valenzuela, Kim & Gil de Zúniga, 2011)。这一方面是由于,规模更大的网络往往具备更大的异质性。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网络中的成员数量越多、互动越为活跃,该网络的同质化程度就越低、网络成员所参与讨论的内容主题也越为多元化(汤景泰,陈秋怡,2020)。内容主题的多元化会增加网络成员接触各种政治信息和观点的可能性(McLeod, Sotirovic & Holbert, 1998),促进彼此的交流反思和公共对话(MacKuen, 1990);另一方面,更大网络中往往包含更多的弱连接,这会促进关于政治参与机会的信息流动,进而增加被邀请参与公民行动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McPherson, Smith-Lovin & Brashears,2006)。
第二,网络整合度。这一维度考察议题网络中各个成员之间互动的紧密程度,以及网络内部是否存在共识(Marsh & Rhodes,1992:251)。一些研究认为,网络内部的政治观点和参与意愿一定程度上是可传递的;网络成员之间的频繁互动,可能会影响彼此的政治参与行为(Vitak et al., 2011)。此外,网络内部的共识程度也与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Valenzuela, Kim & Gil de Zúuiga, 2011)。对中国网民的调查数据也表明,与以获取资讯和个人娱乐为特征的“个体性介入”相比,以“集体性介入”为特征的互动式互联网使用模式,即通过搭建网络社群的方式进行信息讨论和共享,将会推动线上信息流动速度和网民互动质量的提升,进而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孟天广,季程远,2016)。
第三,资源与权力分配。在社会化媒体上的议题网络中,个体不仅能与其他个体,也能与有影响力的组织和行动者相连。这一维度考察议题网络中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权力中心,以及网络中各个成员的资源占有和权力分配情况。一般而言,议题网络的成员所占有的资源差异悬殊,权力分配也往往极不平等(Marsh & Rhodes, 2002)。对社会化媒体上议题网络的考察,需要重点关注网络中有影响力的公共行动者或意见领袖(Tang & Lee, 2013)。他们作为议题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Chen, Chan & Lee, 2016)。与这些关键节点的联系,有助于促进议题网络中的底层民意表达和公共议题形成,进而推动公民参与和政策变迁(曾繁旭,黄广生,2012)。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本文将以雾霾议题和转基因议题为例,通过对新浪微博上相应议题的议题网络的分析,探讨议题网络的各个特征如何与更积极的线上或线下政治参与相连。
本文的案例选择逻辑,主要参考了Przeworski和Teune(1982: 32)提出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设计的主要原则。Przeworski和Teune(1982:32)认为,“最相似”设计原则(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是当下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案例比较的主导性原则,即需要选择关键特征尽量相似的案例作为比较对象,以提升案例之间的可比性。在本研究中,雾霾议题和转基因议题的相似性体现在:第一,从议题属性而言,两个议题同为科学风险类议题,对两个议题的理解和讨论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第二,从议题对个人的影响而言,两个议题都与公众日常生活和个人利益紧密相关,均存在对于公众健康的潜在影响;第三,从议题的社会影响而言,两个议题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甚至社会争议,并引发了相应的公众参与行为。比如雾霾议题中民间兴起的空气自测运动、转基因议题中公众针对转基因研发推广发起的线上或线下的反对行动等。
雾霾议题和转基因议题在以上若干方面的相似性,一方面奠定了两个议题进行比较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也正为我们呈现出科学风险议题中出现的理论困惑,即为何雾霾议题和转基因议题在议题属性和社会影响上高度相似,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公众参与程度。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两个议题中议题网络的分析,提供理解公众政治参与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运用R编程语句,借助新浪微博API接口抓取新浪微博内容和用户评论及公开转发信息。
在雾霾议题中,本研究首先借助新浪微博的关键词热度监测工具“微指数”,⑤分析新浪微博上的雾霾议题讨论热度,时间为2014年10月至今。微指数平台表明,在新浪微博上,用户雾霾议题讨论的峰值出现于2014年10月11日。因此,本研究选取该日期前后共两周的时间(2014年10月4日至2014年10月17日),以“雾霾”为关键词抓取相关微博内容,对所有微博的主题进行内容分析;并选取被转发数量居于前20的热门原创微博,进行议题网络的分析。
在转基因议题中,本研究选择两个时间段,分别是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3月11日,以及2016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14日,共两周。其中,2015年3月5日是2015年至今新浪微博上的转基因讨论热度的最高点,当天农业部副部长宣布中国将增加转基因农产品上市的种类和数量;2016年4月8日,以前化工部长秦仲达为代表的400多人联名签署质询书反对史上最大的并购案(中国化工集团并购瑞士种子与农药公司先正达),⑥体现出转基因议题的微博讨论已经不仅停留在网络空间,而是衍生为包含特定政策诉求的线上或线下公民参与活动。在这两个时间段中,以“转基因”为关键词抓取微博内容,对所有微博的主题进行内容分析;并分别在两个时间段中各选取被转发数量位于前10的原创微博,进行转发网络的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度剖析转基因和雾霾议题网络的关键特征。一方面,本研究将对两个议题中目标时间段内的微博主题进行内容分析。目标时间段内共包含样本2979条,其中雾霾议题1154条,转基因议题1825条。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等距抽样法,每5条微博抽取一条,获得596条微博样本进行分析,其中雾霾议题231条,转基因议题365条。微博主题的分析类目见(表1 表1见本期第52页)。对微博主题的内容分析,主要是为了测量议题网络的整合度,考察议题网络中成员是否具备明确共识,或者在该议题的哪些方面存在争议。
另一方面,本研究将从两个议题的样本中各选取转发数居于前20的热门微博进行议题网络的分析。在该网络中,发表或转发微博的用户成为网络的节点,用户之间评论或转发的关系构成节点之间的有向连接。网络可视化借助Gephi 0.9.0完成。对议题网络的具体测量指标主要包括:(1)网络规模,即每个议题网络中所含节点的数量。(2)网络节点平均聚类系数。聚类系数是指与网络特定节点相连的其他节点也彼此相连的程度,该概念是用于衡量网络节点凝聚程度的指标(Watts & Strogatz, 1998),主要用于测量议题网络的网络整合度。(3)网络中各节点中心度。节点的中心度是指网络中与该点有直接关系的点的数目(刘军,2004)。该概念是用于测量节点权力的一种指标;具备较高点度中心度的节点,往往在网络中居于较为中心地位,并拥有较大的权力(刘军,2004)。该测量指标主要用于衡量议题网络中资源和权力分配的特征。
四、研究发现
(一)议题网络的成员与规模
网络规模是指特定网络中包含的节点数量。在传统的社会网络与公民参与研究中,网络规模越大,通常意味着越大程度的公众政治参与的可能性(Valenzuela, Kim & Gil de Zúniga, 2011)。
从网络规模而言,转基因议题并不具备优势。Gephi统计分析表明,转基因议题网络中共包含6731个节点,而雾霾议题网络中的节点则多达1.5355万个。雾霾议题网络相对于转基因议题网络的规模优势,一定程度上与两个议题本身的特性有关。雾霾议题与公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且专业门槛相对较低,因此该议题网络中包含大量普通民众,他们持续就该议题展开日常化、个人化的讨论。而无论影响的范围还是持续性上,转基因议题对公众的影响力都比雾霾议题小,且具备一定的专业门槛,因此在社会化媒体上,转基因的议题网络规模也相对小一些。
但是,在网络成员的具体构成方面,转基因议题还是呈现出相对明显的政策潜力。一方面,雾霾议题网络由大量松散、游离的普通网民组成,他们占据整个议题网络成员数量的近90%(占比87.92%);普通网民就该议题发表的大量碎片化信息,构成了该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而在转基因议题中,普通网民的比例则相对低一些(占比71.63%)。另一方面,除了普通网民,专家/科技工作者成为转基因议题网络中占比最大的群体(占比11.52%),他们往往借助专业信息进行政治参与的动员;而在雾霾议题网络中,占比仅次于普通网民的成员为媒体机构的官方微博账号(占比6.06%),这些微博账号以发布与雾霾相关的实时资讯为主,其作用更多是信息提供而非参与动员。
(二)议题网络的整合度
议题网络的整合度,主要考察议题网络成员之间互动的紧密程度,以及网络内部是否存在共识(Marsh & Rhodes, 1992:251)。聚类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是用于测量网络整合程度的一项指标,反映了网络中节点之间相互连接和集结的程度;聚类系数越高,表示网络节点的集聚度越高(杜杨沁等,2013)。
Gephi统计显示,转基因议题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为0.035,而雾霾议题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为0.000。这表明,雾霾议题网络存在高度离散的特征,而转基因议题网络则具备一定的整合度。从转基因议题网络图(图1 图1见本期第54页)和雾霾议题网络图(图2 图2见本期第54页)中也可以看出,雾霾议题中存在大量离散节点,这些节点大多为普通网民,他们游离于网络内部,彼此相互独立,缺乏互动。而在转基因议题中,节点则围绕关键意见领袖形成若干凝聚子群,凝聚子群内部成员之间呈现出相对较紧密的联系(Wasserman & Faust, 1994:249)。
然而,虽然转基因议题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相对于雾霾议题网络略高,但从数值上来看,两个网络都较为松散,这意味着网络内部各成员之间尚未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也没有统一的共识。
为了考察在没有形成共识的议题网络中,网络成员从哪些角度对议题进行讨论和争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哪些方面,本研究对网络成员的微博内容进行了主题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 表3见本期第54页)。
卡方分析表明,雾霾和转基因议题的微博讨论中,微博主题存在明显差异(χ2=202.12,p<0.001)。具体而言,在转基因议题中,网络成员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安全争议”和“制度与监管”两大主题。聚焦于“安全争议”这一主题的相关微博侧重探讨转基因议题是否会对民众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的损害,而聚焦于“制度与监管”这一主题的微博则主要探讨国家是否应出台相关法规和条例,对转基因的研发、推广和商业化进行规制。
而在雾霾议题中,日常影响框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框架,占比超过一半(50.22%),相关微博侧重于就雾霾对民众日常出行、生活方式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展开讨论。此外,“伦理与责任”主题也成为民众争论的焦点,相关微博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雾霾的成因和归责问题。
雾霾和转基因议题网络中,网络成员讨论主题的差异,某种程度上是线下政策过程在线上的折射。在我国转基因政策制定中,转基因技术的审批制度和执行制度存在明显的背离(陈玲等,2010)。具体而言,我国对转基因作物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都采取较为严格的审批制度(陆群峰,肖显静,2009),但在政策的实际执行上,我国并未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特殊标记,也没有针对转基因生产过程中违规行为的严格查处惩戒制度(陈玲等,2010)。由于转基因产品与公众关系较为密切,因而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相对放松的监管和政策,容易引发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并使得公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转基因议题的制度与监管问题展开讨论。而在雾霾议题中,由于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政府的空气污染政策制定过程一旦缺乏对民意及时、有效的回应,就会导致公众在社会化媒体上就雾霾对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情绪宣泄(吴柳芬,洪大用,2015),“日常影响”主题因而成为雾霾议题网络中占比最大的主题。
政治参与和公民行动的相关理论,可能有助于解释雾霾和转基因议题中微博话语框架的差异。某种程度上,转基因议题网络中的主导话语框架具备推动公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动员潜力,而雾霾议题中的话语框架则更多停留在认识层面,并未能转化为行动层面对于公众采取实质性政策行为的推动。具体而言,在转基因议题中,通过采取个人化的行动框架,相关微博将转基因议题与民众日常生活和个人权益建立紧密的关联,动员他们采取行动以捍卫自身权益、推动政策改变。事实上,中国政治参与和公民行动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倡导公众通过个人化框架进行政策诉求的表达和互动,甚至要比直接倡导公众参与线下抗争具备更好的传播效果和动员潜力(Huang & Sun, 2016)。而与传统的集体行动框架相比,这种个人化的行动框架在推动民众政治参与方面更具优势(Bennett,2012)。比如,“为了中华民族能永续发展,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站出来反对转基因!”(@杨长玉的微博,2016年4月14日20:10),“令人毛骨悚然的转基因食品,为了后代子孙,我们要拒绝消费”(@琳琅石zz,2015年3月7日16:09)。这样的个人化行动框架,降低了参与门槛,使得包括大多数网民在内的潜在参与行为成为可能。而在雾霾议题中,虽然有超过一半的讨论主题都围绕雾霾的日常影响展开,但是这些线上讨论更多聚焦于描述与调侃现实,缺乏针对具体行动的动员。比如,“雾霾严重,看不到太阳……黑瞎子拉开窗帘,以为自己终于瞎了”(@南派三叔,2014年10月10日21:05)。类似这样的微博内容,成为雾霾议题网络中网民讨论的主要话语框架。认识层面而非行动层面的讨论主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雾霾政策制定过程中较低程度的公众政治参与。
(三)议题网络中的权力分配
议题网络的权力分配这一维度,主要探讨特定网络中哪些节点处于相对的权力中心、具备对其他节点的支配地位,而哪些节点则处于网络边缘、不具备影响力。
对网络节点权力关系的测量,主要依赖节点度(degree)这一指标。节点度是测量特定节点在网络中地位的重要指标,节点度越高,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的权力越大、地位也越重要(刘军,2004)。有向图中的节点度包括点入度和点出度。在本研究的议题网络中,节点的出度(out-degree)反映出用户微博被转发的情况,而节点的入度(in-degree)则体现出该用户转发其他微博的情况。因此,节点的出度越高,表明该用户的微博被转发的次数越多,该用户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
在权力分配这一维度上,雾霾议题网络和转基因议题网络的差异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议题网络中关键节点的身份差异。在转基因议题中,除了用于发布资讯的媒体账号以外,点出度排名前10的节点主要包括专家/科技工作者(如@中流击水三千里、@闲来捉鳖、@陈一文顾问、@吴其伦)以及媒体人(@崔永元)。在动员公众政治参与方面,他们的优势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有明确的政策倾向和诉求,且借助他们掌握的技术资讯和国内外相关政策,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动员,比如“新收到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利尼教授和烹饪大师Douzelet先生合著的新书Culinary Pleasures or Hidden Poisons,继续揭露转基因的危害”(@闲来捉鳖,2015年3月6日22:42)。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节点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身份,因而他们在网络上也拥有相对较高的影响力,能将自己掌握的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化媒体上的动员潜力。
而在雾霾议题中,意见领袖的身份主要为文体名人(如@谢娜、@南派三叔)、网络博主(如@这微博笑死我了、@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以及媒体机构的官方微博账号(如@人民日报、@法制晚报、@央视新闻)。除了用于发布常规资讯的媒体机构微博账号外,其他意见领袖所发布的微博主要集中于雾霾对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这些内容大多以描述事实为主,但更具娱乐化。比如,“就这雾霾,知道是我们在北京,不知道的以为住天庭了……”(@这微博笑死我了,2014年10月10日21:04,转发量1268)围绕雾霾议题的戏谑和娱乐化表达,取代了对雾霾议题本身的反思,以及改变现状的政策诉求。类似微博内容表明,雾霾议题中的意见领袖基本不具备动员民众政治参与的意愿。
第二,议题网络权力结构的差异。除了具备明显权力优势的节点以外,转基因议题中还存在一些具备相对较大影响力的二级节点。这些二级节点的点出度虽然小于权威意见领袖,但是与网络中大量游离的普通成员相比,其节点度较大,因而依然具备较强的影响力。这些二级意见领袖大多为热衷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人(如@袁国宝,点出度139)、学者(如@司马南,点出度196;@顾秀林A,点出度136)、律师(如@陈光武律师,点出度149)等,他们在各自领域也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通过将权威意见领袖所发布的信息进行转发,充当权威意见领袖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传播桥梁,一方面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动员,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网络的整合度。而在雾霾议题中,意见领袖发布的信息大多直接流向松散、游离的普通公众,基本不存在类似于转基因议题网络中的二级意见领袖。
五、结论与讨论:转型中国的议题网络与政治参与
同为对公众日常生活和健康有潜在威胁的争议性风险议题,雾霾议题与转基因议题在公众政治参与的目标、主动性和组织化程度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公众参与程度。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议题网络的概念,来帮助理解不同议题中公众参与程度的差异。研究发现,转基因议题和雾霾议题的议题网络在网络成员与规模、网络整合度、资源和权力分配三个维度上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转基因议题网络虽然在绝对规模方面不一定占据明显优势,但是网络成员专业化程度较高,松散、游离的普通网民占比相对较低;在网络整合度方面,转基因议题网络整合度相对较高,且占主导地位的个人化行动框架降低了参与门槛,从而具备大规模动员的可能性;在权力分配方面,转基因议题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更加具备动员潜力或意愿,且网络中存在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二级意见领袖。
转基因和雾霾议题网络在网络成员与规模、网络整合度、资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两个议题自身的复杂性和政策过程的特征有关。虽然雾霾和转基因议题都被公众认为存在健康风险,但由于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很难取得明显成效,加之该议题也缺乏明确、清晰的归责对象,因而公众倾向于规避明确的、制度化的参与方式(王惠琴,何怡平,2014),该议题的线上议题网络更多呈现出较为松散的情绪化宣泄或戏谑化表达。而在转基因议题中,由于转基因政策过程一般很少向公众开放,而是采用以专家委员会和技术官僚为核心的决策模式(陈玲等,2010),且与转基因相关的审批和管理法规也尚未完全健全和充分公开,因而公众会围绕转基因政策制定的开放性、利益相关方对转基因政策的影响等更为具体、聚焦的角度,表达其反对转基因的诉求,议题网络也会相对紧密一些。
为了理解中国语境下公众政治参与行为,本文超越了传统政治参与研究中从个体特征出发的理论路径,而是更多沿用社会互动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但是,与已有社会互动与政治参与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议题网络的概念引入政治参与研究中,通过对社会化媒体上公众政策讨论网络的操作化测量和量化分析,试图更为清晰地呈现社会网络和公众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也为我们运用议题网络的理论概念进行观察和测量提供了便利。
议题网络这一概念,对于中国公众参与研究具备理论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适用性。一方面,以美国为主的政治学者的研究表明,议题网络以及其中关键网络成员和意见领袖的作用,会影响政策议程,并形塑政策后果(Marsh & Rhodes, 2002)。议题网络的视角不仅能帮助呈现与特定政策议题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社会网络,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分析政策过程的一种理论路径(Borzel, 1998)。另一方面,议题网络也具备在中国语境下的解释力。在中国政治参与面临相对较高政治风险的语境下,联系更为紧密且包含权威意见领袖的议题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动员方式,可能意味着政治风险的降低,进而导致更为积极的公众政治参与。
此外,不同议题网络在网络成员与规模、网络整合度、资源和权力分配三个维度上的差异,或许能为中国语境下的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和判断标准。在特定议题中,如果社会化媒体上的公众政策讨论具备更为专业化的网络成员、更为紧密的网络结构,以及更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那么该议题将更有可能出现较为积极的公众政治参与行为。
比如,在科技风险议题中,转基因、垃圾焚烧、PX、核电等议题,都呈现出线上公众讨论和议题网络带来的公众政治参与的动员潜力。某种程度上,这些科学议题具备“后常态科学”的特征,科学事实不确定、信息不充分带来公众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和巨大争议(陈玲等,2010);加之这些科学风险一旦发生,就会对公众个体安全乃至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后果,因而,这些议题更有可能在线上形成整合度相对较高的意见网络,并经由意见领袖的作用,产生线下的动员潜力和政策影响。
本研究对已有文献中关于社会网络和公众政策参与研究的增补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网络和政治参与的已有研究认为,规模较大的社会网络,往往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具备更大的潜力(Valenzuela,Kim & Gil de Zúniga, 2011)。但本研究发现,特定议题网络的绝对规模并不一定与更为积极的政治参与相连;相比之下,议题网络中的成员构成则更为重要。更具动员意愿和动员能力的网络成员和意见领袖,将更有可能推动网络其他成员的政治参与。
第二,在中国语境下,社会化媒体上的议题网络与线下政策过程存在对应性与差异性。一方面,线上政策网络是线下政策过程在线上的投射,公众在线上的政策讨论围绕线下政策过程展开,特定议题在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管方面的差异,会使得不同政策议题网络的讨论主题呈现出相应的区别;另一方面,在线下政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等政治权威在线上议题网络中缺席,中国语境下的线上议题网络很大程度上成为民间舆论互动与争夺的空间,而在西方语境下,议题网络的成员构成则更为开放而多元,其中包含拥有不同政治权力的网络成员(McFarland, 1987:146)。
第三,已有研究充分强调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情绪化表达对推动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认为微博平台上的情绪化表达更容易引发公众关注、产生大范围影响(Song, Dai & Wang, 2016),甚至可能具备推动政策变迁的潜力(Pan, 2015;杨国斌,2009)。但本研究则表明,议题网络中过多的情绪化表达,将会冲淡对公众实际行动的动员潜力,使网络讨论流于戏谑和调侃,而缺乏推动公众进行政治参与的可能。以雾霾议题为代表的低参与度议题网络一定程度上就具备这样的特征。
在中国语境下,借助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质量参差不齐,很难形成一个统合的意见市场(吴瑛,宋韵雅,刘勇,2016)。无论在转基因议题还是雾霾议题中,社会化媒体上的议题网络都呈现出较为松散的特征。这呈现出作为政策网络的一种形式,缺乏共识、高度分化、权力关系不平等依然是议题网络的主要特征(Marsh & Rhodes, 2002)。
但通过对雾霾议题和转基因议题的对比分析,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语境下,线上公共空间的分化和聚集趋势并存(郑雯、黄荣贵,2015)。一方面,网络空间中的绝大多数节点依然是离散、游离的普通网民,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政治参与程度都相对很低;而另一方面,在特定议题中,经由意见领袖的统合和动员,对相应议题感兴趣的民众会借助议题网络的形式聚合起来,对公共事务进行表达和参与,甚至可能影响政策过程。
当然,社会化媒体上的议题网络与政治参与并不存在必然的相关关系,即使是在具备较大网络规模、网络整合度和有影响力意见领袖的议题网络中,也不一定必然引发积极的公众政治参与。公众政治参与,不仅受到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的影响(王绍光,2008),也受到与特定议题相关的政治机会和政府管制的影响,因而需要具体分析。■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即社交媒体,是指基于web 2.0技术,允许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络应用和平台(参见:KaplanA. M.& Haenlein, M. (2010). Users of the world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 Business horizons,?53(1)59-68.)。因此,本文对于社会化媒体和议题网络的相关研究梳理,已涵盖对社交媒体的相关研究;本文最终得出的社会化媒体上议题网络与公众政治参与的相关结论,也完全适用于社交媒体。
②在社会化媒体上被大量转发的相关内容比如:吕永岩:《【接力赛】抵制转基因,孟山都滚出中国》,2015年5月2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683ce0102vuhh.html。
③如以反对孟山都(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反对转基因为核心诉求的多次抗议活动(2013年2月,北京;2015年5月,北京;2016年4月、5月,北京)、反对中国化工集团并购瑞士种子与农药公司先正达的抗议活动(2016年4月)等。
④比如,反对中国化工集团并购瑞士种子与农药公司先正达的抗议活动中,主要发起人包括前化工部长秦仲达、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前顾问陈一文等。
⑤详见http://data.weibo.com/index。
⑥参见:转基因观察:《北京街头现抗议收购先正达案活动》,2016年4月24日,http://chuansong.me/n/398863651945。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铭译)。北京:三联书店。
陈刚(2014)。“不确定性”的沟通:“转基因论争”传播的议题竞争、话语秩序与媒介的知识再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7),17-34。
陈玲,薛澜,赵静,林泽梁(2010)。后常态科学下的公共政策决策——以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为例。《科学学研究》,(9),1281-1289。
崔岩(2020)。当前我国不同阶层公众的政治社会参与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4(6),9-17。
杜杨沁,霍有光,锁志海(2013)。基于复杂网络模块化的微博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以“上海发布”政务微博为例。《图书情报知识》,(3),81-89。
胡荣(2008)。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5),142-159。
贾鹤鹏,范敬群(2015)。转基因何以持续争议——对相关科学传播研究的系统综述。《科普研究》,(1),83-92。
刘军(2004)。《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伟(2020)。政治效能感研究:回顾与展望。《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5),65-71。
陆群峰,肖显静(2009)。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68-78。
孟天广,季程远(2016)。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43-54。
汤景泰,陈秋怡(2020)。意见领袖的跨圈层传播与“回音室效应”——基于深度学习文本分类及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5),25-33。
王惠琴,何怡平(2014)。雾霾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重庆社会科学》,(12),42-47。
王绍光(2008)。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95-112。
吴柳芬,洪大用(2015)。中国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以雾霾治理政策制定为例的一种分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55-62。
吴瑛,宋韵雅,刘勇(2016)。社会化媒体的“中国式反腐”——对落马官员案微博讨论的社会网络分析。《新闻大学》,(4),104-113。
杨国斌(2009)。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9),39-66。
曾凡斌(2014)。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200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数据。《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6(10),33-40。
曾繁旭,黄广生(2012)。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开放时代》,(4),115-131。
郑雯,黄荣贵(2015)。微博异质性空间与公共事件传播中的“在线社群”——基于新浪微博用户群体的潜类分析(LCA)。《新闻大学》,(3), 101-109。
郑雯,黄荣贵,桂勇(2015)。中国抗争行动的“文化框架”——基于拆迁抗争案例的类型学分析(2003-2012)。《新闻与传播研究》,(2),5-26。
朱旭峰(2008)。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社会学研究》,(2),69-93。
Bennett, W. L. (2012).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 Political identity, social media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644(1)20-39.
Bennett, W. L.& SegerbergA. (2011).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s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4(6)770-799.
BorzelT. A. (1998). Organizing Babylon-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2)253-273.
Brady, H. E. (199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J. P. Robinson, P. R. Shaver & L. S. Wrightsman (eds.)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pp. 737-801.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CampbellD. E. (2013).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633-48.
Castells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H. T.Chan, M.& LeeF. L. (2016). Social media use and democratic engag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9(4)348-366.
Daugbjerg, C. (1998). Linking Policy Network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Nitrate Policy Making in Denmark and Sweden 1970-1995.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2)275-294.
Ekman, J.& Amna, E. (201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Towards a new typology. Human affairs22(3)283-300.
FentonN.& BarassiV. (2011). Alternative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4(3)179-196.
Gil de ZúnigaH.Ardèvol-Abreu, A.& Casero-Ripollés, A. (2021). WhatsApp political discussion, conven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activism: exploring direct, indirect and generational effect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4(2)201-218.
Heclo, H. (1978). Issue networks and the executive establishment. In A. King (ed.). The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uang, R.& SunX. (2016). Dynamic preference revelation and expression of personal frames: how Weibo is used in an anti-nuclear protest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9(4)385-402.
Kenny, C. B. (199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ffects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59-267.
Knoke, D. (1990). Networks of political action: Toward theory construction. Social forces, 68(4)1041-1063.
MacKuen, M. (1990). Speaking of politics: Individual conversational choice, public opinionand the prospec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J. Ferejhon & J. Kuklinski (Eds.)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pp. 59-9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arsh, D.& Rhodes, R. A. W. (eds.) (1992).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govern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sh, D.& Rhodes, R. (2002). Policy communities and issue networks: Beyond typology. In J. Scott (Ed.). Social networks: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4)pp. 89-119.
McClurg, S. D. (2003).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explain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56(4)449-464.
McFarland, A. (1987). Interest groups and theories of power in Americ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7(2): 129-147.
McLeodJ. M.SotirovicM.& HolbertR. L. (1998). Values as sociotropic judgments influencing communication patter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5)453-485.
McPherson, M.Smith-Lovin, L.& BrashearsM. E. (2006). Social isolation in America: Changes in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ver two deca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3)353-375.
Montpetit, E. (2005). A policy network explanation of biotechnology polic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5(3)339-366.
O’Riordan, T.& Jordan, A. (1996).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climate change. In T. O’Riordan & A. Jordan (Eds.).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a European perspectiveLondon: Routledge. 65-105.
Pan, J. (2016). Emotional criticism as public engagement: How weibo users discuss “Peking University statues wear face-mask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33(2)514-524.
ParkN.KeeK. F.& Valenzuela, S. (2009). Being immersed in social networking environment: Facebook groups,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nd social outcome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2(6)729-733.
PrzeworskiA.& TeuneH. (1982).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MalabarFlorida: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RhodesR. A. (2006). Policy network analysis. In MoranM.Rein, M.& Goodin, R. 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425-447.
Scheufele, D. A.Nisbet, M. C.Brossard, D.& Nisbet, E. C. (2004). Social structure and citizenship: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social settingnetwork heterogeneityand informational variable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1(3)315-338.
SongY.DaiX. Y.& Wang, J. (2016). Not all emotions are created equal: Expressive behavior of the networked public on China's social media sit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0525-533.
TangG.& LeeF. L. (2013). Facebook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impact of exposure to shared political informationconnections with public political actors, and network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1(6)763-773.
Teney, C.& HanquinetL. (2012). Hig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high social capital? A relational analysis of youth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5)1213-1226.
ValenzuelaS.KimY.& Gil de ZúnigaH. (2011). Social networks that matter: Exploring the role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for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4(2)163-184.
Verba, S. (1967).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373(1)53-78.
Verba, S.NieN. H.Barbic, A.IrwinG.Molleman, H.& Shabad, G. (1973). The modes of participation: continuities in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6(2)235-250.
Verba, S.SchlozmanK. L.& BradyH. E.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itak, J.Zube, P.SmockA.Carr, C. T.EllisonN.& LampeC. (2011). It’s complicated: Facebook us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2008 election. CyberPsychology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3)107-114.
Waarden, F. (1992). Dimensions and types of policy network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1(1-2)29-52.
Warschaur, M. (2003).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ivide.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Wasserman, S.& FaustK.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Vol. 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tts, D. J.& Strogatz, S. H. (1998). 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networks. Nature, 393(6684)440-442.
王宇琦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曾繁旭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曾繁旭为本文通讯作者。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20JJ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