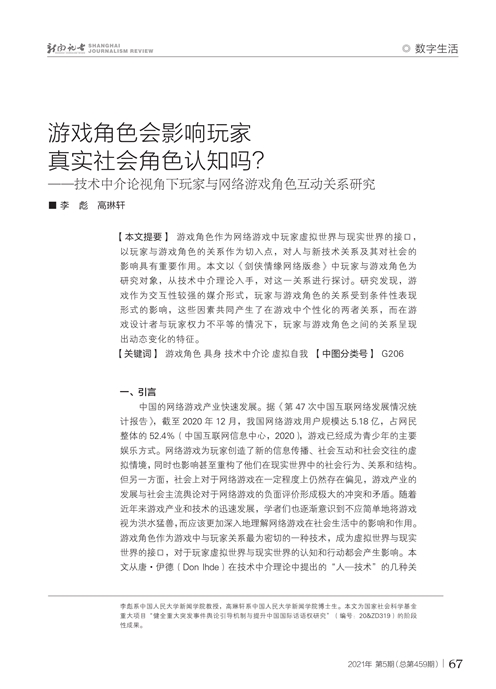游戏角色会影响玩家真实社会角色认知吗?
——技术中介论视角下玩家与网络游戏角色互动关系研究
■李彪 高琳轩
【本文提要】游戏角色作为网络游戏中玩家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接口,以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对人与新技术关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剑侠情缘网络版叁》中玩家与游戏角色为研究对象,从技术中介理论入手,对这一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游戏作为交互性较强的媒介形式,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受到条件性表现形式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产生了在游戏中个性化的两者关系,而在游戏设计者与玩家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
【关键词】游戏角色 具身 技术中介论 虚拟自我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中国的网络游戏产业快速发展。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情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5.18亿,占网民整体的52.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游戏已经成为青少年的主要娱乐方式。网络游戏为玩家创造了新的信息传播、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的虚拟情境,同时也影响甚至重构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行为、关系和结构。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于网络游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偏见,游戏产业的发展与社会主流舆论对于网络游戏的负面评价形成极大的冲突和矛盾。随着近年来游戏产业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不应简单地将游戏视为洪水猛兽,而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网络游戏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游戏角色作为游戏中与玩家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技术,成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接口,对于玩家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行动都会产生影响。本文从唐·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中介理论中提出的“人—技术”的几种关系入手,探讨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尝试进一步促进在新技术影响下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理解。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技术现象学是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讨论,其认为人是由身体和被身体化的东西构成的,而世界是这些东西的延展(张正清,2014)。唐·伊德作为技术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对知觉(perception)的理解,认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必须重新去考察知觉(戴宇辰,2018)。在此基础上,他将知觉分为两类:一类为在实际的看、听、触摸等意向活动中认识到的感知,即微观知觉(microperception);另一类为通过技术所扩展的人类感知,即宏观知觉(macroperception)。这两类知觉的关系并不是派生的,“微观知觉是在它的诠释的—文化的情境中发生的;但是,所有这些情境只有在微观知觉的可能性范围内才得以生成”(唐·伊德,1990/2012:30)。在完成对技术存有论的分析后,伊德重点关注了“人—技术—世界”的基本关系结构,他将这种关系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为中介关系(intermediary relations)、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及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
中介关系是指技术实际处在人与世界的中介位置上(唐·伊德,1990/2012:78),并且所有使用中的技术都不是中性的,它们改变了基本的境况(唐·伊德,1990/2012:80)。他认为这种中介关系具体来看又分为两种:一种为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即技术具于人的自然身体,从而直接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能力(芮必峰,2020);另一种中介关系为解释学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又被翻译为诠释关系,即技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替代品,人们通过经由对技术设备显示的文本进行解释构建“知觉”。
它异关系是指技术成为与人类相异的他者个体。与中介关系不同,此类关系被看成是与技术的关系或有关技术的关系(唐·伊德,1990/2012:102),技术相对于人来说成为一种准他者,在这种关系中人与技术保持着互动关系。而背景关系中的技术隐匿于环境中,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背景条件,这种技术功能的“抽身而去”被称作“不在场”,技术成为人的经验领域的一部分,成为当下环境的组成部分(唐·伊德,1990/2012:114)。
唐·伊德提出的技术中介理论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技术哲学早期的超越论色彩与对技术的消极态度(牟怡,2020),并为后人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研究基础上,科斯蒂·贝斯特(Kirsty Best)进一步将技术的范围缩小到了传播媒介,并引入“媒介世界”的概念,认为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技术,当沉浸在媒体内容时,人们的注意力既不在外部世界,也不在技术本身,而是被困在媒体内容为人们创造的想象世界中,媒介世界与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两个平行的世界,由此将人、技术和世界的关系重新整合为“人—媒介—媒介世界”的关系,即“人—(技术—媒介)—(媒介世界—世界)”之间的关系(Kirsty,2010)。
随着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身体正在从各个学术视角被激活,其中现象学的“具身化存在”论,不但是身体理论的当代发端,也是身体研究中最为重要与基础的理论视角(孙玮,2018)。对于具身关系的讨论成为近年来国内传播学身体研究关注的重点,讨论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对具身关系宏观理论层面的讨论,这一维度通常从传播学界对身体研究的历史入手,一方面梳理从离身观念主导到“发现身体的位置”,回归对身体讨论的过程(刘海龙,2019),反思传播学为何失去了身体;另一方面从宏观学理层面将具身关系作为探讨传播与身体关系的一个切入点,探讨传播与身体是如何互相塑造的,身体如何演化出多种身体形式,身体世界中传播的价值与意义何在,作为交流者的身体如何参与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另一个维度是对具身关系微观展现层面的讨论,将具身关系置于新型媒体环境下,讨论具身关系在某一具体技术中的展现,如AI媒体技术(牟怡,2020)、人工智能主播(於春,2020)等。
针对这些研究,有学者认为目前国内研究对具身性和具身关系的讨论主要关注狭义范畴上的具身,即技术向人的具身,即技术向人的具身,这种具身观从根本上讲并未摆脱工具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广义的具身,即除狭义的具身关系外,还包括解释学关系和背景关系(芮必峰,2020)。新技术环境下,技术与人通常为双向互动关系,人通过技术了解世界,技术也成为解释者,向人类传达信息和解释,并可能对人的行为和活动产生影响,所以仅将具身关系看作人对技术的单向关系是无法真正理解新技术到来所带来的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及其导致的影响,因此“广义的具身”这一研究视野的扩展契合了当前技术的发展规律,为之后对于人与技术关系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四种关系的解释多停留在伊德所反思的胡塞尔(Husserl)的“人—世界”关系模式中,却忽视了其对这一模式中关于反思性维度的补充,伊德认为这一关系模式应为双向维度,反思是在关联更大语境的情况下做出的,是体验的体验(杨庆峰,2015:70)。因此在本研究的讨论过程中,玩家与游戏角色及游戏世界的双向互动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
大陆传播学视角下玩家与游戏角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一方面与我国游戏产业起步与快速发展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电子游戏在我国社会环境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精神鸦片”有关。因此本部分主要对英文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
术语“Avatar”来自梵语,原意指“印度教和佛教中化作人形或兽形的神”,该词作为“虚拟角色”之意最早在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小说《雪崩》 (Snow Crash)中出现,并在计算机及相关学科中普及(Wildt et al.,2019)。Avatar作为虚拟角色通常被定义为“通过计算机技术拟人化的一般图形表现形式”(Belisle & Bodur,2010)。游戏角色正是数字游戏世界中Avatar的一种。本文将游戏角色定义为: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中由玩家创建并控制的人物角色。本文选择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中的游戏角色的原因是,这意味着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呈现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对象,而且是一个主题游戏世界中至关重要的虚拟叙述,是搭建游戏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玩家的主观能动性。
关于角色的争论在传统电影和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部分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物是情节的产物,他们的地位是“功能性的”,他们只希望分析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而不是通过某种外在的心理或道德标准来分析他们是什么(Chatman, 1980:111)。但后续对游戏的研究表明,角色的情节导向设计对于包含叙事(narrative)元素的游戏是有意义的,并且直接与玩家的体验相关(Mallon & Lynch,2014)。随着游戏的发展,角色化和角色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被解构为两种关系,第一种为玩家与预设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游戏角色的行为被游戏设计者预先设定,游戏角色的行为是独立于玩家的;第二种为玩家与控制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只会按照玩家的指示来表现(Mallon & Lynch,2014)。在这两种关系之下,隐藏了游戏设计者与玩家之间的互动,游戏设计者的预设意图本身就会对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玩家如何在已有游戏框架下处理与游戏角色的复杂关系,也是在这一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研究问题1:游戏预设与游戏设计者的存在对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从玩家与游戏角色的互动来看,与其他被动或主动吸引受众且本质上是独立的媒介相反,数字游戏(Video Games)是通过与玩家的互动来吸引受众的(Yoon & Vargas,2014)。在游戏中玩家作为主角开始冒险,他们的选择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游戏比如《超级马里奥兄弟》(Nintendo,1985)和《塞尔达传说》(Nintendo,1986)等,通过将游戏角色作为一个被控制对象达成与玩家之间的初级互动。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游戏在设计中逐渐对这一互动过程进行了改进,让玩家参与到互动体验的多个维度中(Banks,2016)。许多游戏为玩家提供了创建角色并与游戏环境进行互动的功能(Li,Liau & Khoo,2013)。在这种情况下,玩家对他们用来与游戏环境进行交互的游戏角色会产生更加亲密的身份认同或关系。这一时期玩家与游戏角色的研究不再单纯将游戏角色看作玩家的“工具”,而是开始思考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大多将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视为单向的,即其关注角度更多是从玩家对游戏角色来看。梅丽莎·路易斯(Melissa Lewis)等就提出了与电视观众一样,玩家在游戏中与游戏角色的关系是单向、非辩证的,并且这种关系完全存在于玩家的头脑当中,但通过游戏角色的反馈以及游戏机制,玩家与游戏角色好像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互动关系(Lewis,Weber & Bowan,2008)。
随着数字游戏的快速发展,研究者对玩家与角色之间的单向关系提出了质疑,并提出这种关系可能是双向且辩证的(Mendelman et al.,2019)。游戏角色有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参与改变环境(Touraine,2000),也就是说游戏角色是根据游戏内的机制自主运作,并在非战斗环境和游戏故事叙事中合法存在的(Bogost,2012)。在受到玩家控制和影响的同时,角色也会通过游戏中的社会机制对玩家产生影响。通过这些方式,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人类社会中对社会关系的传统定义:两人之间相互影响产生的价值联系(Harvey & Pauwels,2009)。还有些学者将游戏角色视为自我在数字空间中允许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延伸(Banks,2015)。从这一角度来看,数字的自我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重新建构,而是一个人自我的外在投射。
研究问题2: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包括哪些类型?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能否形成真正的社会关系?
研究问题3:在虚拟自我建构过程中游戏角色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玩家在场状态下,玩家的虚拟自我是如何在与游戏角色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类与技术的角度对玩家和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基奥·格布伦丹(Keogh Brendan)将游戏中的玩家看作是一个混合的身体,玩家的肉体、使用的硬件、游戏角色都融入了玩家的身体中。游戏和游戏角色通过屏幕、扬声器等硬件输出的视听感觉将信息发送到大脑,大脑决定玩家动作输出到游戏硬件的输入设备,游戏再次采取这些输入对游戏角色的行为进行改变(Brendan,2014)。玩游戏的瞬间带给玩家的感觉是一种身体器官之间紧密结合所带来的愉悦(Zachery,2016)。这一模型深受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身体现象学的影响,玩家陷入了一个有机的循环当中,而玩家的身体通过其感知游戏的过程也被囊括进了这一循环。
研究问题4:技术如何影响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
总体来看,虽然游戏角色通常因为是虚构角色而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但游戏角色作为一种游戏中的表现技术,从技术及玩家心理层面来看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本文仍是以传统的玩家角度为研究切入点,从玩家的主观视角探求与游戏创建角色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与前人研究关注技术的本质不同,对于伊德来说,他抛弃了对技术的本质追问,更倾向于对具体的经验相关的技术进行分析,所以新技术一直是伊德的后现象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他通过对海德格尔(Heidegger)技术观念的反思,系统性地对新技术观进行阐释,并指出1976年后出现的新技术具有走向微观、改变时空体验、具有多种形态、具有无线特点等特征(杨庆峰,2015:75-76)。受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的限制,他并未完全概括新技术与旧技术的不同之处,技术与人类互动关系的构成也是伊德及其继任者未能更为具体展开的研究对象。本研究所聚焦的游戏角色作为一种借助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而形成的虚拟技术类型,其本身带有与传统技术不同的自主性,即它既是游戏中的一种技术表现和独立存在,也是被玩家赋予特殊意义的在虚拟空间中的“化身”,而这也是构成玩家与游戏角色互动关系的基础。因此,作为对技术的经验研究,伊德的技术中介理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对于游戏角色这一技术的研究有助于对已有理论进行补充和丰富,弥补这一理论在新技术研究方面的不足。
目前唐·伊德的技术中介理论并没有成熟的理论研究框架,根据其提出的“人—技术—世界”关系的连续统(唐·伊德,1990/2012:112),笔者发现在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两组“人—技术”的关系。具体来看,第一组关系为客观现实层面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玩家与游戏外接技术共同构成了与游戏角色互动时的新的身体,而游戏角色成为玩家身体在虚拟世界中外延,帮助玩家了解和参与游戏世界;另一组关系为主观层面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在这组关系中本文更加关注从玩家的主观出发,由他们定义的自身与游戏角色的关系,而非客观现实中呈现出的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玩家主观认知中与游戏角色的关系由于受到玩家自身、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影响更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所以作为这种关系中能动性相对较高的一方,对玩家主观认知的了解有助于扩展研究者对“人—技术”关系的研究视野,能够更好地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定位“人”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二)研究对象
玩家对游戏角色关系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个体性和复杂性,较难通过量化的数据完整地展现,所以本文选择深度访谈这一质化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界定为《剑侠情缘网络版叁》玩家中年龄20-29岁,游戏时间1年以上且在日常生活中有固定游戏习惯的玩家。选择这一游戏的原因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剑侠情缘网络版叁》公测于2009年,已有10年历史,该游戏整体环境建设相对成熟,玩家人数众多,①玩家群体比较稳定,存在较多游戏年龄3年以上的老玩家。这些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互动时间较长且是一个相对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更加具有代表性。二是在游戏中玩家对情节和角色都是有实质性贡献的,玩家可以以不同的目的创建并与游戏角色保持联系,这增加了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关系的多样性,但同时这种自由会受到游戏设计和使用方式的限制。三是相比其他游戏,近年来该游戏的亚文化建设更为活跃,如动画、小说、音乐、舞台剧等衍生品知名度更高,②玩家在游戏之余通过大量作品表达自身对游戏走向及游戏角色的看法。在对玩家主观感受进行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这些作品为研究提供了众多客观资料,使得研究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现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四是笔者作为《剑侠情缘网络版叁》的游戏玩家累计游戏时间超过3年,对游戏本身具有一定的了解,并与自身的游戏角色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作为玩家的参与式观察在访谈材料之外,为研究提供了经验补充。
本文根据研究样本的界定范围,最终选择15名游戏玩家作为访谈对象,访谈时间持续40-90分钟。研究材料收集完成后,使用Nvivo12软件对材料进行编码整理。编码完成后,通过对访谈内容的对比和分析,以概括出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在性别方面,15名游戏访谈对象中有男性6名,女性9名,与该游戏中男女玩家性别比例基本吻合。访谈玩家平均游戏时长为3年,游戏时长较长。游戏角色种族包括15类种族中的9类,种族出现时间和游戏体验跨度较大。③游戏中玩家所属阵营除一直选择的两大阵营外,还包括阵营的转换,情况较为多样。综上所述,所选的15名访谈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对本文起到重要的佐证作用。访谈对象具体情况见表3。
深度访谈主要采用半结构化的提问方式,问题涉及受访玩家的游戏角色选择、受访玩家游戏角色的使用习惯、受访玩家认为的自己与游戏角色的关系、游戏及游戏角色带给受访玩家的影响、受访玩家对游戏的评价等。
四、分析结果
(一)宏观知觉的建构:虚拟情境与文化情境的双重作用
伊德在通过对知觉意义的区分,对胡塞尔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对“人—技术”关系范围应该进行一种双向分析,分析的另一面必须保留“人—技术”关系的文化诠释学(唐·伊德,1990/2012:32),即对身体所处的文化情境进行分析。游戏作为一种宏观知觉,在物质方面为玩家提供了一个即时、沉浸且相对封闭的虚拟情境,另一方面也为玩家提供了一种文化情境,两种情境共同为玩家与游戏角色互动提供了背景环境,玩家通过游戏角色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双方关系得以构建。
1.玩家与游戏设计者的协商:虚拟情境的设置
游戏的虚拟情境主要从两方面构建:一是游戏的整体世界观,二是玩家的个人游戏叙事。游戏整体世界观从根本上决定了游戏的场景设定、剧情发展、角色形态以及角色之间关系。整体世界观一般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游戏的宏观叙事,另一部分为游戏的规则和机制。宏观叙事建构了游戏的背景,帮助玩家通过脚本内容或自我创造的故事与游戏互动,从而使得玩家获得参与感与沉浸感。本文所涉及的游戏参考具体历史进程,游戏开发者为追求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加入了对历史事件的完整想象(闫郡虎,2014)。该游戏背景建构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十几年间,在包含大量大家所熟知的人物的同时,主要视角关注由虚构内容呈现出的武侠世界。背景的真实和流传度增加了玩家在情感上对游戏的熟悉感和代入感,而武侠世界这一带有一定想象色彩的建构又将游戏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进行了区分。受访玩家“人类迷惑行为大赏”表示,在他最喜欢玩该游戏时,游戏带给他的感觉就像是身处另一个世界,游戏中一些在现实空间内无法实现的事情(如轻功、保镖等)、无法再现的场景,带给他独属于虚拟空间的新鲜感。游戏规则和机制则通过规范玩家在游戏内的活动保证了游戏宏观叙事落实到玩家行动中:规则是一种形式上的特质,它在结构上作为玩家行为的框架,对玩家的行为进行语境化处理(Juul, 2005:5)。其与叙事是相互影响、互补的,游戏叙事为规则搭建提供了框架和限制,游戏规则在与玩家互动的过程中丰富了游戏叙事。相比规则更注重游戏内部生态运转,游戏机制——如《剑仙情缘网络版叁》中的门派机制、竞技机制等,主要设计用于玩家与游戏之间的交互(Sicart, 2008),其在调动玩家多种身体感官的基础上,引导玩家与游戏内的元素(如游戏场景、不可操作角色等)互动来进行游戏结构所支持的游戏行为(Squire,2006)。
虽然游戏对玩家的参与设置了限制,但玩家仍有一定的自由选择度,即玩家的个人游戏叙事。个人游戏叙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玩家自身游戏世界观的构建,这通常代表了玩家看待游戏世界的观点,以及寻找自身在虚拟世界中位置的方式,这一世界观往往通过与自我相关联的游戏角色设定及玩家在游戏中的行事方式构建和体现。当游戏整体世界观与玩家个人世界观产生矛盾,即游戏内设定无法满足玩家需求时,就有可能产生“越轨玩家”(transgressive player),玩家通过超出游戏设计者想象的举动,例如利用游戏编程中的漏洞或小故障作弊,反抗“游戏的暴政”,以满足自身的需求(Aarseth,2014)。访谈中玩家“我爱我家”提及他在游戏中利用地图的BUG(漏洞),突破地图限制进行游戏得到很大乐趣。由此可见,在实践个体世界观及与游戏整体世界观斗争的过程中,玩家收获了多重游戏体验,也奠定了玩家与游戏角色关系的基础。二是在游戏叙事模式方面,《剑侠情缘网络版叁》目前采取的叙事模式为线性叙事与分支叙事相结合的模式:在一条主线故事的基础上,每个地图场景中会设立大量与主线故事有一定联系的支线故事,玩家可以根据自身及游戏角色的喜好对故事进行选择性完成,玩家的个人选择从根本上决定了玩家在游戏内的行为和感知方式。三是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社交关系,游戏内的社交关系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呈现双向互动,玩家既可能因为不同玩家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获得新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也有可能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带入游戏当中。玩家在虚拟与现实空间协调的过程中完成了两个空间的勾连,并因此获得跨越空间的情感体验,这也是在访谈中很多玩家提及的与该游戏保持长期联系的原因之一。
游戏虚拟情境设置背后隐藏更多的是游戏设计者的意图,其目的在于保证虚拟空间的完整性和封闭性,以此赋予玩家游戏行为合理性。尽管与其他传统媒介相比,游戏玩家多被作为“积极受众”的代表,但在游戏内他们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因为玩家并不能真正对整体世界的发展进程进行改变。玩家的绝大多数行为仍然是按照游戏设计者的预设进行,这些设定会对玩家的游戏风格产生影响,相比于成为“越轨玩家”,更多玩家关注的是如何在已有设定的规范下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在权力上的不对等状况会对玩家与游戏角色关系产生影响,一方面当游戏角色不能满足玩家的某些行为需求时,玩家会脱离已沉浸的游戏场景并对游戏角色产生疏离感;另一方面,游戏角色成为玩家与游戏设计者协商的对象,为了实现更好的游戏效果,游戏设计者在对游戏角色进行设计和修改时通常会考虑玩家已有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游戏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联系玩家与游戏设计者之间的桥梁。
2.游戏产出对玩家群体认同的建构:游戏文化情境的影响
成为一名游戏玩家不仅与游戏的虚拟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受到游戏产生的文化情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包含了对于玩家这一特定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的认同和实践(Crawford,2012;Shaw,2010;Taylor,2008)。与游戏相关作品的产出在玩家群体认同构建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高质量的作品成为维系玩家与游戏及游戏角色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玩家游戏体验构成的重要部分。
《剑侠情缘网络版叁》作为近几年游戏领域中二次创作极为繁荣的社区,其创作内容丰富,其中既有由游戏官方制作的动画、角色歌、MMD(Miku Miku Dance;三维计算机图形)等,也有由玩家自身制作的同人曲、小说等。这些内容从与游戏本身关联度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为只是借用角色,与游戏关联度不大的内容,这类内容以舞蹈形式的MMD等为主;二为借用游戏世界观,对游戏涉及内容进行延伸的创作,这类内容中游戏角色通常为作品的主角,并会加入官方或玩家自身对游戏及游戏角色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完善游戏叙事的作用;三为抛开游戏故事世界观,专注于讲述玩家游戏的过程,这类内容的主角往往为玩家自己,游戏角色在其中多为玩家在虚拟世界的替身。同时相较于前两类内容,这类作品更容易引起玩家个体的共鸣,如《眉间雪》作为一首描述游戏中玩家师徒故事的同人歌曲,其评论更多不涉及游戏本身叙事,而是回忆并分享自己与游戏好友过去的故事,玩家在抒发自身情感的同时,也通过这些评论对这个玩家群体产生了更强的归属感。
这些二次创作作品对认同的建构主要包括三个维度:首先,它们为玩家提供了将“游戏”输出到游戏之外的机会,玩家通常会将游戏中对角色的主观认知(如角色名称、形象、观点等)通过这些作品扩展到游戏之外。在这个过程中,玩家实现了从“玩”者到“设计”者的角色转变,创作者因此能够获得丰富的亚文化资本,从而提升自我认同(王清华,2020);其次,这些作品对于玩家将体验引入游戏中非常重要,许多玩家通过作品中传达的信息对游戏及游戏角色产生了新的偏好和期望,并会将这些偏好带入游戏中;第三,这些作品为价值观相似的玩家提供了链接的节点,在《剑侠情缘网络版叁》中这种价值观的相似通常体现在对游戏角色门派或阵营认同的基础上。一方面相关作品成为玩家群体拥有的共同回忆,提供了独属于本群体的符号;另一方面,这些来自“民间群体”的内容也为游戏的官方话语提供了新的素材来源,游戏设计者与玩家群体的良性互动帮助玩家获得一种跨空间联通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玩家对游戏的归属感,增加了玩家对游戏的沉浸感,也丰富了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主观认知关系。
(二)玩家与游戏世界的技术中介:玩家对游戏角色的使用
在伊德的理论中,技术作为重要的对象,并非仅仅是知觉的衍生,它更表现为人类身体的外化(杨庆峰,2015:84)。游戏角色作为游戏中重要的核心机制,同时作为一个复杂技术主体,其既是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认为的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再现身体(凯瑟琳·海勒,2012/2017:6-7),是玩家身体活动扩展到游戏世界的表现,又因游戏设计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这种技术的复杂性一方面使得个体玩家在现实空间内一致的感官与理智认知发生分离,即游戏过程中玩家理性认知能够分辨自身与游戏角色的不同,但生理性感官与游戏角色形成一个整体,沉浸于虚拟空间的在场感中;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不同玩家对游戏角色关系理解的不一致。
游戏的外接技术是连接数字游戏角色与玩家现实身体感官的重要中介物,通过玩家的输入和对玩家的输出,外接技术完成了对玩家身体的融合及重构,形成了新的“赛博玩家”身体(孙玮,2018),并与游戏角色进行互动。外接技术主要包括显示装置和控制装置两部分:控制装置主要包括基础的物理硬件,比如鼠标、键盘等。控制装置作为玩家身体的延伸,通过对游戏角色的操作,帮助玩家将其感知和意识扩展到虚拟的游戏世界中。显示装置主要包括游戏内容的呈现硬件,比如屏幕、音响等,显示装置将原本抽象的代码世界具象地展示在玩家面前,通过刺激玩家的感知,从而带给玩家一种身体的“在场感”。外接技术弥合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距离,撕裂了原有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在玩家游戏过程中,这些设备使得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得以重叠存在。同时,玩家为了在游戏过程中达成“技术抽身而去”的效果会不断调整自身的外接设备,这种调整通常建立在长时间的游戏实践基础上。在调整的过程中,玩家与游戏角色的融合感会随着技术的逐渐“透明”而逐渐增加,游戏角色对于玩家的独特性逐渐显现。
游戏角色作为一种用户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虚拟技术,与传统技术在使用者眼中属性相对固定不同,对于使用者而言,其具有两种属性:首先作为游戏设计者统一设计的数字代码,它呈现出一定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游戏设计者希望通过类别化游戏角色向玩家快速传达有效信息,所以刻板印象在游戏中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Banks,2013),为玩家提供了无需冗长或详细的故事框架就可以识别游戏角色和场景特征;而当游戏被启动后,游戏角色则成为玩家实体在游戏世界中的数字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游戏给予了玩家在某些方面赋予游戏角色个性化的权利,例如玩家能够对游戏角色的脸部进行调整,因此每个人不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变成了众多数字化元件或元素的集合,这些元素可以从个体身上分离,并与其他对象结合形成一个新的数字化个体(彭兰,2020:357)。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玩家与游戏角色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狭义的具身关系,游戏角色成为玩家认识和了解被建构的游戏情境的技术中介,同时玩家也会根据对所选游戏角色的预期进行相应的游戏行为,即普罗透斯效应(Proteus Effect;Yee & Bailenson, 2007)。游戏内玩家的游戏行为为玩家与游戏角色共同完成,玩家作为决策者,他的游戏角色是在游戏世界中执行这一行动的主体。行为的执行是根据双方实际得到或感知到的目标、背景、能力等相关资源来实现。这种共同执行是由于玩家或游戏角色被认为在某些能力方面存在缺陷,例如玩家身体无法真正进入游戏世界,与其他非玩家创建角色相比,游戏角色自身的行动意识较弱等。共同执行组合的形成使得游戏角色成为游戏世界中具有一定存在意义的主体,它们与玩家之间共同分享的经验,体现了两个主体在共享空间中的社会共存,也形成了两者互动关系构建的基础和平台。
(三)玩家对多元关系的认知与建构:主观层面中玩家与游戏角色关系
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在以身体形式存在的我通过技术与环境之间交互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杨庆峰,2015:178),因此通过游戏角色与游戏的虚拟情境交互的过程中,不同玩家在主观层面形成了对与游戏角色关系的差异认知。图1的聚类分析表明,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玩家主观对游戏角色这一复杂技术认知角度包含甚广,包括情感表达、社交关系、规则技术、与现实的关系等,不同的认知方式会对玩家对游戏世界的关注和理解产生诸多影响。根据聚类结果与笔者参与式观察的结果,本研究将玩家与游戏角色主观认知关系分为三类,即狭义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和它异关系。
1.狭义具身关系:作为工具战略考量的游戏角色
具身关系是人的身体知觉和技术中介联系在一起,然后去感知世界(张正清,2014)。这种关系下,玩家与游戏角色在玩家观念中通常是分离的。玩家认为游戏角色只是他们融入游戏世界的工具,游戏角色的外观、行为体现了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意志和希望,同时会与玩家及游戏设定的目标相结合。他们无需将游戏角色与自己视为一个整体也可以愉快地进行游戏。玩家与游戏角色通过互动构成的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Mills & Clark,1982),这种利益分为两种:一种为游戏内玩家的利益,享受这种利益的玩家更倾向于为了游戏目的(如取得比赛胜利)使用游戏角色;另一种为现实生活中玩家的个人需求。在访谈中,受访玩家“养了一只南小鸟”就表示游戏角色是他完成功利性任务的一个工具,他的游戏角色一方面满足了他在游戏中的需求,如要有什么技能,能在副本中做什么,另一方面满足他的个人一些需求,比如审美的需求。但他对游戏角色也不是漠不关心,他仍然会为游戏角色的外观、武器等进行消费。由此可见这类玩家对游戏角色抱有感情,但这种感情和关心往往是温和且物体性的,类似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一件喜欢的物品表达的喜爱和关心(Banks,2013)。
身处具身关系的玩家所拥有的游戏角色较少(一般为1到2个),并且这些游戏角色的类型通常较为一致。这一选择通常是为了保证对游戏角色操作的流畅程度,以及保证足够的游玩时间以对游戏角色进行培养。游戏本身是玩家关注的重点,游戏角色是可以被操纵、修改和设计的无生命物体。同时玩家对游戏角色的认知更多是一种泛化的认知,玩家仅仅将正在进行的游戏当做游戏虚拟空间中的一个子空间,在这类玩家的自我意识中,他们是多个游戏空间的主导者,拥有一种跨空间的“掌控感”,而对游戏角色的控制是这种“掌控感”的外在表现。
在这一关系视角下,玩家对游戏世界中其他要素的认知也围绕着战斗和竞技展开。与其他关系相比,这类玩家中较少出现广泛的社交网络,他们主要关心能够帮助他们在游戏中有效竞争的群体。在这类玩家看来,社交群体是游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关系的建立通常以游戏角色的形式出现,同时可以根据个人目标进行操作、塑造或调整。换言之,这些玩家的个人网络中排除了任何可能影响他们将游戏空间当做竞技空间,或不利于他们专注于游戏的社会群体。
2.解释学关系:玩家的自我延伸
与狭义具身关系中技术仅作为知觉的延伸不同,解释学关系是用身体知觉去感知技术中介所感知的世界(张正清,2014)。身处解释学关系的玩家,不仅将游戏角色当做参与游戏世界的工具,也将其当做自己在游戏世界中的“面具”,是玩家表达自身对游戏世界理解的符号表现,同时也是玩家在虚拟空间中自我意识的具象表现。这类玩家形容与游戏角色关系时会使用带有关心、亲近和喜爱的词语来表达对游戏角色的感情,同时也会表达出与游戏角色共享的情感,但他们的描述通常是模糊的,或将游戏角色的功能特征与玩家对其的情感语言相结合。同时他们更加关心游戏角色对玩家游戏理解和自我展示的帮助,而不只是游戏角色如何帮助他们在战斗中取得胜利。
在这一关系中,玩家通常拥有更多的游戏角色数量(一般为3到4个),游戏角色的类型也更加多元,这些游戏角色成为将玩家日常复杂的自我意识转化到游戏世界中的中介。受访玩家“五花肉”在访谈过程中提到她在游戏的两个服务器中一共有3个游戏角色,但她为所有的游戏角色都设定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即行事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这与她在现实空间中的性格类似。由此可以看到,尽管玩家认为自己是双方关系中的主导者,但为了方便自身身份在数字游戏空间中展开,他们会选择与游戏角色共享某些属性和要素,例如玩家在现实空间中已有的外貌或性格特征。
与狭义具身关系不同,社群通常为解释学关系中重要的组成元素。这一关系中主要包含两种社群类型:一类为游戏内社群,在该游戏中游戏内社群(又称为阵营)分为两派,一派为浩气盟,一派为恶人谷,不同的社群拥有不同的行为标准。在谈到对阵营的选择时,受访玩家“秋月梧桐”认为加入恶人谷阵营的人大部分并没有真正贯彻恶人谷所谓的“正义”,所以她在选择阵营时选择了浩气盟。她道出了玩家选择游戏内社群的方式:那些加入游戏内社群的玩家在选择社群时会将自己代入游戏角色的视角,以游戏角色对世界的理解为基础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是属于玩家自身独特标签的一部分,也是完善游戏角色表现的重要因素。
另一类现实空间社群往往由游戏中好友关系发展而来,由于社群内成员通常为现实生活中并不相识的陌生人,所以玩家之间会根据游戏角色的特征进行沟通和相处。同时玩家倾向于创造代表他们对于“我”独特理解的游戏角色,拒绝那些不属于“我”的束缚,而从社群中得到的反应是这一创造的重要参考系。
3.它异关系:玩家自我的反思与实践
与具身关系及解释学关系相比,伊德在著作中对它异关系探讨的篇幅有限,随着虚拟技术的发展,这一关系中所隐含的关于交互主体性的问题逐渐显著。在这种关系中,玩家不仅将游戏角色当做自己在游戏世界中的技术工具,还将游戏角色作为游戏世界中已经存在的个体来操作。与国外相关文献研究结果不同,如图1所示,在访谈过程中,这类玩家会使用工具性的语言表达他们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但与处于狭义具身关系的玩家不同,他们的话语通常以不同主体间对话的方式展现。玩家“神飞云”在谈及他与游戏角色完成任务时使用的话语是“希望他(游戏角色)能够帮助我”,而不是“我使用他”。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游戏角色作为独立个体,玩家更加关心自己游戏角色的幸福,而对能够创造的玩家利益关注程度相对较低。
身处它异关系的玩家通常拥有较高数量的游戏角色(一般为2到3个),游戏角色所属类型相对多样。在这类玩家眼中,游戏角色是游戏世界中一个具有自主能力的主体,其行为会受到玩家意识与游戏角色自主意识两方面的影响,同时有些特征独属于游戏角色,例如与游戏角色身份相关的名字、武器装备、外观外貌特征等。玩家总会在讨论游戏角色时提及相关特征,并将这些特征组合从而获得玩家所认可的游戏角色的独立人格和行事意义。
在组合过程中,不同玩家对游戏角色主观认识的复杂程度是不同的。其中最简单的认知来源于游戏角色以何种方式直接存在于玩家的想象中,这种直接的想象使得游戏角色在玩家脑海中拥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人格,例如受访玩家“折梅可寄卿”对游戏角色认知的形容只有简单的“儿子”两个字。相对复杂的认知中的游戏角色拥有多维度的人物网络,结合了行为、性格、外貌特征等一系列属性,例如受访玩家“五花肉”对她的游戏角色的形容是“生活在唐朝的一个胸无大志的普通平民百姓”,与前一受访玩家对其游戏角色的认知只有模糊的定位相比,她对其游戏角色的认知已经类似于存在于现实空间的真实人类。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玩家主观认知中的游戏角色“人格”复杂,但这些属性的抽取通常是与游戏世界已经建构的背景相关。这表明复杂的游戏角色“人格”的构建更具有目的性,也是将它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关键。换言之,复杂游戏角色的建构是玩家的有意塑造,而不是来自于没有计划或突发的游戏行为。
在这一关系中,游戏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游戏设计者的意志,因此是以“准他者”的身份出现,即比单纯的对象性要强,但弱于人类或动物这类主观能动性更强的他者(唐·伊德,1990/2012:104)。互动过程中,游戏角色这一“准他者”个体作为玩家构建自我的镜子和他者,参与到个体自我的建构对话中,成为与主我互动的客我。同时,游戏角色的视角也随着个体对“准他者”角色的接纳进入个体的自我。同时由于游戏角色作为他者的陪伴,在这类玩家眼中与其他玩家的社交互动并没有过多的必要性,玩家“人类迷惑行为大赏”在访谈中表达了他不愿社交的原因:“游戏里的玩家朋友总会离开,只有游戏角色永远存在于游戏世界中等着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玩家游戏上瘾、与社会脱节的隐患。
总结来看,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主观认知关系是一个解蔽与遮蔽的关系,狭义的具身关系中玩家更关注游戏世界本身带来的体验和感受,而它异关系和解释学关系则更关注在游戏世界获得体验的基础上对自我世界的展现和完善。
(四)游戏价值定义的改变:玩家与游戏角色关系主观认知的动态变化
游戏设计者与玩家权力关系不平等带来的结果之一是游戏设计者意图与玩家需求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了玩家与游戏角色关系的不稳定,其影响因素在于玩家的游戏体验及其对游戏价值的定义。
玩家的游戏体验通常影响玩家对游戏角色的短期态度,并不会对整体认知产生过大的影响。从游戏角色角度来看,玩家游戏体验的来源主要包括游戏角色对玩家的反馈及能够带给玩家的游戏回报。有研究表明,玩家希望作为构建游戏世界的奖励,游戏能够承认他们是游戏角色取得成功不可缺少的要素。因此游戏角色对玩家的反馈对他们来说是反映与游戏角色关系的重要判断依据。通过游戏角色对玩家输入命令及时、合乎逻辑的反馈,玩家的沉浸感和参与感增加,使得玩家获得一种与游戏角色融为一体成为游戏主角的感受;但当游戏角色的反馈迟缓或不合现实常规时,例如卡入空气墙、无法正确举起已选中物体等,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偏差会使玩家的挫折感和对游戏角色控制的无力感上升,正如前文所提及,玩家可能会因此脱离游戏的沉浸环境,对游戏角色产生负面情绪和态度。另一方面,玩家会通过计算付出与回报之间的比例考虑自身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这种比例建立在游戏世界观对于成功定义的基础上,既包括对玩家自身的影响,也包括对游戏角色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中,面对小成本游戏失败时,例如个人挑战死亡,玩家更多会认为自己与游戏角色应该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在考虑自身操作问题的同时,也会考虑到自己游戏角色的能力问题;但当失败责任过于重大,例如一人责任导致队伍全灭时,玩家为了逃避相关责任,会倾向于将自身与游戏角色分割,更多去责怪自己的游戏角色,而不去反思自己如何导致游戏失败。
而玩家对游戏价值的定义则会从宏观层面改变他们对与游戏角色主观认知的变化。具体来看,玩家对游戏价值定义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玩家游戏实践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玩家享受游戏并从中获益的核心。实践动机主要包括四类:战斗与竞争、社交与日常实践、自我协商与意义建构、逃避与划分(Banks, 2013)。游戏实践动机为战斗与竞争的玩家更倾向于将游戏角色作为一种工具;实践动机为社交与日常实践和自我协商与意义建构的玩家更倾向于将游戏角色作为一种自我延伸;实践动机为逃避与划分的玩家则更多将游戏角色看做独立的个体,成为他们“第二人生”的陪伴者。随着玩家对游戏核心需求的满足与变化,玩家对游戏角色的观点和定位也随之发生变化;第二,游戏相关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玩家对游戏价值定义的改变。对于关注相关作品的玩家而言,随着游戏的二次创作对游戏世界观及游戏角色的不断补充和完善,游戏角色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逐渐演变为一个复杂的具象形象。在玩家不断认同作品的过程中,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也从较为浅层的利用关系发展为更为深层的共生关系。
(五)游戏角色对玩家虚拟空间主体性的完善:对虚拟自我产生的影响
尽管伊德的理论推动了技术现象学的发展,但仍有学者,如基兰(Kiran)就对其观点持批判态度(Kiran,2012)。国内有学者认为基兰批评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指出了伊德的技术现象学不能够真正说明技术对于主体性自身的内在建构作用,而这恰恰是现象学之为现象学最为要紧的地方(吴宁宁,2015)。在玩家与游戏角色这一组对象中,无论玩家主观对游戏角色持有何种看法,出于保证自身游戏体验的直接目的,他们会在搭建和维持与游戏角色的关系的过程中建构出虚拟自我用以保持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停留在舒适的虚拟与现实关系框架内。而这种虚拟自我的建构一方面是对“赛博人”玩家在虚拟空间中主体性的完善,另一方面又会对现实空间中实体玩家的自我产生影响。
虚拟自我的建构主要发生在两个维度:首先是玩家对建构虚拟自我元素的筛选和接受,玩家会根据直接经验,以对玩家与游戏角色关系的支持程度为基础,将与游戏角色相关的元素进行划分,主要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支持元素、干扰元素及一般元素。受访玩家“牛奶o0O瓶”在访谈中提到,她为了保持自己游戏角色的设定,会选择刻意做一些与设定相关的事情,这些任务和某一社群的加入被她划分为支持自身与其游戏角色关系的元素,因此她在面对这些元素时选择了积极接受甚至刻意完成的态度。而那些不利于维持双方关系的元素,如游戏内的另一阵营,则被她忽视甚至采取抵抗行为。总结来看,基于玩家对元素的划分,他们会对不同类别的元素做出相应的回应,面对支持元素时玩家会采取接受态度;当面对一般元素时,玩家会被动接受或选择性忽略该元素;当面对干扰元素时,玩家会采取不接受或试图改变的态度。但如果这些元素为游戏中的既定设置无法被消除,玩家为了保持一种舒适的双角色状态会将这些干扰元素的存在合理化,而这种对元素的重新建构是一种重要的自我建构方式。
在虚拟自我建构的第二个维度中,玩家会在对元素筛选和接受的基础上,将这些元素组合,有选择地建构虚拟自我的维度。那些被玩家忽视或“停用”的元素并不是不存在,而是被玩家推到了“后台”(欧文·戈夫曼,1959/2016:24),被激活的元素则相互协调产生了虚拟自我。对于这一虚拟自我建构过程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在玩家和游戏角色两者中同时存在但意义不同的元素,如果这些具有不同意义的元素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是兼容的,那么当玩家与游戏角色建立密切互动关系时,这些元素可能会相互作用形成虚拟空间中的自我。
正如前文所言,虚拟自我是建立在现实自我基础上的,现实自我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都会通过对游戏角色产生作用,从而影响玩家虚拟自我的建构。而当谈到游戏角色对玩家现实生活的影响时,受访玩家司空樱表示万花门派平淡如水的门派内涵改变了她原本看待生活的方式,与游戏角色的互动改变了她作为玩家对自我和事物的认知框架,这个认知框架不仅停留在虚拟空间中,也会通过影响玩家的观念和态度作用于现实空间。同时,虚拟自我作为个体对自我实现的“试验场”,会随着游戏角色和周围情境的改变而产生改变。当个体实现当前目标下的自我维度时,新的虚拟自我维度又会出现,成为现实自我的理想目标,从而进入“虚拟自我→现实自我→虚拟自我”的循环中(马忠君,2010)。
五、结论与讨论
从玩家与游戏世界的角度来看,游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身是从开发者的角度来构思的,所以当玩家与游戏环境互动时,背后隐藏的是玩家与游戏设计者之间的互动协商关系,游戏角色作为处于游戏设计师和玩家之间的载体,既要传递符合游戏世界的设计师意图,又要容纳玩家的自主操作。从“人与技术”的关系视角来看,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融合、动态变化的。与电影、电视剧、小说等媒介只构成一种表现形式,然后受众在特定的接受语境中对其进行解读并与其中角色产生关系(Potzsch & sisle,2019)不同的是,数字游戏包含了一系列条件化的表现形式,如游戏的规则、叙事方式等,然后由玩家进行协商和选择。因此虽然受到游戏设计者预设意图的影响,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仍体现了高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通过游戏实践表现出的内容是玩家意愿和选择与游戏本身相结合的结果。这些因素共同产生了在游戏中有条件的、个性化的玩家与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而在玩家与游戏角色互动的过程中,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人类确实与虚拟的创造物之间形成了真实的关系和情感的依赖,同时这种关系最终表现出的多元层次与现实生活中人类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在唐·伊德的理论框架下,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因此并不能真正揭示技术对于主体的构造,经验的自身性、主体性层面无法得到展开(吴宁宁,2015);同时虽然伊德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双向维度的,但他所确立的人与技术的关系都是基于单向意向性基础的,即从人指向技术(杨庆峰,2015:210)。通过对玩家与游戏角色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玩家与游戏角色不再是站在镜子的对面,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在玩家操纵游戏角色的过程中,游戏角色也在改变着玩家的世界观以及日常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访谈中多数玩家承认在最初为自己的游戏角色赋予了某些设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赋予游戏角色的个性会反过来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游戏一方面能够带给玩家关于道德、历史文化、生存方式等问题的反思,另一方面也为玩家实践自身想法提供了实验平台。游戏角色作为一种包含人类属性、技术属性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对象,通过自身功能及与玩家所建立的情感关系,成为玩家解决自我困境,如形成新的自我维度、逃避现实等,建构玩家内在主体性的重要助力。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访谈对象在年龄、学历等基础信息方面同质性较高,所以在分析时并未出现与国外文献中相似的重度沉浸玩家;其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处于文化情境中玩家的“恰当行为”只进行了较为简单的梳理,并未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在今后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可以以现有研究为基础,将玩家的二次创作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玩家以作品方式体现出的对角色的认知,通过客观材料进一步丰富对玩家与游戏角色复杂关系的认知。■
注释:
①从数据来看,2019年金山软件第四季度财报显示:第三季度金山软件旗下网络游戏每日平均最高用户同步人数约61.16万,每月平均付费账户约253.2万。但由于游戏自身生命周期,用户数量,特别是付费用户面临逐渐减少的压力。
②动画方面,西山居工作室自2018年起制作三部根据该游戏改编的动画《剑网3·侠肝义胆沈剑心》,《剑网3·侠肝义胆沈剑心Ⅱ》,《剑网3·侠肝义胆沈剑心之长漂》,单部播放量均突破千万;音乐方面,多首同人歌曲,如《参商》、《我的一个道姑朋友》等播放量突破千万,评论突破万条,且被多次翻唱。
③《剑侠情缘网络版叁》中游戏角色种族按照上线时间排序包括:凌雪阁(2019年)、蓬莱(2018年)、霸刀(2016年)、长歌(2015年)、苍云(2014年)、丐帮(2013年)、明教(2012年)、唐门(2011年)、五毒(2011年)、藏剑(2010年)、万花(2009年)、纯阳(2009年)、少林(2009年)、七秀(2009年)、天策(2009年)。新的游戏角色种族的上线通常伴随着新资料片的推出。
参考文献:
戴宇辰(2018)。“在媒介之世存有”:麦克卢汉与技术现象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0),82-96+127-128。
哈里·柯林斯(2010)。什么是意会知识。《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凯瑟琳·海勒(2017)。《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海龙,束开荣(2019)。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80-89。
马忠君(2010)。虚拟化生存的基础——虚拟真实与虚拟自我的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118-121。
牟怡(2020)。从诠释到他异:AI媒体技术带来的社交与认知变革。《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2-101。
欧文·戈夫曼(2016)。《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兰(2020)。《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芮必峰,孙爽(2020)。从离身到具身—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国际新闻界》,(5),7-17。
孙玮(2018)。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12),83-103。
孙玮(2018)。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6),4-11。
唐·伊德(2012)。《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清华(2020)。IP社群的符号消费与文化认同—以手游“阴阳师”玩家为例。《东南传播》,(8),84-88。
吴宁宁(2015)。技术中介经验的自身觉知——对伊德技术哲学的现象学批评。《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32-239。
闫郡虎(2014)。电子游戏的叙事模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重庆大学。
於春(2020)。传播中的离身与具身:人工智能新闻主播的认知交互。《国际新闻界》,(5),35-50。
杨庆峰(2015)。《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章戈浩(2018)。数字功夫:格斗游戏的姿态现象学。《国际新闻界》,(5),27-39。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情况统计报告》。检索于http://www. cnnic. net. cn。
张正清(2014)。用知觉去解决技术问题—伊德的技术现象学进路。《自然辩证法通讯》,(2), 86-92+127。
Aarseth, E. (2014). I fought the law: Transgressive play and the implied player. In From literature to cultural literacy (pp. 180-188). Palgrave MacmillanLondon.
Banks, J. & Bowman, N. D. (2016). Emotionanthropomorphism, realismcontrol: Validation of a merged metric for player avatar interaction (PAX).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4(JAN)215-233.
Banks, J. (2015). Object, me, symbiote, other: A social typology of player-avatar relationships. First Monday, 20(2).
Banks, J. & Bowman, N. D. (2016). Avatars are (sometimes) people too: Linguistic indicators of para-social and social ties in player-avatar relationships. New Media & Society18(7)1257-1276.
Banks, J. (2013).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ality and self-network organization: players and avatars in World of Warcraft. Fort Collin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Belisle, J. & BodurH. O. (2010). Avatars as information: Perception of consumers based on their avatars in virtual worlds. Psychology & Marketing27741-765.
BogostI. (2012). Alien Phenomenology: Or 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rendan, K. (2014). Across Worlds and Bodies: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Video Games. Journal of Games Criticism , 1(1)1-26.
Chatman, S. B. (1980).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rawfordG. (2012). Video Gamers. New York: Routledge.
HarveyJ. H. & PauwelsB. G. (2009). Relationship connection: A redux on the role of minding and the quality of feeling special in the enhancement of closenes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385-392.
Kiran, A. H. (2012). Technological Presence: Actuality and Potentiality in Subject Constitution. Human Studies35(1)77-93.
KirstyB. (2010). Redefining the Technology of Media.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Quarterly Electronic Journal14(2)140-157.
Lewis, M. L. , WeberR. & Bowman, N. D. (2008). They may be pixels, but they’re MY pixels: Developing a metric of character attachment in role-playing video games.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11(4)515-518.
LiD. D. , Liau, A. K. & Khoo, A. (2013). Player-avatar identification in video gaming: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1)257-263.
MallonB. & LynchR. (2014). Stimulating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s in narrative games: engaging players with game characters. Simulation & gaming, 45(4-5)508-527.
Mendelman, L. , RatanR. , FordhamJ. , KnittelM. & MilikO. (2019). Sentimental Avatars: Gender Identification and Vehicles of Selfhood in Popular Media From Nineteenth-Century Novels to Modern Video Games. Games and Culturefirst online: https: //doi. org/10. 1177/1555412019879812.
Mills, J. & ClarkM. S. (1982). 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verly HillsCA: SAGE, 121-144.
Potzsch, H. & islerV. (2019). Playing Cultural Memory: Framing History in Call of Duty: Black Ops and Czechoslovakia 38-89: Assassination. Games and Culture14(1)3-25.
ShawA. (2010). What is video game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and game studies. Games and Culture5(4)403-424.
TaylorT. L. (2008). Beyond Barbie and Mortal Kombat: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gamesand computing. 2008Cambridge: MIT Press.
TouraineA. (2000). A method for studying social actor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1(3)900-918.
Wildt, L. D. , Apperley, T. H. , ClemensJ. , FordyceR. & MukherjeeS. (2019). (re-)orienting the video game avatar. Games and Culturefirst online: https://doi. org/10. 1177/1555412019858890.
Yee, N. & BailensonJ. (2007). The Proteus effect: The effect of transformed self-representation on behavior.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3)271-290.
YoonG. & Vargas, P. T. (2014). Know thy avatar: The unintended effect of virtual self representation on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cience251043-1045.
Zachery, R. (2016). My Avatar, My Self: A Posthuman Examination of Video Games and Cyborg Bodies. Huntington: Marshall University.
李彪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琳轩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编号:20&ZD3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