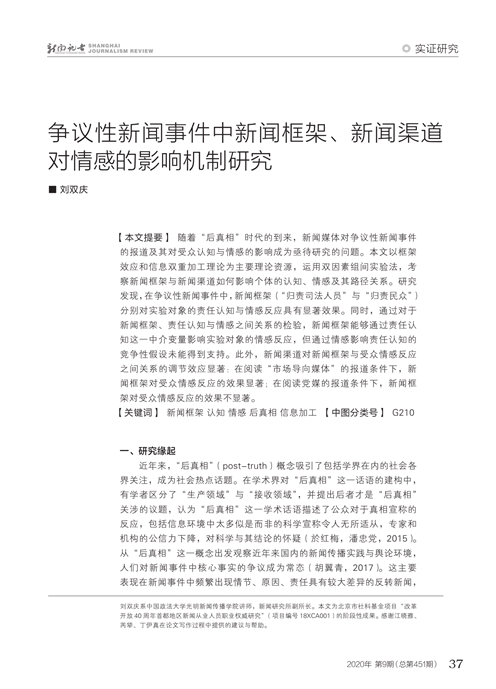争议性新闻事件中新闻框架、新闻渠道对情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刘双庆
【本文提要】随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新闻媒体对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及其对受众认知与情感的影响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以框架效应和信息双重加工理论为主要理论资源,运用双因素组间实验法,考察新闻框架与新闻渠道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及其路径关系。研究发现,在争议性新闻事件中,新闻框架(“归责司法人员”与“归责民众”)分别对实验对象的责任认知与情感反应具有显著效果。同时,通过对于新闻框架、责任认知与情感之间关系的检验,新闻框架能够通过责任认知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但通过情感影响责任认知的竞争性假设未能得到支持。此外,新闻渠道对新闻框架与受众情感反应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在阅读“市场导向媒体”的报道条件下,新闻框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显著;在阅读党媒的报道条件下,新闻框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不显著。
【关键词】新闻框架 认知 情感 后真相 信息加工
【中图分类号】G210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后真相”(post-truth)概念吸引了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在学术界对“后真相”这一话语的建构中,有学者区分了“生产领域”与“接收领域”,并提出后者才是“后真相”关涉的议题,认为“后真相”这一学术话语描述了公众对于真相宣称的反应,包括信息环境中太多似是而非的科学宣称令人无所适从,专家和机构的公信力下降,对科学与其结论的怀疑(於红梅,潘忠党,2015)。从“后真相”这一概念出发观察近年来国内的新闻传播实践与舆论环境,人们对新闻事件中核心事实的争议成为常态(胡翼青,2017)。这主要表现在新闻事件中频繁出现情节、原因、责任具有较大差异的反转新闻,甚至在媒体的调查、澄清与相关责任人的回应之后,事件中的核心责任仍然难以达成共识。这在近年来发生的“医患冲突”、“司法冲突”等争议性新闻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类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往往使用很大篇幅描述事件中的相关责任者。在媒介化时代,新闻报道往往会塑造人们对于争议性新闻事件的认知与情感。框架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
框架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它为新闻媒体如何呈现社会生活、影响人们的认知与情感提供了理论解释。学者们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认知语言学、信息科学等不同学科传统对框架理论进行研究(Borah,2011)。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闻媒体如何呈现社会生活,即“传播中的框架”,而较少涉及新闻框架对人们认知与情感的影响,即“个体心中的框架”。这导致对于媒介心理学传统下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的研究相对不足。
此外,近年来已有研究关于框架对认知和情感的影响机制存在争议(Nabi, 2003),即到底是新闻框架通过认知影响情感还是通过情感影响认知?有研究发现,情感是框架与责任认知之间的中介变量(Major,2011),但近年来也有研究证实,新闻框架通过责任认知这一变量引起受众的情感反应(Kühne, Weber & Sommer, 2015)。除了新闻报道内容(新闻框架)之外,新闻渠道也会影响受众对于信息的加工与解读(Chaiken, 1980),特别是在信息过载、人们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渠道本身也是影响人们对于新闻事件进行解读的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采用思辨研究路径,很少有研究通过数据的收集对这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检验。实验法可以通过对相关变量的控制,以考察核心变量(如框架、渠道、认知、情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此,本文从框架效应与信息的双重加工理论出发,运用双因素组间实验设计(2×2 between-subject design experiment)考察在争议性新闻事件的语境中,新闻框架、新闻渠道如何影响人们对于事件中责任的认知与情感反应,以及它们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具体关系与路径。
二、理论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框架与责任归因
美国政治学者恩特曼(Robert M. Entman)将框架研究描述为一个“支离破碎”的研究范式(Entman, 1991)。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框架进行概念化。总体而言,框架研究可以划分为社会学与心理学两大研究传统。前者聚焦新闻与社会建构中的选择与突出,后者关注个体心中的框架(Borah, 2011)。
框架效应是指对一个议题叙述的变化所带来受众意见的变化。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框架效应关注新闻框架如何影响个体心中框架的过程(Chong & Druckman, 2007; Shulman & Sweitzer, 2018)。在本研究关注的争议性新闻事件的语境中,这一理论为理解新闻媒体对争议性事件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与情感提供了解释。美国传播学者阿岩伽(Shanto Iyengar)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知识中,“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个体常常会对他们观察到的大大小小的现象进行责任归因。而信息环境,如上文论述的新闻框架会通过对特定片段或属性的突出以形塑人们对相关议题中责任归因的认知(Iyengar, 1996)。有国外学者通过对2601篇报纸报道与1522个电视新闻的内容分析后提出,“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框架是使用最广泛的五类新闻框架之一。“责任归因”框架是指媒体在对一个事件或问题进行报道时将其原因或解决方案归结为个人、组织或政府(Semetko & Valkenburg,2000)。同时,有研究对近年来国内媒体关于社会安全、事故灾难等四类具有争议性的公共事件的框架分析后认为,媒体报道中较为注重“责任框架”的使用(张伦,钟智锦,2017)。
在本研究关注的争议性新闻事件中,“责任归因”框架也是新闻报道中频繁使用的框架。例如,近年来新闻媒体对“冀中星”、“夏俊锋”、“于欢”等具体新闻事件的报道中都运用了该框架(陈斌,2014:37-38;殷韵,2018:18;李诚付,韩敏,2014)。这些事件有一个共性:虽然涉案人员存在伤害司法公职人员的事实,但引发冲突的责任主要是公职人员不规范的职业行为还是民众的暴力行为,往往存在较大争议。例如,在“夏俊锋事件”中,夏俊锋在执法现场是否曾遭到殴打成为事件的一个争议焦点。归因往往蕴含着当下社会中特定的文化心理或思维定势。媒体对这些争议性司法冲突事件的报道中,逐渐形成了“官—民”的二元对立框架(袁光锋,2014)。这种“官—民”的二元对立在争议性司法冲突事件的责任归因中表现为,将引起冲突的责任归结于“司法人员的责任”或是“民众的责任”。新闻媒体在冲突事件的报道中会通过对不同片段与不同行为的强调与突出,实现责任分配。例如,有研究通过框架分析发现,在新闻媒体对城管与商贩冲突的报道中,运用了二元对立的操作手法,将责任归结为城管的“不当执法”与商贩的“暴力抗法”(魏云鹏,2017:32)。结合前文论述的框架效应理论,媒体对于新闻事件中特定片段与情节的突出会影响人们对相关事件中责任的认知。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新闻框架会影响实验对象对争议性事件中责任的认知。当新闻框架归责于司法人员时,实验对象倾向于认为司法人员对冲突负有更多责任;新闻框架归责于民众时,实验对象倾向于认为民众对冲突负有更多责任。
(二)情感的转向与“情感作为框架”
随着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情感的转向。近年来,学者们尝试探索新闻框架对于受众情感的影响(Nabi, 2003; Lecheler, Schuck & de Vreese, 2013)。例如,在政治传播领域中,一些学者认为,受众的情感会受到与政策有关信息的影响(Kim & Cameron, 2011)。
然而,作为框架效应关涉的重要心理机制,认知与情感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研究中关于框架对于认知和情感之间的机制与路径存在争议。情感的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ies of Emotion)认为,特定的新闻框架会使受众产生愤怒、恐惧、悲伤等情感。根据该理论,这些不同情感源于受众对于新闻事件的评估。这些评估不仅仅反映一个事件的具体属性,还会与人们的兴趣与偏好发生联系,从而引起特定的情感。换言之,如果受众认为他们收到的信息包括一定的关系主题且与他们个人息息相关,这个文本往往会激发特定的情感。虽然人们基于对外部环境感知的评估是主观的,但包括一定特征的文本能够唤起与特定环境相契合的评估模式。因此,通过聚焦或突出一个事件的某些方面,新闻框架会引起人们相应的认知性评估,从而引起情感反应(Kühne, Weber & Sommer, 2015)。例如,对于恐惧(fear)这种情感而言,当特定信息使受众产生对威胁或危险的认知,往往会唤起恐惧的情感反应(Nabi, 2002)。具体到本研究,新闻框架突出被蓄意冒犯的片段或情节时,往往会引起人们对于特定新闻事件中责任归因的认知性评估,从而唤起消极情感。根据该理论,对于新闻事件的认知先于情感产生。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实验对象对事件中责任的认知是新闻框架与情感反应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与之相对的是,有学者提出了“情感作为框架”这一概念用以描述情感作为框架效应中介变量的发生机制。具体而言,当特定情感频繁与一个图像或认知勾连在一起时,它们之间会产生一种稳定的“情感—认知结构”模式,从而塑造着人们对于现实的认知。这种“情感—认知结构”模式反映了框架的思想意涵,即频繁地将特定情感与相关思想或事件勾连在一起会形塑人们对于这些事件的解读,从而影响他们的世界观(Nabi, 2003)。
此外,有学者认为,以往大多数研究以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等认知因素作为解释框架效应发生机制的中介变量。然而,该类框架效应的认知机制往往忽视了情感作为框架效应的中介变量。具体而言,情感作为“新闻框架——个人框架”这一心理机制中的中介变量能够解释一个具体的框架效果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Lecheler, Bos & Vliegenthart, 2015)。基于此,提出与假设2存在不同理论解释的竞争性假设(competing hypothesis):
H3:实验对象产生的情感反应是新闻框架与争议性新闻事件中责任认知的中介变量。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已有关于框架效应与情感的研究,主要聚焦积极框架与消极框架对于不同情感的影响。例如,索菲(Lecheler Sophie)等人的研究以新闻媒体的移民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积极框架与消极框架对实验对象情感反应的差异(Lecheler, Bos & Vliegenthart,2015)。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基于特定情感的新闻框架是否能够唤起相应的情感反应。例如,金(Hyo J. Kim)等人考察了在危机事件中包含特定情感框架的文本(“愤怒”VS“悲伤”)对于实验对象情感反应的差异(Kim & Cameron, 2011)。然而,以往相关文献很少涉及归责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新闻框架(如“归责司法人员”VS“归责民众)对实验对象情感反应的差异。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具有探索意义的研究问题:
RQ1:新闻框架(“归责司法人员”VS“归责民众”)对实验对象情感反应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三)新闻渠道与情感
除了新闻框架之外,本研究认为,新闻渠道也是影响受众情感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研究受众如何解读信息的经典模型,启发与系统性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HSM)揭示了人们接收与处理信息时的两种模式,一种是不深入思考,而是根据特定标签、线索与暗示处理信息的模式,即启发性模式(heuristic-mode);另一种是通过深入思考来处理信息,即系统性模式(systematic-mode)(Bohner, Moskowitz & Chaiken, 1995)。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倾向于调动过多认知努力,而是根据一些线索、暗示与标签对信息作出判断,如信息源等。因此,启发式信息加工是人们常用的信息处理策略(牟怡,夏凯,Ekaterina,许坤,2019)。具体而言,新闻渠道可以影响人们对于信息的处理,并且发挥启发性暗示(heuristic cue)的功能(Chaiken,1980)。不同新闻渠道因为有不同的属性与特征,因此可以发挥边缘性暗示的作用(Druckman, 2011)。
就中国新闻媒体格局而言,有学者在借鉴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政治场与经济场对新闻场产生影响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对于中国新闻场域内媒介关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经营体制的差异应该成为划分入场者的重要依据(刘海龙,2008:411)。从新闻媒体经营体制出发,党媒与“市场导向媒体”(market-oriented media)是其中两类代表性媒体。对于党媒而言,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布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引导舆论等。因此,党媒也被称为“喉舌型媒体”。而“市场导向媒体”既需要在大的方向上符合党的舆论导向,也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经济效益(方可成,2016)。因为在中国新闻场域中的位置以及与政党、市场之间距离的不同,两类媒体的定位与属性存在差异,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新闻观念与新闻报道风格。例如,相对于“市场导向媒体”而言,党媒往往给人一种严肃刻板的印象。
就媒介与情感的关系而言,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中公共情感的变迁既与社会转型的宏观环境有关,也与“媒介”的变化有关。这里的“媒介”包括由媒介制度变革而产生的都市媒体(“市场导向媒体”)。它们是塑造公众情感的渠道(袁光锋,2018)。相较党媒而言,随着媒介体制改革出现的“市场导向媒体”,面临着自负盈亏的市场压力,形成了以“受众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其中一个表现是新闻报道的情感化,特别是那些资源比较有限的都市媒体。有研究认为,情感倾诉类报道是盛行于全国都市媒体的一种报道方式,充斥着大量人情味的、情感化的表达(高卫华,2015)。此外,在近年来媒体对于争议性事件的报道中,相比党媒而言,都市媒体更倾向于采用情感化叙事,以实现吸引眼球的目的(袁光锋,201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新闻渠道调节新闻框架与受众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即在阅读“市场导向媒体”报道条件下,新闻框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显著;在阅读党媒报道条件下,新闻框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不显著。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网络调查实验(online survey experiment)考察新闻框架、新闻渠道对于受众情感反应的影响机制。实验法可以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被认为是最适合分析框架效应中复杂心理机制的研究方法(Lecheler, Bos & Vliegenthart, 2015)。
(一)实验步骤
通过线上网络问卷的方式收集实验数据,共获得有效样本300个。其中女性126人(42%)。不同年龄段的样本数量分别为, 15-18岁占0.7%、19-25岁占23%、26-36岁占59.3%、36-45岁占14%、46-55岁占3%。通过在问卷平台中对不同版本问卷进行随机分配,以保证实验对象有相同机会被分配到4个实验条件中(N=75)。
首先,通过一个过滤问题筛选出那些不熟悉实验材料中新闻事件的实验对象,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接下来,实验对象被要求阅读不同版本的实验材料,并根据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回答他们对于新闻事件中责任的认知与情感反应等。
(二)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来源于一起真实争议性司法冲突事件的报道,经过简单改编成为实验材料。该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实验研究中(Boukes et al., 2015)。本研究从新闻框架与新闻渠道两个变量对实验材料进行操作设计。据此,我们制作了四个不同版本的实验材料,将新闻框架分别操作为“归责司法人员”与“归责民众”,并通过标注新闻的不同来源(“权威党媒”与“市场导向媒体”),实现对新闻渠道的操作控制。除了新闻框架与新闻渠道之外,稿子的篇幅、段落与字数基本相同。
(三)测量
1.责任认知。实验对象被要求使用7级量表(1=完全没有,7=很大程度)分别回答司法人员与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冲突的发生。4个问题测量司法人员的责任,如“警察在人群密集的集市中贸然掏枪导致了此次警民冲突”等(M=4.20, SD=1.49, α=0.91)。4个问题测量民众的责任,如“村民从肢体上暴力侵犯警察导致了此次警民冲突”等(M=5.03,SD=1.31, α=0.89)。参考以往研究,用认知的民众责任减去认知的司法人员责任获得责任认知指数,数字越大代表认为民众责任越大,数字越小代表认为司法人员的责任更大(Shen, Ahern, & Baker, 2014)。
2.情感反应。实验对象被要求运用7级量表(1=完全没有,7=很大程度)分别回答在阅读材料之后的情感反应,并通过3个问题进行测量(“愤怒”、“恐惧”、“悲伤”),以获得消极情感变量(M=4.21, SD=1.21, α =0.74)。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3个问题构成一个消极情感因子,共解释66.21%的方差变异。其中,KMO值为0.69,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结果具有显著性(P<0.05),表明该量表的效度能够接受。
3.控制变量。社会身份:实验对象被要求回答“是否”为警察或者警校学生,以测量他们的社会身份。警察与民众的数量分别为7人(2.3%)与293人(97.7%)。收入:实验对象被要求回答在当地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6人(2%)、低于平均水平113人(37.7%)、平均水平127人(42.3%)、高于平均水平54人(18%)。
四、假设检验与数据分析
假设1认为,新闻框架会影响受众对冲突事件中责任的认知,当新闻框架归责于司法人员时,受众倾向认为司法人员对冲突负更多责任;当新闻框架归责于民众时,受众倾向认为民众对冲突负有更多责任。双因素协方差分析(ANCOVA)用于对该假设进行检验。其中,自变量为新闻框架与新闻渠道,协变量(Covariate)为社会身份和收入,因变量为责任认知。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新闻框架对实验对象的责任认知具有显著差异,(F(1,294)=10.37, p=0.001, ηp 2=0.03),即相对于阅读“归责司法人员”框架的实验对象(M=0.45, SD=2.09),那些阅读“归责民众”框架的实验对象认为民众的责任更大(M=1.21, SD=2.51);相对于阅读“归责民众”框架的实验对象(M=1.21, SD=2.51),那些阅读“归责司法人员”框架的实验对象认为司法人员的责任更大(M=0.45, SD=2.09)。因此,假设1获得支持(表1 表1见本期第42页)。
假设2认为,实验对象对事件中责任的认知是新闻框架与他们情感反应之间的中介变量。海斯(AndrewF. Hayes)的Process模型4用于分析中介效应,并采用95%的置信区间及5000的自抽样(bootstrap)进行检验(Preacher & Hayes, 2008)。自变量为新闻框架,因变量为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责任认知为中介变量,协变量(Covariate)为社会身份与收入。
结果显示,关于事件中的责任认知对新闻框架与实验对象情感反应的中介效应显著,β=-0.11, SE=0.04, 95%CI=[-0.1942, -0.0378],即新闻框架能通过责任认知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表2 表2见本期第42页)。
假设3预测,实验对象产生的情感反应是新闻框架与事件中责任认知的中介变量。海斯的Process模型4用于分析中介效应,并采用95%的置信区间及5000的自抽样(Bootstrap)进行检验。自变量为新闻框架,因变量为责任认知,中介变量为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协变量(Covariate)为社会身份和收入。
结果显示,实验对象情感反应对于新闻框架与责任认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13,SE=0.07,95%CI=[-0.2904, 0.0002],即新闻框架不能通过实验对象情感反应这一中介变量影响他们的责任认知。因此,假设3未能得到支持(表2 表2见本期第42页)。
研究问题1提出新闻框架(“归责司法人员”VS“归责民众”)对于受众情感反应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双因素协方差分析(ANCOVA)用于对该假设进行检验。其中,自变量为新闻框架与新闻渠道,协变量(Covariate)为社会身份和收入,因变量为情感反应。
结果显示,新闻框架对于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边缘显著,(F(1,294)=3.86, p=0.05,ηp 2=0.01),即相对于阅读“归责司法人员”框架的实验对象(M=4.09, SD=1.28),那些阅读“归责民众”框架的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更大(M=4.33, SD=1.11)(表1 表1见本期第42页)。
假设4预测,新闻渠道调节新闻框架与受众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在阅读“市场导向媒体”报道条件下,新闻框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显著;在阅读党媒报道条件下,新闻框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不显著。双因素协方差分析(ANCOVA)用于对该假设进行检验。其中,自变量为新闻框架与新闻渠道,协变量(Covariate)为社会身份和收入,因变量为情感反应。
分析结果显示,新闻渠道对新闻框架与受众情感反应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F(1,294)=11.90, p<0.001, ηp 2=0.04)。简单效应(simpleeffect)分析显示,在阅读“市场导向媒体”报道条件下,新闻框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显著(β=0.73, t=3.84, p<0.001),即相对于阅读“归责司法人员”框架的实验对象(M=4.03, SD=1.38),那些阅读“归责民众”框架的实验对象的情感反应更高(M=4.71, SD=0.93)。在阅读党媒报道条件下,新闻框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不显著(β=-0.20, t=-1.06, p>0.05)。由此可见,新闻框架与受众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受到新闻渠道的调节。因此,假设4得到支持。
综合以上所有分析结果,建立了相关模型,展示所有显著的假设与路径关系(图1、2 图1、2见本期第43页。由于作为与假设2形成竞争关系的假设3未得到支持,因此,该假设未在图中展示)。
五、总结与讨论
以往国内围绕“后真相”相关争议的思考主要采用思辩研究的路径,缺乏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检验。基于此,本研究以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争议性新闻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因素组间实验法,考察新闻框架、新闻渠道对于实验对象认知与情感的影响及其路径关系。实验法的一个优势在于通过对于核心变量的操作以及其他变量的控制,从而能够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接下来,将对本研究中的主要发现进行讨论。
通过对假设1与研究问题1的分析,研究发现,在争议性新闻事件中,新闻框架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认知,也会影响他们的情感反应。值得一提的是,当新闻报道归责于司法人员(M=4.09, SD=1.28)与归责于民众时(M=4.33, SD=1.11),实验对象所产生的消极情感均大于均值(M=3.5)。这说明,消极的新闻框架会使实验对象产生消极的情感,而且情感反应程度比较高。此外,在本实验的情境中,两种不同框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程度差异并不大,这与一些研究中所宣称的公职人员由于特殊身份,其消极行为更容易引起网民消极情感的断言有差异。但考虑到新闻框架对于实验对象情感反应的主效应是边缘显著,这一样本中的结论与真实世界中的情感反应模式也许并不一致,有待未来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检验。
假设2与假设3的结果表明,新闻框架通过影响实验对象责任认知这一中介变量,从而唤起与之相关的情感反应。而新闻框架通过情感影响人们对于事件中的责任认知,这一竞争性假设并没有得到支持。综观以往关于框架与情感的实验研究,情感主要是作为特定框架与态度、舆论与行为意向等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Bilandzic, Kalch, & Soentgen, 2017; Kühne, Weber, & Sommer, 2015),但相关研究很少将认知作为因变量。这也许是因为与态度、行为意向相比,认知往往相对客观,需要基于特定事实证据以及理性思考。此外,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不论归责司法人员还是归责民众,实验对象都只看到了归责一方且责任非常明确的新闻框架。如果实验对象先后接触了归责于双方的竞争性框架的新闻报道,在责任认知不明确的情况下,也许情感会成为新闻框架与认知之间的中介变量。此外,框架对于实验对象情感反应的直接效应边缘显著(F(1,294)=3.86, p=0.05, ηp 2=0.01),但是通过认知影响情感的这一间接效果的效应量却更大(β=-0.11, SE=0.04, 95%CI=[-0.1942, -0.0378])。这说明框架通过认知影响情感是一个重要机制,情感的产生与认知紧密相关。这与前文提到的情感评价理论的观点相契合。综合假设2与假设3的结果,本文认为,以往一些有关“后真相”研究中所宣称的在“后真相”语境下,情感比事实更能影响人们对事件的认知是值得商榷的,这一结论可能需要附加一些限制条件才能成立。例如,像“情感作为框架”这一概念所宣称的,当特定情感频繁与一个图像或认知勾连在一起时,它们之间会产生一种稳定的“情感—认知结构”模式(Nabi, 2003)。需要强调的是,特定情感需要频繁与一个图像或认知勾连。这也许意味着当两者之间关联程度较高时,情感才能与认知建立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索一些潜在的发生条件与影响因素,即调节变量(moderator)。
最后,根据假设4的结果,新闻渠道能够调节新闻框架与受众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在阅读“市场导向媒体”报道的条件下,新闻框架对于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显著;在阅读党媒报道的条件下,新闻框架对于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市场导向媒体”在类似报道中往往会采用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标签化的社会共识,能够唤起受众更高的情感反应。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以及媒体移动化发展的今天,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浅阅读的浏览状态下消费新闻。因此,人们往往是以边缘路径对新闻信息进行加工。这时新闻渠道能够作为特定认知标签与线索(cue)发挥作用,从而影响新闻框架对于受众情感反应的效果。这也证实了以往研究中关于媒介变革与情感之间关系的论断(袁光锋,2018)。
近年来,情感成为新闻传播学中的热点话题,一些学者尝试重新审视情感的价值及其与新闻业的关系,如情感与认知、事实并不是对立的(白红义,2018;袁光锋,2018;郭小安,2019)。新闻业从未把“情感”拒之门外,新闻业中的情感包括能够唤起公众情感的表达方式。“情感”对新闻的渗入亦因媒介形态而异(袁光锋,2017)。这些研究主要从情感社会学出发,关注社会结构与情感之间的关系,肯定情感的积极意义,如反映个案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类似本研究所关注的公职人员与民众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事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证实,并进一步加以补充与细化。例如,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运用的情感化表达(愤怒、恐惧与悲伤等消极情感)确实能够唤起受众的消极情感。但是,这些消极情感并不是新闻框架与认知的中介变量,即新闻框架不能通过情感影响实验对象对于新闻事件中责任的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主要考察了与争议性冲突事件有关的消极情感,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新闻框架、新闻渠道对于具体不同的情感产生的影响,例如愤怒、恐惧以及希望等具体的情感。本研究聚焦新闻框架、认知、情感之间的路径关系,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察它们对于人们线上或线下集体行动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从新闻报道到集体行动之间的心理机制与路径关系,为新闻媒体对争议性新闻报道的效果及其具体心理机制提供理论解释。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整合相对宏观的情感社会学与微观的认知心理学,从而建构从情感产生到其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态度、意向与行为的中层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8)。“媒介化情感”的生成与表达:基于杭州保姆纵火事件报道的个案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139-149。
陈斌(2014)。《网络环境下争议性事件的报道框架及框架互动机制研究——以凤凰网对“夏俊峰案件”的报道为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武汉。
方可成(2016)。社交媒体时代党媒“重夺麦克风”现象探析。《新闻大学》,(3),45-54。
高卫华(2015)。媒介化社会的情感倾诉及其传播效果:报纸“倾诉类”栏目的内涵与价值取向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141-144。
郭小安(2019)。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 ——从“后真相”概念说起。《国际新闻界》,(1),115-132。
胡翼青(2017)。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当下的危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6),28-35。
李诚付,韩敏(2014)。暴力维权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以“冀中星事件”为例。《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4),88-93。
刘海龙(2008)。《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牟怡,夏凯,Ekaterina,N,许坤(2019)。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信息加工与态度认知——基于信息双重加工理论的实验研究。《新闻大学》,(6),30-43。
魏云鹏(2017)。《城管执法议题冲突报道的偏向性分析——〈以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为例》。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重庆。
殷韵(2018)。《争议性事件的媒介框架分析——“以辱母杀人案”为例》。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南昌。
於红梅,潘忠党(2015)。近眺异邦:批判地审视西方关于“后真相”的学术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5),5-24。
袁光锋(2012)。合法化框架内的多元主义:征地拆迁报道中的“冲突”呈现。《新闻与传播研究》,(4),53-63。
袁光锋(2014)。同情与怨恨——从“夏案”、“李案”报道反思“情感”公共性。《新闻记者》,(6),11-16。
袁光锋(2017)。情感何以亲近新闻业:情感与新闻客观性关系新论。《现代传播》,(10),57-69。
袁光锋(2018)。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一个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105-111。
张伦,钟智锦(2017)。社会化媒体公共事件话语框架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69-77。
Bilandzic, H.KalchA.& Soentgen, J. (2017). Effects of Goal Framing and Emotions on Perceived Threat and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for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39(4)466-491.
BohnerG.MoskowitzG. B.& ChaikenS.(1995). The Interplay of Heuristic and Systematic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6(1)33-68.
Borah, P. (2011). Conceptual Issues in Framing Theory: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a Decade’s Litera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1(2)246-263.
BoukesM.BoomgaardenH. G.MoormanM. , & De Vreese, C. H. (2015). Political news with a personal touch: how human interest framing indirectly affects policy attitud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2(1)121-141.
Chaiken, S. (1980). Heuristic versus syste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use of source versus message cues in persua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5)752-766.
DruckmanJ. N.( 2001). On the limits of framing effects: Who can frame?. Journal of Politics, 63(4)1041-1066.
Chong, D.& Druckman, J. N. (2007). Framing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0103-126.
EntmanR. (1991). Framing U.S.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ntrasts in narratives of the KAL and Iran Air incid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1(4)6-27.
Kim, H. J.& CameronG. T. (2011). Emotions matter in crisis: The role of anger and sadness in the publics’ response to crisis news framing and corporate crisis respon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6)826-855.
Kühne, R.WeberP.& Sommer, K. (2015). Beyond Cognitive Framing Processes: Anger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Responsibility Framing on the Preference for Punitive Measur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2)259-279.
Iyengar, S. (1996). Framing responsibility for political issu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46(1)59-70.
LechelerS.Schuck, A. R. T.& de Vreese, C. H. (2013). Dealing with feelings: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screte emotions as mediators of news framing effects. Communications -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2)189-209.
LechelerS.BosL.& Vliegenthart, R. (2015).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2(4)812-838.
Major, L. H. (2011).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mes and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Health Problem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8(3)502-522.
NabiR. L. (2002). Angerfear, uncertaintyand attitudes: a test of the cognitive-functional model.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9(3)204-216.
NabiR. L. (2003). Exploring the Framing Effects of Emotio.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2)224-247.
PreacherJ. K.& HayesF. A. ( 2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40 (3)879-891.
Semetko, H. A.& Valkenburg, P. M. (2000).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0(2)93-109.
ShenF.AhernL.& BakerM. (2014). Stories that Count: Influence of News Narratives on Issue Attitud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1(1)98-117.
Shulman, H. C.& Sweitzer, M. D. (2018). Advancing Framing Theory: Designing an Equivalency Frame to Improve 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4(2)155-175.
刘双庆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地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权威研究”(项目编号18XCA00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江晓雅、芮牮、丁伊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建议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