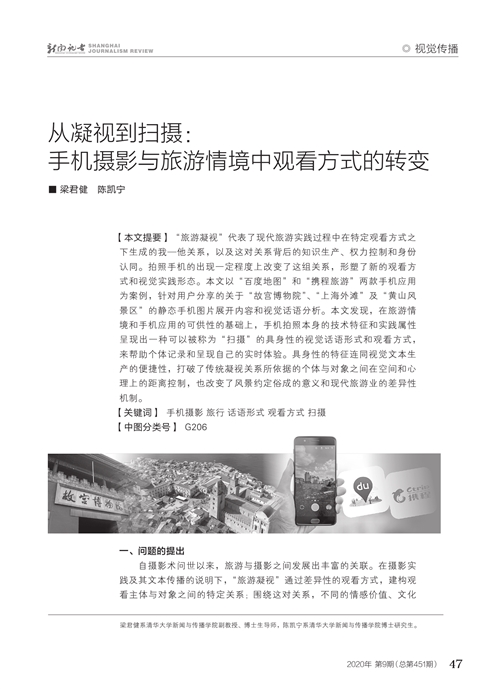从凝视到扫摄:手机摄影与旅游情境中观看方式的转变
■梁君健 陈凯宁
【本文提要】“旅游凝视”代表了现代旅游实践过程中在特定观看方式之下生成的我—他关系,以及这对关系背后的知识生产、权力控制和身份认同。拍照手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组关系,形塑了新的观看方式和视觉实践形态。本文以“百度地图”和“携程旅游”两款手机应用为案例,针对用户分享的关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外滩”及“黄山风景区”的静态手机图片展开内容和视觉话语分析。本文发现,在旅游情境和手机应用的可供性的基础上,手机拍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实践属性呈现出一种可以被称为“扫摄”的具身性的视觉话语形式和观看方式,来帮助个体记录和呈现自己的实时体验。具身性的特征连同视觉文本生产的便捷性,打破了传统凝视关系所依据的个体与对象之间在空间和心理上的距离控制,也改变了风景约定俗成的意义和现代旅游业的差异性机制。
【关键词】手机摄影 旅行 话语形式 观看方式 扫摄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的提出
自摄影术问世以来,旅游与摄影之间发展出丰富的关联。在摄影实践及其文本传播的说明下,“旅游凝视”通过差异性的观看方式,建构观看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特定关系;围绕这对关系,不同的情感价值、文化意义和权力关系得到了建构和再生产。然而,在家用自动相机流行带来的以“柯达文化”为标志的转向之后,本世纪开始出现并流行的智能手机,再一次以技术革新为契机,对既有的观看方式、主客关系以及围绕旅行而建构起来的意义系统带来了新的改变。
在技术给旅行摄影的实践方式和文本意义带来变化契机的背景下,本文期待解答的核心问题是,个体旅行者在通过手机拍照和分享,来捕捉和传播自己的时空经验的过程中所采纳的意义—话语形式,体现了旅游凝视和主客关系方面的哪些变化。上述的核心问题,从宏观上来说针对的是视觉技术和视觉实践议题,即技术应当在什么时候、通过何种方式,成为参与和再造事件的选项(Allan & Peters, 2015:1348-1361)。这种技术实践首先在文本层面体现为一定时间内比较稳定的具有主导性的视觉话语秩序,即一种意识形态(意义)—话语的形式(ideological-discursive formations, IDFs);而这种秩序和形式的更深层次的基础,则是在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所确立的观看方式,即“旅游凝视”。因而,本文的研究问题也包括相对应的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旅游图片文本展开内容和视觉形态的分析,探讨它所建立起来的个体与风景之间的主客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在视觉实践的语境下着重考察技术的特征对于观看方式以及主客关系所带来的变化。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选择了“百度地图”和“携程旅游”两款手机应用,针对用户在这两个应用中分享的关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外滩”以及“黄山风景区”的摄影图片展开研究。本文发现,手机拍照便捷的技术特征以及手机应用的“技术可供性”改变了旅游视觉实践的方式,发展出一种可以被称为“扫摄”的具身性的视觉话语形式,来帮助个体记录和呈现自己的实时体验。相比于“凝视”所强调的长时间的审美和沉浸式的观看,以及建立在“看与被看”基础上的权力建构,“扫摄”有别于传统旅游图片研究所强调的符号学和图像志的意义建构机制,打破了传统的凝视关系所依据的个体与对象之间在空间和心理上的距离控制,稀释了风景约定俗成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旅游凝视中的主客关系与意义建构
“凝视”是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它代表着特定的观看方式以及围绕这种观看方式而产生的主客关系、心理机制和文化实践。首先,凝视是一种现代人获得自我身份的实践,是“主体性赖以建构其自身的一种机制……主体在凝视的过程中发现了他者,并在与他者相互凝视的过程中来建构自己”(姜小卫,2007)。拉康则将凝视视作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镜像关系。他将凝视与分析心理学中的“镜中我”的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儿童第一次在镜子前凝视自己的形象之后、产生了我—他之间的区分,从而建立了自我意识(托比·米勒,2008:104)。其次,凝视还生产了权力关系。福柯认为,自19世纪起,这种由观看而形成的主客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凝视的支配权”,这尤其体现在临床医学的凝视和文学的凝视两个方面(张德明,2004:115-116)。此外,对于拉康来说,凝视还发生了从支配到被支配的转化:个体不再仅仅是观看者,而且成为被凝视的对象,不论是否有一个凝视的主体,个体都开始“用别人的目光打量自己”,进而认同“被凝视”,从而让个体和身体成为规训和消费的场所(张德明,2004:119)。
对于风景的凝视起源于16世纪荷兰风景画家对于客观景象所引入的观看和视觉感知的内涵(Calder, 1981:6)。1990年,Urry(1990)在福柯关于凝视与权力的论述的启发下,提出了“游客的凝视”(tourist gaze)这一概念,在“主人—客人”(host-guest)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分析了西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观看方式与视觉经验。旅游凝视从以下三个方面形塑了主客关系和意义建构方式。首先,与拉康对“我—他”区分的强调类似,旅游凝视对于主客关系和意义建构也来自差异性的获取。在旅游情境下,这种差异性集中体现在日常与非日常之间。旅游扮演了日常与非日常之间的一种转化机制,普通人在旅游中产生了“非普通人”的自我幻觉,而凝视则是这种自我幻觉的一种具体的形成方式,现代个体“通过凝视行为,将这种幻觉主体化、神话化”(周志强,2010:138)。换句话说,旅游首先是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抽离,它是一种非日常的或者说追求脱离日常生活的行动。而旅行过程中的观看和摄影等视觉实践,都是通过对于景点的凝视去捕捉和确认这种主客差异并获得意义的。
旅游凝视的第二个特征是对于距离的控制。这一特征与差异性密切相关,因为正是物理的和文化的距离控制,为我—他之间的差异性提供了基本保证。对于距离的控制也同样地来自于“凝视”这一概念的心理分析机制。人类学和流行文化对于他者的生产都遵循“知晓—占有”的机制(to ‘know’ by possessing and possess by knowing)。而距离(distance)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是观看、现实、欲望和权力的先决条件,允许了观看者控制他者(Hansen, Needham & Nichols, 1991)。
旅游凝视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对于权力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尤其是在后殖民研究的视角下。福柯认为,医学的“凝视”是由医患之间的权力关系发展来的视觉支配关系(福柯,2011:128)。在福柯和拉康那里,“凝视”都涉及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尤其是以“全景监狱”为代表的现代监控技术所带来的对于个体的控制。这种权力关系的建立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视觉权力结构之下的凝视和观察,其次是凝视导致的个体对于权力关系的内化。在摄影领域,通过控制客体,照相机干预和改变了现实, 将摄影和世界的关系转变为“一种长期窥淫癖的关系”(Sontag, 1973:7)。而由于视觉材料所积累下来的意识形态—话语模式不断地在新的领域再生产自身,因而即使当代商业旅行杂志的图像中也仍然延续了对于前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式的凝视和编码(Brito-Henriques, 2014:320-334)。
(二)摄影技术对旅游凝视的强化与改变
“旅游凝视”这一观看方式并非一定诉诸文本,但毫无疑问,大众媒介场域中不同形态的视觉文本,如明信片、绘画、摄影和电视节目等,都围绕和强化了“旅游凝视”所代表的社会文化实践,为主客关系的建立和意义的生成提供了土壤。旅行图片既是对“凝视”这种观看方式的文本记录,又反过来影响和规训旅行中个体的观看。在摄影复制和视觉传播的促进下,旅行图片已经成为生产和维持关于人、地点和文化的话语和意义的核心场域(Caton & Santos, 2009:191-192)。不仅是商业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旅游推广机构,对于以人文教育为目标的非营利机构来说,这种围绕旅游而展开的对于景观和文化的视觉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也在重复和改变着既有的关于旅行、风景与文化他者的印象与意义(Caton & Santos, 2009:191-192)。对于旅行者个体来说,大众媒介场域的各类图片不仅直接影响了旅行者的目的地选择(Brito-Henriques, 2014:322),同时也形塑了旅行者对于空间和地点的感受(Su, 2010:412-434),进而确立了某种形态的主客关系。在旅行过程中,游客往往并非漫无目的地观看,而是在主动地寻找和收集视觉对象,这既包括了完整的独特物体与风景,也包括了特定的文化能指(Francesconi, 2011; Jenkins, 2003; Saidi, 2008)。
在上述过程中,技术实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Henry Jenkins强调了围绕技术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实践的重要性,因为正是技术实践承载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物质关联,而新技术的出现则会让上述这些关联和实践发生变化。在旅游情境中,摄影技术的普及改变了图像制作由旅游业和大众传媒单向主导的局面。照相机赋予个体更大的权力,并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占有技术而获得实质性权力”(Sarewitz, 2009:308)。相比将摄影简单地看作是生活经历的记录和呈现文本,来自人类学和实践理论的视角将其视作一种以相机和拍摄行为为中介的相遇和互动的平台(Singer, 2011:193-194),在这个平台上,主客关系不再仅仅通过观看,而且通过摄影实践得到建立。旅途中的摄影行为能够帮助个体去组织他或她的时空经验,将自然空间建构成为一个休闲和消费的场所(Urry, 1992:172-168)。个体摄影也强化了权力的炫耀,它扩展了通过观看而占有拍摄对象的权力,也将旅游异化为寻找适于拍摄的对象并记录下来的过程。
智能手机提供了对于旅行展开视觉记录的新手段。它的特质可以被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数字图像和手机摄影带来了可复制性和图像生产的进一步解放,让个体在旅行的过程中更加便捷和几乎零成本地去捕捉和分享清晰、细腻且具有一定质量的图片,刺激出关于旅行和风景的海量图片/复制物。本雅明在他的经典文本中考察了机械复制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对于风景和对象物的大量复制提供了哲学基础。在阐释他著名的“灵光”概念时,本雅明专门以风景为例,认为“灵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由距离而产生的独特现象;而当代大众生活中灵光消逝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希望把物品通过机械复制的方式在空间和人性上更加贴近的欲望。“每一天,人们将物品通过相似性和复制在更近的距离占有的欲望都在增强”,而机械复制的能力刺激和帮助达成了人们通过复制品而占有的欲望(Benjamin, 1935:217-243)。数字技术和智能手机在拉近距离、满足占有欲的方面毫无疑问比胶片相机更有技术上的优势。
除了大量复制对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拉近和“灵光”消逝之外,手机摄影在实践中还发展出个人中心主义的特质,这被一些学者命名为“脸书文化”。由于易用性和社交媒体带来的实时连接,手机能够激发个体摄影实践和意义建构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早在2005年的一项探索性的研究中,手机拍照的实践属性就被分为两个向度,分别是情感—功能向度和个体—社会向度(Kindberg, Spasojevic & Fleck, 2005)。照片从保持记忆为主的功能属性转变为通过拍摄和分享来建构个体的身份认同的情感属性(Harrison, 2002:87-111)。尤其是在社交活动和公共活动中,手机摄影都强化和丰富了群体性的实时经验(Kindberg, Spasojevic, & Fleck, 2005);而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介的推动下,在公共平台展示手机拍摄的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变得合法化和正常化(Trivundza, 2015:93-109)。这种摄影实践被一些学者总结为“脸书文化”,它的核心内容是最大程度的自我中心,尤其是展示用户和他们的朋友在社交场合或者假期生活(McLaughlin & Vitak, 2012:299-315)。通过拍摄与分享,手机将个人生活场景变成社会连接的节点,因而营造出社会性和文化属性,并且将常规变成表演,还帮助人们发现了不同的凝视方式(Ibrahim, 2015:42-54)。
(三)问题的提出
手机摄影对于图像复制能力的极大解放,以及实践中所发展出来的个人中心主义特质,都潜在地更新了旅行观看方式,带来了意义建构和个体表达的新的可能性。首先,手机拍摄是最常用的记录和保存位置信息的手段,很多用户采取“拍摄—上传”的方式对到过的地方在相关APP中进行“签到”,从而完成将个体经验媒介化的过程。进一步的,手机拍摄技术的流行,为人与风景、主人与客人、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新的通道;当下的旅行者不仅是既有图像文本的能动的读者,而且是图像文本的主动的生产者和传播者(ozkul & Humphreys, 2015:354)。
因此,本文以中国大陆的位置类和旅游类APP中的旅游图片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在这一案例所展示出的技术对于视觉实践和意义建构的改变。具体来说,本文研究在数字摄影技术和手机应用的可供性的基础上,个体如何通过特定的观看方式,去建构自己与他者、自己与景观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从如何使用技术的角度去思考上述关系,将研究资料还原到人—景观—手机的互动场域中,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手机摄影和手机应用为旅游摄影实践提供了什么样的技术可供性?这些旅游图片文本体现了哪些内容和形式特征,代表了怎样的观看方式?在技术特征和观看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关于旅游的意义生产机制和被生产出来的意义发生了哪些变化?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旅游景点的选择与意义框架
在差异性机制下,旅游凝视的对象既包括了文化上的他者,也就是旅游目的地的原住民,也包括了空间上的他者,主要是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景观和环境。由于本研究是一项关于技术和视觉之间的探索性的研究,为了控制相关因素、更加集中地探讨手机摄影的技术特征所扮演的角色,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游客前往中国大陆景点旅行作为研究案例。具体到景点个案,本文选取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外滩和黄山风景区三处规避了文化差异性并各具类型和图像志特点的地点。
对于旅行者来说,风景是旅行目的地众多要素中具有首要视觉吸引力的内容。Urry(1992)的旅游凝视在思考的最后的结论部分,借用了其他学者提出的“景点—魅力物”(attraction,这一单词既可以和旅游一词组成 “旅游景点”这个短语,同时也代表了“有魅力的事物”,故此处用“景点—魅力物”来对应)的概念(Leiper, 1990:368-384),来描述视觉性和风景之间关系带来的结果。他将“景点—魅力物”视作由三个要素组成的系统,包括了旅游者本身、核心风景以及不同的图像文本制作者。这个系统正是从不同的凝视方式中产生,而这些凝视方式又与多样的制作者和核心风景本身相关。
故宫博物院、上海外滩和黄山风景区分别代表了建筑遗产、当代都市和自然风光这三个最为常见的风景类旅游目的地。并且,三个景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景点—魅力物”的意义系统,对于游客来说具有若干“不言自明”的风景之外的意义。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官式建筑代表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权力中心和宫廷文化;上海外滩的黄浦江、西式建筑和当代建筑表征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也代表了当下的经济繁荣和都市生活;黄山风景区则是中国传统山水美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中国文化对于自然的独特观念,青松、云海、怪石等早已大量地出现在各式绘画作品和媒介内容中。上述三个风景区所具有的不同的潜在意义,对于个体旅行者在旅行过程中的拍摄实践有可能施加不同的影响,他们既会根据这些既有的意义和框架来调整自己的观看和拍摄,来寻找与确认,也有可能探索新的视觉魅力物及其意义空间。不过,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手机拍照技术对于游客的观看方式的整体性影响,因此暂时搁置三个景点因其差异性而带来的具体的意义建构方面的不同。
(二)研究数据的选择与获取
在以上景点个案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来自于“携程旅游”和“百度地图”两个手机APP中的景点评论区的UGC图片作为核心研究资料。根据公开数据,中国大陆的地图类手机应用的前三名依次为“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和“腾讯地图”。其中,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的表现十分接近,前者仅在数据方面略微领先后者,但排名第三的腾讯地图则与前两名差距较大。例如,根据第三方机构“移动观象台”的数据,2018年9月,三个APP的活跃率分别为25.38%、21.11%和2.51%。但是,百度地图积累下来的用户图片数量显著高于高德地图。2018年10月底,百度地图中“故宫博物院”的带图评论累计近200条,而高德地图仅80条;百度地图中“黄山风景区”的带图评论同样有接近200条,而高德地图仅有不到80条;百度地图中“外滩”的带图评论有160余条,而高德地图则有90余条。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在用户提供的带图评论数量的区别,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历史发展导致的专业定位的不同。从2002年成立起,高德地图致力于和车企的合作,业务的主要专注点在定位服务和数据采集方面,它的核心服务情境也主要是驾乘情境;而作为百度旗下的一款地图应用,百度地图最早于2005年推出PC版,2011年推出移动端APP,可以说是借助百度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广泛吸引了网络用户的参与。
中国大陆的综合预订类的旅游手机应用的前三名依次为“携程旅行”、“去哪儿旅行”和“飞猪”,三者之间在活跃率方面差距比较明显。2018年9月,携程旅行的活跃率为4.8%,去哪儿旅行为2.82%,飞猪为0.7%。其中,成立于1999年的携程旅行由最初的在线票务服务公司发展为2017年度“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2018年5月,《中国旅游影响力调查2018》发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旅行社企业的排行榜,其中携程以综合指数93.3分位居榜首。关于手机APP应用中带图评论数,截至2018年10月底,携程旅行“故宫博物院”带图点评共1.2296万条、“外滩”7424条、“黄山风景区”5564条;去哪儿旅行“故宫博物院”带图点评共4943条、“外滩”259条、“黄山风景区”2268条;飞猪“故宫博物院”带图点评共2170条、“外滩”仅93条、“黄山”168条。从统计数量上来看,携程旅行带图点评超过去哪儿旅行与飞猪的总和。综合行业影响力与样本典型性,携程旅行在中国大陆的综合预订类的旅游手机APP应用中具有较高代表性。
研究者在2018年10月24日对上述两个手机应用中三个景点评论区排名前50条的带图评论中的图片及其所配文字进行了手工抓取,共获得图片1715张。其中,百度地图共558张,包括了“故宫博物院”193张、“黄山风景区”217张、“外滩”148张;携程旅行共1160张,其中“故宫博物院”388张、“黄山风景区”426张、“外滩”346张。在这些带图点评中,百度地图普遍配文较少且单一,甚至大部分没有配文,只是单纯的图片呈现,而携程旅行则常见大量配文,该应用自行设定的点评排序也会参考评论内容,在“智能排序”或点赞中靠前的点评除了配图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出众,配文中也交代了大量关于旅游景点的实用信息,如对景点的百科介绍、票价、游览推荐等。本文对于每张图片采取的命名规则为:“序列号+手机APP名称缩写+景点名称缩写+评论发布日期+图片序号”。例如,携程旅行APP故宫点评第1条第1张展现乾清宫内景的图片,被命名为“001-xc-gg-2017-07-23-01”;百度地图APP黄山点评第46条的第3张呈现迎客松的图片,被命名为“046-bd-hs-2015-06-16-03”。
当然,这些文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想的文本,即旅行者个体认为成功和完整地捕捉传递了自己的经验的视觉文本,是可以提出质疑的。不过,由于这些图片均由用户自行挑选上传,因而本研究认定,这些图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在特定的情境和技术可供性的条件下用户本身对于旅行经验的有目的和自主的呈现。
(三)研究方法
对于特定题材和类型的图片展开研究,Rose(2007:72)的建议是首先对于图片进行量化的内容分析,把握文本的基本图式和主题,并发现重复性的要素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仅仅数量并不代表直接的显著性,需要进一步开展符号学和话语分析,来发现图像是如何通过观看来展开意义建构的(Albers & James, 1988)。而“凝视”本身因其暗示了“观者身份”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对于文本形态展开研究的新的转向,它将对于艺术形式的讨论从语言学理论的模式中抽离出来,整合了形式的和社会的研究关切(玛格丽特·奥林,2006:60)。因此,本文对于个体在旅游过程中的手机图片将分别进行文本分析和视觉话语分析。
首先,为了把握个体在旅行过程中的拍摄实践及其图片的基本特征,本文借鉴Brito-Henriques(2014)对旅游图像展开主题分析的类目,对于研究对象展开文本分析。Brito-Henriques采纳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题材的四分法,四个类别分别是风景画(landscape images)、风俗画(genre scenes)、肖像画(portrait)和静物画(still life)。虽然四类图像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旅游摄影中,但毫无疑问,风景画是旅游图像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最直接地体现了个体旅行者与风景/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意义建构。而其他三个类别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旅行图像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其次,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对于具有典型意义和重复出现的呈现要素展开视觉话语分析。相比于内容分析将照片分解成为元素并进行统计,针对视觉话语的研究强调将照片视作一个实践过程,去分析拍摄者在呈现特定要素和题材时所采取的策略及形成的潜在图式。如果说内容分析揭示图像的外在意义的话,那么视觉话语分析则将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置于更为宏观的实践和操作语境中,来探究意义的形成机制及其结构性的模式。对于旅行摄影来说,针对图像文本的话语分析尤其能够揭示出技术的变化带来的观看方式的改变——正是约定俗成的观看方式及其规定出的主客关系,为视觉文本和旅行本身的意义建构提供了潜在结构。
不过,在针对图片资料展开主题和话语分析之前,本文接下来将首先讨论手机拍照和图片分享平台的技术可供性。正是智能手机上的数字拍照技术和特定类别的手机应用,为当下个体在旅游过程中的摄影实践提供了技术基础和操作框架,也将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与其他类型的旅游摄影实践进行了区分。
四、手机拍照与图像分享平台的技术可供性
当下,手机已经成为视觉实践和视觉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技术平台,推动了数字视觉文化(digital visual culture)的出现和流行,也为包括旅行图片在内的视觉生产提供了基础。智能手机不仅借助数字图像技术推动了摄影的普及,而且借助手机应用设计出一整套图片拍摄、后期制作、储存、上传、分享的操作程序。手机的移动化、小巧化、一体化与应用个人化、社交化、智能化,共同造就了日常生活中视觉实践的多元丰富的景观(于德山,2018)。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技术和媒介语境中,普通人的视觉实践及其文化意义差异很大。例如,Instagram和微信等社交平台更多鼓励个体通过图像的自我形塑;以手机拍照加美图软件的技术手段代表着肖像制作的技术赋权,提升了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存在感和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彭兰,2018)。而旅游和地图类的手机应用则为当下的手机旅游图片提供了不同的流动传播语境(West, 2004),也因此形成了与社交媒介不尽相同的视觉题材与呈现形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平台的技术可供性所造成的。
“可供性”(Affordance)最早由心理学家吉布森(Gibson)提出,用来指代个体实践背后所受的环境影响,即“行动是由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决定的”。虽然关于“可供性”本质的本体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出现在不同领域不可通约的现象(Parchoma,2014),但技术哲学和技术人类学领域对于“技术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仍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技术可供性被定义为在社会技术系统中的某种仲裁者,一个设备能够向参与者发放允许或禁止使用的建议(Akrich & Latour,1992)。不过,技术可供性并不仅仅由技术和设备的物质属性单独决定,它不可避免地与特定背景下的参与模式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Bloomfield, Latham & Vurdubakis,2010),因而,技术可供性是由社会实践、技术的物质属性,以及环境特征共同决定的(Pfaffenberger,1992)。Hutchby(2001)在上述基础之上认为行动主体与技术产物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功能性与关系性两方面进行理解,这两个方面框定而不是决定了主体可能采取的行动,由此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兴起,为理解技术作为一种规定性的环境对于行动主体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Gibson, 1977:89)。技术可供性成为媒介研究领域的重要视角,成为探讨数字文化实践的前置基础。例如,Pearce(2020)以Instagram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可供性为基础,探讨了大规模枪击案后“团结”的在社交媒体中的视觉建构(Pearce, 2020);Lobato和Lotz(2020)以Netflix为网络视频平台代表,讨论一种新的分配技术、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流媒体的可供性;陈昌凤与仇筠茜(2018)以“星球大战”的IP培育过程为对象,认为大众媒介在这一过程中的可供性包括认同定位、角色共情和社会关系补足三个方面;冯强与马志浩(2019)在一个鲁中村庄展开针对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发现智能手机兼具共享体验和定制化的技术可供性推动了村民对手机的消费。
具体来看,手机应用为本研究所关注的游客手机图片的拍摄和分享提供了特定的技术可供性。从总体上来说,数字文化催生了“后人类状态”,这种状态将我们的视像和主体性通过技术延伸出肉身之外(Blaagaard, 2013)。在位置类的手机应用上,用户通过数字图像记录位置信息、分享即时的具身感受,正是这种数字文化的具体呈现。本文所研究的两类手机应用首先代表了使用手机图片来记录、保存和分享位置信息的功能。这种功能在全球范围内都广泛存在,外出过程中,很多用户都已经习惯于在相关的位置APP“签到”(ozkul & Humphreys, 2015:354);而在微信等社交网络中,普通用户也常常为发布出来的图片标记位置信息。其次,这两类手机应用还代表了一种基于消费和市场行为的以图片拍摄和上传为手段的主观评价行为,平台鼓励用户通过上传图文评价来为景点评级,对其他潜在客户分享感受、提供参照,从而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平台在具体技术设计上也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在选择“评论”动作之后即跳出对话选项,用户可以直接选择通过手机应用拍摄照片或者上传手机本地已有的照片,通过图文分享自己的经历。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手机应用平台的可供性尤其是这种便捷的图文评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普通用户的图像生产和延长使用时间,从而为自身积累数字资产。
在技术与平台的鼓励下,手机应用构成了当下公共平台上可见的旅行图片的重要类型。相比微信和微博等个体社交平台来说,这类平台上的图像是以地点而非用户为中心的组织逻辑,个体之间的社交性也较弱,除了浏览和点赞外很少出现用户之间的实质互动。但另一方面,由于手机应用平台是以地点为第一逻辑,关于地点的图片也更加集中,并对所有用户可见,因而成为公共话语系统中的图像志的延续与积累。此外,地图类和旅游类APP本身公共平台的属性更加鼓励游客上传关于旅游目的地的景点的图片,而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主体对于客体、具体来说也就是旅游过程中风景—魅力物的观看方式,虽然这两类公共平台上较少体现游客的自拍和合影,但对于本研究的目标来说是合适的。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在技术和平台的上述可供性特征的基础上,对这一案例所代表的视觉实践的多样性及其形成机制展开具体研究。
五、手机旅游图像的内容—主题与视觉话语形式
(一)风景的复制:手机旅游图像的内容分析
来自两个手机应用的图像数据在内容和主题方面呈现出比较一致的偏向性:第一类也是绝大多数都属于写实主义绘画四分法的框架下的风景画,即对于三个旅游目的地风景本身的呈现。这一类型大致包括了宏观和微观两类场景,宏观场景为旅行场所的全景记录,例如故宫太和殿广场、外滩对岸的陆家嘴CBD建筑群。结合点评文本,这类影像记录中经常会出现“震撼场景”与“人山人海”的叙事模式。而微观场景则多为细节呈现,如故宫博物院展品、黄山迎客松特写等。在所有1715张图片中,景点的直接呈现有1550张,占比约为90%(表2 表2见本期第55页)。
第二类内容和主题是对于旅游过程的记录。与景点记录截然不同,此类图片集中呈现拍摄者的“旅行行为”,诸如指示路牌、饮食住宿、纪念品。其中,出现最多的是景点门票或导览地图,如“黄山白云宾馆”餐饮环境、呈现的“故宫博物院电子导游图”等。在所有的研究资料中,这类图片的数量为130张,占比约为7.6%(表3 表3见本期第55页)。
第三类也就是最后一类内容和主题是个人留影。区别于旅行行为记录,这类图片是对旅行者个体的直接呈现,多为他人帮助拍摄的个人图像,即最为典型的“游客照”,大多数表现方式为个人站在景点前的合影。这类留影多为单人照或多人、家庭照,也有少数具有设计感的呈现方式,例如在故宫中摆出特定动作(举着剪刀手的背影)的形式化设计。个人留影的图片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传统的游客照在手机APP用户上传的图片中出现的次数极少;其次,几乎没有出现自拍式的个人留影。个人留影的图片一共仅有35张,占2%(表4 表4见本期第55页)。
从内容分析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结论。首先,正如传统的旅游摄影以及针对网络社区的研究所指出的,既有框架对于个体的旅游视觉实践仍然延续着强大的影响力。有学者研究了Flickr用户发布的在巴塞罗那的旅游照片,发现绝大部分是对旅游手册上的标志性的景象的复制,并且70%的地标图片中没有任何人物;仅有少量内容是对于城市的多元化的呈现(Galí & Donaire, 2015:893-902)。从本文的内容—主题的统计可以看出,这种对于既有魅力物的系统复制在中国大陆旅游和地图类的手机应用中更加明显,占比高达90%。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起传统摄影行业的游客留影,极少出现在本文的研究资料中。
其次,我们还进一步地发现,在90%的景点直接呈现的图片中,还有若干更为集中的魅力物的要素反复出现。例如,在展现故宫博物院的图片中,有70张是展示太和殿的,而且在构图方面也大都采取人眼高度的广角远景来同时展示宫殿建筑和宽阔的广场。黄山风景区中,较为常见的是迎客松的全景,至少出现了26张以迎客松为画面主体的图片;而最为集中的则是外滩的陆家嘴金融中心摩天大楼群,至少有96张照片以之为画面主体。这种集中性还体现在一些用户在上传的图片中,同时选取自己拍摄的同一魅力物的不同角度的图片。
上述的两个基本发现,展示出手机摄影与位置类手机应用的技术可供性给个体生产的旅游图像带来的改变:虽然本文的研究资料并不能够代表旅行者的实际拍摄情况,但在旅行者的上传选择和手机应用的筛选排序之后,最终呈现在公共空间的手机旅行图像在内容—主题方面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对少数吸引力要素的直接呈现,个性化的内容——例如旅游目的地的合影,以及旅游本身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过滤和屏蔽在公共视域之外。直观来看,这在题材和内容上对“个人中心主义”的“脸书文化”提出了挑战的可能性,提供了不同技术平台上的多元景观;或者说,在拍摄个体和传播平台的互动之下,“个人中心主义”是特定平台中的典型景观,对于其他如旅游应用和地图应用等平台,它所积累和筛选出来的图像可能会具备不同属性。
上述如此集中的内容统计结果,展现了手机摄影作为一种廉价、易得的复制手段所带来的影响。在图像时代,照相机镜头在技术的支持下将一切现实转化为“景象的无穷积累”,使“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转向了表征” (Debord, 2002:1)。换言之,摄影术的发明导致了观看对象在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平面化;在此消彼长的趋势下,真实(the real)从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消失,图像文本被大量生产出来,介入真实和观赏者之间,进而变成无生命的符号,主体的本真就这样不断地被延宕,从而失去其整体性,表现为支离破碎的景象,最终印证了米歇尔的论断,即图像表征“不仅干涉我们的认知……而且妨碍、否定认知,并将之碎片化”(Mitchell, 1994:188)。数字摄影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在智能手机上的聚集,毫无疑问强化了上述过程,即对象或客体的平面化和意义的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手机旅行图片所传递出的意义及其对“旅游凝视”所带来的改变,本文将进一步对其视觉话语形式展开分析。
(二)具身性:手机旅游图像的视觉话语形式
正如视觉文本的众多研究者所指出的,主题—内容层面的量化分析并不能直接决定图像的内在意义。尤其在主体—客体借助摄影技术互动的视角下,个体旅行者对于图像内容的拍摄行为和表述方式形成了图像文本中比较稳固的意义—话语的形式,从而完成了对于文本的意义生产,并确立了主客之间的固定关系。
首先,作为内容—题材的风景是旅行的目的地和结果,对它们的拍摄延续了风景画的绘画美学传统中对于风景的审美期待,以及用户对于手机图片的美学期望。布尔迪厄将摄影美学看作阶级性和社会共享而非个人所有的东西,他认为,没有任何人物的地标图片可以被视作继承了浪漫主义美学下对于风景的个人消费(Galí & Donaire, 2015:893-902)。然而,从传统的视觉和摄影美学的标准来看,虽然有少量图片体现了对于形式感的特殊追求,如使用手机全景模式拍摄、添加滤镜和HDR等修饰效果,乃至从专业的图片网站中下载高质量图片上传等,但绝大多数景点图像都是对于标准旅游风景图片的并不成功,甚至是随意乃至拙劣的模仿。例如,70张展示太和殿及前广场的图像,大多数选择了在视线高度拍摄,将太和殿简单地置于画面中心,画面的水平常常左右倾斜,前景充斥着偶然进入画面的人群。从画面来推测旅行者的拍摄行为,极有可能是在被太和殿及其空间特征所震撼的同时,划开屏幕、横置手机进行的简单记录;少数图片甚至采取了更加简洁的操作、直接使用竖屏拍摄。由于旅游者常常无法站在中轴线的正中进行拍摄,虽然太和殿被置于画面正中、两边的建筑物本身遵循了对称美学,但是手机拍摄出来的画面的左右对称往往是不太标准的。而近百张陆家嘴金融中心图片的表现方式更加集中,绝大多数是从旅行者所在的角度,对于东方明珠塔及其周围建筑群的来自地面高度的仰拍。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传统的风景美学的观看方式,对于当下人们的手机摄影来说已经不再具有指导性。由传统风景画系统奠定的个体与风景之间的宗教式的朝圣关系,与本文所研究的这些图片所体现的观看方式之间,并不直接对应。相比于风景画的美学阐释传统,我们更应当将本文所关注的绝大多数旅行图片视作一种街拍的话语方式。与传统的“风景大片”相比,这类图像较少美学上的主动追求;相反,它有意无意地展示出随意和偶然的实践特征,暗示出手机摄影在日常旅行中的便捷与高效,它所展示出的使用方式也更贴近日常生活而非专业摄影师。此外,“纪实”的隐喻及其影响下的手机拍摄观念,提供了关于生活经验的“可靠”叙述,它也许并不具备美学价值,但能够帮助个体让瞬间的经验变成永恒(Brenholdt, Haldrup, Larsen & Urry, 2004:358)。因而,这种图片拍摄实践将旅行视作一种个体经验的情境,而非审美对象。传统上,这种街拍的话语方式在旅游这一题材领域中最为典型的体现方式是与地标建筑和旅行伙伴的自拍。相比而言,无人风景则基本上隔绝了具体的拍摄情境——除了旅行之外,在图片的内容和形态上不进行关于拍摄者和拍摄社会情境的任何暗示。
然而,本文所研究的手机旅行图片的形态特征和传统的街拍实践模式并不相同,它更像是上述两种视觉话语形式的结合:内容上的无人风景,加上随意和非审美的纪实形态。大量的图片是对于风景对象的“随意”记录,还有一小部分是对旅游行为本身的记录。这些图像不直接出现拍摄者和旅行者个人,而是用“纪实”的形态暗示出自身的在场以及主体与景物之间的关系:随意呈现出来的门票、景点说明牌、旅馆,以及餐厅的食物,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也暗示了手机另一侧主体的存在和行为;景点照片的倾斜、前景中分布的无序游客,都展示出个体在旅行中的、个体与景观之间的日常观看方式。这些图片展示出个体与景观相遇时的实时经验,他们被奇观所吸引,在甚至是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举起手机,记录下眼前的景象和自己的感触。
手机旅行图片的上述特征,对传统的视觉符号学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Urry(1992:172-186)将旅游目的地的景观的符号学机制区分为隐喻(metaphor)和换喻(metonym),并且指出,游客的观看是在差异性的指导下而展开的,也就是通过强化景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视觉上不同和区分,来完成意义的建构和陈述。从本文研究对象的题材—内容及其呈现方式来看,手机摄影的确显示和强化了旅行过程中的这种追寻和确定差异性的视觉行为,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符号化的过程,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作为个人中心主义的日常化的技术实践,手机摄影与旅游凝视对于差异性和奇观要求实际上是矛盾的。目前来看,手机摄影对于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是将奇观式的对象纳入日常的观看形式中。由于手机拍照的日常化的便捷特征,个体对这种技术的使用观念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除了少数案例之外,位置类手机应用上的手机旅游图像已经不再是一种精心制作的视觉文本,而成为一种具身性的并且是实时性的表达工具。或者说,手机图像已经不再依靠符号学和图像志的机制来获取意义,而更多地通过对拍摄行为和拍摄者所处情境的记录和暗示,来完成个体体验的表达,进而将个体生活情境建构为一种“平庸美学”特质的分享空间。
因此,手机拍摄技术便捷特征带来的实时性和随意性,打破了个体旅游中“凝视”的观看模式和奇观的再生产,它更像是一种对于面前静物在瞬间完成的“扫摄”和“确认”。手机旅行图片的这种具身性的“扫摄”,可以被定义为通过对个体行为和在场身体的视觉暗示,来传递个体日常体验的视觉实践和意义建构机制,以区别于符号学和图像志的传统的意义建构机制。这种具身性的视觉话语形式及其机制,实际上已经出现在若干不同领域。例如,1950年以来,在影视艺术的视听语言中,就已经逐渐形成了通过手持镜头的晃动来传递真实感和具身性的基本规则。在新闻摄影领域的一个有趣案例是,2004年阿富汗战争中的大多数专业新闻摄影师都会有意识地通过图片中枪械的指向和位置以及摇晃摆动的镜头动作,在视角上去暗示拍摄者与士兵之间的亲密和贴近。研究者认为,这体现出新闻摄影师从关注“看上去怎样”到关注“感觉怎样”;新闻摄影的功能从提供客观事实转变为提供主观体验(Blaagaard, 2013:359-374)。阿富汗战争的案例表明,在职业竞争压力和专业主义价值焦虑的双重作用下,摄影记者已经开始主动或者被迫适应数字技术给摄影观念和功能上带来的转向,强调街拍式的随意性带来的真实感和具身的体会。
六、结论与讨论
在个体旅行者与风景关系的视觉实践的视角下,本文选择了百度地图和携程旅游两个手机应用,针对用户在这两个应用中分享的关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外滩”以及“黄山风景区”的1715张旅行图片展开研究。研究发现,90%的图片都是对于旅行目的地代表性的魅力物的简单记录,另外还包括了对于旅行过程和旅行信息的记录,而传统的旅游图片中的个体肖像类别在这组材料中并不突出。通过进一步的话语分析本文发现,相比于传统旅行图像的基于“凝视”观看方式的符号学和图像志的意义建构机制,这组旅行图片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一种具身性的意义建构方式,通过对旅行目的地景物的快速和随意的记录,来表达个体与风景相遇之后的“扫摄”和“确认”。出于研究的体量和目的考虑,本文在个案选取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旅游凝视中的跨文化因素,以及三个景点在话语形式和意义建构方面的具体差异;同时,由于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方式的限制,也缺乏对于手机拍摄者自身展开文化特质的分析。因此,上述结论尤其是“扫摄”这种具身性的观看方式,还需要通过民族志,尤其是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确认。
不过,本文的结论仍然展现了新的媒介环境,尤其是数字技术,给普通人的生活实践带来的深刻影响。“扫摄”的观看方式首先与特定媒介语境的技术可供性密切相关,技术的可供性赋予了视觉实践多元化的形态,也催生出不同的意义建构机制。地图类和旅游类APP本身公共平台的属性以及外出旅行的使用情境,都更加鼓励游客上传关于旅游目的地景点的图片,而不像脸书和微信等平台一样鼓励个体通过自我肖像展开身份形塑。技术本身的联接和网络的属性强化了分享即时经验的特征,这与以图片拍摄为核心目标的网络社区,如国内的图虫网和国外的Instagram中力求美学标准和形式创新的图片创作,具有明显的差异,相对而言降低了对于影像形式方面的美学期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技术提供的审美参与的可能性甚至会因低门槛和低成本而带来粗陋和快消的危险(张慧喆,2019)。同时,它也和20世纪50年代以家用相机为基础的“快照美学”对于传统摄影技巧的反叛(Zuromskis, 2006)形似而实异。“扫摄”可以被看作是在旅游的即时情境中由手机摄影和位置类应用的技术可供性所形塑出来的特定观看方式和视觉形式,它构成了当下总体视觉文化中的一类视觉意义生产机制。
虽然与本文所选择的分享平台的技术可供性相关,“扫摄”这一视觉话语形态仍然展示出数字技术尤其是手机摄影对于视觉意义生产和我—他关系带来的新的可能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风景依靠凝视而产生的一整套意义系统及其建构机制,在“扫摄”的视觉形态中得到颠覆和改写——被改写的不仅仅是意义本身,也包括了通过视觉形式去建构意义的文化机制。传统的视觉媒介,如风景画、风景摄影以及商业旅游广告,对个体来说都是一种观看方式的训练。这些视觉文本指导个体在旅游过程中以特定的方式去观看,包括了对于时间(一年中的四季,以及一天中的晨昏等)、地点(最佳观看位置和最具代表性的景观等)和情感(结合文化语境和品味要求的崇高感、乡愁、思古幽情等)的建议和要求。在这样的观看方式中,客体提供了凝视的对象,对客体的凝视成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手段。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带来改变的契机。虽然通过手机拍摄的海量照片看上去是对传统风景和吸引物及其观看方式的模仿和意义再生产,但手机带来的具身性的特点和大量的机械复制,又让这种模仿构成对权威的消解或者是一种“灵光消逝”。原先由旅游业精心控制的图像生产过程,现在成为网络平台鼓励下个体的生产和上传行为;个体与风景之间的距离控制在新的技术和传播平台上不再存在。风景—魅力物不再仅仅是一定距离之外的认识对象、符号、象征物和奇观,而是通过手机摄影成为个体在此时此地的具身经验的一部分。
手机摄影技术对于复制能力的解放,加上“扫摄”的观看方式的形成,也意味着个体拥有更大的可能去获得意义生产和阐释的自主性,这同样促成了对于既有的旅游意义结构的改变。在数字图像技术出现之前,图像的生产主要由专业工作者完成,通过对文本生产的技术控制,社会实现了对大众的解读和意义空间的控制(De Certeau, 1984)。在“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探究了视觉奇观与商品拜物教之间的密切关联,但他同时从波德莱尔那里引入了“闲逛者”这一概念,否定了奇观化对于当代个体的完全控制。“闲逛者”的核心特征是一种疏离的、漫不经心的打量带来的祛魅式的观看;依靠这种观看方式,个体实现了对于视觉权力结构的反抗(吴琼,2014:30)。类似地,Fiske也提出“游牧式主体”(nomadic subjectivities)的概念,意指拒绝成为商品的受众在当代媒介文化语境下所展开的与权力之间的对抗和抵制(Fiske, 1989:309)。个体旅游摄影中所体现出的“扫摄”的视觉方式,在大量复制奇观式的景点—魅力物的同时,也通过具身性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凝视”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祛魅式的观看。在位置类手机应用的技术环境中,手机摄影对传统旅游意义结构的“祛魅”主要是通过对个体在场的明示和具身经验的记录,来打破凝视时被对象完全“吸收”的忘我状态以及对对象物的审美式的观看。
第二,“扫摄”还体现了摄影实践在意义建构之外的心理功能。对于传统的旅行摄影,苏珊·桑塔格已经对其开展了心理分析式的考察,个体对于相机的使用往往并非复制和保存,而是用来缓解无所事事的焦虑(格雷厄姆,2016)。桑塔格指出,摄影既给旅游带来了焦虑,让旅行体验因为要寻找拍摄物而变得碎片化、无法全身心融入,它同时也是解决焦虑的方案,被资本主义异化的个体在休闲状态下因为不生产而产生的焦虑可以由这种符号生产行为得到释放(桑塔格,2007:9-10)。手机拍照提供了对个体流动经验的更加便捷的视觉记录手段;日益先进的手机拍照技术,也让用户自我感觉更有能力去展示自己的旅游经验。虽然这种在公共平台展示私人生活的“平庸美学”常常被批评为消费主义的文化建构,但有趣的是,一些经验研究证明了,手机拍照的确有助于改善个体的心理状态,达成一种积极心理学的效应(Cox & Brewster, 2018:113-129)。对平台来说,这种心理功能也帮助平台去激发个体的视觉生产,积累了数字资本,成为盈利链条中的重要推动力。
最后,“扫摄”这种具身性的视觉话语方式,还与新近的旅游研究对于视觉隐喻的反思不谋而合,进而展示了视觉技术对整体生活文化的深层次的介入。不满足于“凝视”所暗含的对于旅游实践的“视觉隐喻”和对于视觉性的过度强调,近年来,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探索游客在旅游实践过程中的各种感官经验,以反思视觉对于这一领域的过分主导。他们认为,旅游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行为,游客应当被视作更加积极的主体,在他们的旅游经验中,除了凝视之外,也进行表演/展演,包括了身体和具身的参与以及物理性的行动(Perkins & Thorns, 200:186)。而另一方面,在数字媒介和数字文化领域也出现了看待媒介实践的新视角。英国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Nick Couldry(2004)就提出,应当将媒介视作一种围绕媒介而展开的开放的实践,来超越媒介文本和生产结构这样的既有认知范式;因为仅仅将媒介视为文本和产品会忽视媒介嵌入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灵活多样的方式。从本文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更加多元的旅游体验,也通过“扫摄”这种具身性的视觉话语方式得以传达;或者说,视觉实践在手机摄影技术的帮助下建立起新的我—他关系,从而对个体的旅游经验乃至于意义表达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符号学和图像志的新的传达手段。■
参考文献:
陈昌凤,仇筠茜(2018)。技术可供性视角下优质IP的媒介逻辑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63-168。
冯强,马志浩(2019)。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国际新闻界》,(11),24-45。
福柯(2011)。《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姜小卫(2007)。凝视中的自我与他者——保罗·奥斯特小说《纽约三部曲》主体性问题探微。《当代外国文学》,(1),29。
玛格丽特·奥琳,曾胜(2016)。“凝视”通论。《新美术》,(2),85-93。
彭兰(2018)。美图中的幻像与自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2),20-24。
托比·米勒(2008)。《凝视的本质》。陈犀禾,陈娟,徐红编译:西方当代电影理论思潮系列连载七:凝视研究。《当代电影》,(9),104。
苏珊·桑塔格(2007)。《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吴琼(2014)。拱廊街·奇观化·闲逛者——本雅明的拜物教批判。《河南社会科学》,(4),22。
于德山(2018)。新型图像技术演化与当代视觉文化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1-25。
张慧喆(2019)。虚假的参与:论短视频文化“神话”的幻灭。《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9),20。
周志强(2010)。从“游客凝视”到“游客化”——评《游客凝视》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贡献。《文学与文化》,(1)。
AlbersP. C. (1988). Travel photography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5(1)134-158.
AkrichM.& Latour, B. (1992). A summary of a convenient vocabulary for the semiotics of human and nonhuman assemblies. In W. Bijker & J. Law (Eds.)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 259-264). Cambridge: MIT Press.
Allan, S.& Peters, C. (2015). Visual truths of citizen reportage: Four research problematic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8(11)1348-1361.
Brenholdt, J. O.HaldrupM.Larsen, J.& Urry, J. (2004). Performing tourist places. London, UK: Ashgate. 358.
Blaagaard, B. (2013). Post-human viewing: A discussion of the ethics of mobile phone imagery. Visual Communication12(3)359-374.
Blaagaard, B.& ChouliarakiL. (2013). Post-human viewing: A discussion of the ethics of mobile phone imagery. Visual Communication12(3)359-374.
BloomfieldB. P.Latham, Y.& Vurdubakis, T. (2010). Bodies, technologies and action possibilities: When is an affordance? Sociology44(3)415-433.
Brito-Henriques, E. (2014). Visual tourism and post-colonialism: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of Africa in a Portuguese travel magazine.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12(4)320-334.
CalderW. (1981). Beyond the View: Our Changing Landscapes. Melbourne: Inkata Press.
Caton, K.& Santos, C. (2009). Images of the Other: Selling Study Abroad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8(2)191-204.
Couldry, N. (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14(2)115-132.
Cox, A.& Brewster, L. (2018). Photo-A-Day: A digital photographic practic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 Photographies11(1)113-129.
DanielS. (2009). Technology and Power. In J. K. B. Olsenet al. (Eds.)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de Certeau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 Rendell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kstrandV.& Silver, D. (2014). Remixing, Repostingand Reblogging: Digital MediaTheories of the Imageand Copyright Law. Visu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1(2)96-105.
Edwards, E.& Morton, C. (2011). Introduction. In C. Morton & E. Edwards. (Eds.) Photography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Expanding the Frame (pp.4). Farnham: Ashgate.
Fiske & John. (1988). Television culture. Routledge.
Francesconi, S. (2011). Images and writing in tourist brochures.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9(4)341-356.
GalíN.& DonaireJ. (2015). Tourists taking photographs: The long tail in tourists’ perceived image of Barcelona.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18(9)893-902.
GibsonJ. J.Shaw, R.& BransfordJ. (1977). Perceiving, acting, and knowing: Toward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Guy, D. (2002).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Press.
HansenC.NeedhamC.& NicholsB. (1989). Skin flicks: pornographyethnographyand the discourses of power. Discourse11(2)64-79.
HarrisonB. (2002). Photographic visions and narrative inquiry. Narrative Inquiry12(1)87-111.
Hutchby, I. (2001). Technologies, texts and affordances. Sociology35(2)441-456.
Ibrahim, Y. (2015). Instagramming life: Banal imaging and the poetics of the everyday. Journal of Media Practice, 16(1)42-54.
Jenkins, O. (2003). Photography and travel brochures: The circle of representation. Tourism Geographies5(3)305-328.
KindbergT.Spasojevic, M.FleckR.& Sellen, A. (2005). The ubiquitous camera: An in-depth study of camera phone use. IEEE Pervasive Computing4(2)42-50.
LeiperN. (1990). Tourist attraction system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7(3)367-384.
LobatoR.& Lotz, A. D. (2020). Imagining Global Video: The Challenge of Netflix. JCMS: Journal of Cinema and Media Studies59(3)132-136.
MasseyD. (1995). Places and their past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39(1)182-192.
MclaughlinC.& VitakJ. (2012). Norm evolution and violation on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14(2)299-315.
MitchellW. (1995).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zkul, D.& HumphreysL. (2015). Record and remember: Memory and meaning-making practices through mobile media.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3(3)351-365.
ParchomaG. (2014). The contested ontology of affordance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ing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for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7360-368.
PearceJ. S. (2020). Instagram’s Affordances and the Visual Construction of Solidarity after a Mass Shooting. IllnessCrisis & Loss, 1054137320906405.
Perkins, H.& Thorns, D. (2001). Gazing or performing? Reflections on Urry’s tourist gaz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in the Antipod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16(2)185-204.
Pfaffenberger, B. (1992).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1491-516.
StaschR. (2011). The Camera and the House: The Semiotics of New Guinea“Treehouses” in Global Visual Cultu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53(1)75-112.
RoseG. (2007).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 Los AngelesCA: Sage.
SuX. (2010). The Imagination of Plac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Lijiang Ancient Town, China. Tourism Geographies12(3)412-434.
SontagS. (1973).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Saidi, H. (2008). When the Past Poses Beside the Present: Aestheticising Politics and Nationalising Modernity in a Postcolonial Time.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6(2)101-119.
Tomanic TrivundzaI. (2015). Are a Thousand Pictures Worth a Single Word? The Struggle between Condemnatory and Affirmative Discourses on Photographic Change in Slovene and UK Mainstream Media News Reports on Selfies. Javnost - The Public, 22(1)93-109.
Urry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UrryJ. (1992). The tourist gaze “revisited”.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36(2)172.
WalterB. (1935).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B.Walter. Illuminations (pp. 217-243).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WestN. (2004). Picturing Poverty: Print Culture and FSA Photographs (review). American Periodicals: A Journal of HistoryCriticismand Bibliography, 14(2)284-285.
Zuromskis, C. (2006). Intimate exposures: The private and public lives of snapshot photograph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凯宁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