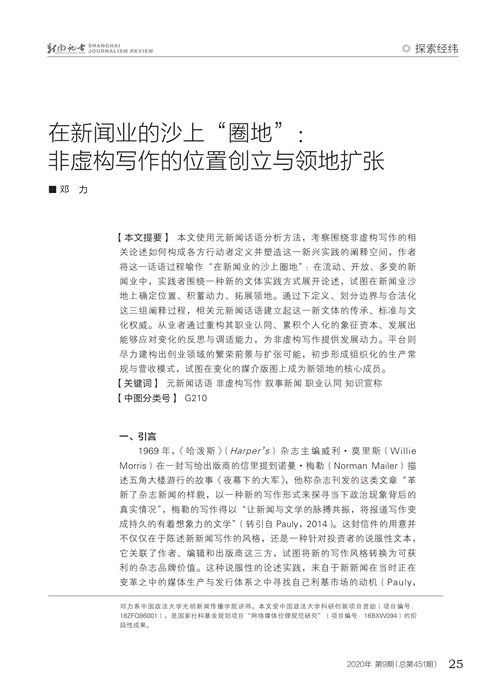在新闻业的沙上“圈地”:非虚构写作的位置创立与领地扩张
■邓力
【本文提要】本文使用元新闻话语分析方法,考察围绕非虚构写作的相关论述如何构成各方行动者定义并塑造这一新兴实践的阐释空间,作者将这一话语过程喻作“在新闻业的沙上圈地”:在流动、开放、多变的新闻业中,实践者围绕一种新的文体实践方式展开论述,试图在新闻业沙地上确定位置、积蓄动力、拓展领地。通过下定义、划分边界与合法化这三组阐释过程,相关元新闻话语建立起这一新文体的传承、标准与文化权威。从业者通过重构其职业认同、累积个人化的象征资本、发展出能够应对变化的反思与调适能力,为非虚构写作提供发展动力。平台则尽力建构出创业领域的繁荣前景与扩张可能,初步形成组织化的生产常规与营收模式,试图在变化的媒介版图上成为新领地的核心成员。
【关键词】元新闻话语 非虚构写作 叙事新闻 职业认同 知识宣称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1969年,《哈泼斯》(Harper’s)杂志主编威利·莫里斯(Willie Morris)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里提到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描述五角大楼游行的故事《夜幕下的大军》,他称杂志刊发的这类文章“革新了杂志新闻的样貌,以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来探寻当下政治现象背后的真实情况”,梅勒的写作得以“让新闻与文学的脉搏共振,将报道写作变成持久的有着想象力的文学”(转引自Pauly, 2014)。这封信件的用意并不仅仅在于陈述新新闻写作的风格,还是一种针对投资者的说服性文本,它关联了作者、编辑和出版商这三方,试图将新的写作风格转换为可获利的杂志品牌价值。这种说服性的论述实践,来自于新新闻在当时正在变革之中的媒体生产与发行体系之中寻找自己利基市场的动机(Pauly, 2014)。这封信也属于一种用来确定“新新闻”的“定义、边界与合法性”的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Carlson, 2016)。本文关注的即是相似的论述实践——在莫里斯写下这封信的半个世纪之后,叙事新闻再次兴起,并在种种围绕着“非虚构写作”的论述实践中被重构。不少非虚构写作者、内容平台和媒体观察者不断展开对话、组织讨论,并向读者推介这一冠以“非虚构写作”名称的本文形式。这些论述并非所谓新闻业实质性变革的附属产品,而是通过话语的方式来重新思考、表述并争论如何做新闻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构成了各方行动者定义并塑造新闻业变革的阐释空间(Carlson, 2016:363)。
在已有对非虚构写作的各类研究中,批判研究着重考察的是其文体兴起与政治经济语境的对应关系(黄典林,2018);文体研究分析其文体特征、认识论与伦理观(陆晔,2018;邓力,2018);而从业者研究则描绘出传统媒体内容生产团队和互联网平台团队出现在同一个竞技场的情形与“创业者”的职业认同重构(王波等,2020;陈楚洁,2018)。本文则尝试将文体层面的微观视角与结构研究的整体性视角加以勾联,纳入社会分析的维度,探讨这一文体如何在变化的媒体生产与发行体系之中寻找利基(niche),市场需求与读者定位如何影响作品的商业化转向,以及组织化常规与机构实践如何决定文体的面貌,即关注场域、机构与个体间的关系(Pauly, 2014;2016)。从关系入手的研究视角既要提供有历史脉络的分析,又要重视新领域中各主体的竞争、位置与策略,并对特定行为及态度背后的结构原因进行质询(Robinson, 2017)。因此,本文将梳理非虚构文体发展,探讨从业者的职业认知调整与机构间的关系形成,也将考察行动主体如何通过竞争和区隔来寻找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从而塑造新的内容生产格局与职业环境,以应对新闻业规则变化带来的挑战。
二、文献综述
本文并不将非虚构写作定义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形式,而是将它放在叙事新闻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这样做正是元新闻话语分析的题中之义——如果想要了解变化之中的新闻业,就不应只考察“新闻形式”(journalistic forms)的演变,还应分析“关于新闻的论述”(discourses about journalism)如何决定了人们对于新现象的理解(Carlson, 2016: 353-354)。因此,文献回顾将对非虚构写作的出现及其文体源头加以语境化的
理解。
(一)“新”文体的“旧”传统:叙事新闻的溯源话语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新闻业中广受关注的“新”报道形式。其实,非虚构写作的前身如“叙事新闻”、“文学新闻”或“新新闻”(Bishop & Starkey, 2006:65)等都曾引发过相似的讨论。可以发现,当时的讨论也都会强调这些新闻文体构成相对传统新闻形式的“新模式”。比如,“新新闻”就是一种曾反复出现的名称,从1860年代到199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至少出现过5次:包括1860年代的媒介评论、1880年代末的黄色新闻、1920年代的爵士新闻、1960年代的文学新闻,以及当下重新兴起的叙事新闻(Zelizer, 2017:249)。每次新闻文体的变化都冠以“新”,这种命名方式的简单重复,也部分说明了在关于新闻业本身历史的讨论中,那些能够总结过去经验并加以反思的“自反性论述”(reflexive discourse)(Zelizer, 2017:248)并不多见。
在新闻文体创新的历史话语中,关于“新”模式的阐释离不开对旧传统的追溯式论述。这种将其与某种传统加以关联的论述,起到了确定新文体的定位与合法性的功能。相隔三十年关于“新新闻主义”和“新新新闻主义”的两轮讨论就体现出这种规律。作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言人,Tom Wolfe(1975:46)在《新新闻写作》一书中将当时兴起的“新新闻”文体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小说写作加以关联,试图为其建立文学家谱中的出身与血统。而三十年后,Robert Boynton(2005:xi)在访谈录《新新新闻写作》中,为“新新新闻写作”在报业传统中找到两个源头:一个是1880年代的“新新闻”和1890年代的“文学新闻”,有着对社会与政治的关切;另一个源头是20世纪60年代重在探索文体形式实验的“新新闻写作”。Boynton(2005:xxviii)认为,“新新新闻写作”作为这两个源头的双重继承者,既延续了写作风格的创新,也同样对社会议题保持关切,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发展出浸入式报道的方法。在Wolfe和Boynton这两本标志性著作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延续传统的互文关系:Wolfe编写的作品集建立起了新新闻的名声,而Boynton访谈的多数作者都愿意承认自己属于Wolfe所定义的新新闻传统或文学新闻传统的一部分。这种追溯“新”文体的“旧”出处的做法一再重现,提醒我们在分析非虚构写作的元新闻话语时,要注意其是如何通过追溯某种传统来定位自身的。
(二)对阐释的追求与反思:叙事新闻的核心知识宣称
关于叙事新闻的论述还关注这类新闻实践所特有的报道方法与新闻观念。从大量的经验总结、媒介评论与学术研究等文本中可以发现,“阐释”成为叙事新闻区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核心“知识宣称”(knowledge claim)(Abbott,1988)。新闻业“阐释”角色的转向(interpretive turn)最早出现在对客观性的讨论和反思之中(Pauly, 2014: 592)。叙事记者拒绝传统新闻写作客观主义与程式化的文本结构,尝试通过丰富细微的描述来解读复杂的社会议题(Pauly, 2014:590)。
对阐释方法的追求还伴随着对阐释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具体体现在对叙事新闻认识论与伦理观的论述之中。在认识论层面,Braman比较了客观新闻与叙事新闻所对应的两种意识过程:前者由一组机构化的描述现实的程序组成,所使用的是可描述、可分类、易于处理的事实,比如通常被新闻机构判断为更可信的官方消息源提供的说法等;后者则是个人化的意识过程,每个写作者对于事实的使用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程序,通过个人化的理解与阐释来为写作对象所叙述的经验赋予意义(Braman,1985:79-80)。叙事新闻要求记者对故事完整的讲述,而不是对事件的简单拼凑;他们需要在阐释过程中以自己为工具,并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实现“充分的阐释力”(interpretive sufficiency)(Christians,Ferré & Fackler,1993:
120-121)。
在伦理层面,有研究者用“认知责任”(epistemic responsibility)来描述叙事记者的写作伦理:他会意识到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会不断自我审视自己如何书写他人的故事,最终以一种觉察与自省的态度来展开写作(Aucoin,2001;2016)。与客观新闻相比,叙事新闻的消息源不是被观察、总结、分类的对象,而是阐释与了解的主体,写作者不得不思考描述或暴露他人生活的方法及其后果(Soffer, 2009:477;Craig, 2006:1; Harrington, 2007:172)。在急速变革的新闻业中,媒介组织以及其他原本权威的信息来源不再为人们无条件地信任,此时,叙事新闻被寄希望于能为新闻业如何重拾信任的讨论提供一种新的方向(Greenberg & Wheelwright,2014:512)。
(三)成为阐释者:叙事记者的职业认同、文化权威与文化资本
首先,相似的阐释实践是叙事记者形成共同职业认同的基础。虽然被称为一个“群体”,但叙事记者并未形成一种社会性或机构性的团体,他们所共享的是对相同的实践方法即报道技艺的投入与信念(a dedication to the craft of reporting)(Boynton, 2005:xxvii)。比如有位作者说他不会自称“新新闻记者”,但非常认同Wolfe所著关于新新闻的文章,因为它能够总结并验证他本人一直以来所使用的报道方法,比如浸入式报道、细节化写作等(Boynton, 2005:7)。
其次,随着职业认同的建立,叙事记者作为“阐释者”的文化权威也逐渐形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新新闻写作者自认为是社会变革的记录者和社会趋势的阐释者(Pauly, 2014: 601),当时有不少作品捕捉到社会变迁与社会断裂的现实,满足了民众理解公共生活的需求,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在美国民权运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Forde,2014)。
最后,叙事记者的文化权威还成为他们获得市场成功(market distinction)的文化资本。相较而言,叙事新闻更强调作者个人的写作技艺与阐释能力。于是,优秀“阐释者”的文化权威也成为叙事记者建立个人名望的“象征资本”(Bourdieu,1989)。已经成名、有代表作的叙事记者更能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群,由此也受到杂志的青睐。媒体机构会去寻找(或独占)那些具有文化权威的作者。比如《君子》(Esquire)杂志主编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就与诺曼·梅勒保持了长年的友好关系,后者在1960年代初为这本杂志带来了最大的销量与最热烈的读者反响(Pauly,2014:599)。
这些文献回顾了叙事记者是如何成为“阐释者”的,也呼应了元新闻话语分析中对行动者(actor)的分析重点,本文也将考察非虚构写作者是如何形成职业认同并应对行业变化的。
(四)应对行业变化与机构需求:叙事新闻兴起与新闻业变革
最后一类论述实践关注的是叙事新闻实践与新闻行业整体变革之间的关系。相关讨论从技术与媒介环境、生产机构与机制这两个层面展开,探讨新的新闻形式与媒介环境是如何相互塑造的。
技术发展造成媒介环境的变化,也为推出或推崇某种新闻形式提供了时机。叙事新闻的出现和兴起,都与新闻业正在面对的媒介环境变革有关。最初,叙事新闻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功能的强调,即是当时以印刷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业,对于新出现的大众传播技术如电影等影像媒介的一种反应(Braman, 1985:77)。如今,叙事新闻热潮的再次出现,也与当下新闻业又一次面临媒介技术变革有关。当新媒体带来竞争压力时,叙事新闻被认为是“重新激发纸媒活力的方法”(Shim, 2014)。在原有媒介类型的各种边界正在消亡时,叙事新闻被认为是一种有着跨界能力的写作类型,可以发挥更多独特的功能(Krieken & Sanders, 2017)。
除了考察宏观的媒介环境,这一视角还对叙事新闻生产的机构与机制展开分析。有研究者分析了在1960年代出现的新新闻背后的市场组织关系,是作品、编辑、出版商与市场之间的机构实践,使得新新闻这一文类得以出现、成立并成为现象(Pauly, 2014)。叙事新闻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也体现出媒体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叙事新闻在荷兰经历了一个重新职业化的过程,它被架构为一种“动人的、必要的和高质量”的新闻新类型(Krieken & Sanders, 2017);而在澳大利亚和斯洛文尼亚,叙事新闻实践就未被从业者充分论述,记者从事叙事新闻写作只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非所在报纸的系统支撑(Joseph, 2010;Merljak Zdovc, 2009)。可见,叙事新闻是否被当作一种指向新闻业未来的实践,并不完全取决于从业者个人,而更多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获得媒体机构的系统支持。
因此,在考察非虚构写作的元新闻话语时,还需纳入行业与机构层面的分析。除了从业者个人,元新闻话语的论述主体还包括了机构性主体,即新兴的非虚构内容平台。
三、研究问题与分析方法
上述文献回顾展现出叙事新闻发展历程中的四组论述——追溯文体传统、阐释的知识宣称、阐释者的职业认同、行业变革与机构应对——将叙事新闻确立为一种重要的、具有生命力的新闻文体。如今,长篇叙事新闻再次兴起,并在种种围绕“非虚构写作”的话语实践中被重构。而此时,新闻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非虚构写作需要面对叙事新闻未曾经历过的新情境。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第一,在当下不断变革的新闻环境中,非虚构写作这一新文体如何通过相关元新闻话语来确立其在行业中的位置?第二,从元新闻话语的论述主体来看,从业者与机构平台如何通过论述来塑造新的新闻实践?第三,相关的论述实践如何体现出行动主体在面对行业变化挑战时的应对与调适能力?
从研究问题出发,本文将元新闻话语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在本文中,元新闻话语理论被用来分析主题式的话语生成,即新闻业新主张、新形式、新领域出现时的相关话语。这类元话语“提供了一个构成性时刻(a constitutive moment),以考察有关新闻业的基本假设是如何创造和流转的”(Carlson & Usher,2016:565)。根据Carlson(2016)对元新闻话语的界定,本文考察的文本将包括对非虚构写作下定义、用来划分其职业边界的话语,以及将其构建成为一种专业性职业实践的各类阐述。这些公开论述包括了从业者的经验分享,也包括了平台机构的推广宣言,能够体现出各方论述主体塑造非虚构写作实践的不同方式与动机。
文本的数据收集采用案例分析的策略,即形成一个有界限(delimit)的文本范围,将材料整理成为有所聚焦的几组文本合集,这样更有利于在特定范围的语境中去理解行动者对其行动及论述所赋予的意义(Carlson,2016:362-363)。如此便将相关文本数据整理为以下几类:1.从业者撰写的总结文章,对从业者的访谈和报道;2.从业者在相关会议讨论的实录;3.平台的创立宣言与机构定位表述,以及机构活动如赛事、榜单、网课的宣传文案;4.关于平台成立、发展、解散等节点的传媒报道与评论文章。这些文本来自不同类型的非虚构从业者、不同机构甚至不同行业的讨论,以及相关媒体评论,可以更好地考察其中的合作与冲突关系。①
元新闻话语的分析方法体现出,话语并非随意流动(free-floating),而是在特定语境中被生产、传播并消费的(Carlson, 2016:355)。因此,文本分析将从元新闻话语的三组话语组成(discursive components)展开。第一是对行动者(actor)的分析,考察哪些行动者通过公开表达来塑造相关的理解与实践。第二是对场所与读者(sites/audiences)的分析,考察话语的文本特征,及其生产、流通与消费的语境。第三是对主题(topics)的分析,既考察围绕单个事件的讨论,也收集评价式、趋势性的讨论。
分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展开。研究者首先阅读所有文本材料,形成第一层次的分析,重点考察关于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定义、传统溯源、边界划分、标准设定、从业者群体认同、职业权威等相关表述。这一层次将确定分析主题和重复出现的话语模式。第二层次的分析则通过反复阅读文本材料,在描述和分类的基础上,从研究问题出发对上述内容进行总结与阐释,形成与理论的互动,探讨这些话语如何塑造一种新的新闻实践及其所附属的意义。
四、研究发现:在新闻业的沙上“圈地”
在一项话语研究中,Berkowitz和Gutsche(2012)发现新闻业的某些争议事件成为各方参与者重新划定新闻边界的机会,新的边界线成为一种“移动的标准”,得以确定或强化不同参与者在行业的位置。研究者将此现象喻为“在新闻业的沙地上划线”(drawing lines in the journalistic sand)——不断变迁的新闻业如同流动起伏的沙地,争议事件使得其边界线不断移动且彼此覆盖,显示出新闻业“标准”改弦更张之易。参照“沙”与“线”的比喻,本文把围绕非虚构写作的元新闻话语喻作“在新闻业的沙上‘圈地’”:各方行动者在流动、开放、多变的新闻业中,围绕一种新的文体、新的实践方式展开论述,试图在新闻业沙地上圈出具有创新与发展潜能的领地。
这些关于“圈地”的话语从功能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固定其位置的“桩”——它们使新的文体和实践获得日益稳定的认可和位置;另一类是促使其发展的“力”——从业者发展出面对变化的调适与反思能力,由此构成推动新领域发展的动力;最后一类是圈定其范围且可拉伸之“绳”——具有弹性的边界,也意味着圈起的领地有收缩或扩张的双重可能。下文将从这三类论述出发,探讨相关行动者如何通过元新闻话语来建构并塑造非虚构写作实践,并影响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
(一)锚定新文体之桩:确定新闻业中的稳定位置
围绕一种新的新闻文体,从业者们通过下定义(definition making)、划分边界(boundary setting)、合法化(legitimization)的论述实践,在新闻业的沙地上圈起非虚构的领地。这些论述发挥了“桩”的作用,确立了非虚构写作的领地范围,并逐步建立起新实践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1.定义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被定义为一种高标准的内容形式,也被定义为一种能够解决读者阐释需求的解决方案。定义是不同行动者由不同视角出发而进行争论的对象,通过定义掌控(definition control),这些论述塑造了大众对于新闻生产新形式的理解(Carlson,2016:359)。掌控定义的过程体现为两组定义者之间的争论:一部分前媒体从业者追溯其新闻业源头,延续的是“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长篇深度的新闻写作”;另一部分写作者追溯其文学源头,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个文学概念”,“是以前作家所做的东西”。尽管定义的过程中既有对新闻业传统的延续,也有对文学领域的嫁接,但它们发挥了同样的功能,即通过追溯传统来确立非虚构作为一种“高品质”、“兼具文学意义和事实意义”的融合性文体。在定义文体的同时,团队也将其生产实践定位为“支持严肃内容和优秀作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王波等,2020)。
2.为非虚构写作划分边界
在划分边界的过程中,非虚构写作的认知权威通过各类写作标准的论述而得到确立。边界能够影响资源的分配,包括“认知权威”的分配,从而确定何为恰当的(appropriate)新闻实践——谁是够格的从业者、哪些是合适的选题、应该遵从何种规范(Carlson,2016:360)。和定义过程一样,不同从业者也会援引不同的符号资源来建构边界、建立标准、确立认知权威。
确立认知权威的符号资源也分别来自传统新闻业的标准与文学的标准。第一类从业者在论述写作标准时,会援引自己过去在传统媒体时期的特稿写作经验,在媒体机构“锻炼出来的采访能力”和“非常严格的培训”,成为将自己区别于“没有从事过写作训练的人”的门槛。原有评价新闻写作质量的标准也被沿用,如强调“反复的采访”和“详细、扎实、丰富的信息细节”。第二类从业者则将标准定位为写作技巧与个人的阐释能力。他们认为新闻写作只是一种“套路化和程式化的”机构写作,非虚构写作的质量取决于“作者对于事件的看法和他的写作能力”。以上两类关于标准的论述常见于业务讨论的场合。非虚构写作者的认知权威也逐步在这些关于标准与门槛的讨论之中得到确立。
3.非虚构写作的合法性
行动者在论证非虚构写作的合法性时,需要通过继承并修补新闻业的合法性来实现,这一协商过程体现在元新闻话语的双重属性之中。任何文体获得合法性都不是理所当然的(assumed),而是一个推进的过程:曾经,新闻作为合法性知识的认知权威是多方行动者协商的结果;当下,非虚构写作的合法性也正经历一个在论述中不断修正成形的过程。具体而言,通过一种“既批评,又继承”传统新闻业合法性的双重话语,非虚构写作试图构建其文体的权威性基础:在对传统新闻业在当下传播环境中的局限进行温和批判的同时,并不颠覆或挑战其核心理念或认识论基础,且仍然依赖新闻业合法性的表述来为新的文体提供正当性。最能说明这种双重属性的例子是谷雨工作室负责人王波对于非虚构写作公共性的表述:
我想特别强调公共性的重要性。三五年前,我们对公共性的考虑还不那么多,因为那时还有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的同行仍然活跃在新闻一线,有他们在操心、支撑着所谓内容的公共性。那时候跟调查报道相比,特稿的公共性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但今天,这种调查报道在外围拱卫公共性的局面慢慢烟消云散,很多深度报道记者都已经转行,而这个社会仍然需要有人来支撑公共性,这是今天的非虚构写作不得不重点考虑的一点。不然,故事讲得再天花乱坠,也不过是讲个故事而已。
公共性里面既包含有传统的调查报道所追问某个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去探求公平正义在哪里,也包含我们基于当下生存环境的理解和认知。我们在操作非虚构选题时,更多强调的是作品和内容怎样更好地让人与人建立连接,人群与人群消除边界,从而相互了解、互相理解(腾讯媒体研究院,2019)。
这一论述在指出非虚构写作能够填补新闻业公共性缺口的同时,也对非虚构的公共性作出新阐释。对公共性的继承不仅具有象征功能,更体现出非虚构写作暂时不能与新闻业传统剥离开来的实际地位。但重建合法性的过程中存在着曲折,一篇团队解散声明中就说:“一篇好的文章,应该是公共性/社会性与个人性的结合……但是,……这一点也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也正是新闻业“沙地”特质的体现:任何新闻文体或实践的权威基础都不再稳固,延续新闻业的合法性不再是非虚构写作合法性的稳定来源,相反,它想要获得的合法性仅仅存在于不断被阐释、评估、改进的流动性之中。
(二)培育从业者之力:具有应变能力的职业群体
新领地既需要确立稳定的位置,还需要培育后续发展的动力,这一动力便来自从业者适应变化与调整创新的能力。非虚构从业者先是建构出一个精英亚群体的职业认同,再将原有的专业象征资本进行个人化的转换,最后发展出反思、调适与应对变化的能力。
1.建立起新的职业认同
通过职业认同的相关论述,非虚构写作者将自身区别于传统新闻从业者,构建出一个更具精英特质、独特价值的亚群体。在面对媒体行业转型及职业发展变化时,记者需要打破重整原有的职业认同论述,来解决认知与评估方面的挑战。两位研究者发现,职业角色脚本(professional role scripts)成为记者用来应对结构性变化的一种资源:记者通过重新阐释职业角色来完成职业身份的调整(Grubenmann & Meckel,2017)。为应对行业变革,原有职业群体中会组建出更小却更为显著的亚群体(subgroups),这部分成员的竞争性实践也成为整个职业变革的驱动力(Hotho,2008)。非虚构写作者就打破原有“记者”这一职业身份的限制,他们通过钻研、交流报道与写作方法,论述自身作为阐释者的角色,构建出区分于原有新闻从业者的亚群体,也构成了一个新领域发展的初始动力。
这一亚群体关于职业认同的论述也分为两类。一类从业者将非虚构写作视作传统媒体时代特稿写作的延续。有人认为传统媒体的“大船”已经沉没,而非虚构是水面上的“桅杆”,“只有少数船员还在抱着那个桅杆”,它“拓展了媒体内容从业者的职业生命线”。而另一类从业者则向“写作人”的身份转换,非虚构写作成为他们“开启独立写作者的探索”的机会。虽然存在差异,但两类论述都体现出这一阐释群体通过谈论自己的职业从而应对行业变化的过程(Zelizer,1993:233),其主题都是将非虚构写作群体定义为一个更为精英、更具独特价值的亚群体,同时也为转型之后的职业发展积蓄动力。
2.专业象征资本的个人化策略
在和传统媒体机构脱钩之后,非虚构写作者通过获取并累积个人化的象征资本,形成对于这一新领域的知识宣称。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记者的内业名望原本是属于媒体组织这一集体性主体(collective agent)的新闻业资本(Meyen & Riesmeyer,2012:389-390),此时它被剥离开来,转化为非虚构写作者个人的象征资本。他们声称“个人写作开始兴起”;“离开了机构,人们急于建立个人名声,让粉丝围绕在自己的名字周围”(郭玉洁,2017:5)。关于非虚构写作标准的讨论和交流,是一种对于本领域的知识宣称,也是一种个人化的策略,将原本依附于媒体品牌的专业象征资本,转化为强调作者写作技艺与阐释能力的个人化资本。
象征资本的获取与累积也围绕着个人来进行,写作者需要持续产出作品并通过同行的认可来证明其价值。已经写出成名作的作者往往成为同行眼中的品牌,并通过不断发表新作来累积个人化的象征资本:“题材不重要,人才最重要。《大逃杀》这个稿子,你换作任何一个人去写,都可能跟杜强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意识地获取并累积个人化的象征资本,成为了非虚构写作者在面对行业变化时所采取的调适策略,也体现出从业者在处置其专业知识时的自反性(reflexivity of knowledge appropriation),而这种自反性也构成了新领域未来发展的动力来源。
3.面对变化的自反性与调适能力
非虚构写作者的自反性还体现在其面对变化的适应性(adaptability)、面对未来的预见性(proactivity),以及面对失败的实验性态度,这种弹性的调适能力为其从事新兴实践提供了必要的认知资源。自反性首先体现为对变化的认知,比如对市场化媒体衰落的陈述——“我们所熟悉和依赖的写作技术,似乎都失效了;我们所衡量和坚持的判断标准,似乎也失效了;我们所依傍和维系的运转模式,被认为难以为继了”,而成立新团队则可以是让“同行、同人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王波等,2020)。
自反性还体现在面对未来趋势的预见性话语(anticipatory discourse)之中。这类论述将互联网视作机遇,并将自己正在探索的非虚构写作视为一种顺应变化、具有潜能、对于新闻业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兴实践。比如有人从“公众号”的出现中看到个人化写作方式兴起的必然性:“整个写作的历史要被改变了……许多媒体的转型都是在顺着这个潮流走。”这种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性论述是新兴领域或创业领域中常见的话语模式。
自反性还体现为面对过去失败与潜在错误的实验性态度。从业者并不回避错误与失败的可能,但能够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围绕2017年ONE实验室团队解散这一事件,就出现了不少关于行业停顿、危机与转型的评论,而前团队成员仍将其视作一种暂停、转折而不是失败或终局,比如称之为“未完成的梦想”,“会继续从事非虚构相关工作”。这组“告别叙事”不仅具有“反思意味”(李娟,刘勇,2018),也体现出这一新兴实践已经开始形成超越具体机构的延续性。对于失败的实验性态度与反思性叙述,有助于形成一种能够适应变化、保持成长与活力的机制(Dyke,2009),这也恰恰是职业转型中的从业者适应行业变化、投入新兴实践时所需要的。
(三)展开圈地之绳:平台的扩张愿望与生产机制
在分析元新闻话语的论述主体时,不仅需要关注职业转型中的从业者个体,还需要考察展开圈地之绳来扩张领地的机构主体。这些非虚构写作平台有双重属性:它们既是直接与受众互动的场所与渠道,体现出其物质性(materiality);也是圈起新领地并试图扩张其边界的行动主体,体现出其意图性(motivation)。
1.作为场所的平台:传播扩张话语
非虚构写作平台既是以价值与增长为主题的扩张话语的生产者,也是这些话语的传播渠道,它们有针对性地向读者群体和潜在投资者展开推广性论述。以扩张为主题的元新闻话语包括了对其文本质量的推介式论述、对其市场价值的评价性论述,以及针对潜在跨界投资者的说服性论述。
首先,平台主要通过论述其文本质量来向读者推介,突出非虚构这类“高品质作品”意在吸引“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读者”。各平台曾采用合作形式,如“榜单”来集中展示不同机构生产的优质作品;或举办非虚构写作大赛,呈现“最好水平”的作品,并确立这一文体的“创作标准”。围绕这些活动的公开报道也提升了这一新领域的可见性。
其次,平台将非虚构写作论述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内容产品,也是值得投入、正在形成标准、具有成长性的内容生产领域,平台间的合作也就此展开。比如,2015年成立的“非虚构作品创作联盟”,就基于各平台对非虚构创作都有“一样的价值认同”,尤其是市场存在“潜在的巨大需求”。内容创业公司还将内容的“价值”与可持续商业模式进行关联:“这种价值不仅是社会价值,更是商业价值,就是写作者可以通过写作获得收益和认可。”
最后,平台还将非虚构写作置于更大的创业领域与更广的媒体场景之中以吸引潜在投资者,如请来“非虚构写作者、出版人和影视人”共同讨论“非虚构平台怎么能够更好对接影视行业需求”,试图打通“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出版、非虚构影视改编三大领域”。这些关于商业合作前景的描绘来自平台对新领域成长性的期待,也是资本扩张动力的体现。
平台合作生产的扩张论述不是应对性的(reactive),而是生产性的(generative),体现出其圈地之后再求拓展的意图。平台主体不仅要在不断变化的行业中确定其位置,更需论证新领域出现增长和繁荣的可能,并以实验性的态度来探索新型的营收模式。
2.作为行动主体的平台:重整生产方式
平台不仅通过公开表达的话语形式来塑造人们对新兴实践的理解,还以机构的角色来直接组织非虚构写作的内容生产。通过重组象征资本、控制时间成本、将内容产品化等方式,非虚构平台开始形成组织化的生产常规,也为这一写作实践赋予了新的机构属性。
平台组织生产的第一步是将象征资本再次机构化:非虚构从业者个人化的象征资本被再次重组为平台的机构资本。一部分象征资本是从业者过去的新闻业资本,一家平台的创立记事就写道,“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往往都是新闻媒体最优秀的记者”,并强调其作品“属于非虚构的标杆之作”。而另一种象征资本则是写作者在非虚构领域新积累起的名望。非虚构写作被论述为一种专业的写作能力,在某平台的网课宣传文案中,非虚构写作被比喻为“一座知识和技艺的殿堂”,而普通人则“需要一个路标和阶梯的指引”,即“非虚构导师”的指导。
平台组织生产的第二步是通过新的生产常规来控制时间成本。几个非虚构团队都曾做过相似的调整——控制单位时间成本,重回媒体生产节奏。在新闻业场域中,从事某类新闻工作的时间成本越高,意味着从业者在场域中有着更高的地位(Meyen & Riesmeyer,2012)。非虚构写作延续了特稿的地位,也同样“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等成本。平台一般用两种方法来应对时间成本和出稿量的矛盾:一是寻找追求品牌价值而不计成本的投资者,但只有少数写作者或团队才能得到“体面地做一件事”的充足时间;二是压缩时间成本,即生产节奏的媒体化和对效率的强化。某平台的选题方向一开始是“做别的媒体不做的东西”,后来则变得“更媒体化了,重大的事件或人物都不能错过”,不能只做“无视时间和时效性”的“强故事”,同时还要做只需“一周时间”的“话题式”选题和“突发热点”。这样,传统新闻业强调时效性的逻辑又重新回到非虚构的生产节奏中来。
平台组织生产的第三步是将非虚构作品定位为需要适应互联网传播逻辑的内容产品,其背后则是更为强势的编辑部。互联网内容产品的定位便要求以频繁的节奏出稿以获得稳定流量,或通过“爆款”快速获得认可。以产品化为目标,这些组织中出现了更加强势的编辑部,如在被称作“大编辑制”的组织结构中,“强编辑”与作者的权力关系在塑造着新的生产常规;还比如采用“介入式和共同写作式编辑”的工作流程,则是为了将大众写作的内容加工为更完善的“非虚构故事产品”。强编辑部的组织架构让平台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生产内容产品。
在使用圈地之绳来拓展领地的过程中,平台也面对着收缩或扩张的双重可能。平台一方面在扩张驱动之下产生了竞争动力,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机构成本与生产效率的压力。这些组织化的机构实践体现出平台既有对于扩张机遇的积极谈论,也有对于维持发展的精打细算。既要扩张又需务实,这或许是任何创业领域的机构主体都需具备的双重思维。
五、小结:“一个需要创立的位置”
布尔迪厄用场域理论分析“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时,认为他们是在文学场域中寻找“一个需要创立的位置”——现成的位置只需占据就够了,而需要创立的位置则处于潜在的状态,但人们已经提出了对它的要求,只有建立一个能在其中找到位置的场,才能令其得以存在(皮埃尔·布尔迪厄,1992/2011:27-33)。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即是在新闻业的沙地上重新“创立位置”的一种实践。本文从文体、从业者和机构这三个层面描述了这一“创立位置”的过程:非虚构作为一种“新”文体通过继承“旧”传统来尝试确立其位置与合法性;从业者通过重构其职业认同来维持变化中自我认知的协调性,其反思与调适能力为新实践的发展积蓄了动力来源;机构主体则尽力建构出创业领域的繁荣前景与扩张可能,也让新实践初步形成了组织化的生产常规与营收模式。
对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与接受的社会条件的分析,并没有简化从业者创作实践的价值与投入,而是通过分析使其“创造者”的独特性成为可以理解的关系。从业者打破了原有“记者”这一职业脚本的限制,通过创业或转型的方式来搭建出非虚构这样一种融合性媒体实践的新空间。他们努力将非虚构建成一个服从自身法则的独立领域,也建立起自己作为创业者的积极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利的,它让人们可以不必拘泥于特殊性,从变化中获益。正是在整体领域的建设活动中,从业者个体的位置与努力被凸显出来,他们的轨迹也组建出整体领域的新规则与持续发展的
前景。
随着各类机构主体的位置确立,新领域的结构也逐渐明晰。但新形成的非虚构场域中也体现出经济力量以“他律”(heteronomous)的维度,与新场域自身独特文化资本以“自律”(autonomous)的维度之间的张力。非虚构场域形成了一套新的认可机制(mechanism of recognition),成名是个体从业者获取象征资本、确认自己在场域中位置的职业动机,而平台则成为主要的认可机构,并和从业者形成一种更为临时与流动的关系,且两者之间也存在张力或冲突的可能。比如,依托于机构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团队“正午”就在2020年初宣告解散,团队负责人之一将其原因归结于机构所遵循的“资本规则”。这样的冲突或许还会重复出现,因为新的组织形式与生产常规正在形成、尚未稳固。未来研究可以考察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如何重新形成关系网络、重新确定各自在场域中的位置,又如何在新的内容生产局势中形成新的文化权威与权力关系。
作为一项基于文本的研究,本文意在呈现话语对新闻实践的塑造作用,注重其中行动者的主体性与反思性,以及新领域的生长与变革可能。若要关注某一个新兴领域的持续发展,未来研究还需要考察非虚构写作当下的认可机制能否在未来仍为身处其中的人及新来者提供布尔迪厄所说的“幻象”(illusion),使得他们仍愿相信这一场域中的游戏赌注和规则——即其中被共同认可的价值——并继续在其中进行认知、情感与时间的投资。此外,非虚构写作的未来还有其他面向,比如它是否沿袭了旧有新闻场域中以“真实性”为目标的新闻写作追求,是否能在互联网时代提供一种公共性传播的可能性,这一场域又是否能形成其独有的理念资源以影响未来新闻业的实践逻辑,这些也是值得研究者持续考察的课题。■
注释:
①研究者将相关文本归类编号,并标注其作者、标题和发布时间等信息,形成文本列表。这些文本来源主要包括:作者在论坛的现场录音及笔记、公众号“地平线NONFICTION”、公众号“谷雨计划-腾讯新闻”、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公众号“刺猬公社”、公众号“三明治”,以及非虚构作者在纪录片、播客中接受访谈的内容。由于篇幅原因,正文中未对所引用文本一一作出标注,如想获取文本列表及具体引用说明可联系作者。
参考文献:
陈楚洁(2018)。“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新闻记者》,(3),4-22。
邓力(2018)。塑造人物与再现偏差——人物类非虚构写作中讽刺修辞的效果及争议。《新闻记者》,(5),52-61。
郭玉洁(2017)。《众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黄典林(2018)。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新闻记者》,(5),35-43。
李娟,刘勇(2018)。变动时代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与重构——基于 ONE 实验室解散的元新闻话语研究。《新闻记者》,(5),62-70。
陆晔(2018)。文学新闻:特征、文化价值与技术驱动的未来。《新闻记者》,(5),71-82。
皮埃尔·布尔迪厄(1992/2011)。《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腾讯媒体研究院(2019)。谷雨:聚焦“公共性”,打破人与人间的隔阂。公众号“腾讯媒体研究院”(2019年12月23日)。
王波,王世宇,宋晓晓,李佳,刘心雨(2020)。新媒体逻辑下的腾讯“谷雨”非虚构内容生产与传播。《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18),77-98。
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ucoinJ. (2001).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and narrative theory: The literary journalism of Ryszard Kapu?ciński. Journalism, 2(1)5-21.
AucoinJ. (2016). The imperative of personal journalism: James Agee and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Journalism, 17(3)281-296.
Berkowitz, D. & GutscheE. (2012). Drawing Lines in the Journalistic Sand: Jon StewartEdward R. Murrow, and Memory of News Gone B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9(4)643-656.
BishopW. & StarkeyD. (2006). Keywords in Creative Writing.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P.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1)14-25.
Boynton, R. (2005). The New New Journalism: 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s Best Nonfiction Writers on Their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BramanS. (1985). The “facts” of El Salvador according to objective and new jour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9(2)75-96.
Carlson, 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Carlson, M. & UsherN. (2016). 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Digital Journalism, 4(5)563-581.
ChristiansC. G.FerréJ. P. & FacklerP. M. (1993). Good News: Social Ethics and the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aig, D. (2006). The Ethics of the Story: Using Narrative Techniques Responsibly in Journ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DykeM. (2009). An enabling framework for reflexive learning: Experimental learning and reflexivity in contemporary moder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28(3)289-310.
Forde, K. R. (2007). Discovering the explanatory report in American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1(2)227-244.
Greenberg, S. & WheelwrightJ. (2014). Literary journalism: Ethics in three dimensions. Journalism, 15(5)511-516.
GrubenmannS. & Meckel, M. (2017).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 resource to cope with change in the industry? Journalism Studies18(6)732-748.
HarringtonW. (2007). Towards an ethical code for narrative journalism. In M. Kramer & L. McCall (Eds.)Telling True Stories (pp. 170-172). New York: Plume.
Hotho, S. (2008). Professional Identity - Product of StructureProduct of Choice: Linking Chang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hanging Profession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21(6)721-742.
JosephS. (2010). Telling true stories in Australia. Journalism Practice, 4(1)82-96.
Krieken, K. & SandersJ. (2017). Framing narrative journalism as a new genre: A case study of the Netherlands. Journalism, 18(10)1364-1380.
Merljak ZdovcS. (2009). More storiesmore readers? Feature writing in Slovene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3319-334.
Meyen, M. & RiesmeyerC. (2012). Service ProvidersSentinelsand Traders: Journalists’ role perception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ism Studies13(3)386-401.
Pauly, J. (2014). The New Journ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interpretation. Journalism, 15(5)589-604.
Pauly, J. (2016). Review of the book The undeclared war between journalism and fiction: Journalists as genre benders in literary historyby D. Underwood. Journalism, 17(7): 934-939.
RobinsonS. (2017). Check Out This Blog: Researching Power and Privilege in Emergent Journalistic Authoritiesin P. Boczkowski and C.W. Anderson (Eds.)Remaking the News: Essays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pp. 217-233). Cambridge: MIT Press.
ShimH. (2014). Narrative jour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newsroom: The rise of new paradigm in news format? Narrative Inquiry2477-95.
SofferO. (2009). The competing ideals of objectivity and dialogue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10(4)473-491.
Wolfe, T. (1975). Part one: The new journalism. In T. Wolfe & E. Johnson (Eds.)The New Journalism (pp. 15-68). London: Pan Books.
Zelizer, B. (2017). What journalism could b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219-237.
邓力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本文受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8ZFQ86001),是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网络媒体伦理规范研究”(项目编号:16BXW09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