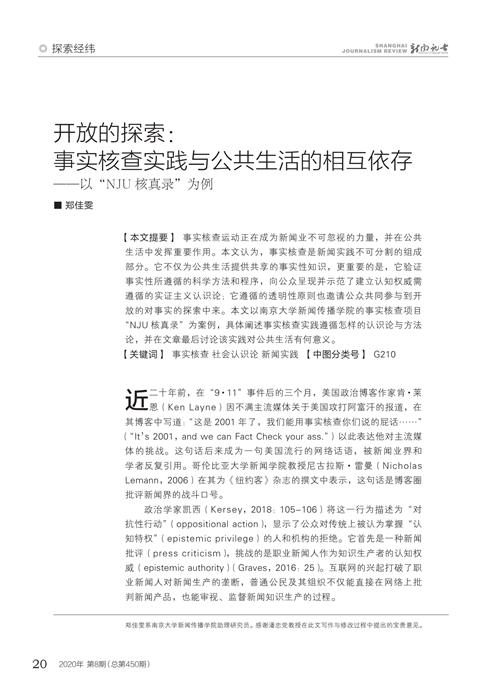开放的探索:事实核查实践与公共生活的相互依存
——以“NJU核真录”为例
■郑佳雯
【本文提要】事实核查运动正在成为新闻业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认为,事实核查是新闻实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公共生活提供共享的事实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事实性所遵循的科学方法和程序,向公众呈现并示范了建立认知权威需遵循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它遵循的透明性原则也邀请公众共同参与到开放的对事实的探索中来。本文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事实核查项目“NJU核真录”为案例,具体阐述事实核查实践遵循怎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并在文章最后讨论该实践对公共生活有何意义。
【关键词】事实核查 社会认识论 新闻实践
【中图分类号】G210
近二十年前,在“9·11”事件后的三个月,美国政治博客作家肯·莱恩(Ken Layne)因不满主流媒体关于美国攻打阿富汗的报道,在其博客中写道:“这是2001年了,我们能用事实核查你们说的屁话……”(“It’s 2001, and we can Fact Check your ass.”)以此表达他对主流媒体的挑战。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美国流行的网络话语,被新闻业界和学者反复引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尼古拉斯·雷曼(Nicholas Lemann, 2006)在其为《纽约客》杂志的撰文中表示,这句话是博客圈批评新闻界的战斗口号。
政治学家凯西(Kersey, 2018:105-106)将这一行为描述为“对抗性行动”(oppositional action),显示了公众对传统上被认为掌握“认知特权”(epistemic privilege)的人和机构的拒绝。它首先是一种新闻批评(press criticism),挑战的是职业新闻人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Graves, 2016:25)。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职业新闻人对新闻生产的垄断,普通公民及其组织不仅能直接在网络上批判新闻产品,也能审视、监督新闻知识生产的过程。
同时,这一对抗性行动的审视对象还包括政治精英和政府工作人员。传播技术的变革也使得越来越多政治精英、政府官员能够巧妙地规避新闻从业者的把关过滤,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向公众发表宣言,试图影响舆论和公民选择。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传播生态中,一些专门的事实核查网站应运而生。核查者试图逐行评阅政治人物所作的公开宣称,监督其事实的准确性。通过这样的挑战,原先那些认知权威的潜在力量被削弱了,公众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到定义事实、发现事实、验证事实的过程中来。
如今,事实核查运动愈发成为新闻业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在各国选举、公共政策等领域为公众提供了大量经过核实的事实性宣称。事实核查运动的支持者们认为,核查事实、报道真相是健康的民主生活中新闻的重要功能,它能督促政治精英和决策者为其言行承担责任,并为公共讨论提供共享的事实性知识(Jamieson & Waldman, 2003:196)。但是质疑者认为事实核查对公共生活的改善是有限的(Uscinski & Butler, 2013)。一些政治学者则认为,对公共事务的错误认知与愈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政治极化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政治现实里,有时人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可以被当作错误,什么又可被认为是事实;有时人们甚至对事实置若罔闻(Edelman, 2001:1-10)。而关于事实核查效果的研究则印证了一点:学者们发现事实核查只能在特定情境下产生温和的纠偏效果,有时甚至因核查结果违背人们的已有观念而产生抵触效果(Nyhan & Reifler, 2010)。
本文认为,事实核查是新闻实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公共生活提供共享的事实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事实性(factuality)所遵循的科学方法和程序,向公众呈现并示范了建立认知权威需遵循的实证主义认识论(positivist epistemology);它遵循的透明性原则也邀请公众共同参与到开放的对事实的探索中来。本文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事实核查项目“NJU核真录”为案例,具体阐述事实核查实践遵循怎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并在文章最后讨论该实践对公共生活有何意义。
一、新闻知识与现实主义的认识路径
正如舒德森(Schudson, 1981:121-160)阐述的,根据客观性原则开展的事实性报道崛起于20世纪早期,它包含一系列规范新闻实践的职业伦理、原则。比如,记者应该无偏差地记录、报道事情本来的样子,尽可能地保持独立和中立、不偏不倚,避免表达主观态度。遵循这些原则开展的新闻活动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基于科学发展进行的社会变革。在科学领域,科学家们通过观察、实验等步骤来验证科学假说的真伪。在新闻领域,如甘斯(Gans, 2004:39)指出的,新闻学和社会学一样,也是一门实证学科;而新闻产品是记者通过实证探索产生的现实判断(reality judgments)。尽管记者竭尽所能保持客观,现实判断也无法与价值脱钩。这些价值既可能来自记者本人,也来自记者依赖的信源。如果记者不对这些价值观进行审视就理所当然地接受它,那么这些价值也就成为“拟似意识形态”(paraideology)。
如果用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 Luckmann, 1967)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术语来说,新闻是记者根据他们共享的知识储备,通过社会生产所创造的对现实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而197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知识社会学研究指出,日常新闻生产所依赖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及相应的报道方法使其创造的新闻产品无法实现新闻业宣称的再现客观现实的目标。舒德森(Schudson, 1991)回顾了这一时期关于新闻知识生产的研究,总结了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三个视角,即组织社会学视角、政治经济学视角和文化人类学视角。这些研究共同指出,作为社会生产的文化产品,新闻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它所赖以发展和运行的政治经济结构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受到庞大的“新闻网”(news net)、新闻机构的组织结构、日常工作流程等因素的影响。
尽管社会学家们认可新闻生产所依赖的日常实践往往是必要的,但仍然认为以这种方式生产的新闻知识在认识论上是有问题的。因为现代认识论往往看重人的认知自主性(epistemic autonomy),即认为人们应该通过自己的感官、记忆和推理等直接经验来获得知识。但是新闻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记者通常无法通过直接经验接触到他们想报道的事,而不得不依靠采访专家、官员、当事人、目击者等中介者,获取他们的证言(testimony)来报道新闻(Godler, Reich & Miller, 2020)。这就意味着记者所获得的大量知识都是二手知识。那么他们如何判断他人提供的证言是否可靠,哪个可以写进报道、哪个不能呢?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帮助我们理解记者在日常采写活动中如何确证事实(Godler et al., 2020)。社会认识论是崛起于20世纪后期的哲学分支,它认识到人并非完全自给自足的认知主体,不可能通过直接经验了解所有知识,也不指望人们在接受别人说的任何宣称前都做充分的研究和调查。相反,社会认识论者继承康德关于“证言”的论述,认为人们认知生活的核心是彼此之间的认知依存,他人的“证言”可以被看成知识的一种合理来源(Fuller, 1987;Gelfert, 2010)。因此,研究知识获取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判断他人的证言是否可靠、可信。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Fricker, 1994)。第一种是休谟(David Hume)关于证言的还原主义认识论(reductionist epistemology)。他认为他人的证言往往是不可靠的,因此接受者在相信他所听到的证言之前,必须做最小程度的核实。第二种是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的非还原主义认识论(non-reductionist epistemology)。与休谟相反,里德假设人们生来有说真话的倾向,也倾向于相信他人所说为事实;因此除非接受者有足够的理由提出怀疑,否则应默认他人的证言为真。
社会认识论为新闻生产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人们可以借此考察记者遵循什么标准和程序来决定哪些证言或宣称可以被当作事实(Godler et al., 2020)。对现实生活中具体新闻实践的考察发现,记者通常需要建构一个事实网络(web of facticity)(塔奇曼,2008:93-111)来证实某一个假定的事实性陈述是否成立。也就是说,记者若要证实一个假定的事实成立,需同时寻找一系列与之关联的其他事实来支持、佐证这第一个事实,而这些用来佐证的事实也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可靠性。其次,事实网络上的每则证据都来自特定的信息源,记者往往通过划分信息源等级来评估不同信源提供的证据的可信度,然后通过引用这些信源的话构成一个相互佐证的事实网络。
一些新闻学者从现象学角度考察这一问题,发现不同样式的新闻在确证(justify)这些引语——或用社会认识论者的术语来说就是“证言”——所遵循的认识论是不同的(Ettema & Glasser, 1987)。比如,日常新闻记者的采写活动围绕“条线”(beat)展开。他们报道的新闻往往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场所,如医院、法院、消防局、市政厅。遵循这一套条线系统,日常报道记者倾向于采取非还原主义认识论立场,默认那些来自合法机构的信源对一件事情的解释为事实性宣称(Godler et al., 2020)。
艾特玛和格拉瑟(Ettema & Glasser,1987)认为日常报道记者的这一倾向既是基于实践考量,也是为了遵循客观性的新闻原则。从实践角度来说,日常报道记者没有很多时间去核实信息,他们不得不根据信源可信度来判断宣称的真实性。鉴于官僚机构掌握的资源和能力,人们通常会认为官方生产和提供的信息具有最高的可信度。而从原则角度来说,“核实”(verification)信息真实性往往意味着记者不得不在报道中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这违背了客观报道的要求。因此,日常报道记者追求的往往是平衡与准确,而不是真实性。但是,正如塔奇曼(2008:93-111)所言,在日常实践中,引用多方解释这套职业程序往往最终被转换为一种“技术工具”,帮助记者卸下判断事实性的责任,使记者和所属新闻机构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又由于媒体机构不可避免地依赖权威信源报道新闻,新闻也就愈发成为政治、商业、文化精英的公关工具(Lau,2004)。
尽管很多人从塔奇曼的论述中引申出“事实不可知”、“新闻客观性法则不是为追求事实性”等结论,但事实上塔奇曼只是提醒人们警惕新闻生产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局限,这种局限性有可能使新闻报道偏离(relocating)追求真相这一目标,她并没有否认新闻生产基于独立验证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事实上,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的记者遵循的也是同样的认识论,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着和日常报道记者同样的局限,只不过调查记者更加能够根据证据的轨迹去挖掘多重证据,并依据逻辑推理去探索事实。
和日常记者默认官方信源具有最高认识权威不同,调查记者会根据他们对真实性的假设来建立“证据阶梯”(hierarchy of evidence)(Ettema & Glasser, 1987)。处于证据阶梯最顶端的是在某个行为发生时产生的物证,比如摄像视频。如果调查记者拿到此类证据就认为有足够证据证明该事件,无需再寻找其他证据了。下一个级别的证据是书面证据,包括各种文件、官方记录等。再下一级证据是关于该行为的事后叙述,如目击证人、专家等提供的证言。撰写报道时,记者需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权衡证据的可靠性,在多重证据链中寻找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从而得出一个记者自己在道德上确信无法被推翻的结论。
近年来的信息技术发展扩大了新闻报道的样式,并深刻影响了新闻生产的认识论。沿着艾特玛和格拉瑟(1987)的研究路径,一些学者考察了新兴新闻样式是如何生产确证的(justified)知识宣称的,如数据新闻(Parasie, 2015)、在线新闻(Matheson, 2004)等。正是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事实核查这种新型的新闻样式如何报道事实。
二、事实核查的认识论
记者核实事实绝非新事物。如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2019:95)所言,“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一般来说,媒体内部有其编辑、审核机制。在新闻报道发表之前,由专门的媒体内部人员对报道中所涉及的事实性信息,如时间、地点等进行核实。有一些媒体,如《时代》周刊、《纽约客》等杂志早期更是在编辑部成立了专职核查部门,在发稿前对细节进行事实核查。而本文所述事实核查实践是一种特定的新闻样式,它不是在文章发表之前媒体的自查,而是验证那些已公开发表的宣称的真实性。核查者对这些宣称的真实性有所怀疑,故通过特定的方法和步骤加以核查。
本世纪初出现了专门核查政治言论的事实核查网站。200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公共政策中心创办了FactCheck.org网站,专门核查政客言论和新闻报道中的政治宣称。2007年,《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创办了PolitiFact网站,《华盛顿邮报》也在同年设立了事实核查部门。如今,事实核查运动席卷全球新闻业。核查对象也趋向多样化,主要包括三种:一种是公众人物(如政治家、政府官员等)在演讲、会议、广告等场合(或文本)中公开发表的事实性宣称,或由媒体在报道中引用的此类宣称;第二种是在传统媒体或自媒体所作单篇报道中,记者或评论员自己陈述的事实性宣称;第三类是社交网络上流传的,或民间口耳相传的流言或传言,这些传言未必有明确的信源,也不一定形成特定的文本,但却因广泛流传而被公众熟知。比如波因特国际事实核查网络(Poynter’s 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建立了“新冠病毒事实联盟数据库”,搜集了100多家事实核查机构核查的5000多条在社交媒体上口耳相传的流言。
尽管各个核查机构在选题范围、核查目标,及对事实的判定标准上均有不同,但总体来说,这些实践包含如下步骤:
第一步,选择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性宣称,并从中选择可验证的事实而非观点进行核查。无论这则宣称是来自专业媒体机构或自媒体上发表的单个文本,还是只经口耳相传,核查者都需区分事实性或观点性宣称;然后选出最有误导性、可能引起误解的事实性宣称;再评估核实的可行性。
第二步,运用各种新闻的或科学的方法搜集、分析证据。那些常规的新闻核实技巧也为核查者所用,如对信息进行溯源、采访确认等。但与传统记者不同,核查者并非完全依靠采访来核实事实,他们的大量时间都需要分析文本、数据、图片、视频等一手材料,如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演讲稿、公司财报、地图等。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和搜索引擎的普及使得当代记者获取数据的能力空前提高,他们经常使用文本分析、数据挖掘、统计等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方法来分析新闻素材。
第三步,依据透明性原则呈现核查结果。在核查实践中,最有争议的分歧是使用打分系统来呈现核查结果。比如说PolitiFact使用“真相欧米表”(truth-o-meter)来标识宣称的准确性。这种量化评分因过于简单粗暴而遭到批判(Uscinski & Butler, 2013)。而在文本论证过程中,核查者需遵守“透明性原则”,即通过直接披露核实、判定的过程来呈现核查结果(Graves, 2017)。其具体操作过程包括:在文章中添加可溯源的链接、向读者呈现所有证据、告知读者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提醒读者核查方法的缺陷等。这是一种近似于对科学方法的复制,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即使核查者判断错误,读者也可追溯信源自行核实。
然而,这套核查模式只是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在具体实践中,核查者从选题到搜证、判定、呈现事实的全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充满主观性。比如,在选择核查对象时,核查者是有倾向的。某些政治人物比另一些人更容易被选中(Uscinski & Butler, 2013)。乌辛斯基和巴特勒还批评核查者采取一种“天真的政治认识论”,假设政治讨论是可以完全基于事实展开的。然而公共讨论中的大量内容其实都是观点性的,而非可验证的事实。还有一些虽然是事实性宣称,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方法,核查者无法得出可靠结论。比如在核查关于因果关系的宣称时,人们对于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一个结果归咎于特定原因是有分歧的。在科学研究中,归因需遵循严谨的实验步骤,并通过严格的统计方法来探究原因。很显然,记者很难在实践中复制这套成熟的科学手段。
鉴于事实核查的局限性,乌辛斯基和巴特勒(2013)警示道:核查者必须认识到政治生活的模糊性,这不是靠事实核查能够完全消除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内部话语中还是公开文本中,核查者都反复强调事实的模糊性与复杂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事实核查需遵循透明性原则,向公众公开搜证、验证的整个过程,使公众能在公共讨论中指出核查者所犯错误,自行探索、补充证据,并依据自己的推理得出事实性判断。正如格雷夫斯(Graves, 2017)采访的一位核查者所说:“我们在报道的时候非常透明,所以即使有人不同意我们得出的真实性判断,也可从我们的报道中学到点什么。”
综上,事实核查新闻遵循社会认识论中蕴含的在社会过程中相互验证这一逻辑。核查者并不默认被核查的宣称为真——即使这些宣称有可能是来自政治精英或政府官员——而是假设它有可能偏离现实或有误导性,然后,通过不断实践实证主义的知识获取方法来确证事实。遵循透明性原则,也使公众能够不断熟悉、学习、模拟这种实证主义求知方法,使他们了解判断事实需遵循怎样的规范性程序和步骤,邀请公众共同参与到纠正错误、探索事实的过程中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事实核查实践具有公共生活中“元传播”范本的意义(潘忠党,陆晔,2017)。
总之,在讨论事实核查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时,我们更应该问的不是它能否判定事实,而是:事实核查实践如何为公共讨论提供共享的事实性知识?它所遵循的认识论以及相应的方法论对于规范公共讨论有何意义?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用一个案例来具体阐述这些问题。
三、NJU核真录的案例分析
与西方国家正在经历后真相危机一样,中国社会的公共讨论也受到大量信息污染。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失实报道使处于惶惶不安中的人们深受误导。在专业媒体主导事实报道的年代,这样的报道活动尚不太容易受到挑战。但在今天,媒体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唯一的阐释者。职业记者、公民记者及普通受众共同参与到挖掘、揭露、公开(publicize)事实的过程中来,形成一种协作式的事实核验活动(Zeng, Burgess & Bruns, 2019)。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事实核查项目“NJU核真录”(以下简称“核真录”)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成立于2017年10月。它原是本文作者开设的“融合新闻报道”课程的课堂实践项目,现已成为南大新传院教学实践课程“未来编辑部”的组成部分。该公众号的采编人员均为该校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作为一个以事实核查为主要内容的项目,它旨在为公共讨论提供经过验证的事实,解释模棱两可的公共政策,并监督公众人物所作宣称的事实性。
本文是参与者反思式的个案分析,以展现事实核查认识论在具体操作中如何体现,核查过程有哪些不确定性和局限性。选取该案例主要出于两点考虑:首先,未来的新闻实践必须包含事实核查所遵循的原则、程序和步骤。新闻报道作为特定的文本再现,也必须包括核查过程和结果的报告。而在国内,专门性的事实核查媒体机构还比较少,核真录是其中之一。相比之下,它依托大学的新闻学院开展实践,更少像媒体企业一般受到商业利益压力和科层组织的官僚化管理约束,因此也能更充分地在实践中落实这一认识论的原则。其次,未来的新闻教育也必须培养核查事实所需的搜证、分析和写作能力,这是一项基本的专业技能训练。核真录作为高校新闻学院设立的新闻实践创新项目,既在实践中体现了事实核查的理念,又为新闻教育创新提供了可参考范本。
但是,该项目所有权和组织结构上的独特性也限制了它落实这一认识论原则的潜能,并限制了它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比如说,由于资源紧缺、经验不足等因素,核真录所能核查的选题往往局限于小规模、复杂程度低的新闻题材。学生在核查过程中所依赖的证据较有限,证据链的拟合程度也相对较低,加大了它误判事实性的概率。尽管如此,核真录仍是目前国内最能体现事实核查认识论的实践范本。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将以此案例展示事实核查的认识论原则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落实的。如上一节所述,事实核查一般遵循三个基本步骤:选择可验证的事实性宣称、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挖掘证据并作出判定、依据透明性原则呈现判定结果。接下来将从这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一)如何选择可验证的事实性宣称
选择合适的事实性宣称来验证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从一篇文章中选择可验证的宣称首先要区分文章中的事实与观点。核查者需在阅读全文后理解作者的主要论点,然后将与作者论点最相关的论据找出来。这些论据中有些是公认的事实,有些则真实性存疑,还有些则是明显的观点。核查者需挑选那些可疑的事实性宣称进行核实,接着根据信源可及性、自己掌握的搜证工具、分析工具等来评估是否有能力核实这则宣称。这里没有金科玉律,核查者的判断能力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粗浅的规则可供参考。
第一类可被当作事实性宣称来核查的是对事物或事件状态的描述,这也是最普遍的一类核查。如一则宣称指称某个事件正在发生,则可核查该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信息。若一则宣称中包含数字信息,则可核查该数字是否准确。另一种与数字相关的宣称是关于“比较格”的核查,如某事物A比另一个事物B更高,或是某事物A是所有对象中最高的等。比如核真录在2020年3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澳洲大火后果严重,信息真实如何判断》的文章中,作者核查了微信公众号“英国报姐”的一篇文章中八则事实性宣称,有七则都是关于事物或事件状态的宣称。如“火势最严重的两个州是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仅有600栋房屋被摧毁,死亡人数为6人”、“过去两年的时间记录了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低的降雨量”、“南澳大利亚多地刷新了11月份的最高记录”等。
第二类核查的内容是关于因果关系的宣称。从一个原因推导出一个结果的推理过程必然要加入个人的认知活动,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主观诠释。因此对于一些认为客观事实必须独立于主观诠释之外的人来说(Uscinski & Butler, 2013),因果推论不应该属于事实的范畴。但包括PolitiFact在内的众多事实核查网站均将因果推论纳入其核查范围,这是因为证据与结论的一致性本身也是事实的组成部分,那些通过逻辑谬误得出的结论应该和那些通过逻辑一致性得出的结论区分开来。
比如《全球雾霾最严重城市的四大事实》一文核查了微博大V @sven_shi 对“煤改气”问题的观点,该博主将北京的雾霾治理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比较,宣称“全球冬天雾霾最严重的地方是蒙古的乌兰巴托,原因就是人口涌入然后大规模的燃煤取暖”。尽管该博主表达的主要是他的个人观点,而观点并非可核查的事实,但其观点仍是依据可验证的事实作出的推论。因此核查者试图通过验证其论据的事实准确性来检验其论点的可靠性。在这则宣称中,前半句是关于最高格的事实性陈述,而后半句则是对乌兰巴托雾霾问题的归因,即因果关系。此处需注意的是,论据缺乏准确性并不意味着其论点本身一定不合理,只是说明其论点缺乏可信的证据支撑。
第三类核查的内容是关于“预测”。它是指特定个人或机构在过去某个时间预测未来某个时间点会发生的事情,核查者在这个未来的时间点到了之后回溯当时的预测是否兑现。典型的预测类宣称所包含的词有“预计”、“有可能”、“将会”等。这是在事实核查实践中颇有争议的宣称类型。乌辛斯基和巴特勒(2013)认为预测是关于未来发生某个事件的可能性评估,它是尚未发生的事情,并非可验证的事实;只有当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才知道预测是否准确。在现实核查中,这确实是最难取舍的一种宣称,在核真录已发稿件中,也只有两则关于预测的核查。其中一则是2018年4月3日关于天宫一号坠落的核查,一篇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宣称:“天宫一号有可能降落的地点包括纽约、巴塞罗那、北京、芝加哥、伊斯坦布尔、罗马和多伦多。”而核查发表时天宫一号已经坠落南太平洋,因此可以判定之前的预测是不准确的。但正如乌辛斯基和巴特勒的批评所言,既然是预测,那么就存在预测错误的可能性,因此即使错误也不能判定预测者撒谎。鉴于人们对这类宣称能否被称为事实有很大争议,核真录在考虑选题时,甚少选择此类宣称。
一则宣称有可能涉及多个层次的事实,如有必要,则需逐一核实。如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某个信源所作宣称,则第一步需对这句话进行溯源,查找出处,然后根据前后语境核实这篇文章在转述时是否被曲解,即核查“复述”的准确性。第二步,若这则宣称是一个事实性陈述,还需核实该陈述所含事实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在2018年5月25日的稿件中,核查者分析了梨视频发布的一个Facebook年度发展大会的视频。视频中,公司CEO扎克伯格在演讲中说:“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婚姻关系是从网上开始的。”这则宣称里包含三个可核查的信息:首先,扎克伯格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他说这句话的语境是什么?第二,如果扎克伯格是从别处引用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的出处是哪里?扎克伯格的引用是否准确?第三,美国真的有三分之一的婚姻关系是从网上开始的吗?像这样,在每分析一则事实性宣称时,核查者需先溯源,再分析宣称包含多少个可验证的事实,然后逐一核实。
(二)如何判定事实准确性
选择了核查对象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判定这一陈述的事实准确性。核查者首先需确定从何处搜集证据来验证该陈述,接着通过对证据的分析、推理判定该陈述的准确性。在方法论上,核真录对每一则信息的核实都要求遵循事实一致性(factual coherence)(Graves, 2017),即遵守“信源三角互证原则”(source triangulation)。如果一则信息只有一个信源,并且这个信源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论证其结论,那么单一证据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但新闻实践的诸多缺陷使得核查者判定事实准确性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说,核查者往往无法直接体验正在发生的事,因此不得不将他人的证言(testimony)作为证据来确证某则宣称的可靠性。这就将核实真实性转变为对他人证言可信度的评估。但是可信度本身并不等同于真实性,可信度高的信源所提供的证言也有可能偏离事实。然而核查者无法准确评估这一偏离的程度。这就使得核查者经常无法完全确证被核查的宣称是否为真,而不得不给出“很可能为真(或假)”的表述。
上述“天宫一号”的稿件核实了一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作报道中的宣称,指“天宫一号”的残片中带有肼类物质,这种物质有剧毒甚至致癌。文章首先确认了报道中所称的这种物质确实为有毒物质,接着核实了“天宫一号”所使用的燃料是否含有该物质。在这个问题上,核查者缺乏渠道也缺乏专业的手段去验证究竟“天宫一号”是否含有这种物质,只能依靠引用媒体报道等二手信源作为证据。但是核查者无法证实(verify)他所引用的媒体报道就一定为真。这时,如社会认识论指引我们的,核查者会根据一些线索来判断引用的证言是否可信(Godler et al., 2020)。比如所引用的媒体报道是否采访了可识别的信源、该信源的身份和经历是否使他具有专业知识来提供足够可靠的证言、该信源的论证是否足够具体和流畅等。
上述“天宫一号”的稿件引用了《新闻晚报》对燃料加注员的采访作为证据。核查者写道:“燃料加注员刘华宾在接受《新闻晚报》采访时称:‘(加注)过程中,嗓子干、经常咳嗽,还有作呕的感觉……’,与外媒报道的接触肼类物质的不良反应基本吻合。”
首先《新闻晚报》的报道中引用的证言来自可识别的、署名信源,即燃料加注员刘华宾。其次,燃料加注员是这一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核查者假设他熟知燃料中所含物质,这就提高了该信源的可信度。并且,燃料加注员在采访中对燃料加注过程的描述非常具体、形象,也加强了该证言的可信度。故核查者选择判定该证言可信。
核查者在分析证据时还经常会碰到互相矛盾的证据。当证据链不完整或证据之间自相矛盾时,核查者在采集证据时应尽量获取一手信源,即证据最初的提供者。有时该宣称没有提及任何信源,只是言说者所作断言,这时核查者往往需要自行搜集公开证据来验证该断言是否符合事实。比如在上述关于乌兰巴托雾霾程度的报道中,一则宣称指出:“民众只要离开乌兰巴托就可重获蓝天白云。”作者对这则宣称未提供任何信源和证据,核查者自行查阅了蒙古国家气象和环境监测部网站上公开的蒙古21个省份的空气质量指数。经比对后发现,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省份PM10数值超标。以此判定,民众即使离开乌兰巴托也不能摆脱空气污染的困扰。
在证据相左时,可识别信源具有优先权,而完全无迹可寻的信源在评判时的权重则相对较低。比如,在《红黄蓝事件十大疑云》稿件中,有一则不明信源的网传家长投诉称:“有小孩在医院查出肛裂。”经溯源,提出这一说法的信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北京青年报》的一则采访视频中一位男性家长说出此话,但是他并非该信息的第一手信源,而是转述他人的发言,他在视频采访中表示:“听说有孩子到医院做检查,确定是肛裂,但原因不明。”至于他是从何处听说这一消息则无迹可寻。无独有偶,另一个说有孩子在医院查出肛裂的,也是一个网传家属投诉。这些线索均无法追溯信源,因此也无法识别其信源可靠性,所以,核查者判定该消息“不太可能”。
(三)呈现事实:遵循透明性原则
核查者是通过新闻文本将核查结果呈现给公众的,因此事实核查能对公众产生怎样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呈现判定的结论。一开始,核真录借鉴PolitiFact的方式,制定了五点“核真指数”量表,为每一则核实的宣称打分,后来核查者逐渐发现大量判定都无法以指数高低来表示。首先,许多判定都因无法追溯信源、缺乏证据而只能判定为“不确定”。第二,同样分值的宣称可能存在不同的问题。比如有的是断章取义,有的是误读,有的是夸大其词,有的是文图不符。以同样的分值来呈现判定结果反而有可能使读者误读结论。第三,更直接的原因是,不同的核查者在打分时无法保持一致,严重损害了打分体系的可靠性。故后来核真录的所有判定都以文字论证方式呈现,不再打分。
而文字呈现判定结果需遵循透明性原则,即通过直接披露新闻生产过程来报道新闻。一些学者认为,“透明性”正在成为,也应该成为新的新闻伦理(Karlsson, 2010; Phillips,2010)。在传统新闻报道中,记者为了体现不偏不倚而让自己尽量置身事外,避免让主观判断影响对事实的呈现,但这种置身事外本身并不能保证记者报道的是事实。比如,权威信源所作宣称对于大多数记者来说都是一个“黑箱”,记者们不知道权威信源是依据什么证据得出结论的。而记者把这些宣称转述给读者时,读者更缺乏能力来判断这一宣称是否可靠。又比如,在有争议的事件中,如果争议双方的宣称都偏离事实,那么只是罗列各自的宣称,而不对信源可信度和宣称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则会使读者更不清楚究竟何为真相。
相对来说,事实核查不要求核查者置身事外、保持中立,相反,它对事实准确性的判定本身就要求核查者作出主观判断。也正因如此,事实核查容许——甚至要求——核查者在作判断的过程中积极发挥自主性。尽管判断具有主观性,但若它要对受众产生影响,使核查者的主观判断成为读者认可的、共享的判断,就要使该判断能被读者理解、采纳,并接受公众对其判断可靠性的问责。这里的“理解”不单是指让读者了解其判断了什么,更要让读者了解核查者是如何得出判断的。这样,受众可以通过评估得出判断的过程来评估该判断是否可靠。
因此,基于公共问责的原则,核查者需要向公众披露其判断的全过程。首先,核查者需明确告知读者,他们依据哪些证据作出判断。哪些证据是核查者自己采访获得的?哪些是从其他信源获得?原则上来说,文章中出现的每一则证据都需进行信源追溯,以确保每一则证据都能被归因于一个具体的、可识别的信源。
第二,核查者还需向读者披露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比如在“红黄蓝幼儿园”的案例中,关于孩子是否被检查出肛裂,文章中写道:“我们可以在多个家长视频、聊天记录中看到,有听说孩子被检查出肛裂。但是鉴于该说法目前的来源均为幼儿家长,暂时还未发现其他信息来源,并且所有发布该信息的家长,都并非自己的孩子有此症状,而是从别人处听来,其准确性难以查证,因此我们认为该消息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否为实情仍然有待进一步查证。”
这段文字中,核查者没有将从家长视频和聊天记录中得到的证据当作假定的事实来报道。相反,核查者披露了自己的推理过程,分析该证据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解释了该证据可信度存疑的原因。这种写作方式不但告诉读者核查者获得了什么证据,更提醒读者应如何评估、使用该证据。
通过披露推理过程,核查者也允许读者检查其推理过程中出现的逻辑谬误。事实上,读者经常在评论回复中指出核查者的推理错误。这看上去是将自己的弱点暴露给读者,但增强透明性也体现了核查者的诚实和真诚,以及愿意对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并接受公众问责的开放态度(Phillips, 2010)。
第三,核查者还需向读者披露其核查过程与结论的缺陷。在传统新闻报道中,记者往往很少在文本里袒露证据和结论的缺陷,而是假设自己所记录的就是真实的。因此,一旦报道被揭露与现实不符,记者往往受到攻击而无法为自己辩护。通过向读者提前预警可能存在的漏洞,核查者也能更好地对潜在批评者作出回应(Graves, 2017)。
四、结语:开放的探索
在实用主义观念里,民主的重要特征是科学与民主过程的紧密联系(Bohman, 1999)。它既要求负责任的机构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和理性管理来解决社会问题,也要求公众能够以求知、探索的精神参与公共事务。在约翰·杜威看来,民主是一种社会探索(social inquiry),它的运行依赖并整合社会的认知劳动分工(cognitive division of labor)(Bohman,1999)。然而,在这一分工体系中,知识精英与公众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公众往往无法掌握专家运用的知识,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去评估专家说的对不对。虽然前所未有的传播技术发展使得新闻知识生产愈发民主化,但也使得掌握这些技术的人和机构能更便利地制造虚假信息、操控舆论(Reilly, 2018)。而原本旨在为公众提供有关公共事务知识的新闻业,又正在失去生产可信知识的能力,陷入了“认识论的危机”(epistemic crisis)(Steensen,2019)。在此背景下,公众能够如何参与公共生活,以及如何与政治、商业、科学精英展开基于共同认识论基础的对话呢?
事实核查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假定如果通过更科学的方法探索事实,至少部分人是有可能对复杂而模糊的公共议题形成更接近现实的判断。作为一种特征清晰的新闻实践,它继承了传统调查性、解释性报道的认识论和探索方法,它独特的新闻文本呈现为公共讨论增添了一种声音、一种力量。
首先,事实核查实践开创了一个新的新闻表达形式。这是一种更接近于甘斯(Gans,2004)所说的,类似社会科学通过实证探索获得的新闻产品。为了核查事实性,核查者既要运用传统新闻活动中的采访技能,有时也需使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步骤,如文本分析、数据挖掘等。从认识论上来讲,事实核查与传统调查性报道一样,都不轻信政治、经济、文化权威提出的证言,而把对现实的判断建立在“事实网络”的互相佐证上。在如今人人皆可成为媒体人的情况下,个人、机构都可通过自媒体来为各自的利益服务,使得策略传播大行其道。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重申经验主义的事实观和方法论也是新闻业巩固其“认知权威”的基础,具有新闻业自身重建正当性(legitimacy)的意义。
第二,事实核查实践向读者呼唤并示范了一种开放的认知动机(epistemic motive),即悬置判断、容忍不确定但坚持探索事实的思考模式(Kruglanski & Webster, 1996)。事实核查要求人们建立一种判断悬置的意识,在缺乏证据时不妄下确切的结论。从对核真录这一案例的分析来看, 事实核查实践产出的新闻知识是核查者对事实准确性得出的尝试性的、暂时的结论,体现核查者的个人选择、推理、判断。这一判断允许容纳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它有可能是一个对真实性的明确判定,也有可能只是告知读者哪些是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基于这一认识论框架呈现的新闻文本也体现了核查者重视建立互相佐证的事实网络。如果一件事尚缺乏足够的证据去判断真假,那么给出“不确定”的判定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这种文本形态能够培养核查者和读者双方都形成与之相应的思考模式。
第三,事实核查遵循的透明性原则还将新闻实践本身变成公共讨论的对象,使个体公民可以参与到探索事实的过程中来。事实核查新闻将新闻知识的获取、生产、加工过程转向前台。对公众而言,核查者得出结论的过程不再处于黑箱中。相反,它邀请公众依据核查报道的文本呈现来讨论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判定事实的共识标准;也邀请公众参与补充证据,探寻证据相互间的逻辑关联,以证据为基础共同搭建事实网络。而在补充证据、裁定事实性的过程中,个体公民也需受此认识程序和步骤的制约,并尊重据此模式获得的认知权威。正是基于对新闻实践本身的公共讨论,使得公众即使在复杂的公共议题上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也可与各种知识权威展开对话,探讨如何建立事实可靠性、证据契合性的认知规范(Bohman, 1999)。
而作为支撑公共生活的重要机构,专业新闻机构理应吸纳事实核查的理念和实践,成为它的践行者、示范者、阐释者(潘忠党,陆晔,2017)。作为践行者,专业新闻媒体有其他组织(如核真录)和个人不具备的权限和资源,因此他们也掌握其他行动者不具备的独有的核查能力。作为示范者,专业新闻媒体的传播广度与深度使其更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文本呈现向受众展示如何理性思考、如何探索未知。作为阐释者,新闻从业者也应反思自己的新闻实践,在其日常业务探讨中更多发起、参与关于如何确证事实、呈现事实的讨论,并且更多地向公众解释其报道是依据怎样的证据搜集过程和推理步骤得出结论的。
最后,核真录近三年的事实核查实践也为学界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提出新的实证问题。核真录的报道旨在帮助公众厘清事实准确性,纠正对虚假信息的错误认知。那么作为被监督对象之一的新闻媒体又是如何看待事实准确性的呢?在记者的日常新闻实践中,他们如何追求准确的信息?而公众对于准确的事实又有何看法呢?事实核查者的努力会影响公众对核查机构的态度以及对公共事务的认知吗?在核真录的实践中我们还发现,当读者不认可稿件中的推理方式和结论时,他们会考虑到学生能力有限,而宽容可能出现的误判,也更愿意相信他们没有被利益或其他不良动机驱使。那么当专业新闻机构在核查事实时得出误判,读者对这些专业新闻机构及其核查活动又会持何种态度呢?这都是此文留给我们继续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4)。《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忠党,陆晔(2017)。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10),6-39。
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BergerP. L.& Luckmann, T. (199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o. 10). USA: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BohmanJ. (1999). Democracy as inquiryinquiry as democratic: Pragmatism, social scienceand the cognitive division of lab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3(2)590-607.
Edelman, M. (2001). The politics of misin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ttemaJ.& GlasserT. (1987). On the epistemology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M. Gurevtich & M. Levy (Eds.)Mas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6). London, UK: Sage.
Fricker, E. 1994. Against Gullibility. In B. K. Matilal& A. Chakrabarti (Eds.)Knowing from words: Western and India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understanding and testimony (pp. 125-162). Dordrecht: Kluwer.
FullerS. (1987). On regulating what is known: A way to social epistemology. Synthese, 73(1)145-183.
GansH.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Gelfert, A. (2010). Kant and the Enlightenment’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epistemology. Episteme, 7(1)79-99.
GodlerY.ReichZ.& Miller, B. (2020). Social epistemology as a new paradigm for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 Society22(2)213-229.
GravesL. (2016). Deciding what’s true: The rise of political fact-checking in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ravesL. (2017). Anatomy of a fact check: Objective practice and the contested epistemology of fact checking. 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 10(3)518-537.
JamiesonKH.& WaldmanP. (2003). The press effect: Politiciansjournalistsand the stories that shape the political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rlssonM. (2010). Rituals of transparency: Evaluating online news outlets’ uses of transparency ri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Sweden. Journalism studies11(4)535-545.
KerseyT. (2018). Constrained elitism and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KruglanskiA. W.& WebsterD. M. (1996). 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2)263.
Lau, R. W. (2004). Critical realism and news production. MediaCulture & Society26(5)693-711.
LemannN. (2006). Amateur hour: Journalism without journalists. The New Yorker, 7(8)006.
MathesonD. (2004). Weblogs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news: Some trends in online jour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6(4)443-468.
Nyhan, B.& ReiflerJ. (2010).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32303–330.
Parasie, S. (2015). Data-driven revelation? Epistemological tensions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 Digital Journalism, 3(3)364-380.
PhillipsA. (2010). Transparency and the new ethic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4(3)373-382.
ReillyI. (2018). F for Fake: Propaganda! Hoaxing! Hacking! Partisanship! and Activism! in the fake news ecolog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41(2)139-152.
SchudsonM. (1981).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udsonM. (1991).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141-159). London: Edward Arnold.
SteensenS. (2019). Journalism’s epistemic crisis and its solution: Disinformation, datafication and source criticism. Journalism, 20(1)185-189.
UscinskiJ.& Butler, R. (2013). The Epistemology of fact checking. Critical Review, 25(2)162-180.
ZengJ.BurgessJ.& BrunsA. (2019). Is citizen journalism better than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for fact-checking rumours in China? How Weibo users verified information following the 2015 Tianjin blasts. Global Media and China4(1)13-35.
郑佳雯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感谢潘忠党教授在此文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