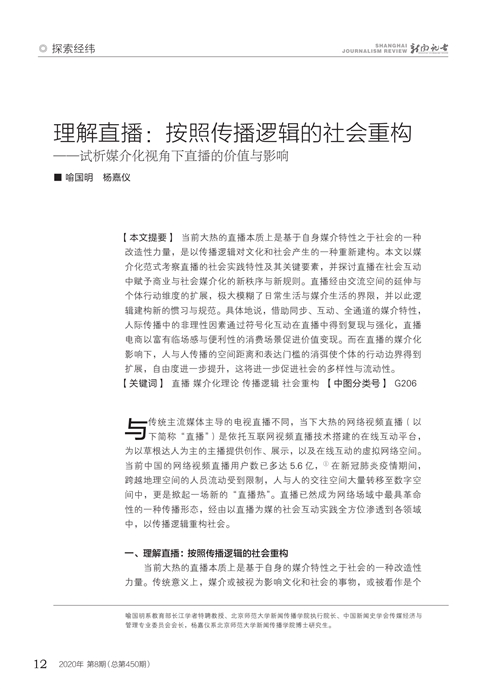理解直播:按照传播逻辑的社会重构
——试析媒介化视角下直播的价值与影响
■喻国明 杨嘉仪
【本文提要】当前大热的直播本质上是基于自身媒介特性之于社会的一种改造性力量,是以传播逻辑对文化和社会产生的一种重新建构。本文以媒介化范式考察直播的社会实践特性及其关键要素,并探讨直播在社会互动中赋予商业与社会媒介化的新秩序与新规则。直播经由交流空间的延伸与个体行动维度的扩展,极大模糊了日常生活与媒介生活的界限,并以此逻辑建构新的惯习与规范。具体地说,借助同步、互动、全通道的媒介特性,人际传播中的非理性因素通过符号化互动在直播中得到复现与强化,直播电商以富有临场感与便利性的消费场景促进价值变现。而在直播的媒介化影响下,人与人传播的空间距离和表达门槛的消弭使个体的行动边界得到扩展,自由度进一步提升,这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多样性与流动性。
【关键词】直播 媒介化理论 传播逻辑 社会重构
【中图分类号】G206
与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电视直播不同,当下大热的网络视频直播(以下简称“直播”)是依托互联网视频直播技术搭建的在线互动平台,为以草根达人为主的主播提供创作、展示,以及在线互动的虚拟网络空间。当前中国的网络视频直播用户数已多达5.6亿,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跨越地理空间的人员流动受到限制,人与人的交往空间大量转移至数字空间中,更是掀起一场新的“直播热”。直播已然成为网络场域中最具革命性的一种传播形态,经由以直播为媒的社会互动实践全方位渗透到各领域中,以传播逻辑重构社会。
一、理解直播:按照传播逻辑的社会重构
当前大热的直播本质上是基于自身的媒介特性之于社会的一种改造性力量。传统意义上,媒介或被视为影响文化和社会的事物,或被看作是个人和组织可加以利用,从而实现不同用途和目的的手段。但当直播这样具有革命性改变的媒介形态渗透至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时,我们不应再将其视为与文化和社会机制相互分离的技术,而应将其理解为与其他社会范畴相互建构的结构性力量。
直播作为媒介技术,何以产生社会性的建构力量?作为媒介,直播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它打破了围观与参与表达的界线,直至直播出现且普及后,以一对多、乃至多对多方式进行即时可交互传播才成为每一位普通网民都能拥有的权利;另一方面,直播极大丰富了场景的构成形态与功能属性,构建了未来消费和生活的种种新场景。正是凭借自身简单而特别的媒介技术逻辑,直播引发了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经由媒介交往和发生关系之模式的变动,使得直播本身的媒介形式作用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意义远胜于其传播的内容,甚至直接出现媒介所造就的行动场域与社会场域(胡翼青,杨馨,2017)。例如在社会表达方面,以草根为主体的直播形式颠覆了传统视频中原有的精英阶层与组织化传播的表达,受众开始以自身的价值维度重新定义什么内容更值得关注;在商业形态方面,直播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与营销模式,成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拉力和传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因此,无论是社会整体表达渠道与媒介使用习惯的转变,还是传统产业与“直播+”的业态再造,从宏观上看,直播对整体社会形态、关系规则、实践逻辑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媒介技术逻辑的普适性影响(莱克维茨,2019:233),直播加入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人类主体以直播开展实践,与之产生个体关系,并以直播的传播逻辑建立关系。在此基础上,直播这一数字技术拥有了塑造社会的力量。
直播以传播逻辑进行的社会重构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化(mediatization)影响,即由于媒介影响的增长,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互动模式发生了变化(Hjarvard, 2008)。这种广泛性影响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媒介化理论视角来理解:从技术主义的视角来看,直播有其互动、同步的技术特性,其本身的空间概念也具有物质的一面,通过它,文化实践与日常生活得以物化(Lundby, 2014:11),这是大众表达与行动空间得以拓展的重要前提。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直播以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的制度形态出现,在直播所塑造的社会行动场域中,一切表达和关系建构的逻辑都要遵循直播的逻辑来展开,遵循其界定、选择、组织、呈现其内容的法则(Altheide & Robert, 1992:468),这是直播重塑各领域实践规则的基本原理。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直播场域中的要素成为社会现实框架的组成要件,在特定结构中扮演社会交往的资源,使社会能动地再生产与变化,对社会产生“制度性”影响;另一方面,直播作为新的传播手段,基于社会建构的传统,即“人可以使用媒介改变社会”的建构方式,为改变人类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可以说,直播作为一种媒介技术,它对个体与社会各个领域的颠覆,亦是以自身技术特性、传播逻辑与社会结构性作用力进行的一场社会的“媒介化重塑”。
在直播技术弥散的社会中,考察直播是如何制度化地嵌入社会关系建构及个体日常生活互动,以及关注无处不在的直播影响下,社会机制和文化进程的特性、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显得尤为重要(戴宇辰,2018)。具体而言,从媒介化影响的视角理解直播,强调直播作为实践制度,而非单纯中介化作用的一面,应当先回视直播如何改造、以何种要素改造了社会实践,再探究在直播媒介化影响下不同社会领域的实践规则变化,才能观照直播和人共同构造的社会现实,理解直播真正的影响与价值。
二、直播的媒介化社会实践:延展、替代、融合与适应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媒介使用一次次重塑个体之间的互动模式,更新知识被社会接受和传播的方式(克劳利,海尔,2011:388-389)。人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是一切社会实践的基础,因此,一种新媒介技术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改变信息传播方式,我们更要看到基于信息交流的各类社会实践在新媒介影响下发生了何种变化。
直播带来了一种新的视频化的生存方式(彭兰,2020),在直播技术的使用实践中,与直播相关的社会实践产生了新的需求指向、规律性惯习以及社会性秩序。这种社会实践的转向大致与舒尔茨(Schulz)所述由媒介承担关键角色之社会变革的四个方面相一致。他将媒介化与传播媒介及其发展所带来的变革联系起来,提出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沟通能力、代替先前面对面的社交活动、通过融合逐渐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使参与者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媒介的形式特征与惯例的四种媒介化社会实践影响(Schulz, 2004)。正是基于延展(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与适应(accomodation)的社会实践特性,直播通过影响受众的行动、流通的意义与形成的制度,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一)延展:直播延伸交流空间
直播在空间维度延展了个体交流的线上场域。便携式上网设备与即时通信传播的普及使人的传播行为不再受时空界限的制约,但不同特性的媒介对交流实践场域扩展的维度是不同的。伊尼斯(Innis)将媒介区分为“空间偏向”与“时间偏向”两种类型,时间偏向是指使信息能够在时间维度上传递得更远,而空间偏向是指能够改变信息空间运动(伊尼斯,2017:103)。直播无疑是一种空间偏向的媒介技术,尽管它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存储、回放的形式保留信息,但直播真正的实践价值在于,它将信息空间延伸为日常行为的空间,将原本的沟通传播空间展开,用“上线”与“在场”赋予线下空间新的传播实践价值。普通的即时通信也能够延展个体传播的空间,但直播将个体传播的情境和场域以尽可能全面的方式,同步复现到直播平台的方寸荧幕中,将全量级、无时限的传播空间以一对多的形式延伸至每一个观看者的个人空间里。在延伸后的空间中,信息并不是单向度传播的,直播中的传受双方以互动的形式进行信息往来,这种同步性只有在交流空间互连后才得以实现。
(二)替代:直播扩展个体行动维度
直播扩展了个体行动的“现实场”与“虚拟场”。借助交流空间的延展,直播使个体在不同空间中的“行动”更加容易。正如戈夫曼(Goffman)所述,交流与互动就像舞台上的表演,参与者在交流互动中寻求达成对当前情境的一种共识(戈夫曼,2008:5)。直播之下的身份与现实也许限制了个体的实践,但走上直播的“前台”,个体行动的维度被大大拓宽了。通过辅助不同情境下的前后台转换,甚至以直播替代原有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机构,直播赋予个体行动更多可能性,这也是“直播+”能够与传统行业结合的重要原因。
一般来说,媒介化可以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Hjarvard, 2004:43)。而直播对个体行动维度的扩展显然是一种直接媒介化影响下的实践转向,即先前的非媒介化活动可以借助直播转化为媒介互动来完成。例如将即时性的表演从舞台搬上直播,将广告营销与销售活动从线下转移到电商直播中,都是将原有的活动转化为媒介中的互动来实现。原本受空间限制而无法完成的行动可以借助直播来完成,在展开的交流空间中获得更广泛的行动意义,这对提升个体在社会中的实践自由度大有裨益。
(三)融合:直播日常化模糊生活与媒介的界限
渐渐日常化的直播使线下生活与媒介生活的界限不再分明,这种广泛的媒介融合是直播技术撬动原有实践逻辑、使社会实践改变的基础。媒介化视角的一个核心出发点是:媒介日益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夏瓦,2018:21)。而当直播逐渐与日常生活相互渗透融合,甚至模糊了生活与直播的界限时,社会实践的媒介化转向也更加突出。一方面,直播渗透到原本日常生活的专业化领域中,个人工作、交往、购物等行动场域部分转移到线上直播,受众渐渐习惯自己的陪伴需求、娱乐需求、自我展露需求等借由直播来获得满足。例如原本的购物从网购又转化为“看李佳琦的直播”;再比如疫情期间,“上课”自然而然成为“上网课”的代称,直播渐趋日常化使线下生活与媒介生活的区隔逐渐模糊。另一方面,个人日常生活在直播中公开,部分直播主甚至将线下生活向网络空间中的观者进行无保留展示,把一些原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私人的行为搬到直播中,例如直播在浴室中唱歌、连麦进行与爱人的真心话大冒险,这些行为背后体现出的不仅是个人在互联网上表达欲、表达权的扩大,还有直播参与者、观看者对直播中生活化展现的习以为常。在他们看来,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在直播中并非泾渭分明,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延伸到媒介中,而媒介实践亦是生活日常的一部分。
(四)适应:直播塑造新的惯习与规范
直播日常化使用促进了新的惯习与规范体系的形成。当原有的社会互动行为被直接媒介化为媒介互动,受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接受行为、规范也将随媒介的技术逻辑发生改变。当惯习的改变发生,媒介的存在感与重要性日益增强,各种不同专业领域的组织或者个人必须依照媒介操作信息的方式进行互动,人们更愿意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媒介逻辑(周翔,李镓,2017)。
首先,直播塑造了媒介日常化使用的惯习,受众将直播纳入自己原有的“媒介菜单”,形成了新的媒介使用习惯,直播成为习以为常之事。甚至有人将直播作为固定的工作,以此为自己创造收入。其次,在不同的实践领域中,“直播+”
结合原场域中的社会行为规范生成了新的不成文规约。这当中既有互动的规范,也有仪式性的规则。在直播平台中,使用者通过特定的话语、行为将人际互动符号化,生成共性的对话框架,参与对话者则以共识性的规范指引自己的互动行为。例如直播中惯用的沟通话语:“宝宝”、“点亮小心心”等,就是直播特有对话规范的具体表现。社会大众亦会主动去适应规范,培养自身的使用习惯。有人试图以直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资本的积累,有人通过直播寻找陪伴感,这些与大众对直播的媒介化“适应”不无联系。而这种“适应”,也是直播作为媒介技术,对每一个基于直播展开行动的个体之实践逻辑、规范与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三、直播媒介化社会实践中的关键要素:同步、互动、全通道
直播平台是基于互联网运作的媒介,其技术可供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本身连接、无时、无域的技术特性。但直播平台的信息流通方式构造了一种新的媒介沟通情境,依托同步、互动、全通道的媒介特性,直播才得以生发出变革性的媒介化社会影响。
(一)同步性沟通满足即时交流需求
“同步性”指的是沟通双方话语轮次的时间间隔,当个体表现出具有共同关注点的、协调一致的行为模式时,他们之间就存在同步性(Herring, 2003)。直播媒介创造了一种沟通双方以及众多他人同时在场、同步交流的状态。这种信息流通方式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沟通情境:参与者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同时交流成为可能(张丽华,骆世查,2019)。同步性媒介具有即时反馈的特性(Swaab et al.,2012),有学者认为即时反馈是影响沟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Dennis & Valacich, 1999),这似乎不需要证明:几乎没有人喜欢缓慢的网络、反应迟钝的通讯设备以及不回消息的朋友。
对于信息传播效率的追求,使得媒介进化合乎逻辑地走向了人性化的动机,即“可以用日益逼真和完美的方式表达的、可以传播的现实的图像”(莱文森,2003:177-178)。直播是所有即时通讯工具中能够尽可能满足同步性沟通需要的媒介技术之一,基于同一种感知速率与交往节奏,传受双方才拥有了即时沟通与互动的基础。电商直播主可以回答顾客的问题,泛娱乐直播主可以针对观众喜好决定表演项目,生活类直播主甚至可以与参与直播的观看者聊天,这是其他媒介技术暂时无法完全替代的独特技术优势。
(二)互动性交流实现跨屏实时联动
直播的同步性沟通让互动性交流成为可能。戴扬在评价电视直播时曾说:电视直播事件之所以产生相应效果的秘密就在于观众从别的机构带来的、使被动观看变为仪式参与的角色(戴扬,卡茨,2000:13-17)。而现在的网络直播技术通过同步性传播,为受众的仪式参与提供了更便利的技术条件与更宽阔的交流场域,且相对于原本的电视直播来说,这种交流场域是可移动、不为特定技术空间所限制的。直播具有互动仪式链的四个要素:两个或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对局外人设置一定界限、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分享共同的情绪体验,而这种可以即时交流的情感亦成为互动仪式的驱动力。观看者在这个时候不再是被迫接受信息的受众,他们充分拥有了选择性体验、参与乃至影响“直播内容”的权利。即网络直播打破了时空限制的壁垒,实现了一场跨屏互动(王艳玲,刘可,2019)。
直播平台可互动性的意义在传受双方均有体现。直播主通过观察受众在直播中的即时反馈(如弹幕、刷礼物),可以及时调整自身行为;借助直播平台的功能可供性,受众从接收信息到做出行动决策的速度大大提升,很容易实现对直播主的行动“响应”。例如打赏直播主,或在电商直播中付诸购物行为,都是借助直播平台的可互动性实现的。这种双向可互动的交流方式勾连了本无瓜葛的一个甚至多个空间,实现了不同物理空间的同步跨屏联动。
(三)全通道传播复现实际交流中的整合性信息
直播是一种尽可能复现面对面交流场景的全通道传播媒介。这种原始的交流方式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人只有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才能建立起强烈的团结意识,“亲身在场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能够发出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从而达到主体间性状态”(柯林斯,2012:105)。这表明了面对面传播场景的优势:这是一个由大量非语言符号、理性与非理性信息交织组成的富媒介传播环境。也许我们无法梳理出所有的信息种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最完整、最全面的信息交流方式。莱文森所指媒介演进的人性化趋势,亦强调将信息传播逐步转化为有温度的信息体验过程(莱文森,2001:73)。直播作为模仿面对面互动的媒介技术,不仅是其替代品,更拓展了面对面交流的场合。可以说,直播中的交流是一种人性化、全通道的传播。
直播作为一种全通道传播的媒介技术,其独特性在于尽可能保留了面对面交流场景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往的传统媒介更注重理性表达与逻辑传播,但在直播中,非理性与非逻辑的内容以符号化的形式被尽可能保留下来,促进传播中的关系认同和情感共振。这种非理性因素的复现在文字中可能比较难,且不具有近似人类社会交流的社会临场感(Hassanein & Head, 2007)。可在直播这一媒介内,传播内容情感属性可以透过表情、声音、语调等非语言符号放大表露,正如麦克卢汉(Mcluhan)所说,“技术的效果不在意见或观念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却逐渐地改变了感官作用的比例(sense ratios)或理解的形式”(Griffith,Seidman & Mcluhan, 1968)。直播扩大了非理性因素作用的比例,对受众的情绪调动与行动促进甚至有超过事实表达和理性表达的趋势(喻国明,耿晓梦,2020)。
四、直播媒介化影响下的各领域实践规则重塑
媒介不仅仅描述世界,更提供了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Couldry, 2012:21)。这种结构性的媒介化作用力并非来自传播链条的完全重构,而是来自对符号形式的重新解读和整合(夏瓦,2018:18)。经由交流空间的延伸与个体行动维度的扩展,直播极大模糊了日常生活与媒介生活的界限,并以此逻辑建构新的惯习与规范。在直播的媒介化影响下,一些传播中原本重要的因素变得比较次要,而一些不起眼的操作成为个体行动转变甚至社会整体性变化的重要“启动器”。具体而言,直播以自身的传播逻辑,在媒介化社会实践中重塑了传播、商业与社会的实践规则。
(一)传播:以非理性因素的符号化运用,实现关系与情感的线上回归
视频表达是一种宽信息容量的表达,传播的情感和关系属性在视频表达中被放大,而同步沟通、即时互动的视频直播更能够引发关系认同与情感共鸣。
在直播中,有两种传统媒介内容中难以展现的非理性因素被符号化应用到传受双方的互动里。一是关系感知。沟通的亲密性研究指出人际关系从疏离到亲密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事实性基础与情感性基础。直播主以特定的称谓或语言反馈拉近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距离,例如观看者不是观众,是我的“宝宝们”;购物者不是顾客,是我的“所有女生”。他们用朋友、知心人的口吻,以一种高密度的信息反馈节奏模拟真实的交往情境,快速建立亲密沟通的事实与情感基础。二是情感共振。直播主以丰富的表情、动作作为情绪调动的自然符号,通过直播中的视觉营造、打赏、对话等符号化的互动方式,在不间断的围观与直播互动中强化群体情感,使受众沉浸其中,产生强大的情感动员力量(汪雅倩,2019)。莱文森说,只有满足人类感官平衡的媒介形式才能在媒介生态中有立足之地(常江,胡颖,莱文森,2019)。直播将非理性因素符号化置入传播场景中,正是在满足受众感官平衡的同时实现了关系与情感的线上回归。
(二)商业:以人性化逻辑构建兼具临场感与便利性的消费场景,实现价值变现
在琳琅满目的“直播+”商业模式中,电商直播成为第一个业界爆点。电商平台以直播的方式将营销与零售整合一体化,搭建媒介化消费场景,让受众向消费者的转化更加顺畅。
一方面,直播为电商塑造了一个独具临场感的消费场景。在电商直播场景中,传统消费场景的四个重要因素被保留下来,即买方、卖方、商品与周边信息。卖方以符号化的表达将真实消费场景复现,结合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进行广告劝服。而作为周边信息的其他参与者让这一消费场景具有更强的消费临场感。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理论指出他人临场会对个体产生唤醒作用,进而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Kushnir, 1981);根据口碑线索做出从众购买决策有可能受到他人临场的作用而被更大程度地激发(Walters & Long, 2012),这种外部的信息性影响能够正向干预受众的行动选择(Quiamzade & L’Huillier, 2009)。因此,直播中他者参与所营造出的临场感是价值变现的有效催化剂。
另一方面,直播为电商提供了极富便利性的媒介工具。根据施拉姆的选择或然率公式,信息或媒介被人们注意和选择的可能性与它能够提供给人们的价值程度成正比,与人们获得它的费力程度成反比(施拉姆,波特,2010:106)。直播这一媒介技术应用在电商销售中,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又能够帮助双方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首先,电商直播以人为主要的广告营销载体,通过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劝服方式,快速强化传受双方的关系纽带,建立起充分的认同感与信任感。在此基础上直播主的推荐更容易让消费者“买账”,跟着直播主的推荐来购物降低了消费者的选择成本,还能够获得特殊的团购折扣,消费者自然更愿意下单。其次,电商直播缩短了买方从接触营销信息到做出购买行动的决策距离,直播同步性互动的特性让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流更便利,无论消费者对商品有什么疑惑,都可以即时沟通咨询。挂靠在直播页面中的快速购买通道让消费者网上下单更加方便,卖方亦可以根据销售数据的反馈,及时调整库存配置与营销策略。可以说,直播以人性化逻辑构建了具有临场感与便利性的消费场景,赋予了商业生态一种新的交换与售卖规则。
(三)社会:以传播空间距离与表达门槛的消弭扩展个体行动空间,提升社会流动性
任何增加社会流动性的传播形态和技术形态,都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对于直播而言,从传统媒体价值来判断,最初兴起时似乎有些粗糙和无趣,也缺乏必要的规则,然而从新的社会价值坐标系来说,直播技术消弭了传播的空间距离与表达门槛,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喻国明,2017)。
一方面,直播打破了公域与私域之间的藩篱,缩短了围观与表达之间的距离,更给予受众被看见的可能。直播即上即播的使用方式比需要剪辑配乐的短视频更为普世化,将普通受众的表达门槛降到了最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表达的能力,但简单易用的直播平台更帮助他们行使了被看见的权利。在“沉默的大多数”都能发声的情况下,人们才能看到世界更丰富、更多元的一面,这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多样性与包容度。另一方面,直播延伸了交流空间,拓展了主体的行动维度。基于广泛的群众基础,已然日常化的直播表达对个体行动空间的延伸提供了便利。2019年全年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营收规模由2018年的495.5亿元增至668.5亿元,②产业飞速发展的背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通过直播就业实现个人价值。作为媒介技术,直播拓展了人的连接方式和表达空间,扩大了个体自主选择权,提升了个体行动的自由度,这也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多样性与流动性。
五、结语
直播是一种兼具可用性与易用性的媒介技术,随着直播用户数的爆发式增长,直播对个体互动及文化社会的广泛影响愈发不可小觑。我们认为,直播的影响是一种媒介化的社会影响,是直播技术以自身传播逻辑对社会各个层面展开的建构。经由交流空间的延伸与个体行动维度的扩展,直播模糊了日常生活与媒介生活的界限,塑造出新的惯习与规范;直播的同步性、互动性、全通道传播,满足了受众的即时传播需求,也为非理性因素效能在传播中的释放提供了技术渠道。在此基础上,直播进一步重塑传播、商业与社会中的实践规范,以符号化互动放大非理性因素传播效果,借助临场感与便利性促进消费变现,以个体表达门槛的消弭和传播空间的连接促进社会多样性与整体流动。
当视频化生存逐渐成为常态,直播将如何形塑大众行为,建构何种新的实践场景与社会文化?以媒介化范式理解直播应用中人类实践的变化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是一个较为恰当的视角。技术是动态发展的,本文站在“迄今为止”的时间节点,横向剖析直播的媒介化社会实践、特征要素与具体影响。未来研究可从纵向观察的视角,进一步分析直播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动态现象与关系。■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②数据引自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2020)。《中国网络表演(直播)市场发展报告》。
参考文献: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2019)。《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保罗·莱文森(2001)。《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保罗·莱文森(2003)。《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常江,胡颖,保罗·莱文森(2019)。媒介进化引导着文明的进步——媒介生态学的隐喻和想象。《新闻界》,(2):4-9。
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2011)。《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董璐,何道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戴宇辰(2018)。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47-156。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欧文·戈夫曼(200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翼青,杨馨(2017)。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缘起:传播学视野中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新闻大学》,(6),96-103+154。
哈罗德·伊尼斯(2017)。《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兰德尔·柯林斯(2012)。《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彭兰(2020)。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中国编辑》,(4),34-40+53。
施蒂格·夏瓦(2018)。《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李鑫,漆俊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汪雅倩(2019)。新型社交方式:基于主播视角的网络直播间陌生人虚拟互动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87-93+72。
王艳玲,刘可(2019)。网络直播的共鸣效应:群体孤独·虚拟情感·消费认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26-29。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2010)。《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喻国明(2017)。从技术逻辑到社交平台:视频直播新形态的价值探讨。《新闻与写作》,(2),51-54。
喻国明,耿晓梦(2020)。未来传播视野下内容范式的三个价值维度——对于传播学一个元概念的探析。《新闻大学》,(3),61-70+119。
约书亚·梅洛维茨(2002)。《消失的地域》(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丽华,骆世查(2019)。同步性中的“存在感”:经由直播媒介的人际交往与日常生活。《新闻与传播评论》,(4),64-77。
周翔,李镓(2017)。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4),137-154。
AltheideD. L.& Snow, R. P. (1992). Media logic and culture: Reply to Oak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and Society5(3)465-472.
Couldry N. (2012). Mediasociety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21.
DennisA. R.& Valacich, J. S. (1999January). Rethinking media richness: Towards a theory of media synchronic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Sciences. 1999. HICSS-32. Abstracts and CD-ROM of Full Papers (pp. 10-pp). IEEEGriffith MSeidman EMcluhan M.(1968)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19(1): 69.
Hassanein, K.& Head, M. (2007). Manipulating perceived social presence through the web interface and its impact on attitude towards online shop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65(8)689-708.
Herring, S. C. (2003September). Dynamic topic analysis of synchronous chat. In New research for new media: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symposium working papers and readings (pp. 47-66).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Hjarvard S. (2004).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Bristo: Intellect Books43.
HjarvardS. (2008).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29(2)102-131.
Kushnir, T. (1981). The status of arousal in recent social facilitation literature: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assumptions implied by the current research model.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9(2)185-191.
LundbyK. (Ed.). (2014).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Vol. 21).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Quiamzade, A.& L’HuillierJ. P. (2009). Herding by attribution of privilege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2(1)1-19.
SchulzW. (2004).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1)87-101.
Swaab, R. I.Galinsky, A. D.Medvec, V.& DiermeierD. A. (2012). The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 model: Explaining the diverse effects of sightsoundand synchronicity on negotiation and group decision-making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1)25-53.
Walters, A.& Long, M. (2012). The effect of food label cues on perceptions of quality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among high-involvement consumers with varying levels of nutrition knowledge. 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Behavior, 44(4)350-354.
喻国明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杨嘉仪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