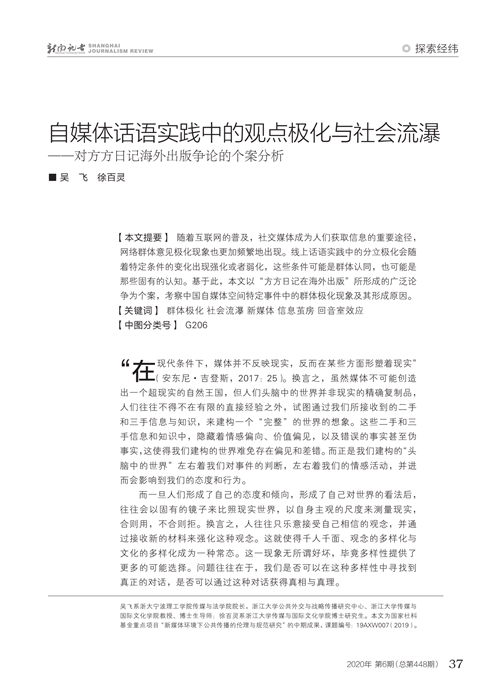自媒体话语实践中的观点极化与社会流瀑
——对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争论的个案分析
■ 吴飞 徐百灵
【本文提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群体意见极化现象也更加频繁地出现。线上话语实践中的分立极化会随着特定条件的变化出现强化或者弱化,这些条件可能是群体认同,也可能是那些固有的认知。基于此,本文以“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所形成的广泛论争为个案,考察中国自媒体空间特定事件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及其形成原因。
【关键词】群体极化 社会流瀑 新媒体 信息茧房 回音室效应
【中图分类号】G206
“在现代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形塑着现实”(安东尼·吉登斯,2017:25)。换言之,虽然媒体不可能创造出一个超现实的自然王国,但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并非现实的精确复制品,人们往往不得不在有限的直接经验之外,试图通过我们所接收到的二手和三手信息与知识,来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想象。这些二手和三手信息和知识中,隐藏着情感偏向、价值偏见,以及错误的事实甚至伪事实,这使得我们建构的世界难免存在偏见和差错。而正是我们建构的“头脑中的世界”左右着我们对事件的判断,左右着我们的情感活动,并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态度和行为。
而一旦人们形成了自己的态度和倾向,形成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后,往往会以固有的镜子来比照现实世界,以自身主观的尺度来测量现实,合则用,不合则拒。换言之,人往往只乐意接受自己相信的观念,并通过接收新的材料来强化这种观念。这就使得千人千面、观念的多样化与文化的多样化成为一种常态。这一现象无所谓好坏,毕竟多样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选择。问题往往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找到真正的对话,是否可以通过这种对话获得真相与真理。
作为线上话语实践的分立极化将会随着特定条件的变化出现强化或者弱化,这些条件可能是群体认同,也可能是那些固有的认知。基于此,本文将以“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所形成的广泛论争为个案,考察中国自媒体空间的话语交往行为。
一、文献分析
(一)对话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
对话的困难之一,是群体极化。学界关注到群体极化现象比较久了(黄河,康宁,2019)。1961年还是麻省理工大学心理学研究生的詹姆斯·斯通纳(James A. F. Stoner)进行了一项旨在探索群体决策问题的研究,他先让每个人对一个难题提出解决方案,然后再让这一群人就这一观点进行讨论,看看能否得到共识。结果发现,在阐述论点、进行逻辑论战时,一些成员变得具有防御性。当人们面对挑衅时或者群体中冒险者占多数时,态度或者做出的决策会变得更为冒险甚至激进。詹姆斯·斯通纳用“冒险性偏移”(risky shift)来指称这一现象(Stoner, 1961)。其后,这一现象引起了更多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后续的研究发现,群体讨论确实能发生“冒险性偏移”,但也出现一种相反的情况,即讨论之前如果某群体对某一议题呈谨慎倾向(cautious),在讨论之后这种偏向不但不会减弱,反而得到了强化(Rabow et al., 1966:16-27;Vinokur, 1971:231-250)。所以学者们又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即“谨慎性偏移”(cautious shift)。莫斯科维奇(Moscovici)和扎瓦洛尼等(Zavalloni)站在更高的维度上,对这种现象进行抽象总结,他们首次使用了“极化”(polarization)和“极化效果”(polarization effect)来描述群体讨论中出现的“偏移”现象,他们认为“冒险性偏移”可能仅仅是“极化效果”的一个方面(Moscovici & Zavalloni, 1969:125-135)。1971年科林·弗雷瑟(Colin Fraser) 、瑟利亚·高基(Celia Gouge)、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在他们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群体极化”这一概念(Fraser et al., 1971:7-30)。阿米拉姆·维诺库(Amiram Vinokur)和尤金·伯恩斯坦(Eugene Burnstein)分析指出,群体讨论开始时,论据非常有限, 且群体成员很容易被指向某个方向。若群体成员已经偏向于该方向,他们会提供更多的论据来支持此方向,与最初观点一致的论据就会显示出更强的说服力,最初观点的确定性就变得更高,群体讨论的结果就会进一步强化已有偏向,导致群体极化的产生(Vinokur , Burnstein, 1978:335-348)。还有学者分析了文化、性别和年龄等在极化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个人主义文化(北美国家,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倾向于重视独立性和风险,而不是依赖和谨慎;集体主义文化(亚洲国家及南美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往往更重视依赖和谨慎,而不是独立和冒险。劳伦斯·洪(Lawrence K. Hong)在1978年的研究表明,由个人主义文化成员组成的群体更有可能经历冒险性偏移,而由集体主义文化成员组成的群体则更有可能经历谨慎性偏移。态度转变的方向也受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玛格·加德纳(Margo Gardner)和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的研究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可能经历危险的决策;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更有可能做出冒险的决策。他们还发现性别差异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小(Gardner, Steinberg, 2005)。
极化不仅仅表现为人们相信什么,还表现在他们对于信源的选择上。有证据表明,近几年来,美国人在媒体资源的使用和信任方面的党派分化已经扩大——共和党人近两年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不信任度显著上升,相反,民主党人对这些媒体来源的信任和不信任程度的变化远小于共和党人。盖洛普基金会(Gallup Foundation)的调查也显示,民主党人士对媒体的信任度在2018年上升至76%,但共和党人对媒体的信任度始终保持低位。(图1 图1见本期第39页)
群体极化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Case·R Sunstein)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最广。桑斯坦指出,当群体成员彼此协商讨论,最终采取了比他们讨论前更加极端的立场时,群体极化就产生了。事实上,他一直关注三种不同现象:从众(conformity)、社会流瀑(social cascades)和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并尝试提出一种统一的解释。他研究发现,“所有形式的政治正确,都通过群体极化而得到发展。而且,当群体极化发生时,通常都是由于信息和声誉性的同时流瀑。暴力有时候也是这样发生的”(桑斯坦,2019)。他认为,当群体卷入仇恨与暴力的漩涡中时,通常不是由于经济损失和最初的怀疑,而是由于信息和名声影响的结果。毫无根据的极端主义通常源自“片面的认识”,绝大多数情况是由于仅仅接触其他极端主义者,而只能得到很少的相关信息。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桑斯坦提出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概念,他认为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信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所以他指出,“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以变成可怕的梦魇”(桑斯坦,2008)。
(二)新媒体与群体极化
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为群体对话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学者们发现,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互动过程,将导致以心理群体或舆论群体形式存在的社会公众的意见极化。而类似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公众广泛参与,而又相对缺乏自净机制,更容易导致群体极化。
从理想状态看,网络媒体的开放性有助于信息环境的多样化,但是在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流行的今天,个性化信息服务使得人们只选择自己关心的或者符合自己需要的信息,更易导致“信息茧房”效应。因为,在互联网上人们很容易找到想法一致的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轻松和频繁”,个人往往会“从志同道合的人那里得到消息”,而且往往是“听不到相反的观点”,从而产生了信息“过滤”(filtering),而那些经过过滤的信息反复地出现在明显的位置,给人的暗示是许多人们都持有它,使得倾向于这些观点的人更加相信它。互联网也很容易促成并强化形成具有共同观念的社区。在社交媒体中,人群出现了分化,以社交圈子以及自身立场为主所进行的信息传播,往往会使人们固守在各自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这就是桑斯坦(Sunstein, 2017)和帕雷泽(Pariser, 2011)所说的互联网产生的“回音室效应”。加布勒也认为,在社交媒体上“志同道合的人”更容易发现彼此,并会“煽动彼此的偏见和不满”(Gabler, 2016)。当人们一起思考的时候,他们往往对“共同知识”给予不成比例的重视,即他们事先分享的信息,相比之下,它们往往对未共享的信息给予太少的权重。在社交媒体中,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共同身份和某种程度上团结的群体的一部分,那么群体的两极分化就会加剧。对共同群体认同的感知将提高他人观点对你自己的影响,而对非共享身份和相关差异的感知将减少甚至消除这种影响(Yardi, Boyd, 2010)。这往往会使人们失去对周围环境的完整判断,因此,互联网也因此增加了群体极化的可能性。
桑斯坦进一步指出,“有限的论证池”(limited argument pools)、“声誉考虑”(reputational considerations)和“佐证效果”(effects of corroboration)等是导致网络群体极化产生的一些重要因素。这一点有助于解释社交网络每天发生的事情,例如,在Twitter上个体的消息来源是由那些有“一样思考的人”或者是“Facebook上的朋友分享”,那么“论证池将受到严重限制”。在YouTube上也存在着大量孤立的剪辑,以及脱离上下文的内容,导致具有共同认知的人最终对一些问题、人或实践产生扭曲的理解(Sunstein, 2018:59-60/71-75)。
在“声誉考虑”方面,人们希望自己被其他群体成员关注,当听到团体成员的声音后,他们经常会调整自己的立场,向占据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这往往只是为了保持某种自我观念和声誉。而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对一些政治问题的讨论时,当人们真的不确定他们的想法时,他们倾向于保持中立。而只有当人们获得自信时,他们的信念才会变得倾向于某一方。此时,其他人的赞同往往会增加个体的自信心。也就是说,当人们得知别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自己最初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后,他们往往变得更自信,因而观点也更加极化(Sunstein, 2018:59-95)。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家方方以每天一篇“武汉日记”的形式,记录“封城”状态下自己的所见所闻,2020年4月8日全球最大的出版商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宣布出版方方日记,并在亚马逊官网上发布宣传内容,此举引发国人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选择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中的争议作为案例,来检视自媒体空间围绕热点议题形塑的话语实践,分析在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各方解读和论争方面,是否也存在相应的极化的现象。如果存在极化的情况,那么在讨论当中人们在表达方式、观点立场上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收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以“方方日记+出版”为关键词在清博大数据平台中对2020年4月8日—4月15日的微博数据进行了检索,共获得28281条微博,经过去重、剔除部分不以此为主题的样本后,对剩余微博进行了等距抽样,以间隔20为一个抽样周期,共获得636条微博样本,并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此外,通过这些微博链接获得微博用户自己发布或者转发相关讨论的文章,共55篇长文,并对其进行了研读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第一,用态度极端化百分比来测量极端态度是否出现并升温(辛文娟,2014)。态度极端化百分比=(强烈支持言论+强烈反对言论)数量/总言论数
量×100%;非极端态度百分比=(比较支持言论+中立言论+比较反对言论)数量/总言论数量×100%。第二,用群体态度倾向百分比来测量两种极端态度的差异。支持态度百分比=(强烈支持+比较支持)言论数量/总评论数量×100%;反对态度百分比=(强烈反对+比较反对)言论数量/总评论数
量×100%。使用以上数据结合言论发布时间顺序来综合判断是否出现极化现象。
对相关样本的数据编码,本研究参考借鉴黄河(2019)、辛文娟(2014)等学者在网络极化研究中使用的编码方法,结合本研究样本的具体情况,将微博留言所反映的态度进行编码。即把每一条微博留言简化成一个态度,用数字1至7表示。态度激烈直接使用辱骂性字眼或主张采取惩罚行为的计为1;强烈反对或谴责,有部分理由陈述的(如指责方方日记内容失实之处,是在给反华势力“递刀子”)记为2;有较明显的反对态度,但用语文明、表述理性的计为3;态度中立,分析客观理性、无明显立场的计为4;有较为明显的支持态度,表述理性的计为5;强烈支持,并有比较强烈的对对方的批评指责,语气较为强烈(如使用感叹、诘问等语气)的计为6;强烈谴责并有辱骂或表达参与支持活动(如指责没有常识的“愚蠢行为”,支持方方日记出版,表达购买日记的愿望)的计为7。其中,将1、2视为反对出版的极端态度,将6、7视为支持出版的极端态度;将3、4、5视为非极端化态度。
此外,我们还通过对文本内容进行主题分析和编码,来考察样本中的话语对话与极化情况,将讨论涉及的内容分为国家利益、事实真相、出版动机、职业责任、自由权利、国家自信、包容理性、情感支持、创作体裁以及其他等十个方面。同时,还对样本中相关争论的内容进行了词频分析,获得支持方方日记出版与反对方方日记出版的讨论中较多的主题词,分别为: (支持方)日记、出版、一个、中国、武汉、国家、美国、疫情、作家、西方;(反对方)日记、出版、中国、武汉、一个、国家、美国、西方、疫情、国外。
三、“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争议中的对话与极化
(一)观点的极化与社会流瀑
在对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争论过程中,出现了十分明显的群体意见极化的情况。这种极化不仅表现在争论双方在主张各自立场时所采用的主题内容上的差异,还表现在经过讨论后持不同立场(支持与反对)数量变化以及态度的极端化程度方面。如图2所示,当4月8日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发布后,迅速成为微博的热议话题。尤其是当人们看到亚马逊官网中对方方日记以“武汉封城日记”为题进行出版宣传时,有78%的人持反对意见(4月8日),有文章评价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会“给中国人一份刺痛”。从4月8日到9日反对意见迅速上升到87.8%,而在讨论中双方所持态度极端化程度则达到了82.5%,并在10日达到顶峰84.1%(见图3)。随着争论的进行,持支持意见的人数上升,在4月12日达到了最高点46.3%,双方意见也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点。但从总体数据来看,反对意见一直占较高百分比,虽然话题数量随着微博热度的下降而总体下降了,但从13日-15日反对意见占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到15日占所有表达意见的77.8%。
人们持有的立场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社会阶层等原因,不仅是针对事件本身,更是延续和强化自身长期以来的既有倾向(Borgida, Stark, 2004)。作为相似观点的聚集地和交互式的“回音室”,互联网环境中的个体倾向于寻找与自身观点、价值取向相同的团体,并在群体互动中将对立情绪升级到仇恨的程度(桑斯坦,2010:153-154)。
随着讨论的推进,质疑声也更多地出现,人们对于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出现朋友反目、互相拉黑的情况,如4月13日微信文章《方方日记逼疯了多少人?北大校友群也开始撕了!》中便呈现此种情况;更有上升到人身攻击,甚至提出要对方方进行肉体讨伐。如4月15日一篇题为《终于,针对方方的大字报出现了》的微信文章中发布的一张照片:“告方方书”,痛骂方方“吃人血馒头”,“享受体制的种种福利,却干着构陷国家的事情”,“强烈要求方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还给国家,然后削发为尼,或者以死的方式向国人谢罪”,“否则……将会对方方进行文攻武伐”。更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声讨方方的视频,号召“趁方方还没有离开武汉,习武之人应该联手声讨……‘败家娘们’”。
值得关注的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表达者的态度一直处于极端化程度较高的状态。即便在11日和12日中出现了较多的理性对话,但仍然不能改变讨论中总体态度极端化的状态,从4月10日极端化态度达到最高点(84.1%)后,极端态度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状态,直到15日微博热度下降时,仍保持较高百分比(66.7%)。
当然,在后续的一些文章中,也对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事件进行了较为客观理性的分析与讨论。如4月14日发布在凤凰新闻的一篇文章《方方日记事件的十大警示》,客观详细地分析了相关事件中所出现的撕裂现象,并提出要警惕出现族群撕裂对立、警惕法治思维缺失、警惕强势话语垄断、警惕狭隘缺乏包容等十大问题。图2显示后期极端态度数值略有下降,而非极端数据有所上升,可能说明更多理性分析声音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极端的态度有所改变。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群体极化理论所坚持的,不同态度和观点持有者不太会改变其原有观点的结论在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一事中,会有不同表现呢?
(二)观点极化背后的价值框架
任何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封闭系统,其意义的生成依靠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嵌入与指涉。作为表征机制的媒介话语,往往处在与之前和之后其他话语的互文性关系之中。当不同话语主体之间“稍微涉及同一个主题框架”,他们就建构起一种对话关系;当单个主体的话语表达中“能读出其他个体的声音”,说明对话也是存在的(巴赫金,1998: 436)。借助话语主题这一分析维度,我们尝试对方方日记争议中的意义争夺与对话加以观察。
在对样本中观点双方的对话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后发现,双方讨论的话题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有:日记、出版、中国、国家、武汉等,这些用词出现频率基本都在300次以上(见表1)。这说明双方的讨论有相应的、比较集中的关注点。
反对方方日记出版的一方认为方方日记涉及国家利益,其出版动机不纯;方方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失实,不能代表武汉及中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表现。而支持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一方则围绕反对者的观点进行批驳,因此,支持一方的话语中也集中出现了日记、出版、中国、国家、武汉等词语。这些争论中尤其以方方对出版争议中的“国家利益”问题进行回应的博文为由头,对其进行的引用、转发以及评论内容较多。
在争论中,双方所使用的高频词也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支持者使用的词中较早出现了“疫情”、“人民”、“自信”这类词,反对者中出现较早的词有“美国”、“西方”、“国外”,说明双方关注点有所不同。支持者更加强调作家的自由权利,肯定作家对疫情这一重大社会事件所进行的反映,提出国民应该有基本自信。反对者则关注日记海外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对英文版的日记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表示担忧甚至是愤怒,对日记内容中信息的真实性提出强烈质疑。这说明在对这一话题的讨论过程中,存在着对话,但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甚至是观点的极化。
在对636份样本的统计中发现,在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争议中,讨论最多的主题有国家利益(57.3%)、出版动机(55.1%)、事实真相(42.2%)这几个方面。具体到内容,反对方方日记出版的一方认为,方方日记中的内容涉及我国疫情防控初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在国外出版是家丑外扬,破坏国家形象,还会授人以柄,国家和人民将为日记的出版埋单;方方日记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翻译出版的各项流程,并由全球最大的出版商出版,而且预售版的封面设计、标题及内容简介充满歧视,歪曲事实,误导读者,动机不纯,目的不良;日记中的内容道听途说,真实性难以保证,不是中国疫情防控的真实情况。而支持方方日记的一方认为,疫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国内外都有,且从全球疫情蔓延来看中国甚至比许多国家做得好,并且日记中也有大量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呈现了来自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在疫情防控中所做的努力,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不但不会给国家抹黑,反而能够起到增进理解、为全球抗疫提供借鉴的作用;方方出版日记也不是另有目的,而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疫情期间每个普通人所经历的苦难;另外,方方日记记录了当时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其体裁属于文学创作,不能用新闻纪实来要求日记的真实性。在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双方不断举出新的例证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驳斥对方的观点,从而引发对其他更多主题的讨论。
通过对上述内容和话语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这场争论中,存在较为明显的话语对立与撕裂。公众对同一主题下的内容讨论,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知。如2020年4月9日一篇《“方方日记”境外出版有何政治意味》的文章提出,方方日记火速出版,是西方“用以攻击中国政府,贬低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中出色表现”的工具,方方借助日记“形成世界性影响”,甚至是获得“某奖的人生最高追求”。而同日的一篇文章《方方日记为何不可以在国外出版?》中,就反对者们所担心的问题进行了逐条的批驳,认为方方日记海外出版没有政治阴谋,更无个人动机,也不会出现抹黑国家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
我们将讨论者立场与讨论内容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反对方方日记出版一方更多地采取国家利益和出版动机主题,而支持方方日记出版的一方,除了就此展开反驳,还倾向于采用社会责任(17.1%)、自由权利(39.0%)、国家自信(18.3%)、包容理性(19.5%)这四个主题来支持方方日记的出版。他们更多地主张出版日记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方方作为作家有责任记录社会现实;对于日记的内容及创作体裁应该抱有更多的宽容和理性的认识;文学作品不可能成为他国提出索赔的证据;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是没有国际话语权,要有国家自信。
四、社交媒体中观点极化与社会流瀑的影响因素
从社会心理来看,人们往往希望自己被其他群体成员关注,当听到团体成员的声音后,他们经常会调整自己的立场,向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而这往往只是为了保持某种自我观念和声誉(Sunstein, 2018)。在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争论中,一些原本支持方方日记的人,当得知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后,也纷纷转向反对的一方。
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可以从人们对固有观念的持有上来分析,即当人们持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时,讨论并不会影响态度的改变(Sunstein, 2018)。当微博中出现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预售海报的图片,以及一些讨论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会给中国带来被动局面的观点时,许多网友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反对方方出版日记的一边。这是因为当讨论涉及国家利益问题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国家利益,而不会去考虑所讨论的问题到底会不会影响国家利益。4月9日的一篇微信文章《方方有点对不起支持她的人》中表达了这类想法,“我不反对方方出版《武汉日记》,这是法律赋予她的权利,但我反对她这么着急出版《武汉日记》”,因为“第一,很多事实没有核实清楚”,“第二,出版时机很不恰当”,“这时候出版这么一本《武汉日记》,就把中国做得很好的方面都抹杀了”。
然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带有很强的回音室效应,人们在微博和微信中获得的信息是那些通过标签以及算法推荐的途径传播出来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中,个人倾向于从与自己有相同观念的人那里获得信息,这些信息经过过滤后被放大,左右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在本研究中发现,微博中有相当数量反对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的人,其所列举的反对意见大多缺乏事实性的依据。如,一些人认为方方日记都是“道听途说”,传播的“谣言”并非武汉疫情的真实信息,这些内容会抹黑中国形象。事实上,方方日记并非全然是晦暗的,失实之处方方也已经做了解释和道歉,但依然有大量的批评甚至是攻击性的语言来针对方方,以及揣测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动机。
在方方日记出版的讨论中,出现了不提出任何事实论据,直接给出评判的话语表达,甚至反对者中不乏对方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以及阴谋论的判断。如有人直接质疑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的动机,甚至有人认为她是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吃人血馒头”。情感两极分化的加剧有可能增加公民之间的不文明,减少他们对妥协的支持(Yphtach, 2016:392-410)。
在本研究所收集的微博样本中存在大量情绪化的表达,类似下面的表达方式很多。
从写作到全世界出版一气呵成,可以拿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发国难财,造谣,耍特权,说你是文化汉奸才是对你最好的称谓。(带三个手机,4月9日18∶28来自微博评论)
起初看到那么多人出来批判她,感觉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啊(当时没仔细了解过)。后来逐渐看到一些信息、文章,今天得知她的日记要在国外出版之后又翻看了她的微博,就感觉这人是金牛座吧,无论别人怎么说就觉得自己是对的,执迷不悟固执己见。(来自火星的猪仙子,4月9日18∶27的微博评论)
如果一个18岁的新生代作家被人利用,我们还可以理解她涉世未深,很傻很天真,但是一个有几十年写作经验的知名作家,如果说自己没想到对方出版社会这样包装自己的书,这是有些说不过去的。我的理解是要钱不要命。(军哥无戏言_wj:4月11日21∶22的微博评论)
观点的对立作为一种基本事实,并不必然带有极化的属性,但当对立双方存在明显情感抵触或相互厌恶,则会成为极化的温床(Lelkes, Sood & Lyengar, 2015)。在对本研究样本内容进行主题统计时也发现没有任何实质性讨论内容仅仅是情绪化表达的就占整个讨论主题的35.1%。这些情绪化表达或极端化立场,缺乏交往理性,但无一例外均获得大量回应,使争论激化。例如,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声讨方方的视频,号召大家对方方进行武力讨伐的人,则将整个讨论的方向引向了极端非理性的泥沼,触及法律的边界。
当然,不排除许多情绪化的表达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取点击量。因为意见表达的倾向性和情感性越强,尽管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同观点的攻击,但客观上提升关注度(Ibrahin & Hoffner, 2008)。与之相反,一些理性的声音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非理性进行了批驳。如微信文章《法学教授:同反对〈方方日记〉的人们聊聊法律》、《方方日记:国内问世没有塌天,海外出版也不会地陷》、《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个人的5点看法》等文提到的一些观点或成为共识的案例,则基本属于理性程度较高者。
五、结语:开放对话的重要性
本研究以“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争议为个案,来讨论中国社交媒体空间的观点极化与社会流瀑问题。研究发现: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明显的观点极化现象。毕竟,“在实践推理中,我们随时可能因为理智上的错误而误入歧途:比如没有充分了解自己所处情境的具体情况,或者超出了论据的范围,因而受到误导或者过分依赖那些未经证实的普遍结论”(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2013:79)。在围绕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的争论中,这几种情况经常发生,甚至方方日记中也存在一些事实上的差错,而其外文版的宣传海报中也出现了价值观上的误导。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的表达往往会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或者追求流量,或者出于政治的野心,或者为了成名,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非理性“讨论”往往会以另类的表达来吸引注意力,虽然他可能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正是桑斯坦(2016)所指的“社会流瀑”现象:当流瀑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以致许多人不是依靠自己实际所知,而是依靠(自己认为)别人持有什么想法。“流瀑既能影响事实判断,也能影响价值判断”(凯斯·桑斯坦,2016:53)。比如在方方日记海外出版这一事件中,一些人相信方方拿了海外的经费来有目的地干抹黑中国的行为。这一指责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权威的事实支持,但不少人在转发和评论时,并非依靠自己掌握的真实信息,而是将判断建立在自己所信任的别人的判断基础之上。许多反对者很明显受到了舆论领袖的影响,如胡锡进发表的《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就被广泛传播。在这篇文章中胡锡进认为,“这个时候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发出来的决不是什么好味道”。其实这一观点仅仅是他个人的感觉,并不是建立在什么事实基础之上的论断。但因为舆论传播中的从众心理,让他这样的观点彼此激荡而成洪流,许多反对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声音,基本就在这一认识框架之内。诚如Lee所言,观点极化并不是来自信息的收集和论据的说服,而更多是受到既有立场倾向与群体认同的影响(Lee, 2007)。本研究也表明,作为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群体交流需要依靠个体交往理性的建构,才能弱化群体极化倾向,促进共识达成和话语共同体的实现。对于一个期望建立良性秩序的社会而言,“让更多的观点呈现在个体面前,这将帮助他们更好地寻求关于‘事实’或者‘接近事实’问题的结论”(拉塞尔·哈丁,2013:263)。问题是一些权力的控制者,乐意选择分裂,鼓励左与右、正与反的撕裂,如此,他们以为可以通过平衡术轻易达到制衡双方的效果——因为权力掌握下的意见与舆论的撕裂往往彼此互博而消耗能量,而没有精力对权力掌握者造成直接的冲突。比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撕裂就是一种观念的平衡术。但这样的结果,并不利于公民理性的培养,也最终会有害于社会共同体。在方方日记是否可以在海外出版问题上,有不同的评论框架,但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相对开放的方式来处理这一舆论事件,这种开放的对话环境,使得围绕这一事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仅仅选取粉丝量较大的微博作为分析对象,未能将其他网友发布的大量短评囊括在内。此外,缺乏多案例的比较,研究结论可能难以推论到总体。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新的案例,探讨共识、极化、偏移等公共议题讨论中的多元形态及其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2013)。《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刘玮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17)。《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巴赫金(1998)。《巴赫金全集》(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黄河,康宁(2019)。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群体极化特征和生发机制。《国际新闻界》,(2),38-61。
凯斯·桑斯坦(2016)。《社会因何要异见?》(支振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凯斯·桑斯坦(2008)。《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凯斯·桑斯坦(2010)。《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尹宏毅,郭彬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拉塞尔·哈丁(2013)。《群体冲突的逻辑》(刘春荣,汤艳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辛文娟(2014)。微博中网民群体极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温岭杀医冶事件的内容分析。《情报杂志》,(6),162-166。
Borgida EStark E N. (2004). New media and politics: Some insights from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48(4)467-478.
FraserColinGougeCelia& Billig, Michael.“Risky Shifts, Cautious Shifts, and Group Polar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1no.11971pp.7-30.
Gabler N (2016).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are increasingly divisive and undermining of democracy. Alternet. Available at www.alternet.org/culture/digital-divideamerican-politics. Accessed February 192017.
Gardner, Margoand L. Steinberg. (2005). “Peer Influence on Risk Taking, Risk Preference, and Risky Decision Making in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An Experimental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4)625-635.
HongLawrence K. (1978). “Risky Shift and Cautious Shift: Some Direct Evidence on the Culture-Value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41(4)342-346.
Ibrahin AYe J & Hoffner C. (2008). Diffusion of News of the Shutter Colombia Disaster: The Role of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Motive fo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25(2)91-101.
James A. F. Stoner, “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1961全文可从以下网址下载http://dspace.mit.edu/bitstream/handle/1721.1/11330/33120544-MIT.pdf?sequence=2&isAllowed=y.
Lee E J. (2007). Deindividuation Effect on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Role of Identification, Public-Self Awarenessand Perceived Argument Qual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7(2)385-403.
Lelkes YSood G & Lyengar S. (2015). The Hostile Audience: the Effect of Access to Broadband Internet on Partisan Affe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34(2)411-421.
Mark JurkowitzAmy Mitchell, Elisa Shearer and Mason Walker (2020). U.S. Media Polarization and the 2020 Election: A Nation Divided: Deep partisan divisions exist in the news sources Americans trustdistrust and rely on, https://www.journalism.org/2020/01/24/u-s-media-polarization-and-the-2020-election-a-nation-divided/
Moscovici, Serge& ZavalloniMarisa, “The Group as a Polarizer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12no.21969pp.125-135.
Sunstein C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Univ PressPrinceton).
Sunstein CR (2018).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Univ PressPrinceton). https://www.jstor.org/stable/j.ctv8xnhtd.6
Pariser E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Penguin, London).
Yardi SBoyd D (2010). Dynamic Debates: An Analy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 Over Time on Twitter[J].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30(5): 316-327.
Yphtach L. Mass Polarization: Manifestations and Measurement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80Special Issue2016pp.392-410.
Rabow, Jerome, Fowler Jr, Floyd JBradford, David LHofeller, Margret A& ShibuyaYuriko.“The Role of Social Norms and Leadership in Risk-taking”Sociometry1966pp. 16-27.
StonerJames AF.“Risky and Cautious Shifts in Group Decisions: The Influence of Widely Held Valu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4no.41968pp.442-459.
Vinokur, A. (1971).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group processes upon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4)231-250.
Vinokur ABurnstein E. (1978). Novel argumentation and attitude change: The case of polarization following group discussion.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8335-348.
吴飞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百灵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的伦理与规范研究”的中期成果,课题编号:19AXW00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