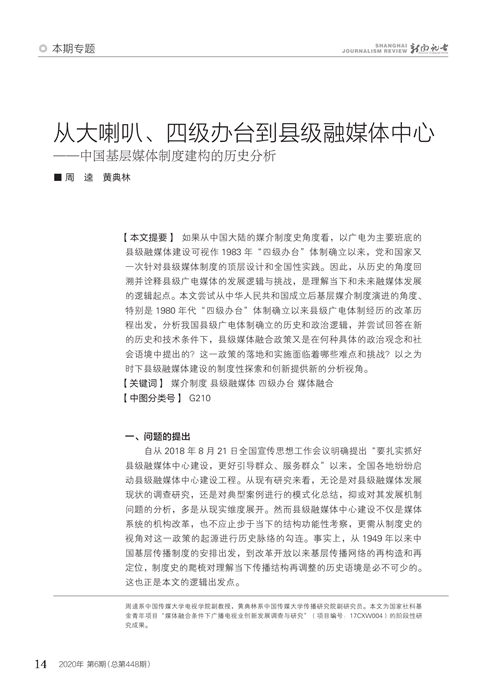从大喇叭、四级办台到县级融媒体中心
——中国基层媒体制度建构的历史分析
■周逵 黄典林
【本文提要】如果从中国大陆的媒介制度史角度看,以广电为主要班底的县级融媒体建设可视作1983年“四级办台”体制确立以来,党和国家又一次针对县级媒体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全国性实践。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回溯并诠释县级广电媒体的发展逻辑与挑战,是理解当下和未来融媒体发展的逻辑起点。本文尝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层媒介制度演进的角度、特别是1980年代“四级办台”体制确立以来县级广电体制经历的改革历程出发,分析我国县级广电体制确立的历史和政治逻辑,并尝试回答在新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下,县级媒体融合政策又是在何种具体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语境中提出的?这一政策的落地和实施面临着哪些难点和挑战?以之为时下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制度性探索和创新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媒介制度 县级融媒体 四级办台 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G210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2018年8月21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启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程。从现有研究来看,无论是对县级融媒体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还是对典型案例进行的模式化总结,抑或对其发展机制问题的分析,多是从现实维度展开。然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不仅是媒体系统的机构改革,也不应止步于当下的结构功能性考察,更需从制度史的视角对这一政策的起源进行历史脉络的勾连。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中国基层传播制度的安排出发,到改革开放以来基层传播网络的再构造和再定位,制度史的爬梳对理解当下传播结构再调整的历史语境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正是本文的逻辑出发点。
在媒体融合已成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具有自身的特殊使命和功能属性。从实践层面看,融媒体中心建设存在着“谁融谁”的结构性问题。目前在建与建成的县级融媒体机构中,多数以县级宣传部与县级广播电视台为主体。这样以广电为主体搭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模式是符合县级媒体发展客观情况的选择。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明确“县级不办报”的原则后,县级报纸大幅度裁撤,既存人员分流后也都不再新招。《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公布的《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仅剩县级报纸19种(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虽然不少县还存在未经合法登记、游离于国家正式报刊管辖体系之外的“内部报纸”,但因其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公开发行,无法开展经营性活动,更无法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其内容基本以政务活动和工作动态等公文性消息为主,因此也不具备新闻媒体的属性,不可能成为县级融媒体建设与转型的结构性功能与责任承担主体。
相比之下,虽然在“四级办台”体制下中国的县级广电同样处境艰难,但总体而言,依然能维持相对完整的系统结构和新闻媒体属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8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共计2106家,这个数字在近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略有上升。①在这样的格局下,依靠县级广电网络及人员队伍进行融媒体中心的搭建,成为较为现实的路径选择。实际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相关调研显示,当前在建与建成的县级融媒体机构中,多数以县级宣传部与县级广播电视台为主体。被当作发展模式的浙江省长兴县、甘肃省玉门(市)县、吉林省农安县等,均以县委直接领导下的广电机构作为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机构班底(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2019)。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广电智库更提出县级广电要成为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主体(国家广电智库,2018)。
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我们都可以把以广电为主要班底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视为1983年“四级办台”体制确立以来,国家针对县级媒体制度进行的又一项顶层制度设计。要准确把握和理解当前县级媒体融合建设政策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考量,就离不开对县级广播电视台在中国媒体整体版图中的位置和功能,及其发展演变过程的把握。要理解中国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政治和传播学逻辑,必须在历史中探寻历次县级媒体制度设计和建设中国家政策和基层实施的逻辑脉络,只有从中国县乡的基层治理和中央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从行动者在技术(电视、广播、以及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融媒体)扩散过程中的角色、动机、观念的形塑的角度,我们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当前县级融媒体建设现象的实质。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县级媒体融合改革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对如下问题进行考察:我国县级广电体制是在何种历史和政治逻辑的主导下确立的?从1980年代“四级办台”体制的确立到融媒体改革之前,县级广播电视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新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下,当前县级媒体融合政策又是在何种具体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语境中提出的?这一政策的落地和实施面临着哪些难点和挑战?
二、结构安排与创新扩散:县级广电体制的制度逻辑
(一)建国初期作为基层宣传与传播网络的县乡“大喇叭”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在“四级办台”的全国性广电结构之下对“县级”媒介制度的调整,而并非对“四级办台”体制的结构性重塑。因此,考察“县级融媒体”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扩散,必须要从基层媒介制度逻辑的沿革出发,追溯到“四级办台”制度设计的本身,乃至再向前追溯到新中国早期媒介制度的确立。1983年确立的“四级办台”制度包括对基层广播网络发展的规划,这实际上正是1949年以来全国政治宣传网络建设的延续。早在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提出要“发展人民广播事业”的要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1952年4月,全国第一座县级广播站吉林省九台县广播站正式播音。而五十年代最具创见、影响最大的传播制度安排正是通过建设县乡“大喇叭”,搭建起触达底层的声音宣传网络(Huang & Yu, 1997)。
大喇叭宣传网络的建立,反映了1949年以后国家主义的政治传达在中国特色的城乡结构中的“技术下沉”实践。这些大喇叭被安装在市县的学校操场、工厂、集市和农村的稻田、公社等空间中的电线杆、房顶或树顶之上。收听户外大喇叭广播也帮助塑造了一种国家归属感的集体经验。1955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更是首次明确提出以“有线广播+大喇叭”的方式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规划。根据这个规划,1956年全国将增加有线广播站900多个,带有喇叭45万到50万个;到1957年底,全国农村将有1800多个广播站,带有136万多个喇叭;到1962年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站将达到5400多个,带有喇叭670多万个,全国所有的村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部分农民家庭都可以被覆盖(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2005)。
有线广播站和大喇叭在当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成为迅速有效地搭建起全国性广播网络的选择(Jan, 1967)。面对低识字率的农村受众,声音媒介传播的覆盖率和有效性超越其他媒体形式;而和普通广播相比,大喇叭更加具有灵活性和低成本的特点,使国家宣传网络迅速下沉到了广阔的农村和偏远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喇叭网络在全国的建立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全国性媒介实践之一(Huang & Yu, 1997)。就农村有线广播的硬件建设而言,反右、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反而成为技术下沉的促进因素(潘祥辉,2019)。1976年底,全国安装的有线喇叭发展到1.13亿只,是文革前数量的17倍多(赵玉明,2006:317)。
特希·兰塔能(Rantanen, 2004)认为,媒介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延续性,而非断裂的。在中国语境下,这种延续性既表现为某项媒介技术本身的延续性,亦体现在不同媒介技术在制度的结构性安排上呈现出的稳定性。就前者而言,曾经发挥了巨大动员作用的农村大喇叭在党的十九大后的政治宣传和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中再次在乡村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后者来说,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大喇叭网络的扩展与改革开放后县乡广电结构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二)权力下放与层级构建:“四级办台”方针的确立和实践
改革开放后新政策宣传导向的目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加速推动了广播电视这一新兴媒体在中国县乡一级和广大农村地区的迅速发展。②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一地方”分权体系日渐深化,使得“条块”中的“块”获得了形成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黄升民,宋红梅,2007)。建立从顶层(中央)触达基层(县乡)的广播政治传播网络拓展的需求和改革开放之初较为拮据的中央财政经费之间的矛盾,使得新兴广电体系的建立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的动力和积极性,在这一背景下,“四级办台”方针应运而生。1982年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设立广播电视部,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强化了国家对于刚刚兴起的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控制和管理能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2)。而如何利用新兴的广播电视媒体加强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特别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的普及推广,提高宣传网络密度和广度,成为刚刚成立的广播电视部的工作重点。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对于当时刚刚开始在全国普及使用的“新媒体”电视,会议认为,“电视已经由城市扩展到农村,这是一件可喜的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会议要求“在三五年内,除特殊有困难的地区以外,要做到县县社社队队都通广播,户户人人能听到广播,全国大多数县能看到电视。到本世纪末,分几个步骤,做到户户人人都能看到电视。到那个时候,要在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现代化宣传网”(葛娴,1983)。正是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电视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当时“中央一地方”分权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四级办台”方针改变了以往的“行业集中”格局,推动权力下放,开始向分散发展,逐步走向“条块分割,以块为主”的新格局。通过这一系列新动作,各级广电最终被纳入地方行政体系内,从而可以合情合理地获得地方的各项支持(黄升民,宋红梅,2007)。简言之,“四级办台”方针的实质是放权,即授予地方开办电视频道的自主权力。在中央财政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电视的积极性,利用地方财政经费和自主创收获得的资金推动了中国基层广播电视网络的发展,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电视媒体的覆盖率。在一些县乡,村民甚至写信、上书或在人代会上提案要求乡镇领导办广播电视,更有积极的村民甚至以私人存款垫资“众筹”的方式开办广播电视。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使得中国全国电视普及率从1982年的57.3%提高到1987年的87.6%(章波,1988)。随着电视机数量的迅速增加,电视信号中转台的数量也从1983年的385座急速增加至1986年的1.5177万座,多数都依靠地方财政的投资。从1984年到1990年,电视地面频道的数量从93座激增至509座。到1990年,全国有超过1000家有线电视台,而这个数字三年后就翻了一番。到1995年底,地面广播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的电视频道的数量已经超过2740家(Keane, 1998)。有学者尝试通过对广播和电视机等大众传媒的普及率进行国际比较,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影响传媒普及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媒普及率的追赶及其动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980年代的电视和1990年代的互联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历的两次全国范围内媒介“扩散”的暴涨期(表1 表1见本期第18页)。从增长弹性的比较来看,1980到1990年的十年间,代表中国电视机普及速率的指标“增长弹性”位列中、俄、日、美、印同期指标之首。同样的现象再次发生是在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间,中国互联网普及速率同样远远超过上述其他四国,成为全球第一(胡鞍钢,张晓群,2004)。
这两次“新媒介”爆发式的扩散是我国传媒普及率整体追赶的主要因素。而中国与世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具有本土特色的集中式自上而下行政力量驱动和指令式动员对于两次媒介技术扩散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电视网络在中国县乡社会的建立和扩散的过程也印证了上述看法,而此后的式微也是行政集中式建设副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为夹杂在政治宣传导向、内容消费主义和公共职能之间的县乡广播电视网络日后发展的矛盾埋下了种子。
三、“四级”结构下县级广电机构的发展与困境:从地方案例到全国画像
四级办电视政策实施后,对于中国县一级广播电视事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南漳县的案例中一窥究竟。③南漳地处鄂西北贫困山区,荆山纵横境内,当地人称南漳地理特征是“八山半水一分半田”,复杂的地貌使得开办广播电视网络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比较艰苦。然而,1982年四级办台政策的制定和放权,赋予了南漳县充分的改革、建设县广播电视网络的动力。县乡级广播电视网络的建立和完善依靠的是县级政府财政投入,南漳县1983年后连续把开办广播电视事业列为全县工作重点,纳入农村基本建设五通工程之一,④财政拨款也随之增加。1983年相关事业的经费投入约为20余万元,1988年相关经费投入就已经超过45万元。此外还充分发动了工程建设的集体动员能力,发起大战九月活动,投入四万劳动力,建设耗资50多万元。
在四级办台政策推动下,南漳县于1986年建立了县广播电台,每天广播时间由1983年的4.5小时增加到6小时,自办文艺节目2.4小时。同年,建成玉溪山卫星地面接收站,县城地区可以同时收看中央、省三套节目。中央电视台、省广播电视台和市台三级电视综合覆盖率超过六成。1986年,随着财政经费的拨付,县电视台还配置了先进的摄录设备,随之而来的是内容生产能力的提升,1987年全年摄制新闻137条,其中上送省台、市台51条,被采用46条,还拍摄了南漳宣传专题片四部。南漳县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如云南在四级办台方针确立后的第十年就实现了县县乡乡都能看到电视,全省电视台从1座增加到15座,广播台从1978年前的2座增加到了22座。
从南漳县广播电视网络基础设施1983年至1987年五年间的变化可以看出:“四级办台”政策的制定落实,大幅度提升了中国基层广播基础设施的数量、覆盖率和内容生产能力。全县区乡广播站从15座猛增至57座,广播专线从4460杆公里上升至9137杆公里,入户广播数量从4.89万只上升至76.78万只;电视差转站也从17座上升至34座,电视覆盖人口从24.6万上升至34万人,电视插播时间也从无到有,达到420分钟。动员式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举将全县村通播率从70%提高到96%,喇叭入户率从56%提高到60%(章波,1988)(表2 表2见本期第18页)。
四级办台对农村县乡广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推动、对于政治宣传起到的作用是显著的。该方针下县乡广播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效地改变了基层政治传播的生态。据当地史料记载,1983年4月8日,全国人大进行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选举。次日,县台就专门组织人员对本地的相关村组进行走访调查,以研究广播网络铺设对政治宣传的实际作用。在调查小组走访的51户村民中有40户已经在家中安有喇叭,走访对象共58人,其中有40人均有安装,除一人因农忙没听广播不知道情况外,有39人说得出选举情况,而家中没有安装喇叭的18人都说不知道。
通过鄂西北县城南漳的案例,我们得以一窥“四级办台”方针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落地后如何催生了传播生态的变化。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鄂西北县城的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仍然需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推敲。为了获得全国层面广电结构性变化的证据,笔者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记载的相关数据,对1980年、1984年和1987年这几个时间节点进行比较(表3 表3见本期第19页)。
从全国层面的数据看,四级办台方针实施三年后,全国无线广播电台数量从167座迅速增加到386座,数量增幅达231.1%,其中县级广播电台的数量更是从45座增加到184座,翻了四倍;全国电视台数量从93座上升至366座,增长率为393.5%,其中县级电视台从23座增加到155座,增幅高达673.9%。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出县级广电网络建立速度,我们对《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Tableau将1986年和1987年统计在册的县级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图1 图1见本期第19页)。相关数据显示,南漳县广电事业发展的个案性增长趋势与全国范围内的总体增长趋势基本一致。
从中央—地方治理关系的角度出发,“四级办台”方针通过“放权”的方式建立起县级广播电视网络,既是1980年代初期改革的产物,同时在实现基层“最后一公里”的政治触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大规模建设运动也带来诸多问题。从国家视角看,权力下放、管理范围缩减,会加强体制内有效治理能力,此时两者的矛盾更多地体现在偏离和失控的情形中。事实上,当时中国大多数县级行政单位并不具备开办电视台的能力,但在政策的鼓励下出现了一拥而上办台的情况。“锦标赛模式”的政绩思维(周黎安,2007)和市场目的的逐利动机,使得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情况非常普遍。用当时一位县级广电系统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一个市区人口不足百万的城市,需要建那么多电视台吗?有的时候一点小的活动,七八台摄像机一起上阵,晚上打开电视,各台几乎播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新闻,省台播了市台播,市台播了区台播,区台播了系统外的台还在播,有这个必要吗?”同时,在节目内容播放上也非常混乱,由于县级台内容生产能力有限、资金有限,为了生存只能播放海外盗版录像,“有些台基本上是一个大录像放映点”。有些台随意切断中央台的节目,插播自己的节目或者广告(章波,1994)。由于“四级办台”的政策目的是迅速建立信息传播层级网络,而一旦网络建立完成,各层级行动者自身的动机又遭遇刚性的制度框架时,“变通方法”就成为普遍的路径(孙立平,郭于华,2000)。
类似“变通方法”的普遍存在反映了中央政策和当地实际状况之间,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官方话语与地方性知识、正式权力与权力的文化网络之间的距离、空隙和弹性(周雪光,2017)。这种落差最终引发了一系列文化后果:文化上的放纵主义,内容庸俗、质量低劣的海外录像节目一度大肆泛滥。偷录和滥放导致版权争议,对广告和观众的争夺又导致了非正当竞争和节目纠纷(郭镇之,1990)。这一情况在南漳县表现得也非常典型:首先,大干快上的动员式建设在迅速改变县乡广播电视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隐患。迫于上级行政压力,在工程建设中,土建工程和设备都比较简陋,短期行为特征明显,全县38个差转站,90%的设备是中低档,37个站没有备用机,坏后就得停播,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从全国数据看广播电视经费支出增长了72.7%,远远低于翻数番的机构数量。第二,不断扩充的机构人员人事制度和待遇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机构编制,因此人员数量弹性较大,商品粮户口和工资得不到解决。这一点从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亦可以体现:全国职工人数在1984到1987年间只增长了16.9%(表3 表3见本期第19页)。第三,重复建设问题明显,市县之间调频广播、电视互相干扰的情况较常发生。例如,南漳县1981年在县城附近的玉溪山用50瓦米波12频道差转湖北省电视台节目,而互距50公里的宜城县此后却购置一台300瓦米博12频道转发卫星节目,干扰南漳县的电视,引发了两县纠纷。
四、从“公共频道”到“网台分离”:县级广电媒体的迷失与转型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调动基层积极性建设县乡广播电视网络的历史任务初步实现后,“四级办台、混合覆盖”的弊端就凸显出来。这一政策导致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出现一味追求规模增长,重复建设过多过滥的情况。最初对于县一级电视网络的国家定位是宣传导向为主,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治宣传目的和县一级广电机构自身的经济性发展需求的矛盾凸显。四级办台十年后的1993年,一些县乡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遇到瓶颈。县乡广播电视的资金来源出现困难,不少县级财政的投入逐年减少直至断奶,有些甚至采取“休克疗法”,设备设施无资金添置,运营维护陷入困难,原本就苦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县级广播电视职工收入随之波动。这导致创收成为这些机构的主要导向,引发了一系列媒介伦理问题,对于一些市场经济活跃程度还很低的地方来说,通过市场性手段支撑县级媒体建设是无法成立的,人才外流严重(章波,1994)。
1996年,针对当时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厅字(1996)37号通知,重点解决擅自建台、重复设台和乱播滥放的问题,规定“现有县广播电视台、电台、有线电视台要合并为一个播出实体,主要转播中央和省的广播电视节目,可自办少量当地新闻和专题节目”。1999年,国务院发布国发办(1999)82号文件,要求“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从此,以成立公共频道为手段而达到逐渐撤销县级电视媒体的改革在全国开展起来。
2001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了《关于市(地)、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工作的实施细则》,在保留1983年四级办台总体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对全国广播电视体系和职能做出重大调整。根据通知要求,县(市)广播电视台,不再保留自办电视节目频道,可在公共频道中插播自办节目。公共频道应当划出一定的时段供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播出当地新闻、专题节目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以及广告等。设立公共频道的电视台应明确县(市)播出机构插播节目、广告的范围、时间、数量,理顺运行机制,妥善解决利益共享等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01)。
这一方针对县乡广播电视机构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以某县级电视台为例,该台从2002年8月开始撤销自办频道,并在公共频道中插播自办内容,共计三个时段一个半小时,分别为12∶00-12∶30,20∶00-20∶30,22∶30-23∶00,这一调整使得该台除了时政新闻外的其他栏目几乎都被迫放弃,观众急剧减少,不少人甚至认为该台“人间蒸发”。2002年9月至11月,该台几乎所有的广告都被客户撤单。同省的另外两个临县电视台的情况也类似,广告锐减超过百万,几乎造成毁灭性打击(张弛,2005)。
在这样的形势下,各地县级电视媒体不得不为了生存绞尽脑汁。一些台开始超出公共电视频道赋予的自办内容时长播出自办内容,另一些则在转播省、市节目时通过插播广告和滚动字幕广告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到2003年夏,县级电视台纷纷开始恢复自有频道。短暂的公共频道改革,使各台在形式上留下了一个“公共频道”,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几乎又回到了之前的做法,内容方面的问题与弊端重新显现。
此后,不少县级财政拨款对县级广播电视台实行包干制,随着退休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待遇的不断提高,在一些县,有限的拨款已经无法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切开支主要靠网络产业创收来解决,形成了以网养台的事实。2010年,广电总局提出年底基本实现“一省一网”的目标和要求,各省开始加快广电网络“一省一网”整合发展。网台分离对县级广播电视是一次重大调整。这意味着曾经占据县级广播电视台收入极大组成部分的网络收视费被剥离,原本广告收入大幅下降、依靠以网养台就捉襟见肘的县级广播电视台发展更加艰难。某县级广电媒体负责人坦言:“节目没人看,媒体就没有什么影响力,直接导致频道的硬广收入大幅下降,依赖传统的手段去创收、增收已非常困难;更要命的是,我们的数字电视网,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一年几千万的收入,一下子就没了,省里收回去上市了。确实是雪上加霜,据我了解,我们周边的许多台现在每个月只有二三十万的收入,要养活上百口的人,怎么发展?拿什么发展?”(张弛,2005)
五、新时代“治县观”与县级融媒体建设发展的治理逻辑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普及,新信息传播技术和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开始对传统媒体产生压力。这种态势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处于财政压力下的县级广播电视台的困境。全国各区县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站虽都有建设存在,但生存处境都极度艰难,发展也处于迷茫和困顿中,资金短缺、人才流失、定位模糊、内容单一让区县级传媒几乎走向绝境。因此,区县一级媒体的未来发展,是融媒体发展态势下国家媒体改革发展整体框架中基层一端的关键,从长远来看是事关整个基层治理和政局稳定的关键,因此势必要求从全新的媒介生态和政府治理逻辑出发,对县级媒体进行重新定位、规划和组织再造。而以县级广电为班底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一项由中央顶层设计并统一协调推动的全国性的县级媒介制度改革行为。从机构功能看,旨在统筹县一级主流媒体,成为县党委宣传部统一领导下的综合性新闻、信息、服务和舆情性功能平台。
(一)县治经验和县级媒体制度再造的顶层设计
郡县治,天下安。县级党政机构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县委是党执政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新华网,2015)。“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习近平,1990)。县级媒体传播力建设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在实践层面,县级媒体“没落”现状与国家现代化治理战略的要求形成鲜明反差。笔者对某一线城市某区县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的调研访谈证实了这一点。该县媒体中心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较为艰苦的硬件设施条件中,“区长带着发改委、财政局来调研,我们连个会议室都没有。屋子的墙皮都是脱落的,楼是危楼,没有任何消防设施,极其破旧”。到了2017年根据上级要求进行频道高清改造时,才勉强使用财政拨款,对危楼进行了改造,对办公环境进行了提升。节目制作的硬件设备也曾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最差的机器是什么?386(笔者注:电脑型号)。你连照片都存不进去,存不进去拿不出来,而且相互(联网)根本就没有,我想我们来的时候,上面还真不重视”。除此以外,内部组织管理混乱也是不少区县级媒体存在的重大问题。“设备和资产管理混乱,随便就能借能拷,然后出去以后都干私活。公家的固定资产和软性资产,可底下的人公司都挂在那儿,我说这是财政资金养着你的设备,养着你这公司人员是吧?这以后肯定也是党组廉政的一个风险点”。⑤笔者所调研的该区县属于一线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其区县媒体发展的状况尚且如此,全国范围的普遍情况可想而知。
从2015年开始,全国多个省推出了扶持县级广播电视台发展的政策。比如2015年9月,浙江省下发《关于扶持县级广播电视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县级广播电视台人员工资、设备维护更新、广电惠民服务工程等所需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切实解决县级广播电视台的实际困难与后顾之忧。同时,从当地文化事业建设费返还资金中安排一定的比例用于县级广播电视台建设,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黄琳,2015)。2017年1月山东省印发《关于促进县级广播电视台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省局将制定出台县级广播电视台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按照“改革、精简、瘦身、转型”的要求,着力推进县级台改革发展(中广互联,2017)。2017年7月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6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扶持县级广播电视台发展的意见》,从理顺体制机制、提高人才素质、加大财税保障等方面,推进县级广播电视台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湖北省广播电视局,2017)。很快,出台此类扶持县级广电媒体的政策在全国范围成为一个普遍现象。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要求,全国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大幕从此正式拉开。
(二)整合科层信息传播系统: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增量功能
县级融媒体建设是在四级办台的广电体制下,对县级广播电视机构的一次组织改造和技术升级。科层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是区县媒体建设的重要政治逻辑。其中包括区县与上一级政府间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对于区县一级的政治传播来说,可以达到既“对上”也“对下”的双重能见度效果。比如在笔者对某区县融媒体中心的调研中,受访者就谈到:“市委W书记和常委们早晨中午在食堂吃饭,经常拿着遥控器看你们各区的频道,一直盯着各个区区委书记、区长今儿都去干什么了。他们还很关注节目质量,经常点评。”因此,作为县级媒体传统定位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本地政治新闻的“全媒体全覆盖”,不能出现“漏题、漏报的重大工作失误”,同时还要和中央媒体、省属媒体、市属媒体“对标对表,了解中央领导、省里领导和市里边领导主要领导关注些什么,以便落实精神,布置选题,策划选题”。⑥
传统上,区县媒体由于受限于台、报和网的条块分割,因此在内部协调上需要消耗大量的沟通成本。比如,在笔者的调研中有受访者说:“以前的选题我们是‘坐堂’等,什么叫‘坐堂’?就是咱们的区里四套班子有活动,通过四办通知总编室,然后自己跑口的记者进行(采访),你们有什么事跟记者联系,整体上我们不把握。也常常出现通知报纸了没通知电视、通知电视没通知报纸,容易漏。这怎么能叫‘全管理全覆盖’?而融媒体中心建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重新整合区县台、报和网等媒体,“上会、上选题,所有的选题全部在这都可以看得到,避免有偿新闻、软文加进去,所有的新闻信息全部在平台。” ⑦
除了科层体制组织内信息传播的优化外,融媒体中心另一个重要的新增功能是改造了科层体制对于社情民意的信息获取能力。在中国的区县治理中,由于复杂的基层政治网络和地方利益团体的影响,常常面临“灯下黑”的传播困境,即本地负面新闻报道常常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进入本地舆论空间,这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形成压力。如笔者所调研的A市B区在2018年就发生过一次类似的舆情事件。由于基层相关部门的瞒报,导致区县和市一级政府大大低估了这次舆情事件的参与人数和影响度。“(一开始)说涉事者大概四五个人,结果通过网络上传播的视频看可能得有几百。这一消息还是通过中央媒体、商业媒体乃至境外媒体‘倒传’回来的,造成了比较恶劣的政治影响”。⑧因此在融媒体建设中,对于此类突发应急事件的现场评估和处置指挥,成为融媒体中心新增的重要功能。笔者调研中的受访者就表示:“可以(通过记者随配的终端设备的GPS定位功能)选最近的记者,出现场以后全部可以实时回传(画面和照片),了解现场实际情况,这样实际上便于领导决策,等到系统升级到2.0b版本后可以给领导开个端口,领导可以在手机里看现场状况,供他判断要不要去现场。不要因为瞒报忽略了重大突发事件,也不要受到其他渠道的炒作夸大影响了他对现场情况的判断。” ⑨
由此可见,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再造科层体制内外信息获取和沟通的流程,使得多部门、多层级的协调能力得以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融媒体中心对提升地方区县级的现代化政府的组织内传播能力有一定的促进意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当传统的政治生态中引入新的技术因素后,技术是如何被传统的政治、社会力学反向形塑和建构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在生态复杂的中国区县一级科层中,技术性平台的搭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再造体制内信息传播的流程有待实证观察。在笔者的考察中,有基层一级工作人员抱怨此类系统有可能沦为形式主义的摆设,或成为向上级进行汇报和展示的面子工程,而并未很好地融入到科层内制度的优化之中。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挑战
1.政策定位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落差
从前文所述区县广电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可以看出,区县广电媒体在四级办台整体制度设计中的最初功能和定位是作为农村广电网络扩散建设主体和上级广电宣传内容的转播平台。在前卫星时代,中国的政治传达正是通过四层网络“混合覆盖”的方式,进行逐层下渗式传播。因此区县广电媒体在政治宣传的“最后一公里”的到达率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区县媒体创办之初的受众也定位于区县一级普通群众。
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媒介技术生态和传播生态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区县的下渗打破了传统上多层级式的传播样态,而让整体传播网络系统更加扁平。进入4G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各大商业性互联网平台也迅速瞄准了“小镇青年”市场。平台的内容和服务下沉到具有极大商业想象力的区县一级市场,也造就了拼多多、趣头条、快手等新兴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崛起。商业性平台在近年来纷纷将发力重点同样指向区县和农村,使得区县用户的互联网使用需求已经最大程度上被各类商业平台细分和抢占。诸如趣头条、今日头条等资讯聚合类平台都与市属媒体和自媒体达成入驻协议,成为本地移动端资讯流量的收割者;支付宝等移动金融平台也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整合平台,成为本地银行金融服务乃至公共服务移动端的主要提供者。
事实上,区县融媒体的定位问题与区县传统广电媒体以及纸质媒体的定位困境如出一辙。地市级媒体在全国性省级卫视和商业媒体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尽管全力开拓本地市场,但近年来依然举步维艰;而区县媒体在全国大多数城市并无和本地都市媒体竞争的实力,因此依靠商业性开发来进行受众和内容定位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传统区县广电媒体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整体传播生态都已经变得“扁平”的语境下,如何定位区县融媒体的受众和内容、如何在全国差异性极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中,因地制宜地设计融媒体的传播定位是确保其建设成功的重要基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显然不能成为全国融媒体建设的标准。”正如有受访者坦言:“你设想全国大概有2000多个县各搞一个APP,它的下载量能是多少?它的日活能是多少?”而笔者所调研的融媒体中心,其推出的重要APP装机量“现在不到1万”。另有一些其他区县的APP通过行政手段推广安装,“注册量突破20万,但日活量微乎其微”。⑩显然,行政主导的政策设计与群众需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落差,如何确保县级媒体融合的政策实施过程与本地民众的信息文化需求之间具有更好的匹配性,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2.建设资金的可持续性
与内容和功能定位相呼应的是区县融媒体中心的资金来源问题。根据笔者的调研,从目前全国状况来看,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经费来源多为政府拨款与单位拨款,各县在新媒体平台建设上的财政投入相对较少。2016年各县在县级新媒体平台建设上的投入约为23.76万元,其中东部地区投入相对较多,约为30.37万元。在经营管理上,县级融媒体以县政府及县党政其他部门为主管部门,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的自主运营为主,自筹资金运营以及吸引投融资的区县占比虽然较小,但依然有17.3%的区县在探索自筹资金的途径与方法,如,重庆巫山县对县级所有新媒体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和市场化运营,获取广告营收(谢新洲,黄杨,2018)。在笔者所调研的B市C区的融媒体中心,由于属于一线城市的较富裕区县,其融媒体中心所采用的网络内容生产管理平台(包括选题策划、采访管理、稿件审阅、播出计划等全流程在线管理)每年的成本投入在130万元左右;网络舆情搜集和管理系统的年成本在170万左右。两者相加仅网络平台的年成本就超过300万,这还不包括建设初期设备的采购和更新、办公场所的改造和租赁费用等。根据谢新洲等的调研数据,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政府拨款比例超过八成,平均投入成本近400万人民币,亦与笔者调研的数据结论相近(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2019)。
有学者也坦言在资金方面,县域范围经济规模有限,融媒体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并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除了依托中央和地方专项财政资金的支持外,还可以面向市场探索多元经营。一方面是承接地方活动和视频等媒体类业务,另一方面是探索大数据、智慧城市等跨界类业务。经营形式可以是自主经营,也可以是合作或合资经营(赵子忠,周代平,2019)。但从实际的情况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县级媒融媒体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要避免历史上区县广电走过的弯路,就必须从制度层面确保政府财政为县级融媒体提供基本运行保障,包括基本人员工资的保障和运行经费,解决长期以来县级台主要依靠自筹资金的问题(国家广电智库,2018)。
3.人事与薪酬制度的困境
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改革核心必然触及人事制度改革。县级区域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区位环境和体制内的工资收入制度,使得融媒体发展急需的专业性传播人才望而却步。目前对于区县融媒体中心人事制度的安排,延续了历史上区县广电媒体人事制度的窘境,使得从业者往往处于“体制内编制”和“体制外”的选择困境之中。
在笔者调研中,有受访者表示:“赶上工资改革后,人均(年收入)降2万,因为都按照规范工资(发放制度和标准),原来那些福利性的东西都没有了。事业单位它有一个封顶工资的问题,就不允许超过全额,你突破不了。市场聘用和事业聘用之间,只能取一头。我们原来报纸有一个骨干,要求稳定想要编制,就拼命想进体制内发展,考进来了(成为了有事业编制的员工),但收入就受到了封顶的影响;生二胎后家庭经济压力增大,他就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我跟他说你只能取一头,自己选择。” [11]一些地方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已开始对此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尝试。在汝州,(县级)市融媒体中心以汝州市广播电视总台人才体系建设为蓝本,实行“档案封闭运行、岗位薪酬管理”的双轨管理新办法,即融媒体中心所有人员,不管什么级别什么身份,统统与编内体制脱钩,档案工资、级别封闭运行。实际工作按岗位进行日常管理,根据职责分工合理设置岗位数量和管理层级,将各项工作任务量化到岗到人,并确定每个岗位的绩效标准,推行以量化考核为主的绩效考核制度。打破原来的以级别资历论薪酬的思维,根据岗位、业绩、贡献实行分配。切实拉开收入差距,实行多劳多得、上不封顶。在邳州,邳州广电“近十年来没有进一个财政在编人员,老人员逐渐减少或退居二线,台聘人员挑大梁,但组织人事部门又不会任用这些人,那么通过集团管理模式和岗位设置,给这些人一个上升通道,一个奔头,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他们的归属感”(杨丕勇,田洪文,2018)。这些地方的改革实验或许可以为全国其他地区县级媒体人事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六、结语
本文试图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广播电视制度的历史源头回溯,探寻历次县级媒体建设的国家政策和基层实施中的逻辑脉络,从中国县乡的基层治理和中央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以技术(电视、广播、以及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融媒体)的扩散中行动者的角色与动机的形塑等角度,理解中国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政治和传播制度性逻辑,并试图以县级广电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显现出的制度性困境,为现今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全国性融媒体中心建设未来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从历史视角看,县级媒体是改革开放以来“四级办台”制度设计的产物,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初创到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进入新世纪后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困境,不仅在财政上难以为继,而且在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的挑战下,其内容吸引力和传播的影响力日渐衰竭,与县级党政机构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和基层社会治理对有效政治传播的需求不相匹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政策出发点是在延续传统“四级”媒体框架的基础上,寻求基层媒体和政治传播困境的政策突破口,试图通过把政策话语与媒体融合的技术逻辑相嫁接,来实现国家整体传播战略的基层落地,同时对县级媒体的地位、角色和功能进行必要的调适,使之适应新的政治生态和传播技术条件下舆论引导和基层政治传播的新使命。
但也如本文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式政策设计意图与在地化的具体实践之间能否形成制度设计者所期待的匹配性,实际上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与上个世纪“四级办电视”政策的设计和落地过程相似,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在整体上同样呈现出中国制度下特有的党政系统主导的运动式动员特征。换言之,它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逻辑的产物。但与当年县级办电视背后强大的市场和经济效益动机相比,当下的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政治考量要远远大于其商业效益的考虑。此外,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公众在媒体和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对基层电视媒体的强大需求不同,县级融媒体在当前的文化和媒体生态中面临公众需求后劲不足和在注意力市场中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意味着无论是从财政、人才和技术的可持续性,还是与真实社会需求的对接性角度来看,县级融媒体建设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而从整体制度设计来看,县级融媒体是嵌入传统广播电视机构的组织外壳之中的,因此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一部分,县级媒体的融合发展在实质上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制度架构的限制,融合后所形成的技术制式、操作模式、内容样态,本质上是传统媒体在新技术平台上的一种形式化嫁接。这种嫁接能否在未来进一步推动媒体体制架构的整体变化、媒体机构体制性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模式的变化,还是最终会作为“规定动作”而成为一种行政逻辑自我实现的仪式性存在,依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注释:
①截至2017年3月底全国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共计2050家,截至2015年6月全国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共计1998家。
②早在大跃进时期,中国大陆就迅速开设了包括北京、吉林等多个省级电视台。1958年至1960年期间,中国29个省中的16个都陆续开设了电视台。但大跃进式的建设脱离实际,观众寥寥,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地区一共拥有的黑白电视机台数仅有12000台。到了1962年,36座电视台中有31台都被要求关停,仅留下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和天津台还保留运作。转引自:Huang, Y.& Yu, X. (1997).?Broadcasting and Politics: Chinese television in the Mao Era1958-1976.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17(4)563-574.
③关于南漳县内容的历史资料来自于当时在湖北南漳县广播电视局工作的章波发表的文章作为二手资料进行的分析,特此说明。
④所谓“五通”工程,指通路、通电、通水、通广播、通电话。
⑤根据2018年9月13日对某一线城市某区融媒体中心的调研录音资料整理。
⑥根据2018年12月9日对某区融媒体中心负责人的调研录音资料整理。
⑦根据2019年1月5日对某一线城市某区融媒体中心的调研录音资料整理。
⑧根据2018年9月13日对某一线城市某区融媒体中心的调研录音资料整理。
⑨根据2018年9月13日对某一线城市某区融媒体中心的调研录音资料整理。
⑩根据2018年9月13日对某一线城市某区融媒体中心的调研录音资料整理。
[11]根据2018年9月13日对某一线城市某区融媒体中心的调研录音资料整理。
参考文献:
杜智涛,张丹丹,柏小林(2019)。融合与跨越:近10年来新媒体研究的多维视域。《信息资源管理学报》,9(3),19-32。
葛娴(1983)。以宣传为中心改革广播电视——记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新闻战线》,(5),15,2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01)。《关于市(地)、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检索于https://law.lawtime.cn/d423684428778.html
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2018年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检索于http://www.cbbr.com.cn/article/130425.html
国家广电智库(2018)。《县级广电要成为融媒体中心建设主体》。检索于http://www.sohu.com/a/271826237_657264
国家广电智库(2018)。《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新一轮事关全局的基层媒体改革》。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239987921_657264
郭镇之(1990)。新时期中国电视的10年。《新闻研究资料》,(2),18。
胡鞍钢,张晓群(2004)。中国传媒普及率追赶的实证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4),3-9,95。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2017)。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关于扶持县级广播电视台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检索于http://gdj.hubei.gov.cn/fbjd/xxgkml/zcwj/gfwj/201811/t20181113_243831.shtml黄升民,宋红梅(2007)。新趋势、新逻辑与新形态——区域媒体的形成轨迹与发展趋势解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5-8。
今评媒(2017)。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对县级广播电视台进行财政支持。检索于http://www.sohu.com/a/156462664_593805
潘祥辉(2019)。“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70年。《浙江学刊》,(6),4-1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1982)。检索于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328229.htm中广互联(2017)。山东大部分区级广播电视台将关停,改为广播电视站。检索于https://m.ithome.com/html/309217.htm
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第21-46页)。厦门:鹭江出版社。
新华网(2015)。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30/c_1115773120.htm习近平(1990)。从政杂谈。检索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016/c389908-25846520.html
谢新洲,黄杨(2018)。我国县级融媒体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中国记者》,(10),53-56。
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2019)。县级媒体融合的现状,路径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和四县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新闻记者》,(3),56-71。
杨丕勇,田洪文(2018)。顶层设计,匹配机制,全面融合——地方电视台融媒体建设的思考。《新闻窗》,(5),65。
章波(1988)。关于“四级办台、混合覆盖”方针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6),71-73。
章波(1994)。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取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3),84-85。
张弛(2005)。从一个县级电视台的生存现状看我国地方电视媒体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重庆。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1986)。《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1987)。《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1988)。《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检索于https://news.qq.com/a/20111116/000896.htm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7),36-50。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文化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黄琳(2015年10月8日)。浙江:加强县级广电新闻传播力建设。《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检索于http://www.gapp.gov.cn/dingshicaiji/contents/3975/265998.shtml周雪光(2017)。《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赵玉明(2006)。《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的通知。检索于https://www.pkulaw.com/chl/56140.html
赵子忠,周代平(2019)。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模式与出路。《网络传播》,(2),72-73。
Huang, Y. & Yu, X. (1997). Broadcasting and Politics: Chinese television in the Mao Era1958-1976.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17(4)563-574. doi: 10.1080/01439689700261001
Jan, G. (1967). Radio Propaganda in Chinese Villages. Asian Survey, 7(5)305-315. doi:10.2307/2642659
Keane, M.(1998). Televis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 22(4)475-503. doi:10.1080/10357829808713211
RantanenT. (2004). The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周逵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黄典林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媒体融合条件下广播电视业创新发展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7CXW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