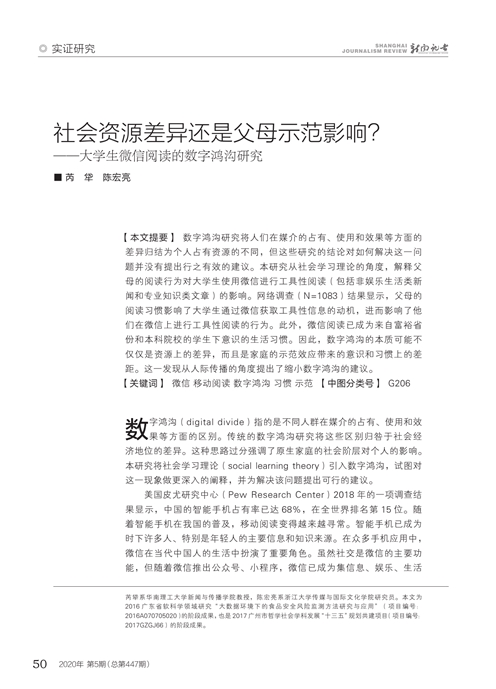社会资源差异还是父母示范影响?
——大学生微信阅读的数字鸿沟研究
■芮牮 陈宏亮
【本文提要】数字鸿沟研究将人们在媒介的占有、使用和效果等方面的差异归结为个人占有资源的不同,但这些研究的结论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本研究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解释父母的阅读行为对大学生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包括非娱乐生活类新闻和专业知识类文章)的影响。网络调查(N=1083)结果显示,父母的阅读习惯影响了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动机,进而影响了他们在微信上进行工具性阅读的行为。此外,微信阅读已成为来自富裕省份和本科院校的学生下意识的生活习惯。因此,数字鸿沟的本质可能不仅仅是资源上的差异,而且是家庭的示范效应带来的意识和习惯上的差距。这一发现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提出了缩小数字鸿沟的建议。
【关键词】微信 移动阅读 数字鸿沟 习惯 示范
【中图分类号】G206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的是不同人群在媒介的占有、使用和效果等方面的区别。传统的数字鸿沟研究将这些区别归咎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这种思路过分强调了原生家庭的社会阶层对个人的影响。本研究将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引入数字鸿沟,试图对这一现象做更深入的阐释,并为解决该问题提出可行的建议。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智能手机占有率已达68%,在全世界排名第15位。随着智能手机在我国的普及,移动阅读变得越来越寻常。智能手机已成为时下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主要信息和知识来源。在众多手机应用中,微信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社交是微信的主要功能,但随着微信推出公众号、小程序,微信已成为集信息、娱乐、生活等不同功能于一体的新媒体平台。一个例证便是,通过微信进行阅读的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例如,2014年34.4%的成年人通过微信进行过阅读,这一数字在2015年就增长至51.9%;而在所有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阅读的用户中,87.4%的人选择了微信作为移动阅读的平台(张贺,2016)。
微信已成为当代中国人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和所有新媒体平台一样,微信上也充斥着种类繁多、题材各异的文章,例如养生、娱乐、专业资讯和政经类新闻 (腾讯科技,2014)。长期阅读不同题材的文章,自然会对用户产生不同的影响。作为微信的主要用户群体之一,大学生正处在关键的人生阶段,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型,所以易受外界影响。因此,大学生阅读何种类型的微信文章,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乃至人格的发展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关注了两种阅读:(1)非娱乐生活类新闻——例如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2)专业知识类文章。按照赵联飞(2015)的定义,我们将这两类阅读统一归为工具性阅读,即阅读者可以从文章中获取重要信息,丰富知识,提升素养,促进个人发展。与出于放松、休闲、社交等目的而进行的非工具性阅读相比,工具性阅读的内容更复杂甚至艰深,对阅读者的动机、知识储备、阅读技能甚至自制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移动阅读日益普遍,媒体内容日趋泛娱乐化,因此,工具性阅读这一媒介使用行为可能更能反映当前社会中的数字鸿沟。现有的研究已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解释了数字鸿沟的成因,但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上却没有提出很好的建议。本研究将通过社会学习理论,揭示父母的阅读习惯对大学生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影响,从而体现父母的示范效应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为缩小数字鸿沟提出解决之道。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鸿沟的定义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普及,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这些技术对社会是否有负面影响。于是,数字鸿沟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并在相关研究中衍生出三道数字鸿沟。
早期研究将数字鸿沟定义为不同人群对新媒体、新技术的接入差距(Cooper & Kimmelman, 1999),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拥有更多资源,可以获取、占有更多媒体和技术资源。第一道数字鸿沟因此被称为接入沟(胡鞍钢,2002)。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新媒体的占有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都存在广泛差异(Chinn & Fairlie, 2007; Fox, 2011)。例如,赵联飞(2015)发现,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和重点院校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拥有上网设备。
随着技术成本的降低,互联网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及开来,因此有学者认为接入沟正被逐渐填平(Devine, 2001)。与此同时,大量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在新媒体的使用目的和方式上存在不同(Hargittai & Hinnant, 2008; Lee & Kim, 2014; Micheli, 2016; 宋红岩,2016),第二道数字鸿沟由此体现为使用沟(Hargittai & Hinnant, 2008)。社会经济地位对新媒体使用沟的影响在许多国家均得到了验证。例如,一项针对韩国手机用户的调查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通过手机获取信息和重要的工作、学习资源(Lee & Kim, 2014)。Micheli(2016)发现,来自精英阶层的意大利高中生更多使用社交媒体经营自己的人脉,培育社会资本;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意大利高中生则更多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娱乐休闲活动。在我国,有关使用沟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例如,宋红岩(2016)针对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显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不仅使用各类交友软件更多,使用阅读类、商务交易类和生活服务类的手机功能也更多。周裕琼的一系列研究着重关注数字鸿沟在代际上的体现,她将子女和父母在新媒体的使用与效果方面的差异命名为“数字代沟”(周裕琼,2014)。她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数字代沟越小;而子女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数字代沟则越大(周裕琼,2014;林枫、周裕琼、李博,2017)。
最后,第三道数字鸿沟主要关注新媒体的使用对个人认知、态度、观念、行为等方面的影响,被称为效果沟(韦路、张明新,2006)。经典研究将效果沟简化为有关政治内容和公共事务的知识差异(Selwyn, 2004)。近年来的研究对效果沟的定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具体包括数字素养(周裕琼、林枫,2018)、电脑和互联网知识(Gui & Argentin, 2011)、健康素养等(刘智妍,2019)。例如,中国青年人的数字素养明显高于其父辈和祖辈(周裕琼、林枫,2018);意大利中学生对电脑和网络知识的掌握则受到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Gui & Argentin, 2011)。
综上所述,数字鸿沟的基本逻辑是,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资源决定了个体在媒介的接入、使用和效果等各个环节的不同。虽然这些研究揭示了数字鸿沟的本质,但对解决这一问题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在如何缩小数字鸿沟这一问题上,现有的研究提供了两条思路:第一条就是为来自贫困地区和家庭的孩子提供有关新媒体知识和技能的教育(Li & Ranieri, 2013; Wang & Wong, 2019)。其次,周裕琼的一系列研究将老年人定义为新媒体的弱势群体,她发现,在家庭内部,年轻人正在教父母、祖父母如何使用新媒体(周裕琼,2014、2018),这种“数字反哺”的现象在人际传播层面为缩小数字鸿沟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本研究试图提出第三种缩小数字鸿沟的思路。与周裕琼的研究相似,本研究也将解决这一问题的环境放在了家庭内部。但本研究试图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揭示父母的示范作用对子女在使用新媒体的动机和行为方面的影响。
(二)社会学习理论和数字鸿沟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脱胎于班杜拉的一系列有关媒体暴力内容的实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班杜拉发现,媒体呈现的暴力内容会影响观众的行为,当儿童观看了含有暴力内容的电视节目后,特别是当节目中的施暴者未受任何惩罚时,儿童会展现出更多的暴力行为(Bandura & McDonald, 1963)。据此,班杜拉提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类行为是通过模仿习得的,而媒体是人类的重要模仿对象(Bandura, 1978),媒体不但示范如何实施某种行为,而且展示了实施这种行为的后果。因此,人类从媒体学到的不仅是如何完成某项行为,更是这项行为的后果。班杜拉将通过媒体展示学习的这一过程称为“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 Bandura, 1978)。
之后有关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主要分成了传播学和发展心理学两个流派。传播学的相关研究将社会学习理论扩展至不同的行为和语境中,例如健康传播(DeSmet, Shegog, Ryckeghem, Crombez, & De Bourdeaudhuij, 2015)和跨文化传播(Ward & Kennedy, 1999);学习的对象也从传统媒体延伸至新媒体(Peng, 2009)。总而言之,传播学有关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媒介对受众的示范效应,虽然这种示范效应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受到个人性格、外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Bandura, 2001a),但在传播学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媒介的示范效应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
而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的相关研究则着重探讨观察学习这一过程的心理学机制。事实上,早在班杜拉提出社会学习理论之前,发展心理学的早期研究就指出了外界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只不过当时的研究并未注意到人类行为的习得性这一特征(Grusec, 1992)。因此,社会学习理论不仅继承了早期发展心理学研究强调外界环境对人类观念和行为影响这一基本观点,还通过提出“观察学习”的概念,将外界环境的示范效应提到了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位置(Grusec, 1992)。发展心理学有关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指出,人类模仿的对象不局限于媒体,还包括父母、朋友、兄弟姐妹等任何个人与群体。这些外界环境主要通过三个过程对人施加影响: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自我效能(self-efficacy)。首先,人们通过观察他人,学习如何完成某项行为(即观察学习,Bandura, 2001b)。其次,在实施这项行为的过程中,人们会收到来自外界环境或正面或负面的反馈,这些反馈形成了人们对这项行为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构成了自我调节的观念基础(Bandura, 2001b; Zimmerman, 2000)。换言之,自我调节指的是关于某种行为是否正当或者在某种情境下是否妥当的价值观,直接影响人类是否实施该行为。第三,在实施这项行为的过程中,人们还会形成对自己是否可以完成这项行为的判断,即自我效能(Bandura, 2001b; Schwarzer, 2014)。综上所述,观察学习教会了人们怎么做,自我效能告诉人们能不能做,自我调节影响了人们会不会真的去做。
这三个概念在大学生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和专业知识类文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父母的阅读习惯与子女的阅读水平密切相关。有阅读习惯的父母,其子女不但会更早开始阅读,而且更有可能养成在课余时间阅读的习惯(Greaney, 1986; Morrow, 1983);这直接体现了观察学习的影响。其次,成长于父母有阅读习惯的家庭,孩子更加认同阅读的重要性,对自身阅读能力的判断也越高(Schunk & Zimmerman, 2007)。换言之,父母的阅读习惯也影响了子女与阅读相关的自我调节与自我效能。
工具性阅读对读者的文化知识和阅读技能都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类文章感兴趣。所以,若按照传统的数字鸿沟理论,单纯地将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差异归结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恐怕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的成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只能保证他们是否可以为孩子提供优良的学习资源,却无法保证孩子一定可以掌握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因为知识技能是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如果大学生成长于一个父母有阅读习惯的家庭环境里,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兴趣便会更强烈,也就会更积极主动地利用新媒体进行工具性阅读,这体现了父母的示范效应对数字鸿沟的影响。
二、研究问题和假设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除了考虑经典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本研究将重点探究父母的阅读习惯对大学生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影响。首先,根据使用满足理论(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3),动机和行为是媒介使用的两个重要维度。所以,我们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大学生通过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动机和行为两个变量。
其次,我们认为,父母的阅读习惯将影响大学生通过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动机与行为。有阅读习惯的父母,其子女使用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动机越强烈,从而激发其利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行为。换言之,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动机是父母阅读习惯(自变量)与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因变量)的中介变量。
H1: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阅读动机是父母阅读习惯与使用微信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的中介变量。
H2: 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阅读动机是父母阅读习惯与使用微信阅读专业知识类文章的中介变量。
此外,本研究将沿袭传统的数字鸿沟研究,继续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影响。这些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三个层面:宏观(省份、城乡)、中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微观(个人就读的大学层次)。通过比较父母阅读习惯与这些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本研究将探讨在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这一现象中,到底是父母的资源还是行为示范发挥了更重要的影响。(图1 图1见本期第54页)展示了所有的研究假设和问题。
RQ1:省份、城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收入水平、个人就读大学的层次对通过微信获得工具性信息的动机有何影响?
RQ2:省份、城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收入水平、个人就读大学的层次对使用微信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有何影响?
RQ3:省份、城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收入水平、个人就读大学的层次对使用微信阅读专业知识类文章有何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和抽样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由于目标人群是全日制大学在校本科生当中的微信使用者,我们联系了全国50所本科和专科院校的老师,请他们将问卷的链接发给本校学生。我们总计收到1291份回答,排除无效问卷后,最终样本量为1083。
(二)问卷设计
问卷的问题涵盖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三个部分。
1.因变量
我们借鉴了Alhabash & Ma(2017)的社交媒体使用动机的量表,测量了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得工具性信息的动机。具体问题有三个:我阅读微信文章是为了获取最新的新闻及时事评论,我阅读微信文章是为了获取当今的时事热点,我阅读微信文章是为了获取专业工具性信息。该量表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克隆巴赫系数:0.79;均值:4.58;标准差:1.07)。
此外,我们让受调查者从一个列表中选出他们经常阅读的文章。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包括两个选项:政经法军类新闻、新闻时事评论。阅读专业知识文章包括以下四个选项:历史文化、艺术文学、宗教、科学技术。为了防止遗漏,我们还添加了一个“其他”选项,让受调查者写出他们经常阅读却未出现在列表中的文章类型。我们依次检验了受访者的回答,将不符合上述两种阅读类型的回答排除在外。最终,选择经常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的均值为0.91(标准差:0.82;最小值:0;最大值:2),选择经常阅读专业知识文章的均值为1.00(标准差:1.00;最小值:0;最大值:4)。
2.自变量
我们让受调查者填写父母在业余时间的阅读频率(1=没有阅读习惯,2=两个月一次,3=每个月一次,4=每两周一次,5=每周一次,6=每周几次,7=每天一次,8=每天几次)。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受调查者父母的平均阅读频率在每两周一次到每周一次之间(均值:4.21;标准差:2.79;最小值:1;最大值:8)。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及上述五个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在回收所得的最终有效问卷样本中,女性共815人(75.25%),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20.84岁(标准差:2.29)。
我们让受访者填写他们来自的省份,受调查者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我国2017年各省人均GDP排名(北京时间,2018),我们将这些省份分为富裕、中等、贫穷三个等级(1=贫穷,排名21以后;2=中等,排名11-20;3=富裕,排名前10)。其中,来自富裕省份的受访者有395人(36.5%),中等省份的有102人(9.4%),贫穷省份的有534人(49.3%),另有52人(4.8%)未提供此信息。我们还让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家乡是直辖市、地级市、县城、乡镇还是自然村,并将他们的回答分为两类——城市(601人)、非城市(475人)。以上为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我们让受访者从以下列表中分别选出其父母的最高学历——无任何教育背景、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然后将二者相加,取其平均数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均值:3.43;标准差:1.22;最小值:1;最大值:8)。此外,参照毕马威的中国2017年收入指数(KPMG, 2017),我们制定了家庭月收入列表,让受访者从该列表中选出其父母收入水平:低于3500元,3500-5000元,5001-8000元,8001-12500元,12501-38500元,38501-83500元,高于83500元(均值:2.82;标准差:1.40;最小值:1;最大值:7)。以上为中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最后,微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为受调查者就读的学校层次(0=专科,1=本科)。专科院校的学生366人(33.8%),本科院校的学生717人(66.2%)。
(三)数据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由Andrew Hayes开发的Process Macro 3.0进行中介效果的检测。中介效应由其效应值(effect size)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显示,若置信区间包括0,则中介效应不显著,推翻研究假设,反之,则研究假设成立(Hayes, 2017)。
四、研究发现
(一)中介效应:父母的示范作用
(表1 表1见本期第55页)和(表2 表2见本期第56页)是所有数据分析的结果。首先,有阅读习惯的父母,其子女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动机更强烈(B=0.03,p<0.05),且这种动机导致他们在微信上阅读更多的非娱乐生活类新闻(B=0.21,p<0.001;(表1 表1见本期第55页))。中介关系的效应值为0.02,其置信区间为[0.01,0.04]。因为该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中介效应成立。H1成立。因为父母阅读习惯对在微信上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B=0.01,p=0.30),因此该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
其次,有阅读习惯的父母,其子女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动机更强烈(B=0.03,p<0.05),且这种动机导致他们在微信上阅读更多的专业知识类文章(B=0.09,p<0.01;见表2)。中介关系的效应值为0.01,其置信区间为[0.001,0.02]。因为该置信区间不包含0,所以中介效应成立。H2成立。因为父母阅读习惯对在微信上阅读专业知识类文章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B=0.02,p=0.22),因此该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父母的阅读习惯对子女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动机有正向影响,但对他们的两种阅读行为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父母的阅读习惯对大学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行为上的,而是间接的、观念上的。
(二)社会经济地位
在宏观层面,家乡省份的富裕程度虽然与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动机仅呈现出边缘性显著的关系(B=0.07,p=0.07),但却直接影响了通过微信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的行为(B=0.07,p<0.05)和专业知识类文章的行为(B=0.10,p<0.01)。出身城乡对阅读的动机和两种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
在中观层面,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对大学生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动机及两种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至少在家庭这个层面,对子女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产生主要影响的并非父母占有的资源而是他们的行为示范。
在微观层面,专科和本科院校的学生在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动机上不存在显著差别。然而,本科院校的学生比专科院校的学生更多地使用微信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B=0.20,p<0.001)。但这两者在使用微信阅读专业类文章这一行为上却不存在显著差别。这可能是因为微信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至少在专业知识类文章的微信阅读上,使用沟似乎正在大学生群体内部被填平。
最后,年龄对通过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动机及两种行为均无显著性影响。在阅读动机上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具体到行为时,男生比女生更多地使用微信阅读非娱乐生活类新闻(B=0.22,p<0.001)和专业类文章(B=0.45,p<0.001),这可能是由性别导致的兴趣差异所致。
五、研究讨论和结语
正如本文开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所显示的,新媒体的接入沟在我国已被逐渐填平,但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沟仍然存在。与以往很多研究不同,我们选择了大学生这个受教育程度较高、数字素养较高的群体,以及微信这个已被大学生广泛接受的新媒体平台。因此,在本研究中,接入沟和使用沟已经被大大缩小了。然而,我们仍然发现了三类造成使用沟的因素——父母阅读习惯、家乡省份的富裕程度及个人就读院校的层次。
首先,通过比较父母的受教育、收入水平及其阅读习惯对大学生使用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影响,我们试图解释数字鸿沟到底是资源分布的不均还是父母示范效应的结果。我们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并没有影响大学生通过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动机及行为。相反,父母的阅读习惯却影响了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的动机。这说明,至少在本研究的语境下,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并非体现在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而是他们以身作则的示范效应。当然,这个结果与本研究探讨的具体问题息息相关——毕竟,使用新媒体进行工具性阅读对人们的知识、技能及动机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父母的阅读习惯为孩子树立了榜样,能帮助他们培养起主动阅读的意识和兴趣,这一点与许多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不谋而合。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无意将社会经济地位(资源)与父母的阅读习惯(示范)对立起来。很多研究显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阅读习惯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通过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动机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两者间的关系可能是经由父母阅读习惯作为中介变量的完全中介效应。虽然本研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可能的完全中介效应,但考虑到本研究使用的样本(非随机抽样)、对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和阅读习惯的测量(单个问题而非量表)以及数据的类型(自我汇报而非客观行为数据),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完全中介效应的可能。然而,就直接影响而言,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父母的教育和收入水平没有直接影响工具性阅读的动机,反而是父母的阅读习惯起到了直接作用。鉴于直接影响的效果往往强于间接影响,我们认为,至少在通过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动机这一点上,父母的阅读习惯即示范效应起到了更强的作用。
使用沟的研究指出,人们之所以会在新媒体使用动机和行为上存在不同,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了个人在知识、技能、观念等方面的差距(Hargittai & Hinnant, 2008)。例如,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会利用新媒体主动积累更多信息和社会资源(Lee & Kim, 2014; Micheli, 2016)。因此,之所以会产生使用沟,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占有的资源不同,而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水平不同。换言之,原生家庭虽然能给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长环境,却并不意味着子女一定能将这些资源转换为超越常人的理念和知识。毕竟,知识的积累需要后天的学习,理念的培养来自耳濡目染和身体力行。因此,将数字鸿沟完全归咎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却忽视了个人学习的作用,这种思路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提出了一条缩小数字鸿沟的途径。如果大学生能坚持阅读习惯,等他们为人父母后,可以对他们的孩子施加正面且长远的影响。因此,缩小数字鸿沟或许是个细水长流的过程,而这千里之行的起点正是家庭,是家长自身的行为。这个结论对数字鸿沟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多数研究仅仅揭示了数字鸿沟的成因,却止步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指出,在家庭内部,父母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子女,可能是更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通过家庭内部的人际传播缩小数字鸿沟,这个思路与周裕琼有关数字反哺的一系列研究(周裕琼,2014,2018)不谋而合。
此外,我们还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影响集中在阅读动机而非行为上。许多心理学、行为学研究指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例如,有研究指出,在初中阶段,同伴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父母的影响(Biddle, Bank & Marlin, 1980);到了高中阶段,同伴的影响开始减弱,个人行为开始呈现出独立自主的特点(Kirby, Levine & Inchley, 2011)。因此,到了大学阶段,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已经很弱了。但本研究显示,到了大学阶段,阅读的意识仍然受到父母的影响。这说明,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子女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减弱,但对其观念、意识的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除了父母的示范效应,本研究还发现,来自富裕省份和本科院校的大学生虽然主观动机上没有刻意使用微信获取工具性信息,但他们的客观行为却体现出,微信已经成为他们获取工具性信息的重要渠道。这说明,对这两类群体而言,通过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或许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是数字鸿沟的一个更高境界。媒介使用不仅具有功能性特征,还有日常化、习惯性的一面,因此,研究媒介的使用者,不但需要了解他们的主观动机,还要理解他们下意识的行为,因为这种下意识的行为更能反映他们使用媒介的真实状态(Potter, 2009)。在本研究中,这种下意识的行为模式是与宏观层面的家乡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人教育程度密不可分的。家乡代表的是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先天影响,而教育程度代表了个人奋斗的后天作用。因此,数字鸿沟虽然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但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逐渐缩小。
虽然本研究发展了现有的数字鸿沟研究,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我们的抽样方式属于非概率抽样,检验的新媒体平台仅限于微信,这些不足都会影响我们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其次,我们的样本中女性占了大多数,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结果的内部效度。此外,我们对微信阅读的测量也存在不足。具体来说,我们让受调查者选出他们经常阅读的微信文章,而不是让他们估算自己阅读每种类型文章的时间、频率或对每种文章的喜爱程度。但是,估算自己阅读每种类型文章的时间、频率或每种文章的喜好程度也可能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更精确的方法是利用数据挖掘进行测量。
除了这些方法论上的局限,本研究在理论上的缺陷也值得注意。虽然我们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通过微信进行工具性阅读的直接影响不及父母的阅读习惯,但正如前文所述,现有的数据并不能排除父母的阅读习惯受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所以,针对本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的非显著影响,读者不能过度解读,更不能做因果推论,而有待于后续研究通过实验或纵贯性问卷调查来进一步验证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阅读习惯对子女的影响。
综合本研究的发现,数字鸿沟是宏观层面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中观层面的父母示范效应,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人奋斗共同影响的产物。因此,缩小乃至填平数字鸿沟,不仅需要在社会层面推动经济文化建设,在学校层面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更需要父母在家庭这个人生中第一所学校为子女树立后天努力的榜样。媒介与人的关系受到各种社会经济差异的影响,但消弭这种不平等并不一定需要依靠宏观层面的建设。在家庭内部,依靠点对点的人际传播,我们或可迈出实现数字社会大同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北京时间(2018)。2017年中国各省人均GDP排名、世界排名。检索于https://item.btime.com/m_2s1cmhy8m1y.
胡鞍钢(2002)。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中国社会科学》,(3),34-48。
林枫,周裕琼,李博(2017)。同一个家庭不同的微信:大学生vs父母的数字代沟研究。《新闻大学》,(3),99-106。
刘智妍(2019)。权健背后的数字鸿沟:我在这头,父母在那头。《中国社会工作》,(5),44-45。
宋红岩(2016)。“数字鸿沟”抑或“信息赋权”?——基于长三角农民工手机使用的调研研究。《现代传播》,(6),132-137。
腾讯科技(2014)。微信上最受欢迎转发最多的文章类型分析。检索于http://www.5icool.org/a/201412/a9572.html.
韦路,张明新(2006)。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新闻与传播研究》,(4),43-53。
张贺(2016)。日均手机阅读首次超过1小时,微信阅读人数过半。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9/c_128907568.htm.
赵联飞(2015)。中国大学生中的三道互联网鸿沟——基于全国12所高校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6),145-168。
周裕琼(2014)。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现代传播》,(2),117-123。
周裕琼(2018)。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7),66-86。
周裕琼,林枫(2018)。数字代沟的概念化与操作化:基于全国家庭祖孙三代问卷调查的初次尝试。《国际新闻界》,(9),6-28。
AlhabashS. & Ma, M. (2017). A tale of four platforms: Motivations and uses of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and Snapcha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Media & Society3(1).
Bandura, A. (1978).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aggress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8(3)12-29.
Bandura, A. (2001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Psychology, 3(3)265-299.
Bandura, A. (2001b).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1)1-26.
Bandura, A. & McDonald, F. J. (1963).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inforcement and the behavior of models in shaping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274-281.
BiddleB.J.Bank, B. J. & Marlin, M. M. (1980). Social determinants of adolescent drinking: What they thinkwhat they do, and what I think and do.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41215-241.
Chinn, M. D. & FairlieR. W. (2007).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global digital divide: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9(1)16-44.
CooperM.& KimmelmanG. (1999). The digital divide confronts the 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 Economic reality versus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Consumer Union.
DevineK. (2001).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e Scientist15(1)28-28.
DeSmetA.Shegog, R.Van RyckeghemD.CrombezG. & De BourdeaudhuijI. (2015).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interventions for sexual health promotion involving serious digital games. Games for Health Journal4(2)78-90.
Fox, S. (2011). Americans living with disability and their technology profi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1/01/21/americans-living-with-disability-and-their-technology-profile/
Greaney, V. (1986). Parental influences on reading. The Reading Teacher39(8)813-818.
GrusecJ. E. (1992).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The legacies of Robert Sears and Albert Bandura.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5)776-786.
Gui, M. & Argentin, G. (2011). Digital skills of Internet natives: Different forms of digital literacy in a random sample of Northern Italian high school students. New Media and Society13(6)963-980.
Hargittai, E. & HinnantA. (2008). Digital inequality: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use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5)602-621.
Hayes, A.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NY: Guilford.
KatzE.BlumlerJ. G. & GurevitchM. (1973).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37(4)509-523.
Kirby, J.LevinK.A. & InchleyJ. (2011). Parental and peer influences on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Scottish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8785-793.
KPMG. (2017). China-Income Tax. Retrieved from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1/12/china-income-tax.html
Lee, J. & KimJ. (2014). Socio-demographic gaps in mobile use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 multi-group analysis of the mobile divide model.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Society17(8)917-936.
LiY. & RanieriM. (2013). Educational and social correlates of the digital divide for rural and urban children: A study 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a provincial city of China. Computers and Education60(1)197-209.
Micheli, M. (2016).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low-income teenagers: between opportunity and inequalit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9(5)565-581.
MorrowL. (1983). Home and school correlates of early interest in literatur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6221-230.
PengW. (2009).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 computer game to promote a healthy diet for young adults. Health Communication24(2)115-127.
PotterJ. (2009). Conceptualizing the audience. In R. Nabi & M. Oliver (eds.)The SAGE Handbook of Media Processes and Effects (pp. 19-34).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hunkD. & ZimmermanB. (2007). Influencing children’s self-efficacy and self-regul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modeling. Reading & Writing Quarterly237-25.
Schwarzer, R. (2014). Self-efficacy: Thought control of action.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SelwynN. (2004).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and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and Society6(3)341-362.
WangX. & Wong, B. (2019). Bridging knowledge divides utilizing cloud computing learning resources in underfunded schools: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57(3)591-617.
WardC. & KennedyA.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3(4)659-677.
Zimmerman, B. J. (2000). Attaining self-regulation: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M. BoekaertsP. Pintrich & M. Zeidner (eds.)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pp. 13-29).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芮牮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宏亮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本文为2016广东省软科学领域研究“大数据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法研究与应用”(项目编号:2016A070705020)的阶段成果,也是2017广州市哲学社会学科发展“十三五”规划共建项目(项目编号:2017GZGJ66)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