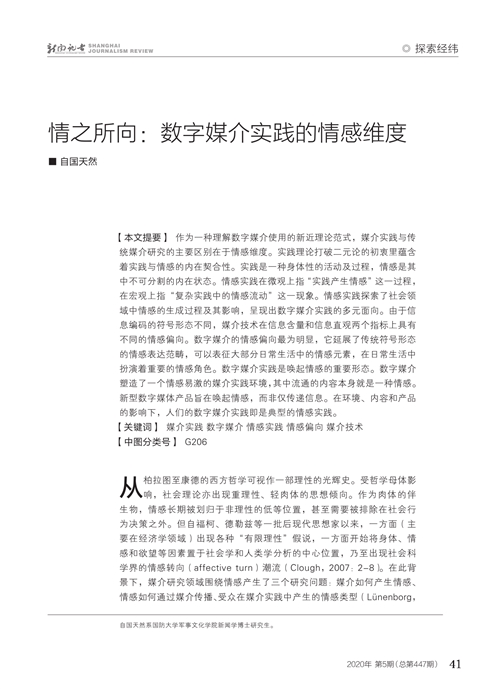情之所向: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
■自国天然
【本文提要】作为一种理解数字媒介使用的新近理论范式,媒介实践与传统媒介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情感维度。实践理论打破二元论的初衷里蕴含着实践与情感的内在契合性。实践是一种身体性的活动及过程,情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内在状态。情感实践在微观上指“实践产生情感”这一过程,在宏观上指“复杂实践中的情感流动”这一现象。情感实践探索了社会领域中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其影响,呈现出数字媒介实践的多元面向。由于信息编码的符号形态不同,媒介技术在信息含量和信息直观两个指标上具有不同的情感偏向。数字媒介的情感偏向最为明显,它延展了传统符号形态的情感表达范畴,可以表征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情感角色。数字媒介实践是唤起情感的重要形态。数字媒介塑造了一个情感易激的媒介实践环境,其中流通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新型数字媒体产品旨在唤起情感,而非仅传递信息。在环境、内容和产品的影响下,人们的数字媒介实践即是典型的情感实践。
【关键词】媒介实践 数字媒介 情感实践 情感偏向 媒介技术
【中图分类号】G206
从柏拉图至康德的西方哲学可视作一部理性的光辉史。受哲学母体影响,社会理论亦出现重理性、轻肉体的思想倾向。作为肉体的伴生物,情感长期被划归于非理性的低等位置,甚至需要被排除在社会行为决策之外。但自福柯、德勒兹等一批后现代思想家以来,一方面(主要在经济学领域)出现各种“有限理性”假说,一方面开始将身体、情感和欲望等因素置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的中心位置,乃至出现社会科学界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潮流(Clough, 2007:2-8)。在此背景下,媒介研究领域围绕情感产生了三个研究问题:媒介如何产生情感、情感如何通过媒介传播、受众在媒介实践中产生的情感类型(Lünenborg, Maier, 2018)。若从媒介实践范式来理解,这些问题都旨在探讨媒介实践中情感的多重功能。媒介实践范式主张在日常生活的脉络中考察人与媒介技术的互构关系,在具体情境中分析媒介使用的细微一面(自国天然,2019)。作为这些细碎日常实践的伴随状态,情感既是具身的(呈现为个体化的情感状态),也是脱域的(呈现为集体化的情感表征),它由此成为在多个维度连接数字媒介实践的线索。因此,作为理解数字媒介使用的理论范式,情感维度是其区别于传统媒介研究的主要特征。
为了深入理解“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本文通过以下三个部分渐次展开讨论:第一,基于实践理论的情感转向脉络,讨论实践与情感的内在联系;第二,被媒介信息编码形态型塑的情感偏向,成为情感实践中的“媒介变量”,而数字媒介则是情感偏向最强的媒介形态;第三,基于当前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现象,探讨数字媒介如何在实践中激发社会成员的情感体验过程,又如何在环境、内容和产品三个层面上引发情感实践。
一、实践理论中的情感维度
社会领域中的情感问题研究流派众多,包括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情感控制理论(affect control theory)、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等(Stets, Turner, 2014:1)。而实践理论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取向,其过程性、具身性和日常性特征使其与情感高度契合,甚至有学者认为情感实践是其最有前途的发展方向(Wetherell, 2012:4)。
情感与实践的紧密关联,可见于实践理论诞生的初衷——打破二元论。无论是主观和客观、文化和自然、个体和社会,二元思维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决定论之中,要么“A决定B”,要么“B决定A”。在二元框架下,情感与理性被对立起来,人类实践的成功根本上仰赖于(实践)理性的参与,甚至狭义的实践就单指一种理智行为(周东启,2011),而情感不过是人类实践的“残余物”。实践与情感也由此被分割开来。目前有三种路径来调和二元论的缺陷:第一,引入第三个概念来调和二元冲突,形成某种三元论(谢晶,2015),或者干脆另起炉灶,创造另一套三元的概念结构,比如布迪厄试图用场域、资本和惯习来解释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之关系;第二,用一元论来统合和超越二元框架,这条线索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的一元本体论延续到如今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s)和情感理论(affect theories)的探索(Fox, Alldred, 2018);第三,放弃一统式的理论野心,用复杂元素的互动过程来解释社会运行规律,比如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若如夏兹金(Theodore R. Schatzki)将实践理论视作一种分析取向,那么实践论就同时包含了一元论和复杂元素论,实践既可以理解为一种构成主体和客体的基础(一元论),也可以视为“一系列主客观组成元素的集合体”(复杂元素论)(顾洁,2018)。前者将实践看作一种本体,后者将实践看作一种过程。在过程视角下,实践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开放式互动过程,多种在场或不在场的元素都形塑了人类实践。以“玩手机”这一实践为例,既包含人的元素,如手指、动机、认知和情感;也包含物的元素,如设备、网络信号、应用软件、网络电磁空间;还包含机构或系统的元素,如运营商、手机厂商、互联网公司等等。
在调和二元论的实践取向之中,实践不再仅仅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情感亦非不足为道的“残余物”,而是无法忽视的一种实践因素。情感或作为推动实践的动力,或成为实践之目的(满足情感需求),两者因而具有内在契合性。在具体的实践论取向下亦是如此:当实践作为一种本体时,无论其结果是否符合特定成员的预期,都会产生某种情感状态(特纳,2007/2009:75-76);当作为一种复杂要素的互动过程时,实践本身就蕴含着情感元素,而且都指向某种情感需求,具有某种情感调节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实践与情感的契合,也反映了人们对理性与情感关系的再认识,即理性与情感是人类实践的协同要素。
在实践与情感这两个概念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有两位德国社会学家分别对两者的概念做了描述性定义。Andreas Reckwitz(2016:118)描述了实践中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而是社会性的;不是一种特质,而是一种活动;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人、物或观念的生理唤起,以及愉悦或不愉悦的状态。Basil Wiese(2019:132)则描述了情感中的实践:是一种身体活动,具有公共性,是一种过程。结合这两个描述性定义,可以大致描绘出实践与情感的关系:实践是一种身体性的活动及过程,情感是这一活动及过程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状态,参与者处于由实践和情感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其实践过程受到情感状态的影响,其情感状态也会伴随实践活动而流动于社会网络之中,影响着其余的社会成员。
由此生成的情感实践同时具有两个层次:在单个实践中,情感作为实践的一个元素被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情感动力或情感目的(产物);在复杂实践中,情感作为横贯其间的维度被凸显出来,多个实践协同产生了情感流动现象,即单个实践产生的情感出现了跨主体的共鸣或传播。其中,单个实践指单一主体的单一具体行动,复杂实践指单一主体的一系列行动集合,或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譬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位心潮澎湃的普通民众冒着感染风险为防疫前线运送物资;这一典范事迹逐渐传播开来,或在手机屏幕面前唤起他人共情,或感召他人加入志愿者行列,“共同抗疫”的情感话语或情感意向扩散至更大圈层、更多维度。在单个实践里,情感仅止于个体动力,而在复杂实践中则会衍化为集体动力或集体记忆。这种情感流动现象在数字媒介时代屡见不鲜。同时需要指出,“情感实践”与“实践中的情感”有所区别,后者主要指实践过程中的情感元素,意在强调理性并非人类实践之唯一或至高要素,情感亦不可或缺;前者则是一种探索个体或集体实践中情感的生成、动力和传播机制的分析取向,它力图以情感为线索挖掘人类(数字媒介)实践的潜在面向,或许还隐有论证“情感比理性更重要”的理论倾向。概而言之,情感实践在微观上指“实践产生情感”这一过程,在宏观上指“复杂实践中的情感流动”这一现象。如Margaret Wetherell(2015)所言,情感实践解释了情感传播的界限,强调关系性和协商性,关注情感事件的流动,能较好结合自然状态、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共同分析情感现象。
情感实践探索了社会领域中情感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此,实践理论中的情感同时具备两层含义:它既是名词(emotion),指作为一种强度和质量的情感状态;又是动词(to affect),指情感唤起的行为。以这两层含义为基础,情感实践包含情绪、身体、认知(意义)三重维度,即喜怒哀乐等具体的情绪(emotion)反映、特定情感对身体施加的影响、实践者对情感的阐释。情绪和身体维度可以纳入生物神经学范畴,认知维度则属于文化社会学范畴。这三个维度并非独立运作,而是相互影响。近年来的认知行为疗法尤其是正念减压法(MBSR)的研究已经初步表明,情绪和身体感受之间有着“刺激—反应”的映射关系,认知在这种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调节认知可以改变“情绪—身体”的反映模式,在正念减少疼痛的过程中,情绪、感知和认知网络、副交感神经网络都同时卷入这一交互过程(Morone,2019)。Arlie Russell Hochschild(1979)早在1979年讨论情绪工作(Emotion work)时,就提出应当研究社会因素对情感和人们对情感认知的双重影响。
情感实践主要指向三类情感对象(affective objects),分别是人(他者)、物(技术物)和观念(符号)(Reckwitz,2016:122)。情感实践可以单独指向一个情感对象,也可以同时指向多个情感对象。当指向的情感对象数量和种类越多,社会成员就越难以用语言表述这种复杂的情感。借助这些丰富而细腻的分析维度,情感实践概念可以呈现社会成员数字媒介实践的多元面向。
二、数字媒介的情感偏向
一般情况下,技术物要么作为情感实践过程的一个元素,要么作为情感实践活动的一个指向对象,其自身性质对情感影响并不大。但媒介技术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情感偏向,使得媒介情感实践也需要将媒介技术自身的形态分析纳入其中。
(一)媒介信息编码形态与情感偏向
媒介偏向问题始自伊尼斯(Harold Innis)对西方文明史的分析。他(1951/2003:28)提出,某些媒介(如石板、黏土等)偏重于在时间上传承知识,而另一些媒介(如莎草纸、广播等)则更偏重于在空间上传播知识。媒介的时空偏向极大影响了不同文化的特征和走向,甚至“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承接伊尼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进一步阐释各种媒介形态本身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其中冷媒介和热媒介便是一种媒介偏向论。他(1964/2011:36)认为,热媒介是“高清晰度”的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给人一种“充满数据的状态”,无需观众参与其中去理解;冷媒介是“低清晰度”的媒介,给人提供的信息量很匮乏,需要受众自己参与其中补足大量(背景)信息。对媒介偏向的思考已经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的一个基本议题: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林文刚,2006/2007:31)。在诸多偏向之中,Christine L. Nystrom认为,因为信息编码的符号形式不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情感偏向(转引自Lum, 2000)。
为什么信息编码的符号形式会导致媒介产生不同的情感偏向?其间经历的逻辑路径是什么?信息编码的符号形态和冷热媒介的区分有关吗?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隐藏在朗格(Susanne K. Langer)的符号理论中。朗格首先区分了信号和符号在理解上的差异。她(1953/1986:36)认为,“对于一个信号, 如果它引起我们对其表示的东西和状况的注意,那它就算被理解了,而对于一种符号,只有当我们想象出其表现的概念时,我们才算理解了它”。这意味着人类能轻易理解信号,但却需要投入相当精力来想象符号表征的对象。而对于不同形态的符号,人类理解(想象)的难度也不尽相同。换言之,某些符号能够轻易在头脑中唤起所指的形象,而另一些则难度更高。这种“想象形象的程度”和麦克卢汉用于划分冷热媒介的“清晰度”标准十分类似,热媒介能轻易唤出符号形象,冷媒介则需要更多的“自我补足”过程。
虽然麦克卢汉对冷热媒介的阐述有许多矛盾之处,媒介技术的进步也打破了原本的一些论述,但其间隐含的两条思考线索仍具有极大价值:信息含量和信息直观。在剔除外界噪音影响(受众个体差异和环境因素)的情况下,信息含量由两个指标构成,内容量(“1000字”或“5000字”)和符号量(“文字”或“文字+
声音+图像”)。内容量和符号量越丰富,信息含量越大,由于人脑无法马上理解丰富的符号编码形态带来的充沛信息量,越需要受众参与其中去理解含义;信息形态越单一,信息含量越小,人脑可以较快理解其含义。信息直观指的是信息编码形态唤起符号背后形象的难易程度,直观程度更高的信息编码形态,更容易让人想象出概念背后的形象,从而理解其含义。比如,同样是描述爱因斯坦的信息编码形态,文字只能引导人们去想象,图像则直接呈现其外貌,视频则更加动态、周全地呈现其形象。从文字到图像再到视频,信息直观程度逐步提高。因此,文字更冷,图像更热;图标(icon)更冷,图表(chart)更热;音频更冷,视频更热。在某些情况下,信息含量与信息直观形成一种反比关系,信息含量越大,信息直观程度越低,越需要受众参与其中去理解其含义,想象概念背后表征的事物形象。归根结底,信息编码形态越接近现实世界的呈现方式,越能创造一个接近真实的拟态环境,这种媒介形态也就越热,从而越能唤起受众情感。
(二)数字媒介的情感偏向
“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正如波兹曼(Neil Postman)(1985/2004:12)所言,媒介史亦可视作一部情感史。沿着“印刷—电子—数字”的演变路径,媒介呈现和激发情感的功能愈发强大,也相应具有愈发明显的情感偏向。相比纸质媒体,电视是一种“情感媒介”,特别适合描绘和唤起情感,而且人们也是在情绪化的场景下观看电视(Pantti, 2010)。由此,甚至有人(Chaudhuri, 1995)称其为塑造全球情感共识的电子情感交流系统(system of electronic emotional communication)。而数字媒介的情感偏向更加明显,其比特化的信息编码形态使得它集几乎所有媒介特征于一体。一方面,数字媒介延展了传统符号形态的情感表达范畴。比如,作为最传统也最抽象的符号形态,文字离情感最远,但如今网络上流行的“颜文字”亦能有效唤起情感,这既是文字象形功能的发展,也是数字媒介拓宽文字形态编码可能性的结果。另一方面,数字媒介还创造了一个最接近现实生活的虚拟世界,可以表征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元素。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所有符号形态及其组合在网络空间自由流动,深度嵌入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它们的浮现源于情感驱动,它们的流动源于情感扩散,它们的消失源于情感转移。情感不仅是维系互联网私领域互动的重要力量,也在互联网公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袁光锋,2014),甚至在公共行动领域形成了某种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Papacharissi, 2016)。
在日常生活中,数字媒介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情感角色。以当前广受用户欢迎的视频聊天这一媒介实践形态为例,数字媒介在其中创造了一种“共同时空下的情感联系”:首先,用户面前呈现出一个多重感官融合的动态画面,熟悉的声音、面孔和动作还原了仅次于人际交流的传播环境;其次,语音的实时通讯塑造了同一时间感,面对面的视频交流则塑造了同一空间感(或共同在场感)。换言之,数字媒介跨越千里,构成了一个共在的情感时空,居中的冰冷屏幕流通着的尽是搅动用户心绪的情感元素:咧开的嘴角、关怀的耳语、无奈的沉默……。心理学家Nico Frijda(1988)提出的情绪显在现实法则(The Law of Apparent Reality)也能说明视频聊天容易引发情感,情绪是由一个人感知情境的方式决定的,如果一个情境被评估为真实的,其真实程度越高,所引发的情感强度也越高。
数字媒介的情感偏向还可以从朗格的符号表征体系中来认识。朗格认为,人类有两种符号使用方式:推理性模式(discursive symbolism)和表征性模式(presentational symbolism)。前者主要指(书面)语言(包括数学符号),人们能借助它进行抽象思考,但难以表达情感;后者则主要指一切非语言的符号体系,如音乐、舞蹈、绘画等,它唤起人的整体性、瞬间性的形象体验,表达人类情感。推理性符号难以传递某些复杂含义,譬如“词不达意”和“一图胜千言”,因此出现了表征性符号。推理性符号唤起理性,表征性符号唤起情感,朗格(1953/1986:51)基于此将艺术定义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印刷媒介以文字为主,多传递推理性符号;电子媒介以音视频为主,多传递表征性符号;数字媒介提供了一个推理性符号和表征性符号同时呈现的融合环境,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表征性符号及其传递形式,比如表情包、表情符号(emoji)、网络直播等,使得人们更直观地感知虚拟世界,进而唤出情感。目前,作为最接近现实世界的数字媒介技术,虚拟现实就通过操纵“存在感(presence)”来实现情感媒介的功能(Riva et al., 2007)。
三、数字媒介唤起情感实践
在信息时代,情感不仅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体验,还是一种被技术中介的文化实践,受到数字媒介及其社会环境的制约。一方面,在诸如数字哀悼实践(digital practices of mourning)等媒介实践形态中,情感的表达和流动居于各种行为和意图的中心,并受到一系列情境和规范的制约(Giaxoglou, Doveling, 2018)。另一方面,数字媒介实践是如今唤起人类情感的重要形态,由此诞生的情感文化贯穿个体、群体和全球层面(Doveling, Harju, Sommer, 2018),融入每一个使用数字媒介的用户生活之中。此时的情感应被理解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力量,它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意义上的完全能动的情动(affect),而非仅存在于身体内部的情状(affection)——一种主体性感受(塞格沃斯,2011/2018:265-266)。在如今的日常情境中,围绕数字媒介的情感实践体现在环境、内容、产品等多个层面上。
首先,数字媒介塑造了一个情感易激的媒介实践环境。前文已经阐明数字媒介的情感偏向,越来越多的表征性符号占据了互联网的大部分空间。随着社交媒体成为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最主要入口,这一趋势愈演愈烈,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种视觉媒介(visual medium),呈现出图像社交的面貌(刘涛,2019)。不仅图像成为网络流量的主要消耗对象,依托图像展开的人际互动也更加活跃。2015年,数据分析公司BuzzSumo发现包含图片的Facebook状态的参与度比纯文字要高出2.3倍(Pinantoan,2015),2018年又发现视频帖子的参与度比其他类型的帖子高出59%,甚至建议不要发帖多于50个字符,否则会被用户迅速忽略(Moeller, 2019)。网络空间充斥着视觉符号,最大限度地让用户处于情感易激的状态之中。
其次,数字媒介中流通的内容本身不再仅仅是一种刺激情感产生的容器,其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从而强化了情感易激的“数字媒介环境”。Brigitte Hipfl(2018)认为,媒体在消费情感的同时,生产出的内容是一种情感产品(affective work)。她由此将媒体称为一种由情感(affects)和知觉(percepts)构成的感觉块(blocs of sensations)。由这些感觉块构成的媒体内容就呈现为一系列可以触发受众感觉或对感觉的认知的意象。在这个视角下,底层由代码构成的互联网数据,一旦浮出图形化界面,进入受众视野,无论其符号形态是文字、图像或音视频,都是强化整个媒介环境情感属性的动力源。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与情感绝缘的客观新闻业,也在重新认识情感与新闻的关系。比如情感并不必然损害新闻的客观性价值(袁光锋,2017),情感对于新闻叙事十分重要(Pantti, 2010),情感甚至重塑了新闻的定义(Beckett, Deuze, 2016)等等。在符号学框架内, Andreas Reckwitz(2016:124)也提出了一个“生产-接受”的关系理论来解释媒介内容与情感的循环关系:“生产实践的目的是使文本、图像和声音信号能够影响人,而接收实践的目的是使其受到影响。”换言之,数字媒介生产的内容是为了唤起受众情感,而用户使用数字媒介,也正是为了体验这些情感。
最后,新型数字媒体产品旨在唤起情感,而非仅传递信息。自传播媒介诞生以来,其原初功能就是储存群体共享的超身体记忆(extrasomatic memory),媒介就是为了储存和提取信息(克劳利,海尔,2006/2011:2),并进而传播和传承知识。这一信息本位的媒介逻辑一直延续到印刷媒介时代。自从电视诞生之后,满足娱乐需求迅速成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功能,围绕大众媒介打造的娱乐工业成长为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巨物,娱乐消费日渐有压倒信息传递的趋势。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碎片化使用、注意力经济等因素使得媒介产品无不以视觉符号攫取消费者使用时间为利润来源,国内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火热,国外如Instagram、Pinterest、Imgur等图像社交软件的流行,都是以引发用户情感共鸣为主要产品机制。作为拥有最大规模用户数量的媒体产品,社交媒体使得大规模唤起用户情感和情感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常态, Bernd Boesel(2018)称其为机器论范式(machinological paradigm)的情感配置模式,即文化工业时代的情感管理模式。假新闻(misinformation)的病毒式传播便以此为基础。
在环境、内容和产品的三重影响下,如今人们的数字媒介实践可以视为典型的情感实践。譬如,最常见的三种数字媒介实践形态——数字游戏、社交媒体、短视频应用——都体现了极强的情感属性。
作为情感驱动的群体性行为,游戏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体验,用户从个体性的游戏行为中获取快感,从集体性的游戏行为中获取归属感。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游戏(play),不仅是个体放松心情的休闲方式,在赫伊津哈(1938/2007:3-27)眼中,游戏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柱石之一。实际上,游戏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日常生活视作一个由重复性和创造性构成的谱系空间,那么游戏无疑偏向创造性一端。在循环往复的日常生活中,数字游戏是人们体会个体自由感、自我决断感和心灵快感的重要渠道。从补偿性的角度来看,人们能“在游戏中寻找其他生活领域中无法得到的快乐”;从情感平衡的角度来看,“游戏使得人的情感状态处于一种最佳态势”(古德尔,戈比,1988/1999:189-191),从而稳定日常情感结构。
社交媒体则是用户与社会关系的维系物,是社会成员与亲友沟通情感的主要线上渠道,催生了表情包、视频聊天等强表征性的符号形态。在异地而处的亲密关系中,视频聊天最接近现实中的面对面交流,最能传递整体化、形象化的感知,也最能塑造一种面对面交流的互动情境感。Saul Greenberg等(2013)发现,视频聊天让异地情侣感受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参与感,增进亲密感,巩固情感联结。而网络表情符号(包)的演进史亦反映出网络交流中情感性渐强的历程,从最初的标点符号表情(如:-)),到emoji表情和用户创建的表情包,再到iPhone上实时模拟人脸表情的3D动画表情Animoji,这一交流形态的演变无疑是数字媒介情感实践愈发普遍、多样的体现,董晨宇(2018)形象地称其为情感的通货膨胀。
短视频应用则是一种视觉娱乐方式,为人们提供碎片化时空里的“刺激性娱乐”。观看短视频,就是体验一个个不同的世界,用户得以收获超拔于循环日常之外的补偿性情感。当前短视频应用的产品特点极易让用户产生快感,从而摆脱生活中的一些负面情绪。纽约大学助理教授奥尔特(2017/2018:64-163)提出上瘾体验的6个设计原理:美好目标、积极反馈、容易进步、渐进挑战、对未尽事宜的紧张感和社会互动。目前主流短视频产品的设计机制都是如此,“上滑观看下一个视频”、“双击点赞”、“自动循环播放”、“抖音挑战”、“分享好友”等功能都在竭力刺激用户情感,“吃掉”用户注意力和时间。面对能缓解疲乏、带来快感的短视频,少有用户能拒绝加入这股大规模的情感流动之中。
身处“情感易激”的数字化实践环境,手握“强情感偏向”的数字化设备,使用“旨在唤起情感体验”的数字应用,穿梭于由感觉块构成的数字内容之中,无数个体在数字媒介实践中不断生产着情感实践的自我强化循环,也持续凸显着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
四、结语
情感是日常生活的根本维度,是日常交往的基础,为日常生活赋予意义感。当各个层面的社会交往都无法脱离数字媒介时,数字媒介实践便与衣食住行一道成为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基本形态。情感总在数字媒介实践中自然“溢出”,情感实践也成为理解人与数字媒介关系的一条关键线索。这条线索不仅在情感与媒介效果研究之外(纪莉,董薇,2018)打开了新路,还为人们思考当今数字媒介的日常性提供了新维度。除了在实践理论脉络中考察情感实践外,本文还将数字媒介的情感偏向归因于信息编码形态,通过信息直观和信息含量两个指标解释媒介的情感偏向程度,指出数字媒介对表征性符号的融合式创造使其具有高度的情感偏向。
情感总是主体间性的产物,不存在没有他者的情感。由数字媒介塑造的赛博空间不是一个与感性显现相分离的世界,而是一个超凡的感性世界(约斯·德·穆尔,2005/2007:57),是由各种人物、象征、叙事交织构成的情感世界。显然,赛博情感空间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工具。如果说双面神雅努斯(Janus)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看门者,那么他的“明面”是注意力经济,“暗面”则是情感经济。情感易激的媒介环境、强情感偏向的媒介设备、高情感唤起的媒介应用,这些要素使得人们的数字媒介实践离不开情感的流动循环。这一循环不仅在个体心灵内部,更在集体成员之间,成为数字时代的显著特征。
如今,围绕情感流动出现了诸多撕裂性的网络景观(如网络暴力与网络援助),这些数字媒介情感实践的异同是什么?产生了哪些情感(政治)后果?单纯用理论显然不足以理解它们。依托(网络)民族志、案例(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个案研究,挖掘出更多复杂的、微观的情感实践经验,并尝试从材料中提炼出适宜于本土语境的分析性概念,将是此领域的第一个发展方向。第二个发展方向则是用情感实践来重新理解数字经济、数字政治、数字性别、数字文化等新兴议题,或许可以避免“旧瓶装新酒”的理论定势,找出不一样的诠释路径。新现象催生新问题,新问题呼吁新理论。或许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数字乌托邦和数字敌托邦的二元争论之外,发现“小粉红”、“键盘政治”、“网络极化”等情感实践现象的潜在面向,甚至有可能将“自我剥削”的情感经济(政治)转变为“自我接纳”的情感体验,在这个巨机器(Megamachine)越来越多的巨时代里,用“情感解放”实现“人的解放”。■
参考文献:
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2006/2011)。《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5版)》(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董晨宇,丁依然(2018)。贫媒介、富使用——互联网中介化交往中的情感补偿。《新闻与写作》,(9),49-53。
格雷戈里·J. 塞格沃斯(2011/2018)。从情状到灵魂。载查尔斯·J.斯蒂瓦尔(主编),《德勒兹:关键概念》 (第255-270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顾洁(2018)。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6),13-32+126。
哈罗德·伊尼斯(1951/2003)。《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纪莉,董薇 (2018)。从情感研究的起点出发:去情绪化的情感与媒介效果研究。《南京社会科学》,(5),116-126。
林文刚(2006/2007)。《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涛(2019)。图像社交的兴起及其“视频转向”。《教育传媒研究》,(2),8-11。
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2011)。《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尼尔·波兹曼(1985/2004)。《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乔纳森H·特纳(2007/2009)。《人类情感》(孙俊才,文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苏珊·朗格(1953/1986)。《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1988/1999)。《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谢晶(2015)。法国社会哲学的“结构主义争论”——从二元符号结构主义到三元话语结构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28。
亚当·奥尔特(2017/2018)。《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闾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袁光锋(2014)。互联网空间中的“情感”与诠释社群——理解互联网中的“情感”政治。《中国网络传播研究》,(8),89-97。
袁光锋(2017)。情感何以亲近新闻业:情感与新闻客观性关系新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57-63+69。
约翰·赫伊津哈(1938/2007)。《游戏的人》(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
约斯·德·穆尔(2005/2007)。《赛博空间的奥德赛》(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东启(2011)。实践概念的分立与统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154-157。
自国天然(2019)。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介:一种实践分析取向的出现。《新闻界》,(6),77-86.
FrijdaN. H. (1988). The laws of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5)349-358.
Hipfl, B. (2018). Affect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otentials and assemblage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6(3)5-14.
Lum, C. M. K. (2000). Introduction: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08(1): 1-7.
Moeller S. (2019). Find the content that works and the influencers who matte. Retrieved from https://buzzsumo.com/blog/facebook-engagement-guide/.
Beckett, C. & DeuzeM. (2016). O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Social Media + Society2(3)2056305116662395.
BoeselB. (2018). Affect disposition (ing): a genealogical approach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emoti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6(3)15-21.
Chaudhuri, A. & Buck, R. (1995). Media differences in rational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advertising.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39(1)109-125.
CloughP. T. (2007). Introduction. In Clough, P. T. & Halley, J. (Eds.).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pp. 1-30). Durham, US: Duke University Press.
DovelingK.HarjuA. A. & Sommer, D. (2018). From mediatized emotion to digital affect cultures: new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flows of emot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4(1)2056305117743141.
Fox, N. J. & AlldredP. (2018). Social structures,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monist sociology: (new) materialist insights. Journal of Sociology54(3)315-330.
Giaxoglou, K. & Doveling, K. (2018). Mediatization of emotion on social media: forms and norms in digital mourning practices. Social Media + Society4(1)2056305117744393.
Greenberg, S. & NeustaedterC. (2013). Shared living, experiencesand intimacy over video chat in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s. In C. NeustaedterS. Harrison, & A. Sellen. Connecting Families: The Impact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n Domestic Life (pp. 37-53). London, UK: Springer.
HochschildA. R. (1979).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5(3)551-575.
Lünenborg, M. & MaierT. (2018). The turn to affect and emotion in media studie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6(3)1-4.
MoroneN. E. (2019). Not just mind over matter: reviewing with patients how mindfulness relieves chronic low back pain.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integrative medicine, 242515690X19838490.
PanttiM. (2010). The value of emotion: 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 notions on emotion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5(2)168-181.
PapacharissiZ. (2016). Affective publics and structures of storytelling: sentimentevents and medialit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9(3)307-324.
Pinantoan, A. (2015). How to massively boost your blog traffic with these 5 awesome image stats. Retrieved from https://buzzsumo.com/blog/how-to-massively-boost-your-blog-traffic-with-these-5-awesome-image-stats/.
ReckwitzA. (2016). Practices and their affects. In A. HuiT. Schatzki, & E. Shove. The nexus of practices (pp. 114-125). Abingdon, UK: Routledge.
RivaG. et al. (2007). Affective interactions using virtual reality: the link between presence and emotion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1)45-56.
Stets, J. E. & Turner, J. H. (Eds.). (2014).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Vol. 2). New York: Springer.
Wetherell, M. (2012). Affect and emotion: a new social science understand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Wetherell, M. (2015). Trends in the turn to affect: a social psychological critique. Body & Society21(2)139-166.
Wiese, B. (2019). Affective practice. In J. Slaby & C. V. Scheve (Eds.). Affective Societies: Key Concepts (pp. 131-139). Abingdon, UK: Routledge.
自国天然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新闻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