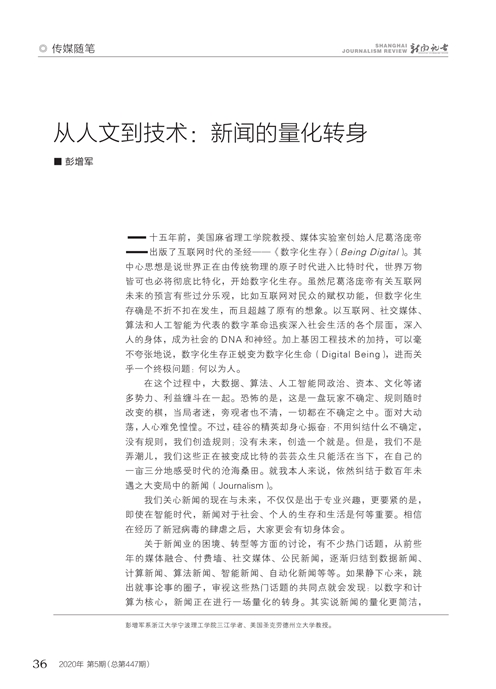从人文到技术:新闻的量化转身
■彭增军
二十五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葛洛庞帝出版了互联网时代的圣经——《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其中心思想是说世界正在由传统物理的原子时代进入比特时代,世界万物皆可也必将彻底比特化,开始数字化生存。虽然尼葛洛庞帝有关互联网未来的预言有些过分乐观,比如互联网对民众的赋权功能,但数字化生存确是不折不扣在发生,而且超越了原有的想象。以互联网、社交媒体、算法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革命迅疾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入人的身体,成为社会的DNA和神经。加上基因工程技术的加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字化生存正蜕变为数字化生命(Digital Being),进而关乎一个终极问题:何以为人。
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同政治、资本、文化等诸多势力、利益缠斗在一起。恐怖的是,这是一盘玩家不确定、规则随时改变的棋,当局者迷,旁观者也不清,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面对大动荡,人心难免惶惶。不过,硅谷的精英却身心振奋:不用纠结什么不确定,没有规则,我们创造规则;没有未来,创造一个就是。但是,我们不是弄潮儿,我们这些正在被变成比特的芸芸众生只能活在当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感受时代的沧海桑田。就我本人来说,依然纠结于数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的新闻(Journalism)。
我们关心新闻的现在与未来,不仅仅是出于专业兴趣,更要紧的是,即使在智能时代,新闻对于社会、个人的生存和生活是何等重要。相信在经历了新冠病毒的肆虐之后,大家更会有切身体会。
关于新闻业的困境、转型等方面的讨论,有不少热门话题,从前些年的媒体融合、付费墙、社交媒体、公民新闻,逐渐归结到数据新闻、计算新闻、算法新闻、智能新闻、自动化新闻等等。如果静下心来,跳出就事论事的圈子,审视这些热门话题的共同点就会发现:以数字和计算为核心,新闻正在进行一场量化的转身。其实说新闻的量化更简洁,之所以要加上“转身”两个字,是想强调这量化并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需要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来考察。
所谓新闻的量化,笼统讲,就是新闻理念和实践、生产及消费被测量和算法主导。首先,新闻生产的生态环境已经量化,社会在飞速数据化,由此,新闻报道的对象量化,新闻的呈现量化,新闻的传播和消费更是彻底的量化——以前的受众是个体的人,而今受众不过是即时的数据点。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媒介融合更加深入,超越了技术的进步,技术、经济、新闻专业主义等融合在算法的麾下,一切皆可测量,一切皆为数据。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今天则可以说,给我技术,我可以测量、算计、控制整个世界。这不但是新闻实践范式的转变,而且是学术范式的转变。一旦可以测量任何东西,可以有足够多的数据,谁还需要什么理论?理论存在的意义正是因为不确定性,当一切都可以直接测量,一切都以通过技术设计来完成,所见即所得的时候,还需要理论去假设、验证什么呢?
以下,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下新闻的两次大转身,即从人文到科学,从科学到技术;其次,讨论一下新闻量化的的表现与后果。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人文”、“科学”、“技术”,是为了表述方便而贴的标签,是指新闻理念和实践发生某种倾向性转变,进入正统主流新闻机构并且常态化,而不是说转变就是替代,量化就一定会丢掉人文,但量变到质变也可能是大概率的存在。
人文到科学的转身
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同样,新闻也派生于文史的根。当然,这个根刨到何时何地,取决于新闻如何定义,究竟指的是新闻事件(news)还是新闻事业(journalism)。远,在西方可追溯到罗马,在中国则可追溯至大唐。一般认为,汉语的“新闻”一词最早出现在初唐,证据是唐人孙处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的感慨。其实,这句话与其当作新闻的开端还不如理解为在初唐新闻事业还没有出现,还要等到晚唐的官报和宋的邸报。
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journalism),大致应该从十七世纪开始。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以后,报纸和杂志不再是官府和权贵的奢侈品,旧时王谢燕,飞入百姓家。在此之前,人口中识文断字的是极少数,唐宋盛世,据估计识字率不超过20%,欧洲十六世纪的识字率仅有11%。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的识字率达到60%,为大众传播时代新闻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顺便提一句,中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识字率也不过65%。
而更为重要是,新闻的思想理论基础开始奠定,其标志当是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弥尔顿首先是伟大的文学家,其《失乐园》可谓英国诗歌的丰碑。当然,新闻思想的萌芽并不代表新闻实践的开始,这要等到另一位英国大文学家的出现,那就是笛福。笛福在1703年写就了《暴风雨纪事》,记述的是亲历者的真人真事,所以一般把笛福作为现代新闻的鼻祖。笛福首先是以小说闻名于世,据说《鲁宾逊漂流记》就翻译的语种来讲,仅次于圣经。
十八世纪的殖民地美国,新闻业尚在发轫阶段。新闻纸不过是印刷店老板随手印的副产品,而这一时期的新闻先驱如托马斯·潘恩、富兰克林等,做新闻靠的是自己的文学天分和生活阅历。新闻无非是政治斗争工具,所谓文人办报、政治家办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到十九世纪,世界文学发展到顶峰,担负起塑造、巩固和发展民族气质和性格的任务,而新闻业也相应进入繁荣期。文学与新闻的血肉联系,从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就可以体现,记者出身的大文学家包括狄更斯、马克·吐温、惠特曼等。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新闻文学性突出,而现代新闻的核心观念和实践体系还有待形成。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新闻开始在文学的根子上长出了自己的枝蔓,逐渐从理念和风格上,形成自己的个性。这个转变的推动力是传播科技的发展,如美国传播学家凯瑞所论述的那样,电报的发明对新闻作为一个行业和文体产生巨大影响。电报使新闻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开始真正“新”起来。而在文体上,电报要求简洁,不可文采飞扬,因为多一个字多一份钱,由此逐渐形成了电讯体,新闻报道也开始流行倒金字塔结构,而文学性退居二线。通讯社稿件为了市场,需要照顾不同党派、政治倾向的媒体,而不得不寻求平衡。新闻从一开始的文学家和政论家依据道听途说的雄辩,开始过渡到第三者的事实报道。记者实地采访,把消息源带入叙述,形成了新闻体,久而久之,渐成性格,新闻终于从文学的根子上自立门户。不过,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究其根本品质,新闻依然是人文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人文到科学的转身。
这里所说的科学,泛指以实证主义为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广义的科学,包括而且主要指的是社会科学。
新闻这个转身可以说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乃政治、社会环境,工业革命后科学的日新月异,民主政体的建立巩固。地利是美国世界领导地位开始形成,美国新闻业在内战以后逐渐同欧洲新闻传统分离,形成了以客观、中立为核心的新闻理念和实践程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新闻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学殿堂。人和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一战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大量欧洲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移民美国,而许多社会科学家都对大众传播有着浓厚兴趣。对美国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是记者出身。他认为,新闻记者不但要有文学的天赋,还应该有术业的专攻,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Robert Ezra Park),年轻时也做过新闻记者。有意思的是,帕克的故乡,正是笔者所在的美国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州一个名叫红翼(red wing)的小镇。这个小镇生产著名的“红翼”牌劳保靴。如今提起这个小镇,估计人们想到的是酷靴而不是帕克。在师从经验主义大师杜威之前,帕克在报社干了十一年。美国新闻传播界的大咖李普曼就更不用说了,被誉为美国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两获普利策奖。舒德森称他是美国新闻学之父,凯瑞赞他是美国媒体学的奠基者。
新闻向科学的转向还有赖于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和。新闻进入大学后,其学科建设主导者的学术出身多为社会学、政治学或心理学,这对于新闻学术乃至业务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师承关系至关重要,徒子徒孙,开枝散叶,天长日久,渐成气候,为新闻从人文到科学的转身提供了导向和学科支持。新闻的理念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自此皈依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体系。这个改变微妙却重要。比方说,人文传统多半注重你文章写得漂亮不漂亮,而科学取向则往往会问你是否科学、客观。
思想上、人才上做好准备之后,最根本的是社会需求。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民调成为热门,公共舆论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科学、医学、环境问题开始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由此,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闻可以说完成了由人文到科学的转向。必须再次讲明的是:不是说有了科学就没了人文,就像我们说唐诗宋词,并不是说宋代就只有词而没有诗,宋代也有苏轼、陆游,只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正如舒德森所说,记者究竟应该是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价值观和职业认同。科学认为世界是客观的、可知的,是现实主义,通过事实说话,因而新闻以求真为第一要务;人文的根本不是求真而是审美,所谓的人文到科学说的是这层意思。
当然,对于这个科学的转身也有成规模的修正或者反抗,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新闻、文学新闻等。
量化转身及其后果
随着统计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广泛运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从菲利普·梅耶(Philip Meyer)倡导的精确新闻,到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记者开始从数据中发现和呈现新闻,新闻业逐渐开始了量化的转身。这个量化的转身,也可以说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身。在科学思想范式确立以后,技术开始在新闻生产和传播中发挥更为直接和关键的作用。大家都知道,科学与技术不同,简单地讲,科学是世界观,是基础理论,而技术是应用,科学为体,技术为用。
同人文向科学的转身一样,新闻的量化转身当然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便是社会的数据化。所谓社会的数据化,粗略地说,就是个人和社会行为量化为可以监视和操控的数据。量化后的数据是对现实的再造,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而这个数据再造的现实往往取代了真实的现实。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人,一举一动都在被测量和评估之中。数据化的社会没有公开与隐私之分,没有前台和后台之别。比如中国预计在2020年完成的社会信用系统,犯罪案底、金融资讯、网络言论、社交情况、交通违规、消费记录、直系亲属、社会关系等统统纳入统计之中。某种程度上,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成为数字化的被生存。数据化的人甚至可以脱离人的本体而存在,所谓虽死犹生,因为你的各种数据依然在,即使不影响到你,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的亲朋好友、子孙后代。也许有人会说,少用或者不用社交媒体不就行了?这话说都不要说,微信的学生家长群,你敢不参加?没有健康码,小区都出不去。
量化已渗透到新闻生产和消费的各个过程和层面。首先涉及的是新闻的本体,即新闻是什么。以前我们说新闻是对客观事件的报道,先事件,后新闻;而今天则可以从电脑里挖新闻,可以通过预先安置的传感器传回数据,由电脑程序生成新闻。新闻采访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以来,可以说是新闻生产的核心,因此新闻人常说“跑”新闻,而现在的新闻可以没有事件、没有采访、没有消息源,真正成了“做”新闻。
社会数据化意味着新闻报道对象的数据化,自然也影响到内容的呈现方式,比如数据可视化。就新闻写作方面,也影响到新闻的语言。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历史上每次技术发展都对语言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电报使语言简洁,减少了修辞,而今天的交流则使用各种表情符号。同时,搜索引擎和算法的优化无形中鼓励了某种语言或者符号的发展,使之更有利于量化和计算。
在传播和消费层面,更是以算法为中心。当然,消费行为的测量和量化由来已久,比如纸媒的发行量和广播电视的收视率。但是,传统上的量化由于各种技术限制,只能通过统计学方法来进行,很难多维度地采集实时监控数据,而数码平台的量化可以实时检测、跟踪,同受众直接互动。
从管理上,通过量化来决定报酬,量化作为管理的手段,成为评价新闻业务的指标。
同新闻从人文到科学的转身根本不同的是:以前的转身,依然是新闻人在主导,人文依然是中枢神经。而现在,这个量化转身不是由新闻人主导,是资本主导,技术推动,数据和算法成为新闻的灵魂。
当然,量化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闻的量化也可以使报道更深入,完成传统上无法完成的复杂项目。例如,2016年巴拿马文件有一千多万份文档,如果没有计算机大数据的处理,根本无法想象。这些益处自不待多言,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新闻量化带来的负面后果。
首先来说,新闻具有公共产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但是量化的根本是商业和市场导向,新闻的本质是人文、道义,当量化成为其灵魂,成为内容和目的,势必同新闻的价值观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笔者在讨论数字革命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时,曾套用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的一大弊端是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的脱离。传统新闻媒体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以后的新闻媒体,其生产资料为资本所控制,新闻人和受众都不掌握生产资料。新媒体革命的一大功绩是可以使普通人通过一个手机和电脑成为新闻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成为新闻信息的生产者。但现在看来,这种美好的赋权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如今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这个生产资料的拥有者非权即贵,不是消费者,也不是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同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分离,同消费者的直接感性经验分离。
当然,量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要害是量化成为理性和客观的代名词,被赋予天然的合法性。然而,量化的只是你可以看到的,或者说选择看到了的。记得在大学上研究方法课,教量化方法的老师讲:世界上之所以那么多的未知,一是因为定义,二是因为测量,只要能定义能测量,就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而教质化方法的老师则强调:凡是能测量的,多半不重要,意义无法量化,而量化的数据没有政治文化经济等背景解释系统,没有意义。一滴水在空中是雨,落入地面或成江河湖海,而到杯子里则可能是茶或咖啡。
新闻量化必然造成文本高度程式化,这是智能和自动化新闻的必然条件和结果。新闻毕竟是讲故事的,而故事化的根本是人性化。武汉疫情,那么多的新闻报道,抵不上方方日记,挺说明问题。就像大家常说的那样:新闻的根本在于人性,一万个死亡数字,不是死了一万个人,而是一个人死亡这件事发生了一万次。
量化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和评价标准,同专业主义的以品质为导向相冲突。新闻的专业性,传统上是通过制定行为的专业标准作价值评估,例如通过行业协会的守则来约束,通过各类奖项来鼓励和引导,而这个专业标准是以社会影响、公共服务,以及道德、伦理而不是量化的市场指标来评判的。《美国职业记者协会守则》的四大准则:追求真实、减少伤害、独立行动、透明负责,哪一条可以量化?
新闻量化的更大问题是对公众的背叛。是的,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增强了参与度,然而,讽刺的是,从表面上看是读者的个性化选择,而实际上,受众的参与越多,为自己挖的坑就越深,受众的数据成为变现的商品,人成为数字,量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物化和商品化的过程,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新闻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数据化的问题。社会逐渐依赖于量化的数据,而不是质性的道德价值取向来决策,并且使政策和行为合法化,以此来重新定义社会关系、政治话语和文化。整个社会标准化、程序化、可计算化,最终量变到质变,技术取代了人本身,质的多样性变成由数据决定的不平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整个世界被少数几个平台来测量,来确定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少数几个私人拥有、以商业为目的的平台作为公共知识的生产者、管理者和提供者。这,细思极恐。■
彭增军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