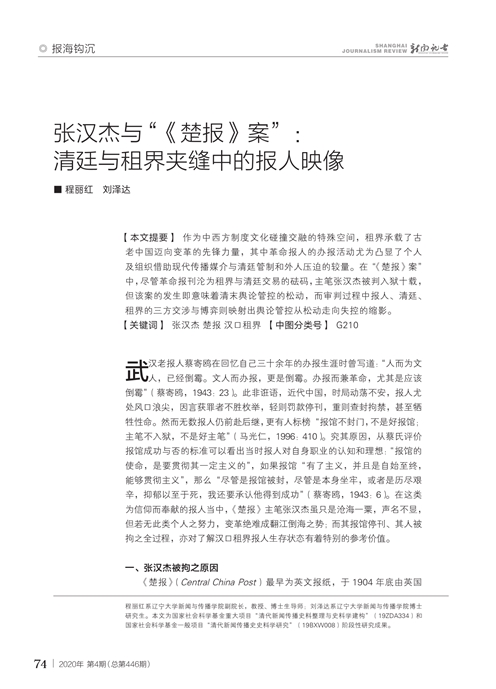张汉杰与“《楚报》案”:清廷与租界夹缝中的报人映像
■程丽红 刘泽达
【本文提要】作为中西方制度文化碰撞交融的特殊空间,租界承载了古老中国迈向变革的先锋力量,其中革命报人的办报活动尤为凸显了个人及组织借助现代传播媒介与清廷管制和外人压迫的较量。在“《楚报》案”中,尽管革命报刊沦为租界与清廷交易的砝码,主笔张汉杰被判入狱十载,但该案的发生即意味着清末舆论管控的松动,而审判过程中报人、清廷、租界的三方交涉与博弈则映射出舆论管控从松动走向失控的缩影。
【关键词】张汉杰 楚报 汉口租界
【中图分类号】G210
武汉老报人蔡寄鸥在回忆自己三十余年的办报生涯时曾写道:“人而为文人,已经倒霉。文人而办报,更是倒霉。办报而兼革命,尤其是应该倒霉”(蔡寄鸥,1943:23)。此非诳语,近代中国,时局动荡不安,报人尤处风口浪尖,因言获罪者不胜枚举,轻则罚款停刊,重则查封拘禁,甚至牺牲性命。然而无数报人仍前赴后继,更有人标榜“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马光仁,1996:410)。究其原因,从蔡氏评价报馆成功与否的标准可以看出当时报人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和理想:“报馆的使命,是要贯彻其一定主义的”,如果报馆“有了主义,并且是自始至终,能够贯彻主义”,那么“尽管是报馆被封,尽管是本身坐牢,或者是历尽艰辛,抑郁以至于死,我还要承认他得到成功”(蔡寄鸥,1943:6)。在这类为信仰而奉献的报人当中,《楚报》主笔张汉杰虽只是沧海一粟,声名不显,但若无此类个人之努力,变革绝难成翻江倒海之势;而其报馆停刊、其人被拘之全过程,亦对了解汉口租界报人生存状态有着特别的参考价值。
一、张汉杰被拘之原因
《楚报》(Central China Post)最早为英文报纸,于1904年底由英国传教士、汉口圣教书局经理计约翰创办,1942年因日本占领武汉停刊,前后历时近四十年,是湖北地区经营最久的外文报纸。1905年4月至5月间,《楚报》中文版创刊,由“汉上富商、买办刘歆生出面主办”,冯特民任经理,吴趼人为主笔。该报“在香港注册立案,馆设汉口英租界”(刘望龄,1991:93),而且为了防止清廷干涉舆论迫害报人,特“聘西人估尼干担任社长”,是“武汉地区最早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方汉奇,1999:893)。
1905年6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影响日盛,渐波及全国,吴趼人激于爱国义愤,辞职返沪,并致书上海反美运动领导人曾铸云:“仆此次辞汉口《楚报》之席而归,亦为实行抵制起见。返沪后,调查各埠之踊跃情形,不胜感佩”(转引自刘望龄,1991:94)。吴氏出走后,陆费逵、张汉杰、冯特民先后出任主笔,三人皆为日知会成员,因而该报革命倾向愈加明显,“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持论颇激昂”(汉口租界志,2003:319)。《楚报》事发前夕,陆、冯二人避居上海,独张氏留汉被捕。陆、冯二人成就颇著,名载革命史,唯张氏名声不显,近乎寂寂无闻,故本文特记之。
张汉杰,名庆怡,字汉杰,浙江山阴人。其家“世业申韩”,以法家修身、立业、传家,法家提倡缘法而治、不分亲疏贵贱,由此不难看出张氏缘何投身革命排满。其父“曾佐左文襄公幕,嗣改官湖北,以废疾故未南旋,清风两袖,四壁萧然”,其母“山阴茂才正乾先生之姊,少娴经史,颇知大义”。出身书香门户的张汉杰“性素诚笃,尚气节”,“少读书,颖悟绝人”,稍长游学遍历沪湘武汉各地,目击国势险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民呼日报,1909年8月10日)。
受聘入职《楚报》后,张汉杰谠言伟论,于扬清激浊之中,大胆评议政治时事,遂不免触怒当事。1905年8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和驻美公使梁成同美国华美合兴公司订立售让合同,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赎回粤汉铁路已筑及未筑权利(征农,陈至立,2013:78)。为筹赎路款,张向英国汇丰银行息借110万英镑,以“粤、湘、鄂三省膏捐(鸦片税)作抵”,且以后如需借款或购买器材,应“由英国银行优先承办”(江岸文史资料,2011:266)。此借款合同尚未公布,便为冯特民“觅得全文,竟夜抄出,悉载报端,撰文掊击”(张难先,2011:87),斥责张之洞此举丧权辱国。当上论尚在发酵之际,同年10月5日,《楚报》论说又登载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前于车站被轰事,文中字里行间“诋諆钦使,崇拜匪徒”,并云“不如于其未行之先,骈而毙之,免他日追悔莫及之憾”(申报,1905年10月15日)。因《楚报》泄露合约机密在先,宣传革命排满、鼓吹暗杀主义在后,两罪并罚,故遭张之洞札饬夏口厅严查。
1905年张之洞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实际上是对1898年向美国合兴公司借款修筑粤汉铁路时所签合约的纠正。原合同向美方“借款总额美金四千万元,九折实付,年息五厘,偿还期五十年,以铁路财产为担保”(郑天挺,1992:698)。如此巨额借款加上高昂利息,未来赎回路权前景堪忧。同时,合兴公司在取得筑路权后,趁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大力攫取铁路沿线开矿、办厂、垄断线路等特权,前后共获相关权利达20项,承担的义务却只有8项(刘晴波,2008:112-136)。抵押路权带来的恶果导致了1904年初至1905年秋的粤汉铁路废约运动,运动形势高涨,但所筹资金无几,遂有张之洞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张自认此合同“不要回扣,也不以铁路作抵押”,“借款方法,甚为公道”(江岸文史资料,2001:266),以一定的代价阻止了更大的损失,《楚报》却抨击他“丧权辱国”,张必然震怒。
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则是清廷为挽救危局的重要行动,亦是清廷走向立宪的关键一步,必然为立志推翻清廷的革命派所不能忍。吴樾刺杀五大臣与《楚报》载文歌颂吴樾事实上皆为革命党人与清廷激烈斗争的一部分,就革命排满而言,张汉杰与吴樾并无异处。故《楚报》被查封虽然为清廷摧残舆论之实证,但其泄露国家政治外交机密,鼓吹革命反抗国家统治,此为当时西方任何文明国家皆所不能容,因而《楚报》涉案亦在法理之中。然而《楚报》的审讯过程却充斥着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博弈,凸显了报人在清廷与租界夹缝中生存之艰难。
二、“ 《楚报》案”审判始末
在1903年发生于上海租界的“《苏报》案”中,清廷为了将章太炎与邹容从租界引渡交由自己审判,用尽办法,甚至不惜以路权与外人相易,却未能如愿,最后落得在自己领土上与自己国民打官司却由外人审判的下场,在国际上颜面扫地。然而在“《楚报》案”中,张汉杰于1905年10月13日晚被租界公堂拘走后(大公报,1905年10月22日),15日早驻汉口英领事就应张之洞电请,将其交与夏口厅冯少竹司马解往武昌,随后发交首府收监(申报,1905年10月18日)。
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楚报》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楚报》尚未出报之时,便曾派人“向驻汉英领事密商两次”,有意“出重资购归官办”,领事不予应允,方才中止。《楚报》发行后,因其革命倾向,“所纪官场各事尽(数)情指摘不少隐讳”(申报,1905年7月20日)。因此,张之洞曾“禁止士人购阅《楚报》”,并且以该报“捏造谣言,意在阻挠新政,奖助乱人,蔑弃礼义,妨碍治安,损害邦交”为由,照会英总领事查照其所定在中国开报之律法,将该报从严究办,然而“领事不答”,只好作罢(大公报,1905年8月22日)。因此,查封《楚报》虽然看似突然,但其实是清廷与革命报刊水火不容的一种必然。而决定一份革命报刊出版时间长短的因素除了其本身言辞的激烈程度之外,更主要的是清廷与租界之间博弈的结果。
张汉杰被押入武昌府监后,由武昌府太守黄以霖奉张之洞严札亲提询问,札中提出问讯要点有三:“一问张是否《楚报》主笔,一问九月初七及五月十三论说是否由张撰述,一问张是否香港秘密会中人。”张供称“为《楚报》记者,现甫三月”,九月初七之论说系“儆戒五大臣而作”,五月十三之论说“称赞党会”,系“前主笔所作”,其不知情,当时亦尚未在报馆任职,“有洋文合同可证”(申报,1905年10月20日)。至于香港密会,则“从未通气”,亦不知情。黄太守据此禀覆张之洞后,颇受申斥,盖因问答过于含糊,且审问太松,因而改派“武昌同知陈姓司马赴府署会讯”。陈司马“素性执拗”,会讯之际张汉杰“语多讽刺”,“触陈之怒,责杖八十”(申报,1905年10月23日)。
10月18日夜间,武汉两府及陈司马再次审讯张汉杰,并命令张“作赎回粤汉铁路论一篇,以观其笔气是否与五大臣论相合”。选择粤汉铁路为题,是因张另一项罪名是泄露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因提讯于“深夜在府署花厅”,故供词未能被报社探听公之于众,唯闻“张于香港秘密堂一节始终未认”(申报,1905年10月23日)。随后张汉杰被拘于武昌府监,“起居颇能自由”,然而“监禁近一月,并未见动静,亦不审讯”(申报,1905年12月5日)。
“《楚报》案”事发后,驻汉口四国领事皆出场干预。针对清廷武汉当局羁押张汉杰拘而不判,英领事提出张氏从租界公廨押往武汉,本应限三日交还,现“已逾一礼拜,既无判断明文,又不交还原人,殊背公约”。而法领事则趁机敲诈,称《楚报》报馆资本“系法国某银行担保,自出报以来耗亏六万两,应归湖北认赔”。美领事针对《楚报》经理估尼干系美国教士,报馆停刊涉案,“则不免辱及该国经理人,教会中不能缄默不辨(辩)”。另有某值年领事直言湖北当局“如此办事,有碍租界权限,不能不争”(申报,1905年10月27日)。四国领事诉求看似公允,实际皆欲借“《楚报》案”从湖北当局谋取利益,所谓“殊背公约”、“教士尊严”不过是粉饰其合理合法的旗号而已。
1906年1月,“援照春间教育普及社蒯光协监禁十年之例”(申报,1906年1月31日),湖北当局判张汉杰监禁十年,“汉口报纸报人不好的遭际,这便是第一次”(管雪斋,1936,24)。张氏入监后,其亲友积极展开营救,尤以其母张董氏为最。1908年1月其亲友曾联名具禀张之洞继任者赵尔巽,恳求开释,并“援引《中华报》杭君辛斋为例”(申报,1908年1月10日),意在将张氏押回原籍交由地方官管束。禀帖由臬司录案,但并无下文。1909年7月,张董氏“一再具禀各衙门请求开释”,臬司杨廉应允将“张已受之刑期不计外,按本受刑期酌减四分之一,改为四年”(申报,1909年7月27日)。1909年8月,张董氏再度具禀,言辞恳切,称其子“舞弄文字,奉饬监禁,现在监患病”,而她本人“年逾七旬,仅此一子”。同时,浙绍旅鄂绅商于上海《民呼日报》刊发公启,呼吁当局应于“预备立宪时代,改良法律之日”,对此案“比附新定报律,酌量改拟”(民呼日报,1909年8月10日)。臬司杨廉查得张汉杰案虽“不在恩赦条款”,但考虑张董氏“衰老多病,情实可怜”,且案犯“在监三载”,“亦尚安分”,因而予以自新,“准将该犯张汉杰援恩释免,递籍管束”(大公报,1909年9月9日)。
张汉杰入《楚报》三个月,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于其人生最宝贵年华中因言获罪,坐监近四年。出狱后张氏声名不显,匿迹于历史长河之中。个人由社会塑造,被历史洪流裹挟推搡而行,但张汉杰凭其心中的信仰与敢言的勇气,为改变“这个社会的形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份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米尔斯,1959/2017:5)。而从张汉杰的经历回归历史,所映射出的是清末汉口租界报人的生存状态,即在租界和清廷地方长官双重压力下的挣扎图存。
三、夹缝中生存的报人
汉口坐落于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交汇处,地处华中,地理条件优越,有“九省通衢”之称,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是一个“不分昼夜、舳舻云集、商贾兴盛的商业城镇”。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被增辟为通商口岸。1861年4月,英租界划定;1895年起,德、俄、法、日借清廷甲午惨败,接踵而至,汉口进出口贸易总额一时大增,1903年达到16717万两,逼近上海,被称为“东洋芝加哥”(汉口租界志,2003:1-5)。然而与上海租界相比,汉口租界晚成立16年(熊月之,2002),其内部组织架构的成熟与完备程度较上海稍逊。
就新闻出版而言,租界工部局针对报纸、杂志、宣传手册的出版、发行和销售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大体参照西法而行。1896年,英租界巡捕房在其“章程”中规定“每年的12月21日以前,是报馆到巡捕房登记时间,在12月31日以前必须照章具呈给工部局书记,请求注册”(汉口租界志,2003:316),获取经领事府签名之执照。注册时需将“报纸名目、主人姓名、印刷人姓名、发行人姓名与其办事处、居家处一一开明,呈于本局”,违者处以“五百两以下罚金,或二月内监禁”(汉口租界志,2003:542)。1903年,发生在上海租界的“《苏报》案”是租界当局审判革命报纸之始,标志着租界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延伸。依英美案例法传统,该案的审判过程为此后租界管控报业提供了标准流程,其审判结果则为此后案件量刑提供了参照。1905年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的“《警钟日报》案”即依照前例,“抓捕审判迅捷明了,无甚争议”(程丽红,刘泽达,2018)。然而“《楚报》案”却与前例相悖,审判张汉杰者为清廷地方长官而非租界会审公廨,审案后不公布结果而将张氏羁押于武昌府中一月有余,最后由湖北当局判处张氏十年监禁。
张汉杰遭如此审判,固然有违常理,但就其身处的汉口租界这一历史环境来看,这一结果又在情理之中。汉口租界地处华中,距离清廷政治中枢较近,且其直面湖广总督而非地方道台,因而所受清廷之压力远甚于上海。而1905年“《楚报》案”发生时,时任总督正是“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张之洞对报纸舆论极为重视,尤其注意到国内报纸良莠不齐与外国报纸控制信息传播的危局。他曾在《劝学篇·外篇》中写道:“外国报馆林立,一国多至万余家,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然而上海报馆“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至于军国大计,“执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国洋报早已播诸五洲”,且洋报“诋訾中国不留余地”(苑书义,1998:9745)。可见张之洞鼓励、提倡办报,但亦清楚了解报纸所蕴含的力量,对管控报纸尤为重视。
在鄂期间,张之洞强调官方报纸与民间报纸不同,应求“正人心而开民智,息邪波而助政教”(刘望龄,1991:90),其所办的《湖北官报》开设“前人论说”、“时人论说”、“往事借鉴”、“辨证谬误”等专栏,用以宣传圣谕,传播新政、立宪等官方意识形态,并对革命活动及言论进行批驳。该报武昌起义后终刊,为清末“各省官报之楷模”(刘望龄,1996)。除加强舆论引导外,张之洞对发表“反动”言论的报刊亦不手软。维新变法失败后,张之洞在湖北对维新派报刊全面查禁,不仅封查报馆,而且严惩递送和阅读“逆报”之人。“《苏报》案”爆发后,张之洞也是力主将章太炎、邹容二人引渡的清廷大员之一,并斥责邹容所著《革命军》“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中国史学会,1957:167)。因而张之洞对《楚报》严加打压,重判张汉杰十年监禁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之洞的身份地位及其镇压革命报刊的态度决定了湖北当局在“《楚报》案”中的立场,但这只是张汉杰惨遭重判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外人对租界报刊的利用态度在该案中亦发挥着重要影响。综观“《楚报》案”前后经过,与粤汉铁路借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争夺路权是清末各侵略国扩展权益、扩大势力范围和打开市场的重要手段。《楚报》报道粤汉铁路借款事是为响应当时鄂、湘、粤三省正在进行的废约运动,各省士绅旨在通过运动拿回路权,而《楚报》则旨在将革命观点掺杂进运动中,借势抨击清廷腐败无能。此举不仅为湖北当局所不容,更为英国为首的汉口租界势力所恶,而《楚报》于正式公布前登载张之洞与英国的借款合同,直接触怒清廷与租界双方。因而租界公堂将张汉杰拘走后即送往湖北当局处,不再以领事裁判权予以庇护。随后四国领事出面以“殊背公约”、“尚欠亏银”、“辱及经理”(申报,1905年10月27日)等情由提出抗议,看似为《楚报》鸣不平,实则以此为借口以在尚未结束的中美还款和中英借款谈判中占据主动,谋取更多利益。
“世变之亟,原有价值体系整个崩溃,新秩序尚未完全稳定,这时最容易看到个人怎么抉择生命意义与事业前途”(李金铨,2013:19)。“《苏报》案”殷鉴不远,邹容瘐死狱中,章太炎尚在服刑,然而张汉杰依然入主《楚报》,走上宣传反满革命的道路。在湖北地方长官与汉口租界当局的双重压力下,他不仅没有“明哲保身”或暂时“偃旗息鼓”,反而放论直言。但是租界报刊身份并没有给予其庇护,租界与清廷联合绞杀进步报业、管控舆论于张汉杰一案展露无遗。而张明知前路如此,却仍义无反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支撑他的正是那个时代的报人所拥有的信仰和理想。回望历史长河,无数报人留下各自精彩后化流星四散,正如老报人蔡寄鸥的唱词:“鸥飞江上波涛远,鹤啸楼头笛韵寒。说不尽兴亡离乱,听澈了铜琶铁板,只剩下流水高山。”(蔡寄鸥,1943:134)
四、结语
从“《苏报》案”到“《警钟日报》案”,再到“《楚报》案”,租界里的革命报刊与报人始终处在清廷与租界的双重压力下。一方面,租界为报业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外人实行的近代法治文明给予报人一定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这些享受着有限自由的报纸与报人又随时可能沦为外人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砝码。其中得罪清廷尚有转圜余地,危及外人利益则绝无生还可能。然而报人并非全无还手之力,清廷与租界之间存在着或可缓解但无法解决的矛盾,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只存在短暂的休整和妥协。利用这些矛盾找到突破口以谋取生存空间,正是清末租界报人发展报业的道路所在。租界为清末报业发展所提供的有限自由,恰恰开出革命之花,结出辛亥之果。因为清廷与租界当局或可以控制报馆和报人的存亡,却无法控制思想观念的传播与扩散,而思想观念的累积,带来的是清廷与租界的管控走向失控。这些传播思想与观念的报人们前赴后继地追逐理想和信仰,有人名垂青史,有人可能如同本文所记录的张汉杰,其影响于当时所见极为有限,其名声于后来亦不彰显,然而正是这些报人们各自做出的微小贡献汇聚成了最后走向变革的中坚力量。■
蔡寄鸥(1943)。《武汉新闻史》。武汉: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
程丽红,刘泽达(2018)。“《警钟日报》案”中的舆论角力。《新闻记者》,(2),16。
大公报(1905年8月22日)。鄂督禁报纪闻。《大公报》。
大公报(1905年10月22日)。报界风潮两志。《大公报》。
大公报(1909年9月9日)。楚报主笔有开释之望。《大公报》。
方汉奇(1999)。《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雪斋(1936)。《武汉新闻事业》。汉口市新闻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特刊,24。
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2003)。《汉口租界志》。武汉:武汉出版社。
李金铨(2013)。《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刘晴波主编(2008)。《杨度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刘望龄(1991)。《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刘望龄(1996)。张之洞与湖北报刊。《近代史研究》,(2),56。
江岸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2001)。《江岸文史资料第3辑》。武汉:江岸区政协。
马光仁主编(1996)。《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民呼日报(1909年8月10日)。楚报主笔沉冤雪乎。《民呼日报》。
申报(1905年7月20日)。鄂督议购楚报馆。《申报》。
申报(1905年10月15日)。楚报馆涉讼原因。《申报》。
申报(1905年10月18日)。楚报馆涉讼续闻。《申报》。
申报(1905年10月20日)。楚报主笔初次讯词。《申报》。
申报(1905年10月23日)。纪楚报主笔第二三次提讯情形。《申报》。
申报(1905年10月27日)。四国领事干预楚报事。《申报》。
申报(1905年11月11日)。楚报主笔并未定罪。《申报》。
申报(1905年12月5日)。楚报案尚无消息。《申报》。
申报(1906年1月31日)。楚报主笔将定以监禁十年之罪。《申报》。
申报(1908年1月10日)。请释主笔张汉杰。《申报》。
申报(1909年7月27日)。减定楚报记者刑期。《申报》。
申报(1909年8月30日)。楚报记者有出狱之望。《申报》。
熊月之(2002)。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学术月刊》,(5),56。
苑书义等主编a(1998)。《张之洞全集第六册(公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苑书义等主编b(1998)。《张之洞全集第十一册(电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苑书义等主编c(1998)。《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书札著述附录诗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约翰·米尔斯(1959/2017)。《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李钧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难先(2011)。《湖北革命知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征农,陈至立主编(2013)。《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郑天挺主编(1992)。《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卷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史学会主编(1957)。《辛亥革命(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程丽红系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达系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闻传播史料整理与史料学建构”(19ZDA33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新闻传播史史料学研究”(19BXW008)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