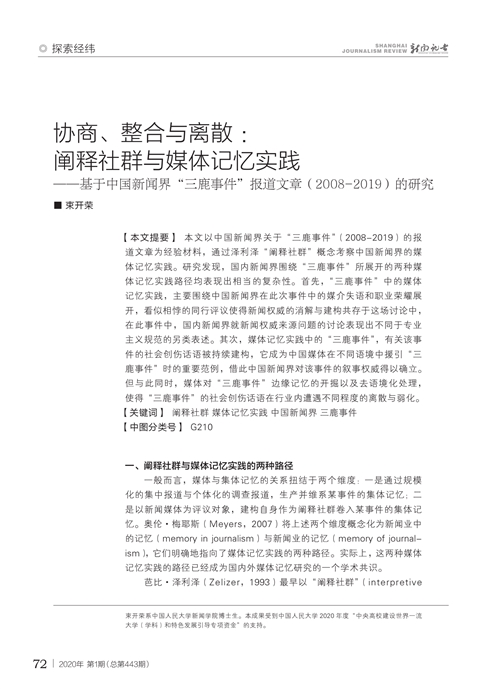协商、整合与离散:阐释社群与媒体记忆实践
——基于中国新闻界“三鹿事件”报道文章(2008-2019)的研究
■束开荣
【本文提要】本文以中国新闻界关于“三鹿事件”(2008-2019)的报道文章为经验材料,通过泽利泽“阐释社群”概念考察中国新闻界的媒体记忆实践。研究发现,国内新闻界围绕“三鹿事件”所展开的两种媒体记忆实践路径均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首先,“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主要围绕中国新闻界在此次事件中的媒介失语和职业荣耀展开,看似相悖的同行评议使得新闻权威的消解与建构共存于这场讨论中,在此事件中,国内新闻界就新闻权威来源问题的讨论表现出不同于专业主义规范的另类表述。其次,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有关该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被持续建构,它成为中国媒体在不同语境中援引“三鹿事件”时的重要范例,借此中国新闻界对该事件的叙事权威得以确立。但与此同时,媒体对“三鹿事件”边缘记忆的开掘以及去语境化处理,使得“三鹿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在行业内遭遇不同程度的离散与弱化。
【关键词】阐释社群 媒体记忆实践 中国新闻界 三鹿事件
【中图分类号】G210
一、阐释社群与媒体记忆实践的两种路径
一般而言,媒体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扭结于两个维度:一是通过规模化的集中报道与个体化的调查报道,生产并维系某事件的集体记忆;二是以新闻媒体为评议对象,建构自身作为阐释社群卷入某事件的集体记忆。奥伦·梅耶斯(Meyers,2007)将上述两个维度概念化为新闻业中的记忆(memory in journalism)与新闻业的记忆(memory of journalism),它们明确地指向了媒体记忆实践的两种路径。实际上,这两种媒体记忆实践的路径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记忆研究的一个学术共识。
芭比·泽利泽(Zelizer,1993)最早以“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为概念框架,从叙事角度将记者围绕特定事件的讲述分为两种:一是对其所报道新闻本身所进行的叙事,即如何呈现新闻故事,二是对其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叙事。前者考察的是“媒体报道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角色、意义和功能,或分析媒体如何基于集体记忆来报道现在的新闻;后者探讨新闻从业者如何塑造媒体的集体记忆,体现了记者作为‘阐释社群’对自身形象、角色定位及职业规范的共识”(陈楚洁,2015)。李红涛与黄顺铭从职业“书写”的角度,指出了这两种媒体记忆实践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新闻人对于周遭世界进行职业/专业性的书写,往往“构成重要乃至唯一的信息来源和记忆基础”(李红涛,2013);另一方面,他们也经常反身性地书写着自己的新闻传播实践,学者们将其称之为“实践反思性书写”(李红涛,黄顺铭,2014)。张志安、甘晨对“孙志刚案”的集体记忆研究,将上述两种媒体记忆实践路径在视角上区分为“新闻史”和“社会史”两种热点时刻,前者指新闻界通过“孙案的纪念报道讲述自己的历史”,后者则“将孙案作为历史语境与历史类比的报道和评论着眼于‘社会史’的记忆建构”(张志安,甘晨,2014)。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新闻业的集体记忆研究往往都与新闻权威密切相关”(陈楚洁,2018)。在泽利泽看来,新闻权威是职业新闻记者作为社会公共事件权威讲述者的角色与能力。它的发生与维系除了职业意识形态之外,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新闻记者在阐释社群内基于共享叙事所进行的话语实践(Zelizer,1990,1993),“可以说,记者作为阐释社群与新闻业作为文化权威一起构成了泽利泽所提出的新范式,前者是这一范式形成的前提,是一种手段和方式,即记者通过对公共事件的阐释形成一个共同体;后者则包含了对新闻业价值和功能的界定、协商乃至重构,表明阐释所实现的意图”(白红义,2018)。也就说,新闻权威根植于记者的阐释性话语实践,而这种对“过去”的描述、阐释乃至于重建,通常表现为新闻记者通过各类叙事文本所开展的媒体记忆实践。相关研究如泽利泽(1992)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分析,发现美国新闻界以多种方式反复建构并巩固其作为该事件权威讲述者的角色定位;同一年,迈克尔·舒德森(Schudson,1992)对美国记者关于“水门事件”集体记忆的研究,指出新闻界倾向于简化并固化“水门事件”之于美国新闻界的里程碑意义,并以此作为标识新闻业文化权威的神话;迈耶斯(Meyers,2007)对著名激进杂志Haolam Hazh在以色列新闻界中历史讲述的考察,揭示了新闻界的职业权威是如何与其对该杂志的合法性建构过程进行互动和形塑的;卡尔森(Carlson,2007)通过分析美国新闻界对著名电视主播David Brinkley和报纸专栏作家Mary McGrory的纪念话语,发现记者以此彰显自身作为集体记忆建构者这一社会角色的文化权威;李红涛、黄顺铭(2015)在对中国记者节话语的研究中认为中国新闻界经由角色模范和新闻传统所折射的历史意识与集体记忆,来标举自身的合法性与文化权威;白红义(2014)将报人江艺平的退休视作中国新闻业的“热点时刻”,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勾勒新闻权威在中国的沉浮轨迹;陈楚洁(2015)对中国新闻界关于央视原台长杨伟光纪念报道的文本分析,发现中国媒体人用央视“黄金时代”的记忆来合法化其在中国电视新闻业发展历程中的文化权威。
白红义(2014)对新闻权威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对新闻权威的分析主要从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新闻范式及其修补的研究路径,二是集体记忆的研究路径。前者主要关注新闻业场域中的“越轨者”,以排除或收编的方式强化或拓展既有的新闻业范式;后者则将前述两种媒体记忆实践的类型与新闻权威研究勾连起来:一是新闻业通过讲述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生产并建构有关该事件的集体记忆,以区别于其他社群的讲述来争夺文化权威;二是新闻记者成为集体记忆的主体,讲述新闻业自己的历史,从而使其成为直接建构、调整与强化新闻权威的过程。泽利泽(Zelizer,1993)在谈及新闻权威的维系和来源时,也将集体记忆与其他两个要素即“叙事”和“语境”并举,经由叙事,“记者得以把历史脉络与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并通过自我反思文本,就关键问题或热点时刻生产大量的阐释性话语”(白红义,2014),以此在动态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新闻权威。由此可见,“媒体记忆对其正当性和专业权威”(李红涛,2013)的建构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除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出场’和‘作为’,媒体也致力于建构新闻业的集体记忆,或通过对新闻业历史的策略性运用,来强化自身的专业权威与正当性”(李红涛,2013)。
基于此,透过媒体记忆实践的两种路径,不失为管窥中国新闻界职业权威建构过程与特点的研究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阐释社群”考察中国媒体记忆实践与新闻权威问题时,需要考虑社会文化语境的迁移和标示。泽利泽的“阐释社群”根植于高度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美国新闻界,共享的职业话语以及围绕“热点时刻”的集体阐释现象比较普遍。反观国内,既有的研究成果,如陆晔、潘忠党(2002)的“成名的想象”研究,童静蓉(2006)的中国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话语的研究,张志安、甘晨(2014)的“孙志刚案”集体记忆研究,李红涛(2016)的新闻界怀旧“黄金时代”神话研究,以及陆晔、周睿鸣(2016)的液态新闻业研究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新闻界的职业状态及其话语生产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对“阐释社群”视域下的媒体记忆实践与新闻权威研究需要更多检视这种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基于个案的有限跳脱,进一步寻求具有一定概括能力的结论。
因此,本文立论的一个重要考量以及创新价值在于,立足中国语境,通过典型个案的选取,较为充分地检视“阐释社群”的媒体记忆实践及其话语实践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所体现的不同媒体组织及其个体化的新闻记者就特定个案建构新闻权威的动态过程。
二、个案选取与研究问题
本文之所以选取“三鹿事件”作为媒体记忆实践与新闻权威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笔者初步检视所检索到的经验材料发现,中国新闻界就“三鹿事件”展开的记忆实践是理想的“一体两面”类型,几乎与事件进展(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相伴而生的是对媒体责任的反思诉求(“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追索上述研究旨趣之所以可能,得益于“三鹿事件”作为典型个案,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同时从两种媒体记忆实践的路径来考察中国新闻界职业权威消解与建构的复杂性及其主要特点的重要契机。其二,“三鹿事件”作为媒体记忆实践的对象,其在我国新闻界的职业化曲折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足够凸显。自2008年9月11日“三鹿事件”被相关媒体点名报道的当天起,十年来,我国媒体并未淡忘该事件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创痛。一直以来,新闻界以各种方式对“三鹿事件”所进行的复述和阐释,为本文考察中国新闻界围绕此事件开展记忆实践的动态过程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时间尺度与较为充足的经验材料。
基于此,本文以泽利泽的“阐释社群”为概念资源,考察中国新闻界就“三鹿事件”所进行的两种媒体记忆实践是如何在文本叙事中展开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新闻业的职业权威是如何在媒体记忆实践的动态过程与复杂叙事中被消解或建构的?
本文对报道文章的检索时间范围从三鹿事件的点名报道——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发表《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至本研究的起始时间2019年7月22日。为了尽可能捕捉相关文章,笔者以“三鹿”、“三鹿事件”以及“三鹿奶粉事件”为关键词,以传统纸媒为检索对象,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中以“标题”为条件进行检索,对所检索到的1126篇报道逐一浏览并进行筛选,筛选原则是将标题或内容重复(包括地方纸媒对主流报刊的报道转载或缩写)的报道文章予以剔除,由此共获得相关报道文章127篇(历年报道数量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笔者以这127篇报道文章为样本池,进一步以媒体记忆实践的两种路径将这些报道文章划分为两类:一是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相关报道文章(91篇),二是“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相关报道文章(36篇)。需要作出说明的是,中国新闻界就“三鹿事件”本身所生产的报道文章体量虽然数倍于行业内部对此事件所进行的反思与讨论,但就媒体记忆实践的分析价值而言,两者是旗鼓相当的。这是因为,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相关报道文章虽然数量较大,但它们各自起伏分布于各个年份,持续阐释的痕迹十分清晰,就报道内容而言,主题较为分散;相比之下,“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相关报道文章的数量虽然较少,但它们的叙事强度较为可观,主题也很集中,一些关键文本的讨论与反思亦较为深入。
三、新闻权威的消解与建构:阐释社群媒体记忆实践的冲突与协商
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国内要闻版以二分之一个版面刊登了一篇《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的调查报道,该报记者简光洲在这篇报道的主标题中点了“三鹿”的名,在此之前,“三鹿”均不曾在国内媒体公开刊发的问题奶粉报道中出现过。但是,在当年的7月底至9月初,甘肃媒体(张云,2008年7月30日,2008年9月6日;沈丽莉,2008年9月9日,2008年,9月10日)曾对此事件刊发数篇不点名及试探性报道。此外,较早在三鹿与婴儿结石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的《南方周末》,相关报道未获得刊发(傅剑锋,2009)。
1.在职业荣耀与职业失范之间:媒介失语的艰难前奏
当《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的“点名”报道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三鹿事件”的同时,中国新闻界自身也在进行着一场纠缠于“职业荣耀”与“职业失范”之间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相关论述为考察中国新闻界作为阐释社群开展媒体记忆实践与建构新闻权威等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
首先,相关媒体就自身在“三鹿事件”报道过程中,媒介失语问题的表述和反应是颇为有趣的。仅就公开发表的文本而言,2008年7月和9月分别以“不点名”方式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的两家甘肃纸媒《西部商报》与《兰州晨报》,均在事后刊文对这种处理方式进行话语层面的修补,这种自我肯定与追认可以比较典型地反映媒体人游走于职业荣耀与职业失范之间的复杂心态。2009年11月25日《兰州晨报》刊文,将其于2008年9月11日(与《东方早报》简光洲点名“三鹿”的报道在同一天)刊发的另一篇报道《著名奶粉生产企业三鹿集团派员来兰了解情况,表示三鹿没有18元价位的奶粉》重点标识,从而将该报9月9日就奶粉问题刊发的“不点名”报道《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结合起来,称“当初如果没有《兰州晨报》率先点名报道以及全国各级媒体的全力跟进,三鹿奶粉事件会不会又跟当年的‘大头娃娃’事件一样,被乳品企业所谓的‘危机公关’掩盖起来?”(《兰州晨报》,2009年11月25日)。相比之下,《西部商报》则以还原调查报道采写过程的方式,强调该报在当年的7月至9月对问题奶粉的追踪调查,并在8月24日就已将怀疑的目光指向三鹿,“但因当时所能获取的数据与信息过于单一,加之食品安全问题向来敏感,见报稿件仍就只关注了这一事件的现象”(李剑兵,唐学仁,2009年3月3日)。
张志安曾对此事件国内媒体的自我审查现象进行“事件-过程”分析,该文对《西部商报》、《兰州晨报》等甘肃纸媒记者的访谈资料,在这里亦有佐证价值。访谈资料显示,《西部商报》记者张云将该报的“不点名”报道解释为“当时所得数据与信息过于单一,不足以证明国内知名的三鹿奶粉存在隐患”(张志安,2013),但这位记者同时强调“最开始写出了‘三鹿奶粉’的名字”,甚至“考虑到最坏的打算,错的话,我个人去承担,大不了我不干这个事”(张志安,2013),由此该记者将其与所在报社出于对诉讼风险的考虑而最终采取“不点名”报道的处理方式切割开来。另外一家媒体,《兰州晨报》以报社名义就“不点名”报道给该报记者的解释是“这篇报道没点三鹿公司名,还有个原因是‘权威证据缺失’”(张志安,2013)。但受访记者表示,“在采访中已经掌握比较确实的证据材料,医院及医生也向其证实了三鹿奶粉的问题”(张志安,2013)。
通过对公开文本以及访谈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媒体在“三鹿事件”中的媒介失语,不论在媒体记忆实践的公开表述还是行业的内部讨论中,都是比较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当事媒体倾向于淡化“不点名”报道所体现的职业失范,而将自身率先关注问题奶粉的时间点作为争取职业荣耀与新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当事记者与其所供职的媒体组织之间就该事件“不点名”报道所指向的自我审查过程的论述存在明显的张力。在话语层面,记者更倾向于使用职业规范或个人担当来解释其之所以采取或接受“不点名”方式报道“三鹿事件”的原因,以此来淡化组织层面的自我审查等来自编辑部场域内的压力对自身新闻权威以及职业成就感所造成的影响和困扰。
如果说,刊发“不点名”报道的媒体尚能通过事后追认的方式对职业失范语境中的新闻权威进行记忆实践层面的修补。那么,媒体人就此事件国内媒体的整体表现所进行的公开反思,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矛盾且不乏痛苦的,与此反思相伴随的是新闻权威的消解。《南方都市报》在社论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指出国内媒体在奶粉事件中暴露的双重性格,“揭开奶粉事件的幕后,我们看到了当地媒体异乎寻常的沉默……媒体责任不由自主的沦落……媒体在奶粉事件中充分暴露的双重性格,是媒体游历于市场与道义之间的天人交战”(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6日)。媒体人傅剑锋对此事件国内媒体的整体表现充满忧虑,他认为后续报道“既不能掩盖,也无法抵消三鹿事件爆发前中国媒体的集体失职。《东方早报》简光洲的出现,仅仅是让颜面丢尽的媒体捡回一些尊严而已”(傅剑锋,2009)。 与此同时,他也对自己及其先前所供职的媒体组织《南方周末》在此次事件中的欠佳表现表达切肤惋惜,“我和同事何海宁,应算是国内最早对三鹿事件进行系统研判与调查的新闻从业者,但最后我们没有首先发出相关调查,实属痛哉”(傅剑锋,2009)。但他那种基于专业媒体人对职业荣誉和新闻权威的格外看重,又试图再次确认和强化《南方周末》在中国媒体格局中的地位,“如果不撤,这篇稿子会给《南方周末》带来巨大的荣光和声誉……《南方周末》将是第一个把结石婴儿与三鹿奶粉直接联系起来的媒体,《南方周末》将会因为揭露这个公共卫生事件高高位于群媒之上”(傅剑锋,2009)。可见,在新闻场域内部涉及新闻权威与专业规范的反思时,媒体人所生产的实践话语纠缠于对现实的扼腕与理想的切近之间。
2.新闻业的高光时刻:新闻权威的修补、追认与竞争
与行业内的反思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新闻界将《东方早报》刊发的“点名”报道(简光洲,2008年9月11日)定义为中国新闻业的高光时刻(highpoint),并经由媒体记忆实践完成了对中国新闻界在此次事件中新闻权威的修补和追认。在梳理这些同行评议的文本时,笔者发现中国新闻界在“点名报道”之后的媒体记忆实践至少在两个脉络中展开。
一类是通过强化“点名报道”的道德合法性来凸显中国新闻界在“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责任,进而修补“不点名”报道以及媒介失语对新闻权威所造成的影响。对此,国内多家纸媒以“勇气”和“良知”来评议同行这篇“指名道姓”的调查报道(王中平,2008年10月28日;程晓龙,牛春颖,2018年12月30日)。《现代快报》(2010年12月5日)把简光洲定于“揭黑记者”行列,将其与王克勤并举,“在此(三鹿事件)之前,简光洲已经做了五六年的揭黑报道,其间经历的种种危险,同样不逊于王克勤。但在简光洲心中,感觉到最危险的一次,仍然是三鹿事件报道签发的那个晚上”。而在报道签发之前,简光洲曾只身前往兰州当地医院实地采访,亲见结石病婴儿在接受治疗时所经历的痛苦之后,他“下定决心在报道中写出三鹿的名字”,从而成为“直笔‘三鹿’第一人”(顾一琼,2008年11月11日)。由此,在新闻报道中,“点名”还是“不点名”成为衡量一个记者、一家媒体之于社会公众的责任。
另外一类是以专业规范为标尺,重申新闻媒体的职业化内核,以此将自身所承载的社会角色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体,进而对中国新闻界在此次事件中没有被明确标举的新闻权威进行追认。2009年12月31日,《南方周末》在“新年特刊”中向其所遴选的新世纪中国传媒业十周年的十位记者致敬,《东方早报》的简光洲位列其中。“南周”给出的致敬理由显得意味深长:“简光洲的故事让公众再次相信舆论监督之锋利”,而“点名”与“不点名”是一种“由非正常的语焉不详到正常的新闻表达,只是遵守了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求”。简光洲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从调查报道的职业化特征——证据链构成与平衡报道的角度来回忆其之所以“点名”三鹿的采写过程:“多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断这可能不是由于水质问题,最大的根源还是出在奶粉……我感觉证据还不充分,于是又联系到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求证……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谨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的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现代快报》,2008年9月28日)。
可以发现,上述中国新闻界修补与追认自身在“三鹿事件”中新闻权威的两个脉络实际上不啻为国内新闻媒体建构新闻权威的两个主要来源,两者共存于当时中国的新闻场域。经由媒体的道德合法性对新闻权威的确认,是在中国媒体尚未获得充分职业化发展语境下的另类表述,它在中国媒体格局中的存在,表明新闻权威的表达与建构路径本身即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需要从具体的个案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入手进行分析和抽象。
此外,更为直接的加冕来自当年的各类传媒奖项,这些奖项中既有来自于官方新闻奖的制度承认,也有声望卓著的媒体同行表达赞誉的奖项榜单。2009年10月30日,简光洲的点名报道获得“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作为中国官方新闻奖系统的最高奖项,包括“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在内的职业称号,都进一步确认了《东方早报》以及简光洲在“三鹿事件”中的职业荣誉,这也成为该报构建媒体记忆实践,彰显自身新闻权威的范例(简光洲,2009年11月9日)。此外,作为同行评议的致敬奖项,《新周刊》在当年12月17日发布年度新锐榜,简光洲获选“年度新锐人物”,颁奖词是“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石剑锋,2008年12月18日)。可见,道德合法性与职业化内核作为新闻权威的两种来源,被糅合于《新周刊》的颁奖词中。
虽然《东方早报》在“三鹿事件”中的表现获得了相当一致的褒奖和赞同。但放眼中国的媒介版图,先前曾刊发“不点名”报道的兰州媒体《西部商报》,讲述了中国新闻界在“三鹿事件”中抢眼表现的另一个版本。《西部商报》2009年3月3日刊文将该报于2008年7月30日的调查稿件《8月大的婴儿肾脏半瓶结石》视为“三鹿事件”的序幕,“张云(该报记者)没有想到,正是这篇看似不太起眼的报道,揭开了后来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李剑兵,唐学仁,2009年3月3日),该报从职业规范方面解释了“不点名”的原因,“由于当时没有任何官方佐证的消息,出于对报道负责的考虑,(因此)本报在报道时没有提及‘三鹿奶粉’”(李剑兵,唐学仁,2009年3月3日),同时又从舆论监督与同行互动的角度强调了自身在此次事件中的新闻权威,“在稿件见报的同时,将情况向卫生厅、工商、质监等部门进行了及时反馈。然而,就是这篇报道,引起了包括同城媒体在内的全国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李剑兵,唐学仁,2009年3月3日)。在“三鹿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时值全国两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热烈讨论,该报将其作为纪念“三鹿事件”的热点时刻,称“《食品安全法》的诞生,让人不得不想起去年波及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而这一切,要从《西部商报》一篇题为《8例幼儿肾结石,奶粉作怪?》的报道说起”(李剑兵,唐学仁,2009年3月3日)。由此,“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成为职业荣耀与新闻权威的竞争场域。
通过上述两个小节的描述和分析,较为充分地呈现了新闻权威在“三鹿事件”媒体记忆实践中被消解和建构的动态过程,有关该事件的媒介失语与职业荣耀得以共存于彼时的中国新闻场域。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人就中国新闻界在此事件中的“集体失语”所建构的媒体记忆实践,其背后所折射出的职业心态是相当复杂的,这种心态与国内媒体人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状态的感知判断以及新闻场域与外部权力、经济场域的互动方式有关。
四、社会创伤话语的搭建与离散:“三鹿事件”的叙事权威与创造性挪用
与“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同时进行,并一直持续着的,还有中国新闻界所建构的“三鹿事件”集体记忆,即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总体而言,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在问责程序与社会创痛的对比框架中搭建“三鹿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其二,通过频繁援引和挪用“三鹿事件”的集体记忆,借以凸显其他报道议题的框架与意义。两者的联系在于,前者是“三鹿事件”集体记忆的主体,中国新闻界就此开展媒体记忆实践的持续阐释,但与此同时,媒体报道对“三鹿事件”集体记忆的去语境化处理及其边缘记忆的开掘,使得持续建构起来的叙事权威愈加离散,与之相关的社会创伤话语也被不同程度地模糊和弱化。
1.“三鹿事件”社会创伤话语的建构与强化:社会创痛与问责程序的对比框架
中国新闻界就此事件所生产的社会创伤话语主要通过一个对比框架来建构与强化。这一对比框架的一边是三鹿事件的社会创痛仍在持续;另一边是三鹿事件问责官员异地复出的情况频频出现。通过这个对比框架所开展的“三鹿事件”媒体记忆实践在中国新闻界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协同。
(1)受害者群体与社会信任:“三鹿事件”社会创伤话语的建构
首先,被中国新闻界反复提及的“三鹿事件”社会创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害者的赔偿与诉讼问题。《南方都市报》试图以受害者的索赔进度来定义“三鹿事件”的社会影响,“三鹿公司被破产后,除了带来被告方的变动外,并不代表受害者提起民事赔偿的官司就此终了……三鹿一去不代表什么,消除三鹿事件对受害者的创伤远未结束”(《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30日)。新京报(2009年12月21日)在社论版刊登评论员文章,从价值理性角度呈现“三鹿事件”后续“个案式维权”及其法律困境,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企业一旦破产,赔偿难以实现。最近的例子是‘三鹿’破产案。如果能以生命健康为更高位阶的权利,来思考法律的意义,就有必要对《破产法》在破产债权的顺序制度中加以规定,即优先满足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是对国产奶粉质量与食品安全问题的预警与监督。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新闻界中的主流大报持续关注由“三鹿事件”所暴露的奶粉质量与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相关报道对“三鹿事件”社会影响的追踪和援引,进一步强化了此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2010年7月10日,《新京报》就青甘吉三省再现问题奶粉事件调用“三鹿事件”媒体记忆,“这种担心是有前车之鉴的,遥想河北三鹿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的处置措施可谓雷厉风行,事后公众似乎颇有雨过天晴的感觉。可没过多久,阴云再度聚拢”。就当下的食品安全议题对“三鹿事件”媒体记忆的召唤,使得此事件被塑造为一种开端,而经由此开端,一个公共议题的历史连续性就被建立起来,《法制日报》(汪军,郑昕,甘泉,2014年12月28日)从“三鹿事件”开始历数2008年之后的奶粉问题事件,认为“随着问题奶粉事件的增多,公众对奶粉行业的信任出现了‘断崖式’坍塌”。这种连续性的叙事与记忆成为媒体用以描述和定义近两年“问题疫苗”社会创伤的尺度,“有‘三鹿事件’的前车之鉴,有关部门对问题疫苗事件的处理应该更上心,从体制机制层面防范问题疫苗成为‘医药行业的三聚氰胺’”(汤嘉琛,2016年3月21日)。
(2)问责程序与“三鹿事件”社会创伤话语的强化
其次,作为这一社会创伤话语冲突框架的另一边,数年时间里,作为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三鹿事件”,近乎被中国媒体的记忆实践建构为问责程序的象征。数年间,中国新闻界对官员复出与问责程序方面报道和评论的强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反复。相关报道出现的时间从2010年的上半年一直持续到2015年下半年,具体报道篇数(滤除标题以及内容重复的报道文章)与篇次(相关报道被转载或同时刊登类似报道的数量)表现出较大起伏,展现这两组数字是为了体现中国新闻界对此议题开展媒体记忆实践的强度和变化趋势,这两组数字在相应年份的分布情况是:2010(7/58),2011(4/28),2012(2/26),2013(4/132),2014(5/260),2015(2/5)。
不难发现,中国媒体对官员复出与问责程序的报道出现三次高峰,分别是2010年、2013年和2014年,之所以会在上述三个年份出现报道篇数/篇次的高峰,与“三鹿事件”被问责的个别官员分别于当年在异地复出有关。由此可见,虽然新闻界就“三鹿事件”对问责程序的关注时间长达6年,但整体过程是以个别涉事官员、企业负责人的复出和减刑作为事件来驱动和维系的。也就是说,中国新闻界就问责程序所开展的媒体记忆实践,其主要特点在于让该议题在“三鹿事件”集体记忆中保持相当程度的可见性。
但亦有例外,《财新周刊》(2013年1月28日)的报道方式显得较为克制,这篇报道先以一句话新闻报道某官员低调复出的消息,随后就“问题官员复出履新引发民众热议”的名义,归纳评论区留言的网友意见。《财新周刊》的这篇综合报道,既将事实与观点有限剥离,又以归纳网友评论的方式,展现公众对此类事件的观点倾向。在“三鹿事件”6周年前夕,《重庆青年报》(2014年7月31日)以“三鹿集团前董事长田文华减刑”为由头,刊发调查报道《福喜阴影下的三鹿事件回访》,以较为平实的笔触勾勒这位商业女强人的成长轨迹,报道的整体基调在于追问减刑细节及其具体缘由。上述两家媒体对“三鹿事件”责任人减刑与问责程序议题的新闻生产,区别于多数媒体从结果正义与道德合法性出发的报道视角,更多遵从“用事实说话”的新闻传统。
不难发现,虽然有关“三鹿事件”的核心事实性报道在2009年之后快速减少,但基于其他事件性新闻,譬如问题奶粉再次流入市场、“三鹿事件”受害者群体与赔偿问题、问责程序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事件,它们成为中国新闻界经由媒体记忆实践持续生产该事件社会创伤话语的主要契机。总体而言,媒体通过“三鹿事件”的社会创痛与问责程序这一对比框架,实现了对“三鹿事件”社会创伤话语的建构与强化,中国新闻界关于“三鹿事件”的叙事权威得以确立。
2.“三鹿事件”的创造性挪用:社会创伤话语的离散与弱化
“三鹿事件”作为一个被重点标识和持续提及的“过去”,中国媒体对这一“过去”的创造性挪用以及有关此事件明确“定义”的缺失使得“三鹿事件”社会创伤话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弱化与离散。“创造性挪用”是指媒体对“三鹿事件”的去语境化处理,以开掘“三鹿事件”边缘记忆的方式,凸显其他议题的框架与意义。另一方面,中国新闻界错失了对“三鹿事件”进行明确定义的契机,尽管媒体尝试以追认的方式定义该事件,但未在阐释社群内形成共识。
(1)规范市场竞争:凸显消费者(网民)权益
从2010年开始,中国新闻界开始在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主流框架下援引该事件,并将其纳入企业竞争秩序的新范畴,由此诉诸公众权益。“三鹿事件”中涉及的企业主体被去语境化处理,相关报道将其泛化为两类范畴:一是消费品生产的实体企业;二是互联网资讯平台。在2010年腾讯与360的“隐私门”争端事件中,不同媒体通过再语境化,经常将上述两类范畴融合在同一篇报道中,从而搭建从“三鹿事件”看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不良竞争以及后者不尊重网民权益的报道框架。
一方面,媒体将“三鹿事件”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视为企业竞争的弊端,“恶意竞争势必造成两败俱伤……三鹿事件后,中国消费者普遍对国产乳业品牌持怀疑甚至排斥态度,洋奶粉趁机强占国内市场”;另一方面,“腾讯与360,你死我活,意味着什么?门户打开,市场丧失”(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2日),“野蛮式的恶意竞争,并非孤立个案,稍远者如三鹿事件”(刘晓忠,2010年11月5日)。经由这一新的叙事语境,“三鹿事件”成为指涉企业不良竞争的范例,“恶战正酣的腾讯和360,映衬出当前中国互联网市场失范的野蛮竞争和败德的商业伦理”(刘晓忠,2010年11月5日),因此“资本的力量应节制,不要恣意妄为,当民众对企业失去信心和信任,互联网行业的‘三鹿’就将出现”(检查日报,2010年11月6日)。此外,就当年腾讯和360之间相互指责对方侵犯网民隐私权,不少媒体均采纳了360的应对声明,提及2008年某互联网公司涉嫌屏蔽“三鹿”的负面信息,以此提示互联网平台应尊重网民权益(张书舟,2010年10月28日;戴欣平,2010年11月6日)。
(2)理解“三鹿事件”的新维度:网络删帖与知情权
紧接上文的讨论,在“三鹿事件”发生当年,有关某互联网公司屏蔽三鹿负面信息的传言盛行于网络,偶尔也有相关报道见诸报端。笔者在慧科新闻数据库进行检索,结果显示2008年和2009年并未有一家媒体使用“公关”来定义该互联网公司与三鹿事件的关系。也就是说,出于事实证据和重要消息源的缺失,中国媒体并没有将此传言纳入“三鹿事件”的主要报道议程。2010年,中国新闻界关于网络删帖与网民知情权的一系列讨论验证了笔者的判断,“虽然这只是三鹿事件的一个次要‘细节’,但它的不良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张邦松,2010年3月15日)。也就是说,相较于该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屏蔽涉事企业负面信息的报道只是“三鹿事件”媒体记忆实践中的边缘记忆。但很快,这一边缘化的媒体记忆被不同媒体予以报道和讨论,该互联网公司与“三鹿事件”的关系在相关报道中被定义为中国网络危机公关的典型案例,“‘网络删帖’中最经典的案例,应追溯到2007年‘三鹿奶粉’的危机公关……”(《新商报》,2010年4月5日),而“三鹿奶粉事件之后,网络公关行业就正式兴起了”(张书舟,2010年3月27日)。由此,原本游弋于“三鹿事件”媒体记忆实践中的边缘记忆经由网络删帖事件的媒体曝光而被贴上危机公关案例的新标签,成为 “三鹿事件”集体记忆的新维度。
(3)被“追认”的食品安全史:作为大事记的“三鹿事件”
自“三鹿事件”发生以来,围绕该事件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在阐释社群内部和外部开展了大规模且时段持续的媒体记忆实践。那么中国新闻界怎样定义“三鹿事件”?大众媒体对社会现实的定义是其作为阐释社群与其他社会群体争夺叙事权威的主要方式,也是其建构和影响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本文研究发现,至少在公开刊发的媒体文本中,中国新闻界并没有形成对该事件的明确定义,该事件作为集体记忆在新闻业阐释社群内部获得的基本共识和理解并未在中国媒体记忆实践的公开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新闻界似乎错失了在“三鹿事件”发生的较短时间内对该事件进行明确定义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曾有两家报刊以纪念“三鹿事件”为契机,尝试定义此事件,《潇湘晨报》在2009年1月21日,也就是“三鹿事件”公开宣判的前一天,该报首次提及“三鹿奶粉这一中国食品安全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09年11月25日,也就是三鹿集团宣告破产一周年,“三鹿事件”直接责任人张玉军、耿金萍被执行死刑的第二天,《兰州晨报》将此事件定义为“我们国家食品安全史上的一个耻辱点,同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两家媒体选择了不同的纪念契机,作出了类似的定义,可惜的是,这一定义很快被“三鹿事件”的其他报道文章所淹没。在“三鹿事件”发生十周年,笔者以“三鹿”+“食品安全史”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只有1家报刊借此纪念,《济南时报》 (2018年9月18日)通过回访“结石宝宝”,援引当地食品工业协会负责人的观点,将“三鹿事件”定义为“我国食品安全史上的转折点”。由此可见,虽然自“三鹿事件”发生以来,国内媒体曾尝试对该事件的社会影响进行明确定义,但零星的定义和追认尚未能够在中国新闻界的阐释社群内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有关“三鹿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在被中国媒体记忆实践持续建构和强化的同时,同样面临着自身对此事件叙事权威的弱化和离散。从当前来看,虽然这一弱化和离散的态势既无法和此事件社会创伤话语本身进行并举,也尚未影响“三鹿事件”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向,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这一事件集体记忆的稳定性,也提示了中国新闻界就“三鹿事件”开展媒体记忆实践的复杂性。
五、结语
十年来,中国新闻界对“三鹿事件”及其周边议题的关注是集中且持续的。通过对典型个案新闻报道与反思文本的描述和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国新闻界就“三鹿事件”开展媒体记忆实践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中国新闻界围绕“三鹿事件”的两种媒体记忆实践路径均展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首先,“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主要围绕中国新闻界在此次事件中的媒介失语和职业荣耀展开,看似相悖的同行评议使得新闻权威的消解与建构共存于这场讨论中。一方面,对于自我审查与媒介失语,媒体人的职业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既从专业伦理、社会责任角度生产了大量严肃且深刻的反思性话语,同时又试图通过媒体记忆实践对“三鹿事件”中的职业失范进行协商和修补,在“三鹿事件”发生后的几个重要纪念契机中,围绕独家线索与首发报道的争夺,“三鹿事件”成为中国媒体获取职业荣耀的竞争场域。另一方面,《东方早报》点名“三鹿”的报道之后,中国新闻界开始就自身在此次事件中的新闻权威展开规模化的言说与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就新闻权威来源问题,中国媒体表现出不同于专业主义规范的另类表述,道德合法性与结果正义成为他们确认和强化新闻权威的重要补充。
其次,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泽利泽“阐释社群”的持续阐释模式,有关该事件的社会创痛与问责程序被持续关注,这两个议题所建构的社会创伤话语被反复建构和强化,它成为中国媒体在不同语境中援引“三鹿事件”时的重要范例,借此中国新闻界对“三鹿事件”的叙事权威得以确立。但与此同时,中国新闻界进一步开掘该事件的边缘记忆,媒体人基于“当下”议题对“过去”的创造性挪用使得“三鹿事件”在频繁援引的过程中被去语境化。此外,由于中国新闻界错失了对“三鹿事件”进行明确定义的契机,对其社会影响的追认难以在行业内形成充分共识。这些都使得此前一直在持续建构和维系的社会创伤话语被一定程度地离散和弱化。
经由本文的个案研究,我们得以概观我国媒体在较长时段内建构重大社会公共事件集体记忆时的主要特征与叙事逻辑。基于中国新闻界媒体记忆实践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种来自媒体记忆领域的复杂性如何在中国新闻业与社会系统其他职业与行动主体的力量关系场域中获得恰切解释?这种复杂性所蕴含的协商、整合与离散等特征,其本身是否意味着中国新闻业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新闻业那种建基于共享叙事和专业主义的职业话语类型?上述问题所提示的研究展望,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立足本土语境,将中国新闻业与媒体记忆研究放置于一个更为宽阔的社会关系场域,同时也更具比较视野的理论资源中加以考察。■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4)。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6),46-60。
白红义(2018)。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8),25-48+126。
陈楚洁(2015)。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12),26-45。
陈楚洁(2018)。意义、新闻权威与文化结构——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新闻记者》,(8),46-61。
程晓龙,牛春颖(2008年12月30日)。2008中国记者素描。《中国新闻出版报》,03。
财新周刊(2013年1月28日)。聚焦三鹿事件被问责官员复出。《财新周刊》,09。
重庆青年报(2014年7月31日)。福喜阴影下的三鹿事件回访。《重庆青年报》,A04,A06。
戴欣平(2010年11月6日)。隐私门升级,“超级名单”成主角。《中国科学报》,B03。
傅剑锋(2009)。三鹿事件前传:我来剥媒体的皮。《南方传媒研究》,(17),123-130。
顾一琼(2008年11月11日)。直笔“三鹿”第一人。《文汇报》(上海),02。
简光洲(2008年9月11日)。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东方早报》,A20。
简光洲(2009年11月9日)。置于公众监督下才会更透明。《东方早报》,A14。
检查日报(2010年11月6日)。法学专家告诫:别做互联网行业的“三鹿”。《检查日报》,01。
济南时报(2018年9月18日)。“结石宝宝”这10年。《济南时报》,要闻版。
李红涛,黄顺铭(2014)。谋道亦谋食:《南方传媒研究》与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4),16-19+28。
李红涛(2013)。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当代传播》,(5),18-21+25。
李红涛,黄顺铭(2015)。传统再造与模范重塑——记者节话语中的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国际新闻界》,(12),6-25。
李红涛(2016)。“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5),6-30。
陆晔,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4),17-59。
陆晔,周睿鸣(2016)。“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件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7),24-46+126-127。
李剑兵,唐学仁(2009年3月3日)。一部报道一部责任一部法律。《西部商报》,A09。
兰州晨报(2009年11月25日)。“三鹿”事件中,假如媒体噤声。《兰州晨报》,A25。
刘晓忠(2010年11月5日)。败德的野蛮竞争无异于杀鸡取暖。《东方早报》,A22。
南方周末(2009年12月31日)。十年十文。南方周末(数字报),36。
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6日)。奶粉事件再检讨:媒体责任的失落与承担。南方都市报,A02。
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30日)。三鹿事件在受害者那里远未结束。《南方都市报》,A02。
石剑锋(2008年12月18日)。《新周刊》2008新锐人物:早报记者简光洲。《东方早报》,C1。
沈丽莉(2008年9月9日)。14名婴儿同患“结石”。《兰州晨报》,A12。
沈丽莉(2008年9月10日)。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一事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省卫生厅展开调查。《兰州晨报》,A05。
童静蓉(2006)。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话语。《传播与社会学刊》,(1),91-119。
汤嘉琛(2016年3月21日)。问题疫苗别成“三鹿”翻版。《新民晚报》,A05。
王中平(2008年10月28日)。要有“指名道姓”的勇气。《江西日报》,B01。
王永(2010年11月22日)。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对手。《人民日报》(数字报),23。
汪军,郑昕,甘泉(2014年12月28日)。重建“奶粉信任”不能仅靠药店销售。《法制日报(电子报)》,综合新闻。
新京报(2009年12月21日)。“个案式维权”还需制度性化解。《新京报》,A02。
新京报(2010年7月10日)。还有多少三聚氰胺在蛰伏之中。《新京报》,A02。
现代快报(2008年9月28日)。企业存亡VS孩子生死,简光洲:一个记者的二选一。《现代快报》A30。
新商报(2010年4月5日)。专业删帖凸现灰色利益链。《新商报》,40。
潇湘晨报(2009年1月21日)。经济人物:2008年的特殊印记。《潇湘晨报》,C04。
鄢烈山(2008年12月30日)。从单向宣传到信息交流的拐点——2008年新闻舆论监督观察。《中国新闻出版报》,02。
张志安,甘晨(2014)。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5-77+127。
张志安(2013)。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研究——以“毒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5),24-43+126。
张云(2008年7月30日)。8月大婴儿肾脏半瓶结石,专家介绍给婴儿过度补钙可能催生结石。《西部商报》,A17。
张云(2008年9月6日)。8例幼儿肾结石奶粉作怪?《西部商报》,A03。
张书舟(2010年10月28日)。360隐私保护器争吵升级,百度等发联合声明抨击360,360再发声明反击。《南方都市报》,A21。
张书舟(2010年3月27日)。揭秘网络公关灰色市场。《南方都市报》(全国版),A32。
张邦松(2010年3月15日)。删帖是对网络生态的野蛮破坏。《经济观察报》,16。
Carlson, M. (2007). Making memories matter: Journalistic authority and the memorializing discourse around Mary McGrory and David Brinkley. Journalism, 8(2)165-183.
MeyersO. (2007). Memory in journalism and the memory of journalism: Israeli journalists and the constructed legacy of Haolam Haze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7(4)719-738.
SchudsonM. (1992).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 Basic Books.
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7(4)366-376. 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0(3)219-237.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束开荣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