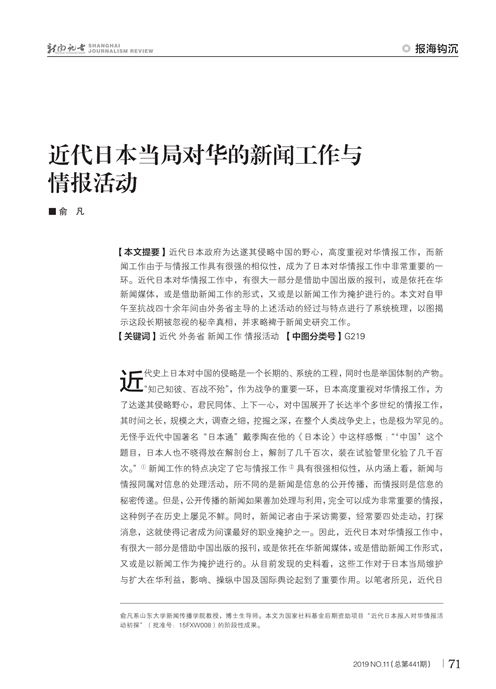近代日本当局对华的新闻工作与情报活动
■ 俞凡
【本文提要】近代日本政府为达遂其侵略中国的野心,高度重视对华情报工作,而新闻工作由于与情报工作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成为了日本对华情报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近代日本对华情报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中国出版的报刊,或是依托在华新闻媒体,或是借助新闻工作的形式,又或是以新闻工作为掩护进行的。本文对自甲午至抗战四十余年间由外务省主导的上述活动的经过与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图揭示这段长期被忽视的秘辛真相,并求略裨于新闻史研究工作。
【关键词】近代 外务省 新闻工作 情报活动
【中图分类号】G219
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同时也是举国体制的产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战争的重要一环,日本高度重视对华情报工作,为了达遂其侵略野心,君民同体、上下一心,对中国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报工作,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调查之细,挖掘之深,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无怪乎近代中国著名“日本通”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中这样感慨:“‘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①新闻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它与情报工作②具有很强相似性,从内涵上看,新闻与情报同属对信息的处理活动,所不同的是新闻是信息的公开传播,而情报则是信息的秘密传递。但是,公开传播的新闻如果善加处理与利用,完全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情报,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同时,新闻记者由于采访需要,经常要四处走动,打探消息,这就使得记者成为间谍最好的职业掩护之一。因此,近代日本对华情报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中国出版的报刊,或是依托在华新闻媒体,或是借助新闻工作形式,又或是以新闻工作为掩护进行的。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这些工作对于日本当局维护与扩大在华利益,影响、操纵中国及国际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笔者所见,近代日本当局对华的新闻工作与情报活动的主管机构演变过程大体如下:甲午战争之前,此项工作主要由军方即参谋本部与陆、海军省主管;日俄战争之后,外务省逐渐取代军方成为主管;“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又接替外务省成为新的主管机构;“七七事变”后,日本设立了内阁情报部统管相关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将其升格为内阁情报局,成为战时日本情报及宣传系统的“巨无霸”。而对于这一重要问题,我国学界似乎尚未予以足够重视。笔者不惮浅陋,以外务省及军部档案为主要材料,对近代日本当局依托新闻工作对华进行情报活动的历史进行简单梳理,以求还原历史,警示后人,并求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大陆浪人”与甲午战争
1854年5月,明治维新“前三杰”之一的吉田松阴写作了著名的《幽囚录》,此书后来成为明治维新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之一。在这本书中,吉田痛陈日本处于世界强国包围中的危殆局势,号召自强自立,并且开出了这样的药方:
凡皇国臣民,不问公私之人,不拘贫富贵贱,均应推荐拔擢,为军师舶司,打造大舰,操练船军。东北,则虾夷、唐太;西南,则琉球,对岛。往来之间日夜留心,以通漕捕鲸,练习操舟之法,熟悉海势。然后,叩问朝鲜、满洲及清国,然后于广东、咬留吧(雅加达)、喜望峰(好望角)、豪斯多拉理(澳大利亚),皆设馆,留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之事……如此不过三年,可知大略。③
1859年11月21日,吉田被幕府斩首,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规划变成现实,但是此后明治政府的“志士”们,却前赴后继地沿着他的规划,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以种种身份为掩护的“探听四方之事”的间谍们,而中国则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
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现今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来华的日本间谍岸田吟香恰好是一位著名报人。岸田早年曾与浜田彦藏等人合作在横滨创办手抄报《新闻志》,被视为日本近代新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④此后,他又供职于《东京日日新闻》,并在牡丹社事件中随军前往台湾,连续发表报道《台湾从军记》,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为当时日本的“名记”,并一度出任该报主笔。1877年,他辞去主笔职务,专心经营其发明的眼药水“精錡水”,并在东京开设“乐善堂”药店。1880年,他在上海开设了乐善堂分店,将事业拓展到中国。在此之前,他还曾于1866及1868年两度来到上海,并曾在沪长期居住,这在当时的日本人中是非常罕见的。他也由此引起了军方的注意,1886年3月,陆军中尉荒尾精受参谋本部派遣前往汉口收集情报,他在中国登陆的第一站便是上海乐善堂,岸田对他进行了详细指导,并慷慨地提供大量商品供其在汉口开设乐善堂分店,以作为在华调查的基地,所售得款便充作调查费用。自此,乐善堂便从一家药店变成了日本在华情报活动的基地。荒尾藉此网罗了大批“大陆浪人”,四处刺探中国情报,调查中国各地各种情况,为当局提供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报告,宗方小太郎便是个中翘楚。
宗方小太郎,日本熊本人,少年时曾从同乡佐佐友房学习,受其力持的“天皇主权论”和“国权扩张论”影响而走上间谍道路。1886年加入乐善堂成为最早的一批间谍。1887年2月-1888年2月期间,宗方游历华北“八省二十三府十八州四十有七县,纵横一万六千余里”,⑤写就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对江苏、山东、直隶、盛京、山西、河南、湖北七省的风土人情、山川道路、地形地貌、财政收入、设官状况、城垣防卫、炮台舰队、驻军巡查、物价汇率,乃至饮食习惯、卫生状况等,靡不毕载,虽网罗广泛却要言不烦,且多为客观记述,少有主观评价,体现出了一个间谍的良好素质,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和当局高层的重视。1893年7月31日,他由岛琦好忠⑥批准成为海军部情报“嘱托”,⑦
从此开始了他“为国效力”的生涯。
宗方情报生涯中的第一个亮点,便是甲午战争中对威海卫海军基地的侦察活动。1894年6月26日,他突接岛崎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命予立即从汉口出发至芝罘会井上氏”,“朝鲜形势紧迫之故也”。⑧宗方遂立即出发,于7月10日抵达威海卫军港,在此地侦察半月,发出机密情报十余份,详细报告了北洋水师及周边防卫炮台的部署、装备、战备及出发等情况,为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立下“奇功”,并于战后获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的“殊荣”,⑨并一跃而成为日本当局制定对华政策的高参之一。
从表面上看,成为高参后的宗方并没有继续从事军事情报工作,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在华出版报刊上面。宗方对于新闻业并不陌生,早在熊本家乡时期,他便已加入佐佐友房组织的“紫溟会”并参与该会《紫溟新报》的编辑与发行工作。来华之后,宗方更是积极“提倡以发行报纸作为对中国的指导机关为当前急务”。⑩他对在华办报的认识,在一封给佐佐友房的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您所知,该国报纸之报道、评论颇具动摇朝野人心之势力,虑及日本今后对清国之政略,于上海、汉口等要地设二、三机关报纸,其必要性自不待言。希望设立,以为国家之事业,为后来之所计。
总之,如不安插各种势力于各地,则举步而维艰。[11]1892年11月12日,《汉报》馆主姚文藻遇到了经营问题,就商于宗方,[12]宗方决定借此机会将该报买下,作为日本在华的宣传机构。经过长期游说,他终于在台湾总督府与海军省的支持下于1896年2月12日买下该报,[13]成为“日本人在清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14]也成为宗方构建日本在华宣传情报活动网络的基础。此时有志于“扬国威于四方”的“大陆浪人”在华活动已逾十年,人数已过百人,亟需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和组织行动。1895年1月,宗方与前田彪[15]等七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以“改革组织,巩固团结,以谋敏活之运动”为目的的“乙未同志会”,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近代日本人在华组织,其人员基本以乐善堂与荒尾精建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成员为主,自此,原本松散的日本间谍群开始有了组织,也有了明确的步骤与计划,而其主要行动之一便是在各地设立报刊,以为宣传及情报活动基地。1897年7月,宗方与前田商议收购《福报》之事,由前田在福州谈判收购条件,宗方负责争取经费。11月5日,宗方从台湾总督府获得“《闽报》再兴费五百六十日元,约定每月补助百五十日元”。[16]12月5日,前田报告《福报》已收购完毕,将改名为《闽报》,“近日将发刊云”。[17]1898年6月25日,“乙未同志会”与近卫笃磨组织的“精神社”在东京合并,组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同文会”,该会“以对中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援助对华事业及促成清日两国人员交流为纲领”,并决定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等地,渐次设汉字新闻”。[18]1899年12月15日,在井手三郎主导下,同文会收购经营困难的《字林沪报》,改名《同文沪报》出版。至此,日本在汉口、上海、福州均办有一份报纸,对华宣传情报网络初步成型。
除了建构在华宣传网外,宗方等人投身报业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可以藉此获得一个与中国上层文人交往的平台。近代以来,许多中国重要文人纷纷投身报业,特别是维新派与革命派等重要政治势力都非常重视报刊的力量,其精英分子多积极投入其中,所以,报业同道的身份,便于与他们接近。从宗方的日记来看,从他1884年来华到1896年主持《汉报》之前,他在中国的交往圈子仍然以在华日本人特别是乐善堂及日清贸易研究所成员为主,几乎不见他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记录,但自1896年起,这种记录逐渐增多,而且与之交往的中国人的地位和层次也逐渐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主持《汉报》后所获得的报馆馆主身份,而这种交往面的扩大也给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宗方与汪康年的交往便是一例:1897年2月26日,宗方离汉抵沪;3月2日,汪邀其赴宴,宗方“以事辞之”;3月5日,宗方至《时务报》馆拜访汪,这乃是宗方与汪的最初会面。作为同行,《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宴请自汉口远道而来的《汉报》馆主宗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宗方与汪的关系也由此逐步建立。宗方之所以要与汪结交,其用意并不仅在于汪,而在于其背后的晚清重臣张之洞。随着两人交往日深,所谈论的话题也日渐深入。是年12月3日,二人晚餐,“盛论当世时务”,汪告其彼“有意于支那内另外创立新国,与予(宗方)所见略同”。[19]翌年4月9日,汪自湖南归后来访宗方,“共谈立国之要务”,宗方问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二氏乃天下之重望,我辈宜说之以大义,使其为我所用,于做事之时,将甚多便益,足下有其意否?”汪答曰:“陈、张二氏,眼前虽不为我用,然当时机来临之日,或可联鑣并驰,共同致力中原。”11日,宗方往访,交汪时事话片十二则,其大要为:“窥时机举义兵,占据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及广东之一部,使其连成一片,以建立一国。并列举有关之方法手段。” [20]这些对于日本当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宗方随即于12日向海军军令部谍报课长安原金次发出“号外信”告知情况;15日,又再追加报告,“警醒我政府必须速与清国达成口头约定,要求其不可将浙江、福建二省让与外国”。[21]宗方日记中记录的他与汪的交往多达百余次,可以说,从1897年3月两人初次会面至1911年11月汪去世,两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虽然这些记录大多仅有只言片语,但从这一事例观之,与汪的交往应当是宗方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
二、外务省主导的对华舆情调查工作
与军方不同,外务省相关工作始于对华定期舆情调查工作,这主要是由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影响。甲午战争中,日本靠精心策划的国际宣传工作把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描绘成“进步、文明”的日本与“落后、野蛮”的中国之间的战争,从而在国际舆论上大占便宜。日俄战争中,日本又利用中国对沙俄的仇恨以及立宪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把这场帝国主义国家间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描绘成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种族战争,大力宣扬所谓中日“同文同种”论,使得许多中国人在战时倒向日本。战后,尝到甜头的日本当局更加重视舆论的作用,而要操纵舆论,首先就需要了解被操纵国家的舆论状况。有鉴于此,1908年5月30日,外相林董电令驻华各使领馆云:
需了解贵地发行的重要报纸(包括中文及英文)的主义、报主、资本、受社会欢迎程度、主笔的派系(属于何机关)及势力等,请至急调查并且详细报告。另外,从以上报刊迄今为止的报道评论中,下裁与帝国有利害关系或有其他参考作用的内容,上呈本省。[22]由外务省主持的对华定期舆情调查工作就此开始。[23]从现存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来看,这一工作始于1909年,结束于1937年。综观现存报告,大体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报告的程序看:此报告一般是在每年1、2月间(个别地方会拖延一些),由日本驻华各地使领馆负责调查其驻在地及周边地区的报刊出版状况,然后形成地区报告上报外务省;待各地报告收齐后,外务省再将其编印成小册子,发给各有关部门参考。
(2)从报告的范围来看:最初仅有27个城市被列入范围,此后逐渐增多,最多时有42个,但基本都集中在东北(如奉天、吉林、大连)——华北(如北京、天津、青岛)——东南(如南京、杭州)——华南(如广州、福州)一线,兼顾华中(如汉口)及西南(如昆明、贵阳)地区,对西北及中原地区的调查则相对比较薄弱。
(3)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此报告一般由主表“支那各地新闻要览”及收录自统计结束至出版期间报刊变化状况的“附录”两部分组成,此外还有一些统计表,主要统计与日本有特殊关系的中国报刊及列强在华出版报刊的情况。“要览”部分由“名称”(即报刊名)、“主义”(即报刊政治背景)、“持主”(即出资人)、“主笔”及“备考”五部分组成,其中“备考”栏内容最为丰富,主要着重于报刊是否具有其他列强背景及是否有反日倾向及其影响力。如1920年报告中《益世报》条目此栏云:
(该报)最初是作为天主教的机关报来发行的,却没有博得法国政府的好感。现在有美国资本介入,在努力拥护美国权利的同时,大肆鼓吹煽动排日。与京津《泰晤士报》和《河北日报》共同列为排日报纸的急先锋。是当地发行的汉语报纸中出售数量最多、势力最大的报纸。[24]随着日本在华利益的不断扩大,原有的表格逐渐不敷使用,1923年12月,外务省发布了新的表格,其内容包括:
一、概说(新闻界的现状,各种不同的新闻团体之间的关系的记述)
二、报纸、通讯社及杂志
1.报纸名(包括:报名、使用文字、国别)
2.政治态度(包括:政治态度、与政党派别的关系、除政党派别以外还与何方保持何种关系、对日本的态度)
3.主持人与社长(包括:主持人或社长的简历、主要出资人简历)
4.主笔及重要记者(包括:主笔及重要记者简历)
5.备考(包括:创刊年月、刊别[25]、每期平均页数、发行量、发行地区、创刊至今简史、新闻特色及其他)。[26]可以看出,新的表格虽未增添类目,但所收集的内容却已较前丰富得多。
(4)从报告的地位上看:此报告的发放范围逐渐扩大,其1909年的发放范围为:
此件发驻清公使馆,上海、天津、哈尔滨、奉天总领事馆及芝罘、牛庄、厦门、苏州、杭州、福州、重庆、汉口、长沙、南京、汕头、广东、铁岭、辽阳、安东、长春、吉林、香港领事馆。[27]由此可见,该报告最初仅为驻华各使领馆与外务省之间内部交流的资料。1915年,此报告发放范围开始扩大:
此件发驻间岛、哈尔滨、天津、奉天、广东、上海、汉口、香港总领事馆;新民、头道沟、局子街分馆;安东、铁岭、长春、珲春、辽阳、牛庄、吉林、齐齐哈尔、济南、芝罘、苏州、南京、长沙、重庆、厦门、杭州、沙市、福州、汕头领事馆及驻英、意、美、法、俄大使馆;中国、荷兰、瑞典、智利、暹罗、西班牙、巴西、墨西哥公使馆;并发陆军次官、海军次官、参谋次长、海军军令次长、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警视总监、内务省警保局局长。[28]到了1919年,其范围再度扩大:
此件发各省(除宫内省)次长,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第一第二部长、总务部长、海军军令次长、陆军军务局长、海军军务局长、关东厅、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青岛守备军司令部、青岛守备军民政长官、内阁书记官长、内阁记录课、拓殖局长官、警视总监、内务省警保局局长、递信省通信局长、大藏省理财局长、农商省商务局长;又发外相、外务次官、政务局长、通商局长、条约局长、政务局第一第二第三课长、通商局第一第二第三课长、条约局第一第二第三课长、电信课长、人事课长、会计课长、文书课长;又送驻英、法、奥、意、美大使,驻荷兰、巴西、西班牙、瑞典、瑞士、墨西哥、比利时、智利、暹罗、阿根廷公使馆;并发在华公使馆、各领事馆及驻香港总领事馆。[29]从上面文件可见,此时该报告的发放范围除包括了外务省系统及各主要驻外使馆外,还包括各省次官、所有殖民地行政长官以及军方主要部门,几乎把当时日本军政两界要害部门一网打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机构设置中,第一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第二部则负责情报工作,此报告专门发到这两个部门,其用途自然可想而知。
“调查”虽然全面、深入,且在日本对华情报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毕竟每年只有一次,缺少时效性。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情混乱,在一些突发重要事件中,各驻华使领馆还会向外务省递交临时报告,以便该省及时掌握中国舆情动态。外务省还会在重要事件发生后进行专门的舆情调查工作,现存“舆论并新闻论调”档案中共有242个簿册,其中大半与中国问题有关,就事件而言,共包括满蒙铁路交涉、万宝山事件、汉口“四三事件”[30]、“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各国对华财政援助计划问题、1931年反蒋运动[31]、“福建事变”、西安事变、济南事变、“俄奉协定”[32]、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中东路事件、苏“满”铁道交涉[33]14个专题,几乎涵盖了20世纪20-30年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所有重要事件。与“调查”专注于收集中国报刊的状况不同,“论调”除收集中国报刊对某一事件的报道外,还集中收集世界各主要国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及评述,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报道与评论,还会专门全文译出并附以收集者的解读,一并上报外务省。两种调查相互配合,足以使日本政府及时掌握各种舆情动向,从而达到操控舆论的目的,济南惨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二次“北伐”,面对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局势,意图控制华北及东北地区的田中内阁为阻挡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北上,决定出兵山东。4月19日,第六师团在青岛登陆,随即控制了青岛及胶济路沿线要地。5月1日,北伐军克复济南;3日上午,日军突然向北伐军发起攻击,残害我军民多人,并将国民政府派往交涉的外交专员蔡公时残忍杀害,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济南惨案”。在这一事件中,外务省与军部密切合作,上演了一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好戏。自出兵后次日至5月3日惨案发生前的23天时间里,外务省共收到来自驻英代理大使佐分利贞男、驻哈尔滨总领事八木元八、驻美大使松平恒雄、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吉林总领事川越茂、驻法大使安达峰一郎、驻敖德萨领事岛田滋、驻巴西大使有吉明、驻香港总领事村上义温、关东厅警务局长、驻芝加哥领事田村贞次郎、驻桑港(旧金山)总领事井田守三发来的多份关于其驻在地报刊对于此次出兵事件态度的报告书,[34]对于日本当局随时掌握舆情动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月11日,日军占领济南;12日,参谋次长南次郎及陆军次官畑英太郎便向关东厅、朝鲜、台湾军参谋长,华北驻屯军参谋以及驻京、沪、汉、粤、哈、英、法、德、奥、意、土、波、美、印、墨、阿、苏武官发出训令,称“济南事件中我军行动的正当性没有受到重视,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一点,应该在宣传方面加大力度”,并提出七条措施:
一、帝国出兵的目的除了保护居留民之外并无其他,我军的行动也是没有超出一步要达成任务所必要的范围。
二、我军从出兵当初,完全服从南北两军,完全没有并且今后也不会有阻止南军北进的企图。
三、济南事件的发端在于南军掠夺性的开枪,并且在于随之而来的计划性挑衅。
四、对方的残暴行为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对方的宣传也是为了以非掩实的虚构之事。
五、八号以来,参照当时的状况,济南附近地区的扫荡行动是为了保护居留民以及铁道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对于他的暴虐完全没有任何报复性的含义。
六、攻击济南城时,运用各种手段不伤害无辜的居民和手无寸铁的中国兵。
七、南军扫荡之后,在济南附近与同地区的当政者协同,一起维持秩序、安抚中国居民。[35]14日,畑英太郎将此七条电告占领济南的第六师团参谋长,并告其“此案足以证明(我方)正在努力使未报告的事实真相得以正确地报告”。[36]18日,内务省又要求该部发布“济南事件中日本侨民残害后尸体照片”。[37]由于1922年2月1日限制军备会议第五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在中国之外国军队决议案》中规定:“中国业已声明志愿并能力担任保护在中国之外人生命、财产”,[38]日本当局上述举动,可谓着着打在了中国的痛处。所以在济案发生之初,国际舆论一度对中国极为不利,《泰晤士报》驻北京通信员明确声称“北京外侨皆欢迎日本对于中国之严厉的自卫手段”;《每日电讯报》社论甚至主张“列强对于此可怕的现象,必须一致取较阔大较清醒的见解,维持商路之开通,保障侨民之安全,应列强共同负责”,公然鼓吹列强共同干涉中国。[39]日本得以在这次事件中抢占舆论先机,这些报告书当居首功。
除了这些舆情调查工作外,外务省还利用日本在华通信社建构情报网。1919年4月14日,外务省政务局制订了《关于新闻政策的新计划案》(新聞政策ニ関スル新計画案),其中第四章“通讯社”中明确规定:日本在华各地通讯网“根据情况同时可作为在外公馆的情报机关”。[40]根据这一文件,外务省决定将1914年10月成立的东方通信社改为该省直属的情报机关。1920年9月30日,情报部第一部向外相内田康哉递上《东方通信社扩张计划案》(東方通信社擴張ニ關スル件),件云:
由于最近支那国内的形势日益恶化,我国对支那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由于目前这种局面很难转变,所以随着支那战场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准确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我国制定和实施对支政策。另一方面为了解开支那官民对我方的误解,要更加重视情报和宣传工作传播我方公平态度,这目前是极为迫切的。……因此,我们利用现有的东方通讯社,将它视为外务省情报部临时设立的直辖事业,通过扩展该通信社来达到上述的目的。[41]在这篇长达近5000字的计划书中,外务省对东方社的人事、财务、业务等方方面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要求该社“表面上要强调是民间企业,但实际上是外务省的事业”,“所有业务应听从情报部长或该地区帝国公使或领事的指示”,“若没能获得情报部长的许可,不许从事或接受其他业务”。如此,东方社便由一家以促进对华宣传为主,兼及情报工作的通信社,完全变成了外务省在华的情报机构。每当中国发生大事之时,东方社都会利用其遍布各地的通讯网刺探消息,并及时向当局汇报。比如1922年5月9日,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张作霖被迫宣布奉军退出关外,一向视东北为自己禁脔的日本当局自然高度关注此事。东方社在这一天连续向关东军参谋长及驻天津军司令官发出五份电报,报告奉军动向,以供当局参考。[42]
三、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相关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对华情报工作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37年之前,从政府层面看,日本的情报工作与新闻工作呈现一种多头管理的局面,仅就舆论调查一项工作来说,当时就有外务省、企划院、陆军省、海军省等多个机构在同时进行,再加上各驻外使领馆以及各殖民地、占领地民政、驻军机构等,可谓是典型的“多龙治水”的局面,这种叠床架屋的模式显然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于是日本政府于1937年9月24日决定在原内阁情报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专门的机构——情报部,该部直属首相,其具体职责为:
一、以贯彻国策为基础,就情报相关各项事务进行联络和调整;
二、就内外报道等进行各厅事务的联络和调整;
三、就启发宣传[43]进行各厅事务的联络和调整;
四、收集不属于各厅的情报,实施报道及启发宣传活动。
在必要情况下,在实行上述职能时,内阁情报部可以要求相关各厅提交情报和资料并进行说明。[44]为了全面战争的需要,1938年4月1日,日本国会颁布《日本国家总动员法》,这标志着日本举国开始正式进入战争体系,其中“情报与宣传”也被列为“总动员业务”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配合战争,1940年9月6日,日本当局又决定在原有的情报部的基础上设立内阁情报局。情报局在继承了情报部全部职权的基础上,其权限又有极大扩充:首先,除报纸外,情报局还拥有对录音、电影、戏剧以及广播的指导与控制权;其次,情报局与内务省警保局[45]的人员可以互相兼职,打通使用;再次,情报局还有监督日本放送协会(NHK)及同盟通信社的权力;最后,情报局还整合了很多其他情报机构的权力,具体包括:
一、外务省情报部的事务
包括:海外情报收集、对外启发宣传、定期召见国内外记者;
二、内务省的事务
包括:图书课对录音产品的查禁以及警务课对电影、戏剧及演出的相关权力;
三、陆军省情报部的事务;
四、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的事务;
五、递信省的事务。
包括:电务局无线课查禁广播内容的相关事务以及对日本放送协会(NHK)进行监督的相关事务。[46]通过上述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情报局几乎整合了日本当时所有的情报及宣传机构的职能,可谓是情(报)宣(传)一体、军政打通、陆(军)海(军)兼修、(国)内(国)外通吃,成为日本战时新闻宣传和情报工作的“巨无霸”。内阁情报局的设立,标志着日本战时情报工作与新闻宣传工作的正式合流,也标志着政府层面对“情宣一体”体制的确认。
在情报局领导下,日本当局以新闻工作为依托对华进行的情报活动大大膨胀起来。但是,由于双方已经开战,两国间正常的交往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以往以外交人员、侨民、学生、旅行者、报人等种种身份为掩护的日本特务已经很难在大后方公开活动,所以大后方公开出版的报刊和广播便成了日本了解国民政府情报的最重要渠道之一,正如内阁情报局首任总裁横沟光晖所言:
无论在国外或是在国内,某事件对于受众方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或者收到一份具有重要性的报道,这些都是所谓的情报。一个情报在发布方看来是一个报道,而从受众方看来就是情报。情报和报道互为表里,但是对于接受方来说它有什么意义才是构成情报内容重要的要素。[47]在日本现存档案中,这类剪报与广播记录文件被统称为“各种情报资料”,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检索主页对这一类目的解释为:
“各种情报资料”簿册中的内容是内阁从国内外报纸、通信社、杂志、广播中收集的各种情报以及相关机关收集的情报,其他对外公布的新闻报道资料等。其中分为陆军省公布,各国报纸论调,内阁情报部情报集等分册。[48]这批“资料”现存共64个簿册,除4册为该部内部文件(“主要文書綴1、3”,“復興情報”,“内閣情報局設置関係書類”)外,实际存有情报60册,其中最早的情报是明治37年(1904年)有关日俄战争各国舆论状况的调查。从各分册名称上来看,共有17册与中国问题直接相关,即“満洲問題ニ関スル情報”、“上海事件ノ情報”、“上海並満洲事件ニ関スル新聞発表”、“満洲及支那事変ニ関スル新聞発表”、“支那事変彙報”、“支那事変関係内国外字新聞論調”各1册,[49] “支那事変ニ関スル各国新聞論調概要”2册,“支那事変ニ関スル情報綴”3册,“北支事変関係情報綴”6册,为所有各主题中之最多。其内容主要是对前述事件中中外媒体发布信息的收集整理,其信息源除中国报刊、广播外,还包括欧美各国广播、报刊及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可谓包罗万象,而具体形式则是以一句或几句话高度概括所收到的信息大意,却并不加以评论,仅仅陈述而已。横沟光晖曾经要求“无论是情报还是报道,必须是没有任何歪曲、没有任何修饰,必须是表现事情原模原样的真相”。[50]至少就这些“资料”看,情报部应当是很好地达到了这一要求。
除了外务省之外,军方也在进行类似工作,所得资料亦汇编成册,题为“重慶側資料”,分为“政府组织”、“华侨”、“参政会”、“外交”、“政治”、“地方政治”、“社会”、“文化”、“特种读物”[51]、“军事”、“财政”、“经济”、“金融”、“中央经济”、“地方经济”“西南经济”、“西北经济”,以及“杂项”等18个分部,至少共260册。现可见编号最早的一册为第11号《财政·日文资料(西南财政 昭和17年10月迄)》 (国立公文书馆档案A03032201000),最晚的一册为第260号《地方经济 (产业、工、矿、商、企、水、渔、劳、建)昭和18年》(防卫省档案C13032403700)。其各簿册情况基本大同小异,以第101号“军事·空军”分册为例:本分册共196页,81条,全部是1942年5月至11月间有关中国空军的内容,其“目录”部分共有“类别”、“细目”、“内容摘要”、“出所”(即出处)、“昭和 年 月 日”、“文別”(即语种)及“页数”等项,根据“出所”一栏显示,在所有81条情报中,来自“重庆英放”(重庆英文广播)的最多,为19条,其余依次为“放送”(广播):12条;“成都英放”(成都英文广播)、“华文放送”(中文广播)、“X”(似应为出处不明):同为11条;“大光报”:5条;“重庆放送”(重庆广播):4条;“K情报”:2条;“建国日报”、“中央社”、“大同日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国民日报”:同为1条。[52]来自各种媒体的情报占了本簿册总数的83.95%,新闻工作对于日本军方情报收集之重要,由此足可见之。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甲午至抗战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日本当局(主要是外务省和军方)通过多种方式,以新闻工作为主要材料、掩护或依托,对中国进行了长期、深入、细致的情报工作。这些工作的成果,对于日本当局把握中国国内局势、制定对华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等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会长期坚持进行这些情报工作,并最终成为日本侵华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往昔那副积贫积弱的模样;而那段任人宰割的历史,也决计不会再重演。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厘清这段历史,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下,想来也是不无裨益。■
①戴季陶:《日本论》第8页,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治到昭和时期日文中的“情報”一词的意思,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通过特殊手段收集的有关军事、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之外,还泛指所有“信息”。但是,本文所讨论的日文史料中的“情報”,主要是指日本军部及外务省以新闻工作为依托对华进行的信息收集活动,这些活动大都是秘密或半秘密进行的,并且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即为日本当局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情報”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军事情报、政治情报等概念并无区别。
③[日]奈良本辰也编:《吉田松陰著作選:留魂録·幽囚録·回顧録》,东京:講談社,2013年11月,中文译文部分据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第39-40页,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
④李明水:《日本新闻传播史》第19页,大华晚报出版社1980年12月第2版
⑤[日]宗方小太郎著,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后文同书引用仅注《宗方日记》+册数+页码
⑥岛崎好忠,旧日本帝国海军军官,1893年5月,日本为筹备甲午战争成立海军军令部,下设两个局,20日,岛崎被从军舰“葛城”号舰长职务上调任第二局局长,专门负责“海军教育及训练,谍报组织及情报编纂”工作,可以认为岛崎此时是日本海军情报部门的直接最高领导人。
⑦《宗方日记·上》第293-294页
⑧《宗方日记·上》第326页
⑨《宗方日记·上》第335页
⑩刘望龄主编:《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11-1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1]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関係史》第74页,研文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阳美燕:《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1896—1900)——日本在华第一家舆论机关的诞生背景及编辑方针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2]《宗方日记·上》第270页
[13]《宗方日记·上》第361-364页
[14]《濑川浅之进致西德二郎报告》,1900年4月2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406692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5]时亦为海军情报人员,在福州活动。
[16]《宗方日记·上》第402页
[17]《宗方日记·上》第406页
[18]戴海斌:《山根立庵、乙未会与〈亚东时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9]《宗方日记·上》第405-406页
[20]《宗方日记·中》第416-417页
[21]《宗方日记·中》第417、421页
[22]《林董致驻华各使领馆训令》,1908年5月3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408306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文部分据许金生:《宣传战的前奏:近代日本在华报刊定期调查活动探析》,《江海学刊》2015年第3期第170-177页
[2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外务省不仅开始对华进行定期舆情调查,也开始对欧(英、法、德、荷、俄、奥、比、瑞典、挪威等国)美(美国、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等国)各主要国家及主要殖民地(如印度等)进行定期舆情调查工作,其用意自然在于掌握舆情状况并在适当时施加影响,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政務局編纂外国新聞調査書配布》第1-5卷相关记录,档案号:B03040673700、B03040675100、B03040676300、B03040678600、B03040679800。
[24]《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提出ノ件》,1920年2月26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档案号:B030408819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5]即日报、周刊、晨报、晚报等。
[26]《机密第二九一号》,1923年12月1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档案号:B030408820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7]《四十二年二月十八日記錄編纂接》,1909年2月18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档案号:B030406739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当时在华各领事馆中,只有新民府、沙市、齐齐哈尔三地领事馆未发。
[28]《〈支那ニ於ケル新聞紙ニ関スル調査〉右公信ナリ機密扱トシテ送付ノコト》,1915年5月19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档案号:B030406766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9]《機密合送第一二一號》,1919年10月2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档案号:B030406809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30]即1927年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屠杀中国工人群众的事件。
[31]即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压力下宣布“下野”的事件。
[32]即1924年9月20日奉俄双方签订的《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
[33]即1933年5月至1935年3月间苏日双方进行的关于出售中东路的谈判。
[34]《済南事件/輿論並新聞論調·第一巻》,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B020300813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35]《済南事件に関し電報の件》,1928年5月12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军部档案C04021700000,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藏
[36]《宣伝資料送付の件》1928年5月14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军部档案C04021700200,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藏
[37]《邦人惨殺死体発表の件》,1928年5月18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军部档案C04021700300,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藏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469页,凤凰出版社1991年版
[39]《日本出兵山东事件之西报评论》,《东方杂志》第25卷第10期,1928年5月25日
[40]《新聞政策ニ関スル新計画案》,1919年4月14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406004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41]《東方通信社擴張ニ關スル件》,1920年9月3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407063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42]参见《亜細亜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奉直紛争·第五巻》,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502452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43]《内閣情報部官制》,1937年9月24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A03022131100,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44]内务省警保局是日本中央警察机关,也是重要特务机构,著名的“特高课”就是其下属机构,主要负责监视、监听、处理危险人物档案等,该局还设有“出版警察”,专门从事对于传播“危险思想”的排查与处理。
[45]“啟發宣傳”是当时日本文件中的用词,根据首任内阁情报部部长横沟光晖的解释,所谓“啟發宣傳”是指“为了达成某种目的,将正确的事情原模原样的进行广泛传播,以引起共鸣和理解。……宣传是一种和平的艺术。事实作为事实只能是无声和静止的。如果事实变成事实加上意义的力量的话,就会结合打动人心的效果。”见横沟光晖:《国家と情報宣伝》,1938年2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防卫省档案C14010448900,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藏。
[46]《内閣情報局設置関係書類》,1940年9月6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A03024734600,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47]横沟光晖:《国家と情報宣伝》,1938年2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防卫省档案,档案号:C14010448900,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藏
[48]《資料內容》,http://www.jacar.go.jp/DAS/meta/MetaOutServlet
[49]“滿洲問題”指东北问题;“上海事件”指1932年1月18日发生的所谓“日僧事件”及其后的“一·二八事变”;“滿洲及支那事変”指“九一八事变”;“北支事変”指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支那事変”指1937年“七七事变”。
[50]横沟光晖:《国家と情報宣伝》,1938年2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防卫省档案,档案号:C14010448900,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藏
[51]指地方概况、游记、通讯报道。
[52]《重慶側資料第101号「軍事」日華文資料合訂本(空軍)昭和17年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日本军部档案C13050209100,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藏
俞凡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初探”(批准号:15FXW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