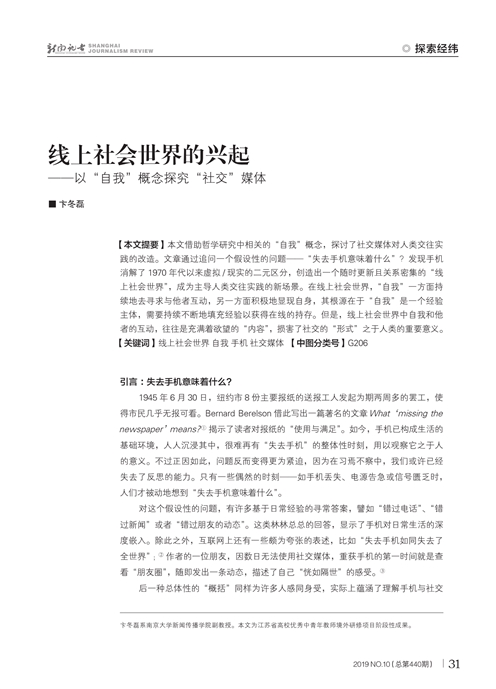线上社会世界的兴起
——以“自我”概念探究“社交”媒体
■卞冬磊
【本文提要】本文借助哲学研究中相关的“自我”概念,探讨了社交媒体对人类交往实践的改造。文章通过追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失去手机意味着什么”?发现手机消解了1970年代以来虚拟/现实的二元区分,创造出一个随时更新且关系密集的“线上社会世界”,成为主导人类交往实践的新场景。在线上社会世界,“自我”一方面持续地去寻求与他者互动,另一方面积极地显现自身,其根源在于“自我”是一个经验主体,需要持续不断地填充经验以获得在线的持存。但是,线上社会世界中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往往是充满着欲望的“内容”,损害了社交的“形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线上社会世界 自我 手机 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引言:失去手机意味着什么?
1945年6月30日,纽约市8份主要报纸的送报工人发起为期两周多的罢工,使得市民几乎无报可看。Bernard Berelson借此写出一篇著名的文章What‘missing the newspaper’ means? ①揭示了读者对报纸的“使用与满足”。如今,手机已构成生活的基础环境,人人沉浸其中,很难再有“失去手机”的整体性时刻,用以观察它之于人的意义。不过正因如此,问题反而变得更为紧迫,因为在习焉不察中,我们或许已经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只有一些偶然的时刻——如手机丢失、电源告急或信号匮乏时,人们才被动地想到“失去手机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有许多基于日常经验的寻常答案,譬如“错过电话”、“错过新闻”或者“错过朋友的动态”。这类林林总总的回答,显示了手机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除此之外,互联网上还有一些颇为夸张的表述,比如“失去手机如同失去了全世界”;②作者的一位朋友,因数日无法使用社交媒体,重获手机的第一时间就是查看“朋友圈”,随即发出一条动态,描述了自己“恍如隔世”的感受。③
后一种总体性的“概括”同样为许多人感同身受,实际上蕴涵了理解手机与社交媒体的重要线索。手机的失去,为什么让人们有失去“世界”的感觉?没有手机的人,难道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恍如隔世”的说法,是否意味着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有,它们有何差异?分别之于人类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一系列疑问涉及了手机、交往和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众所周知,手机是当代人须臾难离的媒介;其中,社交媒体在线又是普遍的常态——不仅可以即时谈话、看到他人动态,亦可第一时间知晓新闻。对此现象,学术界大概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是常识化的,认为手机满足了种种需要,就如市民对报纸的阅读一样。但社会情境早已转换,报纸和手机对生活的介入程度完全不同,对其理解不应止于功能主义的需求论。第二种是自主性技术哲学的,该理论认为技术反转了它和人类的关系,人已是技术的附属,不得不遵从手机的逻辑行动。④这个路径偏向认识论的思辨,给人启发但言犹未尽。第三种是哲学存在论的,指向技术和人的“存有”,即如孙玮对微信的研究,“微信是随身携带的移动场景,通过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践,持续地建构着地方,提供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感,人们通过多个节点主体,实现在世存有”。⑤这个路径以日常经验为基础,并将之上升到存在现象学,有利于解释手机造成的人类交往方式的整体转换,但还没有说明人们为什么以“一直在线”的方式“在世存有”。
本文遵循第三种路径,尝试以“自我”为叙述主体,探究社交媒体对人类交往实践的整体性改造。研究的具体问题是:手机如何创造了一种新的交往场景?这个新场景有何特点?自我在新场景中是怎样展开交往的?更进一步的追问是,自我为什么沉浸在这种交往实践中不能自拔?对人际关系又有何影响?事实上,不少研究已涉及新媒体与自我的关系,譬如Sherry Turkle的系列研究即指出,电脑曾被视作“第二自我”(the second self)体验,众多的虚拟游戏提供了“自我的多个面向”(multiple aspects of self);但这些术语已逐渐过时,随着手机在线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涌现的是一个新的“受牵绊的自我”(tethered self)。⑥这一系列概念命名颇具启示,描述了技术对人类自我的影响。另一种是众多以量化方法探究“自我呈现”的研究,比如Natalya Bazarova & Yoon Hyung Choi将基于传统社会的自我披露的五种功能——社会认同、自我表达、关系发展、身份澄清和社会控制,扩展到社交网络,解释了社交媒体上各种类型的自我披露的原因。⑦这两类研究提供了理解社交媒体和自我的重要线索,但前者偏向现象描述,后者仍然是功能主义范畴内偏向心理学的片段展示。
与它们不同,本文的自我概念是哲学范畴的,不仅关注线上的交往实践,还要从经验上升一层,尝试解释人们为什么如此沉浸于这种线上交往,这就涉及关于自我意识的哲学或自我的持存问题。客观而言,自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哲学上的早期追寻主要关注自我的认识论;随后心理学、社会学、脑科学等也大量触及自我问题。不过,在泰勒(Charles Taylor)看来,心理学的议题多与自我形象有关,这虽然“是有关人的一个事实,他们关心他们的形象能达到社会所引导的某些标准。但是,没有把这看成是对人的人格来说是本质的东西”。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实际上是日常意义上‘自我’和形象这些词的全部太人性的弱点(the all-too-human weakness)”。⑧就本文而言,这里的自我是存在论、互动论以及精神哲学等层面的综合,或许能够稍稍避免泰勒对心理学的自我研究之批评——“这种意义上的自我也是不充分的”。⑨
一、“线上社会世界”
“失去手机如同失去了全世界”,这句话中的“世界”可以用“社会世界”这个术语来替代。这个词来自奥地利现象学家舒茨(Alfred Schutz),指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存在着社会世界,就如同我们身为平常人所接受的,或是从事社会学研究时所习以为常的那般”。⑩社会世界由各种人的交往实践构成,“世界的概念必须以‘每个人’及‘其他人’概念作为基础”。[11]除了前人世界和后人世界,共时性层面的社会世界主要是“周遭世界”和“共同世界”,我们交往的主要对象就来自这两个,“如果我们把周遭世界中的他我成为邻人,共同世界中的他我成为同时代人,则我们可以说,我,和邻人一同活着,是直接经验到他们以及他们的体验,但我对于一同活着的同时代人却不直接掌握他们的体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介对同时代人“进行观察和行动”。[12]社会世界作为人类交往的场景,并非恒定不变的事物。随着互联网、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社会世界逐渐分化甚至整体搬迁,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新的“线上社会世界”,主导着人类的交往和意义的生成。
其历史过程是这样的。在很长的时间里,人类主要生活于一元的世界,交往被绵延的现实所规范,偶有神话、幻觉或梦境的时刻。对一元社会世界发起挑战的是“虚拟”场景的诞生。作为一个概念,“虚拟这个词古老而边缘”,15世纪以来一直用于宗教语境,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获得了现代意义,“在它的现代形式中,虚拟一般与计算机网络的兴起有关,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纳尔逊(Ted Nelson)给了虚拟性关键的现代含义,赋予它“‘感知结构和感觉’以及‘与真实相对’这两重意义”;1970年代起,“人工现实”这个词在计算机圈内受到欢迎;1980年代,雷尼尔(Jaron Lanier)首次提出“虚拟现实”一词,指的是“三维的,被称为‘拟真’的环境”。[13]经过随后数十年计算机和网络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可以称为“网络空间”、“赛博空间”或“虚拟空间”,“暗示着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维度,在这里我们把信息移来移去,我们围绕数据寻找出路,网络空间代表着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由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14]这个描述表明,社会世界从此被分割为两个平行的部分,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虚拟的,两个世界有明显的界限。人们在线上冲浪、游戏和交往,在线下工作、购物或生活,互不打扰,并行不悖。虚拟空间所具有的逃离现实的感觉,一度让人类欢呼鼓舞,以至于让·鲁瓦(Jean-Louis Roy)说:“历史上从未有过可与虚拟世界诞生相提并论的东西,它既是现实世界的副本,又能与之重合。”虚拟世界作为 “实在”,还创造出一种新的自我:“这个虚拟世界并非是现实世界的拷贝或投影,而是作为一个特殊实体存在的……我们不再只是我们自己,每个人从此都拥有一个储存在世界各地数据库中、术语统计学范畴的新自我,成为人类事件永久性索引的组成部分。” [15]然而,“网络空间排挤物理空间”。[16]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虚拟空间逐渐覆盖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人们不再需要见面,不再需要阅读纸质新闻,也不再需要去银行和逛商场。这些虚拟的触角广泛延伸到原来属于现实范畴的事务,将线下社会世界压缩。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说:“电子媒介所形成的日趋同化的信息网络,为个体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社会观点,以及检测自己命运的更广泛的领域。” [17]于是,社会世界向线上转移,自我和他者的交往情境相应发生巨大转变。就像舒茨所说:“让我们设想,有一个面对面的对话,逐步被电话交谈、再来是被信件往返,最后则是被经由第三者传达的讯息等等所取代,从这里便可以看到由周遭世界逐渐转移到共同世界情境的过程。”舒茨进一步将此概念化为“接触情境”[18]的变化。[19]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予虚拟/现实这对二元话语最后一击,使之失去了基本的解释力。手机作为一种技术,具有随时随地的可用性;同时,它还覆盖着繁多的功能——“只要带一部手机就可以出门”这句话即可看出端倪。由此,虚拟和现实之间产生复杂的交错,更准确地说是虚拟打破了它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全面地介入到现实中。这种情况已愈演愈烈,导致虚拟/现实的区分意义逐渐式微,以至于“‘虚拟的’和‘虚拟’这个词几乎要失去它的历史含义的最后碎片,另起炉灶”。[20]如此,社会世界就实现了一种从现实到线上的整体性搬迁。并不是说那个现实世界不再存在,而是人们开始将交往的重心放在了线上世界,在线成为主要的生活场景,就如Sherry Turkle所描述的:
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谈论技术的日常语言假设了一个既在屏幕上也在屏幕之外的人生,我们假设存在着一个分离的世界,可以随时涉入与抽离。但是今天的一些惯用语显示了主体的新位置,如我说“我将在电话上”,那意味着,“你可以接触到我,我的电话开着,我将通过手机而实现(社会)存在”。[21]由此,一个由手机和社交媒体主导的人类交往的新场景已然出现。无论是周遭世界的“邻人”还是共同世界的“同时代人”,都开始集中地出现在线上社会世界。与传统线下的社会世界不同,线上社会世界呈现出一种新的节奏和关系密度。
二、随时更新与密集关系
线上社会世界建立在手机这一基础设施之上,使用者不得不遵从技术的总体逻辑。在时间上,手机是一种即时性技术;在空间上,手机高度浓缩了人类的生活场景。
在现代技术的发展史中,时间压缩始终是核心的逻辑。对于传播媒介而言,就是要消灭信息传输中的任何一点迟滞,直到实现真正的同步。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追溯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设置了同时性装备,人们可以随时通过通信卫星同步传输、交换和生成世界新闻、股市信息、金融交易和电视画面。这些蔚为壮观的同时性镜像最初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22]同时性技术的历史一目了然,先是电报,随后经过广播、电视、电话、电脑,直到手机弥合了最后的时间缝隙,“手机正在迅速加热,飞快地烘干过去那些延迟传播的水坑,手机,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社会,直接性和媒介的关系已成为今天的事实”。[23]内嵌于手机的社交媒体,受控于即时性逻辑,而且它自身的设计也鼓励这一原则。社交媒体内部充满着各种“协议”,“协议是一组技术规则,包括它的编程方式和他们如何由其所有者支配或管理,以及如何获得它的可用性。管理协议提供一组如果用户想通过介质参与互动,用户就必须被迫俯冲的指令”。[24]作为媒体,社交平台上的即时新闻已不足为奇,持续不断的报道在第一时间被推送、转发与评论,其流程已有别于电视。“与程序化的电视流相比,推特流被定义为不受限制、未经编辑、即时、短小、短暂反应的直播流——就像水龙头流出的实时观点和直觉”。[25]作为社交工具,手机早已被证明是可以“永恒联系”、“永久在线”或者“即刻连接性”[26]的技术,寓居于此的社交平台,同样具有这种即时性。
从人的角度看,技术的即时性带来了使用上的“随时”,即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可能。“网络空间的感觉就像是在一种无摩擦、无时间的媒体中进行运输。没有任何跳跃,因为每样东西就在那里。如果不是实实在在的也是不言而喻的,随时唾手可得”。[27]同时,“随时”这个词,更加契合手机作为移动媒体的可携带性。由于可以永远在线,又不受空间的限制,聊天、发布动态、点赞、转发新闻、评价别人等互动可随时展开。莱文森(Paul Levinson)说:“一切新新媒介都这样便利,但twitter上的粘贴和阅读都极其简单,几乎像说话一样流畅,更受制于冲动的影响,因为推文(tweets)是默默无声的,旁人听不见,不会对你想说的话产生抑制。” [28]范·戴克也指出:“连接人、事和思想,也是备受争议的点赞按钮背后的原则,其特点是让用户表达他们即时出现的想法,并共享它。” [29]因此,从时间上看,线上社会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随时更新的世界。
就空间而言,传统的社会世界是分散的,而线上社会世界是高度浓缩的,因此两者包含的人际关系的密度有质的差异。线下的社会世界,是一个关系变化较小的空间,人们交往的对象多是生活中的熟人,这些人在数量和类型上甚至在一生都不会变化太多,“传统的群体关系是根据长期共享地点和生活经历而形成的”。[30]在城市中,现象或许有所差异,人们的活动范围增大,每天可能见到足够多的“陌生人”,至少在有限的实体空间中,人群密度显著增加,不过,陌生人之间很少互动和建立起长期的联系,而更多是一种“避免交流”式的状态。[31]大众传媒的出现,大大扩大了人们的交往,使我们可以知晓更多的同时代人,但这些人常常遥不可及,不会出现在个体日常生活中。与这些场景不同,手机和社交媒体构成的线上社会世界是一个关系高度压缩的空间,形形色色的人都集中在此,包括家人、好友、一般熟悉的好友、工作伙伴、偶然碰面的人、从未谋面但知晓的人、完全的陌生人等,这些人集中在一部手机之中,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眼前,构成为一个高密度的交往空间。在技术的帮助下,人们随时随地推送新闻、发表评论、闲聊或自我呈现,其结果是从前那种缓慢而固定甚至有些静止的交往,变成了实时、密集且公开性的互动。
三、寻求他者
线上社会世界这个新场景,虽然由每一个在线的个体参与而成,但却先验于个体——“预先被给予在那里”,这是社会学的基本事实。舒茨说:“首先是作为‘你’领域及我们的领域而被给予的……更进一步来说,对于属于我意含底下的‘我’之真实存有,乃至他单独个别的‘被自身所体验者’而言,‘你’与社群的真实性是被前给予的。” [32]所以,线上社会世界是个体无法逃离的地方。
在这个随时更新的世界,自我和他者的接触情境发生巨变,但是互动的原理没有变化,自我仍须靠他者才能生成,“在世界里生活就是和他人共同生活并且也为他人而活。我们的日常行动都是指向他人的”。[33]不仅仅是个体意义上的他人,“我们还必须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需要一个控制所有人态度的态度共同体,否则我们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拥有共同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不能享有权利”。更进一步,当共同体扩大到我们难以直接触及的范围——譬如国家和世界,就需要新闻业的帮助,“新闻业所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一望便知,因为它报道的各种情况,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34]就媒介对交往对象的改变而言,“他者”变成了“有中介的一般化他人”。这个概念来自梅洛维茨所描述的1990年代的媒体状况,“包括来自传统群体场景以外的标准、价值和信仰,因此它展示了一种新的观念,人们可以用它来观察自己的行为和身份。新的有中介的一般化他人,绕过了家庭和社区中的面对面交往,并被数百万的其他人所共享”。[35]如今,“有中介的一般化的他者”正密集地聚集于线上社会世界,其经验随时更新,成为自我交往的主要对象。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自我是主体,主体是由经验能力构成的。他必须体会到某种经验才能存在”。[36]米德(George Mead)也说:“自我,作为可以成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而社会经验是互动的产物,“个体经验到他的自我本身,并非直接地经验,是从同一个社会群体其他成员的特定观点,或从他所从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他的自我的”。[37]过去,这些经验主要发生于线下社会世界,或者现实和虚拟二分的世界;现在,主要的经验转移到线上社会世界——一个实时更新的、由不同他者形成的经验之地。在当下,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失去或者仅仅保持较低的自我意识,那么他就必须在线上社会世界持续地寻求他者,这种现象造成了“永恒接触”(perpetual contact)、[38]不断刷新和关注他者的种种行为。
学术界对于这些一直在线、观察别人动态的行为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譬如,范·戴克指出:“对年轻人来说,是社会推动他去保持连接的。因为如果不在脸书上,就意味着没有被邀请去参加晚会,没有得到更新的事件。简而言之,就意味着大概从有吸引力的动态公共生活中断开。” [39]Peter Vorderer等人以“在线警觉”(online vigilance)作为永久在线的心理特性,这种心理状态包括凸显性、回应性及监控三个方面,其中“凸显性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关注在线环境”;“回应性则是对手机现实的动态及行动线上沟通的即时反应程度”;“监控则是持续地观察自己认知的数字环境”。[40]这些研究从心理学层面解释了在线的需求,但若再进一步看,这些心理状态背后涉及存在的问题,即自我害怕失去一种持续的经验能力。
丹顿(Barry Dainton)指出:“我们本质上是一系列持存着的经验能力”;“自我是存在于时间中的东西。” [41]它需要一种持续不断的经验,“经验主体也是一个单一的、不间断的潜能。贯通磁悬浮轨道全程的潜能是顺着空间延展的,而构成一个持续主体的潜能则是顺着时间延展的,并且一旦激活,产生的就是(某种类型的)经验”。将这样的认识论落到线上社会世界,就是一个已经激活的、持续不断的自我的状态,需要不断地寻找他者的经验,“对你我而言,我们对自己的意识体验的关注,随着每一次的相互关联而有所改变”,[42]并且“思想和情感只有被定期地更新,才不会削弱”。[43]由于自我对经验的需要是互相的,因此线上社会世界就不断更新,“只要我们的意识之流不停流动,就不可能认为我们自己不复存在,无论我们可能发生了其他什么变化。你只要连续地具有经验,就会连续地存在”。[44]
四、显现自身
“自我”还有另外的一面,即显现自身的欲望,这几乎是每一个自我意识都要经历的状态。
根据黑格尔(Hegel)的论述,人类的“自我意识”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欲望、承认和普遍的自我意识。欲望指的是“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45]也就是视他者为无物。但是,欲望的自我意识存在悖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它的满足”。[46]这就推动自我意识进入承认的阶段,“对方为他存在,它也为对方而存在,每一方本身通过它自己的行动并且又通过对方的行动完成了自为存在这种纯粹抽象过程”。[47]然而,“相互承认需要有普遍的自我意识……我必须将自身视为有理性的存在者,能独立于我的特殊欲望,并且能基于一切自我来说普遍有效之原则而行动”,[48]以此达到人类心灵的最高能力。
以欲望、承认及普遍自我的概念观察线上社会世界的交往,可以发现线上社会世界的自我,一直在欲望和承认之间徘徊。在线上,人们对自我的表述,要么是一种“内部心情”,要么是“外部的行动和享受”。[49]米德也有类似的论述:“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实现自我。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的自我,它是在与他人关系中实现的自我。它必须得到他人承认,才具有我们想要归之于它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它凭借对他人的优势而实现自身,犹如它在与他人相比时认识到它的劣势一样。” [50]回到经验世界,戈夫曼(Erving Goffman)早已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所进行的角色扮演、印象管理等,“当个体扮演一种角色时,他便不言而喻地要求观察者认真对待在他们面前建立起来的印象。要求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这位人物实际拥有他好像拥有的品性,要求他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将具有自不待言地要求有适于它的那种结果”。[51]尽管接触情境已迥然不同,但戈夫曼从面对面交流中发现的现象,更为显著地出现在线上社会世界。并且,线上社会世界的自我呈现,回避了面对面接触时的即时表演,而变得更为从容,因此容纳了更多的控制策略。“相比较其他大众媒体,社交网站——特别是脸书——为个人用户提供了一个舞台用于打造自身形象,并在亲友圈之外推广这个形象”。[52]这些控制策略已深入人心,以微信为例,其现象包括“在发布每个朋友圈的时候都字斟句酌并反复修改、对点赞和快速回复有所期待、事先考虑朋友圈发出的后果,以及精挑细选要发布的照片等”。[53]研究发现,这种“通过状态更新的通信更加偏向自我导向,因为披露者寻求表达和验证自己而不是与他人的联系”。[54]尽管每个行为似乎都是以他者为对象的,但“我之所以对你说话,是有理由的,可能是要唤起‘你’的特殊态度,或只是单纯要对‘你’说明一些事情。是故,每个告知行为都有目的动机,可用某种方式予以确认”,[55]其最终的目标是自我的内在欲望。范·戴克指出:
在网络环境中,人们想去展示他们是谁,他们在通过分享信息碎片的身份建构中获得利益,因为披露个人自身信息与个人知名度紧密联系。心理学研究专家赫里斯托菲、缪斯和德马雷认为:身份是一种社会产品,不仅通过你所分享的东西创造,而且也通过其他人分享与你有关的东西创造……最受欢迎的人是那些最为积极地参与他们的身份建构的人。[56]不过,自我必须走向承认的阶段,当个体在社交网站不断呈现时,也必须接受另一个个体的自我呈现,“当另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拥有了关于我的如下图像,即我是像他一样的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并且我也意识到他也拥有这一图像,我就得到了这个人的‘承认’。因此想要获得承认,我必须也承认他者。在此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欲望和利益之间,也有特定的相互性、平等性,甚至是同一性”。[57]此一原理,很好地解释了线上社会世界不断更新的循环现象。换言之,每一个自我都是别人眼中的他者,并且,每一个自我呈现都出现在众多他者的目光中,容易获得一种公开的满足。然而,这种相互依赖性也造成本能的社会比较,“看着主页上不断刷新的各种精彩场面,脸书很大程度上只会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更加不满意……这种自卑的基调使得每个人都拼命想要制造和展现属于自己的精彩场面,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集体内部的恶性循环”。[58]所以,当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功能轻易地赋予了自我处于网络中心的能力时,这种“在中心”的感觉却总是短暂而随时会被取代的,因而自我实现的满足来去皆迅速,“欲在其满足对象上总是具有破坏性的,其内容是自私的,而满足只发生于个人(那是转瞬即逝的),在满足这动作中本身又产生了‘欲’”。[59]由此循环,却很难得到真正而持续的满足,因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理念最严重的缺陷就在于,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至少仅仅有个别人)可以一直处于关系网的焦点中心,永远只听到赞美。没有人可以一直扮演上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只能做围着神明转的天使”。[60]
五、社交的受损
如上所述,寻求他者和自我呈现,构成了线上社会世界的重要交往实践,呈现出与传统社会世界交往的不同状况。线上社会世界的随时更新和关系汇聚,使自我可以轻易地寻求到他者——来自于四面八方各种类型的人物,其经验看起来总是新鲜的、多样的而又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因此,持续不断地向自我的持存输送“原材料”;同时,线上社会世界的自我呈现,避免了面对面交流时的即兴,发展出一套更为精心的控制策略,并且由于同时面向多个他者,很容易占据交流网络的中心,因此即便是短暂的,自我也能够获得某一时刻的满足,并产生下一次的期待。
人们为何无法离开线上社会世界?其因素关乎自我的存续。对人类来说,自我是如此重要的事物,米德说:“人能够成为他自身的一个客体,人的行为使他成为比其他低等动物高级的进化产物,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社会事实使他区别于低等动物。” [61]而自我作为经验的主体,需要不间断的经验填充来实现持存,因为“如果我们失去了意识,我们就什么也觉察不到了。由于自我就是觉察,因此失去意识对这样的自我而言就是致命的”。[62]由于手机已造成社会世界的整体转换,线下的交往实践已无法满足自我的生存。
然而,线上社会世界的自我并不理想,而是处于一种短暂的、碎片化的,在欲望和承认之间循环的状态。在传统的社会世界,个体之间其实也一直不断互动,人的自我意识由此产生,“如此这般对于‘你’的意识之注视的相互交错、互为依据,而这当中的看(Blick),又仿佛是在面面相互映照的镜子中进行,自我成为影像被抛回来,这正是周遭世界社会关系的特别之处”。[63]当接触情境转向线上社会世界,可以想象的是,被抛回来的自我影像的数量和速度都呈指数上升,让人目不暇接。尤有进之,社交媒体上的自我,由于抹去共同生活的背景,又更加受制于控制策略,因而偏离真实完整的自我太多,它充其量是自我的一个侧影,“仅仅是我们心里希望揭示出来的那些……替身的自我没有我们真身的那种弱点和脆弱。替身的自我永远不能代表我们。我们越是把虚拟人身(cyberbody)错当成自身,机器就越是把我们扭曲,以适应我们所用的替代物”。[64]因此,这些被抛回来的替身的自我,再也组合不起来那个我们熟悉的、完整而真实的自我,也就达不到精神哲学中理性所规范的那个具有普遍意识的自我。
再从自我转向关系。在线上社会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因为充满着欲望而缺乏意义。按照齐美尔(Georg Simmel)的理论,社交的意义在于“形式”而不是“内容”:“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走到一起,发生互动。这种相聚的形式可以获得自己的生命,脱离与内容的任何联系,它为自身目的而存在,因其本身具有的魅力而扩散开来。” [65]具体地说,人类理想的关系并不需要各种密集性的“自我”呈现,而在于互动的形式本身。成伯清对齐美尔社交思想的解读颇具启发,照录如下:
社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结构,即社交参与者身上任何和聚会无关的属性,不得带入社交圈子中来。个体的财富、社会地位、学识、声望特殊才能在社交中不能当作筹码,“充其量只能作为现实渗透进社交的人为结构中的无形的微妙差异”。不仅附属于人格的这类客观要素需要从社交中排出出去,而且纯属人格深层的个人特质,比如性格、心境、命运,也不能带进社交中去。毫无顾忌地表现个人的抑郁、沮丧、兴奋和激昂,也就是坦露自己内心深层的黑暗与光明,会显得有失分寸,不够圆通。因为这种自我表白,破坏了主导社交的互动准则,会将社交引向由内容决定的社会交往形式,即专注于个人的价值感受。[66]以齐美尔的叙述观照,社交媒体上的交往,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携带着各种内容的社交,这种关系的性质偏离了社交自身的意义。或许齐美尔的标准太高,然而我们从经验上也常常能感觉到使用社交媒体时的无聊,“如果幸福感更多地在于挖掘一种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和不仅仅以享乐为目的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所提供的东西,那么,脸书和类似的社交网络平台就算不上是改善幸福感的良方了”。[67]换言之,社交媒体的原理恰恰与幸福之道相反,其根源就在于违背了社交本来的面貌。
伍德(Allen Wood)指出:“如果要继续获得这种自我确定性,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目标和欲望。更具体地讲,我们需要的是如下这种自我意识,它会承认他者,却不以承认作为回报。” [68]我们可以将这种原则落实于线上社会世界吗?并不是很乐观,因为技术已经给予自我这个欲望主体极大的生存空间,并且“共享、成为好友和点赞,成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观念,其影响力超过了脸书,适用于文化的各个角落,影响了社会性的方方面面”。[69]因此,这样的呼唤可能只具有伦理的意义。
最后再假设一下,“失去手机意味着什么?”概括而言,失去手机就失去了一个随时更新、关系密集的线上社会世界,也就失去了自我的持存;但同时,这个在线上社会世界存续下来的自我,却更加偏离了自我的真实色彩,并损害了社会交往的意义。■
①BerelsonB. (1949). What “Missing the Newspaper” Means. In Paul Lazarsfeld and Frank Stanton(eds.)Communications Research 1948-1949 (pp.111-129).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②飞飞酱:《失去手机如同失去了全世界》,https://www.jianshu.com/p/fa8ca24b2333,2019年6月5日
③该条动态发于2019年4月26日,原文为:“手机宕机五日,只以微信Mac通讯,才发现真正回归‘即时通讯工具’的本义。刚打开朋友圈,竟恍如隔世,颇叹今夕何夕。”取自作者朋友圈。
④对自主性技术的相关讨论,请见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⑥TurkleS. (2008). Always-On/Always- on-You: The Tethered Self. In James Katz(eds.)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 (pp.121-137). CambridgeMA: MIT Press.
⑦BazarovaN. & Yoon Hyung Choi (2014). Self-Discourse in Social Media: Extending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Disclosure Motiv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4(4)635-657.
⑧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45页,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⑨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45页,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⑩舒茨: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25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1]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1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2]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86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3]本段所引,均出自:厄尔霍夫(Michael Erlhoff)、马歇尔(Tim Marshall)编:《设计词典》第404-407页,张敏敏、沈实现、王今琪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4]海姆(Michael Heim):《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79页,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鲁瓦:《全球文化大变局》第43页,袁粮钢译,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
[16]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102页,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7]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123页,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28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9]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28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0]厄尔霍夫、马歇尔编: 《设计词典》第404-407页,张敏敏、沈实现、王今琪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1]TurkleS. (2008). Always-On/Always- on-You:The Tethered Self. In James Katz(eds.)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pp.121-137). CambridgeMA: MIT Presspp.121-122.
[22]诺沃特尼: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第11页,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3]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第57页,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范·戴克:《互联文化:社交媒体批判史》第27页,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5]范·戴克:《互联文化:社交媒体批判史》第72页,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6]黄厚铭、曹家荣:《“流动的”手机:液态现代性的时空架构与群己关系》,《新闻学研究》(台北)2015年第7期
[27]海姆: 《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99页,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8]莱文森:《新新媒介》第37页,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9]范·戴克:《互联文化:社交媒体批判史》第43页,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0]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141页,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卞冬磊:《路上无风景: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流》,《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9年1月
[32]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26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3]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1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4]米德(George Mead):《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45、226页,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35]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123-124页,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6]丹顿(Barry Dainton):《自我》第150页,王岫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37]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25、123页,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38]KatzJ. & Aakhus, M.(2002).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9]范·戴克:《互联文化:社交媒体批判史》第44-45页,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0]Vorderer,P.,HefnerD.,Reinecke,L. & Klimmt,C. (2017). Permanently online, permanently connect: living and communicating in a POPC world. London: Routledge.此处转引自韩义兴:《手机驯化的在线惯性和在线警觉》,《新闻学研究》2017年10月
[41]丹顿:《自我》第103、252页,王岫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42]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21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43]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互动仪式链》第74页,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44]丹顿:《自我》第103页,王岫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4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0页,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1页,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5页,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49页,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49页,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82页,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1]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第17页,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2]范·戴克:《互联文化:社交媒体批判史》第45页,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3]李耘耕、朱焕雅:《朋友圈缘何而发》,《新闻记者》2019年第5期
[54]BazarovaN. & Yoon Hyung Choi (2014). Self-Discourse in Social Media: Extending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Disclosure Motiv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4(4)635-657.
[55]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65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56]范·戴克:《互联文化:社交媒体批判史》第45页,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7]伍德(Allen Wood):《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第141页,黄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58]戴维斯(William Davies):《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第187页,常莹、郭丹杰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59]黑格尔:《精神哲学》第43页,卓伟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戴维斯:《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第187页,常莹、郭丹杰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61]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122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62]丹顿:《自我》第148页,王岫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63]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19页,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64]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103-104页,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5]Simmel, G. (1949). The sociology of sociabilitytranslated by Everett Hugh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55(3)pp.254-261. 中文引自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第110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6]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第111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7]戴维斯:《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第188页,常莹、郭丹杰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68]伍德:《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第142页,黄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69]范·戴克:《互联文化:社交媒体批判史》第59页,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卞冬磊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