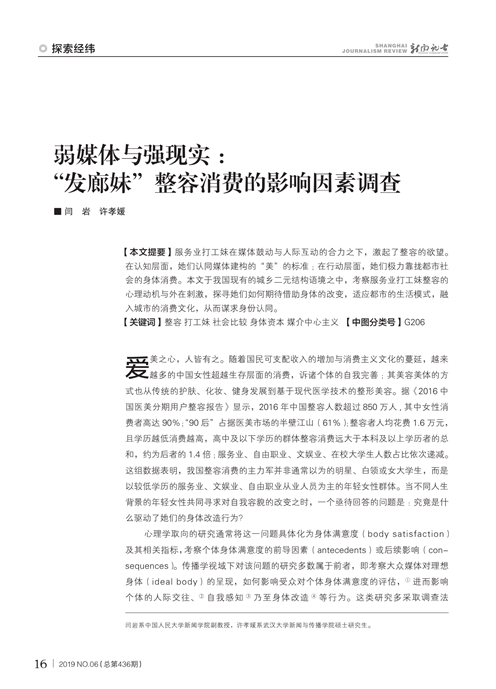弱媒体与强现实:“发廊妹”整容消费的影响因素调查
■闫岩 许孝媛
【本文提要】服务业打工妹在媒体鼓动与人际互动的合力之下,激起了整容的欲望。在认知层面,她们认同媒体建构的“美”的标准;在行动层面,她们极力靠拢都市社会的身体消费。本文于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语境之中,考察服务业打工妹整容的心理动机与外在刺激,探寻她们如何期待借助身体的改变,适应都市的生活模式,融入城市的消费文化,从而谋求身份认同。
【关键词】整容 打工妹 社会比较 身体资本 媒介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随着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与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超越生存层面的消费,诉诸个体的自我完善;其美容美体的方式也从传统的护肤、化妆、健身发展到基于现代医学技术的整形美容。据《2016中国医美分期用户整容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整容人数超过850万人其中女性消费者高达90%;“90后”占据医美市场的半壁江山(61%);整容者人均花费1.6万元,且学历越低消费越高,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整容消费远大于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总和,约为后者的1.4倍;服务业、自由职业、文娱业、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比依次递减。这组数据表明,我国整容消费的主力军并非通常以为的明星、白领或女大学生,而是以较低学历的服务业、文娱业、自由职业从业人员为主的年轻女性群体。当不同人生背景的年轻女性共同寻求对自我容貌的改变之时,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驱动了她们的身体改造行为?
心理学取向的研究通常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为身体满意度(body satisfaction)及其相关指标,考察个体身体满意度的前导因素(antecedents)或后续影响(consequences)。传播学视域下对该问题的研究多数属于前者,即考察大众媒体对理想身体(ideal body)的呈现,如何影响受众对个体身体满意度的评估,①进而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②自我感知③乃至身体改造④等行为。这类研究多采取调查法或控制实验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在长期可得性(chronic accessibility)的认知机制解释框架下,涉及涵化效应、刻板印象等一系列媒介效果理论。然而,绝大多数旨在考察一般心理机制的研究往往基于便利样本,如大学生⑤、高中生⑥或网民⑦,却鲜少覆盖社会中下层的年轻女性。此外,心理学取向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把社会问题个体化,强调认知机制的普遍性,却鲜少测度个体行为背后的群体性和结构性成因。
本文将“整容”行为视为个体更改自我“身体资本”的一种社会行为,将调查对象聚焦于中国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年轻女性。不仅考察其媒介接触和使用行为,更将其置于日常生活的情景之中,考察其工作关系、同侪关系中的人际交流行为,对其身体改造意愿的影响。为了聚焦研究对象,研究集中于美容美发行业的“发廊妹”这一群体,于中国当下的城乡二元语境中,考察其整容消费的心理动机与外在刺激,探讨她们如何借助身体资本的改变,调和身份冲突,融入城市生活。
一、文献综述
(一)边缘人、身份冲突和身体资本
打工妹是城市社会中的“陌生人”(stranger)——如齐美尔 (Georg Simmel)所言,是那些“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继续留下的、社会潜在的流浪者”。⑧陌生人在空间意义上与群体成员距离切近,从社会意义上则又相距甚远。打工妹这一群体在空间上是现代都市的组成部分,往往与群体成员共享咖啡馆、书店、电影院和公共交通设施;但与此同时,她们作为服务者的身份又使其无法融入所活动的社会体系之中。
大部分打工者又是“进城务工人员”,是非城市人口的“外来者”,⑨面临着“城里人—乡下人”的身份游荡和冲突。这使得打工妹群体同时具有了典型的“边缘人” (marginal man) 特质。她们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之中,既不愿超越过去,与原生社会决裂,也不会立刻获得现处社会的成员资格,被新的环境完全接受,处在两种文化与两种社会的边缘。⑩正是因为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种种难以调和的冲突,边缘人也面临着双重矛盾。一方面,面对处于主导地位的上层阶级,他们被迫接受底层地位,渴望融入上流社会,却又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在面对相对弱势的原生文化时,他们则显得阅历丰富,甚至可以成为这一群体的意见领袖,但他们再也不能摆脱新的文化模式的影响,纯粹地回归到本土文化当中。两种文化对他们而言都具有拉力与推力,使得他们反复经受着劣势感与优越感的抵触,耻辱与骄傲的碰撞。[11]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却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主流文化的驯服,而是积极通过自我升值与自我赋权的行动,淡化或摆脱边缘人的身份标签,以此平衡身份冲突,乃至融入城市社会。由于经济资本的缺乏、城市中社会支撑网络的短缺以及包括知识和教养在内的文化资本的不足,身体资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打工妹实现职位向上流动、地位向上提升、获得城市婚姻机会的首要资本。[12]外貌对她们而言便显得尤为重要。她们通常极力期望缩小与城市女性在身体形象上的视觉差异,以获得城市文化的认可与接纳。[13]这种视觉鸿沟的消弭手段包括服饰、发型、口音等非侵入性改变,也包括美容、整容等身体侵入性手段。仅2016年,服务业打工妹的整容人数就独占全国整容总人数的30%。[14]在形形色色的打工妹中,本文聚焦于从事美发行业的打工女性,即“发廊妹”这一群体。一方面,她们具有打工妹的普遍共性。例如,她们在城乡格局、劳工格局以及性别格局中均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也面临“城里人—乡下人”的身份撕裂。另一方面,她们的职业具有特殊性。发廊妹的收入水平通常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但其服务对象却往往是中上层的消费者。工作中频频接触到的都市女性顺理成章地成为她们身体塑造的渴望性参照群体。但吊诡的是,美发这一堪称时尚先锋的行业,其从业者本身不仅要追逐潮流,某种程度上还需要以引领潮流为目标。这意味着,资方在对发廊妹进行形象规训与要求的同时,无意中使其陷入了模仿者与引导者的双重身份当中。因此,发廊妹在阶层、身份、职业等方面的矛盾性,增加了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与研究价值。
(二)媒体使用与身体认知
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认为,当某种行为频繁出现,并具有社会赞许或预期回报等诱因时,人们就会学习和模仿这种有吸引力的行为。[15]大量研究表明,在美容美体领域,人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主要来源于大众媒体和人际互动,两者对女性的身体意象与身体消费影响深远。[16]大众媒体是个体形象感知的一面镜子。受众接触媒介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将媒介中的个体视为客观现实和参照对象。[17]大众媒体通过反复呈现身材瘦削、相貌姣好的明星、模特,影响了人们对“理想女性之美”的认知。在中国电视广告的女性角色中,87%的女性年轻貌美,90%的女性身材苗条;[18]近七成美剧女主人公的体重低于普通女性的体重均值;[19]杂志广告中所使用的模特,偏瘦女性的数量是偏瘦男性的三倍,长期阅读此类杂志的女性,更倾向于以瘦为美。[20]当女性察觉自身形象与媒体人物存在差异时,就可能产生身体不满(body dissatisfaction),进而产生进行整容等改善形象活动的意愿。[21]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指出媒介接触与女性的身体不满和身体改造之间的关系。例如,时尚杂志的阅读与女性的身体不满呈正相关,阅读时间越长,越容易出现厌食症或暴食症;[22]电视收视同样与女性进食障碍、焦虑抑郁、自卑自弃等问题紧密相连;[23]女性网站中诱导女性进行身体改造的图片平均比例为35%,占比居图片信息的首位。经过媒体编码再现的明星模特曲线优美、面容姣好,以此勾起女性提升形象的愿景,刺激女性的身体消费意愿。[24](三)社会比较理论:媒体比较与人际比较
女性对自我身体不满这一感知,通常由社会比较理论来解释。该理论的提出者、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认为,人们具有准确评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和观点正误的心理动机。为此,个体将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和观点与相似的人进行比较来确定自身位置。[25]这种比较按其比较方向可以细分为向上比较(upward comparison,即与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平行比较(lateral comparison,即与和自己相当的人进行比较)和向下比较(downward comparison,即与差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比较方向视比较动机而定,后者包括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自我满足(self-enhancement)和自我完善(self-improvement)三种。[26]当女性主要寻求自我评价时,会主动与媒体中的明星进行向上比较,在发现自我形象与明星形象之间的差距时,可能产生包括身体不满意在内的消极情绪体验;当女性主要关注自我完善时,同样是进行向上比较,但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加出色,明星模特不再是竞争者,而成为学习榜样,此时媒体对女性身体意象的影响是中性或积极的;当女性为实现自我满足的目的时,则会倾向于和比自己差的人比较以维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此时媒体对女性身体意象的影响则是积极的。[27]社交媒体中与美、时尚以及整容相关的信息,按其传播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那些以往由传统媒体发布的一般性信息通过新媒体渠道的“广播”,如整容知识、美容潮流、名人明星等;二是那些以往由人际传播通道传递的特定信息通过新媒体渠道的“窄播”,如亲人、朋友、熟人等的时尚信息更新等。鉴于社交媒体在当前日常信息获取中的重要性,本研究中特别聚焦于女性身体意象和整容消费的社交媒体诱发机制。
人们学习和模仿对象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人际示范。父母和同伴就是人际交往中最鲜活的范本,两者的审美标准和形象要求主要通过两方面作用于个体。其一是强制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又称态度规范是对个体行为“对”与“错”的直接评价;其二是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又称行为规范,是指最常见的实际行动或社会群体呈现出的某种行为。亲友对个体形象的直接评价和自身间接的身体力行,就是两种规范的潜在表达,两者均可能对女性的身体感知产生影响。[28]例如,学者Paxton在对高中生身体感知的研究中指出,父母对子女身体和饮食的负面训斥,无形中导致子女的自我形象不满。[29]其后,学者Smolak、Levine和Shermer 对四五年级的学生及其父母进行了类似调查,发现如果父母正在节食,其子女的身体满意度就相对更低,且女孩受到的影响大于男孩。[30]同样,同伴或朋友对苗条身材的褒奖与对肥胖形体的排斥直接刺激女性的身体感知。如果“瘦”在同龄人之间被普遍奉为真理,个体就更加可能因身体不满而出现头痛焦躁、饮食紊乱等不良反应。[31]与媒体诱发机制相似,社会比较理论有助于探索人际交往活动对身体不满和整容消费的影响。在“发廊妹”的人际互动当中,城市顾客往往是她们进行向上比较的对象,往往充当着社会模范的角色。
基于以往关于媒体使用与社会比较理论的相关研究,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1:对社交媒体中的美容类信息接触越多,a)身体满意程度越低,b)美容意愿越强烈。
研究假设2:社交媒体中的向上比较程度越高,a)身体满意程度越低,b)美容意愿越强烈。
研究假设3:人际交往中的向上比较程度越高,a)身体满意程度越低,b)美容意愿越强烈。
过往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媒体比较或人际比较对女性身体不满与身体消费的影响,却鲜有对两者作用程度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文进一步探究媒体与人际范本对打工妹整容意愿刺激程度的区别:
研究问题1:人际交往中的向上和社交媒体中的向上比较对a)身体满意程度和b)美容意愿的相对影响如何?
(四)风险评估与风险分级
通常所说的“美容整形外科手术”,按其手术的创伤等级,可以分为侵入性(invasive)和非侵入性(noninvasive)两类。前者指运用注射、手术、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的医学技术对容貌和人体各部位进行修复再造伴有疼痛、肿胀、淤血、伤口、出血等不同等级的创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整容;后者是无需医疗器械侵入体内的美容方法,如皮肤的简单护理、化妆修饰、运动健身以及膳食保健等等。[32]在此基础上,我国卫生部颁布的《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又依据技术难度、复杂程度和风险性将侵入性美容分为四级:一级:技术难度较低、手术过程简单、风险度较低。如:双眼皮、开眼角、隆鼻、注射美容等;二级:技术难度一般、手术过程不复杂、风险度中等。如:隆胸、1000ml≤吸脂量<2000ml的吸脂手术等;三级:技术难度较大、手术过程复杂、风险度较大。如:拉皮、洗纹身、2000ml≤吸脂量<5000ml的吸脂手术等;四级:技术难度大、手术过程复杂、风险度大。如:磨颧骨、巨乳缩小、腹壁成形等。[33]可见,整容级别越高,风险越大,潜在的危险程度越高。
然而,媒体对整容的收益和风险的报道却极不均衡。女性杂志一贯将整容描述为帮助女性提升自我、悦己悦人的科学手段;60%的整容新闻选择以正面立场宣传整容在事业、家庭、婚恋等方面所带来的附属价值,对种种风险则避而不谈。[34]实际上,整容手术的死亡率约为1:13000,与一般外科手术相当;一些复杂的整容手术风险可能更高,如吸脂手术的死亡率就高达1:2000,与机动车事故死亡率不相上下。[35]过往研究表明,对整容风险/收益的评估影响人们的整容意愿。在一组对比实验中发现,整容节目对美丽所带来的功利性收益的夸大是观众改造形象的核心驱动。[36]2005年,学者Nabi在对271名女性整容意愿的调查中发现,整容节目的收视与社会比较一方面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整容行为,另一方面,也能够经由收益感知刺激整容意愿,但对风险的感知并没有出现中间作用。[37]鉴于以往研究中收益/风险评估与整容的关系,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4:对美容收益的感知与美容意愿呈正相关。
研究假设5:对美容风险的感知与美容意愿呈负相关。
研究问题2:对美容收益/风险的感知与媒介接触、媒介比较、人际比较与整容意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总体与样本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数据搜集手段,抽样总体为我国从事美发行业的打工女性。受样本特殊性和获取难度的影响,本研究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抽样调查,而是选择湖北省武汉市的“发廊妹”为调查样本。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交通的便利带动了周边省份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推动服务业的兴盛。美发行业的从业女性也随之形成一定规模。此外,《2016中国医美分期用户整容报告》显示,武汉在“最爱整容的城市”中排名第二。[38]由此,选择武汉市的发廊妹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得性。
调查采用目的抽样,于2017年5月4日至15日间,通过问卷星平台设计问卷。问卷的发放采用两大路径:一是通过武汉市某中等规模的美容美发连锁机构,将问卷定点投放至其内部微信群中,共回收问卷104份;二是通过随机选择个体美发店的“发廊妹”传发填答,共回收问卷51份。回收问卷经人工筛查,剔除无效问卷10份,获得有效问卷145份,问卷有效率94%。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美容意愿:即进行美容的愿望程度。侵入性和非侵入性两类美容方式的测量采用Harrison 量表,[39]询问每一个受访者“在不考虑经济因素的情况下,您有多大的意愿从事以下每一项美容?”受访者在5级李克特量表上选出自己对每一个项目的意愿,变异范围从“1=非常不愿意”到“5=非常愿意”。其中,非侵入性美容包括节食、运动健身、护肤品3项;侵入性美容按照手术难度与风险程度划分为低级整容(7项,如做双眼皮等)、中级整容(2项:隆胸、抽脂)、高级整容(2项:磨腮、拉皮)。
2.自变量
社交媒体接触:借鉴学者Lee与Choi 等人的量表,[40]并对其加以修改,将涉及时尚、美容的信息分为四类:美容类(护肤/彩妆/美发)、整容类、健身瘦身类(运动、健身、减肥)和明星时尚类(明星、模特、网络红人的时尚穿搭、街拍等)。受访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通过微博、微信接触以上四类信息的频率。衡量尺度从“1=从不”到“5=总是”。
媒体向上比较:采用关于外表的社会文化态度量表SATAQ (Socialculture Attitudes Towards Appearance Questionnaire) 进行测量。[41]SATAQ为5级自评量表(“1=从不”;“5=总是”),包括“我希望我的容貌像媒体中的女性一样好看”、“我时常把自己的外表和明星的外表作比较”等5个题项。
人际向上比较:采用身体外貌比较量表PACS (Physical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 进行测量。本研究在Schaefer修订后的量表中,[42]通过前测选取了其中的5个题目,测量受访者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向上比较的程度。如“我通过参照都市女性的形象来判断自己外貌的吸引力”、“在公共场合,我会把自己的外貌和别人的外貌作比较”等(“1=从不”;“5=总是”)。
身体满意度:参考Brown和Cash 等编制的多维自我体像关系调查问卷MBSRQ(Multidimensional Body-Self Relation Questionnaire)。[43]该模型包括相貌倾向(Appearance Orientation)、相貌评估(Appearance Evaluation)以及身体部位满意度(Body Areas Satisfaction)等三个维度。相貌倾向是对外貌的在意程度,高分者更加注意自己的容貌,更愿意在形象塑造上花费精力和注意力,共包含4个项目,如“出门之前,我通常花很多时间穿衣打扮”等;相貌评估是指个人对外貌的总体满意度,是对身体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整体感知,包含如“我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等4个问题;身体部位满意度即个体对身体某局部的满意度,包括眼睛、脸型、腰围等9项。所有项目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尺度由“1=完全不同意/不满意”到“5=完全同意/满意”。
收益与风险感知:共9个题项。其中5个涉及收益感知(如“整容可以增加人们的自信”等),4个涉及风险感知(如“整容的后遗症很多”等)。受访者被要求在5级李克特量表上作答,感知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
各个变量均加和求均值;如有分支指标,则优先计算分支指标之均值。(见表1)
3.控制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年龄、岗位、收入、BMI(身体体重指数)以及受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44]其中,年龄要求填报受访者的具体年龄;岗位类别分为前台/收银、洗发员、美发师/美容师、美发总监/美容总监、管理岗以及“其他”六类;收入以千元为单位,分为五类;BMI通过身高与体重计算获得,其计算公式为:BMI=体重(kg)/身高2(m)。
(三)前测
研究于2017年4月实施两次前测。在第二次前测中,样本对象为105名女性大学生,平均年龄22.29岁。KMO与Bartlett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数据的KMO值为.71,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375.550,达到显著,适合进行因素分析。信度检验显示,总量表的ɑ系数为.90美容意愿、媒介接触、媒体社会比较、人际社会比较、身体满意度、收益与风险感知各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82,.72,.85,.84,.85,.71,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符合调查标准。
三、研究发现
(一)数据总量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45份。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年龄分布在15-3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66岁,与美发行业从业者的一般年龄25岁大致相当;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以初中(60人,占41.4%)和高中(61人,占42.1%)学历者居多;个人月收入集中于3500-5000元(41人,占28.3%)和5000元以上(55人,占37.9%),高于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1550元(2015年);从业者数量最多的前三个岗位依次是:美发师/美容师(76人,占52.4%)、管理岗(23人,占15.9%),以及前台/收银(15人,10.3%);BMI的平均值为20.52,其中,22.9%的样本属于偏瘦(BMI≤18.5),72.1%的样本属于正常范围(18.5<BMI≤25),4.3%的受访者属于超重(25<BMI≤30),0.7%的人属于肥胖(BMI>30)。
(二)信度与效度
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数据总体的KMO值为.76,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4324.97,显著性小于0.001(df=1431)。信度检验显示,数据总体的ɑ系数为.92美容意愿、媒介接触、媒体社会比较、人际社会比较、身体满意度、收益与风险感知各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88,.72,.80,.84,.79,.81,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都相当不错,符合问卷分析的要求。
(三)假设的检定
研究假设1-5分别考察了六大自变量(社交媒体中的美容类信息接触、社交媒体中的向上比较、人际交往中的向上比较、身体满意度、美容的收益感知、美容的风险感知)对因变量(美容意愿)的影响。如(表1 表1见本期第22页)所示,研究的所有变量(含细分指标)和自变量均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唯一的例外是身体满意度,其三个维度(相貌倾向、相貌评估和身体部位满意度)中,仅有相貌倾向一个维度与其他变量显著相关。故研究将这一有效维度单独使用,不再并入“身体满意度”这一变量中。
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研究通过SPSS中的Process插件算法,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和中介关系,得到“发廊妹”美容意愿的影响因素路径图。(图1 图1见本期第23页)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收益感知是最显著的直接影响要素,同时影响人们对侵入性和非侵入性美容的意愿。这种影响对侵入性美容意愿尤其明显;收益感知对非侵入性美容的影响在经过相貌倾向的中介后依然显著;收益感知对侵入性美容意愿的影响不受相貌倾向之中介。研究问题2得到了肯定回答。
第二,风险感知是次级显著的直接影响要素,仅作用于侵入性美容的意愿,并且这种影响不受相貌倾向的中介。这两点意味着,整容和美容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决定,而非冲动性行为。收益感知对侵入性美容意愿的正面影响超过风险感知的负面影响,表明人们的侵入性美容意愿是亲收益性的,即,人们倾向于提高美容行为的正面效果在整体决策中的权重,进而夯实侵入性美容的意愿。由此,研究假设4得到了全部支持,研究假设5得到了部分支持。
第三,作为身体满意度的子维度,相貌倾向充当了其他自变量与整容意愿间的中介变量。其他各个要素均通过相貌倾向影响个体实施非侵入性美容的意愿。这表明,是个体对相貌的在意程度(即,我如何能变得更美)而非个体当下的身体满意程度(相貌评估和身体部位满意度两个维度均无显著关联)影响了人们的美容意愿。并且,这种影响仅限于非侵入性美容。
第四,社交媒介中的向上比较对整容意愿的影响最为“遥远”,是唯一没有与两类美容意愿产生直接效果的要素。一方面,媒介向上比较直接影响了个体的相貌倾向。即,与媒体中的明星、模特、网红等的比较增强了个体对容貌的注意力和形象提升的积极性。这一结果印证了社会比较理论的部分观点,即,向上比较的结果并非绝对消极,也可能是中性或是积极的。当个体主要出于自我完善的目的进行向上比较时,参照的群体就不再是赶超对象而成为学习的榜样。在这种情况下,与媒介人物的向上比较属于学习性的虔诚性模仿,不仅不会滋生身体不满,还会催生出人们对相貌的关注度,推动个体的身体改造行为。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向上比较的影响是一种指向广泛的弱影响。所谓指向广泛,是指媒体比较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相貌倾向,而且直接影响个体的人际向上比较。这意味着,那些更关注媒体中女性形象的人,也更会倾向于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亲人、朋友、顾客等)进行人际比较。所谓弱影响,是指媒体比较与两类美容意愿均无直接关系。这表明,与媒体中女性形象的比较是一种泛媒体感知行为,可能影响人们的一些相关的态度、信念和行动,却不具有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由此,研究假设2得到部分支持。
第五,媒介接触仅对非侵入性美容意愿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受到相貌倾向的完全中介。换言之,接触美容信息的频率和数量直接强化了人们对自身相貌的在意程度。媒介所呈现的美容类信息大多是教人变美的时尚圣经或是美妆教程,多数旨在挖掘、激发用户的爱美之心,鼓励女性进行外貌投资,而非有意打击女性的相貌自尊,致使女性自我怀疑或自我不满。无论对自我容貌秉持积极或消极的态度,美容整容信息的接触越多,就会越发在乎自我的相貌,越愿意花费时间精力经营外表。但是,媒介使用的间接影响仅限于非侵入类。这意味着人们对大众媒体的泛泛使用仅会激发对“美”的有限追求,不足以上升到侵入性美容的层面。研究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
第六,人际交往中的向上比较仅对侵入性美容意愿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加入相貌倾向、收益和风险感知等因素的调节后失去了统计学显著性。一方面,与现实生活中其他女性的比较直接催生了个体从事侵入性美容的意愿,这显示出人际交往在个人身体改造行为中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人际比较对侵入性美容意愿的权重低于其他调节变量,由此支持了前文的论述,即,美容行为(尤其是侵入性美容行为)是一项理性评估的产物。研究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
最后,研究问题1 对比了人际比较与媒介比较对美容意愿刺激的强弱。如图1所示,人际比较对相貌倾向的影响程度大于媒介比较;人际比较对整容意愿的影响也较媒介比较更为直接。此外,媒介比较仅仅通过相貌倾向对非侵入性整容意愿产生了间接影响;人际比较则一定程度上影响侵入性整容意愿,尽管这种影响在其他因素的调节下失去了统计学显著性。人际比较的举足轻重与费斯廷格所提出的“相似性假说”相吻合,即人们更倾向于与自己能力和观点相近的人进行比较。这种“相近”并非物理距离,而是一种社会距离。更频繁、强度更高的人际比较更有可能指向态度、意愿乃至行为的改变。
四、结论与讨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将身体概括为一种具有独特性和区隔性的资本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身体资本可以被转译成经济资本(比如物质、经济和服务)、文化资本(比如教育)和社会资本(比如社会关系)。[45]作为都市边缘人的打工妹群体从诞生之初,便无可避免地处于三重弱势地位:“来自农村”,意味着她们在政策上受限,在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上处于城乡格局的边缘;“打工者”,意味着她们面对资方的强势,难以发声抗衡,往往处于某种被压迫的生存环境中,是劳资格局中的弱势;“未婚年轻女性”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表现在女工的地位和待遇上和男性劳工的差别暗含性别格局中的不平等。尽管身处多重边缘,但打工妹群体通过自我升值,尤其是身体资本的升值来改变社会身份的努力却始终持续而强烈。[46]本研究以“发廊妹”群体进行侵入性和非侵入性美容的意愿作为其改变身体资本的替代性指标,考察了媒体、人际和个体三类因素的具体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一)外在刺激:人际强于媒介
在“发廊妹”身体消费的外部诱因中,媒介比较与人际比较均通过相貌倾向作用于美容意愿,但人际比较的刺激强度胜过与媒体人物的比较。从比较方向来看,两者皆为上行比较;但从比较距离来看,则是从近到远,对比的核心目标是最优越群体中的距离最近者。形象越佳、地位越高、距离越近,就越可能成为打工女性的首选对比群体。
尽管媒体定义并传播着美的具体标准和形形色色的美人形象,但媒体镜像中的人物更多的是一种行为典范的领潮者和参照系,并未对个体的感知和意愿产生直接的实质性影响。然而,屏蔽明星模特的光鲜亮丽或许容易,忽视现实人群的光彩夺目则十分困难。切切实实存在于“发廊妹”工作与生活当中的都市女性以及姿色出众的同行女工时时刻刻传递着无形的压力和引力,影响甚至困扰着她们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感知。这些女性一方面代表着发廊妹对或将执行的形象消费结果的想象和预期,标志着身体改造的可行性与可靠性,是她们的“代表比较模型”;[47]另一方面,相近个体之间在外貌上的差异能够相对容易地缩小或扭转,使得人际比较更倾向于一种“竞争性模仿”。同泛泛的媒介使用和媒介比较相比,人际比较的遍在性和缩减差距的可得性使得后者成为更显著的外在次级刺激因素,影响着发廊妹追求美丽之信念(相貌倾向)和实施身体改造之行为(美容意愿)。
(二)内在动机:在意程度显于满意程度
身体满意度的测量使用了MBSRQ问卷。这是一项关于自我体像评估的量表测试,其中关于自我形象满意程度的指标主要包括相貌倾向、相貌评估和身体部位满意度三项指标。该量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较好的适用,在本研究的前测群体——高校女大学生群体中也得到了较好的评测结果。但对“发廊妹”这一群体而言,三项指标中的两项(即,相貌评估和身体部位满意度)与其他所有变量均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群体的特殊性。
对“发廊妹”来说,从事整容消费的心理动机并不在于身体部位或整体的满意程度,而在于个体对相貌的在意程度。换言之,驱动“发廊妹”群体产生整容意愿的并不是基于对现有身体资本的评估,而是对身体资本提升的愿望。
这种愿望的实现一方面直接满足了个体的审美需求。当打工女性朝着期待的方向重组面容,改变的不仅是相貌,还会获得包括获得心理补偿、自我扩张和心理优越感等一系列满足。[48]另一方面,身体资本的提升有可能满足社会功利需求。身体作为一种媒介,与人的社会位置紧密相联。身体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流和转译蕴含了增益性社会回报的可能。打工女性明白运用这套身体资本的转换模式。一张姣好的脸庞和一副婀娜的身姿往往是消费市场上的“硬通货”,可以置换更光鲜的职业工种、更通达的上升渠道,乃至与城市人缔结姻亲,“永久性地生活在城市并且彻底改变社会身份”。[49](三)收益与风险:理性评估主导的身体消费
“发廊妹”群体的身体改造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行为者根据不同类型的整容性质做出清晰的风险和收益评估。对非侵入性美容而言,个体只需评估收益;当收益回报足够充分时,个体便可能实施非侵入性整容。换言之,在进行健身、节食以及护肤这类无创伤或创口的美容行为时,“发廊妹”可以仅仅聚焦收益而完全忽略风险。这些收益包括自尊自信的提升、求职晋升的优待、婚恋家庭的前景以及社会阶级的流动等等。对回报的渴望越迫切,美容的欲望也就越强烈;提升身体资本的愿望越强烈,收益评估对美容意愿的驱动也就越大。
侵入性美容行为则是一个集合了收益和风险综合评估的过程,并且不受个体相貌倾向的影响。在选择诸如隆鼻、隆胸这类侵入性整容行为时,“发廊妹”显得谨慎理智,仔细地权衡利弊,辩证地考量侵入性美容的实在裨益与潜在隐患,以实现身体资本的有效收益和风险规避。
(四)“媒体去中心化”的迷思
“发廊妹”整容的缘由颇为复杂,收益感知、相貌倾向以及人际传播中的向上比较可能是其显而易见的原动力,相比之下大众媒体的影响则略显逊色。大众媒体对“发廊妹”群体整容意愿的弱影响,可能有两个主要成因:一是“发廊妹”群体的特殊性。过往研究所发现媒介接触和使用对身体满意度及其相关指标的显著性影响,往往局限于中等程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或收入水平的群体,如大学生、都市白领、志愿参与的网民,却鲜少覆盖社会边缘人群。这类指标的外部信度亟待在多元化群体中检验。冯强等针对网络食品谣言的一项研究显示,高收入阶层更受信谣程度和感知严重性等一系列指标影响,呈现出符合理论预期的中介效应;但低收入阶层则不敏感得多,他们对谣言风险的感知并不随媒体使用和谣言传播等边缘因素的风吹草动而随时变化,而是受更为庞大而缓慢变化的外部因素的制约。[50]本研究中也发现,“身体满意度”的总体指标在前测的女大学生群体中得到了有效区隔,但在“发廊妹”群体中则唯有“相貌倾向”一个指标的影响显著。这或许表明,大众媒体对个体整容意愿的影响可能因阶层而异。
由此推而广之,则指向媒体弱影响的第二个成因,即去“媒介中心主义”(media centrism)的现实。媒介中心主义认为,人类被悬浮于媒介环境之中,其所思所想,所行所止均受制于媒介的“强效果”。但近年来,“媒体去中心化”的观点则认为,媒介中心主义的论调带有夸大媒介之于人类观念与行动作用的嫌疑;[51]媒体的影响固然重要,但不能高估,更非万能,其传播力、覆盖面、渗透率皆有一定的局限性。[52]对于包括“发廊妹”在内的低收入群体而言,大众媒体并非其日常生活的中心。辅助的非正式访谈资料表明,“发廊妹”群体往往只有极其有限的手机使用时间(上班时间不允许使用手机,下班时间又有相当长的部分被通勤、家庭、日常生活和交际等必要活动占据),且其媒体使用以放松休闲为主(主要是网上看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并没有目的明确的整容信息的接触。这使得媒体接触和使用对于这一群体而言本就处于边缘位置。呼应“媒体去中心化”研究的观点,即,大众媒体的社会效果体现为弱影响和弱控制。
现实中的社会分化映射着媒体影响的社会分层。作为数字化时代主要消费者的城市中产阶层或许时刻处于媒体影响的中心,但对于以忙碌为常态化的中低收入服务业女性而言,她们是为媒介资本主义所边缘化的人群,反过来,媒体在她们的生活决策中也处于边缘地位。对于真正关乎发肤的身体改造,媒体呈现出弱控制、弱效果的特点,而对更美好自我的追求、现实的人际刺激和理性的收益风险评估才是都市边缘女性们的核心驱动力。
五、研究局限
本研究亦存在若干不足。首先是因变量的复杂性:美容或整容是一项具有复杂性与综合性的身体消费行为,除去媒体、人际、相貌倾向、风险和收益等因素,也不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如美容价格、个体自尊、社会认同等。因此,本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阐释并未穷尽所有可能性。其次是话题的敏感性:由于“整容”或“身体不满”等话题难免触及人们的隐私屏障,受访者未必完全如实作答,由此可能会影响数据的效度。最后是样本的局限性:由于“发廊妹”群体的样本获取难度,本研究有效样本量仅有145份,未能采取更精确的分析方法探求变量间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限于从事美发行业的女性打工群体,未能推衍至其他行业的打工妹群体。后续研究如若能扩大抽样范围,当更有代表性。■
①EisendM.&MollerJ. (2007). The influence of TV viewing on consumers body images and related consumption behavior. Marketing Letters18(1/2)101-116.
②KrcmarM. GilesS. & HelmeD. (2008).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How mediated and peer norms affect young women's body esteem. Communication Quarterly56 (2)111-130.
③SohnS.H. (2009). Body Image: Impacts of media channels on men's and women's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and testing of involvement measurement.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919-35.
④NabiR.L. (2009). Cosmetic surgery makeover programs and intentions to undergo cosmetic enhancements: A consideration of three models of media effect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1-27.
⑤FardoulyJ.Pinkus,R.T.&VartaianL.R. (2017). The impact of appearance comparisons made through social mediatraditional mediaand in person in women's -everyday lives. Body Image2031-39.
⑥PaxtonS.J. (1993). A prevention program for disturbed eating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in adolescent girls: a 1 year follow-up.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8 (1)43-51.
⑦Sohn.S (2007). Motivations of Social Comparison and Dynamics of the Body Imaging Process: Path Model Approach. Conference Paper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07 Annual Meeting.
⑧WeisbergerA. (1992). Marginality and its directions. Sociological Forum7(3) 425-446.
⑨严汇、高景柱:《打工妹的身份认同:内涵、根源及影响分析——〈中国女工解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⑩ParkR.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33(6)881-893.
[11]StonequistE.V. (1935). The problem of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1(1)1-12.
[12]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社会》2008年第6期
[13]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4]《2016中国医美分期用户整容报告》2017年1月13日,美业网http://news.138job.com/info/205/103355.shtml。
[15]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Psychology, (3)265-299.
[16]Lee,H.R.LeeH.E.Choi,J.KimJ.H, & HanH. (2014). Social media usebody image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91343-1356.
[17]陈月华:《论电视传播中的身体镜像》,《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
[18]刘伯红、卜卫:《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研究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19]HarrisonK. (2003). Television viewers ideal body proportions: The case of the curvaceously thin woman. Sex Roles48(5/6)255-264.
[20]SohnS.H. (2009). Body Image: Impacts of media channels on men's and women's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and testing of involvement measurement.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919-35.
[21]MoonM. (2015). Cosmetic surgery as a commodity for ‘sale’ in online new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5(1)102-113.
[22]HarrisonK. (2000). The body electric: Thin-ideal media and eating disorders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0(3)119-143.
[23]李曦珍、徐明明:《女性在电视广告中的镜像迷恋与符号异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
[24]宋素红:《消费主义视野下的女性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25]Festinger,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 Human relations7117-140.
[26]FardoulyJ.Pinkus,R.T.&VartaianL.R. (2017). The impact of appearance comparisons made through social mediatraditional mediaand in person in women's -everyday lives. Body Image2031-39.
[27]WesterwickS.K.& Romero,J.P. (2011). Body ideals in the media: perceived attainabili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choices. Media Psychology, 1427-48.
[28]KrcmarM. GilesS. & HelmeD. (2008).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How mediated and peer norms affect young women's body esteem. Communication Quarterly56 (2)111-130.
[29]PaxtonS.J. (1993). A prevention program for disturbed eating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in adolescent girls: a 1 year follow-up.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8 (1)43-51.
[30]SmolakL.Levine,M.&SchermerF. (1999). Parental input and weight concerns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25263-271.
[31]VonderenK.E.V.& Kinnally,K. (2012). Media effects on body Image: examining media exposure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internal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14(2) 41-48.
[32]NabiR.L. (2009). Cosmetic surgery makeover programs and intentions to undergo cosmetic enhancements: A consideration of three models of media effect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1-27.
[33]卫生部办公厅:《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卫生部公报》2009年12月25日,http://www.nhfpc.gov.cn/mohbgt/s10697/200912/45119.shtml
[34]MoonM. (2015). Cosmetic surgery as a commodity for ‘sale’ in online new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5(1)102-113.
[35]NabiR.L. (2009). Cosmetic surgery makeover programs and intentions to undergo cosmetic enhancements: A consideration of three models of media effect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1-27.
[36]Lee,S.Y. (2014). The effects of cosmetic surgery realty shows on women's belief-s of beauty privileges, perceptions of cosmetic surgeryand desires for cosmetic enhancements.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16(1)1-15.
[37]NabiR.L. (2009). Cosmetic surgery makeover programs and intentions to undergo cosmetic enhancements: A consideration of three models of media effect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1-27.
[38]《2016中国医美分期用户整容报告》2017年1月13日,美业网http://news.138job.com/info/205/103355.shtml。
[39]HarrisonK. (2003). Television viewers ideal body proportions: The case of the curvaceously thin woman. Sex Roles48(5/6)255-264.
[40]Lee,H.R.LeeH.E.Choi,J.KimJ.H, & HanH. (2014). Social media usebody image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91343-1356.
[41]ThompsonJ.K.Berg,P.V.D.P.RoehrigM.Guarda,A.S.& Heinberg,L.J. (2004). The Socio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Appearance scale-3(SATAQ-3):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35293-304.
[42]SchaeferL.M. (2013). T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revised(PACS-R). Scholar Commonshttp://scholarcommons.usf.edu/etd/4575.
[43]Brown,T.A.Cash,T.F.& MilulkaP.J. (1990). Attitudinal body-image assessment:Factor analysis of the body-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5(1/2)135-144.
[44]EisendM.&M?llerJ. (2007). The influence of TV viewing on consumers body imagesand related consumption behavior. Marketing Letters18(1/2)101-116.
[45]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6]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社会》2008年第6期
[47]周晓虹:《时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
[48]Young,K. (1951).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F.S.Crofts&Co.
[49]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社会》2008年第6期
[50]冯强、马志浩:《网络谣言的传播效果与社会阶层差异》,《新闻与传播评论》待刊
[51]余建清、强月新:《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
[52]潘祥辉:《非媒体信息、非媒体机构与大众媒体的有限功能——兼及一种去媒体中心化的舆论监督观》,《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闫岩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许孝媛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