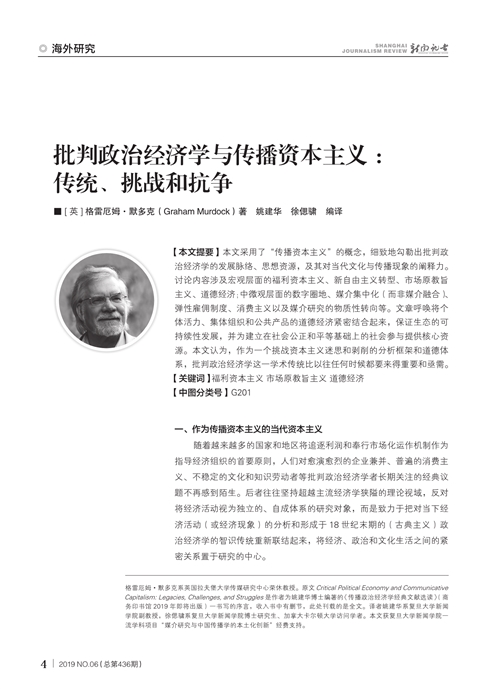批判政治经济学与传播资本主义:传统、挑战和抗争
■[英]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著 姚建华 徐偲骕 编译
【本文提要】本文采用了“传播资本主义”的概念,细致地勾勒出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思想资源,及其对当代文化与传播现象的阐释力。讨论内容涉及宏观层面的福利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转型、市场原教旨主义、道德经济;中微观层面的数字圈地、媒介集中化(而非媒介融合)、弹性雇佣制度、消费主义以及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等。文章呼唤将个体活力、集体组织和公共产品的道德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保证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为建立在社会公正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参与提供核心资源。本文认为,作为一个挑战资本主义迷思和剥削的分析框架和道德体系,批判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重要和亟需。
【关键词】 福利资本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 道德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1
一、作为传播资本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追逐利润和奉行市场化运作机制作为指导经济组织的首要原则,人们对愈演愈烈的企业兼并、普遍的消费主义、不稳定的文化和知识劳动者等批判政治经济学者长期关注的经典议题不再感到陌生。后者往往坚持超越主流经济学狭隘的理论视域,反对将经济活动视为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研究对象,而是致力于把对当下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形成于18世纪末期的(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智识传统重新联结起来,将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置于研究的中心。
毋庸置疑,传播系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发挥着四个核心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极大地加速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复兴。首先,传播系统对有线连接和无线连接的基础设施进行组织和管理,使资本家能够协调和控制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其次,主要通过广告资助的商业媒体为产品的推广和营销提供了畅通的渠道,以此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竭力避免因过度生产而引发的危机。第三,作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公共信息为个人和社会机构提供了必要的象征资源,它对个体的社会和政治参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组织(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是主要的工业复合体(industrial complex),它们控制着一系列生产和营销活动,同时雇用数量庞大的劳动者。
上述传播系统的四个面向对当代资本主义组织的贡献提示我们,乔迪·迪恩(Jodi Dean)提出的“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这一概念在描述对象的范围方面要比“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或“文化资本主义”(cultural capitalism)等概念更具普遍性和包容性。①
在20世纪上半叶,当国家和全球电报与电话网络的铺设基本完成,且现行的印刷和视听媒体组织的主要特征初现时,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批判政治经济学方法才开始在传播分析中复兴。这一时间节点绝非偶然。彼时,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抛弃原有的福利体制,政府对企业活动实施强有力的监管、对核心社会资源享有所有权、为图书馆和其他多样的文化机构(包括欧洲各地的公共广播)提供财政支持等诸多公共职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取而代之的体系积极废除公共供给,将市场活力、私有制和利润创造作为经济组织活力的原则。批判政治经济学一直站在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前沿,揭露它所产生的剥削、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并努力寻找替代性的方案。
二、机器、市场和动员
在经济学中加入“政治”一词,引起了人们对两大核心议题的高度关注。其一,需要怎样的物质条件和象征资源来确保每个个体都能充分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其二,各国政府在提供这些资源方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如何监管资本主义,以平衡企业利益(利润最大化)与工人、公民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当市场失灵或违背公共利益运行时,政府是否应该介入,拥有并运营关键的经济部门?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的基本立场最初由两位核心人物提出: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在此,笔者简要概述一下两位巨擘争论的基本条件。
18世纪的最后25年见证了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交叉革命。总体来说,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大西洋两岸的社会秩序。批判性分析不仅仅聚焦具体事件,更是致力于探究潜在的结构转型过程并追踪其多重后果。1776年发生了三件大事。首先,瓦特推出了他改良后的蒸汽机的第一个商业模型。此后,越来越多的蒸汽机应用于机械制造和能源生产,将生产转移到具有良好运输链的城市中心,并将其集中在大型工厂中,这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从主要以贸易为基础向以大宗商品工业化生产为组织形式的过渡。
第二,《国富论》的出版。在此书中,斯密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市场体系,由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来调节。市场应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作,任何人都能进入市场。在斯密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中,普通人主要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相对而言,对于工人在生产体系中的角色,他的表述既模棱两可,又问题重重。以别针的制造为例,他以庆祝劳动分工带来的效率为《国富论》开篇,其中生产被分解为一系列离散的任务,但这些效率显然有利于资本家。斯密对整天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工人所受到的影响只字不提,但他确实在努力解决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何阻止雇主剥削工人、将绝大部分利润留给自己,以及拒绝为他们的活动造成的任何一种社会或环境损害承担责任。
虽然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承认“富人天生自私和贪婪”,但他却坚持认为:“……他们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对生活必需品进行了几乎相同的分配,如果土地在所有居民中被平均分配的话,那么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也将是相同的……因此,这在无意中……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②斯密进一步强调,资本家作为个人可能天生自私,但他们的集体行为通过激发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服务于公共利益。这种看法自斯密时代以来就一直被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理由,用来反对任何扩大公有制和加强企业活动监管的举措,或发展对富人征收高利率的累进税制,以确保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以及提供公开资料和文化资源,使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从中受益。
其三,美国各州宣布从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以及1791年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克(Saint-Domingue,现为海地)爆发了成功的奴隶起义。这三次暴动都与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决裂,新的共和国建立在充分和平等参与政治的基础之上。在此,人民不再是国王或皇帝的忠实臣民,而是成为具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有权制定他们同意受其管辖的法律,参与到共同关心的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并参加议会代表的选举。
三、作为道德经济的政治经济:从“看不见的手”到“隐秘之处”
宗教权威的更替并不意味着新思想对伦理缺乏兴趣,反之,政经先驱们不仅对他们周围新兴的复杂社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过程充满兴趣,同时也十分关心构成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他们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系,并探究它促进了怎样的伦理原则,以及这些伦理原则影响社会关系的过程。
法国革命者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或者用一个更中性的词,团结。问题在于,这些核心价值观并不完全契合,它们可以用来支持两条截然相反的伦理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把个人自由的价值放在首位,第二条原则则是把社会平等和团结放在首位。因此,斯密和马克思在判断良好社会的道德基础方面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马克思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描述为一部残酷自私的“小说”,并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斯密专注于市场运作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而马克思则关注生产组织,坚持分析必须超越简单的商品流通或交换的范围。③在斯密看来,市场是由激烈的竞争控制的,而马克思则指出,随着生产控制权日益集中在越来越少的有能力操纵市场的大公司手中,企业兼并正在加剧。斯密颂扬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效率,而马克思则揭露了工人遭受的系统性剥削,以及将工作简化为严格组织和重复任务所导致的异化。斯密看到“看不见的手”保证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而马克思则详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情循环,在资本家口袋中系统地存放了大部分利润,以及由此导致的贫富之间收入和财富结构性不平等的再生产。
斯密强调对企业进行最低限度的监管,尽可能减少公有制的作用,以及将核心资源的分配和部署留给私有制和市场机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斯密的上述主张逐渐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基点,这在英美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被重新发现为一个彻底的当代人物。他借用黑格尔的观点,将历史运动呈现为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矛盾和张力,从而创造条件和力量,打破旧秩序,以新秩序取而代之。马克思设想,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正在酝酿一场工人运动,这场运动将确立社会主义,并最终确立共产主义。历史证明他只是部分正确。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成功地节制了私人资本的过剩,并确保了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的核心资源,但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的积累危机引发了一场运动,不是像马克思想象的那样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倒退到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状态。
四、充满争议的传播:公共资源和商业化供给
社会运动带来的压力是规制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同样,政府也开始意识到私营企业无法提供保障公民权利所需的全部资源。政府干预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控制企业行为;供给和运营大部分公共产品;对企业和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并将财政收入用于支持一系列公共设施的建设;制定、颁布和实施相关的法律,保障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和工会为改善工人的薪酬和工作场所的安全而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这种被界定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在1945年至1975年的三十年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旨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全面的、平等的社会参与,这也是完整的公民权的内在规定。
在通信领域,邮政、电报和电话系统提供的连接网络在二战之后的欧洲作为公用事业为政府所有和运营。街角的公共电话亭为那些安装不起私人电话线的人群提供了通道。政府通过对长途和国际电话(主要用户是企业)征收高额的费用来对本地电话服务进行交叉补贴,使其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一时期,电视和广播也被作为国家支持和提供的公共服务传输到每一户家庭,中间很少会插播广告。每个城镇都有公共图书馆,经济拮据的家庭可以在此翻阅平日买不起的书报。许多城镇还建有公共博物馆、艺术画廊和音乐厅。这是战后英国的大环境,也是笔者成长的环境,这一环境在形塑人们对良好社会的愿景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个体都可以平等地获取核心的社会资源,进而实现自我价值,个人的才能和成就服务于整个社会。
与欧洲相比,美国主要依靠监管而不是公有制或公共财政支持来推进公民权的建设。为了使普通民众得益于电话服务的发展,该服务的私营垄断企业(AT&T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受到了政府严格的监管。④电视服务由三大广播网络垄断,它们同时也是美国广播行业的支配者,但彼时,政府限制了电视中广告的数量和类型,并引入了公平原则,以确保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呈现多样的观点。此外,在欧美,政府的监管限制了报业巨头的业务范围,限定了他们控制的市场份额和侵占广播和电视利润的能力。不过,除了上述政府监管之外,美国传媒系统的组织和运营仍围绕着私营企业和产品推广进行,将消费作为个人自由的主要舞台,并将商品理解为自我延伸和表达生活方式的主要途径。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这种个人自由和通过消费实现的理想成为美国输出的主要“产品”,也是与苏联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相抗争的重要武器。随着前殖民地纷纷独立为民族国家,这些解放斗争在系统地摧毁由欧洲列强主导的旧帝国主义秩序的同时,为美国式消费主义开辟了新的疆域。帝国的发展驱动力从对领土的占领转变为对“想象力”的统辖。文化帝国主义逐渐演变为新的全球霸权之战的核心。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优先考虑的是对公民经济和身份的国家管理。印度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韩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为了获得国际贷款而被迫接受重组市场的条件;以及苏联体系的崩塌——这些社会变迁都为消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开辟了新兴市场。在西欧,消费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起就已经积聚了发展势头。经过十年的重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经济进入了充分就业和大众日渐富裕的时期,为美国电影和流行音乐中倡导的消费风格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其结果是,消费者与工人和公民之间的身份认同日益紧张。
这种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学界研究和讨论的核心议题,文化研究也随之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期,并与批判政治经济学呈现出日趋激烈的分歧和对抗。笔者曾深耕于这两种学术传统,并且一直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非竞争。对于传播系统进行综合和完整的分析离不开探讨产业和经济形态、符号表达和抗争的场域,以及组织日常社会生活的资源,而挑战在于厘清上述三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构关系。
对青年亚文化的广泛研究清晰地折射出文化研究的研究旨趣,这集中体现在由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一书中。⑤现在的问题在于文化研究只讲述了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的一部分故事。笔者和其他学者正在研究的青年亚文化是对这些颠覆性变化的回应,我们所支持的传统产业、社区、集体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和破坏,工人身份和劳动团结也在不断消失。公民的理想,连同它对公民责任的邀请,正在迅速为新的消费主义的魅力和它对个人自我实现的承诺所遮蔽。
五、从福利资本主义到市场原教旨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的拥趸看来,政府失灵的必然性在于:政府管制过多,尤其是对经济事务的严重干预;公有制效率低下,且有碍于创新;工会权力过大;沉重的赋税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企业承担风险应得的回报。他们的解决方法极其简单:即向私人投资者(资本家)出售国有资产;放松管制以赋予企业更多的行动自由;降低高企不下的税率;遏制工会的权力,让雇主更多地出于自身的利益来灵活组织劳动力市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虔诚的“信徒”,他们之后,不管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还是独立不久的新兴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上述政策。国家内部每一个经济部门的权力从根本上被颠覆和重新排序。
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和数字技术崛起之间的交叉,将传播产业推到了变革的中心。技术决定论者将技术创新视为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并探究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直接影响。相反,批判学者从剖析当前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入手,追问谁将决定开发何种技术,以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前景和适用范围。他们坚持只有通过将数字技术牢牢嵌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营造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厘清该技术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组织及应用。⑥他们面临着五大核心问题和挑战,即数字圈地、媒介集中化、弹性雇佣制度、消费主义和物质性与相关困境。
(一)数字圈地
中世纪晚期欧洲最初的圈地运动利用了原本公共的自然资源——牧场、可耕地和森林——它们对支持经济自给自足至关重要,并将它们转让给了私人所有者,由他们筑起围栏,以保护自己的专属使用权。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原始积累”一章中,马克思将这一运动描述为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随着农民和原住民部落的土地被私人开发商、矿业公司和农业综合企业收购,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圈地每天都在继续,新自由主义还把(虚拟的)圈地作为包括传播产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的基本动力。
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一直在积极推动公共资产私有化,将它们从公共所有权中剥离出来,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在整个欧洲,各国纷纷效仿英国,将电信运营商私有化,并坚持在提供服务方面引入竞争,向新进入者开放市场。在美国,AT&T受到监管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过去被视为公共事业的基本社会联系网络已转变为创造利润的企业。但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的核心结构和智能手机的许多基本操作功能最初都是在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开发出来的,后来才成为商业消费产品。私人公司一直在搭便车,享受着它们从未为之付费的创新。这意味着大量资源从公共部门被隐形地转移到私营部门。⑦与此同时,计算机算法(它们的业务成功依赖于数据分析)不再受到公众监督,而是受到知识产权条款所设立的法律屏障的保护。这种免费获取核心创新和保护自身运营的商业秘密的结合,推动了西方数字公司进入世界顶级公司名单。这些公司几乎都实行双重股权结构,创始人持有董事会成员资格的多数投票权。外部人士可以投资,但不能左右公司的政策或利润分配决策。尽管这些大型数字公司积极拥抱未来的科技,但它们复制了中世纪王国的结构,在那里,君主的话语统治着一切。
这些公司的大佬也在新自由主义对收入和财富的激进转移过程中受益匪浅。对财富和高收入人群征收税率的连续下调,使他们得以跻身全球最富有人群之列,这无疑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之间持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在美国,从1979年起,“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的人口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富人却一路高歌猛进……最富有的0.01%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了685%”。他们的财富占比几乎翻了四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不到3%增长到2013年的11%”。⑧英国也呈现出类似的两极分化模式,1%的富人拥有全国53%的个人可交易财富,而占总人口数一半的下层穷人只拥有6%。⑨
不断缩小的税基大大减少了用于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公共资金。因此,有关下一代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关键决策,正如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言,都是在公司董事会而不是在政治论坛上做出的。目前主导社交网络的公司也处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物联网等变革性技术研究的前沿。除非受到挑战,否则它们的优先事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开发哪些技术以及用于什么目的,公共政策将永远处于追赶的地位。
(二)媒介集中化
当互联网最初作为一种公共系统推出时,人们普遍认为它可以解除主要媒体公司对传播的集中控制。狂热者们预见这些媒体公司对传播流的垂直、自上而下的控制将逐渐被一种水平网络取代,每个个体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发送和接收材料。但是现实发展却恰恰相反,领先的数字公司已经在其核心业务领域享受垄断或近乎垄断的待遇。
谷歌掌握搜索、脸书主宰社交媒体、亚马逊主导在线零售业。它们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们早早采取了重大举措,松动了公共监管。面对早期互联网公司的强烈游说,美国政府在1996年同意将它们归类为平台,而不是出版商。因此,报纸和广播电台被要求对它们分发给公共互联网的材料实行编辑控制,但平台却可以置身事外。这使它们相对于传统媒体公司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并为一种激进的新商业模式铺平了道路。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有关媒体所有权的规定已经大幅放松,催生了在一系列媒体中持有大量股份的多媒体集团,媒介集中化进程难以遏制。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跨国新闻生意是典型的对监管豁免和漏洞的利用,以此建立了一个全球媒体帝国,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重要新闻机构,美国的国家电视网和电影制片厂,以及欧洲和东亚领先的卫星系统。⑩脸书进入媒体市场时打出了一个口号,暴露其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秩序的意图:“快速行动,打破常规。”传统媒体公司的回应是,试图通过并购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已有大型企业集团的手中。广告收入向在线平台的转移,已迫使出版业加速关闭和整合。在英国,2018年3月,出版全国历史最悠久的热门日报《镜报》(Mirror)和《快报》(Express)的两家公司合并成为一家新公司“到达”(Reach),它的业务占每周全国报纸发行量的近四分之一(23.19%),加上两个主要出版商控制了另外60%,它们对英国公众可获得的印刷新闻达到了高度控制的地步。[11]除了Netflix以外,以亚马逊Prime、苹果电视(Apple TV)和谷歌旗下的YouTube TV为首的主要数字公司也已进入视听娱乐市场,推出了提供电影和电视流媒体服务的部门,并引发了一波并购浪潮,因为电信公司寻求在内容生产方面获得利益,而内容生产商则希望加强对优质品牌和过往库存的掌控。2018年6月,AT&T收购了时代华纳。后者就是《时代》杂志和华纳兄弟好莱坞电影制片厂两家媒体集团此前合并的结果。2018年11月,美国最大的付费电视、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康卡斯特(Comcast)收购了默多克旗下国际天空电视卫星系统(Sky TV)的全部股份。2019年3月,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是以前的主要媒体集团也不再足以在新兴传播市场中进行有效竞争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将其21世纪福克斯部门的电影和娱乐业务出售给了迪士尼公司。
与斯密对竞争活力的信念相反,马克思坚持主张,积累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企业的集中化。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所观察到的:“竞争总是以许多较小的资本的毁灭而告终,这些资本一部分落入征服者手中,一部分完全消失。” [12]这些“征服者”如何利用和滥用他们对公共文化的集中控制,以促进特定的思想、论点和看待、边缘化或压制他人的方式,仍然是批判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三)弹性雇佣制度
与上述媒介组织的集中化进程相伴的是大量劳动者被“负权”的过程。现在,创意和知识劳动者难以像在大型工厂中劳作那样聚集在一起,而更多的是被分散到多个生产“工地”,通常是小作坊或是家中。与此同时,他们的雇佣条款不再是明确为劳动者提供社会福利(主要是养老金)保障的长期雇佣合同,而是弹性雇佣合同——这些合同往往规定了雇主具有终止雇佣关系,且无须补偿劳动者的绝对权力。劳动力区隔化和弹性化极大削弱了工人组织和工会的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它们就工资比率和工作环境与资方达成集体协议的能力。
当代数字网络的连接性使得更多的生产功能被“外包”,这些外包工作一般是具有特定时限的任务或项目。对雇主来说,外包有两大不言自明的优势。首先,他们不再受工会协议的约束,通过“无底线”的降薪将生产成本最小化。项目的竞标过程强化了这种向下的压力传导方式,因为竞标本身就鼓励参与者在最低报价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其次,劳动者的弹性化和将生产转移到公司以外意味着企业将大部分的(生产)成本转嫁给了劳动者,如无须支付工作场所不菲的运营和维护费用,为员工提供带薪的假期、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所有这些成本最终由在家或小作坊中营生的劳动者一力承担。马克思也许已经意识到劳动力的网络化和分散化再现了“异地生产系统”(putting out system)的基本特征,这一生产系统在英国工业化早期曾主导了纺织品的生产方式。资本家为在家工作的劳动者提供原材料和简短的生产说明,并在规定的日期收集成品(或者半成品)。
创意和知识劳动组织的变迁伴随着剥削的严重化。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剥削方式:一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技术进步,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数字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强化这两种剥削方式。数字系统对集中工作于一处的创意和知识劳动者进行常规和持续的监控,旨在确保他们完成生产目标,如在家中工作的自由撰稿人通常面临着不断提前的交付期限,并警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正在严重地侵蚀非工作时间,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使他们能够随时被联系以检查其工作进度。
除此之外,创意和知识劳动者的分散化和弹性化加剧了就业和职业晋升过程中普遍的不平等。像谷歌这样大型数字公司的员工队伍日益呈现出两级化的趋势:即参与企业决策和研发新产品的精英员工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普通员工。是否可以跻身精英阶层与社会背景和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如果孩子的家长是高级职业人士或行政人员,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在精英学校深造,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的优势更为明显。有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已经直接影响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关课程更倾向于制造一种特权或偏好。在数字公司中,女性要是在大学中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她们将获得更多职业晋升的机会,而不是学习科学、数学和技术,这进一步强化了企业中的性别差异。谷歌关于其全球劳动力社会多样性的最新报告揭示:73.9%的领导职位由男性把持,其中66.6%为白人,仅2.6%为黑人。与技术相关的工作岗位亦是如此,男性占77.1%,51.1%为白人,2.1%为黑人。[13]传播产业也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特权模式。例如,近期对英国电视行业就业的官方统计发现,76%的高管是白人,其中59%是男性。女性不仅很少从事管理工作,而且在与创意和内容相关的岗位中也较难寻觅到她们的身影——仅占总劳动力的43%。[14]英国的新闻行业呈现出类似“扭曲”的模式,男性占总劳动力的55%,而女性通常不太可能晋升到管理和编辑岗位,而且她们的收入普遍低于同样岗位的男性。[15]长期就业向弹性就业的变迁正在强化这一颇具歧视性的模式。对于成功的自由撰稿人来说,他们依托于走马灯似的项目,不但能力卓越,而且还有着良好的按时交付的可靠记录,并善于从各种社会资本中攫取资源。上层社会家庭或与创意产业存在千丝万缕关联家庭的求职者更有机会在媒体中找到无薪实习的机会,而实习已经成为在行业内正式就业的入场券,同时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本,编织社交网络,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新型“异地生产系统”的关键所在。
(四)消费主义
过度生产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水涨船高的实际工资和越来越多可获得的消费贷款使种类繁多的大件商品走进寻常百姓家,如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汽车等,它们大幅度提升了普通民众生活的舒适度、便利度和自由度。彼时,厂家尚未采用淘汰更新的策略。这些大件商品一旦发生故障,就会被送修。然而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规定性要求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商品,在更短的时间内更换它们。因此,厂家亟需建立一个强大且有效的推销体系,在商品、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并且持续形塑和强化人们的理念,即消费者的选择权不仅是个人自由的核心条件,而且也是彰显个人成就和身份的最佳方式。[16]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引入了商业电视,但广告时间和内容都受到政府严格的监管,而在西欧的其他国家,电视仍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商业有线电视和卫星频道彻底颠覆了政府电视服务支配者的角色。从那时起,电视为产品推广提供了不胜枚举的新机会。
加拿大批判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反对将节目视为电视公司制作的主要产品,而是基于他在美国的工作经验(当时美国被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广播系统)指出:电视公司制作的主要产品是售卖给广告商的受众,因此受众的注意力而不是节目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17]然而,电视在品牌宣传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广告的持续时间较短(通常为30秒),所以它很难在品牌和消费者的社会身份之间建立强关联。随着遥控设备和视频录制技术的引入,观众可以通过切换频道和快进的方式来避免观看广告。广告商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将产品推广整合到各种文化形式之中,使其成为流行电视剧、电影,以及后来的电子游戏所宣扬的生活方式中最自然和最核心的部分。与此同时,企业赞助往往可以将公司的名称、品牌与流行的或久负盛名的活动和制作过程紧密结合起来。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下,企业旨在通过重新引导消费来恢复盈利的能力,商业互联网的兴起为此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在这方面,互联网相比传统媒体具有两大显著的优势。其一,网络空间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而成为一个开放的实验场,在此,广告商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更好地推广产品和吸引受众注意力,这是商业电视很难做到的。其二,公司为儿童提供免费的在线广告游戏(advergames),这些游戏将玩耍的乐趣与品牌标识和产品无缝地整合到游戏的各种场景之中。
然而,互联网最重要的创新并非产品推广的灵活性,而是将用户不断商品化的能力。斯麦兹所揭示的受众商品理论是建立在收集大量受众信息基础之上的,这些信息包括受众观看电视节目的数量和类型、对节目的评价,以及对他们社会构成进行调研的结果。然而,互联网基于个人用户资料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受众)商品,这些资料来自用户在浏览网站或使用网站服务过程中留下的(或主动提供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最常访问地、常用联系人、消费习惯、个人好恶等,这使得互联网存储的信息量几何级地增长。当用户在免费使用互联网平台的时候,他们同样赋予了后者垄断性的权利去使用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数据,构建个人档案,并将此售卖给从事精准营销的广告商。因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根本的不对称性。
消费者不再是市场神话的主角,而沦为农奴,他们为数字霸主(即互联网平台的所有者)创造盈余,并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监视,这与中世纪小村庄中农民的生活别无二致。“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迅速扩张和强化带来了与个人数据收集、拥有和使用相关的权利分配的新议题。[18]市场政策的支持者强烈反对有朝一日建立以实现资源共享为目标的数据共同体的提议,他们更反对个人享有数据的所有权和售卖权。
(五)物质性与相关困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开宗明义道:在研究任何商品时,我们不仅要分析生产它的劳动力的组织方式,而且还要分析生产它的物质基础。在他看来,商品中除了“包含各种不同的有用的劳动,还存在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因此,“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19]近年来,对资本主义生产物质基础的探索是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最具紧迫性的议题。[20]原因有二:首先,资本家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开发和运输加剧了全球剥夺,这些原材料和能源是数字传播赖以存续的基础设施和多种设备的物质前提。其次,数字媒体使用的快速扩张正在导致全球变暖和环境灾害的频繁发生。
数字媒体的广泛应用要求持续对自然资源进行圈地,剥夺这些资源所在地上的原住民,破坏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对这些资源的开采经常是在最具剥削性的劳动条件下完成的。刚果共和国是钶钽铁矿石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这种矿石是制造智能手机必不可少的稀有矿物。在那里,数量惊人的童工在恶劣和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中长时间地劳动。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剥削模式,说明我们当下“超现代”的数字生活方式高度依赖前资本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对劳动力的圈地及其劳动形式。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通过圈地来获取资源,同时将由奴隶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原始积累。这种行为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因数字技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变得普遍。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恶化了本已严重的环境危机。矿物燃料的使用致使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激增,这是全球温度上升,气候变暖的首要原因。数字媒体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非物质性的世界:连接智能手机的并不是可见的电线,屏幕上显示的均是数字信息。人们的阅读不再依赖随身携带的报纸或纸质图书,音乐的播放也不再需要光盘。但是,上述的非物质性只是一种幻觉:数字设备不仅本身由金属和玻璃制成,而且离不开由稀有矿物质制成的电池。同样的,数字设备的信息传输依赖大规模的物质基础设施,其信息传输和存贮过程同样需要消耗原材料、能源和水资源。将个人数据从插入笔记本电脑的闪存驱动器搬移到基于大型服务器农场(server farms)的数据云的过程,大大增加了对能源供给和冷却水的需求。
此外,在流通领域,数字设备数量的增长及其飞快的弃置速度导致大量不可生物降解的垃圾的产生。媒体的现代历史可以化约为消费日趋个性化的历史:人们从在可以容纳数百人的电影院中观看电影,到围坐在客厅与家人一同收看电视节目,再到摆弄自己的手机、平板电脑或游戏机来达到休闲娱乐的目的。与早期的电视机不同,现在的电视机生产厂商每年都会推出新的系列产品,不断鼓励消费者升级换代,购买新款,淘汰旧款。资本家通过提高消费者消费数字设备和广告营销商品的水平,使数字设备的迭代更好地为资本服务。但就对环境的影响来说,这是一场愈演愈烈的灾难,是全球变暖的“元凶”之一。
传播系统(主要是数字通信技术及其系统)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反对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沿阵地,也是对劳动力剥削进行抗争的前线,劳动力剥削存在于数字设备的生产、物流和弃置等诸多环节。这要求批判政治经济学者拓展其关注的领域,并积极参与对采掘、能源和运输行业的未来以及如何应对环境危机的讨论。
结语:激进经济和可持续性发展生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关心自然世界的伦理观,他指出,“一个国家或者所有同时存在的社会不是地球的所有者,它们只是地球的受益者,而且必须为了后代将它改造得更好”。[21]这一监护原则(principle of custodianship)与资本主义无孔不入地增加积累所导致的猖獗的剥削是绝然对立的。人和地球的和谐关系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如农民和原住民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公有经济,这种和谐关系是公有经济的前提条件。然而,批判政治经济学更多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和国家之间流变的关系,以及市场和公共产品的竞争性道德经济,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忽略了共同体的道德经济。我们迫切需要关注道德经济,并将它融入寻找另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努力之中。
部分评论家认为,共同体提供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原则能够独立于国家来运作,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不可能的。[22]共同体在组织地方性资源方面是有效的,如德国的一些城镇引入的自给自足的、环保的能源发电计划。此外,正如开源运动和维基百科所证明的,它还为数字馈赠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基础,这些时间和专业知识有助于建立开放且可获取的文化和信息资源库。但是,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组织社会核心资源的供给,实现普通民众在公平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制定、颁布和实施相关的法律为社会参与保驾护航。这些核心的社会资源包括教育、住房、医疗、环境等,它们是个人安全和有尊严生活的必备条件。
总之,为了有效对抗传播产业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全方位的企业圈地,我们需要在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将活力、集体组织和公共产品的道德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保证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为建立在社会公正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参与提供核心资源。这在对我们提出巨大挑战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并要求我们在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道主义未来奋斗的过程中,将对传播的批判性分析置于中心。因此,作为一个挑战资本主义迷思和剥削的分析框架和道德体系,这一学术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重要和亟需。■
①DeanJ (2008).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in Megan Boler (ed.) Digital Media and Democracy: Tactics in Hard Times. CambridgeMA: MIT Presspp. 101-122.
②Smith, A (1969[1759])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p. 265.
③MarxK (1976[1867]) Capital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pp. 279-280.
④AT&T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固网电话服务供应商和第一大移动电话服务供应商,此外它还提供宽频及收费电视服务。AT&T公司合计共为1.5亿用户提供服务,其中8510万为无线用户。——译者注
⑤Murdock, G. and McCron, R (1975). “Consciousness of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of Generation”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pp. 192-207.
⑥Murdock, G (2017) “Mediatis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Javnost/The Public, 24(2): 119-135.
⑦Mazzucato, M (2018)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Penguin Books.
⑧Sayer, A (2015) Why We Can't Afford the Rich. BristolUK: Policy Presspp. 5-6.
⑨Dorling, D (2014) Inequality and the 1%. London: Versopp. 22-23.
⑩Murdock, G (2017) “News Corporation” in Bejamin Birkinbine, Rodrigo Gomez and Janet Wasko (eds.) Global Media Giants. London: Routledgepp. 92-108.
[11]Media Reform Coalition (2019) Who Owns the UK Media? London: Media Reform Coalitionp. 5.
[12]MarxK (1976[1867]) Capital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p. 777.
[13]Google (2019). Google: Diversity Annual Report 2019. 参见http://diversity.google/annual-report.
[14]OfCom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2018). Diversity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in Television: UK Broadcasting Industry Report. London: Ofcom. 参见https://www.ofcom.org.uk/tv-radio-and-on-demand/information-for-industry/guidance/diversity/diversity-equal-opportunities-television.
[15]WilliamsO (2016). “British Journalism Is 94% White and 55% Male, Survey Reveals” The Guardian, March 24. 参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network/2016/mar/24/british-journalism-diversity-white-female-male-survey.
[16]Murdock, G (2014). “Producing Consumerism: CommoditiesIdeologies, Practices” in Christian Fuchs and Marisol Sandoval (eds.) Critique, Social Media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pp. 125-143.
[17]Murdock, G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09-119.
[18]Zuboff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London: Profile Books.
[19]MarxK (1976[1867]). Capital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p. 133.
[20]Murdock, G (2018). “Media Materialities: For a Moral Economy of Machin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8(2): 359-368.
[21]MarxK (1981). CapitalVolume 3. London: Penguin Books.
[22]Murdock, G (2018). “Commons Manifestos: A Reply to Bauwens and Ramos” Global Discourse8(2): 343-347.
格雷厄姆·默多克系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荣休教授。原文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Legacies, Challenges, and Struggles是作者为姚建华博士编著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商务印书馆2019年即将出版)一书写的序言,收入书中有删节,此处刊载的是全文。译者姚建华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徐偲骕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访问学者。本文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项目“媒介研究与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创新”经费支持。